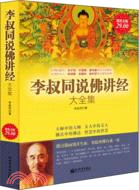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法味
豐子愷
暮春的一天,弘一師從杭州招賢寺寄來一張郵片說:
“近從溫州來杭,承招賢老人殷勤相留,年內或不復他適。”
我于六年前將赴日本的前幾天的一夜,曾在閘口鳳生寺向他告別。以后仆仆奔走,沉酣于浮生之夢,直到這時候未得再見,這一天接到他的郵片,使我非常感興。那筆力堅秀、布置妥貼的字跡,和簡潔的文句,使我陷入了沉思。做我先生時的他,出家時的他,六年前告別時的情景,六年來的我……霎時都浮出在眼前,覺得這六年越發像夢了。我就決定到杭州去訪問。過了三四日,這就被實行了。
同行者是他的老友,我的先生S,也是專程去訪他的。從上海到杭州的火車,幾乎要行六小時。我在車中,一味回想著李叔同先生——就是現在的弘一師——教我繪圖音樂那時候的事。對座的S先生從他每次出門必提著的那只小籃中抽出一本小說來翻,又常常向窗外看望。車窗中最惹目的是接續奔來的深綠的桑林。
車到杭州,已是上燈時候。我們坐東洋車到西湖邊的清華旅館定下房間,就上附近一家酒樓去。杭州是我的舊游之地。我受李叔同先生之教,就在貢院舊址第一師范。八九年來,很少重游的機會,今晚在車中及酒樓上所見的夜的杭州,面目雖非昔日,然青天似的粉墻,棱角的黑漆石庫墻門,冷靜而清楚的新馬路,官僚氣的藤轎,叮當的包車,依然是八九年前的杭州的面影,直使我的心暫時返了童年,回想起學生時代的一切事情來。這一夜天甚黑,我隨S先生去訪問了幾個住在近處的舊時師友,不看西湖就睡覺了。
翌晨七時,即偕S先生乘東洋車赴招賢寺。走進正殿的后面,招賢老人就出來招呼。他說:
“弘一師日間閉門念佛,只有送飯的人出入,下午五時才見客。”
他誠懇地留我們暫時坐談,我們就在殿后窗下的椅上就座,S先生同他談話起來。
招賢老人法號弘傘,是弘一師的師兄,二人是九年前先后在虎跑寺剃度的。我看了老人的平扁的顏面,聽了他的黏潤的聲音,想起了九年前的事:
他本來姓程名中和。李先生剃度前數月,曾同我到玉泉寺去訪他,且在途中預先對我說:
“這位程先生在二次革命時曾當過團長(?),親去打南京。近來忽然悟道,暫住在玉泉寺為居士,不久亦將剃度。”
我第一次見他時,他穿著灰白色的長衫,黑色的馬褂,靠在欄上看魚。一見他那平扁而和藹的顏貌,就覺得和他的名字“中和”異常調和。他的齒的整齊,眼線的平直,面部的豐滿,及臉色的暗黃,一齊顯出無限的慈悲,使人見了容易聯想螺獅頂下的佛面,萬萬不會相信這面上是配戴軍帽的。不久,這位程居士就與李先生相繼出家。后來我又在虎跑寺看見他穿了和尚衣裳做晚課,聽到他的根氣充實而永續不懈的黏潤的念佛聲。
這是九年前的事了。如今重見,覺得除了大概因刻苦修行而蒙上的一層老熟與鎮靜的氣象以外,聲音笑貌依然同九年前一樣。在他,九年的時間真是所謂“如一日”吧!記得那時我從杭州讀書歸來,母親說我的面龐像貓頭;近來我返故鄉,母親常說我面上憔悴瘦損,已變了狗臉了。時間,在他真是“無老死”的,在我真如滅形伐性之斧了。——當S先生和他談話的時候我這樣想。
坐了一會,我們就辭去。出寺后,又訪了湖上幾個友人,就搭汽車返旗營。在汽車中談起午餐,我們準擬吃一天素。但到了那邊,終于進王飯兒店去吃了包頭魚。
下午我與S先生分途,約于五時在招賢寺山門口會集。等到我另偕了三個也要見弘一師的朋友到招賢寺時,見弘一師已與S先生對坐在山門口的湖岸石埠上談話了。弘一師見我們,就立起身來,用一種深歡喜的笑顏相迎。我偷眼看他,這笑顏直保留到引我們進山門之后還沒有變更。他引我們到了殿旁一所客堂。室中陳設簡單而清楚,除了舊式的椅桌外,掛著梵文的壁飾和電燈。大家坐了,暫時相對無言。然后S先生提出話題,介紹與我同來的Y君。Y君向弘一師提出關于儒道、佛道的種種問題,又縷述其幼時的念佛的信心,及其家庭的事情。Y君每說話必垂手起立。弘一師用與前同樣的笑顏,舉右手表示請他坐。再三,Y君直立如故。弘一師只得保持這笑顏,雙手按膝而聽他講。
我危坐在旁,細看弘一師神色頗好,眉宇間秀氣充溢如故,眼睛常常環視座中諸人,好像要說話。我就乘機問他近來的起居,又談及他贈給立達學園的《續藏經》的事。這經原是王涵之先生贈他的,他因為自己已有一部,要轉送他處,去年S先生就為達立學園向他請得了,弘一師因為以前也曾有二人向他請求過,而久未去領,故囑我寫信給那二人,說明原委,以謝絕他們。他回入房里去了許久,拿出一張通信地址及信稿來,暫時不顧其他客人,同我并坐了,詳細周到地教我信上的措詞法。這種丁寧鄭重的態度,我已十年不領略了。這時候使我頓時回復了學生時代的心情。我只管低頭而唯唯,同時俯了眼窺見他那絆著草鞋帶的細長而秀白的足趾,起了異常的感覺。
“初學修佛最好是每天念佛號。起初不必求長,半小時、一小時都好。惟須專意,不可游心于他事。要練習專心念佛,可自己暗中計算,以五句為一單位,凡念滿五句,心中告了段落,或念滿五句,摘念珠一顆。如此則心不暇他顧,而可專意于念佛了。初學者以這步功夫為要緊,又念佛時不妨省去‘南無’二字,而略稱‘阿彌陀佛’。則可依時辰鐘的秒聲而念,即以‘的格(強)的格(弱)’的一個節奏(rhythm)的四拍合‘阿彌陀佛’四字,繼續念下去,效果也與前法一樣。”
Y君的質問引起了弘一師普遍的說教。旁的人也各提出話問:有的問他阿彌陀佛是什么意義,有的問他過午不食覺得肚饑否,有的問他壁上掛著的是什么文字。
我默坐旁聽著,只是無端地悵惘。微雨飄進窗來,我們就起身告別。他又用與前同樣的笑顏送我們到山門外,我們也笑著,向他道別,各人默默地慢慢地向斷橋方面踱去。走了一段路,我覺得渾身異常不安,如有所失,卻想不出原因來。忽然看見S先生從袋中摸出香煙來,我恍然悟到這不安是剛才繼續兩小時模樣沒有吸煙的原故,就向他要了一支。
是夜我們吃了兩次酒,同席的都是我的許久不見的舊時師友。有幾個先生已經不認識我,旁的人告訴他說:“他是豐仁。”我聽了別人呼我這個久已不用的名字,又立刻還了我的學生時代。有一位先生與我并座,卻沒有認識我,好像要問尊姓的樣子。我不知不覺地裝出幼時的語調對他說:“我是豐仁,先生教過我農業的。”他們篩酒時,笑著問我:“酒吃不吃?”又有拿了香煙問我“吸煙不”的。我只答以“好的,好的”,心中卻自忖著“煙酒我老吃了”!教過我習字的一位先生又把自己的荸薺省給我吃。我覺得非常拘束而不自然,我已完全孩子化了。
回到旅館里,我躺在床上想:“杭州恐比上海落后十年吧!何以我到杭州,好像小了十歲呢?”
翌晨,S先生因有事還要句留,我獨自冒大雨上車返上海。車中寂寥得很,想起十年來的心境,猶如常在驅一群無拘束的羊,才把東邊的拉攏,西邊的又跑開去。拉東牽西,瞻前顧后,困頓得極。不但不由自己揀一條路而前進,連體認自己的狀況的余暇也沒有。這次來杭,我在弘一師的明鏡里約略照見了十年來自己的影子了。我覺得這次好像是連續不斷的亂夢中一個欠伸,使我得暫離夢境;拭目一想,又好像是浮生路上的一個車站,使我得到數分鐘的靜觀。
車到了上海,浮生的淞滬車又載了我顛簸傾蕩地跑了!更不知幾時走盡這浮生之路。
過了幾天,弘一師又從杭州來信,大略說:“音出月擬赴江西廬山金光明會參與道場,愿手寫經文三百頁分送各施主。經文須用朱書,舊有朱色不敷應用,愿仁者集道侶數人,合贈英國制水彩顏料vermilion(朱紅)數瓶。”末又云,“欲數人合贈者,俾多人得布施之福德也。”
我與S先生等七八人合買了八瓶Windsor Newton(溫澤?牛頓)制的水彩顏料,又添附了十張夾宣紙,即日寄去。又附言說:“師赴廬山,必道經上海,請預示動身日期,以便赴站相候。”他的回信是:“此次過上海恐不逗留,秋季歸來時再圖敘晤。”
后來我返鄉石門,向母親講起了最近訪問做和尚的李叔同先生的事。又在櫥內尋出他出家時送我的一包照片來看。其中有穿背心、拖辮子的,有穿洋裝的,有扮《白水灘》里的十三郎的,有扮《新茶花女》里的馬克的,有作印度人裝束的,有穿禮服的,有古裝的,有留須穿馬褂的,有斷食十七日后的照相,有出家后僧裝的照相。在旁同看的幾個商人的親戚都驚訝,有的說:“這人是無所不為的,將來一定要還俗。”有的說:“他可賺二百塊錢一月,不做和尚多好呢!”次日,我把這包照片帶到上海來,給學園里的同事們學生們看。有許多人看了,問我:“他為什么做和尚?”
暑假放了,我天天袒衣跣足,在過街樓上——所謂家里寫意度日。友人W君新從日本回國,暫寓我家里,在我的外室里堆了零零星星好幾堆的行李物件。
有一天早晨,我與W君正在吃牛乳,坐在藤椅上翻閱前天帶來的李叔同先生的照片,P、T兩兒正在外室翻轉W君的柳條行李的蓋來坐船,忽然一個住在隔壁的學生張皇地上樓來,說:“門外有兩個和尚在尋問豐先生,其一個樣子好像是照相上見過的李叔同先生。”
我下樓一看,果然是弘一、弘傘兩法師立在門口。起初我略有些張皇失措,立了一歇,就延他們上樓。自己快跑幾步,先到室外把P、T兩兒從他們的船中抱出,附耳說一句:“陌生人來了!”移開他們的船,讓出一條路,回頭請二法師入室,到過街樓去。我介紹了W君,請他們坐下了,問得他們是前天到上海的,現寓大南門靈山寺,要等江西來信,然后決定動身赴廬山的日期。
弘一師起身走近我來,略放低聲音說:
“子愷,今天我們要在這里吃午飯,不必多備菜,早一點好了。”
我答應著忙走出來,一面差P兒到外邊去買汽水,一面叮囑妻即刻備素菜,須于十一點鐘開飯。因為我曉得他們是過午不食的。記得有人告訴我說,有一次杭州有一個人在一個素館子里辦了盛饌請弘一師午餐,陪客到齊已經一點鐘,弘一師只吃了一點水果。今天此地離市又遠,只得草草辦點了。我叮囑好了,回室,鄰居的友人L君、C君、D君,都已聞知了來求見。
今日何日?我夢想不到書架上這堆照片的主人公,竟來坐在這過街樓里了!這些照片如果有知,我想一定要跳出來,抱住這和尚而叫“我們都是你的前身”吧!
我把它們捧了出來,送到弘一師面前。他臉上顯出一種超然而虛空的笑容,興味津津地一張一張地翻開來看,為大家說明,像說別人的事一樣。
D君問起他家庭的事。他說在天津還有阿哥、侄兒等;起初寫信去告訴他們要出家,他們復信說不贊成,后來再去信說,就沒有回信了。
W君是研究油畫的,曉得他是中國藝術界的先輩,拿出許多畫來,同他長談細說地論畫,他也有時首肯,有時表示意見。我記得弘傘師向來是隨俗的,弘一師往日的態度比弘傘師謹嚴得多。此次卻非常地隨便,居然親自到我家里來,又隨意談論世事。我覺得驚異得很!這想來是功夫深了的結果吧。
飯畢,還沒有到十二時。弘一師頗有談話的興味,弘傘師似也喜歡和人談話。寂靜的盛夏的午后,房間里充滿著從窗外草地上反射進來的金黃的光,浸著圍坐談笑的四人——兩和尚,W與我。我恍惚間疑是夢境。
七歲的P兒從外室進來,靠在我身邊,咬著指甲向兩和尚的衣裳注意。弘一師說她那雙眼生得距離很開,很是特別,他說:“蠻好看的!”又聽見我說她歡喜畫畫,又歡喜刻石印,二法師都要她給他們也刻兩個。弘一師在石上寫了一個“月”字(弘一師近又號輪月),一個“傘”字,叫P兒刻。當她側著頭,汗淋淋地抱住印床奏刀時,弘一師不瞬目地注視她,一面輕輕地對弘傘說:“你看,專心得很!”又轉向我說:“像現在這么大就教她念佛,一定很好。可先拿因果報應的故事講給她聽。”我說:“殺生她本來是怕的。”弘一師贊好,就說:“這地板上螞蟻很多。”他的注意究竟比我們周到。
話題轉到城南草堂與超塵精舍,弘一師非常興奮,對我們說:
“這是很好的小說題材!我沒有空來記錄,你們可采作材料呢。”現在把我所聽到的記在下面。
他家在天津,他的父親是有點資產的。他自己說有許多母親,他父親生他時,年紀已經六十八歲。五歲上父親就死了。家主新故,門戶又復雜,家庭中大概不安。故他關于母親,曾一皺眉,搖著頭說:“我的母親——生母很苦!”他非常愛慕他母親。二十歲時陪了母親南遷上海,住在大南門金洞橋(?)畔一所許宅的房子——即所謂城南草堂,肄業于南洋公學,讀書奉母。他母親在他二十六歲的時候就死在這屋里。他自己說:“我從二十歲至二十六歲之間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時候。此后就是不斷的悲哀與憂愁,一直到出家。”這屋的所有主許幻園是他的義兄,他與許氏兩家共居住在這屋里,朝夕相過從。這時候他很享受了些天倫之樂與俊游之趣。他講起他母親死的情形,似乎現在還有余哀。他說:“我母親不在的時候,我正在買棺木,沒有親送。我回來,已經不在了!還只四十幾歲!”大家庭里的一個庶出(?)的兒子,五歲上就沒有父親,現在生母又死了,喪母后的他,自然像游絲飛絮,飄蕩無根,于家庭故鄉,還有什么牽掛呢?他就到日本去。
在日本時的他,聽說生活很講究,天才也各方面都秀拔。他研究繪畫、音樂,均有相當的作品,又辦春柳劇社,自己演劇,又寫得一手好字,作出許多慷慨悲歌的詩詞文章。總算曾經盡量發揮過他的才華。后來回國,聽說曾任《太平洋報》的文藝編輯,又當過幾個學校的重要教師,社會對他的待遇,一般地看來也算不得薄。但在他自己,想必另有一種深的苦痛,所以說“母親死后到出家是不斷的憂患與悲哀”,而在城南草堂讀書奉母的“最幸福的”五六年,就成了他的永遠的思慕。
他說那房子旁邊有小浜,跨浜有苔痕蒼古的金洞橋,橋畔立著兩株兩抱大的柳樹。加之那時上海絕不像現在的繁華,來去只有小車子,從他家坐到大南門給十四文大錢已算很闊綽,比起現在的狀況來如同隔世,所以城南草堂更足以惹他的思慕了。他后來教音樂時,曾取一首凄婉嗚咽的西洋有名歌曲My Dear Old Sunny Home(《我可愛的陽光明媚的老家》)來改作一曲《憶兒時》,中有“高枝啼鳥,小川游魚,曾把閑情托”之句,恐怕就是那時的自己描寫了。
自從他母親去世,他拋棄了城南草堂而去國以后,許家的家運不久也衰沉了,后來這房子也就換了主人。□年之前,他曾經走訪這故居,屋外小浜,橋,樹,依然如故,屋內除了墻門上的黃漆改為黑漆以外,裝修布置亦均如舊時,不過改換了屋主而已。
這一次他來上海,因為江西的信沒有到,客居無事,靈山寺地點又在小南門,離金洞很近,還有,他曉得大南門有一處講經念佛的地方叫超塵精舍,也想去看看,就于來訪我的前一天步行到大南門一帶去尋訪。跑了許久,總找不到超塵精舍。他只得改道訪城南草堂去。
哪里曉得!城南草堂的門外,就掛著超塵精舍的匾額,而所謂超塵精舍,正設在城南草堂里面!進內一看,裝修一如舊時,不過換了洋式的窗戶與欄桿,加了新漆,墻上添了些花墻洞。從前他母親所居的房間,現在已供著佛像,有僧人在那里做課了。近旁的風物也變換了,浜已沒有,相當于浜處有一條新筑的馬路,橋也沒有,樹也沒有了。他走上轉角上一家舊時早有的老藥鋪,藥鋪里的人也都已不認識。問了他們,方才曉得這浜是新近被填作馬路的,橋已被拆去,柳亦被砍去。那房子的主人是一個開五金店的人,那五金店主不知是信佛還是別的原故,把它送給和尚念佛了。
弘一師講到這時候,好像興奮得很,說:“真是奇緣!那時候我真有無窮的感觸啊!”其“無窮”兩字拍子延得特別長,使我感到一陣鼻酸。后來他又說:“幾時可陪你們去看看。”
這下午談到四點鐘,我們引他們去參觀園,又看了他所贈的《續藏經》,五點鐘送他們上車返靈山寺,又約定明晨由我們去訪,同去看城南草堂。
翌晨九點鐘模樣,我偕W君、C君同到靈山寺見弘一師,知江西信于昨晚寄到,已決定今晚上船,弘傘師正在送行李買船票去,不在那里。座談的時候,他拿出一冊白龍山人墨妙來送給我們,說是王一亭君送他,他轉送立達圖書室的。過了一會,他就換上草鞋,一手夾了照例的一個灰色的小手巾包,一手拿了一頂兩只角已經脫落的蝙蝠傘,陪我們看城南草堂去。
走到了那地方,他一一指示我們。哪里是浜,哪里是橋,樹,哪里是他當時進出慣走的路。走進超塵精舍,我看見屋是五開間的,建筑總算講究,天井雖不大,然五間共通,尚不窄仄,可夠住兩分人家。他又一一指示我們,說:這是公共客堂,這是他的書房,這是他私人的會客室,這樓上是他母親的住室,這是掛“城南草堂”的匾額的地方。
里面一個穿背心的和尚見我們在天井里指點張望,就走出來察看,又打寧波白招呼我們坐,弘一師謝他,說:“我們是看看的。”又笑著對他說:“這房子我曾住過,二十幾年以前。”那和尚打量了他一下說:“哦,你住過的!”
我覺得今天看見城南草堂的實物,感興遠不及昨天聽他講的時候濃重,且眼見的房子、馬路、藥鋪,也不像昨天聽他講的時候的美而詩的了。只是看見那寧波和尚打量他一下而說那句話的時候,我眼前仿佛顯出二十幾年前后的兩幅對照圖,起了人生剎那的悲哀。回出來時,我只管耽于遐想:
“如果他沒有這母親,如果這母親遲幾年去世,如果這母親現在尚在,局面又怎樣呢?恐怕他不會做和尚,我不會認識他,我們今天也不會來憑吊這房子了!誰操著制定這局面的權分呢?”
出了弄,步行到附近的海潮寺一游,我們就邀他到城隍廟的素菜館里去吃飯。
吃飯的時候,他談起世界佛教居士林尤惜陰居士為人如何信誠,如何樂善。我們曉得他要晚上上船,下午無事,就請他引導到世界佛教居士林去訪問尤居士。
世界佛教居士林是新建的四層樓洋房,非常莊嚴燦爛。第一層有廣大的佛堂,內有很講究的坐椅,拜墊,設備很豐富,許多善男信女在那里拜懺念佛。問得尤居士住在三層樓,我們就上樓去。這里面很靜,各處壁上掛著“緩步低聲”的黃色的牌,看了使人愈增嚴肅。三層樓上都是房間。弘一師從一房間的窗外認識到尤居士,在窗玻璃上輕叩了幾下,我就看見一位五十歲模樣的老人開門出來,五體投地地拜伏在弘一師腳下,好像幾乎要把弘一師的腳抱住。弘一師但淺淺地一鞠躬,我站在后面發呆,直到老人起來延我入室,始回復我的知覺,才記得他是弘一師的皈依弟子。
尤居士是無錫人,在上海曾做了不少的慈善事業,是相當知名的人。就是向來不關心于時事的我,也是預早聞其名的。他的態度、衣裳,及房間里的一切生活的表象,竟是非常簡樸,與出家的弘一師相去不遠。于此我才知道居士是佛教的最有力的宣傳者。和尚是對內的,居士是對外的。居士實在就是深入世俗社會里去現身說法的和尚。我初看見這居士林建筑設備的奢華,竊怪與和尚的刻苦修行相去何遠。現在看了尤居士,方才想到這大概是對世俗的方便罷了。弘一師介紹我們三人,為我們預請尤居士將來到立達學園講演,又為我們索取了居士林所有贈閱的書籍各三份。尤居士就引導我們去瞻觀舍利室。
舍利室是一間供舍利的、約二丈見方的房間。沒有窗,四壁全用鏡子砌成,天花板上懸四盞電燈,中央設一座玲瓏燦爛的紅漆金飾的小塔,四周地上設有四個拜墊,塔底角上懸許多小電燈,其上層中央供一水晶樣的球,球內的據說就是舍利。舍利究竟是什么樣一種東西,因為我不大懂得,本身倒也惹不起我什么感情;不過我覺得一入室,就看見自己立刻化作千萬身,環視有千萬座塔,千萬盞燈,又面面是自己,目眩心悸,我全被壓倒在一種恐怖而又感服的情緒之下了。弘一師與尤居士各參拜過,就魚貫出室。再參觀念佛堂、藏經室。我們就辭尤居士而出。
步行到海寧路附近,弘一師要分途獨歸,我們要送他回到靈山寺。他堅辭說:“路我認識的,很熟,你們一定回去好了,將來我過上海時再見。”又拍拍他的手巾包笑說:“做電車的銅板很多!”就轉身進弄而去。我目送著他,直到那瘦長的背影沒入人叢中不見了,始同W君、C君上自己的歸途。
這一天我看了城南草堂,感到人生的無常的悲哀,與緣法的不可異議;在舍利室,又領略了一點佛教的憧憬。兩日來都非常興奮、嚴肅,又不得酒喝。一回到家,立刻叫人去打酒。
按語:
文內關于弘一、弘傘兩法師的事實,凡為我所傳聞而未敢確定的,附有(?)記號;聽了忘記的,以□代字。謹向讀者聲明。如有錯誤,并請兩法師原鑒。
代序二
我的畏友弘一和尚
夏丏尊
弘一和尚是我的畏友。他出家前和我相交者近十年,他的一言一行,隨在都給我以啟誘。出家后對我督教期望尤殷,屢次來信都勸我勿自放逸,歸心向善。
佛學于我向有興味,可是信仰的根基迄今遠沒有建筑成就。平日對于說理的經典,有時感到融會貫通之樂,至于實行修持,未能一一遵行。例如說,我也相信惟心凈土,可是對于西方的種種客觀的莊嚴尚未能深信。我也相信因果報應是有的,但對于修道者所宣傳的隔世的奇異的果報,還認為近于迷信。
關于這事,在和尚初出家的時候,曾和他經過一番討論。和尚說我執著于“理”,忽略了“事”的一方面,為我說過“事理不二”的法門。我依了他的諄囑讀了好幾部經論,仍是格格難入。從此以后,和尚行腳無定,我不敢向他談及我的心境。他也不來苦相追究,只在他給我的通信上時常見到“衰老浸至,宜及時努力”珍重等泛勸的話而已。
自從白馬湖有了晚晴山房以后,和尚曾來小住過幾次,多年來闊別的舊友復得聚晤的機會。和尚的心境已達到了什么地步,我當然不知道,我的心境卻仍是十年前的老樣子,牢牢地在故步中封止著。和尚住在山房的時候,我雖曾虔誠地盡護法之勞,送素菜,送飯,對于佛法本身卻從未說到。
有一次,和尚將離開山房到溫州去了,記得是秋季,天氣很好,我邀他乘小舟一覽白馬湖風景。在船中大家閑談,話題忽然觸到蕅益大師。蕅益名智旭,是和蓮池、紫柏、憨山同被稱為明代四大師的。和尚于當代僧人則推崇印光,于前代則佩仰智旭,一時曾顏其住室曰“旭光室”。我對于蕅益,也曾讀過他不少的著作。據《靈峰宗論》上所附的傳記,他二十歲以前原是一個竭力謗佛的儒者,后來發心重注《論語》,到《顏淵問仁》一章,不能下筆,于是就出家為僧了。在傳下來的書目中,他做和尚以后曾有一部著作叫《四書蕅益解》的,我搜求了多年,終于沒有見到。這回和和尚談來談去,終于說到了這部書上面。
“《四書蕅益解》前幾個月已出版了。有人送我一部,我也曾快讀過一次。”和尚說。
“蕅益的出家,據說就為了注《四書》,他注到《顏淵問仁》一章據說不能下筆,這才出家的。《四書蕅益解》里對《顏淵問仁》章不知注著什么話呢?倒要想看看。”我好奇地問。
“我曾翻過一翻,似乎還記得個大概。”
“大意怎樣?”我急問。
“你近來怎樣,還是惟心凈土嗎?”和尚笑問。
“……”我不敢說什么,只是點頭。
“《顏淵問仁》一章,可分兩截看。孔子對于顏淵說:‘克己復禮。’只要‘克己復禮’本來具有的,不必外求為仁。這是說‘仁’是就夠了,和你所見到的惟心凈土說一樣。但是顏淵還要‘請問其目’,孔子告訴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是實行的項目。‘克己復禮’是理,‘非禮勿視’等等是事。所以顏回下面有‘請事斯語矣’的話。理是可以頓悟的,事非腳踏實地去做不行。理和事相應,才是真實工夫,事理本來是不二的。——蕅益注《顏淵問仁》章大概如此吧,我恍惚記得是如此。”和尚含笑滔滔地說。
“啊,原來如此。既然書已出版了,我想去買來看看。”
“不必,我此次到溫州去,就把我那部寄給你吧。”
和尚離白馬湖不到一星期,就把《四書蕅益解》寄來了,書面上仍用端楷寫著“寄贈丏尊居士”“弘一”的款識。我急去翻《顏淵問仁》一章。不看猶可,看了不禁“呀”地自叫起來。
原來蕅益在那章書里只在“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下面注著“僧再拜”三個字,其余只錄白文,并沒有說什么,出家前不能下筆的地方,出家后也似乎還是不能下筆。所謂“事理不二”等等的說法,全是和尚針對了我的病根臨時為我編的講義!
和尚對我的勸誘在我是終身不忘的,尤其不能忘懷的是這一段故事。這事離現在已六七年了,至今還深深地記憶著,偶然念到,感著說不出的悵惘。
代序三
我所崇敬的弘一法師
葉圣陶
在到功德林去會見弘一法師的路上,懷著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凈的心情;也可以說帶著渴望,不過與希冀看一出著名的電影劇等的渴望并不一樣。
弘一法師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國初年;那時上海有一種《太平洋報》,其藝術副刊由李先生主編,我對于所載他的書畫篆刻都中意。以后數年,聽人說李先生已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時,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見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愷先生刊印《子愷漫畫》。丏尊先生給他作序文,說起李先生的生活,我才知道得詳明一點;就從這時起,知道李先生現稱弘一了。于是,不免向子愷先生詢問關于弘一法師的種種。承他詳細見告。十分感興趣之余,自然來了見一見的愿望,便向子愷先生說起了。“好的,待有機緣,我同你去見他。”
子愷先生的聲調永遠是這樣樸素而真摯的。以后遇見子愷先生,就常常告訴我弘一法師的近況。記得有一次給我看弘一法師的來信,中間有“葉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覺慚愧,雖然“居士”不是什么特別的尊稱。前此一星期,飯后去上工,劈面來三輛人力車。最先是個和尚,我并不措意。第二是子愷先生,他驚喜似地向我顛頭。我也顛頭,心里便閃電般想起“后面一定是他”。人力車夫跑得很快,第三輛車一霎往后時,我見坐著的果然是個和尚,清癯的臉,頜下有稀疏的長髯。我的感情有點激動,“他來了!”這樣想著,屢屢回頭望那越去越遠的車篷的后影。
第二天,便接到子愷先生的信,約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會見。是深深嘗了世間味,探了藝術之宮的,卻回過來過那種通常以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態度應是怎樣,他的言論應是怎樣,實在難以懸揣。因此,在帶著渴望的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凈的心情里,更摻著一些惝怳的分子。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導引進那房間時,近十位先到的恬靜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線最明亮的地方,站著那位弘一法師,帶笑的容顏,細小的眼里眸子放出晶瑩的光。丏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后,教我坐在弘一法師的側邊。弘一法師坐下來之后,便悠然地數著手里的念珠。我想一顆念珠一聲阿彌陀佛吧。本來沒有什么話要同他談,見這樣更沉入近乎催眠狀態的凝思,言語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舊友,或是他的學生,在這難得的會晤頃,似應有好些抒情的話同他談,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開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塵凈異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們以為這樣默對一二小時,已勝于十年的晤談了。
晴秋的午前的時光在恬然的靜默中經過,覺得有難言的美。
隨后又來了幾位客,向弘一法師問幾時來的,到什么地方去那些話。他的回答總是一句短語;可是殷勤極了,有如傾訴整個的心愿。
因為弘一法師是過午不食的,十一點鐘就開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經揮灑書畫彈奏音樂的手鄭重地夾起一莢豇豆來,歡喜滿足地送入口里去咀嚼的那種神情,真慚愧自己平時的亂吞胡咽。
“這碟子是谷油吧?”
以為他要醬油,某君想把醬油碟子移到他面前。“不,是這位日本的居士要。”果然,這位日本人道謝了。弘一法師于無形中體會到他的愿欲。
石岑先生愛談人生問題,著有《人生哲學》,席間他請弘一法師談一點關于人生的意見。“慚愧,”弘一法師虔敬地回答,“沒有研究,不能說什么。”
以學佛的人對于人生問題沒有研究,依通常的見解,至少是一句笑話。那末,他有研究而不肯說么?只看他那殷勤真摯的神情,見得這樣想時就是罪過。他的確沒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這東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檢察這東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師,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沒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哪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問他像他這樣的生活,覺得達到了怎樣的一種境界,或者比較落實一點。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覺健康,哀樂的當時也不能描狀哀樂;境界又豈是說得出的。我就把這意思遣開,從側面看弘一法師的長髯以及眼邊細密的皺紋,出神久之。
飯后,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誰愿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并且見過他的文鈔,是現代凈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見一見。同去者計七八人。
決定不坐人力車,弘一法師拔腳便走,我開始驚異他步履的輕捷。他的腳是赤了的,穿一雙布縷纏成的行腳鞋。這是獨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雙這樣的腳!慚愧,我這年輕人常常落在他的背后。
我在他背后這樣想:他的行止笑語,真所謂純任自然的,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這背后卻是極嚴謹的戒律。丏尊先生告我,他嘗嘆息中國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見他的持律極嚴的。他念佛,他過午不食,都為的持律。但持律而到非由“外鑠”的程度,人便只覺他一切純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處自得;似乎他以為這世間十分平和,十分寧靜,自己處身其間,甚而至于會把它淡忘。這因為他把所謂萬象萬事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著的一部分內之故。這也是一種生活法,宗教家藝術家大概采用。并不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的人,除庸眾外,不是貪狠專制的野心家,便是社會革命家。
他與我們差不多處在不同的兩個世界。就如我,沒有他的宗教的感情與信念,要過他那樣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為有點了解他,而且真誠地敬服他那種純任自然的風度。哪一種生活法好呢?這是愚笨的無意義的問題。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別的都不行,夸妄的人卻常常這么想。友人某君曾說他不曾遇見一個人,他愿意把自己的生活與這個人對調的,這是躊躇滿志的話。人本來應當如此,否則浮漂浪蕩,豈不像沒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說尤緊要的是同時得承認別人也未必愿意與我對調。這就與夸妄的人不同了;有這么一承認,非但不菲薄別人,且能致相當的尊敬。彼此因觀感而化移的事是有的。雖說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堅壁;所謂圣賢者轉移了什么什么人就是這么一回事。但是板著面孔專事菲薄別人的人決不能轉移了誰。
到新閘太平寺,有人家借這里治喪事,樂工以為吊客來了,預備吹打起來。及見我們中間有一個和尚,而且問起的也是和尚,才知道誤會,說道:“他們都是佛教里的。”
寺役去通報時,弘一法師從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來(他平時穿的,袖子同我們的長衫袖一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異樣地靜穆。我是歡喜四處看望的,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那房間里,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尚剛洗了臉,背部略微佝著,我想這一定就是。果然,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便對這和尚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我心里肅然。有些人以為弘一法師當是和尚里的浪漫派,看這樣可知完全不對。
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肌理頗粗,表示他是北方人;頭頂幾乎全禿,發著亮光;腦額很闊;濃眉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不戴眼鏡,卻同戴了眼鏡從眼鏡上面射出眼光來的樣子看人;嘴唇略微皺癟: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并肩而坐,正是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而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弘一法師合掌懇請了:“幾位居士都歡喜佛法,有曾經看了禪宗的語錄的,今來見法師,請有所開示,慈悲。慈悲。”對于這“慈悲,慈悲”,感到深長的趣味。
“嗯,看了語錄。看了什么語錄?”印光法師的聲音帶有神秘味。我想這話里或者就藏著機鋒吧。沒有人答應。弘一法師便指石岑先生,說這位居士看了語錄的。
石岑先生因說也不專看那幾種語錄,只曾從某先生研究過法相宗的義理。
這就開了印光法師的話源。他說學佛須要得實益,徒然嘴里說說,作幾篇文字,沒有道理;他說人眼前最緊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險;他說某先生只說自己才對,別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應該。他說來聲色有點嚴厲,間以呵喝。我想這觸動他舊有的忿念了。雖然不很清楚佛家所謂“我執”“法執”的涵蘊是怎樣,恐怕這樣就有點近似。這使我未能滿意。
弘一法師再作第二次的懇請,希望于儒說佛法會通之點給我們開示。印光法師說二者本一致,無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過儒家說這是人的天職,人若不守天職就沒有辦法。佛家用因果來說,那就深奧得多。
行善便有福,行惡便吃苦:人誰愿意吃苦呢?——他的話語很多,有零星的插話,有應驗的故事,從其間可以窺見他的信仰與歡喜。他顯然以傳道者自任,故遇有機緣,不憚盡力宣傳;宣傳家必有所執持又有所排抵,他自己也不免。弘一法師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樹,毫不愧作地欣欣向榮,卻沒有凌駕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氣概。
在佛徒中間,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極了,從他的文鈔里,見有許多的信徒懇求他的指示,仿佛他就是往生凈土的導引者。這想來由于他有很深的造詣,不過我們不清楚。但或者還有別一個原因。一般信徒覺得那個“佛”太渺遠了,雖然一心皈依,總未免感得空虛;而印光法師卻是眼睛看得見的,認他就是現世的“佛”,虔誠崇奉,親接謦欬,這才覺得著實,滿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說,印光法師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來裝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師第三次“慈悲,慈悲”地請求時,是說這里有言經義的書,可讓居士們“請”幾部回去。這“請”字又有特別的味道。
房間的右角里,裝釘作坊似的,線裝和平裝的書堆著不少,不禁想起外間紛紛飛散的那些宣傳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黃智海演述的《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大圓居士說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口義》、李榮祥編的《印光法師嘉言錄》三種。中間《阿彌陀經白話解釋》最好,詳明之至。
于是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辭別。印光法師顛著頭,從不大敏捷的動作上顯露他的老態。待我們都辭別了走出房間時,弘一法師伸出兩手,鄭重而輕捷地把兩扇門拉上了。隨即脫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門內的包車上,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來。
弘一法師就要回到江灣子愷先生的家里,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便與他告別。這位帶有通常所謂仙氣的和尚,將使我永遠懷念了。我們三個在電車站等車,滑稽地使用著“讀后感”三個字,互訴對于這兩位法師的感念。就是這一點,已足證我們不能為宗教家了,我想。
目次
書摘/試閱
斷食日志
——杭州大慈山虎跑寺試驗斷食時所記
丙辰嘉平一日始。斷食后,易名欣,字叔同,黃昏老人,李息。
十一月二十二日,決定斷食。禱諸大神之前,神詔斷食,故決定之。
擇錄村井氏說:妻之經驗,最初四日,預備半斷食。六月五、六日,粥、梅干。七、八日,重湯、梅干。九日始本斷食,安靜。飲用水一日五合,一回一合,分五六回服用。第二日,饑餓胸燒,舌生白苔。第三、四日,肩腕痛。第四日,腹部全部凝固,體倦就床,晨輕晚重。第五日,同,稍輕減,坐起一度散步。第六日,輕減,氣分爽快,白苔消失,胸燒愈。第七日,最平穩,斷食期至此至。
后一日,攝重湯,輕二碗三回,梅干無味。后二日,同。后三日,粥、梅干、胡瓜,實入吸物。后四日,粥,吸物,少量刺身①。后五日,粥、野菜、輕魚。后六日,普通食,起床。此兩三日,手足浮腫。
斷食期間,或體痛不能眠,或下痢,或嚏。便時以不下床為宜。預備斷食或一周間,粥三日,重湯四日。斷食后或須一周間,重湯三日,粥四日,個半月體量恢復。半斷食時服ゾチネ②。
到虎跑攜帶品:被褥帳枕、米、梅干、楊子、齒磨③、手巾、手帕、便器、衣、漉水布、ゾチネ、日記紙筆書、番茶、鏡。
預備期間,一日下午赴虎跑。上午聞玉去預備。中食飯,晚食粥、梅干。二、三、四日,粥、梅干。五、六、七日,重湯、梅干。八日至十七日斷食。十八、十九、二十日,重湯、梅干。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粥、梅干、輕菜食。二十五日返校,常食。二十八日返滬。
三十日晨,命聞玉攜蚊帳、米、紙、糊、用具到虎跑。室宜清閑,無人跡,無人聲,面南,日光遮北,以樓為宜。是晚食飯,拂拭大小便器、桌椅。
午后四時半入山,晚餐素菜六簋(盛食物的圓形器具),極鮮美。食飯二盂,尚未饜,因明日始即預備斷食,強止之。榻于客堂樓下,室面南,設榻于西隅,可以迎朝陽。聞玉設榻于后一小室,僅隔一板壁,故呼應便捷。晚燃菜油燈,作楷八十四字。自數日前病感冒,傷風微嗽,今日仍未愈。口干鼻塞,喉緊聲啞,但精神如常。八時眠,夜間因樓上僧人足聲時作,未能安眠。
十二月一日,晴,微風,五十度。斷食前期第一日。疾稍愈,七時半起床。是日午十一時食粥二盂,紫蘇葉二片,豆腐三小方。晚五時食粥二盂,紫蘇葉二片,梅干一枚。飲冷水三杯,有時混杏仁露,食小橘五枚。午后到寺外運動。
余平日之常課,為晨起冷水擦身,日光浴,眠前熱水洗足。自今日起冷水擦身暫停,日光浴時間減短,洗足之熱水改為溫水,因欲使精神聚定,力避冷熱極端之刺激也。對于后人斷食者,應注意如下:
(一)未斷食時練習多食冷開水。斷食初期改食冷生水,漸次加多。因斷食時日飲五杯冷水殊不易,且恐腹瀉也。
(二)斷食初期時之粥或米湯,于微溫時食之,不可太熱,因與冷水混合,恐致腹痛。
余每晨起后,必通大便一次。今晨如常,但十時后屢放屁不止。二時后又打嗝兒甚多,此為平日所無。是日書楷字百六十八,篆字百零八。夜觀焰口,至九時始眠。夜微嗽,多惡夢,未能入眠。
二日,晴和,五十度。斷食前期第二日。七時半起床,晨起無大便。是日午前十一時食粥一盂,梅一枚,紫蘇葉二片。午后五時同。飲冷水三杯,食橘子三枚,因運動歸來體倦故。是日舌苔白,口內粘滯,上牙里皮脫。精神如常,但過則疲□□。運動微覺疲倦,頭目眩暈。自明日始即不運動。
晚侍和尚念佛,靜坐一小時。寫字百三十二,是日鼻塞。摹“大同造像”一幅,原拓本自和尚假來,尚有三幅,明后續□□。八時半眠,夜夢為升高跳越運動。其處為器具拍賣場,陳設箱柜幾椅并玩具裝飾品等。余跳越于上,或騰空飛行于其間,足不履地,靈捷異常,獲優勝之名譽。旁觀有德國工程師二人,皆能操北京語。一人謂有如此之技能,可以任遠東大運動會之某種運動,必獲優勝。余遜謝之。一人謂練習身體,斷食最有效,吾二人已二日不食。余即告余現在虎跑斷食,亦已預備二日矣。其旁又有一中國人,持一表,旁寫題目,中并列長短之直紅線數十條,如計算增減高低之表式,是記余跳越高低之順序者。是人持以示余,謂某處由低而高而低之處,最不易跳越,贊余有超人之絕技。后余出門下土坡,屢遇西洋婦人,皆與余為禮,賀余運動之成功,余笑謝之。夢至此遂醒。余生平未嘗為一次運動,亦未嘗夢中運動,頭腦中久無此思想,忽得此夢,至為可異,殆因胃內虛空,有以致之歟?
三日,晴和,五十二度。斷食前第三日。七時半起床。是晨覺微餓,胸中攪亂,苦悶異常,口干,飲冷水。勉坐起披衣,頭昏心亂,發虛汗作嘔,力不能支,仍和衣臥少時。飲梅茶二杯,乃起床,精神疲憊,四肢無力。九時后精神稍復元,食橘子二枚。是晨無大便,飲藥油一劑,十時半軟便一次,甚暢快。十一時水瀉一次,精神頗佳,與平常無大異。十一時二十分食粥半盂,梅一個,紫蘇一枚。摹“普泰造像”“天監造像”二頁。飲水、食物,喉痛,或因泉水性太烈,使喉內脫皮之故。午后四時,飲水后打嗝,食小梨一個,五時食粥半盂。是日感冒傷風已愈,但有時微嗽。是日午后及晚,侍和尚念佛,靜坐一小時。八時半眠。入山預斷以來,即不能為長時之安眠,旋睡旋醒,輾轉反側。
四日,晴和,五十三度。斷食前第四日。七時半起床。是晨氣悶,心跳,口渴,但較昨晨則輕減多矣,飲冷水稍愈。起床后頭微暈,四肢乏力。食小橘一枚,香蕉半個。八時半精神如常,上樓訪弘聲上人,借佛經三部。午后散步至山門,歸來已覺微疲。是日打嗝兒甚多,口時作渴,共飲冷水四大杯。摹“大明造像”一頁。寫楷字八十四,篆字五十四。無大便。四時后頭昏,精神稍減,食小橘二枚。是日十一時飲米湯二盂,食米粒二十余。八時就床,就床前食香蕉半個。自預備斷食,每夜三時后腿痛,手足麻木。(余前每逢嚴冬有此舊疾,但不甚劇。)
五日,晴和,五十三度。斷食前第五日。七時半起床。是夜前半頗覺身體舒泰,后半夜仍腿痛,手足麻木。三時醒,口干,心微跳,較昨減輕。食香蕉半個,飲冷水稍眠。六時醒,氣體甚好。起床后不似前二日之頭暈乏力,精神如常,心胸愉快。到菜園采花供鐵瓶。食梨半個,吐渣。自昨日起,多寫字,覺左腰痛。是日腹中屢屢作響,時流鼻涕,喉中腫爛尚未愈。午后侍和尚念經,靜坐一小時,微覺腰痛,不如前日之穩靜。三時食梨半個,吐渣。食香蕉半個。午、晚飲米湯一盂。寫字百六十二。傍晚精神稍佳,惡寒口渴。本定于后日起斷食,改自明日起斷食,奉神詔也。
斷食期內,每日飲梨汁一個之分量,飲橘汁三小個之分量,飲畢漱口。又因信仰上每晨餐神供生白米一粒,將眠,食香蕉半個。是日無大便,七時起床。是夜神經過敏甚劇,加以鼠聲入鼾聲,終夜未安眠。口甚干,后半夜腿痛稍輕,微覺肩痛。
六日,暖晴,晚半陰,五十六度。斷食正期第一日。八時起床。三時醒,心跳胸悶,飲冷水橘汁及梅茶一杯。八時起床,手足乏力。頭微暈,執筆作字殊乏力,精神不如昨日。八時半飲梅茶一杯。腦力漸衰,眼手不靈,寫日記時有誤字,多遺忘。九時半后精神稍可。十時后精神甚佳,口渴已愈。數日來喉中腫爛亦愈。今日到大殿去二次,計上下二十四級石階四次,已覺足乏力,為以前所無。是日共飲梨汁一個,橘汁二個。傍晚精神不衰,較勝昨日,但足乏力耳。仍時流鼻涕,晚間精神尤佳。是日不覺如何饑餓。晚有便意,僅放屁數個,仍無便。是夜能安眠,前半夜尤穩安舒泰。眠前以棉花塞耳,并誦神人合一之旨。夜間腿痛已愈,但左肩微痛。七時就床,夢變為豐顏之少年,自謂系斷食之效。
七日,陰復晴,夜大風,五十四度。斷食正期第二日。六時半起床。四時醒,心跳微作即愈,較前二日減輕。飲冷水甚多。六時半即起床,因是日頭暈已減輕,精神較昨日為佳,且天氣甚暖故早起床也。起床后飲橘汁一枚。晨覽《釋迦如來應化事跡圖》。八時后精神不振,打哈欠,微寒,流鼻涕,但起立行動如常。午后身體寒益甚,擁被稍息。想出食物數種,他日試為之。炒餅、餅湯、蝦仁豆腐、蝦子面片、什錦絲、咸胡瓜。三時起床,冷已愈,足力比昨日稍健。是日無大便,飲冷水較多。前半夜肩稍痛,須左右屢屢互易,后半夜已愈。
八日,陰,大風,寒,午后時露日光,五十度。斷食正期第三日。十時起床。五時醒,氣體至佳,如前數日之心跳頭暈等皆無。因天寒大風,故起床較遲。起床后精神甚佳,手足有力,到院內散步。四時半就床,午后益寒,因早就床。是日食欲稍動,有時覺饑餓,并默想各種食物之種類及其滋味。是夜安眠,足關節稍痛。
九日,晴,寒、風,午后陰,四十八度。斷食正期第四日。八時半起床。四時醒,氣體極佳,與常日無異。起床后精神如常,手足有力。朝日照入,心目豁爽。小便后尿管微痛,因飲水太多之故。自今日始不飲梨橘汁,改飲鹽梅茶二杯。午后因飲水過多,胸中苦悶。是日午前精神最佳,寫字八十四,到菜圃散步。午后寒,一時擁被稍息。三時起床,室內運動。是日不感饑餓。因天寒,五時半就床。
十日,陰,寒,四十七度。斷食正期第五日。十時半起床。四時半醒,氣體精神與昨同。起床后精神至佳。是日因寒故起床較遲。今日加飲鹽湯一小杯。十一時楊、劉二君來談至歡。因寒四時就床。是日寫字半頁。近日精神過敏已稍愈,故夜間較能安眠。但因昨日飲水過多傷胃,胃時苦悶,今日飲水較少。
十一日,陰寒,夕晴,四十七度。斷食正期第六日。九時半起床。四時半醒,氣體與昨同。夜間右足微痛,又胃部終不舒暢。是日口干,因寒起床稍遲。飲鹽湯半杯,飲梨汁。夕晴,心目豁爽。寫字百三十八。坐檐下曝日,四時就床,因寒早就床。是晚感謝神恩,誓必皈依。致福基書。
十二日,晨陰,大霧,寒,午后晴,四十八度。斷食正期第七日。十一時起床。四時半醒,氣體與昨同,足痛已愈,胃部已舒暢。口干,因寒不敢起床。十一時福基遣人送棉衣來,乃披衣起。飲梨汁及鹽湯、橘汁。午后精神甚佳,耳目聰明,頭腦爽快,勝于前數日。到菜圃散步。寫字五十四。自昨日始,腹部有變動,微有便意,又有時稍感饑餓。是日飲水甚少。晚晴甚佳,四時半就床。
十三日,晨半晴半陰,后晴和,多風,五十四度。斷食后期第一日。八時半起床。氣體與昨同。晨飲淡米湯二盂,不知其味,屢有便意,口干后愈,飲梨汁橘汁。十一時飲濃米湯一盂,食梅干一個,不知其味。十時服瀉油少許,十一時半大便一次甚多。便色紅,便時腹微痛,便后漸覺身體疲弱,手足無力。午后勉強到菜圃一次。是日不飲冷水。午前寫字五十四。是日身體疲倦甚劇,斷食正期未嘗如是。胃口未開,不感饑餓,尤不愿飲米湯,是夕勉飲一盂,不能再多飲。
十四日,晴,午前風,五十度。斷食后期第二日。七時半起床。氣體與昨同,夜間較能安眠。五時飲米湯一盂,口干,起床后精神較昨佳。大便輕瀉一次,又飲米湯一盂,飲橘汁,食蘋果半枚。是日因米湯、梅干與胃口不合,于十時飲薄藕粉一盂,炒米糕二片,極覺美味,精神亦驟加。精神復元,是日極愉快滿足。一時飲薄藕粉一盂,米糕一片。寫字三百八十四。腰腕稍痛,暗記誦《御神樂歌序章》。四時食稀粥一盂,咸蛋半個,梅干一個,是日不感十分饑餓,如是已甚滿足。五時半就床。
十五日,晴,四十九度。斷食后期第三日。七時起床。夜間漸能眠,氣體無異平時。擁衾飲茶一杯,食米糕三片。早食藕粉米糕,午前到佛堂菜圃散步,寫字八十四。午食粥二盂,青菜咸蛋少許。夕食芋四個,極鮮美。食梨一個,橘二個。敬抄《御神樂歌》二頁,暗記誦一、二、三下目。晚飲粥二盂,青菜咸蛋,少許梅干。晚食粥后,又食米糕飲茶,未能調和,胃不合,終夜屢打嗝兒,腹鳴。是日無大便。七時就床。
十六日,晴,四十九度。斷食后期第四日。七時半起床。晨飲紅茶一杯,食藕粉、芋。午食薄粥三盂,青菜、芋大半碗,極美。有生以來不知菜等之味如是也。食橘,蘋果,晚食與午同。是日午后出山門散步,誦《御神樂歌》,甚愉快。入山以來,此為愉快之第一日矣。敬抄《御神樂歌》七頁,暗記誦四、五下目。晚食后食煙一服。七時半就床,夜眠較遲,胃甚安,是日無大便。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