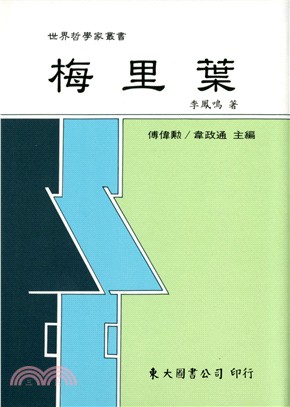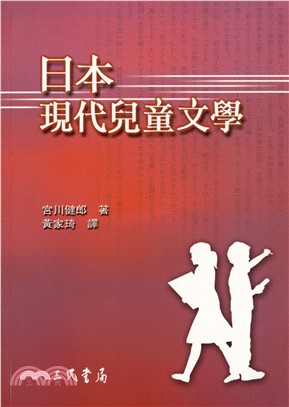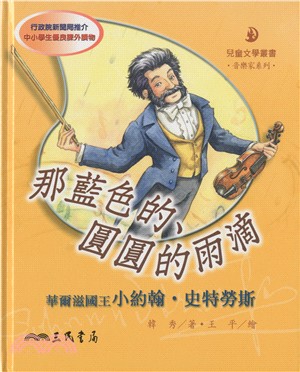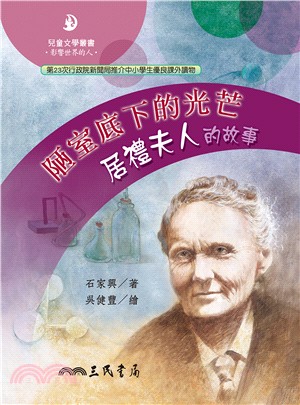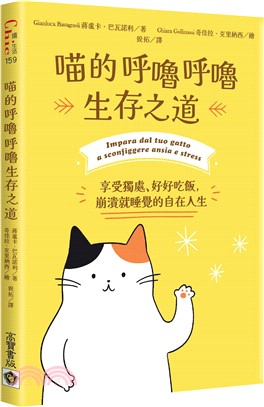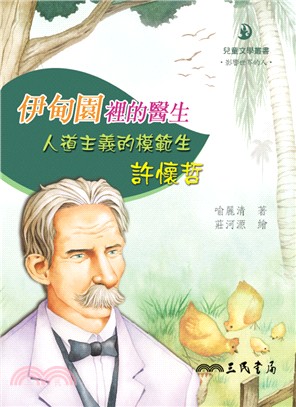新世紀小說大系2001-2010:記憶卷(簡體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張新穎
一
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人,有著什么樣的記憶?倘若把記憶的時間范圍限制在“現代”以來、直至今天的切身歷史中,我們的“現代記憶”可能會是什么樣的圖景?
顯然,這是一個過于龐大、繁雜的問題,千頭萬緒,剪不斷,理還亂。在這令人喟然興嘆不知從何說起的地方,文學卻一直活躍其間,往返穿梭,瞻前顧后,上究下探。這與其說是文學對于歷史的固執興趣,還不如說是文學自身的力量必然不可能不及物地自我消耗,歷史的領域也是它慣常活動的場所。
那么,為什么這一卷小說不命名為“歷史卷”,而叫做“記憶卷”呢?我們可以不用抽象地討論歷史與記憶的問題,而從所選的這些文學作品出發,來感知記憶與歷史之不同,以及記憶與文學之間更加密切的關系。我只想簡單地提及一點,記憶是具體的生命的記憶,哪怕是集體記憶,也是具體的生命的集體記憶,對于歷史來說無關緊要的記憶,對于具體的生命來說卻可能意義重大。慣常理解的歷史所具有的客觀性、規律性一類的東西,對于“歷史題材小說”的敘述可能構成壓抑,甚至先在地決定了小說敘述的視角、結構、進程等等,記憶卻不是壓抑、束縛文學敘述的東西,反倒可能成為啟動文學敘述直至敘述完成的力量。有時候甚至可以說,記憶并不外在于文學敘述,而是與文學敘述一同產生出來的。
記憶比歷史更“感性”,與文學更親近。
二
遺忘是記憶的對立面,還是記憶本身固有的一種屬性?《武昌城》“重現”一九二六年的圍城戰役,即是從遺忘的深層發掘塵封的慘烈記憶。按理說,過去才八十幾年,不會忘得太厲害吧;事實卻是,“現在的武漢人差不多都不知道這段歷史。”方方在二〇〇六年寫成圍城的中篇(即本卷選入的這篇),“最簡單的目的,就是想告訴大家,在我們居住的地方,曾經有過這樣的往事。這是我們應該記住的事情。”二〇一〇年方方再接再厲,又寫攻城的中篇。一守一攻,合并成書,仍舊命名為《武昌城》。這個命名是對一個記憶的堅持:武昌以前是有城的;千年城墻的歷史在武昌戰役之后消失了,但當年的守城和攻城不應該從歷史中刪除。“我曾經問過很多人,你知道武昌城的事嗎?回答仿佛統一過口徑:不知道呀。有一天,我站在大東門,望著蛇山和長春觀的屋頂,心想,你們是知道的。你們都親眼見過那慘烈的場景,你們的身上甚至浸染過血跡。但你們卻只是默然。”記憶曾經存在過,“默然”的記憶等待著打破沉默無語的狀態,開口說話,敘述曾經發生過的一切。
北伐戰爭中的武昌一役,前后四十天,死亡無數。方方關注的重心,不是歷史的進與退,戰爭的成與敗,而是一個個具體生命的遭遇,是具體的人的創痛和命運,具體的人的選擇和代價。“守城和攻城,各有自己的角度,各有自己對事情的看法,也各有自己的痛苦和悲傷。戰爭將人性中的大善大惡都張揚了出來。我相信,無論革命軍還是北洋軍,當兵從武,有人是為了解決饑餓,有人是為了反抗壓迫,有人是因為天性尚武,也有人就是無可奈何。但亦有一些人,為的就是理想。這理想便是希望中國有個美好的未來,希望參與自己的一己之力讓自己的國家和平安寧。”一座城市的記憶,承載了多少生死傷痛的重量。
遲子建的《起舞》,從眼前的現實展開,通向的也是一座城市——哈爾濱——的特殊記憶。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經歷、情感、氣質和這座城市的身世、風俗、人情、文化交織在一起,互相呼應互相闡發,隱秘的記憶和踏實的人生相銜接,百感交集之處雖然不免傷感,卻在傷感之上始終洋溢著對于生活的熱情、對于美好事物的執著。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新世紀的今天,這座北國城市的外在歷史自有敘述,可是它的“秘史”,一部分也許就藏在從齊如云到丟丟這些普通人的內心里。
魏微的《大老鄭的女人》寫的是一個小城,寫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這個小城的風習演變,寫時代的訊息一點兒一點兒具體落實到這個古城的日常生活中,寫這個過程中的人情世故、人心冷暖,人事和背景是不分前后主次的,你可以說小說的主角是大老鄭和他的女人,也可以說是“我們”,更可以說是這個小城。敘事細致、耐心、不驚不乍,好像對一點一滴都懷著珍惜的心情,都要留存在文字中;不然的話,關于小城的記憶,還能保存在哪里呢?
白樺的《藍鈴姑娘》是云南邊地傳奇,這樣的作品在當代文學中很少見到,現代作家中沈從文奇異的湘西故事或許有可以參照比較之處。白樺一九五。年隨先遣部隊進入云南,其時邊地風物千年未改,“地理位置決定了他們的荒蕪和神秘。當時,我對那里的人和事既感到新奇而且難以理解,許多民族都生活在一些大小頭人割據的山谷里,保持著各自的奇風異俗和宗教信仰,多神論的巫師們還決定著大多數民族的精神生活。”可堪尋味的是,當年騎馬訪問少數民族集聚區的生活經驗,六十年后方才化為文字。記憶仿佛需要一個緩慢的發酵過程,緩慢得仿佛沉睡了一般,等待著合適的機緣把它喚醒。“文革”以后,白樺再次訪問云南,“邊地過去和現在的一切,忽然奇跡般鮮活和清晰起來。”醒來之后的記憶,已經和最初的狀態不同了,因為攜帶著記憶的人已經歷盡滄桑,過去感覺神秘莫測的人事已然可以理解。但記憶卻并沒有褪色,白樺筆下的傳奇故事凄美哀艷,色彩鮮明,人物感情強烈,一派梅里美式的浪漫風格。
阿來《遙遠的溫泉》寫的是藏區今昔生活,上篇是“我”的少年時代,溫泉存在于“花臉”的描述中,存在于少年夢境般美麗的想象中;下篇是如今的現實,“我”終于見到了溫泉,卻已經被糟蹋和摧毀了。這不是簡單地批判現代的開發和改造,而是對于美好想象的源泉被輕易毀壞的憤怒和痛心。那種美好的向往、渴望和想象曾經怎樣地滋養和豐富了一個少年的生命,記憶知道;可是現實要抹去這種記憶,抹去這種對美好的向往、渴望和想象,而代之以貧乏、庸俗、丑陋和野蠻。當貧乏、庸俗、丑陋和野蠻不再僅僅是一種樣態,而且還變成了一種力量——一種時代性的力量——的時候,它們真是肆無忌憚到什么都敢去毀壞的程度了。
三
二十世紀中國有若干個重要的歷史時期,我們根據重大的歷史事件為這些時期命名,這些命名早就變成了歷史敘述中的日常詞語,這些命名的詞語被反復、大量地使用,以至于這些詞語似乎就可以代替它們所指稱的歷史,或者說,歷史被名詞化了,歷史被風干成了符號。在通常的歷史書寫之外,那些普通人的生存和遭遇呢?那些具體的、一個個不同的人的哭笑吃喝、生死哀樂呢?正是在這樣的地方,需要記憶,需要文學承載比符號化的歷史豐富得多的記憶。如果說文學比歷史更真實,也正可以從這一點上來理解。
楊顯惠的《定西孤兒院紀事》,寫的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甘肅定西大饑荒造成的人口大量死亡,觸目驚心之筆,迫使你不能不正視,不能不對把大饑荒的災難當成記憶的幻影或者傳說的遺忘機制有所警惕和質疑;《獨莊子》是這個系列中的一篇。畢飛宇的《玉米》寫七十年代一個年輕農村女性的經歷和命運,不動聲色的敘述,卻給人以強烈的震撼。《玉米》之后,畢飛宇又寫了《玉秧》和《玉秀》,組成一個系列。
蘇童《騎兵》里的男孩和嚴歌苓《拖鞋大隊》里的少女,他們少不更事的成長經驗,表面看去似乎不足以對應嚴酷的年代,其實卻在自覺不自覺中深深打上了特殊時代的印記。他們的感受和記憶,也“豐富”、“充實”了那個時代——并非是在反諷的意義上才這樣說。
四
有變化才有記憶,變化的幅度構成記憶的幅度。現代中國接連不斷的劇烈變化,給個體生命帶來巨大的經驗空間,這個空間同時也就是記憶的空間。倘若記憶又有相當的長度,長度里面包含了曲折的過程,那么,這樣的記憶的“總量”,就不是一般的短時期記憶所可比擬的了。
賈平凹的《藝術家韓起祥》寫一個民間藝人大半生的故事。韓起祥原來是陜北流浪的說書人,被收編到延安邊區文工團后,“三弦藝人”的身份中逐漸加重了“三弦戰士”的成分。新中國成立后先是作為革命干部進駐西安,后來又調任北京,舉凡重大活動需要演出,必說《翻身記》。反右時期回住延安,命運隨著時代起起落落。臨死前聽師兄三弦說書,不聽新詞,要聽土的,“三弦說書就是土圪垃里生出來的,說土的好。”韓起祥身份的轉換和命運的變化,能夠引出許多關聯性的問題,譬如意識形態對民間藝術的吸收和改造。文化、藝術、個人和時代的關系,從延安開始直到“文革”結束的文化運作過程,等等。最令人感慨的,還是個人本非所愿、卻又無能為力地被時代裹挾著走,常常無所適從,不知所之。
莫言的《變》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份自敘傳吧:從一九六九年寫起,此后的四十年間,從小學生到工廠臨時工,到參軍當兵,到發表文學作品,到考進解放軍藝術學院,到成就大名及其之后的生活,變化何其多,何其大,何其迅速,似乎出其不意,又似乎合乎邏輯和情理。半生經歷,自是一份漫長的記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回憶過往時的那種感受和狀態:記憶與記憶的主體融而為一。小說就是在這種感受中開始的:“……我的思緒,卻總是越過界限,到達一九六九年秋天那個陽光明媚,菊花金黃,大雁南飛的下午。至此,我的回憶便與我混為一體。我的記憶,也就是當時的我,一個被趕出學校的孤獨男童……”
宗璞《四季流光》的時間跨度更長。時間能夠慢慢累積意義和價值,時間也會一點一滴地銷蝕和侵吞生命。“生命的酒釀不斷地一滴一滴消失/生命的樹葉不停地一片一片飄落”,宗璞借《魯拜集》里的詩句,發出悠長而感傷的喟嘆。《四季流光》寫四個女生,從五十年前寫起,中間她們經歷了社會和時代的變遷,在變遷中遭遇各種苦難,到最后,在衰老和疾病中安度殘生,而有的已經先行去了另一個世界。時代和社會強加到人身上的劫難和對于個體生命的摧殘,對于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對于帶著這種經歷走進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來說,實在是一個很熟悉的話題,也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中國當代文學里的敘述也屢見不鮮。但是,文學怎樣來敘述歷史記憶和苦難,仍然是一個需要深思的問題。理論和思想的力量誠然巨大,個人遭遇的直接性、生命的血肉之痛,對于時代和歷史的刺穿卻也無可替代。《四季流光》寫這四個女生半個多世紀的坎坷波折,并不多么用力于理論的反思和批判,相反,多的是感慨,傷懷,是不甘心又無可奈何:多么美好的生命,就在這樣那樣的情形下,一點一點消失,走到了盡頭。筆調溫婉而憂傷,一句一句訴說著四季女兒,一個一個從“公主”的花團錦簇的熱鬧中走出來,越走花朵越少,越走樹葉越少,花也少葉也少,只剩個自己,而自己所剩的時間也越來越少。用柔弱的生命和生命的變化去直接面對歷史和苦難,用生命盡頭的感傷和感傷中的質問去直接面對時代和遭遇,似乎力量不成對比,其實卻也可能造成力量對比的反轉。 林白一直就是執著于個人記憶的作家,《長江為何如此遠》以大學畢業三十年后的同學聚會為引線,穿插回憶大學生活,卻不僅僅是寫記憶,而是要在對記憶的敘述中嚴厲審視、反省自己過去的生活,特別是審視和反省那個“個人”,那個有些封閉的、自私的、冷漠的、不懂人情世故也不屑于去懂的“自我”。記憶不是自戀的一種方式,而是反省自戀的對象和依據。對比林白早期的代表作《一個人的戰爭》,可以感受到極其明顯的變化。其實從《萬物花開》開始,林白的創作明確地表明了她已經從孤立的個人世界走向了更加寬闊的生活世界。《長江為何如此遠》把這種變化過程中的嚴厲的自我反省,具體化為一種文學敘述,坦誠真切地呈現了出來。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目次
張新穎 二十一世紀初中國人的“現代記憶”
方方 武昌城
賈平凹 藝術家韓起祥
宗璞 四季流光
遲子建 起舞
白樺 藍鈴姑娘
楊顯惠 獨莊子
阿來 遙遠的溫泉
嚴歌苓 拖鞋大隊
畢飛宇 玉米
蘇童 騎兵
魏微 大老鄭的女人
莫言 變
林白 長江為何如此遠
附錄:長篇存目
《新世紀小說大系200l—2010》總目錄
書摘/試閱
城里人扛著行李拿著包袱,匆匆朝城外奔走。人碰著人,一個個繃著臉,惶惶然一副神態,卻不怎么出聲。喜云覺得奇怪,問母親,他們做什么?母親說,少管閑事!喜云說,逃跑嗎?母親又說,叫你少管閑事。喜云說,城里人會不會跑光?母親說,哪來這么多話?找到你爹,得讓他好好管教你。
喜云的母親牽著弟弟喜子。喜子只有六歲。喜子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多人,他很喜歡這樣的熱鬧。喜子說,我好喜歡武昌啊。有人高聲吆喝,讓開讓開!喜子也學著那聲氣叫喊。喜云給了他一小巴掌,說你討打呀。喜子便縮著頭,不吭氣了。
一溜黃包車呼呼地過來,像個車隊。車上面堆著箱籠。箱籠上貼著封條,寬寬的。有個洋氣的小姐,坐在最后一輛車上。她大聲地說話,聲音很是尖細。快點呀,趕不上這趟船老爺饒不了你們。車夫說,大小姐,人太多,走不動呀。小姐說,走不動也要快。
喜云發呆地看那小姐。她想城里的小姐真是漂亮。喜子眼光也落在小姐身上。黃包車走過了,他還扭著看,把小小的身子扭成根麻花。喜子說,我們也坐車好不好?姐姐。城門好大呀,姐姐。爹爹會在這個城門上嗎?姐姐。喜云說,看著路走!爹爹的城門比這個還要大。
母親拽了一把喜子,說喜子,你好好走路。說罷又回頭斥了一句,喜云你跟好我!走丟了,你就活不成,世道這么亂!喜云被母親說得嚇住,趕緊加快步子,緊緊地貼在母親的身后。
喜云對父親幾乎沒有印象。她只知道父親在外面打仗。每年爺爺奶奶都要燒高香保佑父親不要被子彈打死。在村里,只要有人欺負喜子,喜云都會大聲說,你敢碰我家喜子一根手指頭,我就讓我爹爹開槍打死你。
一天清早,土匪摸進村子。搶光了村頭三爺家所有的東西,當著全村人燒掉了他們的房。三爺是村里的大戶。三爺的兒子福生跟喜云頂熟,常拿著喜云開心。福生愛說,咱這村就喜云長得俊,趕明兒嫁給我好了。喜云最煩他這么說,每次都回嘴道,做你的大頭夢,我跟你沒出五服。就是這個福生,擋著不讓土匪欺負他媽,結果被砍了頭。砍他的是個麻臉人。他揚手一揮刀,福生就身首兩處,腦袋一直滾到輾子底邊。這一幕全村人都看得發傻。喜云藏在爺爺背后,一泡尿憋不住,屙在了褲子上。后來她發現,村里很多人的腳下都像她一樣濕了一攤,包括爺爺。
爺爺和奶奶一夜沒合眼。第二天一早就逼著母親把喜云和喜子帶走。爺爺說,不能這么等死。喜云母親說,外面兵荒馬亂,逃出去未必能活。往后宗春回來見咱甩了老人不伺候,會怎么罵我?爺爺怒道,土匪再來你咋辦?你想當福生的媽呀!福生的媽被三個土匪奸污了。土匪一走,她就跳了井。奶奶也罵,說你想死不打緊,我孫子孫女兒不能死。爺爺說,找宗春去!他是當兵的,手上有槍。這世道,你們娘兒幾個也就只有拿槍的人保護得著。喜云也百般不想出門。黃昏時,跟喜子兩個,坐在村頭的大碾子上唱歌,一直把太陽唱落,把星星唱出來,這是比什么都快樂的事。爺爺一巴掌甩在喜云臉上。爺爺吼道,你想死在這里?你沒見土匪怎么殺福生的?你白尿了?
喜云母親沒奈何,立馬打點包袱,帶上父親新近的家書,扯著喜云和喜子出了門。喜云母親只知道,她的丈夫在武昌。
武昌城里的大街小路,到處是大兵晃來晃去。東邊口哨響,一干當兵的踢踢踏踏往東跑。西邊哨聲響,另一干當兵的又踢踏著往西跑。城里混亂得讓人害怕。拉車的挑擔的抬轎的,都朝城門奔走,仿佛有天大的事即將發生。只有一兩個乞丐,坐在墻角,依然見人伸手討要。乞討聲慵懶哀傷,像以往一樣。走過他們身邊,聽那聲音,心會凜然一靜。恍惚之間,以為這世上什么事都沒發生。
一個挑擔老頭迎面過來。喜云的母親扯著問,他大爺,出了什么事?老頭瞪著喜云母親,說外鄉來的?喜云的母親說,是呀,來找孩子他爹。老頭立即喊出了聲,這時候找人?找死差不多。趕緊跑吧!要打仗了。喜云說,我們不怕,我爹就是帶兵打仗的。喜云的母親抬手拍打喜云的頭,說沒讓你講話。老頭臉色就變了,說嗬嗬,嗬嗬,北軍的?好好的不在老家窩著,到這里生什么事?
老頭說完,挑著擔子自顧自地走了。喜云說,爺爺說過,我爹一打仗就朝前沖,他一定在這里。喜子高興叫了起來,姐姐,我也要跟爹一起打仗。喜云的母親臉色很難看,她狠狠地說了一句,你們倆閉嘴!
P4-6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