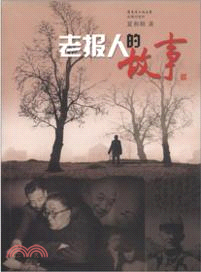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儲安乎、王芸生、羅隆基、浦熙修、徐鑄成、聶紺弩、趙超構、蕭乾、楊剛、范長江、鄧拓、惲逸群,是中國新聞史上、報業史上熠熠閃光的明星。他們形形色色,或左或“右”。在舊時代,他們都不失為敢於向強權抗爭與揭露社會不公的鬥土;而進入新社會之後,面對新問題,他們不約麗同地感覺到彷徨、困惑……作者以凝重冷靜的史家筆墨,展現了他們的個性與才情以及在時代風雲變幻下起伏跌宕的個人命運和心路歷程。十二個人的悲情人生,是那段歷史的最好見證。.
作者簡介
夏和順,安徽郎溪人,安徽師範大學文學學士,中山大學文學碩士。媒體從業人員,現供職於深圳某報。近年從事自由主義文化傳統、嶺南文化等領域的研究。著有《葉啟芳傳一一從教堂孤兒到知名教授》(合著)、《全盤西化台前幕後一一陳序經傳》、《容庚傳》(合著)等,與人合編過《深圳九章》等。.
名人/編輯推薦
夏和順,1964年出生,安徽郎溪人。安徽師范大學文學學士,中山大學文學碩士。媒體從業人員,供職于深圳某報。近年從事自由主義文化傳統與嶺南文化研究,曾合作編寫《深圳九章》,著有《葉啟芳傳》(合著,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全盤西化臺前幕後——陳序經傳》(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等。
其創作的《老報人的故事》以凝重冷靜的史家筆墨,展現了他們的個性與才情以及在時代風云變幻下起伏跌宕的個人命運和心路歷程。
其創作的《老報人的故事》以凝重冷靜的史家筆墨,展現了他們的個性與才情以及在時代風云變幻下起伏跌宕的個人命運和心路歷程。
序
從馬克思、列寧開始,共產主義運動就十分重視報紙工作,十分重視輿論導向。就說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不但有延安《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這樣公開的機關報,還派了一些像夏衍、黎澍這樣高明的宣傳干部去辦左傾的“民營報紙”,還要一些隱蔽的黨員去辦色彩不那么鮮明的報紙。這樣還不夠,統一戰線工作在新聞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像《大公報》、《文匯報》、《新民報》這些很有影響的報紙,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有時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爭取到它們在輿論宣傳上的配合。能夠做到這一點,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報紙的負責人,乃至編輯記者,許多都是有愛國心的、有正義感的、有進步傾向.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對他們頗具吸引力,能夠接受共產黨的宣傳,這樣,統戰工作就奏效了。這些黨外報紙也就心甘情愿地為共產黨作宣傳。例如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新民報》首發了毛澤東的《沁園春》詞,為他在文化人中間吸引了一批仰慕者。內戰爆發,它們的同情在共產黨這一方,國民黨越來越看出它們的敵意,終于把它們封禁了。
當時,國民黨當局對于《新華日報》的發行寄遞竭力加以阻撓,有機會看到的人是很有限的。每日每時影響著廣大知識界(主要是青年學生)、工商界和一般市民的,是《大公報》、《文匯報》、《新民報》這些報紙。共產黨就是通過這些報紙把自己的主張透露出去。1949年人們對共產黨的勝利持歡迎態度,這些報紙在爭取人心方面是起了作用的。
共產黨在內戰~中獲勝了原來被國民黨政府查封的報紙刊物復刊了,這當然是極可欣慰的事情。可是,要怎樣辦報辦刊才能適應新時代的問題,就擺在這許多老報人的面前了。
時代變了,環境變了,這些報人的地位會有怎樣的變化呢?這里且舉一件小事為例。我沒有去查考過,也不知道是從哪一年開始,每年9月1日被宣布為“記者節”,好像這節日并不是國民黨政府決定的,而是記者們公議決定的。但是可以確定地說,共產黨是承認過這個節日的。某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報》的社論,標題就是《紀念我們自己的節日》。我記得,每逢記者節,就有記者們的集會,并且發表一些保障記者權益的宣言或聲明之類。新中國成立,這記者節就被取消了:大約是1 950年8月某日,總之是記者節前不久,報紙上刊登了一條新華社電訊宣布了這事。記不清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發言人的名義,還是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言人的名義宣布的。理由大約是說:現在解放了,新聞記者成了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五一勞動節也就是他們的節日,不必另設記者節了。當然,幾天之後的9月1日也就無聲無息地過去了。
(前一兩年吧,又宣布定某月某日為中國記者節了。對不住,我忘記定的是哪一天了。也不見有誰去反問:在五一勞動節之外另定一個記者節出來,是不是說要把記者從勞動人民中間分離出來呢?我知道的只是,這個新定出來的記者節,并不是保護新聞記者權益的節日,人們也不重視它,所以定的是何月何日我也想不起來了。)
一片落葉報道了秋天的來臨。記者節的廢除標志著新聞記者身價的跌落。老報人必須面對的新問題,是一個接一個地來到了。
丑950年春天,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召開了全國新聞工作會議。《文匯報》的徐鑄成在他的回憶錄里記下了他參加會議的觀感:“從此提出報紙要反對刊載社會新聞,不得發表抒發個人感情及黃色、迷信的報道和作品;反對‘資產階級辦報思想’,報紙宣傳要為黨的當前政策服務;新聞‘寧可慢些’,但要‘真實’。總之,一大套蘇聯模式的清規戒律確定下來了。”從這一段文字的語氣來看,他這位老報人對這種新精神是頗為抵觸的,他明白:他多年積累的經驗、習慣、業務知識,都已經不合時宜了。
這次會議制定了一個文件:《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關于改進報紙工作的決定》。其實就是那“一大套蘇聯模式的清規戒律”的教條文化。應該注意的是:實際上這個文件僅僅針對中央和地方各級共產黨的黨報。對于事實上還存在的少數幾家黨外報紙,文件并無一字涉及。這并不是忽略了這些報紙的特殊性,也不是起草文件的時候疏忽和遺漏了,而是覺得已經沒有必要寫上這一筆了,因為這時已經確定了將這些報紙消滅的方針。如果聽任這些報紙繼續存在,對于實現“輿論一律”是頗有妨礙的了。于是儲安平的《觀察》被新辦的一本命名為《新觀察》的刊物取代了,其實人員組成、刊物的內容、方向和原來的《觀察》毫無延續性,僅僅封面上的刊名還是用原來的字體。從此,那個鋒芒畢露的時評政論刊物就在中國的大地上消失了。《文匯報》呢,先是想把它改變成共青團的報紙,還是由胡喬木親自出面找徐鑄成談的。那時徐鑄成還沒有領會到上面已經下定消滅《文匯報》的決心,商談沒有成功,團中央于是創辦了一張《中國青年報》,而任《文匯報》茍延殘喘,那時《文匯報》的困境在徐鑄成的回憶錄里有清楚的反映:例如他記下了中共上海市委派了一個黨員來擔任副總編輯,這位仁兄很坦率地對人說:我來《文匯報》,就是來消滅《文匯報》的。最後呢,就是以一紙命令將《文匯報》改為教育部管的《教師報》了。
這里我可以插說一件我直接知道的事。1949年9月,我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報《新湖南報》社工作。當時長沙還有一份中國民主同盟的報紙《民主報》,我是親眼看見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承受的種種壓力,終于辦不下去,不久就停刊了。人員星散,有幾位還調到我們報社來了。
《文匯報》的復活,是在那個短暫的“不平常的春天”。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新方針,《人民日報》由每天4版擴大為8版,《文匯報》以原班人馬在上海復刊,一時顯出有意擴大知識分子發言的空間。可是和雪萊說的不一樣,春天來了,冬天就不遠了。這個“不平常的春天”實際上是那個肅殺的冬天——反右派斗爭的前奏曲。說來也有趣,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胡喬木寫的一篇重要的反右派社論,題目就是《不平常的春天》,這篇文章還曾經編入中學生的語文課本里。
對于新老報人來說,這場反右派斗爭真正是肅殺的冬天。這是當然的,毛澤東在表明他決心發動反右派斗爭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里,突出地提到了新聞界。他說:“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再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談到新聞界的右派分子,文章指摘說:“他們否認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他們混同無產階級新聞事業與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原則區別,他們混同反映社會主義國家集體經濟的新聞事業與反映資本主義國家無政府狀態和集團競爭的經濟的新聞事業。他們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反對黨的領導。”這罪名已經夠大了,還有更要命的呢:“新聞界右派還有號召工農群眾反對政府的跡象。”這就屬于犯罪的性質了。
在這篇文章里,再沒有對另外任何一個界別說得像新聞界這么重,這么多的了。在這篇文章之後,毛澤東還發表了兩篇批判《文匯報》的文章,足見他對新聞界狀況關注之深。在一定的意義上來說,反右派斗爭的目的之一,就是肅清報紙的資產階級方向。而這許多體現“資產階級方向”的老報人首當其沖,成了這一場斗爭的打擊對象。像儲安平、徐鑄成、浦熙修這些人,從此脫離了新聞界,不但不再是報人,甚至不再是享有人權和尊嚴的正常的人,被劃成“右派分子”了。
這些事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重要一章,雖說只是從新聞界這一個角度著眼,反映出來的卻是整個的歷史,這段歷史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夏和順先生有志于此,廣泛收集資料,寫出了12個老報人的經歷,寫出他們早年親共的態度和晚年悲慘的結局,是這段歷史最好的見證。
我原先讀過夏和順先生和他的老師易新農先生合著的《葉啟芳傳》(葉啟芳先生也是一位有著報人經歷的右派分子),十分佩服,曾經發表我的讀後感,也就因此同他有了交往。現在他的新著脫稿,給了我先讀的榮幸。并囑作序,我就趁此機會說一點自己對這一頁歷史的看法,并祝賀他新作的問世。
朱正2009年10月23日于長沙
當時,國民黨當局對于《新華日報》的發行寄遞竭力加以阻撓,有機會看到的人是很有限的。每日每時影響著廣大知識界(主要是青年學生)、工商界和一般市民的,是《大公報》、《文匯報》、《新民報》這些報紙。共產黨就是通過這些報紙把自己的主張透露出去。1949年人們對共產黨的勝利持歡迎態度,這些報紙在爭取人心方面是起了作用的。
共產黨在內戰~中獲勝了原來被國民黨政府查封的報紙刊物復刊了,這當然是極可欣慰的事情。可是,要怎樣辦報辦刊才能適應新時代的問題,就擺在這許多老報人的面前了。
時代變了,環境變了,這些報人的地位會有怎樣的變化呢?這里且舉一件小事為例。我沒有去查考過,也不知道是從哪一年開始,每年9月1日被宣布為“記者節”,好像這節日并不是國民黨政府決定的,而是記者們公議決定的。但是可以確定地說,共產黨是承認過這個節日的。某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報》的社論,標題就是《紀念我們自己的節日》。我記得,每逢記者節,就有記者們的集會,并且發表一些保障記者權益的宣言或聲明之類。新中國成立,這記者節就被取消了:大約是1 950年8月某日,總之是記者節前不久,報紙上刊登了一條新華社電訊宣布了這事。記不清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發言人的名義,還是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言人的名義宣布的。理由大約是說:現在解放了,新聞記者成了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五一勞動節也就是他們的節日,不必另設記者節了。當然,幾天之後的9月1日也就無聲無息地過去了。
(前一兩年吧,又宣布定某月某日為中國記者節了。對不住,我忘記定的是哪一天了。也不見有誰去反問:在五一勞動節之外另定一個記者節出來,是不是說要把記者從勞動人民中間分離出來呢?我知道的只是,這個新定出來的記者節,并不是保護新聞記者權益的節日,人們也不重視它,所以定的是何月何日我也想不起來了。)
一片落葉報道了秋天的來臨。記者節的廢除標志著新聞記者身價的跌落。老報人必須面對的新問題,是一個接一個地來到了。
丑950年春天,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召開了全國新聞工作會議。《文匯報》的徐鑄成在他的回憶錄里記下了他參加會議的觀感:“從此提出報紙要反對刊載社會新聞,不得發表抒發個人感情及黃色、迷信的報道和作品;反對‘資產階級辦報思想’,報紙宣傳要為黨的當前政策服務;新聞‘寧可慢些’,但要‘真實’。總之,一大套蘇聯模式的清規戒律確定下來了。”從這一段文字的語氣來看,他這位老報人對這種新精神是頗為抵觸的,他明白:他多年積累的經驗、習慣、業務知識,都已經不合時宜了。
這次會議制定了一個文件:《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關于改進報紙工作的決定》。其實就是那“一大套蘇聯模式的清規戒律”的教條文化。應該注意的是:實際上這個文件僅僅針對中央和地方各級共產黨的黨報。對于事實上還存在的少數幾家黨外報紙,文件并無一字涉及。這并不是忽略了這些報紙的特殊性,也不是起草文件的時候疏忽和遺漏了,而是覺得已經沒有必要寫上這一筆了,因為這時已經確定了將這些報紙消滅的方針。如果聽任這些報紙繼續存在,對于實現“輿論一律”是頗有妨礙的了。于是儲安平的《觀察》被新辦的一本命名為《新觀察》的刊物取代了,其實人員組成、刊物的內容、方向和原來的《觀察》毫無延續性,僅僅封面上的刊名還是用原來的字體。從此,那個鋒芒畢露的時評政論刊物就在中國的大地上消失了。《文匯報》呢,先是想把它改變成共青團的報紙,還是由胡喬木親自出面找徐鑄成談的。那時徐鑄成還沒有領會到上面已經下定消滅《文匯報》的決心,商談沒有成功,團中央于是創辦了一張《中國青年報》,而任《文匯報》茍延殘喘,那時《文匯報》的困境在徐鑄成的回憶錄里有清楚的反映:例如他記下了中共上海市委派了一個黨員來擔任副總編輯,這位仁兄很坦率地對人說:我來《文匯報》,就是來消滅《文匯報》的。最後呢,就是以一紙命令將《文匯報》改為教育部管的《教師報》了。
這里我可以插說一件我直接知道的事。1949年9月,我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報《新湖南報》社工作。當時長沙還有一份中國民主同盟的報紙《民主報》,我是親眼看見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承受的種種壓力,終于辦不下去,不久就停刊了。人員星散,有幾位還調到我們報社來了。
《文匯報》的復活,是在那個短暫的“不平常的春天”。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新方針,《人民日報》由每天4版擴大為8版,《文匯報》以原班人馬在上海復刊,一時顯出有意擴大知識分子發言的空間。可是和雪萊說的不一樣,春天來了,冬天就不遠了。這個“不平常的春天”實際上是那個肅殺的冬天——反右派斗爭的前奏曲。說來也有趣,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胡喬木寫的一篇重要的反右派社論,題目就是《不平常的春天》,這篇文章還曾經編入中學生的語文課本里。
對于新老報人來說,這場反右派斗爭真正是肅殺的冬天。這是當然的,毛澤東在表明他決心發動反右派斗爭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里,突出地提到了新聞界。他說:“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再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談到新聞界的右派分子,文章指摘說:“他們否認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他們混同無產階級新聞事業與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原則區別,他們混同反映社會主義國家集體經濟的新聞事業與反映資本主義國家無政府狀態和集團競爭的經濟的新聞事業。他們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反對黨的領導。”這罪名已經夠大了,還有更要命的呢:“新聞界右派還有號召工農群眾反對政府的跡象。”這就屬于犯罪的性質了。
在這篇文章里,再沒有對另外任何一個界別說得像新聞界這么重,這么多的了。在這篇文章之後,毛澤東還發表了兩篇批判《文匯報》的文章,足見他對新聞界狀況關注之深。在一定的意義上來說,反右派斗爭的目的之一,就是肅清報紙的資產階級方向。而這許多體現“資產階級方向”的老報人首當其沖,成了這一場斗爭的打擊對象。像儲安平、徐鑄成、浦熙修這些人,從此脫離了新聞界,不但不再是報人,甚至不再是享有人權和尊嚴的正常的人,被劃成“右派分子”了。
這些事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重要一章,雖說只是從新聞界這一個角度著眼,反映出來的卻是整個的歷史,這段歷史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夏和順先生有志于此,廣泛收集資料,寫出了12個老報人的經歷,寫出他們早年親共的態度和晚年悲慘的結局,是這段歷史最好的見證。
我原先讀過夏和順先生和他的老師易新農先生合著的《葉啟芳傳》(葉啟芳先生也是一位有著報人經歷的右派分子),十分佩服,曾經發表我的讀後感,也就因此同他有了交往。現在他的新著脫稿,給了我先讀的榮幸。并囑作序,我就趁此機會說一點自己對這一頁歷史的看法,并祝賀他新作的問世。
朱正2009年10月23日于長沙
目次
序 朱正前言一、“《大公報》已沒有必要恢復”:晚年王芸生之痛理想的夢最終會圓少年王芸生王芸生與革命王芸生與張季鸞王芸生與蔣介石王芸生與毛澤東王芸生與陳佈雷王芸生的新聞觀王芸生與《大公報》的結局晚年王芸生王芸生年表簡編二、“陽謀”盯上了徐鑄成“獨身主義”的終結《大公報》的洗禮《文匯報》的掌門人中國歷史嶄新的一頁“蘇聯套套只能老實學習”從“公私合營”到《教師報》親歷“陽謀”“不會有什麼萬一了”徐鑄成年表簡編三、儲安平:我要扛一扛風浪儲安平失蹤之謎新月派的後起之秀負笈英倫從《客觀》到《觀察》《觀察》為什麼被查封《觀察》的迴光返照出任《光明日報》總編向“党天下”進言感到無地自容儲安平年表簡編四、趙超構:軟些軟些再軟些識潮流的雜文家從《朝報》到《新民報》延安和重慶《新民報》之厄運進入新社會的代價“睡不著覺是好事”“老將”再次出馬趙超構年表簡編五、浦熙修:兩帥之間另一帥罐中的兩隻蟋蟀《新民報》的“浦二姐”“我願向他們傾訴一切”“你是坐過班房的記者”“我們應該加倍努力工作”《文匯報》的能幹女將“原來羅隆基是怕紅色”“看見了敞開的社會主義大門”浦熙修年表簡編六、羅隆基:應是良辰美景虛設政論家之大忌從安福到清華書生論政“我要我的兄弟都讀你的社論”政治活動家管木頭的部長“帥上有帥”羅隆基年表簡編七、蕭乾擠進新社會以後從右轉左,是福是禍?流浪少年與新聞結緣從抗日前線到歐洲戰場自由主義者的信念從“新路”向左轉在土地改革中學習“他原來是一條泥鰍”他的第二輩子蕭乾年表簡編八、是誰迫害了聶紺弩?特立獨行者的悲劇文化程度:高小短命副刊的編輯“真正的新聞記者”從特嫌到右派“注詩就是破案”“是淚是花還是血?”聶紺弩年表簡編九、楊剛與《大公報》的終結激情的火焰開始熄滅叛逆的女革命家“浩烈之徒”馳騁報界《大公報》的終結者像機器一樣工作理想主義的殉葬者楊剛年表簡編十、報界“彗星”惲逸群“倒黴人依然活著”“我們要和無恥抗爭”新聞快手與地下情報員大上海的報業巨頭最早中箭落馬者晚年的悲劇遭遇惲逸群年表簡編十一、鄧拓:文章滿紙書生淚書生辦報的末路史學天才選擇了革命紅色報人與毛澤東迷主政《人民日報》反冒進與“書生辦報”“雙百”方針與“死人辦報”“三家村”與鄧拓之死鄧拓年表簡編十二、天才記者遠離了新聞:范長江的幸與不幸他的才能究竟何在?茫然的青年探索者《大公報》的旅行記者延安窯洞的座上客紅色新聞的馬前卒新中國的接收大員失意的科技官員范長江年表簡編附錄一194901957年中國新聞大事記附錄二參考書目後記.
書摘/試閱
王蕓生先生的賢嗣王芝琛,以解放後培養出的理工科高才生的出身,出于對歷史負責的公心,當然也有為父親正名的私心,撰寫了《百年滄桑》和《一代報人王蕓生》這兩部著作,還公布了王蕓生臨終前的有關談話,才讓我們部分地認識到了歷史的原貌。
據說,王蕓生臨終前已大徹大悟,悔恨自己無論有多大壓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該寫那樣“自我討伐”式的長文,那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違心之作”。他臨終前對張季鸞之子張士基說:“《大公報》的歷史不能由我寫,我寫的那個不算數。”
王芝琛認為,其父當時實在頂不住壓力。他的壓力有多大?據說周恩來跟他談過三次話,最後一次告訴他,這是毛主席的意思。文人的傲骨終于在權力意志面前彎折了。
其實王蕓生也算是“自投羅網”,當年楊剛從美國回來,奉命跟他談《大公報》的轉向,楊剛雖是共產黨員,但也并沒有拿槍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對解放區的情況并非一無所知,他甚至看過延安的報紙關于王實味的報道。但他終于“向左轉”,他後來寫《和平無望》、《我到解放區來》和《大公報新生宣言》,很大程度上還是出于自愿。
為什么?因為他離不開這片生他養他的土地,因為他希望《大公報》能一路走下去。說到底,還是因為《大公報》的國家至上主義。
張季鸞過去常說:老記者如果不記就成“老者”了。1949年後的王蕓生徹底變成了“老者”,他知道“文人論政”已成明日黃花,他晚年甚至不愿再寫自傳和回憶錄。
但是王蕓生還算是幸運的,他在臨終前終于吐露了心聲,于後人這仍是一筆寶貴財富。在這里,我們不妨借用他在1948年記者節社評中的那句話:“理想的夢,最終會圓的。”
少年王蕓生
王蕓生生于1901年9月26日,河北靜海人,原名王德鵬。“蕓生”這個名字還是進天津《商報》當總編輯時介紹人信口說出來的。王蕓生常對人說:“蕓生者,蕓蕓眾生之謂也。”
王蕓生出生不久,因為家里破產,父親帶著他從靜海來到天津。他曾經流落到天津西頭芥園廟乞討,後來當過廚工。
王蕓生聰明伶俐,父母省吃儉用,讓他讀了私塾。1937年7月,年近不惑的王蕓生為《宇宙風》寫過一篇題為《一個挨打受罰的幼稚生》的回憶錄,他在文中說:“我是一個大城市邊上的鄉下人,近二十年來雖常生活在城市里,但總是脫不掉這份鄉下人的氣質,因此在這個社會里便不免如上海人所說有些‘吃不開’。人既然沒有出息,又不肯跟在有出息的人後面走,說話既不考慮人家愛不愛聽,做事又常帶著那份鄉下人呆頭呆腦的神氣。”
少年王蕓生有一個夢,就是進南開中學。南開中學是張伯苓先生在天津辦的一所中學,也是中國最有名的私立中學。但是他家里無力開銷昂貴學費。讀了8年私塾後,王蕓生便輟學了,他到一家茶葉店當學徒,白天干活,晚上讀一些中國古典小說。他將這些小說背得滾瓜爛熟,還常常給老鄰居“說書”,老鄰居們聽得津津有味。
正是在這家茶葉店,他讀到了《天津白話午報》,這是他最早接觸的報紙。後來他就到報欄去讀報,讀到的是《益世報》。久而久之,他萌生了給《益世報》投稿的念頭。
後來他又到北方木行當徒工,那里有間閱報室,有北京、上海、天津的各家大報紙。從此,他把工余時間一股腦兒地投入到這些報紙上。當時正值五四運動時期,科學與民主的呼聲喚醒了億萬青年。王蕓生從報刊上既讀到西方各種社會思潮,也讀到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人的文章,他還參加過聲勢浩大的游行。 他在1937年10月《大公報》出版的《蕓生文存·自序》中說:“我是五四時代的青年。五四開始啟迪了我的愛國心,五四使我接觸了新文化,五四給我的恩惠是深厚的……五四在我的心靈上的影響是終生不可磨滅的。”他還說:“五四運動給我打下一個做人的基礎。”
也是在這個木行,他第一次接觸到英文。強烈的求知欲使王蕓生產生學英文的念頭,正巧上海《申報》登出商務印書館函授學校招生廣告,學費約需40元。他硬著頭皮向木行副總經理借了40元錢。憑著一股頑強的精神,不長時間他就能閱讀一些英文書報了。不久他又參加天津新青年會英文補習夜校,學習英語發音。少年時期打下的英文基礎,對他今後的事業有很大幫助。
王蕓生與革命
在加入《大公報》之前,王蕓生曾經參加過國民黨,也參加過共產黨。他是憑著一股熱情,帶著對美好未來的向往參加革命的。但是他卻帶著失望退出了革命。
1927年6月2日,他在天津《大公報》第一版登出一則“王德鵬啟事”,聲明退出一切黨派,專心從事新聞工作。啟事說:“鄙人因感觸時變,早已與一切政團不發生關系,謝絕政治活動,唯從事著述,謀以糊口,恐各方師友不察,有所誤會,特此聲明。”
王蕓生是兩年以前參加革命的,他的辦報經歷也是那時開始的。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天津各界也紛紛聲援上海工人的斗爭。王蕓生參加天津洋行華員工會,并當選宣傳部長,主編工會出版的周刊。後來周刊改出日報,取名《民力報》,由王蕓生與一幫同仁合資經營,他仍任主編。他寫了大量反帝、支持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文章,他的文采開始令人刮目相看。
1925年底,他加入了國民黨。
1926年春天,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在平津一帶與奉直魯聯軍交戰。由于日本艦隊和各國使領館的介入,國民軍悄悄退出天津。3月22日,王蕓生不得不拋棄報館和家人,乘招商局的輪船離開天津逃到上海,他當時“既悲國家的遭際,復傷個人的孤零,且懼眼前的危險,心中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酸楚”。P2-4
據說,王蕓生臨終前已大徹大悟,悔恨自己無論有多大壓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該寫那樣“自我討伐”式的長文,那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違心之作”。他臨終前對張季鸞之子張士基說:“《大公報》的歷史不能由我寫,我寫的那個不算數。”
王芝琛認為,其父當時實在頂不住壓力。他的壓力有多大?據說周恩來跟他談過三次話,最後一次告訴他,這是毛主席的意思。文人的傲骨終于在權力意志面前彎折了。
其實王蕓生也算是“自投羅網”,當年楊剛從美國回來,奉命跟他談《大公報》的轉向,楊剛雖是共產黨員,但也并沒有拿槍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對解放區的情況并非一無所知,他甚至看過延安的報紙關于王實味的報道。但他終于“向左轉”,他後來寫《和平無望》、《我到解放區來》和《大公報新生宣言》,很大程度上還是出于自愿。
為什么?因為他離不開這片生他養他的土地,因為他希望《大公報》能一路走下去。說到底,還是因為《大公報》的國家至上主義。
張季鸞過去常說:老記者如果不記就成“老者”了。1949年後的王蕓生徹底變成了“老者”,他知道“文人論政”已成明日黃花,他晚年甚至不愿再寫自傳和回憶錄。
但是王蕓生還算是幸運的,他在臨終前終于吐露了心聲,于後人這仍是一筆寶貴財富。在這里,我們不妨借用他在1948年記者節社評中的那句話:“理想的夢,最終會圓的。”
少年王蕓生
王蕓生生于1901年9月26日,河北靜海人,原名王德鵬。“蕓生”這個名字還是進天津《商報》當總編輯時介紹人信口說出來的。王蕓生常對人說:“蕓生者,蕓蕓眾生之謂也。”
王蕓生出生不久,因為家里破產,父親帶著他從靜海來到天津。他曾經流落到天津西頭芥園廟乞討,後來當過廚工。
王蕓生聰明伶俐,父母省吃儉用,讓他讀了私塾。1937年7月,年近不惑的王蕓生為《宇宙風》寫過一篇題為《一個挨打受罰的幼稚生》的回憶錄,他在文中說:“我是一個大城市邊上的鄉下人,近二十年來雖常生活在城市里,但總是脫不掉這份鄉下人的氣質,因此在這個社會里便不免如上海人所說有些‘吃不開’。人既然沒有出息,又不肯跟在有出息的人後面走,說話既不考慮人家愛不愛聽,做事又常帶著那份鄉下人呆頭呆腦的神氣。”
少年王蕓生有一個夢,就是進南開中學。南開中學是張伯苓先生在天津辦的一所中學,也是中國最有名的私立中學。但是他家里無力開銷昂貴學費。讀了8年私塾後,王蕓生便輟學了,他到一家茶葉店當學徒,白天干活,晚上讀一些中國古典小說。他將這些小說背得滾瓜爛熟,還常常給老鄰居“說書”,老鄰居們聽得津津有味。
正是在這家茶葉店,他讀到了《天津白話午報》,這是他最早接觸的報紙。後來他就到報欄去讀報,讀到的是《益世報》。久而久之,他萌生了給《益世報》投稿的念頭。
後來他又到北方木行當徒工,那里有間閱報室,有北京、上海、天津的各家大報紙。從此,他把工余時間一股腦兒地投入到這些報紙上。當時正值五四運動時期,科學與民主的呼聲喚醒了億萬青年。王蕓生從報刊上既讀到西方各種社會思潮,也讀到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人的文章,他還參加過聲勢浩大的游行。 他在1937年10月《大公報》出版的《蕓生文存·自序》中說:“我是五四時代的青年。五四開始啟迪了我的愛國心,五四使我接觸了新文化,五四給我的恩惠是深厚的……五四在我的心靈上的影響是終生不可磨滅的。”他還說:“五四運動給我打下一個做人的基礎。”
也是在這個木行,他第一次接觸到英文。強烈的求知欲使王蕓生產生學英文的念頭,正巧上海《申報》登出商務印書館函授學校招生廣告,學費約需40元。他硬著頭皮向木行副總經理借了40元錢。憑著一股頑強的精神,不長時間他就能閱讀一些英文書報了。不久他又參加天津新青年會英文補習夜校,學習英語發音。少年時期打下的英文基礎,對他今後的事業有很大幫助。
王蕓生與革命
在加入《大公報》之前,王蕓生曾經參加過國民黨,也參加過共產黨。他是憑著一股熱情,帶著對美好未來的向往參加革命的。但是他卻帶著失望退出了革命。
1927年6月2日,他在天津《大公報》第一版登出一則“王德鵬啟事”,聲明退出一切黨派,專心從事新聞工作。啟事說:“鄙人因感觸時變,早已與一切政團不發生關系,謝絕政治活動,唯從事著述,謀以糊口,恐各方師友不察,有所誤會,特此聲明。”
王蕓生是兩年以前參加革命的,他的辦報經歷也是那時開始的。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天津各界也紛紛聲援上海工人的斗爭。王蕓生參加天津洋行華員工會,并當選宣傳部長,主編工會出版的周刊。後來周刊改出日報,取名《民力報》,由王蕓生與一幫同仁合資經營,他仍任主編。他寫了大量反帝、支持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文章,他的文采開始令人刮目相看。
1925年底,他加入了國民黨。
1926年春天,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在平津一帶與奉直魯聯軍交戰。由于日本艦隊和各國使領館的介入,國民軍悄悄退出天津。3月22日,王蕓生不得不拋棄報館和家人,乘招商局的輪船離開天津逃到上海,他當時“既悲國家的遭際,復傷個人的孤零,且懼眼前的危險,心中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酸楚”。P2-4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