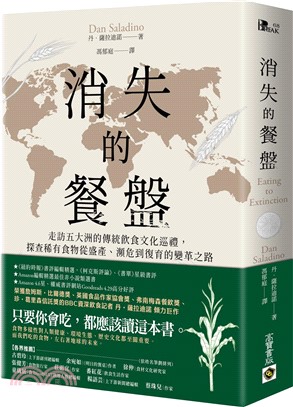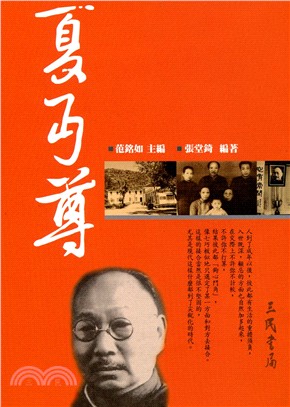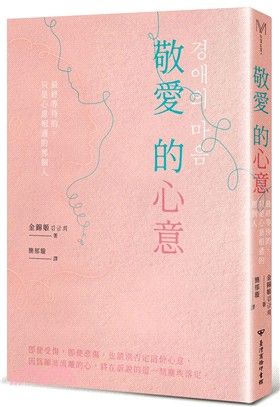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為什麼宣教士就得把「主的工作」放在家庭之先!
本書作者侯約翰為宣教士子女,但這樣的身分帶給他的不是光環,而是一連串的傷痛。父母為了宣教而「拋棄」他和其他手足、山東濰縣日本集中營的生活以及與母親永別的哀傷;為此,他曾怨懟父母和上帝,兒少的經歷成了籠罩在他心裡的黑暗。
當作者回顧並記錄過往人生經歷時,發現在他還年幼時,就深深被「光」所影響,「光」聯結他各樣的人生經歷。《永恆之光》是作者的回憶錄,忠實呈現他如何在黑暗中找到那早已存在生命中的光。
一扇門關了,另一扇門的光就從門縫照進到我的路上。生命的確就是光的角度和顏色交織的寫照。
本書作者侯約翰為宣教士子女,但這樣的身分帶給他的不是光環,而是一連串的傷痛。父母為了宣教而「拋棄」他和其他手足、山東濰縣日本集中營的生活以及與母親永別的哀傷;為此,他曾怨懟父母和上帝,兒少的經歷成了籠罩在他心裡的黑暗。
當作者回顧並記錄過往人生經歷時,發現在他還年幼時,就深深被「光」所影響,「光」聯結他各樣的人生經歷。《永恆之光》是作者的回憶錄,忠實呈現他如何在黑暗中找到那早已存在生命中的光。
一扇門關了,另一扇門的光就從門縫照進到我的路上。生命的確就是光的角度和顏色交織的寫照。
作者簡介
侯約翰(John Hoyte)
內地會醫療宣教士侯文甫(Stanley Hoyte, 1885-1979)之子。出生於中國,兒少時期正值中國戰亂之際。侯約翰自幼成長於以基督信仰為根基的家庭,家人間的關係緊密和樂。
侯約翰成年後主要經歷為:探索漢尼拔足跡並帶領大象攀越阿爾卑斯山,之後去到美國矽谷,在那裡因著研究發明而開創自己的公司,晚年將公司賣給員工。
侯約翰已退休,與妻子露思(Luci Shaw)居住於美國華盛頓貝靈漢。喜好航海、畫畫和彈奏古典吉他。
內地會醫療宣教士侯文甫(Stanley Hoyte, 1885-1979)之子。出生於中國,兒少時期正值中國戰亂之際。侯約翰自幼成長於以基督信仰為根基的家庭,家人間的關係緊密和樂。
侯約翰成年後主要經歷為:探索漢尼拔足跡並帶領大象攀越阿爾卑斯山,之後去到美國矽谷,在那裡因著研究發明而開創自己的公司,晚年將公司賣給員工。
侯約翰已退休,與妻子露思(Luci Shaw)居住於美國華盛頓貝靈漢。喜好航海、畫畫和彈奏古典吉他。
序
推薦序
宣教士兒女的奇幻之旅
繼《恩惠與慈愛》、《航向中國》之後,宇宙光機構推出《永恆之光》(Persistence of Light)這本宣教士後代的傳記。《恩惠與慈愛》是女兒寫父母在戰時中國逃難的故事,《航向中國》是玄孫寫高祖父在南洋與中國拓荒宣教的故事,《永恆之光》則是宣教士的兒子寫自己八十多年人生追求與冒險的故事。三本書作者的角色不同,卻同樣充滿知識、趣味與時代的痕跡,非常值得閱讀。
宣教士回應上帝的呼召,離鄉背井,棲身他鄉,即使環境險惡,甚至面臨割捨親情的抉擇,也多能義無反顧,向主效忠。可是身為宣教士的兒女,他們活在異鄉,並非出於自己的認同與選擇,於是在成長過程中難免會受到各種傷害,而這些傷害的影響也往往歷時一生之久。美國長老會宣教士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 1852-1931)的女兒、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就是一個例子,她在為父親寫傳記時,對父親不惜傾家蕩產狂熱地投入譯經事業頗有微詞。
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許多宣教士的後代,由於從小生活在舒適圈外,習慣於跨文化的思維,鍛鍊出較高的韌性與適應力,也較富於創新冒險的精神,因此後來在職場上有非常優越的表現。例如,義和團刀下的殉道者畢得經(Horace T. Pitkin, 1869-1900),他的兒子Dr. Horace Collins Pitkin(1898-1958)並未聽從父親的遺願繼續獻身中國,而留在美國成為一位著名的骨科專家。「苗族使徒」柏格理(Samuel Pollard, 1864-1915)客死貴州山區,他的兒子Ernest Pollard(1906-1997)成為一位卓越的物理學家。宣教士漢學家恆慕義(Arthur William Hummel, 1884-1975)的兒子恆安石(Arthur W. Hummel, Jr., 1920-2001),年輕時與本書作者一起被日軍拘禁在山東濰縣的集中營,後來出任1981-1985年美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翻譯和合本中文聖經的健將富善(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他的兒子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 1894-1986)成為著名的漢學家,終身執教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這個傑出人物的名單還可以不斷增添下去,足以證明宣教士的後人多有超乎常人的成就。
本書作者侯約翰(John Hoyte)是內地會醫療宣教士侯文甫(Stanley Hoyte, 1885-1979)的兒子,侯醫師在抗戰時期受差會指派前往甘肅蘭州的教會醫院服務,而將六名子女留在煙台的教會學校。珍珠港事變後,這六名孩童都被拘禁在山東濰縣的集中營,也與父母失去聯繫。他們在集中營得知母親病逝於蘭州的噩耗,精神上難免受到重創。戰後,他們輾轉被送到香港與父親團圓,但親情的缺憾已無法彌補。作者在書中多次提到內心憤憤不平的控訴,責怪父親為何將他們拋棄而前往內地,導致失去摯愛的母親。直到父親的晚年,本書作者才真正放下埋怨,正式與父親和好。另一方面,書中也不時提到基督信仰如何在作者面臨人生重大變遷時所帶來的安定力量,這些描述都讓我們感受到身為宣教士的兒女,往往較常人經歷更多采多姿的奇幻人生。
全書以光的七色解析為架構,勾勒出作者的人生故事,如此安排別出心裁,引人入勝。這也讓我想到膾炙人口的經典著作《天路歷程》,當書中主角天路客為了何去何從而不知所措時,有一位傳道者向他走來,問他是否看見遠方的光,並且要他朝那光前進,展開一趟充滿冒險與豐富的天路歷程。本書作者也像這位天路客,一生追求光的美妙,如今將其一生蒙光引導、與光同行的記錄中文版交由宇宙光出版社製作發行,光上加光,再合適也不過了。
魏外揚
中文版自序
我非常高興能為我這本回憶錄的中文譯本寫序。我出生於中國大陸,所以對中國這個地方,心中特別感念萬分。我的這本《永恆之光》英文版出書已有兩年之久。如今回顧起來,可以從讀者的回響中看得出他們對書中或痛苦或正面的故事多有認同。我當初寫書的目的也是希望能藉由分享我的生命經歷,而與當今的讀者產生共鳴和連結。儘管我們如今生活在瞬息萬變又顛簸的世代,有許多現實依舊存留不改變,諸如家人間的相親相愛、真理、饒恕、人心的憐恤和美善等事。而其中最為不變的是神雖然擁有掌管宇宙一切的主權,卻樂意以最親密、愛的方式顯明祂自己的這項事實永遠不變。
當我在開始把許多很廣泛且不相同的生活經驗:即在日本集中營的日子、帶著象隻登山越嶺的冒險旅程、以及在矽谷的職業生涯,化為筆墨寫書時,本以為這些既廣又雜的經歷,恐怕會成為先後不相干的故事情節,直到我寫著在矽谷的生活時,才頓然發現原來「光」這個主題成了這些不同經歷最有力的聯結。我在矽谷的公司所出產的兩項科技產品都與光源有關。於是我由此挑戰自己回顧以往,才重新發現原來「光」這件事在我生命早期就已深深影響了我。
接下來寫作的過程比預期的容易許多了。先是寫到我兩歲時父親為我拍下的一張照片,就是我母親握住我,讓我的腳趾在小溪水流上蕩漾出波光的情景。那道美麗的波光漣漪在我小小的心靈產生極大的震撼,那股被母親緊握同時能觀看到美妙奇景的感受如今仍記憶猶新,我在回憶錄的第 1 章就記錄了這件事。那是我對光、以及對母親有力且無限的愛第一次非常強烈鮮明的經驗。接著是8歲年紀的我在二次大戰期間被日軍以一艘破船送往集中營途中,在半夜看見的月光;然後是看到在集中營的牆角出現的那隻金黃色雀鳥所帶來的那份喜悅。這一連串心動時刻的意義深遠,竟然讓我能在戰事期間聽聞母親在甘肅過世的惡耗時,支撐著我度過那段黑暗的日子。
在我回到英國之後,或是當我獨自在蘇格蘭西岸的天空(Skye)島上的山頭觀景,或是在劍橋有五百年歷史的學院宿舍的河流上泛舟時所見的秋景光輝,光的主題仍然持續著,沒有止息間斷。
後來到了美國,我在矽谷創立的公司的第一項產品是光譜儀。那是我在年老的姨丈家的地下室找到的一件獨特的發明品,就是能把白光透過鏡片發散出虹光的七彩顏色的光譜儀。
就這樣,光的主題由此把我七章的回憶錄給串聯了起來。牛頓所發現的七彩虹光―紅、橙、黃、綠、藍、靛、紫,正好照明了我一生中峰迴路轉的人生旅程。最後的紫色篇章便以我和妻子露思(Luci)從我們在美國西岸的住家往外看得見好幾哩外的島嶼和水道所呈現的夕陽景緻作為全書的結尾。
這本回憶錄最後幾行字是這麼寫的:對我出生地中國的人們,紫色位於彩虹的尾端,卻代表了整個宇宙的那份和諧。這等和諧的存在對我而言,就是神對祂所造的萬物那不可思量的愛和看顧的結果。
此書的封面圖片是一項對「光」的研究,是我和妻子在去到亞利桑那州的羚羊峽谷(Arizona, Antelope Canyon)看到光彩岩石所拍攝的照片。在正午的陽光照射下,陡峭的紅岩石塊發出閃閃的亮光(這項美景有它危險之處,一場暴風雨有可能在幾分鐘內就把窄狹的峽谷給淹沒了)。攀登者在抬頭觀看巨石時會顯得極為渺小,會在被美景震撼的同時也意識到其中的危險性。然而那高空飛翔的鷹鳥卻是希望的指標。我把這幅我自己畫的素描放進原先的回憶錄中,也好增添一點我對光新的一份理解。
附錄中添加的部分是我父母親在1940年跋涉中國荒蕪內地具象的旅途過程中的故事。
宣教士兒女的奇幻之旅
繼《恩惠與慈愛》、《航向中國》之後,宇宙光機構推出《永恆之光》(Persistence of Light)這本宣教士後代的傳記。《恩惠與慈愛》是女兒寫父母在戰時中國逃難的故事,《航向中國》是玄孫寫高祖父在南洋與中國拓荒宣教的故事,《永恆之光》則是宣教士的兒子寫自己八十多年人生追求與冒險的故事。三本書作者的角色不同,卻同樣充滿知識、趣味與時代的痕跡,非常值得閱讀。
宣教士回應上帝的呼召,離鄉背井,棲身他鄉,即使環境險惡,甚至面臨割捨親情的抉擇,也多能義無反顧,向主效忠。可是身為宣教士的兒女,他們活在異鄉,並非出於自己的認同與選擇,於是在成長過程中難免會受到各種傷害,而這些傷害的影響也往往歷時一生之久。美國長老會宣教士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 1852-1931)的女兒、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就是一個例子,她在為父親寫傳記時,對父親不惜傾家蕩產狂熱地投入譯經事業頗有微詞。
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許多宣教士的後代,由於從小生活在舒適圈外,習慣於跨文化的思維,鍛鍊出較高的韌性與適應力,也較富於創新冒險的精神,因此後來在職場上有非常優越的表現。例如,義和團刀下的殉道者畢得經(Horace T. Pitkin, 1869-1900),他的兒子Dr. Horace Collins Pitkin(1898-1958)並未聽從父親的遺願繼續獻身中國,而留在美國成為一位著名的骨科專家。「苗族使徒」柏格理(Samuel Pollard, 1864-1915)客死貴州山區,他的兒子Ernest Pollard(1906-1997)成為一位卓越的物理學家。宣教士漢學家恆慕義(Arthur William Hummel, 1884-1975)的兒子恆安石(Arthur W. Hummel, Jr., 1920-2001),年輕時與本書作者一起被日軍拘禁在山東濰縣的集中營,後來出任1981-1985年美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翻譯和合本中文聖經的健將富善(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他的兒子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 1894-1986)成為著名的漢學家,終身執教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這個傑出人物的名單還可以不斷增添下去,足以證明宣教士的後人多有超乎常人的成就。
本書作者侯約翰(John Hoyte)是內地會醫療宣教士侯文甫(Stanley Hoyte, 1885-1979)的兒子,侯醫師在抗戰時期受差會指派前往甘肅蘭州的教會醫院服務,而將六名子女留在煙台的教會學校。珍珠港事變後,這六名孩童都被拘禁在山東濰縣的集中營,也與父母失去聯繫。他們在集中營得知母親病逝於蘭州的噩耗,精神上難免受到重創。戰後,他們輾轉被送到香港與父親團圓,但親情的缺憾已無法彌補。作者在書中多次提到內心憤憤不平的控訴,責怪父親為何將他們拋棄而前往內地,導致失去摯愛的母親。直到父親的晚年,本書作者才真正放下埋怨,正式與父親和好。另一方面,書中也不時提到基督信仰如何在作者面臨人生重大變遷時所帶來的安定力量,這些描述都讓我們感受到身為宣教士的兒女,往往較常人經歷更多采多姿的奇幻人生。
全書以光的七色解析為架構,勾勒出作者的人生故事,如此安排別出心裁,引人入勝。這也讓我想到膾炙人口的經典著作《天路歷程》,當書中主角天路客為了何去何從而不知所措時,有一位傳道者向他走來,問他是否看見遠方的光,並且要他朝那光前進,展開一趟充滿冒險與豐富的天路歷程。本書作者也像這位天路客,一生追求光的美妙,如今將其一生蒙光引導、與光同行的記錄中文版交由宇宙光出版社製作發行,光上加光,再合適也不過了。
魏外揚
中文版自序
我非常高興能為我這本回憶錄的中文譯本寫序。我出生於中國大陸,所以對中國這個地方,心中特別感念萬分。我的這本《永恆之光》英文版出書已有兩年之久。如今回顧起來,可以從讀者的回響中看得出他們對書中或痛苦或正面的故事多有認同。我當初寫書的目的也是希望能藉由分享我的生命經歷,而與當今的讀者產生共鳴和連結。儘管我們如今生活在瞬息萬變又顛簸的世代,有許多現實依舊存留不改變,諸如家人間的相親相愛、真理、饒恕、人心的憐恤和美善等事。而其中最為不變的是神雖然擁有掌管宇宙一切的主權,卻樂意以最親密、愛的方式顯明祂自己的這項事實永遠不變。
當我在開始把許多很廣泛且不相同的生活經驗:即在日本集中營的日子、帶著象隻登山越嶺的冒險旅程、以及在矽谷的職業生涯,化為筆墨寫書時,本以為這些既廣又雜的經歷,恐怕會成為先後不相干的故事情節,直到我寫著在矽谷的生活時,才頓然發現原來「光」這個主題成了這些不同經歷最有力的聯結。我在矽谷的公司所出產的兩項科技產品都與光源有關。於是我由此挑戰自己回顧以往,才重新發現原來「光」這件事在我生命早期就已深深影響了我。
接下來寫作的過程比預期的容易許多了。先是寫到我兩歲時父親為我拍下的一張照片,就是我母親握住我,讓我的腳趾在小溪水流上蕩漾出波光的情景。那道美麗的波光漣漪在我小小的心靈產生極大的震撼,那股被母親緊握同時能觀看到美妙奇景的感受如今仍記憶猶新,我在回憶錄的第 1 章就記錄了這件事。那是我對光、以及對母親有力且無限的愛第一次非常強烈鮮明的經驗。接著是8歲年紀的我在二次大戰期間被日軍以一艘破船送往集中營途中,在半夜看見的月光;然後是看到在集中營的牆角出現的那隻金黃色雀鳥所帶來的那份喜悅。這一連串心動時刻的意義深遠,竟然讓我能在戰事期間聽聞母親在甘肅過世的惡耗時,支撐著我度過那段黑暗的日子。
在我回到英國之後,或是當我獨自在蘇格蘭西岸的天空(Skye)島上的山頭觀景,或是在劍橋有五百年歷史的學院宿舍的河流上泛舟時所見的秋景光輝,光的主題仍然持續著,沒有止息間斷。
後來到了美國,我在矽谷創立的公司的第一項產品是光譜儀。那是我在年老的姨丈家的地下室找到的一件獨特的發明品,就是能把白光透過鏡片發散出虹光的七彩顏色的光譜儀。
就這樣,光的主題由此把我七章的回憶錄給串聯了起來。牛頓所發現的七彩虹光―紅、橙、黃、綠、藍、靛、紫,正好照明了我一生中峰迴路轉的人生旅程。最後的紫色篇章便以我和妻子露思(Luci)從我們在美國西岸的住家往外看得見好幾哩外的島嶼和水道所呈現的夕陽景緻作為全書的結尾。
這本回憶錄最後幾行字是這麼寫的:對我出生地中國的人們,紫色位於彩虹的尾端,卻代表了整個宇宙的那份和諧。這等和諧的存在對我而言,就是神對祂所造的萬物那不可思量的愛和看顧的結果。
此書的封面圖片是一項對「光」的研究,是我和妻子在去到亞利桑那州的羚羊峽谷(Arizona, Antelope Canyon)看到光彩岩石所拍攝的照片。在正午的陽光照射下,陡峭的紅岩石塊發出閃閃的亮光(這項美景有它危險之處,一場暴風雨有可能在幾分鐘內就把窄狹的峽谷給淹沒了)。攀登者在抬頭觀看巨石時會顯得極為渺小,會在被美景震撼的同時也意識到其中的危險性。然而那高空飛翔的鷹鳥卻是希望的指標。我把這幅我自己畫的素描放進原先的回憶錄中,也好增添一點我對光新的一份理解。
附錄中添加的部分是我父母親在1940年跋涉中國荒蕪內地具象的旅途過程中的故事。
目次
推薦序 宣教士兒女的奇幻之旅/魏外揚
中文版自序
原文版自序
第1章 紅色 在中國的童年
第2章 橙色 戰後的英國――高中和從軍時期
第3章 黃色 劍橋――探索漢尼拔足跡
第4章 綠色 與大象金寶攀登阿爾卑斯山脈
第5章 藍色 矽谷,以及抗拒文化浪潮的年日――走向光明之路
第6章 靛色 戀愛、結婚、生兒養女組大家庭
終章 紫色 詩詞、藝術所沉浸的新生活
附錄一 父母親行過荒郊野地的那趟旅程
附錄二 金寶和牠的象群
中文版自序
原文版自序
第1章 紅色 在中國的童年
第2章 橙色 戰後的英國――高中和從軍時期
第3章 黃色 劍橋――探索漢尼拔足跡
第4章 綠色 與大象金寶攀登阿爾卑斯山脈
第5章 藍色 矽谷,以及抗拒文化浪潮的年日――走向光明之路
第6章 靛色 戀愛、結婚、生兒養女組大家庭
終章 紫色 詩詞、藝術所沉浸的新生活
附錄一 父母親行過荒郊野地的那趟旅程
附錄二 金寶和牠的象群
書摘/試閱
第1章
紅色 在中國的童年
和父親團圓
有一天老師把我叫住說,約翰,你爸爸來了,就在接待室!當下我心跳加速,不但記起在芝罘的時光,還感到一種在時間上、距離上、哀傷心理上因分離所造成的巨大鴻溝。爸爸現在長什麼樣子?他會認出我嗎?我會認出他嗎?最重要的是,媽媽可不可能跟他在一起呢?不過這瞬間的想法馬上就消退了,因為老師只說「爸爸」,沒有說「你父母來了」,只是心裡不免以為恐怕還有那麼一絲絲期盼的希望存在著吧。
我們相互擁抱,我還緊緊依附著他不放。媽媽果然不在。一股又大又新的哀傷幾乎籠罩住我整個心。這股奇怪、新湧上的哀傷不可抗拒到一個地步,完全蓋過了團圓所帶來的喜悅。
小妹伊莉莎白已經在那裡了,於是三人手牽著到外面走走。走到我猛然意識到我不太認識爸爸,現在他就像個陌生人,五年成為孤兒的刺痛湧上了心頭。雖然明知他比我們更受苦,但那種心痛是種離別的哀傷。雖嘗試設身處地為他想,但卻失敗得很悽慘。對一個10來歲的少年來說,感受是很直接的,我似乎感到能坐上士官兵的快速摩托車的吸引拉力,遠比跟這位陌生人走在一起要強烈多了。
但另一方面團圓的喜悅是有的。尤其是想到我們六個孩子現在可以和父親一起長途乘船回英國,一起面對未來的事實。其實我心底是不是還埋怨他怎麼可以把我們留在芝罘這麼多年呢?我還是很愛他,但那是一種遙遠的愛,有必要被搖醒。我深知爸媽對一項緊迫的需求做了很真切、有信心的回應,但我怨恨是整個體制。為什麼宣教士就得把「主的工作」放在家庭之先。那般虔誠的術語和禱告掩飾了家家內部所造成的很深的裂痕。在接下來的幾年間,我有好長一段需要內心醫治的路要走。其他每個孩子也都需要。
在我許多年之後跟露思結了婚,父親94歲高齡去世前,我有好一段時間對心靈這些傷痛有很得幫助的諮商輔導過程。結果終於能放下心中的大重擔,寫了一封信給爸爸,原諒他把我們丟下成了孤兒。我相信自己已找到平安和饒恕。饒恕之光終究淹沒一切憤恨苦毒的黑暗勢力。
我們在香港又必須等上兩星期,才找到軍艦上可以載我們回英國的空位。當然一路都是免費的。英國政府因為我們遭受過囚禁,所以付費讓我們去任何要去的地方,甚至是最後坐車的旅費。父親原本考慮去紐西蘭,但我們在那裡沒有親戚,所以最後決定還是回戰後破損不堪的英國,即使那裡的狀況比起來糟太多了。
在等待上船的兩週,我們有很好的家庭相聚時間。我們去香港島的淺水灣,以及萬金油花園玩。我們還到了一個住在纜車頂端的中國有錢人家裡吃飯。在內陸,我們去參觀了一個基督教信仰和佛教禮儀混雜的退修中心。大門上的標幟是在一朵蓮花中間掛了個十字架。
當我們在退修中心後頭爬上泥土小丘時,反方向走來一排士兵。他們看起來很累的樣子,拖著靴子,裝備也很破舊,還帶著滿布灰塵的槍枝。最引我注意的,是他們安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彷彿所有的力量都用在走路上,再沒有餘剩的力量說話了。我這才突然警覺到中國人還在打內戰。士兵滿身是汗,臭氣薰天,彷彿像剛打了敗仗,只想回去休息。他們一定是國民軍,而且正節節敗退。這幅景致相較於退修中心裡很寧靜的蓮花池、廟宇的殿堂,以及周遭美麗的景色,凸顯出一個遭受戰亂損傷的中國的殘酷事實,至今在我腦海中仍記憶鮮明。
隔天,我已走在九龍的軍營附近,看到一個閱兵場就停了下來。裡面聲音好大,而且還在說些髒話。一位英國士兵向我們解釋說,這是一群在南太平洋很重要的日本指揮官。有位高壯的士官長對著矮小的日本人大聲謾罵。他的話既卑劣又粗魯,真覺得那些軍官好可憐。當下他們不再是把我們帶去集中營造成家人悲慘分離的代號,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跟我一樣脆弱、一樣衰殘。
比起他們的遭遇,我們在濰縣集中營的一切顯得相對溫和。我心中一股惻隱之心完全超過在戰時的憤怒。如果我們像在巴丹(Bataan)列隊受死的犯人所受的那般待遇,是否就會有不同的感受呢?後來我們才知道,在太平洋的日本最高指揮本來計畫在9月初日本轉勝為敗的週年殺掉所有囚犯的,也就是在我們得自由不到一個月之後。如果我早知道這件事,我又會有什麼不同的想法呢?真慶幸戰爭是在那時候結束。可見當時傘兵的救援,的確因為日本最高指揮的威脅而變得相當必要又緊迫。
在回英國的船艦上,我和爸爸還有兄弟姐妹花很多時間相處。爸爸告訴我們許多在內地的生活狀況,還有當時去西部後來又回沿海,種種路途上的艱難,以及有關媽媽的很多事。不過他對媽媽最後的那些日子很難啟齒談論,那種失落恐無言無語可以傾訴。他也從來沒有提到那個日本間諜告訴他我們都被殺的謠言,是幾年後我們從另一位在醫院的宣教士口中才知道的。當時對他而言一定相當痛苦,因為很可能就信以為真,以為我們真的都死了。
第5章
藍色 矽谷,以及抗拒文化浪潮的年日――走向光明之路
反文化――亮光進入新世界
我生活在六十、七十年,熱衷Beat、自由言論、新世紀、政治激進運動的年代,但卻以英式張大的眼光吸收著這些浪潮中的每件事。……
東方思想此時也變得很流行。我到現在還有一本拉姆.達斯(Baba Ram Dass;他在哈佛教書時叫李察.艾爾帕〔Richard Alpert〕)寫的書叫《活在當下》(Be Here Now)。首章就細數他如何從成功的學術界轉到東方的思想。我仔細研究他這本書,也似乎活在那種文化的邊緣地帶,不過並沒有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這個東方思想運動好的一面是能讓年輕人詢問人生大問題:我能找到人生目的嗎?人生終極意義是什麼?任何對人生認真的人都必須面對這些問題。作為基督耶穌的跟隨者,我開始找到的答案是真的有一位愛我們的上帝。對於任何想要好好跟這些問題對話的人,冷漠的態度是最糟糕的。難怪我們年輕人才會想到海特找尋答案。
我問自己:到底基督信仰所提供的內容是否真能回答這些關乎人生意義、罪惡和死亡的問題?針對這波反文化,基督信仰真能帶來解答嗎?我是半島不同教會組成向海特進行拯救宣教任務的男生團隊的一員。我和有6呎3吋高,留有長髮、面帶極友善微笑的友人卡爾.加利文(Carl Gallivan)會開車去到那裡。在我們宣教地方的前面房間沒有擺放家具,我們都是盤坐在一張大毯子上。工作室外面寫著:歡迎各位來到這裡!倘若你在找答案,我們這裡有。室內一直煮著咖啡,而且非常歡迎任何進來的人。果然一點也不奇怪,有好多人進來,許多沒地方住的人,大都是從中產階級家庭離家出走,想找尋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少年。我並不確定我們所說帶有盼望的言論是否很清楚,但是如果我們的生命能顯示出愛與關懷,我相信可以產生影響力。再沒有比有個安全的地方可以睡覺、可以喝碗熱湯要好多了。如果我們能取得電話號碼,然後打電話給父母的話,我們算是找到了一線生機。
在史丹福的學生民主社團(Student for Democratic Societ,簡稱為SDS)
1965年,激進左派SDS社團在舊金山半島形成,而且在史丹福很活耀。1968年,薛華夫婦從瑞士來探望我們,並且十分關切要如何針對這股逆流有所對應聯結。我帶薛華先生去到已經被SDS學生接管的《史丹福日報》(Stanford Daily)的辦公室。結果發現他們原來在推動使用暴力行動來反抗既有的組織機關、大學、史丹福研究中心、洛克西德(Lockheed)和其他機構。他們的三大先知是:馬克思、毛澤東和馬庫色(Marcuse)。顯然這已經超越原先反對越戰的理念了。薛華問他們:「你們要如何重整社會呢?」他們的回答很清楚:「社會已經腐敗到我們必須要全部推翻再建立起來。要讀馬庫色的作品。意謂著我們必須推翻現有制度而變成小型城市國家。我們有必要找到更好的系統才行。」
薛華於是問說:「那麼要怎麼做呢?」但他們並沒有回覆好的解答。我們要離開的時候,薛華未被他們這些暴力性的解決方案所攪擾,反而告訴他們,「歡迎各位來我在瑞士的住處,我們是一個對這些問題很努力在探討的生活群體。」我對薛華回應這些年輕人的方式印象深刻:就是很單純地把基督的愛,以及完全的顯露人的脆弱和無助感的方式觸碰了人們心中的「需要」。後來在70年代,我便以瑞士群體的模式,也在這裡為年輕人設立一個類似的群體,於是就去拜訪了瑞士聖克魯斯山的休莫茲(Huemoz)小村莊,在那裡由好幾間房子組成的庇護所群體。我心中有兩個目標:就是針對真誠的問題給出真誠的回答,並且為有需要的人們提供一個住家。這也正是我們在海特小規模的拯救宣教任務工作室所嘗試在做的事。
紅色 在中國的童年
和父親團圓
有一天老師把我叫住說,約翰,你爸爸來了,就在接待室!當下我心跳加速,不但記起在芝罘的時光,還感到一種在時間上、距離上、哀傷心理上因分離所造成的巨大鴻溝。爸爸現在長什麼樣子?他會認出我嗎?我會認出他嗎?最重要的是,媽媽可不可能跟他在一起呢?不過這瞬間的想法馬上就消退了,因為老師只說「爸爸」,沒有說「你父母來了」,只是心裡不免以為恐怕還有那麼一絲絲期盼的希望存在著吧。
我們相互擁抱,我還緊緊依附著他不放。媽媽果然不在。一股又大又新的哀傷幾乎籠罩住我整個心。這股奇怪、新湧上的哀傷不可抗拒到一個地步,完全蓋過了團圓所帶來的喜悅。
小妹伊莉莎白已經在那裡了,於是三人手牽著到外面走走。走到我猛然意識到我不太認識爸爸,現在他就像個陌生人,五年成為孤兒的刺痛湧上了心頭。雖然明知他比我們更受苦,但那種心痛是種離別的哀傷。雖嘗試設身處地為他想,但卻失敗得很悽慘。對一個10來歲的少年來說,感受是很直接的,我似乎感到能坐上士官兵的快速摩托車的吸引拉力,遠比跟這位陌生人走在一起要強烈多了。
但另一方面團圓的喜悅是有的。尤其是想到我們六個孩子現在可以和父親一起長途乘船回英國,一起面對未來的事實。其實我心底是不是還埋怨他怎麼可以把我們留在芝罘這麼多年呢?我還是很愛他,但那是一種遙遠的愛,有必要被搖醒。我深知爸媽對一項緊迫的需求做了很真切、有信心的回應,但我怨恨是整個體制。為什麼宣教士就得把「主的工作」放在家庭之先。那般虔誠的術語和禱告掩飾了家家內部所造成的很深的裂痕。在接下來的幾年間,我有好長一段需要內心醫治的路要走。其他每個孩子也都需要。
在我許多年之後跟露思結了婚,父親94歲高齡去世前,我有好一段時間對心靈這些傷痛有很得幫助的諮商輔導過程。結果終於能放下心中的大重擔,寫了一封信給爸爸,原諒他把我們丟下成了孤兒。我相信自己已找到平安和饒恕。饒恕之光終究淹沒一切憤恨苦毒的黑暗勢力。
我們在香港又必須等上兩星期,才找到軍艦上可以載我們回英國的空位。當然一路都是免費的。英國政府因為我們遭受過囚禁,所以付費讓我們去任何要去的地方,甚至是最後坐車的旅費。父親原本考慮去紐西蘭,但我們在那裡沒有親戚,所以最後決定還是回戰後破損不堪的英國,即使那裡的狀況比起來糟太多了。
在等待上船的兩週,我們有很好的家庭相聚時間。我們去香港島的淺水灣,以及萬金油花園玩。我們還到了一個住在纜車頂端的中國有錢人家裡吃飯。在內陸,我們去參觀了一個基督教信仰和佛教禮儀混雜的退修中心。大門上的標幟是在一朵蓮花中間掛了個十字架。
當我們在退修中心後頭爬上泥土小丘時,反方向走來一排士兵。他們看起來很累的樣子,拖著靴子,裝備也很破舊,還帶著滿布灰塵的槍枝。最引我注意的,是他們安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彷彿所有的力量都用在走路上,再沒有餘剩的力量說話了。我這才突然警覺到中國人還在打內戰。士兵滿身是汗,臭氣薰天,彷彿像剛打了敗仗,只想回去休息。他們一定是國民軍,而且正節節敗退。這幅景致相較於退修中心裡很寧靜的蓮花池、廟宇的殿堂,以及周遭美麗的景色,凸顯出一個遭受戰亂損傷的中國的殘酷事實,至今在我腦海中仍記憶鮮明。
隔天,我已走在九龍的軍營附近,看到一個閱兵場就停了下來。裡面聲音好大,而且還在說些髒話。一位英國士兵向我們解釋說,這是一群在南太平洋很重要的日本指揮官。有位高壯的士官長對著矮小的日本人大聲謾罵。他的話既卑劣又粗魯,真覺得那些軍官好可憐。當下他們不再是把我們帶去集中營造成家人悲慘分離的代號,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跟我一樣脆弱、一樣衰殘。
比起他們的遭遇,我們在濰縣集中營的一切顯得相對溫和。我心中一股惻隱之心完全超過在戰時的憤怒。如果我們像在巴丹(Bataan)列隊受死的犯人所受的那般待遇,是否就會有不同的感受呢?後來我們才知道,在太平洋的日本最高指揮本來計畫在9月初日本轉勝為敗的週年殺掉所有囚犯的,也就是在我們得自由不到一個月之後。如果我早知道這件事,我又會有什麼不同的想法呢?真慶幸戰爭是在那時候結束。可見當時傘兵的救援,的確因為日本最高指揮的威脅而變得相當必要又緊迫。
在回英國的船艦上,我和爸爸還有兄弟姐妹花很多時間相處。爸爸告訴我們許多在內地的生活狀況,還有當時去西部後來又回沿海,種種路途上的艱難,以及有關媽媽的很多事。不過他對媽媽最後的那些日子很難啟齒談論,那種失落恐無言無語可以傾訴。他也從來沒有提到那個日本間諜告訴他我們都被殺的謠言,是幾年後我們從另一位在醫院的宣教士口中才知道的。當時對他而言一定相當痛苦,因為很可能就信以為真,以為我們真的都死了。
第5章
藍色 矽谷,以及抗拒文化浪潮的年日――走向光明之路
反文化――亮光進入新世界
我生活在六十、七十年,熱衷Beat、自由言論、新世紀、政治激進運動的年代,但卻以英式張大的眼光吸收著這些浪潮中的每件事。……
東方思想此時也變得很流行。我到現在還有一本拉姆.達斯(Baba Ram Dass;他在哈佛教書時叫李察.艾爾帕〔Richard Alpert〕)寫的書叫《活在當下》(Be Here Now)。首章就細數他如何從成功的學術界轉到東方的思想。我仔細研究他這本書,也似乎活在那種文化的邊緣地帶,不過並沒有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這個東方思想運動好的一面是能讓年輕人詢問人生大問題:我能找到人生目的嗎?人生終極意義是什麼?任何對人生認真的人都必須面對這些問題。作為基督耶穌的跟隨者,我開始找到的答案是真的有一位愛我們的上帝。對於任何想要好好跟這些問題對話的人,冷漠的態度是最糟糕的。難怪我們年輕人才會想到海特找尋答案。
我問自己:到底基督信仰所提供的內容是否真能回答這些關乎人生意義、罪惡和死亡的問題?針對這波反文化,基督信仰真能帶來解答嗎?我是半島不同教會組成向海特進行拯救宣教任務的男生團隊的一員。我和有6呎3吋高,留有長髮、面帶極友善微笑的友人卡爾.加利文(Carl Gallivan)會開車去到那裡。在我們宣教地方的前面房間沒有擺放家具,我們都是盤坐在一張大毯子上。工作室外面寫著:歡迎各位來到這裡!倘若你在找答案,我們這裡有。室內一直煮著咖啡,而且非常歡迎任何進來的人。果然一點也不奇怪,有好多人進來,許多沒地方住的人,大都是從中產階級家庭離家出走,想找尋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少年。我並不確定我們所說帶有盼望的言論是否很清楚,但是如果我們的生命能顯示出愛與關懷,我相信可以產生影響力。再沒有比有個安全的地方可以睡覺、可以喝碗熱湯要好多了。如果我們能取得電話號碼,然後打電話給父母的話,我們算是找到了一線生機。
在史丹福的學生民主社團(Student for Democratic Societ,簡稱為SDS)
1965年,激進左派SDS社團在舊金山半島形成,而且在史丹福很活耀。1968年,薛華夫婦從瑞士來探望我們,並且十分關切要如何針對這股逆流有所對應聯結。我帶薛華先生去到已經被SDS學生接管的《史丹福日報》(Stanford Daily)的辦公室。結果發現他們原來在推動使用暴力行動來反抗既有的組織機關、大學、史丹福研究中心、洛克西德(Lockheed)和其他機構。他們的三大先知是:馬克思、毛澤東和馬庫色(Marcuse)。顯然這已經超越原先反對越戰的理念了。薛華問他們:「你們要如何重整社會呢?」他們的回答很清楚:「社會已經腐敗到我們必須要全部推翻再建立起來。要讀馬庫色的作品。意謂著我們必須推翻現有制度而變成小型城市國家。我們有必要找到更好的系統才行。」
薛華於是問說:「那麼要怎麼做呢?」但他們並沒有回覆好的解答。我們要離開的時候,薛華未被他們這些暴力性的解決方案所攪擾,反而告訴他們,「歡迎各位來我在瑞士的住處,我們是一個對這些問題很努力在探討的生活群體。」我對薛華回應這些年輕人的方式印象深刻:就是很單純地把基督的愛,以及完全的顯露人的脆弱和無助感的方式觸碰了人們心中的「需要」。後來在70年代,我便以瑞士群體的模式,也在這裡為年輕人設立一個類似的群體,於是就去拜訪了瑞士聖克魯斯山的休莫茲(Huemoz)小村莊,在那裡由好幾間房子組成的庇護所群體。我心中有兩個目標:就是針對真誠的問題給出真誠的回答,並且為有需要的人們提供一個住家。這也正是我們在海特小規模的拯救宣教任務工作室所嘗試在做的事。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