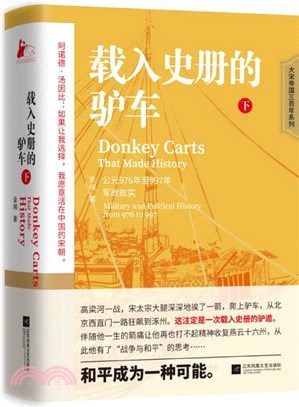載入史冊的驢車‧下(簡體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太宗趙炅,畢生致力“偃武修文”,推演天下文明:編修大書、獎掖人才,創下萬世不朽之文化基業;修訂《刑統》,施行“大赦”,收斂天下刀兵之刑。但皇弟趙廷美之死,讓恪守“兄友弟恭”倫理大義的士大夫側目,更成為太宗一生錐心之痛。
太宗踐祚,“金匱之盟”的“再傳”版本甚囂塵上。繼續“兄終弟及”模式,或重回“嫡子繼承”古制,讓注重個人節操道義的太宗焦躁不安。趙普的“一言之建”,不幸成“趙廷美案”導火索,讀懂此案,可懂大宋皇室大半。 太宗一朝,“搜求天下書”,建“崇文院”,珍藏善本、典籍,刊刻十二部經,編撰《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奠定前所未有的文明文化;修正《刑統》,嚴密法條,嚴擇官吏,懲治兵匪,申理冤滯,“以愛民為心”“法當原情”的司法建設,保障了盛世的開端;逢災必救、有饑必賑、賦重必減、稅濫必除的國家治理,更底定歷經三百年的文明更化。太宗一朝,“仍舊貫”、恪守傳統之理念,延續了大宋帝國的榮光,也使太宗成為有道義、有格局的一代賢君。
作者簡介
金綱
原名李金剛,下過鄉,讀過書,曾為北京大學歷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員,現為思想史研究獨立學者,出版有《論語鼓吹》等著作。“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一語,常置座右。
名人/編輯推薦
編輯推薦
★北大歷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員、知名學者金綱宋史研究數十年心血之作。既忠實於歷史,考證渲染相得益彰,又評判縝密,不乏真知灼見,敘事宏大廣闊,生動有趣,余味無窮,為解讀歷史提供了一個新範本。
★揭開一個被鐵蹄與悲情遮蔽的驚艷盛世!全景再現趙光義致力天下太平的歷史故實。以正史為坯,以野史為料,“復盤”歷史現場眾多詭異難言之處。“文”中帶點野氣,“史”中加了活力。
★戰場殺伐,帝王權術,帷幄兵法,文化盛況,法制革新……抽絲剝繭,揭開歷史迷霧背後宋太宗的功過是非。既有收復藩鎮的統一之景,也有血流成河的遍地廝殺之戰;既有大人物的小算盤,也有小人物的大氣魄。
★精美裝幀,收藏級質量。膜銀卡封面 五色印金:色彩鮮明,呈現金屬光澤,自帶低調的奢華;鎖線精裝:牢固耐翻,典藏佳品,書架上的格調擔當;瑞典輕型內文紙:耐久不易發黃,輕盈可攤開,給予完美的閱讀體驗。
目次
壹 皇弟之死
“金匱之盟”的“再傳”版本 《建隆遺事》中的顧命大臣
為趙炅辯誣:太宗不會謀害親侄 “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
賣直取名 “八大王”趙元儼
“駙馬升行” 荊國大長公主恪守“古禮”
趙普失寵三案 “普由是憤怒”
黎桓襲殺侯仁寶 柴禹錫告發秦王
密奏中的“權幸” 雷德驤與雷有鄰父子
“金匱之盟”的悖論 金明池未遂政變
“兄終弟及”集團 幾千個耳光子
貳 趙普與盧多遜
李符與趙廷美之死 陳國夫人耿氏之謎
“把斷劍門燒棧道, 小胖孩和小瘦孩
西川別是一乾坤” 盧多遜的大見識與小聰明
“倒盧”“倒趙”與“倒秦” “月頭銀”之變
寇準簪花 禳災祈福的趙普
半世評語 “天倫為重,大位為輕”
《宋論》中的四個觀點 瘋癲長子趙元佐
讓國四賢人 趙元佐被廢
“德不孤,必有鄰” “晉邸舊人”柴禹錫
“公當偏霸一方” 江湖險,廊廟更險
參 文治
搜求天下書 “人之嗜好,不可不戒”
《太平御覽》 太宗論劉義隆、楊素、許敬宗
“仁者之愚” “萬歲”與“眉壽”
人君當澹然無欲 “飛白”
契丹的學術成果 《淳化閣帖》盡顯大宋風韻
《孝經碑》與《雍熙廣韻》 “十六字教”
“家法”與“家學” 李覺講《泰卦》
“羈縻文人論”
肆 法制
不完美的聖賢大義 刑罰“鼠彈箏”
好“言事”者王濟 修《刑統》,重“聽斷”
擊登聞鼓“民告官” 申理冤滯,感召和氣
爛蔥案 禮治未病,法治已病
“法當原情” 叔叔告侄內有隱情
寬大兵痞,護持工人 皇子被推問
安崇緒疑案 “采牲”殺人以死罪論
禁“生祠” 鉆法律空子的“刁民”
伍 名臣·名流
大宋精英 “弭冤白謗,天理”
“等身書” 賢者賢,薦賢者尤賢
宇宙小,一身大 人民,本也;疆土,末也
偶像李大亮 畫地十策
法貴有常,政尚清凈 仍舊貫
食料羊 “居官弛慢”與“清凈之理”
願得制度狹小 廣開言路與楚文王
呂蒙正與太宗的博弈 不可奪之志
呂相四故實 風浪中端坐
得嘉賞未嘗喜, 曲突徙薪,方為真智者
遇抑挫未嘗懼 君臣際會的動人之處
風波之言不足慮也 奇才寇準
剛猛宰輔不敢自辯 君臣選太子
價值制衡 若水雪冤
李昉不朝宋太祖 一錢不值
善人君子,父子相繼
陸 王禹偁、柳開、潘閬
磨面為生要致君堯舜 《端拱箴》與《御戎十策》
道安尼姑案 以夷制夷
“讖詩”與“勢利” 貶謫文化
白體詩《畬田詞》 餿主意
謝泌兩批太宗詔書 差點挨板磚的大臣
大言柳開 柳開為官三事
亦俠亦匪 拜求徐鉉“賜之一言”
衛道者與米舒卡 嘲柳開
弩下逃箭 潘閬“隱身”
手把紅旗旗不濕
柒 王小波起事
焦四焦八 梅山峒蠻之變
說“隕獲” 抑制兵變
恐怖大王的克星 均貧富
榷茶 茶馬交易
“蜀民之病” 博買務
“吾疾貧富不均, 孟昶遺孤與灌口二郎神
今為汝均之!” “戰神”王小波之死
蠲免秋稅還是吃不飽 鐘離委珠
寵辱不驚
捌 失蹤的李順
“大蜀國”年號“應運” 劍門固守有驚無險
張雍守梓州 父死於忠,子死於孝
與世無爭崔遵度 屠殺
查道戴枷督稅 王繼恩誰都對不起
後宮與宦官不得幹政 宣徽使與宣政使
陷名將馬知節於死地 地方官與社稷臣
虎翼卒謀反 詔按其罪與封駁詔書
空白任免詔書 乖崖之名,聊以表德
秋光卻似宦情薄, 辣手張詠
山色不如歸興濃 超脫於仁愚、賢不肖之上的智者
李順死生之謎 宋太宗下《罪己詔》
改良“榷茶”制度
玖 太宗之死
向契丹“請和” 御戎三策
撫我則後,虐我則仇 求才
文明競賽 太宗之死
太宗遺制 “來和天尊”的神秘流言
呂端大事不糊塗 趙元佐不見宋真宗
王繼恩遇能吏 太宗的憂心與焦勞
塞濁亂之源 夭折的封禪大典
汴水抗洪 海東青與白花鷹
破解“後宮方程” 慚德與大功
《宋史》蓋棺定論
書摘/試閱
壹 皇弟之死
宋太祖圍困金陵曠日持久,還是不願意無辜殺人;宋太宗攻取太原,契丹隨時可能來援,看到將士爭奮登城,他還是擔心城破之後,將士不受控制而屠城,竟下令攻城稍緩。富有如此這般聖賢氣象的人物,會謀於密室,暗中策劃,殺害自家骨肉?
“金匱之盟”的“再傳”版本
太宗趙炅,一生吞咽了三大苦果:高梁河之敗,岐溝關之敗,皇弟趙廷美之死。這後一個苦果,讓恪守“兄友弟恭”倫理大義的士大夫側目,有一種誅心的說法甚至認為是他暗算了兄弟趙廷美。
趙弘殷和杜太后生有五個兒子。趙匡胤是家中老二,老大早夭;趙炅是老三,趙廷美是老四,還有一個老五,也早夭。按照以杜太后為主角的“金匱之盟”說法,趙匡胤之後,帝位傳兄弟趙光義,而不傳兒子趙德昭。這樣,執掌乾綱者在二代之後,還是成年君主,不至於出現後周柴榮之後孤兒寡母無法控制權力那種弱勢格局,大宋似可因此避免因權力失衡導致的國家動亂。
太宗之後呢?於是,“金匱之盟”的故實中,又有了另外一個“再傳”版本。也即由太太宗,太宗再傳兄弟趙廷美,趙廷美再傳太祖之子趙德昭,由此大宋帝王重新回到太祖譜系。
這個說法來自時人王禹偁。
王禹偁是太宗、真宗兩朝的文人,有一部傳為他所著的《建隆遺事》,“再傳”說,就是由此書發端。
書中講述了一個近於傳奇的故實。
說趙匡胤對杜太后非常孝順,對兄弟非常友愛,這種孝順和友愛,幾乎“曠古未有”。
有一次,趙匡胤在“萬機之暇”,抽空召來晉王趙光義、秦王趙廷美,皇子南陽王趙德昭、東平王趙德芳,以及皇侄、公主等,到杜太后的房閣飲宴。書中有解釋說,秦王趙廷美,乃是宣祖趙弘殷的第三子,也是杜太后親生。有傳言認為趙廷美是太祖的乳母所生,從王禹偁的說法來看,顯然不是。
一家人聚會非常和睦。“酒酣”,太祖對杜太后說:
“我百年之後要傳位給晉王,讓晉王百年後再傳位給秦王。”杜太后聞言大喜,說:“我久有此意,但不願意說出來。我要萬世之下,人們會傳頌一個婦人生了三個天子!你這番話真是大孝,‘成吾之志’!”說罷,讓晉王、秦王趕緊離席,拜謝大哥。太后又對太祖兩個兄弟說:“今天的皇上,過去以布衣身份侍奉周室,曾經多次力戰爭取功名,那真是‘萬死而遇一生’,這才做到節度使。等得到天命,做了皇上,這麼多年來,幾乎沒有一天不在征討,沒有一個月不在打仗,真可以說是‘歷盡艱危,方成帝業’。你們倆沒有功勞卻安享尊榮,成就大的爵賞,應該知道幸運。以後,各自都不得有負於陛下!”然後,對秦王趙廷美說:“我不知道秦王百年後,又將基業托付何人?”
秦王當即回答:“願立南陽王趙德昭。”
杜太后聞言又是一喜,道:“是了!是了!”又說:“傳位事,陛下能有此意,我能料到,但這也是天意!他日,你們各自都要按照今天說的這個約定做,不得逾越——逾越這個約定,‘罪同大逆,天必殛之’!”
趙匡胤聽到這裡,馬上要兒子趙德昭來拜謝杜太后。
在一場家宴中,“再傳”模式被建構起來後,杜太后還不放心,又對趙匡胤說:“可以替我將趙普呼來,令他以今天的約定寫一篇《誓書》,與你們兄弟依次傳而收藏。還要選擇一個吉日,將這個約定上告天地、宗廟。陛下認為是否可行?”
趙匡胤答應下來,當即召趙普入宮,讓他來草擬這篇《誓書》。但趙普推辭說自己不善於作文,於是又召翰林承旨陶谷前來擬文。
王禹偁書中說,這篇《誓書》交給晉王趙光義也即太宗趙炅收藏;等到趙匡胤駕崩,趙炅又將《誓書》交付秦王趙廷美收藏。但後來趙廷美“謀不軌”,“幽死”(幽囚或幽憤而死),《誓書》藏於禁中,後不知道下落。太祖之子南陽王趙德昭也因為犯事,被“逼令自殺”,於是“傳襲之約絕矣”。
這個傳奇故實,講述的“趙匡胤—趙光義—趙廷美—趙德昭”再傳模式,有很多漏洞,與後來發生的“史實”,有難於理清邏輯的地方。譬如,讓陶谷來草擬《誓書》,天下幾乎無人相信。陶谷有躁進之習,品德不佳,乃是太祖太宗都不喜歡的人物,怎麼會召他來做如此機密大事?此外,趙普也並非不能擬文,他有若干上疏,文辭典雅豐贍,也是一才子,如有這大功勛,他更不當推讓。此外,陶谷若做此事,他留下的各類傳世文件中,當有透露,但迄今找不到星點蛛絲馬跡。故陶谷擬文事,必假。
傳奇故實中還說秦王趙廷美先“幽死”,南陽王趙德昭後“自殺”,這個時間就不對,因為趙德昭自殺在太平興國四年(979)八月;趙廷美出事被罷官是在趙德昭自殺三年後的三月。《建隆遺事》記錄的這個故實,在時間、人物、身份說明上,都有令人生疑的地方,所以此事歷來被人打量,不敢肯認。《續資治通鑒長編》作者李燾就在引用這個故實後說,書中語言有很多鄙陋之處,不像王禹偁的風格,因此“不可據信”。但李燾也同時認為:史上記錄太宗之事,趙廷美做開封尹、趙德昭領貴州防御使,正與太太宗之前,讓太宗先領睦州防御使,後又做開封尹的行跡一樣。先領一個防御使,而後再做開封尹,這樣經由歷練,就可以順利接近帝位。因此李燾說:“恐昭憲及太祖意或如此,故司馬《記聞》亦云太后欲傳位二弟。蓋當時多有是說也。”恐怕昭憲太后也即杜太后和太祖當時的本意確實如此,所以連司馬光《涑水記聞》也說太后要太位給兩個弟弟,那是因為當時很多人聽說過這樣的傳說。
李燾的結論性意見是:雖然這個傳奇故實不可據為信史,但也“不可全棄”。他給出的方法就是“兩存其說”,並且相信太祖太宗的盛德,自能在後世為人明了,哪裡是誣言,應該有人知道。
我的結論性意見是:“金匱之盟”可信。杜太后確有趙匡胤之後傳趙光義之提議;而趙光義傳趙廷美,再傳趙德昭,這個約定,則未必為真;但一定是有一種宮內說法,涉及這個模式。而趙廷美、趙德昭也應該知道有此一說。比較有意味的是:趙廷美可能在認真期待此說的實現,在後來的記錄中,他甚至也有推演此說成真的努力。這樣,就有了覬覦皇位進行權力再分配的心思和動作。按照後來的邏輯倒推,趙廷美可能做事不謹慎,且有被他人“陰謀擁戴”的絕大可能性。但故實邏輯開始有了起點的時候,那就只能走向一個個節點,後走向終點。邏輯起點,是“業”是“因”,節點與終點,是“果”,一個個“果”。
趙廷美“覬覦”是“造因”之始,“幽死”是“結果”之終。
而太宗趙炅,終沒有保全兄弟趙廷美,必與“大事不糊塗”的呂端有關。作為內定為太宗未來繼承者的趙廷美,理當行使“太子”職能,這職能之一就是:皇帝外出時,太子負有“監國”的責任。而太宗當年北伐契丹,本來是留下趙廷美監國的,結果趙廷美被呂端一番勸導,竟跟從太宗一起北上了。這事不合帝王家事之習慣法。有此一變,太宗應該對“太子”人選有了不一樣的感覺和心思。這個應該是太宗沒有保全趙廷美的隱秘的動力。
而趙普與盧多遜,這兩位大宋名相,則是趙廷美“幽死”的大力推手。
《建隆遺事》中的顧命大臣
還是要說到王禹偁和傳為他著的《建隆遺事》。
他的書中,趙普和盧多遜幾乎相當於趙匡胤的“顧命大臣”。那又是一個近於傳奇的故實。
說趙匡胤似乎知道自己就要“晏駕”,此前一天,就派中使宦官“急召”兩位名相入宮。在皇上寢閣,二位到了皇上病榻前。趙匡胤說:“我知道我這病肯定是不能醫治了。我要見二位愛卿沒有別的,因為有幾件事還沒有來得及施行,你們拿筆墨來,記錄我的話,我死後你們一定要盡力施行,如此,我‘瞑目無恨’了。”趙普等記錄的幾件事,都關係“濟世安民之道”,趙普、盧多遜二人看後,不禁嗚咽流涕說:“這些事,我們都會依照聖君您的宏謨來執行,但有一件大事,還沒有看到陛下指示。”老趙問何事,趙普等回道:“大宋還沒有立太子,陛下如果有萬一,諸王之中應該立誰啊?”趙匡胤說:“可立晉王。”趙普二人說:“陛下艱難創業,後國家有了升平氣象;如此,自應由聖子受命為帝,不可從諸兄弟間論此事啊!臣等擔心一旦如陛下決定,大事一去,那可就不好回旋啦。請陛下考慮成熟。”趙匡胤說:“我不忍違背太后的‘慈訓’。太后的意思是海內已經小康,但更應選一位‘長君’而不是‘幼君’來管理天下。我意已決,請諸公好好為我輔佐晉王。”說罷,令人取出御府的珠玉金器等賜給趙普、盧多遜,讓他們回到自己府邸去了。第二天,太祖崩。
此後,太宗知道趙普等人有這樣一番不利於自己踐祚的議論,對這二人就有了不滿。等到正式繼位後,就因為盧多遜與秦王趙廷美“謀逆”事有牽連,將他貶死在嶺表之地;趙普則因為有宮中婦人的暗中相助,免予一死。
大意如是。
《續資治通鑒長編》的作者李燾不信這個說法,認為這個“顧命”說法與前面的“再傳”說法,文字間相矛盾,好像趙普不知道有個“再傳”的說法似的。另外,太祖駕崩時,趙普已經罷相,正在外地做節度使,不可能與盧多遜同時為相。
李燾的結論性意見是:這一段故實,大有“污蔑君父”之惡,很有可能是盧多遜親黨幹的活兒。因為趙普得罪人多,更與盧多遜不和,故“盧黨”大肆詆毀趙普,托名王禹偁,將這些事竄入《建隆遺事》中。王禹偁乃是直言人物,多次遭遇太宗貶黜,所以“盧黨”群小借機來做此事,擴大影響,聳動視聽,嫁禍趙普。
我的結論性意見是:確如李燾所論,但趙普勸諫太祖不要傳弟而傳子,也即改變“兄終弟及”模式,回復“嫡子繼承”模式,應確有此事;盧多遜在心理天平上倒向趙廷美,並與之密切來往,商討大計,也應屬實;趙普與盧多遜關係惡化,更是實有其事。不同的是:一系列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已難考證,但根據後來史實倒推,則不難看到,這一段“顧命”故實,有與史實呼應的情節關係,就事件邏輯而不是具體細節而言,並非向壁虛造。
為趙炅辯誣:太宗不會謀害親侄
趙匡胤的兩個兒子都不幸早死。
趙德昭,太平興國四年(979),太宗“乘勝取幽薊”不利,不予頒賞,他勸諫叔父要及時頒賞,遭遇太宗冷嘲訓斥,自殺,年三十二歲。南宋時,他的九世孫是宋理宗,十世孫是宋度宗,十一世孫是宋末三個幼主。
趙德芳,太平興國六年(981)病逝,年二十二歲。南宋時,他的六世孫是宋孝宗、七世孫是宋光宗、八世孫是宋寧宗。坊間往往稱趙德芳為“八賢王”“八千歲”,事實上不確。他死得太早了。
南宋,從孝宗開始,帝王譜系回歸到太祖一支。這是後話不提。
但是因為太祖這倆兒子都在青年時期死去,於是,趙廷美有了不安。
按照古來帝王辣手傳統,父子相殘、兄弟互害的故實太多了。唐太宗一手導演的“玄武門之變”,更是人所熟知,趙廷美也應該不陌生。他在不安中有些不知所措,一些動作也往往令人生疑。
趙廷美不安,可以理解。但將趙匡胤兩個兒子之死理解為太宗所害,此事在大宋朝很難定讞——沒有真實證據,不合推演邏輯。
我不信太宗謀害侄子說,認為這類說法還在“陰謀論”窠臼中打轉。“陰謀論”中,常見的一個說法就是:趙德昭、趙德芳,如果不是被謀害,怎麼會那麼年輕就死掉?
讀五代史、讀宋史,會發現,那個時代,早夭的人物太多了。就這個問題,我願意為趙炅辯誣。看看趙炅他自己的兒子,就知道,宋初,早夭幾乎是一個常見的生命現象。
太宗有九個兒子,長子元佐,次元僖,次即真宗皇帝,次元份,次元杰,次元偓,次元偁,次元儼,次崇王元億。
長子趙元佐瘋癲半世,卻獲長壽,到仁宗天聖五年(1027)去世,年六十二歲。
太宗二子趙元僖,是太宗非常喜愛的一個兒子,年紀輕輕時,就被任命為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廣平郡王,後又進封陳王,改名趙元佑。趙元佐瘋癲後,太宗已經有意要他來繼承皇位。雍熙二年(985),以趙元僖為開封尹兼侍中,進封許王,加中書令。這是立為太子的節奏。淳化三年(992)的一個冬天早晨,元僖早入朝,正坐在大殿旁的一個廬幕中等待上朝,忽然覺得身體不適,就直接回府邸了。太宗知道消息後,趕緊起駕去看望兒子,但元僖病已重。太宗呼叫他,還能勉強應答,一會兒工夫,薨,年二十七歲。
史稱“上哭之慟,廢朝五日”,太宗哭泣得十分悲痛,五天沒有上朝。
元僖“姿貌雄毅,沈靜寡言”,他做京兆尹五年,“政事無失”。他死了以後,太宗一直追念不已,常常“悲泣達旦不寐”,成宿地痛哭,以至於不能入睡。甚至,還專門寫了《思亡子詩》給近臣們看。
元僖之死,還有另一種說法。
說元僖尹開封府時,太宗選了一批名士如呂端、張去華等人輔佐他,又為他娶了功臣李謙溥的女兒為妻。但元僖不喜歡李氏,卻迷戀侍妾張氏。張氏綽號“張梳頭”,應該是一個講究發型的美女。但這個女子心腸狠毒,智商不高,很想謀害李氏,自己來做夫人。淳化三年太宗生日前,家人要做壽禮。張氏預先花了萬金請人製作了一個帶有機關的黃金酒壺,一部分裝美酒,一部分裝毒酒。到了早上入朝見太宗時,元僖夫婦要率先上壽,張氏就為二人斟酒,先給元僖倒了美酒,又給李氏倒了毒酒。但沒有料到的是,夫婦二人無意中臨場互相調換了杯中酒。張氏躲在屏風後觀看,急得揪耳朵跺腳丫,但已經無濟於事。元僖飲酒後,到廬幕中,就覺得不適,已經昏憒不省人事,來不及正式賀壽,就被人扶上馬往府中走去,走在東華門外,還從馬上掉落下來,被人扶著勉強回到家中。回去後,就死了。太宗知道後,當即命人調查,很快破案。當事人都受到了極為嚴厲的懲罰:張氏和製作酒壺的匠人等,在冬至日被“臠釘”於東華門外,元僖府中的輔佐們都被貶官。
記錄這件事的是南宋文人王铚,在《默記》一書中。書中言,張去華的孫子張景山曾經說過這件事,張去華也因此事而貶官,所以張景山知道得很詳細。王铚看到的北宋國史記錄,說到此事,認為多有“微辭”,也即隱晦之詞。他認為張景山說的可能更真實。
史上記錄,往往有采自“坊間想象”者。關於趙元僖,就有另外一個記錄。
說寇準通判鄆州時,被太宗召見。太宗對他說:“知道愛卿深謀遠慮,你試著來為朕決斷一事——但這事不要驚動朝廷內外。此事,我已經與大臣議論很久了。”寇準問什麼事,太宗說:“東宮趙元僖經常做不法之事,他日一定會有桀、紂般的惡行。打算廢了他,但東宮也有兵甲,我又擔心因此而招來禍患。”寇準說:“可以選一個日子,要東宮到某處去主持行禮大典,其左右侍衛都要跟著他去。陛下可以派人搜查東宮,如果真有不法之事,等他回來給他出示,隔開左右不要讓他人進來,這時,就是一個宦官的力量也可以做得。”太宗認為他說得對,就按這法子,在趙元僖的王宮搜查出了很多濫刑之器,有剜眼、挑筋、摘舌等刑具。趙元僖伏罪,這才選了後來的真宗皇帝為太子。
據說,這是宋人張唐英所著《仁宗政要·寇準傳》中的文字。
但這個記錄,與其他史實記錄差異太大,內中漏洞太多,很少有人相信。
太宗三子,就是宋真宗,平安一生,享年五十五歲。
太宗四子趙元份,死時年三十七歲。
他的兒子趙允讓,後來封為濮安懿王,其子就是後來即位的宋英宗。大宋曾有一場著名的“禮儀之爭”,史稱“濮議”。這一場爭論曠日持久,成為聳動朝野的文化大事件,過程複雜而又生動,簡言之,就是宋仁宗無子,而以濮安懿王之子趙曙為子並即位,那麼,應該以濮王為皇考,還是以仁宗為皇考?卷入這一場爭論的有當時的著名大臣韓琦、呂誨、歐陽修、範純仁等,朝中分為兩派,各執一詞,各自有理。在禮制和禮治天下的文明邦國,這類出於孝道的爭論,就是天大的事件。這是後話,容當後表。
元份這個人很寬厚,守禮,氣度不凡,有一種典雅昂然之姿。但他娶了個厲害夫人李氏。史稱李氏“悍妒慘酷”,驕悍、妒恨、殘忍、酷毒,宮中女婢有人小不如她心意,不是鞭打就是杖打,有時甚至將人活活打死。太宗賞賜禮物給諸子時,往往告訴要“均給”,也即府邸中人都有份,但李氏常常都收歸己有,不給他人。她對元份似也無情。元份生病臥床時,太宗親自來看,發現左右居然沒有人侍奉湯藥。元份死的時候,李氏一點憂戚之容都看不出。大宋皇室,男兒往往心地柔軟,身居帝王、親王、皇胄之貴,卻鮮有暴戾恣睢之人。
“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
太宗五子趙元杰,真宗咸平六年(1003)的一個夏天,“暴薨”,忽然死亡,年三十二歲。死因不明。
這是太宗的一個有才的兒子,至道二年(996),授揚州大都督、淮南忠正軍節度使,封吳王;真宗時又授徐州大都督、武寧泰寧等軍節度使,改封袞王,大多為武職,但他骨子裡卻是個文人。史稱元杰“穎悟好學”,他有詩詞天賦,還有書法天賦,草書、隸書、飛白書法都有不俗的成就。他還很年輕的時候,在自家府邸建樓,藏書兩萬卷。又建造大園子,內有亭臺樓閣,且安放了很多假山,作為遊樂休憩的所在。大園子建好後,他很得意,置辦大型酒會,約請僚屬參觀、助興。
有一位府中的翊善名叫姚坦,在一片叫好聲中,獨自低頭不看那些假山。元杰就強令他看看,發表點意見。
姚坦說:“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我只看到血山,哪裡有什麼假山。
元杰驚問何故,姚坦回答:“在鄉下田舍時,看見州縣衙役們來催繳賦稅,有人暫時湊不齊斤兩,就抓人家父子兄弟,送到縣裡鞭笞,只見流血遍體。這些假山都是小民租稅所為,不是血山是什麼?”
元杰聞言,很是不快,但也拿他沒有辦法。
當時太宗也正在苑囿之內做假山,聽到這事後,趕忙叫人停工,將假山全部毀掉,不敢再建。
翊善,詞義是輔佐人善言善行,唐代開始為太子設贊善大夫,宋改為翊善。主要職責是侍從講授。相當於太子老師,是個很有尊榮的職務。
姚坦初入趙元杰府邸時,太宗就曾召見他和其他翊善們,很誠懇地說:
“我這些兒子生長在深宮,不懂世務,所以一定要選擇優秀的士大夫作為輔佐導師,要讓他們每天都能聽到忠孝之道。你們這些翊善,都是朕千挑萬選出來的,各自要勉力做好這件事。”
姚坦的故實,是思想史一大關節,理清個中委曲,對理解中國傳統文人“以訐為直”的特點是一把秘鑰,值得說說。
史稱姚坦性情“木強固滯”,像木石一樣堅硬、固執,不太懂圓通。但這是史上評價,太宗對他的評價卻經歷了一個過程。看清這個過程,可以了解宋代文人性格的複雜與豐富。
趙元杰雖然堆壘假山,不免靡費,但是並不一味搜刮民脂民膏,也並不過分放縱,但是只要稍稍有點“佚豫”,悠閑安樂,姚坦就要“丑詆”,用一些過分的難聽的話矯正他,而且還常常“暴揚其事”,到處傳播趙元杰的“佚豫”。元杰不喜歡這個“老師”,認為他太過分。太宗也漸漸了解到姚坦的“直言”有很大程度的攻訐成分,就勸導姚坦說:
“元杰啊,也算是知書好學的人啦,也差不多算一個賢良的親王啦。即使他有不合於禮法之處,您也應該婉辭規勸開導;何況他並沒有大的過錯,您這麼詆毀他攻訐他,這難道是輔佐贊助之道嗎?”
趙元杰的左右也不喜歡姚坦,就教元杰裝病不上朝。太宗每天讓人來看望他,過了一個多月,“病”還沒有好,太宗很是憂慮,於是召來乳母問元杰的病情。這個乳母正是教他裝病的人,就對太宗說:“王爺本來沒有病,但是這個姚坦總是挑刺,弄得王爺日常活動也不自由,不爽,所以生了病。”太宗一聽這話來了氣,他不是氣姚坦,而是氣兒子和兒子的左右。太宗說:“我好不容易選了端正之士,輔佐兒子為善,兒子不能用師傅的勸諫,現在又裝病!這是要讓我剔除端正之士,你們好放縱自便!做不到!況且我兒年少,一定是你們這些老家伙出的餿主意!”於是讓人將乳母帶到後苑,打了一頓板杖。隨後,又召來姚坦,安慰他說:“愛卿居住在王宮裡,能以正派被群小嫉恨,實在不易。愛卿就這樣,不要擔心別人進讒言,朕必不聽!”
太宗此舉,就叫明察,看上去很簡單的事,但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仁宗朝有個名相呂夷簡評論此事說:
愛憎之不察,為害深矣。妺喜惡鄂侯,讒於桀而脯之。妲己惡比幹,讒於紂而剖之。驪姬惡申生,讒於獻公而殺之。靳尚惡屈原,讒於楚而逐之。絳、灌惡賈誼,讒於文帝而疏之。甚者李林甫讒殺太子,二王及其朝臣韋堅、李邕輩,又逐太子妃韋氏、良娣杜氏。嗚呼 ! 愛憎之不察,為害如此。且小人之心險如山川,毒如豺虎,微失其意,則無所不至。人君不能明之,則讒人得行,善人罹患,可為痛惜者也。太宗明宮人之詐計,知姚坦之見憎,雖堯舜之聰明,殆不過是。
如果不能明察人之愛憎,作為君王,為害就太深了。夏王朝的妺喜憎惡鄂侯,就向君王桀進讒言,結果將鄂侯做成了肉醬。殷王朝的妲己憎惡比幹,就向君王紂進讒言,結果將比幹剖了心。晉國的驪姬憎惡申生,就向獻公進讒言,結果將申生逼得自殺。楚國靳尚憎惡屈原,向楚王進讒言,結果將屈原驅逐流放。漢代的周勃、灌嬰憎惡賈誼,就向文帝進讒言,結果將賈誼外放疏遠了他。更有甚者,唐代的李林甫還進讒言殺害太子、二位親王以及朝臣韋堅、李邕,驅逐太子的妃子韋氏和良娣杜氏。唉!愛憎不能明察,為害就是這樣!況且小人之心傾險起伏如山川,毒辣狠心如豺虎,稍微有一點讓他失意,他報復起來就沒有他做不到的。人君如果不能明察這一點,則讒言就會生效,導致善人遭殃,真是可為痛惜的啊。太宗能明白洞察趙元僖東宮之人的詐計,知道姚坦被他們憎惡,即使是堯舜那樣的視聽聰明,也不過如此。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