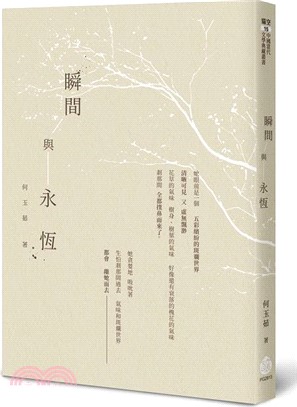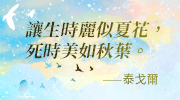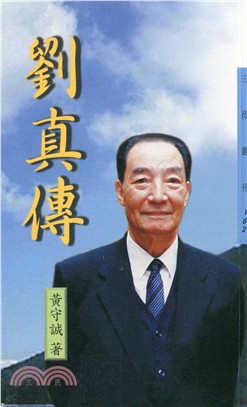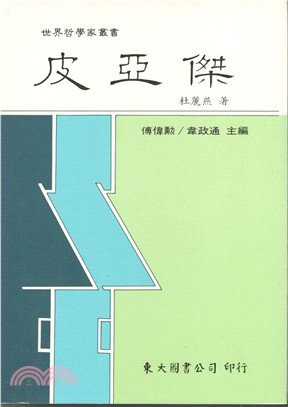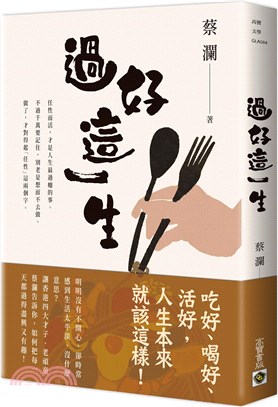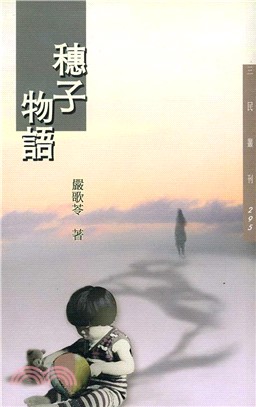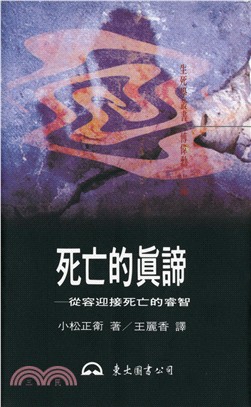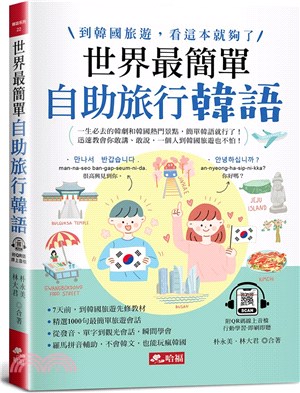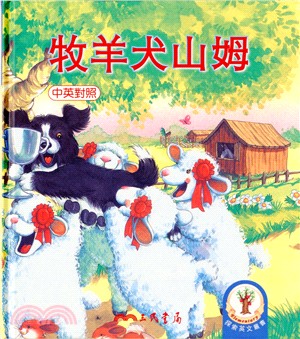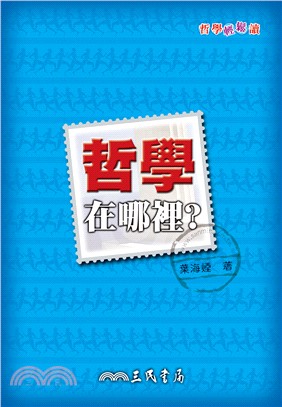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文學是對自由的渴望──而待寫作深入下來,我才開始意識到,寫作其實遠不只是一片浪漫的雲彩,它也許是一種超脫,但它更是一種對世俗生活的回望;只有回望了,那雲彩才可能閃爍出靈光異彩。」──何玉茹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在小城文化館辦報紙的葉建華來到師範學院文學班進修,她沉迷在褚威格、弗洛姆、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細緻又開闊的世界,與同學藍音的交流,也讓她在短時間內重新經歷了前半生的精神跋涉──幼時對閱讀的渴望、文革時與學長偷偷躲在充滿老鼠的圖書館讀《簡愛》,為了脫離農村來到城市擔任臨時雇員,卻發現所謂「城市」、「農村」的分野彷彿只存在於戶口名簿上,人們的口音、行事作風早已沒有了界線,但人與人之間實質的不平等卻依然存在。
於是她試著在書裡、在愛情裡、在工作裡、在寫作裡思索關於「平等」的答案,來到文學班就像是陽光裡有了樹蔭,雨天裡有了雨傘,那沒著沒落、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竟是不知不覺地消失了。只是兩年的時間轉瞬即過,這些思考、迷惘、渴望、愛戀是否能昇華成永恆?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在小城文化館辦報紙的葉建華來到師範學院文學班進修,她沉迷在褚威格、弗洛姆、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細緻又開闊的世界,與同學藍音的交流,也讓她在短時間內重新經歷了前半生的精神跋涉──幼時對閱讀的渴望、文革時與學長偷偷躲在充滿老鼠的圖書館讀《簡愛》,為了脫離農村來到城市擔任臨時雇員,卻發現所謂「城市」、「農村」的分野彷彿只存在於戶口名簿上,人們的口音、行事作風早已沒有了界線,但人與人之間實質的不平等卻依然存在。
於是她試著在書裡、在愛情裡、在工作裡、在寫作裡思索關於「平等」的答案,來到文學班就像是陽光裡有了樹蔭,雨天裡有了雨傘,那沒著沒落、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竟是不知不覺地消失了。只是兩年的時間轉瞬即過,這些思考、迷惘、渴望、愛戀是否能昇華成永恆?
作者簡介
何玉茹
河北石家莊人,曾任《河北文學》編輯、《長城》副主編、河北省作協創作室主任。已出版長篇小說《冬季與迷醉》、《葵花》、《前街後街》等,小說集《天外之音》、《樓下樓上》等,中短篇小說、散文隨筆散見於各文學期刊,多篇獲獎並被譯介至美國、日本等。
河北石家莊人,曾任《河北文學》編輯、《長城》副主編、河北省作協創作室主任。已出版長篇小說《冬季與迷醉》、《葵花》、《前街後街》等,小說集《天外之音》、《樓下樓上》等,中短篇小說、散文隨筆散見於各文學期刊,多篇獲獎並被譯介至美國、日本等。
書摘/試閱
這是一座年輕的師範學院。
從它的樹木就能看出來,成排的楊樹啊、槐樹啊、柳樹啊、梧桐啊,以及各色的果樹、冬青樹什麼的,一棵棵光光溜溜、楞頭楞腦的,就像是初涉社會的毛頭小夥,還看不到任何被損傷的痕跡,更沒有歷經滄桑的老樹一般地穩若泰山,有風吹來,腦袋搖啊搖的,身子也隨了晃啊晃的,叫人都有心想上前扶一扶它們了。但有了它們,到底是不一樣的,青澀的氣息繚繞在空氣裡,繚繞在高高低低的建築裡,與其間學生、老師的氣息纏綿、交融,讓學院的分分寸寸都似有了生機勃勃的意味了。
學院的建築倒不出眾,一座四層的灰色教學樓,十幾排青磚紅瓦的教室,教室後面是幾排紅磚、平頂的宿舍,而矗立於教學樓一側的圖書館,就算是學院最高、最矚目的建築了。它比教學樓高出了許多,據說和同類學校比,無論設施,無論藏書,它都是名列前茅的;還據說,建這圖書館是校長親自督陣的,他每天都要到現場去,也不說話,看一看、轉一轉就走。但已足夠讓那負責施工的認真嚴謹起來,因為他知道校長早年是北大畢業,並留校在圖書館待過幾年,北大的圖書館什麼成色?在這樣的校長面前,任何馬虎眼都是打不得的。
校長姓金,一米八幾的個頭兒,走路挺胸抬頭,目不斜視,出現在哪裡,哪裡的人便仰視過去,一派欽慕。卻也有個別不仰視的,見了他反要低下頭去,就像沒看見一樣。那是幾個專心做學問又頗有個性的教師,對權力人物總有本能的疏遠。這時候校長反會哈下腰來,主動跟他們打著招呼,有時還會開一半句的玩笑。逢到那幾個不笑時,看到的人好替校長尷尬,校長卻也不在意,下次見了仍主動打招呼,倒像他們是他的領導似的。愈是這樣,人們對校長的欽慕就愈持續著,一個懂得尊重學問、尊重下屬的領導,到底還是難得的。
校長是沒有課程安排的,偶爾上一次,也是在那個能容納千人的禮堂裡。就看禮堂的窗口、過道,角角落落都擠得滿滿的,校長渾厚的男中音迴盪其間,讓聽課的學生往往會有一種奇妙的夢境感,他們會想,這是在聽課嗎?分明是一種享受啊!
校長講的是文學課,他善於用一個個的故事連結而成,故事講完了,文學、政治、歷史、哲學什麼的也就涵蓋其中了。大家聽了,坐在禮堂裡怔怔的,像是被擊中了,又像是要延續那享受,直到有人帶頭鼓起掌,暴風雨般的掌聲才忽然響了起來。
葉建華第一次聽校長的課,是坐在靠後的位置上。校長的模樣都沒看清,但她卻最後一個離開禮堂。她覺得自個兒的身體沉重而又輕盈,那剛剛被打開的鳥兒一樣飛翔的思緒讓她有一種強烈的幸福感和永恆感。永恆感,她已經很多年沒有過了,無憂無慮的兒童期過去,永遠都是短暫、漂泊的感覺。
她離開禮堂往教室走。到處是年輕又陌生的面孔。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的感覺,也沒有一個人可以聽她說說這感覺,即便是同班同學,也還不大熟悉,她只勉強可以叫出人家的名字。她晚入學了兩星期,時間不算太長,但已足以將她和班裡同學疏遠開了。她感覺班裡現在是兩個陣營,一個陣營是已經相熟成一片的全體同學,一個陣營則只她葉建華一個。這感覺讓她好孤單,幸好有了校長的這一課,她就像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將自個兒不由分說地一整個地投入了進去。其實她投入的並不僅是校長的講,更是因校長的講而從未經見過的氛圍,臺上臺下,自由活潑,心領神會,心心相惜,彷彿人人都變成了臺上的校長,幽默而智慧,又彷彿校長變成了學生,年輕而充滿活力……。她想,真好,多麼好啊!
走在年輕學生中間,她才感覺到自己的不年輕。今年她三十二歲,已有皺紋悄悄爬上了眼角。與她差不多年齡的班上還有一些,但二十幾歲的也滿眼都是,他們都「大姐,大姐」地叫她,引得那些和她同齡甚至比她大些的也聲聲叫著「大姐」。這叫法沒拉近她和大家的距離,反讓她和大家在心裡做著另外的對比,她只在報刊上發表過幾篇末題小說,而一些同學早都是《當代》、《十月》一類大型文學刊物的作者了。特別是,有一次有同學問起她晚到的原因,她說館長沒點頭,她一直在等館長的表態。同學問:「你是帶工資上學?」她說沒工資,不過是臨時工。那同學便大笑起來,其他同學也笑,就像她愚蠢得不可理喻。半天她才明白,大家原來在笑她的安分,太安分了,既要安分,又何必搞文學呢?文學是什麼,文學是對自由的渴望,不要說臨時工,就是帶工資的正式工,對自由的選擇也是不言而喻的,連對領導說「不」的勇氣都沒有,還何談文學創作啊!
在大家的笑聲中她的臉紅一陣、白一陣的,讓她更難受的是她自個兒也覺得大家的說法是有道理的。當然,等館長表態是有對他的一份尊重。館長一直很器重她,是他慧眼識人,從郊區農村一下提拔了她。那是個區屬文化館,他派她在文化館辦一張民俗小報,那小報已辦得很有起色。
她的解釋讓大家笑得更厲害了,有同學一針見血地指出說:「問題就在這兒,他提拔了你,就想要控制你,限制你的自由。比起自由,他那點提拔算個屁呀!」
是啊,自由和提拔比,當然自由是重要的,那同學話糙理不糙呢。可他的表情、語氣顯然又是自大、小視的,像是在說:「你這樣的,註定是要被控制的,不控制你控制誰?」
就在這時,一個針鋒相對的聲音忽然響起來了:「喲,是哪位這麼深刻、這麼偉大啊?」聲音不高,場上卻立刻安靜下來。葉建華望去,見是一個穿裙子的披肩髮女生。全班總共七個女生,只有這女生每天每天地穿裙子,因此她記住了她的名字──藍音。藍音有一張明亮、乾淨的臉,她的聲音也是明亮的,就聽她說:「這事要換了我,我也會跟葉建華一樣。做人不能只顧頭不顧屁股,自由是一回事,知恩報德又是一回事呢。大文學家你說是不是?」那同學反唇相譏道:「沒看出來,現代的外表下還藏了顆古典的心啊。」藍音臉色一沉,又忽然一笑道:「沒看出來的多著呢,不急,咱一道兩年,你就耐下心來慢慢看吧。」
藍音說完拉了葉建華就走,就好似葉建華是她多年要好的朋友。
從那以後,葉建華和藍音竟是真的好起來了。好的原因還有,藍音從不叫她「大姐」,而是直呼「葉建華」。藍音比葉建華小了一歲,但葉建華喜歡她這麼叫,這麼叫才有平等感。對,平等感,來這裡上學,也許就為的這平等感呢!
與禮堂大課相比,和藍音的好到底真切多了,至少表面的孤單沒有了。藍音常與她結伴而行,圖書館、閱覽室、校前的梨園、校後的小樹林,到處都留下了她們同行的足跡。葉建華後來問過藍音:「那天為什麼要幫我說話?」藍音說:「喜歡你唄。」葉建華臉一紅說:「我才不信。」藍音說:「臉紅什麼,我又不是男的。」藍音哈哈笑了一陣,才說:「是真的,也不知為什麼,一看見你就覺得投緣。」藍音提起葉建華第一天來到學校的情景,背了行李,提了網兜,兩條辮子搭在胸前,就像一個剛回城的知青。藍音那時正在校門口散步,盯了葉建華看了一會兒,忽然就問:「你是葉建華同學吧?」葉建華說:「是啊,你怎麼知道?」藍音說:「一個叫葉建華的女生還沒到,班裡同學都知道啊。」葉建華說:「可你從沒見過我。」藍音說:「人和名字都是上天安排好的,一看就知道。要是我這模樣叫了『葉建華』才奇怪呢。」葉建華不由得笑了,這女同學,眼睛黑黑的,鼻子挺挺的,面皮白白的,細膩得就像小孩子的,看了不由得會叫人疼惜。她穿了件小碎花連衣裙,上搭一件純白色短款線衣,腰圍那裡,一雙大手似就可以圍攏起來。葉建華以為藍音是班裡特意派人來接她的,藍音要替她拿網兜時她便手一鬆遞了過去。誰知沒走多遠,藍音就氣喘吁吁、滿臉通紅了,她說:「你這裝的什麼東西?好沉啊!」後來,葉建華仍自個兒提上,輕鬆自如,臉不變色心不跳,一直走到了她們的教室。
兩人回憶著初次的相遇,說一陣、笑一陣的,藍音說:「那天空了手跟你並排走,知道我一直在想什麼嗎?」葉建華說:「想什麼?」藍音說:「這麼有力氣的女子,她丈夫一定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葉建華說:「這回你可是猜錯了,我丈夫還不知在哪兒呢。」藍音失望道:「不會吧,上天咋會這麼安排呢?」葉建華說:「那你呢?」藍音說:「你看我像是個有丈夫的人嗎?」葉建華說:「有或沒有,於你都不奇怪。」藍音說:「那是有還是沒有呢?」葉建華看了藍音一會兒,說:「說不好有還是沒有,但一定有過。」藍音說:「為什麼?」葉建華說:「你這樣的人,沒有丈夫會影響男女世界的平衡和諧。」藍音不由得大笑:「想不到上天也會讓你這樣的人壞一壞啊!」葉建華喜歡藍音的大笑,那聲音就像一片晴朗的天空;她還注意到,藍音總喜歡說上天、上天的,她後來也不由得多次想過,自個兒和藍音的相遇,是否是上天的意思?
當然葉建華又和藍音認真討論過自由和知恩報德的事,葉建華堅持認為同學們對她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兩者一旦有衝突,自由一定是第一位的。藍音則仍堅持兩者是兩回事,一旦有衝突也不能狗熊掰棒子一樣撿一個扔一個。藍音問葉建華:「晚到學校兩星期,難道你後悔了嗎?」葉建華說:「沒有啊。」藍音說:「還是的,我認為這是解決衝突的最好選擇了。」葉建華說:「要是館長最後不點頭呢?」藍音說:「那就另當別論,說明他對你不是真正的提拔,是有私心的提拔,也就無所謂恩不恩了。」葉建華說:「你這麼說我心裡就踏實了。」藍音說:「什麼意思?」葉建華嘆口氣說:「事實是,館長他最後真就沒點頭,他的理由只是需要我留下來辦那張小報。我說小報別人也能辦,他說別人又沒得到他的提拔。」藍音驚道:「怪不得,原來你是早把自由放在第一位了啊!」葉建華說:「也沒有,那時壓根兒就沒想過自由不自由的,只是渴望,一種渴望壓倒了一切。」藍音說:「什麼渴望?」葉建華說:「上學的渴望。」藍音說:「渴望拿到一張文憑?」葉建華臉一紅說:「你咋會這麼看我?」藍音笑道:「渴望文憑有什麼錯,咱班為一張文憑來的多了去了。」葉建華說:「那你呢,也是為一張文憑?」藍音說:「我就不該為文憑了?」葉建華說:「我才不信,因為我就不是為文憑,我只為上學,上大學,在教室裡聽課,在圖書館讀書,同學間直呼其名,平等相待,然後隨便在哪個角落自由自在地寫小說。」葉建華說:「我沒有一份正式工作,大家也許會認為,為文憑而來的最該是我了,可我真心地告訴你藍音,我就是為上學來的,我好像天生喜歡學校這種地方。」葉建華說:「知道嗎,有一年省文聯辦寫作班,班期只兩星期,可就在這兩星期裡,我幸運地和一個正在上大學的女學員相識了。寫作班結束後這女學員便開始從學校圖書館借書寄給我看,契訶夫的、托爾斯泰的、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屠格涅夫的、羅曼.羅蘭的、史坦貝克的……,太多了。我從沒去過她的大學,一收到書就覺得像是從天堂寄來的,而她便是那天堂裡的天使。」葉建華說:「我這個人,從沒有什麼具體的人生規劃,自從寄書的事發生後,我就更相信人與人、人與事間的精神聯繫了,更難有什麼實際目的了。這麼說大家也許很難相信,可藍音,我覺得你會相信,因為你相信我才把心裡話說出來的!」葉建華的一張圓臉紅通通的,一雙大眼睛亮閃閃的,顯然是有些激動了。藍音從沒見過激動起來的葉建華,她點頭說:「相信,我當然相信。不過我也真心地告訴你葉建華,文憑的確是我上學的目的之一。」葉建華望著藍音明淨的臉,相信藍音說的是心裡話,她想,相互說心裡話就不易了,還要怎麼樣呢?卻到底有些不甘心,還是張口問道:「你已經有一份好工作了,文憑還那麼重要麼?」葉建華曾聽藍音說過,她在一座城市的文化局工作。就聽藍音說:「要是有人總拿你的沒文憑說事,你說重不重要?」藍音的眼睛這時也亮閃閃的,白皙的臉上少有地生出了兩朵紅暈。葉建華覺出,就像剛才自個兒的動心一樣,藍音這是也動了心了,她本想說:「你看重的也許不是文憑,也許只是別人的『說事』吧。」但看著藍音臉上的兩朵紅暈,忽然有一種說不出的心疼,便不由得將嘴邊的話嚥回去了……
葉建華和藍音所在的班,在這所師範學院是個特例,生源全來自省內發過文學作品的青年作者。說是青年,由於年齡放寬到三十五歲,年過三十的幾乎能占一半了。據說這文學班,也是金校長跑上跑下親手創建的,他自己不寫東西,但他熱愛文學,那份熱愛,就如同信仰一般堅定、深厚。葉建華和藍音平時很少能見到金校長,但想到他就有一種莫名的踏實。他就如同校前、校後的樹木,是一種長遠的可依傍的感覺。她們的進修時間只有兩年,但她們的踏實感、永恆感卻是空前的,無比真實的。
從它的樹木就能看出來,成排的楊樹啊、槐樹啊、柳樹啊、梧桐啊,以及各色的果樹、冬青樹什麼的,一棵棵光光溜溜、楞頭楞腦的,就像是初涉社會的毛頭小夥,還看不到任何被損傷的痕跡,更沒有歷經滄桑的老樹一般地穩若泰山,有風吹來,腦袋搖啊搖的,身子也隨了晃啊晃的,叫人都有心想上前扶一扶它們了。但有了它們,到底是不一樣的,青澀的氣息繚繞在空氣裡,繚繞在高高低低的建築裡,與其間學生、老師的氣息纏綿、交融,讓學院的分分寸寸都似有了生機勃勃的意味了。
學院的建築倒不出眾,一座四層的灰色教學樓,十幾排青磚紅瓦的教室,教室後面是幾排紅磚、平頂的宿舍,而矗立於教學樓一側的圖書館,就算是學院最高、最矚目的建築了。它比教學樓高出了許多,據說和同類學校比,無論設施,無論藏書,它都是名列前茅的;還據說,建這圖書館是校長親自督陣的,他每天都要到現場去,也不說話,看一看、轉一轉就走。但已足夠讓那負責施工的認真嚴謹起來,因為他知道校長早年是北大畢業,並留校在圖書館待過幾年,北大的圖書館什麼成色?在這樣的校長面前,任何馬虎眼都是打不得的。
校長姓金,一米八幾的個頭兒,走路挺胸抬頭,目不斜視,出現在哪裡,哪裡的人便仰視過去,一派欽慕。卻也有個別不仰視的,見了他反要低下頭去,就像沒看見一樣。那是幾個專心做學問又頗有個性的教師,對權力人物總有本能的疏遠。這時候校長反會哈下腰來,主動跟他們打著招呼,有時還會開一半句的玩笑。逢到那幾個不笑時,看到的人好替校長尷尬,校長卻也不在意,下次見了仍主動打招呼,倒像他們是他的領導似的。愈是這樣,人們對校長的欽慕就愈持續著,一個懂得尊重學問、尊重下屬的領導,到底還是難得的。
校長是沒有課程安排的,偶爾上一次,也是在那個能容納千人的禮堂裡。就看禮堂的窗口、過道,角角落落都擠得滿滿的,校長渾厚的男中音迴盪其間,讓聽課的學生往往會有一種奇妙的夢境感,他們會想,這是在聽課嗎?分明是一種享受啊!
校長講的是文學課,他善於用一個個的故事連結而成,故事講完了,文學、政治、歷史、哲學什麼的也就涵蓋其中了。大家聽了,坐在禮堂裡怔怔的,像是被擊中了,又像是要延續那享受,直到有人帶頭鼓起掌,暴風雨般的掌聲才忽然響了起來。
葉建華第一次聽校長的課,是坐在靠後的位置上。校長的模樣都沒看清,但她卻最後一個離開禮堂。她覺得自個兒的身體沉重而又輕盈,那剛剛被打開的鳥兒一樣飛翔的思緒讓她有一種強烈的幸福感和永恆感。永恆感,她已經很多年沒有過了,無憂無慮的兒童期過去,永遠都是短暫、漂泊的感覺。
她離開禮堂往教室走。到處是年輕又陌生的面孔。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的感覺,也沒有一個人可以聽她說說這感覺,即便是同班同學,也還不大熟悉,她只勉強可以叫出人家的名字。她晚入學了兩星期,時間不算太長,但已足以將她和班裡同學疏遠開了。她感覺班裡現在是兩個陣營,一個陣營是已經相熟成一片的全體同學,一個陣營則只她葉建華一個。這感覺讓她好孤單,幸好有了校長的這一課,她就像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將自個兒不由分說地一整個地投入了進去。其實她投入的並不僅是校長的講,更是因校長的講而從未經見過的氛圍,臺上臺下,自由活潑,心領神會,心心相惜,彷彿人人都變成了臺上的校長,幽默而智慧,又彷彿校長變成了學生,年輕而充滿活力……。她想,真好,多麼好啊!
走在年輕學生中間,她才感覺到自己的不年輕。今年她三十二歲,已有皺紋悄悄爬上了眼角。與她差不多年齡的班上還有一些,但二十幾歲的也滿眼都是,他們都「大姐,大姐」地叫她,引得那些和她同齡甚至比她大些的也聲聲叫著「大姐」。這叫法沒拉近她和大家的距離,反讓她和大家在心裡做著另外的對比,她只在報刊上發表過幾篇末題小說,而一些同學早都是《當代》、《十月》一類大型文學刊物的作者了。特別是,有一次有同學問起她晚到的原因,她說館長沒點頭,她一直在等館長的表態。同學問:「你是帶工資上學?」她說沒工資,不過是臨時工。那同學便大笑起來,其他同學也笑,就像她愚蠢得不可理喻。半天她才明白,大家原來在笑她的安分,太安分了,既要安分,又何必搞文學呢?文學是什麼,文學是對自由的渴望,不要說臨時工,就是帶工資的正式工,對自由的選擇也是不言而喻的,連對領導說「不」的勇氣都沒有,還何談文學創作啊!
在大家的笑聲中她的臉紅一陣、白一陣的,讓她更難受的是她自個兒也覺得大家的說法是有道理的。當然,等館長表態是有對他的一份尊重。館長一直很器重她,是他慧眼識人,從郊區農村一下提拔了她。那是個區屬文化館,他派她在文化館辦一張民俗小報,那小報已辦得很有起色。
她的解釋讓大家笑得更厲害了,有同學一針見血地指出說:「問題就在這兒,他提拔了你,就想要控制你,限制你的自由。比起自由,他那點提拔算個屁呀!」
是啊,自由和提拔比,當然自由是重要的,那同學話糙理不糙呢。可他的表情、語氣顯然又是自大、小視的,像是在說:「你這樣的,註定是要被控制的,不控制你控制誰?」
就在這時,一個針鋒相對的聲音忽然響起來了:「喲,是哪位這麼深刻、這麼偉大啊?」聲音不高,場上卻立刻安靜下來。葉建華望去,見是一個穿裙子的披肩髮女生。全班總共七個女生,只有這女生每天每天地穿裙子,因此她記住了她的名字──藍音。藍音有一張明亮、乾淨的臉,她的聲音也是明亮的,就聽她說:「這事要換了我,我也會跟葉建華一樣。做人不能只顧頭不顧屁股,自由是一回事,知恩報德又是一回事呢。大文學家你說是不是?」那同學反唇相譏道:「沒看出來,現代的外表下還藏了顆古典的心啊。」藍音臉色一沉,又忽然一笑道:「沒看出來的多著呢,不急,咱一道兩年,你就耐下心來慢慢看吧。」
藍音說完拉了葉建華就走,就好似葉建華是她多年要好的朋友。
從那以後,葉建華和藍音竟是真的好起來了。好的原因還有,藍音從不叫她「大姐」,而是直呼「葉建華」。藍音比葉建華小了一歲,但葉建華喜歡她這麼叫,這麼叫才有平等感。對,平等感,來這裡上學,也許就為的這平等感呢!
與禮堂大課相比,和藍音的好到底真切多了,至少表面的孤單沒有了。藍音常與她結伴而行,圖書館、閱覽室、校前的梨園、校後的小樹林,到處都留下了她們同行的足跡。葉建華後來問過藍音:「那天為什麼要幫我說話?」藍音說:「喜歡你唄。」葉建華臉一紅說:「我才不信。」藍音說:「臉紅什麼,我又不是男的。」藍音哈哈笑了一陣,才說:「是真的,也不知為什麼,一看見你就覺得投緣。」藍音提起葉建華第一天來到學校的情景,背了行李,提了網兜,兩條辮子搭在胸前,就像一個剛回城的知青。藍音那時正在校門口散步,盯了葉建華看了一會兒,忽然就問:「你是葉建華同學吧?」葉建華說:「是啊,你怎麼知道?」藍音說:「一個叫葉建華的女生還沒到,班裡同學都知道啊。」葉建華說:「可你從沒見過我。」藍音說:「人和名字都是上天安排好的,一看就知道。要是我這模樣叫了『葉建華』才奇怪呢。」葉建華不由得笑了,這女同學,眼睛黑黑的,鼻子挺挺的,面皮白白的,細膩得就像小孩子的,看了不由得會叫人疼惜。她穿了件小碎花連衣裙,上搭一件純白色短款線衣,腰圍那裡,一雙大手似就可以圍攏起來。葉建華以為藍音是班裡特意派人來接她的,藍音要替她拿網兜時她便手一鬆遞了過去。誰知沒走多遠,藍音就氣喘吁吁、滿臉通紅了,她說:「你這裝的什麼東西?好沉啊!」後來,葉建華仍自個兒提上,輕鬆自如,臉不變色心不跳,一直走到了她們的教室。
兩人回憶著初次的相遇,說一陣、笑一陣的,藍音說:「那天空了手跟你並排走,知道我一直在想什麼嗎?」葉建華說:「想什麼?」藍音說:「這麼有力氣的女子,她丈夫一定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葉建華說:「這回你可是猜錯了,我丈夫還不知在哪兒呢。」藍音失望道:「不會吧,上天咋會這麼安排呢?」葉建華說:「那你呢?」藍音說:「你看我像是個有丈夫的人嗎?」葉建華說:「有或沒有,於你都不奇怪。」藍音說:「那是有還是沒有呢?」葉建華看了藍音一會兒,說:「說不好有還是沒有,但一定有過。」藍音說:「為什麼?」葉建華說:「你這樣的人,沒有丈夫會影響男女世界的平衡和諧。」藍音不由得大笑:「想不到上天也會讓你這樣的人壞一壞啊!」葉建華喜歡藍音的大笑,那聲音就像一片晴朗的天空;她還注意到,藍音總喜歡說上天、上天的,她後來也不由得多次想過,自個兒和藍音的相遇,是否是上天的意思?
當然葉建華又和藍音認真討論過自由和知恩報德的事,葉建華堅持認為同學們對她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兩者一旦有衝突,自由一定是第一位的。藍音則仍堅持兩者是兩回事,一旦有衝突也不能狗熊掰棒子一樣撿一個扔一個。藍音問葉建華:「晚到學校兩星期,難道你後悔了嗎?」葉建華說:「沒有啊。」藍音說:「還是的,我認為這是解決衝突的最好選擇了。」葉建華說:「要是館長最後不點頭呢?」藍音說:「那就另當別論,說明他對你不是真正的提拔,是有私心的提拔,也就無所謂恩不恩了。」葉建華說:「你這麼說我心裡就踏實了。」藍音說:「什麼意思?」葉建華嘆口氣說:「事實是,館長他最後真就沒點頭,他的理由只是需要我留下來辦那張小報。我說小報別人也能辦,他說別人又沒得到他的提拔。」藍音驚道:「怪不得,原來你是早把自由放在第一位了啊!」葉建華說:「也沒有,那時壓根兒就沒想過自由不自由的,只是渴望,一種渴望壓倒了一切。」藍音說:「什麼渴望?」葉建華說:「上學的渴望。」藍音說:「渴望拿到一張文憑?」葉建華臉一紅說:「你咋會這麼看我?」藍音笑道:「渴望文憑有什麼錯,咱班為一張文憑來的多了去了。」葉建華說:「那你呢,也是為一張文憑?」藍音說:「我就不該為文憑了?」葉建華說:「我才不信,因為我就不是為文憑,我只為上學,上大學,在教室裡聽課,在圖書館讀書,同學間直呼其名,平等相待,然後隨便在哪個角落自由自在地寫小說。」葉建華說:「我沒有一份正式工作,大家也許會認為,為文憑而來的最該是我了,可我真心地告訴你藍音,我就是為上學來的,我好像天生喜歡學校這種地方。」葉建華說:「知道嗎,有一年省文聯辦寫作班,班期只兩星期,可就在這兩星期裡,我幸運地和一個正在上大學的女學員相識了。寫作班結束後這女學員便開始從學校圖書館借書寄給我看,契訶夫的、托爾斯泰的、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屠格涅夫的、羅曼.羅蘭的、史坦貝克的……,太多了。我從沒去過她的大學,一收到書就覺得像是從天堂寄來的,而她便是那天堂裡的天使。」葉建華說:「我這個人,從沒有什麼具體的人生規劃,自從寄書的事發生後,我就更相信人與人、人與事間的精神聯繫了,更難有什麼實際目的了。這麼說大家也許很難相信,可藍音,我覺得你會相信,因為你相信我才把心裡話說出來的!」葉建華的一張圓臉紅通通的,一雙大眼睛亮閃閃的,顯然是有些激動了。藍音從沒見過激動起來的葉建華,她點頭說:「相信,我當然相信。不過我也真心地告訴你葉建華,文憑的確是我上學的目的之一。」葉建華望著藍音明淨的臉,相信藍音說的是心裡話,她想,相互說心裡話就不易了,還要怎麼樣呢?卻到底有些不甘心,還是張口問道:「你已經有一份好工作了,文憑還那麼重要麼?」葉建華曾聽藍音說過,她在一座城市的文化局工作。就聽藍音說:「要是有人總拿你的沒文憑說事,你說重不重要?」藍音的眼睛這時也亮閃閃的,白皙的臉上少有地生出了兩朵紅暈。葉建華覺出,就像剛才自個兒的動心一樣,藍音這是也動了心了,她本想說:「你看重的也許不是文憑,也許只是別人的『說事』吧。」但看著藍音臉上的兩朵紅暈,忽然有一種說不出的心疼,便不由得將嘴邊的話嚥回去了……
葉建華和藍音所在的班,在這所師範學院是個特例,生源全來自省內發過文學作品的青年作者。說是青年,由於年齡放寬到三十五歲,年過三十的幾乎能占一半了。據說這文學班,也是金校長跑上跑下親手創建的,他自己不寫東西,但他熱愛文學,那份熱愛,就如同信仰一般堅定、深厚。葉建華和藍音平時很少能見到金校長,但想到他就有一種莫名的踏實。他就如同校前、校後的樹木,是一種長遠的可依傍的感覺。她們的進修時間只有兩年,但她們的踏實感、永恆感卻是空前的,無比真實的。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