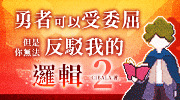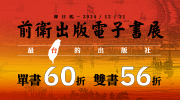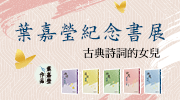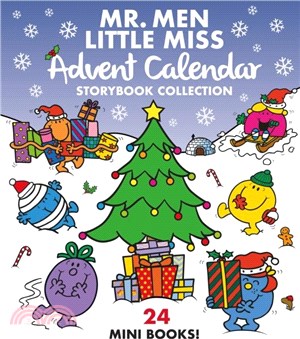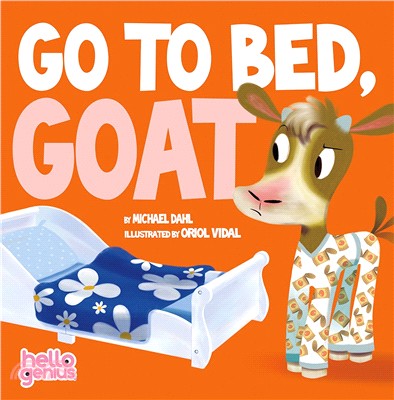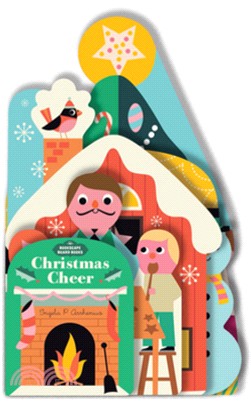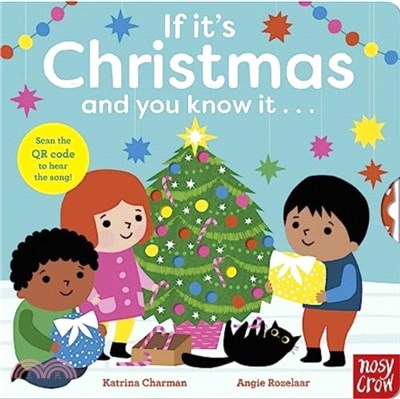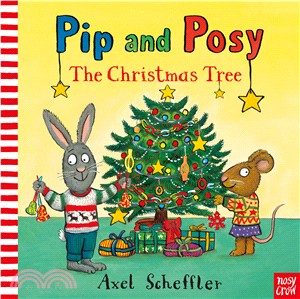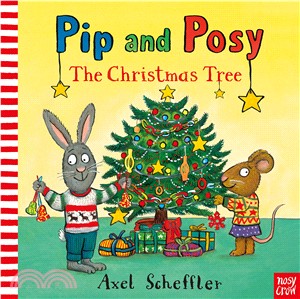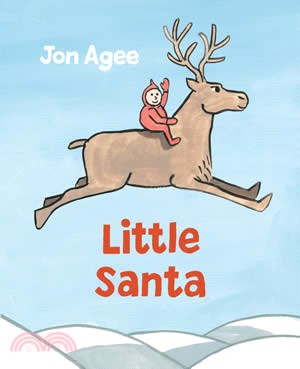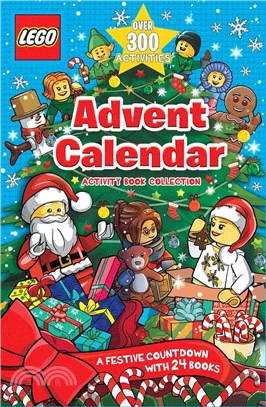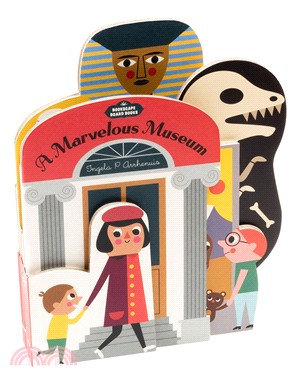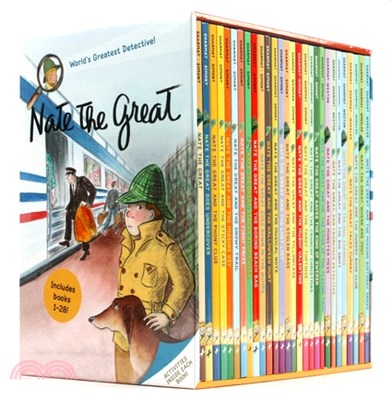定價
:NT$ 150 元優惠價
:90 折 135 元
再版中無法訂購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先秦法家思想,漢後殊多誤解。本書採政治觀點,用歷史眼光,以比較論證之方法,旁參西洋理念及近代知識,而為之辨正發抒,並就法家諸子之原貌,探求真蘊,而歸納於哲學範疇。始自先秦,終於清季,闡其宗派,論及餘波, 凡其理致之能系統化者,均舉而詳之。允為法家哲學唯一完整性之專著。
作者簡介
姚蒸民
四川人,民國十二年生。中央大學法學士,高等考試及格,政治大學高等科畢業。曾任監察院調查專員、人事室主任、參事,逢甲工商學院兼任副教授,中國文化學院、中央、淡江及東吳大學兼任教授。現任考試院考試委員,中央大學及東吳大學兼任教授。
序
修訂版序
拙著法家哲學初版,印行於民國七十三年,兩年後,已無餘書,知其尚可供世人參考也,爰略加修訂,由東大圖書公司印行。修訂版之異於初版者,為增添附註及充實部分內容,意在求法家哲學之通詮,更臻完整。惟是拙著於法家諸子之學,多揚棄昔人見解;於法家哲學之觀點,亦非悉與近人同;此則宜有以說之焉。徵之史籍,先秦各家思想,自其淵源與發展言之,應屬於人生哲學之範疇,而落實於政治層面,即或旁涉形而上之天道鬼神,又或高談倫理、經濟、教育,要亦為解決當日政治問題而提出者。吾人若舍修齊治平之根本思想,以論儒家之學,已失其重心,矧法家之學原以政治需求為急務,而未遑言及其他者乎?此拙著之所以不持今世之文化觀,而出以純政治眼光者,一也。其次,先秦諸子之學,俱各有所承受,各有所創新,亦各以其學影響於當日之社會。今之所謂家數,乃漢人取同舍異之所析歸。故究一家之言與究其中一人之學有異,而一人之學在當日及後世之評價亦有所異。孔孟荀如是,老莊楊墨亦如是。法家諸子之學無不關乎時代之推移,其學說內涵之認定與評價,尤不可不特重其人之時代社會背景。此拙著之所以出以歷史眼光,而不牽拘於今世之法治觀者,二也。抑又思之:儒家之學,自兩漢經師採陰陽、道、法家言,以釋春秋、說易、註三禮而後,已有不醇。惟後世推衍新義,使孔學不為時空所限,今更成為中華文化之根基。法家之學,則漢後無人在理論上有所創新,而又迭經儒生之唯君是尊者所移轉誤用,漸至真蘊泯失,為世詬病,一迄於今。戛戛乎其辨正之難,與夫通詮之不易。此又拙著之所以必究其初貌而又論及其在後世之餘波者,三也。凡此三者,容與他家哲學之研究取向有異。深慚學有未逮,不敢率就其所見者而罄言之。茲雖修訂再版,殆仍僅發凡而已。他日倘能益使之臻於完善,則差堪自慰矣。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 姚蒸民序於臺北
目次
修訂版序
初版自序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中國哲學之本質
第二節 儒道墨法四家哲學之異同
第三節 法家哲學研究法
第二章 法家思想之起源及其哲學之建立
第一節 時代背景
第二節 發展經過
第三章 管子哲學
第一節 序說
第二節 國家道德觀
第三節 尊君順民說
第四節 法治主義
第四章 商子哲學
第一節 序說
第二節 歷史進化論
第三節 法治論
第四節 國家主義
第五章 申子哲學
第一節 序說
第二節 君主論
第三節 術治論
第六章 慎子哲學
第一節 序說
第二節 自然主義
第三節 國家論
第四節 勢治論
第五節 法論
第七章 韓子哲學
第一節 序說
第二節 變古之歷史觀
第三節 務力之社會觀
第四節 自為之人性觀
第五節 勢論
第六節 法論
第七節 術論
第八節 知識論
第九節 餘論
第八章 法家哲學之衰落
第一節 衰落原因
第二節 漢後法家
第三節 法家思想之餘波
主要參考書目
初版自序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中國哲學之本質
第二節 儒道墨法四家哲學之異同
第三節 法家哲學研究法
第二章 法家思想之起源及其哲學之建立
第一節 時代背景
第二節 發展經過
第三章 管子哲學
第一節 序說
第二節 國家道德觀
第三節 尊君順民說
第四節 法治主義
第四章 商子哲學
第一節 序說
第二節 歷史進化論
第三節 法治論
第四節 國家主義
第五章 申子哲學
第一節 序說
第二節 君主論
第三節 術治論
第六章 慎子哲學
第一節 序說
第二節 自然主義
第三節 國家論
第四節 勢治論
第五節 法論
第七章 韓子哲學
第一節 序說
第二節 變古之歷史觀
第三節 務力之社會觀
第四節 自為之人性觀
第五節 勢論
第六節 法論
第七節 術論
第八節 知識論
第九節 餘論
第八章 法家哲學之衰落
第一節 衰落原因
第二節 漢後法家
第三節 法家思想之餘波
主要參考書目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