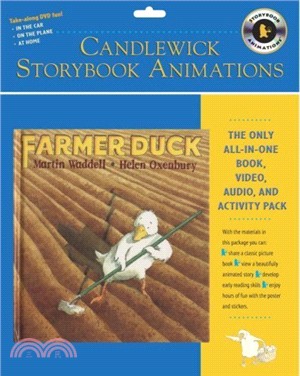商品簡介
死亡,或許是另一個生命的 待續…….
二○○九年十月的一個晚上,于娟教書下課後,騎著腳踏車去超市買牛奶,路上為了避讓來車,她從腳踏車上摔下,瞬間她感到一股抽筋的疼痛從腰間傳來,心想:「不會這樣就扭傷腰了吧?」
第二天,她竟然因腰痛而疼得起不了床,稍微一動,豆大的汗就往下掉。那時候的于娟萬萬沒有想到,這劇烈的腰痛竟是癌細胞已經轉移的徵兆。為了工作,她忍著腰痛,每天晚上還是在辦公室熬到十點鐘,但開始跑醫院看病,接二連三被誤診為腰椎受傷。
直到二○○九年十二月底,痛到全身一動也不能動的于娟被救護車送進醫院急診室;幾番周折,在二○一○年元旦,她被確診罹患乳腺癌四期,也就是癌症末期。當時,距離她留學回國開始教書只有三個月,她的兒子土豆只有十四個月大,她的父母已六十多歲,而她是家中獨生女……在她人生欲展翅高飛之際,突如其來的病痛完全打亂了她的人生步驟,也在她的生命槌下了重重的一擊。
但于娟沒有放棄,她忍住所有化療的痛,拚命想活下去,為孩子、為父母、為丈夫活下去。就像她丈夫光頭寫道:「她真的很堅強,確診得知乳腺癌時,她居然高興地笑,因為乳腺癌相對其他癌症來說更好醫治一些。我也幾乎沒有落淚,只有一次,回家看到她和寶寶的合影,淚如雨下。」
本書收錄于娟確診罹患乳腺癌後寫下的病中日記,她在日記中反思生活細節,並發出「買車買房、買不來健康」的感歎,這時她退回到一個普通的女兒、妻子、母親,發出對生命最單純的感悟。在這些文字裡,很多讀者看到的不是于娟的故事,而是自己;在大陸引起網友關注和眾多媒體熱烈報導,大陸部落客的瀏覽人次高達800萬次。
本書重點
*當你預知了生命只剩下短暫的時間,你將如何過完生活,對人生省思的真人真事,很能引起共鳴與反思。
*大陸首印量首印 40,000 冊,不到一個月迅速加印六次,截至2012年初大陸實際銷售量已超過20萬冊。
作者簡介
于娟(1979年4月~2011年4月)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的講師
*上海交通大學學士(2000)
*挪威奧斯陸大學經濟學碩士 (2007)
*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 (2008)
她是一個兩歲半孩子的母親,一個四十歲男人的妻子,兩個六十多歲老者的女兒,數個失學兒童的資助者,很多人的朋友。
她是復旦大學的講師,研究環境政策和能源政策,積極籌組「能源林」,投身環保公益。
她從容面對癌症,不怨天尤人;她帶走家人的思念和不捨,留給世人堅強的力量。
名人/編輯推薦
大陸媒體推介
記錄黑暗是殘酷的,尤其在感到屬於自己的那盞生命油燈一點點黯淡之時。但于娟決定完完整整寫下這段生命中最黑暗最苦痛的日子,也是她認為過去32年最有意義的日子。——《三聯生活週刊》
復旦大學「抗癌教師」于娟在癌症抗爭的一年半時間,留下數篇抗癌日記和「復旦教師抗癌記錄」微博,這些在生死交叉點上對生命的反思,對年輕人莫透支青春的警誡感動了無數人。——《新民晚報》
名人感動推薦
放下生死與名利,留下的是「平靜」、「率直」、「樸實」與「堅強」,這正是本書作者感人與令人敬佩之處。也提醒世人更要珍惜寶貴生命,更要在有生之年做些有意義的事,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好書。—張金堅博士(台中澄清醫院中港院區院長/乳癌防治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版序
願生命之樹長青
趙斌元(本書作者于娟的丈夫)
2011年4月19日,這個日子越走越遠。
它的到來,如同碎片。它的遠去,如同碎片。所有的記憶,都逐漸成為碎片,不真實,但深刻。
唯有這本書,就像是她,依然在望著我,期待著我,用那一汪我永遠難忘的深情和不捨。
我不敢去細讀這本書。雖然忙碌的生活繼續,但難抑自己的痛楚和傷悲,常會洶湧而至。書裡她熟悉的氣息,一定會淹沒我的自信與快樂。
我更願意在夢裡和她重逢。
生離、死別,實在不可同日而語。生命,實在應該珍惜!
我相信這本書的力量。它能夠讓人更珍惜生命,珍惜時間;會讓人去思考應該怎樣度過這一生;如何去看待逆境和順境,如何與人相處。于娟最大的夢想就是當作家。我真希望有很多人認真去讀這本書,並有所收穫。那樣的話,她會很快樂。
對於這本書在台灣的發行,媽媽說:「只要于娟高興,我都願意。」媽媽現在把能源林的事業當做自己的女兒,也把這本書當做自己的女兒。
我想說,這本書承載了很多人對于娟的愛。我只能把感謝放在心裡,在夢裡向于娟訴說。
願生命之樹長青!
推薦序01
不畏病魔,看見真愛
張金堅博士(台中澄清醫院中港院區院長/乳癌防治基金會董事長)
本人從事癌症醫療超過三十寒暑,接觸無數的乳癌患者,有的諱疾忌醫,延誤治療契機;有的勇於面對,積極治療,重獲新生。本書作者于娟女士,罹癌之時,年僅三十一歲,花樣年華,却得了全身骨骼多處轉移之晚期乳癌,她是一位曾經出國(挪威)深造,並擁有經濟學博士之優秀老師,本來可以發揮所學,教育學子、貢獻社會,並可與夫婿、兒子共創和樂美滿之家庭,無奈事與願違,命運之神却百般折磨,于女士乳癌確診之際,身邊還有亟待照顧年僅一歲多的兒子土豆及需侍奉的雙親。
在一年四個月之抗癌過程中,身心所受之煎熬,倍極辛苦,但她以無比之毅力,寫下病中日記,道出生活的感觸與生命的領悟。她深愛著她的兒子、丈夫與雙親,珍惜生命的每一時刻,從不向病魔低頭,絕不輕言放棄,與醫療團隊高度配合,接受各式各樣難以忍受的治療,可稱是醫師眼裡的模範病人。即使病情惡化,疼痛加劇,她仍試圖以最勇敢的方式撐過,真是生命中之「勇者」。
其實她在日記的字裡行間,也暗藏內心的不安與惶恐,但仍能展現出她的幽默與自信,雖然她自認是平凡的女兒、妻子與母親,却擁有堅忍的意志力與強韌的生命力,尤其在最後的五個月,她很清楚自己的日子不多,早已放下生死與名利,留下的是「平靜」、「率直」、「樸實」與「堅強」,這正是本書作者感人與令人敬佩之處。她也提醒世人要珍惜寶貴生命,更要在有生之年做些有意義的事,于女士留下的文字,值得我們咀嚼與細讀,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好書。
推薦序02
陽光依舊燦爛
周國平 (中國著名作家和學者)
我是在讀這部遺稿時才知道于娟的,離她去世不過數日。這個風華正茂的少婦,是擁有留洋經歷和博士學位的復旦大學青年教師,在與末期癌症抗爭一年四個月之後,終於撒手人寰。也許這樣的悲劇亦屬尋常,不尋常的是,在病痛和治療的摧殘下,她仍能寫下如此靈動的文字,面對步步緊逼的死神依然談笑自若。我感到的不只是欽佩和感動,更是喜歡,這個小女子實在可愛,在她已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樣子的軀體裡,仍蘊藏著這麼活潑的生命力。
于娟是可愛的,她的可愛由來已久,我舉一個小例子。那是她在復旦讀博士班的時候,一晚在夜店,因為有人打群架,她被誤抓進了警察局。下面是她回憶的當時情景——
「警察開始問話寫口供,問到我是做什麼的;我說復旦學生。他問幾年級,我說博一;然後警察生氣了,說我故意耍酒瘋不配合。那天我身上穿著一件亮片背心搭配一條極短的熱褲,一雙亮銀高跟鞋,除了沒有化妝,和小辣妹無異。警察鄙視的眼神點燃了我體內殘存的酒精,我忽地一聲站起來說:「復旦的怎麼了?讀博士怎麼了?上了復旦、讀了博士,就非得穿得人模人樣,也不能上夜店嗎?」
她的性格真是陽光。
多年後,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下,這陽光依然燦爛。我再舉一個小例子,在確診乳腺癌之後,一個男性親戚只知她得了重病,用手機傳簡訊給她:「如果需要骨髓、腎臟器官什麼的,我來捐!」丈夫念給她聽,她哈哈大笑說:「告訴他,我需要他捐乳房。」
當然,在這生死關口,于娟不可能只是傻樂,她對人生有深刻的反思。和今日別的青年教師一樣,她也面臨著雙重壓力,一是體制內的人事升遷,二是現實生活中的買房買車,並且似乎不得不為此奮鬥。現在她認識到,「我曾經的野心是兩、三年內晉升到副教授,於是拚命寫文章、找議題寫論文,雖然對當了副教授之後要做什麼,我非常茫然。為了一個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生目標的事情拚了命撲上去,不能不說是一個傻子做的傻事。生病之後,我才知道,人應該把快樂建立在可持續的長久人生目標上,而不應該只是去看短暫的名利權勢。名利權勢,沒有一樣是不辛苦的,卻沒有一樣可以帶走。」
「生不如死、九死一生、死裡逃生、死死生生之後,我突然覺得一身輕鬆。不想去控制大局小局,不想去多管閒事,我不再有對手,不再有敵人,我也不再關心誰比誰強,課題也好、任務也罷,暫且放著。世間的一切,隔岸看花,雲淡風清。」
「在生死臨界點的時候,你會發現,任何的加班,給自己太多的壓力,買房買車的需求,這些都是浮雲,如果有時間,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買車的錢給父母親買雙鞋子,不要拚命去換什麼大房子,和相愛的人在一起,蝸居也溫暖。」
我相信,如果于娟能活下來,她的人生一定會和以前不同,更加超脫,也更加真實。她的這些體悟,現在只成了留給同代人的一份遺產。
一次化療結束後,于娟回到家裡,當時剛一歲半的兒子土豆趴在她的膝蓋上,童言童語的唱:「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個寶」。她流著淚想:「也許就差那麼一點點,我的孩子變成了草。」她還寫道:「哪怕就讓我這般痛,痛得不能動,每日蓬頭垢面的趴在十字路口上,任千人唾駡,萬人踐踏,只要能看著我爸媽牽著土豆的手去幼稚園上學,我也是願意的。」還有那個也是青年學者的丈夫光頭,天天為全身骨頭壞死、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擦屁股,說最多的一句話是,「我求老天讓妳活著,讓我這樣擦五十年屁股。」多麼可愛的一家子!于娟多麼愛她的孩子和丈夫,多麼愛生命,她不想死,她絕不放棄,可是,她還是走了!
我不想從文學角度來評論這本書稿,雖然讀者從我引用的片斷可以清楚地看到,于娟的文字多麼率真、質樸、生動。文學已經不重要,我在這裡引用這些片斷,只因為它們比我寫的任何文字更能勾勒出于娟的優美個性和聰慧悟性。上蒼怎麼忍心把這麼可怕的災難降於這個可愛的女子、這個可愛的家庭啊!
嗚呼,蒼天不仁!
二○一一年五月七日
推薦序03
老于的森林
鄭培源(于娟的摯友)
今天是老于的頭七。七天前,晚上九點多,我接到于媽媽的電話後趕到中山醫院三號樓二十七病區,見了老于最後一面。
那是一個絕望的夜晚,空氣中瀰漫著死別的氣息,壓得人喘不過氣來。我已經預先感覺到那一晚將要發生的事,在書架上匆匆拿了一本《臨終備覽》。計程車上,我找出相關的章節,在書頁上折一角做記號,車子劇烈的抖動,我的手指居然穩健。老于,我不忍送妳、不願送妳,但機緣造化,上天安排了是我,我要平平靜靜、體體面面的送妳走。
過去的三天,我每天都來看她,也看著她生命之火一點一點的熄滅:她曾經健美的身軀蜷縮的像嬰兒一樣,側臥在病床的左上角, 以至於我一眼看過去還以為床上是空的;她呼吸急促、心跳極快,幾乎吃不下任何東西,說話要拚盡力氣;她的軀殼已經脫韁,衝刺在生命的終點線上,越跑越快,越跑越快。這一晚的九點鐘,她已經失去了意識,進入了彌留階段。
于媽媽就那樣眼睛直直的看著女兒。昨天她一度崩潰,最後的時間,她以知識女性特有的成熟和堅定讓自己平靜下來,商量女兒的後事。光頭始終沒有放棄,他堅定的認為還有希望,還能熬過今夜。但我更相信于媽媽的判斷,母親愛自己的骨血甚於愛自己,對自己骨血的狀態有著「母女連心」式的判斷。
作為家鄉人和于娟最信賴的朋友,我參與了她身後事的討論安排。于媽媽說出了于娟最後的遺願:關於法事和安葬,老人和孩子的安排。她希望葬回山東的能源林,希望父母在上海陪土豆長大,希望能啟程去一個佛的國度。
我離開醫院的時間是十九日淩晨一點多,光頭陪我走到電梯前。我看著這個令我極度佩服和崇敬的大哥,說不出話來。
一夜翻來覆去,半夢半醒。
早晨五點,光頭給我電話,那一刻我心裡還存了一絲絲幻想,但光頭聲音嘶啞著說:「于娟走了……」
老于走了已有七天,敲出上面的文字,眼前依然一片朦朧。
我曾經很認真的跟老于說,「很羡慕妳病後大澈大悟的狀態,情願和妳換一換,經歷妳所經歷、獲得妳所獲得的。」老于用那雙直白大眼睛瞪著我說:「沒有人願意真的和我換,我也不忍心讓你跟我換,太疼了,太累了,太苦了!」
媒體稱老于是抗癌勇士、部落客達人、生命體悟者、環保理想者、才女、高級知識分子、海外歸國學人、博士……這些似乎都對,卻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老于是一個好人,透透徹徹、乾乾淨淨、明明白白的一個好人。這個好人情願自己把苦痛扛了,換成文字來讓大家開心;識透了人情卻沒驚破膽,保留著孩子似的童真和大膽;拚了命的去寫微博,插著氧氣管還要寫微博,就只為了多留些警醒世人的文字;直到她走的時候——那麼痛苦,那麼不捨的離開這個世界——她放不下的還是能源林這個幾乎耗盡她最後一點心力的事。
老于,妳一個癌症晚期病人,為什麼要承受那麼多?
在最後五個月,老于放下了生死,放下了名利權情,赤裸裸的反思和寫作,這也正是她生命最後階段留下的文字如此感人的原因;所有的浮躁沉澱了,所有的偽裝剝離了,所有的喧囂停止了,所有的執著放下了,只剩一個普通的女子、普通的女兒、妻子、母親對生命最單純的感悟。最心痛的地方在於:這個普通女子剝去了凡常所欲的一切,最後所欲的還是為他人謀福祉。
老于,妳走了,好人又少了一個,讓我們這些壞人和不好不壞的人情何以堪?
我很怕媒體把老于解讀成一個關於都市健康的新聞速食話題人物,得出譬如「晚睡導致癌症,請別學于娟、早睡早起」的速食結論。在我的心裡,老于和她的文字無關病症和養生,只關乎理想和靈魂。她是我們這一代人中理想主義者的縮影,胸懷大志、學貫中西,抱著一腔的熱血想給這個世界多留下些什麼。
儘管出師未捷身先死,但是老于留下的文字,卻足以穿越時空,直指人心。
老于,走好。妳的心願,我們來完成。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夜
目次
推薦文<二> 陽光依舊燦爛 周國平
推薦文<三> 老于的森林 鄭培源
台灣版序 願生命之樹長青 趙斌元
Part 1:無畏施
我的堅強與柔軟/義氣和義乳/走鋼絲的孩子/生命故事/孔雀爺爺
/土豆的耶誕節/黑色幽默話自殺/我可愛的朋友們/無畏施/病中病
/誰是我的下一任/病中之最散記/為什麼是我得癌症/落髮/由來笑我看不穿
Part 2:病中記
我的二○一○(一)/我的二○一○(二)/我的二○一○(三)
/我的二○一○(四)/我的二○一○(五)/我的二○一○(六)
/我的二○一○(七)/我的二○一○(八)/我的二○一○(九)
/我的二○一○(十)
Part 3:寫給我的寶貝
不期之孕/寶貝/幸福生活/分離
Part 4:故鄉
一個人的團圓/生死相隔的斷想/清明的風不止/無處安放的楓鬥
/碎落在身後的時光/賣報歌/一簟食/子不語/十年/女人三十
<後記>路有千萬條,但只能走一條 趙斌元
<附錄>土豆成長日記
書摘/試閱
我的堅強與柔軟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特別堅強的人。
二○○九年的最後一個星期,我被救護車抬進上海瑞金醫院,放置在急診室。
病理室主任看到我那渾身黑漆漆的全息CT後,問了一句話,「病人現在用什麼止痛?」
我的老公,那個可愛的光頭男答:「現在還沒有用任何的止痛藥物。」
那個四十多歲的主任,倒吸一口涼氣,一字一句地說:「正常情況下,一般人到她這個地步,差不多痛都能痛死的。」
他們進行這段對話的時候,我只是屏著氣,咬著牙,拚命忍著,沒有死,也沒有哭。
在急診室待了三天兩夜。醫生不能確診是骨癌、肺癌、白血病、還是其他病症。
急診室應該就是地獄的隔壁,一扇隨時開啟的自動門夾雜著寒冬的冷風,隨時有病危的人被送進來。
我身邊的鄰居,雖然都躺在病床上,但似乎都比我的精神好很多,至少不是痛得身體絲毫不能動。然而,就是這些鄰居,夜裡兩點多大張旗鼓地被送進來,躺在我身邊不到兩尺的地方,不等我有精神打個招呼,五點多就會被某些家屬的哭聲吵醒,看到一襲白單蓋住一個人的輪廓,我知道那個人匆匆走了。
如此三天兩夜,心驚膽戰。我沒有哭,表現得異常理智,我只是斷斷續續用身體裡僅有的一點力氣,錄了數封遺書,安慰媽媽看穿世事生死。
後來,一天兩次的骨髓穿刺。其實骨髓穿刺對我來說,並算不上疼痛,光頭在旁邊陪我,看到後來,他轉身面壁不忍再看;媽媽也已經瀕臨精神崩潰邊緣。
我的痛苦在於,當時破骨細胞已經在軀殼裡密佈,身體容不得一點觸碰,碰了,真的就會暈死過去。那種痛不是因為骨髓穿刺,而是癌細胞分分秒秒都在啃噬骨頭。
我還是沒有哭,不是因為堅強,是因為痛得忘了哭,那個時候,只能用盡全力硬撐著。如果稍微分神,我就會痛得暈厥。我不想家人看到我的痛苦。
當二○一○年元旦,我被確診為乳腺癌四期,也就是最晚期的時候,我長舒了一口氣,沒有哭,反而發自內心的哈哈大笑,因為這個結果是我預想的所有結果中最好的一個。既然已然是癌症,那麼乳腺癌總是要強一點。至於晚期,我早已明瞭,全身一動不能動,不是擴散轉移,又能是什麼?
發現太晚,癌細胞幾乎擴散到了軀幹所有重要的骨骼。我不能手術,只能化療,地獄一樣的化療。
初期反應很大,嘔吐一直不停。當時我全身不能動,即便嘔吐,也只能側頭,最多四十五度,枕邊、棉被、衣服、身上,全是嘔吐物,有時候嘔吐物會從鼻腔裡噴湧而出,一天幾十次。
其實,吐就吐了,最可怕的是,吐會帶動胸腔震動,而我的脊椎和肋骨稍一震動,便有可能痛得暈厥過去;別人形容痛說刺骨的痛,我想我真的明白了這句中文的精髓。一日幾十次的嘔吐,我痛到暈厥幾十次。
別人化療時那種五臟六腑的難受,我也有,只是,已經不值得一提。
那個時候,我還是沒有哭。因為我想,堅持下去,我就能活下去。
六次化療結束之後,我回家了!當時兒子土豆剛十九個月,他開心地圍著我轉來轉去。
奶奶說:「土豆,唱歌給媽媽聽吧!」
土豆趴在我膝蓋上,張嘴居然童言童語的唱:「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個寶……」
歌未唱完,我淚先流。
也許,就差那麼一點點、一點點。我的孩子,就變成了草。
于丹說:「一個人的意志可以越來越堅強,但心靈應該越來越柔軟。」
無意之中,我做到了這點。這才發現,這兩者是共通的。
我的二○一○ (三):不疼的小日子
救護人員把我從擔架上移放到急救床時,放得位置有點偏差,使我的腳後跟剛好擺在急救床床腳的鋼邊上。沒有人想到「我不能動」是真的「一動不能動」,也就是說,我壓根沒有能力把腳跟從那個冰涼的鋼邊上移開。我告訴媽媽,我的腳跟很沉很冷,但是她著急卻不敢動手挪動我,急得團團轉,便把羽絨衣脫下來,包著我的腳墊著,直到老爸幫我買來一雙巨大的棉拖鞋。
很久之後,當我能站立了,我才看見那雙鞋子的左右腳分別繡著「不離不棄」的字樣。
置身於一堆生命虛弱的病殘人群裡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病苦纏身已是事實,也就認了;劇痛難耐,不能耐也得耐,也就罷了;偶有寒風刺骨,也就忍了;但怕就怕在整個空間有種莫名的氣氛壓得人喘不過氣來,低沉陰暗,加上身邊病友的哀呼慘叫不絕於耳,似乎加重了原有的病情苦痛。
夜裡三、四點的時候,一個新病人躺著被抬進來,但他精氣神很好,嘟嘟囔囔嗔怪朋友們太小題大作。三十多歲在早餐店打工的河南漢子,一早開工莫名其妙尿了點血,和麵時忽然暈倒了,同事們就七手八腳把他送上了救護車上。他醒來怕花錢,試圖出院,開始和護士討價還價。我和媽媽疲憊不堪的被吵醒,哪知道六點不到,他那在浦東做工的老婆趕到醫院,到他床邊時,他竟已經叫不應了,不是睡著,是再也醒不來了!
說實話,當初的我面對死亡的壓力承受度還是個新生兒,夜裡,身邊的病人接二連三死去,加上突然響起來的慟哭讓我很茫然,我不知道我的病比他們重,還是比他們輕?
或者說,我不知道我距離死亡有多遠。
我不是怕死,我是不知道該怎麼辦?雖然我可以明顯感覺到老師、朋友都開始從四面八方聚攏來,形成一張以光頭馬首是瞻的無形網,來試圖盡全力救助正從懸崖往死亡谷底墜落的我。有時候,電話那邊只有一句擲地有聲的話,「妳說!妳要找誰?我幫妳聯繫?」
可是,光頭和我卻全無方向,我們不知道要找誰才能救命。
躺在那樣的病床上,等著,乾等著病痛蠶食肉體與意志,是非常可怕的。走投無路也許就是這個意思。
急得不知所措的光頭貿然跑去找病理科的金曉龍主任,幾乎踢了人家的辦公室門,火燒屁股的闖進去問哪個是金曉龍醫生。
金醫生一頭霧水地被按著頭看了病歷後,沉吟片刻問:「病人現在用什麼止痛?」
光頭說:「沒有止痛。」
金醫生倒吸一口涼氣,定定看著光頭,很慢很慢的說:「一般人,這種情況下,痛,都能痛死。」
光頭對我的崇拜之情刹那間猶如黃河之水滔滔不絕,因為,我基本上,除了移動震動的外界因素,從來不叫痛。
金醫生可能悲憫我這個年輕媽媽,幾句話講解了他的想法,基於我非常特殊的病情,拿起電話,救火一樣,快速開始聯繫他認識的!最好的醫生替我做骨髓穿刺、CT引導病灶穿刺。
骨髓穿刺時,至少有五分鐘不能亂動,而我時不時會抽搐。這點很致命,也因為這個,我在六院付了費,被推進手術室,又被推了出來;醫生不敢做,怕操作期間我的無名抽搐會導致取骨髓時發生意外,一旦如此,就意味著我要癱瘓一生。
是否要骨髓穿刺,對我來說這個決定非常艱難。我考慮了很漫長的一分鐘,最終選擇了骨髓穿刺。不知道為什麼,冥冥中,我相信我肯定可以控制自己,哪怕這些反應就像膝跳反射一樣不會被人的主觀控制。
因為不能移動,我只是被從簡易病房裡推進咫尺之遙的ICU,靠著那扇磨砂玻璃門開始骨髓穿刺。一個非常可靠且溫柔的男醫生耐心等了我四十分鐘:這四十分鐘裡,我只是做了一個正常人不消一秒鐘就能做到的動作:側身,調整體位,找一個我能做到的姿勢,方便醫生做手術。我能做到的姿勢可能距離醫生希望的很遠,那位醫生是跪在地上幫我取骨髓的。
具體如何操作,我雖經歷但依然不明就裡,我只抱著病床欄杆保持側身,然後聽醫生「嘣嘣嘣」地似乎拿一隻錘子把錐子一樣的東西敲進我的骨頭,還開玩笑說:「妳的骨頭好硬啊!」
光頭扶著我的腿防止我抽搐,所以目睹全過程。我自始至終沒任何動作、聲響、表情,手術完成後,還開玩笑謝謝那位下跪的醫生,因而獲得了他由衷的佩服和崇拜。
骨髓穿刺,不如我之前想像的可怕。可怕的是CT引導病灶穿刺。依然是骨髓穿刺,但是因為上了CT,痛入我生命的最深處,而使我幾近喪命。原諒我,我至今不能面對這段回憶。
做完CT下引導穿刺的那個夜裡,我有些撐不住了,無助而無邊的疼痛裡,我似乎看到屬於我的那盞生命的油燈,一點點黯淡,一點點泯滅。
夜裡兩、三點時,身邊有個不知名的病友停止了他的生命。驚天動地的家屬悲慟哭聲中,我對閉目養神但一直睡不著的媽媽說:「如果我去了,把我在上海火化,然後把我的骨灰帶回山東,在那片我曾經試圖搞能源林的曲阜山坡地,找個地方埋了,至少那裡有蟲鳴鳥叫、清溪綠樹,不要讓我留在上海這水泥森林裡做孤魂野鬼。 」
媽媽無言點頭,我囑咐她,土豆每年生日的時候,帶他去看看我,順便也去過過村野田園的生活。我讓他們一定要照顧好自己,只有照顧好自己才能在關鍵時刻替我照顧土豆。說這些話的時候我有些控制不住,我問自己,究竟放不下的是土豆,還是自己的父母?
我知道土豆會有很多人愛,光頭會照顧好他,而媽媽和爸爸是我最不放心的,但是不懂為什麼,我卻最捨不得那個剛剛學會叫媽媽的胖滾滾娃娃。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紅樓夢》裡的「好了歌」,想到那句「世上都道父母好,只有兒孫忘不了」。
我甚至想,哪怕就讓我這麼痛,痛得不能動,每天像個癱瘓的人,汙衣垢面趴在十字路口上,任千人唾駡,萬人踐踏,只要能看著爸媽牽著土豆的手蹦蹦跳跳去幼稚園上學,我也是願意的。
光頭頂著明晃晃的腦袋在天亮的時候帶來一個好消息,他費盡心力終於找到了J醫生,不等我的檢查結果出來,當機立斷直接搶在元旦休息前把我推去了二十樓。因為那天是十二月三十一號。沒有人知道,如果我在急診室不用任何藥物等到元旦假期結束會是什麼結果。
二十樓是瑞安醫院, 進了瑞安的第一件事是猛嗑止痛藥,先幾粒,掐著錶觀察反應,不管用,然後一把把的吃,效果也不特別明顯。後來決定用強痛定止痛針,結果悲劇的是,我當時太痛了,以至於神經性抽搐,打針會有自我保護般的反應,臀部肌肉太過緊張,針很難扎進去。好不容易扎進去了,護士吃奶的力氣都用光了,就是推不動針管。再後來,用了止痛貼,四張。我瞟見護士手裡那個包裝上寫著:四十歲以上非癌症患者禁用。後來,等我可以下床活動,整理東西時,看到說明書,才知道這個東西貼多了或者貼的位置不對,會影響心肺功能,有生命危險。
無論如何,我可以止痛了!我躺在那張美國進口的電腦升降病床上,聽著電腦裡的「春江花月夜」,這是光頭找來的抗癌音樂。父母陪在左右,我閉著眼睛非常享受這沒有疼痛的時光,信口說:「如果不疼,這小日子過得還是很爽的。」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老媽先是噗哧一笑,然後淚流了下來。後來,這句話成了我生病期間的著名語錄。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