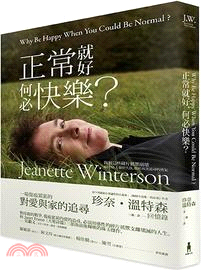正常就好,何必快樂?
商品資訊
系列名:木馬人文
ISBN13:9789865829322
替代書名: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出版社:木馬文化
作者:珍奈.溫特森
譯者:三珊
出版日:2013/08/08
裝訂/頁數:平裝/320頁
規格:21cm*15cm*2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一場傷痕累累的對愛與家的追尋
當今英國最具爭議性的小說家
《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作者 珍奈‧溫特森 回憶錄
關於傷口,關於失落,關於得不到的愛,以及再次追尋的勇氣
一個小說家竟然是在只擁有六本書的家庭長大?英國作家珍奈‧溫特森追溯她的成長:她與母親的關係緊張卻疏離,性別認同的課題使她更格格不入。幸好上了大學,文學為她打開全新世界。成人也成名之後,她得知自己是被領養的孩子,失落感排山倒海而來。她尋找生母下落,這又是一段面對傷口的黑暗過程……
你如何去愛另外一個人?你如何相信另外一個人也愛你?
我一點也不懂。我以為愛就是失去。
為何愛得要失去了才能測量?
本書是一個追尋身世的故事。作者是知名作家,而成名作品就是她半自傳性質的小說,但一直到她有勇氣穿過種種冷漠、忽視、孤單的記憶,仔細辨認諸多感覺,熬過內心惡獸的折磨,她才終於能藉由書寫來面對事實,承認自己是一個被領養的孩子,寫下這一個關於愛與失落、生命與勇氣的故事。
書的前半,作者追溯她在英國工業城市長大的童年。她在一個只有六本書的家庭長大,但他熱愛文字。她生活在一個與文學毫無關係的環境裡,渴望父母的愛卻無法得到回應,還得面對自己明顯喜愛女孩的傾向。她是個在各方面都格格不入的孩子。
這孩子被鎖在家門外不准入內。她坐在門前台階上仰望夜空,想像此刻如果身在他方,星星看來是否相同。
她母親對於生活沒有熱情,心裡同時住著暴君和傳教士,在家中櫃子藏起一把左輪手槍,隨時等候聖經啟示錄裡諭示的末日到來。
女兒與母親,兩人同樣寂寞卻毫無交集。她十六歲某一天,與母親起爭執。母親質問:「若你可以正常,你為什麼要快樂?」這是關鍵句。
隔天,她離家出走了。三年後她進入牛津大學,從此循著文學這一道遙遠卻清晰的光亮匍匐前進。
書的後半,描述這位五十歲小說家設法追蹤生母的下落。她回到她以為自己被遺棄的那一天,從最初開始觀看自己對於失落的恐懼和對於愛的渴望。這個追蹤的過程,對外,她必須與社工人員和法律單位打交道;往內,她要安撫自己內心深處那個被遺棄而沒有名字的嬰兒。嚴重的挫折感與失落感交相打擊,竟然使她進入瘋狂狀態:生活脫序,精神失常,與人群隔離,心情破碎。
歷經一段與內心黑暗進行險惡角力的時光,她逐漸領悟到:她以為自己一直得不到愛,其實她也一直不懂得如何愛人。然後可以大聲說:對自己的愛就是對生命的愛,值得你用盡力氣像鮭魚一樣逆游而上;而傷口,傷口是你永遠的身分,如果你試著清理它,也許它會先來復仇,但最後,傷口就是帶領你回家的印記。
作者簡介
珍奈‧溫特森 (Jeanette Winterson, 1959- )
英國小說家,也寫童書和劇本,目前也未報紙撰寫專欄。現住在英國葛羅瑟郡(Gloucestershire)一棟小木屋裡。
出生於英國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1960年1 月,被溫特森夫婦收養,在小城阿克寧頓( Accrington)長大。
養父是工廠工人,養母為家庭主婦。家裡只有六本書,包括一本聖經和一本《亞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讀到《亞瑟王之死》,開啟了她閱讀和寫作的熱情。
養父母希望她長大後從事傳教工作。可是她後來進入女子中學,十六歲離家出走,一邊打工一邊讀書並申請大學。然後愛上一個女孩。遇到一位老師收留。一年後,取得牛津大學入學許可。進入牛津後,從姓氏字母A的作家開始閱讀,立志讀遍英國文學,直讀到Z字頭作家為止。
大學畢業,進劇場打工。23歲撰寫第一本小說,《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隔年出版。
也創作漫畫,並且為潘朵拉出版社工作。其後轉為全職作家,陸續出版多本小說,作品包括:
Sexing The Cherry、Written On The Body、Art and Lies、Art Objects (散文) 、Gut Symmetries、The World And Other Places、The Powerbook、The King of Capri、Lighthousekeepig、The Stone Gods、Weight。
親自改編《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電視劇本。小說《愛情筆電》亦曾改編成舞台劇,在倫敦和巴黎上演。
創作生涯裡獲獎無數,包括英國的惠布瑞特小說獎(Whitbread Prize)、約翰列威林萊斯紀念獎、E. M.佛斯特獎、坎城影展銀獎。
2006 年,獲頒「大英帝國勳章」(OBE) ,表彰其在文學上的貢獻。(此為超過百年歷史的授勳制度,每年頒授若干等級的勳章。原只授予皇室、將領和立下戰功的軍人,後擴展至社會層面,亦頒給在音樂、運動、電影、表演、文學、時尚等對大眾文化有所貢獻的各界人士。作家之中獲此殊榮者,包括托爾金、阿嘉莎‧克莉絲蒂、JK羅琳等人。)
目前也在倫敦經營一家名為Verdes的商店:她翻新了一棟屋齡逾兩百二十年的廢棄老宅,一樓販售有機農產品和自製餐點,二樓整理為住家。她一開始只是為了弄清楚吃下肚的食物從哪裡來,後來逐步實踐「在地的、自給自足的、合乎道德倫理且有合理利潤的、合作社性質的小型商業」,以此證明,在一個向大企業傾斜的世界裡,我們個人仍然可以盡力而為。
譯者:
三珊
國立政治大學英語研究所碩士,主修英美文學。
曾任英文報紙記者,喜歡嘗試生活的各種可能,在文字和翻譯中找到快樂踏實。
曾獲梁實秋文學獎譯詩組首獎。
名人/編輯推薦
美國「性別文學獎」( Lambda Literary Awards ) 2013 年「最佳女同志傳記出版獎」
英國「世界書籍之夜」(World Book Night) 2013年四月選書
「與母親的戰爭、傷痕累累的愛的追尋,必須用感性的碎片抵禦支離壞滅的人生。
和 Janet Frame《天使詩篇》三部曲前後輝映的珠玉傑作。」
───吳繼文 (文字工作者,小說家,譯者) 真情推薦
「以格林童話的敘述方式,揉合了風趣與驚懼,鋒利如刀刃,驚異如孩童圓睜之眼。」──英國《每日電訊報》
「深具啟發,驚心動魄,唯有靠著溫特森的散文之中,那種帶有節制的優雅,方能領會書中殘酷不堪的細節。」──英國《週日獨立報》
「令人難忘的告白,沒有自憐,只有她透過書寫而生存的掙扎。」──《每日郵報》
「這本書是一顆子彈,填滿驚險、黑暗的詼諧,以及努力贏得的自我認知。當溫特森寫道,『我瞭解文字如何運用,就像有些男孩子知道引擎怎麼運作』,她所言不虛。你在一位建築大師的手中,她把回憶錄重新混合成一部恐怖與美麗交織的作品。」──美國《書評論壇》
「(本書) 生猛有力。從第一頁開始就流露出黑色的聰明……獨樹一格……彷彿電擊般的力道。她與養父母的關係令人震驚,但這個因素卻也造就了她成為今日如此一位作家。」──美國《紐約時報》
「清亮、勇敢而生動,溫特森娓娓道來,以兼具戲劇性及啟示性的方式,直探自我的形塑及文學的解放力。」──書評雜誌《書單》
「傑作……展現了文學與愛的顛覆力量。」──時尚雜誌《Vogue》
目次
1 錯誤的嬰兒床
2 出生的好地方
3 最初的字
4 書的麻煩
5 在家裡
6 教堂
7 阿克寧頓
8 啟示錄
9 英國文學A到Z
10 就是這條路
11 藝術與謊言
中場休息
12 海上夜遊
13 與從前有約
14 奇特的會面
15 傷口
尾聲
珍奈‧溫特森作品列表
書摘/試閱
母親對我發脾氣時――這事經常發生――她總會說:「魔鬼把我們帶錯了嬰兒床。」
魔鬼從一九六零年的冷戰及麥卡錫主義之中抽出空來,造訪曼徹斯特――造訪目的:蒙騙溫特森太太――這影像本身就具有浮誇的戲劇性。她是個浮誇的憂鬱人士;一個把左輪手槍藏在工具櫃,還把子彈放在碧麗珠清潔劑鐵罐裡的女人。一個為了避免跟我父親同床,通霄熬夜烤蛋糕的女人。她器官下垂、甲狀腺出問題,而且心臟腫大,她腿上的潰瘡從來無法癒合,還有兩副假牙――無光澤的那一副每天戴,另一副珠光假牙就留待「最佳場合」使用。
我不清楚她為何不生╱生不出孩子。但我知道,她收養我是想要有個朋友(她沒半個),而我就像一枚丟入世界的信號彈――一種宣告她身在此處的方式――一個標示她所在位置的記號。
她痛恨當個無名小卒,而我跟所有小孩一樣――無論是否被領養――我得要活出她沒能活過的人生。我們這麼做是為了父母――別無選擇。
一九八五年,我的第一本小說《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出版時,她還健在。那是半自傳體的小說,描述一對信奉基督教五旬教派的父母,領養了一個小女孩。這女孩長大後理應成為傳教士,但她愛上了一個女人。災難一場。女孩離開家,進了牛津大學,回鄉卻發現母親已架設好無線電廣播器材,向異教徒傳送福音。母親有個頭銜――叫作「慈光」。
小說開場是這樣的:「跟多數人一樣,我和父母同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我父親愛看人角力,母親愛與人角力。」
我人生中大部分時間,都是赤手空拳的搏擊手。出手最猛的就是贏家。我小時就挨打,早已經學會不哭。如果被鎖在門外過夜,我會坐在門階上,直到送牛奶的人過來,然後我喝掉那兩瓶各一品脫的牛奶,留下空瓶,惹我媽生氣,這才走路上學去。
我們總是走路。我們沒車,也沒錢坐公車。我每天平均要走上五英里:到學校來回兩英里,到教堂來回三英里。
每晚都得上教堂,只有星期四除外。
我在《柳橙》一書裡寫了一些我家的事,此書出版後,母親寄給我一封充滿憤怒的信,以她工整無瑕的字跡命令我打電話回去。
到這時,我們已有數年未見。我已離開牛津,湊合著過日子,年紀輕輕就寫了《柳橙》――此書出版時,我二十五歲。
我走到一座電話亭――我住處沒有電話。她走到一座電話亭――她家裡也沒有裝設電話。
我依指示撥打了阿克寧頓 區碼和電話號碼,跟她通上話――誰需要通訊軟體呢?我從聲音就能夠看見她,她一開口,身影就在我面前成形。
她是個體型頗有份量的女人,身材高大,體重約一百二十五公斤。她穿醫療用褲襪,平底涼鞋,合成纖維材質的連身裙,戴尼龍頭巾。她會在臉上撲點粉(讓自己好看些),但不搽口紅(很快就掉色了)。
她擠滿了電話亭。她的體型比她這個人還大。她像是童話故事裡的人物,體型大小約略而不固定。隱約出現,逐漸擴大。我直到很久以後才瞭解,她把自己看得有多渺小,而那時已經太遲。那個無人認領的嬰兒,沒被帶走的嬰兒,仍在她心中。
但那天,她怒氣沖沖,而她彷彿高高坐在怒火的肩上。「這是我生平頭一遭得用假名訂書。」
我試著解釋我要達成的目標。我是懷有抱負的書寫者――沒有抱負,就什麼都不是;沒有抱負,就一點意義都沒有。一九八五年還不是回憶錄盛行的年代――何況我當時也不打算寫那樣的東西。我只是努力跳脫既定想法,認為女性總是書寫「過去經驗」,以所知的一切作為羅盤;而男性書寫的題材寬廣大膽,他們展開畫布,實驗各種體例。亨利.詹姆斯說珍.奧斯汀只描寫四吋象牙大小的事――意指細雜瑣碎,這說法無甚幫助。許多人也這麼形容艾蜜莉.狄金生和維吉尼亞.吳爾芙 。那些說法令我生氣。再怎麼說,經驗和實驗為何不可並存?觀察與想像為何無法同在?為何女性會受限於任何人或事?為何女性不該對文學懷有野心,對自己有所抱負?
溫特森太太毫無上述困擾。她認定作家都性愛成癮,而且放蕩成性,他們破壞規矩,不肯出外工作。書本在我們家是違禁品――容我稍後說明――因此,我寫了一本書,出版它,得了獎……還站在電話亭裡,跟她滔滔不絕地談論文學,爭辯女性主義……
話筒傳來嗶聲――更多銅板投進投幣口――她的聲音如潮水般湧起又退下,我心想:「為什麼你就不能為我感到驕傲呢?」
話筒傳來嗶聲――更多銅板投進投幣口――然後我再度被鎖在門外,坐在門階上。天氣真的好冷,我在屁股下墊了張報紙,整個人蜷縮在粗呢大衣裡。
有個女人走了過來,我認識她。她遞給我一包洋芋片,她知道我母親是什麼樣的人。
屋裡的燈亮著。爸爸值夜班,所以她可以上床睡覺,但不會睡著。她會整晚讀聖經,爸爸回到家,會讓我進門,他不發一語,而她也悶不吭聲。然後,我們會裝作把小孩整夜留置在外是件稀鬆平常的事,永遠不跟你老公同床也再正常不過。有兩副假牙不奇怪,工具櫃裡面藏著手槍也行……
我們仍在電話亭裡通著電話。她說我的成功來自於魔鬼,也就是那個錯誤嬰兒床的守護者。她抨擊我竟在小說中使用真正的名字――如果故事純屬虛構,主角為何叫做珍奈?
為什麼呢?
記憶中,我無時無刻不在構築屬於自己的故事,好跟她的故事抗衡。我從生命初始就得奮力求生。被領養的孩子需要發明自己,因為我們別無他路;我們生命的開始就有空缺,空白,也是個問號。我們的人生有個很重要的部分猛然消失,像是往子宮裡頭丟了一顆炸彈。
爆炸後,那嬰孩掉進一個未知的世界,那個世界僅能透過某種故事才能認識――當然,每個人都是這麼過活,我們的人生故事就是如此,然而,被領養卻是在故事開始之後,才把你丟在那兒。如同讀一本開頭缺頁的書。如同舞台的帷幕升起後才進場。某樣東西不見的感覺永遠如影隨形,絕不會離你而去――這感覺沒辦法消散也不應該消散,因為有些東西就是不見了。
這件事的本質並不是壞事。那個不見的部分,消失的過往,可以是一個開端,而不是空白。它是入口,也是出口。它是化石紀錄,是另一個生命的印記,而你雖然永遠無法擁有那個人生,你的手指仍在追蹤它可能存在的空間,然後,你用手指學會了一種點字法。
這裡有記號,如鞭笞過後的痕跡一般浮起。閱讀它們。閱讀傷痛。重新書寫它們。重新書寫傷痛。
這就是我之所以是個作家的原因――我不說「決定當一個作家」或「成為一個作家」。此非出於意志,甚至算不上是有意識的選擇。為了逃避溫特森太太那個網目狹小的故事,我必須能夠說出自己的故事。人生本是部分真實,部分虛構,而且永遠是個改編故事。我因為書寫而找到出口。
她說:「這些並非事實……」。
事實?這位女士自己可是把廚房裡的老鼠行動解釋成靈異物質哩。
有座連棟屋子位於蘭開夏的阿克寧頓。我們把那類房子稱為上二下二:樓上樓下各兩個房間。我們三人,在那間屋子同住十六年。我說自己的故事版本――忠實而又加料,精準而又誤記,隨著時間打亂重組。我把自己描寫成船難故事裡面的英雄。這的確是一場船難,我被拋在人類的海岸線,發現它既非全然人性,也並非善類。
當我想到我的改編故事,也就是《柳橙》一書,最難過的地方在於我寫了一個能夠與我共生的版本。另一個故事太痛,我無法在那個故事裡面活下來。
我經常被一種類似勾選表格的方式問道,《柳橙》裡面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曾在葬儀社工作嗎?我開過冰淇淋小貨車嗎?我們是否真有福音帳篷?溫特森太太自己安裝了無線電廣播嗎?她真的用彈弓來嚇貓嗎?
這些問題,我無法回答。我只能說,在《柳橙》書中有個角色叫作見證艾西,她照顧小珍奈,像一面柔軟的牆,抵禦「母親」這角色造成的(橫衝直撞)殺傷力。
我將她寫進故事,只因為我無法忍受把她排除在外。我把她寫進來,只因為我但願事實真是如此。如果你是孤單的孩子,你會找個虛構的朋友。
其實沒有艾西這個人。也沒人像艾西一樣對我。事情比我寫的還要寂寞得多。
我在學校的那些年,大部分時候我都趁著休息時間,坐在校門外的鐵欄杆上。我不是受人歡迎或討人喜歡的小孩;我太多刺,太憤怒,太強烈,也太怪異。經常上教堂使得我不容易在學校交到朋友,校園裡的情況又總是讓格格不入的地方凸顯出來。我裝體育服的袋子上面繡著「夏日結束,我們尚未得救」的字樣,使我格外醒目。
可是,我即使交到了朋友,也絕不讓事情好過。
如果有人喜歡我,我會等她卸下心防,然後宣告我再也不想跟她當朋友。我會觀察她的不解與難過。淚水。接著,我會跑掉,由於獲得掌控而得意洋洋;但勝利感和掌控感迅速消散以後,我會一直大哭,因為我再次把自己留在外頭,在門外的階梯上,而我根本就不想待在那兒。
被領養就是置身局外。你會把一個人沒有歸屬的感受表現出來。表現的方法是嘗試把加諸於你的事拿來對待別人。絕不相信有人可能會愛原本的你。
我從不相信我的父母愛過我。我試著相信他們,但行不通。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學習如何去愛――包括付出與接受。我執迷地書寫愛,我抽絲剝繭辨析愛的種種,而我現在和當時都很瞭解,愛是最高的價值。當然,我小時候愛上帝,上帝也愛我。那算是愛。我也愛動物和大自然。以及詩。問題在於人。你如何去愛另外一個人?你如何相信另外一個人也愛你?
我一點也不懂。
我以為愛就是失去。
為何愛得要失去了才能測量?
這幾句話是我另一本小說的開頭――《書寫在身體上》(一九九二年)。我獵取愛, 圍困愛,失去愛,渴望愛……
真實(truth),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件極為複雜的事。對書寫者而言,你沒寫的事,與你寫進書裡的事,兩者說的話一樣多。文本的邊緣之外還有什麼?攝影者用鏡頭框起照片;寫作者則框起他們的世界。
溫特森太太反對我放進這些事情,但在我看來,那些我刻意不寫的東西,其實是這個故事沉默的孿生子。有太多事情我們沒辦法說,因為它們太過痛苦。我們希望說出來的事能夠緩和剩下沒說的,或者以某種方式平復它。故事帶有補償性。這世界沒有公平正義,無法參透,也不受控制。
我們說故事是在施行掌控,但掌控是要留下一道鴻溝,一個開口。這是一個故事版本,絕不是最終版本。也許,我們期盼沉默會被哪個人聽見,然後故事得以繼續,得以被重新訴說。
我們寫作時,呈現出來的沉默與故事本身一樣多。文字是沉默之中能被說出來的那個部分。
溫特森太太會寧願我保持沉默。
你可記得希臘神話裡面菲洛梅爾的故事?她被強暴,但舌頭被施暴者割掉,使她永遠不能說話。
我相信虛構小說和故事的力量,因為如此一來我們便開口說了話,而非噤聲不語。我們每個人陷入深深的創傷時,都會發現自己遲疑又結巴;我們的語言中出現長長的停頓。想說的事情卡住。我們從別人的語言中找回自己的語言。我們可以求助於詩。我們可以打開書本。有人已在那裡等著,深深沉潛文字之中。
我需要文字,因為不快樂的家庭總是與沉默同謀。打破沉默的那個人永遠不被原諒。他或她得學著原諒自己。
上帝即寬恕――某故事如此說道,但是,我們家的上帝是舊約聖經的那一位,寬恕總得經過重大犧牲才能獲得。溫特森太太並不快樂,所以我們得與她共苦。她在等待天啟。
她最喜愛的歌曲是〈主塗抹了你的過犯〉,過犯應指罪惡,但其實是指任何曾讓她厭煩的人,也就是每一個人。她就是不喜歡任何人,也不喜歡生活。人生是個包袱,背負直到入土才能丟棄。人生是淚之谷 ,是死前的體驗。
溫特森太太每天都在祈禱:「主啊,請讓我死去吧。」這使我和父親都備感沉重。
她自己的母親是個有教養的女人,嫁了一個很有魅力的風流胚子,把錢都給了他,然後看著他玩女人把錢花光。有一陣子,在我大約三到五歲之間,我們得跟我外公同住,好讓溫特森太太照顧她那個罹患喉癌而大限將至的母親。
雖然溫特森太太是虔誠的教徒,她卻相信鬼魂,因此外公所交的女友令她十分不滿,因為那個上年紀又染金髮的酒吧女侍也是個靈媒,還在我們屋裡的房間舉行降神會。
降神會結束後,我母親抱怨屋子裡到處是戰爭時期穿軍服的男人。當我進廚房拿鹹牛肉三明治,她卻要我等到亡靈離開後才准吃。這一等就是好幾個小時,對一個四歲小孩來說還真難捱。
我開始上街遊蕩索討東西吃。溫特森太太跟在我後頭,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關於魔鬼和嬰兒床的黑暗故事……
在我隔壁的嬰兒床裡,躺著一個叫作保羅的小男嬰。他是我的幽靈兄弟,因為每當我不聽話,便會召喚出保羅足以封聖的特質。保羅絕不會把他的新玩偶丟進池子(到底保羅能否拿到玩偶,這個超現實的可能性從開始就不在討論之中)。保羅絕不會在他的捲毛狗睡衣套裡裝滿番茄,玩什麼開腸剖肚的手術遊戲,擠出血一般的汁液。保羅絕不會藏起外公的防毒面具(外公因為某種原因還留著戰時的防毒面具,我超愛的)。保羅才不會沒接到邀請就跑到別人美好的生日聚會,還戴著外公的防毒面具。
如果他們當初帶回保羅,而不是我,事情就會不同,會更好。我本該是來與她作伴的……就像她對自己的母親那樣。
她母親過世後,她就把自己封閉在悲痛之中。我則把自己封閉在食物儲藏室裡,因為我已學會使用小型鑰匙打開鹹牛肉罐。
我有記憶――是真是假?
記憶被玫瑰環繞,這很怪,因為我的回憶其實狂暴而令人傷心,但外公熱中於園藝,特別鍾愛玫瑰。我總愛看他捲起衣袖,穿著針織背心,用一只有噴嘴的光亮銅質水罐為盛開的花朵噴水。他用一種古怪的方式喜歡我,而他討厭我母親,我母親則痛恨他――不是氣他,而是一種具有毒性而屈從的不滿。
我穿著我最喜歡的一套衣服――牛仔外套和一頂流蘇帽。我小小身體兩側都掛著玩具槍。
有個女人走進花園,外公要我到屋裡找母親,她像平時一樣,正在做一堆三明治。
我跑進門――溫特森太太脫下圍裙應門去。
我從門廊遠處窺視。兩個女人在吵架,內容我聽不懂,吵得驚天動地,像是出於動物本能的恐懼。溫特森太太把門用力甩上,倚門稍歇。我從偷窺處爬出來。她轉過身。我站在那兒,身穿牛仔裝。
「那是不是我媽媽?」
溫特森太太一拳打得我往後退。然後她跑上樓去。
我往外走到花園。外公正在給玫瑰花噴水。他沒理我。那裡空無一人。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