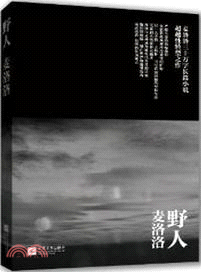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自序
引子
第一章 蒙北監獄
第二章 最後的晚餐
第三章 “報告!”
第四章 故鄉1965
第五章 紙飛機
第六章 烏鴉
第七章 停屍房
第八章 赤裸的信
第九章 我們的喜兒
第十章 百樂門的舞女
第十一章 我是沈世慧
第十二章 “錘子你別死……”
第十三章 墳墓
第十四章 軍區生活
第十五章 道路盡頭
第十六章 天蒼蒼野茫茫
第十七章 電話
第十八章 柬埔寨的中國女郎
第十九章 中秋月彎彎
第二十章 逃犯屎聰
第二十一章 回家路上
第二十二章 趕回上海
第二十三章 重回蒙北
第二十四章 姆娘
第二十五章 老人的歌聲
第二十六章 二十歲那年
第二十七章 出獄
第二十八章 光明
尾聲
書摘/試閱
後來他總是回憶起內蒙古以北的那所監獄,但是他卻記不清監獄裡的景致了。他記得的,是內蒙古持久而暴烈的風沙。沙塵在渾濁的蒼穹間起起落落,原是這風沙將天空染汙了。再後來,他又一點點記起了監獄旁的大樹。樹死了,一年一年長不出新葉,餘下的幾片枯葉,也被風沙裹進了天空,變作風中的塵。那時有開荒隊員,他們開荒了許多年,樹一棵棵被種下,又一棵棵死在沒有營養的沙地裡。只有一種草能夠在如此荒蕪的沙地裡活著,從遠處看,簡直沒法看到這矮叢叢的草,必須俯身探望,才能將草的樣子看清、認准。草連在一起,變成沙地上的一塊大瘡痍。生病的沙地,卻因為這唯一的綠色,而有了絲毫點綴的新意。
那棵死去的大樹就立在監獄的圍牆邊。日復一日,大風將樹幹上的蒼老枯皮一整塊一整塊掀翻乾淨,露出新一層乳白色的樹幹內裡。死去的樹又重新活了。而年輕的樹幹又將在漫漫無期中,變回蒼老枯皮。循環往復。於是樹的靈魂感慨道:原來只有死去了,才能長長久久地活下去啊。
風沙一年年把乳白色的樹幹內裡給染得昏黃,樹便一年年又老了。在它那被大風剝乾淨的樹幹上長出了一對眼睛,在靠近根部的位置。監獄裡的犯人每次出號幹活,樹根就是他們天然的廁所。而獄警只允許犯人在他可及的目光里拉撒,所以黃尿就把樹幹上兩個固定的位置水滴石穿,成了空洞洞的兩隻大眼睛。久了,死去了而仍活著的大樹,它的眼睛也有了生命。它窺視著監獄裡每個人的一舉一動,將所有現在發生的,或將要發生的通通看在眼裡,樹的心就有了歷史的厚重感。
所以,這所監獄也就有了歷史。
一望無際的沙地埋藏著歷史。我們現在回頭去看,這片沙地已可以稱之為沙漠。沙漠上的生物,比如蠍子、蜥蜴、蛇,它們一代代生息繁衍,再惡劣的氣候也沒有把它們趕盡殺絕。它們身上堅硬的盔甲是被風沙磨出來的,天生好鬥的性格要歸咎給惡劣的氣候。它們一方面受控於沙漠,另一方面又將沙漠控制得當。沙漠是它們的世外桃源。從古至今荒蕪著的沙漠,淘汰了一種又一種生物,最後將它們選擇出來,變成這世外桃源的主人。紫灰色晨光裡,它們出擊、匍匐;墨藍如深海的夜裡,它們休憩、安養生息。一天天就這麼過去,從來沒有樹,沒有山,沒有河。水源在地下幾公里,它們挖啊刨啊,終於把一整片沙漠掏空了。
它們的死期很快也就要到了。它們不知道,有一種叫做“人”的生物正從幾千里之外朝這裡跋涉。
它們靜靜地等,把自己等老了,等死了。把後輩們等到一個個都長成了它們自己。人來了。
人的腳步踩在這被掏空的沙地上,一踩便往深處陷落幾釐米,把這裡主人的家給踩散了。它們不知所措,立在沙漠與天空的那一條分界線上,癡癡地望著這群兩足獸。陽光打出了它們的側影,一會兒,也打出了兩足獸的側影。
於是,在這片千古一貫荒著的沙漠上,人類要和蠍子、蜥蜴、蛇們一起主宰。
慢慢地,它們發現人類成了真正的主宰,自己則成了主宰們的奴隸。
它們是在人類的陰謀詭計裡成了奴隸的。人類使盡各種手段,在沙地上設下圈套。勾引它們入套的手段各式各樣,有時是一塊肉,有時則是同類淡淡的哀嚎。但很快,進入人類圈套後的它們,就成了人類口中的美食。
人類還在沙地上蓋起了房子。它們時不時竄進去搗亂,分析著房子內部的構架。它們想,人類真大膽,敢在沙地上蓋起這麼個龐然大物。它們發現,蓋房子用的材料,是自己無聊時玩耍的枯樹幹,或者沙塵和了水之後,再添上一些輔料,配置而成的一種新材料。房子真夠結實的,任憑大風吹刮洗練也不倒下。待到人走樓空,它們又重新變回沙漠的主人後,它們也住進了這些房子裡,直到那時它們才徹底嘆服於人類狡猾的聰慧。
人類抵達沙漠之後,開始妄圖墾荒,將千古未變的沙地掀開,撒上異地的樹苗,播下新鮮的種子。寒冷多霜的內蒙古,就開始了它慢慢從醜陋到美麗的裝裱。回到它們看到這群兩足獸的那天。它們想,你們來得可真不是時候,雪正大著呢,而且將一天天大下去。早來一點兒或晚來一點兒都可以,雪不一會兒就蓋過了兩足獸們的膝蓋。
它們冬眠了。昏沉的睡眠裡,它們隱約聽到鏗鏗的聲響,從大地表層傳進大地內部。等到它們蘇醒過來,看到一幢幢房子立起來了,像春天雨後從大地裡抽出的一截截新筍。
在這群幹活的兩足獸裡,有一個叫做“沈世聰”的人。他是我二哥。我現在要講的,正是他的故事。等到我會寫作的時候,他已經老了,也已經離開了這所監獄。他是這裡的第一批犯人,是1985年進來的。後來到這裡的人總是這樣稱呼他們第一批犯人:老一隊。他是“老一隊”的成員之一,也是最小的老一隊。那些油了的重犯們想,這娃娃到底犯了什麼罪,和他們一起給關到這裡來了?在遷徙的過程中,他們似乎都忽略了他,因為他總是沉默不語地跟在隊伍最後。他長得老高老高,有一米八五,卻又極瘦,人看起來斯斯文文的。老一隊的人後來還發現,他的手是一雙漂亮的手,縱然已被風沙刮得粗糙難看,但還是瘦長的,虎口和手臂的連接處有一條清冷的弧度。他們就湊過去問這問那,他給的回答頂多是笑,然後就是慣性的沉默。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沈世聰”是他案卷裡的名字。他的真名叫沈世慧。沈世聰是我大哥,是和他長得一模一樣的雙胞胎。他們個子相同,五官相同,但性格卻截然不同。被關的正是我二哥:沈世慧。
後來我問姆娘,大哥去哪兒啦?我總是見姆娘默不作聲,眼淚成串地掉下來。也是到我能夠寫作的歲數,我才發現,原來該去蹲監的是我大哥沈世聰,而坐監獄的是我二哥沈世慧。我二哥替我大哥蹲了十八年監獄。直蹲到我大哥成了材,當了公安局長,蹲到自己這一塊奇材被苦難磨成了廢物。
他們一群人花了兩個月時間,從上海一路來到內蒙古。又花了一個月時間把監房蓋起來。這麼多時間加上一路走來的心酸,使犯人們彼此都成了朋友。房子蓋好後,獄警們和犯人們商量著也給這裡取個名字。二十歲的沈世慧,悶在黑壓壓的人群裡,一聲不吭。正因為他的沉默,在眾多爭先恐後的人群裡顯得突兀,獄警就打斷了所有人,叫他給取個名。二十歲的沈世慧抬起一張無辜又無奈的臉,說:“報告管教,我不會取的。”
這時候有人抗議了,說自己在囚車上經常看見“沈世聰”望著車外,滿嘴是詩。說他頂有文化的一個人,取個名字倒不會了。“沈世聰”尷尬地低下頭,一語不發。獄警火起來,罵道:“你狗日的……”才發現並不清楚他的編號,就低頭翻了案卷,將後半句的罵補上,“你狗日的2686,給老子裝是不,老子叫你吃屎!”
我二哥並不介意比他年長的人偶爾當一回他“老子”。他還是不作聲,就這麼強著。獄警叫他站起來。他一站起來,整個一米八五的高挑身材就唬住了獄警。
“老子叫你取你就得取!”獄警抬起腿,想在他身上留下一個完美的射門。他一躲,純屬本能反應。獄警的腳撲了個空,連帶著使身體各部分都失了衡,朝前猛地跌去,摔了個狗吃屎。現在是沈世慧叫獄警吃屎了,惹得老一隊們哈哈大笑。獄警跌跌撞撞爬起來,拍了拍身上的灰土,“請”他歸隊坐好,意思是:苦日子還在後頭,有你受的!沈世慧擠過人群的腿,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他雙手互插在袖口裡,後背微佝,佝僂的後背使脖子往前微微延伸,從側面看,頭和身軀就像脫了節。用不了多長時間,他就把這些犯人的姿勢學會了。他整個人瑟縮在囚服裡,像一個撒了氣的皮球縮進球心。再過一段時間,他就會完全接受這裡的一切。他的接受,是因為習慣,不得已而為之。
散會後,老一隊的人都在討論這個不知好歹的毛小夥。他們一個個也是皮球似的縮在沈世慧身邊,問這問那。沈世慧突然被這股陌生的親昵感動了。他的胸腔中躥出一股灼熱,老一隊的人立馬發現,他又要流淚了。他們就說:“甭哭甭哭,再哭也沒得用。”他就強忍著。
老一隊之一問他:“你是哪兒的?”
他囁嚅著說:“上海。”
老一隊之二又問:“你叫什麼名字?”
“沈世慧”被他從嘴裡周了一圈,然後吞進了肚子裡。他說:“我叫沈世聰。”
老一隊的人對他表示好感,沒有攻擊力的人,天生會讓人產生好感。他們一群人就互相攀著走回了新蓋起來的監舍。
對沙漠來說,每個時段都是黃昏。大概是真正的黃昏時候到了,天空墨黑了,在大漠的盡頭,粗糲糲的一道弧度上,一座監獄就此生根。裡面關押著我的囚犯二哥:沈世慧。
就在真正的黃昏到來之時,獄長把他叫到審訊室裡。審訊室也和監舍一個質地,松垮垮的房子結構還有待加固。獄警說:“我知道你一腦子好文化,我看得出來。”後來我想,這個獄長真是個識貨人,在我二哥被關押的十八年裡,二哥用腦子記下了在蒙北監獄的所有故事,記下了他在監獄裡所度過的前半生,記下了他內心的隱痛和孤獨。他回上海後,把這個故事告訴了我。這就是你現在所看到的,由我寫出來的荒漠故事。
他說:“管教,我真的不會取名字。”
獄長還不死心,他在可以勉強稱之為“桌子”的桌子上攤開一支毛筆和一塊匾額。這是省裡分配給獄裡的,叫他好歹也把新監獄“裝幀裝幀”。毛筆上綴著金粉,匾額被擦得乾淨鋥亮。沈世慧心想:算了,寫就寫吧。
他問獄長:“寫什麼?”
獄長說:“你給咱新家取個名字。”
這裡是他的新家了。沈世慧心裡一陣落空。他的淚水又要掉下來似的,眼眶通紅通紅,但好在風沙迅速把眼淚稀釋,化為烏有。
沈世慧說:“既然是內蒙古以北,就叫‘蒙北監獄’吧。”
獄長一聽,兀自嘟噥道:“蒙北監獄……好!就叫蒙北監獄!
第一章 蒙北監獄
我二哥揮起綴滿金粉的毛筆,在那塊嶄新的木質匾額上寫下四個大字“蒙北監獄”,四個楷書大字在暗沉的木匾額上游龍戲鳳,相互盤亙著,顯得美麗而立體。
他這就等於承認了自己的罪犯身份,也就承認了獄長所謂的“新家”概念。他和獄長都呆呆地望著這四個大字,各自心裡都在想各自的心事。沙塵在屋外狂舞,吹過來蕩過去,將他們的注意力一下子分散,又一下子攏聚。
獄長叫李強,人人叫他李管教。因為順口,他的名字又被簡縮成“李管”。他此刻站在我二哥旁邊,經由他那些淺薄的知識構成,而在心裡感慨道: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瞬間對“沈世聰”刮目相看。他仰臉看著“沈世聰”,笑笑,露出一口大蟲牙,同時吐出臭熏熏的一句重慶話版的“世聰”。
這是李管對我二哥的昵稱,去掉姓氏,只讀名字。好像如此就能和我二哥攀上關係,繼而就能與他腦子裡那一整套的知識構成攀上關係。而他的昵稱使我二哥馬上就有了一個外號:死聰。在監獄眾多的口音裡,這“死聰”慢慢又變成了“失聰”,最後老一隊的人統一口徑,都叫他“屎聰”。
屎聰站立在“蒙北監獄”四個大字面前,凍僵的手像木頭一樣,動作起來成了一節一節機械化的動作。他對著那四個楷體大字淚流滿面,滾燙的淚滑過他乾燥的臉頰,留下一路濡濕。最後淚水流進他皸裂的嘴,皸裂縫隙處乾燥的血已成了絳紫色。血是被凍住的,被眼淚的熱度化開後,又成了黑灰色澤。
屋外已經黑影重重,那些曾經的沙漠主宰們開始了日夜顛倒的活動。據說他們曾經也是正常的,白天出來,夜晚休息。但人類搗亂了它們原本的生活,使正常變成不正常,又使不正常正常化了。它們“嘶嘶”地爬在沙地上,儘量讓自己看起來扁平一點,再扁平一點。好了,這就夠了。忽然,一隻兩足獸的大腳差點踩著它們,但大腳立馬又放過了它們。它們迅速鑽進沙地裡,不一會兒又從遠處的沙地上冒出來。它們看到這只大腳踏進了拔地而起的龐然大物裡。
這是個無風的夜晚。我二哥屎聰很快便能知道,內蒙古無風的夜晚少得可憐。他走進監舍,在門最終要關閉的刹那,借著最後一抹幽幽爬進來的月光,他看見滿屋子的人縮在一團取暖。他們互相依偎,有人在黑暗中流淚,有人在被徒然打破的黑暗中抬起頭,驚慌地與他對視。只需一刹那,他們就迷糊了。這三個月的大遷徙這樣不真,一場夢一樣。
我在後來同二哥幾次深入的談話中,在二哥那些模糊而跳蕩的隻言片語裡,逐漸摸准了一個殘酷的監獄環境。二哥出獄後,宛如一隻從深海的黑暗躍入光明的魚,那詫然間的亮光使他忘卻了監獄裡的情境。現在由我來重新修復他記憶裡的“蒙北監獄”。
就像一個廣角鏡頭,沙漠平整的面上,突然立起了這所監獄。黑壓壓的四幢房子,一幢是監舍,監舍旁邊拉開一幢小土房,是監獄裡的“黑號子”。另一幢是獄警的住所,監獄食堂在獄警住所的後面。四幢房子在天際線這頭遙遙相應,白頭偕老……我在寫這本書之前,曾在網上搜索過“蒙北監獄”,我發現並沒有這所監獄的記錄。我甚至一度以為二哥口中的“蒙北監獄”只是一個時代的廢墟,是我二哥心中廢墟的前半生。後來,在這本稿子即將寫完時,我親自去了一趟內蒙古。我一路尋找,打問,從少年問到青年,再是壯年,最後是老年。終於,我在一個老人的嘴裡問到了這所監獄。老人吸著當地煙,伴著風沙吐出的煙霧也帶著絲絲專屬沙漠的乾燥。老人說:“蒙北監獄2000年被大火燒了,活著的犯人都轉移了。因為蒙北監獄偏僻得很,所以現在沒人知道嘍。”我終於從他滿是鄉音的話語中畫出一條
線路,然後開車找到了那裡。那裡已經重新變成蠍子、蜥蜴和蛇們的歡樂世界。
我看到蒙北監獄以平行的兩條線拉開地界兩端,中間是一塊大平地。已成廢墟的監獄被蠍子、蜥蜴和蛇們掏空了,像大地上拔地而起又迅速萎縮的二頭肌。我走進去,想仔細看一看它的內在結構。就在走進去的瞬間,我感到自己踏進了一片濃霧裡,黑的看不清楚,抹殺了時間與空間。我同時聞到屋子裡因常年尿液糞便的發酵,而將永久盤桓在此的熏臭氣味。我趕緊退了出來。
我站在這片沙漠上,在永久的黑暗中,在沙漠主宰們“吱吱”的叫喚裡,我看到二十幾年前的我二哥,正從濃稠的黑暗裡冒出他瘦長的身影,以及那雙滿含淚水的大眼睛。
屎聰找到一個好位置,屋裡的東南角。松垮的房頂往下簌簌掉著粉塵。不一會兒,粉塵就把他的頭髮染成了土黃。黑暗中,有人抽抽搭搭的哭聲慢慢凸顯出來,並以極快的速度感染著別人。抽抽搭搭的哭聲馬上匯流,變成一片抽泣的海洋。沒有窗,沒有床。只有幾叢幹透的芨芨草鋪在地上,起不到任何床的作用。有人低聲罵了一句:“哭啥!有啥哭的!”聲音迅速以回音的形式震開在每個人的耳朵裡。哭海消失了。
說這話的是個四十多歲的老犯人。我二哥屎聰在第二天知道了他的外號:南瓜臉。由於黑暗,他現在還沒法看清這南瓜臉上的一顆大南瓜頭。南瓜臉的眼睛天生長在別人鼻子的位置上,鼻子又長在別人嘴巴的位置上,總之他一切的五官都比別人往下長,所以順帶著使他的臉看起來特別長,又因為他顴骨極高,往兩旁飛著,整個臉就像一顆大南瓜,又長又寬,添出一絲兇狠,兩成毒辣,三分恐怖。他又低聲罵了一句什麼,就沒人敢做聲了。他的聲音也是兇狠狠的,沙啞的煙嗓因為再沒有煙抽的緣故,變得更加沙啞了。此時,監舍裡的人都看到了從他往下長的眼睛裡射出的兩道凜光。意思是:誰再敢出聲,誰就試試!
隨著寂靜,風沙的吼聲濃了。風沙在繼續。我二哥借著這難得的寂靜睡著了。
我二哥屎聰在睡夢中看到了一隻螢火蟲。在他後來和我訴說這段往事的模糊語言中,這是唯一能被他說准的事物。直到後來我才知道,這只螢火蟲原來不存在。陷入在故事中的我並沒有意識到,在內蒙古如此可怖的氣候裡,怎麼可能會有螢火蟲。我二哥把真實的回憶忘了,卻將自己腦中的虛構記得一清二楚。我二哥出來後,得了精神分裂症,並有很嚴重的幻聽。他說在監舍裡,總能聽到有人對他說話。有時是說一些無關痛癢的話,有些話卻格外地令他緊張。我問他:“那個人說的什麼語言?”他回答我說:“標準的漢語。”我被他繞在裡面了。這只螢火蟲就是他在這時告訴我的。他說:“只要有人和我說話,我就能看見這只螢火蟲。發光的小蟲子在黑暗裡飛啊飛啊,一會兒飛到眼前,一會兒又飛到了幾米開外。”最後他又說:“是螢火蟲在和我說話哩!”就在二哥與我說話的間隙,他抬起手,沖我的眼睛抓來。我躲開。他笑笑說:“螢火蟲掉進了你的眼睛裡。”
我刹那間明白,螢火蟲是他在監獄長久的黑暗裡,祈求的唯一一線光明。
這是螢火蟲第一次出現在他夢裡,在今後十八年的漫長歲月中,螢火蟲逐漸在我二哥的夢中完成了它從虛構到真實的演變。這時的屎聰還能分清現實和虛構,真相和謊言。他沒有意識到,這只螢火蟲將在以後的牢獄之災裡成為自己最好的朋友。在沒有窗戶、沒有光的監舍裡,螢火蟲將是他唯一的點亮。
屎聰看到這只螢火蟲一直圍著他飛,從一邊飛到另一邊。他的眼睛就跟著飛蟲散發的光芒,一會兒移到這邊,一會兒移到另一邊。黑暗裡的時間是靜止的,死水般沉寂。而這光芒就是風吹落在死水上的一抹淡淡水紋。他簡直要為這細微的水紋而震驚了。這一個夜晚,老一隊的人都聽到了屎聰在睡夢中的笑。笑從微笑開始,變成小聲的笑,變成哈哈大笑,變成尖聲怪笑。老一隊隊員們渾身發冷,是被他的笑唬住了。他們想,這毛小夥在夢中想什麼呢?竟能發出如此詭異的笑聲來。
這夜,只有他一個人是睡著的。不一會兒,獄長李管吹起了軍哨,因為李管也睡不著。軍哨劃破夜的沉寂,在蒼穹間拋出一個下落的弧度。這是點名的信號。老一隊們趕緊爬起來,堵在門口。一直到李管來開鎖子,屎聰還沒有醒。一起沒有醒的,還有五個人。那五個人永遠寂靜了,就像這深夜,永遠不會醒來。
我二哥屎聰是被他們震破喉嚨的點名聲吵醒的,這時,他睡夢中的螢火蟲不見了。
他趕緊跑了出去,插在隊伍裡。李管要求重新點名。編號從2680一直叫到2720,中間出現了五個空缺,也就是那五個永遠寂靜的人。四十個老一隊們,在新家落成的第一天,變成了三十五個。
“你、你、你,還有你,去把監舍裡的屍體搬出來!”李管的語氣命令意味十足。四個人就忙活了一陣,將死去的五個編號從監舍裡拖出來,案卷上也將把他們的編號永遠劃除,“死亡原因”一欄裡將寫著“待查”。沒死的人都松了一口氣,這五個人的死,意味著將有更寬敞的空間讓給他們。內蒙古惡劣的氣候還將接著淘汰一批人。
沒有去搬屍體的犯人筆直站在空地上,我二哥屎聰抬起頭,看到天空中密佈的星辰。無風的夜晚過去了,大風來了,將他瘦長的身子不倒翁似的刮蕩起來。
不久,搬屍體的四個人歸隊了。五具屍體躺在他們身邊,像一串編號串在一起,成了死亡的符號。從高處看這一幕,三十五個人站著,五個人躺著,交叉成T字形,而橫與豎的交點上,是生與死的交接口。他們看到原來生與死的界限這樣明確,也就是一步之遙,死亡原來這般輕而易舉。
不遠處的哨崗上,站著兩名軍人,他們手端五六半式,挺拔如楊。屎聰感到內蒙古的天地距離很窄,窄到星辰就散落在軍人的頭頂上。如果再有多一點的時間就好了,他就可以再仔細看看內蒙古的黑夜。內蒙古的黑夜很美,瀕臨死亡的絕美。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