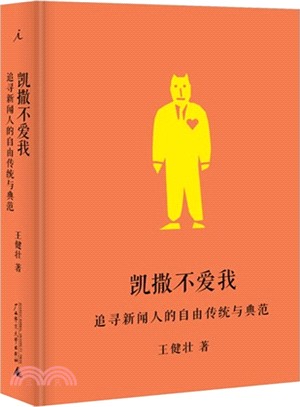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出版《我不愛凱撒》、《看花猶是去年人》、《我叫他,爺爺》等書。現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名人/編輯推薦
★五十二個自由派新聞人,五十二個與當權派、與扭曲的社會風氣唱反調的傳奇故事。作者高擎“自由主義”、“新聞專業主義”兩面旗幟,豎標桿,挽狂瀾。從“扒糞運動”到“最危險的總編輯”,近百年的新聞史,一路縷過來;令我們看見了新聞的理想與目標,切身感受到一代代記者的信念與勇氣。閱讀此書,我們感嘆新聞還是有標準的,而前面正有如此多的典范。
★本書由盧躍剛撰序,龍應臺、錢鋼、陳浩、楊照等名家鼎力推薦。
序
他極少出現在電視上,但若在電視新聞片段里看到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司法戰役后出現,他說話仍然就像一篇寫好的文章,邏輯密實而有思想性,影像里的他讓我想起大衛·布林克利那些第一代的(電視)文人記者。
他的文字讀來有力氣,讀后不妨翻到紙頁的背面,查看有沒有滲透的印子。有些句子頗可頌讀,想與他早年寫詩有關。
但他的眼神從不犀利,談吐有些溫柔。從十八歲那年秋天認識他開始,就想不通他如何能收斂鋒芒,又劍氣充沛,我猜那胸中的江河,是年少讀史的訓練。
他在大報館里留下過傳說,曾是最年輕的“人間”主編,掀起過論戰,然后就走人新聞人的生涯,風雨江湖,星夜有酒。
在時代的墻上留下劍痕的,除了他的文字,必是《新新聞》。十八年來,高潮低潮,人來人往,有些名字或多于或少于《新新聞》,或大于或小于《新新聞》,若說有一人剛好等于,西緒弗斯和石頭,彼得·潘與影子絲密合縫,必是王健壯。
那一日,在溫州街,書肆前,邂逅父子二人。一人身形壯碩一人氣質古典,想二十年前曾說他父子當易名,父日澤生子日健壯。今思所言差矣,十八年可如一日,其志不改,不改不改,斯人當得起健壯二字。
昨日的政治運動與自由啟蒙曾經一身兩任的年代,奮戰威權與爭自由新聞在同一列車上行駛,曾幾何時,運動者大半走上了權力的舞臺,黨派政治耍成前所未見的迷霧,權力話語夾泥沙雜草十面埋伏。
在一個自由新聞傳統如斯斷裂的年代,他還是一心想找尋典范,實踐不能墮落的志向,為人與為文,都與權力人物平起平坐。不特別看得起他們,也不特別看不起他們。反之可能亦然,但不重要。即使左邊是戲臺,右邊有啦啦隊選拔比賽,此人堅持得經常自己也使自己頭疼。
一只獨立清明的筆,寫出五十二個新聞與新聞人的故事,作為還未喪志的人們一路行來的伴唱歌曲。
目次
序二:健壯如斯 / 陳浩
自序:尋找張季鸞
【第一輯】 媒體的礦工:調查記者
總統也怕那只耙子:斯蒂芬斯
吃肉時就想到的名字:辛克萊
密涅瓦打敗泰坦:塔貝爾
到國會抓叛國賊:菲利普斯
茶壺頂上的犬儒:安德森
如果媒體沉默不語:古斯曼
荒涼年代的獨立記者:
只要記住一句話:斯東
別在床上看他的書:哈伯斯坦
天下第一筆:赫什
大家都在等他電話:伍德沃德
最佳拍檔三十年:巴利特與斯蒂爾
邁阿密風云:薩維奇
五千年等于一年:艾倫瑞克
永遠在路上:加勒特
我看我感受我經驗:柯諾瓦
殘酷大街上的奧德修斯:勒布蘭克
死牢天使:普洛提斯
【第二輯】 媒體的哨兵:線上記者
興登堡向他含淚告白:塞爾迪斯
肯尼迪在他面前發抖 :雷斯頓
放膽文章拼命藥:湯普森
七千頁的大秘密:席漢
最后一場決斗:法拉奇
呼叫中國救米勒:米勒
最前線哨兵:梅班克
【第三輯】 媒體的柱子:專欄作家
掛鈴鐺的那只公羊:李普曼
總統向記者低頭:克羅克
停止旋轉的木馬:安德森
他替敵人辯護:阿爾索普
一字一錘敲警鐘:劉易斯
站在馬路中間的圣牛:布洛德
南方有一顆孤星:伊文斯
普利策也捧腹大笑:陶德
二減一不等于四:克魯格曼
美國李敖愛搖滾:阿特曼
他打開了白宮大腦:奧萊塔
部落格進城了:馬歇爾
【第四輯】 媒體的船錨:電視主播
美好的星期二:莫洛
第十七號敵人:肖爾
寧為主播不做總統:克朗凱特
荒原中的綠洲:莫耶斯
上帝開他玩笑:丹?拉瑟
七百二十一個名字:科佩爾
馮光遠的拜把兄弟:斯圖爾特
【第五輯】 媒體的指揮:總編輯與總主筆
沒有廣告的報紙:英格索爾
沒人歌頌的英雄:麥克魯奇
最危險的總編輯:布萊德利
別舔那只喂你的手:道尼
最后堡壘沒有淪陷:柯林斯
放烽火的人:卡崔娜?范登豪沃
沒有終點的游牧:金斯利
屏老
書摘/試閱
二○○五年十月初,在龍應臺客居香港大學面海的沙灣徑宿舍里,二十幾位分別來自北京、上海、廣州、吉隆坡、香港與臺北的老中青三代新聞同業,以華文媒體的未來為題,閉門盍各言爾志了十幾個小時,疲勞轟炸到讓人戲稱被關在集中營里也不過如此。
晚上十點多,集中營打烊,曲終人散前,幾位意猶未盡的新舊朋友又聚在陽臺上,眺望著黑蒙蒙的一片大海閑聊,聊兩岸三地傳媒閑話,聊古今傳媒人物,其中聊到一位是余紀忠先生。
巧的是,我去香港前,《明報》副刊的馬家輝請我寫一篇談臺灣傳媒現狀的文章,在這篇題為“舉目不見一個報人”刊登于我“逃離集中營”隔天的文章中,我舉了兩位老報人為例,其中之一正好就是余先生。這篇文章是這樣寫的:
三年半前,《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過世,許多人稱譽他是臺灣最后的報人,并且感嘆文人辦報的傳統從此將成絕響。當時雖曾有人不以為然,認為江山代有報人出,“余”何人也,豈無“后”乎?但從臺灣這幾年的報業發展來看,期待另一個報人的誕生,確實就像期待彌賽亞降臨一樣,永遠只是個夢。
報老板能被稱為報人,就像reporter能被稱為journalist一樣,都是角色價值的被肯定。但報人辦報與非報人辦報有什么不同?簡單說,報人辦報就是文人辦報,是文人以辦報的方式論政,就像張季鸞曾經說過的:“中國報紙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后,但也可以說是特長……就在于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張季鸞當年辦《大公報》是這樣辦,余紀忠辦《中國時報》也是如此。而且這兩家報紙不但都曾執報業之牛耳,有一言而動天下的影響力,更曾大賺其錢,經營上并不輸商人辦報。
但如果從張季鸞提出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義”來嚴格檢驗的話,余紀忠與張季鸞雖稱得上是報人,卻并非是完美的報人。
張季鸞雖然終身“人不隸黨”,但他與蔣介石在一九三○年代中期開始建立的關系,當時就曾被人批評他對蔣政權其實是“小罵大幫忙”,許多人對他的歷史評價也從未忽略這一點。
余紀忠跟蔣經國的關系,不但跟張季鸞與蔣介石的關系十分相像,而且他還做過國民黨的中常委,“中常委報人”這個身份,雖然讓他能同時論政又問政,但這個身份終究是報人之瑕,有損報人本色。
但即使是這樣不完美的報人,放眼臺灣當今報業,也是百中無一,求之而不可得。
張季鸞的“四不主義”,曾經是臺灣報業追求的最高價值,報紙負責人對這個最高價值,雖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然而現在的報業負責人,卻是黨、賣、私、盲四者俱全,“四不主義”早已被“四全主義”取而代之。
而且,報紙的“文人論政機關”角色日益退化,早已蛻變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實業機關”。以前,“好的報紙”、“好的新聞”(good journalism)就等于是“好的生意”(good business),但現在好報紙、好新聞卻成了壞生意的代名詞。
臺灣報紙何以會變質、退化至此?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報紙與讀者的角色錯置。以前,報紙與讀者的關系是“傳媒領導大眾”(the press lead the public),但現在卻是“大眾領導傳媒”(the public lead the press)。過去傳媒決定要提供什么新聞給讀者,判斷的標準是“什么新聞你需要知道”(What news you need to know),但現在的標準卻是“什么新聞你喜歡知道”(What news you like to know)。
尤其是自香港“壹傳媒”集團進駐臺灣后,臺灣報紙這樣的質變趨勢,更像大江東流一樣,擋也擋不住。
也許有人不喜歡“壹傳媒”,但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壹傳媒”確實在短短幾年內就改寫了半個多世紀的臺灣新聞史,不但改變了傳媒的市場版圖,更重要的是改變了“新聞的定義”。
在“壹傳媒”進入臺灣之前,屬于隱私權范圍內的八卦、緋聞、丑聞,并不是不曾在臺灣傳媒上出現過,在兩大報主宰臺灣報業的時代,《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也曾經多年以爭相報道極盡膻色腥能事的犯罪新聞作為競爭的手段。但依據臺灣傳統對新聞的定義,類似今天這樣的“蘋果化新聞”,不但構不成重要新聞,更上不了報紙的頭版,遑論是頭版頭條。
現在只要“壹傳媒”一爆料,臺灣大小傳媒無不紛紛跟進,而且無一不是以重要新聞處理,“壹傳媒”儼然成了新聞通訊社,成了其他傳媒的供稿中心,也成了引領新聞風潮的龍頭老大。“蘋果潮”像洪水一樣淹沒了每一間新聞辦公室,每一份報紙聞起來都帶有一點蘋果味。
當所有的傳媒都以“壹傳媒”對新聞的定義作為新聞的定義時,文人辦報、文人論政的傳統當然就戛然而止,所謂的報人角色當然也就不復可見。
張季鸞與余紀忠當年是因為《大公報》與《中國時報》的言論影響力,才逼得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蔣經國不得不買他們的賬,不得不對他們以國士之禮待之,甚至不得不授以問政的權力與渠道,對他們進行“軟性的收編”。
文人辦報時代的報人與政治領導人的這種權力關系,雖然在骨子里仍是不對等的關系,但在形式上起碼還能維持平起平坐的表相。
抗戰前,蔣介石有次在南京“勵志社”大宴文武百官與駐外使節的晚宴中,奉“布履長衫的小老頭”張季鸞為主桌上賓,并且公開贊譽他“道德文章,名滿天下”,雖然是惺惺作態,但連“凱撒”也不敢小覷報人,由此可見一斑。現在報老板與政治領導人的關系,甚至與其他更等而下之的政治人物的關系,卻連形式上的平等都早已蕩然無存。
在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公民社會里,傳媒本來應該扮演“不受國家權力控制”也“不被市場規則左右”的主體性角色,但當文人辦報的傳統被商人辦報的現實所取代,當報老板不以報人自期,也不以追求影響力為辦報的最高價值,既向國家權力屈服又對市場規則妥協時,這樣的傳媒其實是背叛了它在公民社會中的角色。
舉國盡是政客,舉目不見報人,這是我們的政治現實,也是我們的傳媒現實。悲乎?悲矣!
我生也晚,無緣得識張季鸞,但對他的文章他的故事,卻從年輕時就略知一二,用流行語來說,我早就是他的隔代“粉絲”。
張季鸞與蔣介石一九三四年夏天在南京“勵志社”見面時,張是《大公報》總編輯,蔣是國民政府主席。“勵志社”的那場晚宴雖是“中國第一報人”與“中國凱撒”蜜月期關系的縮影,但在此之前多年,凱撒與報人之間的關系其實猶如寇讎。
在跟胡政之、吳鼎昌于一九二六年接辦《大公報》之前,張季鸞曾做過多年記者,而且一直是個不畏強權的記者。
一九一三年,袁世凱當總統,張季鸞在他工作的《民立報》上揭發袁世凱善后大借款的內幕,震動全國,但張季鸞與他的同事曹成甫當晚就被逮捕入獄。坐了三個月黑牢后,張季鸞因朋友營救而重獲自由,曹成甫卻已死于獄中。當時張季鸞僅僅二十五歲。
五年后,段祺瑞當國務總理,張季鸞又在他當總編輯的《中華新報》上,披露段祺瑞以膠濟鐵路當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內幕。段祺瑞一怒之下,不但查封了《中華新報》,也逮捕了張季鸞,把他關了半個多月后才釋放。
短短五年,兩度對抗國家最高當權者,兩度揭發政府濫權腐敗內幕,兩度被捕入獄,并曾一度面臨被袁世凱槍決的命運,張季鸞到底是怎樣的一個記者,可想而知。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誕生的《大公報》,就是張季鸞這種記者性格的投射。但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一九二六年,其實是中國新聞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當年四月,張作霖揮軍入京,立刻把他恨之入骨的《京報》老板邵飄萍逮捕。邵飄萍當時有“中國第一記者”之稱,辦報為文一向鐵肩辣手,軍閥,尤其是奉系軍閥,早欲去之而后快。張作霖以“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的羅織罪名,將他槍決。
當年八月,奉系軍閥張宗昌又逮捕了《社會日報》的老板林白水。林白水在邵飄萍被殺后,仍然在報上撰文痛斥奉系軍閥是洪水猛獸,張宗昌的智囊更被他形容是“終日懸掛于腿間的腎囊”。張宗昌氣急敗壞,效張大帥前例,也羅織了“通敵”的罪名,將林白水槍決。
但就在風聲鶴唳的這一年,《大公報》登上中國新聞的舞臺,而且一登臺就是炮火四射。
在創報短短一年內,張季鸞曾寫社評《跌霸》,痛罵獨霸一時的軍閥吳佩孚,“不特治軍經國,有舍我其誰之嘆;即談詩說易,亦覺并世無耦。困頓經年,略無修省,而傲狠乃過于昔日”,但“綜論吳氏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并力無之,但有氣耳”。
他也曾寫社評《嗚呼領袖欲之罪惡》痛斥汪精衛,“以庸才而抱野心,以細人而操大柄”,而且“好為人上”,“一切問題都以適合自己便宜為標準”,“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
對當時權傾一時的蔣介石,張季鸞的抨擊更是毫不留情。一九二七年在中共黨史里所謂的“四一二政變”中,蔣介石曾無情剿殺左派人士,事后張季鸞寫了一篇社評《黨禍》,形容當時的社會“乖戾之氣,充塞天壤;流血之禍,逼于南北”,他痛批蔣介石對共產黨“愛之則加諸膝,惡之則投諸淵”,“且取締則取締已耳,若滬若粵,皆殺機大開,是等于自養成共產黨而自殺之,無論事實上理由如何,道德上不能免其罪也”。
《黨禍》寫完七個月后,蔣介石與宋美齡舉行世紀婚禮隔天,張季鸞又寫社評《蔣介石之人生觀》,痛罵老蔣自稱“自今日結婚后,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是“淺陋無識之言”,他甚至用“兵士殉生,將帥談愛”、“累累河邊之骨,凄凄夢里之人”以及“人生不平,至此極矣”這樣的重話,來嘲諷蔣介石美化“革命與婚姻”的關系。
張季鸞罵吳、罵汪、罵蔣的社評,當時即轟動全國,今日讀之仍是痛快淋漓。臺灣現在寫社論的人早已百無禁忌,但與張季鸞的“三罵”相比,火候功力高低立判。“三罵”奠定了張季鸞的報人地位,《大公報》當然也靠“三罵”建立了它第一大報的影響力。
任何當凱撒的人,都想拉攏甚至收編最有影響力的第一大報,蔣介石當然不例外。當時傳說他在辦公室、官邸、餐廳各放一份《大公報》,走到哪看到哪。而且他發通電給全國報館時,開頭第一句也必定是“大公報轉全國各報館鈞鑒”,儼然已視《大公報》為報業龍頭。至于約見張季鸞“垂詢”國事這種“禮賢下士”的動作,蔣介石更是頻繁為之,南京“勵志社”那場晚宴,更曾被人以“韓信拜相,全軍皆驚”這樣的比喻來夸張形容。
蔣介石以國士之禮待之,當然會影響到張季鸞一向銳利的“反蔣”筆鋒。再加上他的對日政策主張跟蔣介石若合符節,因此不但《大公報》的社評常給人與政府桴鼓相應的印象,張季鸞也確實偶爾扮演過君王策士的角色。
但即使如此,張季鸞仍然很努力在維持他的獨立報人本色,特別是他對蔣介石處理共產黨與異議知識分子的做法不敢茍同,依然大力批判。
兩個較具代表性的例子是:
一九三○年代,在國民黨一片“剿共”聲中,張季鸞卻是最早就派記者到“紅區”采訪的報人。雖然當時的新聞檢查制度十分嚴酷,但《大公報》卻敢不聽黨意、不從流俗,從來不以“共匪”稱呼共產黨,而稱其為“共黨”、“共軍”。遠赴西北邊陲地區采訪的《大公報》記者,更在一系列的新聞報道中,贊美“紅軍紀律嚴明,百姓擁護”,徹底顛覆了國民黨宣傳機器所塑造的“共產黨是流寇土匪”的刻板印象。毛澤東曾經很感慨地對一位《大公報》記者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
蔣介石對《大公報》的“附匪”言論忍無可忍,有一天終于跟張季鸞面對面攤牌。蔣雖然氣得大發雷霆,但張卻不懼不驚,從頭到尾只是以不卑不亢的語氣,反復重申“事實就是如此”,答復言簡意賅,立場平和嚴正,十足報人風范。凱撒再霸,但又奈報人何!
第二個例子是一九三六年的“七君子事件”。張季鸞一向尊重知識分子,他在《大公報》開辟的專欄“星期論文”,曾經是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大本營,左中右各黨各派人士皆在其中寫稿。
因此當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等七人被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逮捕后,張季鸞的痛心不難想象。這七個人只不過是組織了一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了一篇《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呼吁各黨各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釋放政治犯以及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日政權而已,但國民政府卻羅織了一份罪行完全無中生有的起訴狀,企圖誣陷他們。
當時各家報紙對“七君子”案件都噤若寒蟬,舉國不聞異議之聲。但當張季鸞得知身陷牢獄的“七君子”寫了一份答辯狀,逐條逐項駁斥起訴書中各項羅織的罪狀后,他立即打電話給編輯部值班的同事,要求將答辯狀全文立即發排,隔日刊登,而且不必送審,責任由他自負。
以今觀昔,張季鸞當天的決定似乎平常至極,但在當時“國民黨任意捕人殺人的恐怖統治”政治氣氛中,舉國報人卻唯張季鸞一人有此勇氣。“七君子”日后全被釋放,雖有許多主客觀因素,但張季鸞和他的《大公報》能無愧于報人與媒體角色,卻絕對是關鍵因素之一。
由于《大公報》對共產黨與他們的“同路人”一向采取既不歧視也不丑化的立場,甚至常有“同情的了解”,因此共產黨領導人也一樣想拉攏收編《大公報》。蔣介石在南京“勵志社”奉張季鸞為上賓,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宴客時,也曾讓《大公報》記者高居首席。張季鸞病危時,蔣介石多次至醫院探訪,但在他的病榻前,也曾出現周恩來與國民政府衛生部長各坐一側相對無言的“和平”畫面。國共兩黨源出一門,由此亦可見一斑。
張季鸞曾對他的接班人王蕓生說過:“只要不碰蔣先生,任何人都可以罵。”這句話雖然有點老師父叫小徒弟附耳過來交代后事的味道,本來就不想“法傳六耳”,但等到王蕓生撰文轉述眾人皆知后,師徒間的這句私語卻成了張季鸞對蔣介石“小罵大幫忙”的注腳。
但相對來說,他對共產黨又何嘗不是如此?否則周恩來何以奉他為“報界宗師”?毛澤東又何以肯定他“功在國家”,甚至在一九五○年代末期黨內整肅《大公報》時,仍稱贊張季鸞“搖著鵝毛扇,到處作座上客,這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觀察形勢的方法,是當總編輯應該學習的”?
張季鸞為什么能優游于國共兩黨之間,跟兩黨領導人都能保持亦友亦敵的緊張關系?是為了兩邊押注買保險?是心中毫無定見而投機搖擺?都不是。他之所以如此,原因非常簡單: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他的“四不主義”其實就是自由主義的具體而微。他曾經形容自己和他的辦報伙伴:“我們這班人,本來自由主義色彩很濃厚的,人不隸黨,報不求人,獨立經營,久成習性”,“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
近年來研究《大公報》歷史的中國大陸學者,也有許多人認為“《大公報》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的一次實踐”,也是“西方新聞制度在中國的一次漫長旅行”,“雖然早期《大公報》三巨頭都是留日的學生,但他們在新聞理念和政治哲學方面,卻是實踐自由主義思想的”,“在中國報業史上,從來還沒有一份民間報紙亮出這么鮮明的旗幟”。
但張季鸞并不懂復雜的自由主義理論,他只是一個“簡明版的自由主義者”。在他的字典里,自由主義的定義很簡單:不黨、不私、不盲、不賣,不求權、不求利、不求名、不畏強權、不溺富貴,政治民主、言論自由、包容異己,如此而已。不論他當記者、寫社論、當報老板、延攬自由派知識分子寫專欄以及與政治人物打交道,他都是用行動在實踐這么簡單的一個信念。即使偶爾逾矩,跑到了自由主義的對面“表態”,但就像有位大陸學者所說:“他的態度是歷史的態度,也是現實的態度。”比方說,他在對日抗戰時的“國家中心論”主張,雖曾備受批評,更被共產黨列為他政治反動的證據,卻并不足以證明他背叛了自由主義。
更何況,國共兩黨一向視自由主義者“非我族類”,毛澤東更把自由主義者說成是“民主個人主義者”。張季鸞明知左右皆反自由主義,卻仍然高舉自由主義的大旗辦報,他的信念之強、勇氣之大甚至他的孤傲自負,都是不言可喻。
可惜的是,張季鸞在一九四一年才五十四歲就過世了。如果他能活得更長壽,活到國共內戰,活到江山易主以后,《大公報》的命運會有什么不同?他會不會像他的接班人王蕓生在一九四九年發表《大公報新生宣言》那樣,表態“向人民陣營來投降”?他會不會讓《大公報》名存實亡、茍延殘喘到一九六六年才以黯然赧然的結局收場?現實的歷史沒有給我們答案,但張季鸞的辦報歷史卻告訴了我們答案是什么。
也許就是因為對臺灣媒體的集體不為,或者對“張季鸞精神”如煙一般消失得無影無蹤,有些感慨甚至有些恐慌吧,所以我才轉向美國的媒體,想從美國新聞界的歷史與現實里,去尋找像張季鸞與《大公報》那樣的記者、那樣的報老板以及那樣的媒體,既是為了替我的沮喪挫折尋求慰藉,也是為了替我的虛無麻木尋找刺激。沒想到這個自私的動機,這段自我治療的旅程,最后卻寫成了一本書。
在《凱撒不愛我》這本書中,我寫了五十二位新聞人的故事,其中只有一篇是美國以外的故事。這些新聞人幾乎都是自由派,都曾有或仍有影響力,其中多數更是跟凱撒對抗多年、被凱撒恨之入骨。這些人的名字也許跟張季鸞跟你我有別,但他們的際遇與他們的故事,卻跟張季鸞跟你我并沒有太大的不同。他們能做那樣的新聞人,我們呢?難道只能感嘆“豈有豪情似舊時”?只能任憑“花開花落兩由之”?看完這些故事后,再問問我們自己吧。
這本書獻給余紀忠先生,書出之日我已重回他一手創辦的《中國時報》;也獻給《新新聞》每一位工作伙伴,十八年的革命感情永難忘懷;還要謝謝我兒子澤生,這本書是他一字一句敲打出來的,也記錄了我們父子一段知識性的親情互動。
最后一場決斗——法拉奇(Oriana Fallaci)
如果你問我誰是最會問問題的記者,我會毫不遲疑告訴你是法拉奇(Oriana Fallaci)。
米蘭?昆德拉說法拉奇的訪問已經不是對話,而是決斗。著名的斗牛士科爾多貝斯也形容她在訪問時像一頭憤怒的公牛,“她使用語言就像公牛使用牛角一樣”。
她訪問鄧小平時,第一個問題就問:“天安門上掛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第二個問題是:“中國人民把‘文革’的過錯都推給四人幫,但毛主席難道沒錯嗎?”
訪問阿拉法特時,她劈頭就問:“你現在幾歲?”阿拉法特說他不談私人問題,但法拉奇說:“我只不過問你的年齡而已,如果你連年齡都不愿告訴別人,為什么你要告訴世人你是巴解領導人?”
當阿拉法特抱怨西方媒體對他不公平時,法拉奇對他說: “這是你的戰爭,不是我們的。在你的戰爭中,你不能要求我們像你那樣反對猶太人。”
她訪問基辛格時,基辛格像鰻魚一樣滑溜,從不直接回答問題。法拉奇只好下重手問他:“你曾說尼克松不夠格當總統,現在你會覺得尷尬嗎?”“許多人說你眼里根本沒有尼克松,你關心的只是你自己。”由于法拉奇咄咄逼人,基辛格最后終于露出了真面目,形容他自己就像電影里的西部牛仔一樣,孤獨地騎在馬背上帶領著篷車隊穿村過城。
這篇訪問刊登后,基辛格飽受各方抨擊。他獨攬外交功勞,更讓尼克松氣得好幾天不接他電話。基辛格為化解危機, 只好指控法拉奇扭曲他的談話。但法拉奇豈是好惹的人,她發電報給基辛格,威脅要公布采訪錄音,并希望他不要像小丑一樣讓人恥笑。基辛格被嚇得只好三緘其口,并且在事后承認他一生做過的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訪問。
在訪問塞浦路斯總統馬卡里奧斯時,法拉奇對他說:“你讓我想起簡?奧斯汀講的一句話:一個聰明的女人絕對不能讓別人知道她有多聰明。”“但我不是女人啊!”“你不是, 但你太聰明了,聰明到想盡辦法要讓我搞不清楚你在想什么。”法拉奇說馬卡里奧斯當時氣得像一只弓起背的貓。
法拉奇為什么要把訪問弄成像決斗?因為在她的字典里沒有客觀這兩個字,她說客觀是種偽善,不存在也不該存在。她說當她在采訪時,她不是旁觀者,而是參與歷史的人。她形容自己就像是藏在歷史那棵大樹樹干里面的一條蟲,用她的眼她的耳她的腦,去看去傾聽去思考每一件她參與的歷史。她雖然是新聞記者,但更是一個歷史學家。
至于她為什么那么主觀,她的回答更直截了當:“如果我是一個畫家,我在替你畫像時,為什么我不能把你畫成我想要的樣子?”
“九一一事件”發生后,她打破十多年的沉默,寫了一本小書《憤怒與驕傲》,沒想到卻得罪了伊斯蘭的基本教義派, 揚言要像當年追殺拉什迪一樣追殺她。但罹癌已十幾年的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后已經放棄治療,早已視死如歸。更何況她年少時曾參加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游擊隊,在越南戰地跑過新聞,也曾在墨西哥采訪學運時三度中槍,死亡的威脅根本嚇不倒她。
她形容自己就像當年反法西斯的意大利學者薩爾維米尼一樣,雖然他聲嘶力竭警告世人,但因為他反法西斯反得太早,因此沒有人相信他。法拉奇說:“我病了,但西方世界比我病得更重。”她雖然已是風中之燭,但她仍在跟死神進行最后一場決斗。(作者按:二○○六年九月十七日,法拉奇病逝于家鄉佛羅倫薩。)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