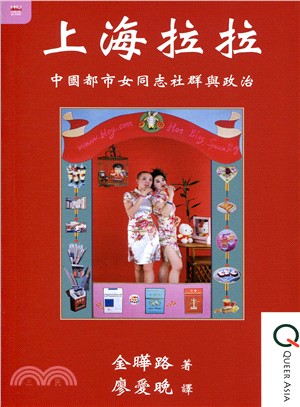商品簡介
本書結合了作者自身的酷兒經歷和堅實的研究成果,詳盡刻劃當今中國都市的女同志社群與政治的現狀,為關於同性關係、恐同、出櫃政治及性管治的全球探討和辯論作出了寶貴貢獻。
作者簡介
廖愛晚,自由譯者,廈門大學人類學碩士,從2008年起參與中國同志運動及性別研究翻譯工作,發表譯文逾三十萬字。
名人/編輯推薦
「本書交織着作者自身的酷兒紀事和來自二十五位拉拉的豐富民族誌資料,不但呈現了中國都市女同志社群及政治的最新面貌,也對關於同性關係、出櫃政治和恐同本質的國際議題作出了貢獻。」——江紹祺,香港大學
序
序——想起(上海女愛工作組)
今年3月有一次在香港與LuLu(金曄路)匆匆見面,想不到她竟然邀請我為她的學術著作中文版寫序,這難免一方面令我受寵若驚,而另一方面我又不禁覺得她實在夠膽大,敢讓我這種不善辭令的人寫點甚麼。因為我正值人生兵荒馬亂時期,所以遲遲無法下筆,也生怕自己寫得格格不入,想要推辭時,LuLu又寄了兩封電郵來,肯定又肯定地對我說「你的序對中文版很重要」,這樣的謬讚令我十分汗顏。
我時常說,在我參與同志運動的路上,最大的幸運是結識了許多有思想而又有力量的女權主義者,她們給了我很多對人、對平等的思考,而LuLu則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位,更可說是亦師亦友。我和LuLu從2005年結識至今,早已從普通網友變成為緊密的同志運動夥伴,她除了帶給我很多關於運動的思考之外,還與我談人生和理想,以及愛情(笑)。
與LuLu結識是因為她要為她的博士論文在上海進行田野研究,她把項目介紹發佈到我建立的華人拉拉網站「花開的地方」,於是我們開始了聯繫。第一次見面,她給我的印象是「謙虛大氣」之外,還有莫名的信任感。其中部分原因,也許來自拉拉身份的認同信任,以及我們彼此認識一些共同的朋友。
在我們認識後的幾年,LuLu一邊為她的研究花費精力,一邊給我個人、上海女愛工作組和志願者帶來越來越多的幫助、啟發。她每一次的上海之行,都給我們帶來大陸之外的同志訊息和書本,介紹我們認識香港的同志機構。
2007至2008年,上海女愛出版的第一本大陸拉拉口述歷史書《她們的愛在說:愛上女人的女人‧上海‧口述歷史(一)》,正是受到LuLu帶來香港拉拉口述歷史書本的影響。她擔任了我們口述歷史項目的培訓導師和顧問,幫助上海女愛完成第一個最重要的項目,而這本拉拉口述歷史也影響了中國各地的拉拉組織,紛紛開始籌劃各地的口述歷史計劃。
為了專注研究,LuLu經常往返香港、上海兩地。她每一次從香港回來,都會和我見面,而我也樂意拉上一些朋友、女愛的志願者們與她一起聚會,因為我知道上海的拉拉朋友們很希望親耳聽到來自香港的拉拉訊息。雖然當時已經有了互聯網,但在拉拉的社交生活中,能面對面聚會交流的機會,其實甚少。我們對於與大陸有着不同體制的香港和台灣兩地的拉拉如何生活,她們又在經歷着甚麼,相當感興趣,很想與LuLu談論和分享,從而多了解和自己一樣性取向的人的生活經驗。
記得當初做拉拉口述歷史書的時候,眼見從古至今,華人世界極少地整理和收集拉拉、拉拉社群、拉拉歷史和研究的資料,所以我十分期待更多的像LuLu一樣的研究者,帶着社群視角,擁有多元觀察,展開社群的研究,使以往的歷史得到重現,也使後來者(包括同性戀或異性戀者)了解和正視我們走過的路。
我要特別感謝和我一起參與了這個研究的人們,謝謝你們的信任。
祝賀LuLu《上海拉拉》中文版的出版。英文版出版後,就已經有好多朋友向我詢問中文版情況,可見我們是如此的期待。
想起(上海女愛工作組)
目次
序:想起(上海女愛工作組) ix
譯者序:廖愛晚 xi
前言 xiii
鳴謝(英文版) xvii
緒論:自我與社群的再連結 1
1.形成中的拉拉社群 17
2.公共論述 35
3.家門内的困局 51
4.周旋於公私之間 63
5.表面的微笑:公共正確政治 77
結論:看見我們當中的多樣性 91
主要報導人簡介 97
參考文獻 101
索引 111書摘/試閱
前言(節錄)
這是一段在十年前開始的旅程。
2005年,我在離開故鄉、移民香港二十多年後,第一次以研究者的身份回到上海,展開田野調查,在陌生的故鄉尋找新興的同志群體。
在田野中我想要找尋的群體,也同樣的既熟悉又陌生。在剛剛開始研究的時候,我參與香港同志社群已有一段時間,但對中國大陸的同志情況,除了零星的資料和對某些早期(1990年代末)運動者的記憶外,幾乎沒有任何概念。這個硏究從一個共同的身份認同出發,連接了我在兩個社會的同志社群經驗。
我做這個硏究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想從一個親密的切入點去了解我離開已久的故鄉上海。我成長於1970年代的上海,那時候「同志」的意思跟「人」沒有區別。無論性別、年齡、職業,每個人都叫「同志」,都是革命的同志。2000年後,「同志」在中國大陸有了新定義,它代表了一個新興的、去污名化的驕傲群體,廣義為英文的LGBTQ,但内部的多元化卻不是LGBTQ可以包羅的。它的成員在不斷增加,邊界也在不斷延伸。
當離開已久的故鄉變成田野,可以是一次充滿驚喜的「尋根」旅程,用好奇的眼光看尋常的事物,用耐心的耳朵聆聽本來難於理解的人情常規。褪色的浪漫故鄉回憶轉化為充實的田野知識,有了1970年代的回憶,我更清晰地看到改革開放後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上世紀末開始,中國大陸的同志運動高速發展,在無法正式登記成立組織的政治環境下,於不少大小城市中都成立了半地下的同志小組,同志網站更是多不勝數。對比香港社會的情況,中國大陸的同志運動者面對着更直接和嚴重的政治打壓。我參與了不少中國大陸同志社群活動,認識到同志運動者如何在多變的政治環境下組織活動和建立社群。面對時刻存在的來自國家社會控制體系的威脅和打壓,中國大陸的同志運動者更需要採取靈活的組織策略,永遠要準備應變的計劃,也需要非常熟悉有關法規和公民權利。
這也反映在上海拉拉派對的組織形式上。我剛到上海做研究的時候,拉拉派對的「遊牧」形式讓我感到非常好奇。派對不是在固定的場所,而是跟着組織者到處「跑」,比如2005年左右曾經有一個叫「蝴蝶」的拉拉派對,每隔一段時間我回到上海,「蝴蝶」又飛到了不同的酒吧舉辦。儘管上海拉拉派對這種沒有固定地點的「包場」形式多出於經濟原因,但它的「遊牧性」和整體同志運動的游擊形態,都凸顯了社會的多變和靈活組織策略的重要性。
面對不可預計、時刻存在的政治干預,中國同志運動者除了需要熟悉法制和權利來保護自己外,還很需要一種面對強權時無畏的幽默感。很多同志活動都會有便衣警察在場監視,而組織者不僅能與警察和平共處,甚至還會對此加以調侃。一個拉拉朋友告訴我,於2009年北京酷兒影展的開幕典禮上,組織者就笑着表示,希望在場的便衣警察也能夠欣賞接下來放映的酷兒電影。
通過研究,我見證了中國大陸同志運動的興起、在困難重重的社會環境下日漸壯大的同志隊伍、年輕熱情的新組織者的不斷加人、面對威脅不畏懼的冷靜和幽默等;作為一個研究者,同時又是同志社群的參與者,這一切令我深受感動。近年,兩地同志運動者的交流越來越密切,在香港的同志遊行,我和中國大陸的代表肩並肩地在銅鑼灣邁步;在北京酷兒影展,來自香港的同志組織者、導演和學者一起坐在狹小的放映室;在中國某中小城市的拉拉培訓營,香港、台灣、海外的組織者和大陸的女同志一起分享經驗,互相勉勵。
這個從2005年開始的研究,讓我完
2014年3月,我在校對翻譯稿的時候,收到一個驚喜的消息。Shanghai Lalas被美國Lambda Literary Awards選為LGBT Studies組別的決賽競選著作之一,這個消息增加了我推出中文版的決心,希望中文讀者和中國的拉拉社群可以讀到這本書,讓我聽到她們的回饋。
金曄路
緒論:自我與社群的再連結
作為一個剛剛聽說「拉拉」一詞的無知新來者,我不曾期待和一群我才認識了幾個小時的拉拉朋友參加一個如此私密的派對。我後來獲知派對上的那對情侶雙方都處於異性戀婚姻當中。回想起來,那個派對為我指明了後來研究中的幾個重要主題:本地拉拉社群的形成、異性戀家庭與婚姻體制、成形中的同志家庭與婚姻,以及拉拉們面對家庭、婚姻乃至社會的日常策略。
我的研究從2005年開始,是一項對上海拉拉的民族誌調査,也是最早對興起中的中國同志政治和社群的參與式研究之一。其時正逢孤立的同志個體被聯結起來,形成同志社群,而先前飽受污名的性主體,也在通過創造新的身份認同來自我賦權。「拉拉」成為了有着同性情慾及其他非正統性與性別身份的女性的一種集體認同,而「同志」作為一個源自社會主義中國、而後在香港被重新定義的稱呼,回歸祖地,煥然一新,成為這個之前數十載都被剝奪了社會能見度的群體的公共身份。非正統的性與性別群體新近獲得的這些公共身份,創造出了新的自我與主體性;對自我的新理解,令這些群體對生活產生新渴望,同時也給異性戀體制的現存規範帶來挑戰。改革開放後的中國(1979年以後),同志社群的形成,凸顯出自我肯定的同志主體,和她/他們在家庭中遭遇的否定之間的分歧,這一切促使我思考中國拉拉所面臨的嶄新挑戰。同志社群的出現,令關於主體性的新話語、親密關係的新形式,以及建立社交網絡的新途徑,都成為可能。新的機遇和新的管控模式並存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鑒於這些新出現的資源與限制,拉拉們的生活在哪些方面異於以往?她們將如何處理新的同志身份?尤其是,將如何應對婚姻的壓力?
本書旨在探討擁有拉拉認同的女性,如何調解新的生活渴望和強加於她們身上的異性戀規條之間的矛盾。具體而言,當她們一再表示家庭和婚姻是日常生活中壓力的主要來源,她們如何在新近獲得的自我理解和異性戀規範的張力之間尋求平衡?我嘗試通過這個研究來回答以下問題:現存的關於同性戀及同志的公共話語,對拉拉們的日常存在有何影響?公共話語如何滲透並控制中國新出現的同志主體和同志政治?尤其是,這一同志主體如何影響拉拉們與否定她們性自主權及性主體性的文化所做的抗爭?換言之,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環境中,將會產生怎樣的同志政治?對於個別的拉拉而言,拉拉社群的出現給她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她們應對異性戀體制的策略帶來了何種影響?同志親密關係的新形式,例如合作婚姻(或稱形式婚姻),2如何導致對異性戀正統主義(Warner1991)、主流規則,重新作出批判性的審視,並為家庭和婚姻開啓了新的想像?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為中國這些鮮活的親密關係實踐和同志運動,設想一種怎樣的未來?
勾勒「中國同志」
改革開放後,在中國無數的社會變遷中,「同志」作為一種重獲新生的身份,是與變革緊密相連的關注焦點。它被放在跨國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酷兒運動及政治的語境中來理解,也常被放在改革開放後中國新公民身份的建構這一語境中來討論。作為一種新近引入的性主體,「中國同志」有着遭受社會及政治污名的歷史,並且仍是各方人士在公共領域中爭奪話語的戰場。本土同志社群、公眾、專家、學者乃至官方都熱衷於為「同志」賦予各種定義。「同志」的内涵仍然虛位以待。
於2005年,首個草根拉拉組織於上海成立,來自全國各地的女同志小組第一次在北京聚首,中國首本拉拉雜誌《les+》(www.lesplus.org)誕生,這一切都發生在短短一年内,而過去十年是中國同志社群形成的重要時期。特別是近五年,中國各地的本土拉拉社群有了迅速的發展。
通訊技術在連結個體和形成社群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1990年代末期,互聯網開始在中國普及,論壇上討論同性戀的話題只是以圈内人通用的詞彙進行。進入2000年後,獨立的拉拉網站開始嶄露頭角,上海當地拉拉當中最受歡迎的三個網站:阿拉島、深秋小屋、花開的地方(簡稱「花開」),均成立於2000年伊始。截至2005年,花開已經擁有超過四萬名註冊用戶。互聯網也加速了華人社會之間同志文化的交流,而中、港、台三地因為在語言、地域及文化上具親緣性,所以後兩者的女同志文化及運動,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拉拉的重要參考。而隨着區域活動的開展,訊息、文本和人際的交流得到進一步加強。例如,拉拉營就是中港台三地女同志社群進行對話的重要平台。這是每年一次在中國舉辦的訓練營活動,參加者是來自中國、香港、澳門、台灣及海外說華語的女同志組織者。從2007年開始,拉拉營把上述區域的本土拉拉社群組織者匯聚在中國,現已成為中國拉拉組織的溫床,同時也是中國同志政治的一個重要話語生產場域。
對普羅大眾而言,近年常見的「同志」一詞,指的是「同性戀者」。對年輕一代來說,這個詞已經完全脫離昔日的社會主義「同志」意涵,但公共論述中還是較多使用「同性戀」一詞。在中國大陸的學術界,「同性戀」比「同志」使用更為廣泛。因此,在日常用法上,「同志」幾乎就是「同性戀」的同義詞。在同志社群内部,正在努力地將這一概念擴展到指代同性戀、雙性戀、無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等多種身份,但公共論述中「同性戀」的用法仍佔主導地位,這兩個詞的混用也很常見。
同性戀,尤其是男同性戀,近年來吸引了大量的公眾關注。在經濟改革的年代,在中國對於性和私人生活的態度不斷變化的大背景中,公眾對同性戀的理解既受制於學術研究的不斷修正和辯論,同時也受到流行文化和曰常交流的影響。國營書店出售同性戀相關的書籍,官方媒體進行同性戀社會接受度的調査。3時至今日,媒體報導的增加、黃金時段電視節目中同性戀者的現身、互聯網論壇上關於同性戀的熱烈討論,以及更加晚近的耽美(BL)漫畫和同志小說在微博上和青年中的流行,都說明了公眾對於這個過去被噤聲的題材充滿好奇。
公眾對同性戀的興趣,是在最近幾十年社會控制方式發生變化的大背景中出現的。改革開放後,個人在空間和社會階級的流動性大為增加。從1990年代開始,個人在地理上的移動性導致都市同志次文化在中國大城市中出現。此外,勞動力市場的開放令國家通過單位(中央分配工作系統)來直接控制人們私生活的做法式微。
1.「拉拉」在過去十年成為了一個被廣泛使用的詞彙,最早使用的時間可以追溯至2000年初。這是從台灣人稱呼「女同性戀」的本土詞彙改造而來。在台灣先是出現「拉子」,是「lesbian」一詞開頭「les」的音譯。中國把這個詞借用和進一步本土化之後,「拉拉」就成為了最廣泛的用法。「拉拉」是中國擁有同性情慾的女性的一種社群身份,經常和「同志」一詞混用,後者是更早出現在香港的一種身份,其完整的或說區分性別的稱呼有「女同」(女同志)和「男同」(男同志);「拉拉」還和「les」混用,後者是「lesbian」的簡稱或非正式用法。不同的身份名稱有着語境的差異,「拉拉」和「les」用於非正式的、日常的、女同志專屬的語境中;而「同志」則用在更正式和政治化的場合,以強調社群的團結。所有這些身份在中國各地的社群當中,都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應用。在本書中,我使用「拉拉」來指女同性戀、雙性戀以及有跨性別認同的女性,「同志」則來指中國的整個LGBTQ社群。而在不特指任何一種具體的文化及地理脈絡的時候,我使用「女同志」和「男同志」。
2.形式婚姻(簡稱形婚,或合作婚姻)是一個拉拉和一個男同志之間自行安排的婚姻,進行形婚是為了應對家庭強加給雙方的婚姻壓力。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