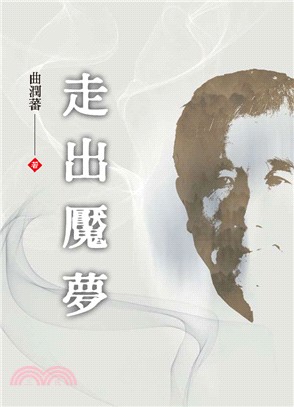再享89折,單本省下36元
商品簡介
本書作者幼年時居於山東老家,家裡慘遭共產黨土地革命的迫害,他的二婆婆、婆婆先後被活生生地打死,母親備受屈辱與折磨,歷經艱險才帶著他和妹妹逃出,與父親重逢,輾轉逃難到台灣。雖然作者在台灣定居後,一路求學都有很好的表現,而後負笈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在事業上更是有著傑出的成就,然而幼年時家族慘遭共產黨迫害的記憶,二婆婆、婆婆和母親的悲慘遭遇,不但是母親一輩子無法走出的夢魘,也是作者一生揮之不去的陰影。2012年退休後,他專心寫作,將這段纏繞於心六十多年的血淚史記於筆下,祭告二婆婆、婆婆和母親在天之靈,陰霾散去後,或終有走出魘夢的一天!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專文推薦】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
童元方(東海大學外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張系國(知名作家、匹茲堡大學教授)
〔序一〕
走不出來的夢魘
◆陳永發 中央研究院院士
好書先睹為快。封德屏女士以為我研究中共歷史,讓我先讀了曲潤蕃先生的《走出魘夢》。雖然有幸先睹,但再次面對中共土地革命的殘酷無情和血腥暴力,仍讓我久久難以釋懷。尤其想到當年毛澤東把地主階級說成十惡不赦,是阻礙中國進步的罪魁禍首,號召農民起來打倒,重新分配其土地和財產。但是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時,農民在單純化到只剩下工農階級和官僚階層的新中國,不僅沒有集體翻身致富,反而成為國家據以汲取工業建設所需人力和資金的主要來源,像歐洲中古時代的農奴一樣,仍身處於社會底層,連亞、非、拉三洲落後國家的窮困農民,相比之下,也不會自慚形穢;到一九八○年代,鄧小平告別毛澤東的階級革命後,他們更成為中共資本主義補課的廉價勞工主要來源,到本世紀之初,他們竟然再次像中古農奴一樣,成為官府和資本家圈地的對象,一度被大量驅離農村,擁入歧視他們的城市,以打工糊口維生。中共這趟土地革命,想起來,真夠諷刺。
一九五○年代,毛澤東號召階級鬥爭,曾動員作家和其他文藝工作人士,以「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手法,描寫地主階級的罪惡,所以現在三十歲以上七十歲以下、吃毛澤東奶水長大的中國大陸人民,幾乎無人不知,四川大邑有位大地主,叫劉文彩,田連阡陌,過極其奢華腐化的生活,好吃人乳,家裡特別豢養女人餵他奶水,收起租來,大斗進,且百般挑剔,尤其不容滯納,稍有不懌,便要狗腿子拳打腳踢,甚至私設水牢,有如冥府地獄再現。不過有位筆名笑蜀的四川知識分子,在毛澤東死後,告訴我們這些壓迫和剝削,全是極度誇張或鄉壁虛構出來的宣傳。然而就是防止這個劉文彩所象徵的地主階級死灰復燃,竟然鼓動了禍及至少一億人口的文化大革命,在更早的土地革命期間,中共已經以類似的宣傳,號召千百萬農民起來推倒地主階級這座據說壓在他們身上的大山,殺、關、管了約兩百萬地主,並將其子女家屬打入戶籍另冊,成為任人隨時可以斥責和辱罵的政治賤民。
曲潤蕃不研究歷史,儘管在電機專業已卓有聲譽,但從山東原鄉到台灣新家的記憶,卻像夢魘一樣,總不時壓迫大腦。囓蝕其心靈深處的不是逃難途中的飢餓、疲累、冷熱、風霜、病痛,而是土地革命帶來的創痛、驚懼、恐慌和癱瘓感。曲潤蕃出身於已開始沒落的地主家庭,父親知道自食其力,對前來成立農村政權的中共抗日游擊隊頗有好感,享受了短暫安定的生活。但是一九四六年中共掀起土地革命,不僅地主本人遭到暴力鬥爭,連其家庭成員的老弱婦孺,也都被掃地出門。曲潤蕃六、七歲,便隨著養育他的兩個婆婆和母親四處流浪,每天目睹長輩被綑綁、鬥爭、辱罵、吊打,而他也只能靠乞討施捨,為活著而活著。他父親這個原已接受中共統治的地主之子,在土地革命的逼迫下,終於走上反共逃難的不歸之路,千幸萬苦從膠東農村逃到青島海港,再避秦至海南,最後在台灣苗栗安家落戶。曲潤蕃母親是傳統型的賢妻良母,吃盡苦頭,好不容易全家終於生活安定,兒子進入大學,卻因為擺脫不了土地革命時為照顧待哺子女被迫改嫁的心理創傷,走上自殺絕路。曲潤蕃深受刺激,懷念深受傳統道德浸潤的母親,認為寫下他和媽媽共同經歷的土地革命和萬里漂泊,可以幫他擺脫自己的夢魘,所以決定提早退休,提筆回憶成長過程。
文學評論大家王鼎鈞說,五十年代的台灣號稱反共,卻始終不見感動人心的反共文學。年輕時候在美國讀書,讀過一些中國大陸作家的作品,也訝異中國大陸在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之後,何以不曾產生反映時代的優秀創作。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是當時最受中共推崇的兩本關於土地革命的小說,時間太久,依稀只記得其中人物都像戴著臉譜一樣,刻板乏味。丁玲筆下的人物,除富農女兒的黑妞以外,其他人早就忘光;周立波小說中的主人翁,更是一點都記不得。後來聽史學界的大陸朋友說明,才知道這個周立波就是毛澤東時代有文藝沙皇之稱周揚的弟弟,他小說中的地主現在證明都不是真正的地主,只是比較富裕的農民而已。我讀書不多,也想不出中國大陸關於中共的土地革命,到底另外出過什麼更好的作品。曲潤蕃無意批判中共,也不想對反共文學有所貢獻,他只是被土地革命的噩夢壓得透不過氣來,想不出在以文字捕捉令其有椎心之痛的經歷以外,尚有什麼其他禳解之道,於是凝視全家被連根拔起以及其後顛沛流離的記憶,寫成這本小書。他的文字乾淨俐落,無半點反共的陳腔濫調,不愧為電機系散文名家陳之藩的入室弟子。倘若王鼎鈞有機會看到本書,我想他會同意我的判斷,這是見證中共土地革命極好的寫實文學。是為序。
〔序二〕
乍見翻疑夢
◆童元方 東海大學外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曲潤蕃是這本《走出魘夢》的作者,他是先夫陳之藩先生在美國休士頓大學執教時的得意門生。多年前我在波士頓見到他時,他已是惠普公司實驗室的傑出工程師。陳先生說到潤蕃時,除了誇他聰明之外,對他沒有完全專注於研究工作,總透著點遺憾,認為他的原創能力遠超乎他在惠普的成就。我總笑他說幹嘛非要人人都去做研究不可。後來我跟陳先生在賭城結婚,他竟做了老師的伴郎。我們去加州看他們夫婦時,曾鬧著一起包山東大水餃來吃,哪知他包得又快又好,一人包辦了。
陳先生過世不久,潤蕃說他打算要退休了,因為有一本書要寫,這書若寫了,陳先生會非常高興。我說,「那你趕快寫罷。」雖然我完全不知道他要寫的是怎麼樣的一本書。後來我離港返台,行色匆匆,沒有來得及告訴潤蕃,兩年後突然接到他打到東海大學的電話,才知他回台探視弟妹,又打聽到我已離港,於是返美前寄了新寫的書稿給我。
沒想到這書稿拿起來就放不下了,憋著一口氣一直看到天亮。認識潤蕃少說也有三十年了,但怎麼都想像不到幾十年來他心中竟埋藏著不忍回想的過去,也許陳先生略知一二,但從未轉述過他的心事。所以我讀此書,是在驚訝裡開始,在震撼中結束。
潤蕃開宗明義說這本書寫的是三個女人的故事,這三個女人是他的二婆婆、婆婆與媽媽。二婆婆是潤蕃爺爺的二嫂,與婆婆二人在中共土地革命清算鬥爭時先後被活生生地打死。第一人稱的敘述回到他的童年,從第三章開始到全書結束,則聚焦在第三個女人,也就是潤蕃母親的一生。這三個女人的故事纏繞在潤蕃的靈魂深處,糾結在他的腦海。從大陸到台灣,再從台灣到美國,如影隨形,成一永遠醒不過來的夢魘。這個夢魘是他個人的回憶錄,而在挖掘回憶的過程中,他重建一幕幕令人腸斷的場景。
在二婆婆、婆婆死於非命之後,潤蕃從他的老家山東牟平縣城南四十里的韓家夼,寫到投奔的煙台,再到搭船去的青島,暫留的靈山島,最後在大風大雨中到了基隆。在這十二章的敘述裡,潤蕃的筆彷彿浸著淚,百般憐惜地看著他的母親在倉惶中對付排山倒海而來的難題。因為罩著一層回憶的薄霧,哀傷的調子有了淡淡的朦朧;或者是不堪回首的細節,或者是莽莽歲月的淘洗,敘事上偶爾顯出斷裂的痕跡。但我在閱讀的過程中,總是因意想不到的轉折而膽戰心驚。身為女子,設身處地對照前代女性的處境,風起雲湧,很難不興感慨,許多情節於我甚至是痛徹心扉。第一件事是生於一九二一年的潤蕃母親,纏纏放放了幾年腳才鬆開,而我母親生於一九一七年,居然逃過了裹腳的命運。不知半大腳的女子,是如何牽著稚齡的兒女在雲草蒼茫的鄉間跋山涉水地逃亡的。
第二件事關乎女童教育。潤蕃母親因是左撇子,說是誤信用左手在學校會挨打,嚇得不敢去上學,因而錯過了問學、讀書和寫字的機會,成為她終身的遺憾。雖說是誤信,我相信當年民智未開,絕對發生過這樣的事。之藩先生也是左撇子,但他用右手寫字,所以我並不知道。直到一次偶然坐在他左邊吃飯,老是撞到他,才注意到除了寫字,所有的事他都用左手。為了用右手寫字,不知挨了他父親多少打。我們對所謂不同的人,一律視為不正常,這是多麼粗暴啊!
第三件則更令人心痛了,是潤蕃平靜地寫下自己母親為了不讓子女遭活埋而情願被逼改嫁,後來還懷了別人的孩子。這麼曲折的段落,潤蕃只是幾筆白描。父母重逢時,母親挺著大肚子,父親不自覺地皺了眉頭;爺爺對母親說,孩子不一定要送人,曲家可以當自己的養;有熱心的老太太,為尚未出生的孩子找一個好人家;母親生下了孩子,是個兒子,但母親不要看;孩子送走時,潤蕃記得他紅彤彤、胖嘟嘟的小臉;幾十年來,他在心裡為他祈禱,祝他平安幸福。亂世人情,我們看到了無奈,也看到了寬容。〈不要看〉這一章,在我的心裡低迴往復許久。
全書共三十一章,第十五章記載了潤蕃一家經台灣到海南島暫住,第十六章則是從海南島再回到台灣。前一半的主軸是逃難,後一半就是在台重新建立一個家。
從海南島到台灣,是軍隊移防,不是撤退,在新的土地上適應新的環境,仍然艱苦,但調子已是拓荒,不再是逃生了。潤蕃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學,他寫苗栗,寫新竹,主要是民國四十年到五十年這一個十年,但依舊是亂離人生。不論悲欣,日子總是往下過,而在後面頂著房樑不倒的是母親,僅為全家吃飽就耗盡了心神。然而在潤蕃的教育上,她取法乎上,她的眼光成就了他的人生,而在從大陸到台灣,從流亡到定居的這一段旅程中,母親幾次面臨重大的抉擇。在生死存亡關頭,她永遠選擇與子女同在,任憑個人的屈辱變成了永恆的傷痛。在不可扭轉的命運底下,她畢竟沒有放過自己,為夢魘的網罟所糾纏,在一九六三年上吊身亡。我們也許可以說,這位母親所承受的,超過了一般人所能承受的,願這份情操能對人性的黑暗稍作救贖,只是以一弱女子而擔如此之重負,讀這位母親的故事,常因忍不住而潸然淚下。
想起陳先生吃飯特別快,而我特別慢,如果吃飯還講話,就更慢了。陳先生總是說:「不是你慢,是我快,你慢慢吃,別噎著了。」之後,總是再加一句:「除了曲潤蕃,沒人更快。」尋常言語,跟陳先生一起生活之後,忽然有了不同的意義──他吃得快,是曾經長期處在飢餓的狀態。這發現使我心痛得不得了,千山萬水,現在更明白了潤蕃所慘然經歷的,他母親所拚命維護的,只不過是人的基本生存權利而已。這也許是潤蕃在休士頓大學讀書時,與陳先生在師生之情外,另外建立起的一種特殊情分。
流亡的過程中,不論是在等船,還是到了港口卻不准上岸,任由風吹雨打的凌虐,潤蕃在書中一一呈現。我又想起在波士頓時,與陳先生在地鐵紅線的轉車大站──公園街站,換乘綠線。綠線有四條支線,但是在同一站頭等車。我問陳先生:「我們去哪裡?」他說:「看什麼車來再決定。如果E車先來,我們去美術館;如果C車先來,我們去看電影。」當時覺得真是浪漫極了,日後卻悟出是逃難的旅程在他身上烙下的傷痕,不管目的地,有車即上,抗戰時陳先生就是如此逃到大後方的。
二戰結束之後,有多少人來不及復員還鄉?有多少人還鄉之後,又再流亡?又有多少人一直在淪陷區,後來又落入中共的手裡?我母親在大陸懷的我,大著肚子在海上顛簸了多少日夜,才在南台灣把我生下。至於爸媽怎麼從南京到廣州,再在基隆下船,最後在屏東住了下來,所有的細節我都不知道,他們在原鄉的點滴,也許就是幾張黑白老照片,以及一口陳舊的樟木箱。
潤蕃比我只大八歲,但我一落地即屬太平世代,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我十五歲以前都在屏東:屏東醫院、勝利托兒所、中正國校、屏東女中。雖然學校集體打蛔蟲、治砂眼、清頭蝨,但生命都在穩定的狀態,不像潤蕃斷手、又得瘧疾。這些我都不知道,不知道就好像這些事都不曾存在過。我是在他的一字一句間,彷彿電影的鏡頭掃過,而親眼目睹了一個兒童幾次在生死線上的掙扎。所有的拼圖碎片加起來反映了一個大時代的悲劇,潤蕃所寫雖然只是其中一小塊圖片,但是多少補上了我出生前的一段歷史。
不知道為什麼,我比過去更常想起已在天上的父母,想起陳先生。我跟他們說話,複習他們人生裡的顛沛與流離。淚在眼眶裡蓄著,心中卻翻滾如浪花。深夜的東海校園,寂然無聲。昏黃的燈下,我想著他們。思念如流水,有時是溪澗,有時是江河,最後總化成大海。思念的潮水上漲,漫開,我的心越發溫柔起來。對此人間世,因為理解而更加悲憫。
潤蕃的母親沒有走出那個夢魘,我感同身受,在字裡行間靜靜陪著走過了這一段旅程。孝順的潤蕃亦在夢魘纏身下赴美留學,繼而成家立業。這血淚,六十多年後,一滴滴從他的心、他的筆滴下,凝結出這本書。潤蕃,你已為自己的手足以及下一代開展了可以自由生長的空間,在新世紀裡做著新的夢,而眼前之夢的甜美轉換了昔日的憂傷。你二婆婆的、婆婆的、母親的悽愴悲涼業已化成文字,留下了永遠的紀錄。他們在困境中的勇敢,因你的愛而寫入了家族史。江海一別,幾度山川,如今,我可以想見你每天清晨在鳥鳴聲中醒來,沐浴在加州的陽光裡。好風好水,陰影終究是散去了。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於東海
序
〔自序〕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曲潤蕃
這是我家的故事,二婆婆、婆婆和我的母親──三個女人的故事,一件發生在五、六十年前的悲劇,持續到現在,我還在滴血的痛傷。
自從來美國留學和定居後,每次我回台灣,都會順道去看望我在那裡的親戚和從前一起逃難的老鄰居,長輩們看到了我,他們的第一句話總是:「你媽真沒有福氣,沒能看到你今天!」早些年,我也總是忍不住在他們面前哭一場。隨著歲月的變遷,這些老人一個個地凋零了,我心想要是不寫下來,等他們都走了,就再也沒有人知道二婆婆、婆婆和我的母親了。
我開始寫是在二○○一年的四、五月,那時父親已是癌症末期,住在台北的振興醫院裡,我睡在他的病榻旁陪伴他。送走了父親後,我斷斷續續地寫,一晃眼就過了十年。二○一二年六月,我的第一個孫子出生,我興奮地把小孫子抱在懷裡,想到七十一年前我出生的時候,二婆婆和婆婆也一定同樣興奮地抱著我,我當下決定辭去我的工作,在家專心地把故事寫完。
在書寫的過程中,我的老師陳之藩教授,我在惠普實驗室的同事夏曉巒、李七根、李孟、潘益宗、郭惠沛、張彤、羅平諸鴻儒,我的老朋友柯乃南夫婦、盧澄乾和周世弘兩位先生,以及台灣中央大學的張立杰教授夫婦,看了我部分的手稿,給了我許多寶貴的建議和鼓勵,使我有了更多的決心和勇氣寫下去,我在這裡向他們致謝。
督促我最力的是我的小弟曲清蕃,他仔細閱讀了我的每一篇手稿,流了很多的眼淚,最後包辦了所有的校對和出版事宜。沒有他,這本書無法出版。想到母親去世的時候,他才一歲零兩個月,母親最放心不下的是他。母親過世後,父親沒有再娶,一個人把他撫養大。他大學畢業後,去美國修得博士學位,回台灣創業陪伴父親,現在有很好的事業。他真是我們家的驕傲,也該是母親最想看,而沒能看到的。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老伴袁英,她免除了我所有分擔家事的義務,給了我一個安靜舒適的環境,讓我定下心把這本書寫完。想想結婚四十多年來,她盡心盡力地幫我照顧我那個歷經滄桑破碎的家,沒有半句怨言。父親生前,他的許多朋友都說他有個好兒子,父親說,不對,他有個好媳婦,好兒子多得是,好媳婦才難得。這些年都虧了她,我們家才能擺脫貧困重新站了起來,對她我有無限的虧欠和感激。
在結束這篇序文之前,我要向在「土地革命」中被屠殺的幾百萬,以及不計其數被迫害的「地主」家屬們致哀,他們很少人能像我這麼幸運:我的母親,帶著我逃了出來;也要向當年與我父親併肩作戰的老兵叔叔伯伯們和他們的後人致敬,他們的犧牲保住了台灣,讓我活了下來。
故事寫完了,我要祭告我二婆婆、婆婆和我的母親。我想對她們說:算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不算了,我們又能怎麼樣呢?不要再折磨自己了!讓我們陰陽兩界的人都安息吧!尚饗。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日午夜
目次
序一 走不出來的夢魘╱陳永發
序二 乍見翻疑夢╱童元方
序三 歷史是不能磨滅的╱張系國
自序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家族親屬一覽表
1、二婆婆
2、婆婆
3、母親的早年
4、母親的選擇
5、四個黑點
6、堅持地活下去
7、父親的口信
8、與父親重逢
9、不要看
10、東鎮小樓
11、遼寧路難民所
12、河馬石
13、靈山島
14、萬民號
15、海南島
16、從海南島到台灣
17、五湖
18、銅鑼中興新村
19、我們的芳鄰
20、上銅鑼國民學校
21、領不到眷糧的日子
22、大弟的出生
23、山上成長的日子
24、升學考初中
25、多事的初中一年級
26、懷念在苗栗中學那段美好的日子
27、搬家
28、上新竹中學
29、八二三砲戰
30、考大學
31、走不出的魘夢
後記
編後記 至性真情,意到筆隨╱封德屏
書摘/試閱
四個黑點
母親在父親和四叔、五叔離開以後,坐立不安,天剛黑她就沉不住氣,抱著妹妹領著我跑到大街上去,看到從田裡回家的人就問,看到我父親和四叔、五叔沒有?怎麼這麼晚了還不見他們回來?其實那時候正是大部分的人從田裡回家的時刻,一點也不算晚。母親本來的目的是要向別人顯示,對於父親和四叔、五叔的逃走她完全不知情,可是這樣一來反而弄巧成拙,成了此地無銀三百兩。這令人起疑的問話,果然被一個回家的幹部聽了出來,他咬牙切齒地對母親罵道:「妳這個屄養的!妳把他們弟兄打發走了,還在這裡裝糊塗,妳等著吧!斬草一定會除根!」母親嚇得放下妹妹跑去跳井,我和妹妹跟著在後面哭叫,井邊有人在挑水,把母親攔了下來。
那天晚上還不到吃飯的時間,幾個幹部背著磨得雪亮的大刀片,來勢洶洶地跑到我們住的三爺家裡來,嚇得所有住在三爺家裡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吃得下晚飯。不知道幹部跟母親說了些什麼,母親認為她活不成了,在炕上翻來覆去地想了一夜,認為與其等著被吊起來活活地打死,或是被活埋了慢慢地憋死,不如先自我了斷,上吊死了來得痛快。一大早不知道母親從哪裡找到了一根繩子,她拿了繩子走到前院原先三爺家長工住的夥計屋裡去,找了一個凳子,踩在上面正要往樑上拋繩子,我跟了進來,看到母親要上吊,我大哭大叫抱住她的腿不放,三爺家的三姑在後院聽到了,忙跑過來把繩子從母親的手裡搶了過去。
斧頭落下來了,第二天早晨幹部來把母親帶了去。中午幹部要三姑來帶我去問話,在路上三姑跟我說:「等一下幹部問你爹走的時候你媽知道不知道,你要說你媽不知道。記住了嗎?」我說:「記住了!」其實三姑不告訴我,我也知道該怎麼回答。
跟三姑去到一間屋子裡,看到母親直挺地站在一條長凳子上,腳上沒穿鞋子,兩隻胳膊各被一根繩子從腋窩下吊到樑上,眼睛被布摀了起來。一個女幹部把我領到那條凳子的頭上,在母親的腳旁邊她蹲下來問我說:「你爹走的時候有沒有告訴你媽?」我哭著說:「沒有!」幹部教三姑把我帶回去。
我跟三姑回去後,不肯進到屋子裡去,站在大門口兩眼遠遠地盯著母親被吊起來的那間屋子,動也不肯動。太陽都快下山了,終於看到母親從那屋裡頭走了出來,我很高興地迎向前去拉著母親的手往家裡走,母親有些不耐煩,甩開了我的手說:「不能回家,要去找保。」我跟著母親挨家挨戶地求人作保,等找到了足夠的保數,告訴了幹部,早就到點燈的時候了。
往後的日子母親沒有活一天算一天的奢侈,只能是活一口氣算一口氣。家裡沒有了男人,她必須自己上山、下田來養活妹妹和我,以及被關起來的婆婆。時時都在提心吊膽,不知道什麼時候,幹部會想起來要我們的命。
我們家在村西北頭山上有塊包穀地,地已經被鬥走了,因為地上的包穀是我父親原先種的,所以幹部允許我們等地上的作物收成了以後,再把地交給他們。地頭上種了些南瓜,那年南瓜豐收,好像整個夏天我們都在吃南瓜。
秋天包穀成熟了以後,我跟隨母親去那塊地上摘包穀穗,她在一行行茂密的包穀叢間邊摘邊往前走,我緊跟隨在她的後頭幫她忙,忽然我抬起頭來,母親不見了,高大的包穀桿和葉子擋住了我四周的視線,我驚嚇得大哭大叫,以為母親又丟下我去上吊了。聽到母親在前頭高聲對我說:「我在這裡,你哭什麼?」有如抓住我的死神突然鬆了手,我又掉回了原地。我用胳臂擦擦淚,撥開前面的包穀葉子,跑上前去緊緊抱住母親的腿。
一個炎熱的下午母親帶了網包,要到地裡去背包穀稭回家燒火煮飯,她要我留在家裡陪妹妹,我怕她去上吊,不放心,不肯。上山的路上,她在前面走,我在後面哭哭啼啼地跟著。母親真被我煩透了,她快步走到前頭轉彎的路上,在一座小橋底下躲了起來。我繼續往前走,到了轉彎的路口看不到了母親,我又驚嚇地大哭大叫,這時候母親突然從橋底下鑽了出來,她怒氣沖沖地向我衝過來,我嚇得往回跑,她抓住我,把我按在地上,用網包使勁地抽打我。有個村裡的人路過,看了心酸,求母親不要再打我了。其實當時我一點也不感覺到痛,因為所有的心思全放在慶幸母親沒有丟下我。
幹部命令母親接替父親為參軍的家屬代耕。那時節主要的工作是翻地瓜蔓,一壟一壟的地瓜長了茂盛的地瓜蔓(藤),為了不讓地瓜蔓的鬚根長到土裡去分散了地瓜的養分,必須用一根長長的棍子把地瓜蔓從壟的左邊翻到右邊去,過一段時間再從壟的右邊翻回左邊來,反覆地左右翻動。這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母親既無力氣又無經驗,翻得不好常引起參軍家屬的不滿,遭到責難。要翻地瓜蔓的時候,母親帶著妹妹和我一起到田裡去。在大太陽底下晒,流很多汗,四歲不到的妹妹常常口渴要水喝,母親要我到地頭上摘片芋頭葉,拿到山澗底下去盛水給妹妹喝。芋頭葉不沾水,水包在裡頭很滑溜,一不小心就灑光了。經常我在山澗裡包得滿滿的一包水,等爬上來到了妹妹面前一滴也不剩了。遠水解不了近渴,我乾脆帶妹妹直接去山澗底下喝水。六歲不到的我背著妹妹一道梯田一道梯田地往山澗底下爬,又一道一道地爬上來,不時望望母親在翻地瓜蔓的側影,不讓她離開我的視線。
在婆婆遇害後,駐煙台李彌將軍的國軍部隊,和在牟平縣西北反抗共產黨的游擊隊,不時地從北邊下鄉來掃蕩。他們要來的時候,幹部不許我們留在村子裡,命令我們母子跟隨村裡的其他人一起往南邊的山上或村莊裡去躲避。在往南的大路上,母親一手抱著妹妹,一手拐個籃子,我跟在她旁邊,孤伶伶地跟隨著大隊往前走。人們像躲瘟似的遠遠地躲著我們。一次突然有人趁幹部不注意向我們飛快地跑過來,丟下一塊東西在母親的籃子裡,又飛快地跑回去。丟下的是塊白麵做的餅。在糧食極端缺乏的當時,這塊連他們自己老人和孩子都捨不得給吃的珍貴食品,竟然冒險送給了我們。我幫母親拉一拉籃子上蓋的那塊布,把餅藏在布底下,裝著若無其事,繼續跟著隊伍往前走。
有一天幹部要我們到南河對岸一個叫「峴上」的村莊去開會,那裡集合了附近幾個村莊被清算鬥爭過的地主,人數不少,擠滿了整個會場。一個共產黨上面派下來的年輕幹部走到台上來,向我們解釋新的罪行積點制度。他說,每家最多只能積到四個黑點,第五個黑點一到馬上就要處死。散會後可以到隔壁的辦公室去查看檔案,看看自己家目前有幾個黑點。母親不認識字,問幹部,幹部說我們已經有四個黑點,原因是我們家是地主,這是第一個黑點;我爺爺當過村長(只要在共產黨來之前當過村長,不管對村子做過多少貢獻,個人做過多少犧牲,一律劃為惡霸),是第二個黑點;我爺爺先逃走了,是第三個黑點;我父親和我四叔、五叔後來逃走了,是第四個黑點。母親向幹部提出抗議,認為我爺爺的逃走和我父親、四叔、五叔的逃走應該合在一起算一個黑點,不應該分開來算兩個黑點,那個年輕幹部不同意。
不等到第五個黑點的到來,我們村裡的幹部就迫不及待地要處置我們母子。傳出來的消息是他們有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活埋我們,洞已經挖好了;另一個是把母親配給村東頭的一個窮無賴,綽號叫「驢痀腿」的瘸子。他們可能內部有所爭議,所以遲遲沒有執行。
有一天晚上開會散會以後,一個人來找母親,對母親說在村東北角上有一個四十來歲叫魏某的鰥夫,他願意娶母親並收養妹妹和我,幹部已經同意了,如果母親願意,今天晚上就過去。母親說今天晚上不行,明天早晨再過去。
6、堅持地活下去
我年紀太小,不知道母親前一天夜裡有沒有合上眼,也無法理解母親當時的感受,不記得她是在怎樣的心情下提了一個小包袱,領了妹妹和我走完那一小段山坡路。我們到了魏家已經快中午了,魏某正在擀麵條。因為家鄉有「起腳的餃子,落腳的麵」的習俗,新媳婦進門要吃麵條。母親接過手把麵條擀好。麵還沒有來得及吃,就有幾個幹部說是來鬧洞房,哪裡有人大白天鬧洞房的,分明是來羞辱母親,他們講了許多不堪入耳的話,母親低著頭坐在那裡,一句話也沒有說,一根麵條也沒有吃。
共產黨把農民分為地主、富農、中農和貧農四個等級。魏家屬於中農,有幾畝地、一棟房子和一頭驢。房子建在山坡上一塊整平的台地上,坐北朝南一排,總共只有三個房間,中間進門的是廚房,廚房的兩旁是臥房,臥房的門通廚房。房子的前面有一長溜溜沒有圍牆的院子,院子的左邊是驢欄,栓那頭驢的地方,右邊種了一棵大槐樹,槐樹的右邊台階下是一條南北向,直通村南的斜坡路,我們就是從這條路走上來的。沿著房子的後頭是一條小路,往東能通到村東頭的大路。魏家只有兩個人,魏某和他的一個十來歲,腦筋有些遲鈍,名叫小喜子的女兒。
要堅持地活下去,嫁到魏家來總比被強迫配給「驢痀腿」好多了。我們母子不再有隨時死亡的威脅和恐懼,我不用再怕母親去自殺而時刻盯住她不放。我們更多了一層新的活動空間,可以拿到路行條去探望外婆和大姨。對外有了交通,有事情可以找親戚商量,不再感到那可怕的孤立和無援。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從此就可以太平無事。第一個警訊發生在過來魏家沒有多久的一天晚上,村裡開會,像往常一樣按階級成分不同分開來坐,幹部命令我們母子去跟地主們坐在一起,能再看到大爺和三爺家的親人自然很高興,但這分明是要告訴我們:我們母子的命運仍然跟過去脫不了關係。
全村的人都在瘋狂地搞清算鬥爭、窮人翻身。那些翻了身,分到了土地的窮人,很少人有心思去種地,因為那要流汗和出力,不如去拿地主現成的來得便捷。加上許多年輕人被迫參了軍,造成種地勞力的不足。更由於共產黨在打仗,戰費浩繁,稅捐極重,收刮走了不成比例的農民收成。這些原因給我們村子裡帶來了空前的饑荒。放眼所及大多數的家庭都在靠野菜(如嫩的蒲公英)、樹葉(如楊柳、榆樹的葉)和樹皮(如楊柳樹皮)充饑。野菜挖光了,連陳年晒黑了的乾地瓜蔓也拿出來用熱水泡開煮來吃。村裡有人餓死。
比較起來我們要好多了。魏某是個典型的勤奮農民,早已過了參軍的年齡,現在有了年輕的母親為他洗衣燒飯料理家務,他可以無後顧之憂,全心全力地去種他那幾畝地,加上人口簡單,因而有足夠的地瓜、地瓜乾和包穀可以讓我們吃飽。
為了節省過日子,母親也學著別人把野菜摻在包穀餅裡當飯吃。
在趕集的時候,魏某把自己種的,數量有限的花生和麥子馱在他那頭驢背上,到市場上賣了換成錢。回來的時候總會買點煮熟的豬頭肉或其他好吃、好用的小東西帶給我們。有一次他買了一件小男孩的舊上衣帶回來給我。母親堅決不讓我穿,和魏某爭吵了起來,因為她怕那是從死人身上剝下來的,死人的怨魂會附在衣服上不散。母親的顧慮看起來有些不近情理,事實上那時候有非常多冤死的大人和小孩,尤其是從前地主家的大人和小孩。
大人都說小喜子的腦筋有些遲鈍,但是當時才六歲的我一點也感覺不出來。或許由於她的智商不高所以沒有壞心眼,我覺得她的心地特別善良,跟她相處在一起是件很愉快的事。秋天過後,山上的闊葉樹如養柞蠶的柞木落了葉,窮人家的半大孩子們都要到山上去扒樹葉,用網包背回家堆積起來,作為爾後煮飯或燒炕的燃料。午飯後太陽晒乾了落葉上的露水,孩子們紛紛上山去扒樹葉,魏某擔心小喜子一個人去會受到壞男孩子的欺負,母親要我陪她一起去。山林裡遍地的紅葉,煞是美麗。我幫小喜子塞滿了網包後,我們到樹叢中去找鳥蛋,在野地裡追兔子,在山上玩夠了,才快樂地踩著夕陽循著下山的路回家,從遠處村裡飄來燃燒樹葉的陣陣炊煙,有一股醉人的芬芳。
母親迫不及待地要到了路行條,到下雨村去探望外婆。記得上一次到外婆家是在一年多以前小姨出嫁的時候,那時候外婆的日子還過得去。這次再看到外婆,她的情況糟透了,外公完全倒向了他姨太太的那一邊去,和外婆分開來吃飯,不再養活外婆了。外婆只好日夜紡紗,賺一點點包穀麵摻合著大部分的野菜來養活自己。我們能活著看到外婆,外婆自然很高興,但是她窮得連管我們一頓飯的能力都沒有。母親料想不到外婆竟會潦倒到這步田地,傷心透了,對外公表示了極度的不滿。
母親對外公的不滿還包括了她認為外公對我們母子的死活漠不關心。原因是由於外公沒有多少土地,加上要養活的人口又多,在下雨村這個比較大的村莊裡,很多人都比他富裕,因而在農民等級劃分的時候,他被評為中農。由於成分良好,他姨太太的一個女兒當上了下雨村「青婦會」的副會長,大小是個幹部。母親抱怨的是,在我們母子遭到極端迫害的時候,外公並沒有利用他的影響力,向我們伸出任何絲毫的援手。
其實外公沒有來營救我們,對我們來說不見得是件壞事情。與我們情況相似,在離我們村不遠的一個村莊裡就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有一家人的丈夫逃跑了,該村子裡的幹部要活埋他的太太和三個女兒。太太娘家的哥哥得到了消息,跑來向幹部求情,希望能讓他帶走一個女兒,幹部滿口答應,問他要哪個女兒,請他在屋裡等等,這就去帶他要的女兒來。幹部出了門,把門從外頭反鎖了起來,立即去把四個人都活埋了,才回來開門放他出去。以我們村裡的幹部之壞、之狠、之毒,同樣的事情很可能會發生在我們母子身上。
要過年了,母親忙著清潔屋子,準備過年的食物。她蒸了一籠一半白麵、一半包穀麵的年糕,做了一籠屜的豆腐,蒸了幾籠普通的餑餑,炸了一些用麵粉裹的肥肉,俗稱酥肉,燉了一盆包含豆腐、酥肉、大白菜和粉條在一起的隔年菜。過年期間能吃到餑餑和年糕配隔年菜,對於平時餐餐蔬菜雜糧,絕少油水的我們來說,有勝於滿漢全席。對了,還有包子,年三十的早晨一定吃包子。
正月裡天冷,風雪不斷,外公還是冒著大雪來女兒家作客。母親雖然心裡對外公不滿,仍然拿出最好的東西來款待他。一直處於半饑餓狀態下的外公能有酒有肉地飽餐一頓,非常的滿意,算是過了一個難得的好年。過完了年的春天,母親把外婆接過來住了一段時間。那時候小姨婆家的情況也不好,小姨丈被徵參軍去了,家裡窮,沒有什麼東西吃,大人和小孩都營養不良,小姨頭胎生下來的孩子沒活多久就夭折了。小姨在家跟她公婆處不好,常來探望外婆和母親。外婆和小姨的到來,帶給母親很多的關懷和慰藉,母親的日子好過得多了。最興奮的是我,老纏著小姨問東問西地不放。晚飯後小姨帶我坐在屋旁的大槐樹下,給我講故事,教我數數,我能輕易地從一數到一百,這讓我後來上學的算術成績比別的同學都好,因為大多數的同學剛開始只能從一數到十。
外婆和小姨回去後,我們的日子又靜了下來。母親和我有很多的時間單獨在一起,母親又禁不住一再重複地問我:「什麼時候才能再看到你爹?」因為母親相信傳說:小孩子能預知未來。我也一再重複地給母親同樣的回答:「過了年。」母親很失望,去年我告訴她過了年,怎麼今年又說過了年?到底要過幾個年?
母親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發生了,母親懷孕了。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