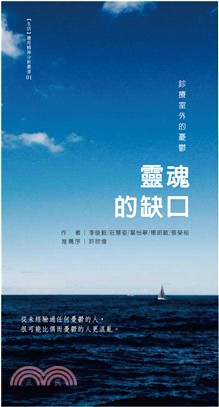定 價:NT$ 320 元
優惠價:90 折 288 元
領券後再享88折
領
團購優惠券A
8本以上且滿1500元
再享89折,單本省下32元
再享89折,單本省下32元
領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可得紅利積點:8 點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關鍵特色
★透過電影故事情節,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解析精神分析裡憂鬱的不同面貌。
★集結臺灣多位專業精神科醫師及臨床師,第一線的觀察,引領讀者貼近的精神醫學的奧秘。
內容說明
【高雄精神分析讀書會】創立多年,在資深精神分析臨床工作者帶領下,經由研讀經典文學作品、電影、戲劇以及各類表達藝術為媒介,從精神分析角度探索主要人物之人格特質,解讀/重讀潛藏在各類創作中之複雜而引人深思的情節;此外,也藉由真實臨床個案的分析,建構與釐清當今社會現象與個人內在世界之間的關係。
本書內容為讀書會授課講師以「憂鬱」為主題,擷取上課精要創作書寫,集結成輯。作者李俊毅醫師、莊慧姿心理師、葉怡寧醫師皆為高雄精神分析課程的領導人物,多年來他們致力於在地經營,活動內容多樣而精緻,本書是作者們長期相互激盪的結晶,再加上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元老蔡榮裕醫師和楊明敏醫師熱情助陣,匯聚成這本台灣本土精彩的應用精神分析文獻。
李俊毅援引重量級法國精神分析師André Green的「死亡母親」概念來闡釋「懼乳:傷心的奶水」和「寂寞鋼琴師」兩部電影中呈現的憂鬱;莊慧姿從電影「狗臉的歲月」的童言童語中探索兒童的憂鬱、分離、依附與救贖;葉怡寧以電影「藍色情挑」的致命創傷為起點來剖析憂鬱底層的愛恨交織與和解過程;楊明敏從康拉德的「吉姆爺」和梅爾維爾的「錄事巴托比」來比較憂鬱的溫度是炙熱或冰冷;蔡榮裕從精神分析角度重新檢視2015年德國之翼空難新聞所伴隨關於憂鬱症的社會心理氛圍。
★透過電影故事情節,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解析精神分析裡憂鬱的不同面貌。
★集結臺灣多位專業精神科醫師及臨床師,第一線的觀察,引領讀者貼近的精神醫學的奧秘。
內容說明
【高雄精神分析讀書會】創立多年,在資深精神分析臨床工作者帶領下,經由研讀經典文學作品、電影、戲劇以及各類表達藝術為媒介,從精神分析角度探索主要人物之人格特質,解讀/重讀潛藏在各類創作中之複雜而引人深思的情節;此外,也藉由真實臨床個案的分析,建構與釐清當今社會現象與個人內在世界之間的關係。
本書內容為讀書會授課講師以「憂鬱」為主題,擷取上課精要創作書寫,集結成輯。作者李俊毅醫師、莊慧姿心理師、葉怡寧醫師皆為高雄精神分析課程的領導人物,多年來他們致力於在地經營,活動內容多樣而精緻,本書是作者們長期相互激盪的結晶,再加上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元老蔡榮裕醫師和楊明敏醫師熱情助陣,匯聚成這本台灣本土精彩的應用精神分析文獻。
李俊毅援引重量級法國精神分析師André Green的「死亡母親」概念來闡釋「懼乳:傷心的奶水」和「寂寞鋼琴師」兩部電影中呈現的憂鬱;莊慧姿從電影「狗臉的歲月」的童言童語中探索兒童的憂鬱、分離、依附與救贖;葉怡寧以電影「藍色情挑」的致命創傷為起點來剖析憂鬱底層的愛恨交織與和解過程;楊明敏從康拉德的「吉姆爺」和梅爾維爾的「錄事巴托比」來比較憂鬱的溫度是炙熱或冰冷;蔡榮裕從精神分析角度重新檢視2015年德國之翼空難新聞所伴隨關於憂鬱症的社會心理氛圍。
作者簡介
作者 李俊毅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理論精神分析碩士
高雄長庚醫院精神科系/身心醫學科主治醫師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無境文化【生活】應用精神分析叢書策劃
作者 莊慧姿
高雄醫學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
臨床心理師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專職於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嬰幼兒心智健康諮商
作者 葉怡寧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理論精神分析碩士
天主教聖功醫院身心科主任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作者 楊明敏
法國第七大學精神病理與精神分析博士
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直屬精神分析師
台大精神部兼任主治醫師
作者 蔡榮裕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一般精神科醫師
松德院區《思想起》心理治療資深督導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 名譽理事長兼執行委員會委員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運用和推廣委員會主委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理論精神分析碩士
高雄長庚醫院精神科系/身心醫學科主治醫師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無境文化【生活】應用精神分析叢書策劃
作者 莊慧姿
高雄醫學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
臨床心理師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專職於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嬰幼兒心智健康諮商
作者 葉怡寧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理論精神分析碩士
天主教聖功醫院身心科主任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作者 楊明敏
法國第七大學精神病理與精神分析博士
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直屬精神分析師
台大精神部兼任主治醫師
作者 蔡榮裕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一般精神科醫師
松德院區《思想起》心理治療資深督導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 名譽理事長兼執行委員會委員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運用和推廣委員會主委
目次
【生活】應用精神分析系列叢書 / 李俊毅
【推薦序】用精神分析之心探觸憂鬱的溫度 / 許欣偉
死亡的母親,死亡的孩子 / 李俊毅
母親和童年憂鬱 / 莊慧姿
聆聽創傷變奏曲 / 葉怡寧
冰冷與炙熱的憂鬱 / 楊明敏
從副機長怎麼了 ,到憂鬱如何被談論 / 蔡榮裕
【推薦序】用精神分析之心探觸憂鬱的溫度 / 許欣偉
死亡的母親,死亡的孩子 / 李俊毅
母親和童年憂鬱 / 莊慧姿
聆聽創傷變奏曲 / 葉怡寧
冰冷與炙熱的憂鬱 / 楊明敏
從副機長怎麼了 ,到憂鬱如何被談論 / 蔡榮裕
書摘/試閱
死亡的母親,死亡的孩子
「…… a subject who never experiences any depression is probably more disturbed than someone who is occasionally depressed.」(從未經驗過任何憂鬱的人,很可能比偶而憂鬱的人更混亂)。這是甫於2012年離世的著名法國精神分析師André Green(1927~2012)講過的一句話,既戲謔又真實,只是這樣的說法恐怕徹底顛覆了一般民眾、甚至精神醫學界對於憂鬱普遍的認知。
憂鬱到底該單純歸類於情緒,還是該被視為一種疾病?這始終是個爭論,因為牽涉層面廣泛,不太可能會有共識;不過,目前精神醫學對於憂鬱的定義、見解、或是描述的字眼,過度強調「具體」與「可研究性」的「症狀」,反而讓憂鬱症與其他身體疾病不容易有效區隔開,精神科對於憂鬱症的診斷證據力也相對被弱化與模糊化,而如此過度醫療化(medicalization)的結果,導致人們對於憂鬱的誤解遠比了解還多。
本文並不在正本清源談論所謂的憂鬱,而是為了突顯憂鬱無所不在,因此藉由一般人知悉的電影與文學作品作為媒介,提供精神分析觀點下的另一種思考模式,讓憂鬱這個議題跳脫出狹隘的精神醫學論述,而這一切歸根究底,還是得從佛洛伊德一百年前發表的<哀悼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5)這篇經典文章談起。這相當精簡的十六頁文章奠定了精神分析看待憂鬱現象的理論基礎,文中有許多對於憂鬱個案深度心理層面的精彩描述,至今依然貼切適用,相較之下,當代臨床精神醫學對於憂鬱症的了解,除了蓬勃發展的生技產業帶出來的藥物治療、神經化學,乃至生物基因觀點外,並無太多新意,基本上是自囚於症狀治療的框架中。
佛洛伊德將哀悼定義為「對於失去所愛之人,或是失去某些抽象事物的尋常反應,譬如: 國家、自由、理想......等等」,這是每個人或早或晚必然得面對的歷程。他接著說:「雖然哀悼會讓生活態度偏離正軌,我們絕不會視之為病態,也不會轉介給醫療處置」,在這樣的架構中,哀悼其實是正常現象,除非後來進入「病態哀悼」狀態,才是我們熟知的憂鬱狀態。何謂「病態哀悼」?這又得回到前一年(1914年)佛洛伊德發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論自戀:一篇導論>,這篇著作中,佛洛伊德認為人一出生將所有性能量,稱為「原欲」,或是「利比多」(libido),聚積於自我(ego)身上,大量的利比多讓人們處在全能自大的心智狀態,稱為「原發性自戀」。利比多有如變形蟲偽足可以從自我向外延伸,依附在適當的客體(object)上,形成後來我們稱為「客體關係」的狀態;利比多也會因為遭致某些挫折而從客體撤回自我身上,我們稱為「次發性自戀」,這相當於人們處在失去重要的人事物,或是處在失落的狀態,這時若能適時讓撤離出來的利比多轉而依附到另一個替代客體的話,基本上是循著「常態哀悼」路徑發展,終至某種程度的穩定狀態;若自我因某些因素不願意放棄已然失去的客體,也就是不願意承認「失去客體」(object loss)這個事實,而強迫將撤回的利比多牢牢封鎖在自我身上,形成自戀膨脹的狀態,這即將依循「病態哀悼」路徑發展成「憂鬱」狀態,藉由這種方式,失去之客體的生命在精神層次上被拉長了;被遺棄的自我受到如此嚴重的創傷,人格結構也因此遭受嚴重的結構性扭曲,佛洛伊德非常漂亮的形容這個狀態:
…… (失去之)客體的陰影籠罩在自我身上,而後者從此被一個特別的代理者監督著,猶如它是一個客體 那個失去的客體。
(Freud, 1917, SE14, P249)
由此觀點而言,憂鬱根本上就是一種自戀狀態。至於人們面對失落時,會依循著常態哀悼路徑或是依循病態哀悼而進入憂鬱的路徑發展?佛洛伊德認為這與人格結構發展有關,也就是說,精神分析建構的憂鬱狀態,並非依據表面症狀,而是「超越」症狀的層次,進入了更深層的人格結構層次。更進一步說,與失去客體之間的關係,決定接下來是常態哀悼或是病態哀悼,如同佛洛伊德所言,憂鬱個案與失去客體之間的關係絕不單純,通常是愛恨交加,也就是愛與恨之間的衝突極為複雜難解。
既然人格結構才是決定個案未來是否因為失去客體而進入憂鬱狀態的關鍵,兒童時期的利比多發展必然是重要的,這時我們必須提到一位德國分析師亞伯拉罕(Karl Abraham, 1877-1925),對於佛洛伊德建構的憂鬱理論他提供許多寶貴的觀點,他認為憂鬱與利比多發展的口腔期有關,由此可見,憂鬱事實上是處在相當原始的心智狀態,這表示治療的困難度相對是高的,這也與多年的臨床經驗不謀而合;此外,亞伯拉罕也認為「成人的憂鬱很可能根源於童年時期的憂鬱」(Depression in adults probably has its roots in a basic depression of childhood.)
果真如此,孩子的憂鬱從何而來?我們先來看看André Green如何在診療室中的移情關係體驗到一個心死的母親如何影響她所照顧的孩子,從而建構一個「死亡母親」(The Dead Mother)的概念來解釋臨床上的憂鬱現象。他是這麼形容的:
死亡母親...... 是一個維持生命狀態的母親,但是在她所照顧的孩子眼中,形同是一種『心死』的狀態。
(André Green, 1983, p142)
這種憂鬱的主要特徵發生於客體(亦即母親)在場的情境中,而客體(母親)本身沉浸於悲慟情境。因為某種特殊原因,母親是處於憂鬱狀態的。英國精神分析師Gregorio Kohon在一次與André Green對談中提到:「死亡母親」實質上強調的並非「缺席」,而是在場的「缺席母親」,這是我們對於這個概念應該有的基本認識。
接下來,用兩部影片來說明所謂的「死亡母親」現象,第一部是秘魯導演克勞蒂亞·尤薩(Claudia Llosa)的作品「懼乳: 傷心的奶水」(The Milk of Sorrow, 2009),此片得到柏林影展金熊獎與柏林影展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也曾作為高雄電影館2011年「電影與精神分析影展」系列5:「關於創傷,說不出口的才算數」之開幕片。這部影片夠沈重,開頭就是一段空靈哀戚的吟唱:
⋯⋯
我向那些混蛋
跪地求饒
那晚我失聲尖叫
山裡傳來回音
而人們卻大笑
⋯⋯
唱這歌的女人
那晚被抓去強暴
他們才不管
我肚子裡未出世的女兒
他們用陰莖和手
強暴我
他們一點也不同情
在我體內注視的女兒
這還不能滿足他們
他們逼我吞下
我丈夫優瑟夫
死後的陰莖
以火藥來調味他那可憐的陰莖
這痛苦讓我大叫
你最好殺了我
再把我跟優瑟夫一起埋了
⋯⋯
畫面上一位形容枯槁、日薄西山的母親對著女兒法斯塔(Fausta)吟唱出這段椎心泣血的過去,唱完旋即無聲無息地含恨而終,短短幾分鐘的獨白道盡這位身心受創的母親一生一世的悲哀。這是八零年代祕魯內戰期間,眾多婦女遭受左派光明之路(Sendero Luminoso)游擊隊軍人慘絕人寰的性暴力後,在揮之不去的倖存者罪惡(survivor guilt)陰影下忍辱含恨走完餘生的心路歷程。
另一部影片「寂寞鋼琴師」(Piano, solo, 2007)是以義大利爵士鋼琴手盧卡·佛洛瑞(Luca Flores, 1956~1995)生平拍成的傳記音樂電影。盧卡的童年在非洲南部的肯亞度過,父親在當地經商,常年在外奔波;母親一肩扛起照顧孩子的責任,經常夜裡未能成眠而藉著彈琴化解心頭鬱悶,善解人意的盧卡經常徹夜未眠陪著母親。一次母親開車時,透過後照鏡與後座的盧卡眉目傳情之際,一不留神發生車禍而當場身亡,盧卡則在這場車禍倖存,但從此憂鬱纏身,這次意外成為盧卡揮之不去的夢魘。盧卡回義大利後,靠著精湛的琴藝在樂壇大放光彩,旋即因憂鬱惡化併發精神病症狀而走下坡;此外,親密關係始終無法穩定,藥物治療與電痙攣療法皆無效,終於在38歲時上吊自殺身亡。我想講的是,盧卡的母親生前顯然已經陷入憂鬱狀態,也就是所謂的「死亡母親」狀態,而盧卡從小高度認同如此「死亡母親」,後來罹患憂鬱症似乎是必然的結果。
......我想討論的並非母親真正死亡後產生的心理影響,而是母親憂鬱之後,深植在孩子心中的一種意象,它殘酷地將一個活生生的個體...... 轉變成一個疏離的個體 沉悶、毫無生氣、形同是無生命狀態。
(André Green, 1983, p142)
法斯塔的母親在如此駭人聽聞的情境之下失去丈夫,可以想像她此後長期籠罩在創傷陰影中,並且深陷憂鬱泥淖。她目睹丈夫被槍殺,並且被迫吞下他死後的陰莖,形同參與並且執行他的死亡過程,這樣的傷痛讓她防衛性地讓自己維持在心死的狀態,如此才能存活在複雜又矛盾的內在衝突之中。原本應該是充滿生命力的母親,在法斯塔面前卻呈現一個毫無生存意志,全然沉浸在哀慟中的母親;失去來自母親的愛,法斯塔如同喪失了生命意義,內在世界彷彿遭遇一場精神層面的毀滅性災難。
當母親突然陷入哀悼瞬間,她同時也瞬間與孩子分開,這個精神生命的轉變被孩子視為一個大災難,因為:愛,在沒有任何預警下,一夕之間完全失去了。
(André Green, 1983, p150)
長期面對如此心死狀態的母親,法斯塔無法哀悼,也不被允許哀悼,心智發展被凍結在當下,不被允許往前進展,有如一位受創嚴重的倖存者,藉由不斷重複創傷情境的方式,被強行羈押在母親內心深層的黑洞中,與母親處於精神上既疏離又緊密結合的狀態;換言之,在精神層面上,法斯塔被母親綁架了,而且共處於死亡狀態。在此共生狀態中,母親將自己揮之不去的恐懼強加於、或說移植在無以迴避的法斯塔心中。對於法斯塔而言,為了存活於如此惡劣的母女關係中,全面認同(identification)母親是唯一可行的心理機轉。在精神分析理論中,認同是一種退行至口腔期的原始心理防衛機轉,此時法斯塔母女間幾乎失去了心理界線,母親經歷的恐懼幾乎原封不動成為法斯塔真實的恐懼。
法斯塔在母親過世後,一次因暈厥送醫時,被醫生發現陰道塞入一顆馬鈴薯,這是內戰時期,某些部落的婦女因為恐懼被軍人強暴的防範措施。這種恐懼理應發生在母親的世代,為何年輕的法斯塔竟然如此戒慎恐懼?彷彿自己置身於當時的恐怖年代,處在隨時會被強暴的恐懼當中。對此,我們即使難以理解法斯塔心中的恐懼,但也毫無立場質疑法斯塔內心的恐懼,因為人類的行為依據的並非外在現實,而是內在/精神現實(internal/psychic reality),而恐懼是無法客觀衡量的。法斯塔內心的恐懼如此真實,真實到近乎妄想的程度,使得法斯塔發展出幾近草木皆兵的妄想行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陰道中的馬鈴薯或許根本就是男性陰莖的具體呈現,象徵法斯塔心理上是處在長期被強暴的狀態中,仿同母親被強暴時的狀態。當護士詢問她是否處女之身時,她猶豫了一下,回答:「不知道」!這樣的回答洩露了法斯塔心中難以言喻的矛盾與混亂 她竟然無法確定自己是否是處女!在母親心中,當時尚未出生的法斯塔在母親的肚子裡,眼睜睜目睹母親被強暴的場景,形同是母親遭受性暴力的見證人,是將母親囚禁於性創傷牢籠中的那個人。藉由塞入陰道的馬鈴薯,母親的性創傷等同於她自己的性創傷,法斯塔被迫維持性創傷的狀態,亦即它的永恆性(timelessness),這在憂鬱狀態尤其明顯,過去的傷痛無法哀悼,當然也就無法構思未來,時間似乎被永遠凍結在當下,猶如死亡狀態一般(Birksted-Breen, 2003)。
「她(亦即母親)被活埋,但是墳墓卻消失了。在原地裂開的洞,讓孤寂變得令人害怕,因為
個案面臨身體與擁有的所有一切,全部沉陷其
中的危險」。
(André Green, 1983, p154)
失去母親之後,盧卡選擇讓自己浸淫於鋼琴演奏與創作,而彈琴是母親生前與盧卡共同擁有的嗜好。先古典,或許象徵著盧卡先是認同母親,維持母親沒有離去的錯覺;後爵士,象徵盧卡嘗試脫離母親的掙扎。創作力(creativity)發展於母嬰之間的互動,作為嬰兒離開母親,或說是嬰兒容許母親離開的準備。為了因應與母親分離帶來諸多巨大的挫折與失落,嬰兒必須發展出有效的外在機制與內在機轉,這就是溫尼考特(D.W. Winnicott, 1896~1971)說的「過渡現象」與「過渡客體」概念。簡言之,藉由藝術創作,盧卡嘗試克服失去母親的分離焦慮,使得旺盛的創作與演奏潛能成為必要條件。沒有創作能力,或是失去創作力,象徵個案無法接受與母親分離這個事實,這個結果往往讓個案進入萬劫不復的憂鬱狀態,甚至終於毀滅自己,譬如自殺。盧卡就是個典型例子,他的演奏生涯雖然大獲成功,但卻不時恐懼自己會發瘋,一直覺得自己身上有怪事發生,靈魂出竅,必須設法控制住,得把自己綁著,極度擔心在觀眾面前發作......。此外,經常伴隨憂鬱的另一個現象 嫉妒,讓他在感情生活無法得到真正的穩定,甚至終於摧毀親密關係,因為他雖然有藝術天份,但基本上「沒有能力愛人」。
「所有藝術創作的本質是,渴望回復失去的愛戀客體(主要是母親)」,也只有失去或死去的客體可以被「使用」於藝術創作中,這是從藝術作為修復功能的觀點談起。佛洛伊德在愛情心理學中也強調:「潛意識對一種獨一無二,不能替代的東西的熱烈渴望,會表現成事實上無休止的追尋 無可休止,因為替身無論如何不可能滿足他的渴望」。再從佛洛伊德的自戀觀點來說,人一出生面臨的困境就是必須說服自己接受自戀逐漸消逝這個事實,而人們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是在試圖回復當初的全知全能的自戀狀態。盧卡在琴藝上一切的努力是如此,但是憂鬱毫不留情的反噬終究將盧卡擊垮,內心深層的罪惡感(罪惡妄想)讓他全面認同「死亡母親」,毫無能力抗拒而被吸入巨大的精神黑洞中,等待著自我毀滅。
這在許多藝術工作者的病理誌(pathography)中屢見不鮮。一般而言,藝術工作者通常有著特別強烈與深沈的心理衝突,而藝術作品本質上就是心理衝突的成果,也是藝術工作者內在狀態的外化。其中,最為人所知的當然是梵谷。文生·梵谷(Vincent Gough)出生前一年的同一天,母親生下死產的長子,名字也叫文生,而這個死產的文生在母親心中是一個「被理想化的死亡孩子」。第一胎孩子死亡對任何母親來說,必然是個嚴重的打擊,母親對此的哀悼一直延續到梵谷出生後,明顯進入了病態哀悼的狀態。梵谷發現自己有個悲傷憔悴的「死亡母親」,既得不到母愛,也無法全心全意照顧自己。梵谷一輩子都在追尋一個「得不到」的女性,而這個女性的原形就是他的母親,可見潛意識的力量多麼可怕啊!
…… people never willingly abandon a libidinal position, not even, indeed, when a substitute is already beckoning to them.
(Freud, 1914, SE 14, p244)
這是佛洛伊德在〈哀悼與憂鬱〉的一段十八字箴言,有人戲稱這應該擺在診療室中,當作每個治療師的座右銘。大意是說,「人們絕不會欣然拋棄利比多位置,即使另一個替代者正在召喚他們」。說白話一點,佛洛伊德不認為人們會輕易放棄失去的人事物,即使有新的誘惑向他們招手;從客體關係而言,自我是如此依戀逝去的客體,因此這個分離的過程,實際上是困難重重的。法斯塔無法輕易甩開母親對她的影響,即使母親過世之後,她的影子總是籠罩著法斯塔,久久不散。相同的,法斯塔的母親被強制與逝去的丈夫緊緊連結在一起,彷彿逝去丈夫的幽靈盤據她的心靈,形成所謂的自戀性認同(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這種認同有如緊箍咒般牢牢將人拴住在創傷當下,這個枷鎖直到老死以終,終究未能一絲一毫鬆開,並且將傷痛傳遞到下一代。法斯塔與母親在無法解決自己內在矛盾的情況下,透過幻覺式的願望否定外在現實,亦即,在內在世界中,法斯塔的母親覺得逝去的丈夫未曾離開她,法斯塔也覺得母親依然如影隨行與她同在,這是受創個案維繫精神存活(psychic survival)之道。
…… 認同因「去灌注」而遺留下來的空洞(並非認同客體)及這個空虛狀態,這經由對於死亡母親充滿情感的幻覺,來填補並且瞬間呈現出來,快速如同一個新的客體被定期挑選來佔據這個空間。
(André Green, 1983, p155)
當女友問起母親是怎麼死的?盧卡回答:「長腫瘤」,語畢隨即轉換話題。然而,盧卡每每在夜深人靜之際,掙扎著回憶起母親,或說質疑自己為何逐漸淡忘母親:「我最氣的是,我不太記得她的事。都是同一場景,我們在非洲的一個長長的海灘上,景色很美,海水很清澈,我跟媽媽在玩球,她一直在旁邊看,她幾乎總是包頭巾,戴50年代風的墨鏡,有點狐眼」。聽得出盧卡對於母親在他腦海中逐漸消逝這件事實,心中滿滿是帶著愧疚的疑惑,然而,他到底真是必須死命著記得母親?還是根本就想忘掉母親呢?這不是個容易回答的問題,尤其是對盧卡而言,記得母親種種似乎是個無可逃避的「責任」,只是這個「責任」何時了呢?從梵谷一生不斷追尋得不到的女人來看,難道盧卡的感情世界也注定如此漂泊一輩子?即使轉進爵士世界,盧卡依然不由自主練習音階,彈巴哈平均律,甚至堅信他用E小調音階殺死了爵士樂小號大師Chet Baker,最後他選擇舊地重遊,回到童年成長的非洲大陸,這難不成
代表盧卡終須回到原點,一切傷痛的原點?如同費倫契(Sandor Ferenczi, 1873~1933)所言:「人類最基本的願望是回到母親的子宮,重拾失去的自戀性整合與完美」。盧卡的琴藝終究未能讓他得以擺脫母親死亡的陰影,他選擇了「認同罹難者」(identification with the victim)的路徑而自殺身亡。在「死亡母親」的照顧下,盧卡已經是個兒童期憂鬱個案;當「死亡母親」真正死亡時,盧卡又是個經歷母親死亡意外的倖存者,這對盧卡而言無非是個致命一擊。
相對於盧卡,母親的死去反而讓法斯塔有機會重新審視她與母親的關係。在此之前,她不被允許脫離母親去看待她所處的外在世界,她的外在世界根本就是母親的內在世界的投射,並非真實的「外在世界」。母親的死去,迫使已經成年的法斯塔必須面對「真實」外在世界的衝擊與挑戰,這包含外在世界普遍存在的利誘、威脅、嫉妒、恐懼、背叛等等;當然,她也同時從外在世界領悟到人與人之間原來還有真誠、信賴、關懷、乃至於愛情。劇末,法斯塔終於願意讓醫生取出陰道內的馬鈴薯,象徵著法斯塔終於決定掙脫母親設下的心靈枷鎖,這顯然與男性園丁互動過程體驗到的信任感有絕對關係。
憂鬱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在精神科執業多年後,拋出如此「小兒科」的問題需要十足的勇氣。但是,我不得不坦承,在診療室中我被憂鬱個案挑起的好奇往往遠比我可以解釋的多。超過二十個寒暑的臨床經驗並沒有讓我輕而易舉地洞悉我眼前的個案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反而讓我越來越困惑於自己是否真實看清了憂鬱個案的真實面貌;我同時也告誡自己千萬不要妄下臆測,因為,個案可能囿於某些原因,不能讓我知道的永遠比願意讓我知道的多太多。如同André Green所言,個案跟治療者初次接觸時,基本上抱怨的並非憂鬱之類的症狀;多數時候,這些症狀或多或少指向親密關係的嚴重衝突。「死亡母親情結」是在治療室中的移情關係裡感受到的。在許多情況下,個案不會主動敘述他的個人史,而是治療者自忖個案在過去某個時間點,必然或是可能在兒童時期罹患過憂鬱症(childhood depression),對此,我們的個案並不會主動提及。
多年來,多虧無數個偶然,讓我有機會踏進他們的內在世界,撲面而來的往往是滿滿的震撼,我驚覺情緒原來是有重量的,撞擊心頭還真會讓人隱隱作痛,個案留下給我的總是滿滿的驚恐與狐疑。我總是等待著他們多告訴我些什麼,多讓我了解他們什麼。我等著......
李俊毅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理論精神分析碩士
高雄長庚醫院精神科系/身心醫學科主治醫師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無境文化【生活】應用精神分析叢書策劃
「…… a subject who never experiences any depression is probably more disturbed than someone who is occasionally depressed.」(從未經驗過任何憂鬱的人,很可能比偶而憂鬱的人更混亂)。這是甫於2012年離世的著名法國精神分析師André Green(1927~2012)講過的一句話,既戲謔又真實,只是這樣的說法恐怕徹底顛覆了一般民眾、甚至精神醫學界對於憂鬱普遍的認知。
憂鬱到底該單純歸類於情緒,還是該被視為一種疾病?這始終是個爭論,因為牽涉層面廣泛,不太可能會有共識;不過,目前精神醫學對於憂鬱的定義、見解、或是描述的字眼,過度強調「具體」與「可研究性」的「症狀」,反而讓憂鬱症與其他身體疾病不容易有效區隔開,精神科對於憂鬱症的診斷證據力也相對被弱化與模糊化,而如此過度醫療化(medicalization)的結果,導致人們對於憂鬱的誤解遠比了解還多。
本文並不在正本清源談論所謂的憂鬱,而是為了突顯憂鬱無所不在,因此藉由一般人知悉的電影與文學作品作為媒介,提供精神分析觀點下的另一種思考模式,讓憂鬱這個議題跳脫出狹隘的精神醫學論述,而這一切歸根究底,還是得從佛洛伊德一百年前發表的<哀悼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5)這篇經典文章談起。這相當精簡的十六頁文章奠定了精神分析看待憂鬱現象的理論基礎,文中有許多對於憂鬱個案深度心理層面的精彩描述,至今依然貼切適用,相較之下,當代臨床精神醫學對於憂鬱症的了解,除了蓬勃發展的生技產業帶出來的藥物治療、神經化學,乃至生物基因觀點外,並無太多新意,基本上是自囚於症狀治療的框架中。
佛洛伊德將哀悼定義為「對於失去所愛之人,或是失去某些抽象事物的尋常反應,譬如: 國家、自由、理想......等等」,這是每個人或早或晚必然得面對的歷程。他接著說:「雖然哀悼會讓生活態度偏離正軌,我們絕不會視之為病態,也不會轉介給醫療處置」,在這樣的架構中,哀悼其實是正常現象,除非後來進入「病態哀悼」狀態,才是我們熟知的憂鬱狀態。何謂「病態哀悼」?這又得回到前一年(1914年)佛洛伊德發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論自戀:一篇導論>,這篇著作中,佛洛伊德認為人一出生將所有性能量,稱為「原欲」,或是「利比多」(libido),聚積於自我(ego)身上,大量的利比多讓人們處在全能自大的心智狀態,稱為「原發性自戀」。利比多有如變形蟲偽足可以從自我向外延伸,依附在適當的客體(object)上,形成後來我們稱為「客體關係」的狀態;利比多也會因為遭致某些挫折而從客體撤回自我身上,我們稱為「次發性自戀」,這相當於人們處在失去重要的人事物,或是處在失落的狀態,這時若能適時讓撤離出來的利比多轉而依附到另一個替代客體的話,基本上是循著「常態哀悼」路徑發展,終至某種程度的穩定狀態;若自我因某些因素不願意放棄已然失去的客體,也就是不願意承認「失去客體」(object loss)這個事實,而強迫將撤回的利比多牢牢封鎖在自我身上,形成自戀膨脹的狀態,這即將依循「病態哀悼」路徑發展成「憂鬱」狀態,藉由這種方式,失去之客體的生命在精神層次上被拉長了;被遺棄的自我受到如此嚴重的創傷,人格結構也因此遭受嚴重的結構性扭曲,佛洛伊德非常漂亮的形容這個狀態:
…… (失去之)客體的陰影籠罩在自我身上,而後者從此被一個特別的代理者監督著,猶如它是一個客體 那個失去的客體。
(Freud, 1917, SE14, P249)
由此觀點而言,憂鬱根本上就是一種自戀狀態。至於人們面對失落時,會依循著常態哀悼路徑或是依循病態哀悼而進入憂鬱的路徑發展?佛洛伊德認為這與人格結構發展有關,也就是說,精神分析建構的憂鬱狀態,並非依據表面症狀,而是「超越」症狀的層次,進入了更深層的人格結構層次。更進一步說,與失去客體之間的關係,決定接下來是常態哀悼或是病態哀悼,如同佛洛伊德所言,憂鬱個案與失去客體之間的關係絕不單純,通常是愛恨交加,也就是愛與恨之間的衝突極為複雜難解。
既然人格結構才是決定個案未來是否因為失去客體而進入憂鬱狀態的關鍵,兒童時期的利比多發展必然是重要的,這時我們必須提到一位德國分析師亞伯拉罕(Karl Abraham, 1877-1925),對於佛洛伊德建構的憂鬱理論他提供許多寶貴的觀點,他認為憂鬱與利比多發展的口腔期有關,由此可見,憂鬱事實上是處在相當原始的心智狀態,這表示治療的困難度相對是高的,這也與多年的臨床經驗不謀而合;此外,亞伯拉罕也認為「成人的憂鬱很可能根源於童年時期的憂鬱」(Depression in adults probably has its roots in a basic depression of childhood.)
果真如此,孩子的憂鬱從何而來?我們先來看看André Green如何在診療室中的移情關係體驗到一個心死的母親如何影響她所照顧的孩子,從而建構一個「死亡母親」(The Dead Mother)的概念來解釋臨床上的憂鬱現象。他是這麼形容的:
死亡母親...... 是一個維持生命狀態的母親,但是在她所照顧的孩子眼中,形同是一種『心死』的狀態。
(André Green, 1983, p142)
這種憂鬱的主要特徵發生於客體(亦即母親)在場的情境中,而客體(母親)本身沉浸於悲慟情境。因為某種特殊原因,母親是處於憂鬱狀態的。英國精神分析師Gregorio Kohon在一次與André Green對談中提到:「死亡母親」實質上強調的並非「缺席」,而是在場的「缺席母親」,這是我們對於這個概念應該有的基本認識。
接下來,用兩部影片來說明所謂的「死亡母親」現象,第一部是秘魯導演克勞蒂亞·尤薩(Claudia Llosa)的作品「懼乳: 傷心的奶水」(The Milk of Sorrow, 2009),此片得到柏林影展金熊獎與柏林影展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也曾作為高雄電影館2011年「電影與精神分析影展」系列5:「關於創傷,說不出口的才算數」之開幕片。這部影片夠沈重,開頭就是一段空靈哀戚的吟唱:
⋯⋯
我向那些混蛋
跪地求饒
那晚我失聲尖叫
山裡傳來回音
而人們卻大笑
⋯⋯
唱這歌的女人
那晚被抓去強暴
他們才不管
我肚子裡未出世的女兒
他們用陰莖和手
強暴我
他們一點也不同情
在我體內注視的女兒
這還不能滿足他們
他們逼我吞下
我丈夫優瑟夫
死後的陰莖
以火藥來調味他那可憐的陰莖
這痛苦讓我大叫
你最好殺了我
再把我跟優瑟夫一起埋了
⋯⋯
畫面上一位形容枯槁、日薄西山的母親對著女兒法斯塔(Fausta)吟唱出這段椎心泣血的過去,唱完旋即無聲無息地含恨而終,短短幾分鐘的獨白道盡這位身心受創的母親一生一世的悲哀。這是八零年代祕魯內戰期間,眾多婦女遭受左派光明之路(Sendero Luminoso)游擊隊軍人慘絕人寰的性暴力後,在揮之不去的倖存者罪惡(survivor guilt)陰影下忍辱含恨走完餘生的心路歷程。
另一部影片「寂寞鋼琴師」(Piano, solo, 2007)是以義大利爵士鋼琴手盧卡·佛洛瑞(Luca Flores, 1956~1995)生平拍成的傳記音樂電影。盧卡的童年在非洲南部的肯亞度過,父親在當地經商,常年在外奔波;母親一肩扛起照顧孩子的責任,經常夜裡未能成眠而藉著彈琴化解心頭鬱悶,善解人意的盧卡經常徹夜未眠陪著母親。一次母親開車時,透過後照鏡與後座的盧卡眉目傳情之際,一不留神發生車禍而當場身亡,盧卡則在這場車禍倖存,但從此憂鬱纏身,這次意外成為盧卡揮之不去的夢魘。盧卡回義大利後,靠著精湛的琴藝在樂壇大放光彩,旋即因憂鬱惡化併發精神病症狀而走下坡;此外,親密關係始終無法穩定,藥物治療與電痙攣療法皆無效,終於在38歲時上吊自殺身亡。我想講的是,盧卡的母親生前顯然已經陷入憂鬱狀態,也就是所謂的「死亡母親」狀態,而盧卡從小高度認同如此「死亡母親」,後來罹患憂鬱症似乎是必然的結果。
......我想討論的並非母親真正死亡後產生的心理影響,而是母親憂鬱之後,深植在孩子心中的一種意象,它殘酷地將一個活生生的個體...... 轉變成一個疏離的個體 沉悶、毫無生氣、形同是無生命狀態。
(André Green, 1983, p142)
法斯塔的母親在如此駭人聽聞的情境之下失去丈夫,可以想像她此後長期籠罩在創傷陰影中,並且深陷憂鬱泥淖。她目睹丈夫被槍殺,並且被迫吞下他死後的陰莖,形同參與並且執行他的死亡過程,這樣的傷痛讓她防衛性地讓自己維持在心死的狀態,如此才能存活在複雜又矛盾的內在衝突之中。原本應該是充滿生命力的母親,在法斯塔面前卻呈現一個毫無生存意志,全然沉浸在哀慟中的母親;失去來自母親的愛,法斯塔如同喪失了生命意義,內在世界彷彿遭遇一場精神層面的毀滅性災難。
當母親突然陷入哀悼瞬間,她同時也瞬間與孩子分開,這個精神生命的轉變被孩子視為一個大災難,因為:愛,在沒有任何預警下,一夕之間完全失去了。
(André Green, 1983, p150)
長期面對如此心死狀態的母親,法斯塔無法哀悼,也不被允許哀悼,心智發展被凍結在當下,不被允許往前進展,有如一位受創嚴重的倖存者,藉由不斷重複創傷情境的方式,被強行羈押在母親內心深層的黑洞中,與母親處於精神上既疏離又緊密結合的狀態;換言之,在精神層面上,法斯塔被母親綁架了,而且共處於死亡狀態。在此共生狀態中,母親將自己揮之不去的恐懼強加於、或說移植在無以迴避的法斯塔心中。對於法斯塔而言,為了存活於如此惡劣的母女關係中,全面認同(identification)母親是唯一可行的心理機轉。在精神分析理論中,認同是一種退行至口腔期的原始心理防衛機轉,此時法斯塔母女間幾乎失去了心理界線,母親經歷的恐懼幾乎原封不動成為法斯塔真實的恐懼。
法斯塔在母親過世後,一次因暈厥送醫時,被醫生發現陰道塞入一顆馬鈴薯,這是內戰時期,某些部落的婦女因為恐懼被軍人強暴的防範措施。這種恐懼理應發生在母親的世代,為何年輕的法斯塔竟然如此戒慎恐懼?彷彿自己置身於當時的恐怖年代,處在隨時會被強暴的恐懼當中。對此,我們即使難以理解法斯塔心中的恐懼,但也毫無立場質疑法斯塔內心的恐懼,因為人類的行為依據的並非外在現實,而是內在/精神現實(internal/psychic reality),而恐懼是無法客觀衡量的。法斯塔內心的恐懼如此真實,真實到近乎妄想的程度,使得法斯塔發展出幾近草木皆兵的妄想行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陰道中的馬鈴薯或許根本就是男性陰莖的具體呈現,象徵法斯塔心理上是處在長期被強暴的狀態中,仿同母親被強暴時的狀態。當護士詢問她是否處女之身時,她猶豫了一下,回答:「不知道」!這樣的回答洩露了法斯塔心中難以言喻的矛盾與混亂 她竟然無法確定自己是否是處女!在母親心中,當時尚未出生的法斯塔在母親的肚子裡,眼睜睜目睹母親被強暴的場景,形同是母親遭受性暴力的見證人,是將母親囚禁於性創傷牢籠中的那個人。藉由塞入陰道的馬鈴薯,母親的性創傷等同於她自己的性創傷,法斯塔被迫維持性創傷的狀態,亦即它的永恆性(timelessness),這在憂鬱狀態尤其明顯,過去的傷痛無法哀悼,當然也就無法構思未來,時間似乎被永遠凍結在當下,猶如死亡狀態一般(Birksted-Breen, 2003)。
「她(亦即母親)被活埋,但是墳墓卻消失了。在原地裂開的洞,讓孤寂變得令人害怕,因為
個案面臨身體與擁有的所有一切,全部沉陷其
中的危險」。
(André Green, 1983, p154)
失去母親之後,盧卡選擇讓自己浸淫於鋼琴演奏與創作,而彈琴是母親生前與盧卡共同擁有的嗜好。先古典,或許象徵著盧卡先是認同母親,維持母親沒有離去的錯覺;後爵士,象徵盧卡嘗試脫離母親的掙扎。創作力(creativity)發展於母嬰之間的互動,作為嬰兒離開母親,或說是嬰兒容許母親離開的準備。為了因應與母親分離帶來諸多巨大的挫折與失落,嬰兒必須發展出有效的外在機制與內在機轉,這就是溫尼考特(D.W. Winnicott, 1896~1971)說的「過渡現象」與「過渡客體」概念。簡言之,藉由藝術創作,盧卡嘗試克服失去母親的分離焦慮,使得旺盛的創作與演奏潛能成為必要條件。沒有創作能力,或是失去創作力,象徵個案無法接受與母親分離這個事實,這個結果往往讓個案進入萬劫不復的憂鬱狀態,甚至終於毀滅自己,譬如自殺。盧卡就是個典型例子,他的演奏生涯雖然大獲成功,但卻不時恐懼自己會發瘋,一直覺得自己身上有怪事發生,靈魂出竅,必須設法控制住,得把自己綁著,極度擔心在觀眾面前發作......。此外,經常伴隨憂鬱的另一個現象 嫉妒,讓他在感情生活無法得到真正的穩定,甚至終於摧毀親密關係,因為他雖然有藝術天份,但基本上「沒有能力愛人」。
「所有藝術創作的本質是,渴望回復失去的愛戀客體(主要是母親)」,也只有失去或死去的客體可以被「使用」於藝術創作中,這是從藝術作為修復功能的觀點談起。佛洛伊德在愛情心理學中也強調:「潛意識對一種獨一無二,不能替代的東西的熱烈渴望,會表現成事實上無休止的追尋 無可休止,因為替身無論如何不可能滿足他的渴望」。再從佛洛伊德的自戀觀點來說,人一出生面臨的困境就是必須說服自己接受自戀逐漸消逝這個事實,而人們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是在試圖回復當初的全知全能的自戀狀態。盧卡在琴藝上一切的努力是如此,但是憂鬱毫不留情的反噬終究將盧卡擊垮,內心深層的罪惡感(罪惡妄想)讓他全面認同「死亡母親」,毫無能力抗拒而被吸入巨大的精神黑洞中,等待著自我毀滅。
這在許多藝術工作者的病理誌(pathography)中屢見不鮮。一般而言,藝術工作者通常有著特別強烈與深沈的心理衝突,而藝術作品本質上就是心理衝突的成果,也是藝術工作者內在狀態的外化。其中,最為人所知的當然是梵谷。文生·梵谷(Vincent Gough)出生前一年的同一天,母親生下死產的長子,名字也叫文生,而這個死產的文生在母親心中是一個「被理想化的死亡孩子」。第一胎孩子死亡對任何母親來說,必然是個嚴重的打擊,母親對此的哀悼一直延續到梵谷出生後,明顯進入了病態哀悼的狀態。梵谷發現自己有個悲傷憔悴的「死亡母親」,既得不到母愛,也無法全心全意照顧自己。梵谷一輩子都在追尋一個「得不到」的女性,而這個女性的原形就是他的母親,可見潛意識的力量多麼可怕啊!
…… people never willingly abandon a libidinal position, not even, indeed, when a substitute is already beckoning to them.
(Freud, 1914, SE 14, p244)
這是佛洛伊德在〈哀悼與憂鬱〉的一段十八字箴言,有人戲稱這應該擺在診療室中,當作每個治療師的座右銘。大意是說,「人們絕不會欣然拋棄利比多位置,即使另一個替代者正在召喚他們」。說白話一點,佛洛伊德不認為人們會輕易放棄失去的人事物,即使有新的誘惑向他們招手;從客體關係而言,自我是如此依戀逝去的客體,因此這個分離的過程,實際上是困難重重的。法斯塔無法輕易甩開母親對她的影響,即使母親過世之後,她的影子總是籠罩著法斯塔,久久不散。相同的,法斯塔的母親被強制與逝去的丈夫緊緊連結在一起,彷彿逝去丈夫的幽靈盤據她的心靈,形成所謂的自戀性認同(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這種認同有如緊箍咒般牢牢將人拴住在創傷當下,這個枷鎖直到老死以終,終究未能一絲一毫鬆開,並且將傷痛傳遞到下一代。法斯塔與母親在無法解決自己內在矛盾的情況下,透過幻覺式的願望否定外在現實,亦即,在內在世界中,法斯塔的母親覺得逝去的丈夫未曾離開她,法斯塔也覺得母親依然如影隨行與她同在,這是受創個案維繫精神存活(psychic survival)之道。
…… 認同因「去灌注」而遺留下來的空洞(並非認同客體)及這個空虛狀態,這經由對於死亡母親充滿情感的幻覺,來填補並且瞬間呈現出來,快速如同一個新的客體被定期挑選來佔據這個空間。
(André Green, 1983, p155)
當女友問起母親是怎麼死的?盧卡回答:「長腫瘤」,語畢隨即轉換話題。然而,盧卡每每在夜深人靜之際,掙扎著回憶起母親,或說質疑自己為何逐漸淡忘母親:「我最氣的是,我不太記得她的事。都是同一場景,我們在非洲的一個長長的海灘上,景色很美,海水很清澈,我跟媽媽在玩球,她一直在旁邊看,她幾乎總是包頭巾,戴50年代風的墨鏡,有點狐眼」。聽得出盧卡對於母親在他腦海中逐漸消逝這件事實,心中滿滿是帶著愧疚的疑惑,然而,他到底真是必須死命著記得母親?還是根本就想忘掉母親呢?這不是個容易回答的問題,尤其是對盧卡而言,記得母親種種似乎是個無可逃避的「責任」,只是這個「責任」何時了呢?從梵谷一生不斷追尋得不到的女人來看,難道盧卡的感情世界也注定如此漂泊一輩子?即使轉進爵士世界,盧卡依然不由自主練習音階,彈巴哈平均律,甚至堅信他用E小調音階殺死了爵士樂小號大師Chet Baker,最後他選擇舊地重遊,回到童年成長的非洲大陸,這難不成
代表盧卡終須回到原點,一切傷痛的原點?如同費倫契(Sandor Ferenczi, 1873~1933)所言:「人類最基本的願望是回到母親的子宮,重拾失去的自戀性整合與完美」。盧卡的琴藝終究未能讓他得以擺脫母親死亡的陰影,他選擇了「認同罹難者」(identification with the victim)的路徑而自殺身亡。在「死亡母親」的照顧下,盧卡已經是個兒童期憂鬱個案;當「死亡母親」真正死亡時,盧卡又是個經歷母親死亡意外的倖存者,這對盧卡而言無非是個致命一擊。
相對於盧卡,母親的死去反而讓法斯塔有機會重新審視她與母親的關係。在此之前,她不被允許脫離母親去看待她所處的外在世界,她的外在世界根本就是母親的內在世界的投射,並非真實的「外在世界」。母親的死去,迫使已經成年的法斯塔必須面對「真實」外在世界的衝擊與挑戰,這包含外在世界普遍存在的利誘、威脅、嫉妒、恐懼、背叛等等;當然,她也同時從外在世界領悟到人與人之間原來還有真誠、信賴、關懷、乃至於愛情。劇末,法斯塔終於願意讓醫生取出陰道內的馬鈴薯,象徵著法斯塔終於決定掙脫母親設下的心靈枷鎖,這顯然與男性園丁互動過程體驗到的信任感有絕對關係。
憂鬱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在精神科執業多年後,拋出如此「小兒科」的問題需要十足的勇氣。但是,我不得不坦承,在診療室中我被憂鬱個案挑起的好奇往往遠比我可以解釋的多。超過二十個寒暑的臨床經驗並沒有讓我輕而易舉地洞悉我眼前的個案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反而讓我越來越困惑於自己是否真實看清了憂鬱個案的真實面貌;我同時也告誡自己千萬不要妄下臆測,因為,個案可能囿於某些原因,不能讓我知道的永遠比願意讓我知道的多太多。如同André Green所言,個案跟治療者初次接觸時,基本上抱怨的並非憂鬱之類的症狀;多數時候,這些症狀或多或少指向親密關係的嚴重衝突。「死亡母親情結」是在治療室中的移情關係裡感受到的。在許多情況下,個案不會主動敘述他的個人史,而是治療者自忖個案在過去某個時間點,必然或是可能在兒童時期罹患過憂鬱症(childhood depression),對此,我們的個案並不會主動提及。
多年來,多虧無數個偶然,讓我有機會踏進他們的內在世界,撲面而來的往往是滿滿的震撼,我驚覺情緒原來是有重量的,撞擊心頭還真會讓人隱隱作痛,個案留下給我的總是滿滿的驚恐與狐疑。我總是等待著他們多告訴我些什麼,多讓我了解他們什麼。我等著......
李俊毅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理論精神分析碩士
高雄長庚醫院精神科系/身心醫學科主治醫師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無境文化【生活】應用精神分析叢書策劃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