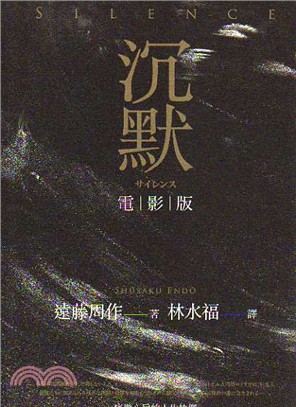商品簡介
台灣美景驚豔全球!
國際金獎大導馬丁史柯西斯 親撰前言
★ 導演馬丁史柯西斯籌備28年改編電影,「非完成不可」的畢生夢想之作。
★ 首部全片在台灣拍攝的好萊塢史詩鉅獻,東西方巨星雲集,電影劇照珍藏收錄。
★ 榮獲第二屆谷崎潤一郎獎,與《深河》同時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日本文學代表作。
「表面上看來,信與疑是不相容的,我卻認為兩者比肩並行,互為滋養。疑會導致嚴重的疏離,但若與信共存──真正的信,始終的信──到最後卻可以達到兩者融合的喜樂極致。正是此一痛苦、矛盾的過程──從確信到懷疑到疏離到融合──遠藤周作知之甚詳,並在《沉默》中做了清楚細膩而優美的闡述。」——馬丁史柯西斯(電影《沈默》導演),〈電影版前言〉
反抗歷史的沉默 探索神的沉默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一生為天主服務、奉獻的遠藤周作先生離開人世,回到主的身旁,家人遵奉遺言把《沉默》和《深河》放入棺中陪伴遠藤;這代表了遠藤對其文學創作的評價與總結。其實,這兩本書除了他自認為是自己的代表作之外,它們同時還被公認為是二十世紀日本文學的代表作。
《沉默》發表於一九六九年,為日本近代文學大家遠藤周作之鉅著,榮獲第二屆谷崎潤一郎獎,其中探討基督宗教在東方社會紮根時面臨的問題,包含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等。之所以取名為「沉默」,理由有二:(一)反抗歷史的沉默;(二)探索神的沉默。
故事發生在德川幕府時代禁教令下長崎附近的小村子,一個葡萄牙耶穌會的教士偷渡到日本傳教,並調查恩師因遭受「穴吊」而宣誓棄教一事,因為這事在當時歐洲人的眼中,不只是個人的挫折,同時也是整個歐洲信仰、思想的恥辱和失敗。
在傳教與尋訪的過程中,信仰與反叛、聖潔與背德、強權與卑微、受難與恐懼、堅貞與隱忍、掙扎與超脫……所有的兩難情境都面臨了,逼迫著他對基督的信仰進行更深層且更現實的思索,最終,他彷彿也走過一趟恩師的心路歷程,擁有自己對信仰的詮釋與實踐。
《沉默》小說改編電影由金獎名導馬丁史柯西斯執導改編,在他第一次讀到便有改編成電影的念頭;一九九二年,《沉默》作者遠藤周作拜訪紐約與馬丁討論將小說改編電影,但全片直至二○一三年才底定拍攝計畫,耗費二十八年始完成電影。二○一五年,電影劇組來台拍攝,是第一部全片在台灣拍攝完成的好萊塢一級製作,演員陣容集結出類拔萃的東西方明星。
新版《沉默》特別收錄導演馬丁史柯西斯為原著小說親自撰寫之前言,及電影劇照數幀,值得珍藏。
作者簡介
近代日本文學大家。一九二三年生於東京,慶應大學法文系畢業,別號狐狸庵山人。一生獲獎無數,曾先後獲芥川獎、新潮社文學獎、每日出版文學獎、每日藝術獎、谷崎潤一郎獎、野間文學獎等多項日本文學大獎,一九九五年獲日本文化勳章。遠藤承襲了自夏目漱石、經芥川龍之介至崛辰雄一脈相傳的傳統,在近代日本文學中居承先啟後的地位。
生於東京、在中國大連度過童年的遠藤周作,於一九三三年隨離婚的母親回到日本;由於身體虛弱,使他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未被徵召入伍,而進入慶應大學攻讀法國文學,並在一九五○年成為日本戰後第一批留學生,前往法國里昂大學留學達二年之久。
回到日本之後,遠藤周作隨即展開了他的作家生涯。作品有以宗教信仰為主的,也有老少咸宜的通俗小說,著有《母親》、《影子》、《醜聞》、《海與毒藥》、《沉默》、《武士》、《深河》、《深河創作日記》等書。一九九六年九月辭世,享年七十三歲。
序
導讀——沉默的世界╱ 林水福
前言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一生為天主服務、奉獻的遠藤周作先生離開人世,回到主的身旁,家人遵奉遺言把《沉默》和《深河》放入棺中陪伴遠藤。
《沉默》不但是探討遠藤周作文學的最重要作品之一,也探討基督宗教在東方社會紮根時面臨的問題,其中包含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等等。
《沉默》與《深河》無疑會是二十世紀日本文學的代表作。
評論家對《沉默》的幾種看法
發表於一九六六年的《沉默》是一部評價極高的作品,但同時也是引起許多爭議的作品。或許,不朽作品往往產生正反兩極的看法吧!谷崎潤一郎獎選考委員之一的伊藤整,即反對把票投給《沉默》,他認為「閱讀之後有昏昏欲睡之感」 ;大岡昇平則坦率地指出末尾的「到今天為止,我的人生本身就在訴說著那個人。」過於傲慢;而三島由紀夫所直陳的缺點是:末尾「那個人並未沉默著」的主題之轉換,不無疑問。
在眾多評論中,無可否認的有搔中癢處者,也有一針見血者:但,未深 入研究且太過武斷之評論,及因忽略末尾「天主教住宅官吏日記」而未正確「讀」出作者深意,甚或因此而產生誤解者亦為數不少。純文學,尤其是作者嘔心瀝血的創作,每一字每一句均經再三推敲始定稿,自無在作品末尾「附」上七頁「贅言」之可能。事實上,「天主教住宅官吏日記」中隱含玄機,非但不可略過,更應再三熟讀。
取名「沉默」的理由
作者取名為「沉默」的理由有二:
(一) 反抗歷史的沉默
遠藤自稱於準備階段時,發現天主教資料中,對許多像吉次郎之類的信徒,或像洛特里 哥神父般的棄教者,都表現出蔑視、憎恨的態度。換言之,天主教史上只對轟轟烈烈而 死的殉教者加以讚美,描述他們的生平或死亡;但是,對像吉次郎或洛特里哥神父般的 信徒或神職人員,則只有漠視相向。亦即,天主教的歷史將他們深埋在沉默之灰下,儘量不讓他們顯露出來。
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被漠視的人,既然身而為人;那麼,對因己身的軟弱而作出的棄教行為,自有不可與他人言的痛苦。能夠替他們說出被深埋在沉默之灰下的痛苦的只有小說家了。因此,「沉默」其實包含了反抗歷史的沉默之意義。
(二) 探索神的沉默
在我們整部人類的歷史當中,或個人的人生裡頭,一定經驗過無數的 「神的沉默」。對神的沉默,冷淡接受者,不是憎恨神的無情,就是不承認曾經見證過。這部小說,表面上看來,似乎是描寫神的沉默;其實,在作品的深處,神並非沉默著。作品中,作者運用多重場面的寫法,隱約透露出這個訊息。茲舉一例,如:
司祭把腳踏到聖像時,黎明來臨,傳來遠處雞啼。
這一行的背後,其實和新約聖經中有名的伯多祿背叛耶穌的畫面相重疊。遠藤作品中常運用這種多重映像重疊的寫法,讀者如不細加咀嚼,不容易察覺到它的巧妙處:那麼,作者的一番苦心當然也無由領會了。一部傳世不朽的作品,自然是作者嘔心瀝血的創作,但讀者也需要付出相當努力的代價,始能心領神會。有關遠藤多重映像重疊的寫法,留待下節中討論。
沉默的主題
作者在《沉默》中探討的問題相當多;當然,所謂探討,事實上就是作者個人對於事情的觀點、看法及至於思想的小說化。
《沉默》中的第一個主題即,神並非沉默著;神是存在的。遠藤文學中的一個基軸——證明神的存在。如何證明神的存在?這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無法用眼睛直接看到神,但神透過我們的人生,告訴我們祂的存在。我們向神祈禱,無法直接得到神的回答,但這並不是說神像冰塊一樣一直沉默著,祂是以我們肉眼看不到的「作用」回答我們的。
《沉默》中,作者透過茂吉、一藏的殉教,以及吉次郎出賣司祭洛特里哥,和洛特里哥本身的棄教過程等等,來告訴我們神的存在。如果神不存在,吉次郎在棄教、出賣洛特里哥神父之後,為何還緊追神父背後不捨;甚至於在神父表面上棄教之後,仍然要神父聽他告解,為他向神祈求寬恕呢?而作品末尾的「縱使那個人是沉默著,到今天為止,我的人生本身就在訴說著那個人。」「那個人」指的是神,也就是耶穌基督。如果《沉默》的故事在此完全結束,無疑的,在小說結構上是一大漏洞,也會讓讀者感到百思莫解。為何洛特里哥會突然發出如此「豪語」呢?不錯,促成洛特里哥踏聖像的是神的愛。棄教的費雷拉神父說服洛特里哥的部分對話如下:
「你認為自己比他們(註:指受穴吊的人)更重要吧!至少認為自己的得救是重要的吧!你如果說出棄教,那些人就可以從洞裡回來,從痛苦中獲救。雖然如此,你還不棄教,因為你覺得為他們背叛教會是很可惜的,像我這樣變成教會的污點是可怕的。」費雷拉憤怒的聲音,一口氣說到這裡,之後逐漸轉弱,「我也是這樣的。在那黑暗而寒冷的夜晚,我也和現在的你一樣。可是,那是愛的行為嗎?司祭必須學習為基督而生,如果基督在這裡的話。」
費雷拉沉默了一瞬間,馬上以清晰有力的語氣說:「基督一定會為他們而棄教的!」
天色逐漸亮了,到目前為止黑漆漆的這圍牆內,也開始出現朦朧的白光。
「基督會為人們而棄教吧!」
「沒有這回事!」司祭以手掩面,聲音從指縫間擠出。「沒有這回事!」
「基督會棄教吧!為了愛,即使犧牲了自己的一切。」
「不要再折磨我,走吧!走得遠遠地!」
司祭大聲哭泣。門栓發出低沈的聲音,掉落地上,門開了。白色的晨曦從打開的門瀉入。
「哪!」費雷拉溫柔地把手放在司祭肩上說。「去做至今沒人做過的最痛苦的愛德行為。」
偷渡到日本之後,司祭目睹過信徒被逼迫的痛苦,以至於殉教的場面;但是,那場 面卻跟聖經中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光榮殉教的場面不同,也跟許多聖人轟轟烈烈的殉教情形不同。那場面看來是多麼淒慘、恥辱,絲毫沒有想像中的「壯烈」氣氛,身為司祭仍免不了有這種「虛榮心」,這種諷刺筆調是遠藤文學的一個特色;對神職人員的描寫亦不例外。然而,最後促使他棄教的是,基督的愛德行為,以及——
凹下的那張臉難過似地仰望司祭。那雙難過似地仰望著自己的眼睛訴說著:踏下去吧! 踏下去沒關係,我是為了讓你們踐踏而存在的。
司祭一生以那個人為學習榜樣,認為那個人的臉是世界上善與美的結合;因此,最後促使司祭決定踏聖像的是那個人--耶穌基督。問題是,如果《沉默》的故事在這兒就完全結束,那麼洛特里哥的棄教,要是被解釋成屈服於威脅利誘下,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在這裡,遠藤設下了《沉默》的後設部分——「天主教住宅官吏日記」,暗示洛特里哥雖然踏了聖像,但並未真正棄教,仍繼續「執行」司祭的任務,在延寶二年兩次被遠江守強迫寫下棄教的切結書。過程是:本應從正月廿日至二月八日書寫,可能後來沒寫;於是在二月十六日書寫,遠江守派傳右衛門、河原甚五兵衛兩名武士到三右衛門(即洛特里哥)住處監視。第二次是在山屋敷書院,從六月十四日至七月廿四日書寫的。兩次被迫書寫期間,受到拷打的可能性也相當大。再則,後來吉次郎被從掛於頸上之「護身符」中,搜出「天主教耶穌像一幀」,吉次郎的好友一橋又兵衛也受到牽連被捕入獄。遠江守親自調查、審問,當時還懷疑「是否三右衛門給的?」由此可見,洛特里哥並非完全棄教,與本文末尾「在這個國家,我現在仍然是最後的天主教司祭。」緊密契合在一起,兩者不可分離。 「天主教住宅官吏日記」的意義在此,絕非可有可無部分。
反過來說,從洛特里哥最後並未完全棄教,以及吉次郎也企圖重新信仰天主教的行為來證明神的存在。神藉著以祂形體創造的人的身上,告訴世人祂的存在;而祂所創造的人,靠著自己的人生來證明祂的存在。
《沉默》的第二個主題是「母性宗教」觀。一九七七年遠藤在(父性宗教、母性宗教)一文中指出:
我要聲明的是,天主教並非如白鳥(註:指正宗白鳥,日本近代作家)誤解的只有父性宗教,天主教中也包括了母性宗教。這並不是像隱匿的天主教崇敬瑪麗亞那麼單純的,而是由新約聖經的性格造成的。新約聖經是在「父性宗教」的舊約世界中導入母性性格,因而形成父性、母性兼具者。
現實生活中,遠藤幼時父母離異,他與母親兩人相依為命,一方面養成了遠藤對母親的依賴;另一方面他曾「背叛」母親,回到父親身旁。同時信仰方面接受了父性宗教的洗禮,可謂雙重背叛。由於這種關係,遠藤文學中一再塑造、強調天主教中的「母性」部分;作品中出現的基督,往往帶有「母性」性格,即寬容的、溫柔的,對犯過錯的信徒一子女,不但原諒他,寬恕他,還接納他,給予恩寵。《沉默》中,暗示母性宗教之處不少,諸如:
聖像中的那個人,由於被許多人踏過,已磨損、凹陷,以悲傷的眼神注視著司祭。從那眼中,有一滴眼淚欲奪眶而出。那張臉,現在,在這黑暗中就在他眼前,默默地;但卻以溫柔的眼神凝視著自己。(你痛苦的時候,)那張臉似乎在訴說著。(我也在旁邊跟著痛苦,我會陪伴你直到最後。)
午後陽光閃爍的港灣前方,一大塊積亂雲鑲著金色的邊緣湧上來。.....自己與卡爾倍和他們有所關連,而且和十字架上那個人結合的喜悅,突然強烈拍打著司祭的心。這時,那個人的臉,以從未有過的鮮明影像向他逼近。那是痛苦的基督!忍耐的基督!他在心中祈禱自己的臉和那張臉馬上接近!
「悲傷的眼神」、「有一滴眼淚欲奪眶而出」、「溫柔的眼神」、「痛苦的」、「忍耐的基督」等等,都是母性影像的特殊描述;至於「和十字架上那個人結合」的說法,更是除非母性、女性,否則無法成立的表現方式,在在都透露出遠藤母性宗教觀的經營苦心。
再者,《沉默》的另一主題——弱者的復權——也與「母性的宗教」觀有著極密切的關連。上述遠藤取名「沉默」的理由之一是,對歷史沉默的抗議,也就是對被迫棄教的信徒、或神父有意加以蔑視而深感不滿。弱者的復權,可說是遠藤文學的一大特色。遠藤作品中的主角,可說無一英雄式的人物。例如:《我.拋棄了的.女人》中,遠藤即以命運坎坷,淪為妓女的森田蜜為主角。《沉默》的主角當是吉次郎。洛特里哥書信中,對吉次郎的印象是這樣子的:
我上次提到的那個日本人吉次郎,也和中國水手們一起搬運行李,幫忙整理船帆。我們一直很注意地觀察著這個可能成為左右我等往後命運的日本人。現在,我們了解到他的個性相當狡猾,而這狡猾是從他軟弱的個性產生的。
在《沉默》的前奏中,已勾勒出吉次郎的個性;而這軟弱、狡猾的男子,卻成為往後左右洛特里哥命運的人物,即暗示著吉次郎在《沉默》中所擔負的意義何等重大!洛特里哥以耶穌基督自擬,而吉次郎即那背信的猶大;如聖經中猶大出賣了耶穌,《沉默》中的吉次郎也出賣了洛特里哥。吉次郎雖然出賣了洛特里哥,但卻仍緊緊跟隨在後,祈求神父原諒他。從以下吉次郎的話及洛特里哥內心的思考,看得出弱者逐漸「復位」,主張弱者亦有其存在的權利。
「茂吉很堅強,就像我們種的長得碩壯的秧苗。可是,軟弱的秧苗無論再怎麼施肥 都長不好,不會結稻穗。神父!像我天生是個懦弱的人,就跟這種秧苗一樣呀……」
如吉次郎所說,世人並不只限於聖人和英雄。要不是生長在這遭受迫害的時代,不知有多少信徒根本不必棄教或捨棄生命,可以一直信守著幸福的信仰呢。他們只是平凡的信徒,最後被肉體的恐怖擊倒了。
……
人,天生就有兩種,即強者和弱者;聖人和凡人;英雄和懦夫。然而,強者在這樣的迫害時代,能忍受囚信仰而被火焚燒或沈入海底吧!可是,弱者就像吉次郎在山中流浪。你到底屬於何者?要不是因為司祭的自尊和義務的觀念,或許我也跟吉次郎一樣踏了聖像。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主角是吉次郎無誤。本來在洛特里哥心目中的吉次郎,是個最卑下的人,較諸惡人猶為不如;因為惡人還有惡人的力與美,但是吉次郎卻如骯髒的破衣服。可是,以基督為典範的洛特里哥想到,聖經上基督所尋找的,不是像患了血漏的女人,就是如被扔石頭的娼婦般、毫無吸引力,一點也不美的人。基督就是愛;然而喜歡有吸引力的、美的東西,這是誰都能辦得到的,那不是愛。不捨棄已褪色、如襤褸般的人和人生,那才是真正的愛。司祭不能無視於弱者吉次郎的存在,最後答應吉次郎的要求,聽了他的告解,也為他祈禱「你安心去吧!」告解是天主教七大奧蹟之一,也就是全能的神對人的救贖:換言之,也是神的愛的表徵。「沒有所謂的強者與弱者。誰又能斷言弱者一定不比強者痛苦呢?」司祭最後悟出的這句話,為弱者下了最好的註腳!
《沉默》中所探討的問題,除了上述三個主題之外,其實還涉及到諸如天主教在日本的改變,以及紮根的問題。洛特里哥與費雷拉的精采對答,道出了遠藤針對天主教土著化的獨特看法;類似的觀點,其實遠藤在初期的評論(諸神與神)與(不合身的西裝)中已明顯指出,在此不再贅述。「棉花的行列」的詩句,不禁衝口而出:「棉花的行列」暗示著「神的羔羊」。《沉默》中,洛特里哥被關在黑漆漆的圍牆內。這黑漆漆是死亡與誕生毗鄰而居的,原初的黑暗,也是女性子宮的象徵。洛特里哥在這裡描繪的基督的臉「以含著溫柔的眼光注視著自己」,那份「溫柔」,無疑的是母性的溫柔,也難怪乎司祭想接近祂。當司祭在心中作最後決定,要踐踏聖像時,黎明的曙光——象徵著神的恩寵——迎接著他。
另外,吉次郎向官吏密告洛特里哥藏身處時,作者以蜥蜴象徵吉次郎。「陽光下,我發覺蜥蜴偷瞄著我的膽怯的臉孔,跟剛剛走掉的吉次郎一模一樣。」尾巴對蜥蜴而言,代表著什麼呢?在形態上沒了尾巴不算完全,但卻不致於威脅到生命的持續;另一方面,蜥蜴沒了尾巴仍會自然再長出來,這不也象徵著吉次郎屢次出賣神父,作出棄教的行為,可是,過一段時間,如尾巴自然長出般,信仰也在吉次郎心中再生長嗎?
結語
《沉默》是遠藤文學的第二高峰(第一高峰為《海與毒藥》),其中所包含的意義,絕非這篇(導讀)所能道盡的。故事的背景雖然在日本,但是遠藤所要探討的卻是普遍性的東西,信仰以及東西文化之異同等等,又何嘗不是我們切身的問題呢?!
目次
前言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一生為天主服務、奉獻的遠藤周作先生離開人世,回到主的身旁,家人遵奉遺言把《沉默》和《深河》放入棺中陪伴遠藤。
《沉默》不但是探討遠藤周作文學的最重要作品之一,也探討基督宗教在東方社會紮根時面臨的問題,其中包含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等等。
《沉默》與《深河》無疑會是二十世紀日本文學的代表作。
評論家對《沉默》的幾種看法
發表於一九六六年的《沉默》是一部評價極高的作品,但同時也是引起許多爭議的作品。或許,不朽作品往往產生正反兩極的看法吧!谷谷崎潤一郎獎選 考委員之一的伊藤整,即反對把票投給《沉默》,他認為「閱讀之後有昏昏欲睡之感」 ;大岡昇平則坦率地指出末尾的「到今天為止,我的人生本身就在訴說著那個人。」過於傲慢;而三島由紀夫所直陳的缺點是:末尾「那個人並未沉默著」的主題之轉換,不無疑問。
在眾多評論中,無可否認的有搔中癢處者,也有一針見血者:但,未深 入研究且太過武斷之評論,及因忽略末尾「天主教住宅官吏日記」而未正確「讀」出作者深意,甚或因此而產生誤解者亦為數不少。純文學,尤其是作者嘔心瀝血的創作,每一字每一句均經再三推敲始定稿,自無在作品末尾「附」上七頁「贅言」之可能。事實上,「天主教住宅官吏日記」中隱含玄機,非但不可略過,更應再三熟讀。
取名「沉默」的理由
作者取名為「沉默」的理由有二:
(一) 反抗歷史的沉默
遠藤自稱於準備階段時,發現天主教資料中,對許多像吉次郎之類的信徒,或像洛特里 哥神父般的棄教者,都表現出蔑視、憎恨的態度。換言之,天主教史上只對轟轟烈烈而 死的殉教者加以讚美,描述他們的生平或死亡;但是,對像吉次郎或洛特里哥神父般的 信徒或神職人員,則只有漠視相向。亦即,天主教的歷史將他們深埋在沉默之灰下,儘量不讓他們顯露出來。
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被漠視的人,既然身而為人;那麼,對因己身的軟弱而作出的棄教行為,自有不可與他人言的痛苦。能夠替他們說出被深埋在沉默之灰下的痛苦的只有小說家了。因此,「沉默」其實包含了反抗歷史的沉默之意義。
(二) 探索神的沉默
在我們整部人類的歷史當中,或個人的人生裡頭,一定經驗過無數的 「神的沉默」。對神的沉默,冷淡接受者,不是憎恨神的無情,就是不承認曾經見證過。這部小說,表面上看來,似乎是描寫神的沉默;其實,在作品的深處,神並非沉默著。作品中,作者運用多重場面的寫法,隱約透露出這個訊息。茲舉一例,如:
司祭把腳踏到聖像時,黎明來臨,傳來遠處雞啼。
這一行的背後,其實和新約聖經中有名的伯多祿背叛耶穌的畫面相重疊。遠藤作品中常運用這種多重映像重疊的寫法,讀者如不細加咀嚼,不容易察覺到它的巧妙處:那麼,作者的一番苦心當然也無由領會了。一部傳世不朽的作品,自然是作者嘔心瀝血的創作,但讀者也需要付出相當努力的代價,始能心領神會。有關遠藤多重映像重疊的寫法,留待下節中討論。
沉默的主題
作者在《沉默》中探討的問題相當多;當然,所謂探討,事實上就是作者個人對於事情的觀點、看法及至於思想的小說化。
《沉默》中的第一個主題即,神並非沉默著;神是存在的。遠藤文學中的一個基軸——證明神的存在。如何證明神的存在?這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無法用眼睛直接看到神,但神透過我們的人生,告訴我們牠的存在。我們向神祈禱,無法直接得到神的回答,但這並不是說神像冰塊一樣一直沉默著,衪是以我們肉眼看不到的「作用」回答我們的。
《沉默》中,作者透過茂吉、一藏的殉教,以及吉次郎出賣司祭洛特里哥,和洛特里哥本身的棄教過程等等,來告訴我們神的存在。如果神不存在,吉次郎在棄教、出賣洛特里哥神父之後,為何還緊追神父背後不捨;甚至於在神父表面上棄教之後,仍然要神父聽他告解,為他向神祈求寬恕呢?而作品末尾的「縱使那個人是沉默著,到今天為止,我的人生本身就在訴說著那個人。」「那個人」指的是神,也就是耶穌基督。如果《沉默》的故事在此完全結束,無疑的,在小說結構上是一大漏洞,也會讓讀者感到百思莫解。為何洛特里哥會突然發出如此「豪語」呢?不錯,促成洛特里哥踏聖像的是神的愛。棄教的費雷拉神父說服洛特里哥的部分對話如下:
「你認為自己比他們(註:指受穴吊的人)更重要吧!至少認為自己的得救是重要的吧!你如果說出棄教,那些人就可以從洞裡回來,從痛苦中獲救。雖然如此,你還不棄教,因為你覺得為他們背叛教會是很可惜的,像我這樣變成教會的污點是可怕的。」費雷拉憤怒的聲音,一口氣說到這裡,之後逐漸轉弱,「我也是這樣的。在那黑暗而寒冷的夜晚,我也和現在的你一樣。可是,那是愛的行為嗎?司祭必須學習為基督而生,如果基督在這裡的話。」
費雷拉沉默了一瞬間,馬上以清晰有力的語氣說:「基督一定會為他們而棄教的!」
天色逐漸亮了,到目前為止黑漆漆的這圍牆內,也開始出現朦朧的白光。
「基督會為人們而棄教吧!」
「沒有這回聲!」司祭以手掩面,聲音從指縫間擠出。「沒有這回事!」
「基督會棄教吧!為了愛,即使犧牲了自己的一切。」
「不要再折磨我,走吧!走得遠遠地!」
司祭大聲哭泣。門栓發出低沈的聲音,掉落地上,門開了。白色的晨曦從打開的門瀉入。
「哪!」費雷拉溫柔地把手放在司祭肩上說。「去做至今沒人做過的最痛苦的愛德行為。」
偷渡到日本之後,司祭目睹過信徒被逼迫的痛苦,以至於殉教的場面;但是,那場 面卻跟聖經中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光榮殉教的場面不同,也跟許多聖人轟轟烈烈的殉教情形不同。那場面看來是多麼淒慘、恥辱,絲毫沒有想像中的「壯烈」氣氛,身為司祭仍免不了有這種「虛榮心」,這種諷刺筆調是遠藤文學的一個特色;對神職人員的描寫亦不例外。然而,最後促使他棄教的是,基督的愛德行為,以及——
凹下的那張臉難過似地仰望司祭。那雙難過似地仰望著自己的眼睛訴說著:踏下去吧! 踏下去沒關係,我是為了讓你們踐踏而存在的。
司祭一生以那個人為學習榜樣,認為那個人的臉是世界上善與美的結合;因此,最後促使司祭決定踏聖像的是那個人--耶穌基督。問題是,如果《沉默》的故事在這兒就完全結束,那麼洛特里哥的棄教,要是被解釋成屈服於威脅利誘下,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在這裡,遠藤設下了《沉默》的後設部分——「天主教住宅官吏日記」,暗示洛特里哥雖然踏了聖像,但並未真正棄教,仍繼續「執行」司祭的任務,在延寶二年兩次被遠江守強迫寫下棄教的切結書。過程是:本應從正月廿日至二月八日書寫,可能後來沒寫;於是在二月十六日書寫,遠江守派傳右衛門、河原甚五兵衛兩名武士到三右衛門(即洛特里哥)住處監視。第二次是在山屋敷書院,從六月十四日至七月廿四日書寫的。兩次被迫書寫期間,受到拷打的可能性也相當大。再則,後來吉次郎被從掛於頸上之「護身符」中,搜出「天主教耶穌像一幀」吉次郎的好友一橋又兵衛也受到牽連被捕入獄。遠江守親自調查、審問,當時還懷疑「是否三右衛門給的?」由此可見,洛特里哥並非完全棄教,與本文末尾「在這個國家,我現在仍然是最後的天主教司祭。」緊密契合在一起,兩者不可分離。 「天主教住宅官吏日記」的意義在此,絕非可有可無部分。
反過來說,從洛特里哥最後並未完全棄教,以及吉次郎也企圖重新信仰天主教的行為來證明神的存在。神藉著以衪形體創造的人的身上,告訴世人衪的存在;而衪所創造的人,靠著自己的人生來證明衪的存在。
《沉默》的第二個主題是「母性宗教」觀。一九七七年遠藤在(父性宗教、母性宗教)一文中指出:
我要聲明的是,天主教並非如白鳥(註:指正宗白鳥,日本近代作家)誤解的只有父性宗教,天主教中也包括了母性宗教。這並不是像隱匿的天主教崇敬瑪麗亞那麼單純的,而是由新約聖經的性格造成的。新約聖經是在「父性宗教」的舊約世界中導入母性性格,因而形成父性、母性兼具者。
現實生活中,遠藤幼時父母離異,他與母親兩人相依為命,一方面養成了遠藤對母親的依賴;另一方面他曾「背叛」母親,回到父親身旁。同時信仰方面接受了父性宗教的洗禮,可謂雙重背叛。由於這種關係,遠藤文學中一再塑造、強調天主教中的「母性」部分;作品中出現的基督,往往帶有「母性」性格,即寬容的、溫柔的,對犯過錯的信徒一子女,不但原諒他,寬恕他,還接納他,給予恩寵。《沉默》中,暗示母性宗教之處不少,諸如:
聖像中的那個人,由於被許多人踏過,已磨損、凹陷,以悲傷的眼神注視著司祭。從那眼中,有一滴眼淚欲奪眶而出。那張臉,現在,在這黑暗中就在他眼前,默默地;但卻以溫柔的眼神凝視著自己。(你痛苦的時候,)那張臉似乎在訴說著。(我也在旁邊跟著痛苦,我會陪伴你直到最後。)
午後陽光閃爍的港灣前方,一大塊積亂雲鑲著金色的邊緣湧上來。.....自己與卡爾倍和他們有所關連,而且和十字架上那個人結合的喜悅,突然強烈拍打著司祭的心。這時,那個人的臉,以從未有過的鮮明影像向他逼近。那是痛苦的基督!忍耐的基督!他在心中祈禱自己的臉和那張臉馬上接近!
「悲傷的眼神」、「有一滴眼淚欲奪眶而出」、「溫柔的眼神」、「痛苦的」、「忍耐的基督」等等,都是母性影像的特殊描述;至於「和十字架上那個人結合」的說法,更是除非母性、女性,否則無法成立的表現方式,在在都透露出遠藤母性宗教觀的經營苦心。
再者,《沉默》的另一主題——弱者的復權——也與「母性的宗教」觀有著極密切的關連。上述遠藤取名「沉默」的理由之一是,對歷史沉默的抗議,也就是對被迫棄教的信徒、或神父有意加以蔑視而深感不滿。弱者的復權,可說是遠藤文學的一大特色。遠藤作品中的主角,可說無一英雄式的人物。例如:《我.拋棄了的.女人》中,遠藤即以命運坎坷,淪為妓女的森田蜜為主角。《沉默》的主角當是吉次郎。洛特里哥書信中,對吉次郎的印象是這樣子的:
我上次提到的那個日本人吉次郎,也和中國水手們一起搬運行李,幫忙整理船帆。我們一直很注意地觀察著這個可能成為左右我等往後命運的日本人。現在,我們了解到他的個性相當狡猾,而這狡猾是從他軟弱的個性產生的。
在《沉默》的前奏中,已勾勒出吉次郎的個性;而這軟弱、狡猾的男子,卻成為往後左右洛特里哥命運的人物,即暗示著吉次郎在《沉默》中所擔負的意義何等重大!洛特里哥以耶穌基督自擬,而吉次郎即那背信的猶大;如聖經中猶大出賣了耶穌,《沉默》中的吉次郎也出賣了洛特里哥。吉次郎雖然出賣了洛特里哥,但卻仍緊緊跟隨在後,祈求神父原諒他。從以下吉次郎的話及洛特里哥內心的思考,看得出弱者逐漸「復位」,主張弱者亦有其存在的權利。
「茂吉很堅強,就像我們種的長得碩壯的秧苗。可是,軟弱的秧苗無論再怎麼施肥 都長不好,不會結稻穗。神父!像我天生是個懦弱的人,就跟這種秧苗一樣呀……」
如吉次郎所說,世人並不只限於聖人和英雄。要不是生長在這遭受迫害的時代,不知有多少信徒根本不必棄教或捨棄生命,可以一直信守著幸福的信仰呢。他們只是平凡的信徒,最後被肉體的恐怖擊倒了。
……
人,天生就有兩種,即強者和弱者;聖人和凡人;英雄和懦夫。然而,強者在這樣的迫害時代,能忍受囚信仰而被火焚燒或沈入海底吧!可是,弱者就像吉次郎在山中流浪。你到底屬於何者?要不是因為司祭的自尊和義務的觀念,或許我也跟吉次郎一樣踏了聖像。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主角是吉次郎無誤。本來在洛特里哥心目中的吉次郎,是個最卑下的人,較諸惡人猶為不如;因為惡人還有惡人的力與美,但是吉次郎卻如骯髒的破衣服。可是,以基督為典範的洛特里哥想到,聖經上基督所尋找的,不是像患了血漏的女人,就是如被扔石頭的娼婦般、毫無吸引力,一點也不美的人。基督就是愛;然而喜歡有吸引力的、美的東西,這是誰都能辦得到的,那不是愛。不捨棄已褪色、如襤褸般的人和人生,那才是真正的愛。司祭不能無視於弱者吉次郎的存在,最俊答應吉次郎的要求,聽了他的告解,也為他祈禱「你安心去吧!」告解是天主致七大奧蹟之一,也就是全能的神對人的救贖:換言之,也是神的愛的表徵。「沒有所謂的強者與弱者。誰又能斷言弱者一定不比強者痛苦呢?」司祭最後悟出的這句話,為弱者下了最好的註腳!
《沉默》中所探討的問題,除了上述三個主題之外,其實還涉及到諸如天主教在日本的改變,以及紮根的問題。洛特里哥與費雷拉的精采對答,道出了遠藤針對天主教土著化的獨特看法;類似的觀點,其實遠藤在初期的評論(諸神與神)與(不合身的西裝)中已明顯指出,在此不再贅述。「棉花的行列」的詩句,不禁衝口而出:「棉花的行列」暗示著「神的羔羊」。《沉默》中,洛特里哥被關在黑漆漆的圍牆內。這黑漆漆是死亡與誕生毗鄰而居的,原初的黑暗,也是女性子宮的象徵。洛特里哥在這裡描繪的基督的臉「以含著溫柔的眼光注視著自己」,那份「溫柔」,無疑的是母性的溫柔,也難怪乎司祭想接近衪。當司祭在心中作最後決定,要踐踏聖像時,黎明的曙光——象徵著神的恩寵——迎接著他。
另外,吉次郎向官吏密告洛特里哥藏身處時,作者以蜥蜴象徵吉次郎。「陽光下,我發覺蜥蜴偷瞄著我的膽怯的臉孔,跟剛剛走掉的吉次郎一模一樣。」尾巴對蜥蜴而言,代表著什麼呢?在形態上沒了尾巴不算完全,但卻不致於威脅到生命的持續;另一方面,蜥蜴沒了尾巴仍會自然再長出來,這下也象徵著吉次郎屢次出賣神父,作出棄教的行為,可是,過一段時間,如尾巴自然長出般,信仰也在吉次郎心中再生長嗎?
結語
《沉默》是遠藤文學的第二高峰(第一高峰為《海與毒藥》),其中所包含的意義,絕非這篇(導讀)所能道盡的。故事的背景雖然在日本,但是遠藤所要探討的卻是普遍性的東西,信仰以及東西文化之異同等等,又何嘗不是我們切身的問題呢?!
書摘/試閱
有一份報告送到羅馬教會,內容中指出:由葡萄牙的耶穌會派往日本的費雷拉.克里斯多夫教父在長崎遭受到「穴吊」的拷刑,已宣誓棄教。這位教父在日本定居了三十三年之久,身居教區長之最高職位,是統率司祭與信徒的長老。
這位教父神學造詣之深,堪稱稀世之才。在德川幕府禁教令下仍潛伏於京都、大阪一帶傳教不輟。他在信中經常表現出堅定不移的信念,因此無論遭遇到任何情況,大家都不相信他會背叛教會。在教會中或耶穌會裡,也有很多人認為那份報告可能是出自異教徒的荷蘭人或日本人捏造的,也可能是誤傳的。
從傳教士的來信中,羅馬教會對在日本傳教的種種困難當然非常了解。自從一五八七年之後,日本的諸侯豐臣秀吉改變以往的政策,開始迫害天主教。他首先在長崎的西坂將二十六名司祭和信徒處以焚刑,還把各地許多的天主教徒驅出家門,施以拷打、殘殺。德川將軍對這政策採取蕭規曹隨,於一六一四年決定將所有天主教的神職人員驅逐出境。
根據傳教士們的報告,這一年的十月六日和七日兩天,包括日本人在內的七十幾名司祭被迫在九州和木缽集合之後,押上開往澳門、馬尼拉的五艘帆船,驅逐出境。那是個下雨的日子,灰色的海上波濤洶湧,在雨中,船從海灣穿向海角,消失於水平線的彼方。儘管日本政府已頒佈了嚴厲的驅逐令,其實還有三十七位司祭,不忍心捨棄信徒,化明為暗仍潛伏在日本並未離去;費雷拉教父就是其中之一。他不斷寫信把陸續被捕、被處死的司祭和信徒的情形向上司報告。他在一六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從長崎寄給巡察師安特列.巴爾美洛神父的信函,現在都還保留著呢!信上對當時的情形有詳細的說明:
我在前一封信中已向您報告本地天主教的情形,現在繼續向您報告後來發生的事。所有的威脅和壓迫方式都跟以往不同。就讓我先從一六二九年之後,五名因信仰問題而被捕的修道士身上所發生的事開始談起吧!那五人即巴爾特洛美.古奇耶列斯、方濟.德.赫斯、比仙提.德.安東尼歐等三位奧古斯汀會士,和我們耶穌會的石田安東歐修士,還有方濟會的卡布列耶魯.德.聖.馬答列納神父。長崎奉行竹中采女強迫他們棄教,並藉此嘲弄我們神聖的教義和祂的僕人,挫信徒們的勇氣;不過,采女很快就了解到光是語言改變不了神父們的決心,因此,他決定改弦易轍利用雲仙地獄的熱水來「侍候」他們。采女下令:將五名司祭帶到雲仙,用熱水「拷問」他們,直到他們放棄自己的信仰為止,但絕不能殺掉他們。除了這五人之外,安東尼歐.達.西魯之妻貝亞特麗吉.達.柯絲達和其女兒瑪利亞,也因為采女長時間勸她們棄教都相應不理,亦被一併處理。
十二月三日,他們從長崎出發前往雲仙。兩名女性坐轎,五名修道士騎馬,和眾
人分別。來到距離不過一reguwa的日見港時,手就被綁起來,連腳也被扣上腳鐐。上了船之後,一個個被分開緊緊地綁在船舷旁邊。
傍晚,他們抵達雲仙山麓的小浜海港。翌日,上山之後,七個人分別被關進小屋裡,手銬腳鐐日夜不離身,還有護衛嚴密監視著。儘管采女的部下人數眾多,代官仍然派遣警吏嚴加戒備。在通往山上的各條路上,均派人監視,除非有官方的通行證,否則一律不准通行。
第三天進行拷問──首先把七個人單獨帶到池邊,強迫他們看著滾燙的池水濺起泡沫,希望他們在嘗到皮肉之苦以前,能放棄天主教的信仰。由於天寒地凍,滾燙的池水更是懾人魂魄,要不是有神的護佑,光看這情景就足以令人昏厥;但是,因為所有的人都有神的支持,勇氣倍增,嚷著快拷問吧!我們絕不放棄自己的信仰。官吏們聽到這堅決的回答,馬上命令他們脫掉衣服,用繩子綁住他們的手腳,然後用半加侖容量的杓子舀熱水淋在他們身上──那還不是一口氣全部倒下去,而是在杓子底下鑽了幾個洞,讓熱水慢慢流下,使痛苦延長。
天主教的英雄們,身子一動也不動地忍受著這種恐怖的痛苦,只有年輕的瑪利亞受不了痛苦而仆倒在地。官吏看到了叫著「棄教了!棄教了!」他們把少女抬到小屋裡,準備翌日送回長崎。瑪利亞拒絕回去,堅決表明自己並未棄教,要和母親和其他人一起接受拷問,但是官吏不從。
其餘六人繼續留置山上,度過三十日。其間,安東尼歐、方濟兩神父和貝亞特麗吉各受到六次熱水的拷問,比仙提神父四次,巴爾特洛美神父和卡布列耶魯神父各兩次,他們連哼一聲都沒有。
安東尼歐神父和方濟、貝亞特麗吉所受的拷問時間比其他人都長,尤其是貝亞特麗吉,雖然身為女性,但是在各種刑罰加身、勸告時,都表現出巾幗不讓鬚眉的勇氣,因此,除了嘗到澆熱水的痛苦之外,還遭受各種刑罰,被迫長時間站在小石頭上挨人辱罵;然而,官吏們越是憤怒,她越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其餘的人由於身體孱弱又有病在身,並未遭到太大的折磨。采女本無殺他們之意,只是希望他們棄教罷了,還特別派了一位醫生到山上來替他們療傷。最後采女覺悟到無論採取任何手段,自己是贏不了的。部下反而向他報告:從神父們的勇氣和力量來看,恐怕在他們還沒來得及改變心意之前,雲仙的所有泉水和池水已先告罄。於是,他決定把神父們送回長崎。一月五日,采女把貝亞特麗吉.達.柯絲達收容在某來歷可疑者的家裡,並把五名神父關入城內的監獄。他們目前還在該監獄裡。我們神聖的宗教終於粉碎了暴君采女先前的計畫、期待,不但贏得大眾的讚揚,更增加了信徒們的勇氣,戰績顯赫。
羅馬教會相信寫這樣的信的費雷拉教父,即使受任何的拷問,也不會放棄神和教會而向異教徒屈服。
一六三五年,以羅比諾神父為主,有四名司祭在羅馬聚會。他們為了洗刷費雷拉棄教的恥辱,計畫無論如何也要偷渡到日本那天主教遭受到迫害的國度裡偷偷傳教。
這種有勇無謀的計畫,教會當局一開始就不贊成。以上司的立場,對他們的熱忱和傳教精神表示讚賞;可是,要把司祭們送到極為危險的異教徒國家,卻不表贊同。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自從聖方濟.薩比耶爾之後,天主教在東方的日本已播下最佳種子,如果因為失去了領導者而使信徒逐漸減少,也很值得重視。不僅如此,從當時的歐洲人眼中看來,費雷拉教父在世界盡頭的一個蕞爾小國被迫棄教,這件事不只是他個人的挫折,同時也是整個歐洲信仰、思想的恥辱和失敗。在這種強烈意識下,經過幾番波折,最後還是准許羅比諾神父和四名司祭渡日。
另外,葡萄牙方面也有三名年輕司祭依不同的理由計畫偷渡赴日。他們是從前費雷拉教父在卡姆波里特左修道院教書時的神學生──佛朗西斯.卡爾倍、赫安提.聖.馬太和薛巴斯強.洛特里哥等三人。他們可以接受恩師費雷拉已光榮殉教的說法,但是他們無論如何都不相信恩師會像狗一樣屈服在異教徒面前。其實,這不只是三名年輕人的共同看法而已,也是所有葡萄牙神職人員的一致心情。三人準備親自到日本調查事情的真相。這裡的情形也跟義大利方面差不多,最初上司也不答應,後來被他們的熱誠所感動,最後允許他們到日本做危險的傳教活動。這是一六三七年的事。
三名年輕司祭馬上準備做長途旅行。當時葡萄牙傳教士要到東方來,通常都先搭乘從里斯本開往印度的印度艦隊,那時印度艦隊的啟航是里斯本市最熱鬧的活動之一。在三人印象中地球盡頭的東方,而且是最邊緣的日本,現在形狀鮮明地浮現在眼前。翻閱地圖時,非洲的對面是葡萄牙、印度,印度前面有眾多的島嶼和亞洲的國家分佈著,而日本的形狀活像一條幼蟲,在東邊爬行,要摸索到那裡,必須先到印度的臥亞,然後渡過許多大海、歷經長期的歲月才能抵達。臥亞,自從聖方濟.薩比耶爾之後,已成為東方傳教的踏腳石。在這裡的兩所聖保祿神學院有從東方各地前來留學的神學生,同時這裡也是發願一輩子都為主服務的歐洲司祭了解各國情況,和為了搭船前往各國需要等候一年半載的候船處。
他們三人盡一切可能去了解日本,幸好路易.佛洛依斯之後,已有許多葡萄牙傳教士從日本送回情報。據說新的將軍德川家光所採取的高壓政策,比起祖父和父親時代更為嚴苛,尤其是長崎地方,自從一六二九年暴虐殘酷的竹中采女任長崎奉行後,常用嚴刑加諸信徒身上,把滾燙的溫泉淋到囚犯身上,強迫棄教,有時候一天的犧牲人數不下六、七十人。費雷拉教父本身也曾經把這情形向祖國報告,所以傳說中的應該是事實。總之,他們一開始就覺悟到在長途而艱辛的旅途結束之後,等候著他們的是比旅途更為嚴厲、無情的命運。
薛巴斯強.洛特里哥一六一○年出生於以礦山聞名的達斯可城,十七歲入修道院,赫安提.聖.馬太和佛朗西斯.卡爾倍出生於里斯本,兩人與洛特里哥一起在卡姆波里特左修道院受教育。他們三人在神學院時,讀書、生活都在一塊兒,對教授自己神學的費雷拉教父記憶猶新。
洛特里哥他們猜想,費雷拉老師現在一定還活在日本的某個地方。有著碧藍而清澄的眼睛,充滿著慈祥光輝的費雷拉老師的臉,受到日本人的拷刑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他們無論如何想像不出受屈辱而扭曲的臉是什麼樣子?他們不相信費雷拉老師會拋棄神、拋棄他的慈祥。洛特里哥和他的同伴無論如何要到日本,探查老師是生或死。
一六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三人搭乘的印度艦隊在貝列姆要塞的大砲祝賀下,從泰約河口出發。他們接受了約翰.達西哥主教的祝福之後,就上了司令官搭乘的「聖.依莎貝爾號」艦。艦隊駛出黃色的河口,在藍色的大海航行時已是正午時分。他們靠著甲板,眺望閃亮著金光的海角、山巒以及農家的紅牆和教會。歡送艦隊的教會鐘聲,隨風飄送到甲板上來。
當時,要到東印度就必須繞到非洲的南端。這支艦隊在出發的第三天,於非洲西岸遇到暴風雨。
四月二日,艦隊抵達波爾多.珊特島,不久過馬迭納島,六日抵達加納利亞諸島之後,雨下個不停又碰到無風狀態。後來,被潮流從北緯三度線沖回五度,撞到幾內亞海岸。
無風時,酷暑難耐,再加上各船均有多人生病,「聖.依莎貝爾號」的船員躺在甲板和床上呻吟的病人也逾百人。洛特里哥和船員忙著看護病人,幫他們放血。
七月二十五日,聖雅各節日,船好不容易才繞過好望角。繞過好望角的那天,又遇到暴風來襲,船的主帆斷裂,掉到甲板上發出巨大聲響。病人和洛特里哥他們都加入搶救的行列,當他們準備搶救前部帆時,船觸礁了,幸好有其他船艦馬上來救援,否則「聖.依莎貝爾號」可能就這樣沉入海底呢!
暴風雨來襲之後,又碰到無風狀態。主帆無力地下垂,只有黑影落在躺於甲板上如死人般的病人的臉和身上。海面上每天閃鑠著燠熱的亮光,看不到微波蕩漾。船航行的日期越長,食糧和水分越缺乏。到達目的地臥亞時已是十月九日。
他們在臥亞所得到的有關日本的情報,比在祖國時更為詳細。據說:就在他們三人出發的那年一月起,有三萬五千名日本的天主教徒起義,以島原為中心和幕府軍苦戰的結果,不分男女老幼全都被殺個精光。這次戰爭結束後,當地變成杳無人跡的荒地,殘存的天主教徒也被像打虱子般消滅淨盡了。不僅如此,對洛特里哥他們打擊最大的消息是,由於這次的戰爭,日本已和葡萄牙全面斷絕通商和貿易,更禁止葡萄牙船入境。
三名司祭知道祖國的船隻不能開往日本之後,懷著絕望的心情來到澳門。這個城市是葡萄牙在極東的根據地,同時也是日本和中國貿易的基地。他們抱著幾許僥倖的期待來到這裡,但很快就受到巡察師威利也諾神父嚴厲的警告。神父說在日本傳教根本不可能,而且澳門的傳教會也不打算利用危險的方法送傳教士到日本。
這位神父十年前就在澳門成立傳教學院,培養傳教士到日本和中國傳教。自從日本禁教之後,也委託他代為管理在日本的耶穌會。
威利也諾神父對三人登陸日本後要尋找的費雷拉教父的說明如下:「自從一六三三年之後,潛伏在日本的傳教士的音信就完全斷絕了。聽從長崎回到澳門的荷蘭船員說,費雷拉教父已被捕,在長崎遭受到『穴吊』的拷刑。由於那艘荷蘭船在費雷拉教父遭受到『穴吊』拷刑的那天啟航,因此以後的事就不得而知了。在當地打聽到的是:由新上任的宗教負責人井上筑後守審問費雷拉教父。」威利也諾神父明白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以澳門傳教會的立場無法同意他們到日本傳教。
現在,我們還可以從葡萄牙「海外領土史研究所」所藏的文書中,看到幾封洛特里哥書函。他的第一封書信如上述,是從他跟兩個同事自威利也諾神父處聽來有關日本的情勢開始寫起的。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