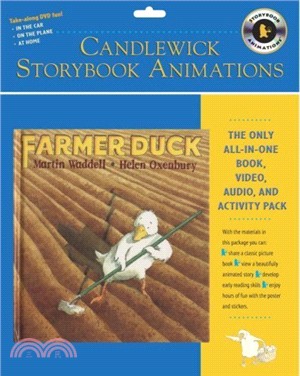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余華第一本全面闡述創作觀、文學觀訪談集
商品資訊
系列名:余華作品集
ISBN13:9789863447184
替代書名: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
出版社:麥田
作者:余華
出版日:2020/01/02
裝訂/頁數:平裝/280頁
規格:21cm*14.8cm*2cm (高/寬/厚)
商品簡介
為什麼寫作?
小說無法改變社會現實,但可以改變讀者對社會現實的看法。
作品翻譯超過40個國家版本、全球銷量累計超過三千萬冊;
華文世界最暢銷的重要文學小說家——
余華第一本全面闡述他的創作觀、文學觀 訪談集
‧卡夫卡對我來說是思想的解放,而川端康成教會了我寫作的基本方法。
‧不是我喜歡用荒誔的方式寫作,而是中國社會充滿了荒誕。
‧一部優秀的小說在敍述上應該是自由的。
‧長篇小說有足夠的時間傾聽虛構人物的聲音。
‧生活只有不斷地去經歷,才能知道生活是什麼;寫作只有不斷地去寫,才會知道寫作是什麼。
‧我寫了那麼多年以後才真正知道一個道理,就是你用一種最誠實的方式去寫小說是最困難的。但是,也就是這種最誠實的寫作,才造就了我們這個世界上那些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小說。
……
《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是余華接受來自世界各方的訪談集結,針對他的創作觀及文學觀、影響他創作的內在外在因素,作了一番文學的深度探討與答辯。
余華從自己的作品《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第七天》……談起,從一部作品如何尋得雛型、對人物的刻畫、創作角度的思索到如何修改完成,余華毫無保留地,逐一細細反芻,吐露他的寫作過程,直探作品核心;關於他小說中形塑的人物之人性、記憶、童年等情狀,精準而動人的描寫,余華藉此回頭思索,他確信寫作的思考本質與對人的理解從來是一致而不悖逆的;文學是不可能改變現實社會的,但是可以影響和改變讀者對於社會的看法,對於現實的感受。
余華也談到閱讀對他的影響。從川端康成、卡夫卡、普魯斯特、海明威,到魯迅、布爾加科夫、馬奎斯、波赫士……余華談到這些大師作品對他的啟發、體會,他往往能從一些不經意的地方,發現我們一般閱讀上難以關注的奇妙內涵。余華認為,對好作品的精細閱讀,讓他在創作時,處理人的生命狀態、確立敘事哲學等,有很大的幫助。
余華說,寫作不論寫什麼故事,裡面所有的人物和所有的場景都不由自主地屬於故鄉。他愈來愈強烈感受到,寫作和家鄉存在著一種「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的情感連結。只有在不寫作的時候,余華才會猛然想起自己是在北京生活……
為什麼要寫作?余華詰問自己。他認為,寫作讓人擁有兩條人生道路,一條是現實的,一條是虛構的。當現實的人生道路越來越貧乏之時,虛構的人生道路就會越來越豐富。作為一個作家,藉由小說可以改變讀者對社會現實的看法,這是讓余華感到自豪的理由。
這部訪談集,是余華最真摯且誠懇的創作答辯。歸結一切,他認為,寫作其實和生活一樣,生活只有不斷地去經歷,才能知道生活是什麼;寫作只有不斷地去寫,才會知道寫作是什麼。
作者簡介
余華
1960年出生,1983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兄弟》、《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呼喊與細雨》、《第七天》、《十個詞彙裡的中國》等。其作品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瑞典、挪威、丹麥、芬蘭、希臘、俄羅斯、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塞爾維亞、波黑、斯洛維尼亞、波蘭、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土耳其、巴西、以色列、埃及、科威特、沙特、蒙古、日本、韓國、越南、泰國、印度、斯里蘭卡和印尼等4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曾獲義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1998),法國文學和藝術騎士勳章(2004),法國國際信使外國小說獎(2008),義大利朱塞佩.阿切爾比國際文學獎(2014),塞爾維亞伊沃.安德里奇文學獎(2018),義大利波特利.拉特斯.格林扎納文學獎(2018)等。
【余華作品及獲獎紀錄】
長篇小說──
第七天
.第12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作家」(2014)
.義大利波特利‧拉特斯‧格林扎納文學獎(2018)
兄弟(上部、下部)
.博客來網路書店年度之最/文學小說(2005)
.新浪圖書年度風雲榜(2006)
.《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小說(2006)
.法國首屆「國際信使」(Prix Courrier International)外國小說獎(2008)
.瑞士《時報》2000至2010世界最重要的十五部小說之一(2009)
.法國《世界報》二戰結束以來世界最具影響的一百部小說之一(2019)
活著
.香港「博益」十五本好書獎(1994)
.台灣《中國時報》十大好書獎(1994)
.張藝謀根據《活著》改編導演的同名電影獲法國坎城電影節評委會大獎和最佳男演員獎(1994)
.義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最高獎項(1998)
.第三屆世界華文冰心文學獎(2002)
.入選香港《亞洲週刊》評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強」(2005)
.入選中國百位批評家和文學編輯評選的「二十世紀九○年代最有影響的十部作品」
.義大利朱塞佩.阿切爾比國際文學獎(2014)
許三觀賣血記
.入選韓國《中央日報》評選的「一○○部必讀書」(2000)
.入選中國百位批評家和文學編輯評選的「二十世紀九○年代最有影響的十部作品」
呼喊與細語
.余華因此書榮獲法國文學和藝術騎士勳章(2004)
中短篇小說集──
世事如煙
我膽小如鼠
黃昏裡的男孩
現實一種
戰慄
鮮血梅花
.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2002)
散文集──
十個詞彙裡的中國
.英國PROSPECT週刊年度最佳圖書(2012)
錄像帶電影
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相關著作:《我只知道人是什麼》《兄弟(上)十週年特別紀念版》《兄弟(下)十週年特別紀念版》《黃昏裡的男孩(新版)》《第七天》《活著(二十週年精裝珍藏版)》《錄像帶電影--從中國到世界,余華的35則文學、文化、政治、時事觀察體驗》《許三觀賣血記》《十個詞彙裡的中國》《呼喊與細雨》
序
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
關於寫作
楊紹斌(自由寫作者):你通常是怎麼構思一篇小說的?
余華:我寫作的開始五花八門,有主題先行,也有的時候是某一個細節、一段對話或者某一個意象打動了我,促使我坐到了寫字桌前。
楊紹斌:《活著》這部小說裡福貴這個形象有來源嗎?
余華:福貴最早來到我腦子裡時是這樣的,一個老人,在中午的陽光下犁田,他的臉上布滿了皺紋,皺紋裡嵌滿了泥土。
楊紹斌:許三觀呢?
余華:他最早的形象是在冬天的時候穿著一件棉襖,鈕釦都掉光了,腰上繫著一根草繩,一個口袋裡塞了一只碗,另一個口袋裡放了一包鹽。但是,這是我開始寫作時的形象,構思的時候還不是這樣。
楊紹斌:那又是怎麼樣的?
余華:關於《活著》,我最早是想寫一個人和他生命的關係,這樣的關係在很長時間裡都讓我著迷,這有點主題先行,可是我一直不知道這篇小說應該怎麼寫。有一天早上醒來時,我對陳虹(作者太太)說,我知道怎樣寫這篇小說了,因為我想出了題目,叫《活著》。陳虹說這個題目非常好。就是因為有了這個標題,才有了這部小說。有時候一個標題也會讓你寫出一部小說。一九八○年代的時候,文學界批判過主題先行的寫作方式,其實完全沒有道理,寫作什麼方式都可以,條條大路都通羅馬。至於《許三觀賣血記》,最早是這樣的,大概是在一九九○年,我和陳虹在王府井的大街上,突然看到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淚流滿面地從對面走了過來。我們當時驚呆了,王府井是什麼地方?那麼一個熱鬧的場所,突然有一個人旁若無人、淚流滿面地走來。這情景給我們的印象非常深刻。到了一九九五年,有一天中午,陳虹又想起了這件事,我們就聊了起來,猜測是什麼使他如此悲哀?而且是旁若無人的悲哀!這和你一個人躲到衛生間去哭是完全不一樣的。
楊紹斌:所以後來在小說裡,許三觀在大街上哭。
余華:這已經是最後一章了。那天,我們兩個人不斷猜測使那位老人悲哀的原因,一直沒有結果。又過了幾天,我對陳虹說起我小時候,我們家不遠處的醫院供血室,有血頭,有賣血的人。我說起這些事時,陳虹突然提醒我,王府井哭泣的那位老人會不會是賣血賣不出去了,他一輩子賣血為生,如果不能賣了,那可怎麼辦?我想,對,這小說有了。於是我就坐下來寫,就這麼寫了八個月。
楊紹斌:許三觀後來就賣不了血。
余華:當時我認為小說最後的高潮,就是他賣不了血,所以他就在大街上旁若無人地哭,因為這意味著他失去了養活自己的能力,他的悲哀是絕望以後的悲哀。這對年輕人來說沒什麼,可是對一個老人就完全不一樣了。我曾經準備在這最後的一章裡重重地去寫,準備將自己吃奶的力氣都寫光,將這一章充分渲染。可是當我寫完第二十八章,也就是結尾前的一章後,我才知道敘述高潮其實是在這一章,就是許三觀一路賣血去上海的那一章,於是最後一章我用輕的方式完成了。根據我寫作和閱讀的經驗,兩個很重的章節並排在一起,只會互相抵消敘述的力量。
楊紹斌:這麼說來,你在動手寫作時,對筆下的人物已經胸中有數了?
余華:還是沒數,其實我根本不知道接下來他會幹什麼,最多只能先給他一些設計,而且有些還用不上。
楊紹斌:你現在還擬提綱嗎?
余華:我在舊信封上做筆記。開始時我怕自己忘了,就隨手拿起一個舊信封記上,一個記滿了,再用第二個,為了風格的統一,我接下去仍然用舊的信封。像《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我都寫滿了一堆舊信封。現在我開始用新的信封,而且必須是國際航空的那一種,上面沒有郵遞區號的紅框,顯得更乾淨。這已經成為了我的寫作習慣。當我寫一部長篇小說的時候,我只要知道開頭一萬多字怎麼寫就行了,後面肯定會出來。要是一萬字寫完了,後面還不出來,那就不應該寫了。這和我早期的寫作已經很不一樣了。我以前小說裡的人物,都是我敘述中的符號,那時候我認為人物不應該有自己的聲音,他們只要傳達敘述者的聲音就行了,敘述者就像是全知的上帝。但是到了《呼喊與細雨》,我開始意識到人物有自己的聲音,我應該尊重他們自己的聲音,而且他們的聲音遠比敘述者的聲音豐富。因此,我寫《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的過程,其實就是對人物不斷理解的過程,當我感到理解的差不多了,我的小說也該結束了。我想起來,一九八七年在黃山的時候,有一天傍晚我和林斤瀾(《北京文學》主編)一起散步,他告訴我有一次他和汪曾祺一起去看望沈從文先生,他問沈先生小說應該怎麼寫,沈先生只回答了一個字:貼。就是說貼著人物寫。這個字說得好!可是當時我沒有很深的感受,現在我才發現的確如此,貼—其實就是源源不斷地去理解自己筆下的人物,就像去理解一位越來越親密的朋友那樣,因此生活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豐富,就是我自己也要比我所認為的要豐富的多。
楊紹斌:你對小說的開頭一句敏感嗎?
余華:非常敏感。第一句要是寫不好,下面的話就白寫了。小說的第一句話,就好比一個人剛從子宮裡出來,要是腦袋擠扁了,這個人就不會聰明。
楊紹斌:你喜歡在白天還是晚上寫作?
余華:不分白天晚上,我只要吃飽了和睡足了,任何時候都能寫作。
楊紹斌:你寫得慢嗎?
余華:我現在比以前快多了。我現在真正寫作的時間不多,一旦寫起來,就很快。我覺得寫作也是一門手藝,熟練之後工作就會變得輕鬆起來;可是另一方面,壓力也加重了,我現在已經寫了一百多萬字了,這對我來說是個包袱,我應該如何去面對我過去的作品?有時候這是很困難的。
楊紹斌:有些作家總是愈寫愈困難。
余華:所有的作家都應該是愈寫愈困難,當我擁有二百多萬字的作品時,我想我會更困難。我慶幸人不能活得更長久,要不這作家沒法當了。如果我能夠活五百年,那麼六十歲以後我肯定不當作家了。
楊紹斌:你在寫作中會碰到哪些具體的困難?
余華:可以說非常多。有很多都是細部的問題,這是小說家必須去考慮的,雖然詩人可以對此不屑一顧,然而小說家卻無法迴避。所以我經常說,小說家就像是一個村長,什麼事都要去管。
楊紹斌:他得充分顧及到細節的清晰和真實。
余華:是的,比如說福貴這個人物,他是一個唯讀過幾年私塾的農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農民的身分來完成的,讓這樣一個人來講述自己,必須用最樸素的語言去寫,必須時刻將敘述限制起來,所有的語詞和句式都為他而生,因此我連成語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連孩子們都願意使用的成語,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
楊紹斌:它對你的限制很大。
余華:是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樣的寫作就放棄了敘述上的追求,相反,這時候的敘述更需要作家下功夫。比如小說中有這麼一段,就是有慶死後,福貴瞞著家珍將有慶埋在一棵樹下,然後他哭著站起來,他看到那條通向城裡的小路,有慶生前每天都在這條小路上奔跑著去學校,這時福貴再次去看這條月光下的小路。我感到必須寫福貴對小路的感受,如果不寫,作為一個作家是不負責任的,可是如何去寫?我記得自己曾經在《世事如煙》裡有過這樣的描述,說月光下的道路像河流一樣,閃爍著蒼白的光芒。如果這時候用這樣的句子來描述一個失去了兒子的父親,顯然是太不負責任了。為了找到一個合適的意象,我費了很長時間,最後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意象—鹽,我這樣寫道:那條通向城裡的小路在月光下像是撒滿了鹽。對於一個農民來說,鹽是很熟悉的;另一方面,又符合他當時的心情,就像往他傷口上撒了鹽一樣。
楊紹斌:是的,我讀到這一段時很感動。
余華:有時候寫作中碰到的困難,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可是會陰差陽錯地要了作家的命,甚至會讓作家感到自卑,感到自己再也寫不下去了,吃不下飯也睡不著覺,可是後來他會突然發現那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問題,隨手一寫就解決了。就像是抱著孩子到處找孩子,戴著眼鏡到處找眼鏡,就是這樣的困難,會讓作家寫作的過程愈拉愈長。
楊紹斌:具體說呢?
余華:我一下子想不起來具體的例子,但它確實是我寫作時隨時都要遇到的困難。可以這麼說,什麼是敘述?它在確立前其實就是一堆雜亂無章的困難,寫作的過程就是不斷地和它們相遇的過程,不斷地去克服它們的過程,最後你才會發現一個完整的敘述成立了。我在寫《許三觀賣血記》時,碰到這樣一個難題,那就是如何讓許玉蘭給許三觀生下三個兒子。在其他方式的敘述裡,這一章可以不寫;可是在這部作品中,我覺得必須寫。雖然這部作品是跳躍的,而且十分簡潔,可是它在敘述上對人物每一段經歷都是無微不至的關懷。後來,我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辦法,讓許玉蘭罵起來。這是第四章,整個一章,都是許玉蘭躺在醫院的產台上罵許三觀。生第一個兒子時,許玉蘭罵得仇恨無比;第二個罵到一半時,孩子出生了;第三個才罵了兩聲,孩子就出來了。不是有個說法嗎,女人在生孩子時是很恨男人的。許玉蘭在產台上罵了三次,敘述裡的時間一下子過去了很多年。其實這樣的方式我在〈我沒有自己的名字〉裡就已經使用過了,我讓來發將父親三十多年間對他說的話在一個句子裡完成。一個一百多字的句子一下子將三十年的時間打發走了,這是我寫作最得意的時候。人的記憶就是這樣,我父親在三十年間對我說的不同的話,我可以在一分鐘裡集中起來。
楊紹斌:你修改嗎?
余華:我是一個熱愛修改的作家,我覺得修改是一種享受,而且修改的過程是我對自己內省的過程,對我以後的寫作都會有說明。
楊紹斌:你是否跟別人談論你正在寫的小說?
余華:以前經常談,現在不談了。以前我的寫作方式決定了我可以和別人談,因為在寫之前我已經知道得很多;現在我寫之前知道的不多了,所以我不談了。
楊紹斌:你對自己的小說語言有些什麼要求?
余華:我對語言只有一個要求:準確。一個優秀的作家應該無休止地剝削自己的才能,讓語言發揮出最大的能量。魯迅就是這樣的作家,他的語言像核能一樣,體積很小,可是能量無窮。作家的語言千萬不要成為一堆煤,即便堆得像山一樣,能量仍然有限。
楊紹斌:你離開海鹽去北京也有十多年了,脫離家鄉的語境和生活,這種遷移本身以及由此而來的一系列變化,對你的寫作有什麼樣的影響?
余華:影響是多方面的,不過決定我今後生活道路和寫作方向的主要因素,在海鹽的時候已經完成了,應該說是在我童年和少年時已經完成了。接下去我所做的不過是些重溫而已,當然是不斷重新發現意義上的重溫。我現在對給予我成長的故鄉有著越來越強烈的感受,不管我寫什麼故事,裡面所有的人物和所有的場景都不由自主地屬於故鄉。
楊紹斌:你認為你的寫作和家鄉存在著一種什麼樣的聯繫?
余華: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當我不寫作的時候,我才想到自己是在北京生活。
關於閱讀
楊紹斌:你喜歡哪些作家?
余華:我喜歡的作家太多了。
楊紹斌:最早的時候你喜歡川端康成。
余華:是的。一九八○年,我在寧波的時候,在一個十多個人住的屋子裡,在一個靠近窗口的上舖,我第一次讀到了他的作品,是《伊豆的舞女》,我嚇了一跳。那時候中國文學正是傷痕文學的黃金時期,我發現寫受傷的小說還有另外一種表達,我覺得比傷痕文學那種控訴更有力量。後來,有五、六年的時間,我一直迷戀川端康成,那時候出版的所有他的書,我都有。但長期迷戀一位作家,對一個寫作的年輕人來說,肯定是有害的。接下來是卡夫卡(Franz Kafka),我最早在《世界文學》上讀過他的《變形記》(Die Verwandlung),印象深刻,過了兩年,我買到了一本《卡夫卡小說選》,重新閱讀他的作品,這一次時機成熟了,卡夫卡終於讓我震撼了。我當時印象很深的是《鄉村醫生》(Ein Landarzt)裡的那匹馬,我心想卡夫卡寫作真是自由自在,他想讓那匹馬存在,馬就出現;他想讓馬消失,馬就沒有了。他根本不作任何鋪墊。我突然發現寫小說可以這麼自由,於是我就和川端康成再見了,我心想我終於可以擺脫他了。
楊紹斌:大概就是在那個時期,你寫出了〈十八歲出門遠行〉。
余華:是的,我寫出了〈十八歲出門遠行〉,當時我很興奮,發現寫出了一篇讓自己都感到意外的小說,不過我還是沒有把握,剛好我要去北京,去參加《北京文學》的筆會,就將小說拿給李陀(《北京文學》副主編)看,李陀看完後非常喜歡,他告訴我,說我已經走到中國當代文學的最前列了。李陀的這句話我一輩子都忘不了,就是他這句話,使我後來愈寫膽子愈大。
楊紹斌:就是說卡夫卡成了你創造力的第一個發掘者。
余華:可以這麼說。不過我現在回頭去看,川端康成對我的幫助仍然是至關重要的。在川端康成做我導師的五、六年時間裡,我學會了如何去表現細部,而且是用一種感受的方式去表現。感受,這非常重要,這樣的方式會使細部異常豐厚。川端康成是一個非常細膩的作家。就像是練書法先練正楷一樣,那個五、六年的時間我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寫作基礎,就是對細部的關注。現在不管我小說的節奏有多快,我都不會忘了細部。所以,卡夫卡對我來說是思想的解放,而川端康成教會了我寫作的基本方法。在喜歡川端康成的那幾年裡,我還喜歡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還有英國女作家曼斯費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等等,那時候我喜歡的作家都是細膩和溫和的。卡夫卡之後,我開始喜歡敘述和情感都很強烈的作家。現在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發現我喜歡的作家越來越多了,而且已經沒有風格上的局限了。
楊紹斌:你說說看,還有哪些作家?
余華:比如說魯迅。魯迅是我至今為止閱讀中最大的遺憾,我覺得,如果我更早幾年讀魯迅的話,我的寫作可能會是另外一種狀態。我讀魯迅讀得太晚了,雖然我在小學和中學時就讀過。
楊紹斌:因為原先幾乎是一種被動接受。
余華:其實魯迅是不屬於孩子們的。我驚訝地發現,我小時候背過的〈孔乙己〉、〈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作品,當我前年重讀時,就像是第一次閱讀,讀完了才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可見那時候我其實是沒有閱讀魯迅,或者說只是旅遊而已,現在我的閱讀是在魯迅的作品裡定居了。重讀魯迅完全是一個偶然,大概兩三年前,我的一位朋友想拍魯迅作品的電視劇,他請我策畫,我心想改編魯迅還不容易,然後我才發現我的書架上竟然沒有一本魯迅的書,我就去買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魯迅小說集》,我首先讀的就是〈狂人日記〉,我嚇了一跳,讀完〈孔乙己〉後我就給那位朋友打電話,我說你不能改編,魯迅是偉大的作家,偉大的作家不應該被改編成電視劇。我認為我讀魯迅讀得太晚了,因為那時候我的創作已經很難回頭,但是他仍然會對我今後的生活、閱讀和寫作產生影響,我覺得他時刻都會在情感和思想上支援我。
魯迅可以說是我讀到過的作家中敘述最簡潔的一位,可是他的作品卻是異常的豐厚,我覺得可能來自兩方面,一方面魯迅在敘述的時候從來不會放過那些關鍵之處,也就是說對細部的敏感。要知道,細部不是靠堆積來顯示自己的,而是在一些關鍵的時候,又在一些關鍵的位置上恰如其分地出現,這時候你會感到某一個細部突然從整個敘述裡明亮了起來,然後是照亮了全部的敘述。魯迅就是這麼奇妙,他所有精彩的細部都像是信手拈來,他就是在給《吶喊》寫自序時,寫到他的朋友金心異來看望他,在如此簡潔的筆調裡,魯迅也沒忘了寫金心異進屋後脫下長衫的一筆。看上去是閒筆,其實是閒筆不閒。用閒筆不閒來說魯迅的作品實在是太合適了。在〈孔乙己〉裡面,當寫到孔乙己最後一次來酒店時,他的腿已經斷了。如果孔乙己腿沒有斷,可以不寫他是如何來的,可是他的腿斷了,就必須要寫,這是一位優秀作家的責任感。魯迅先是讓他的聲音從櫃檯下飄上來,然後讓小伙計端著酒從櫃檯繞過去,看到孔乙己從破衣服裡摸出了四文大錢,這時候敘述就看到了他滿手的泥,魯迅這樣寫:原來他便用這手走來的。魯迅的交代乾淨有力。魯迅作品有力的另一個方面,我想應該是魯迅的寬廣,像他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他在寫百草園時的敘述是那麼的明媚、歡樂和充滿了童年的調皮,然後進入了三味書屋,環境變得陰森起來,孩子似乎被控制了,可是魯迅仍然寫出了童年的樂趣,只是這樣的樂趣是在被壓迫中不斷滲透出來,就像石頭下面的青草依然充滿了生長的欲望一樣。這就是魯迅的寬廣,他沒有將三味書屋和百草園對立起來,因為魯迅要寫的不是百草園,也不是三味書屋,而是童年,真正的童年是任何力量都無法改變的。這就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我想起來當年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發表時,美國很多批評家都認為老人象徵什麼,大海又象徵什麼。海明威很生氣,他認為老人就是老人,大海就是大海,只有鯊魚有象徵,他說鯊魚象徵批評家。然後他給自己信任的一位朋友貝瑞遜(美國藝術史家)寫信,希望他出來說幾句話,貝瑞遜的回信是我讀到的對象徵最好的詮釋。貝瑞遜說老人確實就是老人,大海也就是大海,它們不象徵什麼,但是,貝瑞遜最後說,一部偉大的作品又是無處不洋溢著象徵。
一個真正的老人,一個真正的大海會擁有多少象徵?只有這樣的形象才是無處不洋溢著象徵。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裡,寫出的就是真正的童年,無處不洋溢著象徵的童年。我一直很喜歡以撒.辛格(Isaac Singer)的哥哥對他說的那句話:看法總是要陳舊過時的,只有事實不會陳舊過時。
楊紹斌:普魯斯特對你的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面?
余華:普魯斯特總是能夠綿延不絕地去感受,他這方面的天賦其實遠遠長於《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的長度。他的感受是那樣的獨特,同時又是那樣的親切,讓人身臨其境。他就是在自戀的時候也是非常可愛,當他寫到晚上靠在枕頭上睡覺時,就像是睡在自己童年的臉上,嬌嫩清新。
楊紹斌:你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呼喊與細雨》,我覺得在風格上的細膩與《追憶似水年華》有某種聯繫。
余華:我希望有。喬伊斯(James Joyce)我也很喜歡,因為我找到了閱讀《尤利西斯》(Ulysses)的最好辦法,那就是隨手翻著去閱讀,你會發現這個偉大的作家對細部的刻畫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當他寫一個人從馬車裡出來時,門出了問題,就有了三個的動作,先是用手推一下,然後用胳膊肘去撞,最後是用腳將車門踢開了。
楊紹斌:另外還有哪些作家?
余華:進入一九九○年代以後,我最迷戀的作家是但丁(Dante Alighieri)和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蒙田隨筆中對人與事物的理解是那樣的溫和,同時又那樣的充滿了力量,那種深入人心的力量。所有的法語作家裡,我最熱愛蒙田;所有的義大利語作家裡,我最熱愛但丁;西班牙語應該是賽凡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德語可能是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俄語當然是托爾斯泰;至於英語世界裡,我還找不出一個我最熱愛的作家,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有這樣的可能,如果他作品中的毛病少一些的話。我對他們的熱愛毫無功利之心,不像剛開始寫作時那樣想學到點什麼。剛開始寫作時,卡夫卡、川端康成這樣的作家很大程度就像是在我身上投資,然後我馬上就能出產品,他們就像是一個跨國公司。而現在對但丁和蒙田,我是懷著赤誠之心去閱讀。
楊紹斌:布爾加科夫呢?
余華:布爾加科夫是這樣的,讀到以後大吃一驚。然後我才感到對蘇聯文學的了解是多麼不容易,這是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最早我們知道的是奧斯特洛夫斯基,或者是法捷耶夫
楊紹斌:後來是《靜靜的頓河》。
余華:肖洛霍夫,那是一位偉大的作家,這一點無可非議。然後突然發現還有索忍尼辛、巴斯特納克。我原以為蘇聯文學到這兩位已經見底了,想不到還有一位偉大的作家—布爾加科夫。
楊紹斌:像深淵一樣。
余華:真像是進入了深淵。布爾加科夫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我非常喜歡他,尤其是他的《大師與瑪格麗特》,讀這部作品時,我發現有些輝煌章節的敘述都是布爾加科夫失控後完成的,或者說是他乾脆放任自流。這給我帶來了一點啟示,那就是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不要剝奪自己得來不易的自由。
楊紹斌:再談談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吧。
余華:我是一九八三年開始讀他的小說的,就是《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那時候我還沒有具備去承受他打擊的感受力,也許由於他的故事太龐大了,我的手伸過去卻什麼都沒有抓到。顯然,那時候我還沒有達到可以被賈西亞.馬奎斯的作品震撼的那種程度。你要被他震撼,首先你必須具備一定的反應,我當時好像還不具備這樣的反應。只有覺得這位作家奇妙無比,而且也確實喜歡他。
其實拉美文學裡第一個將我震撼的作家是胡安.魯爾福(Juan Rulfo)。我記得最早讀他的作品是他的《佩德羅.巴拉摩》(Pedro Páramo),那是在海鹽,虹橋新村二十六號樓上三室,你不是來過嗎?
我當時讀的是人民文學版,題目是《人鬼之間》,很薄的一本,寫得像詩一樣流暢,我完全被震撼了。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我當時已經寫作了,還沒有發表作品,正在飽嘗退稿的悲哀,我讀到了胡安.魯爾福,我在那個傷心的夜晚失眠了。然後我又讀了他的短篇小說集《燃燒的平原》,我至今記得他寫到一群被打敗的土匪跑到了一個山坡上,天色快要黑了。土匪的頭子伸出手去清點那些殘兵們,魯爾福使用了這樣的比喻,說他像是在清點口袋裡的錢幣。
楊紹斌:最後一個問題,假如可能的話,在你閱讀過的文學作品中,你願意成為哪一部作品的作者?
余華:我願意成為《聖經》的作者。但是給我一萬年的時間,我也寫不出來。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目次
【輯一】
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
關於寫作
關於閱讀
火焰的祕密心臟
童年是人的一生的基礎
閱讀對我的寫作有著重要的影響
寫作最大的難度在於樸素和誠實
先鋒是一種精神的活動
長篇是一種表達的需要
一個人的記憶決定了他的寫作方向
堅信自己的閱讀感受
文革記憶與對創作的影響
怎麼寫好對話
先峰文學的影響
作為老百姓寫作
寫作中的語言衝突
我想寫出一個國家的疼痛
我並沒有發明故事
作家的性格和運氣
《兄弟》內外
《兄弟》前後
對先鋒文學的所有批評都是一種高估
我想寫出一個國家的疼痛
當代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現狀與未來
選擇好譯者
走入外國主流出版社
外國媒體與讀者評價
新媒體的衝擊與影響
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
【輯二】
答波士頓廣播電台評論員威廉.馬克思
寫作只有不斷地去寫,才會知道寫作是什麼
一部優秀的小說在敍述上應該是自由的
長篇小說有足夠的時間傾聽虛構人物的聲音
答《紐約客》小說主編黛博拉.特瑞斯曼
我在寫小說的時候,必須去考慮很多不會寫進小說的內容
我的寫作總是在變化
答《洛杉磯書評》編輯梅蘭
當前中國文學的現狀與問題
優秀的作家在寫作的時候常常是中性的
任何作家都無法脫離自己和時代的關係
答美國《科克斯評論》編輯梅根
為什麼寫作?
小說無法改變社會現實,但可以改變讀者對社會現實的看法
答紐約亞洲協會網路雜誌《中國檔案》
中國社會現實比小說更荒誕
現實從來沒有中斷過暴力——暴力書寫的轉變
答法國《解放報》
我只是寫了有人做過但又不想說的事
答法國《十字架報》
我總是考慮用幽默來傳遞自己的判斷
我所寫的一切都是基於現實的
答法國《新觀察家》週刊
文革是一個禁欲的時代,今天是一個放縱的時代
暴力只是換了形式
答法國《人道報》
我對自己的寫作曾心存疑慮
《兄弟》這部小說誕生了一個新的余華
答瑞士《時報》
如何成為一個作家
保持簡潔的敍述風格
答義大利《共和國報》
《兄弟》的敍述風格是躁動不安的
我要敍述中國,就必須生活在中國
答義大利《生活》雜誌
文革時全民革命,現在變成了全民經商
中國最大的人權問題是司法不公正的現象太多
答義大利Reset雜誌
中國作家生活在巨大的變化裡,這是我們寫作的財富
作家在寫作時應該滿足自己這個讀者的需要
答義大利《晚郵報》
《第七天》呈現出一個文學文本,同時也呈現出一個社會文本
答瑞典文學雜誌《駝隊》
作家的特別責任是,用虛構的方式表達現實的真實性
答韓國《朝鮮日報》
只要將日常生活寫出來了,也就寫下了一切
答丹麥《基督教彙報》
不是我喜歡用荒誔的方式寫作,而是中國社會充滿了荒誕
答美國Electric Literature雜誌
卡夫卡喚醒了我內心深處的恐懼感,然後我以自己的方式表現出來
答義大利《共和國報》
我寫作時喜歡用諷刺的手法,也有憤世嫉俗的味道
一個真正的作家不只要有政治上的勇氣,更應該有文學敍述上的勇氣
書摘/試閱
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
關於寫作
楊紹斌(自由寫作者):你通常是怎麼構思一篇小說的?
余華:我寫作的開始五花八門,有主題先行,也有的時候是某一個細節、一段對話或者某一個意象打動了我,促使我坐到了寫字桌前。
楊紹斌:《活著》這部小說裡福貴這個形象有來源嗎?
余華:福貴最早來到我腦子裡時是這樣的,一個老人,在中午的陽光下犁田,他的臉上布滿了皺紋,皺紋裡嵌滿了泥土。
楊紹斌:許三觀呢?
余華:他最早的形象是在冬天的時候穿著一件棉襖,鈕釦都掉光了,腰上繫著一根草繩,一個口袋裡塞了一只碗,另一個口袋裡放了一包鹽。但是,這是我開始寫作時的形象,構思的時候還不是這樣。
楊紹斌:那又是怎麼樣的?
余華:關於《活著》,我最早是想寫一個人和他生命的關係,這樣的關係在很長時間裡都讓我著迷,這有點主題先行,可是我一直不知道這篇小說應該怎麼寫。有一天早上醒來時,我對陳虹(作者太太)說,我知道怎樣寫這篇小說了,因為我想出了題目,叫《活著》。陳虹說這個題目非常好。就是因為有了這個標題,才有了這部小說。有時候一個標題也會讓你寫出一部小說。一九八○年代的時候,文學界批判過主題先行的寫作方式,其實完全沒有道理,寫作什麼方式都可以,條條大路都通羅馬。至於《許三觀賣血記》,最早是這樣的,大概是在一九九○年,我和陳虹在王府井的大街上,突然看到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淚流滿面地從對面走了過來。我們當時驚呆了,王府井是什麼地方?那麼一個熱鬧的場所,突然有一個人旁若無人、淚流滿面地走來。這情景給我們的印象非常深刻。到了一九九五年,有一天中午,陳虹又想起了這件事,我們就聊了起來,猜測是什麼使他如此悲哀?而且是旁若無人的悲哀!這和你一個人躲到衛生間去哭是完全不一樣的。
楊紹斌:所以後來在小說裡,許三觀在大街上哭。
余華:這已經是最後一章了。那天,我們兩個人不斷猜測使那位老人悲哀的原因,一直沒有結果。又過了幾天,我對陳虹說起我小時候,我們家不遠處的醫院供血室,有血頭,有賣血的人。我說起這些事時,陳虹突然提醒我,王府井哭泣的那位老人會不會是賣血賣不出去了,他一輩子賣血為生,如果不能賣了,那可怎麼辦?我想,對,這小說有了。於是我就坐下來寫,就這麼寫了八個月。
楊紹斌:許三觀後來就賣不了血。
余華:當時我認為小說最後的高潮,就是他賣不了血,所以他就在大街上旁若無人地哭,因為這意味著他失去了養活自己的能力,他的悲哀是絕望以後的悲哀。這對年輕人來說沒什麼,可是對一個老人就完全不一樣了。我曾經準備在這最後的一章裡重重地去寫,準備將自己吃奶的力氣都寫光,將這一章充分渲染。可是當我寫完第二十八章,也就是結尾前的一章後,我才知道敘述高潮其實是在這一章,就是許三觀一路賣血去上海的那一章,於是最後一章我用輕的方式完成了。根據我寫作和閱讀的經驗,兩個很重的章節並排在一起,只會互相抵消敘述的力量。
楊紹斌:這麼說來,你在動手寫作時,對筆下的人物已經胸中有數了?
余華:還是沒數,其實我根本不知道接下來他會幹什麼,最多只能先給他一些設計,而且有些還用不上。
楊紹斌:你現在還擬提綱嗎?
余華:我在舊信封上做筆記。開始時我怕自己忘了,就隨手拿起一個舊信封記上,一個記滿了,再用第二個,為了風格的統一,我接下去仍然用舊的信封。像《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我都寫滿了一堆舊信封。現在我開始用新的信封,而且必須是國際航空的那一種,上面沒有郵遞區號的紅框,顯得更乾淨。這已經成為了我的寫作習慣。當我寫一部長篇小說的時候,我只要知道開頭一萬多字怎麼寫就行了,後面肯定會出來。要是一萬字寫完了,後面還不出來,那就不應該寫了。這和我早期的寫作已經很不一樣了。我以前小說裡的人物,都是我敘述中的符號,那時候我認為人物不應該有自己的聲音,他們只要傳達敘述者的聲音就行了,敘述者就像是全知的上帝。但是到了《呼喊與細雨》,我開始意識到人物有自己的聲音,我應該尊重他們自己的聲音,而且他們的聲音遠比敘述者的聲音豐富。因此,我寫《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的過程,其實就是對人物不斷理解的過程,當我感到理解的差不多了,我的小說也該結束了。我想起來,一九八七年在黃山的時候,有一天傍晚我和林斤瀾(《北京文學》主編)一起散步,他告訴我有一次他和汪曾祺一起去看望沈從文先生,他問沈先生小說應該怎麼寫,沈先生只回答了一個字:貼。就是說貼著人物寫。這個字說得好!可是當時我沒有很深的感受,現在我才發現的確如此,貼—其實就是源源不斷地去理解自己筆下的人物,就像去理解一位越來越親密的朋友那樣,因此生活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豐富,就是我自己也要比我所認為的要豐富的多。
楊紹斌:你對小說的開頭一句敏感嗎?
余華:非常敏感。第一句要是寫不好,下面的話就白寫了。小說的第一句話,就好比一個人剛從子宮裡出來,要是腦袋擠扁了,這個人就不會聰明。
楊紹斌:你喜歡在白天還是晚上寫作?
余華:不分白天晚上,我只要吃飽了和睡足了,任何時候都能寫作。
楊紹斌:你寫得慢嗎?
余華:我現在比以前快多了。我現在真正寫作的時間不多,一旦寫起來,就很快。我覺得寫作也是一門手藝,熟練之後工作就會變得輕鬆起來;可是另一方面,壓力也加重了,我現在已經寫了一百多萬字了,這對我來說是個包袱,我應該如何去面對我過去的作品?有時候這是很困難的。
楊紹斌:有些作家總是愈寫愈困難。
余華:所有的作家都應該是愈寫愈困難,當我擁有二百多萬字的作品時,我想我會更困難。我慶幸人不能活得更長久,要不這作家沒法當了。如果我能夠活五百年,那麼六十歲以後我肯定不當作家了。
楊紹斌:你在寫作中會碰到哪些具體的困難?
余華:可以說非常多。有很多都是細部的問題,這是小說家必須去考慮的,雖然詩人可以對此不屑一顧,然而小說家卻無法迴避。所以我經常說,小說家就像是一個村長,什麼事都要去管。
楊紹斌:他得充分顧及到細節的清晰和真實。
余華:是的,比如說福貴這個人物,他是一個唯讀過幾年私塾的農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農民的身分來完成的,讓這樣一個人來講述自己,必須用最樸素的語言去寫,必須時刻將敘述限制起來,所有的語詞和句式都為他而生,因此我連成語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連孩子們都願意使用的成語,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
楊紹斌:它對你的限制很大。
余華:是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樣的寫作就放棄了敘述上的追求,相反,這時候的敘述更需要作家下功夫。比如小說中有這麼一段,就是有慶死後,福貴瞞著家珍將有慶埋在一棵樹下,然後他哭著站起來,他看到那條通向城裡的小路,有慶生前每天都在這條小路上奔跑著去學校,這時福貴再次去看這條月光下的小路。我感到必須寫福貴對小路的感受,如果不寫,作為一個作家是不負責任的,可是如何去寫?我記得自己曾經在《世事如煙》裡有過這樣的描述,說月光下的道路像河流一樣,閃爍著蒼白的光芒。如果這時候用這樣的句子來描述一個失去了兒子的父親,顯然是太不負責任了。為了找到一個合適的意象,我費了很長時間,最後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意象—鹽,我這樣寫道:那條通向城裡的小路在月光下像是撒滿了鹽。對於一個農民來說,鹽是很熟悉的;另一方面,又符合他當時的心情,就像往他傷口上撒了鹽一樣。
楊紹斌:是的,我讀到這一段時很感動。
余華:有時候寫作中碰到的困難,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可是會陰差陽錯地要了作家的命,甚至會讓作家感到自卑,感到自己再也寫不下去了,吃不下飯也睡不著覺,可是後來他會突然發現那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問題,隨手一寫就解決了。就像是抱著孩子到處找孩子,戴著眼鏡到處找眼鏡,就是這樣的困難,會讓作家寫作的過程愈拉愈長。
楊紹斌:具體說呢?
余華:我一下子想不起來具體的例子,但它確實是我寫作時隨時都要遇到的困難。可以這麼說,什麼是敘述?它在確立前其實就是一堆雜亂無章的困難,寫作的過程就是不斷地和它們相遇的過程,不斷地去克服它們的過程,最後你才會發現一個完整的敘述成立了。我在寫《許三觀賣血記》時,碰到這樣一個難題,那就是如何讓許玉蘭給許三觀生下三個兒子。在其他方式的敘述裡,這一章可以不寫;可是在這部作品中,我覺得必須寫。雖然這部作品是跳躍的,而且十分簡潔,可是它在敘述上對人物每一段經歷都是無微不至的關懷。後來,我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辦法,讓許玉蘭罵起來。這是第四章,整個一章,都是許玉蘭躺在醫院的產台上罵許三觀。生第一個兒子時,許玉蘭罵得仇恨無比;第二個罵到一半時,孩子出生了;第三個才罵了兩聲,孩子就出來了。不是有個說法嗎,女人在生孩子時是很恨男人的。許玉蘭在產台上罵了三次,敘述裡的時間一下子過去了很多年。其實這樣的方式我在〈我沒有自己的名字〉裡就已經使用過了,我讓來發將父親三十多年間對他說的話在一個句子裡完成。一個一百多字的句子一下子將三十年的時間打發走了,這是我寫作最得意的時候。人的記憶就是這樣,我父親在三十年間對我說的不同的話,我可以在一分鐘裡集中起來。
楊紹斌:你修改嗎?
余華:我是一個熱愛修改的作家,我覺得修改是一種享受,而且修改的過程是我對自己內省的過程,對我以後的寫作都會有說明。
楊紹斌:你是否跟別人談論你正在寫的小說?
余華:以前經常談,現在不談了。以前我的寫作方式決定了我可以和別人談,因為在寫之前我已經知道得很多;現在我寫之前知道的不多了,所以我不談了。
楊紹斌:你對自己的小說語言有些什麼要求?
余華:我對語言只有一個要求:準確。一個優秀的作家應該無休止地剝削自己的才能,讓語言發揮出最大的能量。魯迅就是這樣的作家,他的語言像核能一樣,體積很小,可是能量無窮。作家的語言千萬不要成為一堆煤,即便堆得像山一樣,能量仍然有限。
楊紹斌:你離開海鹽去北京也有十多年了,脫離家鄉的語境和生活,這種遷移本身以及由此而來的一系列變化,對你的寫作有什麼樣的影響?
余華:影響是多方面的,不過決定我今後生活道路和寫作方向的主要因素,在海鹽的時候已經完成了,應該說是在我童年和少年時已經完成了。接下去我所做的不過是些重溫而已,當然是不斷重新發現意義上的重溫。我現在對給予我成長的故鄉有著越來越強烈的感受,不管我寫什麼故事,裡面所有的人物和所有的場景都不由自主地屬於故鄉。
楊紹斌:你認為你的寫作和家鄉存在著一種什麼樣的聯繫?
余華: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當我不寫作的時候,我才想到自己是在北京生活。
關於閱讀
楊紹斌:你喜歡哪些作家?
余華:我喜歡的作家太多了。
楊紹斌:最早的時候你喜歡川端康成。
余華:是的。一九八○年,我在寧波的時候,在一個十多個人住的屋子裡,在一個靠近窗口的上舖,我第一次讀到了他的作品,是《伊豆的舞女》,我嚇了一跳。那時候中國文學正是傷痕文學的黃金時期,我發現寫受傷的小說還有另外一種表達,我覺得比傷痕文學那種控訴更有力量。後來,有五、六年的時間,我一直迷戀川端康成,那時候出版的所有他的書,我都有。但長期迷戀一位作家,對一個寫作的年輕人來說,肯定是有害的。接下來是卡夫卡(Franz Kafka),我最早在《世界文學》上讀過他的《變形記》(Die Verwandlung),印象深刻,過了兩年,我買到了一本《卡夫卡小說選》,重新閱讀他的作品,這一次時機成熟了,卡夫卡終於讓我震撼了。我當時印象很深的是《鄉村醫生》(Ein Landarzt)裡的那匹馬,我心想卡夫卡寫作真是自由自在,他想讓那匹馬存在,馬就出現;他想讓馬消失,馬就沒有了。他根本不作任何鋪墊。我突然發現寫小說可以這麼自由,於是我就和川端康成再見了,我心想我終於可以擺脫他了。
楊紹斌:大概就是在那個時期,你寫出了〈十八歲出門遠行〉。
余華:是的,我寫出了〈十八歲出門遠行〉,當時我很興奮,發現寫出了一篇讓自己都感到意外的小說,不過我還是沒有把握,剛好我要去北京,去參加《北京文學》的筆會,就將小說拿給李陀(《北京文學》副主編)看,李陀看完後非常喜歡,他告訴我,說我已經走到中國當代文學的最前列了。李陀的這句話我一輩子都忘不了,就是他這句話,使我後來愈寫膽子愈大。
楊紹斌:就是說卡夫卡成了你創造力的第一個發掘者。
余華:可以這麼說。不過我現在回頭去看,川端康成對我的幫助仍然是至關重要的。在川端康成做我導師的五、六年時間裡,我學會了如何去表現細部,而且是用一種感受的方式去表現。感受,這非常重要,這樣的方式會使細部異常豐厚。川端康成是一個非常細膩的作家。就像是練書法先練正楷一樣,那個五、六年的時間我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寫作基礎,就是對細部的關注。現在不管我小說的節奏有多快,我都不會忘了細部。所以,卡夫卡對我來說是思想的解放,而川端康成教會了我寫作的基本方法。在喜歡川端康成的那幾年裡,我還喜歡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還有英國女作家曼斯費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等等,那時候我喜歡的作家都是細膩和溫和的。卡夫卡之後,我開始喜歡敘述和情感都很強烈的作家。現在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發現我喜歡的作家越來越多了,而且已經沒有風格上的局限了。
楊紹斌:你說說看,還有哪些作家?
余華:比如說魯迅。魯迅是我至今為止閱讀中最大的遺憾,我覺得,如果我更早幾年讀魯迅的話,我的寫作可能會是另外一種狀態。我讀魯迅讀得太晚了,雖然我在小學和中學時就讀過。
楊紹斌:因為原先幾乎是一種被動接受。
余華:其實魯迅是不屬於孩子們的。我驚訝地發現,我小時候背過的〈孔乙己〉、〈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作品,當我前年重讀時,就像是第一次閱讀,讀完了才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可見那時候我其實是沒有閱讀魯迅,或者說只是旅遊而已,現在我的閱讀是在魯迅的作品裡定居了。重讀魯迅完全是一個偶然,大概兩三年前,我的一位朋友想拍魯迅作品的電視劇,他請我策畫,我心想改編魯迅還不容易,然後我才發現我的書架上竟然沒有一本魯迅的書,我就去買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魯迅小說集》,我首先讀的就是〈狂人日記〉,我嚇了一跳,讀完〈孔乙己〉後我就給那位朋友打電話,我說你不能改編,魯迅是偉大的作家,偉大的作家不應該被改編成電視劇。我認為我讀魯迅讀得太晚了,因為那時候我的創作已經很難回頭,但是他仍然會對我今後的生活、閱讀和寫作產生影響,我覺得他時刻都會在情感和思想上支援我。
魯迅可以說是我讀到過的作家中敘述最簡潔的一位,可是他的作品卻是異常的豐厚,我覺得可能來自兩方面,一方面魯迅在敘述的時候從來不會放過那些關鍵之處,也就是說對細部的敏感。要知道,細部不是靠堆積來顯示自己的,而是在一些關鍵的時候,又在一些關鍵的位置上恰如其分地出現,這時候你會感到某一個細部突然從整個敘述裡明亮了起來,然後是照亮了全部的敘述。魯迅就是這麼奇妙,他所有精彩的細部都像是信手拈來,他就是在給《吶喊》寫自序時,寫到他的朋友金心異來看望他,在如此簡潔的筆調裡,魯迅也沒忘了寫金心異進屋後脫下長衫的一筆。看上去是閒筆,其實是閒筆不閒。用閒筆不閒來說魯迅的作品實在是太合適了。在〈孔乙己〉裡面,當寫到孔乙己最後一次來酒店時,他的腿已經斷了。如果孔乙己腿沒有斷,可以不寫他是如何來的,可是他的腿斷了,就必須要寫,這是一位優秀作家的責任感。魯迅先是讓他的聲音從櫃檯下飄上來,然後讓小伙計端著酒從櫃檯繞過去,看到孔乙己從破衣服裡摸出了四文大錢,這時候敘述就看到了他滿手的泥,魯迅這樣寫:原來他便用這手走來的。魯迅的交代乾淨有力。魯迅作品有力的另一個方面,我想應該是魯迅的寬廣,像他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他在寫百草園時的敘述是那麼的明媚、歡樂和充滿了童年的調皮,然後進入了三味書屋,環境變得陰森起來,孩子似乎被控制了,可是魯迅仍然寫出了童年的樂趣,只是這樣的樂趣是在被壓迫中不斷滲透出來,就像石頭下面的青草依然充滿了生長的欲望一樣。這就是魯迅的寬廣,他沒有將三味書屋和百草園對立起來,因為魯迅要寫的不是百草園,也不是三味書屋,而是童年,真正的童年是任何力量都無法改變的。這就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我想起來當年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發表時,美國很多批評家都認為老人象徵什麼,大海又象徵什麼。海明威很生氣,他認為老人就是老人,大海就是大海,只有鯊魚有象徵,他說鯊魚象徵批評家。然後他給自己信任的一位朋友貝瑞遜(美國藝術史家)寫信,希望他出來說幾句話,貝瑞遜的回信是我讀到的對象徵最好的詮釋。貝瑞遜說老人確實就是老人,大海也就是大海,它們不象徵什麼,但是,貝瑞遜最後說,一部偉大的作品又是無處不洋溢著象徵。
一個真正的老人,一個真正的大海會擁有多少象徵?只有這樣的形象才是無處不洋溢著象徵。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裡,寫出的就是真正的童年,無處不洋溢著象徵的童年。我一直很喜歡以撒.辛格(Isaac Singer)的哥哥對他說的那句話:看法總是要陳舊過時的,只有事實不會陳舊過時。
楊紹斌:普魯斯特對你的影響體現在哪些方面?
余華:普魯斯特總是能夠綿延不絕地去感受,他這方面的天賦其實遠遠長於《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的長度。他的感受是那樣的獨特,同時又是那樣的親切,讓人身臨其境。他就是在自戀的時候也是非常可愛,當他寫到晚上靠在枕頭上睡覺時,就像是睡在自己童年的臉上,嬌嫩清新。
楊紹斌:你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呼喊與細雨》,我覺得在風格上的細膩與《追憶似水年華》有某種聯繫。
余華:我希望有。喬伊斯(James Joyce)我也很喜歡,因為我找到了閱讀《尤利西斯》(Ulysses)的最好辦法,那就是隨手翻著去閱讀,你會發現這個偉大的作家對細部的刻畫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當他寫一個人從馬車裡出來時,門出了問題,就有了三個的動作,先是用手推一下,然後用胳膊肘去撞,最後是用腳將車門踢開了。
楊紹斌:另外還有哪些作家?
余華:進入一九九○年代以後,我最迷戀的作家是但丁(Dante Alighieri)和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蒙田隨筆中對人與事物的理解是那樣的溫和,同時又那樣的充滿了力量,那種深入人心的力量。所有的法語作家裡,我最熱愛蒙田;所有的義大利語作家裡,我最熱愛但丁;西班牙語應該是賽凡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德語可能是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俄語當然是托爾斯泰;至於英語世界裡,我還找不出一個我最熱愛的作家,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有這樣的可能,如果他作品中的毛病少一些的話。我對他們的熱愛毫無功利之心,不像剛開始寫作時那樣想學到點什麼。剛開始寫作時,卡夫卡、川端康成這樣的作家很大程度就像是在我身上投資,然後我馬上就能出產品,他們就像是一個跨國公司。而現在對但丁和蒙田,我是懷著赤誠之心去閱讀。
楊紹斌:布爾加科夫呢?
余華:布爾加科夫是這樣的,讀到以後大吃一驚。然後我才感到對蘇聯文學的了解是多麼不容易,這是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最早我們知道的是奧斯特洛夫斯基,或者是法捷耶夫
楊紹斌:後來是《靜靜的頓河》。
余華:肖洛霍夫,那是一位偉大的作家,這一點無可非議。然後突然發現還有索忍尼辛、巴斯特納克。我原以為蘇聯文學到這兩位已經見底了,想不到還有一位偉大的作家—布爾加科夫。
楊紹斌:像深淵一樣。
余華:真像是進入了深淵。布爾加科夫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我非常喜歡他,尤其是他的《大師與瑪格麗特》,讀這部作品時,我發現有些輝煌章節的敘述都是布爾加科夫失控後完成的,或者說是他乾脆放任自流。這給我帶來了一點啟示,那就是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不要剝奪自己得來不易的自由。
楊紹斌:再談談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吧。
余華:我是一九八三年開始讀他的小說的,就是《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那時候我還沒有具備去承受他打擊的感受力,也許由於他的故事太龐大了,我的手伸過去卻什麼都沒有抓到。顯然,那時候我還沒有達到可以被賈西亞.馬奎斯的作品震撼的那種程度。你要被他震撼,首先你必須具備一定的反應,我當時好像還不具備這樣的反應。只有覺得這位作家奇妙無比,而且也確實喜歡他。
其實拉美文學裡第一個將我震撼的作家是胡安.魯爾福(Juan Rulfo)。我記得最早讀他的作品是他的《佩德羅.巴拉摩》(Pedro Páramo),那是在海鹽,虹橋新村二十六號樓上三室,你不是來過嗎?
我當時讀的是人民文學版,題目是《人鬼之間》,很薄的一本,寫得像詩一樣流暢,我完全被震撼了。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我當時已經寫作了,還沒有發表作品,正在飽嘗退稿的悲哀,我讀到了胡安.魯爾福,我在那個傷心的夜晚失眠了。然後我又讀了他的短篇小說集《燃燒的平原》,我至今記得他寫到一群被打敗的土匪跑到了一個山坡上,天色快要黑了。土匪的頭子伸出手去清點那些殘兵們,魯爾福使用了這樣的比喻,說他像是在清點口袋裡的錢幣。
楊紹斌:最後一個問題,假如可能的話,在你閱讀過的文學作品中,你願意成為哪一部作品的作者?
余華:我願意成為《聖經》的作者。但是給我一萬年的時間,我也寫不出來。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