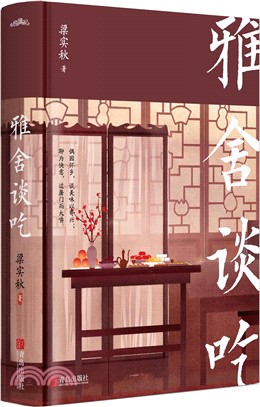雅舍談吃(簡體書)
商品簡介
梁實秋 散文經典
花看半開,酒飲微醺。偶因懷鄉,聊為快意。
嬉笑怒駡,皆成文章。一飲一酌,皆是鄉愁。
1. 本書作者是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汪曾祺,其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鑽研。
2.汪曾祺在新時期文壇上的出現具有觀念革命的意義,其作品連接了新舊兩個時期的小說創作,其中《受戒》一文還曾作為研究新時期中國文學的代表被歐美大學選入教材。
3.本書是一部描述江蘇、雲南、北京等地風土人情的小說集,構築了一個富有魅力的“市井世界”。創作風格趨向現實主義,將目標聚焦在一個個小人物上,關注小人物在大時代浪潮中的命運。
4.書中文字清新自然、樸素洗練,世故卻又童真,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將世間萬物的美濃縮於文字之中。
《雅舍談吃》收錄了梁實秋先生關於吃食的64篇散文,精緻非常,讀來令人口吃生津。全書分為雅舍談吃和余香繞梁兩個部分,從北京到江南,從臺灣到西雅圖,梁實秋用“縱橫捭闔、清麗流暢”的文字帶你領略人世間的美食。
梁實秋的美食散文,不煽情,不以情奪味,對美食的描寫精細而到位。他筆下的人,吃得快樂,吃得幸福。讀他的文字,也能感到快樂,感到幸福。
作者簡介
梁實秋
原名梁治華,字實秋,中國著名的現當代散文家、學者、文學批評家、翻譯家,曾任《新月》雜誌主編,是國內第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權威。梁實秋先生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一生給中國文壇留下了兩千多萬字的著作。其文風率真、自然、灑脫,“縱橫捭闔、清麗流暢”,用平淡真摯抒寫人生百態,在20世紀的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代表作有《雅舍小品》《英國文學史》《沉思錄》(譯作)《莎士比亞全集》(譯作)等。
名人/編輯推薦
生前著作無虛日,死後文章惠人間。
——胡絜青
美食在作家的筆下早已超越了它本身的概念,它更是一種文化底蘊的代表。後來參加工作,拿著菲薄的工資,我專門去把《雅舍談吃》裡寫到現在能找到的美食嘗了個遍。
——陳曉卿(《舌尖上的中國》總導演)
梁實秋的貢獻有許多方面。臺灣讀者最熟悉的該是散文家梁實秋,尤其是《雅舍小品》的作者。其次,該是翻譯家梁實秋,尤其是莎士比亞的傳人。再其次,該是學者梁實秋,尤其是中文版英國文學史的作者。一般學生最熟悉的,則是各種英漢字典的編者梁實秋。臺灣讀者認識的梁實秋,是一位智者,字裡行間閃動著智慧與諧趣。
——余光中
序
本書以初版《雅舍談吃》( 臺灣九歌出版社,1985 年 1 月版)為底本,參考了若干大陸版本加以編校,力圖保持作品原貌。編者查閱相關文獻,對原文的錯漏之處進行了說明,並注釋了疑難詞匯。才力所限,難免有不當之處,敬請各位讀者指正。
子序
這些談吃的文字,前二十一段刊于《聯合報》副刊,以後各段刊于《中華日報》副刊。隨便談談,既無章法,亦無次序,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我不是烹調專家,我只是“天橋的把式——淨說不練”。遊徙不廣,所知有限,所以文字內容自覺十分寒傖。大概天下嘴饞的人不少,文字刊佈,隨時有人賜教,有一位先生問我:“您為什麼對於飲食特有研究?”這一問問得我好生惶恐。我幾曾有過研究?我據實回答說:“只因我連續吃了八十多年,沒間斷。”
人吃,是為了活著;人活著,不是為了吃。所以孟子說:“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專恣口腹之欲,因小而失大,所以被人輕視。但是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這個“小”不是絕對不可以談的。只是不要僅僅成為“飲食之人”就好。
《朱子語錄》:“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學者須是革盡人欲,複盡天理,方始是學。’”我的想法異於是。我以為要求美味固是人欲,然而何曾有背于天理?如果天理不包括美味的要求在內,上天生人,在舌頭上為什麼要生那麼多的味蕾?
偶因懷鄉,談美味以寄興;聊為快意,過屠門而大嚼。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一日甲子中秋,在臺北
目次
目 錄
上篇.雅舍談吃/1
西施舌 / 3
火腿 / 5
醋溜魚 / 8
烤羊肉 / 10
燒鴨 / 12
獅子頭 / 15
兩做魚 / 17
熗青蛤 / 19
生炒鱔魚絲 / 23
醬菜 / 26
水晶蝦餅 / 28
湯包 / 30
核桃酪 / 32
鐵鍋蛋 / 34
瓦塊魚 / 36
溜黃菜 / 38
酸梅湯與糖葫蘆 / 40
鍋燒雞 / 43
煎餛飩 / 45
核桃腰 / 47
豆汁兒 / 49
芙蓉雞片 / 51
烏魚錢 / 53
韭菜簍 / 54
蟹 / 56
炸丸子 / 59
佛跳牆 / 61
栗子 / 64
海參 / 66
滿漢細點 / 68
菜包 / 71
糟蒸鴨肝 / 73
魚翅 / 75
茄子 / 78
蓮子 / 80
白肉 / 82
干貝 / 84
鮑魚 / 86
咖哩雞 / 88
烙餅 / 90
筍 / 92
黃魚 / 95
八寶飯 / 97
薄餅 / 99
爆雙脆 / 101
拌鴨掌 / 103
魚丸 / 104
臘肉 / 106
粥 / 108
餃子 / 110
鍋巴 / 112
豆腐 / 114
燒羊肉 / 117
菠菜 / 119
龍鬚菜 / 121
鴿 / 122
味精 / 124
下篇.余香繞梁 / 127
吃相(其一) / 129
吃相(其二) / 131
讀《中國吃》 / 135
再談《中國吃》 / 145
粽子節 / 151
大菜 / 152
北平的零食小販 / 153
豆腐乾風波 / 160
關於蘋果 / 164
燒餅油條 / 167
酪 / 170
喝茶 / 173
說酒 / 177
飲酒 / 180
醃豬肉 / 184
狗肉 / 187
蛤王 / 190
蘿蔔湯的啟示 / 194
喜筵 / 196
窩頭 / 200
炸活魚 / 203
酒壺 / 206
由熊掌說起 / 209
書摘/試閱
西施舌郁達夫一九三六年有《飲食男女在福州》一文,記西施舌雲:《閩小記》裡所說西施舌,不知道是否指蚌肉而言,色白而腴,味脆且鮮,以雞湯煮得適宜,長圓的蚌肉,實在是色香味形俱佳的神品。案:《閩小記》是清初周亮工宦游閩垣時所做的筆記。西施舌屬?貝類,似蟶而小,似蛤而長,並不是蚌。產淺海泥沙中,故一名“沙蛤”。其殼約長十五公分,作長橢圓形,水管特長而色白,常伸出殼外,其狀如舌,故名西施舌。初到閩省的人,嘗到西施舌,莫不驚為美味。其實西施舌並不限於閩省一地,以我所知,自津沽青島以至閩台,凡淺海中皆產之。清張燾《津門雜記》錄詩一首詠西施舌:燈火樓臺一望開,放杯那惜倒金罍。朝來飽啖西施舌,不負津門鼓棹來。詩不見佳,但亦可見他的興致不淺。我第一次吃西施舌是在青島順興樓席上,一大碗清湯,浮著一層尖尖的白白的東西,初不知為何物,主人曰是乃西施舌,含在口中有滑嫩柔軟的感覺,嘗試之下果然名不虛傳,但覺未免唐突西施。高湯?西施舌,蓋僅取其舌狀之水管部分。若郁達夫所謂“長圓的蚌肉”,顯系整個的西施舌之軟體全入釜中。現下臺灣海鮮店所烹製之西施舌即是整個一塊塊軟肉上桌,較之專取舌部,其精粗之差不可以道裡計。郁氏盛譽西施舌之“色香味形”,整個的西施舌則形實不雅,豈不有負其名? 火腿從前北方人不懂吃火腿,嫌火腿有一股陳腐的油膩澀味。也許是不善處理,把“滴油”一部分未加削裁就吃下去了,當然會吃得舌矯不能下,好像舌頭要粘住上膛一樣。有些北方人見了火腿就發怵,總覺得沒有清醬肉爽口。後來許多北方人也能欣賞火腿,不過火腿究竟是南貨,在北方不是頂流行的食物。道地的北方餐館做菜配料,絕無使用火腿,永遠是清醬肉。事實上,清醬肉也的確很好,我每次作江南遊總是攜帶幾方清醬肉,分饋親友,無不讚美,只是清醬肉要輸火腿特有的一段香。火腿的歷史且不去談它,也許是宋朝大破金兵的宗澤于無意中所發明。宗澤是義烏人,在金華之東,所以直到如今,凡火腿必曰“金華火腿”。東陽縣亦在金華附近,《東陽縣誌》雲:“薰蹄,俗謂火腿,其實煙薰,非火也。醃曬薰將如法者,果勝常品,以所醃之鹽必台鹽,所熏之煙必松煙,氣香烈而善入,制之及時如法,故久而彌旨。 ”火腿製作方法亦不必細究,總之手續及材料必定很有考究。東陽上蔣村蔣氏一族大部分以制火腿為業,故“蔣腿”特為著名。金華本地常不能吃到好的火腿,上品均已行銷各地。我在上海時,每經大馬路,輒至天福市得熟火腿四角錢,店員以利刃切成薄片,瘦肉鮮明似火,肥肉依稀透明,佐酒下飯為無上妙品。至今思之猶有餘香。予亦叨陪。席間上清蒸火腿一色,盛以高邊大瓷盤,取火腿最精部分,切成半寸見方高寸許之小塊,二三十塊矗立於盤中,純由醇釀花雕蒸制熟透,味之鮮美無與倫比。先生微酡,擊案高歌,盛會難忘,於今已有半個世紀有餘。抗戰時,某日張道藩先生召飲于重慶之留春塢。留春塢是雲南館子,雲南的食物產品,無論是蘿蔔或是白菜都異常碩大,豬腿亦不例外。故雲腿通常均較金華火腿為壯觀,脂多肉厚,雖香味稍遜,但是做叉燒火腿則特別出色。留春塢的叉燒火腿,大厚片烤熟夾麵包,豐腴適口,較湖南館子的蜜汁火腿似乎猶勝一籌。臺灣氣候太熱,不適於製作火腿,但有不少人仿製,結果不是粗製濫造,便是醃曬不足急於發售,帶有死屍味;幸而無屍臭,亦是一味死鹹,與“家鄉肉”無殊。逢年過節,常收到禮物,火腿是其中一色。即使可以食用,其中那根大骨頭很難剔除,運斤猛斫,可能砍得稀巴爛而骨尚未斷,我一見火腿便覺束手無策,廉價出售不失為一辦法,否則只好央由菁清 持往熟識商店請求代為肢解。有人告訴我,整只火腿煮熟是有訣竅的。法以整只火腿浸泡水中三數日,每日換水一二次,然後刮磨表面油漬,然後用鑿子挖出其中的骨頭(這層手續不易),然後用麻繩緊緊捆綁,下鍋煮沸二十分鐘,然後以微火煮兩小時,然後再大火煮沸,取出冷卻,即可食用。像這樣繁複的手續,我們哪得工夫?不如買現成的火腿吃(臺北有兩家上海店可以買到),如果買不到,乾脆不吃。菁清持往熟識商肆,老闆奏刀,砉的一聲,劈成兩截。他怔住了,鼻孔翕張,好像是嗅到了異味,驚叫:“這是道地的金華火腿,數十年不聞此味矣!”他嗅了又嗅不忍釋手,他要求把爪尖送給他,結果連蹄帶爪都送給他了,他說回家去要好好燉一鍋湯吃。美國的火腿,所謂 ham,不是不好吃,是另一種東西。如果是現烤出來的大塊火腿,表皮上烤出鳳梨似的斜方格,趁熱切大薄片而食之,亦頗可口,唯不可與金華火腿同日而語。“佛琴尼亞火腿”則又是一種貨色,色香味均略近似金華火腿,去骨者尤佳,常居海外的遊子,得此聊勝於無。 醋溜魚清梁晉竹《兩般秋雨盦隨筆》:西湖醋溜魚,相傳是宋五嫂遺制,近則工料簡濇。直不見其佳處。然名留刀匕,四遠皆知。番禺方橡枰孝廉恒泰《西湖詞》雲:小泊湖邊五柳居,當筵舉網得鮮魚。味酸最愛銀刀鱠,河鯉河魴總不如。梁晉竹是清道光時人,距今不到二百年,他已感歎當時的西湖醋溜魚之徒有虛名。宋五嫂的手藝,吾固不得而知。但是七十年前侍先君游杭,在樓外樓嘗到的醋溜魚,仍驚歎其鮮美,嗣後每過西湖輒登樓一膏饞吻。樓在湖邊,憑窗可見巨簍系小舟,簍中畜魚待烹,固不必舉網得魚。普通選用青魚,即草魚,魚長不過尺,重不逾半斤,宰割收拾過後沃以沸湯,熟即起鍋,勾芡調汁,澆在魚上,即可上桌。醋溜魚當然是汁裡加醋,但不宜加多,可以加少許醬油,亦不能多加。汁不要多,也不要濃,更不要油,要清清淡淡,微微透明。上面可以略撒薑末,不可加蔥絲,更絕對不可加糖,如此方能保持現殺活現時一般餐廳,多標榜西湖醋溜魚,與原來風味相去甚遠,往往是濃汁滿溢,大量加糖,無複清淡之致。 烤羊肉北平中秋以後,螃蟹正肥,烤羊肉亦一同上市。口外的羊肥,而少膻味,是北平人主要的食用肉之一。不知何故很多人家根本不吃牛肉,我家裡就牛肉不曾進過門。說起烤肉就是烤羊肉。南方人吃的紅燒羊肉,是山羊肉,有膻氣,肉瘦,連皮吃,北方人覺得是怪事,因為北方的羊皮留著做皮襖,捨不得吃。北平烤羊肉以前門肉市正陽樓為最有名,主要的是工料細緻,無論是上腦、黃瓜條、三叉、大肥片,都切得飛薄,切肉的師傅就在櫃檯近處表演他的刀法,一塊肉用一塊布蒙蓋著,一手按著肉一手切,刀法利落。肉不是電冰櫃裡的凍肉(從前沒有電冰櫃),就是冬寒天凍,肉還是軟軟的,沒有手藝是切不好的。正陽樓的烤肉支子,比烤肉宛、烤肉季的要小得多,直徑不過二尺,放在四張八仙桌子上,都是擺在小院裡,四圍是四把條凳。三五個一夥圍著一個桌子,抬起一條腿踩在條凳上,邊烤邊飲邊吃邊說笑,這是標準的吃烤肉的架勢。不像烤肉宛那樣的大支子,十幾條大漢在熊熊烈火周圍,一面烤肉一面烤人。女客喜歡到正陽樓吃烤肉,地方比較文靜一些,不願意露天自己烤,夥計們可以烤好送進房裡來。烤肉用的不是炭,不是柴,是燒過除煙的松樹枝子,所以帶有特殊香氣。烤肉不需多少佐料,有大蔥、芫荽、醬油就行。正陽樓的燒餅是一絕,薄薄的兩層皮,一面粘芝麻,打開來會通的芝麻醬燒餅不對勁,中間有芯子,太厚實,夾不了多少肉。我在青島住了四年,想起北平烤羊肉饞涎欲滴。可巧厚德福飯莊從北平運來大批冷凍羊肉片,我靈機一動,托人在北平為我訂制了一具烤肉支子。支子有一定的規格尺度,不是外行人可以隨便製造的。我的支子運來之後,大宴賓客,命兒輩到寓所後山拾松塔盈筐,敷在炭上,松香濃郁。烤肉佐以濰縣特產大蔥,真如錦上添花,蔥白粗如甘蔗,斜切成片,細嫩而甜,吃得皆大歡喜。提起濰縣大蔥,又有一事難忘。我的同學張心一是一位畸人,他的夫人是江蘇人,家中禁食蔥蒜,而心一是甘肅人,極嗜蔥蒜。他有一次過青島,我邀他家中便飯,他要求大蔥一盤,別無所欲。我如他所請,特備大蔥一盤,家常餅數張。心一以蔥卷餅,頃刻而罄,對於其他菜肴竟未下箸,直吃得他滿頭大汗。他說這是數年來第一次如意的飽餐!我離開青島時把支子送給同事趙少侯,此後抗戰軍興,友朋星散,這青島獨有的一個支子就不知流落何方了。 燒鴨北平烤鴨,名聞中外,在北平不叫烤鴨,叫燒鴨,或燒鴨子,在口語中加一子字。《北平風俗雜詠》嚴辰《憶京都詞》十一首,第五首雲:憶京都‧填鴨冠寰中爛煮登盤肥且美,加之炮烙制尤工。此間亦有呼名鴨,骨瘦如柴空打殺。嚴辰是浙人,對於北平填鴨之傾倒,可謂情見乎詞。北平苦旱,不是產鴨盛地,唯近在咫尺之通州得運河之便,渠塘交錯,特宜畜鴨。佳種皆純白,野鴨、花鴨則非上選。鴨自通州運到北平,仍需施以填肥手續。以高粱及其他飼料揉搓成圓條狀,較一般香腸熱狗為粗,長約四寸許。通州的鴨子師傅抓過一隻鴨來,夾在兩條腿間,使不得動,用手掰開鴨嘴,以粗長的一根根的食料蘸著水硬行塞入。鴨子要叫都叫不出聲,只有眨巴眼的份兒。塞進口中之後,用手緊緊地往下捋鴨的脖子,硬把那一根根的東西擠送到鴨的胃裡。填進幾根之後,眼看著再填就要撐破肚皮,這才鬆手,把鴨關進一間不見天日的小棚子裡。幾十百隻鴨關在一起,像沙丁魚,絕無活動餘地,只是名填鴨。一來鴨子品種好,二來師傅手藝高,所以填鴨為北平所獨有。抗戰時期在後方有一家餐館試行填鴨,三分之一死去,沒死的雖非骨瘦如柴,也並不很肥,這是我親眼看到的。鴨一定要肥,肥才嫩。北平燒鴨,除了專門賣鴨的餐館如全聚德之外,是由便宜坊(即醬肘子鋪)發售的。在館子裡亦可吃燒鴨,例如在福全館宴客,就可以叫右邊鄰近的一家便宜坊送了過來。自從宣外的老便宜坊關張以後,要以東城的金魚胡同口的寶華春為後起之秀,樓下門市,樓上小樓一角最是吃燒鴨的好地方。在家裡,打一個電話,寶華春就會派一個小利巴,用保溫的鉛鐵桶送來一隻才出爐的燒鴨,油淋淋的,燙手熱的。附帶著他還管代蒸荷葉餅蔥醬之類。他在席旁小桌上當眾片鴨,手藝不錯,講究片得薄,每一片有皮有油有肉,隨後一盤瘦肉,最後是鴨頭鴨尖,大功告成。主人高興,賞錢兩吊,小利巴歡天喜地稱謝而去。填鴨費工費料,後來一般餐館幾乎都賣燒鴨,叫作叉燒烤鴨,連燜爐的設備也省了,就地一堆炭火一根鐵叉就能應市。同時用的是未經填肥的普通鴨子,吹凸了鴨皮晾乾一烤,也能烤得焦黃迸脆。但是除了皮就是肉,沒有黃油,味道當然差得多。有人到北平吃烤鴨,歸來盛道其美,我問他好在哪裡,他說:“有皮,有肉,沒有油。”我告訴他:“你還沒有吃過北平烤鴨。” 所謂一鴨三吃,那是廣告噱頭。在北平吃燒鴨,照例有一碗滴出來的油,有一副鴨架裝。鴨油可以蒸蛋羹,鴨架裝可以熬白菜,也可以煮湯打鹵。館子裡的鴨架裝熬白菜,可能是預先煮好的大鍋菜,稀湯洸水,索然寡味。會吃的人要把整個的架裝帶回家裡去煮。這一鍋湯,若是加口蘑(不是冬菇,不是香蕈)打鹵,鹵上再加一勺炸花椒油,吃打鹵麵,其味之美無與倫比。 獅子頭獅子頭,揚州名菜。大概是取其形似,而又相當大,故名。北方飯莊稱之為四喜丸子,因為一盤四個。北方做法不及揚州獅子頭遠甚。我的同學王化成先生,揚州人,幼失恃,賴姑氏扶養成人,姑善烹調,化成耳濡目染,亦通調和鼎鼐之道。化成官外交部多年,後外放葡萄牙公使歷時甚久,終於任上。他公餘之暇,常親操刀俎,以娛嘉賓。獅子頭為其拿手傑作之一,曾以製作方法見告。獅子頭人人會作,巧妙各有不同。化成教我的方法是這樣的—— 首先取材要精。細嫩豬肉一大塊,七分瘦三分肥,不可有些須筋絡糾結於其間。切割之際最要注意,不可切得七歪八斜,亦不可剁成碎泥,其秘訣是“多切少斬”。挨著刀切成碎丁,越碎越好,然後略為斬剁。次一步驟也很重要。肉裡不羼芡粉,容易碎散;加了芡粉,黏糊糊的不是味道。所以調好芡粉要抹在兩個手掌上,然後捏搓肉末成四個丸子,這樣丸子外表便自然糊上了一層芡粉,而裡面沒有。把丸子微微按扁,下油鍋炸,以丸子表面緊繃微黃為度。再下一步是蒸。碗裡先放一層轉刀塊冬筍墊底,再不然就橫切黃芽白作墩形數個也好。把炸過的丸子輕輕放在碗裡,大火蒸一個大吸管吸去,使碗裡不見一滴油。這樣的獅子頭,不能用筷子夾,要用羹匙舀,其嫩有如豆腐。肉裡要加蔥汁、薑汁、鹽。願意加海參、蝦仁、荸薺、香蕈,各隨其便,不過也要切碎。獅子頭是雅舍食譜中重要的一色。最能欣賞的是當年在北碚的編譯館同仁蕭毅武先生,他初學英語,稱之為“萊陽海帶”,見之輒眉飛色舞。化成客死異鄉,墓木早拱矣,思之憮然! 兩做魚常聽人說北方人不善食魚,因為北方河流少,魚也就不多。我認識一位蒙古貴族,除了糟溜魚片之外,從不食魚;清蒸鰣魚,幹燒鯽魚,他不屑一顧,他生怕骨鯁刺喉。可是亦不儘然。不久以前我請一位廣東朋友吃石門鯉魚,居然談笑間一根大刺橫鯁在喉,喝醋吞饅頭都不收效,只好到醫院行手術,以後他大概只能吃“滑魚球”了。我又有一位江西同學,他最會吃魚,一見魚膾上桌便不停下箸,來不及剔吐魚刺,伸出舌頭往嘴邊一送,便一根根魚刺貼在嘴角上,積滿一把才用手抹去。可見食魚之巧拙,與省籍無關,不分南北。《詩經‧陳風》:“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本草綱目》說“魴魚處處有之” “河”就是黃河。魴味腴美,。漢沔固盛產,黃河裡也有。鯉魚就更不必說。跳龍門的就是鯉魚。馮諼齊人,彈鋏歎食無魚,孟嘗君就給他魚吃,大概就是黃河鯉了。提起黃河鯉,實在是大大有名。黃河自古時常氾濫,七次改道,為一大災害,治黃乃成歷朝大事。清代置河道總督管理其事,動員人眾,斥付鉅資,成為大家豔羨的肥缺。從事河工者乃窮極奢侈,飲食一道自然精益求精。於是豫菜乃能於餐館業中獨樹一幟。全國各地皆有魚產,松花江的白魚、津沽的銀魚、近海的石首魚、松江之鱸、長江之鰣、江淮之??、遠洋之鯧……無不佳美,難分軒輊。黃河鯉也不過是其之一。豫菜以開封為中心,洛陽亦差堪頡頏。到豫菜館吃飯,櫃上先敬上一碗開口湯,湯清而味美。點菜則少不得黃河鯉。一尺多長的活魚,歡蹦亂跳,夥計當著客人面前把魚猛擲觸地,活活摔死。魚的做法很多,我最欣賞清炸醬汁兩做,一魚兩吃,十分經濟。清炸魚說來簡單,實則可以考驗廚師使油的手藝。使油要懂得沸油、熱油、溫油的分別。有時候做一道菜,要轉變油的溫度。炸魚要用豬油,炸出來色澤好,用菜油則易焦。魚剖為兩面,取其一面,在表面上斜著縱橫細切而不切斷。入熱油炸之,不須裹麵糊,可裹芡粉,炸到微黃,魚肉一塊塊地裂開,看樣子就引人入勝。撒上花椒鹽上桌。常見有些他處的餐館做清炸魚,魚的身分是無可奈何的事,只要是活魚就可以入選了,但是刀法太不講究,切條切塊大小不一,魚刺亦多橫斷,最壞的是外面裹了厚厚一層麵糊。兩做魚另一半醬汁,比較簡單,整塊的魚嫩熟之後澆上醬汁即可,唯汁宜稠而不黏,鹹而不甜。要撒薑末,不需別的佐料。 熗青蛤北人不大吃帶殼的軟體動物,不是不吃,是不似南人之普遍嗜食。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四:“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慶曆中,群學士會于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饔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訝之,使人檢視,則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爛。’坐客莫不大笑。 ”沈括,宋時人,當時可能有過這樣的一個饔人鬧過這樣的一個笑話。北平山東餐館裡,有一道有名的菜“熗青蛤”。所謂青蛤,一寸來長,殼面作淡青色,平滑潔淨,肉微呈黃色,在蛤類中比較,最具乾淨相。做法簡單,先在沸水中燙過,然後掰開貝殼,一個個地都仰列在盤裡,撒上料酒、薑末、胡椒粉,即可上桌,為上好的佐酒之物。另一吃法是做“芙蓉青蛤”,所謂芙蓉就是蒸蛋羹,蒸到半熟時把剝好的青蛤肉擺在表面上,再蒸片刻即得。也有不剝蛤肉,整個青蛤帶殼投在蛋裡去蒸的。這種帶殼蒸的辦法,似嫌粗豪,但是也有人說非如此不過癮。青蛤在家裡也可以吃,手續簡單,不過在北方吃東西多按季節。春夏之交,黃魚、大頭魚上市,也就是吃蛤蜊的旺季。我記得先君在世的時候,照例要到供應水產最為豐富的東單牌樓菜市採購青蛤,一買就是滿滿一麻袋,足足有好幾十斤,幾乎一個人都提不動,運回家來供我們大嚼。先是浸蛤于水,過一晝夜而泥沙吐盡。聽人說,水裡若是滴上一些麻油,則泥沙吐得更快更乾淨。我沒有試過。蛤雖味鮮,不宜多食,但是我的二姊曾有一頓吃下一百二十個青蛤的紀錄。大家這樣狂吃一頓,一年之內不作再吃想矣。在臺灣我沒有吃到過青蛤。著名的食物“蚵仔煎”,蚵仔是台語,實即牡蠣,亦即蠔。這種東西寧波一帶盛產。剝出來的肉,名為蠣黃。李時珍《本草》:“南海人,食其肉,謂之蠣黃。”其實蠣黃亦不限於南海。東北人喜歡吃的白肉酸菜火鍋,即往往投入一盤蠣黃,使湯味格外鮮美。此地其他貝類,如哈螞、蚋、海瓜子,大部分都是醬油湯子裡泡著,鹹滋滋的,失去鮮味不少。蚶子是南方普遍食物,人工培養蚶子的地方名為“蚶田”。《清一統志》:“莆田縣東七十裡大海上,有蚶田四百頃。”規模好大!蚶子用開水一燙,掰開加三合油加薑末就可以吃,殼裡漾著血水,故名血蚶。我看見那血水,心裡不舒服,再想到上海弄堂裡每天清早刷馬桶的人,用竹帚蚶子殼嘩啦嘩啦攪得震天響,看著蚶子就更不自在了。至於淡菜,一名殼菜,也是浙閩名產,曬乾了之後可用以煨紅燒肉,其形狀很醜,像是曬乾了的蟬,又有人想入非非說是像另外一種東西。總之這些貝類都不是北人所易接受的。美國西海岸自阿拉斯加起以至南加州,海底出產一種巨大的蛤蜊,名曰 geoduck,很奇怪的當地的人卻讀如“古異德克”,又名之曰“蛤王”(kingclam)。其殼並不太大,大者長不過四五寸許,但是它的肉體有一條長長的粗粗的肉伸出殼外,略有伸縮性,但不能縮進殼裡,像象鼻一般,其狀不雅,長可達一尺開外,兩片硬殼貼在下面形同虛設。這條長鼻肉味鮮美,可以說是美國西海岸食物中的雋品。我曾為文介紹,可是國人旅遊美國西部者,搜奇選勝,卻很少人嘗過古異德克。知音很難,知味亦不易。我初嘗異味是在西雅圖的高叔哿、嚴倚雲伉儷府上,這兩位都精易牙之術。高先生告訴我,古異德克雖是珍品,而美國人不善處理,較高級餐館菜單中偶然也列此一味,但是烹製出來,儘管猛加白蘭地,不是韌如皮鞋底,就是味同嚼蠟。皆因西人烹調方法,不外油炸、水煮、熱烤,就是缺了我們中國的“炒”。他們根本沒有炒菜鍋。英文中沒有相當於“炒”的字,目前一般翻譯都作 stirfry(一面翻騰一面煎)。高先生做古異德克是用炒的方法,先把象鼻形的那根肉割下來,其餘部分丟棄,用沸水一澆,外表一層粗皺的松皮就容易脫落下來了,然後切成薄片,越薄越好。旺火,沸油,爆炒,加進蔥薑鹽,翻動十來下,熟了,略加玉米粉,使汁稠,趁熱上桌。吃起來有廣東館子“炒響螺”的味道,美。美國人不懂這一套。風行美國各地的“蛤羹”(clam chowder)味道不錯,裡面的番薯牛奶麵粉大概不少,稠糊糊的,很難發現其中有蛤。現在他們動起“蛤王”的腦筋來了,切碎古異德克制作蛤羹,並且裝了罐頭,想來風味不惡。一九八六年五月七日臺灣一家報紙刊出一則新聞式的廣告,標題是《深海珍品鮑魚貝——肉質鮮美好口味》。鮑魚貝的名字起得好,即是古異德克。據說日本在一九七六年引進了鮑魚貝,而且還生吃。在臺灣好像尚未被老饕注意,也許是因為我們的美味種類已經太多了。從未見過。菁清說她從小就喜歡吃,清粥小菜經常少不了它。有一天她居然在臺北一家店裡瞥見了一瓶瓶的黃泥螺,像是他鄉遇故知一般,掃數買了回來。以後再買就買不到了。據告這是海員偶然攜來寄售的。黃泥螺小得像綠豆一般,黑不溜湫的,不起眼,裡面的那塊肉當然是小得可憐,而且鹹得很。 生炒鱔魚絲鱔為我國特產。正寫是□,鱔為俗字,一名曰□。《山海經‧北山經》:“姑灌之山,湖灌之水出焉,其中多。”鱔魚各地皆有生產,腹作黃色,故曰黃鱔,淺水泥塘以至稻田,到處都有。鱔魚的樣子有些可怕,像蛇,像水蛇,遍體無鱗,而又渾身裹著一層黏液,滑溜溜的,因此有人怕吃它。我小時看廚師宰鱔魚,印象深刻。鱔魚是放在院中大水缸裡的,鱔魚一條條在水中直立,探頭到水面吸空氣,抓它很容易,手到擒來。因為它黏,所以要用抹布裹著它才能抓得牢。用一根大鐵釘把鱔魚頭部仰著釘牢在砧板上,然後順著它的肚皮用尖刀直劃,取出臟腑,再取出脊骨,皮上黏液當然要用鹽搓掉。血淋淋的一道殺宰手續,看得人心驚膽戰。《顏氏家訓‧歸心》:“江陵劉氏,以賣鱔羹為業,後生一子,頭是鱔,以下方為人耳。”蓮池大師《放生文》注:“杭州湖墅於氏者,有鄰家被盜,女送鱔魚十尾,為母問安,畜甕中,忘之矣。一夕,夢黃衣尖帽者十人,長跪乞命,覺而疑之,卜諸術人,曰:‘當有生求放耳。’遍索室內,則甕有巨鱔在焉,數之正十,大驚,放之,時萬曆九年事也。”信有因果之說,遂做放生之論。但是美味所在,放者自放,吃者自吃。在北方只有河南餐館賣鱔魚,山東館沒有這一項,食客到山東館子點鱔魚,是外行。河南館做鱔魚,我最欣賞的是生炒鱔魚絲。其他任何配料。這樣炒出來的鱔魚,肉是白的,微有脆意,極可口,不失鱔魚本味。另一做法是黃燜鱔魚段,切成四方塊,加一大把整的蒜瓣進去,加醬油,燜爛,汁要濃。這樣做出來的鱔魚是酥軟的,另有風味。淮揚館子也善做鱔魚,其中“熗虎尾”一色極為佳美。把鱔魚切成四五寸長的寬條,像老虎尾巴一樣,上略寬,下尖細,如果全是截自鱔魚尾巴,則更妙。以沸湯煮熟之後即撈起,一條條地在碗內排列整齊,澆上預先備好麻油醬油料酒的湯汁,冷卻後,再撒上大量的搗碎了的蒜(不是蒜泥)。宜冷食。樣子有一點嚇人,但是味美。至於炒鱔糊,或加粉絲墊底名之為軟兜帶粉。那鱔魚雖名為炒,卻不是生炒,是煮熟之後再炒,已經十分油膩。上桌之後侍者還要手持一隻又黑又髒的搪瓷碗(希望不是漱口杯),澆上一股子沸開的油,?啦一聲,油直冒泡,然後就有熱心人用筷子亂攪拌一陣,還有熱心人猛撒胡椒粉。那鱔魚當中時常羼上大量筍絲、茭白絲之類,有喧賓奪主之勢。遇到這種場面。就不能不令人懷念生炒鱔魚絲了。在萬華吃海鮮,有一家招牌大書生炒鱔魚絲,實際上還是熟炒。我曾問過一家北方名館主人,為什麼不試做生炒鱔絲,他說此地沒有又粗又壯的巨鱔,切不出絲。也許他說得對,在市場裡是很難遇到夠尺寸的黃鱔。江浙的爆鱔過橋面,令我懷想不置。爆鱔是炸過的鱔魚條,然後用醬油燜,加相當多的糖。這種爆鱔,非常香脆,以半碟下酒,另半碟連汁倒在面上,香極了。聽說某處有所謂全鱔席,我沒有見過這種場面,想來原則上和拌鴨掌、糟鴨片、燴鴨條、糟蒸鴨肝、燴鴨胰、黃燜鴨塊、薑芽炒鴨片、燴鴨舌,最後是掛爐燒鴨。全鱔席當然也是類似的做法。這是噱頭,知味者恐怕未必以為然,因為吃東西如配方,也要君臣佐使,搭配平衡。 醬菜抗戰時我和老向在後方,我調侃他說:“貴地保定府可有什麼名產? ”他說:“當然有。保定府,三宗寶,鐵球、醬菜、春不老。 ”他並且說將來有機會必定向我獻寶,讓我見識見識。抗戰勝利還鄉,他果然實踐諾言,從保定到北平來看我,攜來一對鐵球(北方老人喜歡放在手裡揉玩的玩意兒),一簍醬菜,春不老因不是季節所以不能帶。鐵球且不說,那簍醬菜我起初未敢小覷,勝地名產,當有可觀。油紙糊的簍子,固然簡陋,然凡物不可貌相。打開一看,原來是什錦醬菜,蘿蔔、黃瓜、花生、杏仁都有。我捏一塊放進嘴裡,哇,比北平的大醃蘿蔔“棺材板”還鹹!北平的醬菜,妙在不太鹹,同時又不太甜。糧食店的六必居,因為匾額是嚴嵩寫的(三個大字確是寫得好),格外地有號召力,多少人跑老遠的路去買他的醬菜。我個人的經驗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鐵門也有一家醬園,名震遐邇,也沒有什麼特殊。倒是金魚胡同市場對面的天義順,離我家近,貨色新鮮。醬菜的花樣雖多,要以甜醬蘿蔔為百吃不厭的正宗。這種蘿蔔,細長質美,以制醬菜恰到好處。他處的蘿蔔嫌水分太多,質地不夠堅實,醬出來便不夠脆,不禁咀嚼。可見一切名產,固有賴於手藝,實則材料更為重要。甘露,做螺螄狀,清脆可口,是別處所沒有的。丁。過年前後,野味上市,山雞(即雉)最受歡迎,那彩色的長尾巴就很好看。取山雞胸肉切丁,加進醬黃瓜塊大火爆炒,臨起鍋時再投入大量的蔥塊,澆上麻油拌勻。炒出來雞肉白嫩,羼上醬黃瓜又鹹又甜的滋味,是年菜中不可少的一味,要冷食。北地寒,炒一大鍋,經久不壞。另一味是醬白菜炒冬筍,這是一道熱炒。北方的白菜又白又嫩,新從醬缸出來的醬白菜,切碎,炒冬筍片,別有風味,和雪裡蕻炒筍、薺菜炒筍、冬菇炒筍迥乎不同。日本的醬菜,太鹹太甜,吾所不取。 水晶蝦餅蝦,種類繁多。《爾雅翼》所記:“閩中五色蝦,長尺餘,具五色。梅蝦,梅雨時有之。蘆蝦,青色,相傳蘆葦所變。泥蝦,稻花變成,多在泥田中。又蝦姑,狀如蜈蚣,一名管蝦。 ”蘆葦稻花會變蝦,當然是神話。蝦不在大,大了反倒不好吃。龍蝦一身鎧甲,須爪戟張,樣子十分威武多姿,可是剝出來的龍蝦肉,只合做沙拉,其味不過爾爾。大抵咸水蝦,其味不如淡水蝦。蝦要吃活的,有人還喜活吃。西湖樓外樓的“熗活蝦”,是在湖中用竹簍養著的,臨時取出,歡蹦亂跳,剪去其須吻足尾,放在盤中,用碗蓋之。食客微啟碗沿,以箸挾取之,在旁邊的小碗醬油、麻油、醋裡一蘸,送到嘴邊用上下牙齒一咬,像嗑瓜子一般,吮而食之。吃過把蝦殼吐出,猶咕咕嚷嚷地在動。有時候嫌其過分活躍,在盤裡潑進半杯燒酒,蝦乃頹然醉倒。據聞有人吃活蝦不慎,蝦一躍而戳到喉嚨裡,幾致喪生。生吃活蝦不算稀奇,我還看見過有人生吃活螃蟹呢!熗活蝦,我無福享受。我只能吃油爆蝦、鹽焗蝦、白灼蝦。若是嫌剝殼麻煩,就只好吃炒蝦仁、燴蝦仁了。說起炒蝦仁,做得最好的是福建館子,記得北平西長安街的忠信堂是北平唯一的有規模的閩菜館,做出來的清炒蝦仁不加任何配料,滿滿一盤蝦仁,鮮明莊的拿手,館子做不好。飯莊的酒席上四小碗其中一定有燴蝦仁,羼一點荸薺丁、勾芡,一切恰到好處。這一炒一燴,全是靠使油及火候,灶上的手藝一點也含糊不得。蝦仁剁碎了就可以做炸蝦球或水晶蝦餅了。不要以為剁碎了的蝦仁就可以用不新鮮的剩貨充數,瞞不了知味的吃客。吃館子的老主顧,堂倌也不敢怠慢,時常會用他的山東腔說:“二爺!甭起蝦夷兒了,蝦夷兒不信香。 ”)堂倌和吃客合作無間。水晶蝦餅是北平錫拉胡同玉華台的傑作。和一般的炸蝦球不同,一定要用白蝦,通常是青蝦比白蝦味美,但是做水晶蝦餅非白蝦不可,為的是做出來顏色純白。七分蝦肉要加三分豬板油,放在一起剁碎,不要碎成泥,加上一點點芡粉,蔥汁薑汁,捏成圓球,略按成厚厚的小圓餅狀,下油鍋炸,要用豬油,用溫油。炸出來白如凝脂,溫如軟玉,入口松而脆,蘸椒鹽吃。自從我知道了水晶蝦餅裡大量羼豬油,就不敢常去吃它。連帶著對一般館子的炸蝦球,我也有戒心了。 湯包說起玉華台,這個館子來頭不小,是東堂子胡同楊家的廚子出來經營掌勺。他的手藝高強,名作很多,所做的湯包,是故都的獨門絕活。包子算得什麼,何地無之?但是風味各有不同。上海沈大成、北萬馨、五芳齋所供應的早點湯包,是令人難忘的一種。包子小,小到只好一口一個,但是每個都包得俏式,小蒸籠裡墊著松針(可惜松針時常是用得太久了一些),有賣相。名為湯包,實際上包子裡面並沒有多少湯汁,倒是外附一碗清湯,表面上浮著七條八條的蛋皮絲,有人把包子丟在湯裡再吃,成為名副其實的湯包了。這種小湯包餡子固然不惡,妙處卻在包子皮,半發半不發,薄厚適度,製作上頗有技巧。臺北也有人仿製上海式的湯包,得其仿佛,已經很難得了。天津包子也是遠近馳名的,尤其是狗不理的字號十分響亮。其實不一定要到狗不理去,搭平津火車一到天津西站就有一群販賣包子的高舉籠屜到車窗前,伸胳膊就可以買幾個包子。包子是扁扁的,裡面確有比一般為多的湯汁,湯汁中有幾塊碎肉蔥花。有人到鋪子裡吃包子,才出籠的,包子裡的湯汁曾有燙了脊背的故事,因為包子咬破,湯汁外溢,流到手掌上,一舉手乃順著胳膊流到脊背。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不過天津包子確是湯汁多,吃的時候要一個笑話:兩個不相識的人據一張桌子吃包子,其中一位一口咬下去,包子裡的一股湯汁直飆過去,把對面客人噴了個滿臉花。肇事的這一位並未覺察,低頭猛吃。對面那一位很沉得住氣,不動聲色。堂倌在一旁看不下去,趕快擰了一個熱手巾把送了過去,客徐曰:“不忙,他還有兩個包子沒吃完哩。” 玉華台的湯包才是真正的含著一汪子湯。一籠屜裡放七八個包子,連籠屜上桌,熱氣騰騰,包子底下墊著一塊蒸籠布,包子扁扁地塌在蒸籠布上。取食的時候要眼明手快,抓住包子的皺褶處猛然提起,包子皮驟然下墜,像是被嬰兒吮癟了的乳房一樣,趁包子沒有破裂趕快放進自己的碟中,輕輕咬破包子皮,把其中的湯汁吸飲下肚,然後再吃包子的空皮。沒有經驗的人,看著籠裡的包子,又怕燙手,又怕弄破包子皮,猶猶豫豫,結果大概是皮破湯流,一塌糊塗。有時候堂倌代為抓取。其實吃這種包子,其樂趣一大部分就在那一抓一吸之間。包子皮是燙麵的,比燙麵餃的面還要稍硬一點,否則包不住湯。那湯原是肉汁凍子,打進肉皮一起煮成的,所以才能凝結成為包子餡。湯裡面可以看得見一些碎肉渣子。這樣的湯味道不會太好。我不太懂,要喝湯為什麼一定要灌在包子裡然後再喝。 核桃酪玉華台的一道甜湯核桃酪也是非常叫好的。有一年,先君帶我們一家人到玉華台午飯。滿滿的一桌,祖孫三代。所有的拿手菜都吃過了,最後是一大缽核桃酪,色香味俱佳,大家叫絕。先慈說:“好是好,但是一天要賣出多少缽,需大量生產,所以只能做到這個樣子,改天我在家裡試用小鍋製作,給你們嘗嘗。”我們聽了大為雀躍。回到家裡就天天泥著她做。我母親做核桃酪,是根據她為我祖母做杏仁茶的經驗揣摩著做的。我祖母的早點,除了燕窩、哈什瑪、蓮子等之外,有時候也要喝杏仁茶。街上賣的杏仁茶不夠標準,要我母親親自做。雖是只做一碗,材料和手續都不能缺少,久之也就做得熟練了。核桃酪和杏仁茶性質差不多。核桃來自羌胡,故又名胡桃,是張騫時傳到中土的,北方盛產。取現成的核桃仁一大捧,用沸水泡。司馬光幼時請人用沸水泡,以便易於脫去上面的一層皮,而謊告其姊說是自己剝的,這段故事是大家所熟悉的。開水泡過之後要大家幫忙剝皮的,雖然麻煩,數量不多,頃刻而就。在館子裡據說是用硬毛刷去刷的!核桃要搗碎,越碎越好。取紅棗一大捧,也要用水泡,泡到漲大的地步,然後煮,去皮,這是最煩人的一道手續。棗樹在黃河兩岸無處不有,而以河南靈寶裡中藥店所賣的紅棗那樣瘦小。可是剝皮取棗泥還是不簡單。我們用的是最簡單的笨法,用小刀刮,刮出來的棗泥絕對不帶碎皮。白米小半碗,用水泡上一天一夜,然後撈出來放在搗蒜用的那種較大的缸缽裡,用一根搗蒜用的棒棰(當然都要洗乾淨使不帶蒜味,沒有搗過蒜的當然更好),盡力地搗,要把米搗得很碎,隨搗隨加水。碎米渣滓連同汁水倒在一塊紗布裡,用力擰,擰出來的濃米漿留在碗裡待用。煮核桃酪的器皿最好是小薄銚。銚讀如吊。《正字通》:“今釜之小而有柄有流者亦曰銚。 ”銚是泥沙燒成的,質料像砂鍋似的,很原始,很粗陋,黑黝黝的,但是非常靈巧而有用,煮點東西不失原味,遠較銅鍋鐵鍋為優,可惜近已淘汰了。把米漿、核桃屑、棗泥和在一起在小薄銚裡煮,要守在一旁看著,防溢出。很快地就煮出了一銚子核桃酪。放進一點糖,不要太多。分盛在三四個小碗(蓮子碗)裡,每人所得不多,但是看那顏色,微呈紫色,棗香、核桃香撲鼻,喝到嘴裡黏糊糊的、甜滋滋的,真捨不得一下子咽到喉嚨裡去。 鐵鍋蛋北平前門外大柵欄中間路北有一個窄窄的小胡同,走進去不遠就走到底,迎面是一家軍衣莊,靠右手一座小門兒,上面高懸一面紮著紅綢的黑底金字招牌“厚德福飯莊”。看起來真是不起眼,局促在一個小巷底,沒去過的人還是不易找到。找到了之後看那門口裡面黑咕隆咚的,還是有些不敢進去。裡面樓上樓下各有兩三個雅座,另外三五個散座,那座樓梯又陡又窄,險巇難攀。可是客人一踏進二門,櫃檯後門的賬房苑先生就會扯著大嗓門兒高呼:“看座兒!”他的嗓門兒之大是有名的,常有客人一進門就先開口:“您別喊,我帶著孩子呢,小孩兒害怕。” 厚德福飯莊地方雖然逼仄,名氣不小,是當時唯一老牌的河南館子。本是煙館,所以一直保存那些短炕,附帶著賣些點心之類,後來實行煙禁,就改為飯館了。掌櫃的陳蓮堂是開封人,很有一把手藝,能制道地的河南菜。時值袁世凱當國,河南人士彈冠相慶之下,厚德福的聲譽因之鵲起。嗣後生意日盛,但是風水關係,老址絕不遷移,而且不換裝修,一副古老簡陋的樣子數十年不變。為了擴充營業,先後在北平的城南遊藝園、瀋陽、長春、黑龍江、西安、青島、上海、香港、重慶、北碚等處開設分號。陳掌櫃手下高徒,一個個地派赴各地分號掌勺。這是厚德福的簡史。厚德福的拿手菜頗有幾樣,請先談談鐵鍋蛋。會做菜,只會炒雞蛋。 ”說這句話的人一定不會把一盤雞蛋炒得像個樣子。攤雞蛋是把打過的蛋煎成一塊圓形的餅,“烙餅卷攤雞蛋”是北方鄉下人的美食。蒸蛋羹花樣繁多,可以在表面上敷一層幹貝絲、蝦仁、蛤蜊肉……至不濟撒上一把肉鬆也成。厚德福的鐵鍋蛋是燒烤的,所以別致。當然先要置備黑鐵鍋一個,口大底小而相當高,鐵要相當厚實。在打好的蛋裡加上油鹽佐料,羼一些肉末綠豌豆也可以,不可太多,然後倒在鍋裡放在火上連燒帶烤,烤到蛋漲到鍋口,作焦黃色,就可以上桌了。這道菜的妙處在於鐵鍋保溫,上了桌還有響的滾沸聲,這道理同於所謂的“鐵板燒”,而保溫之久猶過之。我的朋友李清悚先生對我說,他們南京人所謂“漲蛋”也是同樣的好吃。我到他府上嘗試過,確是不錯,蛋漲得高高的起蜂窩,切成菱形塊上桌,其缺憾是不能保溫,稍一冷卻蛋就縮塌變硬了。還是要讓鐵鍋蛋獨擅勝場。趙太侔先生在厚德福座中一時興起,點了鐵鍋蛋,從懷中掏出一元錢,令夥計出去買幹奶酪(cheese),囑咐切成碎丁羼在蛋裡,要美國奶酪,不要瑞士的,因為美國的比較味淡,容易被大家接受。做出來果然氣味噴香,不同凡響,從此懸為定例,每吃鐵鍋蛋必加奶酪。現在我們有新式的電爐烤箱,不一定用鐵鍋,禁燒烤的玻璃盆(casserole)照樣的可以做這道菜,不過少了鐵鍋那種原始粗獷的風味。 瓦塊魚嚴辰《憶京都詞》有一首是這樣的:憶京都‧陸居羅水族鯉魚碩大鯽魚多,當客擊鮮隨所欲。此間俗手昧烹鮮,令人空自羨臨淵。嚴辰是浙江人,在魚米之鄉居然也懷念北人的烹鮮。故都雖然嘗不到黃河鯉,但是北平的河南館子治魚還是有獨到之處。厚德福的瓦塊魚便是一絕。一塊塊炸黃了的魚,微微彎卷作瓦片形,故以為名。上面澆著一層稠黏而透明的糖醋汁,微撒薑末,看那形色就令人饞涎欲滴。我曾請教過厚德福的陳掌櫃,他說得輕鬆,好像做瓦塊魚沒什麼訣竅。其實不易。首先選材要精,活的鯉魚、鰱魚都可以用,取其肉厚,但是只能用其中段最精的一部分。刀法也有考究,魚片厚薄適度,去皮,而且盡可能避免把魚刺切得過分碎斷。裹蛋白芡粉,不可裹麵糊。溫油,炸黃。做糖醋汁,用上好藕粉,比芡粉好看,顯著透明,要用冰糖,乘熱加上一勺熱油,取其光亮,澆在炸好的魚片上,最後撒上薑末,就可以上桌了。一盤瓦塊魚差不多快吃完,夥計就會過來,指著盤中的剩汁工夫,一盤像是焦炒麵似的東西端上來了。酥、脆,微帶甜酸,味道十分別致。可是不要誤會,那不是麵條,麵條沒有那樣細,也沒有那樣酥脆。那是番薯(即馬鈴薯)擦絲,然後下油鍋炒成的。若不經意,還會以為真是麵條呢。因為瓦塊魚受到普遍歡迎,各地仿製者眾,但是很少能達到水準。大凡烹飪之術,各地不盡相同,即以一地而論,某一餐館專擅某一菜數,亦不容他家效顰。瓦塊魚是河南館的拿手,而以厚德福為最著;醋溜魚(即五柳魚)是南宋宋五嫂五柳居的名菜,流風遺韻一直保存在杭州西湖。《光緒順天府志》:“五柳魚,浙江西湖五柳居煮魚最美,故傳名也。今京師食館仿為之,亦名五柳魚。 ”北人仿五柳魚,猶南人仿瓦塊魚也,不能神似。北人做五柳魚,肉絲、筍絲、冬菇絲堆在魚身上,魚肉硬,全無五柳風味。樊樊山有一首詩《攘蘅招飲廣和居即席有作》:閑裡堂堂白日過,與君對酒複高歌。都京禦氣橫江盡,金鐵秋聲出塞多。未信魚羹輸宋嫂,漫將肉餅問曹婆。百年掌故城南市,莫學桓伊喚奈何。所謂“未信魚羹輸宋嫂”,是想像之詞。百年老店,摹仿宋五嫂的手藝,恐怕也是不過爾爾。 溜黃菜黃菜指雞蛋。北平人常避免說蛋字,因為它不雅,我也不知為什麼不雅。“木樨”“芙蓉”“雞子兒”都是代用詞。更進一步“雞”字也忌諱,往往稱為“牲口”。溜黃菜不是炒雞蛋。北方館子常用為一道外敬的菜。就如同“三不粘”“炸元宵”之類,作為是奉贈性質。天津館子最愛外敬,往往客人點四五道菜,館子就外敬三四道,這樣離譜的外敬,雖說不是什麼貴重的菜色,也使顧客覺得不安。溜黃菜是用豬油做的,要把雞蛋黃製成糊狀,故曰溜。蛋黃糊裡加荸薺丁,表面撒一些清醬肉或火腿屑,用調羹舀來吃,色香味俱佳。家裡有時宴客,如果做什麼芙蓉干貝之類,專用蛋白,蛋黃留著無用,這時候就可以考慮做一盆溜黃菜了。館子裡之所以常外敬溜黃菜,可能也是剩餘的蛋黃無處打發,落得外敬做人情了。我家裡試做好幾次溜黃菜都失敗了,炒出來是一塊塊的,不成糊狀。後來請教一位親戚,承她指點,方得訣竅。原來蛋黃打過加水,還要再加芡粉(多加則稠少加則稀),入旺油鍋中翻攪之即成。凡事皆有一定的程序材料,不是暗中摸索所能輕易成功的。自從試作成功,便常利用剩餘的蛋黃炮製。直到有一天我膽結石症發,入院照愛克司光,醫囑先吞雞蛋黃一枚,我才知道雞蛋黃有什麼作用。原來蛋黃幾乎全是脂肪,生吞下去之後膽囊受到刺激,立刻大量放出膽汁,這時候給膽囊照相便照得最清楚。此後我是無膽之人,見了溜黃菜便敬而遠之,由有膽的人去享受了。 酸梅湯與糖葫蘆夏天喝酸梅湯,冬天吃糖葫蘆,在北平是不分階級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過東西也有精粗之別。琉璃廠信遠齋的酸梅湯與糖葫蘆,特別考究,與其他各處或街頭小販所供應者大有不同。徐淩霄《舊都百話》關於酸梅湯有這樣的記載:暑天之冰,以冰梅湯為最流行,大街小巷,幹鮮果鋪的門口,都可以看見“冰鎮梅湯”四字的木簷橫額。有的黃底黑字,甚為工致,迎風招展,好似酒家的簾子一樣,使過往的熱人,望梅止渴,富於吸引力。昔年京朝大老,貴客雅流,有閒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廠逛逛書鋪,品品骨董,考考版本,消磨長晝。天熱口幹,輒以信遠齋梅湯為解渴之需。信遠齋鋪面很小,只有兩間小小門面,臨街是舊式玻璃門窗,拂拭得一塵不染,門楣上一塊黑漆金字匾額,鋪內清潔簡單,道地北平式的裝修。進門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一,裡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圍全是碎冰,罐裡是酸梅湯,所以名為冰鎮。北平的冰是從什?海或護城河挖取藏在窖內的,冰塊裡可以看見草皮木屑,泥沙穢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飲料裡喝的。什?海會賢堂的名件“冰是不可思議。有人甚至把冰塊放在酸梅湯裡!信遠齋的冰鎮就高明多了。因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來涼沁脾胃。他的酸梅湯的成功秘訣,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濃而釅。上口冰涼,甜酸適度,含在嘴裡如品純醪,捨不得下嚥。很少人能站在那裡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戰勝利還鄉,我帶孩子們到信遠齋,我准許他們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們連盡七碗方始罷休。我每次去喝,不是為解渴,是為解饞。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動腦筋把信遠齋的酸梅湯制為罐頭行銷各地,而一任“可口可樂”到處猖狂。信遠齋也賣酸梅鹵、酸梅糕。鹵沖水可以制酸梅湯,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邊細啜那樣有味。我自己在家也曾試做,在藥鋪買了烏梅,在乾果鋪買了大塊冰糖,不惜工本,仍難如願。信遠齋掌櫃姓蕭,一團和氣,我曾問他何以仿製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請您過來喝,別自己費事了。” 信遠齋也賣蜜餞、冰糖子兒、糖葫蘆。以糖葫蘆為最出色。北平糖葫蘆分三種。一種用麥芽糖,北平話是糖稀,可以做大串山裡紅的糖葫蘆,可以長達五尺多,這種大糖葫蘆,新年廠甸賣得最多。麥芽糖裹水杏兒(沒長大的綠杏),很好吃,做糖葫蘆就不見佳,尤其是山裡紅常是爛的或是帶蟲子屎。另一種用白糖和了粘上去,冷了之後白汪汪的一層霜,另有風味。正宗是冰糖葫蘆,薄薄一層糖,透明雪亮。材料種類甚多,諸如海棠、山藥、山藥豆、杏幹、葡萄、橘子、荸薺、核桃,但是以山裡紅為正宗。山裡紅,即山楂,北地盛產,味酸,裹糖則極可口。一般的糖葫蘆皆用半尺來長的竹簽,街頭小販所售,多染塵沙,而且品質粗劣。東安市場所售較為均單個獨立,所用之果皆碩大無疵,而且乾淨,放在墊了油紙的紙盒中由客攜去。離開北平就沒吃過糖葫蘆,實在想念。近有客自北平來,說起糖葫蘆,據稱在北平這種不屬?任何一個階級的食物幾已絕跡。他說我們在臺灣自己家裡也未嘗不可試做,臺灣雖無山裡紅,其他水果種類不少,沾了冰糖汁,放在一塊塗了油的玻璃板上,送入冰箱冷凍,豈不即可等著大嚼?他說他製成之後將邀我共嘗,但是迄今尚無下文,不知結果如何。 鍋燒雞北平的飯館幾乎全屬煙臺幫,濟南幫興起在後。煙臺幫中致美齋的歷史相當老。清末魏元曠《都門瑣記》談到致美齋:“致美齋以四做魚名。蓋一魚而四做之,子名‘萬魚’,與頭尾皆紅燒,醬炙中段,餘或炸炒,或醋溜、糟溜。 ”致美齋的魚是做得不錯,我所最欣賞的卻別有所在。鍋燒雞是其中之一。先說致美齋這個地方。店坐落在煤市街,坐東面西,樓上相當寬敞,全是散座。因生意鼎盛,在對面一個非常細窄的盡頭開闢出一個致美樓,樓上樓下全是雅座。但是廚房還是路東的致美齋的老廚房,做好了菜由小利巴提著盒子送過街。所以這個雅座非常清靜。左右兩個樓梯,由左梯上去正面第一個房間是我隨侍先君經常佔用的一間,窗戶外面有一棵不知名的大樹遮掩,樹葉很大,風也蕭蕭,無風也蕭蕭,很有情調。我第一次吃醉酒就是在這個房間裡。幾杯花雕下肚之後還索酒吃,先君不許,我站在凳子上舀起一大勺湯潑將過去,潑濺在先君的兩截衫上,隨後我即暈倒,醒來發覺已在家裡。這一件事我記憶甚清,時年六歲。鍋燒雞要用小嫩雞,北平俗語稱之為“桶子雞”,疑系“童子雞”之訛。嚴辰《憶京都詞》有一首:憶京都‧桶雞出便宜衰翁最便宜無齒,制仿金陵突過之。不似此間烹不熟,關西大漢方能嚼。注雲:“京都便宜坊桶子雞,色白味嫩,嚼之可無渣滓。 ”他所謂便宜坊桶子雞,指生的雞,也可能是指熏雞。早年一元錢可以買四隻。南京的油雞是有名的,廣東的白切雞也很好,其細嫩並不在北平的之下。嚴辰好像對北平桶子雞有偏愛。我所謂桶子雞是指那半大不小的雞,也就是做“炸八塊”用的那樣大小的雞。整只的在醬油裡略浸一下,下油鍋炸,炸到皮黃而脆。同時另鍋用雞雜(即雞肝、雞胗、雞心)做一小碗鹵,連雞一同送出去。照例這只雞是不用刀切的,要由跑堂的夥計站在門外用手來撕的,撕成一條條的。如果撕出來的雞不夠多,可以在盤子裡墊上一些黃瓜絲。連雞帶鹵一起送上桌,把鹵澆上去,就成為爽口的下酒菜。何以稱之為鍋燒雞,我不大懂。坐平浦火車路過德州的時候,可以聽到好多老幼婦孺扯著嗓子大叫:“燒雞燒雞! ”旅客伸手窗外就可以購買。早先大約一元可買三隻,燒得焦黃油亮,劈開來吃,鹹漬漬的,挺好吃,(夏天要當心,外表亮光光,裡面可能大蛆咕咕嚷嚷!)這種燒雞是用火燒的,也許館子裡的燒雞加上一個鍋字,以示區別。 煎餛飩餛飩這個名稱好古怪。宋程大昌《演繁露》:“世言餛飩,是虜中渾沌氏為之。 ”有此一說,未必可信。不過我們知道餛飩歷史相當悠久,無分南北到處有之。兒時,裡巷中到了午後常聽見有擔販大聲吆喝:“餛飩——開鍋! ”這種餛飩挑子上的餛飩,別有風味,物美價廉。那一鍋湯是骨頭煮的,煮得久,所以是渾渾的、濃濃的。餛飩的皮子薄,餡極少,勉強可以吃出其中有一點點肉。但是佐料不少,蔥花、芫荽、蝦皮、冬菜、醬油、醋、麻油,最後撒上竹節筒裡裝著的黑胡椒粉。這樣的餛飩在別處是吃不到的,誰有工夫去熬那麼一大鍋骨頭湯?北平的山東館子差不多都賣餛飩。我家胡同口有一個同和館,從前在當地還有一點小名,早晨就賣餛飩和羊肉餡和鹵餡的小包子。餛飩做得不錯,湯清味厚,還加上幾小塊雞血幾根豆苗。凡是飯館沒有不備一鍋高湯的(英語所謂“原湯”stock),一碗餛飩舀上一勺高湯,就味道十足。後來“味之素”大行其道,誰還預備原湯?不過善品味的人,一嘗便知道是不是正味。館子裡賣的餛飩,以致美齋的為最出名。好多年前,《同治都門紀略》就有讚賞致美齋的餛飩的打油詩:包得餛飩味勝常,餡融春韭嚼來香。這是同治年間的事,雖然已過了五十年左右,飯館的狀況變化很多,但是他的餛飩仍是不同凡響,主要的原因是湯好。可是我最激賞的是致美齋的煎餛飩,每個餛飩都包得非常俏式,薄薄的皮子挺拔舒翹,像是天主教修女的白布帽子。入油鍋慢火生炸,炸黃之後再上小型蒸屜猛蒸片刻,立即帶屜上桌。餛飩皮軟而微韌,有異趣。 核桃腰偶臨某小館,見菜牌上有核桃腰一味,當時一驚,因為我想起厚德福名菜之一的核桃腰。由於好奇,點來嘗嘗。原來是一盤炸腰花,拌上一些炸核桃仁。軟炸腰花當然是很好吃的一樣菜,如果炸的火候合適。炸核桃仁當然也很好吃,即使不是甜的也很可口。但是核桃仁與腰花雜放在一個盤子裡則似很勉強,一軟一脆,頗不調和。厚德福的核桃腰,不是核桃與腰合一爐而冶之;這個名稱只是說明這個腰子的做法與眾不同,吃起來有核桃滋味或有吃核桃的感覺。腰子切成長方形的小塊,要相當厚,表面上縱橫劃紋,下油鍋炸,火候必須適當,油要熱而不沸,炸到變黃,取出蘸花椒鹽吃,不軟不硬,咀嚼中有異感,此之謂核桃腰。一般而論,北地餐館不善治腰。所謂炒腰花,多半不能令人滿意,往往是炒得過火而幹硬,味同嚼蠟。所以有些館子特別標明南炒腰花,南炒也常是虛有其名。熗腰片也不如一般川菜館或湘菜館之做得軟嫩。炒蝦腰本是江浙館的名菜,能精製細做的已不多見,其他各地餐館仿製者則更不必論。以我個人經驗,福州館子的炒腰花最擅勝場。腰塊切得大大的、厚厚的,略劃縱橫刀紋,做出來其嫩無比,而不帶血水。勾汁也特別考究,微帶甜意。我猜想,可能腰子並未過油,而是水?,然後下鍋爆炒勾汁。這完全是灶上的火候功夫。此間的閩菜館炒腰花,往往是粗製濫造,略具規模,而不墊底,當然未嘗不可,究竟不如清炒。抗戰期間,偶在某一位作家的岳丈鄭老先生家吃飯,鄭先生是福州人,司法界的前輩,雅喜烹調,他的郇廚所制腰花,做得出神入化,至善至美,一飯至今而不能忘。 豆汁兒豆汁下面一定要加一個兒字,就好像說雞蛋的時候雞子下面一定要加一個兒字,若沒有這個輕讀的語尾,聽者就會不明白你的語意而生誤解。胡金銓先生在談老舍的一本書上,一開頭就說:不能喝豆汁兒的人算不得是真正的北平人。這話一點兒也不錯。就是在北平,喝豆汁兒也是以北平城裡的人為限,城外鄉間沒有人喝豆汁兒,製作豆汁兒的原料是用以喂豬的。但是這種原料,加水熬煮,卻成了城裡人個個歡喜的食物。而且這與階級無關。賣力氣的苦哈哈,一臉漬泥兒,坐小板凳兒,圍著豆汁兒挑子,啃豆腐絲兒卷大餅,喝豆汁兒,就鹹菜兒,固然是自得其樂。府門頭兒的姑娘、哥兒們,不便在街頭巷尾公開露面,和窮苦的平民混在一起喝豆汁兒,也會派底下人或者老媽子拿砂鍋去買回家裡重新加熱大喝特喝。而且不會忘記帶回一碟那挑子上特備的辣鹹菜,家裡儘管有上好的醬菜,不管用,非那個廉價的大醃蘿蔔絲拌的鹹菜不夠味。口有同嗜,不分貧富老少男女。我不知道為什麼北平人養成這種特殊的口味。南方人到了北平,不可能喝豆汁兒的,就是河北各縣也沒有人能容忍這個異味而不齜牙咧嘴。豆汁兒之妙,一在酸,酸中帶餿腐的怪味。二在燙,只能吸溜吸溜地喝,不能大口猛灌。三在鹹菜的辣,辣得舌尖發麻。越辣越喝,越喝越燙,最後是滿頭大汗。我小時候在夏天喝豆汁兒,是先脫光脊樑,然後才喝,等到汗落再穿上衣服。自從離開北平,想念豆汁兒不能自已。有一年我路過濟南,在車站附近一個小飯鋪牆上貼著條子說有“豆汁”發售。叫了一碗來吃,原來是豆漿。是我自己疏忽,寫明的是“豆汁”,不是“豆汁兒”。來到臺灣,有朋友說有一家飯館兒賣豆汁兒,乃偕往一嘗。烏糟糟的兩碗端上來,倒是有一股酸餿之味觸鼻,可是稠糊糊的像麥片粥,到嘴裡很難下嚥。可見在什麼地方吃什麼東西,勉強不得。 芙蓉雞片在北平,芙蓉雞片是東興樓的拿手菜。請先說說東興樓。東興樓在東華門大街路北,名為樓,其實是平房,三進又兩個跨院,房子不算大,可是間架特高,簡直不成比例,據說其間還有個故事。當初興建的時候,一切木料都已購妥,原是預備建築樓房的。經人指點,靠近皇城根兒蓋樓房有窺視大內的嫌疑,罪不在小,於是利用已有的木材改造平房,間架特高了。據說東興樓的廚師來自禦膳房,所以烹調頗有一手,這已不可考。其手藝屬?煙臺一派,格調很高。在北京山東館子裡,東興樓無疑地當首屈一指。一九二六年夏,時昭瀛自美國回來,要設筵邀請同學一敘,央我提調,我即建議席設東興樓。彼時燕翅席一桌不過十六元,小學教師月薪僅三十餘元,昭瀛堅持要三十元一桌。我到東興樓吃飯,順便訂席。櫃上聞言一驚,曰:“十六元足矣,何必多費? ”我不聽。開筵之日,珍錯雜陳,豐美自不待言。最滿意者,其酒特佳。我吩咐茶房打電話到長髮叫酒,茶房說不必了,櫃上已經備好。原來櫃上藏有花雕埋在地下已逾十年,取出一壇,羼以新酒,斟在大口淺底的細瓷酒碗裡,色澤光潤,醇香撲鼻,生平品酒此為第一。似此佳釀,酒店所無。而其開價並不特昂,專為留待佳賓。當年北京大館風範如此。與宴者吳文藻、謝冰心、瞿菊農、謝奮程、孫國華等。北京飯館跑堂都是訓練有素的老手。剝蒜剝蔥剝蝦仁的小利人,親切周到而有分寸。在這一方面東興樓規矩特嚴。我幼時侍先君飲于東興樓,因上菜稍慢,我用牙箸在盤碗的沿上輕輕敲了叮噹兩響,先君急止我曰:“千萬不可敲盤碗作響,這是外鄉客粗魯的表現。你可以高聲喊人,但是敲盤碗表示你要掀桌子。在這裡,若是被櫃上聽到,就會立刻有人出面賠不是,而且那位當值的跑堂就要捲舖蓋。真個的捲舖蓋,有人把門簾高高掀起,讓你親見那個跑堂扛著鋪蓋捲兒從你門前急馳而過。不過這是表演性質,等一下他會從後門又轉回來的。”跑堂待客要殷勤,客也要有相當的風度。現在說到芙蓉雞片。芙蓉大概是蛋白的意思,原因不明,“芙蓉蝦仁”“芙蓉干貝”“芙蓉青蛤”皆曰芙蓉,料想是忌諱蛋字。取雞胸肉,細切細斬,使成泥。然後以蛋白攪和之,攪到融合成為一體,略無渣滓,入溫油鍋中攤成一片片狀。片要大而薄,薄而不碎,熟而不焦。起鍋時加嫩豆苗數莖,取其翠綠之色以為點綴。如灑上數滴雞油,亦甚佳妙。製作過程簡單,但是在火候上恰到好處則見功夫。東興樓的菜概用中小盤,菜僅蓋滿碟心,與湘菜館之長箸大盤迥異其趣。或病其量過小,殊不知美食者不必是饕餮客。抗戰期間,東興樓被日寇盤據為隊部。勝利後我返回故都,據聞東興樓移帥府園營業,訪問之後大失所望。蓋已名存實亡,無複當年手藝。菜用大盤,粗劣庸俗。 烏魚錢東興樓又一名饌曰烏魚錢。做法簡單,江浙館皆優為之,而在北平東興樓最擅勝場。烏魚就是墨魚,亦稱烏賊,不是我們這裡盛產烏魚子的烏魚。俗謂烏魚蛋,因蛋字不雅,以其小小圓圓薄薄的形狀似製錢,故稱烏魚錢。而事實上也不是蛋,魚卵哪有這樣大?誰又有本領把它切得那樣薄,那樣勻?我一直以為那是蛋。有一年在青島順興樓飲宴,上了這樣一碗羹,皆誇味美。座中有一位曾省教授,是研究海洋魚產的專家,他說這是烏賊的子宮,等於包著魚卵的胞衣,曬乾之後就成了片片的形狀。我這才恍然大悟。烏魚錢制羹,要用清澈的高湯。魚錢發好,洗淨入沸湯煮熟,略勾粉芡,但勿過稠,臨上桌時撒芫荽末、胡椒粉,加少許醋,使微酸,殺腥氣。 韭菜簍韭菜是蔬菜中最賤者之一,一年四季到處有之,有一股強烈濃濁的味道,所以惡之者謂之臭,喜之者謂之香。道家列入五葷一類,與蔥蒜同科。但是事實上喜歡吃韭菜的人多,而且雅俗共賞。有一年我在青島寓所後山坡閒步,看見一夥石匠在鑿石頭打地基。將近歇晌的時候,有人擔了兩大籠屜的韭菜餡發麵餃子來,揭開籠屜蓋熱氣騰騰,每人伸手拿起一隻就咬。一陣風吹來一股韭菜味,香極了。我不由得停步,看他們狼吞虎嚥,大約每個人吃兩隻就夠了,因為每只長約半尺。隨後又擔來兩桶開水,大家就用瓢舀著吃。像是《水滸傳》中人一般的豪爽。我從未見過像這一群山東大漢之吃得那樣淋漓盡致。我們這裡街頭巷尾也常有人制賣韭菜盒子,大概都是山東老鄉。所謂韭菜盒子是油煎的,其實標準的韭菜盒子是幹烙的,不是油煎的。不過油煎得黃澄澄的也很好,可是通常餡子不大考究,粗老的韭菜葉子沒有細切,而且羼進粉絲或是豆腐渣什麼的,味精少不了。中山北路有一家北方館(天興樓?)賣過一陣子比較像樣的韭菜盒子,幹烙無油,可是不久就關張了。天廚點心部的韭菜盒子是出名的,小小圓圓,而不是一般半月形,做法精細,材料考究,也是油煎的。以上所說都是以韭菜餡為標榜的點心。現在要說東興樓的韭潔白無疵,沒有斑點油皮。而且捏法特佳,細褶勻稱,捏合處沒有面疙瘩。最特別的是蒸出來盛在盤裡一個個地高壯聳立,不像一般軟趴趴的扁包子,底直徑一寸許,高幾達二寸,像是竹簍似的骨立挺拔,看上去就很美觀。我疑心是利用筒狀的模型。餡子也講究,粗大的韭菜葉一概舍去,專選細嫩部分細切,然後拌上切碎了的生板油丁。蒸好之後,脂油半融半呈晶瑩的碎渣,使得韭菜變得軟潤合度。像這樣的韭菜簍端上一盤,你縱然已有飽意,也不能不取食一兩個。普通人家都會做韭菜簍,只是韭菜餡包子而已,真正夠標準的韭菜簍,要讓東興樓獨步。 蟹蟹是美味,人人喜愛,無間南北,不分雅俗。當然我說的是河蟹,不是海蟹。在臺灣有人專程飛到香港去吃大閘蟹。好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從香港帶回了一簍螃蟹,分飧了我兩隻,得膏饞吻。蟹不一定要大閘的,秋高氣爽的時節,大陸上任何湖沼溪流,岸邊稻米高粱一熟,率多盛產螃蟹。在北平,在上海,小販擔著螃蟹滿街吆喚。七尖八團,七月裡吃尖臍(雄),八月裡吃團臍(雌),那是蟹正肥的季節。記得小時候在北平,每逢到了這個季節,家裡總要大吃幾頓,每人兩隻,一尖一團。照例通知長發送五斤花雕全家共飲。有蟹無酒,那是大殺風景的事。《晉書‧畢卓傳》:“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我們雖然沒有那樣狂,也很覺得樂陶陶了。母親對我們說,她小時候在杭州家裡吃螃蟹,要慢條斯理,細吹細打,一點蟹肉都不能糟踏,食畢要把破碎的蟹殼放在戥子上稱一下,看誰的一份兒分量輕,表示吃的最乾淨,有獎。我心粗氣浮,沒有耐心,蟹的小腿部分總是棄而不食,肚子部分囫圇略咬而已。每次食畢,母親教我們到後院採擇艾尖一大把,搓碎了洗手,去腥氣。在餐館裡吃“炒蟹肉”,南人稱“炒蟹粉”,有肉有黃,免得自己剝殼,吃起來痛快,味道就差多了。西餐館把蟹肉剝出來,填在蟹匡裡(蟹匡即蟹殼)烤,那種吃法別致,也索然寡味。食蟹而不失原味的唯一方法是放在籠屜裡整只地蒸。在北平吃螃蟹唯一好去處是前門外肉市正陽樓。他家的蟹特大而肥,從天津運到北平的大批蟹,到車站開包,正陽樓先下手挑揀其中最肥大者,比普通擺在市場或攤販手中者可以大一倍有餘。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獲得這一特權的。蟹到店中蓄在大缸裡,澆雞蛋白催肥,一兩天后才應客。我曾掀開缸蓋看過,滿缸的蛋白泡沫。食客每人一份小木槌小木墊,黃楊木制,旋床子定制的,小巧合用,敲敲打打,可免牙咬手剝之勞。我們因是老主顧,夥計送了我們好幾副這樣的工具。這個夥計還有一樣絕活,能吃活蟹,請他表演他也不辭。他取來一隻活蟹,兩指掐住蟹匡,任它雙螯亂舞,輕輕把臍掰開,哢嚓一聲把蟹殼揭開,然後扯碎入口大嚼,看得人無不心驚。據他說味極美,想來也和吃熗活蝦差不多。在正陽樓吃蟹,每客一尖一團足矣,然後補上一碟烤羊肉夾燒餅而食之。酒足飯飽,別忘了要一碗?大甲。這碗湯妙趣無窮,高湯一碗煮沸,投下剝好了的蟹螯七八塊,立即起鍋注在碗內,撒上芫荽末、胡椒粉和切碎了的回鍋老油條。除了這一味?大甲,沒有任何別的羹湯可以壓得住這一餐飯的陣腳。以蒸蟹始,以大甲湯終,前後照應,猶如一篇起承轉合的文章。蟹黃蟹肉有許多種吃法,燒白菜、燒魚唇、燒魚翅,都可以。蟹黃燒賣則尤其可口,唯必須真有蟹黃蟹肉放在餡內才好,不是一兩小塊蟹黃擺在外面做樣子的。蟹肉可以醃後收藏起來,是為蟹胥,俗名為蟹醬,這是我們古已有之的美味。《周禮‧天官‧庖人》注:“青州之蟹胥。 ”青州在山東,我在山東住過,卻不曾吃過青州蟹胥,但是我有一位家在蕪湖的同學,他從家鄉帶來了一小壇蟹醬進一兩匙蟹醬,豈止是“清水變雞湯”?海蟹雖然味較差,但是個子粗大,肉多。從前我乘船路過煙臺威海衛,停泊之後,舢板雲集,大半是販賣螃蟹和大蝦的。都是煮熟了的,價錢便宜,買來就可以吃。雖然微有腥氣,聊勝於無。生平吃海蟹最滿意的一次,是在美國華盛頓州的安哲利斯港的碼頭附近。買得兩隻巨蟹,碩大無朋,從冰櫃裡取出,卻十分新鮮,也是煮熟了的。一家人乘等候輪渡之便,在車上分而食之,味甚鮮美,和河蟹相比各有千秋,這一次的享受至今難忘。陸放翁詩:“磊落金盤薦糖蟹。”我不知道螃蟹可以加糖,可是古人記載確有其事。《清異錄》“煬帝幸江州,吳中貢糖蟹。《夢溪筆談》:“大業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又何胤嗜糖蟹。大抵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蟹加糖蜜,蓋便於北俗也。”如今北人沒有這種風俗,至少我沒有吃過甜螃蟹,我只吃過南人的醉蟹,真鹹!螃蟹蘸薑醋,是標準的吃法,常有人在醋裡加糖,變成酸甜的味道,怪! 炸丸子我想人沒有不愛吃炸丸子的,尤其是小孩。我小時候,根本不懂什麼五臭八珍,只知道小炸丸子最為可口。肉剁得松松細細的,炸得外焦裡嫩,入口即酥,不需大嚼,既不吐核,又不摘刺,蘸花椒鹽吃,一口一個,實在是無上美味。可惜一盤丸子只有二十來個,桌上人多,分下來差不多每人兩三個,剛把饞蟲誘上喉頭,就難以為繼了。我們住家的胡同口有一個同和館,近在咫尺。有時家裡來客留飯,就在同和館叫幾個菜作為補充,其中必有炸丸子,亦所以饜我們幾個孩子所望。有一天,我們兩三個孩子偎在母親身邊閒話,我的小弟弟不知怎麼的心血來潮,沒頭沒腦地冒出這樣的一句話:“媽,小炸丸子要多少錢一碟? ”我們聽了哄然大笑,母親卻覺得一陣心酸,立即派傭人到同和館買來一碟小炸丸子。我們兩三個孩子伸手抓食,每人分到十個左右,心滿意足。事隔七十多年,不能忘記那一回吃小炸丸子的滋味。炸丸子上面加一個“小”字,不是沒有緣由的。丸子大了,炸起來就不容易炸透。如果炸透,外面一層又怕炸過火,所以要小。有些館子稱之為櫻桃丸子,也不過是形容其小。其實這是誇張,事實上總比櫻桃大些。要炸得外焦裡嫩有一個訣竅:先用溫油炸到八分熟,撈起丸子,使稍冷卻,在快要食用的時候投入沸油中再炸一遍。這樣便可使外面焦而裡面不至變老。在鍋裡勾一些鹵,加上一些木耳,然後把炸好的丸子放進去滾一下就起鍋,是為溜丸子。如果用高湯煮丸子,而不用油煎,煮得白白嫩嫩的,加上一些黃瓜片或是小白菜心,也很可口,是為汆丸子。若是趕上毛豆剛上市,把毛豆剁碎羼在肉裡,也很別致,是為毛豆丸子。湖北館子的蓑衣丸子也很特別。是用丸子裹上糯米,上屜蒸。蒸出來一個個地粘著挺然翹然的米粒,好像是披了一件蓑衣,故名。這道菜要做得好,並不難,糯米先泡軟再蒸,就不會生硬。我不知道為什麼湖北人特喜糯米,豆皮要包糯米,燒賣也要包糯米,丸子也要裹上糯米。我私人以為除了粽子湯糰和八寶飯之外,糯米派不上什麼用場。北平醬肘子鋪(即便宜坊)賣一種炸丸子,扁扁的,外表疙瘩嚕蘇,裡面全是一些筋頭麻腦的剔骨肉,價錢便宜,可是風味特殊,當做火鍋的鍋料用最為合適。我小時候上學,如果手頭富餘,買個炸丸子夾在燒餅裡,愜意極了,如今回想起來還回味無窮。最後還不能不提到“烏丸子”。一半炸豬肉丸子,一半炸雞胸肉丸子,盛在一個盤子裡,半黑半白,很是別致。要有一小碗鹵汁,蘸鹵汁吃才有風味。為什麼叫烏丸子,我不知道,大概是什麼一位姓烏的大老爺所發明,故以此名之。從前有那樣的風氣,人以菜名,菜以人名,如潘魚江豆腐之類皆是。 佛跳牆佛跳牆的名字好怪。何物美味竟能引得我佛失去定力跳過牆去品嘗?我來臺灣以前沒聽說過這一道菜。《讀者文摘》(一九八三年七月中文版)引載可叵的一篇短文《佛跳牆》。據她說佛跳牆“那東西說來真罪過,全是葷的,又是豬腳,又是雞,又是海參、蹄筋,燉成一大鍋。……這全是廣告噱頭,說什麼這道菜太香了,香得連佛都跳牆去偷吃了”。我相信她的話,是廣告噱頭,不過佛都跳牆,我也一直躍躍欲試。同一年三月七日《青年戰士報》有一位鄭木金先生寫過一篇《油畫家楊三郎祖傳菜名聞藝壇——佛跳牆耐人尋味》,他大致說:“傳自福州的佛跳牆……在臺北各大餐館正宗的佛跳牆已經品嘗不到了。……偶爾在一般鄉間家庭的喜筵裡也會出現此道臺灣名菜,大都以芋頭、魚皮、排骨、金針菇為主要配料。其實源自福州的佛跳牆,配料極其珍貴。楊太太許玉燕花了十多天閒工夫才能做成的這道菜,有海參、豬蹄筋、紅棗、魚刺、魚皮、栗子、香菇、蹄?筋肉等十種昂貴的配料,先熬雞汁,再將去肉的雞汁和這些配料予以慢工出細活的好幾遍煮法,前後計時將近兩星期……已不再是原有的各種不同味道,而合為一味。香醇甘美,齒頰留香,兩三天仍回味無窮。”這樣說來,佛跳牆好像就是一鍋煮得稀巴爛的高級大雜燴了。北方流行的一個笑話,出家人吃齋茹素,也有老和尚忍耐不住想吃葷腥,暗中買了豬肉運入僧房,乘大眾入睡之後,納肉於釜中,取佛堂燃剩之蠟燭頭一罐,輪番點燃蠟燭頭於釜下燒之。恐香氣外溢,乃密封其釜使不透氣。一罐蠟燭頭於一夜之間燒光,細火久燜,而釜中之肉爛矣,而且酥軟味腴,迥異尋常。戲名之為“蠟頭燉肉”。這當然是笑話,但是有理。我沒有方外的朋友,也沒吃過蠟頭燉肉,但是我吃過“?子肉”。?子就是瓦缽,有蓋,平常做儲食物之用。?子不需大,高半尺以內最宜。肉及佐料放在?子裡,不需加水,密封壇蓋,文火慢燉,稍加冰糖。抗戰時在四川,冬日取暖多用炭盆,亦頗適於做?子肉,以壇置定盆中,燒一大盆缸炭,坐?子於炭火中而以灰覆炭,使徐徐燃燒,約十小時後炭未盡成燼而?子肉熟矣。純用精肉,佐以蔥薑,取其不失本味,如加配料以筍為最宜,因為筍不奪味。 “東坡肉”無人不知。究竟怎樣才算是正宗的東坡肉,則去古已遠,很難說了。幸而東坡有一篇《豬肉頌》:淨洗鐺,少著水,柴頭灶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錢如泥土,貴者不肯食,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而已。也是循蠟頭燉肉的原理,就是?子肉的別名吧?一日,唐嗣堯先生招余夫婦飲于其巷口一餐館,雲其佛跳牆值得一嘗,乃欣然往。小罐上桌,揭開罐蓋熱氣騰騰,肉香觸鼻。是否及得楊三郎先生家的佳制固不敢說,但亦頗使老饕滿意。可惜該餐館不久歇業了。我不是遠庖廚的君子,但是最怕做紅燒肉,因為我性急而健忘,十次燒肉九次燒焦,不但糟踏了肉,而且燒毀了鍋,滿屋濃煙,鄰人以為是失了火。近有所謂電慢鍋者,利用微弱電力,可以長時間地煨煮肉類,對於老而且懶又沒有記性的人頗為有用,曾試烹近似佛跳牆一類的紅燒肉,很成功。 栗子栗子以良鄉的為最有名。良鄉縣在河北,北平的西南方,平漢鐵路線上。其地盛產栗子。然栗樹北方到處皆有,固不必限於良鄉。我家住在北平大取燈胡同的時候,小園中亦有栗樹一株,初僅丈許,不數年高二丈以上,結實累累。果苞若刺蝟,若老雞頭,遍體芒刺,內含栗兩三顆。熟時不摘取則自行墜落,苞破而栗出。搗碎果苞取栗,有漿液外流,可做染料。後來我在嶗山上看見過巨大的栗子樹,高三丈以上,果苞落下狼藉滿地,無人理會。在北平,每年秋節過後,大街上幾乎每一家乾果子鋪門外都支起一個大鐵鍋,翹起短短的一截煙囪,一個小利巴揮動大鐵鏟,翻炒栗子。不是幹炒,是用沙炒,加上糖使沙結成大大小小的粒,所以叫作糖炒栗子。煙煤的黑煙擴散,嘩啦嘩啦的翻炒聲,間或有栗子的爆炸聲,織成一片好熱鬧的晚秋初冬的景致。孩子們沒有不愛吃栗子的,幾個銅板買一包,草紙包起,用麻莖兒捆上,熱呼呼的,有時簡直是燙手熱,拿回家去一時捨不得吃完,藏在被窩垛裡保溫。煮咸水栗子是另一種吃法。在栗子上切十字形裂口,在鍋裡煮,加鹽。栗子是甜滋滋的,加上鹹,別有風味。煮時不妨加些八角之類的香料。冷食熱食均佳。但是最妙的是以栗子做點心。北平西車站食堂是有名的西餐磨成粉,就好像花生粉一樣,乾鬆松的,上面澆大量奶油。所謂奶油就是打攪過的奶油(whipped cream)。用小勺取食,味妙無窮。奶油要新鮮,打攪要適度,打得不夠稠自然不好吃,打過了頭卻又稀釋了。東安市場的中興茶樓和國強西點鋪後來也仿製,工料不夠水準,稍形遜色。北海仿膳之栗子面小窩頭,我吃不出栗子味。杭州西湖煙霞嶺下翁家山的桂花是出名的,尤其是滿家弄,不但桂花特別地香,而且桂花盛時栗子正熟,桂花煮栗子成了路邊小店的無上佳品。徐志摩告訴我,每值秋後必去訪桂,吃一碗煮栗子,認為是一大享受。有一年他去了,桂花被雨摧殘淨盡,他感而寫了一首詩《這年頭活著不易》。十幾年前在西雅圖海濱市場閒逛,出得門來忽聞異香,遙見一意大利人推小車賣炒栗。論個賣——五角錢一個,我們一家六口就買了六顆,坐在車裡分而嘗之。如今我們這裡到冬天也有小販賣“良鄉栗子”了。韓國進口的栗子大而無當,並且糊皮,不足取。 海參海參不是什麼珍貴的東西。但是乾貨,在烹調之前先要發開。發海參的手續不簡單,需要很久時間(現在市場有現成發好的海參,從前是沒有的)。所以從前家常菜裡沒有海參,只有餐館裡或整桌席裡才得一見。我一向以為外國人不吃海參,他們看見我們吃海參,一定以為我們不是嘴饞便是野蠻,連“海胡瓜”都不肯饒。其實是我孤陋寡聞,外國人也吃海參,不過他們的吃法不同。他們吃我們要刮去丟掉的海參裡面那一層皮,而我們吃他們所要丟掉的海參外面帶刺的厚厚一層膠質。活的海參,我在外國的水族館裡看見過,各種顏色具備,黑的、白的、棕色的、斑駁的。咕咕嚷嚷的,不好看。鮮的海參,沒吃過。因為海參並不太珍貴,所以在飯莊子裡所謂“海參席”乃是次等的席,次於所謂“魚翅席”“燕翅席”。在海參席裡,海參是主萊,通常是一大盤“趴爛海參”,名為趴爛,其實還是卜楞蔔楞的居多。如果用象牙筷子去夾,還不大容易平平安安地夾到嘴邊。餐館裡有一道名菜“紅燒大烏”。大烏就是黑色的體積特大的海參,又名烏參。上好的海參要有刺,又叫刺參。紅燒大烏以淮揚館子做得最好。五十年前北平西長安街一連有十幾家大大小小的淮揚館子,取名都叫什麼什麼“春”。我記不得是哪一家春了,所做溫又顯得美觀。紅燒大烏上桌,茶房揭開碗蓋,赫然兩條大烏並排橫臥,把蓋碗擠得滿滿的。吃這道菜不能用筷子,要使羹匙,像吃八寶飯似的一匙匙地挑取。碗裡沒有配料,頂多有三五條冬筍。但是汁漿很濃,裡面還羼有蝦子。這道菜的妙處,不在味道,而是在對我們觸覺的滿足。我們品嘗美味有時兼顧到觸覺。紅燒大烏吃在嘴裡,有滑軟細膩的感覺,不是一味的爛,而是爛中保有一點酥脆的味道。這道菜如果火候不到,則海參的韌性未除,隱隱然和齒牙作對,便非上乘了。我離開北平之後還沒嘗過標準的海參。涼拌海參又是一種吃法。夏天誰都想吃一點涼的東西,酒席上四個冷葷,其實不冷,不如把四個冷葷免除,換上一大盤涼拌海參。海參煮過冷卻,切成長長的細絲,越細越好,放進冰箱待用。另外預備一小碗三合油(即醬油醋麻油),一小碗稀釋了的芝麻醬,一小碟蒜泥,上桌時把這配料澆在海參上拌勻,既涼且香,非常爽口,比裡脊絲拉皮好吃多了。這是我先君傳授給我的吃法,屢試皆受歡迎。 滿漢細點北平的點心店叫作餑餑鋪,都有一座細木雕花的門臉兒,吊著幾個木牌,上面寫著“滿漢細點”什麼的。可是餑餑都藏在裡面幾個大盒子、大櫃子裡,並不展示在外,而且也沒有什麼貨品價格表之類的東西。進得鋪內,只覺得乾乾淨淨,空空洞洞,香味撲鼻。滿漢細點,究竟何者為滿何者為漢,現已分辨不清。至少從名稱看來,“薩其瑪”該是滿洲點心。我請教過滿洲旗人,據告薩其瑪是滿文的蜜甜之意,我想大概是的。這東西是油炸黃米麵條,像蜜供似的,但是很細很細,加上蜜拌勻,壓成扁扁的一大塊,上面撒上白糖和染紅了的白糖,再加上一層青絲紅絲,然後切成方形的塊塊。很甜,很軟和,但是很好吃。如今全國各處無不制售薩其瑪,塊頭太大太厚,麵條太粗太硬,蜜太少,名存實亡,全不對勁。蜂糕也是北平特產,有黃白兩種,味道是一樣的。是用糯米粉調製蒸成,呈微細蜂窩狀,故名。質極鬆軟,微黏,與甜麵包大異其趣。內羼少許核桃仁,外裹以薄薄的豆腐皮以防粘著蒸器。蒸熱再吃尤妙,最宜病後。花糕、月餅是秋季應時食品。北方的翻毛月餅,並不優於江南的月餅,更與廣式月餅不能相比,不過其中有一種山楂餡的翻毛月餅,薄薄的小小的,我認為風味很好,別處所無。大抵月餅不宜過甜,不宜太厚,山楂餡帶有酸味,故不覺其膩。至於花糕,則是北的是兩片棗泥餡的餅,用模子製成,兩片之間夾列胡桃、紅棗、松子、縮葡之類的乾果,上面蓋一個紅戳子,貼幾片芫荽葉。清李靜山《都門匯纂》裡有這樣一首竹枝詞:中秋才過近重陽,又見花糕各處忙。面夾雙層多棗栗,當筵題句傲劉郎。一般餑餑鋪服務周到。我家小園有一架紫藤,花開累累,滿樹滿枝,乃摘少許,洗淨,送交餑餑鋪代制藤羅餅,鮮花新制,味自不同。又紅玫瑰初放(西洋品種肥大而豔,但少香氣),亦常摘取花瓣,送交鋪中代制玫瑰餅,氣味濃馥,不比尋常。說良心話,北平餅鉺除上述幾種之外很少有令人懷念的。有人豔稱北平的“大八件”“小八件”,實在令人難以苟同。所謂“大八件”無非是油糕、蓼花、大自來紅、自來白等,“小八件”不外是雞油餅、卷酥、綠豆糕、槽糕之類。自來紅、自來白乃是中秋上供的月餅,餡子裡面有些冰糖,硬邦邦的,大概只宜於給兔爺兒吃。蓼花甜死人!綠豆糕噎死人!“大八件”“小八件”如果裝在盒子裡,那盒子也嚇人,活像一口小棺材,而木板尚未刨光。若是打個蒲包,就好看得多。有所謂“缸撈”者,有人寫作“乾酪”,我不知究竟怎樣寫法。是圓餅子,中央微凸,邊微薄,無餡,上面常撒上幾許桂花,故稱桂花缸撈。探視產後婦人,常攜此為饋贈。此物鬆軟合度,味道頗佳,我一向喜歡吃。後來聽一位在外鄉開點心鋪的親戚說,此物乃是聚集簸籮裡的各種餑餑碎渣加水揉和再行烘制而成。然物美價廉不失為一種好的食品。“薄脆”也不錯,又薄又脆,都算是平民食物。 “茯苓餅”其實沒有什麼好吃,沾光“茯苓”二字。《淮南子》: “千年之松,下有茯苓。 ”茯苓是一種地下菌,生在山林中松根之下。李時珍說:“蓋松之神,靈之氣,伏結而成。 ”無端給它加上神靈色彩,於是乃入藥,大概吃了許有什麼神奇之效。北平前門大街正明齋所制茯苓餅最負盛名,從前北人南游常攜此物饋贈親友。直到如今,有人從北平出來還帶一盒茯苓餅給我,早已脆碎堅硬不堪入口。即使是新鮮的,也不過是飛薄的兩片米粉糊烘成的餅,夾以黑糊糊的一些碎糖黑渣而已。滿洲餑餑還有一品叫作“桌張”,俗稱餑餑桌子,是喪事人家常用的祭禮。半生不熟的白麵餅子,稍加一些糖,堆積起來一層層的有好幾尺高,放以靈前供臺上的兩旁。凡是本家姑奶奶之類的親屬沒有不送餑餑桌子的。可壯觀瞻,不堪食用。喪事過後,棄之可惜,照例分送親友以及傭人小孩。我小時候遇見幾次喪事,分到過十個八個這樣的餑餑。童子無知,稱之為“死人餑餑”,放在火爐口邊烤熟,啃起來也還不錯,比根本沒有東西吃好一些。清人得碩亭竹枝詞《草珠一串》有一首詠其事:滿洲糕點樣原繁,踵事增華不可言。唯有桌張遺舊制,幾同告朔餼羊存。 菜包華北的大白菜堪稱一絕。山東的黃芽白行銷江南一帶。我有一家親戚住在哈爾濱,其地苦寒,蔬菜不易得,每逢陰年請人帶去大白菜數頭,他們如獲至寶。在北平,白菜一年四季無缺,到了冬初便有推小車子的小販,一車車的白菜沿街叫賣。普通人家都是整車地買,留置過冬。夏天是白菜最好的季節,吃法太多了,炒白菜絲、栗子燒白菜、熬白菜、醃白菜,怎樣吃都好。但是我最欣賞的是菜包。取一頭大白菜,擇其比較肥大者,一層層地剝,剝到最後只剩一個菜心。每片葉子上一半作圓弧形,下一半白菜幫子酌量切去。弧形菜葉洗淨待用。準備幾樣東西:一、蒜泥拌醬一小碗。二、炒麻豆腐一盤。麻豆腐是綠豆制粉絲剩下來的渣子,發酵後微酸,作灰綠色。此物他處不易得。用羊尾巴油炒最好,加上一把青豆更好。炒出來像是一攤爛稀泥。三、切小肚兒丁一盤。小肚兒是豬尿泡灌豬血芡粉煮成的,作粉紅色,加大量的松子在內,有異香。醬肘子鋪有賣。四、炒豆腐松。炒豆腐成碎屑,像炒鴿松那個樣子,起鍋時大量加蔥花。五、炒白菜絲,要炒爛。取熱飯一碗,要小碗飯大碗盛。把蒜醬抹在菜葉的裡面,要抹勻。把麻豆腐、小肚兒、豆腐松、炒白菜絲一起拌在飯碗裡,要拌勻。把這碗飯取出一部分放在菜葉裡,包起來,雙手捧著咬而食之。吃完一個再吃一個,吃得滿臉滿手都是菜汁飯粒,痛快淋漓。據一位旗人說這是滿洲人吃法,緣昔行軍時沿途取出菜葉包剩菜而食之。但此法一行,無不稱妙。我曾數度以此待客,皆讚不絕口。 糟蒸鴨肝糟就是酒滓,凡是釀酒的地方都有酒糟。《楚辭‧漁父》:“何不鋪其糟而歠其釃? ”可見自古以來酒糟就是可以吃的。我們在攤子上吃的醪糟蛋(醪音撈),醪糟乃是我們人人都會做的甜酒釀,還不是我們所謂的糟。說也奇怪,我們臺灣盛產名酒,想買一點糟還不太容易。只有到山東館子吃糟溜魚片才得一嘗糟味,但是有時候那糟還不是真的,不過是甜酒釀而已。糟的吃法很多。糟溜魚片固然好,糟鴨片也是絕妙的一色冷葷,在此地還不曾見過,主要原因是鴨不夠肥嫩。北平東興樓或致美齋的糟鴨片,切成大薄片,有肥有瘦有皮有肉,是下酒的好菜。《儒林外史》第十四回,馬二先生看見酒店櫃檯上盛著糟鴨,“沒有錢買了吃,喉嚨裡咽唾沫”。所說的糟鴨是剛出鍋的滾熱的,和我所說的冷盤糟鴨片風味不同。下酒還是冷的好。稻香村的糟鴨蛋也很可口,都是靠了那一股糟味。福州館子所做紅糟的菜是有名的。所謂紅糟乃是紅麴,另是一種東西。是粳米做成飯,拌以曲母,令其發熱,冷卻後灑水再令其發熱,往復幾次即成紅麴。紅糟肉、紅糟魚,均是美味,但沒有酒糟香。現在所要談到的糟蒸鴨肝是山東館子的拿手,而以北平東興樓的為最出色。東興樓的菜出名地分量少,小盤小碗,但是精,不能供大嚼,只好細品嘗。所做糟蒸鴨肝,精選上好鴨肝,大小合度,剔洗乾淨,以酒糟蒸熟。妙在湯不渾濁而味濃,而且色澤鮮美。有一回梁寒操先生招飲于悅賓樓,據告這是於右老喜歡前去小酌的地方,而且以糟蒸鴨肝為其雋品之一。嘗試之下,果然名不虛傳,唯稍嫌粗,肝太大則質地容易沙硬。在這地方能吃到這樣的菜,難得可貴。 魚翅魚翅通常是酒席上的一道大菜。有紅燒的,有清湯的,有墊底的(三絲底),有不墊底的。平平淺淺的一大盤,每人輪上一筷子也就差不多可以見底了。我有一位朋友,篤信海味必須加醋,一見魚翅就連呼侍者要醋,侍者滿臉的不高興,等到一小碟醋送到桌上,盤裡的魚翅早已不見蹤影。我又有一位朋友,他就比較聰明,隨身自帶一小瓶醋,隨時掏出應用。魚翅就是鯊魚(鮫)的鰭,脊鰭、胸鰭、腹鰭、尾鰭。外國人是棄置不用的廢物,看見我們視為席上之珍,傳為笑談。尾鰭比較壯大,最為貴重,內行人稱之為“黃魚尾”。抗戰期間四川北碚厚德福飯莊分號,中了敵機投下的一彈,店毀人亡,調貨狼藉飛散,事後撿回物資包括黃魚尾二三十塊,暫時堆放捨下。我欲取食,無從下手。因為魚翅是乾貨,發起來好費手腳。即使發得好,烹製亦非易易,火候不足則不爛,火候足可又怕縮成一團。其中有訣竅,非外行所能為。後來我托人把那二三十塊魚翅帶到昆明分號去了。北平飯莊餐館魚翅席上的魚翅,通常只是虛應故事,選材不佳,火候不到,一根根的脆骨劍拔弩張的樣子,吃到嘴裡紮紮呼呼。下焉者翅須細小,芡粉太多,外加陪襯的材料喧賓奪主,黏糊糊的像一盤糨糊。遠不如到致美齋點一個“砂鍋魚翅”,所用材料雖非上選的排翅,但也不是次貨,妙在翅根特厚,味道介乎魚翅魚唇之間,下酒下飯,兩極其美。東安市場裡的潤明樓也有“砂鍋翅根”,鍋較小,翅根較碎,近于平民食物,比我們臺灣食攤上的魚翅羹略勝一籌而已。唐魯孫先生是飲食名家,在《吃在北平》一文裡說:“北方館子可以說不會做魚翅,所以也就沒有什麼人愛吃魚翅,但是南方人可就不同了,講究吃的主兒十有八九愛吃翅子,禎元館為迎合顧客心理,請了一位南方大師傅,擅長燒魚翅。不久,禎元館的‘紅燒翅根’,物美價廉,就大行其道,每天只做五十碗,賣完為止。”確是實情。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