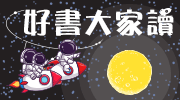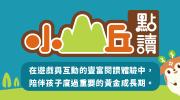商品簡介
致敬 七等生
超越時代的前行者
他的創作歷程示現了幻譎奇偉的生命之歌
「當我已為你們盡力,也祈望你們放手不再干預我。我們條件談妥了,你們回去,也告訴所有的人,要他們不再干預私人的事。」--〈跳遠選手退休了〉
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一年發表的〈結婚〉、〈真實〉、〈跳遠選手退休了〉、〈僵局〉、〈巨蟹集〉、〈絲瓜布〉等三十三篇小說,其中〈結婚〉曾於一九九五年拍成電影,一九九八年改編為同名電視劇。
七等生的短篇小說多數帶著黯淡憂鬱的色彩,裸裎出現實社會的虛偽和墮落。他認為:「現代文學的產生是個人人格的建立,這也是真
作者簡介
本名劉武雄,1939-2020。生於苗栗通霄,台北師範藝術科畢業。自1962年首次在《聯合報》發表短篇小說〈失業、撲克、炸魷魚〉起,共發表124篇小說、137篇散文(含雜記、序文),及56首新詩。1989年重拾畫筆,將創作重心轉向繪畫,於1991、92年舉辦過兩次個展。
1966、67年連獲第一和第二屆台灣文學獎。1976年獲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1983年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邀約訪美。1985年獲中國時報文學推薦獎和吳三連文藝獎。小說作品《沙河悲歌》、〈結婚〉亦曾改拍同名電影、電視劇
序
【出版前言】
削廋卻獨特的靈魂
生命裡不免會有令人感到格格不入的時候,彷彿趔趄著從一眾和自己不同方向的人群中穿行而過。然而如果那與己相逆的竟是一個時代、甚至是一整個世界,這時又該如何自處?一生以叛逆而前衛的文學藝術屹立於世間浪潮的七等生,就是這樣一位與時代潮流相悖的逆行者。他的創作曾為他所身處的世代帶來巨大的震撼、驚詫、迷惑與躁動,而那也正是世界帶給他孤獨、隔絕和疏離的劇烈迴響。如今這抹削廋卻獨特的靈魂已離我們遠去,但他的小說仍兀自鳴放著它獨有的聲部與旋律。
該怎麼具體描繪七等生的與眾不同?或許可以從其投身創作的時空窺知一二。在他首度發表作品的一九六二年,正是總體社會一意呼應來自威權的集體意識,甚且連文藝創作都被指導必須帶有「戰鬥意味」的滯悶年代。而七等生初登文壇即以刻意違拗的語法,和一個個讓人眩惑、迷離的故事,展現出強烈的個人色彩與自我內在精神。成為當時一片同調的呼聲中,唯一與眾聲迥異的孤鳴者。
也或許因為這樣,讓七等生的作品一直背負著兩極化的評價;好之者稱其拆穿了當時社會表象的虛偽和黑暗面,凸顯出人們在現代文明中的生存困境。惡之者則謂其作品充斥著虛無頹廢的個人主義,乃至於「墮落」、「悖德」云云。然而無論是他故事裡那些孤獨、離群的邊緣人物,甚或小說語言上對傳統中文書寫的乖違與變造,其實都是意欲脫出既有的社會規範和框架,並且有意識地主動選擇對世界疏離。在那個時代發出這樣的鳴聲,毋寧是一種挑釁,也無怪乎有的人視之為某種異端。另一方面,七等生和他的小說所具備的特殊音色,也不斷在更多後來的讀者之間傳遞、蔓延;那些當時不被接受和瞭解的,後來都成為他超越時代的證明。
儘管小說家此刻已然遠行,但是透過他的文字,我們或許終於能夠再更接近他一點。印刻文學極其有幸承往者意志,進行「七等生全集」的編輯工作,為七等生的小說、詩、散文等畢生創作做最完整的彙集與整理;作品按其寫作年代加以排列,以凸顯其思維與創作軌跡。同時輯錄作者生平重要事件年表,期望藉由作品與生平的並置,讓未來的讀者能瞭解台灣曾經有像七等生如此前衛的小說家,並藉此銘記台灣文學史上最秀異特出的一道風景。
目次
(代序)論文學
結婚
真實
跳遠選手退休了
天使
誇耀
碉堡
父親之死
浪子
僵局
虔誠之日
我的戀人
俘虜
爭執
呆板
空心球
木塊
回響
希臘、希臘
分道
訪問
銀幣
海灣
來罷,爸爸給你說個故事
巨蟹集
眼
絲瓜布
流徙
使徒
離開
笑容
墓場
漫遊者
禁足的海岸
書摘/試閱
結婚
楊鎮旗山街和仁愛路口那塊街角有間紅磚砌築的兩層古樓房豎立著,從樓下敞開的門一直深進內壁所堆集排列著的物品看來,便知道是個很大的雜貨總匯。這間雜貨店代表著這個小鎮的歷史:守舊、雜亂和古老。靠近走廊的幾個方形的瓷缸,表面上清晰地寫著它盛裝的物品的黑色方體字:那是各種的米、鹽、白糖和黑糖。粗糙的木桶盛著豆類。木框盒子充塞著骯髒的各種乾蔬菜,另一邊是大小不同的繩索圈和麵粉袋。一箱箱的洗衣肥皂,香肥皂和毛巾牙刷等類的物品排列在玻璃櫃內。兩面牆壁的木架框上,排列著酒類、醬油及醋,紙標鮮明,整齊有如列隊的士兵。木架的下一層,靠近地板,要彎下身體才能拿到的是一些矮胖的瓶子,那是農藥酒精和殺蟲劑之類的東西。角落還有桶裝的米酒。那張橫在中央的巨木櫃長一丈高四尺,一端的上面放置的玻璃箱是當時公賣局出品的各種香煙。五年前,巨木櫃的另一端通常站著一位短髮的活潑少女,她的名字叫曾美霞。她勤奮地走來走去,取貨品給買客,把錢折摺後塞進櫃面的小方窄洞,需要找回零錢時,她便翻開一截櫃板,在腰腹折彎,把頭探進幽黑的櫃裡摸索銅幣。每天早晨到中午這一段時間,生意很好,她來回不知疲倦地為客人服務。當然,這麼龐雜的店鋪一定還有其他的家人;那便是那位壞了一隻眼睛的父親,以及家族中閒空的人都會在店裡照顧生意。買客對她的印象很好,她總是露出一種喜歡聽人吩咐的笑容,這和她天生圓形的面龐顯得很適切。她剛過十七歲,初級中學剛畢業不久,長得豐滿健康,附著在她身上面孔上的平庸卻比美麗更得人緣和親切感。
同一條街,與這間雜貨店僅隔著一條讓行人走路的小巷,豎立著鎮上的標誌──一座新建的新樣式的農會大樓,白色的細石牆壁閃耀著陽光,國旗飄揚在屋頂之上,襯著美麗的青空,象徵著鎮轄管區農業的興盛。雜貨店的左邊,屬於仁愛路的第一幢房子,則是一間木板釘成的日本式的優雅兩層樓房子,黑色厚重的瓦,板牆漆成墨綠色,它是一所十分高尚的醫院。於是,以雜貨店為中心,座落在兩條主要街道的這三座毗連且互相異趣的房子,正是這個鎮上的代表和存在的光榮。
隨著曾美霞的長成不可避免地發生在她身上的事的當時,雜貨店裡居住著的正是一個典型的大家庭,維持著傳統的生活習慣,卻不堪新的思想的侵襲而顯露著日漸的崩潰。由於老曾的失聰,三個兄弟間都逐漸顯露著敵意,尤其是老大、老二的女人們間的裂隙十分顯明。是老曾在日據時代開創了這間雜貨店的,那時三個年輕兄弟還未娶妻,表現得十分融洽合作;得興和得財在店裡幫忙他們的父親,他們的小弟得智學業很好,被送到新竹大城市去讀書,現在他也在新竹成家,時常回到楊鎮來。他們的母親做全部的家事,一切的主意都得聽命於老曾;他能幹,和藹且帶點商人的詼諧的性格,和鄰居鎮民相處得很和諧。楊鎮那時初長成,雜貨店是鎮民一切生活必須品的供應所。
老曾的老伴,隨著早年老曾初開雜貨店的艱苦和操勞,以及負責管束三個男孩,使她變成一個愛好囉囌多嘴的女人。她膽怯,小心謹慎和過份的節儉,於是以她狹窄的心胸管教孩子時,那種氣氛就是一味的嘮叨,缺少理智、技巧和幽默;她的觀念就是屬於對的一切。不過,她本性慈藹,那樣的心胸正好也容納不了罪惡和暴力。當晚年,老曾因血壓高成了一個呆癡的無用老人時,她親見一個龐雜的家庭的日漸多事和紛擾,使她煩亂得成了一個苦惱,患著偏頭痛的歇斯底里亞的神經質老婦人。她的指責的語聲對於家庭中的女人和小孩像是一種日常聽慣的市街的噪音。她的兒子們也變質了(在她看起來一定如此),她唯一的慰安是鄰居們還十分願意傾聽她對日常家事的述怨。好在,老曾已經什麼都置之度外了,否則,我們相信這位昔日奮鬪過的老人,一定會牽著他的那位高大乾扁而病黃色的老伴離開這間不再屬於他的雜貨店。
曾美霞被聚集在農會休憩室的年輕男女們稱為羅雲郎的愛人。那一天午後,羅雲郎手中握著曾美霞遞給他的肥皂,他倚靠在雜貨店的櫃台和她談話,告訴她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
「妳猜今天誰回來了。」
「我怎麼會知道呢,到底是誰?」
「黑狗。」羅雲郎說。
「那一位黑狗?」美霞疑問著,腦中掠過許多鎮上被稱為黑狗的年輕男人。
「我的同學,那位搬到台中做生意姓邱的兒子。」
「喔──我記起來了,那個調皮鬼,以前喜歡毆打女學生。」
「是的,他帶了女朋友一起回來。」
「女朋友?」美霞被這個名詞逗得興奮起來。
「她美麗嗎?」她再關心地問著。
「看起來像個太妹。」羅雲郎表示了他的觀點。
「黑狗是個太保,正好相配嘛。」美霞高興地說。
「晚上他會帶她來農會。」
「我一定去看看她長得怎樣。」
「黑狗還帶回來許多新唱片。」
「他一定變得很多了,那是什麼唱片?」
「舞曲,他要教我新的舞步。」
「他幾點鐘會來?」
「大概七點左右。」
「我看見他們從門口經過時,我就去。」
「好的,一定來啊。」
「我一定去。」
他離開櫃台,走出雜貨店,回頭再對美霞微笑一下。他常藉故來雜貨店買東西和她攀談。羅雲郎出生在農村,距離楊鎮五里遠的北勢窩。他的父母以及附近的農夫都是勤儉的客家人,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十分迷信。他的母親罔市尤其保守固執,是位能幹如男人的健壯婦人,所以他的父親相反的異常沉默和羸弱。羅雲郎從高農畢業後依然還如此樸實和溫和,那張英俊的面孔看起來顯得鄉氣愚傻,都是他的母親嚴刻管教束縛的結果。楊鎮的農會雇用他,是學校推薦的,學校認為他樸實可靠。他在校學業成績優良,本來可以再繼續到大城市去考大學的農學系,但他的母親捉住著農會給他的這份有薪水的職位,認為教育太多並沒有大用處,反而學壞了。
有一天晚上,金妹親自走到農會的休憩室窗外,對裡面雜亂而有趣的情形窺視一番;她看見無數的未婚男女集在那一間寬敞的室內談笑和跳舞,一架落地的電唱機囂鬧著音樂,她輕聲叫喚她的女兒,把她從羅雲郎的手中叫回到家裡。
「他是誰?」
「羅雲郎,農會的職工。」
「妳不是告訴我妳不會跳舞嗎?」
「現在大家都在學著呀,我也學學。」
「妳早上在店裡做生意,我准妳晚上出去,但我不許妳學跳舞,不要再被我撞見了。」
「好的,媽媽。」
美霞長得酷似她的母親。這是一個非常嘈雜和猜忌的煩亂家庭,所以金妹對待美霞常常是過份的約束,連帶美霞的一位弟弟,也整日價地被她關在她的臥室裡讀書寫字。
許多日子之後,美霞也感覺到她自己是雲郎的愛人了。有一個早晨,媒婆阿里出現在雜貨店門口,她看見她直往內室,且拉著她母親的手臂走進臥室,她開始逐漸感到羞嚇和顫抖。阿里告訴了金妹兩個年輕人相戀的事,金妹有些困惑和慍怒,她不相信美霞能逃過她的監視,偷偷地與一位農夫的兒子戀愛。金妹否認了這件事;她說:羅家的罔市喜歡她的女兒做媳婦,她感到榮幸,不過她的女兒年紀還很輕,店上也需要她再幫忙一段日子。這是她在阿里詳細的回答有關羅家的一切狀況的詢問之後表示的意思;她婉轉地辭退了阿里,心裡很不快樂那種把她的女兒和粗俗的農人家庭連親的說法。她一聽到羅家是客家人,住在深山裡耕農,她的女兒要住在泥土塊做的屋子裡,她感到一陣陣的嫌惡。阿里也不快樂地走了。金妹馬上呼叫美霞進來臥室,她的心和肢體都在顫抖,她反應著內心懷著受刑的恐懼,她有點兒遲疑不前,她早在阿里走出雜貨店時的面目表情獲得了警告。金妹衝向她,在她的大腿皮上擰了一下,她在她的威脅的逼問下承認了那件事。隨著是一陣幾近瘋狂地宣洩憤怒的毒打,第一次引起全家族的震驚。
這件事情騷擾之後的轉變便是:羅雲郎不敢白天再跑來雜貨店和美霞攀談,甚至買東西都跑到另一條街的小鋪子買。美霞被關在樓上一間幽黑的空臥室幾個晚上,不准外出。當第三天她再在櫃台後面出現時,便接到由農會的另一位職工偷偷遞給她的一封羅雲郎的信箋,信裡面充滿這位初戀的男人的哀傷、忠懇和對愛永恒不渝的信守,這樣的信使她第一次獲得親屬之愛以外的安慰和勇氣。由於那位天性好事的職工的幫忙,美霞和雲郎間的情愫就靠著信箋的往返傳遞著,使這位少女的思慕之情藉著拙笨簡單的文字,也發揮到無比貞潔和崇高的境地。
於是人們開始漸漸發覺櫃台後面的美霞,代表著青春和坦率的笑容逐漸被一種更豐富而奇妙的表情替代,除了那位愛沉逗在報紙的獨眼父親外,來來去去的顧客都有這樣的感覺。有時,美霞會躲在香煙櫃後面,坐在一張圓木凳沉思起來,把手托著腮部。她的父親關於子女的事總聽命於金妹,媒婆阿里來後,他也認為金妹這樣做並沒有什麼錯誤。不料,連信件的來往也被金妹發覺了;首先,金妹發覺那位傳信的職工也步著那位農夫的兒子的後塵來和美霞談戀愛,對於這位矮小好事的農會職工,他是鎮上無人不曉的清道夫啞吧松的兒子,金妹當然更看不起他這種貧賤出生的男人,所以上前來干涉,不料就這樣意外地揭穿了這幕隱情的戲劇。金妹把美霞拖進臥室,要她把所有的信件都繳出來,美霞曾冒著一陣毒打的危險堅持著說:除了那一張,不再有其他的信件了。後來當她反抗她的母親時又說:即使有我也不拿出來,那是我的,不是妳的,或其他人的。全屋子的人都為了這件事再度掀起了一陣爭論,藉著這個機會,女人們之間的事都搬出來互相攻擊指罵,這時,老曾的老伴的規勸沒有人願意聽從,老大得興出差到彰化,老二得財──美霞的父親,不願加入這場爭論,他只無效地叫停他的女人,當沒有獲得絲毫的反應時,便捉起報紙坐在雜貨店門邊,像在把守裡面的騷亂免得引起外人的窺視。老曾獨坐在這幢樓房的最末一間臥室,臉孔紅潤,僵硬地把身體靠在椅背上,絲毫聽不到震動全屋各角落的吵鬧聲。美霞忍受不住無情的竹棒的拍打,且親睹全族的暴亂起源於她身上,才把信件搬出來。她的母親燒掉那些信件後,整個家庭仍沉浸在吵鬧中。
第二天,全家庭決定把美霞送到新竹的叔父家去,且安排在新竹做事,甚至希望以後在新竹覓得高尚人家成婚。
至於羅雲郎的母親罔市,聽到媒婆阿里的讒言之後,斷定對方是在嫌棄和輕視著他們羅家的家世和環境,罔市懷著被卑視和欺辱後的憤怒警告她的兒子。可是這種記恨在當時並不能影響到熱戀的當事人;雲郎僅僅口頭答允他的母親,鬱鬱不樂地回到鎮上,依然沉溺在思慕的哀痛中,從此很少回家。倒是美霞離開楊鎮的消息震驚了他,他悵亂而悲觀,直到一星期後接到她從新竹寄來的信,才像赦免般從絕望中釋放出來。
美霞在新竹,她的情感意外地受到叔母惠珍的尊重;惠珍叔母受託要為美霞在城市中找到一個上等的家庭結親一事,當親自聽到了美霞坦率傾露事實的真相之後,不但放棄了對二兄嫂金妹的承諾,反而大加讚許美霞的勇氣和高尚的情感。於是,當羅雲郎在一個月後偷偷赴新竹與美霞會面後,美霞的笑容再度像花朵一樣地綻開了。羅雲郎受到惠珍叔母的款待,惠珍叔母並且答應保密這件事,等到美霞的法定年齡到來,擺脫了父母的監護後。可是有一個條件,惠珍叔母羞赦而莊重地暗示他們不可偷偷做那件事。
美霞被介紹到一家百貨商行做店員,她開始留長頭髮,注意服飾,也開始再學跳舞。從此,除了信件無阻的往返外,羅雲郎瞞著母親,每一個月請假二天,那是星期五和星期六兩天,搭火車趕去新竹和美霞會面,如此繼續有一年。可是,突然羅雲郎的母親罔市另擇了一女子要他早日成婚,當然他是拒絕了,敷衍著他的母親;金妹也要求惠珍答覆美霞的近況;這樣的事開始打擾兩個年輕人的順利的愛戀,他們不得不迅速計劃結婚,於是,互相立下了永遠相守的誓言。兩個人都頗具信心要以行動來說服雙方的家長。他們以這樣的心況擁抱在一起時,不免沉溺在一些結婚計劃的美妙幻想中。
「我們一定要好好地去蜜月旅行。」
「我們到我們都不曾去過的地方──」
「那裡?」
「東部的花蓮。」
「喔,蘇花公路。」
「還有台東……」
「真美妙。」
美霞高興地喚起來。
「我們一定要做這件事。」
「死也要去那個地方走一趟。」
有一天,得智叔叔帶著美霞回到楊鎮,得智是個又高又胖的男人。看起來有點書呆樣子。他(她)們下火車,美霞過去的同學都看見她好像大小姐帶著城市的摩登回來,不似離開楊鎮前的那種天真稚氣的模樣。她帶回來許多衣服,她去了一年三個月,她自己積了一些錢,但她的身體裡面也帶回來三個月大胎兒。後面垂披著長髮,她看起來就像少婦一樣地成熟。她的得智叔叔一點兒不知情。他常常一個人回來楊鎮,因為現在他是雜貨店的合夥人之一,平時他在縣政府做事,他的外表就像一個不會容納煩惱的人。夏日的黃昏照著他(她)們的背影,他(她)們走進雜貨店,家庭中沒有人不高興,對美霞變得像個有教養的高尚和好看的女人感到快樂。除了老曾獨居在後房,永遠是呆癡僵硬的姿態,家庭中由於美霞的歸來,突然像增加了幾倍的人一樣地熱鬧。美霞走進後房老曾的臥室,握著祖父老曾的手,老曾點點頭,莫名其妙地望著美霞,然後他移開了眼睛,便不再理睬她。晚上,家庭的情緒平靜下來了,美霞走進母親的臥室,一會兒,金妹氣呼呼地衝出來,找得智叔叔,她毫不客氣地指罵他。
「我不知道啊──」得智喚叫時愈加顯露他的呆癡模樣。
「你不知道!」
「我一點兒也不明瞭到底曾發生了什麼事。」
「你看見過他嗎?」
「連他的樣子我都記不得啊。」
「我要惠珍替我負責。」
「這跟惠珍有什麼關係,嫁給他不就行了嗎?」得智天真地說。
「什麼嫁給他,沒有那麼便宜。」
「那麼妳能怎麼辦?」
「我要控告他。」
「這樣做是不好的,不能小題大做。」
「我還要好好教訓她一頓。」
「唉──」得智嘆息地說。
金妹說完走進臥室,家庭中的人都從床上再起身,身上披著衣服出來包圍得智,得智一點兒說不出話來。視力不好的得財衝進臥室,告訴他的妻子金妹好好修理她一頓,然後他氣憤地走出來,在雜貨店的櫃台後面走來走去。老曾的老伴,孩子們的祖母,面孔憂戚地走進金妹的臥室,但馬上被金妹罵出來。整個家庭開始漸漸掀起一陣的爭辯,只有老大得興出差回來,喝醉了酒,躺在床上,其他的孩子們都坐在床沿等候著,聽到美霞被金妹拖上樓上堆積雜貨的那間幽黑的臥室,始終期望著能聽到美霞有反抗的聲音。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