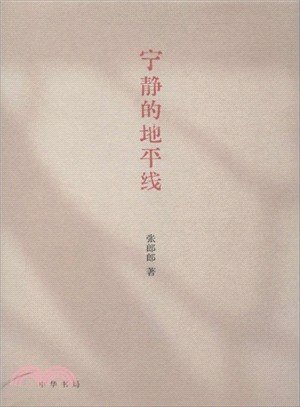寧靜的地平線(簡體書)
商品簡介
四十年前的1973年,出生于延安的張郎郎在禁獄里度過了他的而立之年。此前,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這是一個深受俄蘇文學和黃皮書灰皮書影響的文學青年,他和他的朋友們組織了文學沙龍“太陽縱隊”,他們天真而浪漫,大膽而真誠,然后,青春戛然而止。
十四年前的1999年,新疆的一家出版社出了一本書,《沉淪的圣殿》,書里講的大多是關于北京或北京青年的故事。其中有一篇文章,名《“太陽縱隊”傳說及其他》,作者正是張郎郎。四五年前,香港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北京的三聯書店,相繼出版了北島、李陀主編的《七十年代》繁、簡版,許多讀者記住了其中的一篇文章《寧靜的地平線》,這是張郎郎講述十年牢獄經歷的長文。
2013年10月,張郎郎先生的新作《寧靜的地平線》由中華書局出版。這部最新結集的作品收錄了作者在漫長的漂泊生涯中寫下的十一篇文字,不僅包括《“太陽縱隊”傳說及其他》和《寧靜的地平線》,也有《月洞門》、《孫維世的故事》、《關露及其他》等以及講述海外生活的《迷人的流亡》。張郎郎講述的故事與眾不同,他講述故事的語調也是耐人尋味。這些風格鮮明的文字,并沒有濃烈的情感抒發或悲傷憤怒的控訴,而是往往充滿了鮮明的畫面感與黑色幽默的色彩,這使此書具有歷史與文學的雙重價值,呈現出獨特的閱讀魅力。
作者簡介
曾任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教員、院刊編輯。之后曾任《中國國際貿易》雜志編輯、《國際新技術》雜志總經理、《中國美術報》副董事長、華潤集團中國廣告公司駐京辦事處主任、《九十年代》雜志專欄作家。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曾為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學者;康乃爾大學東亞系駐校作家,同時在語言系教授漢語;海德堡大學漢學系駐校作家,同時教授漢語及中國文化。后又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教授漢語及中國文化。現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員。著有《從故鄉到天涯》、《大雅寶舊事》、《寧靜的地平線》等。
名人/編輯推薦
序
寫書是個寂寞的活兒。
素未謀面的李世文先生通過北島找到我,說中華書局想出我的書。聽到這個消息,頓時就暈了。作為一個讀書人,對我國幾家出版社都有一份崇敬,中華書局是其中的佼佼者。作為一個業余寫者,能在這里出版作品,過去從來都不敢想。
時代在變遷中,再加上編輯一時糊涂,就成了我的運氣。
細想,和“地平線”這個故事也有關系。許多讀者,是看了這個故事以后才知道有這么個我,一直在講故事。
我從小就喜歡講故事,這可能是遺傳。我父親、母親都喜歡講故事。我在育才小學講故事,為了爭得一席之地,因為打架打不過別的孩子。到了中學,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以后,在人生的各個關口,我似乎都是靠會講故事僥幸蒙混過關。考上一零一關鍵是作文,考上中央美術學院關鍵是一篇文章。此后,在各種艱難的環境中得以生存,也是靠講故事。
到了香港能給《七十年代》寫專欄,只因為會胡掄。進普林斯頓當訪問學者,以及到幾個學校冒充“駐校作家”,其實還是靠侃山。說實在的,和我眾多同學、朋友在學術領域中不可同日而語。不是我學不會,主要是我沒下工夫。主要時間,全得侃山。
所以,有的朋友說我是個“鼓書藝人”,這個定位很準確。所以,在此重申,我講的這些故事,要么是自己“看到的”或“以為的”,都是單鏡頭的管窺之見;要么就是道聽途說,覺得是那么回事兒,就這么組成了故事。
我這么一說,你那么一聽。
千萬別指望在我故事里找歷史,找哲學,找教益,頂多就有點兒意思。
這本書里收集的文章,都是講一類故事。
以后也許還有其他胡同里的故事和傳說,再收集成冊,算是講故事的人,留個話本。那些和這本不太一樣,而是和《大雅寶舊事》屬于一類。
終于,我可以用每天最好的時段,來編輯自己的故事。對我來說,這就是幸福,就是意義。
希望這本書,偶爾幫你解悶兒。
目次
月洞門
曉紅
琴聲
孫維世的故事
關露及其他
王莊
家書
金豆兒
“太陽縱隊”傳說及其他
寧靜的地平線
迷人的流亡
書摘/試閱
十六歲那會兒,想學太極。
人們都笑了,說:玩假穩呀。隨便說,我還是學,想:太極修身養性,練好了,一通百通。嗯,就顛顛兒地去景山公園。見天如每。千年暗綠,虬結古柏下,片片晨霧像蚊帳扯來扯去。我們忽而白鶴亮翅,忽而野馬分鬃,氣息漸順,覺著天靈蓋快會喘氣了。
我問:“師傅,快了吧?”她說:“早著呢。”笑笑,又說:“一別性急,二別叫我師傅,難聽。”
本想再說兩句,看她那么認真地云手,就靜靜瞧著。盡管遠方沒人簫吹春江花月夜,看她凝重的風云流動,步步韻律,我心想:太極多咱才能練到這份兒上。
“超華,”劉老師腦瓜锃亮,黑灑鞋,白小褂,密門緊扣,嗽嗽嗓子:“這哪兒是打拳呢,純粹跳舞,快不如這孩子了。”說著使下巴指指我,轉身四方步,蹬蹬向別處走去。
她做個鬼臉,笑了:“瞧,師傅怎么說?”拿白手絹輕輕拍拍臉,說:“走人。”
出了景山東門,沿著大紅墻根兒往筒子河邊慢慢溜達。她一路連哼帶唱,蜻蜓點水:
“一道黑,那個兩道黑,三四五六七道黑……”
我慢慢跟著。
按我們學校的傳統,該叫她大姐姐。本來么,她已經是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的學生了。她不讓,讓我叫她名字。
在我們這伙中學土匪眼里,她是雙重的崇拜對象,又是藝術家,又是美女。
其實,她并不是流行的漂亮,只是精彩。渾身是戲,渾身靈氣。伶牙俐齒,思路敏銳,話不饒人。這辰子正修著民間曲藝課呢,滿口鼓詞,穿著緊身黑毛衣,頭發扎成一束馬尾,干凈利索。
“呀!瞧這孩子,好看死了!”她嚷。
一個傻乎乎的孩子,糊了一臉鼻涕泥,看得我兩眼發直。
“這類孩子,可人疼……誰不知是哪一家的大掌柜的吧?”話音未落,自己笑得捶胸頓足岔氣。 最煩別人說她好看,可還好說別人。一天,看照片,指著她倆妹妹,說:“怎樣?出落得特別漂亮吧?一比,我成歪瓜爛棗了。”
我笨嘴拙舌:“她們有她們的漂亮,你有你的。別自卑……”簡直不知所云。
“廢話!”狠狠瞪我一眼,“哪跟哪兒啊?再胡說不帶你玩了……象牙的煙袋烏木的桿兒,掐頭去尾是一道黑……”嚇得我不敢吱聲。
其實她小妹我見過——歐陽永華,在我們學校就打眼得出名。身條修長,勻實。冬天好戴著大白口罩,光露著兩只濃眼,就能氣死明星。脖子跟天鵝一樣,潔白而高抬。兩眼永遠朝前,和男生不過細言,高不可攀。
一天,我還露個大怯。下午跟超華去瞧大夫,那是梅花針祖師爺孫惠卿的閨女。她說:“孫大夫忒靈,有病治病,沒病健身。讓她也給你敲兩下。”
一進候診室,陽光耀眼。超華說:“這是我妹妹蜀華,這是郎郎。”
蜀華微微一笑:“我見過他,還介紹什么。”她嗓音沉穩,兩眼溫和地直視你。
我張口結舌,說:“是挺面熟,好像見過……”
超華一笑橫斷:“嘿,玩《紅樓》啊?”
我愣那兒了。蜀華騰地臉紅了,緩緩地說:“人家沒看過那書,別亂說。”
超華爽朗大笑,問我:“看過《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嗎?”
“沒有……”
“回去好好看看,再說話。別閃著。”
我整個莫名其妙。
蜀華說話至少比她姐慢三拍,笑笑說:“別當真,我們姐妹好胡說八道……”
“是你自己胡說八道,”超華利索搶斷,“郎郎,走……二姐姐打鬢又描眉,左照右照是兩道黑……”
回到家,翻《紅樓)),恍然大悟,敢情。
來回轉腰子,蝎里虎子喝煙袋油,坐不是,站不是。幾天不敢去她家。這超華哪兒哪兒都抓哏,急不得惱不得。 她突然來電話,命令式現在進行時:
“立刻來,有蘇聯回來的朋友。”
那是東四頭條,文化部后身有三個小院,北京罕見的小洋樓。第一家是茅盾先生,第三家是錢俊瑞先生,超華她們家在中間。我想,她說的“朋友”準是原本借住在錢家的劉振惠,他從列寧格勒回來一掠而過,山呼海嘯然后就泥牛入海了。沒準他從老家回來了……
興沖沖走進小院,春光普照。
蜀華,紅毛衣,靠在竹躺椅邊,看大厚書。永華,白毛衣,剛洗了頭,慢慢攏呢。超華,還是黑毛衣,斜靠在月洞門邊。粉皮墻,灰瓦檐,一叢金迎春花,斜刺里撲出。屋里誰在彈鋼琴。沒法喘氣。
雖說我來前擦了把臉,可剛在三尺浮土胡同里,踢了場球。這會兒后脊梁的粘汗又冷又硬,盤球熟練的雙足,此時只會挪橫步。
她們家的人,把我震暈了。她們家的景,照樣震,賽過電影。我們是在胡同里彈球、逮老兒、拍洋畫的土匪,這會兒離了眼、散了魂,六神無主。
超華一蹦一跳過來:“嘿,我哥回來了。永華,帶他去聽聽哥帶回來的新唱片……粉皮墻上寫川字,上看下看是三道黑……”還黑呢,我都兩眼發黑了。她是一道黑閃。
小妹一擺頭,我像讓她拍了花子,走哪兒跟哪兒。那厚重的木樓梯,那清雅的閣樓,真是個“帶閣樓的房子”,我仿佛直接走進了電影。
她放上一張《天鵝湖》,好像那是她們家的湖,不時自言自語似的輕聲說:
“白天鵝出來了……這是黑天鵝……這是王子……”這時候,你說你自己就是那位公主,我也信。沒什么新鮮。音樂和空氣混成一鍋粥,灑落的花瓣是鍋里的蔥花,點點全是清香。那天,那地,那曲,有點兒超自然,反正不像北京,不像我們活的這塊地兒,不是我們的日子口。P5-9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