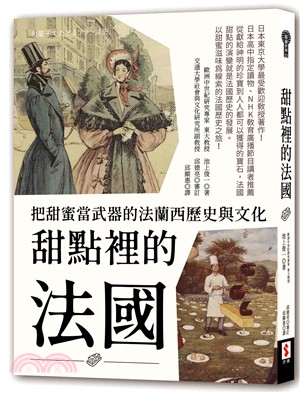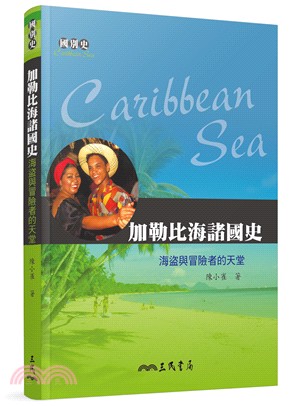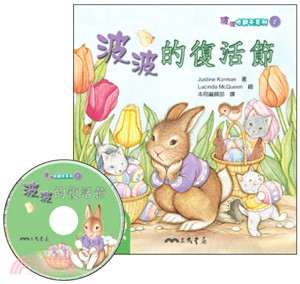再享89折,單本省下28元
商品簡介
儘管書寫日常,鄉鎮人物的樸實形象、敦厚的情感不斷從字裡行間表露而出,讓我們一再得見小鎮獨特的味道,人物的投足扭身、街巷屋舍、生活起居……等等,好似為我們追回那段令人眷戀的年代,誠如作家方梓所說:「作者以樸實的文字,沉靜的語調,從小鎮出發再現小鎮歷史,也開創小鎮的新視野。」
作者簡介
雲林縣斗南人。現任台北市閱讀寫作協會秘書長,並擔任寫作班老師。作品曾獲梁實秋文學獎散文創作類優等獎、懷恩文學獎社會組首獎、宗教文學獎小說二獎、新北市文學獎散文組二獎、雲林縣文學創作獎短篇小說佳作。著有散文集《鷺鷥飛入山》。小說集《唐棉》獲國家文藝基金會文學創作類補助。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序 平凡的魅力 讀《唐棉》/方梓
談都市文學,對位就是鄉村/鄉土文學,就像黑白一樣,十分兩極沒有中間地帶。其實在都市和鄉土文學的夾縫一直有「小鎮文學」的存在,但早期多數被歸屬在鄉村。小鎮,這個介於都市與鄉村的地域,既兼有都市的某些便利機能,又有鄉村的樸實熱情,在書寫情調上也比較多元。這一、二十年來小鎮文學萌發,最具代表的小說便是陳雨航的《小鎮生活指南》,詳實描述小鎮的地誌、文化、歷史,再現小鎮風華。
小說是從日常的經緯佈局出發,去展現平凡/普通性的魅力。廖淑華《唐棉》輯一以小鎮書寫,輯二是從小鎮出發至北部/他鄉謀生的故事,但繫牽著小鎮生活。她由小鎮的一家一戶,逐漸拉出一條街,一方小鎮的樣貌。年代由一九六○年代開始,細寫小鎮的人物、景象。小鎮裡每個家庭都有一、二件可大可小的事情,一、二個比較「活潑」的人,不管是「雞事一樁」,還是「西藥店的兩個老婆」,小鎮就靠這些活潑生趣了。
文學的第二種力量就是它的再現力,一切都應有它本身的味道。在本書第一篇〈那一年,國雄的夏天〉廖淑華開宗明義定調起小鎮地理位置、環境,「小鎮從火車站前的中山路切成兩半,一半稱新市,一半叫做舊市,說話時大家習慣加個『ㄚ』的尾音。舊市ㄚ這一半就屬福德街土地公廟周圍最聚市、最熱鬧,正對土地公廟的一排房舍後方有條大圳溝,圳水來自鎮外的大溪……」。《唐棉》輯一的幾篇小說都展現了小鎮獨特的味道,人物的投足扭身、街巷屋舍、生活起居,廖淑華寫來彷彿活脫脫呈在讀者眼前,如影像播映,琇雲的溫婉、阿連的男人女相、阿英的乾瘦、小街的樣貌、餅舖、西裝店的陳設…一目了然,宛如回到一九六○年代。
細節藏著功夫,小地方看格局;廖淑華擅長描述細節,「小鎮清早的街市,三三兩兩行人,女人家小心托著月桃葉上的豆腐,稍急步伐扭動的身軀如手上剛出鍋的豆腐一顫一抖地;老人拎著藺草綁著的油條,走過路口的土地公廟時仍不忘虔誠合十拜了拜。」大半的作品,廖淑華都細述景與人的互動,以及人物特寫去彰顯情節的演繹,以小托大,厚實了小說的豐富、可讀性。
《唐棉》輯一、輯二大半以女性做為主要敘述,廖淑華剔盡了女人的心思,〈阿英孵蛋〉透徹了偏房處境、生與不生的兩難;〈回家〉入骨了「她」的寂寞及悲思、反諷女人的「回家」;〈唐棉〉中女人的靭性與無奈……
寫作從廢墟出發,從無到有創造了新境界;廖淑華以樸實的文字,沉靜的語調,從小鎮出發再現小鎮歷史,也開創小鎮的新視野。
目次
推薦序 平凡的魅力 讀《唐棉》/方梓
輯一
那年,國雄的夏天
家在圓環
神聖的一票
雞事一樁
連姨
三月天
阿英孵蛋
回家
志成與蚵仔伯們
身後
輯二
台北新鮮人
頭家
唐棉
有夢
退場
後記
書摘/試閱
身後
三月初春的高速公路,過了臺中之後天空明顯的藍了許多,車裡的溫度也暖升些許;窗外馳過幾棵早發的羊蹄甲,粉紫襯川在嫩綠的葉間,讓從溼涼臺北出發的她,有股去霉的舒爽。
抬眼,見後視鏡裡,父親身上的蓋毯斜斜滑落,似乎睡著了,出發時緊抓著車門吊把的手指,鬆開了,然而食指中指仍微屈地勾住環緣。她難得開快速道路,更不曾自己一個人開長途車,難怪父親緊張。他一向搭慣了兒子開的車。她也緊張。開車,一直以來都是丈夫的差事,恢復單身後她返鄉有時搭火車、有時搭姊姊的便車,這回要不是父親跟母親嘔氣,率性地開了老爺車上臺北來,這時候也不會讓她被編派連人帶車送父親回家。無子女、此刻又無固定工作的她,似乎總被認定為隨時可以差用的閒人。父親適才還絮絮碎唸,擔心她手邊積蓄不豐,老來無依,而後又好似想起這項代誌已經說過太多次了,女兒一定覺得很厭煩吧,唸著唸著聲音只剩在嘴巴裡。她在後視鏡裡和父親的眼光碰個正著,老人家的話尾巴收了音,才停一會又開始:「就算有孩子也無路用,養兒是義務,萬事還是要靠自己,妳自己要有打算啦。」
近年來,父親老了,威嚴傾圮了;她也老了,拘謹的性子鬆綁許多,才比較能與父親獨處,此刻她真後悔沒邀姊姊陪同南下。氣氛好沉悶。她裝輕鬆語氣回父親說,前些日才剛與朋友參觀過養生村,現在行情漲了不少呢,每個月伙食雜支少說也得要準備個兩萬元才夠,朋友們都說要努力攢錢多存養老本,要不哪住得起。
以後呢?她從後視鏡看著問話的父親。
「以後」就買塔位啊,誦經普度照合約按步來,哎呀,人都走了,還想那麼多……
之前,哥開車送父親過來的時候說父親在生氣。她以為父親這回會多住幾日,怎麼才過一夜就要回家?隔著車窗探看,不覺得父親有生氣的神色。哥哥沒什麼表情,說還不是為了遷公媽牌位的事。父親搖下車窗招喚她,嚷說不下車了,要趕緊返去;又朝兒子擺擺手,叫他趕快去上班。她不知怎麼說父親,傻嗎?哥早幾年不都說了嗎,「住家太小沒有適當方位安放神明案桌」、「上班工作沒有空祭拜」,父親怎還要自己惹氣生呢?她曾經幫忙說話,大哥的家在沒有電梯的公寓四樓,客廳格局還真難騰出空間來設置公媽香案。
父親對她的緩頰不置可否,只淡淡地說:「若有心就有所在,人家誰誰三坪大的摩托車店、誰誰家還跟別人租的呢,不也照樣可以拜。」這幾年兄嫂同修自悟了一些道理,父親更聽不入耳了,「說啥人死去魂就散去啊,散在虛無空界,不是寄附在那塊神主牌!伊也不是信耶穌,信同款拿香的,竟講不拜祖先,這是啥道理!」她沒接話。她沒「修」。不懂。不想讓老父更傷感,勸父親「看開一點」的言語也說不出口,那只會換來「無效啦,讀冊讀去胛脊胼」如此這般拉雜的怨懣。
隨著年歲增長,對人情世故她也多少調整了年輕時非黑即白的「正義感」,學習體諒有些時候、有些人對有些事的「不為」,然而體諒不等於認同,對於自己也未必做得到亦無法代勞的,她只能選擇沉默。
車子駛離北部,沿路景象也換了樣,就拿人生終站來說吧,北中部高速公路或遠或近的山崙還望得到一處一處墳場,進入平緩的西部平原後,散置綠茵間的土坏群落景觀變成水泥疊塔。未出嫁前清明掃墓,一年一次上墳,父親總這樣介紹著要哥哥記住:那是祖太,阿祖,喔,彼個查甫祖、這個查某祖,阿公的墓在另一區……。哥哥閒閒地在墓園周圍走來走去,大人也不會特地叫他幫忙做事,倒是她們幾個女孩子忙著小心攀長身子刈去墳頭墓草、壓上墓紙,因為父母再三叮囑著,女孩子不可以踩上墳。一年一年,父親擎香喃喃稟報祖先,哪個子孫讀書工作順遂與否,哪個子孫新婚又哪個子孫添丁……。紙灰焚燃煙塵飛揚,幾炷清香,灑下水酒,擲筊問卜,祈求平安。親人先後撿骨晉塔,她曾隨父親挨擠在祭拜的人群中,在高過她頭頂的牆櫃搜尋,憑藉記憶在迂廊曲道尋著阿公阿嬤寄身的小方格,稟告老人家,家人來「做清明」了,請他們來領受子孫的孝思。母親則在家中準備祭品,拜公媽。
三層樓的老家,母親日日爬上頂樓公媽廳拂拭香案、敬茶上香,攀幾坎階梯就得停步,待喘得過氣了再往上爬。她不敢多想,逢年過節時,兩位老人家得上下那直陡的樓梯幾趟才能將牲禮敬果運送上下樓?僅有那麼幾回年節她剛好返鄉,端著牲禮上樓尚不覺得吃力,下樓時由上望下,窄直的階梯連她也下意識地老覺得踩不實腳步,幾度有就要栽下的錯覺。近年,母親老化的速度明顯,家務種種一件件放手移交給父親,她們幾個孩子心疼母親,慶幸看來還腰挺腳健的父親猶能照顧母親,卻輕忽了父親近來連眉毛都灰白了。父親雖不喊苦,然而幾次提及遷移公媽要哥哥承擔祭拜責任,對一向自詡從不求人的父親而言,可見真的力竭了。
死者已矣,至於魂歸何方,甚至存在否,自來就沒有肯定的答案,對奉祀公媽久久不能交棒,父親心情縈縈難紓,她能懂得;「對祖先要有交代」的責任感驅使父親焦慮,如何說與先人明白,後代子孫的家竟覓無方寸供他們容身?她不捨父親,也心疼案桌上的公媽,因為那之中有她親愛的阿嬤。阿嬤做「對年」時,司公請下公媽牌位,掀開背面隔板取出木摺頁,以細楷寫上「某媽某某」,司公說這叫做「合爐」。她看著生前未冠夫姓的阿嬤,逝後本家名姓退次,背負孕育香火責任的女人,在葉落之後歸的不會是原來的根,即使是未出嫁或是離了婚的女人,身後亦未得回歸根源。對於身後種種,她不曾有過如那刻的思緒翻湧,步入中年,人生的歷練體悟讓她自認能瀟灑淡定,然而彼時竟興起絲微惶惑:若她,孤身零落,若靈猶有知,誠真死無歸處?
父母尚健,她避諱,不把身後事當話題談,不過瑣瑣碎碎地也寫了一些身外物作何處理交代子姪甥輩,有時閒來取出瀏覽,恍如打開未來。她思及自己的未雨綢繆偶爾也不覺一哂,人生來去空空,自己尚罣礙如斯,終究算是想得開抑或放不下呢?
她覺得老一輩人的順其自然,倒也是一種想得開。曾經,她不經意問起家鄉的鄰居長輩,阿嬤總是以一種透徹的豁達說:「某某?早『回去』嘍。」或「妳還記得某某?骨頭莫不可以打鼓嘍。」有幾次阿嬤有意無意地對她說:「講經的師父說得也對,其實用燒的較衛生。」她頗覺驚奇,與民國同年的阿嬤能接受火化的觀念,然而終了因為並無確切遺言交代,後輩仍按土葬習俗辦理。
逝者不知,那麼有所感應皆為生者的牽掛嗎?她曾兩次夢見阿嬤。一回,看到老人家置身在空無一物的寬闊屋內,伸手觸及不到的大扇窗戶外有湍急的水流過,夢中沒有言語,阿嬤望著窗戶對她微笑。另一回,阿嬤坐在塋頭,指著身後隆起的、綠草新生的土堆,「厝內淹水!」是誰在說話?抑或她自身恍惚?放不下夢中的阿嬤,她打電話請父親一定要去墓園看看。父親回說去墓園巡視過兩趟,從外觀察不見有水滲入墓內的跡象。直到撿骨晉塔,父親打來電話期期艾艾說阿嬤墳墓後的排水溝底崩裂,水進到墓室,棺木底泡爛了,阿嬤的骨頭罩在重重水氣……;痛啊,逝者已邈肉身無覺,是她的心,揪絞成結。
一陣刺鼻的化工氣味,她按了阻絕車內外空氣流通的按鍵,氣味仍自車門車窗縫隙抑或哪個來不及閉鎖的孔道竄進來,中彰路段這股熟悉消蝕不去的氣味就如到站播報,不用看里程路牌,她知道再十多公里就是家鄉的交流道了。
父親的車子內也有一種味道,老人的味道,微微若無地飄浮。父親開車出門隔天才到臺北哥哥家,她想,節儉的父親應該就在車上過夜的吧,把母親慣用的靠墊做枕、護膝小毯當被,如初生蜷曲在車上瑟縮了一夜?已過從心所欲年歲的他是否怨苦委屈?
父親向來簡淨,紙盒什細隨手即棄,未有撿惜小物的習性,以往他指揮掌廚的母親,採買數量、飯菜準備務必精確,不准有隔夜餐,到母親退位、父親全盤接收後,家中簡白幾乎到淨空的境界,彷彿隨時交代清楚明白,無須勞煩他人,完全是父親的行事作風。這回就因為母親找不到原本藏在鞋盒的金飾,打電話向女兒們告狀,先是說一定是被當成不要的紙盒扔了,後來說一定是被誰拿走了。家裡不就兩個人嗎?她聽過太多退化健忘的老人,把財物東藏西藏以致後來自己都忘了藏在哪,她試著引導母親回想,老人家惱怒了:「妳和妳爸爸一樣,當我倥倥。」父親氣不過被誣指,撂下話說「那幾塊鼻屎大金子,我還看不上眼!」開車出門人都還未到臺北呢,母親打電話來說了,「找到了!」金飾一樣藏在鞋盒,只是換了另一個,幾時換的?她忘了。
父親睡著的神情未顯慍色,對於母親現今腦力身不由己的混亂,她相信父親能體諒,脾氣發過不悅也就過了,看他灰白髮色下的面容,兩條法令紋森森嚴肅地拉垂至嘴角,哥說父親為遷公媽牌位的事生氣,她覺得父親應是悒鬱的多。這些年他幾乎已不提公媽牌位的事了,一向標榜自少年就靠自己打拚的父親,一身傲骨腰桿隨時打得挺直,這回為什麼會再舊事重提呢?
聽到聲音看父親起身拾起蓋毯,她問父親渴嗎?置物袋有礦泉水。
「妳知影妳阿兄換新厝了嗎?」
嗄?
「恁平平在臺北怎麼不知道?平日都無往來嗎?兄弟姊妹要互相照顧,父母總會年老,妳無聽過彼句話嗎?」
死老父後頭遠,死老母後頭斷,從小聽老人掛在嘴邊的。好傷感呵,爸爸,我們不要說這個好嗎?她在心裡說。
「喔,我和老哥平時都有電話聯絡呀!新厝有電梯吧?以後你和媽媽來住毋免爬四樓,就方便多了。」
「新厝企在十五樓。有三間房,兩個小孩各人一間,妳阿兄阿嫂一間,擱有一間小間的鋪榻榻米,打坐用的。」
沒有客房?她吞下問話。又從後視鏡看父親,心想著,必定是因而才又提起公媽牌位的事吧,她躊躇著如何接話。
父親提醒她快到交流道了,要她切到慢車道。邊疊毯子邊告訴她:毯子是在市場開百貨的王老闆送的,因為店要收掉了。王老闆的牽手去年過身,伊自己身體也不好,一個人照顧不來,孩子都吃頭路無興趣開店。王老闆兩個兒子都信基督教,伊煩惱後擺公媽無人拜,兒子不肯聽伊講,伊就跟女婿講,伊若走,公媽要幫伊顧乎好。哎,悲哀,自己家的公媽怎麼拜託女婿?這樣人家也很為難。我現在已經不想那麼多了。我就跟王老闆講,人走都走了,孩子要怎麼樣,隨在他們啦……
她抬眼,後視鏡裡正在整裝的父親神情平和。她想,她也不必費神找話說了。
啊,快到咱厝了,返來自己的厝較快活。我兩晚不在,妳媽媽一定睡不好,藥毋知有按時吃無,回去要記得先幫伊量量血壓……,父親像是自說自話。
轉進巷子,她遠遠看見母親在門口澆花,聽見車停聲音,母親旋身,陽光將蓮蓬頭灑出的水珠熠耀得五彩發光,笑開了。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