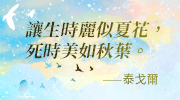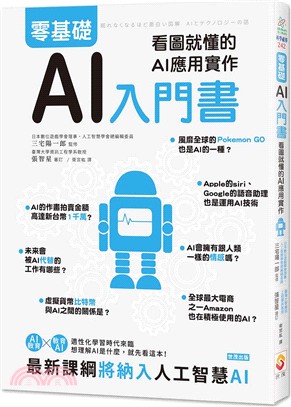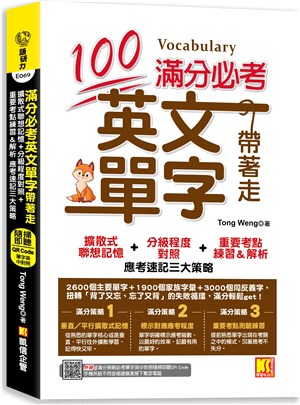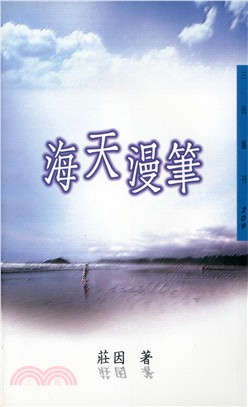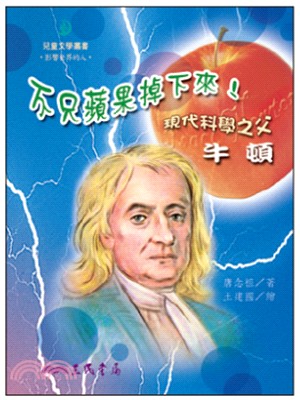商品簡介
梭羅以手中的妙筆來描繪瓦爾登湖:“生長在雜草蔓生的林間小路上的香蕨木和木藍上的露珠會把你下半身打濕。叢生櫟的葉子泛光,好似有液體在上面流過。透過樹木看見的小塘像天空一樣滿是光亮。……你見到月光從森林深處一個個樹樁上返射回來,仿佛她在照耀萬物時有所選擇,她的星星點點的光芒使人想起一種叫做月亮籽的植物──似乎是月亮把它們種在這些地方……”
這是一本寧靜、恬淡、充滿智慧的書。其中分析生活,批判習俗處,語語驚人,字字閃光,見解獨特,耐人尋味。許多篇頁是形象描繪,優美細致,像湖水的純潔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綠;也有一些篇頁說理透徹,十分精闢,給人啟迪。
這是一本清新、健康、引人向上的書,對于春天,對天黎明,都有極其動人的描寫。這里有大自然給人的澄淨的空氣,而無工業社會帶來的環境污染。讀著它,讀者自然會感覺到心靈的純淨,精神的升華。
作者簡介
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年7月12日-1862年5月6日)
美國作家、哲學家,著名散文集《瓦爾登湖》和論文《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又譯為《消極抵抗》、《論公民的不服從》)的作者。
梭羅出生於麻塞諸塞州,1837年畢業於哈佛大學。1845年7月4日梭羅開始了一項為期兩年的試驗,他移居到離家鄉康科德城(Concord)不遠,優美的瓦爾登湖畔獨自築屋耕種,嘗試過一種簡單的隱居生活。他於1847年9月6日離開瓦爾登湖。1854年出版於的散文集《瓦爾登湖》詳細記載了他在瓦爾登湖畔兩年又兩個月的生涯。
他不僅從事原始的農耕漁獵生活,遠離塵世也讓他在大自然奇景及和野生動植物一同生活中, 更冷靜、客觀地觀察自然生存法則。他討厭土地被過度開發,反對自然景觀被破壞,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是「環保專家」,
亨利梭羅在最後十年的歲月裡,投入對野生果實、野草及森林演替之觀察研究。他巨細靡遺地蒐集資料、觀察及繪製圖表,架構出「種子的信仰」一書,成功地在文 學和自然科學間搭建了互動橋樑。
他的著作讓我們從更宏觀的角度思索大自然和土地的倫理。所以說亨利梭羅是最具影響力的自然文學大師、科學家或呈現生命之美的藝術家均當之而無愧。
譯者簡介
徐遲(1914年10月15日-1996年12月12日)
中國現當代詩人,散文家,翻譯家,著名報告文學作家。
其代表作《哥德巴赫猜想》與《地質之光》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他的作品被譽為「別具特色的科學詩篇」。
自然生存法則。他討厭土地被過度開發,反對自然景觀被破壞,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是「環保專家」,
亨利梭羅在最後十年的歲月裡,投入對野生果實、野草及森林演替之觀察研究。他巨細靡遺地蒐集資料、觀察及繪製圖表,架構出「種子的信仰」一書,成功地在文 學和自然科學間搭建了互動橋樑。
他的著作讓我們從更宏觀的角度思索大自然和土地的倫理。所以說亨利梭羅是最具影響力的自然文學大師、科學家或呈現生命之美的藝術家均當之而無愧。
序
你能把你的心安靜下來嗎?如果你的心並沒有安靜下來,我說,你也許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靜下來,然後你再打開這本書,否則你也許會讀不下去,認為它太濃縮,難讀,艱深,甚至會覺得它莫明其妙,莫知所云。
這個中譯本的第一版是一九四九年在上海出版的。那時正好舉國上下,熱氣騰騰。解放全中國的偉大戰爭取得了輝煌勝利,因此注意這本書的人很少。
但到了五十年代,在香港卻有過一本稍稍修訂了它的譯文的,署名吳明實︵無名氏︶的盜印本,還一次次再版,達六版之多。
這個中譯本的在︵中國大陸︶國內再版,則是在初版之後三十三年的一九八二年,還是在上海,經譯者細加修訂之後,由譯文出版社①出第二版的。這次印數一萬三千冊。幾年前,︽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編委會決定,將它收入這套叢書,要我寫一篇新序。那時我正好要去美國,參加一個﹁國際寫作計畫﹂,有了可能去訪問麻塞諸塞州的康科特城和瓦爾登湖了。在美國時,我和好幾個大學的中外教授進行了關於這本書的交談,他們給了我很多的幫助。於今回想起來,是十分感謝他們的。
對這第二版的譯文我又作了些改進,並訂正了一兩處誤譯,只是這一篇新序卻總是寫不起來。一九八五年寫了一稿,因不滿意,收回重寫。然一連幾年,人事倥傯,新序一直都沒有寫出來。為什麼呢?最近找出了原因來,還是我的心沒有安靜下來。就是因為這個了,這回可找到了原因,就好辦了。心真正地安靜了下來,這總是可以做到的。就看你自己怎麼安排了。為何一定要這樣做?因為這本︽瓦爾登湖︾②︵Walden︶是本靜靜的書,極靜極靜的書,並不是熱熱鬧鬧的書。它是一本寂寞的書,一本孤獨的書。它只是一本一個人的書。如果你的心沒有安靜下來,恐怕你很難進入到這本書裡去。我要告訴你的是,在你的心靜下來以後,你就會思考一些什麼。在你思考一些什麼問題時,你才有可能和這位亨利.大衛.梭羅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則。
這位梭羅先生是與孤獨結伴的。他常常只是一個人。他認為沒有比孤獨這個伴兒更好的伴兒了。他的生平十分簡單,十分安靜。一八一七年七月十二日梭羅生於康科特城;就學並畢業於哈佛大學︵一八三三∼一八三七年︶;回到家鄉,執教兩年︵一八三八∼一八四○年︶。然後他住到了大作家、思想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家裡︵一八四一∼一八四三年︶,當門徒,又當助手,並開始嘗試寫作。到一八四五年,他就單身只影,拿了一柄斧頭,跑進了無人居住的瓦爾登湖邊的山林中,獨居到一八四七年才回到康城。
一八四八年他又住在愛默生家裡;一八四九年,他完成了一本叫作︽康科特河和梅里麥克河上的一星期︾︵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Merrimack Rivers︶的書。差不多同時,他發表了一篇名為︽消極反抗︾︵On Civil Disobedience︶的極為著名的、很有影響的論文。按字面意義,這也可以譯為﹁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後面我們還要講到它。然後,到了一八五四年,我們的這本文學名著︽瓦爾登湖︾出版了。本書有了一些反響,但開始的時候並不大。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影響越來越大。一八五九年,他支持了反對美國蓄奴制度的運動;當這個運動的領導人約翰.布朗竟被逮捕,且被判絞刑處死時,他發表了為布朗辯護和呼籲的演講,並到教堂敲響鐘聲,舉行了悼念活動。此後他患了肺病,醫治無效,於一八六二年病逝於康城,終年僅四十四歲。他留下了︽日記︾︵The Journal︶三十九卷,自有人給他整理,陸續出版,已出版有多種版本和多種選本問世。
他的一生是如此之簡單而馥鬱,又如此之孤獨而芬芳。也可以說,他的一生十分不簡單,也毫不孤獨。他的讀者將會發現,他的精神生活十分豐富,而且是精美絕倫,世上罕見。和他交往的人不多,而神交的人可就多得多了。
他對自己的出生地,即麻省的康城,深感自豪。康城是爆發了美國獨立戰爭的首義之城。他說過,永遠使他驚喜的是他﹁出生於全世界最可尊敬的地點﹂之一,而且﹁時間也正好合適﹂,適逢美國知識界應運而生的、最活躍的年代。在美洲大陸上,最早的歐洲移民曾居住的﹁新英格蘭﹂六州,正是美國文化的發祥之地。而正是在麻省的康城,點燃起來了美國精神生活的輝耀火炬。小小的康城,風光如畫。一下子,那裡出現了四位大作家:愛默生,霍桑,阿爾考特,和他,梭羅。一八三四年,愛默生定居於康城,曾到哈佛大學作了以︽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為題的演講。愛默生演講,撰文,出書,宣揚有典型性的先知先覺的卓越的人,出過一本︽卓越的人︾︵Great men︶,是他的代表作。他以先驅者身份所
發出的號召,給了梭羅以深刻的影響。
梭羅大學畢業後回到康城,正好是他二十歲之時。一八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那天他記下了他的第一篇日記:
﹁﹃你現在在幹什麼?﹄他問。﹃你記日記嗎?﹄好吧,我今天開始,記下了這第一條。
﹁如果要孤獨,我必須要逃避現在—我要我自己當心。在羅馬皇帝的明鏡大殿裡我怎麼能孤獨得起來呢?我寧可找一個閣樓。在那裡是連蜘蛛也不受干擾的,更不用打掃地板了,也用不到一堆一堆地堆放柴火。﹂
那個條文裡面的﹁他﹂,那個發問的人就是愛默生。這真是一槌定了音的。此後,梭羅一直用日記或日誌的形式來記錄思想。日記持續了二十五年不斷。正像盧梭寫的︽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思想︾③︵Les re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一樣,他寫的也是一個孤獨者的日記。而他之要孤獨,是因為他要思想。他愛思想。
稍後,在一八三八年二月七日,他又記下了這樣一條:
﹁這個斯多葛主義者︵禁欲主義者︶的芝諾︵希臘哲人︶跟他的世界的關係,和我今天的情況差不多。說起來,他出身於一個商人之家—有好多這樣的人家呵!—會做生意,會講價錢,也許還會吵吵嚷嚷,然而他也遇到過風浪,翻了船,船破了,他漂流到了皮拉烏斯海岸,就像什麼約翰,什麼湯麥斯之類的平常人中間的一個人似的。
﹁他走進了一家店鋪子,而被色諾芬︵希臘軍人兼作家︶的一本書︵︽長征記︾︶迷住了。從此以後他就成了一個哲學家。一個新生的日子在他的面前升了起來︙︙儘管芝諾的血肉之軀還是要去航海呵,去翻船呵,去受風吹浪打的苦呵,然而芝諾這個真正的人,卻從此以後,永遠航行在一個安安靜靜的海洋上了。﹂
這裡梭羅是以芝諾來比擬他自己的,並也把愛默生比方為色諾芬了。梭羅雖不是出身於一個商人之家,他卻是出生於一個商人的時代,至少他也得適應於當時美國的商業化精神,梭羅的血肉之軀也是要去航海的,他的船也是要翻的,他的一生中也要遇到風吹和浪打的經歷的,然而真正的梭羅卻已在一個安安靜靜的海洋上,他嚮往於那些更高的原則和卓越的人,他是嚮往於哲學家和哲學了。
就在這篇日記之後的第四天,愛默生在他自己的日記上也記著:﹁我非常喜歡這個年輕的朋友了。仿佛他已具有一種自由的和正直的心智,是我從來還未遇到過的。﹂過了幾天,愛默生又在自己的日記裡寫:﹁我的亨利.梭羅可好呢,以他的單純和明晰的智力使又一個孤獨的下午溫煦而充滿了陽光。﹂四月中,愛默生還記著:﹁昨天下午我和亨利.梭羅去爬山,霧濛濛的氣候溫暖而且愉快,仿佛這大山如一座半圓形的大劇場,歡飲下了美酒一樣。﹂
在愛默生的推動之下,梭羅開始給︽日晷︾︵The Dial︶雜誌寄詩寫稿了。但一位要求嚴格的編輯還多次退了他的稿件。梭羅也在康城學院裡作了一次題為︽社會︾的演講,而稍稍引起了市民的注意。到一八四一年,愛默生就邀請了梭羅住到他家裡去。當時愛默生大事宣揚他的唯心主義先驗論,聚集了一班同人,就像辦了個先驗主義俱樂部似的。但梭羅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先驗主義者。在一段日記中他寫著:﹁人們常在我耳邊叮嚀,用他們的美妙理論和解決宇宙問題的各種花言巧語,可是對我並沒有幫助。我還是回到那無邊無際,亦無島無嶼的汪洋大海上去,一刻不停地探測著、尋找著可以下錨,緊緊地抓住不放的一處底層的好。﹂
本來梭羅的家境比較困難,但還是給他上了大學,並念完了大學。然後他家裡的人認為他應該出去闖天下了。可是他卻寧可回家鄉,在康城的一所私立中學教教書。之後不久,只大他一歲的哥哥約翰也跑來了。兩人一起教書。哥哥教英語和數學,弟弟教古典名著、科學和自然史。學生們很愛戴他們倆。亨利還帶學生到河上旅行,在戶外上課、野餐,讓學生受到以大自然為課堂,以萬物為教材的生活教育。一位朋友曾稱梭羅為﹁詩人和博物學家﹂,並非過譽。他的生活知識是豐富,而且是淵博的。當他孤獨時,整個大自然成了他的伴侶。據愛默生的弟弟的回憶,梭羅的學生告訴過他:當梭羅講課時,學生們靜靜地聽著,靜得連教室裡掉下一根針也能聽得清楚。
一八三九年七月,一個十七歲的少女艾倫.西華爾來到康城,並且訪問了梭羅這一家子。她到來的當天,亨利就寫了一首詩。五天後的日記中還有了這麼一句:﹁愛情是沒有法子治療的,惟有愛之彌甚之一法耳。﹂這大約就是為了艾倫的緣故寫的。不料約翰也一樣愛上了她,這就使事情複雜化了。三人經常在一起散步,在河上划船。登山觀看風景,進入森林探險,他們還在樹上刻下了他們的姓氏的首字。談話是幾乎沒完沒了的,但是這個幸福的時間並不長久。
這年春天,哥兒倆曾造起了一條船。八月底,他們乘船沿著康科特河和梅里麥克河上作了一次航行。在旅途上,一切都很好,只是兩人之間已有著一些微妙的裂痕,彼此都未言明,實際上他們已成了情敵。後來約翰曾向她求婚而被她拒絕了。再後來,亨利也給過她一封熱情的信,而她回了他一封冷淡的信。不久後,艾倫就嫁給了一個牧師。這段插曲在亨利心頭留下了創傷。但接著發生了一件絕對意想不到的事。一八四二年的元旦,約翰在一條皮子上磨利他的剃鬚刀片時,不小心劃破了他的左手中指。他用布條包紮了,沒有想到兩三天後化膿了,全身疼痛不堪。趕緊就醫,已來不及,他得了牙關緊閉症,敗血病中之一種。他很快進入了彌留狀態。十天之後,約翰竟此溘然長逝了。突然的事變給了亨利一個最沉重的打擊。他雖然竭力保持平靜,回到家中卻不言不語。一星期後,他也病倒了,似乎也是得了牙關緊閉症。幸而他得的並不是這種病,是
得了由於心理痛苦引起的心身病狀態。整整三個月,他都在這個病中,到四月中他又出現在園子裡了,才漸漸地恢復過來。
那年亨利寫了好些悼念約翰的詩。在︽哥哥,你在哪裡︾這詩中,他問道:﹁我應當到哪裡去/尋找你的身影?/沿著鄰近的那條小河,/我還能否聽到你的聲音?﹂答覆是他的兄長兼友人,約翰,已經和大自然融為一體了。他們結了綢繆,他已以大自然的容顏為他自己的容顏了,以大自然的表情表達了他自己的意念‧‧‧大自然已取走了他的哥哥,約翰已成為大自然的一部分: 從這裡開始,亨利才恢復了信心和歡樂。他在日記中寫著:﹁眼前的痛苦之沉重也說明過去的經歷之甘美。悲傷的時候,多麼的容易想起快樂!冬天,蜜蜂不能釀蜜,它就消耗已釀好的蜜。﹂這一段時間裡,他是在養病,又養傷;在蟄居之中,為未來作準備,在蓄勢,蓄水以待開閘了放水,便可以灌溉大地。
在另一篇日記中,他說:﹁我必須承認,若問我對於社會我有了什麼作為,對於人類我已致送了什麼佳音,我實在寒酸得很。無疑我的寒酸不是沒有原因的,我的無所建樹也並非沒有理由的。我就在想望著把我的生命的財富獻給人們,真正地給他們最珍貴的禮物。我要在貝殼中培養出珍珠來,為他們釀製生命之蜜。我要陽光轉射到公共福利上來。我沒有財富要隱藏。我沒有私人的東西。我的特異功能就是要為公眾服務。惟有這個功能是我的私有財產。任何人都是可以天真的,因而是富有的。我含蘊著,並養育著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時。﹂
恢復健康以後的梭羅又住到了愛默生家裡。稍後,他到了紐約,住在市裡的斯丹唐島上,在愛默生弟弟的家裡。他希望能開始建立起他的文學生涯來。恰恰因為他那種獨特的風格,並不是能被人,被世俗社會所喜歡的,想靠寫作來維持生活也很不容易,不久之後,他又回到了家鄉。有一段時間,他幫助他父親製造鉛筆,但很快他又放棄了這種尚能贏利的營生。
於是到了一八四四年的秋天,愛默生在瓦爾登湖上買了一塊地。當這年過去了之後,梭羅得到了這塊土地的主人的允許,可以讓他﹁居住在湖邊﹂。終於他跨出了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一八四五年三月尾,我借來一柄斧頭,走到瓦爾登湖邊的森林裡,到達我預備造房子的地方,開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聳入雲而還年幼的白松來做我的建築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們感到難過的冬天正跟凍土一樣地消溶,而蟄居的生命開始舒伸了。﹂
七月四日,恰好那一天是獨立日,美國的國慶,他住進了自己蓋起來的湖邊的木屋。在這木屋裡,這湖濱的山林裡,觀察著,傾聽著,感受著,沉思著,並且夢想著,他獨立地生活了兩年又多一點時間。他記錄了他的觀察體會,他分析研究了他從自然界裡得來的音訊、閱歷和經驗。決不能把他的獨居湖畔看作是什麼隱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奮人生,闡述人生的更高規律。並不是消極的,他是積極的。並不是逃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並且就在這中間,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獨特方式,投身於當時的政治鬥爭。
那發生於一個晚上,當他進城去到一個鞋匠家中,要補一雙鞋,忽然被捕,並被監禁在康城監獄中。原因是他拒絕交付人頭稅。他之拒付此種稅款已經有六年之久。他在獄中住了一夜,毫不在意。第二天,因有人給他付清了人頭稅,就被釋放。出來之後,他還是去到鞋匠家裡,等補好了他的鞋,然後穿上它,又和一群朋友跑到幾裡外的一座高山上,漫遊在那兒的什麼州政府也看不到的越橘叢中—這便是他的有名的入獄事件。
在一八四九年出版的︽美學︾︵Aesthetic Papers︶雜誌第一期上,他發表了一篇論文,用的題目是︽對市政府的抵抗︾︵Resistance to CivilGovernment︶。在一八六六年︵他去世已四年︶出版的︽一個在加拿大的美國人,及其反對奴隸制和改革的論文集︾︵A Yankee in Canada,with Anti-Slavery and Reform Papers︶收入這篇文章時,題目改為︽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Civil Disobedience︶。此文題目究竟應該用哪一個,讀書界頗有爭論,並有人專門研究這問題。中國一般地慣用了
這個︽消極反抗︾的題名,今承其舊,不再改變。文中,梭羅並沒有發出什麼政治行動的號召,這毋寧說正是他一貫宣導的所謂﹁更高的原則﹂中之一項。他認為政府自然要做有利於人民的事,它不應該去干擾人民。但是所有的政府都沒有做到這一點,更不用說這個保存了奴隸制度的美國政府了,因此他要抗議和抵抗這一個政府,不服從這一個政府。他認為,如果政府要強迫人民去做違背良心的事,人民就應當有消極抵抗的權利,以抵制它和抵抗它。這篇︽消極抵抗︾的論文,首先是給了英國工党和費邊主義者以影響,後來又對於以絕食方式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印度聖雄甘地的﹁不合作運動﹂與﹁非暴力主義﹂有很大的作用,對於一九六○年馬丁.路德.金,在非洲爭取民權運動也有很大的作用,對托爾斯泰的﹁勿以暴抗暴﹂的思想也有影響,以及對羅曼.羅蘭也有一些影響。
梭羅是一生都反對蓄奴制度的,不止一次幫助南方的黑奴逃亡到自由的北方。在一八四五年的消極反抗之後,他還寫過︽麻省的奴隸制︾︵一八五四年,Slaver y in Massachusetts︶一文,他和愛默生一起支持過約翰.布朗。一八五九年十月,布朗企圖襲擊哈潑斯渡口失敗而被捕,十一月刑庭判處布朗以絞刑,梭羅在市會堂裡發表了︽為約翰.布朗請願︾︵A Plea for Captain John Brown︶的演說。布朗死後,當地不允許給布朗開追悼會時,他到市會堂敲響大鐘,召集群眾舉行了追悼會。梭羅關於布朗的一系列文章和行動都是強烈的政治言行。
這期間,梭羅患上了肺結核症,健康明顯地變壞。雖然去明尼蘇達作了一次醫療性的旅行,但病情並無好轉。他自知已不久人世了。在最後的兩年裡,他平靜地整理日記手稿,從中選出一些段落來寫成文章,發表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他平靜安詳地結束了他的一生,死於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未滿四十五歲。
梭羅生前,只出版了兩本書。一八四九年自費出版了︽康科特河和梅里麥克河上的一星期︾,這書是他在瓦爾登湖邊的木屋裡著寫的,內容是哥兒倆在兩條河上旅行的一星期中,大段大段議論文史哲和宗教等等。雖精雕細刻,卻晦澀難懂,沒有引起什麼反響。印行一千冊,只售出一百多冊,送掉七十五冊,存下七百多冊,在書店倉庫裡放到一八五三年,全部退給作者了。梭羅曾詼諧地說,我家裡大約藏書九百冊,自己著的書七百多冊。
他的第二本書就是︽瓦爾登湖︾了,於一八五四年出版。也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甚至還受到詹姆斯.洛厄爾以及羅勃特.路易士.斯蒂文生的譏諷和批評。但喬治.艾略特在一八五六年元月,卻在︽西敏寺週報︾︵Westminster Review︶上給他以﹁深沉而敏感的抒情﹂和﹁超凡入聖﹂的好評。那些自以為是的,只知道要按照他們的規範,來規規矩矩地生活的人,往往受不了他們毫不理解的事物的價值,自然要把梭羅的那種有歷史意義的行為,看作不切實際的幻夢虛妄了。
隨著時光的流逝,這本書的影響是越來越大,業已成為美國文學中的一本獨特的,卓越的名著。他一生所寫的三十九卷手稿,是他的日記或日誌,其中記錄著他的觀察、思維、理想和信念。他在世時的,在報刊上發表過的文章,他去世後已收集、整理好,出版了的計有︽旅行散記︾︵一八六三年,Excursions︶、︽緬因森林︾︵一八六四年,The Maine Woods︶、︽科德角︾︵一八六五年,CapeCo d︶三種。他的全集出版有︽梭羅文集︾,有一九○六年的和一九七一年的兩種版本。此外是他的日記,有︽梭羅:一個作家的日記︾、︽梭羅日記︾兩卷本、︽梭羅日記之心︾的精選本等。
以上只是梭羅生平的一個簡單的介紹。下面再說一點他的這本書。
對於︽瓦爾登湖︾,不須多說什麼,只是還要重複一下,這是一本寂寞、恬靜、智慧的書。其分析生活,批判習俗,有獨到處。
自然頗有一些難懂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說過,﹁請原諒我說話晦澀,﹂例如那失去的獵犬,栗色馬和斑鳩的寓言,愛默生的弟弟愛德華問過他是什麼意思。他反問:﹁你沒有失去嗎?﹂卻再也沒有回答了。有的評論家說,梭羅失去過一個艾倫︵斑鳩︶,一個約翰︵獵犬︶,可能還失去了一個拉爾夫︵栗色馬︶。誰個又能不失卻什麼呢?
本書內也有許多篇頁是形象描繪,優美細緻,像湖水的純潔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綠;有一些篇頁說理透徹,十分精闢,有啟發性。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書,至今還未失去它的意義。在白晝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時讀它還讀不進去,似乎我異常喜歡的這本書忽然又不那麼可愛可喜了,似乎覺得它什麼好處也沒有,甚至弄得將信將疑起來。可是黃昏以後,心情漸漸的寂寞和恬靜下來,再讀此書,則忽然又頗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處辨不出味道的章節,語語驚人,字字閃光,沁人心肺,動我衷腸。到了夜深人靜,萬籟無聲之時,這︽瓦爾登湖︾毫不晦澀,清澄見底,吟誦之下,不禁為之神往了。
應當指出,這本書是一本健康的書,對於春天,對於黎明,作了極其動人的描寫。讀著它,自然會體會到,一股向上的精神不斷地將讀者提升、提高。書已經擺在讀者面前了,我不必多說什麼了,因為說得再好,也比不上讀者直接去讀了。
人們常說,作家應當找一個僻靜幽雅的去處,去進行創作;信然,然而未必盡然。我反而認為,讀書確乎在需要一個幽靜良好的環境,尤其讀好書,需要的是能高度集中的精神條件。讀者最需要有一個樸素淡泊的心地。讀︽瓦爾登湖︾如果又能引起讀者跑到一個山明水秀的、未受污染的地方去的興趣,就在那樣的地方讀它,就更是相宜了。
梭羅的這本書近年在西方世界更獲得重視。嚴重污染使人們又嚮往瓦爾登湖和山林的澄淨的清新空氣。梭羅能從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這些生活之必需出發,以經濟作為本書的開篇,他崇尚實踐,含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
譯者曾得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先生暨夫人鼓勵;譯出後曾編入︽美國文學叢書︾,一九四九年出了第一版。一九八二年再版時,參考了香港吳明實的版本。譯文出版社在第二版的編審過程中,對譯文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校訂工作。對所有這些給過我幫助的人們,就在這裡,深致感謝。
目次
補充詩篇
我生活的地方;我為何生活
閱讀
聲
寂寞
訪客
種豆
村子
湖
倍克田莊
更高的規律
禽獸為鄰
室內的的取暖
舊居民;冬天的訪客
冬天的禽獸
冬天的湖
春天
結束語
書摘/試閱
我生活的地方;我為何生活
到達我們生命的某個時期,我們就習慣於把可以安家落戶的地方,一個個地加以考察了。正是這樣我把住所周圍一二十英里內的田園統統考察一遍。我在想像中已經接二連三地買下了那兒的所有田園,因為所有的田園都得要買下來,而且我都已經摸清它們的價格了。我步行到各個農民的田地上,嘗嘗他的野蘋果,和他談談稼穡,再又請他隨便開個什麼價錢,就照他開的價錢把它買下來,心裡卻想再以任何價錢把它押給他;甚至付給他一個更高的價錢,—把什麼都買下來,只不過沒有立契約,—而是把他的閒談當作他的契約,我這個人原來就很愛閒談,—我耕耘了那片田地,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我想,耕耘了他的心田,如是嘗夠了樂趣以後,我就揚長而去,好讓他繼續耕耘下去。這種經營,竟使我的朋友們當我是一個地產掮客。其實我是無論坐在哪裡,都能夠生活的,哪裡的風景都能相應地為我而發光。家宅者,不過是一個座位,—如果這個座位是在鄉間就更好些。我發現許多家宅的位置,似乎都是不容易很快加以改進的,有人會覺得它離村鎮太遠,但我覺得倒是村鎮離它太遠了點。我總說,很好,我可以在這裡住下;我就在那裡過一小時夏天的和冬天的生活;我看到那些歲月如何地奔馳,挨過了冬季,便迎來了新春。這一區域的未來居民,不管他們將要把房子造在哪裡,都可以肯定過去就有人住過那兒了。
只要一個下午就足夠把田地化為果園、樹林和牧場,並且決定門前應該留著哪些優美的橡樹或松樹,甚至於砍伐了的樹也都派定了最好的用場了;然後,我就由它去啦,好比休耕了一樣,一個人越是有許多事情能夠放得下,他越是富有。
我的想像卻跑得太遠了些,我甚至想到有幾處田園會拒絕我,不肯出售給我,—被拒絕正合我的心願呢,—我從來不肯讓實際的佔有這類事情灼傷過我的手指頭。幾乎已實際地佔有田園那一次,是我購置霍樂威爾那個地方的時候,都已經開始選好種子,找出了木料來,打算造一架手推車,來推動這事,或載之而他往了;可是在原來的主人正要給我一紙契約之前,他的妻子—每一個男人都有一個妻子的—發生了變卦,她要保持她的田產了,他就提出賠我十元錢,解除約定。現在說句老實話,我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角錢,假設我真的有一角錢的話,或者又有田園,又有十元,或有了所有的這一切,那我這點數學知識可就無法計算清楚了。不管怎樣,我退回了那十元錢,退還了那田園,因為這一次我已經做過頭了;應該說,我是很慷慨的囉,我按照我買進的價格,按原價再賣了給他,更因為他並不見得富有,還送了他十元,但保留了我的一角錢和種子,以及備而未用的獨輪車的木料。如此,我覺得我手面已很闊綽,而且這樣做無損於我的貧困。至於那地方的風景,我
卻也保留住了,後來我每年都得到豐收,卻不需要獨輪車來載走。關於風景,—
我勘察一切,像一個皇帝,
誰也不能夠否認我的權利。
我時常看到一個詩人,在欣賞了一片田園風景中的最珍貴部分之後,就揚長而去,那些固執的農夫還以為他拿走的僅只是幾枚野蘋果。詩人卻把他的田園押上了韻腳,而且多少年之後,農夫還不知道這回事,這麼一道最可羡慕的、肉眼不能見的籬笆已經把它圈了起來,還擠出了它的牛乳,去掉了奶油,把所有的奶油都拿走了,他只把去掉了奶油的奶水留給了農夫。
霍樂威爾田園的真正迷人之處,在我看是:它的遁隱之深,離開村子有兩英里,離開最近的鄰居有半英里,並且有一大片地把它和公路隔開了;它傍著河流,據它的主人說,由於這條河,而升起了霧,春天裡就不會再下霜了,這卻不在我心坎上;而且,它的田舍和棚屋帶有灰暗而殘敗的神色,加上零落的籬笆,好似在我和先前的居民之間,隔開了多少歲月;還有那蘋果樹,樹身已空,苔蘚滿布,兔子咬過,可見得我將會有什麼樣的一些鄰舍了;但最主要的還是那一度回憶,我早年就曾經溯河而上,那時節,這些屋宇藏在密密的紅色楓葉叢中,還記得我曾聽到過一頭家犬的吠聲。我急於將它購買下來,等不及那產業主搬走那些岩石,砍伐掉那些樹身已空的蘋果樹,剷除那些牧場中新近躍起的赤楊幼樹,一句話,等不及它的任何收拾了。為了享受前述的那些優點,我決定幹一下了;像那阿特拉斯①一樣,把世界放在我肩膀上好啦,—我從沒聽到過
他得了哪樣報酬,—我願意做一切事:簡直沒有別的動機或任何推託之辭,只等付清了款子,便佔有這個田園,再不受他人侵犯就行了;因為我知道我只要讓這片田園自生自展,它將要生展出我所企求的最豐美的收穫。但後來的結果已見上述。
所以,我所說的關於大規模的農事︵至今我一直在培育著一座園林︶,僅僅是我已經預備好了種子。許多人認為年代越久的種子越好。我不懷疑時間是能分別好和壞的,但到最後我真正播種了,我想我大約是不至於會失望的。可是我要告訴我的夥伴們,只說這一次,以後永遠不再說了:你們要盡可能長久地生活得自由,生活得並不執著才好。執迷於一座田園,和關在縣政府的監獄中,簡直沒有分別。
老卡托—他的︽鄉村篇︾是我的﹁啟蒙者﹂,曾經說過—可惜我見到的那本唯一的譯本把這一段話譯得一塌糊塗,—﹁當你想要買下一個田園的時候,你寧可在腦中多多地想著它,可決不要貪得無厭地買下它,更不要嫌麻煩而再不去看望它,也別以為繞著它兜了一個圈子就夠了。如果這是一個好田園,你去的次數越多你就越喜歡它。﹂我想我是不會貪得無厭地購買它的,我活多久,就去兜多久的圈子,死了之後,首先要葬在那裡。這樣才能使我終於更加喜歡它。
目前要寫的,是我的這一類實驗中其次的一個,我打算更詳細地描寫描寫;而為了便利起見,且把這兩年的經驗歸併為一年。我已經說過,我不預備寫一首沮喪的頌歌,可是我要像黎明時站在棲木上的金雞一樣,放聲啼叫,即使我這樣做只不過是為了喚醒我的鄰人罷了。
我第一天住在森林裡,就是說,白天在那裡,而且也在那裡過夜的那一天,湊巧得很,是一八四五年七月四日,獨立日,我的房子沒有蓋好,過冬還不行,只能勉強避避風雨,沒有灰泥墁,沒有煙囪,牆壁用的是飽經風雨的粗木板,縫隙很大,所以到晚上很是涼爽。筆直的、砍伐得來的、白色的間柱,新近才刨得平坦的門戶和窗框,使屋子具有清潔和通風的景象,特別在早晨,木料裡飽和著露水的時候,總使我幻想到午間大約會有一些甜蜜的樹膠從中滲出。這房間在我的想像中,一整天裡還將多少保持這個早晨的情調,這使我想起了上一年我曾遊覽過的一個山頂上的一所房屋。這是一所空氣好的、不塗灰泥的房屋,適宜於旅行的神仙在途中居住,那裡還適宜於仙女走動,曳裙而過。吹過我的屋脊的風,正如那掃蕩山脊而過的風,唱出斷斷續續的調子來,也許是天上人間的音樂片段。晨風永遠在吹,創世紀的詩篇至今還沒有中斷;可惜聽得到它的耳朵太少了。靈山只在大地的外部,處處都是。
除掉了一條小船之外,從前我曾經擁有的唯一屋宇,不過是一頂篷帳,夏天裡,我偶或帶了它出去郊遊,這頂篷帳現在已卷了起來,放在我的閣樓裡;只是那條小船,輾轉經過了幾個人的手,已經消隱於時間的溪流裡。如今我卻有了這更實際的避風雨的房屋,看來我活在這世間,已大有進步。這座屋宇雖然很單薄,卻是圍繞我的一種結晶了的東西,這一點立刻在建築者心上發生了作用。它富於暗示的作用,好像繪畫中的一幅素描。我不必跑出門去換空氣,因為屋子裡面的氣氛一點兒也沒有失去新鮮。坐在一扇門背後,幾乎和不坐在門裡面一樣,便是下大雨的天氣,亦如此。哈利梵薩②說過:﹁並無鳥雀巢居的房屋像未曾調味的燒肉。﹂寒舍卻並不如此,因為我發現我自己突然跟鳥雀做起鄰居來了;但不是我捕到了一隻鳥把它關起來,而是我把我自己關進了它們的鄰近一隻籠子裡。我不僅跟那些時常飛到花園和果樹園裡來的鳥雀彌形親近,而且跟那些更野性、更逗人驚詫的森林中的鳥雀親近了起來,它們從來沒有,就有也很難得,向村鎮上的人民唱出良宵的雅歌
的,—它們是畫眉,東部鶇鳥,紅色的磧,野麻雀,怪鴟和許多別的鳴禽。
我坐在一個小湖的湖岸上,離開康科特村子南面約一英里半,較康科特高出些,就在市鎮與林肯鄉之間那片浩瀚的森林中央,也在我們的唯一著名地區,康科特戰場之南的兩英里地;但因為我是低伏在森林下面的,而其餘的一切地區,都給森林掩蓋了,所以半英里之外的湖的對岸便成了我最遙遠的地平線。在第一個星期內,無論什麼時候我凝望著湖水,湖給我的印象都好像山裡的一泓龍潭,高高在山的一邊,它的底還比別的湖沼的水平面高了不少,以至日出的時候,我看到它脫去了夜晚的霧衣,它輕柔的粼波,或它波平如鏡的湖面,都漸漸地在這裡那裡呈現了,這時的霧,像幽靈偷偷地從每一個方向,退隱入森林中,又好像是一個夜間的秘密宗教集會散會了一樣。露水後來要懸掛在林梢,懸掛在山側,到第二天還一直不肯消失。
八月裡,在輕柔的斜風細雨暫停的時候,這小小的湖做我的鄰居,最為珍貴,那時水和空氣都完全平靜了,天空中卻密佈著烏雲,下午才過了一半卻已具備了一切黃昏的肅穆,而畫眉在四周唱歌,隔岸相聞。這樣的湖,再沒有比這時候更平靜的了;湖上的明淨的空氣自然很稀薄,而且給烏雲映得很黯淡了,湖水卻充滿了光明和倒影,成為一個下界的天空,更加值得珍視。從最近被伐木的附近一個峰頂上向南看,穿過小山間的巨大凹處,看得見隔湖的一幅愉快的圖景,那凹處正好形成湖岸,那兒兩座小山坡相傾斜而下,使人感覺到似有一條溪澗從山林穀中流下,但是,卻沒有溪澗。我是這樣地從近處的綠色山峰之間和之上,遠望一些蔚藍的地平線上的遠山或更高的山峰的。真的,踮起了足尖來,我可以望見西北角上更遠、更藍的山脈,這種藍顏色是天空的染料製造廠中最真實的出品,我還可以望見村鎮的一角。但是要換一個方向看的話,雖然我站得如此高,卻給郁茂的樹木圍住,什麼也看不透,看不到了。在鄰近,有一些流水真好,水有浮力,地就浮在上面了。
便是最小的井也有這一點值得推薦,當你窺望井底的時候,你發現大地並不是連綿的大陸;而是隔絕的孤島。這是很重要的,正如井水之能冷藏牛油。當我的目光從這一個山頂越過湖向薩德伯裡草原望過去的時候,在發大水的季節裡,我覺得草原升高了,大約是蒸騰的山谷中顯示出海市蜃樓的效果,它好像沉在水盆底下的一個天然鑄成的銅幣,湖之外的大地都好像薄薄的表皮,成了孤島,給小小一片橫亙的水波浮載著,我才被提醒,我居住的地方只不過是乾燥的土地。
雖然從我的門口望出去,風景範圍更狹隘,我卻一點不覺得它擁擠,更無被囚禁的感覺。盡夠我的想像力在那裡遊牧的了。矮橡樹叢生的高原升起在對岸,一直向西去的大平原和韃靼式的草原伸展開去,給所有的流浪人家一個廣闊的天地。當達摩達拉的牛羊群需要更大的新牧場時,他說過,﹁再沒有比自由地欣賞廣闊的地平線的人更快活的人了。﹂
時間和地點都已變換,我生活在更靠近了宇宙中的這些部分,更挨緊了歷史中最吸引我的那些時代。我生活的地方遙遠得跟天文家每晚觀察的太空一樣。我們慣於幻想,在天體的更遠更僻的一角,有著更稀罕、更愉快的地方,在仙後星座的椅子形狀的後面,遠遠地離了囂鬧和騷擾。我發現我的房屋位置正是這樣一個遁隱之處,它是終古常新的沒有受到污染的宇宙一部分。如果說,居住在這些部分,更靠近昴星團或畢星團,牽牛星座或天鷹星座更加值得的話,那末,我真正是住在那些地方的,至少是,就跟那些星座一樣遠離我拋在後面的人世,那些閃閃的小光,那些柔美的光線,傳給我最近的鄰居,只有在沒有月亮的夜間才能夠看得到。我所居住的便是創造物中那部分;—
曾有個牧羊人活在世上,
他的思想有高山那樣
崇高,在那裡他的羊群
每小時都給予他營養。
如果牧羊人的羊群老是走到比他的思想還要高的牧場上,我們會覺得他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每一個早晨都是一個愉快的邀請,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自己同樣地簡單,也許我可以說,同樣地純潔無瑕。我向曙光頂禮,忠誠如同希臘人。我起身很早,在湖中洗澡;這是個宗教意味的運動,我所做到的最好的一件事。據說在成湯王的浴盆上就刻著這樣的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③我懂得這個道理。黎明帶回來了英雄時代。在最早的黎明中,我坐著,門窗大開,一隻看不到也想像不到的蚊蟲在我的房中飛,它那微弱的吟聲都能感動我,就像我聽到了宣揚美名的金屬喇叭聲一樣。這是荷馬的一首安魂曲,空中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④,歌唱著它的憤怒與漂泊。此中大有宇宙本體之感;宣告著世界的無窮精力與生生不息,直到它被禁。黎明啊,一天之中最值得紀念的時節,是覺醒的時辰。那時候,我們的昏沉欲睡的感覺是最少的了;至少可有一小時之久,整日夜昏昏沉沉的官能大都要清醒起來。但是,如果我們並不是給我們自己的稟賦所喚醒,而是給什麼僕人機械地用肘子推醒的;如果並不是由我們內心的新生力量和內心的要求來喚醒我們,既沒有那空中的芳香,也沒有回蕩的天籟的音樂,而是工廠的汽笛喚醒了我們的,—如果我們醒時,並沒有比睡前有了更崇高的生命,那末這樣的白天,即便能稱之為白天,也不會有什麼希望可言;要知道,黑暗可以產生這樣的好果子,黑暗是可以證明它自己的功能並不下於白晝的。一個人如果不能相信每一天都有一個比他褻瀆過的更早、更神聖的曙光時辰,他一定是已經對於生命失望的了,正在摸索著一條降入黑暗去的道路。感官的生活在休息了一夜之後,人的靈魂,或者就說是人的官能吧,每天都重新精力彌漫一次,而他的稟賦又可以去試探他能完成何等崇高的生活了。可以紀念的一切事,我敢說,都在黎明時間的氛圍中發生。︽吠陀經︾⑤說:﹁一切知,俱於黎明中醒。﹂詩歌與藝術,人類行為中最美麗最值得紀念的事都出發於這一個時刻。
所有的詩人和英雄都像曼儂,那曙光之神的兒子,在日出時他播送豎琴音樂。以富於彈性的和精力充沛的思想追隨著太陽步伐的人,白晝對於他便是一個永恆的黎明。這和時鐘的鳴聲不相干,也不用管人們是什麼態度,在從事什麼勞動。早晨是我醒來時內心有黎明感覺的一個時候。改良德性就是為了把昏沉的睡眠拋棄。人們如果不是在渾渾噩噩地睡覺,那為什麼他們回顧每一天的時候要說得這麼可憐呢?他們都是精明人嘛。如果他們沒有給昏睡所征服,他們是可以幹成一些事的。幾百萬人清醒得足以從事體力勞動;但是一百萬人中,只有一個人才清醒得足以有效地服役於智慧;一億人中,才能有一個人,生活得詩意而神聖。清醒就是生活。我還沒有遇到過一個非常清醒的人。要是見到了他,我怎敢凝視他呢?
我們必須學會再蘇醒,更須學會保持清醒而不再昏睡,但不能用機械的方法,而應寄託無窮的期望於黎明,就在最沉的沉睡中,黎明也不會拋棄我們的。我沒有看到過更使人振奮的事實了,人類無疑是有能力來有意識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能畫出某一張畫,雕塑出某一個肖像,美化某幾個物件,是很了不起的;但更加榮耀的事是能夠塑造或畫出那種氛圍與媒介來,從中能使我們發現,而且能使我們正當地有所為。能影響當代的本質的,是最高的藝術。每人都應該把最崇高的和緊急時刻內他所考慮到的做到,使他的生命配得上他所想的,甚至小節上也配得上。如果我們拒絕了,或者說虛耗了我們得到的這一點微不足道的思想,神示自會清清楚楚地把如何做到這一點告訴我們的。
我到林中去,因為我希望謹慎地生活,只面對生活的基本事實,看看我是否學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東西,免得到了臨死的時候,才發現我根本就沒有生活過。我不希望度過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這樣的可愛;我卻也不願意去修行過隱逸的生活,除非是萬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穩穩當當,生活得斯巴達式的⑥,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東西,劃出一塊刈割的面積來,細細地刈割或修剪,把生活壓縮到一個角隅裡去,把它縮小到最低的條件中,如果它被證明是卑微的,那末就把那真正的卑微全部認識到,並把它的卑微之處公佈於世界;或者,如果它是崇高的,就用切身的經歷來體會它,在我下一次遠遊時,也可以作出一個真實的報導。因為,我看,大多數人還確定不了他們的生活是屬於魔鬼的,還是屬於上帝的呢,然而又多少有點輕率地下了判斷,認為人生的主要目標是﹁歸榮耀於神,並永遠從神那裡得到喜
悅﹂。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