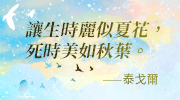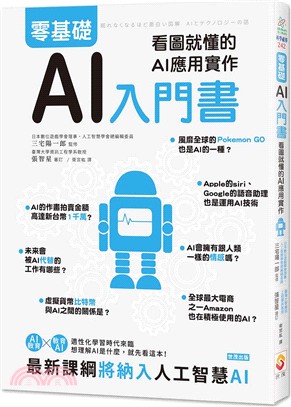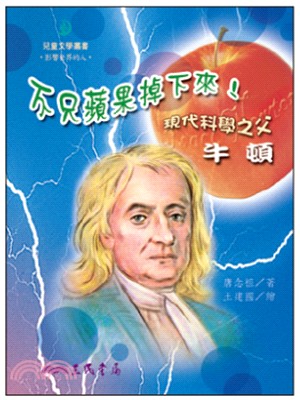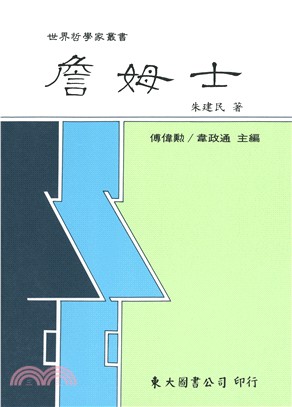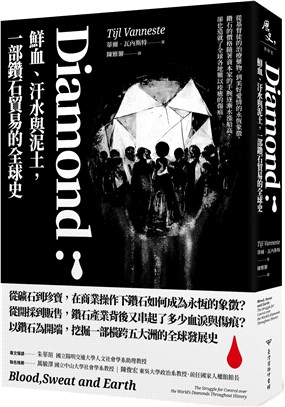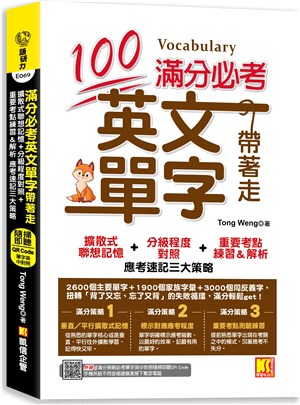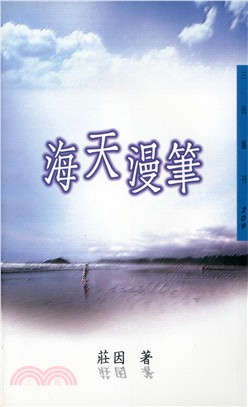人民幣定價:160.00 元
定價
:NT$ 960 元優惠價
:87 折 835 元
絕版無法訂購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商品簡介
本書的出發點是中國土地和人口關係的演變,因為這是中國農業生產的給定基本條件。對明清以來到當代的演變,無論是“資本”還是現代科技投入,無論是財產制度和相關法律,還是社會結構或市場關係,都不能脫離土地-人口關係基本條件的背景來理解。改革時期的農業去集體化和家庭化以及市場化演變也同樣如此。這絕對不是要單獨突出人口為單一的決定性因素,而是要澄清人口與土地間的給定“基本國情”,由此分析這與其他生產要素、制度和社會演變之間的關係。
本書的特點之一是通過翔實的關於基層小農場運作的經濟人類學資料來分析並說明其生產邏輯。這是一個由微觀的生產實踐來說明宏觀的經濟邏輯的研究進路和方法,由此展示它和現代工業經濟的不同。本書所試圖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家庭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在歷史上到底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今天又如何?這方面,中國與現代西方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其前景又如何?
在認識論層面上,筆者一直有意識地擺脫意識形態化的理論先行研究,而採用從經驗證據出發,由此提煉概念,而後再返回到經驗證據的研究進路。目的是試圖掌握一個題目最基本的事實,然後借助與現有理論的對話來提煉自己的概念。這和當前流行的從理論到經驗,再到理論的做法正好相反。
本書的特點之一是通過翔實的關於基層小農場運作的經濟人類學資料來分析並說明其生產邏輯。這是一個由微觀的生產實踐來說明宏觀的經濟邏輯的研究進路和方法,由此展示它和現代工業經濟的不同。本書所試圖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家庭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在歷史上到底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今天又如何?這方面,中國與現代西方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其前景又如何?
在認識論層面上,筆者一直有意識地擺脫意識形態化的理論先行研究,而採用從經驗證據出發,由此提煉概念,而後再返回到經驗證據的研究進路。目的是試圖掌握一個題目最基本的事實,然後借助與現有理論的對話來提煉自己的概念。這和當前流行的從理論到經驗,再到理論的做法正好相反。
作者簡介
黃宗智
1940年生,著名歷史學家。普林斯頓大學學士,華盛頓大學博士。師從著名學者蕭公權教授。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歷史系教授,1991年晉升"超級教授"(Professor, Above Scale),2004年榮休。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主任(1986- 1995年)。Modern China(《近代中國》)創刊編輯(1975年至今)。《中國鄉村研究》(Rural China)創刊編輯(2003年至今)。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主要學術興趣為明清以來的社會史、經濟史和法律史。主要著作有:《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法典、習俗與司法實踐:清代與民國的比較》 《過去和現在:中國民事法律實踐的探索》 《經驗與理論: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實踐歷史研究》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最佳著作獎)《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最佳著作獎) 等。
1940年生,著名歷史學家。普林斯頓大學學士,華盛頓大學博士。師從著名學者蕭公權教授。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歷史系教授,1991年晉升"超級教授"(Professor, Above Scale),2004年榮休。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主任(1986- 1995年)。Modern China(《近代中國》)創刊編輯(1975年至今)。《中國鄉村研究》(Rural China)創刊編輯(2003年至今)。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主要學術興趣為明清以來的社會史、經濟史和法律史。主要著作有:《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法典、習俗與司法實踐:清代與民國的比較》 《過去和現在:中國民事法律實踐的探索》 《經驗與理論: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實踐歷史研究》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最佳著作獎)《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最佳著作獎) 等。
名人/編輯推薦
編輯推薦
黃宗智教授關於中國鄉村問題思考的集大成之作,也代表了海外漢學家研究中國鄉村問題的最高水準。
本書所試圖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家庭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在歷史上到底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今天又如何?這方面,中國與現代西方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其前景又如何?
名人推薦
黃宗智教授關於中國鄉村問題思考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海外漢學家研究中國鄉村問題的最高水準。
黃宗智教授關於中國鄉村問題思考的集大成之作,也代表了海外漢學家研究中國鄉村問題的最高水準。
本書所試圖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家庭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在歷史上到底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今天又如何?這方面,中國與現代西方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其前景又如何?
名人推薦
黃宗智教授關於中國鄉村問題思考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海外漢學家研究中國鄉村問題的最高水準。
序
總序
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
歷史、理論與現實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未經明言的基本假設是: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和單位產出都可以大幅度擴大。同時,假設這些要素都像機械世界中那樣分別存在,相互間處於一種單一方向的推、拉關係之中。如此的基本假設當然源自機械世界的工業經濟經驗,但今天被相當普遍應用於農業經濟。
一、農業和工業經濟的不同
實際上,農業中的有機要素——土地和勞力——其產出的可能擴大和提高幅度是和工業經濟中的無機要素——資本和科技投入——十分不同的。人力和土地的產出和總量其實都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前工業化的農業產出必須主要取決於給定的土地和在其上的人力投入。固然,在未經人們定居的地方,單位土地面積上所施加的勞力可以在長時期中加大不少,甚至達到四五十倍之多。正如農業理論家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 1965)指出,農業演變的主要歷程是從20年到25年一茬的森林刀耕火種到6年到10年一茬的灌木刀耕火種,到三年兩茬的“短期休耕”,再到一年一茬、兩茬的耕作制度(部分地區可以達到三茬)。但是,我們需要指出,刀耕火種大多只見於人類早期的農業歷史之中。一旦充分定居,一個區域農業生產的提高一般都主要來自從一年一茬提高到一年兩茬,其產出提高的幅度不到一倍。在種植頻率之外,每一茬所施加的人力和能量可以通過使用牲畜的力量來提高(例如在18世紀的英國農業革命中那樣),但充其量也不過是幾倍的幅度。再則是通過人的勤奮度——精耕細作——來提高其能量投入,或從比較粗放的作物(如糧食)改種勞動更密集化的作物(如蔬菜、棉花、蠶桑),但其產出所可能提高的幅度也比較有限。
正如英國經濟史理論家瑞格裡指出,“基於礦物能源”(mineralbased energy economy)的無機工業經濟則十分不同。一個煤礦工人一年可以挖掘200噸的煤炭,足夠產生自己個人勞力許多倍的能量(E. Anthony Wrigley 1988:77)。人們今天普遍使用以幾百馬力來計算的汽車能量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瑞格裡估算,1馬力/小時大約相當於5.1~7.6個人的人力(Wrigley 1988: 39)。也就是說,一輛普通轎車的能量可以輕易達到不止1000人的人力。這就意味著在生產的能量投入上有完全不同幅度的可能擴大量。正是後者的基本情況和邏輯塑造了現代經濟學這方面的認識和假設。但是,作為“有機經濟”的農業,則完全不可能如此。
這裡,有的讀者也許會反駁,一旦引入機械,農業不是變成和工業同樣的產業嗎?比如,在美國今天的農業中,一個勞動力耕種百倍甚或數百倍於中國的一個農業勞動力,用的是機械化的耕—播—收和自動灌溉、施肥、除草等。今天美國農業和中國農業間的差別是1000多畝地(166.7英畝)一個勞動力對不到10畝地一個勞動力。難道這不正是單位勞動力產出可以大規模提高的很好例證嗎?
但如此的論證所忽視的是土地這個有機因素。首先,土地常常是個限定的要素,尤其是在中國這樣的農業早發展、高人口密度國家。中國老早就在各大江河流域形成高度勞動密集的耕作制度,而在14~18世紀則更多移民進入山地和邊疆,達到基本飽和的程度。之後,中國便進入了多個世紀的土地與人口比例逐步遞減的歷史進程。
更重要的是,土地是個有機因素。這裡最管用的其實是一個在中國(今天已經被現代經濟學所遺忘的)農學和農史領域中長期被廣泛使用的概念——“地力”。這是個與“人力”並行以及相互關聯的概念。正如中國的農學和農史專家所非常清楚地認識到,地力只能被小額擴增——比如,通過精耕細作或肥料使用來提高。即便如此,在同一塊土地上加多一茬便意味著加重了地力的負擔,而多施肥料或用更好的肥料只能解決問題的局部,譬如,明清時代長江三角洲在人、畜肥之上使用豆餅肥料來增加土地的營養和力氣。
地力和人力概念其實清楚地說明了人們對它們作為有機體的認識 而機械的“馬力”概念則混淆了無機和有機體,反映的是前工業世界對工業世界在話語層面上的影響。——一個相當普遍被現代經濟學所忽視的基本認識。中國農業史中廣泛使用的諸如“田面”和“田底”那樣的詞彙只能作為隱喻來理解,絕對不能機械地來理解——譬如,按照現代工業經濟學和現代法律的傾向那樣,要求明確“田面”權所指到底是多少尺寸的深度?農民會直覺地把“田面”理解為類似於人體的有機體,不會無稽地要求知道其深入人體皮膚多少。“一田兩主”的概念同樣不可憑現代人的意識來要求明確其具體深度。
在歷史上充分定居的地方,單位土地產出只能通過勞動集約化,如種植頻率的提高,或精耕細作,或灌溉設施,或肥料投入等方法來提高。但那樣只能做到逐年小額的提高,充其量在數個世紀之中達到幾倍的增長幅度。正如珀金斯(Dwight Perkins 1969)的計量研究所證實,在1368年到1968年六個世紀中,中國人口增加了約七到九倍,而農業平均畝產量提高了才約一倍(而耕地——由於山區和邊疆移民——擴增了約四倍,共同把農業總產出提高到之前的八九倍)。
這裡,我們也可以18世紀英國的農業革命為例。當時其土地對人口的比例約百倍於中國,在一個世紀之中,農業產出提高了約一倍,亦即0.72%/年,主要是人們通過配合畜力的使用和諾福克糧食和飼料的輪種制度(在圈地之前,農民不可能在共有土地上如此輪作)。再則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所謂“綠色革命”,即通過化肥、機械和科學選種等現代投入做到單位土地年產出2%~4%的提高,亦即在18年到36年期間提高一倍,之後便不容易持續提高。如此的增長顯然低於人們所廣泛假設工業和“現代經濟”所能達到的幅度。
正是人力—地力關係的局限約束了前工業時代中國農業經濟的發展,而即便是在工業時代,在具有現代投入的條件之下,也主要是土地和地力的限度約束了土地的產出,由此限制了農業單位勞動力的可能產出。這一點最簡潔、精確的表述其實是人們慣常用的“人多地少”概念,十分恰當地被認作中國的“基本國情”(而18世紀的英格蘭和現代的美國則可以代表相對“地多人少”的情況)。今天,它仍然限制了務農人員的可能人均產出。機械、化肥和科學選種固然擴大了中國農業發展的空間,但那個空間仍然受到土地(相對人口)稀少和地力有限的苛刻限制。
地少人多排除了像美國農業那樣簡單憑藉機械動力的投入來大規模提高單位勞動力產出,而地力的限制則嚴格限制了單位土地的產出。前者在美國和中國農業間的差別十分懸殊,達到百倍的幅度,而後者則中國高於美國,雖然只是不到一倍。這樣的事實本身便說明地力的可能提高幅度十分有限——它是個自然界的約束。同理,正是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排除了其採用美國的土地集約型農業模式的可能。事實是,中國農業不可能根據來自工業經濟經驗的假設來理解。農業的有機要素(人力和地力)和工業的無機要素(資本和科技投入)的不同關鍵在於它們的產出和絕對量的可能擴大幅度。
同時,人力和地力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雙向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決定的有機關係,而不是無機要素之間那樣的單向的推與拉的機械關係。人多地少的基本條件既決定了中國農業的人力使用模式,也決定了其土地使用模式,共同導致了中國的精耕細作農業模式。人力和地力之間的關係類似於一個“生態系統”之內的雙向互動關係,其中任何一個“要素”的演變都會帶動其他組成部分相應的演變,正如吉爾茨在他早期的“農業內卷化”書中所闡明的那樣(Geertz 1963)。人力和地力不能夠像無機體間的機械關係那樣分開來理解,因為農業說到底是人在土地上生長植物的有機問題,不是一個機器生產的無機問題。
這裡要對博塞拉普的理論作進一步的討論。她敏銳地說明了人口壓力必然會推動土地使用的勞動密集化,但她所沒有充分說明的是,土地生長作物的“地力”受到不可逾越的限制。在人類的農業史中,種植頻率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年三茬。如果人少地多,人們可以借助使用更多的土地來提高單位勞動力的產出,其道理等於是把博塞拉普的模式倒過來理解。但是,在人多地少的給定情況下,單位土地和勞動力的產出都受到不可逾越的限制。單位土地不可能超越一年三茬,而每茬作物所能夠有效吸納的勞動力投入同樣有一定的限制,不可避免的是邊際報酬遞減的限制,並且顯然具有一定的“極限”。 裴小林2008特別突出土地“極限”的問題。
瑞格裡把這個道理表述為“有機”經濟的能源方面的限制,很好地說明了有機(農業)和無機(現代工業)經濟之間在能源生產(和投入)方面的一個關鍵差別,但瑞格裡沒有明確說明的是,有機經濟這方面的約束主要來自人力和地力在生長作物過程中相互間所形成的限制。地多人少的話,所受到的限制來自人力,其可能擴大幅度十分有限;地少人多的話,所受的限制則來自地力,其可能擴大幅度同樣十分有限。人力和地力由此相互決定了農業產出的限制。人力和地力與資本和技術在這方面的不同才是有機和無機經濟間不同的關鍵。
正是上述的基本約束突出了“邊際報酬遞減”的經濟規律。在人多地少和土地的自然生產力有限的現實下,單位土地面積上越來越多的人力投入只可能導致其邊際報酬的遞減,與地多人少的農業環境十分不同。從一年一茬到兩茬,甚或三茬,每茬產出(相對投入)的遞減便是最好的例證。同時,通過比耕作更高度勞動密集的手工業“副業”(另一個十分貼切的普通用詞)來輔助小規模農業生產的不足,也是一個好的例證。中國農民這種同時依賴不止一種生產活動來支撐生活的特徵一直持續至今,與西方相對地多人少的農業系統十分不同。這就是本書之所謂的農業“內卷化”或“過密化”。
我們需要從以上的角度來理解恰亞諾夫所指出的(小農經濟)農業的特徵,即其基本生產單位是家庭而不是工業經濟那樣的個體化產業工人,而同時,小農家庭既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一個消費單位,和僅是一個生產單位的資本主義企業十分不同(Chayanov 1986[1925])。在依據工業經濟經驗的經濟學占霸權地位的今天,這些特徵很容易被忽視。作為一個消費單位,家庭農場的經濟行為不僅取決於生產考慮,也取決於消費需要。正是單位土地的地力,相應勞動力投入的邊際報酬遞減,說明了恰氏打出的基本理論:農戶在單位土地上的勞動力投入取決於其勞動力邊際產出的“辛苦度”和家庭消費邊際需要間的平衡。據此,恰氏更進而考慮到農業與手工業間的關係,以及農業與人口壓力間的關係。
在這些方面上,本書《華北》和《長江》兩卷有比較詳細的說明。拙作的特點之一是通過翔實的關於基層小農場運作的經濟人類學資料來分析並說明其生產邏輯。這是一個由微觀的生產實踐來說明宏觀的經濟邏輯的研究進路和方法,由此來展示它和現代工業經濟的不同。
《華北》卷論證,清代後期以來冀—魯西北平原地區足足有一半以上農戶(“貧農”)的農場規模在十畝以下,因此農業中的“就業不足”問題嚴重,必須同時依賴(農業)打工或家庭手工業來輔助、支撐生活。《長江》卷則論證,長江三角洲土地更少(雖然其地力比華北相對較高),更高度依賴手工副業,也更高度商業化。但是,兩個地區的貧農扶著農業—打工/手工業兩炳拐杖來支撐生活的基本原則是一樣的。而這樣的手工業與農業緊密結合的經濟組織,由於其所依賴的勞動力比雇用長工的經營式農業來得“便宜”,能夠支撐更高的地租和地價,並因此在長江三角洲排除了(明清之際還相當普遍的依賴雇傭勞動的)經營式農業。
以上說明的經驗證據和其所包含的道理是本書之所以挑戰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 1964;1979)著作的原因。他堅持農業和工業是由同樣的經濟規律所主宰,並假設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是同樣性質的,其總量和產出幾乎可以無限制擴大。同時,由於他認為市場機制必定會導致最佳的資源配置,他認為人口過剩(也就是說,土地相對人口的嚴重不足)不可能存在,完全沒有認識到人—地關係乃是農業的先決條件。
同時,他單獨突出“人力資本”,堅持只要具備前提性的私有產權和市場機制,加上“綠色革命”那樣的現代技術投入,便必定會推動、導致“傳統農業的改造”。像他那樣把有機的“人力”和無機的“資本”兩個概念混淆起來使用於農業,本身便是對有機體和無機體的基本差異的忽視。農業絕對不應該被等同於無機工業產業,不應該被簡單地以基於工業經驗的假設的經濟學的“規律”來理解。中國農業不可能像在美國的地多人少基本條件之下,借助市場機制,通過資本和技術的投入,幾乎無限制地提高單位勞動產出。
回顧中國的經濟歷史,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之前的六個世紀中,農業相當高度商業化,但是市場機制的擴延從來沒有解決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問題。在20世紀上半期,引入現代投入,依然沒有解決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後,在集體化下更多地引入現代投入,同樣沒有解決問題。本書第三卷詳細論證,即便是中國今天的農業,仍然強烈地受到人口—土地關係的影響,完全不同于舒爾茨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所想像的那樣。
正是由於上述原因,本書的出發點是中國土地和人口關係的演變,因為它是中國農業生產的給定基本條件。對明清以來到當代的演變,無論是“資本”還是現代科技投入,還是財產制度和相關法律,或社會結構,或市場關係,都不能脫離土地—人口關係基本條件的背景來理解。改革時期的農業去集體化和家庭化以及市場化演變也同樣。這絕對不是要單獨突出人口為單一的決定性因素,而是要澄清人口與土地間的給定“基本國情”,由此來分析其與其他生產要素和制度和社會演變之間的關係。
這裡要進一步說明,本書也絕對不是要否認市場經濟在改革時期所起的作用,因為它確實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筆者所突出的市場作用是完全出於舒爾茨視野之外的。首先,舒爾茨完全沒有考慮到的人民消費轉型。具體來說,人們的收入,尤其是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加,導致中國食物消費的基本轉型,從8∶1∶1的糧食∶肉/魚∶蔬菜/水果的比例向4∶3∶3轉化,而那樣的市場需求則促使中國農業結構的轉化,導致近二十年中的一個(我稱之為)“隱性農業革命”,促使中國農業生產轉向越來越高比例的高值農產品——即從糧食轉向更多更高值的蔬菜和肉食生產。這是一個比之前歷史上的農業革命,例如18世紀的英國農業革命和20世紀六七十年代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綠色革命,增加幅度要大的革命,在最近20年達到每年6%產值(可比價格)增長的幅度。正如我在書中所強調,市場機制所起的強大作用是無可否認的,但其所導致的農業革命的肇因是完全不同于舒爾茨所提倡和想像的“綠色革命”。
同時,今天中國土地—人口的有機關係仍然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它排除了美國那樣簡單的土地、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農業;小規模家庭農業將長期佔據中國農業的主體地位。中國農業的基本生產單位仍然將是最多幾個英畝的家庭農場,其農場的規模迥異于舒爾茨的想像。它們固然越來越多的是(我稱之為)“資本和勞動雙密集化”的小規模農場(例如,拱棚蔬菜、種養結合的小農場,果園、魚塘等,它們比“舊農業”使用更多的化肥、農藥、塑膠棚和塑膠膜、人工飼料等)。這些(我稱之為)“新時代的小農場”同樣需要從中國人多地少的給定條件,以及有機的土地—人口關係來理解。
拙作論證的是,把農業想像為一個和工業產業同樣性質的“產業”並服從同樣的經濟學“規律”,其實是個無稽的想像。
把農業想像為一種(無機工業)產業,
首先是對農業的誤解,它無視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這等於無視中國經濟歷史。那樣的想像其實也是一個源自現代主義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它最終想像的中國農業是,或者認為應該是,和美國的一樣。那是對中國農業史和經濟史錯誤的認識,也是對中國現實錯誤的判斷。更要命的是,它提倡的是個錯誤的改革方案,想像的是大規模農場的規模效益,而不是小規模農場的給定條件和效益。
令人特別擔憂的是,上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整套理論今天居然已經成為中國的“現代經濟學”的“主流”,其中也包括農業經濟學。這也是作者在這裡如此帶有緊迫感和使命感地提出對其批評的原因。
二、中國的非正規經濟
中國的人口—土地關係不僅是中國農業的先決條件,也是中國國民經濟整體的先決條件,在改革時期尤其如此。全球資本進入中國以及中國本土資本主義企業的興起,使中國也呈現出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半個多世紀以來早已普遍存在的現象,即農村廉價勞動力大規模湧入城鎮打工。從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的角度來看,這正是其所需要的廉價勞動力,也是其跨國公司普遍進行“外包”(outsourcing)的緣由。從農村勞動力的視角來看,它帶來的是受歡迎的較高報酬的就業機會。
兩者的結合在全球範圍內帶來的是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稱作“非正規經濟”的大規模興起。1969年,ILO因其為全球“非正規經濟”人員爭取“有尊嚴的待遇”而獲諾貝爾和平獎。正因為農村具有“無限的勞動力供應”(W. Arthur Lewis 1954,1955),資本可以用(相對)最低的工資、最壞的工作環境、最低等的(或根本就沒有)福利來雇用工人,無論當地勞動法規如何。從資本的視角來看,這完全是市場經濟的客觀供需規律所使然——當然也正好偏向資本。而從當地政權的視角來看,外來資本的湧入意味著在本地的投資和其所帶來的“經濟發展”,為此相當普遍被認為是優先于工人生活狀況和社會公正的事。正是這樣,促使無視當地法規的“非正規經濟”快速興起和擴增。因此, ILO對“非正規經濟”的基本定義正是:沒有法律保護和沒有福利的經濟,並呼籲為非正規經濟人員爭取法律的保護和有尊嚴的待遇。事實上,半個世紀以來,在全世界各地發展中國家,非正規經濟已擴展到城鎮總就業人數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甚或更多(ILO 2002)。在中國的後計劃經濟時代,與印度和印尼等較高人口密度國家相似,非正規經濟員工已經達到城鎮就業人員總數的三分之二的比例。
但是,由於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和土地承包制度,今天中國絕大多數的“工人”不是城鎮居民而仍然是農村戶籍的農民。一方面,由於戶籍制度他們很難成為城鎮的合法居民。同時城鄉生活水準的差距也妨礙大多數的農民工在城市買房長期居留。另一方面,由於承包地的地權,農村對他們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在城鎮打工的農民不會像在其他國家那樣完全脫離農村,而是形成了一個跨城鄉的、具有一定“中國特色”的結合務工和務農的龐大群體。
今天,傳統的城鎮工業“工人”和農村務農“農民”這兩個人們慣用的範疇已經不再適用於中國。這是因為大多數的城鎮工人已經不再是城鎮居民而是農村戶籍人民;同時,大多數的農民家庭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務農人員,而是同時務農和務工(以及其他非農就業)的人員。本書第三卷詳細論證,在今天的中國,幾乎每一戶所謂的農民都有人在外打工。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家庭主要是緊密結合工業(和其他非農就業)與農業的“半工半耕”人員。在我看來,我們不應該像國際勞工組織那樣把“非正規經濟”範疇限定於城鎮,而應該把中國的半工半耕勞動人民也計算在非正規經濟範疇之內。那樣,可以避免不符合實際的、具有嚴重誤導性的傳統“城鎮”和“鄉村”以及“工人”和“農民”的劃分,更好地突出今天中國社會經濟的實際和特點。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的非正規經濟是和社會主義革命傳統的勞動立法和制度並存的,在這點上也和大部分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有一定的不同。中國共產黨是以勞動人民——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先鋒隊名義取得勝利的。一旦掌權,革命的共產黨成為了執政的共產黨,而工人則從革命階級轉化為“領導階級”。因此,工人順理成章地和國家黨政官員一起被納入國家正規“職工”的範疇,受到革命勞工運動所爭得的勞動法律的一系列保護和保障,包括有尊嚴的工資待遇、安全的工作環境、合理的工作時間、超額工作的成倍報酬以及各種福利——醫療、退休、失業、工傷、生育。但是,今天具有如此待遇的 “藍領”工人不過是全部勞動人民中的很少數。他們實際上和國家黨政官員以及大企業白領職工一起形成一個正規經濟身份的特權階層。這是作者第三卷中最新的探索所論證的要點,也是作者研究中最直接連接經濟和法律兩大領域的論點(相關討論亦見筆者新版的法律三卷本最後的“進一步的探索”)。
吊詭的是,這個源自革命傳統的現實使中國的正規和非正規經濟之間的差別比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傳統的國家更加懸殊。今天,處於非正規經濟範疇的大多數勞動人民被排除在法定的正規“勞動關係”之外,被歸入不受勞動法律保護的非正規“勞務關係”範疇之下。今天回顧,國家早在1958年1月便開始執行的嚴格戶籍制度(當時是為了限制農民大規模湧入城市而造成混亂),後來實際上成為一個把占少數的正規職工和占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劃分為兩個壁壘森嚴的等級。今天勞動法規已經幾乎完全成為衛護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的法律制度。
中國正規和非正規經濟間的差別不僅是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差別,也是法定身份的差別。今天,除了頂層的國家官員和大企業家之外,中國社會的上層實際上是占所有就業人員中的16.8%的正規經濟,其半數是國家黨政機構和事業單位以及國營企業的人員,半數是較大的民營企業的職工。他們是所謂的“中產階級”的大多數,其生活方式正日益向全球的中產階級消費者趨同——包括在房子、傢俱、汽車、食物消費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另一邊則是底層的、占83.2%的非正規工—農勞動人民。他們承擔的是最低報酬的工作,絕大多數沒有勞動法律的保護也基本沒有(或只有低等的)社會福利。
兩者間差別的一個具體表現是,在交通事故導致死亡的情況下,農村戶籍人的補償標準是8萬元到10萬元,而城市戶籍的則是20萬元到30萬元。更有甚者,在國家2009年以來建立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下,一個60歲以上的農民每個月可以拿到55元,而一個公務員的退休金則約6000元。 “養老金雙軌制被指為最大不公:公務員6千農民55元”,載《經濟觀察報》2013年5月3日。農村戶籍的半工半農人民無疑是一種二等公民,其身份地位不僅遠低於國家官員和大型企業的“白領”職員,也遠低於一般的市民。
以上敘述的經驗事實都明顯與主流經濟學家們的意見不相符。他們根據所謂的“路易斯拐點理論”而堅持中國今天已經從一個“二元經濟”(一“元”是具有“無限勞動力供應”的“傳統農業”部門,另一元是城市的“現代經濟”部門)進入一個完全整合的、沒有城鄉差別的勞動力市場的經濟體系。一組具有很大影響力的人口學—經濟學家幾年前便已開始堅持這個論點,完全無視低工資—低福利的非正規經濟和高工資—高福利的正規經濟間的顯著差別。實際上,兩者間的差別非但沒有像“路易斯拐點理論”預期的那樣伴隨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快速增長而消失,反而是日益懸殊。世界銀行等國際單位歷年估算的基尼係數便是很好的證據。與“拐點論”類似,新自由主義社會學家們則採用了來自美國的“中產階層”和“橄欖型”社會理論,爭論中國社會的結構已經類似於美國的中產階層占到全社會大多數的模型,完全無視中國社會貧富懸殊的實際。本書第三卷比較詳細地討論了上述情況和問題的方方面面。
從經濟史的視角來看,中國兩大社會經濟等級—階層間的差別的最終根源還是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今天中國農業仍然處於人均不到10畝以及土地生產力的嚴格限度的小規模經營的苛刻約束之下。農業中的“隱性失業”和勞動力就業不足因此仍然存在。近年來的“隱性農業革命”,固然(像本書詳細論證的那樣)通過勞動和資本雙密集化的小規模新農業吸納了更多的勞動力,因此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同時,農民在城鎮和農村的非農就業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正規與非正規經濟間的懸殊待遇,以及城市比農村的更快速發展,使農村依然日益落後於城市,也使測量中國分配不公程度的基尼係數大幅度攀升。
從改革時期的經濟歷史來看,中國在GDP增長方面的成功和其嚴重的社會不公問題顯然是來自同一根源的。正是中國龐大的廉價農村勞動力使其得以成為“世界的工廠”;同時,也正是這個勞動力的低等待遇導致中國嚴峻的社會不公以及當前的社會危機。
從更長遠的歷史視角來看,中國的小規模勞動密集型農業既是傳統中國特早的城市發展的來源,也是其18世紀以來大規模農村貧困和社會不公的根源。中國在江河流域早已形成的高密度小規模農業正是中國大型複雜城市(和輝煌的城市文化)興起的先決條件。正如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 1981)的另一理論洞見指出,在前現代的物流條件(沒有冷藏設備和現代運輸條件)下,食物供應被限定於一定的較小空間範圍。一個同一面積的地區,如果有1000萬人口,即便其生產剩餘相對低(譬如10%),仍然能夠支撐一個100萬人的城市(如唐代的長安),而同一面積的地方,如果只有100萬人口,即便其生產剩餘相對高(譬如30%),只能支撐一個30萬人口的城市(如中世紀的倫敦)。同時,(勞動密集的)小規模農業,以及其所導致的勞動生產率遞減,乃是城鄉差別的根源。它也是現代中國革命的主要導因。
今天的社會不公其實和歷史上的城鄉差別有一定的關聯。明清以來農村農戶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下,長期結合農業+(農業)打工和手工業的生產方式來應付生存壓力。改革以來,農村農戶根據同樣的邏輯,越來越多地依賴農業和工業打工來支撐家庭開銷。今天,城市中16.8%的正規經濟的“中產階級”和城鄉83.2%的相對貧困非正規經濟間的差別,歸根到底也和中國的人多地少的基本農村國情相關。
當前,貧富不均是一個亟須緊急處理的問題。為此,本書也初步探討了一個地方,在中央的直接指示下,通過實驗所突出的統籌城鄉方案。它在處理農民工問題方面已經探尋出一些可行的措施,但在農村本身方面則尚需繼續探索。
三、一個不同的探索方法
在多年的農村研究中,筆者曾多次向自己提問:當下流行的意見為什麼會對上列的基本事實視而不見?我們需要怎樣來改正這樣的盲點和誤區?
意識形態和理論偏向肯定是一個重要因素。在理想的狀態中,理論可以為我們澄清繁雜的事實,並凸顯其間隱藏的關聯。正因為如此,一個認真的研究者必須要掌握相關的學術理論。但是同時,學術理論很容易被意識形態化,筆者對“意識形態”的理解是,它是背後有政治權力推動的一套理論。並被表達為絕對、普世的真理。 今天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基本和美國新保守主義相同)和過去的馬克思主義學術理論都是如此。今天,後者的盲點和誤區要比前者的比較容易被覺察,部分原因是它今天已經相當廣泛地被人們所拒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在今天的“社會主義”中國其實比在美國更完全、更徹底地被年青一代拋棄。)在今天的全球思想氛圍中,所真正不容易掌握的其實是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洞見部分。新自由主義則正好相反,它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統治全球經濟的意識形態,難以洞察的不是其洞見而是其盲點和誤區。
市場資本主義能在全球佔據霸權地位,部分原因固然是人們相當普遍認為資本主義企業的高經濟效率已被證實;同時,資本主義企業的破壞性(如對環境)和剝削性(如對勞動人民),今天也許尚未達到顯而易見的毀滅性地步。另一原因則是缺乏社會主義國家的制衡。在中國,尤其是在經濟學界,新自由主義的勢力吊詭地比在西方還要強盛,新近海歸的博士顯示的是新近皈依信徒所特有的那種簡單、絕對的信仰。
但意識形態的勢力只是部分原因,更基本的也許是人們相當普遍傾向接受當權者提倡的意識形態、傾向接納絕對和簡單的答案。要獨立追求真實須要特殊的努力和執著,比接受簡單、時髦的理論難得多。更容易的道路是追隨意識形態潮流和本行的“權威”。這一切在過去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統治時期非常顯著。在早期的、世俗化之前的西方,宗教曾經佔據同樣的地位,而今天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意識形態的地位一定程度上類似於過去的宗教。
問題也可以從認識論的層面上來理解。作為學者,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好奇而不是簡單的信條,真誠的求真而不是懶惰的接納,系統的探討而不是時髦的答案,質疑而不是給定的意識形態或理論。僅憑我們的日常經驗,大家都知道真正獨立思考的學者是比較少見的。獨立的學術研究路徑當然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努力。要針對某一個題目做出原創性的貢獻,必須系統掌握經驗知識和證據並對之進行獨立的思考和分析。那樣的研究,比從給定的“理論”“假設”或“命題”出發,拼湊相關材料/資料、進行公式化表述要難得多,花時間要多得多,但在現有制度下獲得研究資助的可能則要低得多。
這些是國內外學術研究今天所普遍面對的問題,其不同只在意識形態控制的程度。我們的“最優秀、聰明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青年學生當然很快便會掌握上述的這些“遊戲規則”,很快便會採納更容易被人接受的做法。那樣的研究更容易獲得本行“權威”的認可,也更容易在“核心刊物”上發表。只有極少數的青年學者會願意投入“十年磨一劍”的扎實、獨立研究。
在認識論層面上,筆者一直有意識地要求擺脫意識形態化的理論先行研究,而採用從經驗證據出發,由此提煉概念,而後再返回到經驗證據的研究進路。目的是試圖掌握一個題目的最基本的事實,然後借助與現有理論的對話來提煉自己的概念。這和當前流行的從理論到經驗到理論的做法正好相反。
這不是要提倡無視或拒絕理論,而是要把理論當作工具而不是給定答案。學術理論可以對我們的問題意識有很大的幫助。比如,處於理論和經驗證據的交鋒點是很好的問題。筆者曾經把如此的問題表述為與人們廣泛使用的“規範認識”(“範式”)相悖的(“悖論”)經驗證據和現實,強調悖論的現象是特別需要重新分析和理解的現實。(該文納入《長江》卷後作為進一步的思考。)再則是來自不同理論傳統的交鋒點的問題——譬如,新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或實體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理論傳統的交鋒點,都會是很好的研究問題。從那樣的視角出發,會促使我們擺脫單一(意識形態化)理論傳統的束縛,也會促使我們和現有理論對話,藉以澄清、深化自己的思路。其中的關鍵在於從真正的問題而不是給定的答案出發,從真正的經驗證據探討出發而不是從來自空洞、抽象理論建構出發。
在筆者看來,由此獲得的初步答案需要返回到真實的經驗證據去檢驗。譬如,如果恰亞諾夫關於小農經濟家庭農場的“實體主義”理論洞見確實比馬克思主義或形式主義理論更接近中國的歷史實際、更能幫助我們理解經驗證據,那麼,它是不是也能夠更好地理解當前的實際?是不是也能夠説明我們認識到當前問題的更好解決方案?家庭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在歷史上到底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今天又如何?這方面,中國與現代西方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其前景又如何?這是本書所試圖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
以上表述的也是連接歷史與現實的問題意識。它源自筆者近十年來在國內教學所形成的對現實問題的積極關懷,不同於過去在美國的消極關懷(只想不寫)。這點應該可以說是筆者近十年來的研究的主要動力,也是筆者自覺在問題意識上與當今美國一般的中國研究不同的關鍵。後者所關注的多是最新理論潮流和意識形態所突出的問題,最終主要關乎美國本身的社會或思想,而不是中國現實中的社會或思想問題。譬如,20世紀50~70年代的主導問題是“共產主義”對美國/西方的挑戰或“威脅”,八九十年代則一方面是市場主義的普適性(來自新保守主義,即便是假裝為“去西方中心化”的論點),一方面是認識論上的焦慮(對一切“實證”“事實”的懷疑,來自後現代主義)。(雖然如此,美國的中國研究,無論在經驗還是概念層面上,都不能簡單排斥為“東方主義”的研究,像其帝國主義時代更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學術那樣。)從筆者自身的經歷來審視,前者更容易脫離中國實際,而後者則更容易受國家意識形態主宰。說到底,最好的學術和現實關懷還是真誠“求真”的學術,而不是為了迎合意識形態或時髦理論,或為名為利的研究。
筆者認為,即便當我們由於經驗證據而傾向於某一種理論傳統的時候,我們仍然需要維持原來的探索精神來對待其他的理論。筆者自己發現,經驗實際(例如,滿鐵的翔實調查材料所展示的農村實際,以及明清以來眾多的訴訟案件檔案所展示的司法實踐和社會實際)要遠比任何理論來得複雜、多維和多變。在遇到自己傾向接受的理論傳統不能理解某些經驗證據的時候,我們需要考慮到其他理論傳統的洞見是否能夠更好地理解這些經驗證據。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願意改造自己原來的概念,或創造新的概念來理解新的證據。經驗證據以及歷史感與真實感,而不是理論,更不是意識形態,應是我們最終對概念取捨或重新塑造的標準。
如果這裡的研究明顯地試圖綜合三大理論傳統——形式主義(新自由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和實體主義,識別力強的讀者應該還能看到,此外我還受到後現代主義理論洞見較深的影響。不然,不可能對新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包含的現代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提出如此持續的批評和反思。
雖然如此,筆者個人認為我研究的基石在於對中國鄉村社會經濟歷史經驗證據的長期積累和認識(也包括其與世界其他相關地方的經驗的比較)。在四十多年的研究歷程中,筆者一直在盡可能開放地和系統地積累來自經驗證據和自己的真實感的認識。後者才是筆者對各種不同理論的不同評價和使用的最終依據。
如果筆者的第一、二卷是綜合三大理論傳統——形式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實體主義——的研究,而其中更多地側重實體主義理論,讀者會發現,在第三卷中,筆者雖然仍然傾向既非資本主義也非社會主義理論的第三選擇,但是,面對改革時期市場經濟所起的作用,筆者較多地引用了形式主義理論視角(如關於市場機制在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所起的作用),這方面比之前(如在《華北》和《長江》兩卷中用投資組合理論來理解農民農作物組合型)更顯著。同時,讀者也會注意到,當前的龐大的非正規經濟實際引導筆者返回到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階級視角,雖然筆者採用的絕對不是一般的生產關係或階級分析,而更多的是突出中國現實與經典理論預期的不同。
筆者個人認為,這三卷所表述和顯示的研究路徑可以用“從證據到理論再到證據”來簡單總結。筆者用“證據”來表述的尤其是來自實踐歷史經驗(區別於其表達)的證據。因此,我也用了“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的表述。這裡所說的“實踐”是區別於理論、表達和制度意思的實踐,指的是行動(相對於理論)、實際運作(相對於表達)和運作過程(相對於制度)。如此的表述的用意都是要區別於今天學術界慣用的“從理論到經驗到理論”的方法,因為我認為那完全是一種理論主導的方法,不可能由此得出真正原創性和求真性的研究成果。
筆者也用了“實踐經濟學”和“實踐歷史”的表述,以及“實踐社會學(人類學)”、“實踐法學”和“歷史社會法學”幾個詞彙來簡單總結筆者提倡的學術方法,為的是區別于理論先行的研究。這不是一個簡單由任何單一理論傳統所主宰的方法,而是一個要求經驗證據與理論概念不停地相互作用和連接的方法,也是我四十年來在這三卷中試圖運用的方法。謹請讀者自己決定這樣的方法是否真正適合中國鄉村社會經濟的研究以及今天的國內外學術界。
黃宗智
2013年3月初稿,2013年5月定稿
中文版序
本書使用的史料,主要出自30年代人類學家實地調查所得的資料,尤以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研究人員在華北平原33個自然村實地調查所得的資料為主。作為一個侵略國發起的研究,滿鐵的調查,肯定有其局限性。調查的具體情況及其引起的史學問題,將在本書第二章中進行詳細討論。作者十年來詳細閱讀這些資料,把它們和中西學者在二三十年代作的調查加以比較,進行校對,又于1980年訪問了其中的兩個村莊,通過實地的調查,來核對、補充這些資料。最後,作者得出的結論是:滿鐵資料不失為用現代經濟人類學方法來研究中國農村的一組數量最大而內容又極為豐富的資料。它們的品質甚至可能高於本世紀前半期世界任何其他小農社會的有關資料。此外,1979至1980年間,此書英文初稿寫成之後,作者承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接待,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清代的刑部檔案和寶坻縣的戶房檔案。作者試圖把滿鐵資料所顯示的一些本世紀的社會經濟變化趨勢追溯到清代前期,而對近數百年來華北農村的演變型式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本書在分析概念上,同時得助于農民學和中國歷史研究中的三大學術傳統,即革命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歷史研究,西方“形式主義經濟學”和“實體主義”(本書對它們的稱謂,見第一章)的學術著作,以及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和實體主義的研究成果。
在聯繫史實和概念的研究過程中,作者有意識地循著從史實到概念再回到史實的程式進行研究,避免西方社會科學中流行的為模式而模式的作風,和國內“文化大革命”期間以論帶史的傾向。本書試圖從最基本的史實中去尋找最重要的概念,然後再不斷地回到史料中去驗證,提煉自己的假設。
國內和國外的學術著作,對於如何處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不同的習慣。在國內,應用他人研究成果時,一般只要求引述原始資料。此外,在與他人商榷時,避免直接指名道姓地提意見。國外則不然:學術著作的第一個要求,是總結前人的成果,劃清他人與自己的貢獻。與人商榷時,要求注明作者和書名,以便查對。作者覺得在這方面,國外的習慣是可取的,因為它體現了要求學術通過一代代的積累而不斷前進的科學精神。本書採用了西方的這種習慣,而以相當的篇幅總結過去中、日以及西方各家學派的研究成果,並提出自己的觀點,與之商榷。
本書寫作過程中,承蒙國內外一些學術界的朋友慷慨幫助,都在正文有關部分一一注明。作者受惠幹李文治和劉永成兩位先生尤多。此外,1982至1983年間,美國不同學科的二十二位同行,以及中山大學的葉顯恩先生,對此書的初稿和第二稿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中華書局李侃先生,熱誠促進中美學術交流,使拙作得以在國內出版,十分感謝。
寫譯此書過程中,首尾兩章,特殊概念頗多,由我自擬初稿,其餘各章都由我的研究生葉漢明女士先譯成初稿,然後經我自己逐段修改。葉女士自己關於山東濰縣近百年農村社會經濟演變的博士論文,1985年底即可完成。她協助我翻譯中間各章,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全書最後定稿之前,承蒙劉永成和赫治清兩位先生慷慨為拙稿做文字上的修飾,不勝感激。作者長年在國外工作,平日寫作全用英語。這次等於用左手書寫此稿,加之原稿是用英文寫的,又用了一些特殊的概念,書中難免有不少半西半中的詞句和段落,還望國內讀者鑒諒。我花了近一年的功夫寫改此書的中文稿,目的是要為溝通中外學術交流盡本人微薄之力。我堅信海內外的學術若能真誠交流,相互促進,必定會使我們對中外歷史及其包含的真理,掌握得更深刻更全面。謹以此與國內同仁共勉!
明清以來的鄉村社會經濟變遷:
歷史、理論與現實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未經明言的基本假設是: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和單位產出都可以大幅度擴大。同時,假設這些要素都像機械世界中那樣分別存在,相互間處於一種單一方向的推、拉關係之中。如此的基本假設當然源自機械世界的工業經濟經驗,但今天被相當普遍應用於農業經濟。
一、農業和工業經濟的不同
實際上,農業中的有機要素——土地和勞力——其產出的可能擴大和提高幅度是和工業經濟中的無機要素——資本和科技投入——十分不同的。人力和土地的產出和總量其實都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前工業化的農業產出必須主要取決於給定的土地和在其上的人力投入。固然,在未經人們定居的地方,單位土地面積上所施加的勞力可以在長時期中加大不少,甚至達到四五十倍之多。正如農業理論家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 1965)指出,農業演變的主要歷程是從20年到25年一茬的森林刀耕火種到6年到10年一茬的灌木刀耕火種,到三年兩茬的“短期休耕”,再到一年一茬、兩茬的耕作制度(部分地區可以達到三茬)。但是,我們需要指出,刀耕火種大多只見於人類早期的農業歷史之中。一旦充分定居,一個區域農業生產的提高一般都主要來自從一年一茬提高到一年兩茬,其產出提高的幅度不到一倍。在種植頻率之外,每一茬所施加的人力和能量可以通過使用牲畜的力量來提高(例如在18世紀的英國農業革命中那樣),但充其量也不過是幾倍的幅度。再則是通過人的勤奮度——精耕細作——來提高其能量投入,或從比較粗放的作物(如糧食)改種勞動更密集化的作物(如蔬菜、棉花、蠶桑),但其產出所可能提高的幅度也比較有限。
正如英國經濟史理論家瑞格裡指出,“基於礦物能源”(mineralbased energy economy)的無機工業經濟則十分不同。一個煤礦工人一年可以挖掘200噸的煤炭,足夠產生自己個人勞力許多倍的能量(E. Anthony Wrigley 1988:77)。人們今天普遍使用以幾百馬力來計算的汽車能量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瑞格裡估算,1馬力/小時大約相當於5.1~7.6個人的人力(Wrigley 1988: 39)。也就是說,一輛普通轎車的能量可以輕易達到不止1000人的人力。這就意味著在生產的能量投入上有完全不同幅度的可能擴大量。正是後者的基本情況和邏輯塑造了現代經濟學這方面的認識和假設。但是,作為“有機經濟”的農業,則完全不可能如此。
這裡,有的讀者也許會反駁,一旦引入機械,農業不是變成和工業同樣的產業嗎?比如,在美國今天的農業中,一個勞動力耕種百倍甚或數百倍於中國的一個農業勞動力,用的是機械化的耕—播—收和自動灌溉、施肥、除草等。今天美國農業和中國農業間的差別是1000多畝地(166.7英畝)一個勞動力對不到10畝地一個勞動力。難道這不正是單位勞動力產出可以大規模提高的很好例證嗎?
但如此的論證所忽視的是土地這個有機因素。首先,土地常常是個限定的要素,尤其是在中國這樣的農業早發展、高人口密度國家。中國老早就在各大江河流域形成高度勞動密集的耕作制度,而在14~18世紀則更多移民進入山地和邊疆,達到基本飽和的程度。之後,中國便進入了多個世紀的土地與人口比例逐步遞減的歷史進程。
更重要的是,土地是個有機因素。這裡最管用的其實是一個在中國(今天已經被現代經濟學所遺忘的)農學和農史領域中長期被廣泛使用的概念——“地力”。這是個與“人力”並行以及相互關聯的概念。正如中國的農學和農史專家所非常清楚地認識到,地力只能被小額擴增——比如,通過精耕細作或肥料使用來提高。即便如此,在同一塊土地上加多一茬便意味著加重了地力的負擔,而多施肥料或用更好的肥料只能解決問題的局部,譬如,明清時代長江三角洲在人、畜肥之上使用豆餅肥料來增加土地的營養和力氣。
地力和人力概念其實清楚地說明了人們對它們作為有機體的認識 而機械的“馬力”概念則混淆了無機和有機體,反映的是前工業世界對工業世界在話語層面上的影響。——一個相當普遍被現代經濟學所忽視的基本認識。中國農業史中廣泛使用的諸如“田面”和“田底”那樣的詞彙只能作為隱喻來理解,絕對不能機械地來理解——譬如,按照現代工業經濟學和現代法律的傾向那樣,要求明確“田面”權所指到底是多少尺寸的深度?農民會直覺地把“田面”理解為類似於人體的有機體,不會無稽地要求知道其深入人體皮膚多少。“一田兩主”的概念同樣不可憑現代人的意識來要求明確其具體深度。
在歷史上充分定居的地方,單位土地產出只能通過勞動集約化,如種植頻率的提高,或精耕細作,或灌溉設施,或肥料投入等方法來提高。但那樣只能做到逐年小額的提高,充其量在數個世紀之中達到幾倍的增長幅度。正如珀金斯(Dwight Perkins 1969)的計量研究所證實,在1368年到1968年六個世紀中,中國人口增加了約七到九倍,而農業平均畝產量提高了才約一倍(而耕地——由於山區和邊疆移民——擴增了約四倍,共同把農業總產出提高到之前的八九倍)。
這裡,我們也可以18世紀英國的農業革命為例。當時其土地對人口的比例約百倍於中國,在一個世紀之中,農業產出提高了約一倍,亦即0.72%/年,主要是人們通過配合畜力的使用和諾福克糧食和飼料的輪種制度(在圈地之前,農民不可能在共有土地上如此輪作)。再則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所謂“綠色革命”,即通過化肥、機械和科學選種等現代投入做到單位土地年產出2%~4%的提高,亦即在18年到36年期間提高一倍,之後便不容易持續提高。如此的增長顯然低於人們所廣泛假設工業和“現代經濟”所能達到的幅度。
正是人力—地力關係的局限約束了前工業時代中國農業經濟的發展,而即便是在工業時代,在具有現代投入的條件之下,也主要是土地和地力的限度約束了土地的產出,由此限制了農業單位勞動力的可能產出。這一點最簡潔、精確的表述其實是人們慣常用的“人多地少”概念,十分恰當地被認作中國的“基本國情”(而18世紀的英格蘭和現代的美國則可以代表相對“地多人少”的情況)。今天,它仍然限制了務農人員的可能人均產出。機械、化肥和科學選種固然擴大了中國農業發展的空間,但那個空間仍然受到土地(相對人口)稀少和地力有限的苛刻限制。
地少人多排除了像美國農業那樣簡單憑藉機械動力的投入來大規模提高單位勞動力產出,而地力的限制則嚴格限制了單位土地的產出。前者在美國和中國農業間的差別十分懸殊,達到百倍的幅度,而後者則中國高於美國,雖然只是不到一倍。這樣的事實本身便說明地力的可能提高幅度十分有限——它是個自然界的約束。同理,正是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排除了其採用美國的土地集約型農業模式的可能。事實是,中國農業不可能根據來自工業經濟經驗的假設來理解。農業的有機要素(人力和地力)和工業的無機要素(資本和科技投入)的不同關鍵在於它們的產出和絕對量的可能擴大幅度。
同時,人力和地力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雙向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決定的有機關係,而不是無機要素之間那樣的單向的推與拉的機械關係。人多地少的基本條件既決定了中國農業的人力使用模式,也決定了其土地使用模式,共同導致了中國的精耕細作農業模式。人力和地力之間的關係類似於一個“生態系統”之內的雙向互動關係,其中任何一個“要素”的演變都會帶動其他組成部分相應的演變,正如吉爾茨在他早期的“農業內卷化”書中所闡明的那樣(Geertz 1963)。人力和地力不能夠像無機體間的機械關係那樣分開來理解,因為農業說到底是人在土地上生長植物的有機問題,不是一個機器生產的無機問題。
這裡要對博塞拉普的理論作進一步的討論。她敏銳地說明了人口壓力必然會推動土地使用的勞動密集化,但她所沒有充分說明的是,土地生長作物的“地力”受到不可逾越的限制。在人類的農業史中,種植頻率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年三茬。如果人少地多,人們可以借助使用更多的土地來提高單位勞動力的產出,其道理等於是把博塞拉普的模式倒過來理解。但是,在人多地少的給定情況下,單位土地和勞動力的產出都受到不可逾越的限制。單位土地不可能超越一年三茬,而每茬作物所能夠有效吸納的勞動力投入同樣有一定的限制,不可避免的是邊際報酬遞減的限制,並且顯然具有一定的“極限”。 裴小林2008特別突出土地“極限”的問題。
瑞格裡把這個道理表述為“有機”經濟的能源方面的限制,很好地說明了有機(農業)和無機(現代工業)經濟之間在能源生產(和投入)方面的一個關鍵差別,但瑞格裡沒有明確說明的是,有機經濟這方面的約束主要來自人力和地力在生長作物過程中相互間所形成的限制。地多人少的話,所受到的限制來自人力,其可能擴大幅度十分有限;地少人多的話,所受的限制則來自地力,其可能擴大幅度同樣十分有限。人力和地力由此相互決定了農業產出的限制。人力和地力與資本和技術在這方面的不同才是有機和無機經濟間不同的關鍵。
正是上述的基本約束突出了“邊際報酬遞減”的經濟規律。在人多地少和土地的自然生產力有限的現實下,單位土地面積上越來越多的人力投入只可能導致其邊際報酬的遞減,與地多人少的農業環境十分不同。從一年一茬到兩茬,甚或三茬,每茬產出(相對投入)的遞減便是最好的例證。同時,通過比耕作更高度勞動密集的手工業“副業”(另一個十分貼切的普通用詞)來輔助小規模農業生產的不足,也是一個好的例證。中國農民這種同時依賴不止一種生產活動來支撐生活的特徵一直持續至今,與西方相對地多人少的農業系統十分不同。這就是本書之所謂的農業“內卷化”或“過密化”。
我們需要從以上的角度來理解恰亞諾夫所指出的(小農經濟)農業的特徵,即其基本生產單位是家庭而不是工業經濟那樣的個體化產業工人,而同時,小農家庭既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一個消費單位,和僅是一個生產單位的資本主義企業十分不同(Chayanov 1986[1925])。在依據工業經濟經驗的經濟學占霸權地位的今天,這些特徵很容易被忽視。作為一個消費單位,家庭農場的經濟行為不僅取決於生產考慮,也取決於消費需要。正是單位土地的地力,相應勞動力投入的邊際報酬遞減,說明了恰氏打出的基本理論:農戶在單位土地上的勞動力投入取決於其勞動力邊際產出的“辛苦度”和家庭消費邊際需要間的平衡。據此,恰氏更進而考慮到農業與手工業間的關係,以及農業與人口壓力間的關係。
在這些方面上,本書《華北》和《長江》兩卷有比較詳細的說明。拙作的特點之一是通過翔實的關於基層小農場運作的經濟人類學資料來分析並說明其生產邏輯。這是一個由微觀的生產實踐來說明宏觀的經濟邏輯的研究進路和方法,由此來展示它和現代工業經濟的不同。
《華北》卷論證,清代後期以來冀—魯西北平原地區足足有一半以上農戶(“貧農”)的農場規模在十畝以下,因此農業中的“就業不足”問題嚴重,必須同時依賴(農業)打工或家庭手工業來輔助、支撐生活。《長江》卷則論證,長江三角洲土地更少(雖然其地力比華北相對較高),更高度依賴手工副業,也更高度商業化。但是,兩個地區的貧農扶著農業—打工/手工業兩炳拐杖來支撐生活的基本原則是一樣的。而這樣的手工業與農業緊密結合的經濟組織,由於其所依賴的勞動力比雇用長工的經營式農業來得“便宜”,能夠支撐更高的地租和地價,並因此在長江三角洲排除了(明清之際還相當普遍的依賴雇傭勞動的)經營式農業。
以上說明的經驗證據和其所包含的道理是本書之所以挑戰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 1964;1979)著作的原因。他堅持農業和工業是由同樣的經濟規律所主宰,並假設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是同樣性質的,其總量和產出幾乎可以無限制擴大。同時,由於他認為市場機制必定會導致最佳的資源配置,他認為人口過剩(也就是說,土地相對人口的嚴重不足)不可能存在,完全沒有認識到人—地關係乃是農業的先決條件。
同時,他單獨突出“人力資本”,堅持只要具備前提性的私有產權和市場機制,加上“綠色革命”那樣的現代技術投入,便必定會推動、導致“傳統農業的改造”。像他那樣把有機的“人力”和無機的“資本”兩個概念混淆起來使用於農業,本身便是對有機體和無機體的基本差異的忽視。農業絕對不應該被等同於無機工業產業,不應該被簡單地以基於工業經驗的假設的經濟學的“規律”來理解。中國農業不可能像在美國的地多人少基本條件之下,借助市場機制,通過資本和技術的投入,幾乎無限制地提高單位勞動產出。
回顧中國的經濟歷史,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之前的六個世紀中,農業相當高度商業化,但是市場機制的擴延從來沒有解決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問題。在20世紀上半期,引入現代投入,依然沒有解決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後,在集體化下更多地引入現代投入,同樣沒有解決問題。本書第三卷詳細論證,即便是中國今天的農業,仍然強烈地受到人口—土地關係的影響,完全不同于舒爾茨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所想像的那樣。
正是由於上述原因,本書的出發點是中國土地和人口關係的演變,因為它是中國農業生產的給定基本條件。對明清以來到當代的演變,無論是“資本”還是現代科技投入,還是財產制度和相關法律,或社會結構,或市場關係,都不能脫離土地—人口關係基本條件的背景來理解。改革時期的農業去集體化和家庭化以及市場化演變也同樣。這絕對不是要單獨突出人口為單一的決定性因素,而是要澄清人口與土地間的給定“基本國情”,由此來分析其與其他生產要素和制度和社會演變之間的關係。
這裡要進一步說明,本書也絕對不是要否認市場經濟在改革時期所起的作用,因為它確實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筆者所突出的市場作用是完全出於舒爾茨視野之外的。首先,舒爾茨完全沒有考慮到的人民消費轉型。具體來說,人們的收入,尤其是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加,導致中國食物消費的基本轉型,從8∶1∶1的糧食∶肉/魚∶蔬菜/水果的比例向4∶3∶3轉化,而那樣的市場需求則促使中國農業結構的轉化,導致近二十年中的一個(我稱之為)“隱性農業革命”,促使中國農業生產轉向越來越高比例的高值農產品——即從糧食轉向更多更高值的蔬菜和肉食生產。這是一個比之前歷史上的農業革命,例如18世紀的英國農業革命和20世紀六七十年代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綠色革命,增加幅度要大的革命,在最近20年達到每年6%產值(可比價格)增長的幅度。正如我在書中所強調,市場機制所起的強大作用是無可否認的,但其所導致的農業革命的肇因是完全不同于舒爾茨所提倡和想像的“綠色革命”。
同時,今天中國土地—人口的有機關係仍然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它排除了美國那樣簡單的土地、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農業;小規模家庭農業將長期佔據中國農業的主體地位。中國農業的基本生產單位仍然將是最多幾個英畝的家庭農場,其農場的規模迥異于舒爾茨的想像。它們固然越來越多的是(我稱之為)“資本和勞動雙密集化”的小規模農場(例如,拱棚蔬菜、種養結合的小農場,果園、魚塘等,它們比“舊農業”使用更多的化肥、農藥、塑膠棚和塑膠膜、人工飼料等)。這些(我稱之為)“新時代的小農場”同樣需要從中國人多地少的給定條件,以及有機的土地—人口關係來理解。
拙作論證的是,把農業想像為一個和工業產業同樣性質的“產業”並服從同樣的經濟學“規律”,其實是個無稽的想像。
把農業想像為一種(無機工業)產業,
首先是對農業的誤解,它無視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這等於無視中國經濟歷史。那樣的想像其實也是一個源自現代主義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它最終想像的中國農業是,或者認為應該是,和美國的一樣。那是對中國農業史和經濟史錯誤的認識,也是對中國現實錯誤的判斷。更要命的是,它提倡的是個錯誤的改革方案,想像的是大規模農場的規模效益,而不是小規模農場的給定條件和效益。
令人特別擔憂的是,上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整套理論今天居然已經成為中國的“現代經濟學”的“主流”,其中也包括農業經濟學。這也是作者在這裡如此帶有緊迫感和使命感地提出對其批評的原因。
二、中國的非正規經濟
中國的人口—土地關係不僅是中國農業的先決條件,也是中國國民經濟整體的先決條件,在改革時期尤其如此。全球資本進入中國以及中國本土資本主義企業的興起,使中國也呈現出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半個多世紀以來早已普遍存在的現象,即農村廉價勞動力大規模湧入城鎮打工。從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的角度來看,這正是其所需要的廉價勞動力,也是其跨國公司普遍進行“外包”(outsourcing)的緣由。從農村勞動力的視角來看,它帶來的是受歡迎的較高報酬的就業機會。
兩者的結合在全球範圍內帶來的是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稱作“非正規經濟”的大規模興起。1969年,ILO因其為全球“非正規經濟”人員爭取“有尊嚴的待遇”而獲諾貝爾和平獎。正因為農村具有“無限的勞動力供應”(W. Arthur Lewis 1954,1955),資本可以用(相對)最低的工資、最壞的工作環境、最低等的(或根本就沒有)福利來雇用工人,無論當地勞動法規如何。從資本的視角來看,這完全是市場經濟的客觀供需規律所使然——當然也正好偏向資本。而從當地政權的視角來看,外來資本的湧入意味著在本地的投資和其所帶來的“經濟發展”,為此相當普遍被認為是優先于工人生活狀況和社會公正的事。正是這樣,促使無視當地法規的“非正規經濟”快速興起和擴增。因此, ILO對“非正規經濟”的基本定義正是:沒有法律保護和沒有福利的經濟,並呼籲為非正規經濟人員爭取法律的保護和有尊嚴的待遇。事實上,半個世紀以來,在全世界各地發展中國家,非正規經濟已擴展到城鎮總就業人數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甚或更多(ILO 2002)。在中國的後計劃經濟時代,與印度和印尼等較高人口密度國家相似,非正規經濟員工已經達到城鎮就業人員總數的三分之二的比例。
但是,由於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和土地承包制度,今天中國絕大多數的“工人”不是城鎮居民而仍然是農村戶籍的農民。一方面,由於戶籍制度他們很難成為城鎮的合法居民。同時城鄉生活水準的差距也妨礙大多數的農民工在城市買房長期居留。另一方面,由於承包地的地權,農村對他們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在城鎮打工的農民不會像在其他國家那樣完全脫離農村,而是形成了一個跨城鄉的、具有一定“中國特色”的結合務工和務農的龐大群體。
今天,傳統的城鎮工業“工人”和農村務農“農民”這兩個人們慣用的範疇已經不再適用於中國。這是因為大多數的城鎮工人已經不再是城鎮居民而是農村戶籍人民;同時,大多數的農民家庭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務農人員,而是同時務農和務工(以及其他非農就業)的人員。本書第三卷詳細論證,在今天的中國,幾乎每一戶所謂的農民都有人在外打工。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家庭主要是緊密結合工業(和其他非農就業)與農業的“半工半耕”人員。在我看來,我們不應該像國際勞工組織那樣把“非正規經濟”範疇限定於城鎮,而應該把中國的半工半耕勞動人民也計算在非正規經濟範疇之內。那樣,可以避免不符合實際的、具有嚴重誤導性的傳統“城鎮”和“鄉村”以及“工人”和“農民”的劃分,更好地突出今天中國社會經濟的實際和特點。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的非正規經濟是和社會主義革命傳統的勞動立法和制度並存的,在這點上也和大部分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有一定的不同。中國共產黨是以勞動人民——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先鋒隊名義取得勝利的。一旦掌權,革命的共產黨成為了執政的共產黨,而工人則從革命階級轉化為“領導階級”。因此,工人順理成章地和國家黨政官員一起被納入國家正規“職工”的範疇,受到革命勞工運動所爭得的勞動法律的一系列保護和保障,包括有尊嚴的工資待遇、安全的工作環境、合理的工作時間、超額工作的成倍報酬以及各種福利——醫療、退休、失業、工傷、生育。但是,今天具有如此待遇的 “藍領”工人不過是全部勞動人民中的很少數。他們實際上和國家黨政官員以及大企業白領職工一起形成一個正規經濟身份的特權階層。這是作者第三卷中最新的探索所論證的要點,也是作者研究中最直接連接經濟和法律兩大領域的論點(相關討論亦見筆者新版的法律三卷本最後的“進一步的探索”)。
吊詭的是,這個源自革命傳統的現實使中國的正規和非正規經濟之間的差別比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傳統的國家更加懸殊。今天,處於非正規經濟範疇的大多數勞動人民被排除在法定的正規“勞動關係”之外,被歸入不受勞動法律保護的非正規“勞務關係”範疇之下。今天回顧,國家早在1958年1月便開始執行的嚴格戶籍制度(當時是為了限制農民大規模湧入城市而造成混亂),後來實際上成為一個把占少數的正規職工和占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劃分為兩個壁壘森嚴的等級。今天勞動法規已經幾乎完全成為衛護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的法律制度。
中國正規和非正規經濟間的差別不僅是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差別,也是法定身份的差別。今天,除了頂層的國家官員和大企業家之外,中國社會的上層實際上是占所有就業人員中的16.8%的正規經濟,其半數是國家黨政機構和事業單位以及國營企業的人員,半數是較大的民營企業的職工。他們是所謂的“中產階級”的大多數,其生活方式正日益向全球的中產階級消費者趨同——包括在房子、傢俱、汽車、食物消費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另一邊則是底層的、占83.2%的非正規工—農勞動人民。他們承擔的是最低報酬的工作,絕大多數沒有勞動法律的保護也基本沒有(或只有低等的)社會福利。
兩者間差別的一個具體表現是,在交通事故導致死亡的情況下,農村戶籍人的補償標準是8萬元到10萬元,而城市戶籍的則是20萬元到30萬元。更有甚者,在國家2009年以來建立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下,一個60歲以上的農民每個月可以拿到55元,而一個公務員的退休金則約6000元。 “養老金雙軌制被指為最大不公:公務員6千農民55元”,載《經濟觀察報》2013年5月3日。農村戶籍的半工半農人民無疑是一種二等公民,其身份地位不僅遠低於國家官員和大型企業的“白領”職員,也遠低於一般的市民。
以上敘述的經驗事實都明顯與主流經濟學家們的意見不相符。他們根據所謂的“路易斯拐點理論”而堅持中國今天已經從一個“二元經濟”(一“元”是具有“無限勞動力供應”的“傳統農業”部門,另一元是城市的“現代經濟”部門)進入一個完全整合的、沒有城鄉差別的勞動力市場的經濟體系。一組具有很大影響力的人口學—經濟學家幾年前便已開始堅持這個論點,完全無視低工資—低福利的非正規經濟和高工資—高福利的正規經濟間的顯著差別。實際上,兩者間的差別非但沒有像“路易斯拐點理論”預期的那樣伴隨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快速增長而消失,反而是日益懸殊。世界銀行等國際單位歷年估算的基尼係數便是很好的證據。與“拐點論”類似,新自由主義社會學家們則採用了來自美國的“中產階層”和“橄欖型”社會理論,爭論中國社會的結構已經類似於美國的中產階層占到全社會大多數的模型,完全無視中國社會貧富懸殊的實際。本書第三卷比較詳細地討論了上述情況和問題的方方面面。
從經濟史的視角來看,中國兩大社會經濟等級—階層間的差別的最終根源還是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今天中國農業仍然處於人均不到10畝以及土地生產力的嚴格限度的小規模經營的苛刻約束之下。農業中的“隱性失業”和勞動力就業不足因此仍然存在。近年來的“隱性農業革命”,固然(像本書詳細論證的那樣)通過勞動和資本雙密集化的小規模新農業吸納了更多的勞動力,因此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同時,農民在城鎮和農村的非農就業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正規與非正規經濟間的懸殊待遇,以及城市比農村的更快速發展,使農村依然日益落後於城市,也使測量中國分配不公程度的基尼係數大幅度攀升。
從改革時期的經濟歷史來看,中國在GDP增長方面的成功和其嚴重的社會不公問題顯然是來自同一根源的。正是中國龐大的廉價農村勞動力使其得以成為“世界的工廠”;同時,也正是這個勞動力的低等待遇導致中國嚴峻的社會不公以及當前的社會危機。
從更長遠的歷史視角來看,中國的小規模勞動密集型農業既是傳統中國特早的城市發展的來源,也是其18世紀以來大規模農村貧困和社會不公的根源。中國在江河流域早已形成的高密度小規模農業正是中國大型複雜城市(和輝煌的城市文化)興起的先決條件。正如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 1981)的另一理論洞見指出,在前現代的物流條件(沒有冷藏設備和現代運輸條件)下,食物供應被限定於一定的較小空間範圍。一個同一面積的地區,如果有1000萬人口,即便其生產剩餘相對低(譬如10%),仍然能夠支撐一個100萬人的城市(如唐代的長安),而同一面積的地方,如果只有100萬人口,即便其生產剩餘相對高(譬如30%),只能支撐一個30萬人口的城市(如中世紀的倫敦)。同時,(勞動密集的)小規模農業,以及其所導致的勞動生產率遞減,乃是城鄉差別的根源。它也是現代中國革命的主要導因。
今天的社會不公其實和歷史上的城鄉差別有一定的關聯。明清以來農村農戶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下,長期結合農業+(農業)打工和手工業的生產方式來應付生存壓力。改革以來,農村農戶根據同樣的邏輯,越來越多地依賴農業和工業打工來支撐家庭開銷。今天,城市中16.8%的正規經濟的“中產階級”和城鄉83.2%的相對貧困非正規經濟間的差別,歸根到底也和中國的人多地少的基本農村國情相關。
當前,貧富不均是一個亟須緊急處理的問題。為此,本書也初步探討了一個地方,在中央的直接指示下,通過實驗所突出的統籌城鄉方案。它在處理農民工問題方面已經探尋出一些可行的措施,但在農村本身方面則尚需繼續探索。
三、一個不同的探索方法
在多年的農村研究中,筆者曾多次向自己提問:當下流行的意見為什麼會對上列的基本事實視而不見?我們需要怎樣來改正這樣的盲點和誤區?
意識形態和理論偏向肯定是一個重要因素。在理想的狀態中,理論可以為我們澄清繁雜的事實,並凸顯其間隱藏的關聯。正因為如此,一個認真的研究者必須要掌握相關的學術理論。但是同時,學術理論很容易被意識形態化,筆者對“意識形態”的理解是,它是背後有政治權力推動的一套理論。並被表達為絕對、普世的真理。 今天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基本和美國新保守主義相同)和過去的馬克思主義學術理論都是如此。今天,後者的盲點和誤區要比前者的比較容易被覺察,部分原因是它今天已經相當廣泛地被人們所拒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在今天的“社會主義”中國其實比在美國更完全、更徹底地被年青一代拋棄。)在今天的全球思想氛圍中,所真正不容易掌握的其實是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洞見部分。新自由主義則正好相反,它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統治全球經濟的意識形態,難以洞察的不是其洞見而是其盲點和誤區。
市場資本主義能在全球佔據霸權地位,部分原因固然是人們相當普遍認為資本主義企業的高經濟效率已被證實;同時,資本主義企業的破壞性(如對環境)和剝削性(如對勞動人民),今天也許尚未達到顯而易見的毀滅性地步。另一原因則是缺乏社會主義國家的制衡。在中國,尤其是在經濟學界,新自由主義的勢力吊詭地比在西方還要強盛,新近海歸的博士顯示的是新近皈依信徒所特有的那種簡單、絕對的信仰。
但意識形態的勢力只是部分原因,更基本的也許是人們相當普遍傾向接受當權者提倡的意識形態、傾向接納絕對和簡單的答案。要獨立追求真實須要特殊的努力和執著,比接受簡單、時髦的理論難得多。更容易的道路是追隨意識形態潮流和本行的“權威”。這一切在過去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統治時期非常顯著。在早期的、世俗化之前的西方,宗教曾經佔據同樣的地位,而今天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意識形態的地位一定程度上類似於過去的宗教。
問題也可以從認識論的層面上來理解。作為學者,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好奇而不是簡單的信條,真誠的求真而不是懶惰的接納,系統的探討而不是時髦的答案,質疑而不是給定的意識形態或理論。僅憑我們的日常經驗,大家都知道真正獨立思考的學者是比較少見的。獨立的學術研究路徑當然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努力。要針對某一個題目做出原創性的貢獻,必須系統掌握經驗知識和證據並對之進行獨立的思考和分析。那樣的研究,比從給定的“理論”“假設”或“命題”出發,拼湊相關材料/資料、進行公式化表述要難得多,花時間要多得多,但在現有制度下獲得研究資助的可能則要低得多。
這些是國內外學術研究今天所普遍面對的問題,其不同只在意識形態控制的程度。我們的“最優秀、聰明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青年學生當然很快便會掌握上述的這些“遊戲規則”,很快便會採納更容易被人接受的做法。那樣的研究更容易獲得本行“權威”的認可,也更容易在“核心刊物”上發表。只有極少數的青年學者會願意投入“十年磨一劍”的扎實、獨立研究。
在認識論層面上,筆者一直有意識地要求擺脫意識形態化的理論先行研究,而採用從經驗證據出發,由此提煉概念,而後再返回到經驗證據的研究進路。目的是試圖掌握一個題目的最基本的事實,然後借助與現有理論的對話來提煉自己的概念。這和當前流行的從理論到經驗到理論的做法正好相反。
這不是要提倡無視或拒絕理論,而是要把理論當作工具而不是給定答案。學術理論可以對我們的問題意識有很大的幫助。比如,處於理論和經驗證據的交鋒點是很好的問題。筆者曾經把如此的問題表述為與人們廣泛使用的“規範認識”(“範式”)相悖的(“悖論”)經驗證據和現實,強調悖論的現象是特別需要重新分析和理解的現實。(該文納入《長江》卷後作為進一步的思考。)再則是來自不同理論傳統的交鋒點的問題——譬如,新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或實體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理論傳統的交鋒點,都會是很好的研究問題。從那樣的視角出發,會促使我們擺脫單一(意識形態化)理論傳統的束縛,也會促使我們和現有理論對話,藉以澄清、深化自己的思路。其中的關鍵在於從真正的問題而不是給定的答案出發,從真正的經驗證據探討出發而不是從來自空洞、抽象理論建構出發。
在筆者看來,由此獲得的初步答案需要返回到真實的經驗證據去檢驗。譬如,如果恰亞諾夫關於小農經濟家庭農場的“實體主義”理論洞見確實比馬克思主義或形式主義理論更接近中國的歷史實際、更能幫助我們理解經驗證據,那麼,它是不是也能夠更好地理解當前的實際?是不是也能夠説明我們認識到當前問題的更好解決方案?家庭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在歷史上到底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今天又如何?這方面,中國與現代西方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其前景又如何?這是本書所試圖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
以上表述的也是連接歷史與現實的問題意識。它源自筆者近十年來在國內教學所形成的對現實問題的積極關懷,不同於過去在美國的消極關懷(只想不寫)。這點應該可以說是筆者近十年來的研究的主要動力,也是筆者自覺在問題意識上與當今美國一般的中國研究不同的關鍵。後者所關注的多是最新理論潮流和意識形態所突出的問題,最終主要關乎美國本身的社會或思想,而不是中國現實中的社會或思想問題。譬如,20世紀50~70年代的主導問題是“共產主義”對美國/西方的挑戰或“威脅”,八九十年代則一方面是市場主義的普適性(來自新保守主義,即便是假裝為“去西方中心化”的論點),一方面是認識論上的焦慮(對一切“實證”“事實”的懷疑,來自後現代主義)。(雖然如此,美國的中國研究,無論在經驗還是概念層面上,都不能簡單排斥為“東方主義”的研究,像其帝國主義時代更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學術那樣。)從筆者自身的經歷來審視,前者更容易脫離中國實際,而後者則更容易受國家意識形態主宰。說到底,最好的學術和現實關懷還是真誠“求真”的學術,而不是為了迎合意識形態或時髦理論,或為名為利的研究。
筆者認為,即便當我們由於經驗證據而傾向於某一種理論傳統的時候,我們仍然需要維持原來的探索精神來對待其他的理論。筆者自己發現,經驗實際(例如,滿鐵的翔實調查材料所展示的農村實際,以及明清以來眾多的訴訟案件檔案所展示的司法實踐和社會實際)要遠比任何理論來得複雜、多維和多變。在遇到自己傾向接受的理論傳統不能理解某些經驗證據的時候,我們需要考慮到其他理論傳統的洞見是否能夠更好地理解這些經驗證據。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願意改造自己原來的概念,或創造新的概念來理解新的證據。經驗證據以及歷史感與真實感,而不是理論,更不是意識形態,應是我們最終對概念取捨或重新塑造的標準。
如果這裡的研究明顯地試圖綜合三大理論傳統——形式主義(新自由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和實體主義,識別力強的讀者應該還能看到,此外我還受到後現代主義理論洞見較深的影響。不然,不可能對新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包含的現代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提出如此持續的批評和反思。
雖然如此,筆者個人認為我研究的基石在於對中國鄉村社會經濟歷史經驗證據的長期積累和認識(也包括其與世界其他相關地方的經驗的比較)。在四十多年的研究歷程中,筆者一直在盡可能開放地和系統地積累來自經驗證據和自己的真實感的認識。後者才是筆者對各種不同理論的不同評價和使用的最終依據。
如果筆者的第一、二卷是綜合三大理論傳統——形式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實體主義——的研究,而其中更多地側重實體主義理論,讀者會發現,在第三卷中,筆者雖然仍然傾向既非資本主義也非社會主義理論的第三選擇,但是,面對改革時期市場經濟所起的作用,筆者較多地引用了形式主義理論視角(如關於市場機制在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所起的作用),這方面比之前(如在《華北》和《長江》兩卷中用投資組合理論來理解農民農作物組合型)更顯著。同時,讀者也會注意到,當前的龐大的非正規經濟實際引導筆者返回到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階級視角,雖然筆者採用的絕對不是一般的生產關係或階級分析,而更多的是突出中國現實與經典理論預期的不同。
筆者個人認為,這三卷所表述和顯示的研究路徑可以用“從證據到理論再到證據”來簡單總結。筆者用“證據”來表述的尤其是來自實踐歷史經驗(區別於其表達)的證據。因此,我也用了“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的表述。這裡所說的“實踐”是區別於理論、表達和制度意思的實踐,指的是行動(相對於理論)、實際運作(相對於表達)和運作過程(相對於制度)。如此的表述的用意都是要區別於今天學術界慣用的“從理論到經驗到理論”的方法,因為我認為那完全是一種理論主導的方法,不可能由此得出真正原創性和求真性的研究成果。
筆者也用了“實踐經濟學”和“實踐歷史”的表述,以及“實踐社會學(人類學)”、“實踐法學”和“歷史社會法學”幾個詞彙來簡單總結筆者提倡的學術方法,為的是區別于理論先行的研究。這不是一個簡單由任何單一理論傳統所主宰的方法,而是一個要求經驗證據與理論概念不停地相互作用和連接的方法,也是我四十年來在這三卷中試圖運用的方法。謹請讀者自己決定這樣的方法是否真正適合中國鄉村社會經濟的研究以及今天的國內外學術界。
黃宗智
2013年3月初稿,2013年5月定稿
中文版序
本書使用的史料,主要出自30年代人類學家實地調查所得的資料,尤以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研究人員在華北平原33個自然村實地調查所得的資料為主。作為一個侵略國發起的研究,滿鐵的調查,肯定有其局限性。調查的具體情況及其引起的史學問題,將在本書第二章中進行詳細討論。作者十年來詳細閱讀這些資料,把它們和中西學者在二三十年代作的調查加以比較,進行校對,又于1980年訪問了其中的兩個村莊,通過實地的調查,來核對、補充這些資料。最後,作者得出的結論是:滿鐵資料不失為用現代經濟人類學方法來研究中國農村的一組數量最大而內容又極為豐富的資料。它們的品質甚至可能高於本世紀前半期世界任何其他小農社會的有關資料。此外,1979至1980年間,此書英文初稿寫成之後,作者承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接待,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清代的刑部檔案和寶坻縣的戶房檔案。作者試圖把滿鐵資料所顯示的一些本世紀的社會經濟變化趨勢追溯到清代前期,而對近數百年來華北農村的演變型式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本書在分析概念上,同時得助于農民學和中國歷史研究中的三大學術傳統,即革命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歷史研究,西方“形式主義經濟學”和“實體主義”(本書對它們的稱謂,見第一章)的學術著作,以及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和實體主義的研究成果。
在聯繫史實和概念的研究過程中,作者有意識地循著從史實到概念再回到史實的程式進行研究,避免西方社會科學中流行的為模式而模式的作風,和國內“文化大革命”期間以論帶史的傾向。本書試圖從最基本的史實中去尋找最重要的概念,然後再不斷地回到史料中去驗證,提煉自己的假設。
國內和國外的學術著作,對於如何處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不同的習慣。在國內,應用他人研究成果時,一般只要求引述原始資料。此外,在與他人商榷時,避免直接指名道姓地提意見。國外則不然:學術著作的第一個要求,是總結前人的成果,劃清他人與自己的貢獻。與人商榷時,要求注明作者和書名,以便查對。作者覺得在這方面,國外的習慣是可取的,因為它體現了要求學術通過一代代的積累而不斷前進的科學精神。本書採用了西方的這種習慣,而以相當的篇幅總結過去中、日以及西方各家學派的研究成果,並提出自己的觀點,與之商榷。
本書寫作過程中,承蒙國內外一些學術界的朋友慷慨幫助,都在正文有關部分一一注明。作者受惠幹李文治和劉永成兩位先生尤多。此外,1982至1983年間,美國不同學科的二十二位同行,以及中山大學的葉顯恩先生,對此書的初稿和第二稿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中華書局李侃先生,熱誠促進中美學術交流,使拙作得以在國內出版,十分感謝。
寫譯此書過程中,首尾兩章,特殊概念頗多,由我自擬初稿,其餘各章都由我的研究生葉漢明女士先譯成初稿,然後經我自己逐段修改。葉女士自己關於山東濰縣近百年農村社會經濟演變的博士論文,1985年底即可完成。她協助我翻譯中間各章,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全書最後定稿之前,承蒙劉永成和赫治清兩位先生慷慨為拙稿做文字上的修飾,不勝感激。作者長年在國外工作,平日寫作全用英語。這次等於用左手書寫此稿,加之原稿是用英文寫的,又用了一些特殊的概念,書中難免有不少半西半中的詞句和段落,還望國內讀者鑒諒。我花了近一年的功夫寫改此書的中文稿,目的是要為溝通中外學術交流盡本人微薄之力。我堅信海內外的學術若能真誠交流,相互促進,必定會使我們對中外歷史及其包含的真理,掌握得更深刻更全面。謹以此與國內同仁共勉!
目次
第一編背景
第一章探討的問題 /
中國的小農 /
農民學中三個不同的傳統 /
對分化中的小農經濟的一個綜合分析 /
農村演變的型式 /
過去的研究 /
人口與生產關係 /
經濟落後的問題 /
帝國主義的問題 /
中國的農村 /
過去的研究 /
華北的村莊 /
20世紀的變化 /
第二章引用的史料與研究的村莊 /
滿鐵調查的資料 /
對滿鐵資料的批判性評價 /
調查的村莊 /
檔案史料 /
地方檔案和社會史 /
第三章生態環境 /
水利與政治經濟結構 /
災害頻仍的旱地農作與高密度的人口 /
澇災和社會經濟結構 /
生態、居住型式與自然村結構 /
第二編經濟內卷和社會分化
第四章20世紀30年代的經營式農場與家庭式農場 /
農村社會經濟的分析 /
村中“富戶”和經營式農作 /
經營式農場主的面貌 /
數量估計 /
經營式農場主和出租地主 /
經營式和家庭式農業 /
第五章清代前期的小農經濟和莊園經濟 /
清代前期的小農場和大莊園 /
經營式莊園 /
清代前期富農和經營式農業的擴展 /
最近國內的研究 /
法律對新的社會現實的承認 /
租佃關係的變遷 /
18世紀的土地分配狀態 /
第六章清代前期的農業商品化和小農分化 /
20世紀資料中所見的農業商品化和小農分化 /
冀中、冀南和魯西北的農作物商品化型式 /
明清時期的棉花種植 /
農業商品化和人口增長 /
經營式農作和手工業的商品生產 /
第七章20世紀農業的加速商品化 /
中國農業和世界經濟 /
棉花種植的增長 /
棉花和世界經濟 /
棉手工業和世界經濟 /
變遷和延續 /
第八章經營式和家庭式農場的對比:耕畜的使用和農場生產力 /
滿鐵資料 /
耕畜使用的經濟 /
農場、牲口、肥料和純作物農業經濟 /
清代時期 /
第九章經營式和家庭式農場勞動生產率的對比 /
勞動生產率的對比 /
經營式農場上小組耕作的較高效率 /
貧農之背離合理經營模式 /
貧農農場上的就業不足和物質刺激力的遞減 /
第十章經營式農業何以發展不足 /
經營式農場通常在100畝以上的原因 /
經營式農場通常在200畝以下的原因 /
經營式農作和出租地主制的對照 /
經營式農作和社會政治體系 /
革新的可能 /
一個“高水準均衡的陷阱”? /
第十一章家庭式農場的牢固性 /
對土地的壓力 /
貧農農場收入 /
高利貸 /
家庭式農場和家庭手工業生產 /
家庭式農場和短工 /
家庭式農場和長工 /
第十二章生產關係的商品化 /
從分成租到定額租 /
分成租制 /
定額租制 /
地租負擔的比較 /
雇傭勞動 /
第三編村莊與國家
第十三章清政權下的村莊 /
華北平原村落的閉塞性 /
村莊各階層的相對閉塞性 /
20世紀前的村莊與國家 /
19世紀的自然村與士紳 /
宗族 /
自然村內生的權力結構 /
共同體領導抑或國家政權代理人 /
自然村和農民的集體行動 /
清代的經濟和政治結構 /
第十四章自然村結構的變化 /
自耕農和雇農的差別 /
婚俗中的階級差別 /
貧農的雙重性質 /
兩個緊密的村莊及其“封閉” /
部分無產化和村莊共同體的解散 /
分裂了的村莊 /
第十五章20世紀的自然村與國家 /
地方政府的軍事化和現代化 /
縣政府的財政 /
賦稅負擔 /
稅款的徵收 /
地方豪霸與村級惡棍的崛起 /
第十六章結論 /
農村演變的型式 /
貧農經濟的結構 /
經濟落後的根源 /
半無產化與人口趨向 /
半無產化了的村莊和20世紀的地方政權 /
貧農與中國的革命 /
附錄一滿鐵調查的33個村莊社會經濟輪廓 /
附錄二河北、山東人口(1393~1953) /
附錄三河北、山東耕地面積(1393~1957) /
引用書刊目錄 /
索引 /
第一章探討的問題 /
中國的小農 /
農民學中三個不同的傳統 /
對分化中的小農經濟的一個綜合分析 /
農村演變的型式 /
過去的研究 /
人口與生產關係 /
經濟落後的問題 /
帝國主義的問題 /
中國的農村 /
過去的研究 /
華北的村莊 /
20世紀的變化 /
第二章引用的史料與研究的村莊 /
滿鐵調查的資料 /
對滿鐵資料的批判性評價 /
調查的村莊 /
檔案史料 /
地方檔案和社會史 /
第三章生態環境 /
水利與政治經濟結構 /
災害頻仍的旱地農作與高密度的人口 /
澇災和社會經濟結構 /
生態、居住型式與自然村結構 /
第二編經濟內卷和社會分化
第四章20世紀30年代的經營式農場與家庭式農場 /
農村社會經濟的分析 /
村中“富戶”和經營式農作 /
經營式農場主的面貌 /
數量估計 /
經營式農場主和出租地主 /
經營式和家庭式農業 /
第五章清代前期的小農經濟和莊園經濟 /
清代前期的小農場和大莊園 /
經營式莊園 /
清代前期富農和經營式農業的擴展 /
最近國內的研究 /
法律對新的社會現實的承認 /
租佃關係的變遷 /
18世紀的土地分配狀態 /
第六章清代前期的農業商品化和小農分化 /
20世紀資料中所見的農業商品化和小農分化 /
冀中、冀南和魯西北的農作物商品化型式 /
明清時期的棉花種植 /
農業商品化和人口增長 /
經營式農作和手工業的商品生產 /
第七章20世紀農業的加速商品化 /
中國農業和世界經濟 /
棉花種植的增長 /
棉花和世界經濟 /
棉手工業和世界經濟 /
變遷和延續 /
第八章經營式和家庭式農場的對比:耕畜的使用和農場生產力 /
滿鐵資料 /
耕畜使用的經濟 /
農場、牲口、肥料和純作物農業經濟 /
清代時期 /
第九章經營式和家庭式農場勞動生產率的對比 /
勞動生產率的對比 /
經營式農場上小組耕作的較高效率 /
貧農之背離合理經營模式 /
貧農農場上的就業不足和物質刺激力的遞減 /
第十章經營式農業何以發展不足 /
經營式農場通常在100畝以上的原因 /
經營式農場通常在200畝以下的原因 /
經營式農作和出租地主制的對照 /
經營式農作和社會政治體系 /
革新的可能 /
一個“高水準均衡的陷阱”? /
第十一章家庭式農場的牢固性 /
對土地的壓力 /
貧農農場收入 /
高利貸 /
家庭式農場和家庭手工業生產 /
家庭式農場和短工 /
家庭式農場和長工 /
第十二章生產關係的商品化 /
從分成租到定額租 /
分成租制 /
定額租制 /
地租負擔的比較 /
雇傭勞動 /
第三編村莊與國家
第十三章清政權下的村莊 /
華北平原村落的閉塞性 /
村莊各階層的相對閉塞性 /
20世紀前的村莊與國家 /
19世紀的自然村與士紳 /
宗族 /
自然村內生的權力結構 /
共同體領導抑或國家政權代理人 /
自然村和農民的集體行動 /
清代的經濟和政治結構 /
第十四章自然村結構的變化 /
自耕農和雇農的差別 /
婚俗中的階級差別 /
貧農的雙重性質 /
兩個緊密的村莊及其“封閉” /
部分無產化和村莊共同體的解散 /
分裂了的村莊 /
第十五章20世紀的自然村與國家 /
地方政府的軍事化和現代化 /
縣政府的財政 /
賦稅負擔 /
稅款的徵收 /
地方豪霸與村級惡棍的崛起 /
第十六章結論 /
農村演變的型式 /
貧農經濟的結構 /
經濟落後的根源 /
半無產化與人口趨向 /
半無產化了的村莊和20世紀的地方政權 /
貧農與中國的革命 /
附錄一滿鐵調查的33個村莊社會經濟輪廓 /
附錄二河北、山東人口(1393~1953) /
附錄三河北、山東耕地面積(1393~1957) /
引用書刊目錄 /
索引 /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