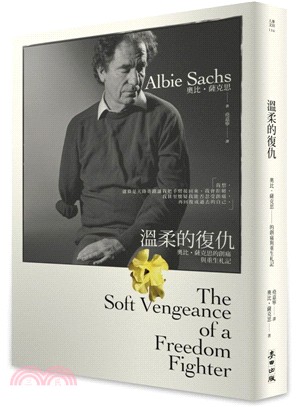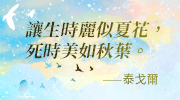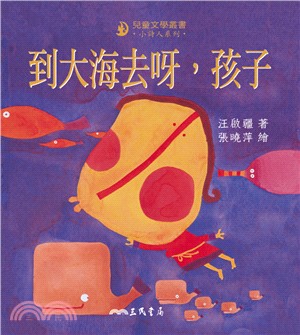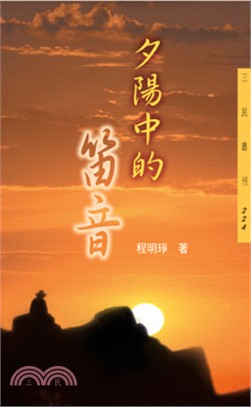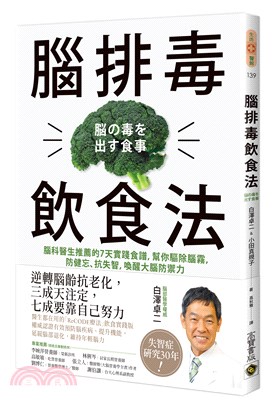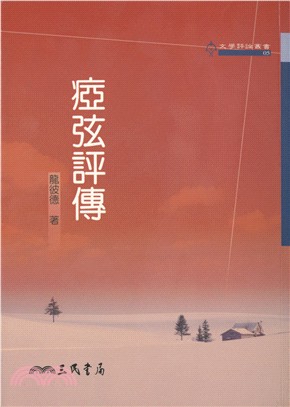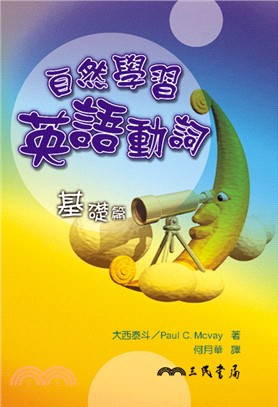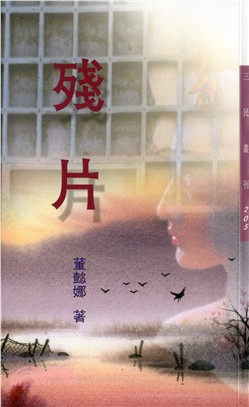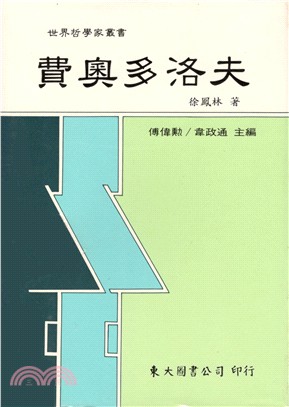商品簡介
◆二○一四年九月,本書作者薩克思因「提升吾人對法治之理解,對普世人權及正義所作出卓越之貢獻」,獲頒首屆唐獎法治獎。
面對恐怖、暴力與傷害,我們能如何回應?
破碎的身體與心靈,要如何再次挺立,勇敢向前?
當代憲法典範的締造者.唐獎法治獎第一屆得主「奧比.薩克思」
重回汽車炸彈攻擊現場,用最坦率誠實而詩意的文字,細述他的創痛與重生。
在《斷臂上的花朵》之前⋯⋯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想法,卻讓我感到極度痛苦。難道那就是我們奮鬥的目標嗎?一個充滿獨臂俠和獨眼龍的南非?這是自由的意義嗎?只有一種復仇能夠讓我的手臂不會白白犧牲,一種基於歷史的復仇:爭取到我們奮鬥的目標,讓我們的理想取得勝利。」
一九八八年四月七號,莫三比克,一個晴朗的夏末。長期反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奧比.薩克思忙裡偷閒,準備了啤酒與書,要到海邊去消磨時光。南非政府特務安置的汽車炸彈打斷了他的計畫,奪去了他的右手與左眼,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
「我不是一個受害者,我不希望能夠復仇、得到補償或是同情,我是自願投身於追求自由的奮鬥之中,原本就知道有某種程度的風險,但是我很高興我還活著,而且決定要重建我與這個世界的關係——積極而快樂的關係。」
沒有懊悔、沒有恨,在新的「短手臂」(薩克思堅持那不是「殘肢」)的陪伴下,他一面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一面反思生命與人權運動的真諦。
在《斷臂上的花朵》中對棘手的法律議題展現出溫暖智慧的奧比.薩克思,將在《溫柔的復仇》裡回到改變他一生命運的爆炸現場,完整、坦率呈現出他最內在的私我。各個參與他不凡一生的人物--父親索里、母親蕾、前妻史蒂芬妮、前女友露西亞、看護梅爾巴--也將在他的復健與重生中一一浮現
作者簡介
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退休南非大法官,一九三五年出生。在六歲生日前夕,奧比・薩克思收到父親的一封賀卡。信裡父親對他說,希望他將來長大能做一名為自由奮戰的鬥士。到了十七歲,薩克思開始了他一生為人權奮鬥的志業。二十一歲,他開始當執業律師,並致力於為受到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規定與戒嚴法侵害的人民發聲辯護,為此他得罪當局,並被國安警察盯上,被限制行動自由,甚至在沒有任何審判的情況下被非法囚禁。
一九六六年開始,他被迫流亡海外,流浪於英國與莫三比克之間,一九八八年遭受汽車炸彈攻擊,天幸大難不死。這是因為他在八○年代與南非的流亡組織──非洲國民議會(後來由曼德拉領導)──的領導人合作,為其制訂行動守則與相關內部條例。康復之後,他全心全意投入為南非草擬一部民主的新憲法。一九九○年,他回到南非,以憲法委員會委員的身分,協助南非推動民主轉型。
一九九四年,曼德拉當選總統,並指派薩克思做剛成立的憲法法院大法官。在十五年的大法官生涯當中,薩克思與其同僚為南非制訂了許多獨到且深具前瞻性與開拓性的法律判決,在人權保障方面甚至足以做為西方先進國家的表率。大法官卸任後,他經常在世界各國的大學與法律機關進行演講,分享南非的民主轉型與憲政成就。
二○一四年九月,薩克思因「提升吾人對法治之理解,對普世人權及正義所作出卓越之貢獻」,獲頒首屆唐獎法治獎。
序
#前言
我想,就算是天降奇蹟讓我把手臂接回來,我也會拒絕。有時候,我看著照片裡的自己,右邊的袖口空空如也,我會感到震驚。其實,當我走在顛簸的山徑,看著自己不完整的影子,我也會感到驚嚇。我已經完全熟悉自己的新形體,而且我也知道,即使我的意志決定扭轉生命的篇章,我的軀殼卻已經緊緊繫在我的國家這股向前去的衝勁上。我對於自己以現在的模樣存於世上,已處之泰然,我甚至懷疑我能否忍受創痛,再回復成過去的自己。當我看著自己「在爆炸案之前」的照片,其實也不是沒有任何問題。我愛那個年輕小夥子的正經樣─他有著茂密的長捲髮,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充滿幹勁,對於他明顯外露的同袍情誼,也忸怩的流露出渴望,那副充滿希望的態度──有時甚至會惹惱他的同伴,因為他們相信這會招來磨難,而不是榮耀,而當他們得知這個小夥子遭到汽車炸彈攻擊時,他們覺得自己一直以來最不祥的預感成真了。這值得嗎? ──對於這天,他們見如不見而問若未問──這是值得的嗎?
#一、爆炸
我罵了一聲髒話。突然間,所有東西變得漆黑一片,我覺得好奇怪,而且看不到任何東西。海灘,我是要去海灘的,我還帶了冰啤酒,要在跑步完以後喝呢,有哪裡不對勁吧。我又罵了一聲髒話,我好像撞到頭了,就像是我以前在開普敦爬桌山(Table Mountain)時常發生的事,我一邊夢想著奮力向上,另一邊,頭卻撞上了突出的岩石。會過去的,我只要保持冷靜和等待就好了。給熱帶植物的盆栽澆澆水,盯著我美麗公寓裡的巨大非洲塑像(它有十個頭)。噢,去你的,我怎麼這麼不小心呢? 黑暗還未消散,應該是出了一件嚴重的事,我發生了什麼大意外吧,我整個人在旋轉,無法保持平衡.當我在等待意識回復和重見光明時。我感到頸後受到重重的一擊,然後又是另外一擊。我感到一股威脅性,而且這感覺越來越強烈,我被什麼壓制住了,我不知所措。我必須戰鬥,我必須堅持。我覺得好像有一雙手臂從背後環抱住我。我被綁架了,他們從普里托利亞(Pretoria)來,要把我拽過邊界,審問我、監禁我。這是我們幾個還在莫三比克工作的非洲國民議會成員─一直在等待的時刻,雖然害怕,但也帶著某種莫名的急切。
「放開我」,我聲嘶力竭的吼著。「放開我!」
我用盡吃奶的力氣扭動肩膀、揮舞手臂。我總是在想:在那個時刻來臨時,不知道我會怎麼反應,我會以肉身盡力抵抗、冒著殉死的危險,還是我會保持安靜,靠我的腦子、和必須堅持的道德勇氣?
「放開我! 放開我!」我死命的嘶吼,又用英語,又用葡萄牙語(這個新獨立的國家、我住了十年的國家的官方語言)。在流亡二十年之後,我已經忘了南非荷蘭語,我竭盡所能的放聲大吼,不過還有一些節制,也維持禮貌,因為在名義上,我畢竟是一個中年律師。
「我寧可死在這兒,放開我! 我寧可死在這兒!」
我掙扎著,同時感到突然有股亢奮的感覺和力量,讓我用盡全身的力氣幫自己掙脫。我可能是個知識分子吧,但是在這個重要的時刻─沒有時間去計畫或者思考了,我也只能勇敢的戰鬥著,拿出索維托(Soweto)青年的勇氣─雖然我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暴力經驗,似乎是在學生時代抱著橄欖球、用擒抱摔倒對方球員。我聽到我背後有聲音傳來,是很緊急、緊張的聲音,不是在交談,而是在發布或是在接收指令,而且是關於我的事。
一片漆黑,不過我還是聽到間斷急促的對話。
「把他抬起來,放在這兒。」
我又不是什麼他,我是我,你不能把我像個箱子一樣拿來拿去。但是我沒法再掙扎了,我只能接受將要發生的事,我的意志慢慢起不了作用了。
我們移動得很快,路上坑坑窪窪的,他們也把我弄得太不舒服了吧! 如果他們要綁架我,至少可以用台彈簧好一點的車。我的意志已經消失了,我不能決定任何事,甚至連自己的身體都動不了。但是我還有意識,我想,所以我還活著。我一下子意識到自己在這兒、一下子又什麼都不知道,一下子好像昏過去了、一下子又清醒過來,我就攤在那裡,腦子裡有一點正在想什麼,但是待會兒又什麼都忘了,然後又清醒過來,我沒有在想要做什麼,但是很清楚的知道:我的身體正在被移動到什麼地方,我還活著,雖然我自己什麼都決定不了。我想著是不是已經到南非邊境了,我想知道綁架我的人是誰,他們長得什麼樣子,他們有名字嗎? 眼前一片漆黑,讓我什麼都不知道。
更急促的聲音傳來,他們講話時帶著快速的活力,對待我就像在對一個東西一樣,我被抬起來又被放下去,這樣移那樣挪────我可以感覺周圍的人碰到我的肌膚,以及他們在動來動去,在我的周圍、在我的上方、在我旁邊,又在我後面。好像沒有人把我當人看──看著我說話,或是和我溝通。我好像一團什麼,我有人形,但是沒有人格,我就只是別人決定的客體。他們彼此看著對方講話,但是沒有人轉過來對著我,我就在這裡,所有活躍對話的中心,但是我好像完全被排除在外,我的意志、我的存在都被侵犯了,好像就算在團體裡,我也是被排除在外的。
一切都是這麼沉寂而平靜,好像靜止不動、沒有聲音,也沒有人在活動。我被包裹在完全的黑暗和寧靜中了。如果我死了,我也不知道這件事,但如果我還活著,我也沒有感受到這件事,我什麼都不知道了,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我周圍的事,就是什麼(人或事)都不知道了。
「奧比……」,在黑暗中,有一個聲音對著我說話(而不是和別人談論我的事),他叫著我的名字, 而且不像其他聲音那樣急促到刺耳。「……奧比, 我是艾佛. 賈瑞多(Ivo Garrido)」,他的聲音很輕柔,讓人感到極富同情心,我知道艾佛,他是一位年輕優秀的外科醫生,也是朋友,」…… 你現在在馬布多中央醫院(Maputo Central Hospital)……我很遺憾你的手……」,他用了一個很委婉的葡萄牙語詞彙,來形容我的手臂,跟英國比起來,莫三比克文化實在是非常的細膩啊,我待會兒一定要問他那個字是什麼,」……我們要為你動手術了,你知道事實之後,一定要堅強起來。」
我沐浴在一種完全的滿足和平靜中,我現在是在莫三比克解放陣線(Frelimo)、在莫三比克政府手中,我安全了。
「發生了什麼事?」我向著黑暗提出我的疑問,聽到艾佛的聲音之後,我的意志回來了,我又重新存在了,我是一個活著的人。
有一個聲音在我耳邊回答我,我想是一位女性的聲音,「…… 汽車爆炸……」,然後我就睡下了,內心微笑著,進入夢鄉。
#六、前女友露西亞
她蜷曲在我的臂彎中,我的手好好的那一邊──也就是左邊,她靠我靠得這麼近,以至於我根本看不到她,只能感覺到她,她有可能是任何人,不,不是任何人,一定是位女性,這種肉體的柔軟和親密,我不太可能從一個男人身上感受得到,或是──我想──碰觸到。是露西亞。當她進來時,臉上顯著疲累和緊張──我注意到她戴著一雙可愛的耳環,那是她用我送給她的石頭做的--似乎沒怎麼睡,我也看到她的長黑髮上出現了灰髮。她把一個手提包放在我的床附近,我微笑了,極高興能與一個醫院外的人分享我生存的喜悅,她來自我所熟悉的世界,那個世界很大,容納了許多人和許多心情,而且還有其他活動──除了躺在這兒之外,我也很高興能夠轉換進那個世界,和張開口。她帶來了那個世界的感覺,也即將帶走我的感覺。看到我溫暖的微笑,她也快速的報以一個熱烈的微笑──在她開心時,總是閃過她的臉龐的微笑。接著,她走向我,主動而勇敢的抱住我,當我們在一起時,這種主動和勇氣總是使我非常的著迷啊。
我想要說點什麼,我想要告訴她什麼,但是在那之前,我想要用全心去感受。說到感受,女性優於男性太多了。男人會微笑著和你說話,用一些類似勇敢、堅強和奮鬥之類的字眼,但是跟我那隻搖晃的手臂握完手、用些簡單的開場白安慰我之後,他們會坐回椅子中,繼續用話語跟我交談。女人們則會走向前來,握住你的手、摩挲你的臉頰,將你的手繞過她們的頭、撫摸她們的頭髮,讓你感受到她們用全身給你的愛和安慰,同時你也會感到自己的溫柔散發出來。醫生的部分已經結束了,現在我需要的是盡可能的撫摸和溫暖。這很奇怪,我知道那些對我做的事並不是針對我,做這件事的人很可能從來沒有見過我,對我也沒有特別的感覺或恨意,但我還是覺得在這個世界的某處,存在著對我的強大惡意,而且,雖然我認為自己的存活是一種勝利,但我還是屈服於自己的原始需求──希望誰來肯定我有作為人的價值。我想要有人來摸摸我,我想要被慰撫、被愛,而不是聽別人說我有多勇敢,或是聽演講(雖然那些話真的很溫暖而且有同理心)……
露西亞,露西亞,妳來到我的身邊,幫助我,用妳的肩膀、手臂和面孔安慰我,愛我這個人,雖然妳的心裡有著別人。我想要擁有妳能夠給我的所有感染力和愛,幫助我,讓我不會覺得自己毫無價值、是應該從這個地球表面消失的一片垃圾、是註定要被消滅的。不管我的理智怎麼說,不管我有多高興自己還活著,我的內心深處還是感受到那個炸彈的侵犯性、我的存在帶來的衝擊,以及某種敵意正在策畫我的毁滅。救救我,救救我──雖然我什麼都沒說,但我的身體已經準備好要接受妳的溫暖──幫幫我,幫幫我,我們已經不再相愛,但是現在請陪在我身邊。沒有人會相信,如果我說論及單純的受苦、或是在情感上的苦痛,失去妳的愛,遠比失去我的手臂更讓我感到痛不欲生;托爾斯泰(Tolstoy)筆下的一位角色曾經說過──而且可能就是因為我在托爾斯泰的書中讀到,這句話才顯得如此深刻:誰能懂人的心呢?所以,拜託了,我的愛,我曾經愛過的人,就讓我繼續輕撫妳的頭、妳的髮、妳的臉頰、妳的頸子,而且如果妳找到我身上的什麼部位並沒有掩蓋在紗布之下,請妳也能永遠摩挲、撫摸這些地方。
她起身時,手輕輕滑過、並且撫摸我的手臂,她拿起放在我床邊的手提包,從裡面拿出一個小塑膠盒,我認得這個盒子,以前我們一起去海邊時,都是用這種盒子,裝沙拉帶去海邊的。露西亞喜歡實際的東西,她越感性,就越喜歡一些具體的安排。我剛好相反,我在某個時刻的感覺越強烈,就越不切實際。她打開蓋子,給我看裡面多汁的滷牛里肌肉,滷得棒透了,這是毋庸置疑的。她作菜的功夫是一流的,這也激勵我學好作菜,並且享受美食──其實我覺得這透露出我們的關係,我們會在生活中發現樂趣,享受美好的事物(為了美麗而美麗,沒有其他目的),買一些絲綢、耳環和黃金(噢,我就停在黃金了;就算是對不符清規的樂趣有極大的興趣,也還是有外在的限制);我們花了半生試圖建立戒律、和對自我否定,讓所有的小行動都受到教化,然後又竭力讓另外半個自我去除道德的束縛。全力奮鬥並且願意給出生命,並不代表我們一定要沒有自我風格、不帶感情,或是對任何樂趣都沒有熱情。
在政治上,她常常比我更嚴格,並且不願原諒,但是以社會性來說,在我們同居的這幾年,她顯然比我更寬厚、更帶有朝氣。現在,當我用左手拉她靠近我纏著繃帶的肩膀時,我感到心靈不再迷惑,我直覺的認為所有惡都屬於想要殺我的一方,而所有的善都歸屬於我的醫生、我的護士、警衛組、我的同志、我的朋友、我的家人、露西亞,當然還有──我自己。也許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一直覺得很快樂;我終其一生都在奮鬥,我的內心一直覺得每件事、工作、愛情、掙扎、家庭關係、甚至於我的樂趣,都脫離不了矛盾,而突然間,我的世界不再有矛盾和兩難,我的個人路線變得很清楚而開放,而且沒有情感的壓力;他們想殺我,但是失敗了,就是這樣,我只需要變得更好,這就是我個人的、美好的、純潔的、政治的、公眾的、而與我最緊密的目標。
「我不吃」,我說,一邊看著那小塊肉,但是沒有胃口。
她看起來很驚訝。
「對我來說太多了。」
她其實是特別為我做的,以為我一定會喜歡她的體貼。我們有點像是在互吼,我的聽力有點受損,雖然我只是想柔聲說話,但我感到自己的聲音有點像在命令。
「一個半熟的蛋,煮三分半鐘,再加上一點香茅茶,我就只想要這些。」
她笑了,就在我的後面跪下,我知道她是要親我。不能親我的嘴唇啊,那太性感了,不能親我的鼻子啊,那太可笑了,但是我其他地方都纏滿了繃帶。她的嘴一邊往前,最後剛好落在我的脖子上,一小塊裸露的皮膚。經過這種種之後,我感受到她的嘴唇那柔軟而令人感到十分舒服的重量。
「我們還以為你已經死了。」她喃喃的說。
#二十一、該不該赤裸?
玫瑰,數也數不清的粉紅色、紅色、緋紅色和鮮紅色的玫瑰,一大叢一大叢的,又有橘色、黃色和白色,無盡的延伸到眼睛可見的遠處,多到不像真實的真實景像,就在我的眼前延伸出去,我坐的長椅爬滿了高高低低的爬藤,周圍點綴著美麗的小花,我的肩膀上是一大堆小小的玫瑰,帶著非常……玫瑰的顏色。
我得趕快作出決定,而且這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將會大大影響我的未來,但是讓我先往後在長椅上躺一會兒,好好享受我的第一次日光浴。當約翰的同居人建議我們一起來這攝政公園(Regent's Park)的玫瑰花園時,其實我很不情願離開屋子,但是我找不到任何好理由拒絕她的提議。我穿上了瑪格麗特買給我的淺綠色運動服,這是一種鮮明的、適合春天的顏色,一瘸一瘸的,穿過擠在公園入口旁邊的人群。約翰和露西亞(是的,她也叫露西亞)手挽著手走進了公園裡,留我在後面,因為我要求這樣──這是我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坐在大眾公園的長椅上。
我其實還不太習慣坐進車裡,然後去一個景點。在開普敦,至少在我有幸得以居住的地方,到處都有美景,你只需要選擇今天想去海灘、山上,還是兩個都想去。如果你想要帶著烤餅和奶油去的話,車子是很重要,但車子不是為了把你帶到一個漂亮的景點。總之,這就是倫敦,美是被營造出來的,就像其他東西一樣,而且我在這裡享受世界上的奇景之一——一大堆早夏的英國玫瑰,開在倫敦中心一個美麗的英式公園中。太陽不算很大,但是讓我感覺身體暖和了起來,而且給花瓣上了一抹明亮的顏色,照亮了一堆顏色擠在一起的陰影,變成了粉色上的白色線條、鮮紅色上的一絲淡紅色、橘色上的黃褐色斑點。孩子們在玫瑰花圃之間的草地上奔跑,藏在灌木叢之間,他們的父母在後面追著他們。有許多照相機——美不能只被感受,還必須要被捕捉(我們從來不帶相機到山上),而且有許多遊客應該是日本人,用一種安靜而低調的方式觀賞著。每個人都很放鬆,從容而緩慢的走著,完全在享受這個花園的美景,大家共通的有著一己的樂趣,所以似乎沒有人看我。
只是坐著,很有趣但是也很無聊。我對於身處室外感到很陌生,還不太習慣這些聲音、動作和顏色。我沒辦法休息,這次與外界的相遇非常艱難,我並沒有做任何事,只是在經歷。問題在於……
問題在於我究竟要不要脫掉我的運動服。我真的很熱,幾乎有點不舒服了,而且我想要讓陽光直接曬在我滿是瘡痍的皮膚上。但是我的手沒了,而且很醜陋。我想,以我自己來說,我並不在意;讓人們看吧,我可以承受。我的身體就是這樣,我也沒有打算隱藏什麼。人們確實注意到有什麼不太對,有什麼東西不見了——嗯對,有一隻袖子裡沒有手了。他們沒有停下來看,或者是說什麼,但是他們注意到了,我知道。(我想起我的非洲國民議會同志曼格茲[Manghezi]說他第一天在哥本哈根搭公車時,有一個孩子指著他,他的母親叫他閉嘴,而我也想起一位黑人南非護理師,說她在一個法蘭克福診所作血液檢查時——整個房間裡的人都盯著試管,似乎覺得氣泡應該向下,而不是往上。)只有孩子們會直接盯著我的手看,這讓他們的父母覺得很尷尬,而我則覺得很有趣;我想要和他們說話,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我相信他們不會被嚇到,而是會被吸引,因為我(可能像個孩子)是這樣的。進這花園時我走得很慢、我的拐杖、我那剪短的頭髮,這些都標示出我是一個殘疾的人,這應該讓經過的人比較容易理解這幅景象。而我坐下時就比較複雜了。我好像只是一個安靜坐在長椅上的人,看不出來是一個正在復原的病人,所以當路人看到我的獨臂時,他們會更加感到驚訝。
所以問題不在於我的感受,而是這個花園的訪客們的感受。他們想來這兒看美麗的事物,而不是一隻殘缺不全的手臂,他們有權享受視覺上的平靜,不需要看到醜陋的事物。這就是我的難處——我到底有沒有權利,讓這些選擇午后來常花的人們,必須看到我殘缺不全的手臂。
從一方面來看……或說另一方面……難道我是為自己找了另一個麻煩嗎?我想不是的。這是我自己真的必須面對的問題,並且要找出我內心真正相信什麼才是對的事。這關係到我與外界、與其他人、與社會大眾的整體關係,我必須要自己釐清,並且導正這層關係。我今天出門的時候,以為我是來看玫瑰的,沒想到我要作這麼重大的決定,要決定我將如何重新融入這個世界。也許所有的重大變遷都像這樣吧,它們突然之間就發生了,而你只好在毫無準備的狀況下回應。這件事其實比較無關乎我的殘疾,而是與我的醜陋比較有關,我的外貌會造成別人的不舒服,而我必須決定我對這件事情應該有多少敏感度。
我到底應不應該呢?你不可能把衣服脫到一半,要不就是脫,不然就是不脫。不可能等到我再壯一點、而且比較常外出時,再來決定這件事。到時候的問題還是一樣;這基本上是一個道德的問題,是根據我怎麼看自己而決定的,與經驗無關。這次激烈的自覺、對於思考的檢視,讓我不太自在。我在想的不是那個決定本身,而是要怎麼作決定。是要用我的腦袋、我的意志、還是用我整個身體來作這個決定呢?
突然之間,我想到我要怎麼做,而且為什麼這麼做了。這不是一個經過徹底思考之後的結果,我應該停止思考,讓直覺來作主,我也許會怕怕的,但是會很確定,感覺可以總括我的意志、身體和腦袋,但是不會依賴其中一個,它可以綜合過去的經驗、情緒和想法,但是不會把各種成分混雜在一起,它只會是一個單一的信念。
我又再往前彎一點,把衣領拉過我的頭頂。然後熟練的把我的短臂拉出捲起的袖子,按住上衣的下襬,把整個右半邊拉出頭頂。我的左手還在袖子裡;我把袖口咬在嘴裡,猛地把袖子脫掉,我頓時覺得涼快多了,而且陽光直接照在我的皮膚上,我覺得舒服多了。我還穿著汗衫,它蓋住了我大部分的傷口,我看得到的皮膚十分蒼白,而且像張地圖一樣坑坑疤疤的。我把脫下來的衣服摺起來,放在我的背後,給我一些支撐,現在我看到我的短臂最後用線縫起來的皮膚,並不太美觀。
我重新在長椅上坐好,盡情享受太陽照在皮膚上的刺痛感。人群依然熙來攘往,沒有更或比較不注意我。大多數遊客是日本人,我不太容易讀懂他們的表情,不是因為他們莫測高深,而是因為他們太有禮貌了。一對年長的夫婦走過來了,臉看起來像英國人。他們會坐在我隔壁的那張長椅上嗎?他們走過來了、走過來了,並且坐下來了,繼續著我剛才看到他們時,他們在進行的對話。我知道他們有看到我的手,但是似乎沒有很在意。我閤上眼,讓自己作作白日夢。我的直覺是對的。如果我自己的心裡覺得氣勢很弱、很可恥,我的行為和肢體語言就會洩露出來;如果我對自己的現狀感到很自豪、很自在,我便可以接受自己,而且這個世界也會知道這件事。勝利了,我走過來了,而我感到最開心的事,是我竟然在玫瑰叢中,作出了或許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一個決定。
目次
唐獎基金會讚詞:充滿驚嘆號的一生——陳振川
推薦序(一):破碎與重生——宋承恩
推薦序(二):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單德興
序——德斯蒙德.屠圖
導讀——努亞布羅.努德貝拉
前言
二〇一四版前言(待補)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後記
二〇一四版後記(待補)
尾聲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