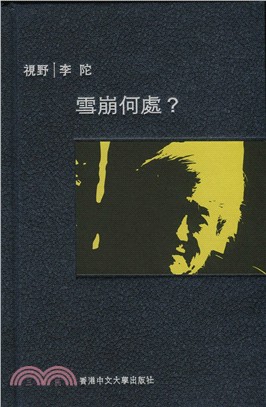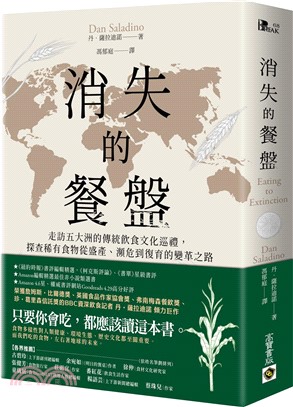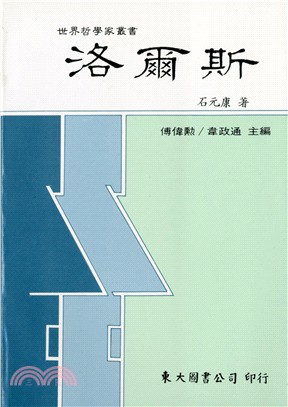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寫在前邊的話
回顧自己過去寫過的文字,很像一個人回顧自己的一生。不過,回顧自己的生平和回顧自己的文字,有很大的不同。在記憶裏看自己的過去,很難不帶感情,動情之下,記憶中的圖畫很不穩定,有些輪廓會變形,有些色彩被顛倒,甚至被完全塗改。回顧自己寫過的東西就完全不一樣了,因為你面對的是文字,它們像一塊塊黑色的花崗岩嚴嚴實實地堆砌在一起,結實,牢固,堅硬;感情在它們面前,就像是海濤衝擊礁石,浪花可以飛濺得很高,但是被水清洗後的石頭,嶙峋依舊,只能更加結實和堅硬。
大概是出於對文字有這樣的敬畏,面對自己過去的文章,會經常產生一種很強的疏離感,我常常疑惑:寫了這些文章的人,是我嗎?是不是另一個人,是另一個叫李陀的人?
這樣的錯覺有個好處,就是你有機會成為自己文章的旁觀者,可以平心靜氣地檢討這些文字的得失,而且,也能夠借這機會觀察一下自己,不只是文章的好壞對錯,還有思想的變化和發展,特別是,走過什麼岔路,經歷什麼曲折,在什麼地方撞牆,在什麼地方迷途知返,又從哪個路口停了下來,耐心地為自己畫出一個新的地圖,然後再出發,再探索──如果沒有鋪在路上的那些堅硬的文字,你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現在,當我要把過去的一些文章結集起來的時候,一直很猶豫,不知道該用一個什麼線索、什麼理由,把這些文字挑選、組織再串聯起來?最後,還是堅硬的文字提醒了我──為什麼不盡可能做一個自己的旁觀者呢?當然,這樣的「旁觀」,不可能完完全全真地站在一旁來「觀」,儘量吧。
依照這個原則,我這裏彙集起來作為第一部分的文字,不是我在報刊上的文章,而是一組網絡上的帖子──那是2005年,在陳村主持的網站「小眾菜園」上,我和吳亮有一場相當激烈的論戰,兩個人從那年的5月開始,你來我往一直吵了一個多月,在當時很熱鬧了一番。
李陀
目次
ix 「視野叢書」總序 北島
xi 寫在前邊的幾句話 李陀
第一部分 在小眾菜園上的九個帖子
3 吳亮致李陀(2005 05 26)──我對文學不抱幻想
9 李陀致吳亮之一(2005 06 02)
23 吳亮致李陀之二(2005 06 03)──論私人化寫作的公共性及社會性
27 吳亮致李陀之三(2005 06 04)──我們,期盼,以及迷惘
31 吳亮致李陀之四(2005 06 06)──壓迫、反抗、以及批判
35 也說壓迫、反抗和批判──再答吳亮(2006 06 14)
51 吳亮致李陀(2005 06 15)
53 吳亮致李陀(2005 06 15)
55 李陀致吳亮(2005 06 16)
第二部分 八十年代的五篇文章
61 意象的激流
69 閱讀的顛覆──論余華的小說創作
77 昔日頑童今何在
83 也談「偽現代派」及其批評
99 1985
第三部分 從哪裏開始轉向
123 雪崩何處?
133 現代漢語與當代文學
149 丁玲不簡單──革命時期知識分子在話語生產中的複雜角色
181 汪曾祺與現代漢語寫作──兼談毛文體
第四部分 一個新視野:大眾文化研究
225 開心果女郎
237 「大眾文化研究譯叢」序
243 失控與無名的文化現實
第五部分 關於九十年代的大分裂
261 讓爭論浮出海面
273 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裏?
第六部分 三篇評論,一篇序言
295 一隻色彩斑斕的牛虻──喜劇《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觀後
307 腐爛的焦慮──評格非短篇小說《戒指花》
321 徐冰,現代藝術的叛徒──評大型裝置作品《鳳凰》
333 《波動》序言──新小資和文化領導權的轉移
書摘/試閱
雪崩何處?
漢語裏原本沒有「阿Q」這麼個詞,它是
希望以上這些說法不要引起誤會,似乎我認為「阿Q」這一詞就能整個地改變中國人的觀念。我只不過舉一個例子,想說明文學作用於生活的複雜性,或者說作品──讀者相互作用的方式的複雜性。許多年來,中國的讀者以及評論者形成了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認識:如果讀者由於讀了一部作品而產生某種思想波動,甚至改變了對事物的看法,那主要是作品所包含的思想主題對他發生了作用。至於作品的藝術性,例如語言的優美動人,雖則也能影響讀者,那主要是審美趣味上的陶冶,其作用遠不能與「內容」的作用相比。但是這樣認識作品-讀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實在是太簡單,也太片面了。這種看法的一個主要缺陷,就是完全忽視了文學作品通過語言層面的種種運作,來影響、改變人們的言語行為中的詞語系統和語義系統,並進一步影響、改變人們的思考方式,乃至改變深層心理的可能性。
實際上,自有文學以來,文學作品從來都是一方面通過藝術形象所蘊含的意義,和具體的讀者發生聯繫,一方面又通過不斷破壞語言的實用性、常規性,從而以語言的創造活動和一般人(不論是不是讀者)發生聯繫──這種聯繫對人類至關重要,因為語言的更新,歸根結柢意味着世界的更新。當然,反過來,也正是保存在古典文學中的那些昔日的語言,使我們能面向歷史,使我們精神的根能夠伸向遙遠的過去。但是,多年來我們很少以這樣的眼光來看待文學的意義。時至今天,無論在文學史研究領域,還是在當代文學評論的領域,能夠從文學語言符號和一般語言符號的關係切入來討論文學意義的人,可以說少而又少。然而,如果這樣的狀況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並沒有成為什麼問題,至少在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之間沒有形成尖銳的衝突,那麼,自1987年以來的文學發展已經使這種狀況的延續成為不可能。因為兩年的時間雖不算長,但是又一批年紀輕輕的作家異常迅速地成熟起來。他們寫出的許多中短篇小說,正在劇烈地改變着中國當代小說的面貌,形成新的文學圖景。自1978年以來,中國文學一直處於不停的激烈變革當中,「變」似乎已經成為一件尋常事,然而這次變革卻有着非常的性質和意義:它使我們看到了一種新的寫作方式和寫作態度。這樣的寫作態度不僅使語言在文學活動中真正上升為第一位,而且試圖從根本上改變作品-讀者、文本-批評、文學-社會之間互相作用的關係。
如果要觀察、研究文學發展的這一動向,我以為首先要注意的作家是余華。
自發表《十八歲出門遠行》以來,兩年左右的時間裏,他以一連串實驗性很強的小說(《一九八六年》、《河邊的錯誤》、《現實一種》、《古典愛情》、《世事如煙》等等)在文學界引起一連串的驚異。無論是愛好文學的一般讀者,還是以閱讀為職業的批評家,在余華的小說面前禁不住都要如此發問:為什麼要這樣寫小說?這樣的疑慮和追問是不奇怪的,甚至是必然的。因為這裏使人陌生的,不是小說的某些風格和技巧,而是作家的寫作方式和寫作態度──如果說近幾年的文學發展已經產生了一種新的寫作方式和寫作態度的話,余華無疑是一個突出的代表人物。
我很難忘記第一次閱讀《十八歲出門遠行》時的種種感受。那是1986年11月,一個如以往一樣光禿禿的寒氣凜冽的冬天(其時《北京文學》正在一家服務低劣又髒兮兮的旅館中舉辦一個「改稿班」),編輯部的傅鋒鄭重地向我推薦了一篇小說,即余華剛剛寫出的《十八歲出門遠行》。由於我當時正沉浸在1985年新潮小說勝利進軍的喜悅裏,從韓少功、張承志、阿城、馬原、莫言等人的小說中所獲得的閱讀經驗,不僅使我激動不已,而且已經成為什麼是好小說的某種標準,進入了我的「前理解」,從而也控制了我的閱讀。然而《十八歲出門遠行》的閱讀,卻一下子使我「亂了套」──想不到,伴隨着那種從直覺中獲得藝術鑒賞的喜悅的,是一種惶惑:我該怎樣理解這個作品,或者我該怎樣讀它?《十八歲出門遠行》發表於1987年1月號《北京文學》,而且是「頭條」。當我拿到刊物把它重新讀了一遍之後,我有一種模模糊糊的預感:我們可能要面對一種新型的作家以及我們不很熟悉的寫作。
後來余華以他的一系列作品證實了我的預感。我對他的寫作的追踪和關切,也成了我對自己在寫作閱讀上所持的習慣立場和態度進行不斷質疑的過程。這些質疑,已經改變了而且將來或許會更根本地改變我對人的寫作和閱讀這類活動的看法。這裏我不能詳述這些改變的方方面面和種種細節,但是有一點應該特別強調,那就是:我認為余華的小說從根本上打破了我們多年來所習慣的文學與現實生活、語言與客觀世界之間的關係的認識。余華自己說:「我覺得我所有的創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實。我的這個真實,不是生活裏的那種真實。我覺得生活實際上是不真實的。生活是一種真假參半、魚目混珠的事物。」余華的這種態度滲透在他的每一篇小說裏。這使得他的小說不僅不再是他自己以及他的讀者「認識」生活和世界的一個窗口,不再是現實生活的某種反映,而且可以說與現實世界
沒有多少實在的關係。小說在余華手中成為一種以語言構成的自足的實體,語言在他的小說中已不再是為了傳達、表現什麼,其重心已不再是某種與現實有一定關聯的實用功能的實現。余華關心的是語言自身,是如何推動、幫助語言完成自我目的化,即把語言符號的美學功能,推向極致以後看看究竟能形成什麼樣的文本。我猜想,余華也時常會為自己的語言魔術的結果,感到驚異,感到意外。但不管怎麼說,只有以這樣的態度操縱語言所形成的文本,對余華才是「真實」的。他只認可這種真實。因此,余華不關心現實生活中的真實,認為「實際上它是一片混亂」,作家對所謂「真實」都不過是某種符號編碼所賦予事物的一定秩序。作家對這一點似乎已徹底了悟,雖然他沒有用符號學的概念對此進行表述。對寫作這件事持這樣一種態度,在西方或許已不是什麼特別新鮮的事,但是在當前的中國,它卻有着非常革命的意義。實際上,由於前有馬原、殘雪的開闢,後有余華、葉兆言、格非、蘇童、孫甘露、北村等人的發揚,這種寫作態度已經造成中國當代小說的又一次革命。
這個革命的第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出現了新型的文學。這裏我不能不援引羅朗.巴特的某些看法。羅朗.巴特認為文學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種是讀者的文學。屬這類文學的作品,往往都是以規範的語言和規範的藝術程式寫作的,其「能指」和「所指」的聯繫,是清楚明白的,因此讀者的閱讀是沿着一條熟悉平坦的冰道痛快地滑行,但這種舒服的閱讀的結果是有代價的,那就是讀者做了文本的俘虜,他除了被迫接受潛在於作品中的思想傾向和意識形態之外,別無選擇。另一種文學則是作者的文學。屬這類文學的作品,由於作者並不遵循已有的語言規範和寫作規範,其寫作活動的首先目的就是打破既成的語言秩序,從而不僅對已有的各種文學的和文化的編碼方式提出質疑,而且把寫作活動變成探索,變成創造一個新的世界的充滿危險而又令人振奮的過程;讀這樣的文本,讀者就必須有強烈的參與意識,把面前的文本當作是一個半成品,是一個尚待實現、需要相當困難的努力去重新建構的東西。總之,這時候讀者要和作者一起高舉反叛的旗幟。回顧一下中國幾十年來的文學發展,我想我們只有前一種文學而無後一種文學是顯而易見的。當然,之所以會如此,有着深刻的現實及歷史方面的原因。對這些原因進行研究將會饒有興味,並使我們有可能重新認識中國現當代的文學史。不過眼前的事是:由於有了余華等一批新型作家的出現,我們已經有了羅朗.巴特所說的作者的文學。我以為這是文學上一件很大的事情。因為,如果說自進入八十年代以來,當代文學的發展對幾十年形成的「工農文學」這一格局形成了破壞性的衝擊的話,那麼,作者的文學的出現,可以說是工農文學時代正式結束的標記。一種新的文學格局正在形成,例如嚴肅文學 / 通俗文學、先鋒文學 / 傳統文學、作者的文學 / 讀者的文學等兩分都是對這個新格局的某個側面的描述。今天許多人,特別是一些批評家之所以對當前的文學局面表示失望和悲觀,甚至做出文學進入「低谷」、先鋒文學陷入「困境」的或深為惋惜或幸災樂禍的批評和判斷,其原因之一,恐怕正是對這一文學新格局有困惑或反感。
新的寫作方式帶來的第二結果,是作家對語言的新態度引發了又一次的「語言的解放」。這或許比第一個結果更有意義,也更有深遠的影響。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我當然不以為這種「語言的解放」只是由作家們發動,並只侷限於文學範圍的一個運動。實際情形當然要複雜得多。特別是,考慮到毛澤東長達幾十年的寫作所形成的詞語體系的無所不在的影響,考慮到這種「毛文體」在現代漢語中所實現的大一統的空前局面,以及它對一切以現代漢語作符號的語言領域的絕對控制,所謂語言的解放,當然絕不只是涉及語言學或文學寫作領域的事,參與其事的人,當然也絕不只限於一些作家。但是無論如何,如果我們認真回憶1978年以來文學的發展,則應該看到並且承認,對「毛文體」的一統天下的衝擊,畢竟首先是從文學領域發動、並且率先在文學領域中取得成效的。例如當年的「朦朧詩」之爭,其實是由詩人們對「毛文體」的冒犯引起的,只是爭論雙方當時對這一點都不甚自覺而已。今天,這一段公案已成歷史,「朦朧詩」的地位和成績已得到大體公正的評價。但是,「朦朧詩」的作者們對變革現代漢語的現狀的巨大功績,評者似乎還沒有給予充分的注意。這或許和我們文學發展的實際水平對人們的注意力的限制有關。很長時間以來,無論談到文學語言或一般語言,人們都已經十分習慣在修辭學或一般意義的文體學的層面上進行論說,但是,今天情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例如余華以及葉兆言、格非、孫甘露等作家的寫作,已和以往的寫作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他們的寫作活動中最重要的,不是他們對現實的態度,而是對語言的態度。這樣的寫作不能不對現代漢語產生深遠的影響。「五四」的白話文運動開創了現代漢語的新紀元,也造成了現代漢語多面多向發展的可能性。我們只要比較一下魯迅、郭沫若、謝冰心、沈從文、徐志摩、李金髮、茅盾、巴金、老舍、聞一多諸人的各自成體的詞語系統,只從印象中也可以看出,那時的現代漢語的發展是多麼輕鬆活潑;我們也就不奇怪,為什麼那個時候會有那麼多色彩鮮明、性格各異的有趣人物,這些人為什麼又能發明那麼多或新鮮有趣或稀奇古怪的思想。那麼,今天會不會再一次重演這樣的局面呢?我想有一定的可能。有着新的寫作態度的青年作家們,無論在語言實驗的自覺性上,還是在進行這種實驗時所必需的有關語言操作的具體經驗上,都有着比他們的前輩更好的條件。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對現代漢語的發展和發明做出影響深遠的、意義重大的貢獻。只要一想到世界上有着十幾億人使用漢語,再想到人的思維以及人的歷史創造活動怎樣受着語言的控制和制約,這樣一個事業真是激動人心。
這當然是一個十分艱難的事業。
但是想想余華今年才27歲,他的許多同道也都不足30歲(聽說葉兆言較大,但也只是三十出頭),我們就又充滿信心。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無庫存之港版書籍,將需向海外調貨,平均作業時間約3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縮短等待時間,建議您將港書與一般繁體書籍分開下單,以獲得最快的取貨速度。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