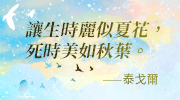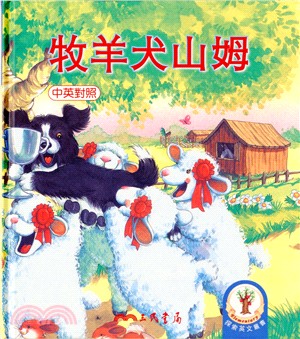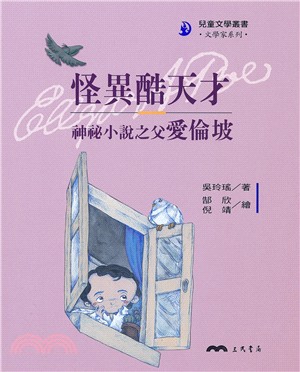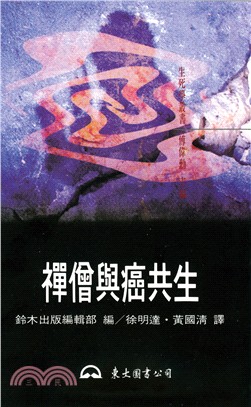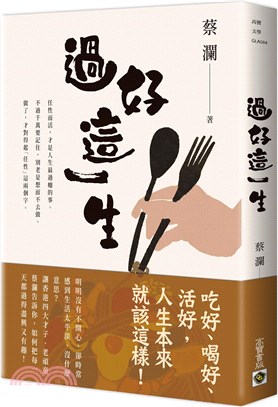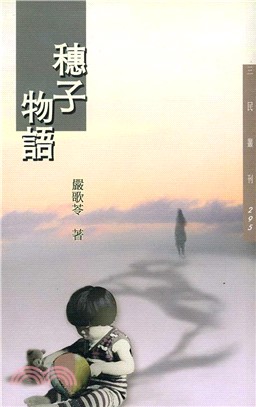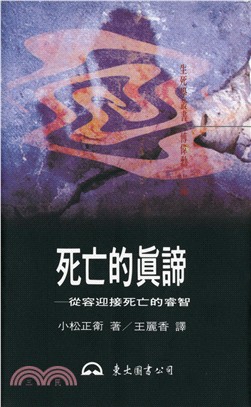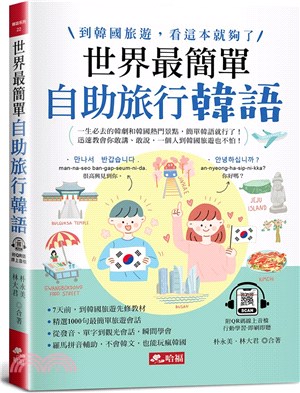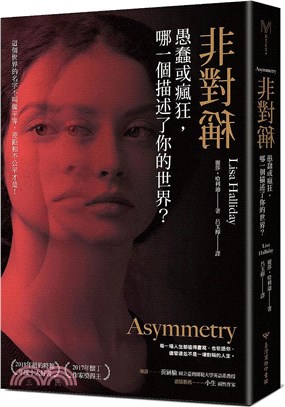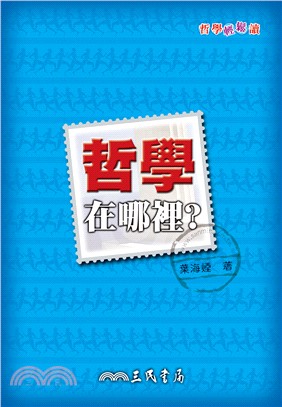商品簡介
◆高人氣作家 淡櫻 全新抒寫古代女核雕大師曲折的奮鬥歷程與盪氣迴腸的恩怨情仇。
◆網路原名《小藥妻》
“我非聖人,無辜又與我何干?”
“到底什麼與你有幹?”
“你。”
聖上覺得她配不上微臣,微臣願舍侯爺之名,棄一生榮華,只換一個她。
當皇帝的人,都是高高在上,脾氣自然不會好,可我不一樣,脾氣壞為了你我願意改。
我是聖上手裡的刀,剷除政敵,蕩平動亂,守護大興這片錦繡山河。現在除卻山河,我想要守護的還有你。
她手裡有一把刀,雕得是桃核,是人心,抑或恢弘壯闊的大好河山?
“永平有個說法,七夕之夜一起放花燈的人會一生一世糾纏不清。方才你與我放了三十八盞花燈,”穆陽侯緩緩抬眼,看著她,“我們有三十八世纏在一起,你無處可逃。”
傳聞,穆陽侯嗜血成性,恃強淩弱,常年攜帶“飲血鞭”,令人聞風喪膽。
阿殷從未想過有朝一日會被這樣一位侯爺纏上。
彼時,她只是一個爹不疼、娘不愛的姑娘,僅有祖父傳下的核雕手藝傍身。
所幸,她生對了年代,這是一個重核雕的盛世。
從一介默默無聞的平民到名震天下的核雕師,途中的辛酸阿殷從不在意,她在意的是自己手裏雕核的刀以及那一個孤高自傲的侯爺。
作者簡介
淡櫻
90後作家,現居上海,正努力追逐自己的夢想。文章構思新穎,擅長多種題材,文風溫暖甜蜜。至今已簽約出版多部小說,銷往大陸、港臺、海外。
科幻懸疑新坑《我的畫風不太對》在晉江文學城連載。
代表作:《長恨》《師父別來無恙》《以寵為名》《雕心引》等。
即將上市:《仙媚》
微博:@淡櫻
微信公眾號:danying717
目次
第二章初露鋒芒 / 17
第三章侯爺有請 / 42
第四章為君侍疾 / 64
第五章高山流水 / 93
第六章鬥核大會 / 116
第七章最終回合 / 140
第八章跟我回去 / 173
第九章綏州拜師 / 212
第十章侯爺歸來 / 243
第十一章進入核學 / 269
第十二章黃雀在後 / 296
第十三章何為情傷 / 323
第十四章前往永平 / 350
第十五章站穩跟腳 / 395
第十六章情意漸濃 / 418
第十七章風波悄起 / 443
第十八章貴人相助 / 466
第十九章陰陽二蠱 / 486
第二十章執子之手 / 502
番外一成親 / 524
番外二婚事 / 532
後記/ 536"
書摘/試閱
第一章:陰錯陽差
傳聞穆陽侯隨身攜帶一鞭,名為飲血鞭,不管對方是何等身份,脾氣上來時先抽了再說。
正值早春時節,恭城的桃園結了新果,青青澀澀的小果子掛在樹枝上,翠瑩瑩的,像極了圓潤的小碧玉,地上還有些桃花瓣,粉白粉白的,宛如豆蔻少女臉頰上的胭脂。
一雙棉鞋踏過花瓣,杏色繡海棠花的裙裾輕輕揚起。
是一個生得如花似玉的姑娘,兩道柳葉眉彎起,黑漆漆的瞳眸漾開一抹嬌羞。她忽然停下腳步,撫平衣袖上的褶皺,隨後又輕撫烏髮上的發簪,生怕有一絲淩亂。
薑璿低笑出聲:“即便西施在世,見著阿殷姐姐也只能自慚形穢。”
阿殷嗔她一眼,佯作惱怒地捶她一下,說:“就懂得笑話我!”
薑璿眺望遠處,只說:“是妹妹的錯,妹妹自罰在此處替姐姐把風,好讓姐姐與謝郎敘舊。”“敘舊”兩字話音拖得老長,頗有調侃之意。
阿殷哪會聽不出,只是此時時間緊迫,她又嗔她一眼,提起裙裾匆匆走入桃園深處。
“阿殷!”不遠處的青年眼睛倏然一亮,三步並作兩步地行到阿殷身前,他眉目俊朗,上下左右地打量著眼前的姑娘,目光中有著說不出的歡喜。
阿殷抿唇笑道:“傻呆子!”
謝少懷被她這麼一喚,跟著傻笑:“嗯。”
五年前第一眼見到她,他便像是著了她的魔——美人如雲,可他只想娶她。
“阿殷,我母親終於鬆口了,明日便遣媒人去殷家提親。”
阿殷聞言,不由得一喜,道:“當真鬆口了?”
她家只是小門小戶,家中有點積蓄,還是當年殷家祖父行商得來的,而謝郎卻是恭城縣令的嫡幼子,正所謂士農工商,她又是萬般不願做妾的,因此兩人雖情投意合,但直到阿殷長成雙十年華的大姑娘,婚事仍然遲遲未訂。
謝少懷頷首,說:“等提親後,我便立馬求母親挑個好日子,迎娶你過門。我們盼了這麼多年,終於等到這一日了。”
阿殷眉開眼笑,說:“瞧你猴急的。”
他握住她的手,不願鬆開:“阿殷是少懷心中的朱砂痣,少懷哪能不急?”
兩人又說了會兒體己話,直到薑璿忍不住前來催促時,兩人才依依不捨地分開。謝少懷目送阿殷離去,目光癡癡,仿佛無論如何都看不夠。待阿殷消失在他的視線裏後,他方惆悵地歎了一聲。
他母親之言歷歷在耳:“……她給你灌了什麼迷魂湯?那殷氏也不想想自己是何等身份,嫁入我們家做妾已經是抬舉了她,還妄想當正妻?兒啊,她若真想進我們謝家的門,真心想嫁給你,當妾她怎會不願?唉,別跪了,起來起來,娘怕了你……這樣吧,正妻是不可能的,但以正妻之禮迎娶過門卻也不是不行。你是我們謝家的嫡子,正妻之位自是不能給殷氏。殷氏的母親倒是明理之人,我已遣人指點了她母親。你瞧瞧,她女兒都是大姑娘了,有人娶已是上輩子燒了高香,何況還是我們這等人家。你聽娘說,等她入門後,生米煮成熟飯了,她想反悔也不成。”
他喃喃自語:“但願阿殷別惱了我。”
桃園位於桃山。
桃山以前喚作恭山,後來被綏州上官家買下後,改了名兒,才喚作桃山。阿殷自小隨祖父出來野慣了,對這座桃山格外熟悉,知道許多小徑小道,輕車熟路地避開了守園的幾位小廝,與薑璿一道下了山。
天色將黑,阿殷卻走得不快。
薑璿說:“姐姐,再不走快一些,恐怕夫人會不高興。”
阿殷仿若未聞,似是陷入了沉思。
姜璿察覺到阿殷的不妥,輕聲問:“姐姐怎麼了?可是與謝郎爭吵了?”
阿殷回神,輕輕搖首,隨後苦笑一聲:“恐怕遲早也要吵了,方才謝郎話語裏頗有躲避之意,若我猜得不差,想必我與他的婚事沒那麼簡單。”
薑璿啊了一聲,問:“姐姐此話何解?”
阿殷道:“謝郎為人單純,幾次與我不合皆與他母親有關,此回定是他母親與他說了什麼。這門婚事,謝郎母親不可能這麼早鬆口的。”
薑璿好一會兒才明白過來,驚詫地道:“姐姐的意思是謝郎母親應承這門婚事了?”
阿殷搖首:“其中必有詐,只是我卻有一疑惑,聽謝郎的語氣,似是爹娘這邊已經首肯,可母親向來不願我做小的,她不可能會應承的。”
阿殷回到家中時,天色已然全黑。
殷家人口不算少。殷家祖父離世後,兩房分了家,大房人口多,置辦了一個兩進的院落,位置極偏,磚磚瓦瓦雖破舊,但在阿殷母親秦氏的打理下,也算井井有條。
守門的老叟喚作秦翁,是秦氏的遠房親戚。
秦翁給阿殷開了門,阿殷甜甜地道了聲:“多謝秦翁。”秦翁笑得眼睛眯成一條細縫。
姜璿問阿殷:“姐姐可是要先去夫人的屋裏?”
阿殷說:“嗯,我去和母親說一聲我回來了,妹妹不必跟著我。”一頓,她又從袖袋裏摸出一個小巧的玩意,約莫有一寸大小,是個刻成猴頭模樣的核雕,說,“送到浩哥兒屋裏,便說是我今日偶然得之,然後你仔細觀察浩哥兒屋裏有什麼不一樣了。”
薑璿接到掌心裏,借著月光看清楚了猴頭核雕。
她感慨地道:“姐姐的技藝愈發精湛了,外頭的都及不上姐姐的半個手指頭。”
阿殷笑說:“你若勤學苦練,亦能如此。”說罷,阿殷擺擺手,轉身便往秦氏的屋裏走去。
她剛進門,秦氏便嚷道:“你這死丫頭,又去哪兒野了?”
“娘,我和你提過的,昨夜夢見祖父了,今早去給祖父上香的。”
秦氏哪會不知女兒的性子,說是給祖父上香,哪有上香到入夜才歸家的?不過秦氏也不點破,嚷了句便算消氣,對阿殷招招手,說道:“過來,娘給你買了好東西。”
秦氏打開一個木匣子,裏頭有一對金簪。
“娘今日特地出去將你外祖母給的金鐲子熔了,找工匠做了一對金簪,等你出嫁時正好可以戴上。阿殷,這世間也只有當娘的才會對你這麼好,你以後嫁人了可不能忘了娘。”
阿殷不動聲色地問:“娘,可是謝家那邊有動靜了?”
秦氏眉開眼笑地道:“明日是個提親的好日子。”
“娘,謝夫人真的鬆口了?”
秦氏眉頭一橫,道:“我們的阿殷萬般好,要娶你回去自然是得用正妻之禮。”
秦氏合上木匣子,語重心長地道:“我瞧謝家的小郎君願意等你幾年,也是個真心的,阿殷,如果一個男人真的心裏有你,其實當正妻也好,當妾室也罷,都是一樣的,不過是名分不同罷了。”說起這個話茬,秦氏不由得看向窗外。
不遠處,二姨娘陸氏的尖細嗓門不知說了什麼,惹得殷修文哈哈大笑。秦氏面色陰鬱,又說:“陸氏就是掃把星,打從她進了門,不僅克死了你祖父,還害得你父親不思進取。你若嫁了人,以後千萬不得狐媚夫婿,定當賢良淑德,操持家業。”
提起陸氏,秦氏滿腹埋怨,一股腦兒地說了半個時辰,方放了阿殷回去。
阿殷回了房。
因著父親生性風流,除了二姨娘之外,前不久又納了個三姨娘。二姨娘生有一子一女,如今萬般得寵,與大房同擠在最裏頭的院落,東邊是大房,西邊是二房。東邊有三個房間,從大到小依次分佈,阿殷的房間在最尾處。
阿殷推開門,薑璿已經回來了。
姜璿是阿殷祖父的故人之子的遺孤,從小與阿殷一塊長大,祖父離去後,秦氏本不大想養個閒人,虧得阿殷遊說,秦氏才勉強答應讓薑璿留下來。
兩人感情甚好,同吃同住,比親姐妹還要親。
“可從浩哥兒屋裏發現了什麼?”
浩哥兒是阿殷的二弟,今年十歲。阿殷還有個同胞親弟,比阿殷小兩歲,自小喜歡行商,四五年前便離開了家,出去闖蕩,每逢過年才會回家。
薑璿低聲說:“我進屋的時候,浩哥兒正在念書,書是新的,書皮上寫了‘壽全學堂’四字。”
此話一出,阿殷登時怔住。
春寒席捲而來,她的心口似有一道細縫,冷得她渾身打戰。薑璿問:“姐姐怎的臉色如此蒼白?”阿殷半晌才回過神,喃喃地道:“壽全學堂哪是我們這些人能進去的。”
她定定神,又道:“時候不早了,妹妹先睡吧。”
姜璿曉得阿殷是個心裏有主意的,也不多問,給阿殷沏了一壺茶,便先鑽進被裏。阿殷喝了口茶,熱茶滑過喉嚨,落入心底,可胸腔處仍然冰涼一片。
她一直知曉母親最疼兩個弟弟,她只是個女孩兒,不能替母親在父親面前爭寵。這些她從不計較,可是她卻沒想到有朝一日,為了浩哥兒的前程,母親一聲不吭就將她的婚事給賣了。
壽全學堂是恭城最為有名的學堂,也是出了名的門檻高。
學堂的夫子都是從都城永平過來的,創辦這所學堂的正是恭城的謝縣令,進者需得有聲望的人舉薦,且一年的學費足足要二十兩銀子。二十兩銀子,足夠小家小戶半年開銷,他們家不過是小家小戶,多虧祖父行商時留下的積蓄,才能維持如今的生活。
她低眉斂目。
過了許久,她從箱籠裏抱出一個紅木匣子,坐在梳粧檯前,打開了匣子。
匣子裏整整齊齊地擺著六把小刀——毛銼刀、平銼刀、平錐刀、圓錐刀、尖錐刀、斜刀。
這是祖父留給她最寶貴的東西,核雕的必備器具。
她低聲道:“母親,你不疼我,我只能自己疼自己了……”
雞還未鳴,秦氏便起了。
丫鬟冬雲給秦氏打了水,侍候秦氏梳妝。殷家全家上下就只有一個丫鬟、一個雜役,還有一個看門的秦翁。秦氏對待下人不薄,體諒冬雲侍候一家子辛苦,時常將多餘的小物賞給冬雲。
冬雲為此很是感恩戴德,侍候秦氏比侍候陸氏要用心。
“把那對碧雲簪拿出來,今日謝家來提親,可不能丟了我們殷家的臉面。”
冬雲將碧雲簪比畫了會兒,插在秦氏的髮髻上,說:“碧雲簪最襯夫人的雍容,夫人戴上這對碧雲簪,有種說不出的氣度。”
秦氏人逢喜事精神爽,聽得冬雲此話,更是笑得合不攏嘴。
“你這張小嘴真會說話。”手指在妝匣裏挑了挑,秦氏取出一對半舊的珍珠耳環,“今日我們殷家有喜事,賞你了。”
冬雲連忙謝過。
秦氏心裏是實打實地歡喜。
女兒已年有二十,若非她喜歡的人是謝家小郎,無論如何她也會強迫著女兒在十八歲之前嫁出去的,鄰里街坊這幾年的閒言碎語她聽得耳朵都能生出繭子了。
不過現在不一樣了,謝家終於要來提親了!
雖說當妾是有點委屈女兒,但謝家小郎真心一片,又對女兒言聽計從,即便以後娶了正妻,心到底還是在女兒這邊的。本來她亦是不願女兒當妾的,但浩哥兒本該八歲就上私塾的,老爺卻非得堅持要浩哥兒上最好的私塾,托人四處拜訪,都不得入壽全學堂的門路。如今謝家那邊開了口,既能把女兒嫁出去,又能讓浩哥兒上壽全學堂,連未來幾年的學費都全包了。
且那邊願以正妻之禮迎娶,仔細想來,也算給足了殷家臉面。
辰時一過,謝家遣了當地最有名望的媒人李婆上殷家提親。
謝夫人礙著謝少懷的懇求,在彩禮上費了一番功夫,足足十二擔,流水一般湧向殷家。李婆在門口吆喝,惹得周遭鄰里頻頻矚目,認出了李婆身後是謝家的總管。
殷修文與秦氏早已候著,可謂是春風滿面地開了門,迎了一眾人進去。
兩家暗地裏早已達成共識,如今請媒人過來也不過是走個過場。
殷修文一直盼著自己的兒子能上壽全學堂,如今美夢即將成真,與李婆還有謝總管說話時,連髭須也透露出一股子喜氣。媒人說了兩個迎親日子,一個是五月,一個八月,都是難得的好時日。
殷修文沒有任何猶豫便道:“五月好。”
他語氣裏的著急令謝總管微微側目。斂去鄙夷的目光,謝總管淡淡地說:“我們夫人亦屬意五月初八,日子已然定下,如今時候不早,我……”
倏然,一道匆忙的腳步聲傳來。
一抹青色人影慌慌張張地出現在大廳,薑璿哭紅了雙眼,臉色白得嚇人:“老……老爺……夫……夫人……不好了!不好了!阿殷姐姐不知得了什麼病,臉也不知怎麼了……老爺夫人快去看看吧!”
秦氏面色頓變。
殷修文幾乎是瞬間便望向了謝總管。謝總管也不走了,起身溫和地道:“我們謝府與周章大夫頗有交情,李婆你隨殷夫人去看看,若殷姑娘有何事,我還能立馬請周大夫過來一趟,以免誤了病情。”
秦氏卻輕擰起了眉頭。
這謝家總管好生圓滑,言下之意不外乎是先看看她家閨女病得如何,若是重了,這婚事說不定便暫且擱下了。秦氏正想回絕李婆,然而殷修文感激地看了謝總管一眼,道:“多謝謝總管了,李婆,這邊請。”
夫君話已出口,秦氏只好順著夫君的意思,帶著李婆去了阿殷的閨房。
一進閨房,秦氏就傻了眼。
昨天夜裏還如花似玉的女兒,如今不過短短一夜,臉上、脖子上、手上密密麻麻地爬滿了米粒大小的紅點,右臉頰上還有一處拇指大小的紅印,淌著血。
李婆頓時明瞭,一看阿殷的右臉頰,不由得可惜地歎了聲。
長水痘可不能隨便撓的,一旦抓破便會留下痕跡。殷家姑娘哪都不抓,偏偏抓在如此明顯的地方,好好的一張臉便這麼毀了,真是可惜了這張五官精緻的臉蛋。
秦氏眼眶泛紅,正要上前,阿殷捂住臉,尖著嗓子道:“不要過來!”
秦氏生怕她又抓臉,連忙道:“好好好,娘不過去,你莫要抓臉,只是水痘而已,半個月便能消了。”
阿殷說:“娘,祖父不是給我留了間屋子嗎?讓我去那邊養病,浩哥兒還未出過水痘,免得我傳染給了弟弟。”
秦氏本是有幾分猶豫的,但一聽提到浩哥兒,便道:“也好,娘請大夫過去那邊,讓薑璿跟著你去。”
殷家祖父離去時,兩房分了家,殷家祖父還特地給阿殷留了一份嫁妝。二房原本是不樂意的,憑什麼長孫女能得一間屋子?不過去瞧了眼屋子後,便沒人再吭聲。
屋子建在蒼山山腳。
蒼山最是荒涼,離屋子不到兩裏的距離挖滿了荒墳,路過之人都覺陰風陣陣,更莫說住在那兒了,白給也不願要。
李婆出來後,與謝總管嘀咕了幾聲,謝總管便立馬道:“想來是今日提親的日子挑得不好,才令殷姑娘出了水痘。提親講究和和美美,如今出了這般事,還請殷老爺允許在下回去稟報夫人,擇日再來提親。”說著,與李婆飛快地離開了。
殷修文面色不佳,看向秦氏的目光多了幾分怒色:“你怎麼看女兒的?早不出遲不出,偏偏這種時候出了水痘。”
秦氏委屈得很,也惱了:“女兒出了水痘,你也不關心一下?”
殷修文這才道:“請了大夫沒有?”
秦氏說:“阿殷說要去父親留給她的屋子裏養病,我怕傳染給浩哥兒,答應了。”
殷修文說道:“在哪養病都一樣,別傳染給浩哥兒才是最重要的,讓薑璿跟著過去照顧,把水痘養好了,謝家小郎一樣會娶我們家女兒。”
秦氏附和:“妾身也是這麼想。”
當天,秦氏便讓家裏僕役去租了輛牛車,準備載著阿殷與薑璿前往蒼山。秦氏倒不是很擔心女兒的安危,她生的這個女兒打小就與尋常姑娘不太一樣,力氣特別大,八歲那年家中遭賊,阿殷靠著蠻力卸了小賊的兩條胳膊,將全家都震驚了。事後問女兒,女兒也糊裏糊塗的,甚至不知當時發生了何事。自此,她便曉得女兒在危急之時有神明庇佑,能爆發與眾不同的蠻力。
阿殷上車時,被秦氏裹得像是一個大粽子。
鄰里街坊今日都尤其關注殷家,特別是看到謝家帶著彩禮離去時,好奇之心便收不住了,如今見著一個大姑娘上了牛車,家家戶戶都探長了脖子。
恰好此時,有風吹來,拂開了阿殷的面紗,露出了她斑斑點點的右臉頰。
秦氏哎喲一聲,趕緊讓姜璿將阿殷扶進牛車。
馭夫趕著牛,慢悠悠地趕往蒼山。待牛車消失在眾人的視線裏後,不到半個時辰,殷家大姑娘長水痘還撓破了臉的消息便傳遍了整條東街。
秦氏心裏苦,板著臉關了門。
而此時此刻的阿殷卻優哉遊哉地摘了面紗,好不自在地伸了個懶腰,問:“妹妹,有帶吃的嗎?”
薑璿歎了聲,說:“姐姐這是何苦呢?”說著,把食盒裏的小米糕遞給阿殷。
阿殷咬了口,吃得津津有味。薑璿又遞上一塊帕子,阿殷順手擦了擦臉,臉上的斑斑點點、紅印子,通通化為虛無,臉蛋光滑得像是剝了殼的白煮蛋。
她吃了兩塊小米糕,才道:“我曾和謝郎說過,若他不能娶我為正妻,我們好聚好散。可他應承了我,最後卻騙了我。阿璿,祖父曾告訴過我一句話,他的人生裏容不下任何欺騙,我亦然。至於母親那邊——”她慢條斯理地擦去手背上的紅印,方道,“沒人疼我,我便自己疼自己。”
薑璿聽了,眼眶微微泛紅:“姐姐,以後我疼你。”
阿殷莞爾道:“好,我們姐妹倆互相疼,用不著其他人來心疼。”
薑璿又道:“姐姐,你真不想嫁給謝郎了嗎?等你水痘好了,謝郎那般喜歡你,一定會再上門提親的。”
“此言差矣。謝郎最聽他母親的話,他母親又怎會允許一個右臉破了相的姑娘嫁進謝家?且東街的鄰里最是嘴碎,不用幾日,整個恭城都曉得殷家的大姑娘右臉破相了,如此,爹娘也不會再拿我的婚事做文章。妹妹,你信不信,我養病的一個月裏,謝夫人必定會給謝郎張羅一門親事!”
“姐姐聰慧,妹妹自是信的,可姐姐這招無疑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以後沒人娶姐姐,該怎麼辦呢?”
阿殷說:“爹娘讓我寒了心,此回能為浩哥兒上學堂和外人一起賣了我後半輩子,以後還不知能怎麼賣了我,我得為自己多做打算。爹娘都不能依靠,嫁人倒是次要了,我只能依靠自己,幸好祖父還傳了我一門手藝,以後不至於窮困潦倒。”
蒼山與桃山只隔了條蒼恭河,並不遠,大半個時辰便到了殷家祖父留給阿殷的屋子。阿殷對這間屋子並不陌生,祖父還在世時,經常帶她來這裏。
此屋非尋常屋舍,乃是殷家祖父費了一番功夫方尋得的寶地。
雕核雕核,又豈能無核?
時下人雕核大多用桃核和杏核,從樹上摘下來的新鮮桃子和杏子,去肉摘核,還需在陰涼之處自然曬乾,等成了舊核方能開始雕刻。
此屋,殷家祖父取名為核屋。
阿殷大半月沒來,屋裏生了不少灰塵。她拿起屋舍外的掃帚開始打掃,薑璿連忙道:“姐姐,我來。”
阿殷攔住她,說道:“不,我來,我需要你做其他事情。”
薑璿說:“但憑姐姐吩咐。”
阿殷說:“母親找來的大夫應該差不多到了,以母親平日裏的習慣,請的定是東柳巷的張大夫。張大夫醫術平平,是個好逸惡勞的。他大老遠來到這兒,必要經過那處荒墳,你在那邊等著他,好打發了他。”
“好。”
待薑璿離開後,阿殷邊打掃邊開始思考要如何借助祖父的手藝掙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儘管恭城只是綏州的一座小城,可因盛產桃子,引來許多商人,甚至偶爾還會有達官貴人經過此處,只為挑得好核。
阿殷是知道的,原先核雕只是一門繁複的手藝,並不為人們所賞識,直到後來太祖皇帝改朝換代,因尤愛核雕,才使得民間核雕漸漸盛行,核雕人才層出不窮。去年新帝登基,對核雕的癡迷更甚于太祖皇帝,四處搜羅核雕珍品,令許多核雕技者一夜暴富。她祖父曾感慨過,如今是太平盛世,更是核雕技者的盛世。
姜璿回來時,阿殷已經打掃完了,手裏還多了把小銅鏟。
她道:“我去取點東西,你留在屋裏。”說完又不太放心,叮囑道,“無論遇到什麼人都不能開門。”
薑璿不由得笑道:“知道啦,妹妹會小心的。”
屋舍往西,約莫有五裏的距離,種了一棵杏樹。
那是阿殷出生時祖父種下的,如今二十年已過,杏樹亭亭如蓋,杏花飄香。阿殷圍著杏樹轉了一圈,忽然蹲下,用小銅鏟鏟出一堆泥土。
一個鏽跡斑斑的鐵匣子漸漸露了表面。
一挖一鏟,動作如行雲流水,鐵匣子俐落地到了阿殷手中。
她撬開鐵匣子,裏頭端端正正地擺了一錠銀子。見到這錠白銀,阿殷的小心肝撲通撲通急跳著,有一種油然而生的喜悅——這錠白銀是她打懂事起便開始積攢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小時候花了五六年的時間,攢了一兩銀子,後來被母親發現了,直接充公,她沮喪了好幾日,之後便想了另外一個法子——藏在土裏。
多虧有祖父打掩護,她這些年來才藏得如此順利。
阿殷左擦擦右摸摸,心裏頭蕩漾得如恭城含光湖上的漣漪,一圈又一圈,蕩個不停。
意識到爹娘不可靠後,眼前的銀子便愈發迷人,在她心目中已經上升到第二位,第一位自然是核雕。祖父的這門核雕手藝,她從八歲那年便開始學了,連平日裏鮮少誇人的祖父都稱讚她天賦異稟,下刀又准又狠。
起初她只是貪玩,後來越學越覺喜愛,只覺寸尺之間,有著大千世界。
阿殷掂了掂銀子,這錠銀子估摸著能換五兩銀子,足夠她做不少事情。她把銀子收進衣襟,將鏟出的泥土填回,正打算回去時,冷不丁有一道細微的呻吟聲響起。
她腳步一頓。
她抬首望向天際,天色昏沉,此時此刻出現在蒼山,還發出這般痛苦的聲音,約莫是個麻煩。
她目前惹不起麻煩,遂佯作聽不見,抬步前行。
豈料剛行一步,背脊處登時爬上一絲絲冷寒,刹那間,阿殷只覺得自己像是被一條毒蛇盯上了。咣當一聲,一個晶瑩通透的白玉扳指滾落在阿殷腳邊。
“帶我離開這裏。”聲音格外低沉,帶著一絲壓抑。
阿殷的目光觸及地上的白玉扳指,她不懂玉,可也知這是上好的白玉。
“它能換十錠黃金。”
此話一出,阿殷的耳根子微微紅了。
這人好生無禮!居然一聲不吭地將她對銀子的狂熱看了個遍!她正想出聲反駁,卻忽然一愣,白玉扳指上有一絲血跡,鼻間的血腥味也愈發濃厚。
……不是她能得罪的人。
她無聲地撿起扳指,問:“貴人方才可有看清我的臉?”
“無。”
阿殷又看了眼天色,蒼山林木鬱鬱,加之天色昏暗,的確不一定能看清她的臉。她又道:“貴人的手能動否?”
“能。”聲音愈發低沉,還有一絲不耐。
阿殷往後退了幾步,扔下一方手帕,道:“還請貴人以帕覆眼,我好帶貴人離開。”言下之意,便是你不擋住眼睛,我就自己離開。
身後沉默了許久,半晌才有衣料窸窣聲響起。
“帶我走。”
阿殷這才放心地轉身,她依舊沒看那人的臉,微垂著眼,看著他帶血的衣裳。墨藍的蘇繡麒麟紋圓領錦袍,衣料一看便知價值不菲,敢穿麒麟紋的,果真是個貴人。
她判斷得不錯。
這樣身份高貴的人,她不宜牽扯上。
阿殷力氣大,輕而易舉就扶起了沈長堂,他半個身子都依附在她身上。她發現他傷得很重,上半身幾乎要被鮮血浸透,方才竟還能保持神志與她說話,還能系上帕子,非尋常人可比。
“貴人要去哪兒?”
沈長堂遲遲沒有回答。
阿殷心裏想的卻是離核屋越遠越好,免得傷了阿璿,遂扶著他往西邊走去。男人身子很沉,在血腥味的掩蓋之下,還有一股特別的味道,不是熏香,也不是任何香味,阿殷說不出來,只覺似曾相識。
男人的身子越來越燙,隔著一層薄薄的春衣,阿殷能感受到他燙熱的身體。
她停下來,抽出一隻手探向男人的額頭。
還未碰著,一隻如烙鐵般燙熱的手緊緊地箍住她的手腕。
“沒死。”聲音極冷。
阿殷問:“貴人要去哪兒?”
手腕上的大手力度越來越大,仿佛要捏碎她的手腕似的,令她不由得抬眼望向男人的臉。不望還好,這一望阿殷嚇得小心肝都在抖。
他的額頭、臉頰、下巴都冒出一條一條的青筋,像是蠕動的青蟲。
“你……”
此時此刻兩人離得極近,阿殷一張口,氣息便如數噴到他的臉上。手腕被狠狠一拉,她的腰肢被緊緊箍住,隨之而來的是欺上來的薄唇。
毫無防備的,一條粗暴的舌,竭盡所能地在她嘴內搜刮。
她的蠻力無處可用,被他倒騰得像是一攤軟泥。
許久,阿殷的力氣才恢復過來。
她正要一個手刀劈去,方才還氣勢如虹的男人居然徹底昏倒,癱軟在她身上!阿殷惱極,氣極,怒極!雖說她不指望嫁人了,但也沒說能隨便被人親。
登徒子!流氓!
右足在他小腿上狠狠地踩了一腳,阿殷內心的氣才消了不少。
“侯爺——”
“侯爺——”
……
遠處傳來的呼喊聲令阿殷打了個激靈,瞧著他雪白裏褲上鮮明的腳印,她沒來由地有點心虛,趕緊解了他眼上的帕子,又擦了擦他的褲腿。可惜方才踩得用力,腳印只能擦掉一小半。
聽著聲音越來越近,阿殷咬咬牙,把白玉扳指塞回男人身上,提起裙裾匆匆離去。
大興朝驛站尤其多,每隔二十裏設一。近年來因核雕技藝興盛,來往恭城收核的人多,朝廷怕人多口雜,特地在恭城外每隔十裏設一驛站,以防生事。
張驛丞隔壁的驛丞姓元,是個年輕的小夥子,為了做出政績,整日勤快得不行,將過往的官員服侍得妥妥帖帖,最近還來搶他的地盤。他年有四十,打算在這兒養老,也不與他計較。正好今日春寒得緊,張驛丞早早便歇了,橫豎元驛丞派了人守在附近,一有人來便會立馬招攬過去。
然而,張驛丞被窩還沒暖好,便聽得劈裏啪啦的聲音響起,緊接著是咚咚咚的走在地板上的聲音。
張驛丞一張老臉沉沉,推門喝道:“吵什麼?”
家僕慌慌張張:“大人,不好了。”
張驛丞沒好氣地道:“姓元那黃口小兒又做了什麼?”
家僕說:“元驛丞見著穆陽侯的馬車,嚇得連滾帶爬地回了他的驛站。現在穆陽侯的馬車正往我們這邊來,約莫再過一刻鐘便到。”
“穆陽侯”三字簡直如雷貫耳。
弱冠之年驅逐蠻夷,被先帝封為穆陽侯,又曾是皇帝的伴讀,當今太子太傅,現下年僅二十八歲。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是穆陽侯心狠手辣,脾氣暴躁。
傳聞穆陽侯隨身攜帶一鞭,名為飲血鞭,不管對方是何等身份,脾氣上來時先抽了再說。
張驛丞揣著一顆養老不成便給自己送終的心壯烈地候在驛站門口。
馬車停下。
然而張驛丞連能送自己上西天的穆陽侯的臉都沒看清,便徹徹底底地被忽略在一邊。半晌,才有個白麵郎君風馳電掣地過來,問:“驛丞在何處?”
“正是下官。”
“把恭城最好的大夫找來。”
那名郎君喚作言深,生得一副好模樣,可此刻卻對另外一名黑面郎君怒目而視:“若侯爺有個三長兩短,你我全家都得陪葬!”
言默抽出匕首,寒芒刺骨,一言不發便往手背上劃去,鮮血流了一地:“此事錯在我,是我一時不察才讓那小兒傷了侯爺。”
“人呢?”
“已命人前去捉拿,他為侯爺所傷,又服了軟骨散,跑不遠,今夜子時之前必能捉回。”言默暗想:若侯爺真有個三長兩短,他定當手刃那小兒,再跟隨侯爺而去。
言深方才的話雖如此說,但心裏知曉這點傷于侯爺而言,算不得什麼。他們家侯爺體質略奇,不論多重的傷,只要能得到充足的歇息,很快便能痊癒。
他此刻擔心的倒是另一點。
他壓低聲音問:“侯爺的怪疾可有發作完?”
言默亦低聲回道:“發現侯爺時,侯爺面上青筋已然全消。”一頓,言默又道,“只不過有一事頗怪,侯爺的褲腿上有半個腳印。”
向來淡定自若的言深聞言露出詫異的神色,隨即眉眼一斂,怒道:“那小兒當真膽大包天,連我們侯爺的金腿也敢踩!待捉到他,老子生吞了他!”
仿佛為了應和他這一番豪言壯語,房門嘎吱作響。
一小童跑出,喜出望外地道:“兩位爺,侯爺醒了。”
言深與言默皆是一怔。
若是以往,侯爺必定要昏迷個幾日才能醒的,如今昏迷了多久?一個時辰?不,半個時辰都沒有。兩人立即奪門而入。軟榻上的男人已經坐起,一旁的小童跪在床沿下烹茶,茶香撲鼻而來。
小童斟滿半杯,茶湯色澤蒼翠,是一兩百金的早春泉城綠。
杜鵑啼血白釉薄胎茶杯在男人過於修長的五指中沉穩如山,他輕聞茶湯,再聞,三聞。小童捧起手,接回茶杯,盡數倒掉,伏地一禮,輕手輕腳地離去。
沙啞低沉的嗓音響起:“人在何處?”
言深與言默齊齊跪下,言默道:“侯爺,子時之前必能帶回。此次是屬下辦事不力,請侯爺責罰。”
沈長堂看了眼言默的手,道:“言深領十鞭,言默領五鞭,下不為例。”
“是,侯爺。”
言默又問:“那小兒……”
“處心積慮取我命的人,天下間唯有一個。時候未到,這一次暫且記下。至於那小兒……”沈長堂輕描淡寫地道,“殺了,不必留全屍。”
說話間,沈長堂的長眉忽然輕擰。
手指挑開血跡斑斑的衣襟,一個帶血的白玉扳指落入他的掌心。
言深趕忙喚小童去馬車取來乾淨的衣袍,回來時,卻見自家侯爺掀開了薄被,望著褲腿兀自凝神。言深心領神會,立即咬牙切齒地道:“豈有此理,區區小兒竟敢糟蹋侯爺的褲腿!待人一帶回,必將他挫骨揚灰!”
豈料沈長堂卻露出萬年難得一見的笑意:“倒是個膽大的。”
言深以為自己眼花,眨了眨眼,才發現自家侯爺嘴角是千真萬確的笑意。外頭進來一個小童,輕聲說:“恭城數一數二的大夫都帶來了。”
沈長堂慢條斯理地戴回白玉扳指,淡淡道:“讓他們都回去。言默,”微微一頓,他細長的丹鳳眼深邃如墨,緩緩地道,“你去恭城尋一個姑娘。”
言默以為自己聽錯了。
他家侯爺要找一個姑娘?說找一隻母豬都更能讓他相信!
薑璿見到一身血的阿殷時,都快嚇哭了。
阿殷不想她擔心,隱瞞了自己遇到麻煩的事情,溫聲道:“別擔心,只是今天去挖銀子的時候摔著了,偏不巧摔在一攤血跡上,才沾了一身的血。”
姜璿是曉得阿殷埋銀子的事情的,只道:“姐姐險些嚇死我了。”
阿殷笑道:“死不了,姐姐在一日,定不會讓你死。”
她從衣襟裏摸出那一錠白銀,薑璿眼睛睜得老大,說:“姐姐竟藏了這麼多銀錢!這錠白銀有十兩銀子嗎?”
“最多五兩。”
“五兩也很多了。”
阿殷道:“不多,現下我們用錢的地方多著呢。我們當務之急要做的是掙更多的銀錢,才能保以後無憂。恭城太小,且人多口雜,我們不能出現在恭城。”
她微微沉吟。
薑璿道:“我聽秦翁說,近幾年鄰近多了座鎮子,因離恭城近方便淘核才興起。”
阿殷也正有此考慮,道:“明天我們去鎮子上轉轉,看看有何機會。”
薑璿有些擔心:“核雕技者大多是男子,姐姐一介女子,可要女扮男裝,好方便行事?”
聽到此話,阿殷歎道:“我也有想過女扮男裝,只是……”她瞅了眼自己,很直白也很客觀地道,“我能遮掩自己容貌上的女氣,亦能刻出喉結,胸也不必裹,可聲音卻無法改變,一旦開口必會露餡,引得他人猜疑,倒不如坦坦蕩蕩。”
薑璿的目光忍不住看向阿殷的胸。
兩人相差三歲,可若說薑璿的乃是胸如丘壑,阿殷的便是胸如平川。
老天爺賞了她在危急之際爆發的蠻力,還有與蠻力配套的平胸,悲哉……
阿殷重咳一聲。
薑璿的臉微紅,道:“姐姐,我沒其他意思。那……那……如果明日夫人遣人過來了怎麼辦?”
提起母親,阿殷心中更是悲戚,她道:“冬雲要侍候殷家八口人,脫不開身;秦翁年邁,離不開殷家;剩下的一個僕役,卻是要侍候浩哥兒的。況且以母親的性子,定覺得我能應對,她不必操心。謝郎正妻未定之前,想來爹娘暫時都不會想到我。”
薑璿很是心疼,說:“姐姐莫要傷心,是謝郎配不上你。”
阿殷扯唇笑了下:“哪有什麼傷心不傷心的,其實我早就想明白了,與其說是我等謝郎五年娶我為妻,倒不如說我用了五年來死心。他騙了我,我反倒放下了。何況在爹娘心中,謝郎對我的傷根本不值一提。”
阿殷與薑璿歇下時,隱隱覺得胸有點疼,沒來由地想起了今日林中所遇的貴人。
她揉了揉胸。
……但願以後別再遇上。
小鎮離蒼山不是很遠,但也有小半日的腳程。阿殷雇了兩頭驢子,將近晌午時分,兩人才抵達小鎮。小鎮原來有名兒的,大老遠的便瞧見一塊巨石上,刻有朱紅的“核雕鎮”字樣。
薑璿捂嘴偷笑,說:“這般明晃晃地刻在巨石上,生怕別人不知鎮裏住的都是核雕技者。”
阿殷很是興奮。
以前祖父從不允許她在外面顯露核雕技藝,她學核雕時,能夠交流的人只有祖父和阿璿。而如今裏頭全都是核雕技者!全!都!是!
她翻身下驢,駐足在巨石前觀摩,只道:“字跡蒼勁有力,可見刀功,若有核雕,真想見一見。”
一聲不輕不重的嗤笑響起。
阿殷抬首望去,只見一明豔姑娘對她露出一臉的不屑,漫不經心地對身邊侍婢打扮的姑娘說:“這年頭阿貓阿狗都能談核雕了,核雕又豈是那些平庸之輩能夠談及的?真真可笑。”
侍婢輕笑:“姑娘說得是。”
“走,進去,免得有人汙了我的耳。”
薑璿微惱,正想出聲反駁,卻被阿殷拉住。她輕輕搖頭,道:“如今核雕興盛,有才華者能得賞識。方才那姑娘看起來不過二八年華,若也是核雕技者,這個年紀心高氣傲也是應該的。”
薑璿嘀咕道:“姐姐十六歲的時候,外頭賣得最貴的核雕都及不上姐姐的呢。”
阿殷嗔她一眼,說:“出門在外自該謙遜,何況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不,姐姐才是最厲害的。”
阿殷哭笑不得,卻也拿她沒辦法。
入了鎮子後,阿殷發現街道上行走的姑娘不少,經打聽才知原來大多是替主人家來買核雕的侍婢。鎮裏攤檔商鋪琳琅滿目,皆是售賣核雕的,因水準參差不齊,有的門庭若市,有的則門可羅雀。
阿殷佯作挑選核雕的樣子,問:“我方才見到一位姑娘,生得五官明豔,看似對核雕有所涉獵,攤主可識得?”
她本想再形容一番那姑娘的容貌,攤主卻一拍大腿,道:“你說的是恭城洛家的掌上明珠,洛三姑娘!她與尋常人可不一樣,去年洛家出了一位核雕天才,正是洛三姑娘的長兄,他的核雕為當朝丞相所喜愛,去年年底已被招去永平,成為丞相府中的門客,如今可是丞相面前的紅人。小姑娘,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知道嗎?現在莫說我們核雕鎮裏的人,連恭城的人都得讓他們洛家三分。”
洛家之事,阿殷有所耳聞,只是當時並沒有在意。
那攤主又道:“這位洛三姑娘也是有點天賦的,如今憑藉著她長兄的威名,在核雕鎮裏打橫走都沒人敢管她。我們雕核的,是為了什麼?不就是為了有朝一日出人頭地嗎?我雕核已有三年,出來的核雕形神韻工都是不差的,你瞧瞧這個,買回去當扇墜是極有面子的。瞧你是頭一回來我們核雕鎮吧?我馬大核的名聲那是整條街都知道的。”
隔壁攤檔有人笑了一聲。
馬大核面不改色地道:“笑什麼笑?有本事賣得比老子多再來笑!”
那人面色訕訕。
馬大核搓著手,道:“小姑娘,你瞧著如何?賣得不貴……”上下打量眼前的阿殷,他眯眼笑道,“看你頭一回過來,折個二錢,便只收你三十文錢。”
三十文錢,冬雲半年的月錢。
薑璿咋舌,道:“姐姐,這不是搶錢嗎?”
阿殷也不表態,手指拈起核雕,放在掌心端詳。
是一個猴頭頂壽桃的核雕。
春光明媚,映射在阿殷纖細潔白的五指上,格外刺眼。馬大核的心虛來得突然,不知怎的,眼前這姑娘看起來不過是個黃毛丫頭,談吐亦是平平,可當她安靜地端量自己的核雕時,那雙看起來分外瘦弱的手卻如此沉穩有力,仿佛能夠輕而易舉地翻雲覆雨。
馬大核粗著嗓子道:“買不買?不買別擋路!”
阿殷問:“這是三十文錢的核雕,一百文錢的核雕又是哪種?”
馬大核一聽,以為遇到一個揮金如土的主兒,當即笑吟吟地道:“有有有,我馬大核這裏什麼都有。”他打開一個木箱子,又取出一個緞面錦盒,裏頭正是一個羅漢核雕。
阿殷微笑道:“原來馬老闆擅長羅漢核雕。”
“我拜師學藝三年,雕刻羅漢無數,我這裏賣出的羅漢核雕念珠沒有一百也有八十了。”
他望了眼阿殷手裏的猴頭頂壽桃核雕,又道,“當然,我雕刻的猴子亦是不凡,難得你一個小姑娘家懂得欣賞我的技藝,羅漢核雕我賣你一百一十文錢,正好今年猴年,你手中的便當作添頭送你了。”
阿殷又問:“我若買下,這個核雕憑我處置?”
“你想砸碎了都成!”
阿殷說:“我只帶了三十文錢,先買手中的這個核雕。”說著,當真取了三十文錢出來,遞給了馬大核。
馬大核收了錢,心底樂呵,問:“另外一個羅漢核雕,姑娘打算何時來買走?我給你留著。”
他心裏頭喜滋滋的,今日遇著傻財神了!
阿殷道:“一刻鐘後。”
馬大核聞言,目光越過阿殷,望向鎮外。平坦的空地上齊齊地停了數十輛馬車。他立馬諂媚地道:“我可以陪姑娘出去一趟,免得姑娘來回麻煩。”
“不麻煩。”她指著馬大核板凳下的木箱問,“這是你雕核的器具吧,能否借我一用?”
馬大核愣愣地看著她,好一會兒才回過神,莫名其妙地把木箱給了阿殷。阿殷打開一看,還算滿意,取出一把尖錐刀,隨後低聲在薑璿耳邊說了幾句。
姜璿會意,眼睛微亮,張嘴便喊:“這裏有小猴獻桃的核雕,只賣一百一十文錢,走過路過,都來看看嘍!”
此話一出,馬大核宛如遭到雷劈,用看傻子一樣的眼神看著阿殷。
隔壁攤檔的攤主聞言,不由得哈哈大笑。
馬大核的攤檔離小鎮的出口不遠,正是人來人往的熱鬧之地,方才已有不少人在一旁觀看,如今聽一個水靈靈的姑娘脆生生地喊著如此荒謬的話,圍過來的人漸漸增多。
馬大核的厚臉皮都覺得受不了,惱羞成怒地道:“喂,你……”"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