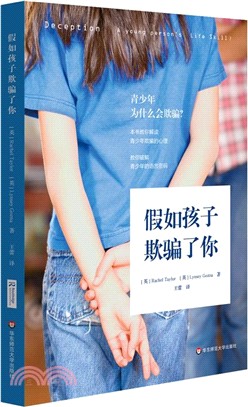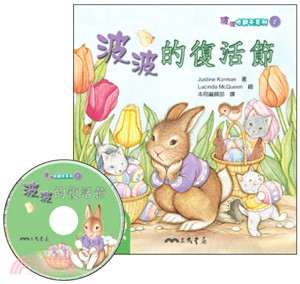假如孩子欺騙了你(簡體書)
商品資訊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這本書思考的是欺騙在青春期的作用,探討了青少年為什麼要欺騙,這些欺騙是否會成功,以及父母和從業者察覺青少年欺騙的方法。雖然在有些環境裡欺騙被看做是反社會,甚或是病態性的行為,但是本書的主要觀點是,欺騙可能是一種對青少年建立自尊來說必不可少的有技巧的行為。
在本書中,作者認為,欺騙交流和誠實交流都只是交流而已。本書會給家長和從業者提供一些實用的建議,並鼓勵他們採用靈活的方法來覺察欺騙,來為他們提供一個參考框架。本書會教家長和從業者使用動態系統的方法和發展心理學的方法理解青少年。
在本書中,作者認為,欺騙交流和誠實交流都只是交流而已。本書會給家長和從業者提供一些實用的建議,並鼓勵他們採用靈活的方法來覺察欺騙,來為他們提供一個參考框架。本書會教家長和從業者使用動態系統的方法和發展心理學的方法理解青少年。
作者簡介
王蕾,華東師范大學心理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學報編輯。先后在《南京師大學報》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曾參譯《兒童心理學手冊》、《心理學史:觀點與背景》、《存在: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的一種新方向》、《學習理論導論》等,參編《潛意識的意義——精神分析心理學》(上)、《外國心理學家評傳》、《弗洛伊德主義新論》等。
名人/編輯推薦
以前關於青少年欺騙的大部分研究認為,欺騙是負面的和病理的行為。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有時欺騙是為了保護自己和身邊的人,有時是為了為了保護自己的隱私或獲得自主性,因此是合理的,有時雖然不能用“好”來描述欺騙,但是肯定也不是心理病理化或較差的父母關係的證據。總之,欺騙並不應該得到“病理化”的標簽。事實上,有些欺騙更多說明的是青少年在人際交往中的敏感性和社會技能。此外,青少年有分寸,有些事他們不會說謊,有些人他們不會對其說謊。他們理解信任的本質,說謊並不是某種總讓他們感覺很爽的事情。
目次
致謝/4?
導言/6?
第1章欺騙性交流的發展/7?
界定青春期/9?
界定欺騙/9?
對欺騙進行學術研究的挑戰/10?
對從業者的挑戰/11?
一種發展的方法之貢獻/13?
發展的過程論/14?
欺騙資源庫和任務-資源互動/18?
本章小結/19?
第2章 影響青少年交流的因素/20?
生物學因素/20?
技能/25?
社會資源/27?
結構資源/30?
本章小結/33?
第3章 欺騙性的交往與交流/34?
說謊的動機/36?
策略和成功/45?
接受度/52?
本章小結/54?
第4章 人際互動的策略和技巧?
嫌疑人在警察問詢中的交流/58?
法庭//判決前評估/73?
支持年輕犯罪者的信念/77?
本章小結/91?
第5章 行為與人格的挑戰/92?
行為障礙/93?
人格障礙/95?
精神障礙/101?
案例/107?
本章小結/109?
第6章 覺察欺騙的技術/110?
最初考慮/110?
對從業者人際關系的考慮/116?
變色龍訪談法/117?
本章小結/124?
第7章 結論、思考及未來方向/125?
欺騙不是一個孤立的方向/125?
交流不是一個孤立的方向/125?
研究者和從業者之間進一步協作是必要的/126?
即使一個“日常的”謊言也有一個廣泛的背景/126?
理解系統將有助于那些在系統內工作的人/127?
青少年的謊言不都是負面的、有風險的和病理的/128?
青少年交流(欺騙性的和誠實的)是終身發展的一部分/128?
本章小結/129?
參考文獻/186?
主題索引/200
導言/6?
第1章欺騙性交流的發展/7?
界定青春期/9?
界定欺騙/9?
對欺騙進行學術研究的挑戰/10?
對從業者的挑戰/11?
一種發展的方法之貢獻/13?
發展的過程論/14?
欺騙資源庫和任務-資源互動/18?
本章小結/19?
第2章 影響青少年交流的因素/20?
生物學因素/20?
技能/25?
社會資源/27?
結構資源/30?
本章小結/33?
第3章 欺騙性的交往與交流/34?
說謊的動機/36?
策略和成功/45?
接受度/52?
本章小結/54?
第4章 人際互動的策略和技巧?
嫌疑人在警察問詢中的交流/58?
法庭//判決前評估/73?
支持年輕犯罪者的信念/77?
本章小結/91?
第5章 行為與人格的挑戰/92?
行為障礙/93?
人格障礙/95?
精神障礙/101?
案例/107?
本章小結/109?
第6章 覺察欺騙的技術/110?
最初考慮/110?
對從業者人際關系的考慮/116?
變色龍訪談法/117?
本章小結/124?
第7章 結論、思考及未來方向/125?
欺騙不是一個孤立的方向/125?
交流不是一個孤立的方向/125?
研究者和從業者之間進一步協作是必要的/126?
即使一個“日常的”謊言也有一個廣泛的背景/126?
理解系統將有助于那些在系統內工作的人/127?
青少年的謊言不都是負面的、有風險的和病理的/128?
青少年交流(欺騙性的和誠實的)是終身發展的一部分/128?
本章小結/129?
參考文獻/186?
主題索引/200
書摘/試閱
第1章欺騙性交流的發展
欺騙交流是一個日常的、畢生的和複雜的過程。它可以在一系列不同的環境裡,在與陌生人、朋友、合作者和家庭成員的關係中出現,甚至所有年齡群體都有。例如,我們可以想像一位五歲的小孩,假裝她沒吃巧克力蛋糕(儘管她嘴邊沾著的巧克力,已經證明她吃了),父親對他蹣跚學步的孩子說,要做個好孩子, “否則聖誕老人不來看你”,宣稱在朋友家“學習”的青少年,實際上打扮一番去了酒吧。我們也可以想到,因非常規交易而被調查的銀行家,因懷疑從商店偷東西,而被拘捕的領養老金者,以及偷車超速行駛被抓到後,正在接受訪談的青少年。考慮到有這麼多可能的欺騙情境,每一個都建立在一種不同的欺騙者和目標之間關係的基礎上,每一個都被一個不同的結果或動機驅使,我們怎樣才能將這些不同種類的欺騙弄明白?
完成這個任務的一個辦法是:制定一些明確的一般規則,它們可以嚴格應用到每一種欺騙情境。雖然這可能不完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們能用它來解釋人們說的大部分謊言――至少如果這個原則足夠一般的話。這肯定會正確嗎?畢竟,這正是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聲稱去做的,不是嗎?關於說謊者的行為之信念研究表明:對於說謊者做什麼,我們秉持普遍的知覺,這些在全世界範圍內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全球欺騙研究團隊,2006)。然而,當提到說謊者展現出來的真實行為的研究時(例如,DePaulo,Lindsay,Malone,Muhlenbruck,Charlton,& Cooper,2003),情景就沒那麼清晰了。實際上,區分說真話者和說謊者的那些線索,受到下列因素的影響:與目標的關係,做出計劃的數量,謊言本身的目的或動機。因此,我們明顯應該強調,欺騙交流的完整範圍,包括:目的、關係、背景和說謊者的年齡。在這本書中,我們考慮人生中的一段時期――青少年時期――並且檢驗欺騙的交流過程如何發展。
因此,這本書考慮,青少年何時和為什麼選擇去說謊,他們有多成功,以及他們的謊言可能怎樣被成年人或其他同齡人發現。它包括來自一系列生活環境的青少年的資料:那些來自明顯穩定的家庭背景,他們在學校成績也較好;那些來自混亂的家庭環境,或有行為或人格障礙;以及那些發現自己處在他們“被迫”說謊境地,以擺脫麻煩或支持朋友。不管怎樣,這本書的主要觀點是:不可能離開更廣泛的行為,單獨考慮欺騙,因此,我們提出一種整體的方法,來理解和解釋這樣的行為。欺騙的交流,在成功需要的欺騙量上可能有所不同,有些交流,包含的真實內容,要比欺騙內容多。因此,只考慮欺騙,不強調說實話,是人為的和不切實際的――不考慮真實與謊言之間,存在的灰色地帶,來接觸這個領域,是不可能的。與此類似,在兩個人之間的一次互動,如果我們理解:這兩個人都是帶著一組先入之見、目標和動機,進入到那個互動中來,所有這些都可能影響互動的過程,只有這樣,才有意義。因此,為了理解這些欺騙,我們需要考慮,它們發生的更廣泛的背景。這對於父母、學術研究者和從業者來說是重要的,因為作為一種情景的方法,可以為那些捲入到覺察欺騙當中的人面臨的挑戰,提供解決的辦法。在下一部分,我們將給這些挑戰中的一些下定義。然而,首先,我們要給出欺騙和青少年時期的定義,以確保當使用這些術語時,你對它指的是什麼,有一個清楚的理解,和我們在整個這本書,採取的方法和觀點。
界定青少年時期
為了本書的目的,我們將“青少年時期”界定為10到21歲之間的一個人生階段,我們選擇這個定義,出於以下幾種原因:
1 它通常包括已達法定責任年齡(即,那些被認為可以為他們的行為負責,並受刑事司法體系某種形式的制裁)的年輕人。現在,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犯罪責任年齡是10歲,儘管12歲以下的兒童,除非犯一種嚴重的罪,那種一個成年人犯會被判至少14年監禁的類型,否則不會受到監禁判決(青年司法局,2009)。此外,18到21歲之間,受到監禁判決的犯罪者,將在年輕犯罪者的機構中拘留,或在成年人監獄,隔離出來的部分中拘留,也由刑事司法體系另行受理(監獄機構,2009a,2009b)。
2 這樣一個定義,涵蓋所有像術語“十幾歲的孩子”和“青少年”所指的所謂的“青少年時期”,至少對大部分人來說,可以替換使用。因為在英國的年輕人,住在家裡的時間越來越長(在英國,2006年,年齡在20-24歲之間的年輕人,有58%的男性和39%的女性仍然與他們的父母住在家裡,與之相比,1991年,分別為50%和32%;國家統計局,2007),與建立自主性有關的問題,同樣可以很好地應用到那些19或20歲人身上,在西方社會,傳統上已視之為成年人。
3 因為青少年時期是一個過渡時期,在這段時期,我們從那些適用于兒童期的欺騙方法,轉移到成年人使用的欺騙策略,這樣一種跨度,需要考慮這些改變。在家庭中,權力關係的變化,在教育和司法系統中,為行為負責,和成年人在一系列環境裡秉持的,對青少年的知覺,都只是這個過渡時期的一些特徵。
界定欺騙
在該領域,普遍接受的欺騙定義是Vrij提出的(2008,p.15)那些定義,他說欺騙是:“一種成功的或不成功的有意企圖,沒有提前預警,給別人創造一種交流者知道是不真實的信念”;Ekman(2001,p.41)認為,說謊具體指的是:“……誤導一位目標的有意選擇,一點兒也不告訴你,想要這麼做。說謊有兩個主要形式:隱瞞……和歪曲。”
這兩個定義都包括:欺騙者一方,有意的成分,欺騙目標一方,沒覺察到欺騙,和信念或理解上的一種改變。二者都沒有要求欺騙一定要成功。然而,這是顯而易見的,包括大量不同的行為,例如,直接說假話,歪曲事實和隱瞞某些真相。我們說謊的目的也千差萬別,可能包括:讓我們自己顯得更好,保護他人,獲得某種形式的物質利益和避免懲罰而去欺騙。DePaulo和同事們對日常謊言進行的日記研究(DePaulo,Kashy,Kirkendol,Wyer,& Epstein,1996)發現,在日常的欺騙交流中,所有這些都是重要的目的。我們也可以在面對面或通過媒介的交流中,有或沒有第三方支持和共謀的情況下,通過言語或非言語的手段,誤導他人。因此,儘管在領域內普遍接受欺騙的定義本身,但是,在這些定義中,所指的交流行為是極為不同的,常常可能既複雜又深奧。實際上,欺騙只是一系列可能的交流策略和選擇之一。青少年(和成人)常常會選擇誠實地交流或部分欺騙,即使這對直接的目的似乎沒有完全優勢;常常因為直接目的可能沒有長期目的那麼突出。這意味著,欺騙呈現很多不同的挑戰,既有來自學術的,也有來自實踐的觀點。現在,我們考慮這些。
對學術欺騙研究的挑戰
欺騙行為的心理學方法,是設計用來解釋,為什麼謊言失敗和說謊者表現出的行為類型。一般來說,因為兩類原因,預期謊言會失敗:由於情緒喚起(和相關的過度控制)和認知負載(例如,Ekman,2001;Vrij,2004)。預期說謊的行為會喚起情緒,這是因為假定:欺騙的行為將導致內疚的感覺,害怕被抓或“欺騙的快感”(與一種成功地欺騙有關的興奮)。然而,這些欺騙的方法是基於如下一種觀點:欺騙是對情境的反應,而不是有意的策略性的選擇,以呈現他們自己最好的一面。最近關於考慮策略和自我-呈現(例如,Hartwig,Granhag,&Strömwall,2007),而不依賴具體的欺騙線索的研究,特別是根據近期大範圍元分析(DePaulo等,2003)的研究,給予支持。然而,還要進一步研究,發現這些方法的真正好處。
此外,雖然在考慮欺騙者和欺騙對象之間,如何聯繫(例如,對朋友與對陌生人說話)方面,有一些嘗試,但是,對於這些互動的複雜和動態本質,理解仍然不充分。先前考慮欺騙的互動本質的嘗試(例如,Buller & Burgoon,1996),沒有取得完全地成功(例如,DePaulo,Ansfield,& Bell,1996),而且,雖然通過計算機-調節的交流,在理解欺騙方面,取得一些進步(例如,Carlson,George,Burgoon,Adkins,& White,2004),但是日常的和法庭欺騙的過程,仍不清楚。
最後,對於主要依賴大學生樣本的很多學術研究來說,生態效度一直是一個挑戰,雖然有些研究的確包括一些更年長的成人,或者來自社會(例如,Vrij,Akehurst,Brown,& Mann,2006)或者來自從業者群體(例如,Vrij,Mann,Robbins,& Robinson,2006)。後面這些研究,常常探索覺察的組間差異,認為:在這些方面,訓練或從業者的經驗是重要的。正如在下一節中將會討論的那樣,需要提出有關此類研究應用到真實世界情境的普遍性的問題。然而,還有一個跟本書特別有關的更基本的問題出現。這些研究中,大多數都有這樣一個假設:除了性別、職業、人格或有限的情境變量(通常單獨逐一操縱)外,所有欺騙者,自十幾歲開始,在他們的能力方面,大致是相似的。換句話說,沒有考慮,在特定情境下,採取的欺騙策略,或選擇欺騙還是說實話方面,存在畢生的發展。考慮到不同種類的經驗,或者是關係熟悉度方面(例如McCornack & Levine,1990a,1990b),或者是從業者的經驗(例如Vrij等,2006),被認為是有關的,採用這樣一種假設,太讓人意外了。畢竟,當兒童進入青少年時期時,諸如閱讀能力、抽象推理,和親密關係中的交流,這樣的認知和社會能力的發展並沒有停止;恰恰相反,它持續一生。因此,有什麼理由認為,欺騙的選擇和能力,在青少年時期和成年期之間,就應該停止發展嗎?
當然,對於這種普遍的模式來說,也有一些例外,一些研究者讓年輕人說出關於他們說謊的類型和這樣做的理由(Arnett-Jensen,Arnett,Feldman,& Cauffman,2004;Perkins & Turiel,2007)。此外,說謊的可能性,與父母關係和青少年的人格有關(例如,Engels,Finkenhauer,& van Kooten,2006)。然而,在這些文獻中,大部分假設一直是:欺騙是一種負面的或有問題的行為,至於欺騙交流的功能性或適應性的本質,尚未被充分考慮。此外,很少有人關注青少年成功進行非誠實交流的方式。理解這些,以及青少年謊言的不同動機,最終可能幫助欺騙學術研究領域,並能採取一種將欺騙的情境看作是一個整體的更廣泛的觀點。
對從業者的挑戰
正如學術研究者所面臨的挑戰一樣,那些從事年輕人工作的人也面臨挑戰,尤其是與他們的決定和互動有關的問題。這類挑戰特別適用於當一位年輕人表現出欺騙或有挑戰性的行為時,但是與孩子從事中度功能性/適應性欺騙的父母和教師也有關。第一個挑戰要考慮:年輕人在情境中的表現――採用一種整體的方法,專為討論中的個體量身定做。這個情境應該包括:青少年的背景信息,是否有任何障礙存在(例如,人格或行為障礙),他們之前與目標的經驗,以及與討論中的問題有關的其他證據或信息。這既需要理解展現出來的行為和此類行為背後的動機,還需要理解這類動機的起源。採用這種整體的方法,可以讓我們洞悉,表現和表現風格本身的來源。這與第6章中談及的變色龍表現特別有關,這也是它的一個關鍵特徵,但是對於解釋第3章中討論的人際謊言也有用。
除了理解“整個人”以外,從業者面臨的進一步挑戰是:與他們與之談話的年輕人有效地交流。與一位這樣的人交流,例如,在過去多個場合,一直對重要的成人失望,可能存在特定的信任問題。然而,與那種看起來順從,但是拒絕承認“他們的行為可能是一個問題”的年輕人交流,同樣存在挑戰。因此,對於父母、教師和其他從業者來說,靈活的交流方法尤為重要,讓他們有效地回應一系列挑戰性交流。當一個年輕人呈現出複雜的和有挑戰性的行為:包括一些欺騙的成分和一些真實的信息,沒有“客觀的”方法鑒定給出的信息時,尤其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從業者可能面臨管理困難行為,也面對獲得與訪談目標最有關係的信息的問題。在政界,政治家對直接質疑的反應,可以說明這種挑戰,直接質問能導致回避的和模棱兩可(Bull,2006)。這樣一種避免對一個問題作出充分回應的策略,年輕人可以輕鬆採用,這些在第3章和第5章個案例子中,將非常明顯。
對於那些從事實踐工作的人來說,最後一個,也與有效交流挑戰有關的挑戰是:有效回應。在這裡,從業者再次需要確保:訪談的目標能夠實現,它們能在他們的整個互動過程中,都堅持目標。一個有利的因素是:理解為什麼是青少年說謊。因此,這也是本書關鍵目標之一――在第3和第5章中提出。然而,作為這的一部分,從業者需要瞭解他們自己對他們訪談的年輕人之預期,以及過去的經驗和接觸,如何既能幫助,也能阻礙我們接下來的交流。我們從社會認知中的研究知道:人們的先在概念,可以影響他們對模棱兩可的信息(例如,Wilkowski,Robinson,Gordon,& Troop-Gordon,2007),他們提出的問題類型,甚或記得的互動方式的解釋。此外,關於內隱的社會認知的研究表明:這些預期,即使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但仍有一種影響(例如,Knowles,Lowery,& Schaumberg,2010)。
因此,對他們自己的預期,缺少洞察,可能會起反作用,阻礙年輕人與從業者之間的成功地交流。當說謊是功能性和適應性的,人際表現是用來實現一個與發生的互動無關的目標時,這尤其有關。從業者對這樣一種交流,有一種過份負面或防禦性的反應,可能正是被訪談者所尋求的,因為這正好肯定了他們對自己的看法,或他們對成人如何看他們的看法。與此類似,正如在下一章中將會看到的那樣,當指控年輕人一些他們實際上沒做過的事時,他們可以體會到強烈的不公正或不公平的感覺,而這可能會對年輕人與相關指控者之間的關係有負面的影響。在某些社區,管轄年輕人時,感知到的英國警察叫停和搜查權力的不公正、非法或濫用的相關報道,已經引起那些被挑出來檢查的人的反感,並常常成為媒體和政黨批評的對象,這也說明了這種負面的反應。在這樣的例子中,年輕人報告說:跟其他們社區的其他成員相比,他們被叫停的次數過多,儘管警察正確叫停一個人的次數報道為較差。這可能會導致年輕人認為:這樣的權利是不合適的,因此他們更難信服它們被使用。例如,Porter和Hirsch的“自由中心”博客(2009年9月2日)描述在索爾茲伯裡市藝術中心的一起事件,在那裡,兒童參加舞蹈和搖滾活動,專門設計用來“解釋”叫停和搜查權利。組織者認為,這是在涉及年輕人的群體內,建立更高水平的社區參與和公民權的一種手段。然而,組織者實際上可能將他們可接受的童年期觀點“強加”給該群體。這種觀點顯然是Porter和Tirsch的共識,他們海報的題目是“訓練兒童服從”,提出關於這類行為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問題。與此類似,英國的喜劇演員Mark Thomas,曾為可能成為非法搜查對象的人們,生產過一部“手持可下載卡”。這張卡警告警官:“我發誓,如果你決定浪費我的時間,我也要浪費你的時間”(2009年2月10日,“監護人”)。儘管對專業的警察活動來說,這是一種輕率無禮的反應,但是這種批評也反映了與從業者特別有關的一個問題,即何時正確地假定欺騙,何時接受一位年輕人說他們是無辜的斷言。畢竟,如果你的決定不僅被基層管理人員,而且也要被那些媒體和大眾“判斷”和“問責”,那麼,權衡一位年輕人表現的任務,遠沒有那麼抽象了。雖然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是,這本書的內容,是為幫助那些從業者做出最好的決定而寫。
一種發展的方法之貢獻
在前兩個部分,已經發現對學術欺騙研究和實際方面的一些問題。在這本書中,主要觀點之一是:一種發展的方法,特別是一種動態系統的方法,提供一種必要的整體觀,學者和從業者都可以採用,來加強他們對人際表現中,可信性評估的理解。這是因為一種動態系統的方法:
• 通過連接所有水平的系統(從個體的生理水平,到更廣泛的社會因素,例如,政治系統),調節發展。這些連接是動態的,兩個方向都可以進入。
• 認為個體和周圍環境系統,都是可以改變的。
• 考慮不同學科工作的人之間的互動,對全面理解發展,至關重要。
• 考慮到系統內“限制”的可能性。
• 拒絕簡單的二分法(Lerner,2006)。
因此,當我們考慮青少年表現的可信性,並採取一種動態系統方法(該方法也有上面Lerner列出的特徵)時,我們才有可能看到,一位年輕的犯罪者承認攻擊,如何可以掩藏正在發生的犯罪或非犯罪活動,或一個地區經濟不穩定,如何導致一位11歲的人,由於擔心父母被解雇,而變得內向和退縮。在一種動態系統方法內,我們也有可能看到,一位在6個月的時間裡,曾經為了每週去酒吧至少兩次,而與父母說謊的一位15歲女孩,與一群“壞傢伙”混在一起,不寫作業,最終在23歲時,從大學畢業,同時獲得一個碩士學位的顯著差別。最後,這種方法使我們能洞悉一位年輕人離開家之前,說了一句“媽,我去Lucy家學習”這句話的深意,表面上這是真的,但最終卻呈現一個完全不同的內容(即,我是去那裡,但是我沒告訴你的是,我的男朋友也會去那裡)。因此,這種方法是整體的、靈活的,提供對親社會和反社會行為的洞察,對從業者和學者都有利。
下一個部分將更詳細地考慮,如何應用這種方法。首先,我們將籠統考慮過程論――包括關於發展軌跡的研究。然後,將更詳細地討論,動態系統的方法。最後,一個具體的系統方法――發展挑戰模型――將被呈現,作為處理年輕人的交流選擇和相關後果問題的一種方式。
發展的過程論
發展軌跡
畢生方法和那些考慮發展發生過程的方法,已經應用到青少年發展的相關領域。與犯罪學中“犯罪生涯方法”(例如Farrington,2003)一致,在犯罪領域工作的研究者,長期以來一直對犯罪軌跡,以及那些持續犯罪的人與那些停止犯罪的人之間的差異感興趣。例如,Moffitt(1997)發現兩組青少年犯罪者:那些“只在青少年時期”犯罪的人和那些“畢生持續”犯罪的人。提出兩個非常不同的犯罪群體,每一種都有不同的原因和解釋框架,這種主張,為青少年時期出現犯罪行為的高峰,提供一種有力的解釋。
據Moffit(1997)看,與人生其他時期相比,在青少年時期,犯罪盛行率和發生率增加,不僅僅是因為,一小組青少年的犯罪率增加了,而是因為,很多其他青少年,暫時從事犯罪行為。因此,很難區分那些“僅僅在青少年時期”犯罪的人與那些變得多產並且以犯罪為職業的人。然而,給年輕人貼上犯罪的標簽,有潛在的困難,因為這隨之帶來大量來自社會的相關知覺,在有些個案中,可能會導致個體只好接受這樣的事實:他們總是被看作是“犯罪者”。
Moffitt認為:畢生堅持犯罪,可能源於各種因素,包括有問題的父母關係,對於社會情境,未能學會親社會的或恰當的方法和一系列“封鎖”逃離反社會行為機會的決定。動態系統方法認為:自由度可能受生活選擇的限制,從事反社會活動,可能表示缺乏社會敏感性,控制衝動也較差。Huesmann,Eron,Lefkowitz和Walder(1984)檢查參與者三代的攻擊行為,也探索攻擊行為從8歲到30歲的穩定性。雖然在8歲到30歲的年齡區間,觀察到攻擊水平的一些穩定性,但是在比較兒童、父母和祖父母時,可以看到更大的穩定性――那些有攻擊性的人,往往有一個有攻擊性的祖父母和父母。這種攻擊的代際傳遞,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結果,強調某些行為,在一個家庭看來,能成為一個可以接受的部分的程度。
除了這些所謂的環境因素,Moffitt還認為:畢生堅持犯罪,可能與心理病理水平有關,例如,兒童的行為障礙和心理病理。反社會人格障礙(APD)可能也與畢生堅持犯罪有關,因為患有APD的人,容易感到挫敗,非常衝動,並且很少考慮或顧及別人的觀點或情感。因此,很明顯,這個群體有一系列的相關問題,這可能會影響他們改變他們軌跡的能力或決定。
與畢生堅持犯罪者相比,Moffitt(1997)發現僅限於青少年時期的犯罪行為。Moffit認為:這是被一種想要自主的願望驅使,有一種感覺:那些已經捲入犯罪的人,沒有遭受同樣的限制,因此,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模擬。隨後,這又被犯罪帶來的明顯物質得利所強化,例如,偷衣服、汽車或高端電子設備。另一方面,這種行為還會通過成為犯罪同伴團夥中一員之社會交流,或通過保持已經得到的一種聲譽的需要,而被強化。這種觀點已得到下述證據的支持,該證據表明:與畢生堅持犯罪的年輕人在童年早期(Coie,Belding,& Underwood,1988)和成年期所處的邊緣化地位相反,他們在青少年期,在主流的同伴群體中實際上起著更重要的作用(Elliott & Menard,1996)。然而,這組犯罪者因為以下幾個原因不再犯罪,包括:承認並發現各種犯罪導致的負面後果;體會到刑事司法體系之現實(例如,被送到一個少年犯機構);成為犯罪的一個犧牲品;或者已經進入一個正確的軌道。這可能是因為,僅限於青少年時期犯罪的人,很少有人格障礙和認知的局限性,或者是因為,組已經擁有發展一種親社會行為技能的機會。然而,已經出現精神問題特徵的年輕犯罪者,仍然有可能樂於將他們的關注點轉向積極的目標,這取決於他們衝動的水平和相關的行為。
Livingston,Stewart,Allard和Ogilvie(2008)採用這種理論觀點,對澳大利亞一個超過4000人的年輕犯罪團夥,進行了長達6年的數據追蹤。在他們的樣本中,發現三種不同的犯罪軌跡:一組“早高峰-變緩”犯罪者,一組“晚開始-變緩犯罪者”,一組長期的犯罪者。在這個樣本中,跟其餘兩個犯罪群組相比,長期犯罪者更可能是男性和土著人群成員,出現在一個成年人法庭上可能,也要比其它兩個犯罪組別高兩倍。這表明:檢查一系列因素並採取一種畢生的方法之重要性。與其他系統方法,諸如,生態方法,所共有的特徵,將在接下來討論。
布朗芬布倫納的生態學方法(Bronfenbrenner’s ecological approach)
布朗芬布倫納的生態學方法(例如,Bronfenbrenner,1979)並沒有將發展概念化為一系列有質的區別的階段。與此相反,將發展發生的過程,作為人與環境之間一個“進化互動”的結果,來討論和闡述(p.3)。這種人-環境互動,在不同分析水平上考慮,因此,構成不同的環境,也構成它們之間的互動。正如布朗芬布倫納(1979,p.3)說的那樣:“生態環境被認為是一系列嵌套結構,一個套在另一個裡面,像俄羅斯套娃一樣。”
第一個水平,微觀-系統(micro-system),由個體及其所處的直接環境(諸如學校、家庭)組成。接下來就是外-系統(exo-system),這個術語指的是發展的更廣泛環境,還有宏觀-系統(macro-system),仍然更廣泛,並包括社會特徵和文化規範。此外,這個模型包括不同微觀-系統之間的動態互動,這稱為中系統(meso-systems)。例如,一位15歲的人,在一個特別的晚上,決定對他打算去酒吧的事,向他的父母說謊,這個決定可能取決於:
他與他父母的關係(微觀-系統)
父母彼此之間的關係(對父母來說是一個微觀-系統,對15歲的孩子來說是一個外-系統)
對一位15歲大的孩子去哪裡是可以接受的社會界定(宏觀系統)
青少年-父母關係與父母-父母關係之間的相互作用,在這個例子當中就是中系統。儘管在此之前,這個模型沒有應用在欺騙的研究上,但是這個模型在解釋和理解欺騙行為方面,有獨特的優勢,因為它考慮到多個因素之間的動態交互作用,並且承認交流的基礎明顯是兩個微觀-系統之間的聯繫,也就是中系統。然而,僅這個模型本身,不足以讓我們詳細解釋基本機制,該機制預測欺騙選擇和欺騙成功。因此,為了充分理解它,我們有必要利用另外一種方法,發展挑戰模型在這裡是關鍵的,因為它充分闡述不同系統水平之間的關係,並且能解釋這些如何能應用到一個特定的目標上。
發展挑戰模型
Hendry 和 Kloep(2012)的發展挑戰模型有三個成分:資源庫、潛在任務庫和任務-資源互動。基本觀點是:通過成功完成適當的挑戰任務,發展才能發生。對每個個體來說,他擁有的“資源庫”都是獨一無二的,是一個生物學特質、社會資源、技能、自我-效能和結構特徵的組合物。這個可能的資源庫,然後用來滿足特定的挑戰,關鍵是:一個人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擁有的資源恰好用來滿足面臨的挑戰。下面,我們將根據面臨的挑戰和一個人可用的資源,來解釋任務的結果:
•如果任務是適當的挑戰,並能被成功處理,那麼發展發生。
•如果資源不足以滿足任務,並且這種事件狀態持續一段時間,那麼很可能會出現某種形式的延遲。
•如果任務不是適當的挑戰,那麼有可能:一個個體將發生停滯――在心滿意足的停滯或不高興的停滯之間,做出一種區分。
選擇欺騙,作為一種交流方式,是滿足一個具體情境中挑戰的一個可能手段,這種選擇本身將取決於可用的資源(和這個人對它們的準確評估)。已經做出欺騙的選擇後,將它成功執行出去,將進一步取決於可用的資源數量,和它們與一個特定的欺騙任務要求的匹配。
儘管對每個人來說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是對具體任務來說,最適合的因素類型,還是有可能做出一些概括,在下面的部分,將呈現一個“欺騙資源庫”。像Bronfenbrenner一樣,Hendry和Kloep(2012)呈現一個動態系統,有些是成功滿足挑戰後進化的結果,而且這考慮到包含反饋和反饋將如何影響未來發展。Hendry和Kloep考慮了常態和非常態的轉變(對大多數人來說,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的確發生或沒發生的那些事),在這裡是重要的,因為對青少年來說,“嘗試”新的身份和要求自主性是至關重要的發展過程,但是作為常態事件的一部分,可能並不總是發生。
此外,常態和非常態的社會定義,可能對這些挑戰出現的方式,有強烈地影響,因此,直接影響到欺騙選擇和欺騙成功。最後,構成資源庫的因素範圍,和發展中的個體面臨的可能的任務範圍,似乎強調一些在當代欺騙研究模型中缺少的,相互作用和策略的複雜性的問題。
修訂版的發展挑戰模型
修改版的發展挑戰模型,應用到欺騙時,繼續對人類發展,採取一種系統的畢生方法。正如與Hendry和Kloeap(2012)呈現的發展挑戰模型一樣,修改版的模型,對發展採取一種多維“系統的”過程方法。這與傳統的階段論,或甚至是發展的簡單線性過程,形成對照。但是,這個修訂的模型,的確偏離原來的模型,它強調“開放系統”的作用,因而,將人與他或她可能所處的更大系統之間的邊界,移除了。
正如Kloep和Hendry(在出版中)指出那樣,開放系統不斷接受信息流、能量流和資源流。這意味著:個體的狀態,可能會因為更大系統的變化而改變。例如,某個站出來在一群同齡人面前作一個報告的人,最初,他們的演講可能有點緊張,當他們看到,有些聽眾點頭和微笑時,可能變得更加自信,但是,當他們的老闆走進房間時,他的自信心可能經歷一個短暫地下降。
在其他情境,也就是眾所周知的吸引子狀態(attractor states),系統可能在某一時間階段表現得穩定,但是隨著信息、能力和資源的累積,接著就發生變化。例如,有些人,可能開心地在保險公司工作15年(一個吸引子狀態或一種平衡狀態),然而,一個看似無關的事件(他的父母退休,移居西班牙),可能讓他決定,重新回到大學,為獲得一個高等學位而學習。如果對這個人的這個決定進行深度訪談,那麼他可能會談到“意識到生命是值得一過得”,也會引用他的伴侶感覺,他在他或她的工作中被低估,過去一年裡他們自己感覺健康出了狀況,以及他們的孩子升到中學。因此,從吸引子狀態中移出,並不是一個事件,而是能量的累積。這解釋了:為什麼同一個人,與一個目標,在一次交流時,決定去說謊,與同一個目標,在另一次交流時,決定要誠實。例如,一位12歲的孩子,對週一去一位朋友家學習,決定對父母說謊,但是在週五,就說實話要去參加派對。或者同一位12歲的孩子,可能會在為什麼一周都遲到的問題上成功說謊,但是在家庭作業為什麼沒有完成的事情上,就不能用一個謊言僥倖成功了。這個修訂的模型,也考慮欺騙交流的動態本質――這隨欺騙者、發現者和欺騙情境(每一個都帶著特徵給交流過程)之間的互動而展開。最後,吸引子狀態的概念可以為,對欺騙的交流仍保留“孩子般”方法的青少年,將成功的欺騙轉移到更危險的欺騙情境的青少年,或者即使面臨明顯的不相信,依然堅持不成功的交流策略的青少年,提供一種有用的解釋機制。
欺騙資源庫和任務-資源互動
欺騙學術研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即使欺騙行為的當代交流模型,也沒有充分解釋欺騙察覺中涉及的過程。這些模型,在將欺騙過程看作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整合欺騙者和察覺者的觀點,體現反饋對雙方的觀點方面,做了一個積極的嘗試。然而,對於如何用反饋機制,真正改變下一次遇到欺騙之前發生的事,不管是這兩方之間,或是他們中的一個人與另外一個人之間,少有考慮。此外,這些模型是設計用來解釋已經發生的欺騙行為,並沒有充分考慮,作為一系列策略之一的欺騙選擇,背後的過程。這正是Hendry和Kloep(2002)的發展挑戰模型的用武之處:理解發展如何可能成功發生,而不是導致停滯或衰退,以及這如何影響未來的互動。它進一步給我們提供一個機會,去探索人們如何選擇欺騙,作為一種滿足他們面臨的交流任務的一個合適的策略。畢竟,如果一個人沒有充足的資源,能說謊成功,那麼他或她可能認為,誠實才是最好的方法。然而,另一方面,情況可能不是這樣,我們在後面章節中將會看到,有些例子個體堅持說謊。
雖然這本書的餘下部分,探索這些問題,但是,這一章的剩餘部分,強調“欺騙資源庫”的一些關鍵特徵(圖1.1)。有些成分是由Hendry和Kloep建議,而其他的一些成分,由於它們與欺騙有具體關係,而一直被包括進來。資源庫的所有方面,都可以獨立操作,或彼此互動,究竟哪種情況,取決於交流任務的要求。也應該注意:不管年齡,欺騙資源庫將可能包含類似的成分,儘管個體資源量和資源與任務匹配的充分性,不管怎樣,隨年齡而變。例如,在生活中,通過一系列社會交流累積的經驗,可能會增加可用的社會技能資源。正如從圖1.1能看到的那樣,這些進入到五個不同的類別:
圖1.1 欺騙資源庫
圖1.1 欺騙資源庫
在下一章中,我們將給每一個類別,選出一些最突出的例子,對考慮的一系列相關因素,提供一個概述,並進行回顧。正如從這個信息中將看到的那樣,預測青少年欺騙的因素,極其多樣,可能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影響欺騙過程。然而,在本書中,不可能對此盡述,這也正為什麼,我們只包括最突出因素。有關欺騙資源庫的更詳細內容,可見Gozna和Taylor(2011),在那裡,給出更大範圍的可能資源,此外還進一步詳述,關於這些如何應用到欺騙選擇和成功欺騙中。
本章小結
儘管欺騙學術研究,已超過40年,但是,還有很多空白,需要填充。最大的空白之一是:未能充分強調,欺騙是一個過程,其中,經過個體一生的過程,他們能成功地(或者,甚至不成功的策略)發展。很多研究工作,還有一個生態效度的問題,這限制可以應用到真實世界環境的知識。此外,對於那些與年輕人一起工作的人來說,已經發現一些挑戰,具體說來,在採取一種整體的和靈活的方法,還有有效交流,以實現一個特定的交流目標方面。理論的空白和實踐的挑戰,二者都為應用一種發展的方法,特別是動態系統的觀點所強調。這種觀點,明確考慮一個人的個人特點與更廣泛的個體間或情境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可以提供廣泛的、靈活的總覽,而這正是這個領域的理論者和從業者可能正在尋求的。隨後,我們將呈現,既可以應用到欺騙選擇,也可以應用到欺騙成功的一個動態系統方法的例子。發展挑戰模型(例如,Hendry and Kloep,2012)將發展看做是:通過成功完成一系列挑戰來實現;當一個人有充份的資源,來處理面臨的挑戰時,成功完成發生。這些資源符合五種不同類別,在下一章,我們將給出這些類別的例子。
欺騙交流是一個日常的、畢生的和複雜的過程。它可以在一系列不同的環境裡,在與陌生人、朋友、合作者和家庭成員的關係中出現,甚至所有年齡群體都有。例如,我們可以想像一位五歲的小孩,假裝她沒吃巧克力蛋糕(儘管她嘴邊沾著的巧克力,已經證明她吃了),父親對他蹣跚學步的孩子說,要做個好孩子, “否則聖誕老人不來看你”,宣稱在朋友家“學習”的青少年,實際上打扮一番去了酒吧。我們也可以想到,因非常規交易而被調查的銀行家,因懷疑從商店偷東西,而被拘捕的領養老金者,以及偷車超速行駛被抓到後,正在接受訪談的青少年。考慮到有這麼多可能的欺騙情境,每一個都建立在一種不同的欺騙者和目標之間關係的基礎上,每一個都被一個不同的結果或動機驅使,我們怎樣才能將這些不同種類的欺騙弄明白?
完成這個任務的一個辦法是:制定一些明確的一般規則,它們可以嚴格應用到每一種欺騙情境。雖然這可能不完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們能用它來解釋人們說的大部分謊言――至少如果這個原則足夠一般的話。這肯定會正確嗎?畢竟,這正是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聲稱去做的,不是嗎?關於說謊者的行為之信念研究表明:對於說謊者做什麼,我們秉持普遍的知覺,這些在全世界範圍內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全球欺騙研究團隊,2006)。然而,當提到說謊者展現出來的真實行為的研究時(例如,DePaulo,Lindsay,Malone,Muhlenbruck,Charlton,& Cooper,2003),情景就沒那麼清晰了。實際上,區分說真話者和說謊者的那些線索,受到下列因素的影響:與目標的關係,做出計劃的數量,謊言本身的目的或動機。因此,我們明顯應該強調,欺騙交流的完整範圍,包括:目的、關係、背景和說謊者的年齡。在這本書中,我們考慮人生中的一段時期――青少年時期――並且檢驗欺騙的交流過程如何發展。
因此,這本書考慮,青少年何時和為什麼選擇去說謊,他們有多成功,以及他們的謊言可能怎樣被成年人或其他同齡人發現。它包括來自一系列生活環境的青少年的資料:那些來自明顯穩定的家庭背景,他們在學校成績也較好;那些來自混亂的家庭環境,或有行為或人格障礙;以及那些發現自己處在他們“被迫”說謊境地,以擺脫麻煩或支持朋友。不管怎樣,這本書的主要觀點是:不可能離開更廣泛的行為,單獨考慮欺騙,因此,我們提出一種整體的方法,來理解和解釋這樣的行為。欺騙的交流,在成功需要的欺騙量上可能有所不同,有些交流,包含的真實內容,要比欺騙內容多。因此,只考慮欺騙,不強調說實話,是人為的和不切實際的――不考慮真實與謊言之間,存在的灰色地帶,來接觸這個領域,是不可能的。與此類似,在兩個人之間的一次互動,如果我們理解:這兩個人都是帶著一組先入之見、目標和動機,進入到那個互動中來,所有這些都可能影響互動的過程,只有這樣,才有意義。因此,為了理解這些欺騙,我們需要考慮,它們發生的更廣泛的背景。這對於父母、學術研究者和從業者來說是重要的,因為作為一種情景的方法,可以為那些捲入到覺察欺騙當中的人面臨的挑戰,提供解決的辦法。在下一部分,我們將給這些挑戰中的一些下定義。然而,首先,我們要給出欺騙和青少年時期的定義,以確保當使用這些術語時,你對它指的是什麼,有一個清楚的理解,和我們在整個這本書,採取的方法和觀點。
界定青少年時期
為了本書的目的,我們將“青少年時期”界定為10到21歲之間的一個人生階段,我們選擇這個定義,出於以下幾種原因:
1 它通常包括已達法定責任年齡(即,那些被認為可以為他們的行為負責,並受刑事司法體系某種形式的制裁)的年輕人。現在,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犯罪責任年齡是10歲,儘管12歲以下的兒童,除非犯一種嚴重的罪,那種一個成年人犯會被判至少14年監禁的類型,否則不會受到監禁判決(青年司法局,2009)。此外,18到21歲之間,受到監禁判決的犯罪者,將在年輕犯罪者的機構中拘留,或在成年人監獄,隔離出來的部分中拘留,也由刑事司法體系另行受理(監獄機構,2009a,2009b)。
2 這樣一個定義,涵蓋所有像術語“十幾歲的孩子”和“青少年”所指的所謂的“青少年時期”,至少對大部分人來說,可以替換使用。因為在英國的年輕人,住在家裡的時間越來越長(在英國,2006年,年齡在20-24歲之間的年輕人,有58%的男性和39%的女性仍然與他們的父母住在家裡,與之相比,1991年,分別為50%和32%;國家統計局,2007),與建立自主性有關的問題,同樣可以很好地應用到那些19或20歲人身上,在西方社會,傳統上已視之為成年人。
3 因為青少年時期是一個過渡時期,在這段時期,我們從那些適用于兒童期的欺騙方法,轉移到成年人使用的欺騙策略,這樣一種跨度,需要考慮這些改變。在家庭中,權力關係的變化,在教育和司法系統中,為行為負責,和成年人在一系列環境裡秉持的,對青少年的知覺,都只是這個過渡時期的一些特徵。
界定欺騙
在該領域,普遍接受的欺騙定義是Vrij提出的(2008,p.15)那些定義,他說欺騙是:“一種成功的或不成功的有意企圖,沒有提前預警,給別人創造一種交流者知道是不真實的信念”;Ekman(2001,p.41)認為,說謊具體指的是:“……誤導一位目標的有意選擇,一點兒也不告訴你,想要這麼做。說謊有兩個主要形式:隱瞞……和歪曲。”
這兩個定義都包括:欺騙者一方,有意的成分,欺騙目標一方,沒覺察到欺騙,和信念或理解上的一種改變。二者都沒有要求欺騙一定要成功。然而,這是顯而易見的,包括大量不同的行為,例如,直接說假話,歪曲事實和隱瞞某些真相。我們說謊的目的也千差萬別,可能包括:讓我們自己顯得更好,保護他人,獲得某種形式的物質利益和避免懲罰而去欺騙。DePaulo和同事們對日常謊言進行的日記研究(DePaulo,Kashy,Kirkendol,Wyer,& Epstein,1996)發現,在日常的欺騙交流中,所有這些都是重要的目的。我們也可以在面對面或通過媒介的交流中,有或沒有第三方支持和共謀的情況下,通過言語或非言語的手段,誤導他人。因此,儘管在領域內普遍接受欺騙的定義本身,但是,在這些定義中,所指的交流行為是極為不同的,常常可能既複雜又深奧。實際上,欺騙只是一系列可能的交流策略和選擇之一。青少年(和成人)常常會選擇誠實地交流或部分欺騙,即使這對直接的目的似乎沒有完全優勢;常常因為直接目的可能沒有長期目的那麼突出。這意味著,欺騙呈現很多不同的挑戰,既有來自學術的,也有來自實踐的觀點。現在,我們考慮這些。
對學術欺騙研究的挑戰
欺騙行為的心理學方法,是設計用來解釋,為什麼謊言失敗和說謊者表現出的行為類型。一般來說,因為兩類原因,預期謊言會失敗:由於情緒喚起(和相關的過度控制)和認知負載(例如,Ekman,2001;Vrij,2004)。預期說謊的行為會喚起情緒,這是因為假定:欺騙的行為將導致內疚的感覺,害怕被抓或“欺騙的快感”(與一種成功地欺騙有關的興奮)。然而,這些欺騙的方法是基於如下一種觀點:欺騙是對情境的反應,而不是有意的策略性的選擇,以呈現他們自己最好的一面。最近關於考慮策略和自我-呈現(例如,Hartwig,Granhag,&Strömwall,2007),而不依賴具體的欺騙線索的研究,特別是根據近期大範圍元分析(DePaulo等,2003)的研究,給予支持。然而,還要進一步研究,發現這些方法的真正好處。
此外,雖然在考慮欺騙者和欺騙對象之間,如何聯繫(例如,對朋友與對陌生人說話)方面,有一些嘗試,但是,對於這些互動的複雜和動態本質,理解仍然不充分。先前考慮欺騙的互動本質的嘗試(例如,Buller & Burgoon,1996),沒有取得完全地成功(例如,DePaulo,Ansfield,& Bell,1996),而且,雖然通過計算機-調節的交流,在理解欺騙方面,取得一些進步(例如,Carlson,George,Burgoon,Adkins,& White,2004),但是日常的和法庭欺騙的過程,仍不清楚。
最後,對於主要依賴大學生樣本的很多學術研究來說,生態效度一直是一個挑戰,雖然有些研究的確包括一些更年長的成人,或者來自社會(例如,Vrij,Akehurst,Brown,& Mann,2006)或者來自從業者群體(例如,Vrij,Mann,Robbins,& Robinson,2006)。後面這些研究,常常探索覺察的組間差異,認為:在這些方面,訓練或從業者的經驗是重要的。正如在下一節中將會討論的那樣,需要提出有關此類研究應用到真實世界情境的普遍性的問題。然而,還有一個跟本書特別有關的更基本的問題出現。這些研究中,大多數都有這樣一個假設:除了性別、職業、人格或有限的情境變量(通常單獨逐一操縱)外,所有欺騙者,自十幾歲開始,在他們的能力方面,大致是相似的。換句話說,沒有考慮,在特定情境下,採取的欺騙策略,或選擇欺騙還是說實話方面,存在畢生的發展。考慮到不同種類的經驗,或者是關係熟悉度方面(例如McCornack & Levine,1990a,1990b),或者是從業者的經驗(例如Vrij等,2006),被認為是有關的,採用這樣一種假設,太讓人意外了。畢竟,當兒童進入青少年時期時,諸如閱讀能力、抽象推理,和親密關係中的交流,這樣的認知和社會能力的發展並沒有停止;恰恰相反,它持續一生。因此,有什麼理由認為,欺騙的選擇和能力,在青少年時期和成年期之間,就應該停止發展嗎?
當然,對於這種普遍的模式來說,也有一些例外,一些研究者讓年輕人說出關於他們說謊的類型和這樣做的理由(Arnett-Jensen,Arnett,Feldman,& Cauffman,2004;Perkins & Turiel,2007)。此外,說謊的可能性,與父母關係和青少年的人格有關(例如,Engels,Finkenhauer,& van Kooten,2006)。然而,在這些文獻中,大部分假設一直是:欺騙是一種負面的或有問題的行為,至於欺騙交流的功能性或適應性的本質,尚未被充分考慮。此外,很少有人關注青少年成功進行非誠實交流的方式。理解這些,以及青少年謊言的不同動機,最終可能幫助欺騙學術研究領域,並能採取一種將欺騙的情境看作是一個整體的更廣泛的觀點。
對從業者的挑戰
正如學術研究者所面臨的挑戰一樣,那些從事年輕人工作的人也面臨挑戰,尤其是與他們的決定和互動有關的問題。這類挑戰特別適用於當一位年輕人表現出欺騙或有挑戰性的行為時,但是與孩子從事中度功能性/適應性欺騙的父母和教師也有關。第一個挑戰要考慮:年輕人在情境中的表現――採用一種整體的方法,專為討論中的個體量身定做。這個情境應該包括:青少年的背景信息,是否有任何障礙存在(例如,人格或行為障礙),他們之前與目標的經驗,以及與討論中的問題有關的其他證據或信息。這既需要理解展現出來的行為和此類行為背後的動機,還需要理解這類動機的起源。採用這種整體的方法,可以讓我們洞悉,表現和表現風格本身的來源。這與第6章中談及的變色龍表現特別有關,這也是它的一個關鍵特徵,但是對於解釋第3章中討論的人際謊言也有用。
除了理解“整個人”以外,從業者面臨的進一步挑戰是:與他們與之談話的年輕人有效地交流。與一位這樣的人交流,例如,在過去多個場合,一直對重要的成人失望,可能存在特定的信任問題。然而,與那種看起來順從,但是拒絕承認“他們的行為可能是一個問題”的年輕人交流,同樣存在挑戰。因此,對於父母、教師和其他從業者來說,靈活的交流方法尤為重要,讓他們有效地回應一系列挑戰性交流。當一個年輕人呈現出複雜的和有挑戰性的行為:包括一些欺騙的成分和一些真實的信息,沒有“客觀的”方法鑒定給出的信息時,尤其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從業者可能面臨管理困難行為,也面對獲得與訪談目標最有關係的信息的問題。在政界,政治家對直接質疑的反應,可以說明這種挑戰,直接質問能導致回避的和模棱兩可(Bull,2006)。這樣一種避免對一個問題作出充分回應的策略,年輕人可以輕鬆採用,這些在第3章和第5章個案例子中,將非常明顯。
對於那些從事實踐工作的人來說,最後一個,也與有效交流挑戰有關的挑戰是:有效回應。在這裡,從業者再次需要確保:訪談的目標能夠實現,它們能在他們的整個互動過程中,都堅持目標。一個有利的因素是:理解為什麼是青少年說謊。因此,這也是本書關鍵目標之一――在第3和第5章中提出。然而,作為這的一部分,從業者需要瞭解他們自己對他們訪談的年輕人之預期,以及過去的經驗和接觸,如何既能幫助,也能阻礙我們接下來的交流。我們從社會認知中的研究知道:人們的先在概念,可以影響他們對模棱兩可的信息(例如,Wilkowski,Robinson,Gordon,& Troop-Gordon,2007),他們提出的問題類型,甚或記得的互動方式的解釋。此外,關於內隱的社會認知的研究表明:這些預期,即使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但仍有一種影響(例如,Knowles,Lowery,& Schaumberg,2010)。
因此,對他們自己的預期,缺少洞察,可能會起反作用,阻礙年輕人與從業者之間的成功地交流。當說謊是功能性和適應性的,人際表現是用來實現一個與發生的互動無關的目標時,這尤其有關。從業者對這樣一種交流,有一種過份負面或防禦性的反應,可能正是被訪談者所尋求的,因為這正好肯定了他們對自己的看法,或他們對成人如何看他們的看法。與此類似,正如在下一章中將會看到的那樣,當指控年輕人一些他們實際上沒做過的事時,他們可以體會到強烈的不公正或不公平的感覺,而這可能會對年輕人與相關指控者之間的關係有負面的影響。在某些社區,管轄年輕人時,感知到的英國警察叫停和搜查權力的不公正、非法或濫用的相關報道,已經引起那些被挑出來檢查的人的反感,並常常成為媒體和政黨批評的對象,這也說明了這種負面的反應。在這樣的例子中,年輕人報告說:跟其他們社區的其他成員相比,他們被叫停的次數過多,儘管警察正確叫停一個人的次數報道為較差。這可能會導致年輕人認為:這樣的權利是不合適的,因此他們更難信服它們被使用。例如,Porter和Hirsch的“自由中心”博客(2009年9月2日)描述在索爾茲伯裡市藝術中心的一起事件,在那裡,兒童參加舞蹈和搖滾活動,專門設計用來“解釋”叫停和搜查權利。組織者認為,這是在涉及年輕人的群體內,建立更高水平的社區參與和公民權的一種手段。然而,組織者實際上可能將他們可接受的童年期觀點“強加”給該群體。這種觀點顯然是Porter和Tirsch的共識,他們海報的題目是“訓練兒童服從”,提出關於這類行為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問題。與此類似,英國的喜劇演員Mark Thomas,曾為可能成為非法搜查對象的人們,生產過一部“手持可下載卡”。這張卡警告警官:“我發誓,如果你決定浪費我的時間,我也要浪費你的時間”(2009年2月10日,“監護人”)。儘管對專業的警察活動來說,這是一種輕率無禮的反應,但是這種批評也反映了與從業者特別有關的一個問題,即何時正確地假定欺騙,何時接受一位年輕人說他們是無辜的斷言。畢竟,如果你的決定不僅被基層管理人員,而且也要被那些媒體和大眾“判斷”和“問責”,那麼,權衡一位年輕人表現的任務,遠沒有那麼抽象了。雖然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是,這本書的內容,是為幫助那些從業者做出最好的決定而寫。
一種發展的方法之貢獻
在前兩個部分,已經發現對學術欺騙研究和實際方面的一些問題。在這本書中,主要觀點之一是:一種發展的方法,特別是一種動態系統的方法,提供一種必要的整體觀,學者和從業者都可以採用,來加強他們對人際表現中,可信性評估的理解。這是因為一種動態系統的方法:
• 通過連接所有水平的系統(從個體的生理水平,到更廣泛的社會因素,例如,政治系統),調節發展。這些連接是動態的,兩個方向都可以進入。
• 認為個體和周圍環境系統,都是可以改變的。
• 考慮不同學科工作的人之間的互動,對全面理解發展,至關重要。
• 考慮到系統內“限制”的可能性。
• 拒絕簡單的二分法(Lerner,2006)。
因此,當我們考慮青少年表現的可信性,並採取一種動態系統方法(該方法也有上面Lerner列出的特徵)時,我們才有可能看到,一位年輕的犯罪者承認攻擊,如何可以掩藏正在發生的犯罪或非犯罪活動,或一個地區經濟不穩定,如何導致一位11歲的人,由於擔心父母被解雇,而變得內向和退縮。在一種動態系統方法內,我們也有可能看到,一位在6個月的時間裡,曾經為了每週去酒吧至少兩次,而與父母說謊的一位15歲女孩,與一群“壞傢伙”混在一起,不寫作業,最終在23歲時,從大學畢業,同時獲得一個碩士學位的顯著差別。最後,這種方法使我們能洞悉一位年輕人離開家之前,說了一句“媽,我去Lucy家學習”這句話的深意,表面上這是真的,但最終卻呈現一個完全不同的內容(即,我是去那裡,但是我沒告訴你的是,我的男朋友也會去那裡)。因此,這種方法是整體的、靈活的,提供對親社會和反社會行為的洞察,對從業者和學者都有利。
下一個部分將更詳細地考慮,如何應用這種方法。首先,我們將籠統考慮過程論――包括關於發展軌跡的研究。然後,將更詳細地討論,動態系統的方法。最後,一個具體的系統方法――發展挑戰模型――將被呈現,作為處理年輕人的交流選擇和相關後果問題的一種方式。
發展的過程論
發展軌跡
畢生方法和那些考慮發展發生過程的方法,已經應用到青少年發展的相關領域。與犯罪學中“犯罪生涯方法”(例如Farrington,2003)一致,在犯罪領域工作的研究者,長期以來一直對犯罪軌跡,以及那些持續犯罪的人與那些停止犯罪的人之間的差異感興趣。例如,Moffitt(1997)發現兩組青少年犯罪者:那些“只在青少年時期”犯罪的人和那些“畢生持續”犯罪的人。提出兩個非常不同的犯罪群體,每一種都有不同的原因和解釋框架,這種主張,為青少年時期出現犯罪行為的高峰,提供一種有力的解釋。
據Moffit(1997)看,與人生其他時期相比,在青少年時期,犯罪盛行率和發生率增加,不僅僅是因為,一小組青少年的犯罪率增加了,而是因為,很多其他青少年,暫時從事犯罪行為。因此,很難區分那些“僅僅在青少年時期”犯罪的人與那些變得多產並且以犯罪為職業的人。然而,給年輕人貼上犯罪的標簽,有潛在的困難,因為這隨之帶來大量來自社會的相關知覺,在有些個案中,可能會導致個體只好接受這樣的事實:他們總是被看作是“犯罪者”。
Moffitt認為:畢生堅持犯罪,可能源於各種因素,包括有問題的父母關係,對於社會情境,未能學會親社會的或恰當的方法和一系列“封鎖”逃離反社會行為機會的決定。動態系統方法認為:自由度可能受生活選擇的限制,從事反社會活動,可能表示缺乏社會敏感性,控制衝動也較差。Huesmann,Eron,Lefkowitz和Walder(1984)檢查參與者三代的攻擊行為,也探索攻擊行為從8歲到30歲的穩定性。雖然在8歲到30歲的年齡區間,觀察到攻擊水平的一些穩定性,但是在比較兒童、父母和祖父母時,可以看到更大的穩定性――那些有攻擊性的人,往往有一個有攻擊性的祖父母和父母。這種攻擊的代際傳遞,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結果,強調某些行為,在一個家庭看來,能成為一個可以接受的部分的程度。
除了這些所謂的環境因素,Moffitt還認為:畢生堅持犯罪,可能與心理病理水平有關,例如,兒童的行為障礙和心理病理。反社會人格障礙(APD)可能也與畢生堅持犯罪有關,因為患有APD的人,容易感到挫敗,非常衝動,並且很少考慮或顧及別人的觀點或情感。因此,很明顯,這個群體有一系列的相關問題,這可能會影響他們改變他們軌跡的能力或決定。
與畢生堅持犯罪者相比,Moffitt(1997)發現僅限於青少年時期的犯罪行為。Moffit認為:這是被一種想要自主的願望驅使,有一種感覺:那些已經捲入犯罪的人,沒有遭受同樣的限制,因此,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模擬。隨後,這又被犯罪帶來的明顯物質得利所強化,例如,偷衣服、汽車或高端電子設備。另一方面,這種行為還會通過成為犯罪同伴團夥中一員之社會交流,或通過保持已經得到的一種聲譽的需要,而被強化。這種觀點已得到下述證據的支持,該證據表明:與畢生堅持犯罪的年輕人在童年早期(Coie,Belding,& Underwood,1988)和成年期所處的邊緣化地位相反,他們在青少年期,在主流的同伴群體中實際上起著更重要的作用(Elliott & Menard,1996)。然而,這組犯罪者因為以下幾個原因不再犯罪,包括:承認並發現各種犯罪導致的負面後果;體會到刑事司法體系之現實(例如,被送到一個少年犯機構);成為犯罪的一個犧牲品;或者已經進入一個正確的軌道。這可能是因為,僅限於青少年時期犯罪的人,很少有人格障礙和認知的局限性,或者是因為,組已經擁有發展一種親社會行為技能的機會。然而,已經出現精神問題特徵的年輕犯罪者,仍然有可能樂於將他們的關注點轉向積極的目標,這取決於他們衝動的水平和相關的行為。
Livingston,Stewart,Allard和Ogilvie(2008)採用這種理論觀點,對澳大利亞一個超過4000人的年輕犯罪團夥,進行了長達6年的數據追蹤。在他們的樣本中,發現三種不同的犯罪軌跡:一組“早高峰-變緩”犯罪者,一組“晚開始-變緩犯罪者”,一組長期的犯罪者。在這個樣本中,跟其餘兩個犯罪群組相比,長期犯罪者更可能是男性和土著人群成員,出現在一個成年人法庭上可能,也要比其它兩個犯罪組別高兩倍。這表明:檢查一系列因素並採取一種畢生的方法之重要性。與其他系統方法,諸如,生態方法,所共有的特徵,將在接下來討論。
布朗芬布倫納的生態學方法(Bronfenbrenner’s ecological approach)
布朗芬布倫納的生態學方法(例如,Bronfenbrenner,1979)並沒有將發展概念化為一系列有質的區別的階段。與此相反,將發展發生的過程,作為人與環境之間一個“進化互動”的結果,來討論和闡述(p.3)。這種人-環境互動,在不同分析水平上考慮,因此,構成不同的環境,也構成它們之間的互動。正如布朗芬布倫納(1979,p.3)說的那樣:“生態環境被認為是一系列嵌套結構,一個套在另一個裡面,像俄羅斯套娃一樣。”
第一個水平,微觀-系統(micro-system),由個體及其所處的直接環境(諸如學校、家庭)組成。接下來就是外-系統(exo-system),這個術語指的是發展的更廣泛環境,還有宏觀-系統(macro-system),仍然更廣泛,並包括社會特徵和文化規範。此外,這個模型包括不同微觀-系統之間的動態互動,這稱為中系統(meso-systems)。例如,一位15歲的人,在一個特別的晚上,決定對他打算去酒吧的事,向他的父母說謊,這個決定可能取決於:
他與他父母的關係(微觀-系統)
父母彼此之間的關係(對父母來說是一個微觀-系統,對15歲的孩子來說是一個外-系統)
對一位15歲大的孩子去哪裡是可以接受的社會界定(宏觀系統)
青少年-父母關係與父母-父母關係之間的相互作用,在這個例子當中就是中系統。儘管在此之前,這個模型沒有應用在欺騙的研究上,但是這個模型在解釋和理解欺騙行為方面,有獨特的優勢,因為它考慮到多個因素之間的動態交互作用,並且承認交流的基礎明顯是兩個微觀-系統之間的聯繫,也就是中系統。然而,僅這個模型本身,不足以讓我們詳細解釋基本機制,該機制預測欺騙選擇和欺騙成功。因此,為了充分理解它,我們有必要利用另外一種方法,發展挑戰模型在這裡是關鍵的,因為它充分闡述不同系統水平之間的關係,並且能解釋這些如何能應用到一個特定的目標上。
發展挑戰模型
Hendry 和 Kloep(2012)的發展挑戰模型有三個成分:資源庫、潛在任務庫和任務-資源互動。基本觀點是:通過成功完成適當的挑戰任務,發展才能發生。對每個個體來說,他擁有的“資源庫”都是獨一無二的,是一個生物學特質、社會資源、技能、自我-效能和結構特徵的組合物。這個可能的資源庫,然後用來滿足特定的挑戰,關鍵是:一個人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擁有的資源恰好用來滿足面臨的挑戰。下面,我們將根據面臨的挑戰和一個人可用的資源,來解釋任務的結果:
•如果任務是適當的挑戰,並能被成功處理,那麼發展發生。
•如果資源不足以滿足任務,並且這種事件狀態持續一段時間,那麼很可能會出現某種形式的延遲。
•如果任務不是適當的挑戰,那麼有可能:一個個體將發生停滯――在心滿意足的停滯或不高興的停滯之間,做出一種區分。
選擇欺騙,作為一種交流方式,是滿足一個具體情境中挑戰的一個可能手段,這種選擇本身將取決於可用的資源(和這個人對它們的準確評估)。已經做出欺騙的選擇後,將它成功執行出去,將進一步取決於可用的資源數量,和它們與一個特定的欺騙任務要求的匹配。
儘管對每個人來說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是對具體任務來說,最適合的因素類型,還是有可能做出一些概括,在下面的部分,將呈現一個“欺騙資源庫”。像Bronfenbrenner一樣,Hendry和Kloep(2012)呈現一個動態系統,有些是成功滿足挑戰後進化的結果,而且這考慮到包含反饋和反饋將如何影響未來發展。Hendry和Kloep考慮了常態和非常態的轉變(對大多數人來說,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的確發生或沒發生的那些事),在這裡是重要的,因為對青少年來說,“嘗試”新的身份和要求自主性是至關重要的發展過程,但是作為常態事件的一部分,可能並不總是發生。
此外,常態和非常態的社會定義,可能對這些挑戰出現的方式,有強烈地影響,因此,直接影響到欺騙選擇和欺騙成功。最後,構成資源庫的因素範圍,和發展中的個體面臨的可能的任務範圍,似乎強調一些在當代欺騙研究模型中缺少的,相互作用和策略的複雜性的問題。
修訂版的發展挑戰模型
修改版的發展挑戰模型,應用到欺騙時,繼續對人類發展,採取一種系統的畢生方法。正如與Hendry和Kloeap(2012)呈現的發展挑戰模型一樣,修改版的模型,對發展採取一種多維“系統的”過程方法。這與傳統的階段論,或甚至是發展的簡單線性過程,形成對照。但是,這個修訂的模型,的確偏離原來的模型,它強調“開放系統”的作用,因而,將人與他或她可能所處的更大系統之間的邊界,移除了。
正如Kloep和Hendry(在出版中)指出那樣,開放系統不斷接受信息流、能量流和資源流。這意味著:個體的狀態,可能會因為更大系統的變化而改變。例如,某個站出來在一群同齡人面前作一個報告的人,最初,他們的演講可能有點緊張,當他們看到,有些聽眾點頭和微笑時,可能變得更加自信,但是,當他們的老闆走進房間時,他的自信心可能經歷一個短暫地下降。
在其他情境,也就是眾所周知的吸引子狀態(attractor states),系統可能在某一時間階段表現得穩定,但是隨著信息、能力和資源的累積,接著就發生變化。例如,有些人,可能開心地在保險公司工作15年(一個吸引子狀態或一種平衡狀態),然而,一個看似無關的事件(他的父母退休,移居西班牙),可能讓他決定,重新回到大學,為獲得一個高等學位而學習。如果對這個人的這個決定進行深度訪談,那麼他可能會談到“意識到生命是值得一過得”,也會引用他的伴侶感覺,他在他或她的工作中被低估,過去一年裡他們自己感覺健康出了狀況,以及他們的孩子升到中學。因此,從吸引子狀態中移出,並不是一個事件,而是能量的累積。這解釋了:為什麼同一個人,與一個目標,在一次交流時,決定去說謊,與同一個目標,在另一次交流時,決定要誠實。例如,一位12歲的孩子,對週一去一位朋友家學習,決定對父母說謊,但是在週五,就說實話要去參加派對。或者同一位12歲的孩子,可能會在為什麼一周都遲到的問題上成功說謊,但是在家庭作業為什麼沒有完成的事情上,就不能用一個謊言僥倖成功了。這個修訂的模型,也考慮欺騙交流的動態本質――這隨欺騙者、發現者和欺騙情境(每一個都帶著特徵給交流過程)之間的互動而展開。最後,吸引子狀態的概念可以為,對欺騙的交流仍保留“孩子般”方法的青少年,將成功的欺騙轉移到更危險的欺騙情境的青少年,或者即使面臨明顯的不相信,依然堅持不成功的交流策略的青少年,提供一種有用的解釋機制。
欺騙資源庫和任務-資源互動
欺騙學術研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即使欺騙行為的當代交流模型,也沒有充分解釋欺騙察覺中涉及的過程。這些模型,在將欺騙過程看作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整合欺騙者和察覺者的觀點,體現反饋對雙方的觀點方面,做了一個積極的嘗試。然而,對於如何用反饋機制,真正改變下一次遇到欺騙之前發生的事,不管是這兩方之間,或是他們中的一個人與另外一個人之間,少有考慮。此外,這些模型是設計用來解釋已經發生的欺騙行為,並沒有充分考慮,作為一系列策略之一的欺騙選擇,背後的過程。這正是Hendry和Kloep(2002)的發展挑戰模型的用武之處:理解發展如何可能成功發生,而不是導致停滯或衰退,以及這如何影響未來的互動。它進一步給我們提供一個機會,去探索人們如何選擇欺騙,作為一種滿足他們面臨的交流任務的一個合適的策略。畢竟,如果一個人沒有充足的資源,能說謊成功,那麼他或她可能認為,誠實才是最好的方法。然而,另一方面,情況可能不是這樣,我們在後面章節中將會看到,有些例子個體堅持說謊。
雖然這本書的餘下部分,探索這些問題,但是,這一章的剩餘部分,強調“欺騙資源庫”的一些關鍵特徵(圖1.1)。有些成分是由Hendry和Kloep建議,而其他的一些成分,由於它們與欺騙有具體關係,而一直被包括進來。資源庫的所有方面,都可以獨立操作,或彼此互動,究竟哪種情況,取決於交流任務的要求。也應該注意:不管年齡,欺騙資源庫將可能包含類似的成分,儘管個體資源量和資源與任務匹配的充分性,不管怎樣,隨年齡而變。例如,在生活中,通過一系列社會交流累積的經驗,可能會增加可用的社會技能資源。正如從圖1.1能看到的那樣,這些進入到五個不同的類別:
圖1.1 欺騙資源庫
圖1.1 欺騙資源庫
在下一章中,我們將給每一個類別,選出一些最突出的例子,對考慮的一系列相關因素,提供一個概述,並進行回顧。正如從這個信息中將看到的那樣,預測青少年欺騙的因素,極其多樣,可能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影響欺騙過程。然而,在本書中,不可能對此盡述,這也正為什麼,我們只包括最突出因素。有關欺騙資源庫的更詳細內容,可見Gozna和Taylor(2011),在那裡,給出更大範圍的可能資源,此外還進一步詳述,關於這些如何應用到欺騙選擇和成功欺騙中。
本章小結
儘管欺騙學術研究,已超過40年,但是,還有很多空白,需要填充。最大的空白之一是:未能充分強調,欺騙是一個過程,其中,經過個體一生的過程,他們能成功地(或者,甚至不成功的策略)發展。很多研究工作,還有一個生態效度的問題,這限制可以應用到真實世界環境的知識。此外,對於那些與年輕人一起工作的人來說,已經發現一些挑戰,具體說來,在採取一種整體的和靈活的方法,還有有效交流,以實現一個特定的交流目標方面。理論的空白和實踐的挑戰,二者都為應用一種發展的方法,特別是動態系統的觀點所強調。這種觀點,明確考慮一個人的個人特點與更廣泛的個體間或情境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可以提供廣泛的、靈活的總覽,而這正是這個領域的理論者和從業者可能正在尋求的。隨後,我們將呈現,既可以應用到欺騙選擇,也可以應用到欺騙成功的一個動態系統方法的例子。發展挑戰模型(例如,Hendry and Kloep,2012)將發展看做是:通過成功完成一系列挑戰來實現;當一個人有充份的資源,來處理面臨的挑戰時,成功完成發生。這些資源符合五種不同類別,在下一章,我們將給出這些類別的例子。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