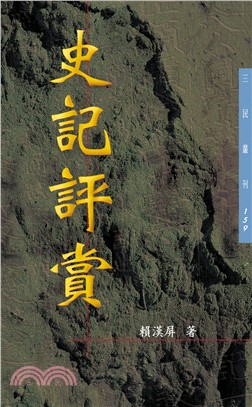商品簡介
★在抗戰烽火中,訴說流亡學生的顛沛和堅韌。
★以切身的動盪,文學靈魂首次舒展雙翼。
★多項得獎紀錄:
第十八屆國家文藝獎
歷史嘉年華歷史書寫者致敬奬
在場主義㪚文獎(與許知遠合得)
新浪網年度好書
廣州南方都市報年度好書
光明日報光明好書榜
北京新京報年度好書
人民日報年度好書
華語傳媒大奨提名第一名
入選深圳各媒體合辦十大好書
在《怒目少年》那樣的年紀,開始窗隙窺月,霧裡看花,一路挺胸昂首,沒有天使指引、先知預告,自以為是,坎坎坷坷。沒關係,只要你長大。人活著,好比打開一架攝影機,少年時底片感光,不曾顯影,一直儲存著,隨年齒增長,一張一張洗出來。──王鼎鈞
流亡是逃命,是拚命,是乩童跳灰過火。
流亡不是東張西望,看山看水。
流亡不是前仰後合的唱歌,看見一塊草地就坐下來。
流亡者,沒有那份閒心。
《昨天的雲》裡那位不識愁滋味的少年,到了《怒目少年》那樣的年紀,漸漸知悉世事道理。因為戰爭,離別、勞碌、疾病、飢餓、欺騙甚至死亡交集;因為戰爭,忍耐、鍛鍊、擔當、覺悟與理想,皆於是覺醒。
此為作者回憶錄二部曲,記述一九四二年前往抗戰後方,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為止,少年事猶如血的化身,是作者對中國社會所作的見證。
作者簡介
王鼎鈞
1925年生,山東省臨沂縣人。抗戰末期棄學從軍,1949年來台,曾任中廣公司編審、製作組長、專門委員,中國文化學院講師,中國電視公司編審組長,幼獅文化公司期刊部代理總編輯,《中國時報》主筆,「人間」副刊主編,美國西東大學雙語教程中心華文主編。目前旅居美國。
曾獲金鼎獎,台北中國文藝協會文藝評論獎章,中山文化基金會文藝獎,中國時報文學獎散文推薦獎,吳魯芹散文獎。1999年《開放的人生》榮獲文建會及聯合副刊評選為「台灣文學經典三十」。2001年,獲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傑出華人會員」獎牌。
著有散文「人生三書」《開放的人生》、《人生試金石》、《我們現代人》;《碎琉璃》、《山裡山外》、《左心房漩渦》、《小而美散文》。小說《單身溫度》。論著「作文四書」《靈感》、《文學種籽》、《作文七巧》、《作文十九問》等。
序
與生命對話
1
這些年,常常看見有人在文章裡質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中國人會生氣,敢生氣,也曾經怒不可遏。「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一齊怒火炙心的時候,也曾使「山岳崩頹、風雲變色」,一個人忍無可忍的時候,也曾「忘其身以及其親」。
遠者固無論矣,以我及身所見所聞,中國人為了「華人與犬不得入內」而生氣,為了揮動東洋刀砍掉中國人的腦袋再哈哈大笑而生氣,直氣得開著大卡車衝進黃埔江,氣得把一排木柄手榴彈綁在前胸後背往坦克車底下鑽。中國人也為了從香港到重慶的飛機上有一隻洋狗而生氣,也曾為了莊稼漢沿街叫賣他的小女兒而生氣,直氣得拋下老婆孩子遠走高飛、隱名埋姓,二十年後再回來清算他的親族鄉黨。
中國人生了氣,有時候像滾水,有時像火山。抗戰軍興,中國人蓄怒待發,出氣的對象有變化,先對外國,後對本國。許多事我或在局外、或在局內,許多人我或者理解、或者迷惑。許多人,包括我在內,我們不知道何時,何故發生這種載舟覆舟的變化,我們不是秋風未動蟬先覺,而是秋風已動蟬先落。原來人的情緒那麼不可測,後果那麼不可預估,許多人這才修心制忿。
出入於兩種怒氣(對外國和對本國)之間的我,以一個少年人的受想行識,構成《怒目少年》這本書的內容。繼《昨天的雲》之後,這是我的第二本回憶錄,──應該說是第二部分。它記述由一九四二年我前往抗戰後方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為止,我對中國社會所作的見證。「兩種怒氣」的消長即發生在這段日子裡。
2
奇怪為甚麼有人寫文章?寫作,依我看,有如下的效用:
謀利益(經商)賺了錢
出惡氣(快意)報了怨
結世緣(交友)得了名
廣信念(傳心)載了道
盡善美(入聖)登了峰
參化育(法天)成了神
排列起來似乎有等級,越往後境界越高,到「盡善美、參化育」幾乎高不可攀。儘管如此,它們仍然存而不廢,做天下後世追求的目標。
多年以前,中國作家處境惡劣,有時連傳心交友都有不測之禍,「謀利益」只好作政治投機,「出惡氣」與虐待狂難分,所謂信念,淪為「一紙崇高神聖之胡言亂語」,盡善美、參化育乃是雲霄羽毛,四顧茫茫。如此作品,不但「今日所作、明日必悔」,也是「昨日所作、今日已滅」。一九七七年後中共推翻文革,政策開放,大陸上有一位老作家放聲大哭,他說他寫了幾十年都白寫了。我從報上看到這句話悚然良久,連忙檢查自己的作品還能剩下多少,謝天謝地,畢竟此善於彼,我還有些「私房」手工,有些「無用之用」的古調,可以「自其不變而觀之」。我還眼前有紙,手中有筆,冥冥中有些春夏秋冬,可以補平生不平。
作家的遭際、見聞、思考,都是上天給他的訊息。作家接收訊息,「譯」成文學,縱不能參化育也要盡善美,縱不能盡善盡美也要求善求美,在有限的善美中表現無限天機。世緣可得可失,恩怨可了可忘,利益可有可無,吾生有涯,朝聞道、夕死可矣。
3
寫回憶錄需要回憶和反省,需要資料幫助回憶和激發反省。要清理五十年前少年事,得找到五十年前少年人。一九八二年,我對中國大陸展開了連續四年的通訊搜索,向「隔世」尋找我「前世」的舊識。那時,中國大陸的經濟繁而未榮,要他們花兩元人民幣回一封航空信是個負擔,我到集郵商店高價買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郵票貼在信封上,打好通信地址,把信封一個一個寄給他們使用。那幾年,我幾乎每天收到由中國大陸來的信,補足這本書需要的資料(抗戰生活),也為我寫下一本書提供助力(內戰經驗)。
五十年了,經過那麼長的戰爭和那麼多的政治運動,舊人怎會仍在原處?不錯,內戰期間的大遷徙,戰爭停止後的大清洗,他們在數難逃。他們的星球爆炸了,他們散落在黑龍江、內蒙、新疆、青海、雲南、廣西、西康,做舊世界的碎片。謝天謝地,他們還活著。種種磨難都是事實,可是他們活了過來。謝天謝地,外面風傳的大滅絕並未發生。
這些人,又是如何被我找到的呢?這多虧了中國大陸各地的僑務辦公室,簡稱僑辦。大陸上由中央到地方每一級政府都有僑辦,即使鄉鎮也有一個人兼辦這方面的業務。只要我能提出某人的原籍地址,他們一定有辦法弄個水落石出;只要我能提出某人「最後」住在何處,他們也多半能有個交代。他們人口管理嚴密,名不虛傳,僑辦執行政策之徹底我們自歎弗如。──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一九八六年以後,四海交流,統戰成功,除了有影響力的僑領,很難、或者根本不能再接到他們的回信,時也,勢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無論如何我感謝他們,我的願望已在一九八六年以前實現。我把他們的名字牢牢的記在心裡,寫在日記裡,保存在通信的檔案裡,但是不必寫在這裡。
4
我還需要閱讀。我讀戰史、方志、名人的回憶錄,我從那些書裡沒找到多少可用的材料。我說過,我關懷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貼近泥土的「黔黎」,歷史忽略了他們,不願筆生花,但願筆發光,由我照亮某種死角。說來傷感,打開那些書,皇皇巨著之中,赫赫巨人之下,青年只是一行數字,軍人只是一個番號,縣長鄉長無論有多大貢獻,總司令也不知道他姓張姓李,少將以上的部隊長才有個名字,下級官兵只在「傷亡過半」或「全體壯烈犧牲」之類的官式用語中含混提及,無定河邊骨向來不設戶籍,更無論老百姓的汗和淚了。那些書裡有天下,沒有蒼生。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東方圖書館發現一大批刊物,是中國大陸各省各縣印行的《文史資料》,這些刊物在各省各縣政協的主持下定期出版,他們長期搜集整理地方史料,作成紀錄。這一批刊物對我幫了大忙。
以我涉獵所及,一九八二年以前你在中共治下很難找到信史。但《文史資料》記鄰里鄉黨之事,影響甚小,上級不甚指導,執筆者又多是十室忠信,樸實無華,他們大概還沒聽說「上帝給我們語言文字,正是要我們掩飾事」,或者聽說過,還不能領會,他們居然不偏不倚的寫出許多真相來。──我自己身歷其境的事,是真是假我當然知道。
根據《文史資料》中的線索,我在大陸上買了一些書。隔洋買書,我的辦法是「不管有魚沒魚、先撒一網」。看見書名,猜想它的內容,買來再說,網中也許空空,那麼再撒下去。幸而大陸上出版的書,書名和書的性質大致符合,不像臺灣,書名往往脫離書本單獨供人欣賞。感謝大陸親友,他們在官吏的猜疑下、在人與人還不能和睦對待的地方辦事,忍受公車司機的喝斥、乘客的互相踐踏、書店職員的白眼、郵局櫃臺的頤指氣使,寄來我需要的著作物。我也把他們的名字牢牢的記在心裡,寫在日記裡,保存在通信的檔案裡,但是不必寫在這裡。
5
在《昨天的雲》裡那樣年紀,我們思想單純,七竅混沌,受父母庇護,無須面對挑戰,眼睛明亮然而只朝空氣看。沒關係,只要你長大。
在《怒目少年》那樣的年紀,開始窗隙窺月,霧裡看花,一路挺胸昂首,沒有天使指引、先知預告,自以為是,坎坎坷坷。沒關係,只要你長大。
人活著,好比打開一架攝影機,少年時底片感光,不曾顯影,一直儲存著,隨年齒增長,一張一張洗出來。
下一本書我打算寫三年內戰。那三年我又大了幾歲,「攝影機」的性能提高,並且知世事有遠因近果,有表象內幕,有偶然必然,有真誠偽裝。重要的是學會了作出決定並面對後果,在驚駭、抗拒、疑惑、悲痛中認識人性,長大真好。
長大了,由窗隙窺月、中庭步月進入「高臺玩月」,人生的祕密次第揭露,應驗了聖經上的話:「所有在暗室中隱藏的,都要在房頂上宣揚出來。」種種昨日,作成了一個人,這人憑天賜的基料作成了一卷或幾卷書,這一生算是,還諸大地」。
米蘭昆特拉說「回憶是依稀的微光」,我的回憶「在我大量閱讀有關史料之後」是望遠和顯微。
克莉斯蒂說「回憶是老年的補償」,我的回憶「在我洞明世事練達人情之後」是生命的對話。
有些中國老人怕回憶,如果他是強者,他有太多的孽,如果他的弱者,他有太多的恥,兩者俱不堪回首。他的回憶錄不等於回憶。
有些事情我還得仔細想。生命不留駐,似光;不停止,似風。山川大地儘你看,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浮雲。」實際上也帶不走,連袖子也得留下。不能攜帶,只有遺留或遺失,這是生命的特徵。
現在,電、報紙天天有人談論青少年。正是:
水流少年色 風飄少年春
未了少年事 又有少年人
上帝在天上,他們都會長大。
6
《怒目少年》本來由我自己出版,老友黃力智兄督印,吳氏圖書公司吳登川先生發行。現在加以修改增訂,修訂的緣由,卷末〈難忘的歲月〉一文作了交代。
《怒目少年》的寫作和發表,得到多位編輯人的支持,他們是:聯合報副刊主編瘂弦先生,中華日報副刊主編應平書女士,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梅新先生,新生報副刊主編劉靜娟女士,美國世界日報副刊主編田新彬女士,中國時報副刊主編楊澤先生。
目次
用青春走出一段青史
代序
與生命對話
第一部
出門一步,便是江湖
最危險的事情最簡單
第二部
我,一個偽造的人
要皇宮,還是要難民營?
撒豆成兵,聚沙成塔
我是校長,不是總司令
我一定能帶好你們幾千個娃娃
「入魯」並未認真實行?
戰爭是一架機器,製造祕密
師友,在光陰裡
莫等閒小看了疥癬之疾
將門子弟品嘗抗戰滋味
這樣那樣,漸漸長大
都是生物惹的禍
小說女主角會見記
貧窮的母親養育了太多的孩子
五叔毓珍
一百塊錢欠了四十年
群眾的憤怒轉向了
那天,戰爭幾乎吞噬我
我不敢感謝上帝
第三部
跟著摩西過紅海
夢中,文峰塔上的歌聲
從流亡三部曲中醒來
把好酒留到末日
世界上最長的散步
黃土平原上一行腳印
宛西,我聞我見我思
漢江,蒼天給我一條路
一個讀莊子的人談論政局
第四部
如果……這裡就是江南
最好的哲學老師
凡是你不知道的事就是新聞
從軍文告引發澎湃的熱情
悲壯與荒謬:無可評論
牛老師,戲劇與人生
新師表如此如此
孤雁不堪愁裡聽
愛情,苦悶的象徵?
千里萬里,愛情的網羅裡
打日本,我過足癮了!
總得讓我想一想
抗戰勝利,別有一番滋味
形象是日漸磨損的幣面
遲到的歌聲:散了吧
王吉林:死有銳於利刃
興安日報,文學之路第一步
第五部
大結局
附錄 難忘的歲月
參考資料
書摘/試閱
出門一步,便是江湖
詩人鄭愁予的名句:「出門一步,便是江湖。」離家五百里算是很遠了吧,哪想到後來更遠,更遠……
我一生漂泊無定。十四歲的時候開始「半流亡」,離開家,沒離開鄉。十七歲正式流亡,離開鄉,沒離開國。後來「國」也離開了。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一身之外,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說不完。
現代中國,有個名詞叫流亡學生,它前後有三個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青年入關。第二梯次,七七抗戰開始,沿海各省青年內遷。第三梯次,內戰期間,各地 青年外逃。我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那時流亡是一種潮流,流亡的青年千萬百萬,流亡很苦,很孤獨,有時也壯烈,危險。
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天離開家鄉,前往安徽阜陽。一九四二,那是個甚麼樣的年頭?
那年是民國三十一年,我十七歲。
那是中國對日抗戰第六個年頭,第二次世界大戰(依照歐美人的說法)第三個年頭。那年中日兩軍在浙贛路會戰,在太行山會戰,在湖北宜昌會戰,在湖南長沙第三次會戰。這年中國遠征軍赴緬甸與日軍作戰,英美聯軍在北非登陸,德軍進攻史達林格勒,與蘇聯苦戰。
那時,山東省鐵路公路沿線的據點,腹地重要的城鎮,都駐紮日軍,我們稱為淪陷區。但日軍以線制面的構想完全失敗,廣大的農村和山區由三種武力分治,那就是:國民政府派出的正規軍,老百姓稱為中央軍,加上親國民政府的游擊隊,他們的地盤稱為游擊區;還有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游擊隊,老百姓通稱之為八路軍,開闢了解放區。今日話當年事,這些名稱先要交代一番。
那時,日本的打算是把全中國變成日本的屬國,先用暴力侵略,後用懷柔安撫。但是,民族主義是無法融化的冰。中國人對暴力造成的傷害不忘記,對懷柔施予的恩惠不感激,想加減換算,沒那麼便宜,大家指天為誓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尤其是年輕人,憤懣之情溢於言表,罵「日本鬼子」,唱「中國的青年遍地怒號」。
中國人管日本人叫「鬼子」,一直叫到抗戰勝利,叫到對日和約簽訂,叫到一九七幾年,我在台北進電視公司當編審組長,政府官員以電話指示,電視劇對白的「日本鬼子」一律換成「日軍」或「日本軍閥」,大家才心不甘情不願的改了口。
對日和約簽訂後,日本政府在台北設立大使館,抗戰時期的憤怒青年雖然漸漸老大,胸中怒氣未消,每逢行經館外,總要對著太陽旗罵句髒話。日本在台北舉辦第一次商展,開幕之日,群眾一擁齊上,把日本館的太陽旗扯下來。
且說華北的「淪陷區」裡,日本控制學校,修改文史課程,培養以日本為宗主的思想,辦理各種親日的活動。青年人和他們的家長拒絕這樣的教育,大批失學的青年另尋出路,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成立了一所又一所戰時學校,收容他們。在日本的高壓之下,中年老年懂得世故分寸,可以苟全,年輕人血氣方剛,看鬼子不順眼,心裡窩一把火,留在家裡很危險。「出門一時難」,但是在家已非千日好,家長們千方百計把孩子送出去。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長篇小說的名字,成了當時流行的一句話。都說那個時代是洪爐,說這話的人自命是鐵匠,他要把人百煉成鋼。現成的燃料,那就是每人胸中的怒火。半個中國給日本佔了,國仇家恨。鐵匠以高明的技術使我們自我熔化,再乒乒乓乓打造。
小時候,我身體孱弱,家鄉話有個很好的形容,叫「病病歪歪」。老師家長從來不督促我用功,而是叮囑不要太用功。有一次,母親帶我去外婆家,一連幾天沒上學,等我回學校上課,跟那些不知情的老師同學見了面,有人問我:「好了吧?」他們以為我又病了。我家雖住在鄉下,但世代重視子女教育,做流亡學生縱然千辛萬苦,父母終於下了決心,我已十七歲,實在不能再拖延了。
這一年,魯籍名將第廿八集團軍總司令李仙洲,率九十二軍駐紮安徽阜陽,就地成立「私立成城中學」(不久改稱國立第二十二中學),收容山東逃出的流亡青年。阜陽離我家五百華里,那時交通不便,人們又安土重遷,我的家鄉蘭陵鎮一帶沒人去過阜陽,沒人聽說過這個地名。只因為李仙洲是山東長清人,山東老百姓相信他;只因為我的二表姐已經早走一步,入學讀書;只因為那時基督教掩護抗日青年,而我家是基督徒。所以我在這年夏天也到了阜陽,從此天涯海角,再無歸路,山東,臨沂,蘭陵,永遠只能在地圖上尋找。
七七事變發生後,有一個青年對他的母親說:「我已經十八歲了,不應該留在家裡,我要去參加抗戰。」
母親非常感動,問他打算跟誰一起。
他說:「我去參加八路軍,您看好不好?」
母親說:「很好!很好!」動手為兒子準備行李。
三年以後,這個青年的弟弟對母親說:「我也十八歲了,我要去參加抗戰。」
母親非常感動,問他打算跟誰一起。
他說:「我去參加中央軍,您看好不好?」
母親說:「很好!很好!」動手為兒子準備行李。
可憐的老百姓,可愛的青年,他們怎能預料,他們以後用很多很多時間互相廝殺。
那時,有人到大後方(後來叫做國統區),有人去解放區(當時也叫共區),大半由因緣決定,人人以為殊途同歸,誰能料到這一步跨出去,後來竟是刀山血海,你死我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二十二中的老同學屢次受到嚴厲的責問:你當年為甚麼不投奔解放區?被問的人啞口無言,因為他實在沒有答案。
一九八○年,中國對外開放,內戰期間逃出來的人回鄉探親,回首三十多年,家鄉的親人少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歷劫餘生悲憤怨恨,責問歸人:你當年為甚麼投奔國統區?這一問,只有一把鼻涕一把淚,也沒有答案。
李仙洲氏辦這所學校,網羅了山東的許多精英,他用人以行政幹部和黨工為主,沒有倚重教育家。以二分校的骨幹而論,戰後有人做濟南市長,做青島市民政局長,做省幹訓團教育長,做國大代表,做行政督察專員,窮則辦學,達則做官,教育理念和專業熱忱有局限,似乎談不到春風化雨。
那時國立一中與六中與我們聲氣相通,校長都是教育家。教育家的作風是自由開放,而那時,一中六中都在偏僻的地方,觸角不及於省會,遑論歐風美雨。那時所謂自由開放,只能表現在閱讀左傾書刊、包容中共地下組織、資助學生投奔延安等幾件事情上。這和二十二中可說是大異其趣了。
那時日本侵略中國,中共以聯合抗戰為號召,熱血青年同仇敵愾但各有因緣,不管北上延安或西去重慶,不管進二十二中還是進一中六中,應該說大家都對。不幸後來有了內戰,內戰後又有徹底清洗,在中共那把銖兩分明的大秤上,二十二中校友的罪孽沉重。留在大陸上受盡政治運動煎熬的那些同學,頗有人恨自己「走錯一步」。然而中國大陸解放以後,人人知道毛澤東做了些甚麼,那一中和六中的進步青年,後來也多是傷心人。
抗戰勝利後,李仙洲將軍再度入魯,兵敗被俘。在中共的統治技術下,只有李陵,沒有蘇武,從台灣的角度看,他是降將,我在台灣是降將的學生,常常被人多看幾眼。總之,不論在大陸,在台灣,李仙洲的學生都有歷史問題。司馬桑敦的長篇小說《野馬傳》,主角是一個綽號「野馬」的女人,國民政府要捉她,因為她是共產黨,可是共產黨也要捉她,因為她對黨不能絕對服從。一位韓國小說家寫《嗚呼朝鮮》,南韓北韓交戰,他從北韓逃到南韓,南韓認為他是北韓間諜,連忙逃回北韓,又被認為是南韓間諜。這都是造化弄人,只有哭之笑之。
平心而論,我當初入二十二中讀書,並沒有錯;像我這樣的人,中共要計較階級成分,他也沒錯;台灣操危慮深,處處防患於未然,更沒有錯。推而廣之,中國人的這一場大悲劇,竟以「誰都沒錯」釀成,真是詭異極了!
最危險的事情最簡單
「最危險的事情最簡單」,據說,這句話是列寧留下來的。列寧哪會知道他的嘉言給我們壯了膽,那年代兵凶戰危,人人冒險過日子,於是,在我的家鄉,這句話大為流行。
中國對日抗戰中期,敵我對峙,日軍在兩軍交界的邊沿,設置長長的封鎖線,嚴格檢查往來行人。在那關卡隘口,多少中國人被捕,被毆打,被狼狗咬!多少婦女被脫衣搜查!青年穿過封鎖線到大後方加入抗戰的行列,至親好友捏一把汗。可是我們斷然上路,自己告訴自己:不要怕,最危險的事情最簡單。如果我們禱告,也是祈求列寧這句話成真。
事情似乎很簡單,只要走出蘭陵鎮的西門,沿公路西行五十華里,到嶧縣城南關基督教會,找楊成新牧師。楊牧師安排同行的夥伴,向警察局申辦探親證明,代買火車票,把我們送上火車,那時,嶧縣有鐵路和津浦線連接。楊牧師辦來駕輕就熟,可是擔當多少風險!
楊牧師家中常有年輕人或他們的父母來訪,商量怎樣到後方去念書。
有一個嶧縣中學的學生對我說,他早就想到後方去,下不了最後的決心,直到日本兵一個耳光打得他鼻孔冒血。有一個蒼白少年,穿得整整齊齊,頭上還戴著靛青緞子做的「帽殼兒」(瓜皮小帽的一種),天天來央求楊牧師。他父親開綢布店,要他站櫃檯學生意,又要給他娶媳婦。他說,日本兵太可恨了,待在家裡,早晚給氣死。楊牧師說,到大後方抗戰是好事,不過你年紀還小,我得先問問你父親。他一聽到「父親」,轉身就跑,可是並沒有回家。後來有人在河南流亡學生接待站裡看見他,很瘦,眼睛很大,一身肉都曬黑了。
這天是星期天,禮拜之後,留下了兩個女學生,其中一個,漆黑的頭髮像盔一樣蓋在頭上,前額梳著小簾似的瀏海,一張臉皓白,那時女學生不化妝,最難得眼眉唇線乾乾淨淨清清楚楚。身上是小鳳仙式的夾襖長褲,沒有腰身,腳上機器織的線襪,平底圓頭的黑皮鞋。
她最受人注意。在她出現之前,她的故事先流傳過來。她家鄉的警察局長想娶她,託人提親。她反對,也就罷了,她多說了一句話,「我要到大後方去找對象,不在家鄉結婚。」到大後方?不是有封鎖線嗎,封鎖線上不是有日本軍用的狼犬嗎?她說:「寧願讓狼狗咬,也不嫁給漢奸。」咳,她就是多了這句話。那年代常說沉默是小代數,語言是大代數,語言引起的問題比較麻煩,難解。有人把這句話傳過去,當警察局長還怕沒人通風報信?那人哈哈一笑,也放出一句話來:「好吧,有一天我讓她嘗嘗狼狗的滋味,也讓狼狗嘗嘗她的滋味。」她的父母得到消息,央楊牧師趕快把女兒送走。
辦探親證明有個插曲。嶧縣警察局有個巡官是基督徒,他帶我進警察局。進去一看,滿屋子制服筆挺,佩件全新,簡直明盔亮甲,很有些朝氣,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家鄉的警察,沒這個氣派。那巡官的年紀三十出頭,鬍子刮得乾乾淨淨,頭髮剪得整整齊齊,看他站在那裡兩足落地生根,胳臂腿肌毫不懈怠,就知道受過嚴格訓練。漢奸怎麼會是這個樣子,根本不像嘛!
探親證明的大標題是「良民通行證」,鉛印,重磅紙,紙面發亮,拿在手裡嘩嘩響,精神一振。那巡官跟我談汪精衛,汪在一九三九年投奔日本,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汪是中華民國開國元勳,是追隨中山先生的革命先進,他怎麼會當漢奸?有人猜測,汪在抗戰局勢最惡劣的時候有此一舉,是國家設定的計謀,汪蔣兩人之間有默契,他這個漢奸是假的。這猜測在淪陷區流行,使下水當漢奸的人也可以有一番說詞。那巡官說:「我認為汪先生不是漢奸,我才跟著汪先生走。你到重慶去打聽打聽,來封信告訴我,他到底是真漢奸還是假漢奸。」
我沒能替他辦到,他太高估了我。也許,他並不真正需要答案,只是向我,向一個到大後方參加抗戰的人表明心跡,儘管我還是個孩子。看來汪精衛還是發生了作用,使做漢奸的人有個道德立場,對人對己,有個交代。
到一九四五年,我才聽到對汪精衛的評論,我沒有辦法轉告給他,只能事後寫在這本書裡。
那時,我對行程只有模糊的概念,楊牧師則有精密的計畫。依照計畫,我們在嶧縣上火車,江蘇宿縣下火車。宿縣教會為我們安排住宿的地方,代僱手推的太平車,車伕一半運行李,一半作嚮導。阜陽的位置在宿縣西南,尹寶璽同學在〈難忘的歲月〉一文中,對那一段路有準確的記述。由宿縣到蒙城,一百三十華里,中間有個叫蘆溝集的地方,是日軍偽軍最後一道盤查哨,也就是封鎖線。過了封鎖線,經過所謂無人地帶,也就是雙方都不設防的緩衝區,到蒙城之北三十里板橋集,是國軍的最前線。蒙城到阜陽,還有一百八十華里。
帶我同行的是兩個女學生,她們到重慶去讀大學。依照計畫,我和她們過渦河以後分手,她們向西,我向南。
女學生是一個變數,我惴惴不安。當年,女學生這個名詞的含意,今人很難體會。
那年代,在我們家鄉,「女學生」一詞的含意比現在複雜。讀小學讀初中的女孩只是「女生」,不是女學生。帶職進修或退休後再讀大學的白髮女學士從來沒有,至少是沒人見過。所謂「女學生」,通常是泛指由高中到大學,十七、八歲到二十出頭。那時女子能受高等教育,必定是家裡有錢,家長的思想也開明,有這種背景的女孩子多半漂亮。那時讀大學同時是一種享受,有音樂、有體育、有社交,這些女孩子多半明朗可愛。那時候,「女學生」一詞中有個甚麼樣的形象,可以想見。
所以,那年代,女學生在眼前出現是一件大事,使女人嫉妒,男人窺伺,使男人女人都放下手裡的工作想一想自己的命運。那年代,某一支游擊隊攻打日軍防守的城池,指揮官發明了一句口號:「打進××城,一人一個女學生」,每個人都知道絕對不會這麼辦,可是仍然提高了士氣。眼前的這兩位女學生敢闖封鎖線,敢闖大後方,不怕道路坎坷、人心險惡,了不起,可是我找人同路原是圖個安全,與女學生同行,豈不等於伴著兩枚炸彈?
既而一想,此行本來就是冒險嘛!怕甚麼?最危險的事情最簡單!
拂曉時分,楊牧師送我們上火車,增添了一個男生,名叫楊大維,年紀比我小一些。鄭重約定,四人分散穿插在滿廂乘客裡,誰也不看誰,誰也不跟誰說話,萬一有誰被鬼子識破,誰也不管他死活。聽最後一句我打了個寒噤,馬上又處之泰然。
火車慢慢開行,似乎步履艱難。用家鄉話來說,我做的事情叫「連根拔」,即使動力萬鈞的火車頭,也拔得如此吃力。火車經過徐州,在車站上停留了很久,我正襟危坐,沒敢向這個四戰之區望一眼。咳,徐州是我的傷心地,抗戰勝利次年,也就是四年以後,我再坐火車經過徐州,火車也是在車站上停留了很久。那時,我的父親帶著我的弟弟和妹妹逃難,暫時在徐州落腳,我仍然只能端坐在滿車乘員之中,不敢下車一步。我有幾個傷心地:徐州、瀋陽、上海……
好不容易在宿縣下車。我看見日本兵站在月台上,有槍有彈,他們對面四隻狼犬一字排開,傲然高坐,咻咻吐舌。我看見日兵踢打小販,用刺刀劃破小販背負的布袋。我看見一個鄉下人已經通過檢查,日本兵喝令他回來,他一面走回來,一面全身發抖,恰似我有一年患了瘧疾。
檢查行李由中國人動手,日兵監看。檢查員一面翻箱倒櫃,一面偷看日兵的臉色,如果日兵心不在焉,他就馬虎一點。那「鬼子」,忽然命令中國助手打開箱子,提起箱蓋,把東西抖落在地上,以便他一覽無餘。然後,他嫌行李的所有人收拾得太慢,用槍托搗那人的腰部,那人急忙合上箱子,落荒而逃,捨棄散落在地上的衣服。
那幾個日兵絕不離開那一排四隻狼犬,跟狼犬在一起,他覺得安全。日軍信任這種畜生,任憑牠揪出抗日份子,據說狼狗能察言觀色,有誰作賊心虛,牠就撲上來,別人不肯帶我同行,就是怕我沒見過場面,在這節骨眼兒上驚慌失措,連累了他。我從狼狗鼻子前面走過,不敢看同行的女學生,頭皮發麻,她們使問題複雜,也更危險。焉知她們不同樣估量我!當地受日軍指揮的中國部隊(當時稱為偽軍)有一位軍官,他受教會付託,來車站暗中協助我們,可是,在日本人面前,他沒有半句發言權。
我要慎重的記下來,最後越過封鎖線的時候,全靠女學生的機智和勇氣,化險為夷。詳細經過我寫進小說體的《山裡山外》第一篇,大致情形是,檢查哨所的偽軍早就識破我們的行藏,等到行人過盡,夕陽西下,由一個上校來親自處理,我猜檢查哨的勤務由他指揮。我們編好的謊話,他搖頭不聽,我們提出的探親證明,他擺手不看,一定要我們實話實說,才肯放行。可是,說了實話真能過關嗎?萬一結果相反呢?當時的情況危險極了,可是也簡單極了,拖到不能再拖的時候,那位漂亮的女學生在上校耳旁悄悄說了一句:「我們是到阜陽升學的學生。」
後來,女學生說,反正那句話別人聽不見,只有「他」聽見,如果「他」翻臉,我就賴。真想不到,上校很爽快:你早說這句話,不早就過河了嗎!他真的聽到實話就放行,他這樣做,為的是證明他也支持抗戰,身在曹營心在漢。
現在我追憶前塵,感念那位同行的大姐,不知道她們進了哪家大學,是否順利完成學業,後來天下大亂,她們是否仍能逢凶化吉。現在我知道,由山東臨沂到安徽阜陽有鐵路可通,行人省去多少辛苦。我知道嶧縣已廢縣改市,鐵路已拆除,南關教會的建築,只是被革命群眾打壞了幾塊玻璃。至於楊牧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嚴禁宗教活動,嶧縣教會與美國的淵源深,楊牧師的身分敏感,他又堅持奔走各鄉,廣傳福音,在當時是嚴重的罪行,因此受到許多懲罰,下落不明。我再三打聽,也沒人能提供他最後的行蹤,他是牧師,上帝會接待他的靈魂,保佑他的兒女。
我也常常想起那幾位漢奸,他們分裂的人格,可有小說家費心描寫?後來知道,南京汪精衛政權的要員,大都和重慶的國民政府通氣,重慶派到上海南京的情報人員,竟然能把無線電台設在高官的家裡。併吞異族太難了,被征服者表面的馴順,背後用加倍的反叛來平衡,他們是砂子,使你盲腸永遠發炎。從征服者的角度看,異族都忘恩負義,反覆善變,殊不知這正是他們的正義。咳,天下本無事,侵略者自擾之!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