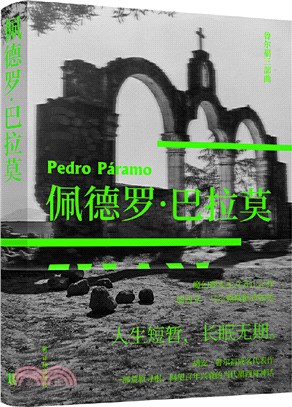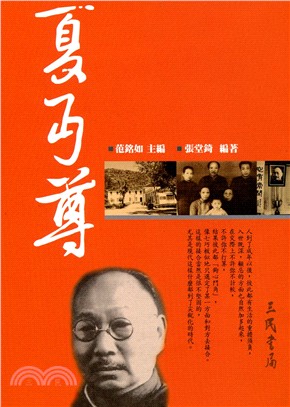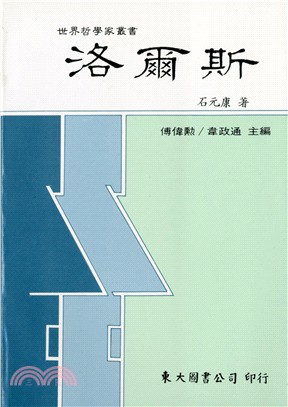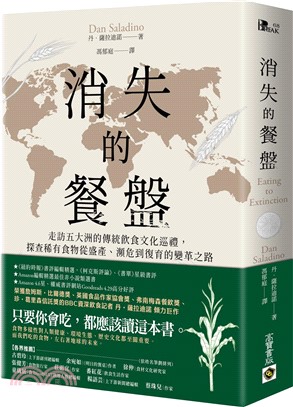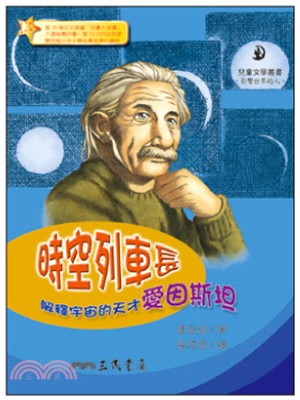佩德羅‧巴拉莫(簡體書)
- 系列名:魯爾福三部曲
- ISBN13:9787544784269
- 替代書名:Pedro Páramo
-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 作者:(墨西哥)胡安‧魯爾福
- 譯者:屠孟超
- 裝訂/頁數:精裝/191頁
- 規格:21cm*14.5cm (高/寬)
- 版次:一版
- 出版日:2022/02/01
商品簡介
《佩德羅·巴拉莫》是胡安·魯爾福的代表作。這部作品不僅立意深刻,而且,在藝術形式上也富有新意,迄今仍被認為是“拉丁美洲文學的巔峰小說之一”,被譯成多國文字,在世界各國廣為流傳。作者因此被譽為“拉丁美洲新小說的先驅”,1970年獲墨西哥國家文學獎
為完成母親的遺願,我來到小城科馬拉,尋找從未謀面的父親佩德羅·巴拉莫。好心的趕驢人指引我投宿愛杜薇海斯太太家——她似乎一早就在等待我的到來。村莊荒蕪凋敝,卻時常能聽見擦地而行的腳步聲、像蜂群一樣壓得緊緊的嗡嗡聲,那裡的生命好像在低聲細語,隨風蕩漾……
通過和他們的交談,往日的科馬拉漸漸浮現:佩德羅·巴拉莫幼年家道中落,靠著巧取豪奪一躍成為統治者,無惡不作。然而,他唯一承認的兒子墜馬而亡,歷經半生娶到的愛妻瘋癲而死,他詛咒整個村莊,自己也在劫難逃……
作者簡介
墨西哥小說家,被譽為“拉丁美洲新小說的先驅”,一生只留下篇幅極其有限的作品,卻被眾多作家奉為文學偶像。墨西哥國家文學獎、比利亞烏魯蒂亞文學獎、西班牙阿斯圖裡亞斯王子文學獎得主,墨西哥語言學院院士。與奧克塔維奧·帕斯、卡洛斯·富恩特斯並稱墨西哥文學20世紀後半葉的“三駕馬車”。
1917年,魯爾福出生於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小鎮。處女作刊發於自創雜志《美洲》,此後陸續創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說,並於1953年以《燃燒的原野》為題結集出版。
1955年,《佩德羅·巴拉莫》問世。小說不僅立意深刻,在藝術形式上也富有新意,迄今仍被認為是“拉丁美洲文學的巔峰小說之一”,在世界各國廣為流傳。
1956年,魯爾福回到首都寫作商業電影腳本,此後不久《金雞》完成。《金雞》於1964年拍成電影,文本卻直至1980年首次面世。
1986年,魯爾福於墨西哥城逝世。
名人/編輯推薦
☆ 魔幻現實主義小說流派的開山鼻祖,被譽為“拉丁美洲新小說的先驅”,引領拉美“文學爆炸”的潮流
☆ 沒有魯爾福,或許就沒有《百年孤獨》
《百年孤獨》經典開篇的雛形,靈感來源於《佩德羅·巴拉莫》
從魯爾福的作品中,加西亞·馬爾克斯“找到了繼續寫書而需尋找的道路”
☆ 一生只留下篇幅極其有限的作品,卻被眾多作家奉為文學偶像——
加西亞·馬爾克斯、大江健三郎、勒克萊齊奧……他們都熱愛魯爾福描寫原野的筆觸;
余華、莫言、蘇童……他們都曾受到魯爾福的深刻影響
--------------------------------------
“魯爾福三部曲”之《佩德羅·巴拉莫》
◎ 魯爾福最為人熟知的成名代表作,魔幻現實主義開山之作
◎ 一部荒原尋根、回望百年興衰的當代墨西哥神話
通過一段尋找亡父的故事,展現拉美人鬼莫辨的土地。作品不僅立意深刻,在藝術形式上也富有新意,迄今仍被認為是“拉丁美洲文學的巔峰小說之一”,被譯成多國文字,在世界各國廣為流傳
◎ 知名翻譯家、學者屠孟超從西班牙語直譯,附精彩譯後記,收錄加西亞·馬爾克斯長文序言
◎ 封面*家採用魯爾福私人攝影,展現作家眼中廣袤而迷人的墨西哥大地,藏讀兩宜
序
對胡安·魯爾福的簡短追憶
加西亞·馬爾克斯
發現胡安·魯爾福,就像發現弗蘭茲·卡夫卡一樣,無疑是我記憶中的重要一章。我是在歐內斯特·海明威飲彈自殺的同一天到達墨西哥的——1961年7月2日,我不但沒有讀過胡安·魯爾福的書,甚至沒聽說過他。這很奇怪。首先,在那個時候我對文壇動向十分了解,特別是對美洲小說。其次,我在墨西哥最先接觸到的人, 是和馬努埃爾·巴爾巴查諾·彭斯一起在他位於科爾多瓦街上的德庫拉城堡工作的作家, 以及由費爾南多·貝尼特斯主持的《新聞》文學增刊的編輯。他們當然都很熟悉胡安·魯爾福。然而,至少六個月過去了,卻沒有任何人跟我說起過他。這也許是因為胡安·魯爾福與那些經典名家不同,他的作品流傳很廣,本人卻很少被人談論。
我當時與梅塞德斯以及還不到兩歲的羅德里戈住在安祖雷斯殖民區雷南街一套沒有電梯的公寓裡。我們大臥室的地上有一個雙人床墊,在另一個房間裡有個搖籃,客廳的桌子既是飯桌也是書桌,僅有的兩把椅子用途更廣。我們已經決定要留在這座城市,這城市雖大,卻還保有人情味,空氣也清新純淨,街道上還有繽紛奪目的花兒。但是,移民當局似乎沒有分享我們的喜悅。有一半時間,我們都是在政府辦事處的院子裡排隊,有時候還得冒著雨,而隊伍卻總不往前走。閒暇時,我便寫些關於哥倫比亞文學的筆記,在當時由馬克斯·奧伯主持的大學電台播出。那些筆記太過直率,引得哥倫比亞大使打電話給電台提出了正式抗議。他認為,我的言論不是關於哥倫比亞文學的筆記,而是抨擊哥倫比亞文學的筆記。馬克斯·奧伯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我以為,我在六個月裡找到的唯一的糊口法子就這麼完了。但是,事情正相反。
“我一直沒時間聽那個節目,”馬克斯·奧伯對我說,“但如果它是像你們的大使所說的那樣,那應該是很好的。”
我當時三十二歲,在哥倫比亞當過很短時間的記者,剛剛在巴黎度過了很有用但也很艱苦的三年,又在紐約待了八個月,我想在墨西哥寫電影劇本。那一時期墨西哥作家圈子與哥倫比亞的很像,我在這個圈子裡十分自在。六年前,我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說《枯枝敗葉》,還有三本尚未出版的書:大概在那時候於哥倫比亞面世的《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不久以後由文森特·羅霍請求時代出版社出版的《惡時辰》,以及故事集《格蘭德大媽的葬禮》。最後這一本當時只有不完整的草稿,因為在我來墨西哥之前,阿爾瓦羅·穆蒂斯就已經將原稿借給我們尊敬的埃萊娜·波尼亞托夫斯卡,而她把稿子弄丟了。之後,我重組
了所有的故事,由阿爾瓦羅·穆蒂斯請塞爾吉奧·加林多在維拉克魯茲大學出版社出版。
因此,我是一個已寫了五本不甚出名的書的作家。但是,我的問題不在於此,因為,無論在當時還是之前,我寫作從不為成名,而是為了讓我的朋友更加愛我,這一點我認為我已經做到了。我作為作家最大的問題是,在寫過那些書以後,我覺得自己進了一條死胡同,我到處尋找一個可以從中逃脫的縫隙。我很熟悉那些本可能給我指明道路的或好或壞的作家,但我卻覺得自己是在繞著同一點打轉。我不認為我已才盡。相反,我覺得我還有很多書未寫,但是我找不到一種既有說服力又有詩意的寫作方式。就在這時,阿爾瓦羅 · 穆蒂斯帶著一包書大步登上七樓到我家,從一堆書中抽出最小最薄的一本,大笑著對我說:
“讀讀這玩意,媽的,學學吧!”
這就是《佩德羅·巴拉莫》。
那天晚上,我將書讀了兩遍才睡下。自從大約十年前的那個奇妙夜晚,我在波哥大一間陰森的學生公寓裡讀了卡夫卡的《變形記》後,我再沒有這麼激動過。第二天,我讀了《燃燒的原野》,它同樣令我震撼。很久以後,在一家診所的候診室,我在一份醫學雜誌上看到了另一篇結構紛亂的傑作:《瑪蒂爾德·阿爾坎赫爾的遺產》。那一年餘下的時間,我再也沒法讀其他作家的作品,因為我覺得他們都不夠分量。
當有人告訴卡洛斯·維羅,說我可以整段地背誦《佩德羅·巴拉莫》時,我還沒完全從眩暈中恢復過來。其實,不只如此——我能夠背誦全書,且能倒背,不出大錯——並且我還能說出每個故事在我讀的那本書的哪一頁上,沒有一個人物的任何特點我不熟悉。
卡洛斯·維羅委託我將胡安·魯爾福的另一個故事改編成電影,這是我那時候唯一沒讀過的故事:《金雞》。文章是密密麻麻的十六頁紙,薄紙,已快破成碎片了,由三台不同的打字機打成。即使沒人告訴我這是誰寫的,我也能立刻感覺出來。這個故事的語言沒有胡安·魯爾福其他的作品那麼細膩,也沒有多少他獨有的技巧手法,但是,他的個人魅力卻流露於字裡行間。後來,卡洛斯·維羅和卡洛斯·富恩特斯邀請我為根據《佩德羅·巴拉莫》改編的第一部電影進行一次檢查與修改。
這兩件工作的最終結果遠遠談不上好,我提到它們是因為它們促使我更深刻地去了解一部我確信已比作者本人更熟悉的作品。說起作者本人,我是直到幾年以後才認識他的。卡洛斯·維羅做了件令人驚異的事情:他將《佩德羅·巴拉莫》根據時間片段剪開來,再嚴格按照先後順序重組成戲劇。作為純粹的工作方式,我認為這很合理,可結果卻成了一本不同的書:平板而凌亂。但是,這對讓我更好地理解胡安·魯爾福的匠心獨具很有幫助,也更體現了他非凡的智慧。
在《佩德羅·巴拉莫》的改編中有兩個根本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名字。無論看起來有多麼主觀,任何名字都與用這名字的人有某種相似,這一點在文學中比在現實生活中要明顯得多。胡安·魯爾福說過,或者有人讓他這麼說過,他是一邊讀著哈利斯科公墓裡的碑文一邊構思他小說中人物的名字的。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沒有比他書中的人名更恰當的專有名詞了。當時我認為——現在仍然這麼認為——要找到一個與所飾演的人物名字毫無疑問地相契合的演員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個問題——它與前一個問題不可分割——是年齡。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胡安·魯爾福都很小心地不去留意人物的年齡。納西索·科斯塔·羅斯不久前做過一次非凡的嘗試,想確定《佩德羅·巴拉莫》中人物的年齡。純粹出於詩意的直覺,我一直認為,當佩德羅·巴拉莫終於將蘇薩娜·聖胡安帶回他半月莊的廣袤領土時,她已是一個六十二歲的女人了。佩德羅·巴拉莫應該比她大五歲左右。其實,如果劇情沿著一段得不到慰藉的黃昏戀的懸崖急轉直下,我會覺得這戲劇更加偉大,更加可怕但美麗。科斯塔·羅斯為兩人所設定的年齡與我所設想的不一樣,但是相差不是很遠。可是,這樣的詩意和偉大在電影裡是無法想像的。在黑暗的電影院裡,老年人的戀情感動不了任何人。
這些珍貴的研究有個壞處,那就是,詩歌中的情理並不總是基於理性。某些事情發生的月份對分析胡安·魯爾福的作品十分重要,但我懷疑他本人是否對這一點有所察覺。在詩歌中——《佩德羅·巴拉莫》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詩歌——詩人運用月份來達意,卻不顧時間上的精確性。不僅如此:許多時候,連月份、日期甚至年份都被改變了,僅僅是為了避免一個不好聽的韻腳或者同音重複,而沒有想到那些變化可以促使評論家做出某種斷然的結論。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月份與日期上,花也是一樣。有些作家常用花朵,純粹只是因為它們的名字響亮,而沒有註意到它們是否與地點和季節相符合。因此,在好書中看到開在海灘上的天竺葵和雪裡的鬱金香,都已不稀奇。在《佩德羅·巴拉莫》中,要絕對地確定哪裡是生者與亡人之間的界限已屬不可能,其他方面的精確更是空談。實際上,沒有人能夠知道死亡的年歲有多長。
我說這些,是因為對於胡安·魯爾福作品的深入了解,使我終於找到了為繼續寫我的書而需要尋找的道路,因此,我寫他,就必然會顯得一切都像是在寫我自己。現在,我還想說,為了寫下這些簡短的懷念之詞,我又重讀了整本書,我再次單純地感受到了第一次讀時的震撼。他的作品不過三百頁,但是它幾乎和我們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樣浩瀚,我相信也會一樣經久不衰。
目次
佩德羅·巴拉莫
譯後記
書摘/試閱
我來科馬拉是因為有人對我說,我父親住在這兒,他好像名叫佩德羅·巴拉莫。這是家母告訴我的。我向她保證,一旦她仙逝,我立即來看望他。我緊緊地握著她老人家的雙手,表示我一定要實現自己的諾言。此時她已氣息奄奄,我打算滿足她的全部要求。 “你一定要去看看他呀,”她叮囑我說,“他時而叫這個名字,時而又那麼稱呼。我認為見到你他一定會高興的。”我當時只能一個勁兒地對她說,我一定照她說的去辦。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說著這同樣的一句話,一直說到她的雙手僵直,這才費勁地抽回我的兩隻手。
早先她也對我說過:
“你千萬別去求他辦什麼事。不過,我們的東西,也就是說他該給我們的,你該向他要。他該給我的東西就從來沒給過我……孩子,他早把我們給忘了。為此,你可得讓他付出代價。”
“我一定照辦,媽媽。”
然而,我一直沒有打算兌現我的諾言。近日,不知怎的,我的幻想多起來了,頭腦中老是愛想入非非,於是,在對一位名叫佩德羅·巴拉莫的先生,即我母親的丈夫的期待中,我逐漸構想出了一個世界。正因為這樣,我才上科馬拉來。
那裡正值酷暑,八月的風越刮越熱,吹來陣陣毒氣,夾帶著石鹼花的腐臭味。
道路崎嶇不平,一會兒是上坡,一會兒是下坡。 “道路隨人來人往或起或伏,去者登坡,來者下坡。”
“您說山坡下面的那個村莊叫什麼來著?”
“科馬拉,先生。”
“您能肯定這是科馬拉嗎?”
“能,先生。”
“這兒的環境看起來為什麼這樣淒涼?”
“是因為年頭久了,先生。”
往昔我是根據母親對往事的回憶來想像這裡的景況的。她在時異常思念故鄉,終日長吁短嘆。她總是忘不了科馬拉,老是想回來看看,但終於未能成行。現在我替她了卻心願,來到這裡。母親的眼睛曾注視著這兒的景物,我將這雙眼睛帶來了,因為她給了我這雙眼睛,讓我看到:“一過洛斯科里莫脫斯隘口,眼前便呈現一派美景,碧綠的平原點綴著熟玉米的金黃色。從那兒就可以看見科馬拉,它使大地泛出一片銀白,在夜晚又將其照亮。”她當時說話的聲音異常輕微,幾乎都聽不見,彷彿在自言自語……我的母親啊。
“如果方便問的話,請問您去科馬拉幹什麼?”我聽到有人在問我。
“去看我父親。”我回答說。
“啊!”他說。
於是,我們又沉默了。
我們朝山坡下走去。我耳中響起驢子小跑時在山谷中傳來的迴聲。八月的盛暑使人昏昏欲睡,我困倦得連眼皮都抬不起來了。 “您上那裡去,全村可要熱鬧熱鬧了,”我又聽到走在我身邊的那個人的聲音,“這麼多年沒有人到這個村子裡來,見到有人來,人們一定會高興的。”
接著,他又說:
“不管您是誰,大夥兒見到您一定會興高采烈的。”
在陽光的照射下,平原猶如一個霧氣騰騰的透明湖泊。透過霧氣,隱約可見灰色的地平線。遠處群山連綿,最遠處便是遙遠的天際了。
“如果方便問的話,請問令尊的模樣是怎樣的?”
“連我自己也不認識他,”我對他說,“我只知道他叫佩德羅·巴拉莫。”
“啊,原來是他!”
“是的,我聽說是這麼稱呼他的。”
我聽見那趕驢人又“啊”了一聲。
我是在洛斯恩谷恩德羅斯遇到他的,那是幾條道路交會的地方。我在那裡等了他一會兒,直到這人最後總算出現了。
“您上哪兒去?”我問他。
“我下坡去,先生。”
“有個叫科馬拉的地方,您知道嗎?”
“我就是到那裡去的。”
我就跟著他走了。起先我走在他的後面,總想跟上他的步伐。後來,他似乎覺察到我跟在他的後面,便有意放慢了腳步。接著,我倆離得是那麼近,以至於肩膀都快靠在一起了。
“我也是佩德羅·巴拉莫的兒子。”他對我說。
一群烏鴉“啞——啞——啞——”地驚叫著掠過晴空。
翻過幾座小山,地勢越來越低。在山上走時還有陣陣熱風,一到山下悶熱得連一絲風也沒有了。這裡的萬物彷彿都在期待著什麼。
“這裡真熱呀。”我說。
“對,不過,這點熱算不了什麼,”他回答我說,“請別煩躁。到了科馬拉您會覺得更熱的。那個地方好像擱在炭火上一樣熱,也彷彿就是地獄的門口。不瞞您說,即使這麼熱,那裡的人死後來到地獄,還得回家拿條毯子呢。”
“您認識佩德羅·巴拉莫嗎?”我問道。
我之所以敢向他提這個問題,是因為從他的雙眼中看到了一絲信任的目光。
“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我又追問了一句。
“是仇恨的化身!”他回答我說。
說完,他朝驢子揮了一鞭。這樣做其實毫無必要,因為它們趁著下坡,早已遠遠地走在我們前面了。
我此時感到放在我襯衣口袋中母親的那張相片在我心口陣陣發熱,她好像也在出汗。這是一張舊相片,四邊已遭蟲蛀,但這是我看到過的她僅有的一張相片。我是在廚房櫥子裡的一隻砂鍋中發現它的,砂鍋裡還有許多藥草,有香水薄荷葉子,還有卡斯蒂利亞花和芸香樹枝。之後我就將它珍藏在身邊。這是她唯一的一張相片。母親生前一貫反對拍照。她常說,照相是一種巫術。說起來照相倒真有點像巫術。就拿她這張相片說吧,上面盡是針眼般的小洞,在她心口處還有一個特別大的洞,這洞大得可以伸進一個中指。
我這次帶來的便是這張相片。我想,有了這張相片,對父親承認我會有好處。
“您瞧,”趕驢人停下腳步對我說,“您見到了那個形狀像豬尿脬的山丘了嗎?半月莊就在這小山的後面。現在我轉到這個方向來了。您看到前面那座小山的山峰了嗎?請您好好看一看。現在我又轉到另一個方向上來了。您看見遠處那隱隱約約的另一座山頂了嗎?半月莊就在這座山上,佔了整整的一座山。常言道,目之所及皆為此地。眼睛望得見的這整塊土地都是佩德羅 · 巴拉莫的。雖說我倆都是他的兒子,但是我們的母親都很窮,都是在一片破席子上生的我倆;可笑的是佩德羅·巴拉莫還親自帶我們去行了洗禮。您的情況大概也是這樣吧?”
“我記不清了。”
“媽的,見鬼了。”
“您說什麼?”
“我說我們快到了,先生。”
“對,我已經看到了。這兒發生什麼事了?”
“這是一隻‘趕路忙’,先生。這是人們給這種鳥起的名字。”
“不,我問的是這個村莊,為什麼這樣冷冷清清,空無一人,彷彿被人們遺棄了一般。看來這個村子裡連一個人也沒有。”
“不是看來,這村莊確實無人居住。”
“那麼,佩德羅·巴拉莫也不住在這裡嗎?”
“佩德羅·巴拉莫已死了好多年了。”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