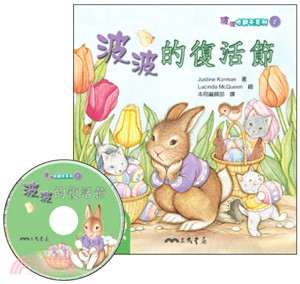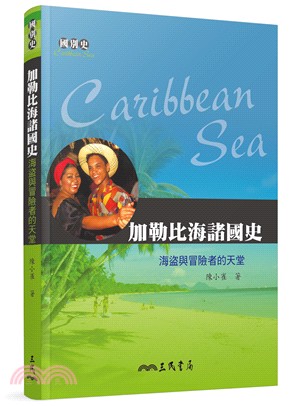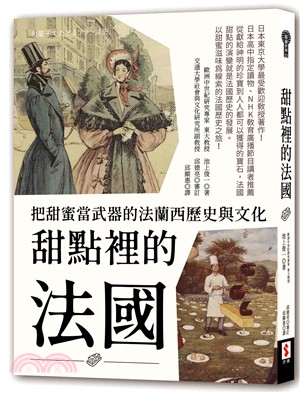再享89折,單本省下40元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卷一 地緣
清邁的聲音
還願到烏杭
桂遊二札
烏敏島的雷雨
高雄公園的鳥聲
願望之泉
大街以外的寧靜
在農莊裏觀自然之音
去來東平洲
大館張眼
卷二 本色
衣履
浴室
對時
本色
鴛鴦
罐頭
驚蟄
極速理髮
楓香和鐵芒萁
萵苣和蛇舌草
秋聲稀澀,樂句悠揚
兒女情,風雲氣
輕鐵駛過無夢的市鎮
卷三 藝境
藝境
觀棋
說柳
恐懼症
學國語
癖與趣
給愛麗絲
嗅的藝術
鷹的故事
自述平生
胡說黑白
不是牆,是路
偵探是吃什麼的?
卷四 史臆
煙耶雲耶,皆由心造
龔自珍的書法
像聲戲劇家
貴族的復仇
王者的內心
書摘/試閱
鴛鴦
說「鴛鴦」是香港道地的飲品,我無法提出反對的證據。但三十多年前,在離香港不遠的一個小城,我親耳聽到有人在餐室揚聲:「一杯鴛鴦!」那些餐室自然十分簡陋,沒有過膠的餐牌,也沒有午餐、常餐之設。是否有餐室老闆發明這飲料,更無從稽考。大概是有客人這樣「柯打」,才有「水吧」(調製飲品的服務員)為客人泡製。最有趣的版本可能是:「一天,某餐室的伙計因為跟女友拌嘴,心情不好,有意無意把咖啡注入半杯紅茶上枱。客人呷了一口,竟覺其味無窮,深入查詢,始知是『咖啡溝奶茶』,於是街知巷聞,為人所愛。」
這當然是虛構。總之「鴛鴦」是什麼,餐室與客人早有默契。一杯「鴛鴦」就是一杯「鴛鴦」,無須說明咖啡與紅茶的比例,也無須爭辯其味道或質感。反正是客人愛喝才落單,假如不信任這餐室,也不耐煩在裏面坐上一句鐘,讓一把舊式吊扇,習習地吹拂着一陣滲出杯沿的香氣,吹拂着手上報紙的頭版和副刊。
不管是否道地的出產,「鴛鴦」之名不脛而走、無翼而飛,餐牌雖沒有寫明,人人卻心照不宣。誰會認真討論它的好壞呢?這「鴛鴦」卻是如假包換的「大眾文化」。有人也許看不起它,說它是一種混雜而成的hybrid,既剝奪了咖啡的豪邁濃烈,也破壞了紅茶的優雅細致。文化人會搖頭,說它反映了香港人貪婪兼併的心理、不講純粹的取態。但關心身體的人說:咖啡太燥,紅茶偏濕,「鴛鴦」正好取其所長、去其所短,燥濕互濟,實有益身心。
我非本土文化的捍衛者,但覺得像「鴛鴦」、「西炒飯」、「中式牛柳」等飲食,都應有其適當的品位。只要你選對了店子,水吧服務員絕對不會介意為你調弄一杯「鴛鴦」。看他一手提起咖啡壺,一手提起茶壺,合乎比例地,向透明的玻璃杯注入兩道熱流,姿勢並不特別優雅,然而,在電光火石之間茶啡同體,陰陽互補,東西文化就這樣調合交融,不離不棄。
我樂意見到「鴛鴦」在餐牌上出現(英文叫它tea-coffee或yuanyang也無妨),超級巿場買到即沖即飲的包裝,飲食專家討論種種調製的竅門。但與其把它標準化,成為高級餐廳的時髦飲品──收費昂貴卻又品質淪落──倒不如仍讓它在民間流傳,仍讓我們坐在那至愛的餐室一角,一個水吧服務員為我們沖調泡製。既然「鴛鴦」是我們的文化,就應像文化那樣,自由地發展、演變、延續它的生命力。
罐頭
記憶裏最早食用的罐頭是再造奶,俗名「煉奶」。這「煉」字用得妙,千錘百煉才得這麼一小罐,要用溫水開。甜,不必加糖,小時候把淮鹽餅乾放入奶水裏,使其變軟,再吃,味道挺佳。
其次是午餐肉。食店裏早已有售。把罐裏的豬肉取出,切片,放油煎成深紅色。那濃郁的香味,任何肉類都煎不出來。放到白麵包中作三文治,取名「午餐肉」,卻多用作早餐。
要打開罐頭,最頭痛的事情,是使用開罐刀。旋轉式的開罐刀大概是七十年代才發明的,大大省力之餘,罐頭開出的邊沿也十分整齊。舊式開罐刀能開汽水瓶、能拔酒塞,雖輕便耐用,卻是一柄帶原始風味的工具。開罐時,要用上面那一把半月型小刀的尖端俯衝而下,在罐面刺開一個小裂縫,並在柄端重重拍擊一兩下,擴大那裂縫,小心地用這小刀撬開罐面。這整套動作,真要非凡的技巧。
開罐頭的訓練,從八九歲開始,就是暴動宵禁那年頭。解禁的時候,父親從外邊買罐頭回來。菜市已關閉多天,難得辦館還開,只是價格漲了。我們就是從小受訓,打開一隻隻厚薄不一、弧度不同的罐子,取用那些在好幾個月前已烹透煮爛、防腐兼消毒的食物。
通過開罐頭這關,餘下一切事情都簡單了。吃罐頭拉肚子,大概是因為太過油膩,而不是有毒。假如把罐內食物擱在空氣裏半天,就會變壞,這情況跟普通食物一樣。當然你必須看看罐底的製造日期,假如那年、月、日還屬未來,你便可安心享用。二十年前你看得懂那些數字真了不起。但有時招紙不翼而飛,我們也斗膽開罐。不吃,像垃圾一樣丟棄,太可惜了。
一百五十多年,英國探險家弗蘭克林爵士(Sir John Franklin)率領一百二十多人到加拿大西北極寒之地,帶了不少食物隨行,罐頭也不少。在白皚皚的雪地上,一群船員興致勃勃,遠望星垂平野的地極。飢餓時,就在孤伶伶的船上吃東西。他們逗留在北極兩年,忽然有一天,大部分船員無故暴斃,弗蘭克林也掉了命,那年是一八四七年。死因一直是謎。不久前,科學鑑證家才確定他們中了鉛毒。最可疑的毒素來源是罐頭,不是新鮮食物。
我同意寫《食物歷史》的Fernández-Armesto所說:罐頭已成為一種不可缺少的口味。一百多年前,食用罐頭並不講究。到了二十世紀,尤其戰後的歲月,罐裝食物不但建立品牌形象,更在消費者之間建立了真正的taste。作為戰後的一代,我們完全不曉得罐裝食物的軍事意義,反正它有特別的taste,那就逃不過我們的饞嘴了。
我們用「地捫」的切片菠蘿做點心,吃浸滿橄欖油的「葡國老人牌」沙甸魚。我們打開「鬱金香」和「長城」火腿午餐肉,鄉愁一樣取用美味的肉食。我們不認識那個繪畫「金寶罐頭湯」叫 Andy Warhol 的普普藝術大師,但我們喝了不少這牌子的清雞湯、羅宋湯、字母湯。曾經,我們愛吃罐裝菠蘿甚於新鮮菠蘿,愛喝字母湯甚於老火湯,做父母的要禁止也不行。他們不想孩子吃罐頭,本來一番好意;我們貪方便,養成不煮食的習慣,也很需檢討。
上帝創造世界,應許一切地上的生物可供人類食用。但短短幾年間,瘋牛症、禽流感、豬瘟以及受污染的海產,已把伊甸園那大自然食庫弄污弄糟。近日上超級巿場,買一點很少吃的罐頭,驚覺價格飛漲。這恐怕是買的人多了,少吃了所謂新鮮但可能有毒的食物。罐頭技術越出色,正是污染越嚴重的年代,使人有不可回頭的感歎。
三四十年間,罐頭由代用品變成避難所,真是一個諷刺。也許,到了這個地老天荒的廿一世紀,我們要為有二百年歷史的罐頭寫下新的一頁。 2005.10.3
驚蟄
──也是香港回憶
又是三月天,本是「雷驚天地龍蛇蟄,雨足郊原草木柔」的日子,走過灣仔鵝頸橋,卻另見一番熱鬧。上了年紀的女人,坐在橋底一角,設爐焚香,手執一隻鞋子,向一張繪了人像的黃紙用力抽打。
這是一年一度的「打小人」節日。有些女人為自己打,也有些是受托的,由僱主提供受打人的身份。「打小人」習俗,淵源無法考證,但應該是民間道教符籙派的產物。這群上了年紀的女性(我不敢稱之為「巫婆」),不但撾之以履,更且咒之以嘴,向其目標「小人」的頭部、眼睛、四肢,各打足一定次數,鞋聲節奏均勻,咒語鏗鏘有致。不懂咒語者還有口訣印備可即時參考,什麼「打你個小人肚,等你日日畀人告」、「打你個小人口,等你有錢都唔識收」等,無論是音色或意義,均具本土情懷。惡毒的話,要念足百遍,兼且在那些象徵無恥小人的黃紙上施行剪舌、挖心、劏肚等刑罰,才算完成整個儀式。
請人「打小人」的大概有兩類人。一類可稱為例行公事,出發點是為求全年好運,免受小人侵擾,而實際上自己諸事順遂,生活得很好。另一類可說是時運不濟,終年晦氣,或生意阻滯,情場失意。假如小人有名有姓,則「打小人」便由泛打變成獨打,心中有了該等小人的面目,用一個心理轉移法,把小人移到黃紙上,或以高跟鞋,或以爛拖鞋,或以寸厚木屐,實行毒打。打之不足,更以針刺其心,以剪斷其體,以火焚其屍。
中國以農立國,農民性格保守,難免自利然後利人。雖然如此,即使農作失收,頂多怨怪天時不順,而不會將禍患轉移到鄰里身上。反而是商賈官吏,因為貨品交通、文書往來,與人磨擦的機會較多,小人從中作梗的機會也大增。孔子也常批評小人,但卻未致加以毒咒甚或要屠宰他們,況且《論語》裏所說的小人,跟驚蟄時所打的有本質上之不同。可笑的是:被打的是小人,那麼出手打人的,同樣作為磨擦爭端的參予者,豈不也是小人心中的另一批小人?清人戴震說得好:「凡有所施於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施於我,能受之乎?」打小人的,要想想身旁另一個舉着爛鞋念念有詞的,是不是仇人派來打自己的。那紙人若是自己的身體,能受之乎?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