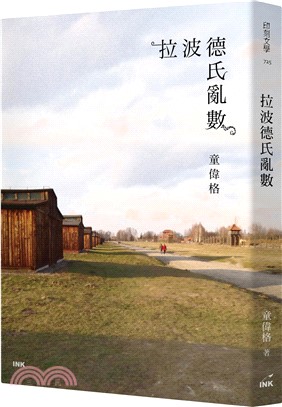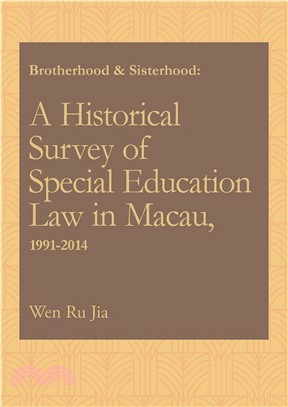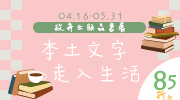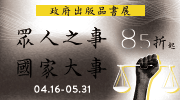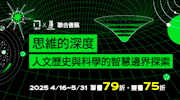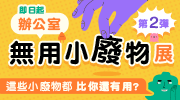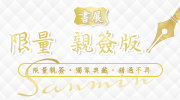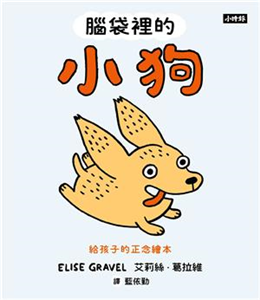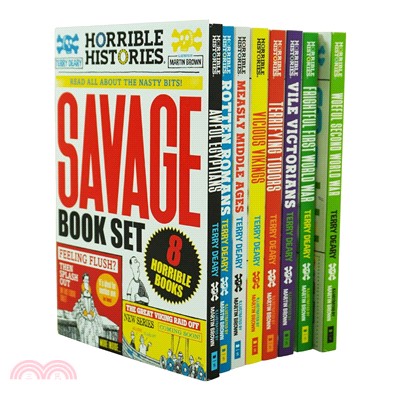拉波德氏亂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拉波德氏變色龍,一種時間劫後的遺族。
每年四月,旱季起始,彼時,一整個世代的牠們,都將在旱地裡死絕,無一可能倖免。──童偉格
龐大的苦難,被收摺再收摺,凝煉成時光劫後,末世的證詞
紀實的碎片,虛構的臨在
每一次的書寫,都在無數次絕望中重生
俱是受辱時空的修繕,人的話語的奪還
骨灰池畔,水的冷冽,火的餘燼,人的消亡
他將自己的全副心魂,擠迫壓縮進累劫人類世思索者意識流,將漫長幽困於殘酷歷史的不可解,以共感臨現的同在回返,重新兌換了一次記憶的誓約。
預言者、倖存者、受難者、失蹤者、行刑者、死亡助手、屠殺者後裔,以及各種不可理喻的見證者、書寫者,他們的故事被掘取點燃,重新誕生。
追尋卡夫卡理應拭滅的字證,預視了體制與屠殺的成真。
跋涉於杜斯妥也夫斯基逃死的餘生,思索認罪長路,罪與罰的惶惑。
將普利摩.李維躍下冥河前的剪影倒帶──彼日,一個新世界的少年說「這是沒有的事」。再往前,往苦難極地,以夜鳥之眼瞪視,形上思維死去的場所,人文無憑,詞語的被褫奪。
悄聲逡巡園中地堡,逐一照探落實施行細則的士兵、法醫助手,甚至元首的牧羊犬,直視其無異於同類的行狀。亦借柯慈的疏離,提示文學的多重義理,切勿將這一切,簡化為普世立解的隱喻。
.請不妨這樣,理解我將對你說出口的殘酷。
.悲願是:應當要有文學創作,來為將臨的大屠殺作證。縱使作證,目前是預先的作證。縱使,在未來讀者的回顧裡,它預證過的將來,已是讀者實歷了的過去。
.永遠有一個可能:不是因為無法同理,不是的;正是因為擅長想像他人痛苦,一個人,才能成為優秀的行刑手。
.所有人都能找到自我圓說的邏輯,讓自己免於良心折磨。
.所謂「地獄」,是一個所有語彙、所有表達都無差別的地方。所謂「地獄」,就是一個人們會一再由衷地,嘔出地獄的地方。
每年四月,旱季起始,彼時,一整個世代的牠們,都將在旱地裡死絕,無一可能倖免。──童偉格
龐大的苦難,被收摺再收摺,凝煉成時光劫後,末世的證詞
紀實的碎片,虛構的臨在
每一次的書寫,都在無數次絕望中重生
俱是受辱時空的修繕,人的話語的奪還
骨灰池畔,水的冷冽,火的餘燼,人的消亡
他將自己的全副心魂,擠迫壓縮進累劫人類世思索者意識流,將漫長幽困於殘酷歷史的不可解,以共感臨現的同在回返,重新兌換了一次記憶的誓約。
預言者、倖存者、受難者、失蹤者、行刑者、死亡助手、屠殺者後裔,以及各種不可理喻的見證者、書寫者,他們的故事被掘取點燃,重新誕生。
追尋卡夫卡理應拭滅的字證,預視了體制與屠殺的成真。
跋涉於杜斯妥也夫斯基逃死的餘生,思索認罪長路,罪與罰的惶惑。
將普利摩.李維躍下冥河前的剪影倒帶──彼日,一個新世界的少年說「這是沒有的事」。再往前,往苦難極地,以夜鳥之眼瞪視,形上思維死去的場所,人文無憑,詞語的被褫奪。
悄聲逡巡園中地堡,逐一照探落實施行細則的士兵、法醫助手,甚至元首的牧羊犬,直視其無異於同類的行狀。亦借柯慈的疏離,提示文學的多重義理,切勿將這一切,簡化為普世立解的隱喻。
.請不妨這樣,理解我將對你說出口的殘酷。
.悲願是:應當要有文學創作,來為將臨的大屠殺作證。縱使作證,目前是預先的作證。縱使,在未來讀者的回顧裡,它預證過的將來,已是讀者實歷了的過去。
.永遠有一個可能:不是因為無法同理,不是的;正是因為擅長想像他人痛苦,一個人,才能成為優秀的行刑手。
.所有人都能找到自我圓說的邏輯,讓自己免於良心折磨。
.所謂「地獄」,是一個所有語彙、所有表達都無差別的地方。所謂「地獄」,就是一個人們會一再由衷地,嘔出地獄的地方。
作者簡介
童偉格
一九七七年生,萬里人,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著有《萬物生長》、《童話故事》等書,合著有《字母會A~Z》。合編有《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一九七七年生,萬里人,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著有《萬物生長》、《童話故事》等書,合著有《字母會A~Z》。合編有《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目次
序篇:史前的朋友
大霧清晨抵達美國
沒有的事
夜鳥
石頭世界
夏令營
林中空屋
愛犬I
愛犬II
拾骨
證人
維也納海岸
失蹤者
巴達維亞號經過
雪與鱷魚
大霧清晨抵達美國
沒有的事
夜鳥
石頭世界
夏令營
林中空屋
愛犬I
愛犬II
拾骨
證人
維也納海岸
失蹤者
巴達維亞號經過
雪與鱷魚
書摘/試閱
序篇:史前的朋友
頭一天他們穿行過一座高山,暗藍色的懸岩以其尖尖的楔子向列車逼近,人們從窗戶向外探身,徒勞地尋找著峰頂,幽暗、狹窄、被撕裂的山谷張開著,人們用手指頭指引著那些山谷漸漸隱去的方向,寬闊的山澗在連綿起伏的丘陵上像巨浪一樣匆匆湧來,夾帶著萬千洶湧的泡沫浪花,它們從火車駛過的橋下奔騰而過,它們離人如此之近,以致它們那涼絲絲的氣息讓你的臉冷得打顫。
──法蘭茲.卡夫卡,《美國》(《失蹤者》)
我無法讀卡夫卡的長篇小說和日記。不是因他對我太陌生,而是因我離他太近了。青春的迷惘,隨後幾年內外交困的處境,不斷幻滅的幸福憧憬,猝不及防被剝奪的所有權利,日益加劇的孤獨與隔絕,那段憂煩與恐懼肆虐的蒼白時日,使我對耐心承受苦難的卡夫卡博士此人醉心不已。對我而言,他始終不是一個文學事件。他對我的意義遠不僅於此。多年以來,卡夫卡博士一直是我的人性的庇護所。他是位以其善良、寬容和坦誠,鼓勵且保護我在冷風淒雨中開展自我的人。他是我的認知和感覺的基礎,使我如今,猶能在這魍魎亂世裡苟存。
──古斯塔夫.亞努赫,《與卡夫卡對話》
在捷克第一共和國境內,只有本國法人,才能申請電影院營業執照。體操協會開的電影院,叫「獵鷹」;退伍軍人協會開的叫「西伯利亞」;紅十字會開的,就叫作「健康」。卡夫卡博士最喜歡的電影院名,是「盲人」,由視障者關懷協會開設。他說,所有電影院都應該叫這個名字。古斯塔夫在「盲人」打工,擔任樂手。領到第一筆薪水,他將博士的〈司爐〉、〈判決〉與〈變形記〉等三篇小說,裝訂成精裝書,送給博士。那是惟一一次,他令博士深感尷尬。博士,也是他認識的惟一一位,覺得作品應當銷毀的寫作者。因為,「沒有人可以因自己絕望,而使病人的情況雪上加霜」。
然而,開始是死亡,後來是病房,最後,才是生命的成真。卡夫卡:某種倒裝的時程。病房遠在維也納。彼時,卡夫卡年當不惑,肺結核蔓延到喉頭,令他無法吐聲、吞嚥也困難,鎮日在高燒中,靜緩地自耗。必要與人交談時,他寫紙條。紙條說:今日換服這藥片很好,入口如玻璃渣,化掉像炭火,暫時蓋過呼吸時的劇痛了。住院滿好,院裡人人皆待我好。這樣也好:總算校對完《飢餓藝術家》書稿,自知文學夢遠不可企及,從此斷念。往後不要書本了,請帶易讀報刊來即好,有園藝知識的最好。分崩離析,很疲累,睡前覺得每個肢體,都是「一個人」。
古斯塔夫從不曾去探過病。主要因為湊不出旅費。也因恐怕探病之舉,只會更傷勞病人(他記起博士的尷尬之言了)。他小卡夫卡足足二十歲,是彼此難得的忘年交。卻又因此,他總自覺有義務,節用朋友的心力。三天兩頭,他去勞工意外保險局,探看博士離職後的辦公室。
進窄廳,上三樓,檔案櫃夾道中,聞見熟悉的殘煙與灰塵。他敲門走入,瞥見博士坐了十四年的辦公桌,如今換人坐了。他默默退出。認識的清潔婦,斯瓦提克太太說,博士「就像一隻小老鼠」,一聲不響就不見了。工友拿走了備用外套:博士衣櫃裡,僅有的衣物。舊文具都被丟光了。斯瓦提克太太交給他,一組博士喝茶用的杯碟。他收下,小心代為保管。他繼續等候。直到卡夫卡下葬後九天,他才得知博士,早由維也納被送回了。
之後,一個二十年過去,他也年當不惑了。不時他還是會想:或許,和卡夫卡當朋友,本來就是件挺孤單的事。這孤單無關年紀、不受熟稔程度影響,卻隨博士辭世,在他心底驟然加重,從此,再不可祛除。只因自那以後,他總覺得若遺忘他,會是嚴重的過失,近乎犯罪。但回想他,或以誠摯意念去記述他,不免意謂記述者,將要獨自往下挖掘,直到存有的更深困境裡。在那裡,人人毋寧都孤獨。
而諷刺的是,過去年歲,竟真像朋友早能預知似的:一定有人誣告了古斯塔夫,因為,他沒幹什麼壞事,某天卻突然被捕了。在惡名昭彰的潘克拉奇監獄,他遭囚年餘。獲釋後,他還是摸不清,這般懲罰所為何來。他只知道,這般無由懲罰,宣告往歷的死滅。因為記憶片紙不存:遭捕當日,妻立刻焚盡了他的日記與手稿。因為之後,記憶的共有人也相繼故去:妻病逝;女兒死於車禍。他仍然拮据,以致竟無法負擔接踵喪儀,長久,為此自責不已。
後來,總是雪中送炭(外包給他編輯和翻譯工作)的出版社老闆自殺了。新老闆毀約,不願償付稿酬。他激烈抗爭,遂遭業界封殺。再後來,總算順利出版了個人著作、獲邀宣傳,他卻在德國書展上,和新納粹分子打了起來,成為國際認證的怪角。到最後,年邁的他退回老家,坐對一屋莫名舊物──相當尷尬,他發現跟自己將來可能「遺物」,自己一點也不熟。但一生,就要這般跌撞過盡了。
一個二十年、再一個二十年過去,他的歲數,如今是彼時兩地,兩人的總和了。獨自清整、以備來路時,他愈頻繁幻見彼此。就說此刻所困,家屋細瑣,當時,都能變賣成路資好了。他確曾不計代價,前去探病,浪費了博士一點氣力。就說,博士也曾沙沙寫紙條,請託他:剪掉病房內,花瓶上,紫丁香的枝葉。因據說這樣,花會多活幾天。他當然照辦。只是舉手之勞,一點也不困難。對他而言。他與博士同坐,靜靜看花。孤枝上,單獨只有花。後來他聽說了:崩離病苦中,博士特別敬愛植物,因為直到死去伊刻,它們殘軀,都還貪婪飲水。直到全然朽壞的一刻。
就說他曾與卡夫卡,這般默對一個死生悖論,在那間,本就不是為了治病而設的病房裡。就說龐然未來,曾在此頓停一瞬,於事雖無補,卻也無損。而他,獨自記憶如斯。那麼或許,此刻舊屋,就他所見的來路,將會比較宜人、遠為空闊—至少,不會是一名老怪,坐對從前那名拮据青年,恐怕可能,他自認的愛惜,終究,也還就是對朋友的吝嗇罷了。
他徒負年歲,逐日走向死境。卡夫卡卻才要出生。因為,他們違背他的遺願,不將他的生命施以火焚,而是裝箱,漂洋過海,去向應許之地。他的生命,是好幾沓紙:各種形制的筆記本、散頁、碎紙張。紙上筆跡,一律細小縝密,意外地,極少塗改之痕。像本真的他,原來就是薄脆如紙,一頁一頁,棲滿了工整的蟻群。像行李箱,本就是更適合他的一種宮腔──絕不透光,沒有一絲可供竄逃的縫隙。他別無選擇,只好耐心地聽任萬有,傾海搖晃他。
萬有並無所圖。萬有只是隨手搖晃他,像搖一箱零件散錯的鐘,直到或然一瞬,零件全數正確接榫,然後鐘復活。萬有,都是這麼花時間,來修繕時間的。它放任那艘船上,有人遠眺見海,跪下禱告—「聽啊,以色列!」有人,呼喚死滅故土,也就是未來國名,像要專程,喊給母胎裡的他諦聽。
然後他出生,重新開口,說起新土之上,最不受歡迎的那種語言。需要更多時間。需要更多預言歸攏,才能使人讀懂他每部未完的手書,他的挫敗,像聽明白各自的曾歷與將臨。預言式的解讀,最早發自班雅明,這位倒楣哲學家。時間點,則是卡夫卡下葬十週年,納粹掌政的隔年,哲學家一路西逃,以個人悲願,密譯博士隱語。悲願是:應當要有文學創作,來為將臨的大屠殺作證。縱使作證,目前是預先的作證。縱使,在未來讀者的回顧裡,它預證過的將來,已是讀者實歷了的過去。
這是受辱時空的修繕,人的話語的奪還。所以應當要是卡夫卡,使人得以理解,那始終被禁止,由人去充分理解的──體制;律法;大屠殺。他的小說裡,個別角色的獨特體驗,成為人的集體經驗。他的《失蹤者》遺稿裡,那長列穿山貼澗、奔赴烏有之鄉的火車,那「冷得打顫」的手跡待續處,留白了日後,人盡皆知的那種死難。
自此,他的生命才悍然成真。像之前個人病苦,只是為了令肉身徹底脫耗。像肉身,也不過就是另種宮腔。像再更之前,他本就是一名從未活過之人:他是以全身,封緘一種機密識見,去行走,去辦公,去談話,去尋常地愛戀與棄絕。是他,從來知曉那個惘惘前景,卻不忍、也無法實寫它,只好以寫作,來擱延實然的寫作。卡夫卡:多年以後,一個事關「書寫之不可能」的文學事件。或如哲學家班雅明所言:一個以敘事技藝,去「推遲未來」的文學事件。
有生之年,古斯塔夫目送博士,這麼活進眾人通識的歷史中。彷彿自此,兩人才真確遠別──他掛念不忘的,僅是朋友的史前。時間之中,一邊是不文的史前;另一邊,則是有文的歷史。哲學家班雅明這樣畫出分界線。在有文空間裡,記憶總是個人的,但遺忘不是。因為,「每件忘卻之事,都與被忘記的史前世界交織在一起」。被遺忘的史前,總是集體的容器。
於是最終,古斯塔夫為己得證:當卡夫卡的史前朋友,意謂悖逆通識──事實是,他所保有的博士記憶,一經記述,必將是公眾共有的;只有獨他知曉的遺忘路徑,才仍屬於這個私我情誼所有。私我有據,情誼就仍猶在。友誼是悉心的忘卻。儘管這近於罪過。
人們不理解他的吝嗇:長久以來,不論個人境遇如何,他總拒絕評析博士作品,或提供關於卡夫卡的史料,或者,談資也好。他標注的路徑,局限在博士埋首的那間辦公室,或相處四年來,兩人同行過的幾條窄巷。一部封印他整個青春年代的博士語錄。此外無它了。
是在辦公桌邊,只為讓他也有事忙,博士又翻出筆記簿,讓他讀裡頭,那些總無標題的故事。故事主角格拉胡斯,是黑森林裡的獵人。幾百年前,為了追捕羚羊,他意外墜崖,獨自癱躺峽谷底,流盡鮮血而死。奇特的不是過程的安靜與漫長。奇特的,是獵人毋寧樂意死去,就像曾愉快活過一樣。他耐心等候死亡駁船到來。當船終於抵達,他高高興興,扔開背包和獵槍,好像一生所謂「獵人」,從來只是他的扮裝。他登船啟航。卻不知出了什麼錯,死亡駁船,偏離了航向—可能,是因船夫扳錯了舵,或因黑森林美景而分了心,總之,數百年來,他一直未能抵達彼岸,只在無限寬廣的天梯游移,忽上忽下,時左時右。「現在我在這裡,只知道這麼多,」格拉胡斯如是說:「我的駁船沒有舵,只能隨風而去,那風,颳自死亡深淵的最底層。」故事結束。
讀完,古斯塔夫說不上來,這故事有何寓意,但結尾那陰森自白,從此刻印在他心中。他探頭,看看周遭,一個如常的保險局:人人案牘勞形,卻無人不可或缺。他看看正埋首,在斟酌一紙「最速件」公文用語的博士。博士您──當時,他想問的只是──為何認定扮裝一生的格拉胡斯,一生幸福快樂呢?
遺忘路徑的開始,是父親。古斯塔夫十七歲,某天,父親要他同去局裡,向一位同事,卡夫卡博士請益。父親知道,有段時日了,少年天天熬夜,偷偷寫東西。家裡電費帳單,告發了少年。或者,洩密者主要還是少年自己:他用尋常卷宗藏手稿,卻在封皮上,醒目地題寫了「美之書」幾字。每天,父親偷讀一點「美之書」,讀不明白,遂用速記法背下,到辦公室,用打字機謄出來。謄打完,還是不明白。父親拿給那位同事參詳──鑑定傷殘程度,乃同事專職。同事要父親別擔心,說那是詩。是某種無關藝術的詩,直接來自青春期副作用,代表生命力過剩。父親聽了,其實沒有比較放心。
父親這樣留意古斯塔夫,令他有些受寵若驚。畢竟,也有一段時日了,每天,父親皆過得不順遂。首先是工作:雖然早無升遷之念,但保險局這僵硬磨具,還是磨輾父親的意氣。其次是母親。她大父親十四歲,成天懷疑父親出軌(這需要想像力),缺乏證據,就怨怪父親狡詐(這需要更大的想像力)。父親下班,穿過大半個城市回到家,沒有晚餐吃。父親遂又出門,到隔壁木工作坊,借方寸空間,叮叮咚咚,敲打自製餐桌。父親釘好就拆,拆好了又釘,因自家窄仄,無法多置擺設。父親就借用那點地頭,花光個人的自由。
木工是父親僅剩嗜好。母親卻以為,這是專為折磨她。父親挨餓出門,母親就關在房裡哭,不理勸解。少年無法,遂回自己桌前,試圖讀點書。字好不容易進了眼,他又看見父親慢慢踱回來,推門進屋。然後哭聲停了。然後他開始覺得悲傷。他覺得自己的存在很神祕,不太理解,當初,父母是怎麼決定要廝守終身的。更悲傷的只是:並不保證一對善良的人,就不會互相傷害。
他自己都恥於宣稱,自己寫的那叫「詩」。那只是當四周終於安靜時,自己的一點呢喃。像相當懦弱的反抗。然而,當父親帶他走進辦公室,從桌後,博士站起,鄭重迎接了他。好像若要談文學,就該鄭重。好像在勞工意外保險局裡談文學,本來,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事實上,最初幾次會面,會語出譏誚的,反而總是少年自己──泰半因為莫名羞赧,或自我關注作祟。他如是談自己讀的書,學校,父母,那張叮咚拆釘的餐桌,像一切都很可笑。他看見博士微笑,藍灰色眼珠閃動。博士要他找機會,親自去木工作坊看看。博士說,父親木工極出色。父親(在他眼中,那麼庸碌的父親),是博士最敬重的人之一。
他頓時愣住。他花了一點時間,才判斷出博士不是戲言。博士比他想像的認真。因為不久,他就在筆記簿裡,讀到博士更多年前寫的,關於木工的段落了。故事中有人,苦練技術,只為釘起一張桌子,只為讓「釘釘子是真正的釘釘子,同時又什麼都不是」。多年以後,他還讀到:在哲學家的詮釋中,這「什麼都不是」,竟也就是卡夫卡一生的真確追求。彼時他再探頭,視線有些模糊了。他發現自己可能誤會了:博士鄭重待他,自然不為與他談文學,而是因那些蒙昧話語,曾由特定某人,默存過大半個城市,猶然不解,卻深自不忘了。
路徑的終局,是卡夫卡的〈司爐〉。多年以後,世人皆知:那是博士長篇的起點,《失蹤者》的首章。那卻是他讀完的,最後的卡夫卡小說了──他曾精裝過的回贈,他的史前的愚行。〈司爐〉也在行李箱內,也隨船而去了,只待岸上,預言的證成。惟一神祕的只是:這個篇章寫的,正是離船登岸的故事。彷彿朋友決心令萬有困惑一瞬,疑心不知為何,它傾海去搖晃的,會是另一面已然靜停的海。
世人從此,多知其後了。他們知道在聚會時,當卡夫卡朗讀〈司爐〉給朋友們聽時,人人都被逗笑了。他卻更願深記:此篇寫的,同時,也就是一則悼別朋友的故事。是這樣的:當小說主角卡爾.羅斯曼,由舅舅接引,將離大船、沿梯步下登岸小艇時,在最高一個梯級上,卡爾「嚎啕大哭起來」。卡爾深深遺憾,自己做得不夠多,也不夠好,不足以援助他想為之辯護的、無法自陳的司爐。當視線矇矓,卡爾再一眨眼,卻「彷彿司爐,已不復存在」了。
那是純粹悲傷的眼淚,只在起點出現。那也是終將被忘卻的眼淚,來自K之前的K,歸於史前,倒逆颳自死淵之風而行。像朋友最祕密、卻也最慷慨的回贈。
頭一天他們穿行過一座高山,暗藍色的懸岩以其尖尖的楔子向列車逼近,人們從窗戶向外探身,徒勞地尋找著峰頂,幽暗、狹窄、被撕裂的山谷張開著,人們用手指頭指引著那些山谷漸漸隱去的方向,寬闊的山澗在連綿起伏的丘陵上像巨浪一樣匆匆湧來,夾帶著萬千洶湧的泡沫浪花,它們從火車駛過的橋下奔騰而過,它們離人如此之近,以致它們那涼絲絲的氣息讓你的臉冷得打顫。
──法蘭茲.卡夫卡,《美國》(《失蹤者》)
我無法讀卡夫卡的長篇小說和日記。不是因他對我太陌生,而是因我離他太近了。青春的迷惘,隨後幾年內外交困的處境,不斷幻滅的幸福憧憬,猝不及防被剝奪的所有權利,日益加劇的孤獨與隔絕,那段憂煩與恐懼肆虐的蒼白時日,使我對耐心承受苦難的卡夫卡博士此人醉心不已。對我而言,他始終不是一個文學事件。他對我的意義遠不僅於此。多年以來,卡夫卡博士一直是我的人性的庇護所。他是位以其善良、寬容和坦誠,鼓勵且保護我在冷風淒雨中開展自我的人。他是我的認知和感覺的基礎,使我如今,猶能在這魍魎亂世裡苟存。
──古斯塔夫.亞努赫,《與卡夫卡對話》
在捷克第一共和國境內,只有本國法人,才能申請電影院營業執照。體操協會開的電影院,叫「獵鷹」;退伍軍人協會開的叫「西伯利亞」;紅十字會開的,就叫作「健康」。卡夫卡博士最喜歡的電影院名,是「盲人」,由視障者關懷協會開設。他說,所有電影院都應該叫這個名字。古斯塔夫在「盲人」打工,擔任樂手。領到第一筆薪水,他將博士的〈司爐〉、〈判決〉與〈變形記〉等三篇小說,裝訂成精裝書,送給博士。那是惟一一次,他令博士深感尷尬。博士,也是他認識的惟一一位,覺得作品應當銷毀的寫作者。因為,「沒有人可以因自己絕望,而使病人的情況雪上加霜」。
然而,開始是死亡,後來是病房,最後,才是生命的成真。卡夫卡:某種倒裝的時程。病房遠在維也納。彼時,卡夫卡年當不惑,肺結核蔓延到喉頭,令他無法吐聲、吞嚥也困難,鎮日在高燒中,靜緩地自耗。必要與人交談時,他寫紙條。紙條說:今日換服這藥片很好,入口如玻璃渣,化掉像炭火,暫時蓋過呼吸時的劇痛了。住院滿好,院裡人人皆待我好。這樣也好:總算校對完《飢餓藝術家》書稿,自知文學夢遠不可企及,從此斷念。往後不要書本了,請帶易讀報刊來即好,有園藝知識的最好。分崩離析,很疲累,睡前覺得每個肢體,都是「一個人」。
古斯塔夫從不曾去探過病。主要因為湊不出旅費。也因恐怕探病之舉,只會更傷勞病人(他記起博士的尷尬之言了)。他小卡夫卡足足二十歲,是彼此難得的忘年交。卻又因此,他總自覺有義務,節用朋友的心力。三天兩頭,他去勞工意外保險局,探看博士離職後的辦公室。
進窄廳,上三樓,檔案櫃夾道中,聞見熟悉的殘煙與灰塵。他敲門走入,瞥見博士坐了十四年的辦公桌,如今換人坐了。他默默退出。認識的清潔婦,斯瓦提克太太說,博士「就像一隻小老鼠」,一聲不響就不見了。工友拿走了備用外套:博士衣櫃裡,僅有的衣物。舊文具都被丟光了。斯瓦提克太太交給他,一組博士喝茶用的杯碟。他收下,小心代為保管。他繼續等候。直到卡夫卡下葬後九天,他才得知博士,早由維也納被送回了。
之後,一個二十年過去,他也年當不惑了。不時他還是會想:或許,和卡夫卡當朋友,本來就是件挺孤單的事。這孤單無關年紀、不受熟稔程度影響,卻隨博士辭世,在他心底驟然加重,從此,再不可祛除。只因自那以後,他總覺得若遺忘他,會是嚴重的過失,近乎犯罪。但回想他,或以誠摯意念去記述他,不免意謂記述者,將要獨自往下挖掘,直到存有的更深困境裡。在那裡,人人毋寧都孤獨。
而諷刺的是,過去年歲,竟真像朋友早能預知似的:一定有人誣告了古斯塔夫,因為,他沒幹什麼壞事,某天卻突然被捕了。在惡名昭彰的潘克拉奇監獄,他遭囚年餘。獲釋後,他還是摸不清,這般懲罰所為何來。他只知道,這般無由懲罰,宣告往歷的死滅。因為記憶片紙不存:遭捕當日,妻立刻焚盡了他的日記與手稿。因為之後,記憶的共有人也相繼故去:妻病逝;女兒死於車禍。他仍然拮据,以致竟無法負擔接踵喪儀,長久,為此自責不已。
後來,總是雪中送炭(外包給他編輯和翻譯工作)的出版社老闆自殺了。新老闆毀約,不願償付稿酬。他激烈抗爭,遂遭業界封殺。再後來,總算順利出版了個人著作、獲邀宣傳,他卻在德國書展上,和新納粹分子打了起來,成為國際認證的怪角。到最後,年邁的他退回老家,坐對一屋莫名舊物──相當尷尬,他發現跟自己將來可能「遺物」,自己一點也不熟。但一生,就要這般跌撞過盡了。
一個二十年、再一個二十年過去,他的歲數,如今是彼時兩地,兩人的總和了。獨自清整、以備來路時,他愈頻繁幻見彼此。就說此刻所困,家屋細瑣,當時,都能變賣成路資好了。他確曾不計代價,前去探病,浪費了博士一點氣力。就說,博士也曾沙沙寫紙條,請託他:剪掉病房內,花瓶上,紫丁香的枝葉。因據說這樣,花會多活幾天。他當然照辦。只是舉手之勞,一點也不困難。對他而言。他與博士同坐,靜靜看花。孤枝上,單獨只有花。後來他聽說了:崩離病苦中,博士特別敬愛植物,因為直到死去伊刻,它們殘軀,都還貪婪飲水。直到全然朽壞的一刻。
就說他曾與卡夫卡,這般默對一個死生悖論,在那間,本就不是為了治病而設的病房裡。就說龐然未來,曾在此頓停一瞬,於事雖無補,卻也無損。而他,獨自記憶如斯。那麼或許,此刻舊屋,就他所見的來路,將會比較宜人、遠為空闊—至少,不會是一名老怪,坐對從前那名拮据青年,恐怕可能,他自認的愛惜,終究,也還就是對朋友的吝嗇罷了。
他徒負年歲,逐日走向死境。卡夫卡卻才要出生。因為,他們違背他的遺願,不將他的生命施以火焚,而是裝箱,漂洋過海,去向應許之地。他的生命,是好幾沓紙:各種形制的筆記本、散頁、碎紙張。紙上筆跡,一律細小縝密,意外地,極少塗改之痕。像本真的他,原來就是薄脆如紙,一頁一頁,棲滿了工整的蟻群。像行李箱,本就是更適合他的一種宮腔──絕不透光,沒有一絲可供竄逃的縫隙。他別無選擇,只好耐心地聽任萬有,傾海搖晃他。
萬有並無所圖。萬有只是隨手搖晃他,像搖一箱零件散錯的鐘,直到或然一瞬,零件全數正確接榫,然後鐘復活。萬有,都是這麼花時間,來修繕時間的。它放任那艘船上,有人遠眺見海,跪下禱告—「聽啊,以色列!」有人,呼喚死滅故土,也就是未來國名,像要專程,喊給母胎裡的他諦聽。
然後他出生,重新開口,說起新土之上,最不受歡迎的那種語言。需要更多時間。需要更多預言歸攏,才能使人讀懂他每部未完的手書,他的挫敗,像聽明白各自的曾歷與將臨。預言式的解讀,最早發自班雅明,這位倒楣哲學家。時間點,則是卡夫卡下葬十週年,納粹掌政的隔年,哲學家一路西逃,以個人悲願,密譯博士隱語。悲願是:應當要有文學創作,來為將臨的大屠殺作證。縱使作證,目前是預先的作證。縱使,在未來讀者的回顧裡,它預證過的將來,已是讀者實歷了的過去。
這是受辱時空的修繕,人的話語的奪還。所以應當要是卡夫卡,使人得以理解,那始終被禁止,由人去充分理解的──體制;律法;大屠殺。他的小說裡,個別角色的獨特體驗,成為人的集體經驗。他的《失蹤者》遺稿裡,那長列穿山貼澗、奔赴烏有之鄉的火車,那「冷得打顫」的手跡待續處,留白了日後,人盡皆知的那種死難。
自此,他的生命才悍然成真。像之前個人病苦,只是為了令肉身徹底脫耗。像肉身,也不過就是另種宮腔。像再更之前,他本就是一名從未活過之人:他是以全身,封緘一種機密識見,去行走,去辦公,去談話,去尋常地愛戀與棄絕。是他,從來知曉那個惘惘前景,卻不忍、也無法實寫它,只好以寫作,來擱延實然的寫作。卡夫卡:多年以後,一個事關「書寫之不可能」的文學事件。或如哲學家班雅明所言:一個以敘事技藝,去「推遲未來」的文學事件。
有生之年,古斯塔夫目送博士,這麼活進眾人通識的歷史中。彷彿自此,兩人才真確遠別──他掛念不忘的,僅是朋友的史前。時間之中,一邊是不文的史前;另一邊,則是有文的歷史。哲學家班雅明這樣畫出分界線。在有文空間裡,記憶總是個人的,但遺忘不是。因為,「每件忘卻之事,都與被忘記的史前世界交織在一起」。被遺忘的史前,總是集體的容器。
於是最終,古斯塔夫為己得證:當卡夫卡的史前朋友,意謂悖逆通識──事實是,他所保有的博士記憶,一經記述,必將是公眾共有的;只有獨他知曉的遺忘路徑,才仍屬於這個私我情誼所有。私我有據,情誼就仍猶在。友誼是悉心的忘卻。儘管這近於罪過。
人們不理解他的吝嗇:長久以來,不論個人境遇如何,他總拒絕評析博士作品,或提供關於卡夫卡的史料,或者,談資也好。他標注的路徑,局限在博士埋首的那間辦公室,或相處四年來,兩人同行過的幾條窄巷。一部封印他整個青春年代的博士語錄。此外無它了。
是在辦公桌邊,只為讓他也有事忙,博士又翻出筆記簿,讓他讀裡頭,那些總無標題的故事。故事主角格拉胡斯,是黑森林裡的獵人。幾百年前,為了追捕羚羊,他意外墜崖,獨自癱躺峽谷底,流盡鮮血而死。奇特的不是過程的安靜與漫長。奇特的,是獵人毋寧樂意死去,就像曾愉快活過一樣。他耐心等候死亡駁船到來。當船終於抵達,他高高興興,扔開背包和獵槍,好像一生所謂「獵人」,從來只是他的扮裝。他登船啟航。卻不知出了什麼錯,死亡駁船,偏離了航向—可能,是因船夫扳錯了舵,或因黑森林美景而分了心,總之,數百年來,他一直未能抵達彼岸,只在無限寬廣的天梯游移,忽上忽下,時左時右。「現在我在這裡,只知道這麼多,」格拉胡斯如是說:「我的駁船沒有舵,只能隨風而去,那風,颳自死亡深淵的最底層。」故事結束。
讀完,古斯塔夫說不上來,這故事有何寓意,但結尾那陰森自白,從此刻印在他心中。他探頭,看看周遭,一個如常的保險局:人人案牘勞形,卻無人不可或缺。他看看正埋首,在斟酌一紙「最速件」公文用語的博士。博士您──當時,他想問的只是──為何認定扮裝一生的格拉胡斯,一生幸福快樂呢?
遺忘路徑的開始,是父親。古斯塔夫十七歲,某天,父親要他同去局裡,向一位同事,卡夫卡博士請益。父親知道,有段時日了,少年天天熬夜,偷偷寫東西。家裡電費帳單,告發了少年。或者,洩密者主要還是少年自己:他用尋常卷宗藏手稿,卻在封皮上,醒目地題寫了「美之書」幾字。每天,父親偷讀一點「美之書」,讀不明白,遂用速記法背下,到辦公室,用打字機謄出來。謄打完,還是不明白。父親拿給那位同事參詳──鑑定傷殘程度,乃同事專職。同事要父親別擔心,說那是詩。是某種無關藝術的詩,直接來自青春期副作用,代表生命力過剩。父親聽了,其實沒有比較放心。
父親這樣留意古斯塔夫,令他有些受寵若驚。畢竟,也有一段時日了,每天,父親皆過得不順遂。首先是工作:雖然早無升遷之念,但保險局這僵硬磨具,還是磨輾父親的意氣。其次是母親。她大父親十四歲,成天懷疑父親出軌(這需要想像力),缺乏證據,就怨怪父親狡詐(這需要更大的想像力)。父親下班,穿過大半個城市回到家,沒有晚餐吃。父親遂又出門,到隔壁木工作坊,借方寸空間,叮叮咚咚,敲打自製餐桌。父親釘好就拆,拆好了又釘,因自家窄仄,無法多置擺設。父親就借用那點地頭,花光個人的自由。
木工是父親僅剩嗜好。母親卻以為,這是專為折磨她。父親挨餓出門,母親就關在房裡哭,不理勸解。少年無法,遂回自己桌前,試圖讀點書。字好不容易進了眼,他又看見父親慢慢踱回來,推門進屋。然後哭聲停了。然後他開始覺得悲傷。他覺得自己的存在很神祕,不太理解,當初,父母是怎麼決定要廝守終身的。更悲傷的只是:並不保證一對善良的人,就不會互相傷害。
他自己都恥於宣稱,自己寫的那叫「詩」。那只是當四周終於安靜時,自己的一點呢喃。像相當懦弱的反抗。然而,當父親帶他走進辦公室,從桌後,博士站起,鄭重迎接了他。好像若要談文學,就該鄭重。好像在勞工意外保險局裡談文學,本來,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事實上,最初幾次會面,會語出譏誚的,反而總是少年自己──泰半因為莫名羞赧,或自我關注作祟。他如是談自己讀的書,學校,父母,那張叮咚拆釘的餐桌,像一切都很可笑。他看見博士微笑,藍灰色眼珠閃動。博士要他找機會,親自去木工作坊看看。博士說,父親木工極出色。父親(在他眼中,那麼庸碌的父親),是博士最敬重的人之一。
他頓時愣住。他花了一點時間,才判斷出博士不是戲言。博士比他想像的認真。因為不久,他就在筆記簿裡,讀到博士更多年前寫的,關於木工的段落了。故事中有人,苦練技術,只為釘起一張桌子,只為讓「釘釘子是真正的釘釘子,同時又什麼都不是」。多年以後,他還讀到:在哲學家的詮釋中,這「什麼都不是」,竟也就是卡夫卡一生的真確追求。彼時他再探頭,視線有些模糊了。他發現自己可能誤會了:博士鄭重待他,自然不為與他談文學,而是因那些蒙昧話語,曾由特定某人,默存過大半個城市,猶然不解,卻深自不忘了。
路徑的終局,是卡夫卡的〈司爐〉。多年以後,世人皆知:那是博士長篇的起點,《失蹤者》的首章。那卻是他讀完的,最後的卡夫卡小說了──他曾精裝過的回贈,他的史前的愚行。〈司爐〉也在行李箱內,也隨船而去了,只待岸上,預言的證成。惟一神祕的只是:這個篇章寫的,正是離船登岸的故事。彷彿朋友決心令萬有困惑一瞬,疑心不知為何,它傾海去搖晃的,會是另一面已然靜停的海。
世人從此,多知其後了。他們知道在聚會時,當卡夫卡朗讀〈司爐〉給朋友們聽時,人人都被逗笑了。他卻更願深記:此篇寫的,同時,也就是一則悼別朋友的故事。是這樣的:當小說主角卡爾.羅斯曼,由舅舅接引,將離大船、沿梯步下登岸小艇時,在最高一個梯級上,卡爾「嚎啕大哭起來」。卡爾深深遺憾,自己做得不夠多,也不夠好,不足以援助他想為之辯護的、無法自陳的司爐。當視線矇矓,卡爾再一眨眼,卻「彷彿司爐,已不復存在」了。
那是純粹悲傷的眼淚,只在起點出現。那也是終將被忘卻的眼淚,來自K之前的K,歸於史前,倒逆颳自死淵之風而行。像朋友最祕密、卻也最慷慨的回贈。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