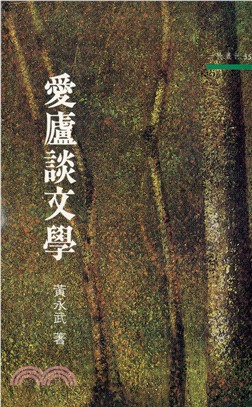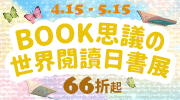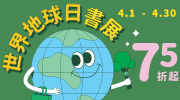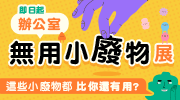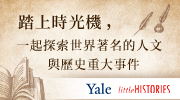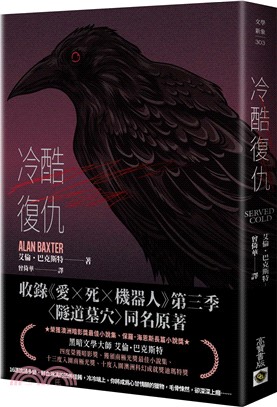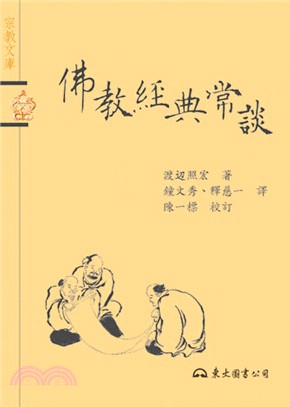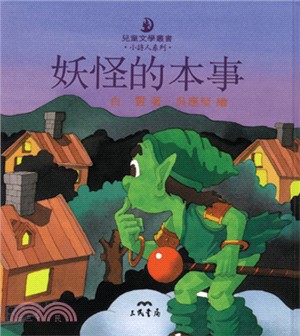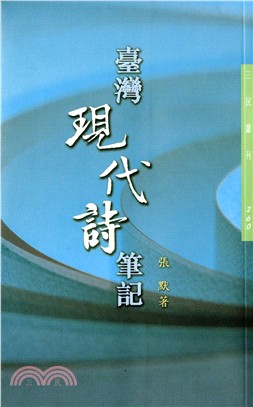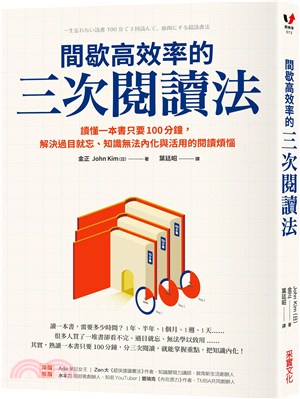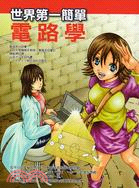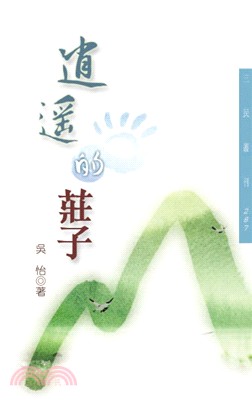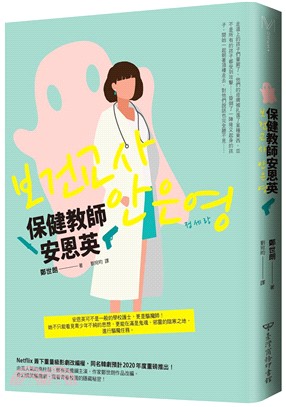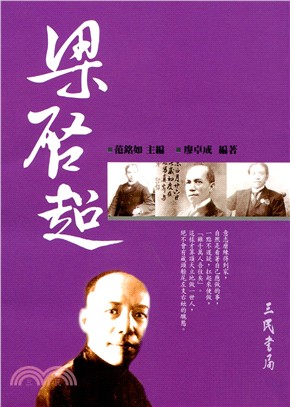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商品簡介
本書以中國文學詩歌為主體,其中為維護中國文字的正體字,而大聲疾呼;為光揚中國古典詩在現今生活美學中的價值,而細心闡發;對於敦煌新發現的寫卷資料,也用淺顯筆法,作應用的示範; 並對四洋星座起源的追索,以 及對「圖象批評」的分析,均極具啟發性。由本書亦可以窺見作者近年來對明代六千種善本書鑽研的興致。
作者簡介
黃永武
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歷任高雄師大國文研究所所長暨教務長、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現為專任教授,一心寫作。曾獲文藝理論類國家文藝獎、散文類國家文藝獎。著作有《愛廬談文學》、《愛廬談心事》、《詩與情》等三十餘種。
序
序
《愛廬談文學》是我今年所出版的第七本書,經過長期的蘊積,快意的抒發,到今日密集地出書,自有豐年祭的歡愉。每到新書將出版要寫一篇序文時,總為這即將呱呱問世的新生命而充滿著期待的心情。
我覺得新出書的心情有兩種:一本尚未寫出來的書,還在作者胸中孕育時,常是作者自己所最愛的,期待極高,寄望殷切,等到接近完稿時,作者仍有雀躍的自許。直待到書已殺青,校讀三過,那分內心在鼓掌的心情,陡然降下來,難怪黃侃在他的驚世名作《文心雕龍札記》問世後二週,別人提起他的新著,他居然悶聲不響,甚至有點懊惱,讓別人再也搭腔不下去。這是一書初成,「半折心始」的心情吧?
另一種心情則相反,由於並不曾事先想定寫作的遠大目標,也沒有立言不朽的自我預期,除了有編輯催稿,乘興揮幾筆,有學術會議,順勢撰一篇之外,只是話題偶到,默思追索;讀書興起,隨筆雜記而已,待到積稿成冊付梓校對時,好像偶在田野拾穗,而不知不覺盈襜盈襭,這種不曾刻意經營,而意外累積的喜悅,不就像無心插柳、忽爾成蔭麼?
我想這本《愛廬談文學》是屬於後者的心情,看得出來,筆下仍想保持廣博的興趣:文字繁簡的論戰、星座生肖的探索、敦煌殘卷的勘讀、以及大量明代詩文集中生活藝術的抉發,方面雖廣,到了筆下,全部仍以文學趣味為主,並不想專癡什麼,營戀什麼,不過,文思轉來轉去,依然在研究古典詩的輻射範圍之內的。
如果要問:書為什麼寫得如此勤?那大概是相信讀書著書是滔滔亂世裏安度災的最佳方策吧?面對著當前滄海橫流的時代,鬱盤的忠義之氣,姑且化作悠然孤往的文辭吧,萬境自鬧,我心自閒,曾國藩在荒唐的世局裏,體會出尋找快樂的三種方法:先勤勞而後獲得憩息,滿身暢快,是第一種快樂;以最淡的心,消除忮害嫉妒,到處可以是安身之所,是第二種快樂;讀書琅琅,讀出金石的聲音來,不知書外還有世界,是第三種快樂。我反省自己,這些年來,工作超量,寫書編書,夠勤勉的,現在可以優游涵泳一番,真快樂;回到臺北一所袖珍型的學校教書,婉謝許多高位厚薪的聘邀,以不忮不求自勉,更快樂;附近中央圖書館裏善本圖書盈千上萬,誰不希望在識盡天下英雄豪傑之後,能再讀盡天下奇書秘笈呢?福緣如此,能不快樂?匯集曾國藩的三件樂事於一時,再適逢新書刊行,數量上是北斗七星,內容上是詩文雅事,正當秋風高爽,銀河閃亮,保持天底下一顆乾淨的方寸之地,俯仰無愧,當然樂上加樂了。
民國八十一年十月於臺灣臺北
目次
序
簡體字就是紅衛兵
救字如救火──再談收拾掉簡體字
科舉漫談
西洋星座原產中國?
誰是千里馬
世間第一樂地──古典詩中的「親情」
寂寞
扭轉挫折──古代知識分子的應付策略
談灑脫
讀詩偶記
八對之謎
大手筆沒情趣?
李杜相會
李杜的老師
詩與詞
唐詩與宋詩
臺灣詩與臺灣史
六言律詩與同性戀
詩與燈謎
詩鐘比賽
唐詩鑑賞的方法
窗前草不除
發現玄奘詩?
讀敦煌本李嶠詩
「錯、錯、錯」「莫、莫、莫」新解
新發現兩首敦煌曲
虞美人怨
敦煌曲〈鬥百草詞〉試釋
「圖象批評」與明代文評
透視治學讀書的門徑
讀詩又記
折字詩
猜猜「離合體」
「歇後」玩笑大
回文的妙趣
文字遊戲
重複也是美
諧合一氣
詩愛說反話
印象批評
詩需要奇想
簡體字就是紅衛兵
救字如救火──再談收拾掉簡體字
科舉漫談
西洋星座原產中國?
誰是千里馬
世間第一樂地──古典詩中的「親情」
寂寞
扭轉挫折──古代知識分子的應付策略
談灑脫
讀詩偶記
八對之謎
大手筆沒情趣?
李杜相會
李杜的老師
詩與詞
唐詩與宋詩
臺灣詩與臺灣史
六言律詩與同性戀
詩與燈謎
詩鐘比賽
唐詩鑑賞的方法
窗前草不除
發現玄奘詩?
讀敦煌本李嶠詩
「錯、錯、錯」「莫、莫、莫」新解
新發現兩首敦煌曲
虞美人怨
敦煌曲〈鬥百草詞〉試釋
「圖象批評」與明代文評
透視治學讀書的門徑
讀詩又記
折字詩
猜猜「離合體」
「歇後」玩笑大
回文的妙趣
文字遊戲
重複也是美
諧合一氣
詩愛說反話
印象批評
詩需要奇想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