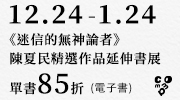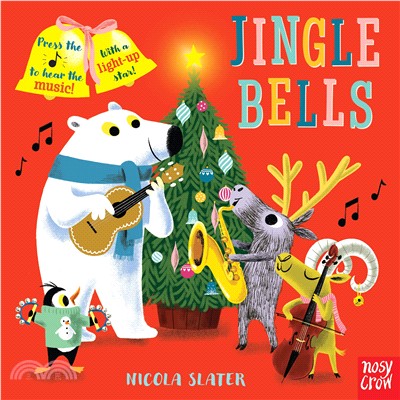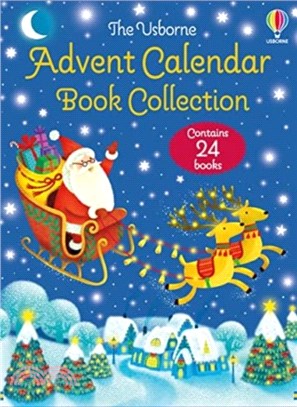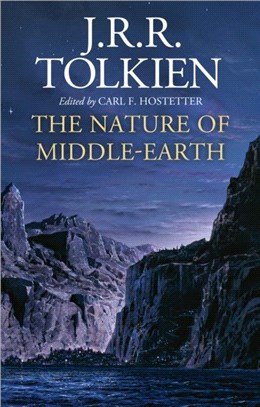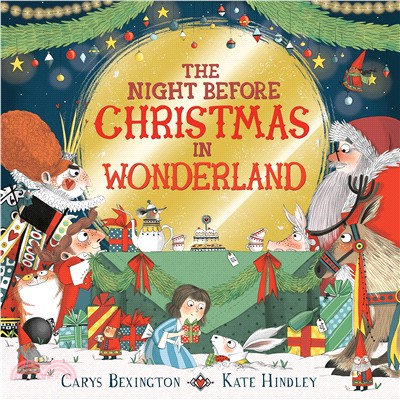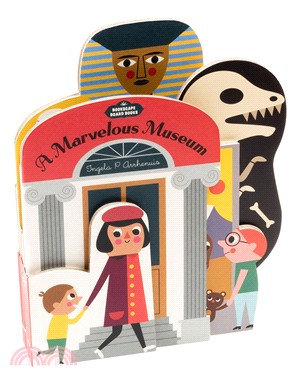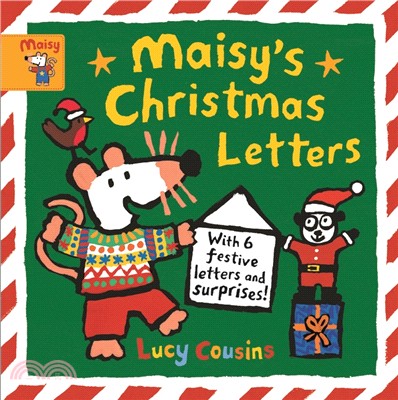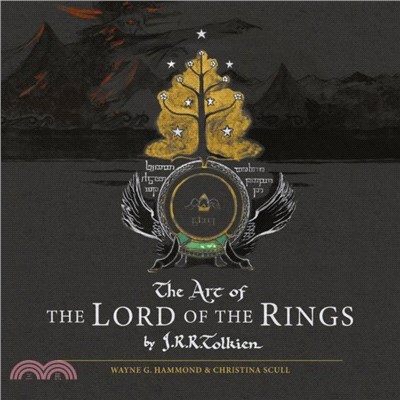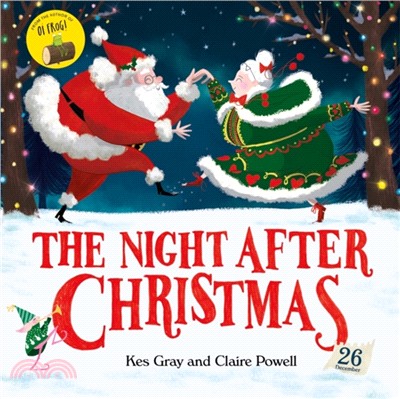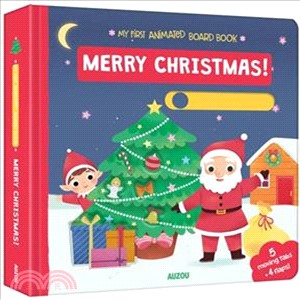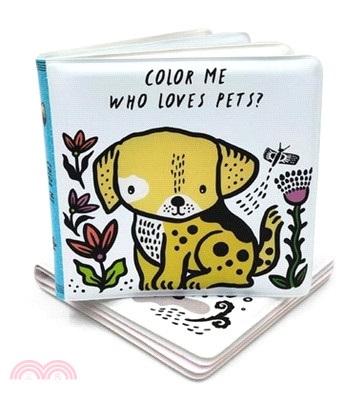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近幾年來,由於現代文學研究的日益深化,「白馬湖作家群」此一議題亦陸續提出。作者曾兩度造訪白馬湖,並獲得珍貴資料以完成此書。本書內容一方面以「人」為主體,討論這群作家所代表的文人型態、思想特質與人格量,另一方面以「作品」為中心,討論其文學藝術、特別是散文方面的表現,力求展現這群作家在思想上與文學上的集體風貌。
作者簡介
張堂錡
1962年生,臺灣新竹人。臺灣師大國文系所畢業,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曾任報社、出版社主編工作多年,並歷任東吳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中央大學等校兼任講師。目前專任於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現代《域外知音》、《文學靈魂的閱讀》、《舊時月色》等書。
序
序 李瑞騰
堂錡的文學歷程起始於創作,出版有小說集《青青校樹》、散文集《夢裡的木棉道》。這點和我很像,當大學生的日子,創作是我生活裡主要的部分,詩、散文、小說,樣樣都來,後來詩和散文出了書,小說則始終不敢示人。堂錡好像不寫詩,比較起來,彼此勉強扯平。
我後來在學府和媒體兩棲作戰,堂錡亦然,因工作和興趣的需要,他出過兩本人物報導文集:《生命風景》、《域外知音》,我除在早先零星寫過幾篇報導,近年另有兩冊《文學尖端對話》。有趣的是,堂錡對域外來的漢學家特感興趣,而我當研究生的時候受邀幾次採訪,對象也都是堂錡所謂的「域外知音」。這部分也算不相上下。
我虛長他十歲,原無師生關係,且不相識。他十年前來找我,要跟我一起研究晚清,他後來做了黃遵憲,用功的程度讓我驚歎,掌握資料、解讀原典的能力都不錯。那時我在「文訊」復興南路的舊址有一工作室,他常來,執弟子之禮甚恭,進退得體。我當他是朋友,但心裡高興有了這麼一個開門弟子。
堂錡出身國立臺灣師大國文系,擔任過國中教師,拿到碩士學位,想回母系擔任助教而不可得,當時想必受傷嚴重。那時,他人在《中央日報》副刊任編輯,頗受已故梅新先生的器重,他反應快、下筆也快,做事有分寸,也算是一個行動派,繼續走編輯之路亦未嘗不可,但他似乎比較喜歡學院生活,後來以南社研究計畫考上東吳中文研究所博士班,一邊還在編《中央日報》長河版。
長河版定位在近現代,完全契合堂錡的志趣。這版面之於他,如「文訊」之於我。我在八○年代初也編過幾年的報紙副刊,在編輯現場是有實戰經驗的,對我來說,編務與學業非但不妨礙,還有相輔相成的效果,堂錡想必亦然。他偶有困惑,便到復興南路來看我,我的結構性思考及務實的特性,對他應有所助益。我便也在這時相往來的過程中更加了解他。
我的晚清文學思想之探討,碰了一點「南社」,建議他博士論文作南社研究,通過晚清這個革命文藝團體去追蹤背後的大時代。他後來改作民國白馬湖作家群,顯然是不想一直停留在晚清,對他來說這是個躍進。我在學校長期教新文學史,堂錡沒上過我這個課,這個部分他完全走自己的道路,我除了在觀念和方法上提供一些建議,讀他論文之際隨手校正幾處筆誤之外,對他幫助不大。平心而論,他的學力已足應付這個研究。
我對文學史的思考,最終都落在作為知識分子的文學作家如何對應外在客觀環境的變化上。堂錡考察白馬湖作家群,把知識、文學、教育當作行為表現,去看其變與不變,個性與群性之間的關聯,他用民間性格與崗位意識兩個主要概念去解析這一群知識分子的行為表現,左徵右引,行文通達,論點深得我心。
堂錡辭報社職寫論文,通過博士學位考試以後,我希望他能來中央大學,結果他靠自己的能力去了政大,我不免遺憾,但也替他高興,木柵有山野之趣,自然與人文之合,使白馬湖成為文學聖地,指南山下應該也是一片可耕可讀的文藝天地。
目次
序/李瑞騰
自 序
第一章 緒 論
一、「白馬湖作家群」釋名
二、研究意義與開展空間
三、研究思路與進程
第二章 「白馬湖作家群」形成論
一、一師學潮的直接催化
二、春暉辦學的教育需求
三、地理人文的薰染化育
四、散文共性的集體呈現
五、同事‧同志‧同道:立達、開明的延續深化
第三章 「白馬湖作家群」的文人型態
一、「遠離喧嘩」的心境追求
二、名士雅集,文人本色
三、相知相重,真情實義
四、佛學後光,共結善緣
五、「從邊緣出發」的人間情懷
第四章 「白馬湖作家群」的民間性格
一、重返民間:世紀初知識界的覺醒運動
二、從「學在民間」看白馬湖作家群的民間性格
三、從「到民間去」看白馬湖作家群的民間性格
四、從「新村意識」看白馬湖作家群的民間性格
五、走向民間:世紀末知識分子的一種可能
第五章 「白馬湖作家群」的崗位意識
一、廟堂‧廣場‧崗位:知識分子三種價值取向
二、教育:白馬湖作家群的崗位之一
三、出版:白馬湖作家群的崗位之二
四、崗位意識的時代意義
第六章 「白馬湖作家群」的教育理念
一、新的教育
二、人的教育
三、愛的教育
四、動的教育
五、美的教育
六、教改先驅:一個深耕教育的突出參照系
第七章 「白馬湖作家群」作品論(上)
一、樸實、清醇、雋永的「白馬湖風格」
二、夏丏尊:具象與情緒並重,親切如摯友談心
三、豐子愷:瀟灑有餘音,人間情味多
四、朱自清:意在表現自己,風華從樸素中來
五、朱光潛:以美學為底韻,說理清澈深刻
六、俞平伯:自然適意,灑脫名士風
七、葉聖陶:清新簡約,腳踏實地
第八章 「白馬湖作家群」作品論(下)
一、大好湖山詩畫緣:經亨頤詠白馬湖舊詩
二、難得湖山夜色:劉大白詠白馬湖新詩
三、詩詞風‧家常味‧人間相:豐子愷漫畫的獨特魅力
四、科學與人生:劉薰宇、劉叔琴、匡互生作品
第九章 結 論
一、大潮與分流:「白馬湖風格」在現代散文史上的意義
二、顯隱與多少:白馬湖風格「影響」問題的討論
三、開拓與局限:本課題研究的階段性總結
徵引及參考書(篇)目
附錄一 「白馬湖作家群」文學活動年表
(一九一九─一九二九年)
附錄二 春暉中學校內刊物知見篇目
附錄三 「白馬湖作家群」小傳(依生年序)
附錄四 春暉中學校園平面圖
附錄五 春暉中學及白馬湖現況照片
自 序
第一章 緒 論
一、「白馬湖作家群」釋名
二、研究意義與開展空間
三、研究思路與進程
第二章 「白馬湖作家群」形成論
一、一師學潮的直接催化
二、春暉辦學的教育需求
三、地理人文的薰染化育
四、散文共性的集體呈現
五、同事‧同志‧同道:立達、開明的延續深化
第三章 「白馬湖作家群」的文人型態
一、「遠離喧嘩」的心境追求
二、名士雅集,文人本色
三、相知相重,真情實義
四、佛學後光,共結善緣
五、「從邊緣出發」的人間情懷
第四章 「白馬湖作家群」的民間性格
一、重返民間:世紀初知識界的覺醒運動
二、從「學在民間」看白馬湖作家群的民間性格
三、從「到民間去」看白馬湖作家群的民間性格
四、從「新村意識」看白馬湖作家群的民間性格
五、走向民間:世紀末知識分子的一種可能
第五章 「白馬湖作家群」的崗位意識
一、廟堂‧廣場‧崗位:知識分子三種價值取向
二、教育:白馬湖作家群的崗位之一
三、出版:白馬湖作家群的崗位之二
四、崗位意識的時代意義
第六章 「白馬湖作家群」的教育理念
一、新的教育
二、人的教育
三、愛的教育
四、動的教育
五、美的教育
六、教改先驅:一個深耕教育的突出參照系
第七章 「白馬湖作家群」作品論(上)
一、樸實、清醇、雋永的「白馬湖風格」
二、夏丏尊:具象與情緒並重,親切如摯友談心
三、豐子愷:瀟灑有餘音,人間情味多
四、朱自清:意在表現自己,風華從樸素中來
五、朱光潛:以美學為底韻,說理清澈深刻
六、俞平伯:自然適意,灑脫名士風
七、葉聖陶:清新簡約,腳踏實地
第八章 「白馬湖作家群」作品論(下)
一、大好湖山詩畫緣:經亨頤詠白馬湖舊詩
二、難得湖山夜色:劉大白詠白馬湖新詩
三、詩詞風‧家常味‧人間相:豐子愷漫畫的獨特魅力
四、科學與人生:劉薰宇、劉叔琴、匡互生作品
第九章 結 論
一、大潮與分流:「白馬湖風格」在現代散文史上的意義
二、顯隱與多少:白馬湖風格「影響」問題的討論
三、開拓與局限:本課題研究的階段性總結
徵引及參考書(篇)目
附錄一 「白馬湖作家群」文學活動年表
(一九一九─一九二九年)
附錄二 春暉中學校內刊物知見篇目
附錄三 「白馬湖作家群」小傳(依生年序)
附錄四 春暉中學校園平面圖
附錄五 春暉中學及白馬湖現況照片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