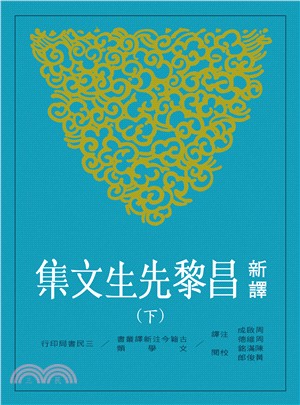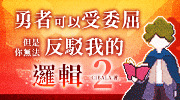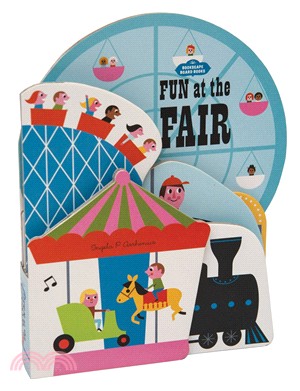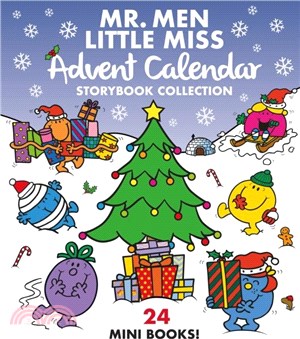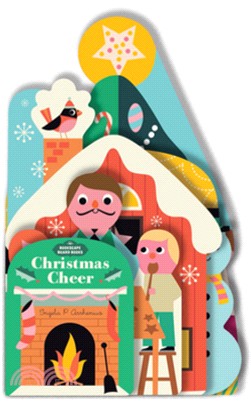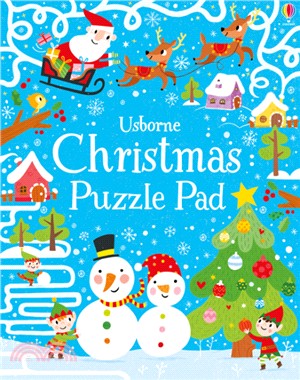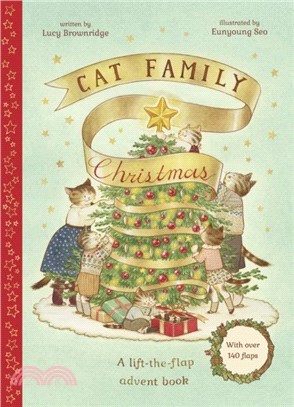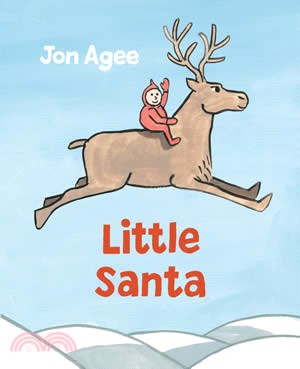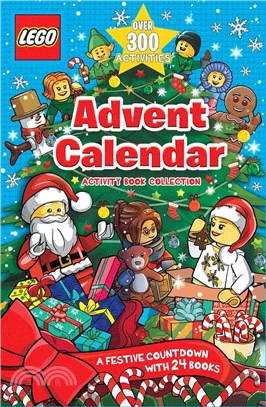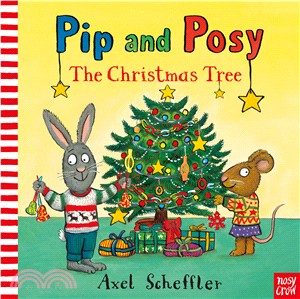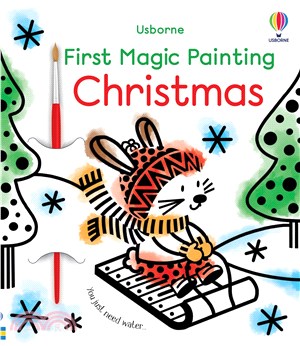商品簡介
韓愈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古文「唐宋八大家」之首。
作者簡介
周啟成,曾任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出版古籍整理和研究著作多種。
序
韓愈,字退之,我國唐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西元七六八年)。祖籍河南河陽(今河南孟縣)。昌黎(三國魏郡名,隋時已廢)韓氏為一時著名的望族,韓愈常自稱「昌黎韓愈」,後人亦稱他為韓昌黎。
韓愈的生平
韓愈的先世出於漢代韓王信、弓高侯頹當之後。祖先中也出過一些封王封侯的顯貴大官,但到他曾祖、祖父、父親這三代,都只做過小官吏。他的曾祖韓泰為唐曹州司馬,祖父韓睿素為桂州都督府長史,父親韓仲卿歷官潞州銅鞮尉,調補武昌令,後改鄱陽令。韓愈的家族有著文學傳統,他的二叔韓雲卿曾被李白稱為「文章冠世」(《李太白全集‧武昌宰韓君去思碑頌》),他的長兄韓會也能文,柳宗元說他「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柳河東集‧先君石表陰先友記》)韓愈就是在文學氣氛濃厚的環境中長大的。韓愈出生在京城長安,當時他的父親韓仲卿正在長安任祕書郎。韓愈出生才二月,他的母親便逝世了,三歲時,父親又去世了,於是只得依賴長兄韓會和嫂嫂鄭氏的撫養。十歲時,韓會被貶為韶州(今廣東曲江縣)刺史,他隨兄嫂同至韶州。不久,韓會病故,他又隨寡嫂北歸河陽,時值戰亂,乃輾轉南下,來到宣城,靠微薄財產度日。孤苦的身世更激起了他勤奮好學的精神,新舊《唐書》本傳都說他「自以孤子」,「刻苦學儒,不俟獎勵」,「日記數千百言」,所以他十三歲便能文,並且從獨孤及、梁肅等人遊學。他曾自稱「自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岳陽樓別竇司直〉)可見少年時在胸中就懷有雄心壯志,欲為國家做一番大事業。貞元二年(西元七八六年),韓愈十九歲,來到京城長安考進士。由於家中沒有什麼產業,而京中物價又高,因而他的生活相當窘困,不得不奔走於權豪勢要門下,甚至攔馬求見北平王馬燧,乞求給予接濟。在科場上,儘管他文才出眾,卻連遭挫敗。先後參加四次進士考試,直到貞元八年,方才榜上有名。這次考試由宰相陸贄任主考官,梁肅、王礎為佐,先試詩賦,再經推薦,終於定了下來。一同登進士第的有李觀、李絳、崔群、歐陽詹、王涯、馮宿、庾承宣,他們「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新唐書‧歐陽詹傳》)當時,科舉歸禮部管,選官歸吏部選,因此中進士後還要通過吏部考試才能分發做官。韓愈參加了三次吏部博學宏辭科考試,都沒有中選。三次給宰相上書,亦未得一覆。失望之餘,只好走「幕府吏」的道路。貞元十二年(西元七九六年)七月,韓愈受汴州(今河南開封)刺史、宣武軍節度使董晉的辟舉,被任為觀察推官,旋又試授祕書校書郎(虛銜)。他的生活雖因而較為安定,但作為僚屬小吏,心中是不滿意的。貞元十五年二月,董晉死,韓愈護喪柩去洛陽。才離開四天,汴州就發生兵變,行軍司馬陸長源等被殺。三月底他攜三十口之家逃難到徐州,被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署為節度推官,試協律郎。他與張建封相處得很不和諧,次年五月即被免職。不久,張建封卒,徐州又亂。貞元十六年(西元八○○年)七月,韓愈赴長安參加吏部詮選,翌年三月,順利通過。秋末冬初,三十四歲的韓愈被任為一個位置不高的學官四門博士(從七品上階)。由於他一面倡導古文,一面向考官舉薦有才之士,所以許多舉子都投到他的門下,稱為「韓門弟子」。他這種好為人師的行為,頗受社會上某些思想狹隘者的議論和責難,韓愈乃寫了〈師說〉一文對此作出了公開的答覆和駁斥。貞元十九年(西元八○三年)七月,韓愈被擢升為監察御史。到任不久,京城附近一帶大旱,他忠於職守,上〈論天旱人饑狀〉,敘述人民「寒餒道塗,斃踣溝壑」的困苦情狀,要求停徵當年的賦稅。為此他被幸臣所讒,貶為連州陽山(今屬廣東)令。貞元二十一年初,唐順宗即位,韓愈接到大赦赦書,即離開陽山來到郴州候訊。這年八月順宗遜位,憲宗繼位,改元永貞,韓愈又得赦書,移官江陵(今屬湖北省),任法曹參軍。元和元年(西元八○六年)六月,韓愈奉召回長安授權知國子博士。後以避讒,請求外調,遂以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洛陽。次年改為真博士分司。元和四年(西元八○九年)六月,韓愈改授刑部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兼判祠部。他根據六典,把東都寺觀的管理權從宦官手中收歸祠部,並懲辦誅殺了一批不法僧尼、道士,這就大大得罪了宦官們,遭到他們的激烈攻擊。元和五年冬,韓愈改任河南縣令(縣治仍在洛陽)。在河南令任上,他又敢於對藩鎮在東都私邸的犯禁軍士依法處置。元和六年(西元八一一年),韓愈入朝為尚書職方員外郎,次年二月由於為華陰令柳澗辯罪,復左遷為國子博士。元和八年三月由於宰相認為他「學識精博,文力雄健」,被擢升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他修撰的《順宗實錄》,記禁中事頗為切直,因而為宦官不滿,屢遭刪削。元和十年(西元八一五年)十二月,韓愈轉吏部考功郎中、知制誥,後又遷中書舍人。當時藩鎮跋扈已極,鎮州節度使王承宗曾遣人刺死宰相武元衡,刺傷御史中丞裴度,「是日京城大駭」。而淮西吳元濟又反叛,朝廷中對此形成主戰和主和二派。一派以宰相裴度為首,主張採取用兵的政策;一派以宰相李逢吉、韋貫之為代表,主張採用安撫的政策。韓愈堅決站在裴度一邊。他曾上奏〈論淮西事宜狀〉,指出淮西「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這一來引起了李逢吉等的不快,就藉口裴均父子事件,將韓愈由中書舍人改為太子右庶子,又一次受到降級處分。元和十二年八月,唐憲宗決定對吳元濟用兵,乃命裴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裴度則奏請韓愈為行軍司馬。十月,李愬雪夜入蔡州,生擒吳元濟,淮西叛亂始告平息。鎮州節度使王承宗也大恐,上書請求歸服。這一戰打擊了藩鎮的囂張氣焰。韓愈因功遷刑部侍郎。他曾奉詔撰〈平淮西碑〉,由於多敘裴度事,為李愬妻所訴,詔令磨去,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刻石。元和十四年(西元八一九年)正月,唐憲宗派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宮中,供奉三日後送寺,從而在王公士庶中掀起一片佞佛的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論佛骨表〉,竟說歷代信佛的帝王大都「運祚不長」,要求將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憲宗大怒,要處韓愈以極刑。幸而裴度、崔群及國戚貴人為他說情,方貶為潮州刺史。同年十月,因大赦被量移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他在潮州和袁州任內,都頗有政績。穆宗即位後,於元和十五年九月,韓愈奉詔調為國子祭酒。他對主管的國子監進行了整頓,使國子監的面貌有所改觀。長慶元年(西元八二一年)七月,韓愈轉任兵部侍郎。時鎮州兵亂,殺死節度使田弘正,立王廷湊,朝廷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率兵進討。結果,牛元翼被鎮州兵包圍,形勢緊張。翌年二月,穆宗命韓愈前往宣撫。韓愈憑著過人的膽識,面折強橫,曉以利害,使王廷湊解除深州之圍。九月,韓愈轉任吏部侍郎。長慶三年(西元八二三年)六月,韓愈轉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向來複雜難理,韓愈到任執法公正,不避權貴,懲治了一批驕兵巨猾,社會秩序大為改善。後來由於宰相李逢吉的挑撥,韓愈與御史中丞李紳不協,十月,調任兵部侍郎,後又改任吏部侍郎。長慶四年正月,敬宗即位,仍任吏部侍郎不變,故後人亦稱他韓吏部。韓愈晚年官高俸厚,潤筆豐富,所以生活優裕。長慶四年(西元八二四年)五月,他生病告假,八月告假滿百日,免去吏部侍郎。十二月二日卒於長安靖安里第,終年五十七歲。朝廷贈他禮部尚書,諡號曰文,故後人常尊稱他為韓文公。
韓愈的文學主張
魏晉以後,文章漸趨駢儷化,這類作品全篇以儷句為主,講究對仗和聲律。唐代科舉取士也規定用駢體文,因而駢體文更加流行。這種文體雖也出過一些好作品,但對作者才情的發揮無疑有很大的束縛作用。武后時陳子昂開始革新文體。開元、天寶以後,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和柳冕等人相繼竭力宣傳為文必須尊儒、宗經、載道,取法三代兩漢,有助社會教化等。待到韓愈、柳宗元,更是大力反對駢文,提倡古文(指先秦兩漢時通行的散體文),終於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文學革新運動古文運動。韓愈特別強調修辭為了明道,「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答陳生書〉)而「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送陳秀才彤序〉)「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爭臣論〉)這就是說他要提倡古道古學,所以要竭力提倡表現古道古學的古文,在他看來,著文乃是為了明道的。韓愈很重視作家的修養,他在〈答李翊書〉中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他認為作者的德行是根本,言辭文章是德行的外部表現;德行深厚,則文章華實並茂。他還很重視養氣,在〈答李翊書〉中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他還介紹了自己的養氣過程,始而「戛戛乎其難哉」,中而「汩汩然來矣」,最後是「浩乎其沛然矣」。氣,就是作文之氣,由修養而致,修養到家則氣盛,氣盛則發為文章,無施不可了。在學習古文的方法上,韓愈提出既要師古,又要注意創新。他說自己開始學習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答李翊書〉),他尤其重視西漢的文章,特別推重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這一方面他和那些固守宗經者不同,表現出評價古代文學的獨特眼光。但是他又強調對古人之文要「師其意,不師其辭。」(〈答劉正夫書〉)他十分注意創新,反對摹擬,他說:「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答李翊書〉)在〈樊紹述墓誌銘〉中說:「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稱讚樊紹述的文章「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
韓愈散文的藝術特色
韓愈提倡寫古文,其實他所寫的文章並不是先秦兩漢通行的那種文體,而是一種吸收了古代文學滋養而加以創造的一種新體散文。他的文章無論是論說,是記敘,還是抒情,都多姿多采,富於藝術特色。氣勢充沛,雄健奔放,是韓文的一大特色。如〈進學解〉,文章次第展開,步步緊扣,抑揚頓挫,辭約義豐。文中用典相當自然。他甚至還倣傚騷賦體裁隔句押韻,但不刻意追求,好似信手拈來。因而全文酣暢淋漓,豪放灑脫。皇甫湜、蘇洵和茅坤曾以奔騰不息的長江浪濤和瞬息萬變的迅雷閃電,來比喻韓文的氣勢,是具體而貼切的。議論縱橫,說理透闢,也是韓文的一大特色。他的許多論辯性文章,論點很鮮明,圍繞著論點廣徵博引,多方論證,邏輯推理嚴密,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如〈諱辯〉、〈論佛骨表〉等文都是代表性的作品。呂大防評韓文說:「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健,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韓吏部文公集年譜》跋尾)用銳、健、嚴三字恰切地概括了韓愈論說文的發展過程。韓文取譬工巧,向為人所稱道。他學習了先秦諸子大量使用比喻、寓言的技法,在〈送石處士序〉中一連使用五個比喻,準確勾勒出主人公的形象。在〈雜說〉、〈毛穎傳〉、〈送窮文〉等作中虛構了「龍」、「千里馬」、「毛穎」、「窮鬼」等物和人,用龍、馬象徵聖君和懷才不遇之士,「毛穎」代表有功被棄之人,「窮鬼」則映有作者自己的影子,貼切而生動,深入而淺出,在詼諧中寓有莊嚴,遊戲裡語含酸楚,頗發人深思。韓愈文章感情色彩非常明顯。這點,尤其可在一些祭文和送別的序文中看出。如〈祭十二郎文〉,如與亡者對語,瑣瑣絮絮,令人不厭其煩,真切感人之至。還有一些送知交遠行的序,或勸勉,或諷諭,感情寄寓很深,讀來令人難忘。韓愈在駕馭語言上表現出高超的技巧。他善於從口語中提煉語言,也善於借鑑古人有生命力的語言,他把口語、古語、僻語、奇語熔於一爐之中,因而他的文章的語言極其凝煉、精粹,極富表現力。他的一些生動的語句,常被後人提煉為成語,如「不平則鳴」、「駕輕就熟」就出於〈送孟東野序〉、〈送石處士序〉等文中,這類例子舉不勝舉。他還善用虛字,利用虛字,使文章的語氣節奏更為靈活多變,酣暢淋漓。如〈祭十二郎文〉中寫到聽說老成之死內心感受一段,前人指出:「僅三十句,凡句尾連用『邪』字者三,連用『乎』字者三,連用『也』字者四,連用『矣』字者七,幾於句句用助辭矣。而反覆出沒,如怒濤驚湍,變化不測,非妙於文章者,安能及此!」(宋費袞《梁谿漫志》)韓愈雖反對駢文,但他也注意吸收駢文的技巧來為己所用。他特別善於使用對偶和排比的手法,他的不少文章駢散間行,造成一種特殊的瀏亮頓挫而富於辭采的格調。
韓愈在中國散文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韓愈由於其鮮明的文學主張、傑出的藝術成就和對後學的培植獎掖,因而在當時文壇上處於極高的地位,和他同時代的劉禹錫就稱他「為文章盟主」,說他「手持文柄,高視寰海」,「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祭韓吏部文〉)。他和柳宗元等大力倡導的古文,沉重地打擊了居於統治地位的駢文,開創了中國散文的新傳統,所以蘇軾推崇他「文起八代之衰」(〈祭韓吏部文〉)。古文的勃興,使文體相對地得到了自由,這就促進了同時代傳奇小說的發展。韓柳古文作品還影響到晚唐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的創作,他們所作諷刺小品正是韓柳散文的一個發展。但是,從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古文運動實際趨向衰落,駢文恢復了統治地位。到了北宋初期,柳開、王禹偁、姚鉉、穆脩等,重又標榜韓柳古文,反對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風;到了中葉,在新的現實條件下,以歐陽修為首,再一次掀起了古文運動。在文學主張上歐陽修與韓愈一脈相承,他說:「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答吳充秀才書〉)同時他還主張文章「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與黃校書論文書〉)。由於他主持科舉,有很大的政治權力,再加上他與曾、王、三蘇等人在古文創作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因而古文運動終於取得了勝利,韓柳古文遂成新傳統。明代唐順之、歸有光等的古文和清代桐城派的古文,也都是以韓、柳為首的唐宋古文新傳統的直接繼承和發展。這個新傳統支配中國文壇共達一千多年。
韓集的流傳
韓愈死後,他的作品是由他的女婿兼門人李漢編纂成集,命名為《昌黎先生集》。據李漢說,他「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共輯得詩、賦、文共七百一十六篇,連同目錄合為四十一卷;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見李漢〈昌黎先生集序〉)。在這以後,韓集在唐宋間出現了許多傳本,並且漸漸還把集外逸文佚詩匯集附錄。在流傳過程中,韓集中字句的缺墜訛誤之處極多,因而到南宋淳熙年間方崧卿乃匯集多種刻本和十七個碑本,對韓集作了一番認真的校勘考訂工作,寫下《韓集舉正》十卷。慶元年間,著名學者朱熹,在方崧卿《韓集舉正》基礎上,進一步作了《韓文考異》十卷,使對韓集的校訂更進了一步。後來王伯大把《考異》散入韓集正文之中,並加了一些音釋,編為《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集傳一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於是世間大都倣照此本翻刻,宋末、元、明、清以後,各種韓集刻本大多數都是此本的後裔。韓昌黎注本影響最大的是宋魏仲舉《新刊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這是個集注性質的注本,所謂「五百家」實是個誇大的說法,而且一些注也是互相牴觸矛盾的,但是這部書保存了大量今已罕見的宋人注說和豐富的資料,為研究者提供了可貴的線索。另一個注本為廖瑩中的世綵堂注《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書成於宋度宗咸淳年間,此書是在《五百家註》基礎上編撰而成的,原文以朱熹《韓文考異》為準,注解則酌取魏本而參以己意,自成一家。其後韓詩注解尚有多家,韓文則以近代桐城名家馬其昶的《韓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西元一九五七年)最為精當。本書正文即依據《韓昌黎文集校注》,選目是在參考了歷代多種重要選本及歷代主要評論而確定下來的。保存了韓集的絕大部分篇章,僅刪去少數歌功頌德、官場應酬之作,違心失實之文及平淡枯槁之篇,碑與墓誌寫同一人者,擇取其一。本書的選目及雜著、書、啟、序之注譯由周啟成承擔,哀辭、祭文、碑誌、表狀、賦等之注譯則由周維德承擔。錯誤不足之處,敬祈讀者指正。
目次
下 冊
賦
感二鳥賦
復志賦
閔己賦
祭 文
祭鄭夫人文
祭田橫墓文
歐陽生哀辭
題哀辭後
祭穆員外文
獨孤申叔哀辭
祭十二郎文
祭郴州李使君文
祭薛助教文
祭房君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祭河南張員外文
祭鱷魚文
潮州祭神文五首
袁州祭神文三首
祭柳子厚文
祭湘君夫人文
祭張給事文
祭竇司業文
祭侯主簿文
祭馬僕射文
祭女挐女文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碑 誌
李元賓墓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崔評事墓銘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施先生墓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唐故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襄陽盧丞墓誌銘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烏氏廟碑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衢州徐偃王廟碑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袁氏先廟碑
曹成王碑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平淮西碑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唐故相權公墓碑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柳子厚墓誌銘
南海神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
韓滂墓誌銘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黃陵廟碑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柳州羅池廟碑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女挐壙銘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表 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
太傅董公行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復讎狀
為裴相公讓官表
論淮西事宜狀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順宗實錄
李 實
宮 市
五坊小兒
陽 城
附 錄
韓愈簡譜
評論 新增評論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