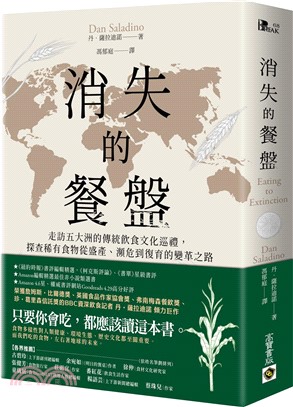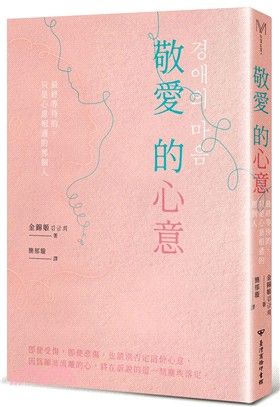再享89折,單本省下33元
商品簡介
為了生存,人們通常是健忘的,
但歷史應該被如實記錄下來。
恐懼不是生存的方式……
死亡不過是生命的一個階段罷了,
我們沒有什麼值得恐懼的。
美國國家書卷獎得主哈金最新長篇小說。
繼《等待》後最受注目的長篇小說。
中國版《辛德勒的名單》!
故事以1937年南京大屠殺為背景,描述時任金陵女子學院校長的美籍傳教士明妮.魏特林,在日軍侵犯南京之際,以自己美國公民身分留守當地,保衛避居在校內超過一萬名無助的中國婦孺。本書描述明妮當時如何與日軍斡旋攻防的經歷,及至回到美國,明妮依舊鎮日為大屠殺期間,無力保護而犧牲的生靈哀悼……
哈金以近乎新聞報導的方式,描寫戰爭的暴行,素樸的文字傳達出更深沉的力量。明妮.魏特林是真實人物,小說中她以基督教徒的身分為上帝服侍。然而就像所有偉大的英雄一樣,明妮竭心盡力,雖然受眾人愛戴,卻也不免落人口實、遭人非議,使她最終因自己的無能為力而精神崩潰,走上絕路。哈金描寫人性的功力在此又可見一斑,使本書既有史詩般記錄歷史的宏大格局,又有小說刻畫人物的細膩之處。
作者簡介
哈金
本名金雪飛,1956年出生於中國遼寧省。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服役五年。在校主攻英美文學,1982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英語系,1984年獲山東大學英美文學碩士。1985年,赴美留學,並於1992年獲布蘭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博士學位。現任教於美國波士頓大學。
著有三本詩集:《於無聲處》(Between Silence)、《面對陰影》(Facing Shadows)和《殘骸》(Wreckage);另外有四本短篇小說集:《光天化日》、《新郎》、《好兵》,和《落地》;六部長篇小說:《池塘》、《等待》、《戰廢品》、《瘋狂》、《自由生活》、《南京安魂曲》。
短篇小說集《好兵》獲得1997年「美國筆會/海明威獎」。
長篇小說《等待》獲得了1999年美國「國家書卷獎」和2000年「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為第一位同時獲此兩項美國文學獎的中國作家。
《新郎》一書獲得兩獎項:亞裔美國文學獎,及 The Townsend Prize 小說獎。《等待》一書則已譯成二十多國語言。
《戰廢品》一書入選2004年《紐約時報》十大好書。
《自由生活》為2007年33萬字長篇小說,是作者第一次將故事背景搬離中國,直視美國的作品。
譯者簡介
季思聰
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1989年赴美留學,先後獲教育學碩士和圖書館學碩士,現在美國新澤西州某公立圖書館任職。著有《魂不守舍》,與他人合著《一家之言》、《格林斯潘傳》等書,翻譯出版有長篇小說《戰廢品》(哈金英文原著,原著獲美國筆會/福克納獎)和《自由生活》(哈金英文原著)。
名人/編輯推薦
「安魂曲是必要的證詞……哈金的忠實讀者會覺察到一種直率-- 實際上更加大膽,直視上個世紀黑暗的中心。收藏優秀文學的館室都須擁有。」-《圖書館雜誌》,星級書評
「哈金以近乎報導的文體來描述恐怖的行為,給了有關暴力和匱乏的紀事一種悲慟的真實感……」--《出版人週刊》
「哈金繼續一絲不苟地挖掘埋沒了的中國經驗……用驚心的威嚴筆調,哈金堅決地描述了無法解釋的恐怖和神奇的抵抗。」--《書目》雜誌,星級書評
「這位小說家精細的技巧豐富了這部作品……一個實在、坦率的敘述,富有深沉的撞擊力。」--《科克斯書評》,星級書評
序
--哈金,《南京安魂曲》,台灣版自序
目次
序 003
第一部 首都淪陷 009
第二部 慈悲女神 109
第三部 諸種瘋狂 169
第四部 此恨綿綿 237
尾聲 331
作者手記 345
謝詞 349
書摘/試閱
第一部 首都淪陷
本順總算開口說話了。我們聚在飯廳裏,聽那孩子講了整整一晚上。他說:「那天下午,魏德林院長要我把進咱們難民營隨便逮人的情況報告給拉貝先生,我就國去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部。我就要到那兒時,被兩個日本兵攔住,一個用刺刀對著我肚子,另一個把槍戳在我背上。他們把我的紅十字袖章扯下來,朝我臉上打了好幾拳。然後他們把我押到了白雲寺。廟裏邊有個池塘,水裏有不少鯉魚和鱸魚。和尚們早都跑得光光了,就剩兩個老的,已經被他們打死,屍首給扔在廁所裏。日本兵想捉魚,可又沒有網。有個當官的朝池塘裏把手槍子彈打光,也沒打中一條魚。另一個往水裏扔了幾顆手榴彈。轟隆隆一陣巨響之後,鱸魚鯉魚都被震昏了,肚皮朝上地漂在水面上。日本鬼子用刺刀戳著我們四個中國人,命令我們脫掉衣服下水,把魚都撈上來。我不會游泳,怕得要命,也只好跳進池塘去。那水冰冷刺骨,幸好只有齊腰深。我們把所有半死的魚都撈上岸,日本兵用槍托砸魚頭,把魚打死,拿麻繩穿了腮,串成串兒,繫在扁擔上,讓我們給抬到他們兵營去。那些魚都很大,每條至少十二三斤。
「日本兵晚飯吃炸魚,可什麼也不給我們吃。不僅不給吃的,還讓我們赤手去撿他們騎兵留下的馬糞。天快黑時,他們又把我們押到一個彈藥庫去裝卡車。加上已經在那邊的,我們共有十一個中國人在給他們幹活,把子彈箱都搬上卡車。裝完之後,他們又要我和另外三個人跟車去下關。那一帶那麼多房子都被燒了,看得怕人,很多房子的火還在燒著,火苗子劈哩叭啦,燒得呼呼響。一路上的電線杆都起火了,就像一根根大火把似的。沒毀的只剩下揚子旅館和一座教堂了。卡車在一個小斜坡停下,我們又從車上往下卸彈箱。岸邊不遠集中了好大一群人,上千都不止,裏邊有中國士兵,也混著很多老百姓,還有女人和孩子。有幾個人在人群裏舉著白旗,旁邊一棵樹上懸掛著一條白單子。離人群不遠的路堤上,停著三輛坦克,坦克上的炮塔就像倒扣的大盆子,炮口都對著人群。離我們不遠的地方,一些日本兵圍著插在地上的一面戰旗坐成一圈,從一個用稻草蓆子裹著的大桶往外舀出米酒喝著。一個當官的走過來,大吼了幾聲命令,可是機關槍旁邊那些當兵的,你看我我看你,都沒行動。那當官的發火了,一把拔出刀來,用刀背猛剁一個當兵的,啪,啪,啪!然後,他的眼光又落在我們幾個蹲在旁邊的中國苦力身上。他把刀一舉,發出一聲狂吼,衝著我們當中最高的一個撲過來,一刀劈掉了他的腦袋,兩股子鮮血噴向空中足有三尺高,那人一聲都沒來得及哼出來就倒了下去。我們全都跪倒在地,不停地磕頭,求他饒命。我嚇得尿了褲子。
「機關槍旁邊的士兵先是目瞪口呆,接著一挺機關槍先開了槍,然後是另外兩挺。其他地方的機關槍,緊跟著也都響了起來,坦克也跟著開了火。人群炸了窩,連喊帶躥,可是擠得太密,每一顆子彈都能射穿好幾個人。不到十分鐘,他們就全倒下了。一群士兵跑過去,看見沒有斷氣的就用刺刀刺死。我嚇壞了,止不住地發抖和叫喊。旁邊一個工友一把抓住我的頭髮狠命一搖,說,『不要出聲!別把他們引過來。』我才住了聲。
「我們跟著卡車回來,給日本兵搬運他們的戰利品,主要是傢俱。他們並不是什麼都留,把很多東西扔進他們營部前的火堆裏。火堆上,插在鋼條上烤著的有豬有羊,還有分成一塊塊的水牛,火上還燒著幾個滾開著的大鍋,到處飄著烤肉的味道。那天夜裏,他們把我們鎖在一間屋子裏,給了每人一個飯糰和一杯水。後來兩天,他們把我們押到中央大學那一帶,又是給他們搬運戰利品。他們把每一處房子裏值錢的東西搶光之後,就一把火把房子點著燒掉。有個日本兵還帶著撬開保險箱的工具,不過他們一般不用工具,就在保險箱底部鐵皮比較薄的地方安顆手榴彈把它炸開。他們很喜歡手錶和珠寶,所以專找那些東西。有個很年輕的傢伙還搶來一部嬰兒車。我弄不明白他要那個幹什麼用,他年紀輕輕不會有孩子的。
「後來,他們帶了我們六個人出了城,向東到了句容,我們在那邊幹了一天,運炮彈和彈殼。到了晚上,他們把我們幾個放了,說我們可以回家了。我們已經快累垮了,摸黑往回趕,也走不快,第一天夜裏只走了三十里。一路上,所有的水塘,所有的小河裏都有死屍,人的屍首,動物的屍首,水都變了顏色。渴極了的時候,我們只好喝那些臭水。天哪,我現在還忘不了那些腐爛屍體的惡臭。有的屍體,眼球都暴出眼眶好遠,可能是因為他們身體裏有氣膨脹。我們還看見一個女人的屍體,一隻腳沒有了,黑色的血水還從傷口往外滲著,另一隻腳上穿著小小的花鞋——是個小腳。好些女人下半身光著,日本鬼子強姦完又把她們刺死了。每次經過一堆屍體,我的腿就抖得不聽使喚。
「我們不斷地被日本兵攔住。幸好,放了我們的那個當官的給我們寫了張字條,所以一路上那些哨兵沒有把我們逮起來,放我們回到了南京。有個同伴,拉肚子拉得脫了水,再也走不動了,我們什麼辦法也沒有,只能把他留在路邊,他現在一定沒命了。離他不遠的地方我們看見一個小孩子,也就兩三歲,坐在廢棄的汽車站旁邊,餓得哇哇大哭。我給了他一塊餅,可他還沒來得及吃,四個日本兵走過來,用皮靴在他身上踢來踢去。有一個鬼子掏出傢伙來,對著孩子嘴裏撒尿,聽那孩子哭聲越來越大,那幾個鬼子卻哈哈大笑。我們不敢再呆著看下去,趕快走開了。我想另外三個鬼子也會往孩子嘴裏撒尿的。他們不殺他就是他的運氣了。
「天哪,人命突然之間就變得不值錢了,死屍到處都是,有些屍體的肚子被切開,腸子都流出來,有的被汽油燒得半焦了。鬼子殺了那麼多人,把小河、池塘、水井都弄髒了,連他們自己也找不到乾淨的水喝了。就連他們吃的米飯都發紅了,因為都是用帶血的水煮的。有個日本伙伕給了我們幾碗米飯,我吃完以後,好幾個鐘頭滿嘴血腥味兒。說老實話,我根本沒想到還能活著回來,還能再見到你們。到現在,半夜裏我的心還亂跳呢。」
一邊聽本順講,我一邊把他說的都記下來。
一
「早上好,安玲。」我走近主樓的時候碰上了明妮,她向我問好。主樓是金陵女子學院裏的幾座建築裏最大的一座。我倆接著一起朝吳校長在南山宿舍樓的寓所走去,我們三人已經定好在她那裏吃早飯。十一月底的空氣挺冷冽,我能看見周圍人們嘴邊呼出的白汽。一大群野鴨嘎嘎叫著向北飛去,一雙雙翅膀好像一對對小槳在划動,很快它們就消失在鉛灰色的天空中了。大塊大塊厚重的烏雲,蘊涵著濃濃的雨氣,這也意味著,日本轟炸機今天不會來了,所以,儘管天氣又陰又冷,人們見面卻會打招呼說,「多好的天哪」。一個陰霾天氣,讓所有的人都心情好些。
吳校長在收拾行李,挑出學校要緊的文件好隨身帶走。有幾個教師也在準備離開,可是很多職工無處可去,他們也在忙著,把食物和值錢的東西收藏好。明妮什麼東西也沒收拾。作為學院的教務長,她想留下來。她對我說:「我不怕丟什麼,豁出去了。」
吳博士興致勃勃地在等我們。桌上擺著法式麵包片,一條黃油在小碟裏放著,還有一小瓶果醬和一小罐蛋黃醬。一看到西式早餐,明妮眼睛發亮了,嘆道:「呵,每天早上稀粥就鹽水花生我都吃了幾個星期了。你打哪兒弄來的這些好吃的?」
「蔣夫人昨天送我的,」吳校長答道,一邊用指尖正了正眼鏡。她經常去見第一夫人,因為她們都受過美國教育——蔣夫人讀的是衛斯理學院,吳校長是在密西根大學得到的昆蟲學博士學位。她是蔣夫人當會長的戰時婦女救濟會中的一員,不斷地召集各種大小集會,為國軍和孤兒院等籌集捐款。吳校長年紀不大,已經是名人,她是第一位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中國女性,又是金陵女子學院首屆五位畢業生之一。1928年,我國政府規定,外國人在華創辦的所有大學和學院,都必須由中國公民來擔任校長,於是她接替了丹尼森夫人,當上了金陵女子學院的校長。「請坐吧,咱們邊吃邊談,」吳校長招呼著我們。她身穿一件黑色絲綢衣服,領口那枚銅紐扣很像一個大金幣。雖然將近四十歲了,她看上去還年輕得很,一雙明亮生動的眼睛,顴骨挺高,大概是因為她一直沒嫁人,從來沒有小孩子和家務的負擔吧。
我用暖瓶裏的開水沖了三杯奶粉,遞給吳校長和明妮每人一杯。
「謝謝,」明妮邊說邊在麵包片上薄薄地抹上一層果醬和蛋黃醬,咬了一口。「嗯,真好吃!要是能有加火腿、奶酪和蘑菇的黃油炒蛋就好了。」她的國語略帶口音。「真想吃一頓中西部的豐盛早餐啊。」
「我也是,「吳校長說,「好想吃燻鹹肉。」
我們都笑了。我喝了一口熱奶,味道濃香,有點甜。真想省下來給我那兩歲的外孫帆帆喝。
我們學校在紐約的董事會剛剛來了指示,要吳校長也跟著最近遷往成都的學校一起到西南大後方去,而明妮•魏德林,按照她自己要求的,作為代理校長留守南京。吳校長要我也留在這裏,協助明妮管理學校,我答應了。我們三人需要好好商量一下保護校園的各種計劃。學校保險櫃裏的貴重物品都放進了一個大皮箱,回頭送到美國大使館去。我們擔心這些東西會遭到中國軍隊的搶劫,那些大兵軍紀很差,到了潰敗和急眼的時候,就更是無法無天了。
「我聽說,大使館馬上要撤退到班乃號上去。」明妮說的班乃號是美國的一艘炮艇。
「沒關係,」吳校長蕩了蕩她的奶,喝了一口,「我們的東西交給他們保管會比較安全。」
「咱們的現金藏在哪裏好呢?」我問她。
我們都明白,很快就沒有銀行會開門了,而且會發生全面的物資短缺。吳校長微微一笑,建議我們只留一百元在保險櫃裏,其餘的四千多元,藏在只有明妮和我知道的幾個不同地方。
明妮問我:「丹尼森夫人的銀器也在保險櫃裏嗎?」
「是的,我們把它們放哪兒呢?」我說。
「是很貴重的銀器嗎?」吳校長問。
「我不知道。」我搖搖頭。
「那是她嫁妝的一部分,」明妮回答說,「很精緻的一套,大概值四百元。」
「把它打進箱子裏,」校長說。
明妮簡要地對我們介紹了一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所進行的工作。這個難民救濟會,是由一些留在南京的外國人建立的,他們不顧自己國家大使館的催促,不肯撤離。位於南京市中心的安全區佔地近四平方公里,曾是外國大使館、領事館和一些教會學校最密集的區域,現在這塊地方將變成一個中立區,為非戰鬥人員提供庇護。中國政府支持這些外國人的努力,向他們提供了八萬元現款和45噸大米和麵粉,用以建立難民營。感謝老天,長江流域今年的大米收成很好,所以南京城裏大米充足。不過,車輛卻非常短缺,經常被軍隊隨便徵用,中立區雖有配給的糧食,卻沒有足夠的交通工具來運輸。如果不是委員會的干預,一些撤退的部隊還差點將儲存在下關江岸附近的數百噸大米付之一炬。蔣委員長自己也掏出十萬元給委員會,不過到這時剛送來四萬。委員會通過美國大使館向日本當局交涉過,但日本方面沒有直接對中立區做出承諾,只是說,皇軍將「在與其戰事需要不衝突的前提下,儘量尊重安全區的中立」。
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由十五位來自美國和歐洲的人士組成,大多是傳教士,也有一些商人和大學教師。主席是五十五歲的約翰•拉貝,他是德國人,是西門子公司駐南京代表。西門子公司為南京城市建造了全城電話系統,為發電廠維護機器,並為我們的幾家醫院提供了現代化設備。拉貝還辦了一個規模不大的德語學校,他把學校連同他的住宅,一起向難民敞開了大門。委員會裏沒有女性成員,因為很顯然她們可能會碰上難以想象的危險,比如直接和日本兵面對面。不過,還是有兩名美國婦女實際上參與了救濟工作,一個就是我面前的明妮•魏德林,另一位是霍莉•桑頓——一個半職的英語播音員。我很喜歡霍莉,她四十歲,是個寡婦,已經入了中國國籍。明妮和霍莉兩人都是約翰•馬吉牧師領導的南京國際紅十字會的成員。有好幾個美國人,既是安全區委員會的成員,又是紅十字會的成員。
聽了明妮介紹的救濟工作情況,還有金陵女子學院的校園將被用來收容婦女兒童難民的前景,吳校長低下了頭。她那一頭短髮剪得比平頭長不了多少,眼睛黯淡了,漸漸湧上淚水。她沈默了一會兒,對明妮說:「你覺得怎麼合適、怎麼必要,就怎麼做吧。我忍不住想起十年前,外國人在這裏的遭遇。現在,倒只有一群外國人可以幫助難民。真令人羞恥啊。」
吳校長想起的是中國軍隊對外國人的暴行。一九二七年三月,幾支中國軍隊對城裏的外國人大肆施暴,搶劫、放火,摧毀他們的學校和住宅。都說是共產黨煽動的,好嫁禍當時率領北伐軍的蔣介石,破壞他和西方的關係。有些士兵毆打外國人,還強暴婦女。有一小隊人闖進金陵學院,從生物實驗室搶走了幾臺顯微鏡,還搶了教員的私人用品。在南京大學,有六個外國人被槍殺。我還記得有幾個傳教士怎麼樣爬下城牆,投奔美國和英國的戰艦。那些戰艦向城裏開了炮,來阻擊中國軍隊接近一群被困在山頭上的外國人。所有的西方人都先後逃離了南京,明妮和我們學校其它外國教員逃到青島,不敢再回來教書。當時覺得他們來華的使命就此終結了,可是六個月以後,他們中間有些人又返回來了。明妮是第一個回來的,她要繼續完成一座宿舍樓和玫瑰園的修建。
二
明妮到美國大使館送皮箱去了。瑟爾•貝德士騎著自行車到我們學校來檢查救濟工作的準備情況,順便收集一下學校附近一些婦女們製作好的紅十字會旗子。他身著華達呢大衣,腳登一雙勞動靴,使他看上去帶幾分英氣。他身高一.七五米,體型偏瘦,是個近視眼。他告訴我,安全區內計劃一共設立十九個難民營,不過,除了我們學校,只有南京大學的宿舍樓是專門接收婦女和兒童的難民營。瑟爾還捎來了一些信件和一捆《字林西報》,這是我們學校教員訂閱的一份英國報紙。自從日本人八月裏進攻上海,報紙就總是晚到兩個星期,一來就是一捆。
瑟爾是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他們學校大多數教員已經跟著國民政府撤到內地去了。他在耶魯大學拿到中國歷史的博士學位,會說漢語、日語和俄語。我丈夫在戰前曾經和他共過事,所以我認識他已經好幾年了,很喜歡他這個人。我陪他察看了幾個大教室,裏邊的桌椅都搬走了,騰出地方來準備接收難民。我告訴他,按照一個人佔地一.五平方米的估計,我們最多可以接收兩千七百人,不過,我們覺得只該接收兩千人,可以比較從容。他微笑著點點頭,棱角分明的臉上顯出些微皺紋。他在筆記本上飛快記下數字,派克水筆在他有勁的手中一閃一閃的。我們走過院子時,他頭歪向院子當中在地上鋪展開來的一面九米多長的美國國旗,那是給天上的轟炸機看的,告訴它們這裏是美國的財產。
「這辦法不錯呀,」他說。
「哎呀,花了我們一個多月才做好的,」我告訴他。「這種時候,找到一個能幹的裁縫可不容易。那個裁縫一開始把星星放到右上角去了,費了好大勁才把它們都換到左邊去。」
瑟爾咯咯地笑了。他咂了咂舌頭,「你們這片小天地多麼漂亮啊。」金陵學院以它美麗的校園著稱,種植了各種各樣的林木花草,每年秋季,這裏都會舉辦花展,可是今年沒有花展了。
突然,防空警報響了起來,好像一大群人在哭喪。人們開始向防空洞跑去。「咱們去那裏躲躲吧,」我指著小教堂對他說,那座樓裏有個地下室。
瑟爾搖搖頭。「我等看見炸彈掉下來再躲也不遲。」
我拉住他的袖子說:「快走吧,就當檢查工作了。你得看看我們的防空洞,對不對?」
「這是假警報。」
近來假警報太多了,所以人們都不把第一級警報當回事了。不過,就在這時,第二級警報響起來了——更短促,更急速,這是告訴你,必須躲進地下。更多的人跑起來。瑟爾和我剛剛跨出學校的前門,就聽見我們東邊兩三里遠的住宅區一帶響起了爆炸聲,像是在西華門附近,那是滿族人的老城,現在是貧民區。沖天的白煙昇起來,高射炮這時開火了,炮彈像一團團黑花朵在空中綻放。
「咱們就去那裏吧,」我邊說邊帶著瑟爾走向最近的一個防空洞。一陣高射炮彈的碎片刷刷地從樹梢間落下來,砸到屋頂上,也有一些落在我們腳前,揚起一股塵土。
防空洞裏,一些婦女懷裏抱著嬰兒,身邊坐著大一點兒的孩子。一位母親喝叱著她的幾個孩子,不許他們在洞口朝外看。角落裏,兩位老人坐在馬札上,伴著豆油燈,對著一副棋盤廝殺正酣,仿佛他們常在這裏消磨時光,全神貫注地對弈已經好長時間了。空氣中彌漫著一股像炸魚的味道。瑟爾和我坐下來後,我對他說起坐在周圍的那些婦女,「現在她們對空襲都習以為常了。剛開始的時候,她們連大氣都不敢出,說是飛機上有一種儀器,能探聽到地上說話的聲音。」
瑟爾哈哈大笑。笑過之後,他說,「這麼轟炸住宅區,真是太可惡了。我要向日本大使館提交抗議。」
「那些飛行員轟炸平民一定挺開心,」我說,「混帳東西,他們應該明白這是犯罪!」
「如果日本戰敗,我相信他們中有的人會被送上法庭的。」
我不知道這場戰爭會是什麼結果,沒再說話。我轉身去看一個正在用錐子和麻繩納鞋底的老太婆,她的食指尖上裹著膠布。
沒一會兒,瑟爾又說:「這裏只能看見老人、孩子和婦女。」
我沒吱聲,知道有些外國人對中國人表示懷疑,尤其對我們中間那些社會精英和受過教育的人,他們大多數都走掉了。可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隨著國民政府逃往西南和內地?為什麼他們沒有留下來,和軍人一起作戰?就算不上前線,至少幹些事給軍隊鼓鼓士氣,或者照顧照顧傷病員也好啊。怎麼這仗好像只是靠那些窮人和弱者在打?對於這種質疑,我丈夫和我都無法爭辯。這些天來,我腦海里怎麼也擺脫不了那些在城裏看到的新兵,很多人還是十幾歲的孩子,一看就是鄉下來的,面有菜色,目不識丁,照料自己都不行。送他們上前線,除了當炮灰送死沒有別的。
警報解除之後,瑟爾騎車離去了,我便朝辦公樓走去。快到樓前的時候,看見明妮正在大門前跟大劉說話。大劉身高一米九,高大得好像一名很久前就退役了的籃球隊員。我走上前去和他們打招呼。
大劉正在請求明妮允許他們一家人搬進我們校園。明妮從去年春季以來一直在跟他學古文,對他十分信任,所以她答應了他的請求。我很高興,因為大劉是個頭腦清醒、富於機智的人,又懂英文,給外國人教授中文已經好些年了。有他在旁邊,是件很不錯的事。
「謝謝你,魏德林小姐,」大劉聲音洪亮地說道。
「叫我明妮,」她提醒他說。
「明妮,」他一臉嚴肅地重複。
我們都笑了。這邊很多人管明妮叫「魏德林院長」,這一稱謂似乎讓她不大自在,當然,不熟的人這麼稱呼,她也不會反對。
這時明妮想起一個主意,她眨著褐色的大眼睛,對大劉說:「乾脆,你替我們工作吧。我們的秘書孔先生回鄉下老家了,現在我們有幾百封信都沒回呢。」
「你要僱我?」大劉問道。
「沒錯,做我們的中文秘書。」
「此話當真?」
「她現在是校長啦,」我告訴他。
「對啦,我任命你啦。」我從明妮的聲調裏聽到一種激動。顯然,她對自己的新角色十分驕傲。
「好極了!我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大劉粗獷的面孔頓時發光。
大劉一直在找工作,有個十幾歲的女兒和一個更小的兒子需要他養活呢。他下個星期一就開始上班,薪水暫定每月二十五元。和大家相比,這可真算不少了,因為我們所有人的薪水都削減了百分之六十,明妮現在每個月五十元,我是三十元。她建議他們全家住到東院去,那是校園東南角的一個四合院,明妮十年前監工修建的,原來是為傭人設計的住房,由於建造得太好,以致有些中國教員抱怨說,那裏比他們自己的房子都高級。我們家也住在東院,這樣一來,劉家就成了我們的鄰居。
第二天,日軍猛烈的炮火一刻不停地轟擊著南京城。校園裏,我們人人心神不安,但還是繼續幹著活兒。北校園的兩座宿舍樓中間,搭建起一些竹蓆窩棚,我們讓小販在窩棚裏向難民賣吃的,蒸米飯五分錢一碗,不帶芝麻的燒餅,一個也是五分錢,不過,每人一次限買兩個或兩碗,不得買雙份。當地的紅十字會已經答應在這裏開設粥場,只是到現在還沒設立起來。有些難民既沒食物,身上又沒錢,就只好挨餓了。到十二月十一日中午為止,我們已經接納了大約兩千難民,總算還能把他們都安排住下。
我正在用木頭水舀子給疲憊不堪的新來的難民分發熱水,約翰•馬吉牧師來了。我讓手下的一個人替我接著分發,自己起身去迎他。「我剛從城裏來。」他對明妮和我說:「那邊情況可怕極了,福昌飯店和首都劇場門前躺了幾十具屍體。有家茶館被打中了,胳臂腿被炸得滿天飛,掛在電線上和樹梢上。日本人隨時會開進城來。」
「你是說,中國軍隊放棄抵抗了?」明妮一下子憤怒了,兩眼噴火。
「我說不準,」馬吉回答,「我在安全區裏看到些軍人,在搶商店裏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呢。」
「他們就這麼散夥了?」我也火了,想起了他們以「保衛南京城」為名義,在郊區燒毀的那些農舍。
「現在還很難說,」馬吉回答說:「還在作戰的也有。」
他告訴我們,下關一大片地區都在火海之中。南京城最漂亮的建築、斥資兩百萬元建造的交通部大樓,連同它那富麗堂皇的禮儀廳,都被付之一炬。凡是帶不走的,中國軍隊一律將之毀掉,把很多房屋都燒了,包括蔣委員長的夏宮,軍事學院,現代生化戰爭學校,農業研究實驗室,鐵道部,警官培訓學校——全都燒了。也可能這是他們發泄憤怒的方式吧,因為他們現在才知道,蔣介石和所有當官的都撤走了。
約翰•馬吉正說著,一個戴著一頂護耳毛氈帽、拄著手杖的駝背男人走過來,另一隻手裏牽著一個小女孩。
「能收我們進來嗎?」那人聲音微弱地問道。
「這裏只接收婦女和孩子。」明妮說。
那男人微笑了,兩眼一亮。他站直了身子,用沙啞的女聲說:「我是女人,請看。」她摘掉帽子,從口袋裏扯出一條印花大手帕,把臉上的塵土和煙灰擦去。原來她相當年輕,二十多歲,瘦削的臉上仍留著一道一道的黑灰。不過她的脖子現在伸長了,柔軟的後背顯出她的楊柳腰。
我們讓她和小女孩進來。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
「燕英,」她說:「這是我小妹妹燕萍。」她伸出胳臂摟住女孩。
燕英告訴我們:「我們鎮子被日本鬼子燒了,他們抓走了好多女人和男人。我家鄰居龔阿姨和她的兒媳在家裏被折磨死了。我爹叫我們趕快跑,我弟弟不敢在大白天裏出來,所以我沒帶他,自己就和妹妹來了。」
明妮把她們送到霍莉管理的中心樓。這時喬治•費奇來了,他穿了件燈芯絨大衣,香煙插在個小煙嘴兒上,看上去很象支彎曲的小煙斗。他一臉倦容,頭髮稀疏,琥珀色的瞳仁濕濕的。費奇是美國基督教青年會南京分會的負責人,也是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行政主任;他出生在蘇州,蘇州話講得地道,以致有人把他當成了維吾爾人。他告訴我們,有好幾百名中國士兵來到南京大學醫院難民營,要投降,很多人扔下了武器,請求讓他們進入難民營;不然的話他們就要破門衝進來。他可以斷定,更多的士兵,會有上千吧,都會進入安全區來請求保護,這樣一來,國際委員會在與日本戰勝者打交道時,就陷入很大的麻煩。馬吉和費奇一刻也沒敢耽誤,就一起動身去醫院了。從後邊看,瘦弱的費奇今天似乎背更駝了,馬吉則強壯結實,虎背熊腰。明妮對我說:「我希望中國士兵別來金陵學院避難。」
「反正我們也沒地方給他們了。」我說。
那天晚上,校園裏的三座樓都已經滿了,其它幾座還在接收著新難民。最後保留的藝術樓,剛剛也開放了。紅十字會還沒有把粥場建立起來。我們兩天以前建起來的臨時廚房,連一小半人的肚子都沒法應付。明妮提議,由我們自己來開設一個粥場,可是,粥場的工作人員,還有大部分的定額的分配,都是當地紅十字會的人掌控,他們堅持說,粥站要由他們來開設。很顯然,這裏邊有個賺錢的問題。他們在這種局面下還在考慮贏利,讓明妮大為惱火,派了路海再去找紅十字會總部,申請辦粥場的許可。
第二天早上,四週安靜得好像仗已經打完了。我們感到日本人也許已經攻破城門,控制了南京城。有傳言說,日本攻城部隊爬上城牆,用炸藥炸開了幾個口子,中國守軍潰敗,日軍高喊著「天皇萬歲」,揮舞著戰旗蜂擁而入,卻幾乎未遇任何抵抗。大劉說,他看見愛惠中學一帶的街道上到處是屍體,大多是老百姓還有孩子,除此之外,鬧市區已經成了死城。
整整一上午,明妮不停地抓撓她的後脖頸,覺得渾身又癢又粘。她和衣而臥已經連續好幾天了,自從五天前到車站看望傷兵回來,就再沒顧上沖過一次澡。她都無法連續睡上兩個小時,就會被槍聲吵醒,或是不得不起身去親自處理一些緊急情況。什麼時候實在太累,不歇一下不行了,她就打個盹,所幸她總是可以一沾枕頭就睡著。要是今天仗真打完了,她說要好好泡個熱水澡,再一覺睡上十個小時。
我是個覺很輕的人,夜裏一多半時候都是在學校門房和不同的樓裏值班。謝天謝地,我身體很好,一天睡三四個小時就可以應付,但就算這樣,我還是感到睡眠不足。有時候,累得沒法繼續幹下去,我就在體育樓裏找間貯藏室,在裏邊小眯一會兒。這些天來,我頭都是木的,眼球疼痛,步履不穩,可我必須在校園裏巡查,必須處理太多的事情。我丈夫和女兒開玩笑說,我已經成了「流浪漢」了,不過,家裏沒我他們還可以應付。
快到傍晚,明妮想到江邊去看看情況。大劉要陪她去,可她對他說:「不用,你還是留在家裏吧。」霍莉也要跟她一起去,明妮卻說:「你應該守在這裏,萬一有什麼緊急情況你好處理。安玲跟我去就行了,哪國部隊也不會傷害兩個老女人的。」其實,我五十歲,比明妮還小一歲,可她看上去也就是四十出頭,而我都有不少灰頭髮了,幸好體型還沒發胖。於是我和她一起坐進吉普,那是馬吉牧師給我們的一輛舊車。明妮開起車來,讓我們每個人都驚訝不已,因為她似乎笨手笨腳,不是霍莉那類對開車十分嫻熟的女人。
「希望這車不會半道拋錨。」明妮說。確實,這輛車的響動得太厲害,像是不大牢靠。
「我要是會開車就好了。」我說。
「等戰爭結束了,我就教你學開車。」
「但願到那時候我還沒老得學不成。」
「什麼話,別那麼悲觀嘛。」
「好吧,希望這話能實現。」
我們先到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部去了一下,看到約翰•拉貝、瑟爾•貝德士和愛德華•施佩林都在。他們一臉憂鬱,告訴我們說,中國軍隊已經開始撤退了。德國保險公司經紀人施佩林,其實在三個小時前剛從日本人的前線回來,他受中國軍隊委託去交涉,希望就停火進行談判。但是,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宮將軍,拒絕了他的建議,說要給中國一個血的教訓,打算「血洗南京」,好讓中國人看看,蔣介石是多麼無能的領袖。
拉貝告訴我們的情況更加令人震驚。昨天,唐將軍接到蔣委員長的命令,要他立刻組織撤退。可是唐的部隊激戰正酣,把他們撤出來已經不可能了。如果他執行這一命令,就將意味著拋棄他的部隊。他跟委員長的總部聯絡,探探虛實,看蔣會不會收回成命;蔣卻決心已定,再次電告唐司令,指令他必須實施撤退,保存部隊,即刻跨過長江。唐甚至無法把命令送達到所有部隊,有幾個師不僅失去通訊設備,而且官兵來自各邊遠地區,諸如廣東、四川,還有貴州,彼此方言不通,互相交流都很困難,以至無法傳遞命令。更糟糕的是,那天早上,日本艦隊已經駛進長江,正向上游而來,我們沒有戰艦抗擊敵人的海軍,所以中國軍隊的撤退路線很快就會被全部切斷。唐將軍萬般無奈,緊急求助於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懇求外國人代表中國出面干預,實現三天的停火。愛德華•施佩林今天過午時分出城,向西跋涉,到日本前沿陣地,揮著一塊白單子,白旗上用日語寫著「休戰,和平!」是那個黃眼睛的年輕俄國人寇拉寫上去的。施佩林滾圓的肩膀上擔負著我們首都的重量,希望避免更多的流血。
親王朝香宮將軍長著蒜頭鼻子,留著八字鬍,讓他看上去像是兔唇。他接見了施佩林,一口啐在他臉上,又抽出刀來厲聲喊道:「去告訴中國人,是他們自己找死。現在才僱來你這麼個和平掮客,晚啦!他們真的想要和平,就先把唐生智交出來。」
「請把我們的請求轉告松井將軍。」施佩林再次懇求。
「我是這裏的指揮官。告訴唐生智,我們要將南京城殺個雞狗不留!」
施佩林只好趕回來,如實向唐將軍轉告。這位使者急得把腳脖子都扭傷了,走路只好拄著根棍子。現在,部分守城部隊一定已經得到了撤退的命令,開始向城外撤退了,但是很多部隊卻還蒙在鼓裏,還在盲目地作戰,全不知兩翼已經空虛,注定會被殲滅。
聽完拉貝關於停火斡旋失敗的陳述,幾個人好長一陣沈默。我很想哭,但還是克制住,用手遮住了臉,幾乎喘不過氣來。
「兵敗如山倒啊。」瑟爾對明妮說,用了句中國成語。
「蔣介石應該對這場災難負責。」她氣憤地說。
「對,他應該被送上軍事法庭。」瑟爾說。
「問題是,他就是自己法庭上的法官。」拉貝用玩笑的口氣加了一句,擺弄著掛在脖子上的望遠鏡帶子。儘管是在調侃,他的聲音卻很沈重。
瑟爾要動身去一個星期前在外交部設立的臨時醫院了。市政府已經交給國際紅十字會五萬元——瑟爾和明妮都是國際紅十字會的成員——用來建立醫院,可是即使有這筆不小的資金,他們也沒有足夠的人手。瑟爾無法找到醫護人員,不停地抱怨中國醫生全跑光了。到目前為止,留在城裏的只有一個外科醫生——羅伯特•威爾森,他剛從哈佛醫學院畢業不久,眼下在南京大學醫院裏,忙得不可開交。明妮和我跟著瑟爾一起出門,上了我們的吉普。我倆開上了上海路,向城東北駛去。
我們左轉上了中山路,這條路通向挹江門,出了挹江門可以到達下關碼頭。我們剛轉上來,就被眼前恐怖的場面驚呆了。整個城市都在逃命,人流都朝著江邊湧去。我們經過的每一條街上,到處都是我們的士兵脫下扔掉的軍服。道路兩邊排滿了正在燃燒的車輛,火炮旁邊摞著成箱的炮彈,重機槍還捆在死驢子身上。一群騾子站在那裏,身上馱著高射炮的部件和彈藥,不知所措地動不了窩。一匹帶著馬鞍的雜色馬,對著雲彩高聲嘶叫,彷彿遭到什麼看不見的猛獸的襲擊。大批的士兵向北蜂擁而去,大多數人兩手空空,但有一些人皮帶上還掛著搪瓷飯碗。滿地的鋼盔、步槍、手槍、水壺、捷克式輕機槍、背包、軍刀、手榴彈、大衣、靴子、迫擊炮、火焰噴射器、短把鐵鍬、鎬頭等等。一支黃銅軍號旁邊,放著一隻生豬的腦袋,它的大鼻子朝天,可兩隻耳朵都不見了。我們快到國際俱樂部時,路面上塞滿了翻倒的車輛、三輪摩托車、牲口拉的馬車、電線杆和亂糟糟的電線,弄得車子不可能再往前開了,於是我們決定步行。我們拐向右邊,把車開進德國大使館的院子,徵得脾氣急躁的喬治•羅森的許可,我們把吉普停在他那裏。羅森是政治事務秘書,是留下沒走的三個德國外交官之一。跟他的同事不一樣,羅森是半個猶太人,不能佩戴納粹黨的卍字徽記。
明妮和我徒步向北走去,只想看看我們的部隊是不是還控制著撤退的路線。大都會飯店出現在眼前,已經被濃煙和火焰包圍了。我們經過的那一刻,一隊仍然荷槍實彈的士兵朝我們跑過來。一共九個人,都穿著草鞋,在我們面前停了下來,扔掉步槍,兩手抱在胸前,請求明妮接受他們的投降,好像她也是個佔領者。他們的班長一臉淚花,向明妮懇求道:「大嬸,救救我們吧!」
這一舉動使明妮慌亂不安,我對她說:「他們一定以為所有外國人都有辦法替他們找到避難所。這些當兵的真可憐,被當官的拋棄了。」我一邊說著,眼淚就嘩嘩地流下來。我太傷心了,俯下身去痛哭起來。
明妮拍著我的頭,用中文對那幾個人說:「我們沒有資格接受你們的武器。如果你們想留在城裏,到安全區去吧,你們在那裏可以得到保護。」
那幾個人搖著頭,仿佛被嚇得再也不敢返回那個方向了。他們向後一轉,跑掉了,槍也丟掉不要了。明妮揀起一支步槍,還很新,槍托上印著這樣四個字:「人民血汗」。這些字來自委員長的教誨,刻在國民黨軍隊的很多武器上。明妮兩道濃眉擰成了結,深深嘆息著扔下了槍。
我一邊擦眼淚一邊告訴她:「在我們國家裏,一個農民幹一輩子才能買得起一支步槍。想想他們扔掉的那些裝備——天大的糟蹋啊。」
「是啊。路易斯說,他看見一些嶄新的大炮被丟棄在郊外,一次還沒有放過呢。」
我們繼續向城門走去。看到四週的一切都被摧毀,真讓人難過萬分,大半樓房和平房都被燒毀了,有些還在冒著煙。走過英國大使館之後,遠遠便可以看見挹江門,可我們已經太累,再往前就走不動了,而且我們意識到,想出城門去看看江邊是什麼情況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停下了腳步。從這裏遙望,城門前堵著沙包,架著機關槍,成串的士兵用繩子、消火水管和雲梯,在攀登十五米多高的城牆。逆著煙霧彌漫的落日,可以朦朦朧朧看見城牆頂上,還有兩層的樓閣邊上,都趴滿了人。從人群移動的樣子,我們看得出碼頭一定還在中國部隊手裏。我們轉身返回,朝德國大使館走去。
暮色降臨了,幾隻蝙蝠掠來掠去,像是鬼頭鬼腦的蝴蝶。往回走我們得逆流而行,明妮走在我前邊,一邊推搡一邊喊:「讓我們過去!讓我們過去!」人們都在不顧一切地急於往外逃,遇到我們擋道礙事,就罵起來。突然響起汽車鳴笛聲,身穿便裝的衛兵們揮著盒子槍,大聲吼叫:「閃開道!閃開道!」
那些來不及讓開的人,便被衛兵連推帶搡。只見衛兵身後開過來兩輛長轎車。「看!唐將軍!」明妮對我說,指著坐在第二輛別克後排座位上那個瘦臉男人。將軍垂著腦袋,好像正在打盹。我們注視著這位南京守軍總指揮,這時半塊磚頭打在他的車上,一個聲音大喊道:「王八蛋,我操你祖宗八代!」磚頭只在車窗上留下一個白點兒,衛兵什麼也沒說,瞪了叫罵的那人一眼,就只管往前繼續清道去了。幾分鐘以後,轎車向左轉彎,看不見了。天黑後唐將軍一定有他自己的辦法過江。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