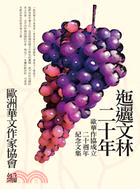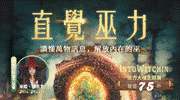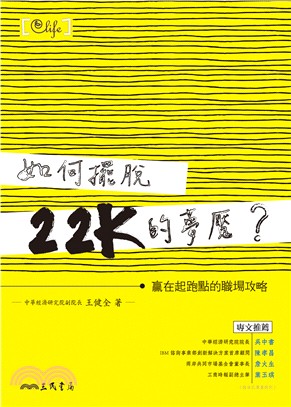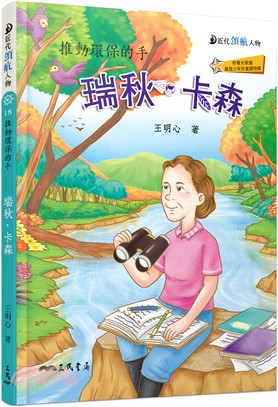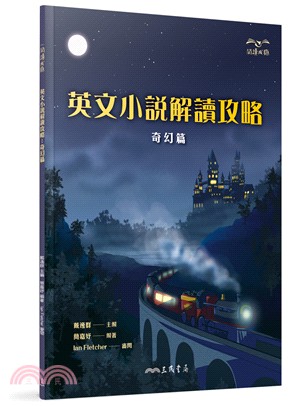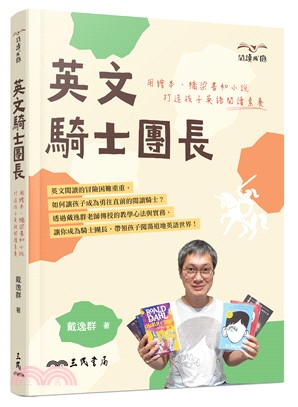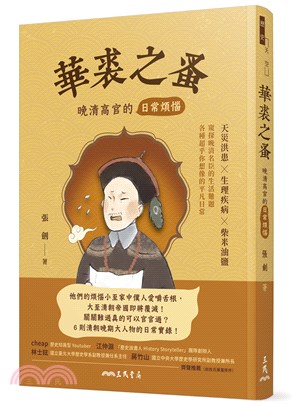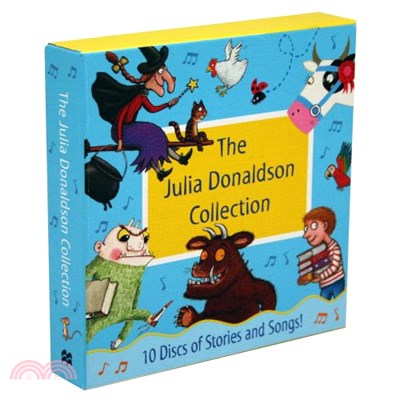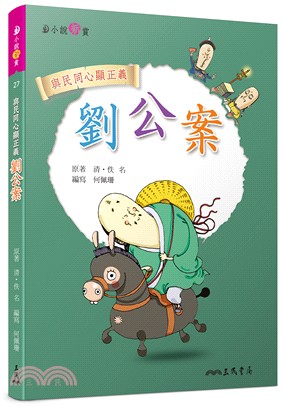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於一九九一年在巴黎成立,為歐洲第一個華人文學團體,首任會長為著名作家趙淑俠女士,前任會長為俞力工先生,現任為朱文輝先生。多年來本會集合歐洲的中文創作力量,在海外辛勤筆耕並取得可喜成績。
序
瑞士 趙淑俠 歐洲華文作家協會永久榮譽會長
那時真的很矛盾,雖然公司給了種種便利,譬如為了不妨 礙照顧孩子,允許我在家裡工作,設計圖案做好,派人來取,並 漲薪資。卻仍穩不住我的心:回歸文學的意念已在我腦中鼓動了 很久,難的是缺乏放下手上那隻畫筆的決心。猶猶豫豫的拖了好 幾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把心一橫,將一切作畫用物,紙張,白 綢,顏料等等,都分送給同事們。終於停止了美術設計工作,回 歸到我少年時代就想走的文學路上。 從那時起,我的寫作之筆便沒停過。到一九八○年代中期, 已出版二十來本小說和散文,其中多種是海峽兩岸同出。接著翻 成德語的短篇小說集《夢痕》(Traumspuren)和《翡翠戒指》 (Der Jadering)也問世。我個人的文學腳跟已站穩,似乎該做 點服務性質的事了。我想:諾大一個歐洲怎可沒個華文文學的 「文壇」!僅靠三兩個出名的作家是稱不上文壇的。文壇如花 壇,要有四季盛開經久不斷的紅花綠草。那應該是一夥愛好文學 的人,共同耕耘的美麗園地。這些想頭使我萌生組織一個文學會 社的念頭。
其實我早就希望歐洲能有一個華文文學的會社。但這會社從那兒來?誰來號召,誰來組織?難道我自己上陣嗎?那怎可能!我住在華人稀少的瑞士,彷彿是二十世紀中華文化的蘇武,多年來「悶頭苦寫」已屬不易,讓我再一次開天闢地如何使得!但後來環顧左右看看,覺得這個燙手山藥還真得我來接,否則沒人肯管這閒事。於是,我開始了搜索工作,像偵探一樣探尋哪兒有華文作家,哪個作家住在哪兒?
歐洲華人社會在生態上起了根本性的變化,是近三十年的事。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臺灣的注意力也不再只集中於美國,兩岸都有大批的留學生湧向歐洲。其他方面的交往,譬如經貿,科技,藝術和文化方面,也漸漸的有了接觸。對歐洲人來說,中國不再只是地理上的名詞,而是與之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實體。在變化中的新僑社裡,知識分子佔了很大的比例,其中有愛好文學,以寫作為專職的,但他們在哪裡,哪國哪城,門牌幾號可有人知?一個孤軍奮鬥的旅歐華文作家,雖有打開局面的決心,實際上是難得不知從何著手。
由歐洲的華文報刊上,我讀到許多旅歐作家的作品。他們在自己的居住國,繁忙工作之餘,偷閒默默耕耘,寫出洶湧在胸懷中的感情、感想、感覺。字裡行間看得出,這些寫作人是孤單而寂寞的。如果組織一個文學會社提供以文會友,相互切磋的機會。想來會得到支持。但我僅知他們的名,不識人,更不知住址,只好大海撈針一般,寫信到各國的相關機構請求幫助找作家。發出的數十封信絕大部份有回音。偏遠國度,如北歐諸國和希臘和葡萄牙等,都回信說當地「沒有華文作家」。但也有幾個國家,如法、德、意、比利時、西班牙等國比期待的更多,遺憾的是他們只知其名,卻不知住在何處。於是我再寫信去拜託協助,研究聯絡方式。那一年裡,一向懶寫信的我,少說也寫了上百封的信,另加無數個長途電話解釋:在那個兩岸交往還不像今天這樣暢通的時代,我的「在歐洲華文文學的大前題下,不管他和她從那裡來,都是我們的文友」的言論,無可避免的會引起很多人疑慮。說服作家們成為會員不是易事。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六日,經過一年多的努力與摸索之後,「歐洲華文作家協會」在巴黎成立。建會的籌備工作,是當時的巴黎會員執行,我則每天以電話連繫。
屬於歐洲的,具有歐洲特色的海外華文文學社團,終於具體有形的誕生了。是歐洲有華僑史以來,第一個全歐性的華文文學組織,成立大會原訂於三月初。因為突然聽說寫小說的鄭寶娟在法國,以文學創作和電視播報雙得名的眭澔平在英國,我便決心要找到他們,將會期推遲來等待。結果這兩位早慧的作家終於被找到。那時鄭寶娟三十二歲,已出書數本,她在讀大學二年級時,以長篇小說《望鄉》驚豔文壇,眭澔平是暢銷書作家,知名媒體人,在臺灣家喻戶曉,那時三十歲,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鄭,眭,在創會會員六十四人中,是年紀最輕的。
我和創會元老們,除余心樂和呂大明,與其他人如郭鳳西,麥勝梅,王雙秀,楊玲等,都是大會成立前夕,在我們住宿的「伯爵旅社」晤面,有的是在成立大會會場上初次相見。現任會長俞力工也是創會元老,本說要來,卻因臨時有事缺席,所以成立大會時沒見到。
余心樂原是瑞士蘇黎世大學學生,後來留下就業,相識多年。但我從不知他會寫小說,直到有朋友聽說我在組會,告知我《歐洲日報》上的推理小說〈松鶴樓〉是朱文輝寫的,才知他有一筆名叫余心樂。與呂大明見面,是因為創建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已奔走策劃數年的符兆祥先生,得知我正為成立歐華作協在作籌備,要到歐洲看看究竟,若是情況合適,便擬將歐華納入在未來的世華大家庭之內。約好在巴黎相見,我應允一定邀到旅法作家呂大明。巴黎商談後都覺滿意,當即決定歐華為世華的洲際支會之一,歐華成立後,總會將給予支持。那是我與呂大明的初次相識。符兆祥則於八○年代在臺北有過一面之雅。歐華成立大會之時,符兆祥和那時的《聯合報》副刊主編?弦先生,《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梅新先生,遠從臺北光臨來做嘉賓,使我們的成立大會生色不少。
這段過程,是我多年來的一貫記憶,堪稱刻骨銘心,但卻與某幾位文友弟妹的記憶不太一樣。我曾為與他們一致做了修改。但改後心裡不安,因堅信自己是對的,一個作家不該寫自己不相信的東西,是我一向的信念。所以又改回來。我想要怪只能怪時間,年代太久遠,每個人都可能有屬於他個人的記憶。事實上決定在巴黎建會後,我曾兩度單身去巴黎。那時以巴黎的文友最多,我與他們商談的事情,並非每個未來的會員都清楚,也無機會向大家報告。我想可貴的是我們的會已成立,而且發展得如此美好。不如就容每個人任由自己的認同、保存這點糢糊而美麗的記憶吧!
「歐洲華文作家協會」的誕生,受到國內外文化界的重視。大會成立當晚舉行餐會慶祝,連來賓共一百多人。還請來國樂家演奏,倫敦的華僑京劇票房來表演清唱。第二天歐洲日報和臺北聯合報副刊以全版給出專刊。認為「歐洲華文作家協會」的成立,很有氣勢和意義。而且我們以「歐洲華文作家協會」的名字,向會址所在地的法國政府文化部,及臺北的僑務委員會正式註冊立案。這樣做,因我們志在整個華文文學和整個歐洲。
說起來很好玩,有點像中國人辦婚禮,小門小戶也要虛張聲勢,場面堂而皇之,大日子一過立即回家勤儉務實的過日子。歐華也是這個作風,屬於我們自己的家已經建立,未來就要學著「巧婦要為無米之炊」,在沒有任何經費的支持下,要能自力更生,勤懇寫作,篤實推行會務。
我們這群身負中華文化「包袱」,也多少受到一些住在國文化特色的薰陶,既不同於母國的本土作家,也不同於僑居國的作家,彷彿已習慣了以這兩種特質的混合觀點來看人生,看世界的熱愛文學的「邊緣人」想做甚麼?當時就有人開玩笑說:「我們該不是要用筆桿子起義吧!」
我們當然不是要起義,而是要做事,想叫顯得有點冷清的歐華文壇興盛起來,想讓主流社會知道,在他們的國土上有用方塊字寫詩,寫散文,寫小說的東方移民。世界很大,華人的移民潮方興未艾,我們想與別洲的華文作家接軌,希望有華人處就有華文文學。最重要的事莫過於要營造一片園地,有效的向前發展,避免重蹈「天狗社」的覆轍:「天狗社」是徐悲鴻和張道藩等人,二○年代在巴黎建立的文學會社,當時興旺一陣因後繼無人而結束。
二十年的山山水水,歐華作協走過的路算得漫長,我們做了點甚麼嗎?雖然我們有心,周圍的環境是否能任我們揮灑自如?正如我們會中年紀最輕,受過最專業的文學訓練,會員黃世宜寫給我的信上所言:「歐洲不像東南亞,不是美加澳,是西方文明藝術的發源地,移民政策也抓得更緊,這裡的華人有更深切的惆悵孤寂感。在這片處處是文采的大地上,我們這群炎黃子孫要為自己的文化做些甚麼,需要加倍又加倍的努力。」
大會成立前夕,我們鄭重其事的制定了會章,其中有一條是:「提攜後進培植新人」。我認為這一條非常重要。由於本身的經驗,我深深認識到海外華文作家生存之不易,而我們這些會員都是第一代移民,當這批人退下之後誰來接手?歐華作協既已成立,就當代代相傳,屹立於世。承文友們的信任,一致推舉我為首任會長,從扛起擔子的第一天,我就注意這個問題,總鼓勵文友們多創作,發表,出書,並要不斷地與當地的主流文化團體,或大學的漢學研究部門,合作舉辦活動。
十年前我移居美國紐約,將這個正在發展中的文學組織,整個交給那群與我一起打拼的兄弟姐妹。他們一刻也沒停歇,積極推展會務,以文會友,相互切磋,努力的書寫,培植了不少新作家。
歐華作協自協會成立以來,已經出版了三本會員文集。第一本《歐羅巴的編鐘協奏》於一九九八年出版。二○○四年的《歐洲華人作家文選》為第二本。二○○八年,第三本會員文集,《在歐洲的天空下》也出來了。今年為了紀念創會二十年,居然大手筆的建立了「歐華作協文庫」。
歐華作協無固定經費支援,能保持正常運作良性發展已屬不易。坦白的說,像創建文庫這樣的大動作,是我在發起組織這個會的初期,從未明朗的出現在藍圖之內的。如今「歐華作協文庫」已然誕生,顧名思義便知:「文庫」的目標不是只出眼前幾本文集,而是要源源不斷的推出新作,不論會員們個人創作,還是集體合出專書,也不論是那種文類,只要是歐華作協會員的作品,都可收入文庫之內。第一批四本,類別多樣化:《對窗六百八十格─歐洲華文作家微型小說選》、《東張西望─看歐洲的家庭教育》、《歐洲不再是傳說》,和一本歐華作協二十華誕紀念文集《迤邐文林二十年》。
歐華作協的規模並非很大,但信心,勇氣,氣魄和成就是罕見的。很實在的說,歐華作協能做成的事,很多其他的會社未見得能做到。一般團體中易犯的毛病:如爭名奪位,忌妒,互相毀謗,一心為己等人性中的弱點,歐華的同仁們不會犯。我常說歐華作協成員最寶貴的資源,除了與生俱來的寫作才華外,是他們都有最佳的團隊精神,和一顆坦然大度的心。大家兄弟姐妹相稱,彼此謙讓,推崇,一人得了榮譽全體為之歡呼。他們愛文學,愛自己所屬的這個團體,真心誠意的相處,希望把會發展得更好。這樣的一個文學團體是可以做些事的。
歐華作協想與別洲的華文作家接軌,也完成了一些心願:每兩年舉辦一次雙年會,並盡力爭取與當地的著名學術機構合作,以求廣交天下志同道合的文友。一九九三年在瑞士伯恩的年會是與蘇黎世大學合作;一九九六年在德國漢堡開會,與漢堡大學同具名;一九九九年與維也納漢學界合作;二○○五年與匈牙利漢學界;二○○七年與捷克漢學界等合辦文學研討會;二○○九年在維也納召開第七屆的年會,是和中國內地專程組團前來的文壇先進們、進行交流與合作。
眼下是文學的黯淡時代,兩岸三地,隨時可聽到「文學就要死了」的聲音。文學真的會死嗎?我的回答是:「不會。」至少從歐華作協看不出文學的衰敗之相。歐華作協的會員精誠團結,不管來自何方,都是會中兄弟姐妹,在會中的份量都同樣重要,對會務也都有熱情承擔。每個人在自己的領域裡用功書寫,在個人耕耘的同時,歐洲華文文壇自然就更形豐茂,紮根亦愈深。歐華文學未來將不斷的增加新血,一代接著一代,會把這塊在沙漠中灌溉出的綠洲,漫延得更堅實廣大。如今的「歐洲華文作家協會」會員來自十九個國家,掌握十三種語言。這是歐華的作家們,對「海外華文文學史」所做的最自豪的工作。
歐洲和中國一樣,都有古老而豐富的文化。有文化的民族最懂得尊重不同文化,所以在歐洲,歐華雙方文化交流之際,總在尋找異中求同的平衡點。歐華的作家們都有完整的中華文化背景,但也都有雅量去發現歐洲文化的精邃之處,求自身文化的精益求精。歐華作家們秉持著這些理念,並無文化悲情,他們懷著欣愉的心緒,在自己選擇的新鄉里,找尋文化的對流與融合。在歡慶歐華作協雙十年華的今天,只覺風飛雲會,這邊景色正好。
目次
書摘/試閱
夢歸湖邊德國 穆紫荊每當燕卿來到那個湖邊時,她總是感覺自己是又走入了那個夢境。碧綠而閃爍著鱗鱗波光的湖面,隱射著斜斜的陽光。那是一個初春的早晨,清冷的空氣中透著些許的濕潤。燕卿沿著湖邊的小路輕輕地飄著。小路上鋪滿了鬆軟的枯葉,黃褐色的片片相疊,在微微的晨風中梭梭地輕響。小路邊的森林密密又暗暗。有一個人影在林中忽隱忽現。耳中傳來布穀鳥在林中一聲接一聲的歌唱。偶然地,也會傳來幾下清脆的梆梆聲,也是一下接一下的,那是啄木鳥在工作。梆!梆梆!湖面平整得如同一面鏡子,靜靜地在晨光中舒展著如同一床柔軟而又稠綿的錦緞。燕卿在夢中沿著湖邊的小路輕輕地飄著……飄著…… 在燕卿的書房裡,有一隻專門用來存放和中國有關物品的抽屜,比如她小時候的照片、幼稚園的報名單、年輕時代的日記本,以及出國時所帶的一本寫滿了中國親戚和朋友的通訊錄。儘管後來位址和電話幾乎全都變了,作為通訊錄形同廢紙,然而燕卿不但沒有把它扔掉,反而每次搬家時都帶了一起搬過去。因為,在這個抽屜裡留存了燕卿對故土的一些夢般的原始記憶。這些陳舊而泛黃的紙張和本子一直靜靜地放在抽屜裡。每逢燕卿打開那個抽屜,靜靜地翻閱和流覽時,她都會因著上面那些筆跡而眼眶濕潤。比如父親在那張幼稚園報名單上用其粗大而有力的筆跡在備註裡寫道:「膽小,害怕打雷。」一件如此微小的事情,體現了父母對燕卿的厚愛。讓燕卿從中感受到父母生怕她在短短的幾小時內,若遭遇打雷時會因少了親人的呵護而受驚。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漂亮的打著蝴蝶結的盒子也躺在抽屜裡。燕卿每每拿出來看著它並撫摸它時便心生一股淡淡的暖意。那是一隻小小的紙糊的盒子,除了盒底畫了一條魚外什麼也沒有。而只有燕卿知道,那盒子裡曾裝過一張張美麗而又雅緻的花箋,有的是粉色的,有的是淡綠或淺藍色的。一張張上面都或多或少地寫了一些話。那還是當燕卿年輕時,一個自稱是魚的男子所寫給她的信。已記不清是哪一年的夏天了。燕卿常常喜歡在湖畔的一塊石頭上坐著看風景。還記得那一年湖畔的野薔薇開得特別地旺盛。那一天,當燕卿像往日那樣閑坐著時,風吹花顫,野薔薇的花瓣隨風飄零。有幾片不經意地落到了燕卿的身上,讓當時也正在湖畔閑坐著看風景的魚扭頭看見了,便舉手叫燕卿別動。他說,燕卿的藍衫襯著綠水,又被幾片紅色的花瓣點綴了實在很美。如果燕卿不介意的話,他可以用燕卿手裡的相機為她留個影。燕卿卻指了對方的頭笑,魚被笑得莫名其妙地摸了摸頭,只見從他自己的頭上也摸下兩片野薔薇的花瓣來。於是魚便也不自禁地跟著燕卿一起笑了。燕卿便是如此認識了魚的。那一年的夏天,魚也常常在湖邊坐著看風景。燕卿對他的身影是熟悉的,然而卻也沒想過有一天會和他說起話來。還記得魚當時在自我介紹時說,他只是一條在湖中隨波逐流的魚。於是燕卿便也說自己只是一隻在天上順風而飄的燕。魚聽了說:「啊哈,原來我是在水裡,妳是在天上。」燕卿隨之也笑了,說:「你在水裡遊,而我在天上飄。」「啊哈!」魚聽後又點點頭,便沉默不語了。如果不是因為當時的年輕,如果不是因為那個夏天的傍晚,有點過於地令人舒適,原本兩個萍水相逢,只是偶然在一起欣賞著湖畔落日的人,是不會說話的。而那一刻,對燕卿來說,真正的姓甚名誰似乎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獨處時,有個人在你的邊上和你說著一些讓你覺得還有些意思的話。多少年後,每當燕卿看著這個空盒子的時候,她還差不多能記得魚所說過的每一句話。那天魚和燕卿說了自己的名字後,便接著說他是個沒家的流浪漢。流浪漢有自願和不自願的。燕卿倒是曾認識過兩個自願的,一個是當年未滿十八歲便離家出走闖蕩到柏林去的小叔子。十幾年裡,家裡誰都沒有他的消息,後來當他終於過夠了流浪的癮頭回來後,燕卿曾聽他說,無奈得山窮水盡之時也曾坐到大街上去伸手討過錢的。另一個是燕卿的朋友,他曾為了應徵一份工作退了房子來到遠方的一個城市。而到了以後,才知道工作沒了,他不肯告訴家人,於是便做了足足兩個多月的流浪漢,一邊流浪一邊找工作。餓了在火車站的流浪漢救濟站裡排隊領碗湯喝,晚上則和其他流浪漢們一起擠在市郊給流浪漢們所準備的集裝箱裡。這樣的流浪精神,在中國人看來是很不可思議的。然而燕卿在德國的時間已經夠長,倒也見怪不怪。只是總以為流浪漢在一般人的眼裡都免不了幾分愁苦潦倒的神態,而此刻在燕卿眼前的魚,卻是一個渾然不覺自身潦倒,反而在美麗的景色前還會湧動出勸燕卿留影的頗具幾分詩情畫意的人。後來燕卿便把手裡的相機給了魚。魚欣欣然站起來為燕卿左右都各照了一張後,才又滿意地坐下。還記得那天湖裡的水因著接連幾天的下雨,水面變得很寬,水位漲得很高。平時灰灰的湖水,此時變得厚厚的墨墨的,如一層蠕動的由植物所組成的被子漂浮在兩岸的中間。傍晚的夕陽正在西下,河面上灑下了星星點點的光斑。魚看了看正獨自面對著湖面出神的燕卿,突然示意她和他去湖邊的那塊石頭上坐。坐下後他當著她的面,解開了自己的鞋帶,然後對燕卿抬了抬手指。後來,每次當燕卿回憶起這一幕時,都驚訝魚幾乎沒對她說過一個字。魚就是這樣用手指,微微地示意了一下,燕卿便跟了他,坐到了石頭上。不過燕卿並沒有鬆開她自己的鞋帶,她只是好奇地看著魚,看他做什麼。而魚把鞋子脫掉了。脫掉鞋子以後,魚又繼續把襪子也脫掉了。脫完襪子後的魚光了一雙腳,看著燕卿,然後伸出一根手指向燕卿的腳示意著,燕卿猶豫地搖了搖頭。魚便收回手指不再理會她,自顧自地把一雙光腳插進了水裡。燕卿觀察著魚,只見他輕輕地從鼻子裡哼出一聲「嗯」,便無比舒服地閉上了眼睛。那副神態如同咽下一口茅臺美酒,燕卿不由得暗生羡慕。過了片刻,燕卿見魚一直閉著眼睛享受著,便不動聲色地把自己的鞋子和襪子也脫了,學著魚的樣子,把一雙腳探入水裡。「啊!」入水的瞬間,燕卿一聲尖叫,差點從石頭上滑下水去。魚被燕卿的驚叫一嚇,睜眼道:「出了什麼事?」燕卿哆嗦著牙關說:「水,好涼……」魚聽了只輕輕地噓了一聲說:「不是好涼,是好舒服。」說著他伸出自己的手臂,摟住了燕卿的肩膀。讓燕卿靠近他,穩住了自己。然後他們的腳便在水下輕輕地動著。一會是魚的腳,在燕卿的腳背上,把燕卿的腳踩下去,一會又是燕卿的腳在魚的腳背上,把魚的腳踩下去。如此不久,一股清爽的涼意便從腳心升起,酥酥地麻醉了燕卿經年來的疲勞。燕卿微微地歎了口氣,說:「唉,如果一個人不需要活著,就這樣坐著也很好。」魚沉默地拍了拍燕卿的肩。許久之後,他自言自語地說道:「現實是殘酷的……」現實是殘酷的。那天傍晚分手以後,魚就不知去向了。然而分手時魚記下了燕卿家的地址。因為燕卿說:「讓我們保持聯繫吧!」於是燕卿後來便有了來自魚的隻言片語。魚居無定所,然而所用的信紙卻不是香煙殼子或麵包口袋,而是一些不知道他從哪裡去弄來的色彩柔和的花紙。一張一張的,或大或小,或粉或綠,讓燕卿幾乎以為自己變成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魚的信寫得很簡短,隻言片語的,常常令燕卿覺得魚所要表達的,不過就是開頭的問侯和結尾的祝福。然而,這對燕卿來說也足夠了。因為燕卿看到魚的信,感覺便等於是看到了魚本人。所謂的見信如晤,對燕卿來說便是如此。燕卿拿了花紙便彷彿又回到湖畔和魚同坐的時光。在後來燕卿的回憶裡,似乎從來沒有過那樣令人放鬆的一刻了。那一刻雖然很短,卻讓生活所帶來的沉重和煩惱都悄悄地褪去了,眼前和心中只蕩漾著湖畔的美麗和安逸。這便是為何燕卿始終捨不得丟掉魚的信,始終把它們一張一張都收進了盒子的原因。因為在它們裡面,隱藏了一份對生活的如釋重負。一年又一年,每當燕卿想到魚時,她都會去把那只盒子拿出來,摸一摸和看一看那些美麗而又雅致的信紙,讀一讀信紙上面,魚所寫的那些隻言片語。令人奇怪的是,每次讀魚的信,燕卿都不會感到魚是在流浪,因為魚總是在信裡對燕卿輕描淡寫地說東道西。而更多的時候,是燕卿毫無魚的消息。魚居無定所,一切用電的東西魚都沒有。沒有電腦,沒有手機。因此,燕卿便只能當魚是在某個石縫裡睡覺。而她便像是守著一條睡美魚似地守著那些魚的信和魚信裡所說的那些話。也因此每一次,當燕卿打開信箱,意外地看見有魚的來信時,感覺便如同打開了一扇門後,突然看見魚站在屋子裡向她微笑一樣。令燕卿欲哭還笑地對自己的眼睛產生疑惑。因為對她來說,收到魚來信的同時,也往往意味著是她再次失去魚的任何消息的開始。快樂和痛苦總是交替地在燕卿的心裡沉浮。時間,就這樣過了一年又一年。多少年過去了,燕卿盒子裡的花紙漸漸地滿了起來。而終於在一個落葉飛舞的秋天,魚的信又來了。這一次魚在信中寫道,他有可能在近日搭車再一次路過燕卿所在的城市,他說他將會在傍晚的時光在湖畔的石頭那裡等燕卿。不用說,在接下來的幾天裡,燕卿是每天下午便來到湖畔的那塊石頭邊,直坐到落日西下才回去。她在那塊石頭上坐著等魚。那天下午,她還沒有走近湖畔時,便遠遠地看見了石頭上有個人,燕卿的心怦怦地直跳起來,因為她看到了那個在石頭上的人腦袋,是白白的一片。竟然全白了!燕卿禁不住直打哆嗦。那一天晚上,魚走時把盒子裡的花紙全都帶走了。因為他把那些花紙拿出來放在鼻子上聞了聞後,說他聞到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他認為那就是來自燕卿的香味。而燕卿也順從地讓他帶走了,那是因為她把它們早已都深深地刻入了腦子,閉著眼睛都背得出內容。只是燕卿說盒子空了,以後看起來會令人覺得難過。於是魚便拿出一支筆來,在盒底溜溜地畫了一條魚。那真是一條漂亮而又寫意的魚呀,小肚子胖胖歪歪的。燕卿看著它不禁又呆了。魚笑了笑輕輕地對燕卿說:「我是一個愛畫畫的人。」原來魚的居無定所都是和他的愛畫畫有關。魚喜歡畫畫,喜歡讓自己每天都沉浸在美麗的風景和幻想之中。因此他辭掉了固定的工作,到處遊蕩。遊到哪裡畫到哪裡。曾經有過的幾個女友,都漸漸地無法適應而離開他。魚最終變成了一個自願的流浪漢。燕卿認識魚的那天,魚已經很久不畫畫了。然而,當他拿到燕卿給他的地址以後,當他開始用花紙給燕卿寫上隻言片語的時候,他那久已丟失了的創作熱情,又慢慢地回到了他的身上。他走了很多地方也畫了很多的畫,只是這些他都沒拿出來給燕卿看。那天魚再見過燕卿以後,便幾乎徹底地失蹤了。一年又一年,燕卿在春夏秋冬的季節變換裡,時不時地默想著魚的一封封信。然而,魚始終沒有再出現過。燕卿後來也住進了養老院。那一年的秋天,當樹上的最後一片葉子快凋零時,養老院的護理給燕卿送來了一捲郵筒,說是從燕卿的老地址轉過來的。燕卿看不清上面的字,便請護理替她唸,唸後才知道那是由一個教會機構給她寄過來的。燕卿請護理幫她拆。只見郵筒打開以後,從裡面倒出厚厚的一捲畫來,全部都是些用鉛筆畫出來的小幅素描。一幅一幅的風景,十分地美麗和飄然。而每一幅畫的邊角上,全都有幾筆勾出的女人的臉。護理指著那張臉對燕卿說:「那不是您嗎?」每一張畫的邊角上,都有一張燕卿的臉。而每一張畫的背後,都貼了一片形狀不規則的花紙,那是魚當年給燕卿所寫的信。現在它們附在魚的畫後面,又回到了燕卿的手中。隨畫寄來的還有來自教會機構的一封信。信上說,魚目前正在教會機構屬下的一所收容所裡,由於患病,行動不便。近日,他把自己的畫都捐給了教會屬下的基金會,目前正在收容所的大廳裡展出。而這一部分,即全部都畫有女人臉的部分,魚特別囑咐了必須贈送給燕卿。燕卿讀後,沉默良久。然後,她要護理為她安排去探望魚的旅程。那一夜,燕卿重新又夢到了那一片湖。在夢中,她和魚一起又坐在了那一塊石頭上。春日的太陽,暖暖地灑在身上,她看見魚脫掉了自己的鞋子,於是燕卿也脫掉了自己的鞋子……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