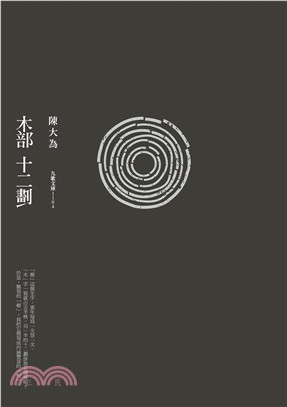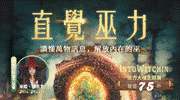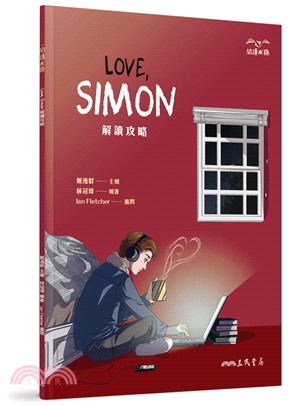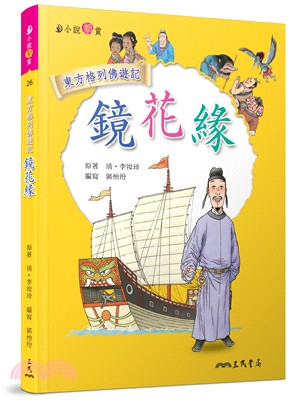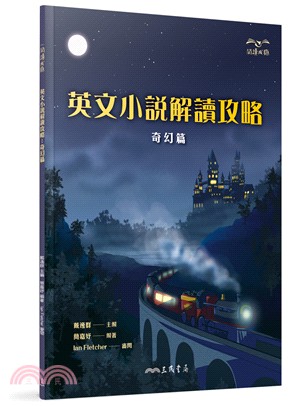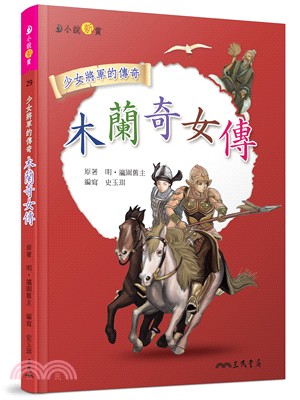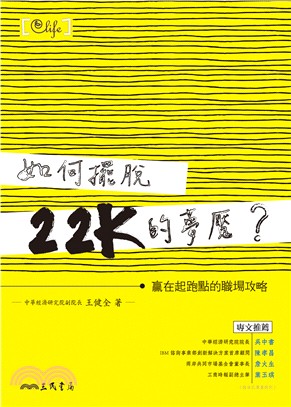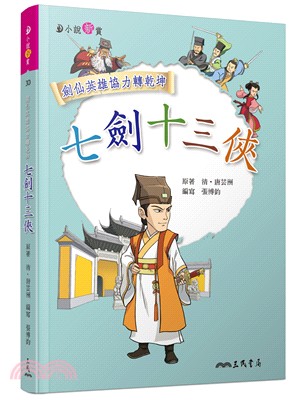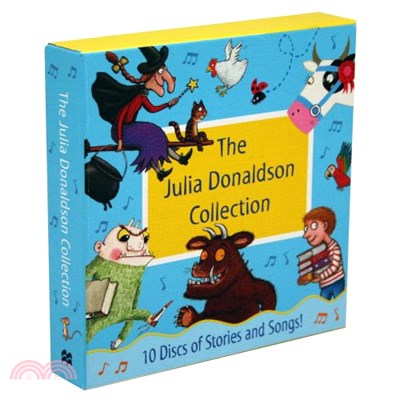商品簡介
《木部十二劃》以不同時期創作的篇章連綴,成為一部海外華人的流浪者之歌。敘事起自曾祖父輩遷徙的移民身世為本書開端,以南洋的不朽童年往事以及家鄉軼事作為終點。
陳大為在〈卷一〉壯寫家族移民遷徙至南洋,對原鄉文化的緬懷,如會館、茶樓等等的興衰,詩意般的文字穿越時空,感嘆域外華人花果飄零般的身世,情濃筆淡,令人掩卷嘆息;〈卷二〉則是大敘述後的親人圖像,從早夭的妹妹到外婆、外公、父親、兄弟以及妻子等,他以或憂傷或諧趣的文字,一遍遍召喚熟稔的親友,在他鄉用回憶安慰心靈,與原鄉憂歡對話。
俠骨柔情的文字風格,以及輾轉的生命經歷,陳大為置身異鄉台北眺望南洋原鄉,以創作重現一種常被忽略的移民史觀,重新繪製一張身世流動的圖卷。
作者簡介
陳大為
一九六九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怡保市,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台北大學中文系教授。 曾獲:台北文學年金、聯合報新詩及散文首獎、中國時報新詩及散文評審獎、中央日報新詩首獎及散文次獎、教育部新詩首獎、星洲日報新詩及散文推薦獎、世界華文優秀散文盤房獎等重要大獎。著有:詩集《再鴻門》、《盡是魅影的城國》、《靠近 羅摩衍那》,散文集《流動的身世》、《句號後面》、《火鳳燎原的午後》,論文集《亞洲閱讀:都市文學與文化》、《風格的煉成:亞洲華文文學論集》、《中國當代詩史的典律生成與裂變》等。
名人/編輯推薦
序
歲 月(自序)
原鄉,是一個在現實中越來越萎縮越來越模糊,卻在記憶中越來越富饒越來越清晰的地理圖象。表面上,是歲月和空間的距離決定了它的質感;暗地裡,書寫者對土地的感受和意圖,才真正決定了它的深度,和規模。原鄉的書寫者,不一定有什麼樣強烈或具體的鄉愁,令人不能自拔的因素,很多事物只是在日常言談裡,偶然浮現,成為幾個亮麗的句子,或一段意外回甘的舊事。在某些作家手裡,說不定原鄉書寫只是一種純粹的寫作策略,但總是有評論家喜歡在原鄉敘事中誤讀出二元對立的姿態,並由此推斷出作家對異鄉的疏離。馬華旅台作家群當中,有這樣的例子。
曾經有人問我:為何寫了這麼多南洋和怡保的故事,台灣呢?台北呢?究竟在我的生命歷程中後者有多少的份量?我一貫的答覆是:十九年的怡保歲月在前,二十餘年的台北/中壢歲月在後,所以我選擇先完成怡保老家的寫作,接下來才正式輪到台灣(雖然我也零星寫過幾篇台灣生活的散文和詩)。居住時間的先後決定了書寫的順序,合情也合理。
南洋是一個龐大、湮遠的華人移民史,所有壯烈或迷人的章節,都跟我沒有直接的關係,我頂多是個遲到的說書人。怡保卻是真實的存在,是我全部家國情感的根據地,馬來西亞比較是一個名詞,或者較方便定位自己的國籍身分。國籍是很重要的。我為了堅持馬來西亞國籍,自然在台灣喪失某些機會和利益,也會有些不便。可是呢,現實生活中的馬來西亞籍,卻讓我跟台灣人在接觸往來之間,產生許多樂趣。極大部分跟我閒聊的台灣人,不出五分鐘,就會設法找個縫隙,沿著我的廣式國語展開一連串的猜謎遊戲,從香港到新加坡,最後才追蹤到馬來西亞。當然,我得告訴他們怡保的位置,它在大家比較熟悉的檳城和吉隆坡之間,通常是那些在馬來西亞小住或工作過的台灣人,才會知道這個地方。我喜歡當馬來西亞人,雖然我比較喜歡台灣的環境和生活。
我在怡保住了十九年,渡過無憂無慮的童年和少年時期。一九八八年來台灣讀書,至今已滿二十三年。在台大宿舍住了四年,很多時間都耗在校園之內,台灣社會對我這種留學生而言,完全是一個異鄉。畢業之後,我到基隆工作了大半年,後來又回到台北展開六年半工半讀的歲月,真正安定下來的日子,從中壢開始。這是我最熟悉、最自在的生活圈,十年來建立了許多屬於自己的生活動線和節點。在中壢住久了,回到怡保反而不太適應。台北是我留學的所在,中壢是我定居的家園,怡保是我成長的家鄉。三個地方,各有重要性。但怡保,永遠是第一順位的。
在怡保,除了自己的親友和曾經生活過的地方,有些事物漸漸陌生起來。後來發現自己在閒聊之間,經常冒出「我們台灣」的字眼。一來,是親友們都喜歡問起台灣和馬來西亞的差異;二來,是我自己心裡老是浮現一個台灣標準。其實兩個國家各有優缺點,都不完美。這兩個大異小同的華人社會,讓我在眾多事物的思考上,獲得更多元和開闊的視野。
離鄉二十年,馬來西亞這個名詞所蘊含的內容日漸萎縮,怡保則日益強大,很多時候,怡保悄悄佔據了馬來西亞的版圖,國家變成家國。但我對地誌學或文化地理學層次的怡保並不感興趣,我只在意我自己的怡保。從童年到少年,太多說不完的故事,還可以從中衍生出更多的故事。它是一座寶藏,源源不絕的提供我寫作的鈾礦。
我在第一部散文集《流動的身世》(一九九九)寫了幾篇跟怡保相關的散文,後來在《句號後面》(二○○三)寫了一整本家族傳記,在《火鳳燎原的午後》(二○○七)也寫了幾個短篇,去年在〈聯合報副刊〉連載了十幾則尚未打算結集的「陳年小事」。如果加上處於草稿階段的文字,以及計畫中的篇章,值得下筆的怡保故事,足夠寫滿(完整的)三部散文集。於是我決定把怡保好好的整理一番,從散文到詩,用幾年時間慢慢的寫。
最早的《流動的身世》和《句號後面》都絕版多年,我不想直接再版,這次我重新挑選了十八篇散文,分兩卷,試圖勾勒一個感性的怡保圖象,命名為《木部十二劃》。卷一的七篇,前四篇是南洋主題的詩化書寫,後三篇是童年記憶的一系列狂想曲,這些少作一共得過五個散文獎。卷二的十一篇,則是一個完整的家族史寫作計畫,我稱它作列傳。有部分情節故意在不同篇章裡重複出現,有些人物穿梭於故事與虛實之間,甚至某些主題分成兩篇來寫。在我所有的散文創作當中,這是我最喜歡的一輯。〈句號後面〉,則是我最喜歡的一篇
這篇新版的小序,寫不了什麼新鮮事,真正要講的全寫進散文裡去了,留待讀者自己去發現。
陳大為 二○一一年十二月于中壢
目次
卷一 木部十二劃
會 館 012
茶樓消瘦 025
抽 象 035
在南洋 044
流動的身世 054
木部十二劃 064
從 鬼 075
卷二 垂立如小樹無風
垂立如小樹無風 088
句號後面 098
將 軍 108
蟬 退 119
左 右 129
家有女巫一隻 139
急急如律令 149
瘦鯨的鬼們 160
青色銅鏽 172
大 俠 185
憑 空 198
書摘/試閱
這個字,老喜歡跟童年糾葛在一起。
木部,十二劃;這個「樹」曾是我最討厭的生字。每寫一次就怨一次吳剛:為什麼他的巨斧不砍掉這些惱人的笨筆劃?不然還能怨誰呢?我的見聞還那麼瘦小,會砍樹的只認識吳剛。要知道這雜草般的生字,可是小手最大的夢魘,它還害我被豬頭老師罰抄,整整兩百遍。沒錯,我是故意把它簡寫成「村」的,誰叫它這麼難寫!
老師好不容易找出原因─我總是把左邊的「木」寫得很大,占半格,而且枝幹粗壯,儼然是上了年紀的老喬木;其餘筆劃變得好幼小,像吋短的豆苗苟活在地表,後來乾脆拔掉。為了此「樹」,老師在作業簿上澆了半升口水,我同時聽到兩種躍然紙上的呼聲:喬木得意地冷笑,豆苗在溺斃邊緣求饒。占半格的問題,我足足反省了一支冰淇淋的時間。我一點都沒錯!樹是大木,所以「樹」字的「木」旁一定要夠大。奇怪,老師怎麼想不通這道理。
學無止境的生字對我而言,等於一棵特大號的喬木,我是那有待進補的白蟻,六肢虛軟,觸角迷茫。張開成長中的複眼,我跟豆苗一起蹲在地表,仰望喬木的身軀,沿著說不上尺吋的根莖,仰望仰望再仰望,直到痠了眼睛疼了頸項。就這樣,我被生字一筆一筆地揠苗助長,長成書生的呆模樣。
我討厭「樹」,是因為我喜歡樹。
樹,在我的作文和散文裡出現了好幾百次,有時說好只是露露臉,後來卻成為喧賓奪主的熱意象;有時很聽話,乖乖地佯裝成某個故事的冷背景,靜靜杵在字裡行間。我小時候也常常杵在樹蔭底下,聽風如何剽竊鳥語、如何丈量歲月。樹蔭涼快了我半個童年,所以每篇作文都飄進幾片樹葉。
可是我萬萬想不到,連土地公公也不知是哪個閒人,在這塊空地植下十幾棵榕樹。只聽說後來要鋪馬路,不得不請吳剛來砍掉八字較輕的幾棵。外婆很沒有把握的接著說:在媽媽出生那年,還剩下十一棵,數十年來先後被雷劈掉長相猙獰的兩棵妖榕……。這番說詞像狐狸,躡手躡腳走過我的耳膜。外婆常常唬我,等我嚇青了臉再哄回去,用童話,或新奇的玩具。該不該相信狐狸的小腳印呢?可惜外婆陳述榕樹野史的表情,我早已忘記。
但我還記得在榕樹底下乘涼的每個午後。
樹蔭把感覺裁成壁壘分明的兩個世界。蔭影之外,是灼熱的炎陽在烘烤所有移動或靜止的事物,熨平了馬路,煎軟了石墩,更設法燙傷我用來描述景象的詞藻。各種可能的創意都中暑了,每位作家在仲夏流下一樣的汗,記述一樣的豔陽天,統治大地的盡是火部的惡字眼。還有微焦的風,吹來一股燜感覺。所以躲在密不透光的老榕樹下,是最廉價的避暑方法。
別忘記,這是九棵巨大榕樹拼湊起來的,超大號的蔭涼。其間雖有陽光礙眼的小縫隙,但不礙事。色澤昏暗的影子是一張幸福的地圖,幾乎全村的閒人、土狗和賤鳥都會到此避暑兼聊天,於是樹下匯聚了不同物種的語言。把天聊得最起勁的是閒人俱樂部,其成員不外乎:小頑童、長舌婦、老骨頭。長舌婦手裡端著頑童的午飯,嘴裡應答著老人家,匙也掏掏,舌也滔滔;如此三位一體,彼此咀嚼著彼此的午後心情。
其中一棵老榕樹長了顆古怪的瘤,遠看似金魚浮凸的蠢眼睛,近看又像水牛飯後的副產品。總之刺眼,後來它半推半就地擔任起我們的箭靶,所有自制的武器都往它身上招呼,像動了再動的超級手術。有一回我突發奇想─要是一手抓住根鬚,一手握著利器,學羅賓漢兼泰山,從這棵榕樹的外圍盪進來,一槍往靶心刺去!越想,越刺激。那是一個紀念屈原投江的中午,吃過阿倫他祖母裹的粽子,我們聚集在靶前作初步的沙盤推演。沒騙你,我隱約聽到瘤靶子顫抖的怪聲音,嘎啦嘎啦的,原來它也怕死。大夥眉飛色舞的比擬著刺靶大計,然後搬運高凳、物色韌鬚,再漆紅了靶心、並墊護可能撞擊和墜落的地方……。忙了一個小時,只等主角上場。
時間在雙腳騰空之際停頓了一陣子,再緩緩滑動。跟電影裡靜止的畫面很相似,每一張崇拜的嘴巴呆住,加油的聲波形成氣狀的漣漪,一環一環地朝我叩拜過來。差點忘記應有的動作─拔槍,瞄準,刺殺。整個過程大約四秒:欣賞一秒的風景、一秒的表情,再愕去一秒,到了拔槍的第四秒,瘤靶子已近在眼前了。不過我還是不負眾望,連人帶槍一併擊中目標,同時被目標擊中。原來瘤靶子是一顆重量級的拳頭。如果不是早有防備,我肯定槍毀人亡了,不止是左腳挫傷而已。這件事成了歷久彌新的飯後笑話。
不過我那群有良心的夥伴可不這麼認為,他們覺得這是件很壯烈的事蹟,作文最高分的胖子當仁不讓地挺身而出,他說要發揮過人的修辭能力,用國中生才懂的文言文,寫一篇非常厲害的碑文來記載此事。結果他真的寫了,用刀,在樹瘤左邊刻字─「辛亥年端午,不世英雄○○○,在此一擊」。當時他還很得意的解說了一番:辛亥年,是孫中山革命成功的年份,是一個威風的年份,用在這裡更能說明擊樹一事的偉大。五天之後,我們才知道天干地支的正確用法。不管怎樣,「辛亥」一詞雖然會誤導後人對此事的考據(萬一我成為偉人的話),但從中卻可看出胖子等人對我那份至高無上的崇敬。「他裹著石膏的殘軀,在樹蔭底下顯得十分悲壯,有一股風瀟瀟兮易水寒的感覺;我的整顆眼珠子,好像漂浮在淚湖上面。」若干年後,我在胖子發表在副刊上的一篇散文,讀到當時的自己。他沒有忘記那件事,只是把「英雄擊樹」改成「英雄撞樹」。
想想也對。除了樹,難道我們沒有更值得記錄的事物?除了樹,童年就舉不出更盡興的玩具?難道,除了這片老得快成精的榕樹林,以及附近幾棵落單的松樹、兩叢觀音竹,作文就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故事背景?
於是我把回憶逐格倒帶回來,然後假想─如果沒有榕樹林,我們這群不學無術的村民,會以什麼樣的形態來消磨時間?最先想到水部五劃的「河」。易寫,又好記的「河」,偏偏水濁不見魚,流勢又急如催命,當然不是一條人緣很好的流域。河的兩岸是讓頑童著迷的鵝卵石灘,但石太滑且多陷阱,每隔幾年就有孩子成為水鬼的收藏品;洗衣也不行,太濁的水質有股越洗越髒的土味;至於那群終日閒閒的老骨頭,即使再怎麼窮極無聊,也絕不肯跋涉兩哩到此釣魚。在河邊,我們的童年找不到聚集的理由,孩子的作文都不喜歡凶險的水聲。
太遠,太濁,太滑,太急。筆劃很少的「河」,絕對是一個被排除的地理。
山部五劃的「岩」呢?村口有數十塊由山壁崩落的花崗岩,大者如丘,小者如球。想想也不妥當。難不成叫老態龍鍾的長輩來攀岩?更難說服長舌婦頂著火部的字眼,跑到岩縫間話家常。要是任由孩子從岩頂野到岩底,在山部裡書寫一節陡峭的生命,那我們的童年足以成就一部琳瑯滿目的傷殘紀錄。我真不敢想像─萬一胖子失足夾進石縫裡的窘態,他可能在散文裡這麼自述:「在巨人齒縫間,我是那半條賴死不走的韭菜,塞得滿滿的,休想三兩下把我剔出來。除非你找來盤古,將齒縫闢寬……。」這必定是一個成天瘀血的童年。易寫,但凶險的「岩」,並非一個滋長得出生活情趣的好地點。
排除了五劃的岩堆與河水,只剩下田了。田部零劃,太單調的阡陌,只能吸引青蛙到此玩耍。
我不知道筆劃是否跟生活內容保持某種神祕的正比例。但那些筆劃太少的山水,確實無法架構起童年既豐饒又雜亂的記憶。唯有木部十二劃的「樹」,才能讓我從容地攤開、晾起微潮的歲月。榕樹之外,我們的村子還有幾十棵散布各處的喬木,知名或不知名的,像一個巨大厚實的胎盤,呵護著頑童的世界。我忍不住要下定論:火部的存在,是為了突顯木部的涼快價值;樹所以存在,為的是替童年添幾分神彩、替作文布置最立體的舞台。
於是我寫了一篇叫〈木部十二劃〉的散文,用這兩句話來結尾:「我喜歡樹,因為它可以簡寫成內涵豐富的村。」
《聯合報‧聯合副刊》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六日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