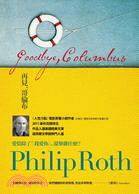商品簡介
安東尼‧霍普金斯主演《人性污點》電影原著小說作者
菲利普.羅斯26歲初試啼聲的成名之作
被譽為美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
探究社會現況、深富洞察力的成名之作
一場熾熱的盛夏愛戀 在少年的猶太世界裡卻是道德的禁忌
愛情除了「我愛你」之外,還參雜了什麼?
《再見,哥倫布》由中篇小說〈再見,哥倫布〉和五個短篇小說組成。全書呈現二次戰後美國貧富差距的社會境況及五○年代猶太家庭生活,題材涉獵愛情、宗教、新舊猶太社群中的變化等。作者機智、富有敏銳的觀察力,以及對人物的憐憫之情,在故事中體現無疑。這第一部出版的中篇故事不僅是羅斯的成名作,也是之後所有故事的雛形。
「是我內心裡的什麼東西將追求和攫取轉為愛情,然後又和盤托出?又是什麼使勝歸於敗,又把敗──誰知道──轉為勝?我相信我愛過布蘭妲,但站在那裏,我知道我已無法再愛她。」
<再見,哥倫布>:尼爾‧克勒門,一個在圖書館工作的二十三歲猶太少年,在盛夏的泳池畔與布蘭妲相遇,進而踏入與他原生家庭截然不同的世界。城郊的生活有吃不完的食物,還有流行音樂,人們的話題是球隊比數和運動員戰績…尼爾口裡吃著來自各地新鮮的水果,聽著那些從沒聽過的人名-多半是球員-他意識到自己與布蘭妲之間的陌生差距,但青春的慾望與內心無以名狀的渴求,驅使他維持這段關係…
〈猶太人的改宗〉:奧齊是個十三歲的孩子,對於課堂上老師口中的上帝充滿著好奇,他聰明愛發問,但問題卻讓老師十分震怒,母親還因此動手打了他。於是他開始「失控」…
〈護教者〉:馬克思中士是一位忠於職守的老兵,尚保有對猶太教虔誠的心。三位猶太新兵在宗教的庇護下做出種種違反軍紀的事情,身為上司的馬克思相當猶豫,是該處置還是放任他們…
〈愛波斯坦〉:一位中年男子對於枕邊人日漸凋零的身軀絲毫提不起興趣,偶然間發現朋友小孩與對街年輕女孩偷嚐禁果,喚起不具名的渴求,瞞著家人和一位女士出遊後,發現身上男性器官起了疹子,以為過幾天就會癒合,此時竟被老婆發現…
〈世事難料〉:猶太中學生艾伯托有前科也不愛讀書,在寫完職涯測驗後,老師認為他往後將成為律師。本性調皮的他還串通全班同學一起開老師的玩笑,在課堂上趁老師寫黑板時全班彎腰綁鞋帶、帶頭唱美國國歌。老師堅信職涯測驗的結果,要他到法院裡去實習,而他卻臨陣脫逃…
〈狂熱者伊萊〉:猶太律師伊萊受新興猶太社區居民的委託,要他驅離社區中的傳統人士,但他們不願離去,雙方的堅持讓他備感壓力,卻又希望能找到協調的方法。此時他的第一個小孩又即將出生,讓伊萊十分地焦慮…
作者簡介
20世紀美國最具代表性的猶太作家
諾貝爾文學獎熱門人選、入選美國經典文庫的作家
羅斯出生於1933年美國紐澤西州的紐華克,芝加哥大學英文研究所碩士畢業後,原計畫攻讀博士,但在24歲時放棄研究,專攻寫作,自此筆耕不斷,源源不絕的創作能力在美國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至今年近八十的他,筆鋒猶健,仍有旺盛的寫作精力,每年一部高質量的作品仍持續影響文壇。
身為文壇長青樹的他,獲獎無數。自26歲發表第一部作品《再見,哥倫布》時,即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在寫作生涯中曾三次獲選福克納小說獎、兩次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兩次書評獎、美國筆會/福克納獎、白宮頒發的美國國家藝術獎章、美國藝術與人文學院最高獎-小說金獎等的殊榮, 1998年以《美國牧歌》這部作品拿下普立茲小說獎,擊敗同時入圍的唐.德里羅。
美國國家圖書館在2005年出版他的系列作品,將他生平中所有作品選入「美國經典文庫」永久保存,此舉動表示已將羅斯與梅爾維爾、霍桑、費茲傑羅、福克納等美國名作家並列,他也是繼歐朵拉.韋爾蒂(Eudora Welty, 1909-2001)和索爾.貝婁之後,唯一在生前就獲得此殊榮的作家,甚至在比他們二位還要年輕的時候,就被選入文庫裡。
2011年,羅斯再獲英國曼布克國際文學獎,這一個獎項對他的作家聲望來說,無疑是錦上添花,受到國際文學獎的肯定,再一次證明了他作品中人性描繪的普世價值。
名人/編輯推薦
「一部傑出的作品!」
-─《新聞週刊》Newsweek
「跟我們一般人不同的是,我們是哭哭啼啼來到這世界,眼睛看不見,身上甚麼也沒有。羅斯先生一出生就有指甲、頭髮及牙齒,說話有條理。他老練、風趣、充滿活力,他的『演出』具有大師風範。」
-─索爾‧貝婁(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翻開菲利普‧羅斯作品的第一頁,就像是聽見生命中的熱火『轟』一聲點燃。我們體驗到的是熱情,而且非常熱情。」
-─《衛報》Guardian
目次
再見,哥倫布
猶太人的改宗
護教者
愛坡斯坦
世事難料
狂熱者伊萊
書摘/試閱
心靈乃半個先知。──意第緒諺語
一
第一次見到布蘭達時她要我幫她拿眼鏡。然後她邁步走到跳水板邊緣,矇矇矓矓地向池子裡瞧;此時要是池水都排光了,近視的布蘭達也是不會知道的。她姿態優美地躍入水中,一會兒後便游回池邊;她那頭棕紅色短髮在軀幹前方昂起,宛如一朵綴在長莖上的玫瑰。她滑向池邊,然後坐在我身旁,說道:「謝謝。」她兩眼水汪汪地,不過那水可不是游泳池的水。她伸手向我要回眼鏡,可是直到轉身走後才戴上。我望著她離去的倩影。突然,她將雙手往身後一擺,用大拇指和食指拉了一下泳衣的底部、再彈回去,將露出來的部位包覆好。我的血壓驟升。
當天晚飯前,我就撥了通電話給她。
「你打電話給誰?」格蕾蒂斯舅媽問道。
「就今天遇到的女孩。」
「多麗絲介紹給你的那個?」
「多麗絲?她一個池子排水工也不會介紹給我的,格蕾蒂斯舅媽。」
「別老這麼酸不溜丟地講話。她到底是你堂妹呀。你是怎麼遇上她的?」
「也算不上什麼遇不遇上。是我看見她的。」
「那她是誰?」
「她姓帕丁金。」
「我不認識什麼姓帕丁金的……」格蕾蒂斯舅媽說道,彷彿她認識每個格林道鄉村俱樂部的會員。「你還不認識她,就要打電話給她?」
「對。」我解釋道:「我會向她介紹我自己的。」
「大情聖。」她邊說邊回去準備舅舅的晚餐。我們不同桌吃飯:格蕾蒂斯舅媽五點吃晚飯,蘇珊表姐五點半吃,而我是六點,舅舅則到六點半才吃。這純粹就是舅媽的怪脾氣,沒什麼好多作解釋的。
「那本市郊電話簿呢?」我把塞在電話桌底下的書統統翻了出來之後問道。
「什麼?」
「市郊電話號碼簿,我要打到肖特山莊。」
「是那本薄薄的書?咦,這整間屋子裡不都有那種書嗎?可我從沒用過。」
「在哪?」
「被斷了隻腳的櫥櫃壓著哩。」
「我的老天。」我說。
「問查號台吧。你一定會在那邊扯來扯去,把櫥櫃裡的抽屜翻得亂七八糟。 別再煩我了,你看,你舅舅就快到家了,而我還沒讓你吃飯!」
「舅媽,今晚我們就一起吃吧。天氣很熱,這樣你也比較輕鬆。」
「好啊,那我就一次準備四份不同的菜色好啦。你想吃燉肉,蘇珊想吃鄉村起司,你舅舅要吃牛排。星期五晚上可是他的牛排夜,我不想讓他失望。而我呢,我想吃一點冷雞肉。難不成要我忙進忙出二十幾趟?我幹麼?做苦力嗎?」
「那我們都吃牛排好了,或冷雞肉──」
「這個家我都照料二十年了。去打電話給那個女孩吧!」
電話是通了,然而布蘭達‧帕丁金不在家。接電話的女人告訴我布蘭達在俱樂部用晚餐。她吃完飯會回來嗎(我的聲調比唱詩班的男童還高兩個八度音)? 我不知道──對方說──她也許會去打高爾夫球。請問你是?我咕噥了幾句──嗯沒什麼她不認識我我再打過來好了沒什麼要緊事謝謝抱歉打擾了……我大概說到那邊就把電話給掛了。這時舅媽喊我,我只得強打起精神去吃晚飯。
她把嗡嗡作響的黑色電扇開到高速,吹出來的風輕輕吹起自廚房電燈垂下的那根軟線。
「你想喝哪種汽水?這裡有薑汁汽水、德國礦泉水、黑覆盆子,要我開一瓶香草汽水也可以。」
「不用了,謝謝。」
「你要水嗎?」
「我吃飯時不喝東西的。格蕾蒂斯舅媽,這一年來我天天都這麼說呀──」
「只要一點碎肝,你麥克斯舅舅就可以喝上一箱飲料。他整天都在賣力地工作。如果你也這麼賣力,你也會喝得很多的。」
火爐上的盤子裡堆滿了燜牛肉、滷汁、水煮馬鈴薯、青豆和紅蘿蔔。她把盤子放到我面前,食物的熱氣迎面撲來。她又切了兩片黑麥麵包,擱在我身邊的桌上。
我用叉子把馬鈴薯切成兩半吃下去,坐在對面的舅媽一直盯著我看。「你不想吃麵包?」她說。「早知道我就不切了,會壞掉欸。」
「我想吃。」我回答。
「你不喜歡有籽的,對吧?」
我把其中一片麵包撥成兩半吃了。
「肉的味道如何?」
「還好──很好。」
「先吃馬鈴薯和麵包的話一下就會飽了,你要是把肉剩下我就只好全都扔掉。」
她驀地從椅子上跳起來──「鹽!」她回到飯桌時,砰地一下把鹽罐撂在我面前──這個家裡沒有胡椒,因為她聽過蓋倫‧德雷克 在廣播裡說胡椒不為人體所吸收。一想到自己做的食物僅僅是為了在食道、胃、腸裡周遊一趟,格蕾蒂斯舅媽就會感到於心不安。
「你在揀豆子吃嗎?早告訴我的話,我就不跟紅蘿蔔一起買了。」
「我愛吃紅蘿蔔。」我說。「我愛吃啊。」我把一半的紅蘿蔔塞進嘴裡、另一半則塞進了褲袋,以示證明。
「豬喔。」她說。
儘管我非常愛吃點心,尤其是水果,但我決定不吃,免得在這炎熱的夏夜,話題都圍繞在選新鮮水果而不選罐頭水果,還是吃罐頭水果而不是新鮮水果上。不管我選哪一類,格蕾蒂斯舅媽的冰箱裡總會塞爆另一類水果,多得像偷來的鑽石。「他要吃水蜜桃罐頭,但冰箱裡滿滿的都是葡萄,需要快點吃掉……」可憐的格蕾蒂斯舅媽,生活對她而言就是在處理東西。她的最大的樂趣是丟垃圾、清空家裡的食物儲藏室、為那些仍被她稱之為「苦命的巴勒斯坦猶太人」準備一捆捆的破爛貨。但願她死時冰箱空空如也,否則她在棺材裡也會嚷嚷著奶酪發霉了、無籽橙的底部長毛了,擾得子孫後代永不得安寧。
麥克斯舅舅回家了。當我再次撥著布蘭達的電話號碼時,可以聽見廚房裡汽水瓶被打開的砰砰聲。這回接起電話的聲音高高的,話說得很簡略,還顯得十分疲憊。「嗨囉。」
我開始連珠炮似地說:「哈囉-布蘭達-布蘭達-你不認識我啦-你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今天下午在俱樂部時我有幫你拿眼鏡……你叫我幫妳拿眼鏡-我不是俱樂部的會員-我堂妹多麗絲、多麗絲‧克勒門是會員-我打聽過妳……」我喘了口氣,好讓她有機會接話,不過電話的那一端沒有答應,於是我又說了起來。「多麗絲嗎?就是一直在讀《戰爭與和平》的那個女孩呀。當多麗絲讀《戰爭與和平》時,就表示夏天到了。」布蘭達沒有笑,打從一開始,她就是個很務實的女孩。
「你叫什麼名字?」她問。
「尼爾‧克勒門。我在跳水板邊幫妳拿過眼鏡。有印象嗎?」
她提出另一個問題作為回答。而這個問題,我敢說,無論長得醜或長得美的人都會因此而感到難堪。「你長得怎麼樣?」
「我長得……黑黑的。」
「你是黑人嗎?」
「不是。」我答道。
「那你到底長什麼樣子?」
「不如今晚我去找妳,妳自己看看?」
「好。」她笑了。「晚上我會去打網球。」
「不是打高爾夫球?」
「已經打完了。」
「那打完網球之後呢?」
「我會滿身是汗。」布蘭達說。
這倒不是在警告我見面時應該掐著鼻子轉身跑開,這是在陳述事實。布蘭達顯然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只是想事先聲明一下。
「我不介意呀。」我說,但語氣中卻流露出一份想望,希望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一個既不過分講究、也還不算邋遢的地方。「我開車去接妳好嗎?」
她沒馬上回答。我聽見她喃喃地說:「多麗絲‧克勒門……多麗絲‧克勒門……」然後她說:「好。八點十五在布里亞帕斯山莊。」
「我會開一台──」我避開車子的出廠年分。「黃褐色普利茅斯,妳就知道那是我了。我要怎麼認出妳?」我帶著狡猾卻笨拙的笑聲問道。
「我會滿身是汗。」說完她便掛了電話。
我駛出紐瓦克,經過艾明頓、擁擠紊亂的鐵路平交道、扳道工棚屋、木工廠、冰雪皇后 和中古車商場之後,傍晚逐漸涼爽了起來。郊區的地面雖只比紐瓦克高出一百八十呎,卻讓人更接近天堂,太陽變得更大、更低、更圓,不久,我駛過彷彿自轉著露珠的長長草坪,駛過一間間屋宅,那些房子門前的平台上空無一人,卻亮著燈、緊閉著窗,屋裡的人們不願與屋外的我們共同體驗生命的甘苦,將溼氣不多不少地調節至皮膚所能接受的程度。時間才八點;我不想早到,便駕車在馬路上兜風。這些街道都是依東部大學的校名命名,彷彿多年前,當這個鄉鎮在為街道命名時,也一併規劃了它公民們後代子孫的命運。我想起麥克斯舅舅和格蕾蒂斯舅媽:他們在灰暗的小巷裡,坐在海灘椅上分食著一條椰子巧克力棒,襲襲的涼風也如此甜膩,有如來世的應許。不久後,我便開上布蘭達打網球的那條小公園石子路。置於前座雜物箱裡的《紐瓦克市街》地圖,好似已變形成蟋蟀,對我來說,那些長達數哩的柏油路不復存在,夜晚的喧囂大聲地,像血液般重擊著我的太陽穴。
我把車停在三棵蔥蔥郁郁、亭亭如蓋的橡樹下,朝著網球的聲音走去。我聽到一個聲音惱怒地說:「又平手了!」那是布蘭達,看來她已經汗流浹背了。我劈啪劈啪地在石子路上慢慢走著,又聽見布蘭達喊道:「我領先一分。」當我拐一個彎、不小心沾了一褲腳的刺果,又聽見她喊了「局點」。我走入網球場時,只見她俐落地接住在半空旋轉的球拍。
「嗨。」我喊了一聲。
「嗨,尼爾。再一局就好。」她說道。她的對手──一個棕髮、沒布蘭達那麼高的可愛女孩──似乎被這句話給惹火了,於是不繼續找從她身邊飛過的球,反而向我和布蘭達白了一眼。我一下就明白事出何因:布蘭達目前以五比四領先,她對於再一局便可取勝的自負模樣,讓她的對手遷怒到我們兩個頭上來。
不過布蘭達終究是贏了,雖然局數比她預料得多。另一位女孩──名字聽起來像辛普還是什麼的──在打成六平時顯得異常快活,而布蘭達則前前後後不停地東蹦西跳,最後我只看見她那副閃爍發亮的眼鏡、皮帶頭、襪子和運動鞋在黑暗中移動,有時還可看見球在空中飛舞。不知道為什麼,隨著夜幕的降臨,布蘭達在網前衝殺得更狠,明明稍早還有點餘暉時,她始終退在後面,即使扣殺一記挑高球時得跑向網子,她看起來還是不太願意離對手的球拍太近。一股想永保青春之美的強烈慾望似乎壓倒了她每分必爭的熱情。我猜要是她的臉頰被網球擊中而留下一塊紅腫,那一定比失掉世上所有的分數更令她痛苦。然而暮色驅使著她,她也更用力地擊球,打到後來辛普好像還拐到腳踝呢。比賽結束時,辛普拒絕了我開車送她回家的提議,以某部老電影中凱瑟琳‧赫本的台詞作為託辭,說她「應付得來」,顯然她府上大宅就在附近荊棘叢地的不遠處。雖然我因為她討厭我而感到煩惱,但敢肯定的是,我看她更不順眼呢。
「她誰啊?」
「蘿拉‧辛普森‧斯托勞維奇。」
「那為什麼不叫她斯托勞?」我問。
「在班寧頓大家都這麼叫她。那自作聰明的傢伙。」
「妳學校在那邊?」我問。
她撩起身上的衣服擦汗。「不是,我學校在波士頓。」
我不喜歡她這種回答方式。每當有人問我在哪念書,我都會脫口說出「羅格斯大學的紐瓦克學院」。我可能說得太明確、太迅速、太司空見慣,但是我就會這麼回答。布蘭達立即讓我想到那些在放假期間從蒙特克萊爾到圖書館、鼻子長得像巴哥犬的混帳東西。當我為他們的書蓋出借章時,那些人就站在一旁扯著身上笨重的圍巾,直到它們垂到腳跟為止,以暗示自己在「波士頓」和「紐黑文」上學。
「波士頓大學?」我問,並轉向旁邊的樹。
「拉德克利夫學院。」
我們仍然站在以白線劃出邊界的球場上。在球場後面的灌木叢那,螢火蟲在沉悶的空氣中飛舞,繞成了「8」字,當夜色突然降臨,樹葉便倏地發光,彷彿剛剛被雨水所浸潤。布蘭達走出球場,我則跟在她的身後,僅有一步之遙。現在我已經適應了黑暗,她也不再是「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布蘭達了,那陣因「波士頓」而惹出的怒氣也煙消霧散,我開始欣賞她的軀體。她的手沒有拉自己的底褲,但是在貼身的卡其百慕達短褲之下,她的臀形若隱若現。她穿一件白色小領子的Polo衫,背後印著兩塊濕濕的三角形;如果她有一雙翅膀,那兩處就是翅膀長出來的地方。講得再完整一點,她還繫著一條格紋皮帶,穿著白襪與白色網球鞋。
她邊走邊拉上球拍套的拉鍊。
「妳急著回家嗎?」我問。
「沒有呀。」
「我們在這裡坐一下好了,這裡很舒服。」
「嗯。」
我們在草坡上坐下,那坡的斜度幾乎可以讓我們舒適地靠著。從一旁看起來,我們就像正準備仰望天象,親證一顆新星誕生、月亮由虧轉盈。布蘭達一邊講話,一邊扯拉著球拍套上的拉鏈,第一次露出侷促不安的樣子,這使我又緊張了起來。因此,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好要──奇妙的是,一切似乎都會進行得很順利──正式見面了。
「你堂妹多麗絲長得怎麼樣?」她問。
「她皮膚蠻黑的──」
「她是──」
「不是。」我說。「她臉上有雀斑,黑頭髮。她長很高。」
「她學校在哪?」
「在北安普敦。」
她沒有回答。不曉得我的話她究竟理解多少。
「我想我不認識她。」過了一會兒之後她說。「她是新會員嗎?」
應該是吧。他們一、兩年前才搬到利文斯頓。」
「喔。」
沒有新星出現──至少在接下來的五分鐘之內沒有。
「妳記得上次我幫妳拿眼鏡嗎?」我問。
「現在記得了。」她說。「你也住在利文斯頓嗎?」
「沒有,我住紐瓦克。」
「我很小的時候就住在紐瓦克。」她主動地說。
「妳想回家嗎?」我突然生氣了。
「還不想。我們走走吧。」
布蘭達踢了一下小石子,走到我的前面去了。
「為什麼妳天黑之後才會衝到網子前面打?」我問。
她轉過身來,對著我微笑。「你發現了嗎?可憐的辛普阿呆還沒注意到哩。」
「為什麼呢?」
「我不喜歡靠網子太近,除非我確定她回不了球。」
「為什麼?」
「因為我的鼻子。」
「什麼意思?」
「我擔心我的鼻子,我的鼻子整過形。」
「啊?」
「我的鼻子動過手術。」
「妳鼻子怎麼了?」
「有點凹凹凸凸的。」
「很嚴重嗎?」
「沒有。」她說:「以前我就挺漂亮的,不過現在更漂亮。我哥今年秋天也要去整他的鼻子。」
「他也想變得更漂亮?」
她不予理會,又走到我的前面。
「我不是說著玩的,我想知道他為什麼要整形。」
「他就是想……除非他當上體育老師……但那不可能。」她說。「我們都長得像我爸。」
「他也要整鼻子?」
「你為什麼要這麼刻薄啊?」
「我沒有啊。對不起。」轉而我想提出一個聽起來既有趣,又能讓她覺得我不算失禮的問題,不過還是事與願違──我說得太大聲了。「那要花多少錢?」
過了一會兒,布蘭達答道:「一千美金。找屠夫的話就比較便宜。」
「讓我看看那錢花得值不值得。」
她又轉了回來;她站在長凳旁,將她的網球拍放在上面。「如果我讓你吻我,你可不可以別再這麼刻薄了?」
為了不讓接吻的姿勢過於蹩扭,我們還得朝對方多走兩步;但我們聽從衝動就在原地接吻。她一隻手搭在我的脖子上,我把她摟過來(好像太用力了),雙手從她的腰際往上滑行,繞到她的背部。我觸碰到她肩胛骨上的兩塊濕漬,再往下,我明顯地感覺到一陣微弱的顫動,彷彿她前胸的深處有什麼在激動著,覆上一件Polo衫也能感覺得到。那猶如翅膀的拍振,一雙比她乳房還小的翅膀。我不嫌那對翅膀小──因為我無須老鷹將我向上馱升一百八十呎,到比紐瓦克涼爽宜人的肖特山莊享受夏夜。
得獎作品
1959年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