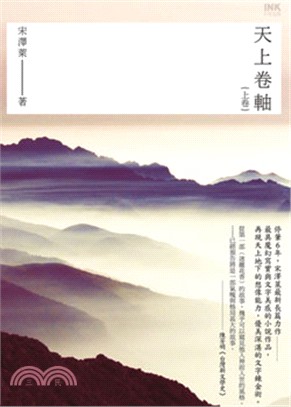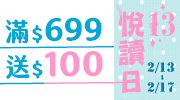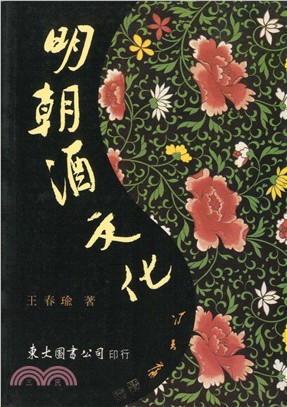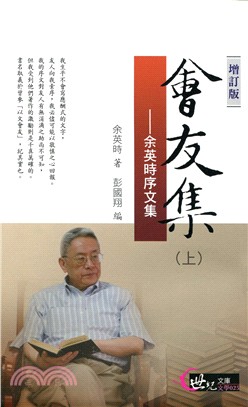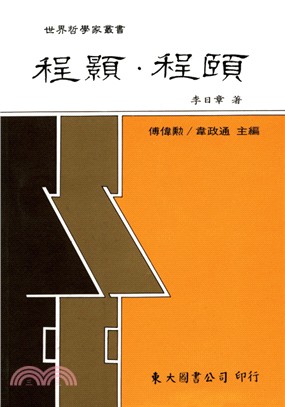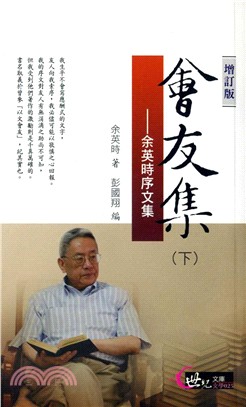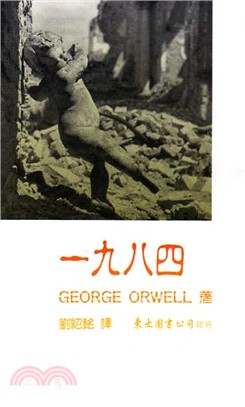商品簡介
停筆6年,宋澤萊最新長篇力作──
最具魔幻寫實與文字美感的小說作品,
再現天上地下的想像能力,優美深湛的文字鍊金術。
從第一部〈迷離花香〉的故事,幾乎可以窺見他入神而入世的風格。
……已經預告將是一部氣魄與格局甚大的故事。──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
本書是宋澤萊停筆6年,再度創作的長篇小說。可說是宋澤萊小說中最具魔幻寫實,最具文字美感的文學作品。再現了宋澤萊天上地下的想像能力,以及優美深湛的文字鍊金術。
故事的主角是北部一位有為、善良的青年。他在令人厭惡、痛心的藍綠惡鬥中離開了北部,一路向著南方,展開驚心動魄的身分認同之旅。他急急奔跑的腳步聲、痛徹心肺的呼喊聲,震動了深埋在地層中千百年前神祕的西拉雅。沿途的迷離花香、山光水色、魔影神蹟構成一幅幅奇異風景,連綴成五彩繽紛的絢麗卷軸。
台灣文學史名家陳芳明曾評價說:「從這樣的理解來觀察,宋澤萊在二○一○年即將發表的長篇小說《天上卷軸》,便是值得期待的全新作品。從第一部〈迷離花香〉的故事,幾乎可以窺見他入神而入世的風格。據說這部小說還在撰寫,現在發表的六萬字成稿,已經預告將是一部氣魄與格局甚大的故事。書信體的這部小說,是一位名叫阿傑的基督教徒,寫信給麥格那牧師的長篇告白。阿傑是一位戰後出生的台灣知識分子,他之信仰基督教,與一位美麗女性潘紫音的點撥息息相關。……」
文學雜誌名編輯家周昭翡曾評價說:「主人翁歷經台灣二○○四年那場撕裂、形成藍綠壁壘分明的總統大選……來到島嶼南端,大量文字勾勒出南方鄉鎮、街景、建築與人物,外在的環境變化對應難以觸及的心靈祕境,進行一場身世的拆解、填補與重現。小說涵蓋相當豐富的元素,我初讀它時,湧現的情感卻異常單純,像故事中那股偶然聞得的花香,彷彿進入一段奇妙的希望之旅。」
前立委、名小說家王世勛曾評價說:「《天上卷軸》除了文字意涵外,也在視覺和聽覺上,帶給讀者心靈極大的滿足感。」「每一個情節、場景的建構與描寫,都令人驚嘆。基本上小說和《聖經》的結合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天上卷軸》卻如此流暢與優美。人稱和描寫和敘述角度的變化,有如畢卡索的傑作!」「真的是嘔心瀝血之作!」
作者簡介
宋澤萊
本名廖偉竣,1952年生,雲林縣人。1976年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一直任教於彰化縣福興國中至2007年退休。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寫作班成員。小說家、詩人、文學評論家、雜誌編輯。曾任大葉大學文學授課駐校作家;現任彰師大台灣文學研究所短期授課作家。
1978年以「打牛湳村系列小說」轟動文壇。兩年間又出版呼應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風格的五本小說;1980年一度轉向參禪;1985年以《廢墟台灣》復出小說界,獲選為當年度台灣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1994年創作魔幻寫實長篇小說《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以及2001年出版的長篇《熱帶魔界》則揉合了寫實、魔幻、大眾的文學技巧,神奇莫測;2002年又出版短篇小說集《變成鹽柱的作家》。除小說創作,尚著有梵天大我散文集《隨喜》、詩集《福爾摩莎頌歌》、論著《禪與文學體驗》、《台灣人的自我追尋》以及台語詩集《一枝煎匙》《普世戀歌》。2011年所出版的《台灣文學三百年》為其最新論著,此書並獲巫永福文學評論獎。
除了作家與教師身分,宋澤萊同時也是台灣本土意識及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和理論奠基者,曾結合同志創辦《台灣新文化》、《台灣新文學》、《台灣e文藝》等雜誌。曾獲吳濁流小說及新詩首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聯合報文學獎佳作獎、吳三連文學獎、東元科技人文獎。
目次
代序
宋澤萊與胡長松的文學筆談
──台灣的魔幻寫實主義小說、基督教小說、西拉雅書寫
手札一:迷離花香
手札二:水面戰爭
書摘/試閱
入神與入世的宋澤萊
陳芳明
堅持一枝果敢的筆,宋澤萊在一九七○年代登場之後,就不再出現任何退卻的神色。縱然他多次回憶年少時期的體弱多病,甚至造成精神頹敗,並無損他長期持續的創造能量。躋身於戰後世代的小說家行列,宋澤萊從未錯過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的政治波動。他的思想與他的書寫幾乎融為一體,他的信念就是他的風格;是七○年代崛起的作家中,少有的堅毅實踐者。
以〈打牛湳村〉在文壇奠定位置之後,他的小說便未嘗須臾偏離台灣社會。在那時代,很少有年輕作家敢於揭露破敗農村長期遭受剝削的真相。宋澤萊在到達一九八○年代之前,就已完成《打牛湳村系列》、《等待燈籠花開時》、《蓬萊誌異》的傑出作品。雖然他為這三個軸線分別命名為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三個時期,對台灣社會表達的關懷卻毫無二致。技巧或藝術上的定義,完全不能遮掩他的入世行動。或者確切而言,如果宋澤萊是台灣意識的重要旗手,他在一九七九年之前的書寫工程早已擘劃他的思想內容。與同輩作家比較,他的小說風格誠然貫徹了他的精神與意志。
在干涉現實之餘,他的文字總是潛藏人道主義的宗教情懷。無上的救贖與無邊的黑暗,構成他小說中的相互拉扯而顯現無比張力。內在的辯論以不同的形式、故事在他的文字裡不斷湧現,尤其進入一九八○年後更為顯著。整個世代在價值觀念上產生巨變,絕對與外在現實的重大事件息息相關。宋澤萊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再也毫不掩飾他的戰鬥批判性格。然而,他並非是單獨一人有此轉向。凡是在一九五○年前後出生的那個世代,無論在島上或海外,都同時承受美麗島事件所挾帶而來的歷史衝擊,每位作家因悲憤而在思想上出現劇烈迴旋。宋澤萊是其中旗幟最為鮮明的一位,既投身於小說創作,也挺筆介入文學評論。
宋澤萊的評論,並非停留於文字藝術的剖析,而是以人權的普世價值來檢驗文學。這樣的批評路數,不僅針對事件後所顯露的精神創傷,也指向往後台灣文學所崛起的新世代。他的行動絕對不是孤立,而是在於延續美麗島運動所標舉的人權精神。他的轉向,可謂用心良苦。當爭取人權的政治運動遭到重挫,他繼之以文學形式維繫其精神於不墜。自稱體質衰弱的宋澤萊,進入一九八○年代以後,一掃過去的陰霾之氣,為當時已呈力竭的台灣文學注入前所未有的批判。
他向文壇繳出一冊雄辯的《誰怕宋澤萊》。書中所收的論文,一時驚駭向來極為持重的前輩作家。以自己的筆名刷印在書的封面,就足夠表現他過人的勇氣。筆鋒所過之處,橫掃了葉石濤、陳千武、陳映真、七等生、楊牧的文學信念。在八○年代漸成氣候的統獨兩派文學,都被他納入批判的行列。宋澤萊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人權派。對他而言,文學之為文學,並非只是負載意識形態而已,重要的是能否以人道精神看待作家所處的社會。如果文學不能面對傷痕,不能治療傷痛,卻只是在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上游移並猶豫,就不可能帶來救贖的力量。
對於當時正在撰寫台灣文學史的葉石濤,在書中被批判為「老弱文學」。文學不能永遠停留在揭露人性的黑暗與社會的黑暗,卻未對自己的生命的徹底反省,將陷於絕望與絕境。他在書中說得非常明白:「我倒覺得作家的條件是對自己有反省,對有限的自己有謙虛,對他人的悲慘有同情,對世界的生老病死有哀悽,對無限的自由有嚮往,對萬物有愛情,對世界的不平等有義憤。」這是宋澤萊首度對自己、對讀者揭示的宗教情懷。也正是在此情懷的驅使下,他無法接受葉石濤的文學信念之欠缺救贖力量。不僅如此,對於陳映真把台灣的民主運動簡單概括為「民主資產階級」,更是表達極大不滿。如果民主運動的目標在於提升人權價值,則陳映真的袖手旁觀與虛假階級意識,只不過是一種精神囈語。
從強烈的批判精神,宋澤萊開啟往後他在宗教信仰上無盡無止的追尋。要理解他在二十一世紀的小說書寫策略,就無法避開討論他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的決裂點。當他為自己立下批判的範式,日後的詩、小說、評論便再也沒有離開台灣社會。從詩集《福爾摩莎頌歌》作為起點,他開始使用台語創作,正如他自己所說,這冊詩集把他帶入「台灣情感的中心地帶」。他的文學動力進入了飛躍時期,關心社會的層面不斷加寬加大。一九八五年完成的《廢墟台灣》,幾乎就是電影《日本沉沒》的台灣版。它可能是到現在為止的唯一反核小說,既揭發台灣人在經濟上的貪婪,也警告台灣人對土地的傷害。它所引起的關注,對後來的反核運動頗具推波助瀾之效。幾近科幻的這部小說,展現了宋澤萊的文字想像,以及他對台灣未來所抱持的危機感。更重要的是,他的台灣意識不再停留於庸俗的政治層面,而是突破個人的信念,使文學救贖擴充到整個歷史命運。他的勇於實踐,在此獲得有力印證。
然而,八○年代以後的宋澤萊,帶給台灣文壇的最大訝異,莫過於他在佛學的浸淫,並由此而延伸出來的文學體驗與思想實踐。很少有一位作家能夠像他那樣,在堅持宗教信仰之際,對於文學創作仍然還是緊抓不放。每部表現宗教關懷的作品,包括《禪與文學體驗》、《隨喜》,以及引發爭論的《被背叛的佛陀》,都顯現了他對佛學的專注投入。佛學可以使人的心靈超越世俗,但是,他在實踐之餘,卻從未超越台灣格局。當他以出世的態度與原始佛教展開對話,並沒有捨棄對台灣社會的關心。或者,確切地說,他的宗教情懷是具有清楚的國籍。充滿台灣意識的宗教觀,再次證明他堅持文學的救贖觀念越來越強化。清楚理解台灣歷史苦難的他,縱然如何抱持何等出世的態度,對於自己身處社會的關心始終是入神而入世。
使台灣文壇感到震撼的是,這位精通佛學的作家,在一九九二年竟陷入困頓狀態,即使他能提升自己抵達無上的阿羅漢境界,卻無法解除他已有家累的事實。這種世俗的羈絆,並不能協助自己完成真正的昇華,反而造成「肉體病變」;一如他自己承認,患了一次腎結石,又為自己帶來嚴重胃酸。他捨棄十餘年的佛教追尋,在一九九三年竟然感覺基督教的「聖靈實體降臨下來」。從一位佛學作家轉向成為基督教作家,可能是台灣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事。然而,沒有經過親身的體會與覺悟,可能會視為神祕的事件。但是,對於一位在精神與思想上產生會通的作家,或許不是奇異的經驗。沒有穿越如此奧妙的轉折,宋澤萊就不可能到達《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
長達二十餘萬字的這部小說,幾乎可以說是他文學經驗的集大成。全書主旨環繞台灣的黑金政治,以選戰為中心,直探社會底層的貪婪慾望。小說筆法融入現代主義、寫實主義、魔幻與偵探的種種敘述技巧。他忠實於自己的聖靈體驗,也忠實於自己的社會經驗。他的小說是要寫給教外的人來看,但不必然是寫給台灣以外的人來看。歷史的體悟,使他的宗教小說永遠貼近台灣,而且是赤裸裸貼近台灣的政治現實。具體而言,在他的信念裡,他優先要使台灣獲得救贖,然後才能及於其他。因此,他的宗教精神完全不可能像外國傳教士那樣,可以捨棄自己的鄉土,遠赴異國去宣揚神諭。他的宗教與文學,牢牢根植於台灣這小小海島。這種具有國籍的信仰,完全迥異於基督教傳統。這正是宋澤萊的文學特質,沒有任何一位作家能夠輕易模仿或取代。
從這樣的理解來觀察,宋澤萊在二○一○年即將發表的長篇小說《天上卷軸》,便是值得期待的全新作品。從第一部〈迷離花香〉的故事,幾乎可以窺見他入神而入世的風格。據說這部小說還在撰寫,現在發表的六萬字成稿,已經預告將是一部氣魄與格局甚大的故事。書信體的這部小說,是一位名叫阿傑的基督教徒,寫信給麥格那牧師的長篇告白。阿傑是一位戰後出生的台灣知識分子,他之信仰基督教,與一位美麗女性潘紫音的點撥息息相關。
整個故事以雙軌敘事的方式開展,一是二○○四年的選舉持續了綠色執政,一是阿傑這位藍色陣營人物無法承受本土政權的崛起,而開始尋找失聯已久的夢中女性阿紫。敢於斷言這是格局巨大的小說,在於整個故事寫到六萬字時,阿傑仍在依循神蹟式的花香去尋找阿紫,卻還未確定她的蹤影。在尋找過程中,阿傑反覆表現了他對綠色執政的厭惡,彷彿遭到天譴一般,甚至還數度否認自己是基督徒。這可能是二十一世紀台灣政治的最佳寫照,也是當前台灣知識分子意識形態迷障的最好反映。在敘事過程中,毫不避諱描述神蹟的出現。但是,他並不傾向於魔幻技巧,而是回歸到素樸的寫實手法。
由於小說還停留於未完階段,任何臆測都有可能落空。但是,進入五十歲後半期的宋澤萊,創作能量未嘗稍緩。新小說或許將成為另一傑出作品亦未可知,畢竟故事所觸及的議題,頗為引人入勝。從七○年代就已整裝出發的他,小說技巧變化多端。在創作之餘,又涉入評論工作。宋澤萊之迷人與惱人,就在於他以各種文體干涉政治、干涉社會,而且引發不計其數的論爭。他的宗教信仰,由佛教轉入基督教,更創造了他文學生涯的神奇,以宗教關懷來追求救贖之道,卻又全然沒有犧牲文學應具備的藝術分量,這正是宋澤萊成為宋澤萊的最大魅力。
絕望中的希望之旅
周昭翡
對宋澤萊的印象,首先是「鄉土」。就他過去的創作成績,這也是最廣為人知的。
三十多年前,宋澤萊的《打牛湳村》系列小說,深刻記述了台灣農村的變遷與困境,農村人口的老化流失,標榜民主的台灣選舉文化在農村帶來的影響,生動反映了農人的喜怒哀樂。全然不同於過去鄉土小說純樸的基調,宋澤萊以犀利的筆調陳述,農村成為了鄉代、立委聚斂善良農民血汗錢的所在,作為農民,無論順從、叛逆,在不合理的機制之下,遭受的命運一樣悲慘無助,可說是國民政府長期對台灣鄉土資源貪婪、無能的政治作為之下的證據。這一系列作品「把爭論紛云的鄉土文學推向一個新的水平」(陳映真語),為鄉土文學開創出新的里程碑。
越是相信小說的社會改革力量,殘酷的現實越令人感到苦悶絕望。八○年代的宋澤萊,投注極多心力在佛教義理的鑽研,尤其是從原始宗教經典中解析人生奧義,宗教色彩進入鄉土寫實小說中而溢出寫實,《蓬萊誌異》、《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等,帶著幽微神祕的氣氛充滿宗教天啟的意義。
他小說中罕見的批判視角,在在形成主流之外的獨特聲音,彌足珍貴。
然而,「宋澤萊是個出人意料的作家。」(施淑語)。作為鄉土文學標竿性人物的宋澤萊,本期發表了六萬字新作《天上卷軸》。儘管觀念上,「以血統、文化來論身分可能毫無意義」,但小說中,設定的主角身分卻明晰可辨:外省第三代成長於都市,具基督教信仰。這小說角色對宋澤萊無疑是一次大膽嘗試。主人翁歷經台灣二○○四年那場撕裂、形成藍綠壁壘分明的總統大選。「忘記了一向思考的制高點,被困於這個沒有答案的人世間,被困於這個貧乏的必死的自己內心,終而在鬱鬱的情緒中找不到出路。」主人翁也藉由這明晰的身分,在寫給牧師一封一封獨白信中,一道一道反覆破解生命的難題,重新看待故鄉及異鄉的意義,在懷疑否定中逐漸感受神的意旨,在勇於更改行程中尋找心靈的平靜。原對島嶼地名甚至都是陌生的主人翁,來到島嶼南端,大量文字勾勒出南方鄉鎮、街景、建築與人物,外在的環境變化對應難以觸及的心靈祕境,進行一場身世的拆解、填補與重現。
這部集大成式的小說,可以從很多層面來理解:台灣的魔幻寫實主義、基督教小說、西拉雅書寫等(見宋澤萊與胡長松筆談)。於現實意義上,人生不免一再面對絕望的時刻,特別是這人心徬徨的年代。雖然小說涵蓋相當豐富的元素,我初讀它時,湧現的情感卻異常單純,像故事中那股偶然聞得的花香,彷彿進入一段奇妙的希望之旅。
我必須朝著南方走
*95.
在今年初,剛過新曆年,天氣還在隆冬中,學姊阿紫已經準備好要動身到日本去進修課業。臨行的前幾天,他邀我去淡水玩。我問她為什麼不到其他地方,她說只有港口才能給他的家鄉的感覺,因為喜歡海,即使不是汪洋一片,只要接近海邊,看到漁船,就能略減她對家鄉的思念。我只能說:「是。」就下山,到校舍找她,而後就與她搭了捷運,往著淡水而去了。
這是幾百年前的凱達格蘭部族的故鄉,經過西班牙人佔領,荷、鄭的統治,先變成一個禁錮於海峽的小港灣,到一八六二年因為清朝打了敗仗,才開放向外國通商,自此以後,開始繁榮起來,本身等於一個小型的台灣歷史。我開始大量研讀台灣本土文化,就是由台北這個小港口出發;我認為學姊阿紫早知道我讀了許多這個市鎮的風物,她暗中在鼓勵我實地考察,也等於暗中參與了我的研讀,我真感謝她的體貼。
因為是星期日,人潮比較多,我們一大早就出發,準備先在老街,再到紅毛城,再到漁人碼頭玩一整天,直到晚上才回來。
那天,天氣稍微回暖,冷風大減,太陽還露出了臉。我還記得,由於要出去遊玩,她背著一個輕巧的紫色皮包,臉上只做了淡妝,頭髮稍稍剪短,留了一個輕盈飄逸、散發知性的包伯頭,但是她的眼睛仍然顯得烏黑而深邃,宿含了著一種顫動的靈魂,一直伴著她細長玲瓏的身子往上升高,不過她彷彿故意將那種靈動掩蓋在剪齊的額髮下,盡量收斂,彷彿怕人看到了那裡頭的美。她的燙捲黑髮分垂兩肩,細長玲瓏的身子穿一件卡其色連帽針織長柔外套,內搭白色毛領上衣,咖啡色緊身尼絨長褲,圍著一條卡其色圍巾,咖啡色平底鞋,總之是一身巧克力色的打扮,如此成熟而誘人。我穿了一套外出藍、白兩色搭配的冬日休閒服,背著咖啡色小相機。當我們抵達淡水時,已是早上九點。
麥格那牧師,我不知道一個女孩子會有多少細如髮絲的心思,也不知道她會有多少種不為人知的變貌,這些我都不太懂,因為我軍人的家庭叫我為人要耿直、莊重,祖父所教導的國家、領袖、責任、榮譽觀念都制約了我的行為,自幼以來接觸的女孩子太少。我和學姊阿紫是牽過手的,也背靠背坐著談心過,但是我對她仍然很無知。那天,我被她的變貌所驚嚇。她一點都不像是以往的提琴社社長,態度和談吐與往日很不相同。我猜想她大概是要暫別台灣了,不再被這裡的工作所束縛,所以她放開了音樂演奏家的身段,恢復成一個真正的單純的女孩子。由於穿平底鞋,身高已經比我略矮,她的崇高的味道不見,行動顯出了我想不到的靈巧敏捷。
她竟說她要「瘋」一下。
在淡水老街,我們彷彿放棄了基督徒的身分,在雕龍畫鳳的「福佑宮媽祖廟」「落鼻祖師廟」和「龍山寺」參觀起來,這三家寺廟都是百年以上的寺廟,香火鼎盛,古老的浮雕、燻黑的神龕、風化的板岩,都烙滿歲月的痕跡,以旺盛的生命力,延續立足在這個地方。在祖師廟,她問我,爲什麼那個神像叫做「落鼻祖師」。我就說我曾在風物介紹書籍裡看到,當中法戰爭時,由於這個神明要警告淡水的人防禦法軍,就犧牲自己,落下鼻子,告訴人們這個危機將至,果然不久,法軍就攻打淡水了。阿紫聽了,很驚訝,她就說這和耶穌犧牲自己拯救人類有共通的意思;她就說有一天要到淡水來傳教,說落鼻祖師就是耶穌的弟子,只是大家不明白而已;我就誇讚她很有想像力。在昔日繁華褪盡的媽祖廟裡,她愉快起來,說她來到了女性主義的聖地,就說要和我捉迷藏,她說她要當鬼,讓我捉她,如果捉到了,要犒賞我。我們於是就在寺廟裡奔跑起來,由前殿跑到後殿,由左側廂房跑到右側廂房,追逐不停,她被我抓到了,不甘心,就又重來一次。由於太瘋狂了,腳步驚動了熙攘往來的參觀者,竟以為我們出了什麼事。後來,我們奔出了寺廟,在中正路、重建街、捷運站附近快速蹓韃起來。阿紫不放過任何一個該參觀的地方,我們逛過淡水禮拜堂、馬偕石像公園、藝品店、電影院、傳統糕餅店、牛角麵包店、手工餅舖、吃巨霸霸冰淇淋……。到了中午,我們餓了,重回龍山寺附近的市場來,在喧鬧的攤販座位坐下,她叫來了蚵仔煎、炸粿、魚丸湯,吃完,不滿意,竟叫來一甕佛跳牆,大聲地說:「我不是淑女喔,我不是淑女喔!」然後大大地吃起來。我驚訝非常,想要制止她,開玩笑地對她說:「要是如此,將來你的丈夫一定會在幾天之內被你養胖,變成一個大腹便便的不倒翁!」她用美麗的眼睛盯著我看,就說:「這就是一般世俗人所說的幫夫運,我有幫夫運喔!你不相信嗎?」她哈哈大笑,又吃起來。於是我只能說:「是,是!」也不服輸地和她搶起佛跳牆了。後來她說吃佛跳牆就是捉到她的犒賞!
*96.
下午,在「紅毛城」,我們看得更為仔細。最早被西班牙人命名為「聖‧薩爾瓦多」的這個城,到現在已經將近四百年的歷史了。但是最早的西班牙建築風貌已經無可揣摩。它應該是拆毀以後,由荷蘭人再在原來的地基上再蓋起來的。它也不完全是荷蘭時期的原貌了,而是歷經了明鄭、滿清的改造,後來清廷又租借給英國人,做為英國領事館才變成如今的面貌的。據文獻記載,英國人租城以前,主城堡是一棟有著灰白顏色外牆的城,以後再改為紅色。主城以外,英國人於一八七七年在旁邊又建了一棟英國設計師所設計的領事官邸,也是二層紅磚建築,屋身較低,但顯然風格比較精緻講究。因此,我們就必須兩邊都加以考察了。
我們在主城的內部仔細用手撫摩過每個牆面,感到那歲月的腳跡依稀跳躍在我們的皮膚上。那主城內部的半圓筒形窟窿結構建築手法實在高明,阿紫看了很滿意,她說她去過歐洲許多次,有許多古老教堂邊的房子內部也有這種結構,對她來說,似曾相似,很有意思。我就告訴她,文獻上記載,在英國租借期間,主城的一樓曾經改為四間監獄,實際上監禁過許多人。阿紫一聽,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後來,阿紫說她又要「瘋一下」。這次她要扮成天使,消失在我的眼前,要我去找她。她有可能出現在主城的內外,也可能出現在旁邊領事官邸的一、二樓,她限定時間,要我找到她,如果找到她,仍然要犒賞我。我實在有些受不了,因為早上爲了捉她,跑得有些累了。但是我不能推辭,就說:「好!」因此,我必須更加擴大規模,在兩棟建築的內外穿梭起來,忙亂地找她了。我們迅速的腳步震響建築的每個內部角落、外面走廊,完全不管參觀的人,引來許多的側目,他們大概覺得我們真的瘋了。在一個多小時裡面,我身上出汗,她也被我找到了許多次。後來,我們來到領事官邸的一個優雅的歐式會客室,內部有一個精雕長桌,和十張豪華高背繡花皮面椅子;桌面有十副潔白咖啡盤盃,排列整齊;旁邊有一個典雅的壁爐,上頭掛一幅淡水漁港風景;那精緻厚重的窗簾掀開,可以見到窗外的冬日草木;整體反映出昔日歐洲家居韻味的古色古香。阿紫跑到這裡,就不再跑。她居然拉開椅子,就坐在長桌主人座位上。我告訴她,這是官邸展示家具,不是給參觀的人坐的。一會兒,她才起身,狀極滿意。她說這個會客室真好,如果誰有這樣一個會客室,她就嫁他!我就說,那阿紫不就是嫁給歐式會客室了。她笑得很開懷說:「這只是表示我很有眼光!」我只能說:「是,是!」之後,我們走到外面的咖啡座來喝茶;再後來,我們到了冬日草坪上,背靠背,坐下來看冬日的天空,這時,我聞到了她的身體所散發的香味,就說:「阿紫,妳好香。」她就說這是對我的另一次犒賞!
*97.
不知不覺,黃昏來臨,我們走到了漁人碼頭來了。本來只是一個小小漁港,如今經過了改造,變成了漁業和觀光並行的一個現代港口。不論浮動碼頭或是半圓形的劇場或是景觀平台或是戶外的雕塑公園或是防波提上架設的三百公尺的木棧道,都具有很高的當代感。尤其是去年,橫越港區的人工大橋徹底完成,被命名為「情人橋」後,這裡人潮更加暢旺起來,這座流線型彎曲造型單面的斜張橋,彷彿張開白色風帆的一艘長船,遠遠伸張在天空與水色之下,更加深了這裡的流動感。我們靠近了鋼製的情人橋橋塔,要別人幫我們拍了照片,留下紀念;又在約五公尺寬的橋上行走,看著橋下的海水和漁船,真正感到我們的確已經離開了台北的喧囂和雜亂,有了一種清靜。
此時,正值冬季的枯水期,港口的水是少了一點,但是浮動碼頭邊的漁船仍然擁擠。一艘艘的船繫在圓形的木樁上,羅列在水上,猶如一張張休閒用的小床。我們並坐在港邊的行人座上,看著動盪海水的碼頭,甚感愉快。阿紫滿意地說,幼年唸小學的時候,常常到故鄉的碼頭去送餐點給親戚,她被那些熱帶的彩色船迷住,就在那裡寫生和遊玩,往往忘記回家,她說碼頭給她許多的回憶。然後,她站起來,對我說她又要「瘋一下」。這次,他既不扮鬼,也不扮天使,她要扮人。她又宣佈規則說,這次她要在廣闊港區四周走,她不躲藏,讓我始終都能看到她,但是她要先離我遠一點,叫我去追她,如果我能追到她,一樣要犒賞我。我不知道這個女孩子在想什麼,先前我們已經玩得那麼火熱,這時她也應該很累了,居然還有力氣玩。但是阿紫說得那麼認真,我就是不忍心推辭,就說:「好!」於是她以非常快的速度衝出去,在碼頭區奔跑起來,在遙遠的地方大喊:「來追我呀,來追呀!」我也不客氣,開始在她身後追起來。我從沒想到阿紫的跑步能力這麼高,她放足奔跑,猶如一匹小馬,充滿動力,腳程快捷,真的表現了海邊女孩那種赤足在海岸狂奔的能力。好幾次,我幾乎要趕上她,觸摸到她時,她都跑掉了,到最後,就只能遠遠盯著她,不讓她離開我的視線而已。有好幾十分鐘,我們就這麼維持了遠距離的關係,她一點點都不讓我靠近她,我只能一心一意,盯著她看。最後一個時段,我不甘心,下定決心一定要追到她,就更改策略,沿著港區緊迫釘人,契而不捨地急走,想要磨掉她的體力,她發現我的詭計,跑上了情人橋,在那裡高高看我。此時,淡水夕照早已經展開多時,天邊現出了金、紫、青、紅的雲彩,天色恐怕就要轉暗了。我馬上也追上去。不過,就在情人橋的尾端,要走下橋的地方,我發現她似乎突然跌倒,整個身子彎了下去,蹲坐在那裡,再也無法站起來。我非常震驚,立刻跑過去,發現她斜撐著身子,臉面有些發白。我迅速蹲身下去,把她抱起來,用右手一把攬住了她的腰,她斜躺在我臂灣,頭往後仰,左腳彎曲無力踩著地面。我大聲說:「到底怎麼了,阿紫,妳怎麼了?」她急速喘氣,說:「沒什麼,好像腳扭傷了,你不要放開我,扶我到底下小花園那裡去。」於是,我摟著她,朝著造景小花園往下走。這時,我才發現女孩子的腰竟然這麼柔軟,就好像接觸到滑動的深水,若有似無,虛實之間無法叫人用手指把握。這時我已警覺到我的手竟然放在她內搭的白色衣服上面,她腰間的體溫正透過薄衣,不斷傳到我的手掌上。我大吃一驚,差一點把手縮回來,忍不住對她說:「阿紫,妳的腰好軟!」她停止喘氣,對於我的卑劣行為渾然不覺,笑起來,說:「這叫做玉軟花柔,只有美女才會有的喔,你們男生不是最喜歡這樣嗎?」我真的怕她的腳繼續痛,聽了,只好趕快說:「是,是!」我補充說,她真的不要跑得那麼快,我又不是黑天使會吃她,何必怕我追到她,這樣一定會跌倒的。她卻說:「不這樣,你敢過來抱我嗎?你敢過來摟我嗎?傻瓜。」我聽了,臉似乎就熱起來,只能又說:「是,是!」就更加摟緊她的腰,往小花園走過去了。之後,她當然說摟她是給我的第三次犒賞!
*98.
到晚上,他的腳傷已經復原,我們重回淡水街上,率意地在街上走。她要我陪她去逛女性服飾店,一家看過ㄧ家,凡是試穿時,她都要我給她一些意見;她買了幾件要攜往日本的典雅冬裝,很有重量,我趕快幫他提著。最後,我們來到男性服飾店,她替我買了一條圍巾,卡其色的,就像她圍在頸子上的那條圍巾!
當我送她回到盆地底的學校時,已經深夜,商店都關了門,四周的人家都已經睡了,雖然冬風不大,但是仍感酷寒,街上行人稀少。
在校門口,我和她告別,她用手過來撫摸我的臉,低聲地說:「謝謝你陪我玩了一天,由日本回來後,希望你能再這樣地陪我玩一次,我覺得很好;我去日本後,如果想我,就寫信給我。」然後,又用眼睛盯著我看,說:「不要生病了,阿傑,萬事都有神為我們撐著,要勇敢走主的道路,就像今天一樣,起來奔跑,像保羅一樣,一點點都不要氣餒退怯,對吧,帥哥!」這時她在冬風中的手顫抖起來,好像心底有了重大的負擔,我竟發現她的眼睛裡有一串的淚。她的一句「不要生病了」這時打醒了我,我才醒覺,原來她已經知道我的病況,她必定已經由麥格納牧師您那裡探聽到我生病的消息,也一定知道我不定時會在床上發病的事。原來今天她所做所為,包括我們不停的奔跑,包括她扭傷了腳,都是為了要誘導我離開不振的世界,為了掃除我內在裡的陰霾,使我能重新振作行動起來。我竟叫一個好端端的女孩,犧牲了一天的時間來取悅我,我算什麼男孩子!?然而我竟也會在一天之內無知無覺!想到這裡,我非常震驚,我竟然不了解學姐阿紫對我的用心。我萬分愧疚,只能點點頭,顫抖地去抱她,說:「阿紫,不要哭。」……。
*99.
是的,阿紫對我我的期待如此深重,她的情義足以讓我用一生去報答,而上帝小小的初步回答,就透過她那天給我的情義顯露出來了:
記得就在那個情人橋上,她腳扭傷坐在小花園旁邊不久,夕陽消失,她卻勇敢地站起來,堅持說要陪我看夕照。我趕緊攙扶著她,走到狹長的棧道上,靠著欄杆,望著西邊看。那時,夕陽早就下山了,所有的霞光只剩下暗金色,所有的西邊晩雲俱已烏黑,連同那海水也成為影子。我不禁開始爲阿紫做默禱,希望她的傷勢立刻好起來;同時我也爲自己的沮喪再做一次禱告,希望擺脫無邊虛無的異教大監牢。這時,由於冷風吹來,我摟著她的腰,併肩越靠越緊,阿紫的香味就從針織長柔外套暗暗傳過來,這時我感到很愉快,就又想要再一次告訴她說她很香。忽然就看到已經黑暗的西邊天際彷彿裂開了,一時之間,天光明亮,彷彿正午,眼前洞開了一片的汪洋大海,比碼頭外的大海更大,更加遼闊,一片無限的湛藍,我彷彿是在半空望下看,發現在那片海水中,有一個島,上頭許多高聳的海礁,有一個人站在礁石上,指著海面,那海面浮起「得救」「南」這幾個中文字,然後隨著海流,悠然地流向遠方,直到不見,那視景就消失了。
我大吃一驚,倒退了幾步,在阿紫的背後說:「現在是正午嗎?是正午嗎?天空怎麼那麼亮?」阿紫囘過頭來,笑著說:「不要胡說嚇人,現在已經是夜晚了!」我趕緊鎮定心神,閉口,趕快過去摟她,什麼也不敢再說了!
麥格那牧師,這正是另一個全新的異象,聖靈給我的的異象,那「得救」「南」三個字正是祂給我的回答,似乎告訴了我,唯有我朝著「南方」,才能找到「得救」的答案。這也正是我如今來到南台灣的原因之一啊!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