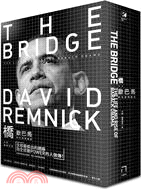橋:歐巴馬的生命和崛起
商品資訊
ISBN13:9789868845404
替代書名:The Bridge: The Life and Rise of Barack Obama
出版社:八旗文化
作者:大衛.雷尼克
譯者:林曉欽 等
出版日:2012/06/27
裝訂/頁數:精裝/656頁
規格:23cm*17cm*4cm (高/寬/厚)
版次:1
適性閱讀分級:672【十一年級】
商品簡介
目前唯一一本關於歐巴馬的最權威傳記。
全球最傑出的總編為全球最耀眼複雜的政治偶像做傳!
× × ×
他,歐巴馬,二十一世紀初全球最耀眼的政治偶像,究竟是什麼、又不是什麼?他何以重要?值得書寫,並在人物傳記史上居於何種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此之前,我們唯一可以深度瞭解歐巴馬其人的只有他的回憶錄,1995年的《歐巴馬的夢想之路──以父之名》。這是一個男孩如何尋找父親,並從中領悟到自己是黑人的真諦;而本書中,大衛•雷尼克提供給讀者的是,他如何成為他自己(種族意義上的那個非裔美國人),如何成為象徵美國的種族及多元文化歷史敘述的美國人(而非黑人),並最終成為一名美國總統的歷程。這是一本更浩瀚磅礴、客觀深入、更抽絲剝繭、歸根就底地完整呈現歐巴馬是誰、他的生命哲學和政治哲學的偉大傳記。
作者鉅細靡遺地調查了歐巴馬幾乎所有的相關文獻與言論,包括他的身世、家族背景、投票記錄,發表的文章,更訪談了上千名和他相關的人,更多次深度採訪歐巴馬本人,取得大量第一手實證資料,從而再現斯人,再現其生命及其崛起的歷程。
歐巴馬是誰?他打哪兒來?他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最終如何說服民眾相信,正是美國文化中特有的東西塑造了他,而他個人的歷程,恰恰是這個國家的政治歷程。歐巴馬的故事,也正是這個國家的敘事,他從小生活在多元文化的印尼,以及種族天堂的夏威夷白人家庭中,他的種族身份不夠白,也不夠黑,但他恰恰用自己黑白混血的身份贏得更大的支持,並進而讓美國人團結起來共同推動政治與道德上的進步。他本人不一定是創造這個歷史趨勢的英雄,但他恰恰有可能是這個趨勢中的巔峰。最後,他走進了那座由黑奴建造的白宮。
作者把歐巴馬的生命個體置身在全球各地——肯亞、印尼、夏威夷、美國本土,在宏大縱深的政治歷史文化背景中檢視何以這個初出茅廬的非裔美國人可快速崛起。他是美國融合了多元種族和文化的象徵,非裔美國人的歷程正是美國的歷程,前者的權利日益完整,後者才會漸趨完美。因此,這本書與其說是一個總統歐巴馬的政治成長史,不如說是一個偉大的人如何在大歷史中定義自我,並塑造那個自我的歷史。
「是的,這就是我的故事。」歐巴馬如是言,他的身份既是先天既定的,也是後天選擇的;他追尋著這一身份,也習得了這一身份,因此,他才可能帶領美國人跨越那座融通了不同的種族、膚色、紅藍各州、保守派和自由派,以及不同世代的無形之橋。
全書共有五十多萬字,是名人傳記類登峰造極的鉅作。除了文字上令人愉悅和震撼外,這本書對於台灣的讀者也別具意義,台灣的政治和政黨一直糾纏於族群議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歐巴馬的故事令人深思,提供了借鑒。台灣的政治和道德上的進步,需要一位在族群議題上和歷史與當代包容、連接和貫通在一起的典範嗎?如果答案是需要,我們進一步要問的是:他是誰?在何方?何時會出現?
本書特色
★ 經濟學人雜誌2010年十大好書。
★ 普立茲獎得主, 《紐約客》雜誌總編輯大衛•雷尼克宏大鉅作。
★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盛讚:「全球最傑出的總編為全球最有Power的人做傳!」
★ 訪談人物超過千位,鉅細靡遺,資料翔實,敘事深厚,是瞭解歐巴馬人生和政治哲學的最佳作品!
★《橋》由Alfred A.Knop出版公司於2010年4月6日上市,首刷精裝本就賣了十二萬冊,書評界更是佳評如潮。
★《最寒冷的冬天》大衛.哈伯斯坦讚譽雷尼克乃媒體「明日之星」。
作者簡介
★ 一九九四年以報導蘇聯解體的《列寧的墳墓》榮獲普立茲獎!
★ 擔任《紐約客》總編已十餘年,被讚譽為美國文壇最閃亮的巨星!
★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盛讚此書為「全球最傑出的總編為全球最有權勢的人做傳!」
大衛•雷尼克(David Remnick)
美國久負盛名的記者、編輯和作家。他從1998至今擔任美國《紐約客》雜誌總編輯,1994年以《列寧的墳墓:蘇維埃帝國的輓歌》一書榮獲普立茲獎,1999年獲選為「年度最佳編輯」。他關於拳王阿里的傳記也被《時代》評為2000年年度最佳傳記。
雷尼克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主修比較文學及俄文,一畢業即到《華盛頓郵報》當社區記者和體育記者,後出任該報駐莫斯科特派員。在《郵報》服務十年後,雷氏於一九九二年轉至《紐約客》當主筆,六年後升任總編輯迄今。他不僅把《紐約客》帶到另外高度和風格,也網羅寫手如雲,如何偉(Peter Hessler)等,其《尋路中國》等中國三部曲的部分章節最初刊發於《紐約客》。雷氏文筆汪洋恣肆,感染力極強,往往深入鋪陳,把讀者帶入歷史縱深,他立論中肯,講求細節的豐富和實證態度,故一本書所採訪的對象多達千人。當年,大衛.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就預測,雷尼克乃是文字媒體的「明日之星」。
書摘/試閱
第一章|複雜的命運
一九五一年,肯亞首都奈洛比,一個再平常不過的一天。一名城市衛生檢驗員獨自坐在辦公室裡,他二十一歲,圓臉,眼睛分得很開,是個聰明又年輕的非洲小夥子。在一個政治動盪的年代,他的抱負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但彼時的他還正在為當地衛生部門檢驗牛奶樣品。二戰結束之後,肯亞的獨立運動開始興盛,殖民政府當時就已經開始鎮壓。而到了一九五二年,英國人則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並且採取一整套方案,如逮捕,拘留,刑訊和謀殺等等,以此鎮壓基庫尤民族主義運動(Kikuyu),也就是英國人所謂的「茅茅叛亂」(Mau Mau rebellion)。
門開了,一個白人女子跨了進來,手裡提著一瓶牛奶。為了確保食品在流入市場之前沒有感染病菌,農民,歐洲人和非洲人都會三番五次地到這間辦公室來送檢食品。
這名年輕的小夥子主動起身,希望提供幫助。在衛生局裡當一名訓練有素的職員,當時被認為是個體面的工作。小夥子出生長大於肯亞東部的乞力馬柏格農場,那是一處廣袤無際的劍麻地,主人威廉•諾斯魯普•麥克米倫爵士,屬於那種上層的白人階級。這片農場位於錫卡附近的一片「白人高地」之中,其土地全部歸歐洲人所有。農場主總是隨身帶著一根河馬皮做的鞭子,掄起鞭子來毫不遲疑。這名衛生檢驗員的父親目不識丁,但他擁有一個相對特權的工作:在這片土地上擔任工頭。這家人住在一間沒有電也沒有水的竹泥棚屋裡,但父親一個月可以掙七美元,足夠把兒子送到曼古鎮上的一家教會學校——聖靈學院去讀中學。這個年輕人在那裡學習了英語,也學到了亞伯拉罕•林肯和布克•華盛頓的事蹟。然而,沒過多久他就走進了死胡同:在學校裡只能學到這些東西,沒有教科書,學生們有時只好在沙子上寫功課。肯亞沒有大學,歐洲的孩子會回「家」去上學,少數念得起大學的黑人得去東非的其他地方。儘管這個年輕人曾想努力學習,以便將來能當上神父,但是,正如他後來說的,肯亞的白人傳教士「和其他人一樣,一直告訴這個非洲人,他還沒有為各方面的發展作好準備,他必須保持耐心,相信上帝,等待著他能夠充分發展的那一天。」因此,年輕人擱下了當神父的念頭,靠領取獎學金,就讀於皇家衛生協會旗下的一所衛生檢驗員培訓學校。
歐洲女人冷冷的看著這個年輕的小夥子。年輕人名叫湯姆斯•約瑟夫•穆博亞(Thomas Joseph Mboya),但女人看上去並不想知道他的名字。
「這裡沒人嗎?」她說,眼睛直盯著湯姆•穆博亞。
當湯姆還住在威廉爵士農場上的時候,他父親曾經告訴他說,「不要和白人作對。」但湯姆無法忍受農場主,無法忍受他的皮鞭,無法忍受他頤指氣使般的昂首闊步;他還無法忍受一個事實,檢驗局裡白人同事的薪水是他的五倍;而如今,在這尋常的一天,他無法忍受這名無禮的白人女子,她凝視著他,卻絲毫無視他的存在。
「夫人,」他說,「您的眼睛可能出問題了。」
女人大步踏出檢驗室。
「我必須得找歐洲人幫我檢驗,」她說。「這男孩真夠粗魯。」
彼時的湯姆•穆博亞和其他無數肯亞人一樣,在傾聽著喬莫•肯亞塔(Jomo Kenyatta)的演講中長大。喬莫人稱「燃燒的長矛」,是老一輩政治家,也是肯亞獨立運動中的意見領袖。不僅僅是肯亞,反殖民主義運動正在整個非洲蓬勃發展,包括奈及利亞、剛果、喀麥隆、黃金海岸、多哥、塞內加爾和法屬蘇丹組成的馬利聯邦、索馬利亞、馬達加斯加。
一九五五年,當穆博亞二十五歲時,他贏得了一份難得的獎學金,前往牛津大學的拉斯金學院學習一年,在那裡,他鑽研政治與經濟學,加入了工黨俱樂部和社會黨人俱樂部,還發現了一個由反殖民主義的自由黨派教授組成的圈子。穆博亞此前沒有上過大學,在拉斯金的這一年促使他思考一個問題,即其他的肯亞人是否有機會從國外的高等教育中得到些什麼。
在穆博亞回到奈洛比後的第二年,他便開始以活動家和工會組織者的身份聲名鵲起。殖民統治的最後十年,喬莫•肯亞塔幾乎都是在監獄中度過的,因此,出身少數民族盧奧部落(Luo tribe)的穆博亞,便因其年輕有為又富有領袖魅力而嶄露頭角,這十年間,人們視之為後殖民時代肯亞的未來領袖以及新一代的政治家。肯亞塔固然是獨一無二的肯亞英雄,但他屬於老一派的反殖民鬥士,是靠著身邊一群忠心耿耿的基庫尤人起家的。相比之下,穆博亞更有前瞻性,他希望肯亞能夠超越部落隔閡,藉由民主自治和自由經濟的發展而凝聚起來整個國家。
一九五七年,在肯亞立法會議中的非洲人席位數目上,英國人作出了讓步,二十六歲的穆博亞代表奈洛比選區贏得一席。這個選區主要講基庫尤語,而他出生的盧奧部落,則是來自肯亞西部維多利亞湖附近的地區。不久,穆博亞就成了肯亞非洲民族聯盟(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以及肯亞勞動聯合會(Kenya Federation of Labor)的總書記。他既是一個魅力四射的演說家,也是個成績斐然的外交家。還不到三十歲,穆博亞就成了國際上知名的反殖民主義與民權運動的標誌性人物。在美國,他見過埃莉諾•羅斯福、理查•尼克森、瑟古德•馬歇爾、羅伊•威爾金斯,在一次民權集會上他甚至與馬丁•路德•金恩共用一方舞臺,發表演說。在肯亞塔不在的時期,穆博亞率領代表團前往倫敦的蘭卡斯特宮,商談關於肯亞獨立的最後協議。一九六O年三月,《時代》的編輯將穆博亞選為封面人物,奉之為非洲大陸獨立運動的榜樣。
這場獨立運動的一個重大障礙在於肯亞青年的教育。對於肯亞塔和穆博亞而言,終結殖民主義似乎是容易的,但要讓接受過足夠教育的非洲菁英來統治肯亞,卻難如登天。「在這場民族鬥爭中,有太多次,」穆博亞寫道,「批評者告訴我們說,非洲人還未能為獨立作好準備,因為一旦殖民政權撤走,非洲人當中沒有足夠的醫生、工程師和行政官僚來接管政府機構。這種批評從來都沒被證實過,殖民政權也從來不會為殖民地某一天的獨立而有意教育大眾。這個問題需要肯亞人自己動手解決。」
穆博亞試圖說服英國人拿出一筆獎學金,讓肯亞一些最有企圖心的年輕人出國讀書。他想出了那個把年輕人「空運」到國外大學的主意。他跟一些富有的自由派美國人密切合作,尤其是實業家威廉•艾克斯•沙因曼,希望能實現這個想法。對美國人而言,空運計劃背後還有一層冷戰動機:如果獨立後非洲國家的年輕菁英能去美國和西歐上大學,這些國家就可能跟西方,而不是蘇聯靠得更近。一九五八年,隨著穆博亞「空運」觀念的提出,肯亞讀大學的黑人當中,有幾百人在非洲學校上學,有七十四人在大不列顛上學,還有七十五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上學。曾經在美國國務院和平隊擔任過教育專家的阿爾伯特•西蒙斯估計,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陸,每三千個孩子當中只有一人上過中學,每八萬四千個孩子中只有一人讀過「任何一類」的大學。當然這就是六萬五千名歐洲殖民者為什麼能如此長久的統治六千萬非洲人的原因。
但殖民當局拒絕了穆博亞的空運提議,他們告訴穆博亞,他的那個空運計劃就像一場「空難」,其政治意義大於教育意義,而且大多數學生毫無準備,費用也不足,註定要被美國大學開除。
美國國務院也不想因為援助穆博亞而惹來英國的反感。於是穆博亞來到美國,私下籌措資金。在六個星期的時間裡,他每天在大學校園裡演講六場,希望激發起人們的興趣,說服學校承諾提供獎學金。他收到了成效,有不少學校答應合作,尤其是像塔斯基吉大學,菲蘭德•史密斯大學等傳統的黑人大學,以及像墨瑞汶學院和聖法蘭西斯•賽維爾大學等帶有宗教背景的學校。
穆博亞與他的美國新朋友一起,成立了非裔美國學生基金會,以便籌措更多的資金。一九五九年秋,在基金會與幾十所美國大學的支持下,空運終於開始了。計畫捐贈人有八千多名,既包括像傑基•羅賓遜、西德尼•波蒂埃、雷夫•邦奇夫人、哈利.貝拉方特這樣的黑人名流,也包括自由派白人比如柯拉•威斯、威廉•艾克斯•沙因曼。
回到奈洛比後,穆博亞並沒有多少時間來細看學生的申請——每天都有幾百號人排隊在他的門外,請求幫助解決醫療、離婚裁決、嫁妝、土地紛爭等問題。然而,穆博亞還是仔細閱讀了一大堆申請檔案。那麼多的肯亞年輕人在中學裡曾刻苦學習,如今卻做著單調而又卑賤的工作,遠遠低於他們的能力。學生們的申請真摯感人,透著愛國情懷。他們的抱負並不是移民,不是逃離肯亞,而是出國接受教育,然後回國為獨立的肯亞效勞。
空運持續到一九六三年,這一計畫影響深遠,並且很快擴展到了其他非洲國家。「我父親是少數幾個在村落裡和在白金漢宮都一樣感覺自在的肯亞政治家之一,」穆博亞的女兒蘇珊說。「非洲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你需要一個接受過教育並且足夠精通世務的人,把那些不同的世界翻譯給彼此,讓他們相互瞭解。少了這一點,你就會茫然不知所措。空運恰恰為肯亞的未來提供了許許多多那樣的人才。」
在肯亞尋求獨立的歷史時期,空運是一次標誌性事件。奈洛比大學的一份報告顯示,後殖民政府中百分之七十的高級職務由空運計畫的畢業生擔任。他們當中既有環保主義者旺加里•馬塔伊(Wangari Maathia),首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非洲女性,也有一位抱負滿滿的經濟學家,擁有洪亮悅耳的嗓音和充滿自信的舉止。他來自維多利亞附近某個村莊裡的盧奧部落,名字叫做巴拉克•胡珊•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在塞爾瑪,巴拉克•歐巴馬曾經說過,他「之所以能站在這裡」,原因可以追溯到甘迺迪家族,因為甘迺迪一家曾經透過湯姆•穆博亞的教育專案向肯亞的年輕人捐款。無論從事實,還是從詩意來說,歐巴馬的說法都有些誇大其辭。甘迺迪一家並沒有捐款給一九五九年九月的第一次空運,而正是那次空運把歐巴馬的父親連同另外八十個人從奈洛比帶到了美國。在塞爾瑪演講的一年之後,據《華盛頓郵報》報導,一九六O年七月,第一次空運過後,穆博亞在海恩尼斯港的甘迺迪莊園見到了甘迺迪。那時甘迺迪擔任參議院非洲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並且正在競選總統。聽了提議之後,甘迺迪從家族基金中拿出十萬美元交給穆博亞,那個家族基金是以他在二戰中喪生的兄長約瑟夫命名的。那一年,副總統理查•尼克森和甘迺迪是競選對手,尼克森同樣渴望贏得黑人選票,他早就試圖在艾森豪當局那裡支持這個計畫,但沒有成功。這一失敗,再加上甘迺迪即將大肆宣傳自己的慷慷解囊,讓尼克森深感沮喪。尼克森的支持者,參議員休•史考特指控甘迺迪為了達到政治目的,不惜從免稅基金中拿出錢來捐贈。這一指控被甘迺迪稱作是他「在十四年從政生涯中聽過的最不公、最歪曲、最歹毒的攻擊」。
歐巴馬的競選發言人比爾•伯頓(Bill Burton)為約書亞一代演講中的這一錯誤致了一份姍姍來遲的歉意,然而,歐巴馬在塞爾瑪所講述的要點並非欺騙之詞。他在肯亞的家人並沒有逃過歷史。歐巴馬的父親是轉型一代的一分子,他見證了非洲從殖民主義躍進為民族獨立、參與了非洲從高壓隔離到敞開大門迎向世界舞台這一歷史過程。而歐巴馬本人不僅想作為第一個問鼎白宮的非裔美國人,他同時還想以一個非裔家族的成員身份進駐白宮,就在一個世代之前,這個家族還在殖民統治之下過著落後而沒有自由的生活。
歐巴馬在二○○三和二○○四年競選參議員之時曾經說過,他父親「在幾年之內從十八世紀跨進了二十世紀。從非洲小村莊的牧羊人,變成了夏威夷大學獎學金的獲得者,後來還上了哈佛。」歐巴馬的父親或者祖父都只是個「牧羊人」,這一概念也是一種浪漫的誇張。靠勞力為生從來都不是他們的命運或者職業。牧羊是所有村民都會做的事,包括像歐巴馬家的男人們那樣的尊貴長老。「我們這些所有在鄉下長大的人都是兼職牧民,」奧拉拉•奧圖努說,他也來自盧奧部落,曾經擔任烏干達的外交部長,是歐巴馬父親的密友。「這絕對沒什麼了不起的,它就是你在學校裡會做的事。用非洲人的標準來看,歐巴馬的祖父屬於中上階層。他買得起瓷器和玻璃製品!如果用西方的標準衡量,他給英國人當廚子掙得的收入比較微薄,但他掙來的就是拿在手裡的實實在在的現金。他在村裡很是受人尊敬。歐巴馬的父親在此基礎上長大,並且還更上層樓。看看《歐巴馬的夢想之路:以父之名》那本書的封面,歐巴馬的父親穿著他母親的裙兜;看看歐巴馬父親的左邊,歐馬的祖父穿著西式服裝。真正的『牧羊人』一定是系著腰帶的。顯然,歐巴馬的祖父要西化得多,而這個家族後來的歷史正是從這裡起步。」
老巴拉克•歐巴馬的父親歐揚格•歐巴馬於一八九五年出生於肯亞西部。他無法容忍鄉村生活。「據說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他的第三任妻子莎拉•奧格薇曾經說。他學了英文讀寫,然後花了兩個星期長途拔涉到奈洛比,在那兒謀了一份給英國白人當廚子的差事。歐巴馬在訪問科格洛時見到一張「傭工隨身攜帶的登記表」。從表上可以看出,一九二八年,三十三歲的歐揚格給人當過「貼身僕役」,表上還有來自東非調查集團的狄克森先生、哈福德船長、雪麗博士、亞瑟•科爾先生留下的簡短評價。狄克森先生盛讚歐揚格的廚藝(「他的糕點做得太完美了」),但是科爾先生卻聲稱歐揚格「不合適也不夠格領取一個月六十先令的薪水。」
在第一任妻子荷麗馬發現自己無法懷孕之後,歐揚格比另一個男人出了更高的價錢,花了十五頭牛做嫁妝,娶了一個名叫阿庫姆•妮顏約佳的年輕女子。一九三六年,阿庫姆生下了兒子巴拉克。不久後,歐揚格•歐巴馬遇見了莎拉•奧格薇,並且娶她為妻。後來,阿庫姆覺得丈夫蠻橫苛刻,她離開了他,把兩個孩子留給他照料。在巴拉克心目中,阿庫姆和莎拉都是他母親。(並且,直到今天,年近九旬的奧格薇還住在科格洛村裡,歐巴馬管她叫「奶奶」或者「莎拉祖母」。)莎拉給她的孫子講她丈夫神話般的冒險之旅——在長途拔涉前往奈洛比的路上,如何用短刀趕走豹子,如何上樹,在樹枝上待了兩天,只是為了躲避一隻發狂的水牛,還有他如何在鼓裡發現了一條蛇。
歐揚格精通草藥,他是個醫生,是個受人尊敬的農夫,也是個在他們村裡頗有名望的男人。跟盧奧部落的大多數男人一樣,歐揚格也是個嚴厲的父親,他要求孩子們在給英國人幹活時,表現得像個乖乖小男孩或者小女孩。「哇,這人太刻薄了!」歐巴馬引用他同父異母的兄弟阿邦戈的話。「他會讓你坐在晚餐桌上,像英國人那樣在瓷具裡擺上食物。只要你說錯一件事,或者用錯叉子——砰!他就會拿棍子打你。有時候他打了你,你得到第二天才明白是怎麼回事。」老歐巴馬出生之前,歐揚格在桑吉巴住過一陣,在那兒他皈依了伊斯蘭教。在盧奧部落裡,基督教徒的比例大大超過了百分之九十;歐揚格轉變信仰的決定十分異常,理由也很含糊。歐揚格往自己的名字里加了個「胡珊」,巴拉克出生之後,這個名字就傳給了他。
二戰期間,歐揚格在緬甸給英國軍隊當廚子。他有可能附屬於英王非洲步槍團,那是一支駐紮在非洲大陸英屬殖民地上的軍團。英國軍官和士兵管歐揚格叫「小子」,在這種環境下,歐揚格也承受了身為非洲黑人所需面對的其他一切侮辱。這份工作本身就是:在盧奧部落,男人不下廚。「所以,這個顯赫的村中長老,這個顯要家族的首領,卻為白人幹著女人才幹的活。他在心理上必須適應。」歐巴馬父親的烏干達朋友奧拉拉•奧圖努說,「這些宗主國居民對他們的僕人非常差,他們粗暴無禮,任何人當『苦力』都會覺得受傷害——『苦力』是傳統的殖民地的說法——對於像歐揚格這樣的村落領袖來說尤其如此。」
歐揚格也開始支持獨立運動。由於給英國人幹活,他在採用新貨幣的經濟體系中掙到了現金,但同時也累積了許多不滿。「他不喜歡英國士兵和殖民主義者對待非洲人,尤其是對待基庫尤中央聯盟成員(Kikuyu Central Association)的方式。當時,這些成員被殖民政府認為秘密盟誓,誓言中包括殺掉白人移民和殖民主義者,」莎拉•奧格薇說。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殖民政府試圖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來粉碎非洲人的起義,包括沒收土地、午夜搜捕、強迫搬遷、大規模逮捕、拘留、強制勞動、剝奪飲食和睡眠、強姦、拷打、還有死刑。殖民政府向英國和全世界的媒體提供的是野蠻的茅茅黨人和造反匪徒種種駭人聽聞的故事,說這些匪徒在反殖民主義鬥士德丹•基馬蒂(Dedan Kimathi)的領導下,立下狂熱而秘密的誓言,要屠殺歐洲人。殖民政府辯稱,歐洲人在十九世紀來到這片「黑暗的大陸」,其實僅僅出於「傳播文明使命」的一片熱忱,此外沒有任何企圖。除了思想最為自由的團體和左翼人士外,幾乎沒有人可以客觀的評論茅茅運動或者反殖民主義運動。英國殖民者指控說,肯亞叛亂者的盟誓並非他們自己所說的保護領土和追求自由,而是要大開殺戒的「黑人邪法」。
殖民政府策劃了一個精心設計的劇本,通過誇張和重複的手法編造出大量故事,將非洲人描繪成嗜血的野蠻人,而英國的官員與士兵們則為了捍衛崇高的歐洲文明而戰鬥。這些故事出現在英國報紙上、出現在電臺裡、出現在《生活》雜誌裡,激發起英國人的民族仇恨,為一場場殘酷的復仇運動提供了政治藉口。殖民政府修建了大量的拘留營,如蘭加塔、卡米提、恩巴凱西、加屯都、姆韋魯、阿西裡弗、邁雅尼、馬金農羅,歷史學家卡洛琳•艾爾金斯(Caroline Elkins)後來把這些拘留營稱作「肯亞的古拉格」。英國人宣稱,這些地方僅僅臨時關押過幾千名基庫尤人,它們只是再教育場所和心理醫療中心,教授一些公民常識和手工製作的基礎課程。事實上,殖民當局在一九五二年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之後,進行了一場「肅清」運動,這場運動讓人想起歷史上最為惡劣的國家恐怖暴行。一九五四年四月,殖民政府展開鐵砧行動(Operation Anvil),在將軍喬治•厄爾斯金爵士(George Erskine)的帶領下,英國士兵屠殺了奈洛比所有的基庫尤人。隨著行動的進展,大規模逮捕行動變得愈發殘酷。在茅茅起義的幾年之中,喪命的歐洲人不到百人,而英國人殺害的非洲人卻數以萬計甚至百萬計。一九五六年,茅茅黨領袖德丹•基馬蒂被捕,他隨即被吊死,屍體埋在無人知道的地方。
「在緊急狀態之中,」穆博亞在他的回憶錄《自由及自由以後》一書中寫道,「絕大多數宣傳都圍繞著茅茅黨幹了什麼,而治安部隊的所作所為則極少被提及。那些許許多多失蹤之後再無音訊的非洲人,那些許許多多在夜間被捕再也沒能回家的非洲人,還有那些報導中提到的治安部隊殺死一個黑人就可以領取許多先令的事實——這些暴行在當時的庭審中只被說出了一小部分。整個故事永遠不可能重見天日,因為在絕大多數區司令部,跟緊急狀態時期有關的文件都已被焚毀。但是,事實是燒不掉的,也不可能被遺忘。」
整個故事直到二十一世紀才浮出水面,一旦它浮現,證據便排山倒海般撲面而來。多年來,歷史學家卡洛琳•艾爾金斯一直在整理英國和非洲的歷史檔案,她得出了一個結論:拘留營曾經關押過的肯亞人遠遠不止一百萬。犯人們遭受的拷問方法令人毛骨悚然,那些方法在英屬馬來島和其他英帝國的前哨基地已經被採用過。為了寫作《帝國的懲罰》一書,艾爾金斯採訪過幾百名曾經被虐待,但倖存下來的肯亞人,其中包括一名被英國軍官拷問過的基庫尤女子,名叫瑪格麗特•奈雅茹(Margaret Nyaruai)。她說:
他們拷問我發了多少次誓,我丈夫去了哪兒,我的兩個異父(母)兄弟去了哪兒(他們已經跑到森林裡去了)等問題。我被他們剝光,拿鞭子狠狠地抽打。他們完全不考慮我剛剛生了孩子。事實上,我覺得我的孩子很幸運,沒有像其他孩子那樣被殺掉……除了毆打,他們還用香蕉葉和香蕉花往女人的陰道和直腸裡插,拿鉗子去夾她們的乳房,女人就只好什麼都說出來,太痛苦了……為了逼供,他們甚至拿鉗子去夾男人的睾丸!遭受了這樣的酷刑之後,我什麼都跟他們說了。我在飽受折磨後活了下來,但直到今天,我身上還有很多傷痛。
施暴者毫無天良可言,艾爾金斯寫道,「嗜虐的行凶者們想到哪兒做到哪兒。」一個名叫莎洛姆•麥娜的女人在接受艾爾金斯採訪時說,殖民部隊的人打她、踢她、把她們的頭猛撞在一起,把紅辣椒和水混在一起,猛灌進她的「產道」——這一切只是為了逼她承認與茅茅黨有關係。她從這些侮辱中醒來後,她說,他們就用電擊她:
他們把小小的導體放在我的舌頭上,胳膊上,或者其他任何他們想放的地方。起初,他們逼我把導體抓在手裡,我被電得旋轉個不停,直到自己撞在牆上。他們拿一種什麼線把導體固定在你的舌頭上的時候,你就會不停搖晃,一直到你自己都不知道導體什麼時候被撤掉了。
儘管有一些批評家指責艾爾金斯極盡所能的淡化了非洲人對歐洲人實施的暴力,這些批評家的絕大多數指責似乎還是出於歷史上的偏見,殘暴的殖民遺跡此前很少被提及,並且非洲人和西方人對此都缺乏瞭解,而如今批評家們要適應它的存在。這就是老巴拉克•歐巴馬記憶中的,他青年和成年早期的肯亞。
二○○八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許多外國記者前往科格洛村拜訪了莎拉•奧格薇,每一次電視新聞採訪車和衛星天線到來的時候,她都會畢恭畢敬的坐在她的芒果樹下、或是坐在家裡,回答關於她丈夫、繼子、還有孫子的問題。倫敦《泰晤士報》對奧格薇做的一次採訪顯示,一九四九年,有個白人雇主曾經向殖民當局告發歐揚格,接著,歐揚格因疑似結交「肇事者」而被捕。殖民當局直到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年才在文書中承認了茅茅運動;胡珊•歐揚格•歐巴馬是盧奧部落的人,而非基庫尤人,可是英國人完全有可能認定他支持反殖民運動。拘留本身並不是什麼值得全世界傳播的新聞——歐巴馬在《歐巴馬的夢想之路:以父之名》裡提到過這一點——新聞點在於莎拉•奧格薇對歐揚格獄中遭遇的詳盡描述。
「白人士兵教唆非洲獄警每天早晚都要拿鞭子抽他,直到他招供。」《泰晤士報》引述莎拉•奧格薇的話。她說,「白人士兵」每隔幾天就去造訪這所監獄,執行針對囚犯的「紀律處分」。「他說,他們有時候會拿兩根大小差不多的金屬棍夾他的睾丸。他們還把他的手腳綁在一起,讓他臉朝下,拿尖釘刺他的指甲和屁股。」 奧格薇說,她不能去探訪,也不能送吃的。他一直被毆打,直到他發誓「再也不加入任何反對白人統治的團體」。她說,歐揚格有一些獄友就在監獄裡死於酷刑。
年輕的歐揚格從未蔑視過英國人,他是村裡第一個穿襯衫和長褲的人,他還在英國人那裡謀了個當廚子的差事。但是現在,從拘留處回到家中的歐揚格滿腔怨恨。「就在那時,我們發覺英國人事實上並不是朋友,而是敵人。」莎拉•奧格薇說,「我丈夫以前那麼勤快的給他們做事,結果竟然是被他們拘捕。」
就算沒有文件記載,歐揚格的命運以及莎拉在《泰晤士報》中的描述也是合情合理的。儘管殖民當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開始「系統」地進行拷打,但在此之前,疑似政治不忠的非洲人有時也會被逮捕,並且遭受虐待。歐巴馬在《歐巴馬的夢想之路:以父之名》一書中寫道,他祖父被拘留了六個月,回家之後看起來又老又瘦又髒——起初,由於精神上受到太大創傷,他並不願意多說自己的遭遇。「他走起路來有困難,」歐巴馬寫道,「頭上滿是蝨子。」學者們也說,在奧格薇接受採訪期間,肯亞緊張的政治氣氛會極大的影響到歷史記憶和歷史敍述。在幾十年的沉默、羞辱和遺忘之後,輿論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揣測,很難去證實這些敍述的每一個細節是否全都真實可信。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歐揚格在牢獄中遭受了悲慘的虐待,但至於細節恐怕就難有定論了。
老巴拉克•歐巴馬的固執絕不在歐揚格之下,但他的學識遠在歐揚格之上。老歐巴馬還是孩子的時候,不願去離家最近的學校上學,因為那裡的老師是個女人。「小學生們不聽話會被打屁股,」莎拉•奧格薇回憶道。「他告訴我,『我可不想被女人打屁股。』」於是,她在六英里之外的一所小學給巴拉克報了名,他要麼步行上學,要麼就是奧格薇騎車載他去。他讀書很用功,也很自傲。「我今天拿了個最高分,」他放學回家的時候會這麼對奧格薇說,「我是最聰明的男孩。」老巴拉克上的是珍堤亞小學,奈伊亞國中,一九五O到一九五三年之間,他上了聖公會(Anglican Church)開辦的馬賽諾民族學校。老歐巴馬跟湯姆•穆博亞一樣,考試成績很好,能拿很高的分數,但因為各種違紀行為被學校逐出了校門,比如偷偷溜進女生廁所,或從附近的農場偷雞。他沒拿到畢業證書就離開了馬賽諾。老巴拉克被學校開除的時候,歐揚格拿棍子打了他一頓,打得他背上鮮血淋漓。
一九五六年,老巴拉克搬到奈洛比,當了一名辦事員。在盧奧的一個鄉村舞會上,他遇見了一個名叫凱齊婭(Kezia)的女孩。那時的她十六歲。「舞會上他請求跟我一起跳舞,我沒法拒絕他。」她說,「他從在場的好幾個女孩中挑了我。幾天之後,我嫁給了他。他拿十四頭母牛作嫁妝,分兩批送了過來。這是因為他太愛我了。」
像大多數受過教育的非洲年輕人一樣,老巴拉克欽佩肯亞塔,也讚賞反殖民運動。他甚至因參加肯亞非洲民族聯盟(K.A.N.U.)一次在奈洛比的會議這一罪名而被拘留了幾天。
沒有正式的教育背景和學位,他無處可去。老歐巴馬因此陷入了困境。而他在馬賽諾(Maseno)的一些朋友贏得了去烏干達的馬凱雷雷大學進修的機會,另一些人則從馬凱雷雷繼續前往英國深造。在閒暇時間裡,老歐巴馬受到了兩位在奈洛比工作的美國教師的鼓勵,一位是海倫•羅伯茲 (Helen Roberts),另一位是伊莉莎白•穆尼•柯克(Elizabeth Mooney Kirk)。因此他參加了函授課程,拿到了中學同等學歷證書。然後,他在美國使館參加了大學申請考試,並取得優異成績。他給美國的大學寫了幾十封信,包括歷史上的黑人學府摩根州立大學、聖芭芭拉初等學院(Santa Barbara Junior College)、舊金山州立大學等等,最終他被夏威夷大學錄取,這是剛開發不久的的美國太平洋前哨的一所不那麼顯赫的學校。湯姆•穆博亞的空運計畫會把他載到那裡。伊莉莎白給歐巴馬在夏威夷的部分費用作了擔保。
「老歐巴馬的智慧給我父親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穆博亞的女兒蘇姍說。「我父親比他大不了多少歲,但他們之間發展出了一種父子般的關係,我父親希望他學成之後能變成一個偉大的人物,對肯亞有所作用。」
一九五九年九月,老歐巴馬正準備前往美國。他和凱齊婭剛剛有了一個兒子,名叫羅伊(Roy)。此時凱齊婭又有了三個月的身孕,是個女兒,他們給她取名叫歐瑪(Auma)。老歐巴馬告訴他的妻子說,他一定會回來,她應該等著他。幾乎沒有人會攔著他接受這次旅行的機會,年輕的老歐巴馬自信得無所顧忌,他向朋友們誇下海口說,等他從國外學完經濟學回來,將「改造非洲的命運」。
「湯姆•穆博亞為我、老歐巴馬還有其他人所做的一切,我們說也說不盡。」菲德烈克•歐卡查(Frederick Okatcha)說,他當時去密西根州立大學攻讀教育心理學。「那次空運拯救了我們!我們從奈洛比起飛,大家都沒有去過任何地方,也沒人坐過飛機。不久之後,飛機著陸在蘇丹的首都喀土穆加油,我們全都以為已經到了美國!我生長的地方和老歐巴馬長大的地方大概相差十五英里地。多年以來,我從來沒穿過鞋。巫術這類東西已經嵌進了傳統社會,我外公擔心,心懷忌妒的巫師會給我們那架飛往美國的飛機施以魔法。這些就是人們相信的事。老歐巴馬高中畢業前讀的學校深受英國影響,因此,空運帶給他的震撼沒那麼大。但是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將會永遠的、徹底的改變。」
「那時候,所有人都非常激動。」湯姆•穆博亞的妻子潘蜜拉•穆博亞說道。作為一名年輕女子,潘蜜拉已經透過第一次空運去了俄亥俄州的一所大學。「我們去美國接受教育,因此我們應該回來接手管理這個國家,這也正是我們後來做的。」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