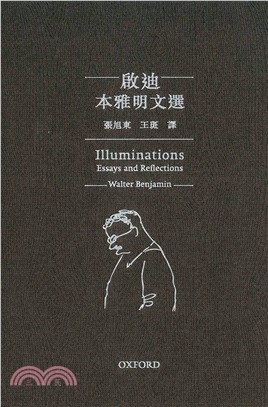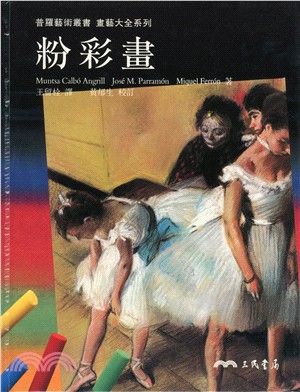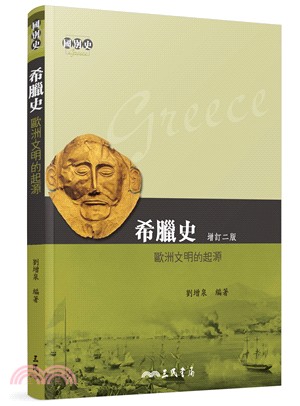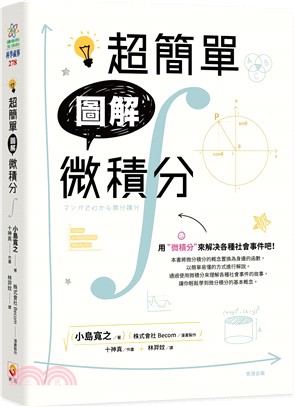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堪稱現代西方最著名的「文人」,1892年出生於德國,1940年9月27日自殺身亡,他憑風格獨特的著述贏取了巨大的身後之名,在西方思想界的地位和影響,自六十年代以來,一直蒸蒸日上,目前已毫無疑問地躋身於二十世紀最偉大作者的行列。而在這一小群傑出人物之中,本雅明又屬於更稀有、更卓爾不群的一類。
譯者簡介
張旭東
現為美國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研究系教授。1986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杜克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新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東亞系。著有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Cultural Fever, Avant-garde Fiction, and New Chinese Cinema, 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The Last Decade of China's Twentieth Century,《幻想的秩序:批評理論與現代中國文學話語》、《批評的蹤跡︰文化理論與文化批評》、《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西方普通主義話語的歷史批判》等。譯有《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等。
王斑
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系William Haas講座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先後任教于紐約州立大學、新澤西羅格斯大學。學術寫作涉及文學、美學、歷史、國際政治、電影及大眾文化。主要著作有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Irony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Fiction, 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歷史與記憶——全球現代性的質疑》(香港:牛津)。1997與2001年兩次獲美國人文基金學術研究獎勵。
書摘/試閱
打開我的藏書-談談收藏書籍
我正在打開我的藏書。是的,我在做這件事。書本還未上架,還沒沾染歸列有序的淡淡乏味,我還不能在它們的行列前來回巡視,向友好的觀眾展示。這你們不用擔心。相反,我得邀請你們跟我一道進入打開的、狼藉遍地的箱簍中。空氣中瀰漫着木屑塵埃,地板遍佈紙屑,我得請你們跟我涉足於黑暗中待了兩年後重見天日的成堆書卷,從而你們興許能夠和我分享一種心境。
這當然不是哀婉的心緒,而是一種企盼,一個真正的收藏家被這些書籍激發的企盼。因為這樣一位收藏家正在跟你們談話,而細心觀察你會發現他不過是在談論他自己。假如我為了要顯得客關實再而令人信服,把一個藏書的主要部分和珍品向你們一一列數;假如我向你們陳述這些書的歷史,甚至它們對一個作家的用處,我這不是太冒昧了嗎?我本人至少有比這正明確、更不隱晦的意圖:我真正關心的是讓你們瞭解一個藏書家與他所藏書籍的關係,讓你們瞭解收藏而不是書冊的搜集。如果我通過詳談不同的藏書方式來論說收藏,那完全是隨意的。
這種或別的作法僅僅是作為一個堤壩,阻擋任何收藏家在觀賞其藏物時都會受其拍擊的記憶春潮。任何一種激情都瀕臨混沌,但收藏家的激情鄰於記憶的混沌。事情還不止於此:那貫注於過往年代,在我眼前浮現的機遇和命運在這些書籍習以為常的混亂中十分醒目。
因為,這堆藏書除了是習慣已適應了的混亂,以至於能顯得秩序井然,又會是別的什麼呢?你們當中誰都聽說過有人丟了書就臥病不起,或有人為了獲得書而淪為罪犯。正是這些領域裏,任何秩序都是千鈞一髮,岌岌可危的平衡舉措。「唯一準備的知識」,安納托‧法郎士(Anatole France)說,「是出版日期和書籍格式的知識」。的確,如果一個圖書館的混亂有什麼對應,那就是圖書目錄的井然有序。
因此,在一個收藏家的生活中,有一辯證的張力居於混亂與有序兩極之間。當然他的存在還牽連着許多別的事情:他與所有權有神秘的的關係,這點我們下面會再談;他與物品的關係,就中他不重視物件的功用和實效,即它們的用途,而是將物件作為它們命運的場景、舞台來研究和愛撫。兌收藏家來說最勾魂攝魄的莫過於把單獨的藏物鎖閉近一個魔圈裏,在其中物件封存不動,而最強列的興奮,那獲取的心跳從它上面掠過。
任何所憶所思,任何心領神會之事,都成為他財產的基座、畫框、基礎和鎖閉。收藏物的年代,產地,工藝,前主人──對於一個真正的收藏家,一件物品的全部背景累積成一部魔幻的百科全書,此書的精華就是此物件的命運。於是,在這圈定的範圍內,可以想見傑出的相面師──收藏家即物象世界的相面師──如何成為命運的關係者。我們只需觀察一個收藏家怎樣把玩心賞存放在玻璃櫃裏的物品就能明白。他端詳手中的物品,而目光像是能窺見它遙遠的過去,彷彿心馳神往。關於收藏家神魔的這一面,他年深日久的形象,我就談這些。
書籍自有它們的命運,這具拉丁格言大概有意將書籍的品性一言以蔽之。所以像《神曲》(The Divine Comedy)斯賓諾莎(Spinoza)的《倫理學》和《物種起源》這樣的書有其各自的命運。然而收藏家對這句格言卻有不同的理解。對他,不但書籍,而且一部書的版本另冊都有各自的命運。在這個意義上,一本書最重要的命運是與收藏家遭遇、與他的藏書會際。當我說對一個真正的收藏家,獲取一本舊書之時乃是此書的再生之日,並不是誇張。這是收藏家的童稚之處,與他老邁習性相混合。兒童能以以上百種方式毫厘不爽地翻新現存事物。
在兒童中,收藏只是翻新的一個過程;其他手段有摹寫物態,剪裁人形,張貼裝飾圖案,以及從給物品塗色到為其命名等等正套兒童的收藏方式。更新舊世界,這是收藏家尋求新事務實最深刻的願望。這就是之所以一位舊書收藏家比尋求精裝點籍的人更接近收藏的本源。書籍怎樣跨越收藏的門檻成為收藏家的財產呢?下面我就談談獲取書籍的歷史。
所有獲得書籍的途徑中,自己寫書被視為是最享譽的方法。提起這個,你們不少人會不無興味的想起讓‧保羅(Jean Paul)的窮困小教師吳之(Wutz)的藏書。吳之在書市的書目上看到許多他感興趣的書名,他反正買不起,就都寫成書,這樣逐漸建立了他的大圖書館。作家其實並不是因為窮才寫書賣文,而是因為他不滿意服務那些他買的起但又不喜歡的書。女士們,先生們,你們也許會覺得關於作家的這個定義時分離奇。
但上面從一個真正的收藏家的角度所作的言談都是離奇怪異的。獲取書籍的尋常手段中,最適合收藏家的是借了書意味着不歸還。我們這裏推想的真正出色的借書者其實是個資深的藏書家。這並不是因為他狂樂地捍衛他借來的財寶,也不因為他對來自日常法律世界的還書警告置若罔聞,而是在於他從不讀借來的書。假如我個經驗可權作證據的話,借書者通常是屆時還書,很少會讀過此書。那麼,不讀書,你們會反問,應是生藏家的特點嗎?這真是聞所未聞,你們會說。
這一點也不新奇。我說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事,專家們可為我作證,但引用安納托‧法郎士給一個市儈的回答已足矣。這個市儈羨慕他的藏書之後問了一個千篇一律的問題:「那麼這些書你都讀過嗎,法郎士先生?」「不到十分之一。我想你也不會每天都用你的塞維赫瓷器吧?」
順便提一句,我對這種態度的特權做過試驗。有幾年時間,至少占我藏書歷史的三分之一,我的藏書擁有不到兩三個書架,一年內只增加幾寸。這是它軍紀嚴格的時期,沒有證據說明我還沒讀過,任何書一律不准進入我的收藏。這樣,要不是因為價格上漲,我也許不會把藏書增至堪稱圖書館的規模。一時間,重點轉移,書籍獲得真正的價值,或乾脆就是難以獲致,至少在瑞士是如此。危及之時,我從那裏寄出一個大宗訂書單,因而能購置像《蘭騎士》(Der Blaue Reitier)和巴霍芬(Bachofen)的《塔那基的智者》(Sage von Tanaguil)這樣的絕本。這些書那時還能從出版商那兒買到。
你們也許會說,你探討了所有這一切旁門左道後,我們最終該走上獲取書籍,即買書的大道了吧!買書是通衢大道,但並不平直舒坦。一個藏書家購書和一個學生在書店裏買課本,一位紳士為淑女買禮品,或一個商人為消磨火車旅途買書,沒有什麼共通之處。在旅途上作為過客,我也有過極難忘懷的購買。財產和所有屬於戰術的領域,收藏家稟有戰術本能。經驗教會他們,攻取了一座陌生城市時,最卑微的古董店會是一座堡壘,最偏僻的文具店可能是戰略要地。在我尋求書籍的征途中,不知有多少城市像我袒示了它們的秘密。
並不是所有最重要的購買都是在書商的店舖裏進行的。郵購書目的作用大的多。即使郵購者對欲購之書瞭如指掌,個別的版本總是令人感到意外。郵購總不免有賭博的意味。購置的書有時令人沮喪,有時則有欣喜的發現。舉個例子。記得有一次,我為我原有的兒童書籍訂購一本有彩色插圖的書,原因僅是書中有格林寫的童話,由位於圖林加的格林瑪書局出版。格林瑪書局出版了格林編輯的一本童話書。
有了這十六幅插畫,我這本童話書就是上世紀中葉生活在漢堡的傑出德國書籍插圖畫家萊色(Lyser)的早期作品的現存絕本。另外,我對人名的同音反應是正確的,因此我又發現了萊色的一部作品,即《琳娜的童話書》。萊色書目的編著者還不知有此書,它應有比我這裏首次介紹的更詳細的說明。
購買書籍絕不僅僅關乎金錢,或單單有專門知識即可。兩者相加還不足以建立一個真正的藏書庫。一個真正的藏書庫總是有些深不可測,同時又是獨絕無雙的。任何通過書目郵購的人除了以上說到的品格外還必須有鑒賞力。出版日期,地點,規格,先前的主人,裝幀以及諸如此類的細節必須向買主有所暗示──不是枯燥孤立的的事實,而是一個和諧的整體。
根據這和諧的整體的品質和強度他必須能夠鑒別一本書是否中他的意。拍賣場合則要求收藏家有另一套本領。對書目的讀者,書籍本身要會言傳意授。或者,如果版本的來源已確定的話,有可能表示先前的所有主。一個有意參加拍賣的人,除了要保持冷靜的頭腦以面被競爭沖昏了頭,還必須給予書籍和對手相當的注意。這樣的事頻頻發生:某人因出價越來越高,便死抓住一項高價貨不放,多半是為了彰顯自己而不是為了買書。
另一方面,一個收藏家記憶中最精彩的時刻是拯救一部他曾未想過更沒用憧憬的目光流連過的書,因為他瞥見此書孤伶伶地遺棄在書市,就買下,賦予它自由。這猶如《天方夜譚》中的王子買到一個美麗的女奴。你看,對一個收藏家,一切書籍的真正自由是在他書架上的某處。
巴爾扎克的《驢皮記》(Peau de chagrin)在我的藏書庫長列的法文書中脫穎而出,至今仍是我在一個拍賣行最激動的經歷的見證。這發生在一九一五年,在愛彌爾‧赫什(Emil Hirsch)主辦的魯曼拍賣行。赫什是一位最傑出的做書人,也是一位出色的書商。我的的這個版本一八三八年由拉布斯出版社印行於巴黎。
我拿起這部書,在上面看到的不僅是它的魯曼行的編號,甚至還有前買主九十年前以現今價格的八分之一買下此書的商店的標籤。上面寫着:「帕比特利‧法郎諾」。那真是一個好時光,還能在一家文具商那裏買到如此精美的版本。此書的鋼刻畫是由法國最傑出的裝幀圖像藝術家設計,由最優秀的的刻印家鐫刻。但我要告訴你們我怎樣得到這本書。我事先去愛彌爾,赫什的拍賣行巡察了一下,瀏覽了四十至五十本書。
巴爾扎克那本特別的書激起了我永遠占有它的強烈願望。拍賣的日子到了,幸運的是,據拍賣的時間安排,《驢皮記》的版本前面先拍賣此書的全套彩色插圖,與書分開印在印度紙上。賣主們坐在一條長桌邊,與我直角相對坐着第一輪拍賣中有個眾目所屬的人,他是慕尼黑有名的收藏家巴倫‧馮‧西莫林(Barcon von Simolin)。他對這套插畫興趣極大,但面臨出價對手。總之,競爭十分激烈。結果這套插圖贏得整個拍賣最高的出價,遠遠超過三千馬克。
沒人預料到這麼高的數目,在場的人都頗為興奮。愛彌爾‧赫什一直顯得無動於衷,不知是想爭取時間還是有別的什麼考慮,他俓直轉向下一個拍賣品,沒有人對此有太多的注意。他喊了價,此刻我的心怦怦直跳,深知我不實這幫收藏家中任何一位的對手,我只叫了一個比通常稍高的買價,拍賣商沒有引起買主們的注意就履行了通常的手續,說道,「還有出價的嗎?」他的木槌三聲震響,中間短暫的間歇有如永年,接着便加上拍賣的費用。
第二天早晨我去當鋪的經歷說起來就離題了,我倒願意談談我想稱為拍賣的反面的另一件事。那是去年在柏林的一家拍賣行。拍賣的書籍在質量和題材上五花八門,僅有幾部論述神秘論和自然哲學的稀有著作值得注意。我為幾部書喊了價,但每次都注意到坐在前排的一個人似乎專等着我出價,然後出個更高的價來對抗,顯然準備擊敗任何出價。幾輪之後,我已無望購買那天我最感興趣的書。這部書是希罕的《一位青年物理學家的遺言》,由約翰‧威廉‧里特(Johann WilhelmRitter)於一八一O年在海德堡以二卷本出版。
這書從未重印過,但我一直認為其前言是德國浪漫主義個人文體最重要的範本;編著者通過他為據稱是過世的無名朋友寫訃告來講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其實作者與他的朋友毫無二致。當這本書推出拍賣時我突然靈機一動。事情再簡單不過了:反正我一出價拍賣品便會被那傢伙奪走,乾脆不喊價了。我控制住自己,緘口不言。我所希望的如期而至:沒人有興趣,沒人出價,書被擱置一旁。我覺得隔幾天再問津此書較明智。結果當我一周之後造訪書店時,發現那本書已擱在二手書部門。我獲致此書是得益於無人有興趣。
一但你走向成堆城山的箱簍,從中發掘書籍,讓它們重見天日,或者說不眠於夜色,有多少記憶蜂擁而至!能最清楚地顯示打開藏書之魅力的,莫過於要中斷這活動真是難上加難。我從中午開始,直到半夜才收拾到最後幾箱。此刻我拿起兩本由退色的紙板裝訂的冊子。嚴格地說這些冊子不應在書箱裏。
它們是我從母親那兒繼承的兩個相冊,裏面有她小時貼上的黏滯照片。它們是兒童圖書館裏的種子,至今仍在繼續生長,雖然不在我的書園裏。沒有一個現存的藏書庫不擁有幾冊貌似書籍的藏品裝飾着藏書的邊角。這些不必是可粘貼照片的薄冊或合家相冊,不必是作者簽名的書,裝有小冊子和宗教箴言的夾子。有些人熱衷於傳單或內容簡介,其他人則嗜好手寫的複件或無法獲致的書的打字稿本。
期刊當然也是藏書庫多采多姿的邊邊角角的一部分。我們再回到剛才提到的相冊。實際上,繼承是獲得一份收藏的最佳途徑。因為一個收藏家對其所有物的態度源於物品所有主對其財產的責任感。因而,在最高的意義上,收藏家的態度是一個繼承人的心願。一份收藏最顯著的特徵總是它的可傳承性。你們應該知道我現在談這些,心裏完全明白這個關於收藏的精神氣候的討論,會加強你們不少人持有的收藏的熱情已過時的信念,加深你們對收藏家這類人的懷疑。
我完全無意動搖你們的信念和疑心,但有一件事應注意:隋着收藏物失去了主人,收藏的現象也喪失了意義。儘管公共的收藏從社會角度講也許弊端更少,於學術興許比私人收藏更有用,但物品只有在後者才獲得自身應有的價值。我不是不知道我在這兒討論的、有點多此一舉地向你們展示的這種人已行將絕跡,但正如黑格爾(Hegel)所說,只有當夜幕降臨,智慧女神之梟才展翅飛翔。收藏家滅絕之時也是他被理解之日。
現在我已收拾到最後一個半開的紙箱,時間已過了半夜。我心中充滿與現在所談很不同的想法──並不是思想而是意象,是記憶。我發現那麼多東西的各種城市的記憶:里加,拿波里,慕尼黑,丹茲格,莫斯科,佛羅倫薩,菲色,巴黎;記憶中還有羅森塔爾(Rosenthal)在慕尼黑豪華的住房,丹茲格證券交易所,已故的漢斯‧勞爾(Hans Rhaus)的期票在那而支付,蘇森古在柏林北部的霉氣熏人的書窖。
記意呈現這些書所在的房間,我在慕尼黑的學生宿舍,在波恩的的房間,伯蓮茲河畔的伊色瓦德的幽靜,最後是我兒童時代的房間,現在我擁有的數千本有四五千本先前就在那個地址。啊,收藏家真幸福,閒人真快樂。人們對這種人要求最少,他們中最能適愜心者,莫如那個戴着普畢茲維特格「書蟲」(Spitzweg’s Bookworm)面具,能過名譽不佳生活的那個角色。
因為他內在有種精神,或至少是小精靈。這精靈確保一個收’藏家──我指的是真正的;名副其實的收藏家──擁有藏物,使之成為他與身外之物品所能有的最親昵的關係。並不是物品在他身上復活,而是他生活於物品之中。於是我在你們面前建構了他的居室,用書籍作為建築的磚瓦,現在他就要退隱內室了,這也理應如此。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