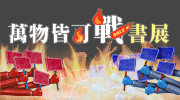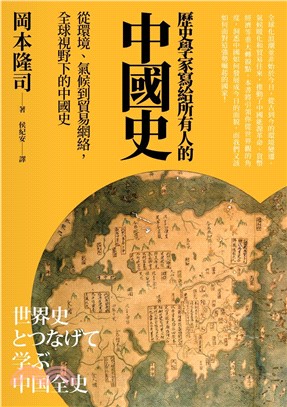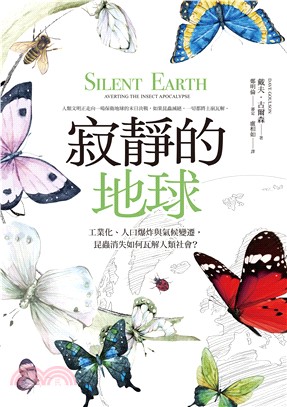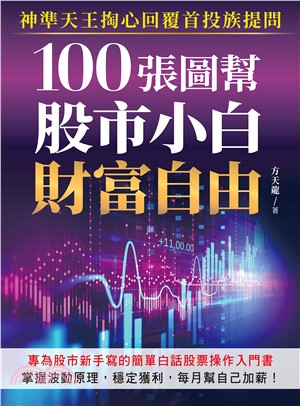夢遊祕境的女孩
商品資訊
系列名:POSH
ISBN13:9789866076695
替代書名:Girl in Wonderland
出版社:馥林(泰電)
作者:倪采青
出版日:2013/07/05
裝訂/頁數:平裝/320頁
規格:21cm*15cm*1.5cm (高/寬/厚)
版次:1
適性閱讀分級:558【七年級】
商品簡介
◎ ◎療癒系人氣作家-夏霏、主持人/作家-段慧琳、晉江原創網官推作者-謝金魚(爆走金魚)真情推薦!
◎ ◎臺灣都會小說家倪采青繼「第一屆馥林都會小說獎」首獎作品《潛入婚紗的女人》後,再度推出構思已久、潛藏五年的長篇小說作品《夢遊祕境的女孩》。
◎ ◎《夢遊祕境的女孩》中,倪采青以精煉細膩的筆法、纏綿悱惻的劇情、飽富情感張力的人物,交織成一段痛並甜蜜著的深刻記憶。
◎ ◎《雙河彎》生活閱讀誌連續六期連載,深獲讀者好評。
我始終覺得,不出口的愛,往往比出口的更美、更準確。
語言學高材生蘇玉凝,
某天醒來發覺自己遍體鱗傷流落至滇北祕境,卻渾然想不起為什麼。
她千方百計想逃走,怎奈原始部族以信仰為名禁止她離開。
這才發現學術理論在此無用武之地,任憑讀書破萬卷,沒有體力也惘然。
她只得乞求一位戰士帶她去找行李,實則打算投奔敵寨,
表面對戰士明哄暗騙,不捨之情竟綿綿而生。
可是,不用說她也明白,這是一場註定無望的愛戀……
作者簡介
倪采青
台大外文系畢,台大語言所肄。現專職小說創作、寫作研究及書評撰寫,並長期擔任《双河彎》書評專欄作家,不定期接受各界邀請演講或評審。著有《變身暢銷小說家》、《金匙小姐不矜持》、《潛入婚紗的女人》及《夢遊祕境的女孩》。
《變身暢銷小說家》為倪采青第一部完整統合大眾小說寫作技巧之教學書;《金匙小姐不矜持》則為其第一部華文創作之都會小說。由於2011年《潛入婚紗的女人》獲得「第一屆馥林都會小說獎」首獎,《夢遊祕境的女孩》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期待。
名人/編輯推薦
「這部作品裡頭的人物已經太『活』,我愛他們太深,不只一次暗自咬牙:若不將你們化為實體,我誓不停歇。」──《作者後記》
「奇異瑰麗,令人心折的愛情故事,有如夢中夢般,每次翻頁都是意想不到的轉折。」──夏霏 (療癒系人氣作家)
「全然意外的旅程,是最具記憶的旅程。無須言語的愛情,是最有靈犀的愛情。在采青的作品裡,我看到深刻。旅程和愛情都深刻。」──段慧琳 (主持人/作家)
「擁有精細的語言就是文明?沒有語言就是野蠻?采青以一個如怒江般奇麗的故事,讓我們看見了超越語言的感情。」──謝金魚/爆走金魚(晉江原創網官推作者)
序
後記
《夢遊祕境的女孩》初稿完成於二○○七年,當時我還是個素人作者,在網路上貼文,一天能有三十人來看就偷笑了。這部作品貼出之後,受到的迴響超乎預期,是我第一次認知到自己的文字也許能夠感動一些人。有些作品可以拋棄,但這部作品我始終深懷感恩,裡頭的人物已經太「活」,我愛他們太深,不只一次暗自咬牙:若不將你們化為實體,我誓不停歇。
時隔五六年,我已非昔日之我,對這部作品的感情卻一絲不減。每每在困倦之際,想起了這些人物,想起我對玉凝與蒼狼的承諾,才得以抬起腳步向前行。
就在人人都說是世界末日的那一年,我成為全職作家了,頭一件事就是把這部作品拿來全面重寫。我曾經為了出版、為了得獎,不敢不打喜劇安全牌,這一回終能從心所欲,寫下市場上比較罕見的路線。
玉凝和蒼狼不能在一起,這是故事開始前便已註定的。
我們看過太多幸福快樂的愛情故事,在這些故事中,愛情的力量被放大,足以克服一切,但這不符合我在現實社會的觀察。世間還有許多愛情,是軟弱的,是精算的,是不得不屈服於現實的。更有許多時候,愛情並非生命中最優先的考量。
但是,這種不得不放棄的愛情,往往最魂牽夢縈。
為了這部作品,我曾對雲南少數部落做了廣泛的研究,不過為了配合戲劇需要,仍做了大幅度的調整。小說畢竟是杜撰,奠基於想像之上,但情感比什麼都真。
倪采青
二○一三年二月六日於台北
書摘/試閱
第1章
我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這麼幽暗,這麼靜謐,唯有斗室內淡淡的火光掩映,在我身邊嗶嗶剝剝地輕響?
我想要看清楚四方,眼皮卻像被榔頭壓住那麼沉重。黑暗朝我撲了下來。
第2章
我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有這麼多彩虹飄來飄去,黑色的頭晃呀晃的,一大團聲音……應該是對話聲……風風火火傳進我耳中,我卻聽得支離破碎?
莫非還在夢中?
啊……頭好暈。
第3章
我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額頭熱辣辣的,渾身刺癢痠疼,左小腿像是被電鑽鑽進去一樣疼痛。我是怎麼了?
我勉力睜開眼,想要坐起來竟是痛徹心扉,只好瞇著眼睛,環頸四顧。
這……這是什麼地方?
殘破不堪的木板房,三五坪大,屋頂只鋪了茅草,沒有電燈。屋心燃著柴火,熱呼呼的,地面散放幾個鍋碗瓢盆,髒兮兮的,除此之外別無他物,空盒子一般。金沙似的日光透過窗子斜射進來,可那窗子其實就是幾個碗公大的洞。
簡陋,破敗,蠻荒,有如打入十八層地獄的貧民窟。
遠處隱約傳來嗚嗚的號角聲。節奏緊迫,好似防空演習,不曉得是什麼玩意。
我伸手往附近摸索,找到了我的黑膠框眼鏡,但……左邊的鏡片不見了,右邊鏡片磨損得嚴重,鏡腳也歪掉了,好像經過某種慘烈的意外,但我絲毫沒有印象。
我掀開棉被,驚見左腿包在木頭削成的夾板裡,手臂遍布擦傷,臉頰似被萬根針刺到,少數完好的皮膚也被蟲咬得紅點遍布──救命啊,我不會殘廢或破相吧?
我嚇得雙手捂住嘴巴,壓抑驚恐的情緒。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外面傳來嘎吱嘎吱的腳步聲,是在上臺階,隨著腳步聲一響一響,木地板跟著一晃一晃,原來這屋子是建在二樓,架空的。
我的腦袋彷彿也架空了,像航行於一片乾冰海,幽幽微微,霧霧茫茫。現在是什麼情況?
慢慢的,我憶起了智銓的金邊眼鏡。
「妳行李準備好了沒?」他打手機問我,有點興師問罪的口吻。
原本應該在Google雲南氣溫的我,才發覺自己開了十幾個視窗都是雲南的動物生態圖片。一小時前開始整理的衣服還長袖短袖混在一起,粉彩交揉,散落滿床。
我手機夾於耳肩之間,兩手敲鍵盤,慢了半拍回答:「嗯。」
「我就知道妳還沒準備好。這一趟有多難走妳知不知道,裴教授雇了兩個當地嚮導,說要翻山越嶺,衣服厚的薄的全都要帶,妳還拖拖拉拉,又在看那些小貓小狗的圖片是不是?愛麗絲。」
「我不叫愛麗絲,我叫Yuni。」
他半逗半嘲諷:「妳就是那個最愛夢遊仙境的愛、麗、絲,成天追著兔子跑的愛、麗、絲。」
「Yuni、Yuni、Yuni!」
「聽得見兔子說話的愛、麗、絲。」
我又羞又急,吶吶地回不出口。智銓反倒覺得他講贏了,嘿嘿笑著掛掉電話。
大約是國中時候就發現自己有幻聽,從不敢告訴任何人,之所以告訴智銓是因為我覺得伴侶應該坦誠相對。他不知道我承認這件事多難受,這等於承認自己有精神分裂,他不安慰我就罷了,反而拿這個來取笑我。
放下手機,我就哭了。
所以,我應該是已經到了雲南吧?
我記得所上是要到雲南採怒族語料沒錯,機票買了,護照也辦了,我跟裴教授、Catherine教授、智銓、雲雯一行人都摩拳擦掌好久了。可是,他們人呢?怎麼我記得昨晚才在跟智銓不開心,今天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怔忡不定地等待腳步聲的主人現身在門口。當那一刻來臨時,更加證實了我的猜測。那是個黝黑的男人,赤腳,袒露左肩,身上綁著一方五彩紋飾布匹,像掛一塊歐洲國旗在身上。他油膩的頭髮披散到肩膀,霎時間我以為自己進了《賽德克‧巴萊》的拍片場景。
當他走得更靠近時,我嚇壞了。他醜到爆,眼形似蛇,顴骨高削,身材很高卻瘦得不像樣,偏偏骨節特別大,像根行動竹子。嗯……那樣形容還算恭維了,他簡直是陰間來的白無常,完全不像善類。
他見到我,皺個鼻子就把手上提的竹篾籃放到地板,朝門外長嘯了一串方言。
我研一一進來就幫裴教授整理怒語語料,兩年下來,多少懂得一些,甚至於班上同學間還會用怒語互開玩笑,因此我確定那是怒語。他在說:「快來喲!這女人醒了。」
他並沒有對我點頭微笑或打任何招呼,就盤腿坐下,拿著一根鬃毛刷在木碗裡沾取濃稠綠藥膏,臉色像邪氣的壞魔法師,與其說是要幫我擦藥,還不如說是磨刀霍霍要凌遲我。我聞到藥味嗆鼻,不禁問:「不好意思,請問您是醫生嗎?」
他轉為口音怪異的漢語說:「笨蛋,不然妳以為我是誰?」
我受他的無禮所愕,無法搭腔。
「妳傷得很重,臉會變成大花貓,左腳斷掉,以後會瘸。」他蛇一般的細眼朝我睥睨過來,好醜,好醜。
我臉色大變,「什麼?我的腿是怎麼個斷法?閉鎖性骨折、粉碎性骨折,還是開放式骨折?照過X光嗎?這附近有沒有大醫院?你們……恕我冒昧,請問您有醫師執照嗎?」
「妳說那是什麼鬼東西?我這兩天已經幫妳換過好幾次草藥了,是我祖傳的獨門靈藥。遇到我,算妳幸運。」
一聽到「草藥」,我臉都綠了,連忙問:「請問那個藥是經過衛生機關核可的嗎?」
「妳說什麼?」
「不好意思,冒昧請教一下,您從業幾年了?」
「我七歲就會醫牛了。」
「您是獸醫?」我難掩驚恐。
「也醫人。」
我渾身都冰涼了,慌亂抬眼,只見他掀起嘴脣,嘲諷地笑:「人跟獸有啥兩樣?」
我呆了大概有五秒。
「阿卡查,你別嚇著她了。」一位矮矮壯壯的男人從門外轉了進來,對我綻出好大的笑容,「姑娘,我一聽到阿卡查在叫,馬上就趕來了,就怕他嚇著妳。他是醫生沒錯,這方圓百里最好的醫生。妳放心給他治傷,包妳的皮膚明天就會跟剛出生的羔羊肚子一樣嫩,三天內就能站起來跑到布達拉宮去──對了,我忘了先介紹自己,我叫孔更‧朋索‧阿客恰‧頂。我們族人取名字不像漢人那麼簡單,是要家族名加上父名、愛稱和排行,像我就是孔更家、朋索的兒子、愛稱阿客恰、排行第四的。
外地人通常記不起來,所以妳叫我的漢語名字『孔豐松』就好。」他擺手向那個醜男人,「我們這位醫生叫阿卡查.博力.丁板鼎.朋,他是獨龍寨主,身分高貴,很驕傲的,不取漢語名,妳叫他『阿卡查』就好。」當他說話時,唱作俱佳。我差點以為他接下來會學俄羅斯歌舞團,雙手當胸交叉,跳起踢腿舞。
我看這孔豐松鵝蛋臉,精靈滑頭,大圓眼骨碌碌轉個不停,類似曬過日光浴又健身成功的納豆,滿有親切的氣質,心頭稍微寧定,也回禮說:「孔更‧朋索‧阿客恰‧頂先生和阿卡查.博力.丁板鼎.朋先生,你們好。」
孔豐松面露驚奇,「妳會講我們的話?講得這麼準。」
我謙虛笑笑,「我大三的時候修過語音學,雖然只拿了九十分,不過各國語言只要有音標我都能發得出來,西班牙的彈舌音例外,那個我真的學不會。你們講的怒語我算是比較熟,尤其是語音方面,研究計畫長期接觸過。」
「嗯……我們講的不算是怒語。」他臉色微變而猶疑。
「你們這裡不是怒族嗎?」
「不是!」他先是瞪大眼否認,卻又搔了搔頭:「應該……不是……吧。」
「那麼這裡就是獨龍族了?」
我曾在圖書館架上看過一本《獨龍語簡誌》,就放在《怒語簡誌》旁邊,但因為灰塵積得太厚,書側爬著一隻蠹魚,我就不敢碰了,不過起碼我知道獨龍族和怒族都是雲南的少數民族,分布地域相鄰,語言相近是自然。
「我們不是獨龍族,阿卡查才是。」孔豐松說:「獨龍族是全中國人口最少的一族,只有七千多人,我們寨子的人比獨龍族還少,只有兩百多人。兩個寨子離得很近,像蚌殼一樣黏在一起,吃穿講話都相通,所以外面的人常常以為我們是同一族的,其實不是。」
「那請問這個寨子到底是哪一族的?」
豐松原本笑笑的鵝蛋臉凝固成雕像,好像我問的是高等微積分,答不上來。
我追問:「總該有個名稱吧?」
他想了半天,不甚確定地說:「我們寨主姓鹿,妳就跟鄰近的寨子一樣,叫我們『鹿寨』好了。」
我的胃不舒服地抽動。這個寨子裡的人連自己算什麼族裔都搞得不是很清楚,我該怎麼找人來救我回家?再說,我們是要去採怒語語料,依教授的意思,要找的必是最純正的怒族耆老,不太可能選擇一個莫名其妙的鹿寨,我怎麼會跑到了這裡來?
我說:「能不能麻煩您把我到這裡的經過告訴我一遍。」
豐松十分驚奇,「我們才想問妳呢!妳是怎麼會來到這裡,傷成這個樣?」
「我……有點忘了。」
「妳失憶了?」
「不!」我伸手摸頭,目光渙散地說:「我的腦筋非常正常,我只是……還沒完全清醒。」
豐松面露同情,「姑娘,妳是在前天蒼狼去外頭打獵的時候發現的……」
「等等,你們訓練狼去打獵?」遇到跟動物有關的事,我就情不自禁打破砂鍋。老毛病了。
他們同時噗地大笑,幾至我耳膜嗡嗡鳴。
豐松說:「蒼狼是我們族人,那是我們給他取的漢語名,蒼山裡的狼。」
阿卡查插口:「是蒼老的蒼。」
豐松嘻嘻笑了兩聲,說:「蒼狼不愧是我們的第一勇士,幫妳裹了傷之後,只用了一根手指頭,就把妳和一隻岩羊、一隻山麂子和三隻雉雞扛了回來,送來鹿寨主家裡。他把妳照顧得很好,路程中碰到了一隻山虎和一隻野猴來搗亂,他也射了下來,完全沒有讓妳再受損傷。一回到寨子,就把妳送來鹿寨主家裡,還找了阿卡查來看妳。妳的左腿雖然沒有外傷,可是阿卡查不愧是一等一的醫生,發現妳骨頭裡有一點點小傷,憑他的醫術沒兩三天就好了。總之,我們把妳照料得無微什麼……漢語有句成語叫無微……無為而治!」
我笑不出來,特別受他誇飾的言詞所擾,不確定這整件事到底是真的,還是某種惡意的玩笑。
豐松用近乎歌劇的詠嘆調說:「姑娘啊,妳啥都不必擔心,就在這美麗的獨龍河谷安心養傷。這可是塊寶地,走出大門就是平地人想見都見不到的神祕的獨龍江,夏天清澈見得到底,冬天成了一條銀帶,瞧它多美麗,流得多湍急。」他居然唱起了山歌。鏗鏘有力,鐘鼓齊鳴。
可惜這場表演對我一點都沒有作用,我只留意到他把「湍」的塞音誤讀成塞擦音了。
猝不及防,阿卡查拿著一把看起來生鏽的大剪刀對著我的臉。我受到驚嚇,向後避開。阿卡查擲下剪刀,大罵:「妳的臉是想破相還是想潰爛?」
我實在覺得這人不可理喻,拿棉被蒙住了臉,說:「不好意思,我想我還是回臺灣再接受醫療救護比較妥當。」
豐松笑笑說:「姑娘,妳放心把臉交給阿卡查。我們這邊,上到孔當寨,下到馬庫寨,這方圓一萬里的大病人小病人、雞、狗、豬、鴨,沒有不被阿卡查罵過的。被他罵是很幸運的,罵得愈兇,圍觀的人愈多,他醫得愈來勁,要是病人的頭被他用剪刀柄敲破,更是代表他醫得用心,要不然人家怎麼會叫他『有一張毒蛇嘴巴的神醫』呢?妳等等,我這就幫妳叫更多人過來看。」說完,他還真一溜煙跑出去吆喝了。
阿卡查搖頭說:「叫再多人來都沒用。這條腿,永遠好不起來了。」一雙極不友善的眼,把我瞧得不寒而慄。
沒多久,豐松就帶來了幾個人進來。阿卡查像是看到雛妓的嫖客一樣興奮起來了,硬是掀開我的棉被,持著剪刀尖對著我,見我快被嚇到尖叫時,忽地擲下剪刀,冷冷地說:「笨蛋,妳的傷口早就縫過了,現在只要上藥就好了。哈哈哈。」
他拿一支沾取藥膏的鬃毛刷揮了過來。我雖然不情願,總比剪刀好一點,於是就像個被狗叼住頭的布偶娃娃,忍受當頭而下的噁心氣味。
我以為上個藥不過是一兩分鐘的事,然而數到五百下,阿卡查還像畫眉毛似地蘑菇,沒有結束的意思。見他醜不拉嘰的臉在我面前兩寸肆虐,兇巴巴又怪模怪樣,我不禁覺得,去找牙醫拔智齒還比較幸福。
終於,一個脆如鳥啼的女孩嗓音出面替我解了圍:「阿卡查,你替她上藥上那麼久,不會是想娶她做老婆吧?」
阿卡查噎住了,立刻放開我的臉。
女孩大剌剌進了門,穿著跟阿卡查和豐松一樣的五彩布疋,唯多加一身的項鍊、串珠、耳環與染色油藤腰圈,隨著她大方的步伐沙沙響,掩不住體態的健美。當她調侃阿卡查時,明眸燦如彗星,眉間竟帶英氣。
她皺眉對眾人說了一些怒語,從情境配合零碎的辭彙推斷,意思大致是:「一個女孩子傷成這樣,有誰會想給別人看。你們都出去。只有阿卡查跟孔豐松留下。」一聲令下,眾人都唯唯諾諾地出去了。
我鬆了口氣,把感激的眼神投向她。她正巧也望向我,臉色一怔說:「啊,妳其實挺好看的。」
我抿抿嘴角,做出一個困頓的微笑。
她用下巴點著我,「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蘇玉凝。蘇軾的蘇,玉珮的玉,凝聚的凝。」我偷眼打量她,她跟得上。
「蘇意凝?」
「玉凝。」
「我知道。就是意珮的意,林黛意葬花的意,蘇意凝。」
她真的懂,只是發音不準。我遲疑了一忽,決定不糾正了,畢竟「玉」這個音對世界上許多人來說都很困難,於是我點頭說:「對。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臺灣來的研究生。呃,臺灣是一個很遠的海島,研究生的意思就是……很資深的學生。」
「臺灣人,是漢人嗎?」孔豐松插嘴,被女孩白了一眼。
「呃……算是吧,可是其實臺灣有很多種民族,三四十種語言,語言生態豐富到很多國外的學者都特別來研究,有很多南島語言正在瀕臨滅絕……」我見他們的眼神愈來愈迷惘,趕緊拉回,「是漢人沒錯。我是跟我老師和同學一起來的,請問你們有看到他們嗎?」
宛翠卻不答話,微皺眉心瞧著我,近乎失神。
我被瞧得不好意思,就開口問她:「小姐,請問我該怎麼稱呼您?」
她「啊」地一聲才回過神來,說:「我有個漢語名字,叫『鹿宛翠』。野鹿的鹿,董小宛的宛,翡翠的翠。妳就先這麼叫我吧。」
「鹿小姐,妳是在山下讀過書嗎?」
「我父親教我的。」她仰起下巴,指尖朝牆角指去,要不是她指去,我絕對不會注意到那裡有一堆破舊書。
豐松豎起大拇指說:「宛翠就是鹿寨主的女兒,我們鹿寨主是這附近幾個寨子裡,唯一到昆明上過學的人,他讀的可是中國文學。可他沒有留在昆明,反而回到獨龍河谷,教我們漢語。這附近的人說起鹿寨主,個個都當把他當靈魂一樣崇敬。」
我心念一動,像是被綁的肉票找到救星。鹿寨主既然會教女兒用「董小宛」來自我介紹,不是選「音容宛在」這種負面詞,也不是選「宛轉」這種會跟「婉轉」搞混的同音詞,表示他確實讀過點書,可以好好溝通,於是我問宛翠:「請問鹿寨主在不在?」
「妳的聲音這麼小,也只有蒼狼聽得見。」她神思飄渺。
「……」
「還好是蒼狼救了妳,他跟阿卡查是最好的朋友,否則阿卡查不見得會醫妳。」
「謝謝妳告訴我。」我扣住她的手臂搖了一搖,「請問鹿寨主在不在?」
「噢。」她終於回神說:「妳得快快離開這裡,下山回妳的家去。」
「是。」我發自心底微笑,「鹿小姐都知道我在想什麼。拜託您們幫忙了。」
孔豐松忽然伸手阻在我和宛翠中間,「不行不行,她的腿傷還過不了吊橋跟溜索。」
阿卡查也尖聲說:「到時候她終身殘廢,就不要說我醫術不好。」
宛翠說:「她現在沒辦法自己走下去,你們就揹她,把她揹到貢山縣城交給公安不就得了。」
孔豐松彷彿看見什麼極端恐怖的東西,「宛翠,這……這不是鬧著玩的。前面那個吊橋今年就已經摔死了第五個人,再過去第二個溜索快斷了,都魯布家的牛前兩天被馬幫路上的螞蝗群活活咬死,自己一個人走就很危險了,誰還敢揹人下去?」
宛翠說:「那是你不敢。蒼狼就敢。」
豐松低頭攤手說:「好,好,我不敢。妳去找蒼狼揹她。」
宛翠臉色反轉為難,啞聲半晌之後突然大罵:「你們這群沒用的東西,如果蒼狼揹他下山,誰來負責打獵?糧食不夠,害大家餓肚子怎麼辦?」
豐松陪著笑臉,小心翼翼地反問:「自從蒼狼會拿弓,糧食曾經不夠過嗎?」
阿卡查唱起尖酸的即興歌謠:「蒼狼苦命喲──打獵要他,揹人要他,剷雪要他,挖墳墓要他。等他自己死翹翹,是誰會幫他挖墳墓?」
宛翠伸掌巴向阿卡查的頭,「你再胡亂詛咒,我捏爛你嘴巴。」
他們後來幾句都轉為怒語,我漏了幾句聽不懂,寨裡的事情我也插不上嘴,只好作壁上觀,暗自希望鹿宛翠一個人吵得贏他們兩個。
直到門外傳來傳來「篤、篤」的規律聲響,並不甚大,但他們聽到之後,不約而同安靜下來。
門口進來一位蓄著張大千鬍鬚的老先生,持著雕有鹿頭的木製拐杖,以杖擊地說:「貴客醒了。你們吵什麼吵,讓人家見笑了。」他的漢語不僅口音清晰,用詞也特別文雅。
我想這人大概就是他們說的「鹿寨主」了,點頭行禮說:「請問是鹿寨主嗎?您好。」
豐松和宛翠同時你一言我一語幫鹿寨主補充進度,爭相請寨主主持公道。鹿寨主聽完之後,不置可否,慢條斯理對我點頭說:「小姐,我可以稱呼您『意凝』嗎?」
「是的,我叫蘇『玉』凝。」我不著痕跡糾正。
「意凝啊,見到蒼狼把妳救回來,我很高興,好久沒有跟漢人說說話了。妳已經知道我的漢語姓是『鹿』。我替自己取了個漢語名,叫『鹿放翁』。」
我說:「宋朝好像有個詩人陸游也叫這個名字。」
「妳果然有知識。」鹿寨主點頭,垂到胸前的鬍鬚,每次開口都一顫一顫的,「我們族人沒有姓氏,姓都是按地名或動物取的,漢化深一點也跟漢人姓。我大概是這附近漢化最深的人吧。唔……見到了妳,我想起當年在昆明上學的時光。人真矛盾不是,在城市裡成天想著學漢人,回到家鄉雄心勃勃把漢人文化教給下一代,卻害怕下一代忘記祖先的本,下了山,看到平地的花花世界,就不回家了。我的大兒子就是這樣丟的。唉!當初送他下山讀書,全寨子傾家蕩產,就期盼他來改善我們的生活,沒料到會像石塊丟進獨龍江,就這樣不見了。幾年一次託人送錢回來,可是錢在這裡有什麼用處,還不如送些食物或傷藥比較實在。要不要漢化,像走獨木橋,很難平衡不是。妳身為漢人,應該很難體會我們這樣的情緒吧?」
「這大概跟我讀外文類似,又要西化,又怕太西化,同樣的矛盾吧。」我微笑應答,但心裡急著,他幹嘛跟我扯這些?我要回家……
鹿寨主像是漂浮在迷離的往日夢境,悠然說:「我私心是很希望妳留在這裡這段時間,多教教這些孩子禮貌。他們啊,從小是跟著我學漢語,底子都還不錯,可畢竟是習慣拿刀動劍的,動不動就……唉,不好意思,我說多了。聽說妳是失憶了?」
「……」我不願承認。做學術的人不能幻聽又失憶,絕對不能。
他以為我默認了,目光同情地說:「聽說失憶的人看到熟悉的景物,能喚起印象。等妳傷勢好了之後,我們就請蒼狼帶妳去他發現妳的地方。」
「不好意思,請問我的傷勢大約什麼時候會好呢?因為我目前聽到的訊息不是很一致,孔先生說兩三天就好,阿卡查先生說永遠好不了。」
鹿寨主表情淡定不以為意,說:「妳應該能在封山前好起來。」
「封山?」
「這裡每年冬季都會下大雪,車馬不通,會斷絕交通大半年。大約是從一月中旬左右開始。」
我聽到「一月中旬」就傻眼了,我應該是十一月就要回臺灣了,怎麼能等到一月中旬?等於我下半學期都缺席了,要是影響到學位,對我來說跟記大過留級沒有兩樣,我的人生將留下汙點,不敢想像媽會有什麼反應。
我連忙說:「不好意思,請問今天是幾月幾日?我必須趕在機票回程日期之前離開。」
宛翠走向牆角,拿來一條細麻繩給鹿寨主。鹿寨主數數繩結,說:「今天是十月十八日。陰曆。」
我試著不露出詫異,鎮定地問:「陽曆呢?」
「不知道。太久沒記了。」
「……不要緊,反正,我需要立刻到機場。立刻。」講到這裡,我才想起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我的行李,皮夾、護照、機票都在裡面,還有一個裝了3G 網卡的智慧型手機。如果連得上線,那將是救命仙丹,因此我問:「請問你們有沒有看到我的行李?」
「沒有。」鹿寨主說:「蒼狼發現妳的時候,妳大概就沒帶著行李了。如果他有看到,不可能沒帶回來。」
「那個背包是綠色的帆布後背包,大約這麼大,有點重。」我用手比劃,「我揹起來是覺得吃力了一點。」
鹿寨主說:「沒有。」
我不得不把話說白:「會不會是蒼狼揹不動?」
「不可能!」宛翠大聲插嘴,好像我褻瀆了最尊貴的神明,「就算妳的背包跟公鹿一樣大,他也帶得回來。」
我心中一寒,該不會是被那個叫蒼狼的私吞了吧?這地方窮鄉僻壤,餓肚子的人做得出什麼事,誰料想得到?唉,不管怎樣,離開這裡優先,只要連絡上臺灣,機票、護照、臺胞證都好解決。
「鹿寨主,拜託您。」我拉住鹿寨主的五彩衣角,以示嚴重,「我現在正在學期中,要趕論文畢業,如果等到傷好才回去,會影響到學位。請不管用什麼方法務必要盡快送我下山,我會請我父母給您們酬勞。感謝您了。」
鹿寨主應允說:「好,既然這麼急,趕明早就請蒼狼揹妳下山,他的腳程特別快,大約三天就能到貢山縣城──豐松,你去找蒼狼過來。」
「謝謝!謝謝!」我喜極了,目送豐松快步出了門。
在等待那個「蒼狼」的過程中,宛翠問我:「論文是什麼?」
我說:「那是一種學術研究的文章。研究者會先蒐集資料,經過一些研究方法或科學實驗方法的設定,去執行並且分析之後,得到的綜合論述結果。」
宛翠歪頭,瞇著眼睛:「為什麼妳說的每個字我都聽得懂,可是意思我全都不懂?」
鹿寨主低頭對她解釋說:「那是都市人追求的一種東西,就像蒼狼追猛嘎,或巫醫追陰陽草一樣。」宛翠立刻點頭表示了解,似乎這是個多麼傳神的比喻。
我感到很洩氣,雖然明知學術之路愈往上愈孤寂,但是每當聽到媽說:「到了金字塔頂端,要習慣沒人對話。」我還是不禁想:是金字塔,還是象牙塔?每次光是跟人家解釋什麼是語言學,就足以花掉二十分鐘,難道一輩子都要這麼累嗎?
正當我怔忡間,外頭又傳來「嗚──嗚──」的號角聲。所有人都交換眼色,默不吭聲,那種樣子有點像災難片裡的末日降臨之類的。
我不禁問:「請問那號角聲是幹什麼的?」
鹿寨主轉頭對宛翠說:「去準備酒菜,為意凝好好接風又餞行一下。」
我依然側頭想聽出端倪,那個號角聲像催魂的喪鐘,不似音樂。
豐松展開臂膀,笑說:「這是我們為妳準備的舞曲,因為妳不能跳,我跳給妳看。」他踏地歌舞,鏗鏘有力,嘹亮的歌聲把號角聲蓋了過去,一雙長毛的粗腿孔武躍動,整個竹房都在上下震盪。
宛翠進了屋來,白了豐松一眼,用怒語罵了一句大約是「神經病,要跳出去跳去」之類的話。她左手抱著幾管竹筒釀的包穀酒,右手捧著一大碗麵糊狀物,倒到屋心炭火堆上架設的石板,滋的一聲,餅香四溢。她衝著我一笑:「這是石板粑粑。城市肯定沒有的。」
大家都坐定之後,一位叫「楠拉」的老婆婆隨後過來,她臉上紋著蝴蝶狀的黥面,據說是寨中的巫師兼名廚,因為地位尊崇,因此也受邀。她不會說漢語,用手勢教了我:「這炭火堆叫『火塘』。族人穿的衣服叫『約多』。」我用語音學訓練習得的發音技巧,一次就把音發得九成準,引得大家紛紛鼓掌。
楠拉打開一盅說是燒酒燜雞的沉重瓦罐,並放了一盤據說是當地珍饈在我面前。我先是在蒸汽中聞到一股混合野蒜和辣椒的撲鼻香,眼前冒出許多小小、白白,挺可
愛的豆子狀菜餚,並不真的是豆子,比較像是……蟲子。
宛翠說:「這是蜂蛹,最滋補的。」
「啊──」我後避尖叫,「拿開,拿開。」
所有人盡皆錯愕。
「對不起,我我……我不敢吃蟲。」
阿卡查皺起鼻子罵:「妳別有眼無珠,這可是這裡最講究的菜,要不是鹿寨主交代,大家想吃還吃不到。」
「抱歉。」我趕緊低頭,「我不是故意要辜負你們的心意,只是我超級怕蟲。我連蝴蝶或蠶寶寶都不敢接近,連圖片都不敢摸。」
「很好吃的。」宛翠當先舉筷夾了一粒蜂蛹送到口中,「牠又不會咬妳。妳吃吃看就知道,獨龍族有好多百歲人瑞,都是因為吃了蜂蛹。」她夾了另一粒,送到我嘴前。「吃。」
她不是像臺灣女孩那樣習慣膩聲說「吃嘛」、「吃吧」,也不是說「吃一口好不好」這種疑問句,就是簡簡單單卻不容拒卻的一個「吃」,就把我推上了刑臺。
正當極度尷尬的時分,豐松衝了進來,急切得像衣服背後著了火似的,大聲嚷嚷:「寨主,蒼狼他……蒼狼他……」他用極驚奇極崇敬的眼光瞅著我,竟然朝我跪了下來。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