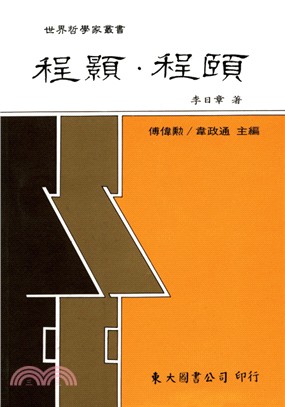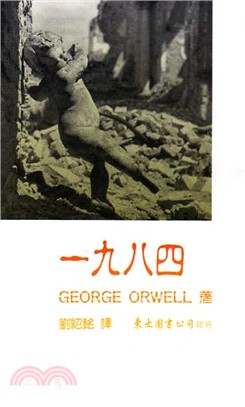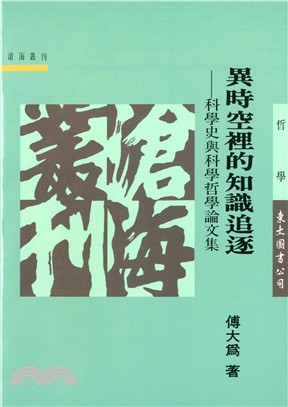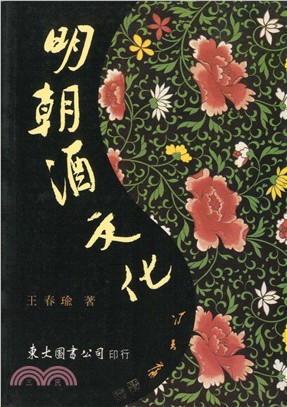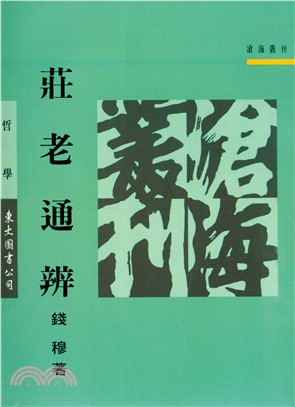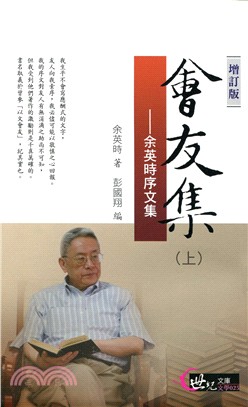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海日汗」,一個蒙文名字,海日代表山岳,海日汗則指令人喜愛。他是一個存在於詩人想像中的少年,也是每個人內心深處懵懂的自我。
21封寫給海日汗的信,是席慕蓉發掘自我的軌跡與告白,字字沁人心肺,值得珍藏。
親愛的海日汗,我們可能見過,也可能從不相識。
我要提筆寫給你的信,希望可以對你有些用處。
讓你能在百萬、千萬,甚至萬萬的人群之中,安靜又平和地尋找到真正的自己。
詩人及畫家席慕蓉,以六年的時光、綿密的筆觸,寫下她想對心中那個生活在內蒙古的少年族人的期許,分享她在這條「原鄉尋覓」的長路上,與最陌生又最熟悉的事物一次次的邂逅。
席慕蓉從不曾忘記,在1955年初中二年級的那一天,老師在講堂上對蒙古人的輕率與武斷。而這是所有來自於蒙古族的孩子的共同記憶,有人大聲抗議,有人憤而離座,有人因此被記過處分……但這是一個對於思索根源的覺醒,是生命最重要的一堂震撼教育。
直到1989年,席慕蓉才初見父母親誕生的蒙古高原。從此魂縈夢繫,前往蒙古成為年復一年的歸鄉行腳,因為那裡始終存在著最終的孺慕,如同海洋之於萬物。
我們都曾經是小小的海日汗。不論屬於何種國籍、血統、姓氏,不論居住在哪一塊土地上,我們始終在尋找自己的根源、自己的定位。透過席慕蓉的文字,這份「懷鄉」的憂愁與情感,終於找到了最好的詮釋。
21封寫給海日汗的信,是席慕蓉發掘自我的軌跡與告白,字字沁人心肺,值得珍藏。
親愛的海日汗,我們可能見過,也可能從不相識。
我要提筆寫給你的信,希望可以對你有些用處。
讓你能在百萬、千萬,甚至萬萬的人群之中,安靜又平和地尋找到真正的自己。
詩人及畫家席慕蓉,以六年的時光、綿密的筆觸,寫下她想對心中那個生活在內蒙古的少年族人的期許,分享她在這條「原鄉尋覓」的長路上,與最陌生又最熟悉的事物一次次的邂逅。
席慕蓉從不曾忘記,在1955年初中二年級的那一天,老師在講堂上對蒙古人的輕率與武斷。而這是所有來自於蒙古族的孩子的共同記憶,有人大聲抗議,有人憤而離座,有人因此被記過處分……但這是一個對於思索根源的覺醒,是生命最重要的一堂震撼教育。
直到1989年,席慕蓉才初見父母親誕生的蒙古高原。從此魂縈夢繫,前往蒙古成為年復一年的歸鄉行腳,因為那裡始終存在著最終的孺慕,如同海洋之於萬物。
我們都曾經是小小的海日汗。不論屬於何種國籍、血統、姓氏,不論居住在哪一塊土地上,我們始終在尋找自己的根源、自己的定位。透過席慕蓉的文字,這份「懷鄉」的憂愁與情感,終於找到了最好的詮釋。
作者簡介
席慕蓉
祖籍蒙古,生於四川,童年在香港度過,成長於台灣。於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後,赴歐深造。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
在國內外舉行個展多次,曾獲比利時皇家金牌獎、布魯塞爾市政府金牌獎、歐洲美協兩項銅牌獎、金鼎獎最佳作詞、中興文藝獎章新詩獎及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藝獎章等。曾任台灣新竹師範學院教授多年,現為專業畫家。
著作有詩集、散文集、畫冊及選本等五十餘種,讀者遍及海內外。近十餘年來,潛心探索蒙古文化,以原鄉為創作主題。現為內蒙古大學、寧夏大學、南開大學、呼倫貝爾學院、呼和浩特民族學院等校的名譽(或客座)教授,內蒙古博物院榮譽館員,鄂溫克族及鄂倫春族的榮譽公民。
詩作被譯為多國文字,在蒙古國、美國及日本均有單行本出版發行。
祖籍蒙古,生於四川,童年在香港度過,成長於台灣。於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後,赴歐深造。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
在國內外舉行個展多次,曾獲比利時皇家金牌獎、布魯塞爾市政府金牌獎、歐洲美協兩項銅牌獎、金鼎獎最佳作詞、中興文藝獎章新詩獎及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藝獎章等。曾任台灣新竹師範學院教授多年,現為專業畫家。
著作有詩集、散文集、畫冊及選本等五十餘種,讀者遍及海內外。近十餘年來,潛心探索蒙古文化,以原鄉為創作主題。現為內蒙古大學、寧夏大學、南開大學、呼倫貝爾學院、呼和浩特民族學院等校的名譽(或客座)教授,內蒙古博物院榮譽館員,鄂溫克族及鄂倫春族的榮譽公民。
詩作被譯為多國文字,在蒙古國、美國及日本均有單行本出版發行。
目次
導讀 席慕蓉的鄉愁 賀希格陶克陶
闕特勤碑
刻痕
泉眼
時與光
回音之地(一)
回音之地(二)
京肯蘇力德
我的困惑
伊赫奧仁
疼痛的靈魂
我的位置
兩則短訊
察干蘇力德
夏日塔拉
察哈爾部
回顧初心
一首歌的輾轉流傳
生命的盛宴
聆聽大地
嘎達梅林
草原的價值
嘎達梅林
附錄兩篇 (1)鄉關何處
(2)額濟那十年散記
闕特勤碑
刻痕
泉眼
時與光
回音之地(一)
回音之地(二)
京肯蘇力德
我的困惑
伊赫奧仁
疼痛的靈魂
我的位置
兩則短訊
察干蘇力德
夏日塔拉
察哈爾部
回顧初心
一首歌的輾轉流傳
生命的盛宴
聆聽大地
嘎達梅林
草原的價值
嘎達梅林
附錄兩篇 (1)鄉關何處
(2)額濟那十年散記
書摘/試閱
刻痕
可是,「侵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
不也是一種逐日的完成?
海日汗:
好久沒提筆了,最近過得很忙亂,不過,心裡還是常常惦念著要給你寫信這件事。說是給你寫信,其實,也是寫給我自己。
好像在向你訴說的同時,另外一個我也在慢慢醒來……
海日汗,我們的身體和心魂,不是只有這短短幾十年的記憶而已,有些細微的刻痕,來自更長久的時間,只是因為長年的掩蓋和埋藏,以致終於被遺忘了而已。我們需要彼此互相喚醒。
在這封信裡有幾張相片,其中有兩張,是上封信提到的紀念第二突厥汗國三朝老臣暾欲谷的碑石。
有一張是在極近處所攝到的碑文,海日汗,請你看一看,這碑石上的文字刻得有多深!
這些至今依然清晰的碑文,當然令我著迷,可是,更令我著迷的,還是石碑本身在一千多年無情風霜的侵蝕之下,所呈現出來的面貌。
海日汗,請你細看,原應是打磨得很光滑的平面已成斑駁,原來切割得很銳利的直角已成圓鈍,可是,你會不會覺得,這樣才更顯石碑的厚重與深沉?
我們可以說,「侵蝕」是一種逐日的削減。可是,一千多年裡每一次的風雪雨露,構成難以數計的細小和微弱的碰觸,「侵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不也是一種逐日的完成?
海日汗,如果我們每日所觸及的細節都是人格形成的一部分,那麼請你試想一下,在蒙古高原之上,在一整個又一整個的世代裡,在眾多的游牧族群的心魂之中,那不可見的刻痕又會有多深?
而也就是這些刻痕,讓我們能長成為今天的蒙古人。
所以我們才會彼此靠近,覺得親切,甚至熟悉,好像有些話,不必說出來就已經明白了……
所謂「族人」,應該就是這種關係了吧。
去年(2007)秋天,有個傍晚,黃昏的霞光異常的光明燦爛,站在金紫灰紅的霞光裡,站在一大片茫無邊際的芨芨草灘上,我新認識的朋友查嘎黎對我說了一句話:
「蒙古文化的載體是人,只要人在,文化就在。」
我相信這句話。
去年八月,參加在伊克昭盟(今稱鄂爾多斯市)烏審旗舉行的「第二屆察罕蘇力德文化節」。中間有一天,朋友帶我們去看薩拉烏素河。
海日汗,你應該知道,這是在人類考古史上赫赫有名的河流,在這裡,考古學者發掘出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活動的遺址,離今天有五萬到三萬五千年以前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認為是在十四萬年到七萬年以前,屬舊石器時代中期。)
對這片流域的考古發掘,最早是由一位蒙古牧民旺楚克的引導開始。他是帶領法國神父桑志華走向薩拉烏素河岸的領路人,因為在那片河岸上,旺楚克曾經發現一些奇異的化石。
1922到1923年,桑志華神父和隨後前來的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在這裡采集到了一些人類和脊椎動物的化石,還有石器和用火的遺跡。
其中有一顆小小的牙齒化石,經過測認後,確定是屬於一個幼童的左上方的門牙,已經石化很深了,這個孩子應該只有八、九歲。
當時,這是很轟動的發現。經時任北京協和醫院解剖室主任加拿大的解剖學家步達生在研究與測認之後,把這顆門牙定名為「Ordos Tooth」(鄂爾多斯齒)。不過,後來中國的考古學者斐文中在四十年代時,卻很不夠專業地把這個名字轉譯成「河套人」,又把這個地區的文化命名為「河套文化」,因此,多年來都使得社會大眾(包括我在內),對這個珍貴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確切地點,有了混淆和偏差。
幸好,在後來的多次發掘中,又有了許多難得的發現,是屬於這個地區所獨有的特質。最後,考古界終於把這一處遺址的發現與研究,在漢文裡定名為「薩拉烏素文化」。今日有學者也極力主張,認為「河套人」應該重新正名為「鄂爾多斯人」。
「薩拉烏素」,漢文的直譯是「黃水」。不過,這條河在蒙文裡還有一個外號,是鄂爾多斯當地人給她起的,叫「嘎拉珠薩拉烏素」。這「嘎拉珠」就是「瘋狂」的意思,所以,直譯成漢文,就是「瘋子黃河」,或者「瘋狂的黃水河」。我猜想,大概是因為這條河流有道很大的河彎,那幾乎180度迴轉的大河彎,彎曲度之大超乎我們的想像了吧?
這個外號,是查嘎黎告訴我的。
那天,一車人興高采烈地直往薩拉烏素河的大溝灣而去,那裡就是旺楚克與桑志華發現「薩拉烏素文化」的第一現場!
我坐在駕駛座右邊,查嘎黎剛好坐在我身後,我們原本不熟,才剛剛認識了兩、三天而已。但是,他在說了「嘎拉珠薩拉烏素」這個外號之後,緊接著,又給我講了一段民間傳說,他說:
關於這條河,還有個很老的故事。
說是很久很久以前,有個征戰多年的武士,終於可以回家了,就跨上駿馬,沿著蒙古高原的邊界直奔故鄉而來。奇怪的是,走了很多很多天,明明覺得應該早就到家了,眼前曠野無垠,卻怎麼也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有天夜裡,疲憊的武士還在東尋西探,摸索前行。走著走著,卻總是覺得身後有響動,說不出來那是什麼樣的聲音緊跟在身後。好像他走,那聲音也跟著走,他停,那聲音也跟著停。武士雖然是個有膽量的人,可是,月夜裡,走投無路的他來到一座又高又黑的大山梁之前,也不禁有些遲疑。
於是,猛然回頭一看,才發現,原來緊跟在身後的響動,竟然是一條河的水流。月光下,那條河好像也找不到路,跟在武士的身後,也像他一樣的東張西望,猶疑難決。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襯得高大的山梁更深更暗,那條河的水流倒是很清澈,剛才不能分辨究竟是什麼的響動,原來是水聲,叮叮咚咚的,還挺好聽。
武士心想,如果放心地流動起來,應該是條很漂亮的小河吧,眼前卻只能畏畏縮縮地緊跟在陌生人的身後,怎麼也不敢超前一步。
原來,迷了路的河,也跟迷了路的自己一樣可憐啊!
武士心裡忽然覺得很悲傷,不禁抬頭望向天空,高聲呼求:
「蒼天啊!請讓迷路的人找到自己的家鄉,讓迷路的河找到自己的河道吧!」
這邊話聲剛落,忽然間,那邊黑色的山梁就自動往左右分開了。前面再無障礙,那條原本是猶疑觀望的河流,頓時就直直往前衝去,並且身軀暴長,變成一條水流洶湧、水勢兇猛,河面極為寬闊的大河,轉瞬間就把武士推開,把他遠遠地攔在北邊的河岸上了。
武士迷惘驚詫的眼光終於從河面收回之後,一轉身,他和他的坐騎就看見了回家的路,沿著河岸再往北走,沒有多久,就找到自己的家了。
那天,在行駛的車中聆聽查嘎黎的講述,對我來說,是一段很奇妙的經驗。認識這位身材高大壯碩、神情嚴肅的蒙古朋友,不過只有兩、三天而已,沒聽他說過幾句話,在宴席上總是沉默不言。
但是,在薩拉烏素河邊,他忽然變得喜笑顏開,滔滔不絕。在他講述這段傳說的時候,好像生命內在的活潑和熱情如泉湧般呈現,還帶著一種質樸與天真的詩人特質,讓我這個聽者驚喜萬分……
海日汗,與其說我是受了這段傳說的感動,不如說我是受了查嘎黎講述這段傳說時,他內在的生命力強烈噴湧迸發的狀態而感動。
這想必就是一個蒙古人在與他珍愛的文化共處時的生命狀態了。
海日汗,我就是從那一刻開始真正認識了這位朋友的,是多麼歡喜的感覺啊!
那一天,更讓我喜出望外的是薩拉烏素河。
原來,我從書冊的文字裡得到的印象,這應該已是一條瀕臨乾涸枯竭的河流了。在文字裡,關於薩拉烏素河的介紹,除了「遺址」「化石」「骨骸」等等以外,就是什麼「放射性碳素」「鈾系法」等等作為斷代依據的科學名詞,總讓我以為,這裡和許多書本上呈現的考古現場的圖片一樣,在河岸和河床上都遍布著碎裂的岩塊、無止無盡的黃沙,景象荒涼已極。
但是,2007年的八月十六日,我所見到的薩拉烏素河卻和自己的想像完全相反。
當然,最初從大溝灣的上方俯瞰之時,是有些荒涼的感覺。雖然也有綠色植被,但是岩塊與沙土也占了很大的面積。不過,再往峽谷下方行去,走到一條擁有許多泉眼的源流之時,我所見到的薩拉烏素河就是一條生意盎然、綠意盎然的河流了。
海日汗,這是從多少年前流到現在還沒有枯竭的泉眼,從多少年前活到現在還沒有老去的河流,水聲如傳說裡一般的琤瑽悅耳,河岸上芳草鮮美,林木蒼翠。海日汗,這是神話仙境在我眼前顯現的真實版本啊!
可惜在此只能給你看一、兩張相片而已,不能完整傳達那種讓我萬分驚喜的美麗和親切。
是的,海日汗,我說的是「親切」。
我終於來到在書冊裡翻尋過無數次的薩拉烏素河的河邊了,驚喜過後,心中湧出的卻是一種無邊的安靜與滿足,好像在我周遭的景物,包括河面上每一寸細碎的波光,河岸上每一株小草的柔嫩多汁,林間每一陣微風穿過之後葉片的顫動,所有的光影、色面與線條的變幻,都在同時緩慢而又銳利地進入了我的身心,彷彿是輕輕的觸動,卻又留下了極為繁複與細微的刻痕……一切似曾相識。
海日汗,我想,應該就是這樣的刻痕,一日復一日地讓我逐漸長成為一個我所希望能成為的人──
一個不再迷路的回家的人。
夜已深了,今天就寫到這裡。
祝福。
慕蓉 2008年2月8日
可是,「侵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
不也是一種逐日的完成?
海日汗:
好久沒提筆了,最近過得很忙亂,不過,心裡還是常常惦念著要給你寫信這件事。說是給你寫信,其實,也是寫給我自己。
好像在向你訴說的同時,另外一個我也在慢慢醒來……
海日汗,我們的身體和心魂,不是只有這短短幾十年的記憶而已,有些細微的刻痕,來自更長久的時間,只是因為長年的掩蓋和埋藏,以致終於被遺忘了而已。我們需要彼此互相喚醒。
在這封信裡有幾張相片,其中有兩張,是上封信提到的紀念第二突厥汗國三朝老臣暾欲谷的碑石。
有一張是在極近處所攝到的碑文,海日汗,請你看一看,這碑石上的文字刻得有多深!
這些至今依然清晰的碑文,當然令我著迷,可是,更令我著迷的,還是石碑本身在一千多年無情風霜的侵蝕之下,所呈現出來的面貌。
海日汗,請你細看,原應是打磨得很光滑的平面已成斑駁,原來切割得很銳利的直角已成圓鈍,可是,你會不會覺得,這樣才更顯石碑的厚重與深沉?
我們可以說,「侵蝕」是一種逐日的削減。可是,一千多年裡每一次的風雪雨露,構成難以數計的細小和微弱的碰觸,「侵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不也是一種逐日的完成?
海日汗,如果我們每日所觸及的細節都是人格形成的一部分,那麼請你試想一下,在蒙古高原之上,在一整個又一整個的世代裡,在眾多的游牧族群的心魂之中,那不可見的刻痕又會有多深?
而也就是這些刻痕,讓我們能長成為今天的蒙古人。
所以我們才會彼此靠近,覺得親切,甚至熟悉,好像有些話,不必說出來就已經明白了……
所謂「族人」,應該就是這種關係了吧。
去年(2007)秋天,有個傍晚,黃昏的霞光異常的光明燦爛,站在金紫灰紅的霞光裡,站在一大片茫無邊際的芨芨草灘上,我新認識的朋友查嘎黎對我說了一句話:
「蒙古文化的載體是人,只要人在,文化就在。」
我相信這句話。
去年八月,參加在伊克昭盟(今稱鄂爾多斯市)烏審旗舉行的「第二屆察罕蘇力德文化節」。中間有一天,朋友帶我們去看薩拉烏素河。
海日汗,你應該知道,這是在人類考古史上赫赫有名的河流,在這裡,考古學者發掘出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活動的遺址,離今天有五萬到三萬五千年以前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認為是在十四萬年到七萬年以前,屬舊石器時代中期。)
對這片流域的考古發掘,最早是由一位蒙古牧民旺楚克的引導開始。他是帶領法國神父桑志華走向薩拉烏素河岸的領路人,因為在那片河岸上,旺楚克曾經發現一些奇異的化石。
1922到1923年,桑志華神父和隨後前來的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在這裡采集到了一些人類和脊椎動物的化石,還有石器和用火的遺跡。
其中有一顆小小的牙齒化石,經過測認後,確定是屬於一個幼童的左上方的門牙,已經石化很深了,這個孩子應該只有八、九歲。
當時,這是很轟動的發現。經時任北京協和醫院解剖室主任加拿大的解剖學家步達生在研究與測認之後,把這顆門牙定名為「Ordos Tooth」(鄂爾多斯齒)。不過,後來中國的考古學者斐文中在四十年代時,卻很不夠專業地把這個名字轉譯成「河套人」,又把這個地區的文化命名為「河套文化」,因此,多年來都使得社會大眾(包括我在內),對這個珍貴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確切地點,有了混淆和偏差。
幸好,在後來的多次發掘中,又有了許多難得的發現,是屬於這個地區所獨有的特質。最後,考古界終於把這一處遺址的發現與研究,在漢文裡定名為「薩拉烏素文化」。今日有學者也極力主張,認為「河套人」應該重新正名為「鄂爾多斯人」。
「薩拉烏素」,漢文的直譯是「黃水」。不過,這條河在蒙文裡還有一個外號,是鄂爾多斯當地人給她起的,叫「嘎拉珠薩拉烏素」。這「嘎拉珠」就是「瘋狂」的意思,所以,直譯成漢文,就是「瘋子黃河」,或者「瘋狂的黃水河」。我猜想,大概是因為這條河流有道很大的河彎,那幾乎180度迴轉的大河彎,彎曲度之大超乎我們的想像了吧?
這個外號,是查嘎黎告訴我的。
那天,一車人興高采烈地直往薩拉烏素河的大溝灣而去,那裡就是旺楚克與桑志華發現「薩拉烏素文化」的第一現場!
我坐在駕駛座右邊,查嘎黎剛好坐在我身後,我們原本不熟,才剛剛認識了兩、三天而已。但是,他在說了「嘎拉珠薩拉烏素」這個外號之後,緊接著,又給我講了一段民間傳說,他說:
關於這條河,還有個很老的故事。
說是很久很久以前,有個征戰多年的武士,終於可以回家了,就跨上駿馬,沿著蒙古高原的邊界直奔故鄉而來。奇怪的是,走了很多很多天,明明覺得應該早就到家了,眼前曠野無垠,卻怎麼也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有天夜裡,疲憊的武士還在東尋西探,摸索前行。走著走著,卻總是覺得身後有響動,說不出來那是什麼樣的聲音緊跟在身後。好像他走,那聲音也跟著走,他停,那聲音也跟著停。武士雖然是個有膽量的人,可是,月夜裡,走投無路的他來到一座又高又黑的大山梁之前,也不禁有些遲疑。
於是,猛然回頭一看,才發現,原來緊跟在身後的響動,竟然是一條河的水流。月光下,那條河好像也找不到路,跟在武士的身後,也像他一樣的東張西望,猶疑難決。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襯得高大的山梁更深更暗,那條河的水流倒是很清澈,剛才不能分辨究竟是什麼的響動,原來是水聲,叮叮咚咚的,還挺好聽。
武士心想,如果放心地流動起來,應該是條很漂亮的小河吧,眼前卻只能畏畏縮縮地緊跟在陌生人的身後,怎麼也不敢超前一步。
原來,迷了路的河,也跟迷了路的自己一樣可憐啊!
武士心裡忽然覺得很悲傷,不禁抬頭望向天空,高聲呼求:
「蒼天啊!請讓迷路的人找到自己的家鄉,讓迷路的河找到自己的河道吧!」
這邊話聲剛落,忽然間,那邊黑色的山梁就自動往左右分開了。前面再無障礙,那條原本是猶疑觀望的河流,頓時就直直往前衝去,並且身軀暴長,變成一條水流洶湧、水勢兇猛,河面極為寬闊的大河,轉瞬間就把武士推開,把他遠遠地攔在北邊的河岸上了。
武士迷惘驚詫的眼光終於從河面收回之後,一轉身,他和他的坐騎就看見了回家的路,沿著河岸再往北走,沒有多久,就找到自己的家了。
那天,在行駛的車中聆聽查嘎黎的講述,對我來說,是一段很奇妙的經驗。認識這位身材高大壯碩、神情嚴肅的蒙古朋友,不過只有兩、三天而已,沒聽他說過幾句話,在宴席上總是沉默不言。
但是,在薩拉烏素河邊,他忽然變得喜笑顏開,滔滔不絕。在他講述這段傳說的時候,好像生命內在的活潑和熱情如泉湧般呈現,還帶著一種質樸與天真的詩人特質,讓我這個聽者驚喜萬分……
海日汗,與其說我是受了這段傳說的感動,不如說我是受了查嘎黎講述這段傳說時,他內在的生命力強烈噴湧迸發的狀態而感動。
這想必就是一個蒙古人在與他珍愛的文化共處時的生命狀態了。
海日汗,我就是從那一刻開始真正認識了這位朋友的,是多麼歡喜的感覺啊!
那一天,更讓我喜出望外的是薩拉烏素河。
原來,我從書冊的文字裡得到的印象,這應該已是一條瀕臨乾涸枯竭的河流了。在文字裡,關於薩拉烏素河的介紹,除了「遺址」「化石」「骨骸」等等以外,就是什麼「放射性碳素」「鈾系法」等等作為斷代依據的科學名詞,總讓我以為,這裡和許多書本上呈現的考古現場的圖片一樣,在河岸和河床上都遍布著碎裂的岩塊、無止無盡的黃沙,景象荒涼已極。
但是,2007年的八月十六日,我所見到的薩拉烏素河卻和自己的想像完全相反。
當然,最初從大溝灣的上方俯瞰之時,是有些荒涼的感覺。雖然也有綠色植被,但是岩塊與沙土也占了很大的面積。不過,再往峽谷下方行去,走到一條擁有許多泉眼的源流之時,我所見到的薩拉烏素河就是一條生意盎然、綠意盎然的河流了。
海日汗,這是從多少年前流到現在還沒有枯竭的泉眼,從多少年前活到現在還沒有老去的河流,水聲如傳說裡一般的琤瑽悅耳,河岸上芳草鮮美,林木蒼翠。海日汗,這是神話仙境在我眼前顯現的真實版本啊!
可惜在此只能給你看一、兩張相片而已,不能完整傳達那種讓我萬分驚喜的美麗和親切。
是的,海日汗,我說的是「親切」。
我終於來到在書冊裡翻尋過無數次的薩拉烏素河的河邊了,驚喜過後,心中湧出的卻是一種無邊的安靜與滿足,好像在我周遭的景物,包括河面上每一寸細碎的波光,河岸上每一株小草的柔嫩多汁,林間每一陣微風穿過之後葉片的顫動,所有的光影、色面與線條的變幻,都在同時緩慢而又銳利地進入了我的身心,彷彿是輕輕的觸動,卻又留下了極為繁複與細微的刻痕……一切似曾相識。
海日汗,我想,應該就是這樣的刻痕,一日復一日地讓我逐漸長成為一個我所希望能成為的人──
一個不再迷路的回家的人。
夜已深了,今天就寫到這裡。
祝福。
慕蓉 2008年2月8日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