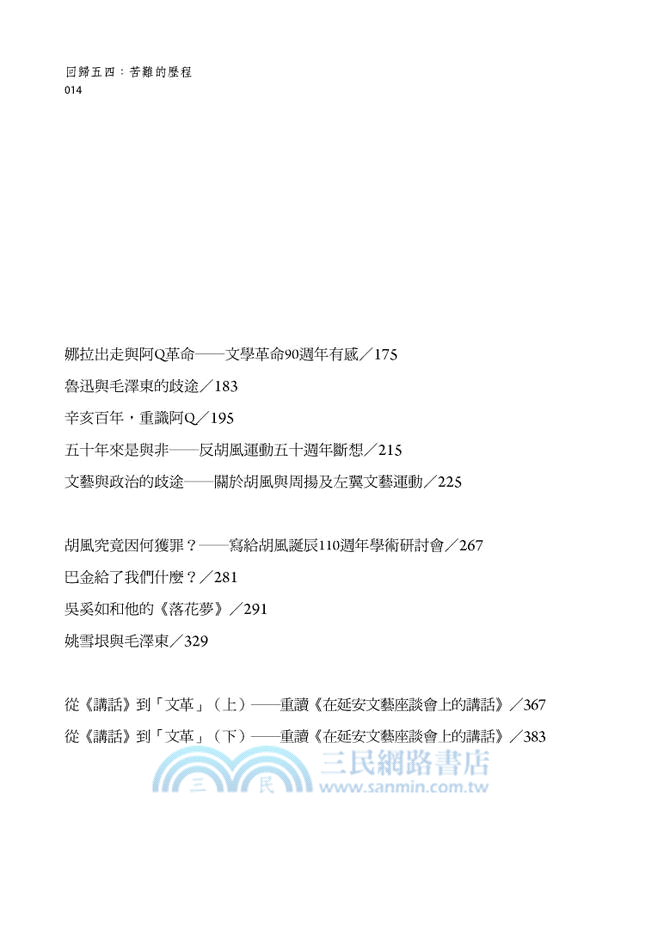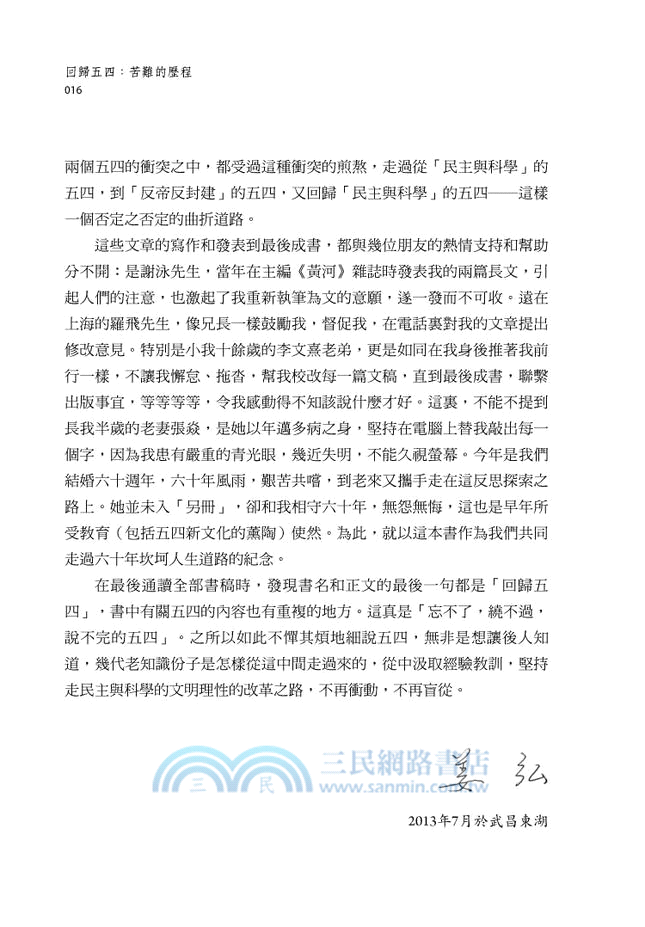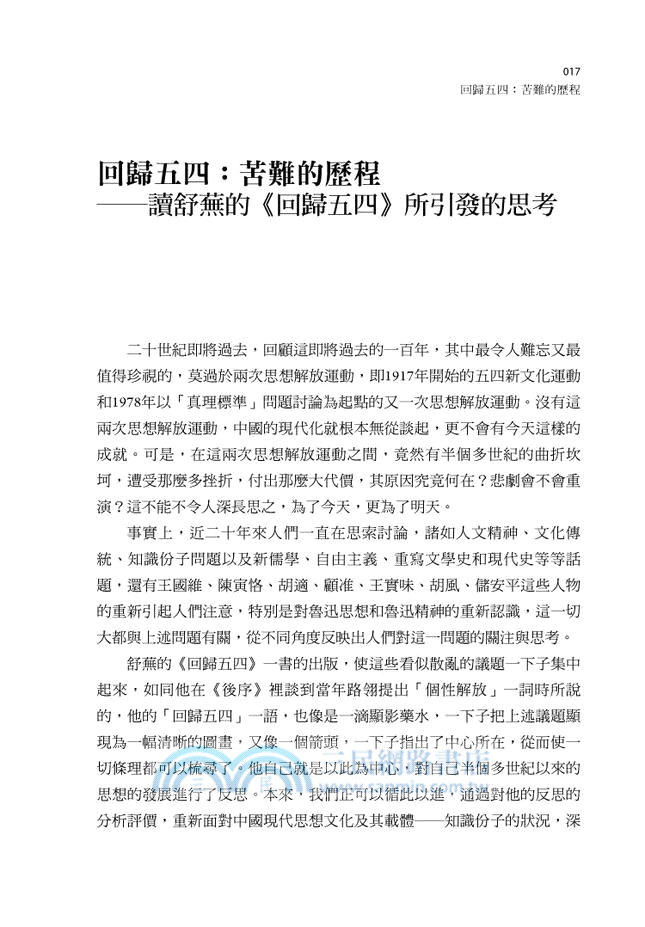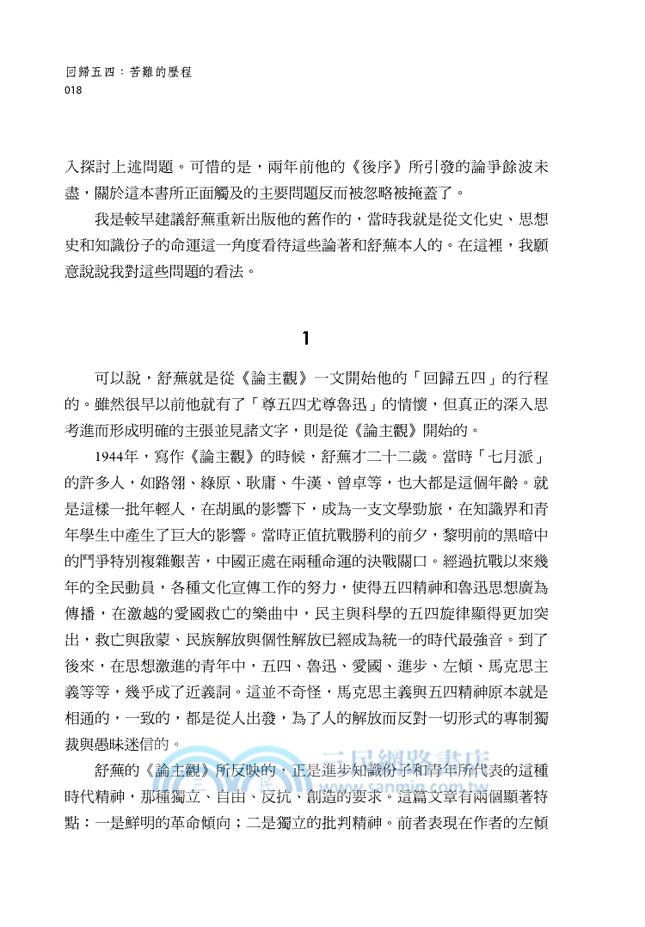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原籍浙江紹興,1932年1月出生於河南焦作。上世紀五十年代,先後在武漢市文聯創作研究部、中南作家協會《長江文藝》編輯部工作。親歷了1955、1957、1966年的煉獄。曾在中學代課,後在大學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和美學,退休後從事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化史和知識份子問題的研究。
序
前言
──關於本書的由來
這是我的第一本書,收錄的是西元2000年以來發表的部分論文,是在朋友們的鼓勵、催促和幫助下編成的。為感謝朋友們的鼓勵和幫助,我應該在這裏說說這些文章和這本書的由來,特別是思想觀念的形成與發展的脈絡。
我從1951年發表第一篇文學評論起,至今已經過去了六十二年。這六十二年間曾經兩次擱筆──1957年反右以後的二十二年;1989年「六四」以後的十年,加起來共三十二年。前一次擱筆是被迫的,後一次是自願的。在這之外的舊作中,有一部分是寫於1979年以後的反思文字,曾有過敝帚自珍的情緒,想留作紀念,後來也在朋友的勸說下決心割愛,因為那些文章還未跳出「凡是」牢籠,雖然不再「凡是」毛了,但還在「凡是」馬恩,依然在「我們」的群體裏代表著什麼,沒有回歸「自我」,說「我」自己的話。所以最後決定那幾十萬字統統不要了。
這裏收錄的文章中,有多篇是談論五四的,特別是涉及「兩個五四」的問題。這要感謝兩位我最敬佩的思想先驅和三位我認識的長者。是《顧准文集》和《殷海光選集》(原版),把我從文藝的窄狹空間拉到了近現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長河中,並讓我從中看到了我自己的身影。在和劉緒貽、李慎之、王元化這三位長者的交往中,我受到了更多啟發,他們所講述的自身經歷和思想變化,不僅印證了我對顧准和殷海光的理解,也看到了我和他們的共同之處──這幾代出生於上世紀前期的知識份子,都處在兩個五四的衝突之中,都受過這種衝突的煎熬,走過從「民主與科學」的五四,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又回歸「民主與科學」的五四──這樣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曲折道路。
這些文章的寫作和發表到最後成書,都與幾位朋友的熱情支持和幫助分不開:是謝泳先生,當年在主編《黃河》雜誌時發表我的兩篇長文,引起人們的注意,也激起了我重新執筆為文的意願,且欲罷不能。遠在上海的羅飛先生,像兄長一樣鼓勵我,督促我,在電話裏對我的文章提出修改意見。特別是小我十余歲的李文熹老弟,更是如同在我身後推著我前行一樣,不讓我懈怠、拖遝,幫我校改每一篇文稿,直到最後成書,聯繫出版事宜,等等等等,令我感動得不知該說什麼才好。這裏,不能不提到長我半歲的老妻張焱,是她以年邁多病之身,堅持在電腦上替我敲出每一個字,因為我患有嚴重的青光眼,幾近失明,不能久視螢幕。今年是我們結婚六十周年,六十年風雨,艱苦共嘗,到老來又攜手走在這反思探索之路上。她並未入「另冊」,卻和我相守六十年,無怨無悔,這也是早年所受教育(包括五四新文化的薰陶)使然。為此,就以這本書作為我們共同走過六十年坎坷人生道路的紀念。
在最後通讀全部書稿時,發現書名和正文的最後一句都是「回歸五四」,書中有關五四的內容也有重複的地方。這真是「忘不了,繞不過,說不完的五四」。之所以如此不憚其煩地細說五四,無非是想讓後人知道,幾代老知識份子是怎樣從這中間走過來的,從中汲取經驗教訓,堅持走民主與科學的文明理性的改革之路,不再衝動,不再盲從。
姜弘
2013年7月於武昌東湖
目次
序/謝泳
前言──關於本書的由來
回歸五四:苦難的歷程
──讀舒蕪的《回歸五四》所引發的思考
關於「回歸五四」問題致舒蕪
──附:舒蕪的回信
百年啟蒙,兩個五四
──讀殷海光、顧准著作所想到的
關於百年啟蒙問題致王元化先生
關於五四與遊民文化問題致王元化先生
有關王元化先生反思五四的幾個問題
──給李文熹的兩封信
和李慎之先生談魯迅和知識份子的命運問題
和李慎之先生談「新啟蒙」
──一封沒有寄出的信
正本清源說五四
──讀王福湘的《魯迅與陳獨秀》
和五四同行
──讀劉緒貽先生的囗述自傳
與時代共進,和五四同行
──賀劉緒貽先生百歲華誕
娜拉出走與阿Q革命
──文學革命九十周年有感
魯迅與毛澤東的歧途
辛亥百年,重識阿Q
五十年來是與非
──反胡風運動五十周年斷想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關於胡風與周揚及左翼文藝運動
巴金給了我們什麼
──巴金逝世一周年有感
吳奚如和他的《落花夢》
姚雪垠與毛澤東
從《講話》到「文革」(上)
──重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從《講話》到「文革」(下)
──重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書摘/試閱
回歸五四:苦難的歷程
──讀舒蕪的《回歸五四》所引發的思考
二十世紀即將過去,回顧這即將過去的一百年,其中最令人難忘又最值得珍視的,莫過於兩次思想解放運動,即1917年開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和1978年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為起點的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沒有這兩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國的現代化就根本無從談起,更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成就。可是,在這兩次思想解放運動之間,竟然有半個多世紀的曲折坎坷,遭受那麼多挫折,付出那麼大代價,其原因究竟何在?悲劇會不會重演?這不能不令人深長思之,為了今天,更為了明天。
事實上,近二十年來人們一直在思索討論,諸如人文精神、文化傳統、知識份子問題以及新儒學、自由主義、重寫文學史和現代史等等話題,還有王國維、陳寅恪、胡適、顧准、王實味、胡風、儲安平這些人物的重新引起人們注意,特別是對魯迅思想和魯迅精神的重新認識,這一切大都與上述問題有關,從不同角度反映出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與思考。
舒蕪的《回歸五四》一書的出版,使這些看似散亂的議題一下子集中起來,如同他在《後序》裡談到當年路翎提出「個性解放」一詞時所說的,他的「回歸五四」一語,也像是一滴顯影藥水,一下子把上述議題顯現為一幅清晰的圖畫,又像一個箭頭,一下子指出了中心所在,從而使一切條理都可以梳尋了。他自己就是以此為中心,對自己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思想的發展進行了反思。本來,我們正可以循此以進,通過對他的反思的分析評價,重新面對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及其載體──知識份子的狀況,深入探討上述問題。可惜的是,兩年前他的《後序》所引發的論爭餘波未盡,關於這本書所正面觸及的主要問題反而被忽略被掩蓋了。
我是較早建議舒蕪重新出版他的舊作的,當時我就是從文化史、思想史和知識份子的命運這一角度看待這些論著和舒蕪本人的。在這裡,我願意說說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1
可以說,舒蕪就是從《論主觀》一文開始他的「回歸五四」的行程的。雖然很早以前他就有了「尊五四尤尊魯迅」的情懷,但真正的深入思考進而形成明確的主張並見諸文字,則是從《論主觀》開始的。
1944年,寫作《論主觀》的時候,舒蕪才二十二歲。當時「七月派」的許多人,如路翎、綠原、耿庸、牛漢、曾卓等,也大都是這個年齡。就是這樣一批年輕人,在胡風的影響下,成為一支文學勁旅,在知識界和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正值抗戰勝利的前夕,黎明前的黑暗中的鬥爭特別複雜艱苦,中國正處在兩種命運的決戰關口。經過抗戰以來幾年的全民動員,各種文化宣傳工作的努力,使得五四精神和魯迅思想廣為傳播,在激越的愛國救亡的樂曲中,民主與科學的五四旋律顯得更加突出,救亡與啟蒙、民族解放與個性解放已經成為統一的時代最強音。到了後來,在思想激進的青年中,五四、魯迅、愛國、進步、左傾、馬克思主義等等,幾乎成了近義詞。這並不奇怪,馬克思主義與五四精神原本就是相通的,一致的,都是從人出發,為了人的解放而反對一切形式的專制獨裁與愚昧迷信的。
舒蕪的《論主觀》所反映的,正是進步知識份子和青年所代表的這種時代精神,那種獨立、自由、反抗、創造的要求。這篇文章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鮮明的革命傾向;二是獨立的批判精神。前者表現在作者的左傾立場和所宣傳的馬列主義觀點上。在文章裡,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領導以及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景等等全涉及到了,而且還一再引述馬、列、斯的觀點作為論據;雖然用的是卡爾、伊裡奇、約瑟夫,但明眼人都知道說的是誰。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戰時重慶,能說到這個地步,夠激進也夠大膽了。
至於文章的獨立批判精神,則主要體現在後面對「機械—教條主義」的批判上。在前面幾節的歷史考察中,已經對國民黨現政權進行了批判,等於宣告了它的必然滅亡的命運。後面對「機械—教條主義」的批判,則是直指共產黨領導下的左翼文化界,實際上已經觸及到了延安的主流意識。這種左右開弓的架勢,頗有點當年魯迅先生「橫站著作戰」的遺風。他所概括的那種教條主義特徵,我們太熟悉了,「一方面是對若干最基本的原則的死死株守,另一方面是對一切新探討新追求的竭力遏抑。他們就依賴著教條來鞏固自己的存在,當然最大的工作也就是鞏固那些教條本身。在他們看來,每一個新事象的發生,都只為了又一次證明那些教條的正確,──其實是又一次證明他們自己的存在的鞏固。所以,就把幾個基本原則看成絕對第一義的東西,而客觀新事象反被看作填充原則的『例證』,似乎新事象本身沒有任何意義,只有被填進理論原則時才有意義。」──這一切,五六十年代以來,我們不是都一再領教過了嗎?對於這種大有來頭而又經久不衰的東西,在它剛剛形成的時候就能夠及時發現並且公開提出批評,這種膽識這種精神,應該說是很可貴的,何況那時舒蕪還是個二十幾歲的小青年。
當年批判他的人可不這麼看。他們既不承認《論主觀》一文的總的革命傾向,也不正面接觸教條主義問題,而是緊緊抓住文章在表述方面所暴露出來的破綻:因追求體系的龐大完整而造成的概念和邏輯上的混亂。這一點確實是抓准了,《論主觀》的確有這方面的毛病──為了充分論證主觀的作用,作者把人的歷史、社會發展史、革命史、認識史全部拉了進來,而且把「主觀」與「主體」兩個概念互用,把歷史的主體、實踐的主體、認識的主體等等也混在一起了。真的是辮子一大把,很容易被抓住。從這裡,《論主觀》一文就被判定為「披著馬列主義外衣宣揚主觀唯心主義」。
這實在是冤枉。當年舒蕪寫這篇長論文,並不是在一般地談論哲學問題,而是有感而發,有為而作的。面對當時大後方知識份子中出現的精神危機,特別是那種虛浮的教條主義和庸俗的市儈主義以及它們在文藝上的表現,他認為問題的根源並不在理性或感性的多少,而在於是否能扎扎實實生活──「最根本的,是真正健全的開闊的積極發揚主觀作用的現實生活」,也就是「把主觀作用培育得日趨健全,把健全的主觀作用積極發揚起來。」很顯然,他這裡所說的「主觀」,也就是指人的自我、個性,所謂培育、發揚主觀作用,就是個性解放。於是,這就構成了《論主觀》一文的又一大罪狀:鼓吹資產階級的個性解放、個人主義。
更重要的是,當年的批判者所注意的不僅僅是舒蕪個人的思想見解,他們把《論主觀》的寫作和發表與胡風及整個《希望》雜誌相聯繫,認為這是一種思潮,一種思想傾向,一種政治動向,用後來的話說就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這種估計雖然過於嚴重,卻也不是毫無根據,因為胡風和舒蕪確實是胸懷大志、有意為之的。他們不滿於當時大後方知識界的虛浮庸俗狀況,意圖發起、推動一個思想運動,一個以發揚五四精神、堅持魯迅方向為目標的思想啟蒙運動。舒蕪在文章裡說得很明白,他的「這個研究,不是書齋裡的清談,而是我們當前生死存亡的關鍵」。胡風在《編後記》裡也明確指出:「《論主觀》是再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使中華民族求新生的鬥爭會受到影響的問題。」提得這麼高這麼重要,所以被看做是一種思潮、傾向、動向,並不為過。
聯繫《論主觀》和整個《希望》雜誌的反封建主導傾向,這裡「再提出」的問題顯然是指五四時期提出的「個性解放」。說「再」提出,表示過去已經提出、後來被忽略了掩蓋了,所以今天要再次提出。胡風自己也承認,他那篇發表在同一期《希望》雜誌上的《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裡面》,好像是和舒蕪的文章相呼應似的。胡風這篇文章的題目和主旨都是為民主而鬥爭,文中明確提出,「沒有人民的自由解放,沒有人民的力量的勃起和成長,就不可能摧毀法西斯的力量,不可能爭取到民族的自由解放。」後來胡風解釋說,「再提出」云云,是回應延安整風的,那就說明他確實把那次整風當成了像「五四」一樣的思想解放運動了。
當時的實際情形正是這樣:在舒蕪,是他力圖用最新最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方法闡發五四精神和魯迅思想的開始;在胡風,則是他再一次重申他的一貫思想和一貫主張。早在1938年,他就明確指出過:「中國的民族戰爭不能夠只是用武器把『鬼子』趕出去了事,而是需要一面抵抗頑敵,一面改造自己。必須通過這個改造,才能取得最後勝利。」他的創辦《希望》,發表《論主觀》、寫作《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裡面》等等,全都是為了推動這種旨在「改造自己」的民主思想啟蒙運動。
這場由《論主觀》一文所引發的論爭,後來的文學史家稱之為「對反動的『主觀論』的鬥爭」或「與錯誤的『主觀論』的鬥爭」。無論怎麼說,「反動」也好,「錯誤」也好,事實上這場論爭或鬥爭開始不久就被沖淡了──勝利、和談、內戰接踵而來,巨大的政治風暴席捲全國,人們已經不大關心這種高懸在空中的思想文化理論問題。待到歷史進入了新的房間以後,這場論爭才又繼續下去,不過那以後雙方的地位和心態已經大大不同了,論爭的方式也不同了。
更重要的是,論爭的雙方從開始到後來,一直都處在錯位的狀態:舒蕪和胡風所關心所探求的是藝術創造和思想啟蒙,是人的覺醒、人的現代化問題;而他們的批判者所執行的卻是政治批判和階級鬥爭的任務,是要在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領域佔領陣地和奪取領導權。在舒蕪和胡風看來,藝術創造和思想啟蒙的主體和動力,當然主要是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革命知識份子。可是,在他們的批判者的心目中,這一切──包括以往的所有思想文化及其載體知識份子,全都是革命的對象,也就是批判、鬥爭、改造、利用的對象。對於這種錯位,當時胡風已經有了感覺,他在給舒蕪的信裡談到胡喬木的批評時說:「本來可走的路很多,我們也從未希望得到批准,無奈他們總要審定,因而從此多事。」──他沒有想到,後來竟然無路可走,而這「多事」竟變成了無數的災難。正是魯迅先生早就指出的這種「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這種知識份子與政治家之間的「隔膜」,造成了那麼多曲折反覆,那麼多悲劇和苦難。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