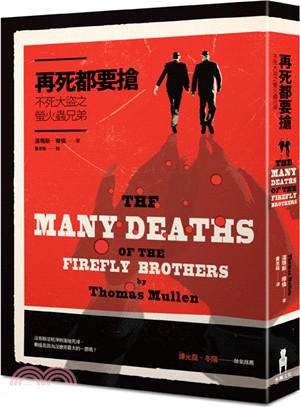再死都要搶:不死大盜之螢火蟲兄弟
商品資訊
系列名:木馬文學
ISBN13:9789865829704
替代書名:THE MANY DEATHS OF THE FIREFLY BROTHERS
出版社:木馬文化
作者:湯瑪斯.穆倫
出版日:2013/11/28
裝訂/頁數:平裝/416頁
規格:21cm*14.8cm*3cm (高/寬/厚)
版次:2
商品簡介
裁判,可以讓人開槍打了又打、打了又打,還死不透嗎?
譚光磊。冬陽。——帥氣推薦
第一次,傑森與惠特全身光溜溜地跟死條子一起躺在警局的停屍間,洗乾淨的七萬塊贓款被沒收,還不記得自己是怎麼死的。
第二次,「天啊,本來以為面對第二次會簡單一點,但是……」惠特受不了地說。
第三次……傑森有種直覺:從死亡裡復生這種事,絕對是有限度的。
這晚,兩兄弟第一次翹了辮子。
傑森和惠特在冷颼颼的停屍間醒來,身上只蓋著一條被單,胸前滿是彈孔,外加從胸膛直達腹部的縫線。
兩人不記得發生什麼事,只知道銀行搶匪不該光溜溜地躺在警察局裡——警局裡頭幾乎空無一人,大夥都在外頭慶祝什麼——直到兩人逃脫、看了第二天的報紙,才知道原來是宣布緝拿/擊斃兩人歸案的盛大記者會。
在此之前,傅傑森和傅惠特是遠近馳名的銀行搶匪,他們劫富濟貧的形象深植人心——然而事實上,兄弟倆只想幹完最後一大票,從此帶著心愛的女人退隱江湖……
裁判,可以讓人開槍打了又打、打了又打,還死不透嗎?
帶著生前(?)未完成的心願,傑森與惠特又規劃了一場銀行搶案。被打死。醒來。又規劃一場。惠特忍不住想,他們兄弟倆究竟食不是被惡魔附身了?
作者簡介
湯瑪斯‧穆倫(Thomas Mullen)
身為一位小說家,湯瑪斯‧穆倫在部落格上形容自己:「家住離亞特蘭大市中心不遠處,過著一個看似平靜的生活。然而在附近鄰居絲毫沒有懷疑的情況下,他謀殺、瘋狂編造令人費解的陰謀理論;時間旅行、重塑過去、令死人復活、與他自己創造的女人戀愛、威脅幼童、釋放瘟疫、發動戰爭、拯救生命、虛晃一招,或發明新的隱喻。」
他的第一本小說《末日小鎮》(繁體中文由木馬出版),被《今日美國》評為2006年最佳處女長篇小說,並受到大專院校「一書計畫」(One Book programs)學生的廣大歡迎。作者自嘲:「這部小說的電影版權由夢工廠取得,但在企業大變動之後,他們忘了拍電影,是讓人覺得有點可惜的地方。」
他的第二部小說《再死都要搶》,講的是經濟大蕭條時期一對搶銀行的兄弟;它被《紐約時報》書評形容成「魔幻黑魅主義」。作者也說:「將經濟大蕭條時代與我們當前極相似的經濟恐怖並列是無心插柳,因為在寫它的時候,作家本人正興高采烈地騎在房地產泡沫上。」
最新的小說《修正主義》,則是多份報章媒體「年度最佳科幻小說」的口袋名單。
穆倫喜歡在美麗、陽光明媚的日子寫作,因此非常高興住在南方。有兩個可愛的兒子和一個了不起的妻子。
譯者簡介
黃思瑜
台大外文系畢業,英國巴斯口筆譯研究所碩士。曾任國際非營利組織總部秘書、自由譯者,現為美商公司專職口譯。譯有《未來一百年大預測》等書。
名人/編輯推薦
【Amazon.com,2010年1月選書】……一個關於不斷變化的正義、真理,以及刺激又挑釁的故事。
【紐約時報書評】……美妙地說明了1930年代的美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黑暗英雄,以及它與我們現在正經歷的經濟衰退有多相似。
【今日美國】(作者)明白非法的浪漫情懷,他召喚出相當機敏的魔幻現實主義,啟動了兩個拒絕死亡的全民公敵這場歡樂的追趕跑跳碰。
【書單】穆倫用了出人意料的超現實主義來包裝這個大蕭條時期的黑幫故事,提升它的層次……穆倫應得到讚揚,因為他在冒險在這類型揉合的犯罪驚悚中加入了文學性。
【多倫多星報】非常厲害的創作……令惡名昭彰的罪犯成為不死之身的大眾神話,充滿了奇幻的隱喻……令人無法喘息、無法停手……高明地在歷史小說與誇張幻想故事之取得平衡。
【出版人週刊書評】……穆倫令大蕭條的絕望感躍然紙上。讀者將看得目不轉睛。
【Mountain Express】高潮迭起、迷人……引人矚目的小說……這個令人上癮、完美無瑕的故事,值得強烈推薦!
書摘/試閱
他很習慣姿勢怪異地醒在各種各樣的環境裡:地板、少了襯墊的爛沙發架、乾草棚裡滿是刺的蕁麻堆、路邊汽車的方向盤;能動的跟不動的,傅傑森都照睡不誤。他可以在公車、四輪馬車、火車貨車廂內打盹,管他站著、坐著,還是睡到摔倒。
但這次情況不一樣。
一開始他不知道自己躺在什麼東西上,只感覺冷颼颼的,皮膚貼著金屬,身上一絲不掛,胸口以下蓋著一張薄床單。
傅傑森撞車的經驗多到不能再多,車禍翌日早晨醒來的皮肉痛也不是新鮮事,但這次更嚴重。
他深吸了口氣。他也很能接受在清醒時聞到各種氣味,比方樓下穀倉牲畜的騷味,房間裡一群沒洗澡罪犯的臭汗味,妲希偶爾搞砸早餐的燒焦味。但這是一股陌生而刺鼻的藥水味,徒勞無功地想要掩飾如體味、尿騷味及血腥味等人類存在的跡象。房間亮晃晃的,黃疸色的光芒來自天花板上的兩盞燈及兩旁的檯燈。他看看左邊,見到一張金屬窄桌,上頭擺著冷酷的醫療器材,有些用紗布或布包著,全浸在一灘乾涸的血水裡。所以,這是間病房嘛。他從沒有在病房裡醒來過,記上一筆好了。這裡不是尋常醫院,傑森掃視一番,清點了一下醫生遺留下的各樣東西,跟嚇人工具一道擺在桌上的,還有一台相機與外接的長閃光燈、一包抽完的煙跟滿出來的煙灰缸。
每隔幾秒,房裡的某盞燈就會閃爍一下。天花板上方傳來沉重的腳步聲,沿著他看不見的通道走動。他感覺得到喉頭後方殘餘的血腥,同時乾澀得難以吞嚥。
瓷磚地板骯髒,一道道劃過病房的泥痕,就像是他的醫生也兼差當養豬戶似的。高度及腰的櫃檯沿著四面牆包圍房間,角落還有一台搖搖欲墜的收音機,播音員正流暢而嚴肅地報導就業促進署的新方案。最讓人怵目驚心的是門後鉤子上掛著的一頂警帽、三堵牆上警察面無表情的裱框照片,以及他床後那面牆上、像一尊對他眥目相向的肥胖神像——他猜測那是局長。有這種下巴的傢伙,必定這一類人物。
他也發現自己左手指尖沾了黑色墨水。那五個汙點,是罪惡感、恥辱跟霉運當頭的貼切寫照。
在房間遙遠的另一頭,有個和他一樣一絲不掛、半蓋著床單的男人,躺在緊貼著牆壁的窄床上,好像希望離傅傑森越遠越好。
傑森這才發現,那其實不是一張床。
他用手撐起上半身時,床單滑落腰際,胸膛上可怖的傷痕讓他瞪大了眼睛。傷口像是用骯髒手術刀割過的瘡疤、感染了細菌,在他的肉裡長出又黑又乾的硬皮。兩個傷痕就位在他的胸膛上半部、鎖骨的正下方,還有一個在左下方,離他的左乳只有幾吋。腹腔上面則有三個傷口。傑森一向以自己的身材自豪,有那麼一下子——就那麼短短的幾秒鐘——他的思緒被深深的失落攫住:這些傷口破壞了他比例良好的胸肌跟平坦的小腹。他不是沒被槍打過,幾個月前左上臂才捱過子彈,因此儘管理智告訴他不可能,但憑藉經驗,傑森知道這些傷痕是什麼東西造成的。
一陣驚慌中他掀開被單,任它像被驅逐的鬼魂一樣掉落磁磚地板。傑森想摸摸傷口但又不敢。
「真是乖乖不得了。」
他坐了好一會兒,才勉強自己轉動脖子,再度環視房間。之前還很模糊的東西,現在都看清楚了;他右邊有第三張解剖檯,之前因為隔了一張桌子所以沒看清楚。他認得躺在解剖檯上的那張側臉——怎麼可能認不出來?唯一的差別就在於,傑森從沒看過弟弟這麼平靜的表情。
傑森站起身,腳底磁磚傳來一陣冰涼。他眼睛張得大大地瞪著惠特,接著伸出手,猶疑不決了一陣才碰了碰弟弟滿是鬍渣的左頰。觸感冰涼,但是在這種時候什麼東西摸起來都是冰的。傑森一把抓住蓋至弟弟脖子的床單,等了一會兒才慢慢往下拉。像是命中標靶的靶心一樣,惠特的胸膛中間有個貨真價實的彈孔。
看到這一幕,傑森不禁緩緩吐氣。沒錯,雖然他身體裡面鐵定有一堆子彈,像個小豬存錢筒一樣搖起來會噹噹作響,但最少他還有呼吸。悲痛欲絕的傑森彎下腰,無意間右手擱在弟弟的上臂,忽然感到弟弟的手臂肌肉緊張一縮、頭接著轉向傑森。只見惠特下顎一緊,眉頭一皺,眼睛倏然睜開。
「你沒穿衣服。」惠特說。
「這完全不是重點吧!」兩個人的聲音都又粗又啞。
惠特坐起身,眼睛仍盯著傑森坑坑疤疤的胸膛不放,最後才回視自己,身子立刻往後一震,好像又被射中一槍,差點就從解剖檯上跌下來。
「搞什麼——?」
「我不知道。」
兩個人盯著彼此好長一陣,都在等對方開口解釋狀況或是拆穿這場惡作劇。
傑森嚥了嚥口水。會痛。他開口說道:「為了有個頭緒,我只問這一句:你以前遇過這種事嗎?」
「做噩夢也沒這麼慘。」
「我以為你根本記不住做過什麼夢。」
「喂,像這種事情你想我怎麼會忘記!」
「噓!行行好,我們在警察局裡。」
惠特跳下解剖檯。「你還記得什麼嗎?」
「不記得。」傑森倒轉腦海裡的記憶地圖,瘋狂搜尋每個轉角跟崎嶇的小路。「我記得去了底特律,記得開車載著錢去跟歐尼碰頭——就這樣。我甚至不記得我們有沒有抵達餐廳。」
「我也是。記憶全都一片模糊。」
傑森突然有股強烈的感覺,想回頭看看自己的那張解剖檯。說不定他其實是個遊魂,離開了自己的軀殼。但他知道不是。
惠特又再度環視房間,似乎想找出完美的合理解答。說不定胸膛上的並不是彈孔而是其他東西。
「我們怎麼可能——」惠特試著開口。「我們怎麼都這樣了還能活命?」
「我不知道。目前為止,我們撿回一條命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這次為什麼不——」
惠特指著自己的胸口。「看清楚,傑森!」
「噓!小聲一點,別嚷嚷。還有,心領了,我已經看夠了。」
惠特轉過身去。「子彈穿出的傷口在哪裡?你覺得子彈有沒有可能偏了,沒有打中重要器官?」
傑森連看都不看就揮手否定。「我的這些傷口,你又怎麼解釋?」
惠特轉回來迅速檢查了一下哥哥的胸口。「我不知道,說不定子彈——」然後他突然盯住傑森的臉。「你的臉白得跟紙一樣。」
傑森輕拍自己的臉頰。「我們離開這裡以後,氣色就會變好的。來吧,我們找法子出去。」
惠特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接著閉上眼睛,過了一陣子才張開。「我不覺得我死了。」
「謝謝,你不說我還真沒發現。」
「不是,我是說,我還在呼吸。你在呼吸嗎?你感覺怎樣?」
「我覺得渾身僵硬,可是——沒什麼不一樣。」實際上,傑森覺得隨著身體活動,痠痛的感覺就跟著越來越少,好像他的筋骨只需要放鬆活動一下。「不可思議耶,感覺正常。你呢?」
惠特點點頭。「可是如果說我們大難不死,在這邊躺了幾個小時,或是幾天才好起來,我們不是應該——要有點不舒服嗎?」
「我不知道,說不定他們給我們注射了什麼亂七八糟的藥物。還是他們用了某種新型子彈。天知道啊?聽好,警察局不是討論這種事情的地方。我們沒時間了。」
傑森關掉收音機,仔細看了掛在牆上的警帽。上面的字告訴他,現在他們是在印第安納州的北點市。他告訴惠特。
「北點市是什麼鬼地方?」
「離瓦爾帕拉索不遠。」傑森回答。他們原本在底特律把現金脫手,打算接著前往瓦爾帕拉索郊外的汽車旅館載小妞們離開。所以,現金已經成功脫手,他們是在接小妞們前才出事的嗎?
傑森比了比房間另一端的第三張解剖檯。「來吧,看看我們的共犯是誰。說不定他有答案。」
傑森走向屍體,惠特則是把床單圍上腰際後才跟過去。
躺在第三張檯子上的男人蓋著被單,也一樣光溜溜兼體無完膚。這個男人身材高大,但以前顯然生氣勃勃的身體如今卻萎靡不振;射中他頸子左邊的那一槍不只留下一個大傷口,還撕裂了鬆垮垮的皮膚,讓他皮開肉綻。歪掉的鼻梁則清楚顯現,他在挨這槍之前已經先受到猛烈的一擊。
「我不認識他。」惠特說。「你呢?」
傑森搖搖頭。這傢伙的臉型,加上醫生或法醫特別將他與兄弟二人分開這點,使傑森確定他生前是個警察。
「嘿,老兄。」傑森喊道,音量提高了一點。「醒著嗎?」他在男人的臉前彈指,但毫無動靜。惠特跟著拍了拍那人的臉頰。
「放尊重點。」傑森說,等了一下,但是拍他的臉頰顯然得不到反應。傑森於是把大姆指放在那人的右眼與右眉毛之間,壓住眼眶,再掀起眼皮檢查下方動也不動的褐色眼珠。看來這傢伙已經死透、隨人擺布了。
「看樣子我們身上的鬼東西不會傳染。」傑森說完,拍拍屍體冷冰冰的胸膛。「好吧。兄弟,安息吧。」
這間房只有一扇又小又高的窗子。暮色逐漸散去,窗邊的時鐘顯示現在是八點一刻。今天星期幾啊?傑森隱約覺得記憶已經空白了整整一天。至少一天。
「見鬼了,到底是怎麼回事?」惠特問道。
「晚點再傷腦筋。先逃得遠遠的再說。」
死者的腳後就是一扇木門,門上的兩個掛勾不只掛了一頂警帽,還有一件醫師白袍,傑森一把扯下。白袍勉強可以蔽體,但是衣料很薄,幾乎是透明的。
傑森一個個拉開左邊牆上櫃子的抽屜,希望可以找到派得上用場的東西。有醫生在附近總是讓他渾身不自在,更何況待在滿是泥土碎石的診間裡。傑森覺得自己好像是古老默片裡面的呆瓜,一步步深入妖怪的巢穴,卻沒有發現背後的陰影越來越大。傑森翻出一捲透氣膠帶跟幾塊紗布時,惠特一臉困惑。
「我也不知道,說不定待會兒用得上。」
傑森繼續翻動桌子上那堆鑷子、鉗子跟剪刀,取了兩把最長的手術刀,遞了一把給弟弟。
「爬窗嗎?」惠特問。
「你想光著屁股晃來晃去隨你便,但我想先穿上衣服。」
活躍時期的傑森有過好幾次硬闖突圍的經驗,包括是警察局、槍械室、被聯邦政府監視的親友住宅、郡監獄,甚至包括他媽的行駛中的火車。有幾次他都是赤手空拳,但是從來沒有一絲不掛過。這讓傑森覺得自己沒衣服穿是不公平的劣勢。這些條子已經打破了基本江湖道義。
木門對面還有一扇門。兩兄弟各將耳朵貼在牆上,最後決定死條子旁邊的那扇最保險——另外一扇門後隱約傳來活動的聲響。
傑森緩緩轉動門把,回頭注視只有一步之遙的弟弟,朝他點了點頭。接著他用全身的重量抵住門,右手緊握那把沾有自己乾涸血漬的解剖刀。
門外是一道狹窄的走廊,地板鋪著白色磁磚,白灰牆壁沒有上漆。前方又有一道門,穿過後是置物櫃間,可移動的木頭板凳沿牆擺放,空氣中飄著肥皂及汗臭味兒;左側牆邊有個入口,裡面有幾個隔間,大概是淋浴間。到處都靜悄悄的。
傑森悄悄打開幾個沒上鎖的置物櫃,但是一無所獲。惠特也一樣從另一邊開始搜索,兩人最後在中間相會。
雖然傑森的心跳快速(要嘛是他的心臟仍在跳動,要嘛就是他還可以感覺得到消失在他胸膛裡的脈動回聲,類似幻肢疼痛那樣),他還是渾身冰冷,貼著腳底板的磁磚讓他身體打顫。傑森退回房間中央,發現兩個置物櫃中間懸著一面鏡子,可以照出他全身。他照舊一看鏡子就分神。他盯著單薄袍子掩不住的深色彈孔,然後才發現自己的頭髮有些不對勁。他用手指梳了梳,但頭髮還是垂在額前,像被狗啃過一樣。
「天啊,他們剪了我的頭髮。」
大家都說螢火蟲兄弟長得很像,但是傑森一點也不覺得。惠特的臉比較窄,下巴輪廓較為鮮明,這點遺傳自兩人的母親,有稜有角的愛爾蘭反骨不僅呈現在骨架上,惠特一開口總是有新的怨言這點更是明證。惠特也比較開朗,有著一對濃眉,還有鬍渣——就算他才剛刮過鬍子,連刮鬍刀都還沒洗,鬍渣就已經又從臉頰上冒出來了。傅家三兄弟裡,他也是唯一一個能以藍眼睛自豪的,傑森永遠都忌妒他這點;因為惠特的臉現在血色全無,這對眼睛似乎比記憶中的更藍了。
馬桶的沖水聲轉移了兩人的注意力。心有靈犀,兩兄弟立刻背靠入口兩側的牆面。惠特才剛解開床單的結好讓雙手可以自由活動,一個穿制服的條子就走了進來,手忙著調整帽子,眼睛則盯著自己閃亮的褐色靴子。惠特溜到他身後,左臂穿過條子左脅、橫過脖子壓住喉嚨,右手上的手術刀離那警察的眼睛只有幾吋。傑森走到警察前面,亮了亮手裡的刀子,白袍隨著身體走動翻擺,活像要拿倒楣鬼開刀的變態醫學生。
「警察大人,」傑森像跟條子寒暄地說:「我們要報案,有偷褲賊。你幫我們調查的時候,我們想要借幾件衣服來穿穿。」
條子的眼睛已經因為出其不意的偷襲而睜得老大,再看到傑森站在面前時又瞪得更大了,不僅下巴差點掉了下來,一張臉更是嚇得全無血色。
「喔噢,」傑森對惠特說道。「最好讓他靠著這面牆。快。」
惠特聞言照做,警察腳一軟就癱跪在地上,眼睛圓睜。如果你以為他的眼睛已經張得夠大,那可大錯特錯。只見這條子喉頭一嘔就吐了起來,兩兄弟立刻退開。
「惠特,說真的,」傑森打量這亂糟糟的一幕,「他體型跟你比較接近,你可以穿他的衣服。」
惠特往前一站,抓住警察的領子把他推到寄物櫃上。
這個警察身材瘦削,體型的確跟惠特相差不遠,只是矮了幾吋。傑森解下警察的配槍(柯爾特點三八左輪手槍),檢查了一下。槍裡有子彈。要是他有口袋就可以把槍收起來了。
那警察張開眼睛,一直盯著地板。
「怎麼——?怎麼會——」
惠特在警察面前晃了晃手術刀,差那麼一點就割了他礙事的鬍子。「幫我們拿幾件衣服來。」
警察輕手輕腳,領著兩兄弟找到他的置物櫃,一路上眼睛都只盯著地板,手指抖個不停,試了兩次才終於打開櫃子。櫃子裡有一條褲子、一件白棉衫跟一雙鞋,惠特一看就知道鞋子對他來說太大了。
傑森從警察褲子口袋裡拿走錢包,迅速瞥了一眼,抽出裡頭的一張五元鈔票跟兩張一元紙幣。「就當作我們的調查經費好了。」
突然,像是被重重打了一拳,傑森想起他們開著車去跟歐尼見面時身上帶了多少現金。老天爺,傑森想著,那筆錢可能還在這棟大樓裡,但周遭都是虎視眈眈的條子,而不是每個人看到螢火蟲兄弟就會嚇昏過去。
「警察先生,請坐。」惠特邊說邊把警察轉過來,讓他背靠著置物櫃。那男人緩緩滑坐下去。惠特更衣的時候,傑森拿著左輪手槍瞄準警察的胸口,另一隻手握著解剖刀,七美元的紙鈔繞著刀柄。
「看著我。」傑森命令道,那警察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照做。「哪個置物櫃主人的體型跟我最像,給我指出來,要快。」
警察說了一個號碼,傑森先確定槍膛裡沒有子彈後,才用槍托去敲鎖。
「太大聲了。」惠特指責道。此時他就站在警察前方,手裡拿著解剖刀以防不備。
沒多久傑森就穿好衣服,卻仍打赤腳,因為置物櫃裡沒有鞋子。撬開另外一個置物櫃的風險太高,所以他只得將就沒鞋穿。
「把你的鑰匙給我。」惠特命令警察。警察從口袋裡拿出鑰匙,乖乖交了出去。「你的車是哪一輛?」
「綠色的龐帝克,停在外面後頭。車牌號碼六三九五七八。」
惠特問了槍械室在哪裡,雖然警察也說了,傑森還是搖搖頭;太冒險了。他們必須將就那把柯爾特左輪手槍。
「這裡為什麼這麼安靜?」惠特問道。
「大家都在外面接受記者採訪。宣布你們落網的消息。」
「警察先生,你也參與了這次突擊行動嗎?」傑森問。
「沒有,沒有,我不在,去了岳父岳母家。」警察越講聲音越慌張。「我今天下午進來的時候才聽到消息。不過我是怎樣也不可能參與的——我覺得你們的事蹟真的是大快——」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傑森截斷他的話。
警察的眼神慢慢飄向傑森。「你們中槍了。」
「還要你說嗎?怎麼會?什麼時候?」
「是誰幹的?」惠特補上一句。
「你們把我們的錢拿去哪兒了?」
「你們中槍了。」那條子又說了一次,聲音空洞。「你們躺在那裡,我碰了你們一下,冷冰冰的。醫生說,醫生說你們死了。」
「可是他們怎麼會弄錯?」惠特質疑警察。「他們到底對我們做了什麼好事?」
「還有他們把錢放在哪裡?」
「你們兩個都冷透了。」一道汗水從警察頰上滑下。「也硬透了,局長還假裝要跟惠特握手,可是他的手沒辦法彎。」
惠特彎了彎左手手指,然後握拳,青筋浮出。
警察呻吟了一聲,垂下頭。
「噢,老天啊,又來了。」傑森抱怨,但警察只是倒了下來,四肢像斷線的木偶般攤開。傑森放下手術刀,彎腰用手撐著警察昏迷的頭,將他輕輕放到地上。
兩兄弟穿著偷來的衣服,肩並肩站著。此時應該有人開口說話,但沒人知道該說什麼。
頭頂上傳來的腳步聲讓兩人一驚,建築另一頭原本很微弱的嗡嗡聲,此時也突然大了起來。是笑聲,也有掌聲,前頭那些人正樂著呢,而且是很多人,多到讓傑森心痛。得留下那筆錢了,你帶不走的,傑森心想。
傑森將手槍上膛後,才踏入空蕩蕩的走廊檢視兩側是否安全。惠特跟在他後頭,一起朝出口走去。傑森提起門閂,對弟弟點點頭再用力一推,但是門沒有他想的那麼沉重,一推就撞上了磚牆。警局側面延伸了有二十碼遠,眼前的停車場上擠了十多輛車,更前方店鋪的紅磚牆有三層樓高,窗戶旁的防火逃生梯排列得對稱又整齊。但每扇窗戶後面都一片漆黑,一如頭頂上不見星子的夜空。
人骨般的樹枝綜橫交錯,明明是仲夏,樹卻枯死了。一旁葉繁枝茂的榆樹迎著微風搖曳,然而這棵樹卻文風不動,絕望又無助。
兩兄弟搜尋了一會兒車牌,終於找到了。傑森把左輪手槍遞給惠特,然後打開駕駛座車門。
他發動汽車,開出停車場,車燈照出凹凸不平的路面。從這裡他們看得見警局的側邊,而警局前顯然聚集了不少人。兩側的街道跟主街上停了滿坑滿谷的車子,就算隔著那些車子的車窗,傑森還是看得到攝影記者此起彼落的閃光燈。警局前擠滿了人,穿深色衣服的、戴著帽子的,每個人影都隨著笑聲及致詞聲晃動。
「裡面的人——」惠特出聲,但話不成句。他又試了一次。「裡面的人——」
「算了,恭喜他們。這些可憐蟲至少還可以沾沾自喜幾個鐘頭。」
傑森左轉,把警局拋在車後,沒多久就開上了鎮上的主街。
「認得出是哪裡嗎?」他問弟弟。
「不行。」
傑森手指輕敲方向盤。沒人帶路的風險極大,不是老手的作風。主街黑鴉鴉的,電影院入口的遮棚熄了燈,看不見店家玻璃窗後的東西,只是折射龐帝克的頭燈。傑森想起自己來過北點市一次,大概是路過吃個午餐或加個油之類的,但是他去過那麼多州,看過那麼多主街,搞混是常有的事。
車子繼續穩定以時速二十五哩前進。好一陣子後,道路兩旁擁擠的建築物終於換成熄燈住宅寬敞的前院,傑森才催起油門。
「你餓不餓?」傑森問道。
「不餓。」
「渴不渴?」
「不渴。」
「我也是。老天,好怪啊。」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