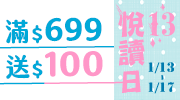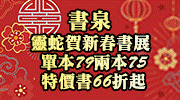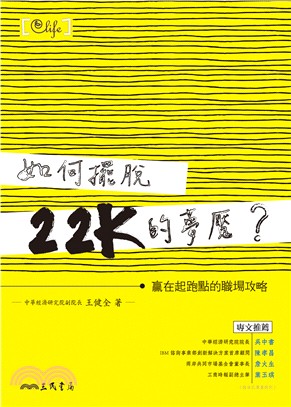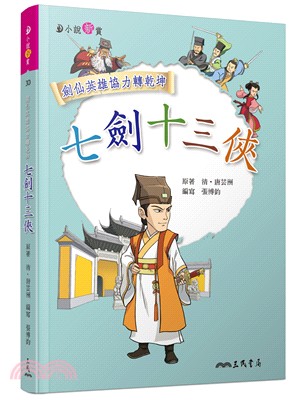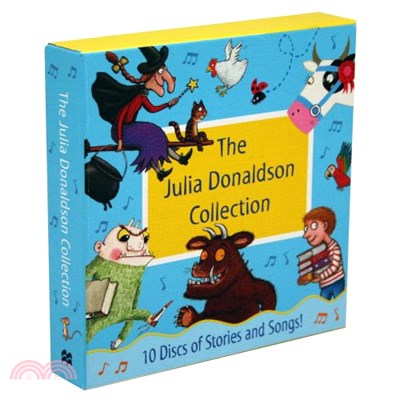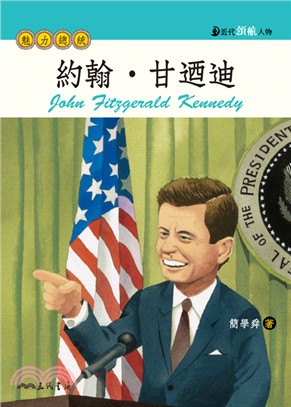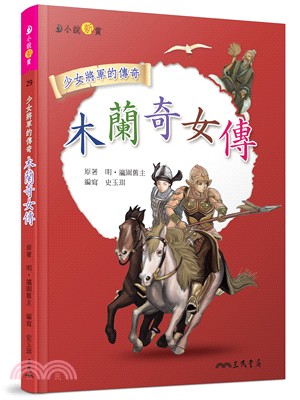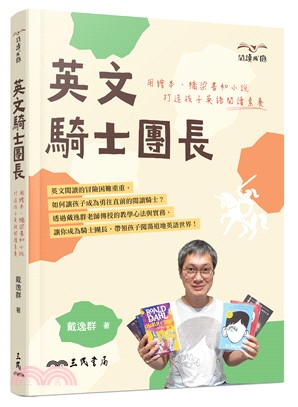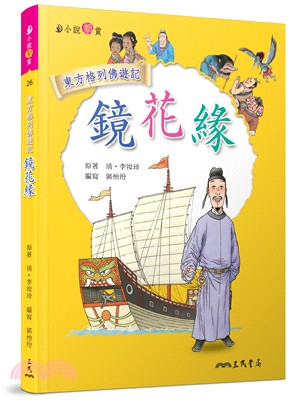彳亍:陳伯軒散文集
商品資訊
定價
:NT$ 290 元優惠價
:90 折 261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7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彳亍》結集了作者過去十年發表於各處的散文佳篇。
「十年荏苒,畢竟也不短。常常不斷自問的是,我懂事了嗎?總覺得,我越來越懂的是人情世故,無論出自於滿腔無奈或冷眼旁觀,透視的眼光似乎都能夠成為下一篇書寫的題材。然而,如果好的文章必須來自於人世的掙扎,究竟是值得慶幸的事情嗎?」
本書會帶你重溫過去的感動瞬間。
本書以細膩的筆觸,
勾勒生活中稍縱即逝的、沉默的瞬間。
十年荏苒,那創作的初心,依舊熠熠光亮。
「十年荏苒,畢竟也不短。常常不斷自問的是,我懂事了嗎?總覺得,我越來越懂的是人情世故,無論出自於滿腔無奈或冷眼旁觀,透視的眼光似乎都能夠成為下一篇書寫的題材。然而,如果好的文章必須來自於人世的掙扎,究竟是值得慶幸的事情嗎?」
本書會帶你重溫過去的感動瞬間。
本書以細膩的筆觸,
勾勒生活中稍縱即逝的、沉默的瞬間。
十年荏苒,那創作的初心,依舊熠熠光亮。
作者簡介
朋友總說是愛夢想的孩子,不小心長成了善感的性情。在淘氣絮聒與沉默冷峻之間,我攢蹙舒放每一種展現自我的可能。常常不斷挖掘情感的各種樣貌,試圖由不同的角度理解生活中的種種況味。是學生,也是老師。聽課,也講課。在黑暗中尋求光明,又將繽紛的世界看成最為深沉的負片。
你好,我是陳伯軒。移動,是我生命中一項重大的正向能量。所以,《彳亍》。
你好,我是陳伯軒。移動,是我生命中一項重大的正向能量。所以,《彳亍》。
目次
序 顫動與靈犀
輯一
起床歌
餓食表
阿強一號
黃惑
小共產主義
走過北門街
鬼說
見棺
曼普拉喜特
輯二
如流的閃爍
對窗
山巨人
過程
櫻月
走過死亡,與世界和解―導讀〈櫻月〉/宇文正
同名的故事
幽靈
記憶空白的地方
輯三
茶思
天竺鼠會不會飛/潘彥廷
武陵農場的約定
空號
錶骸
聲聲慢
遺忘
彳亍
輯四
同是去年人
浮塵
凝視
沉吟
翻頁
錯過
輯一
起床歌
餓食表
阿強一號
黃惑
小共產主義
走過北門街
鬼說
見棺
曼普拉喜特
輯二
如流的閃爍
對窗
山巨人
過程
櫻月
走過死亡,與世界和解―導讀〈櫻月〉/宇文正
同名的故事
幽靈
記憶空白的地方
輯三
茶思
天竺鼠會不會飛/潘彥廷
武陵農場的約定
空號
錶骸
聲聲慢
遺忘
彳亍
輯四
同是去年人
浮塵
凝視
沉吟
翻頁
錯過
書摘/試閱
櫻 月
那一年,我們悄悄掩埋了一個秘密。
我才國中,距離阿公倒下已經三年。當初,說是因為骨刺壓到神經,使得他往後的日子必須仰賴阿嬤和輪椅。剛開始阿公很用心地復健,家中的每個人都小心翼翼陪伴他,後來到臺大醫院住院觀察,準備進行連醫生都沒有把握的手術。偌大的房屋少了老人家顯得寂寞,偏偏多餘的空間並沒有造成一種寧靜舒緩的節奏,大哥成天在外打架鬧事,時常深夜不歸,爸爸總歸咎於媽媽疏於管教。一次又一次,媽媽在客廳靜靜地等,靜得沒有一點情緒,我請她先去睡,她只是搖頭。低氣壓使整個家無法呼吸,我戒慎恐懼地活著,深怕再多一口誰的喟嘆,會立刻引起強烈的風暴。
只是誰也不可能想到,釀成風暴的,竟是一陣急促的電話聲響。堂姐發生車禍,必須立刻進行手術,當時聯絡不到大伯,爸媽立刻趕過去,才出門五分鐘,電話又再一次響起,大哥放下電話之後,只說:「死了。」「死了?」至今仍然能夠感受當時不可置信的恐懼,兩層樓的房子,留下詭異的節奏。我輕抱著熟睡中的弟弟,用力緊閉眼睛:睡吧,睡吧,這只是一場太過真實的噩夢。夢不知道進行了多久,在暗黑的意識中聽見爸媽的惋惜:這麼年輕的一個孩子。
失序的生活使我忘了悲傷,只是在每次的祭奠中,聽著法師的喃喃,按照規矩重複一次又一次的祝禱。偶爾,也會很不誠懇地想著還沒算完的數學、回去要背英文單字,升學的壓力並不趁此悲憫我,總覺得好累好想睡……。死亡好冷,夜深的寒風迸發冥紙堆砌起的巨大火光,那是僅有的光明溫暖的意象。殯儀館大概是世界上最少笑聲的地方,而我卻不知道該怎麼哀悽,只能平平整整放好五官,不笑不語是我唯一的表情。
我的情緒異常地凹陷,思量著街坊鄰居對堂姊的讚美與追念,到底有什麼價值,只是為了加強一嘆可惜的語氣嗎?這些問題根本禁不住疑問。我變得更加尖銳,用冰冷的視野審視每個人的行為。當全家人準備驅車前往殯儀館,鄰居問我們要去哪,不等爸媽回答便搶著說:﹁要去拜你!﹂爸媽倒不甚介意我的無禮,反正所有失常的行為,在他們眼中都只是一時的叛逆。
是的,我是生而叛逆的,提早來到這個世界,被家族賦予莫大的罪孽。關於我早產的故事聽聞太多了,不管是怎樣的情節與邏輯,結論一定是我的存在耗盡了阿公阿嬤的錢。「你知道那些錢可以買多少房子嗎?」這個問號是所有長輩給我的考題,無法回答,我只能相信自己的命很值錢,在毫無能力決定任何事情的時候,已虧欠太多。於是我顯得乖巧,彷彿是一種贖罪的姿態,向所有的長輩宣示:「大家,對不起。」但是這樣的乖巧除了得到無關痛癢的讚美外,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與包容,甚至慢慢地失去存在感。我真是耗盡力氣想要爭取一點關心,管他是誰都好;可我知道,當我懂得把自己的一切打理得好好時,很有可能在長輩忙碌的生活中,成為最不起眼的那個。
我開始厭惡這個家,以及家裏的每個人,甚至上演了翹家的戲碼,每次被爸媽拎回家就展開冷戰。我只要學習大哥翹課打架,父母的注意力就不得不放在我身上了。無奈,我嚥不下氣又狠不下心。
只有堂姊安慰我。
那是在一個昏黃的午後,我和媽媽到臺大醫院探望爺爺,在那剛好遇到了堂姊。媽媽向阿公抱怨我一連串失去理智的行為,說到激動處,窗外的餘暉把雪白的牆壁燃燒起來,同時引爆我所有的不滿,胡亂說了些賭氣的話,把頭別過去,一語也不發。堂姊看我已經拒絕與媽媽溝通,就坐在我旁輕輕地說;要懂事、要體諒。我難掩激動的情緒告訴姊姊自己的委屈。她說她懂,只是大家都在忙的時候就要更懂得忍讓。
「你現在的功課好不好?」整個家,不會有人管好不好。
「我的數學不好,我覺得線性函數很難。」
堂姊答應要教我數學的那一年剛好畢業,回到了板橋,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房屋仲介公司上班,她的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份合約,預計在晚上簽訂,就是當晚我們接到電話,那份合約再也簽不了了。原來,當我紅著眼眶,在醫院和媽媽生氣,想著堂姊細細的安慰,望著烏黑的長髮,米白色的長裙使得醫院的色澤柔軟了些。那個緩緩離去的背影,款款的道別,竟是我這些年來任憑記憶如何模糊也無法忘記的,充滿光影的印象。
再次見到她,靜靜地躺著,只要不呼喚,那和睡著沒兩樣。但我總還是忍不住地偷偷問:姊姊,妳什麼時候醒來?
告別式當天,起了個大早,到了殯儀館的時候一切尚未就緒,坐在外面守候,看見爸爸從廳堂走了出來,泛紅的眼眶想必是目睹了堂姊的遺照。照片真美,彩色的半身照,照片中的她微微側著身子,對著鏡頭展現略帶羞澀的笑容。那種笑,彷彿可以從葬儀隊的冰冷喧鬧中滲透出來。那樣的生活照,比起在相館正襟危坐的大頭照美多了。我甚至在心中暗暗決定,一定要為自己預留一張滿意的照片。
儀式結束,靈柩要送往火化,我們向她深深鞠躬,到了此時,才出現一道清晰的聲音告訴自己:姊姊沒了。也是至此,才深刻明白這些日子以來的冷靜,其實不是不傷悲而是不死心。一直都以為是夢是夢,總認為事情不可能就這樣發生,這樣結束。其實只是自己一廂情願的妄想,就是不甘心。我就是存了這麼一點痴心,心中隱隱希冀死者復生,當時的我就是如此渴望著大夢乍醒。
該醒的人太多,但堂姊是不會醒的。我們帶她來到一個悠靜的寺廟,眾人合議替她挑選了一個位置,一尊尊的佛像都是一個個的故事,所有關於她的往日都要塵封深埋於選定的佛像中。把骨灰慢慢移到罈中,過程中,我緩緩蹲下執起意外掉落的,手卻抖得厲害,這是我姊,這就是我姊呀!一切都結束了,我們只能誠心祝禱,生死殊隔,願諸佛菩薩能夠渡化亡者。
往後我對她的想念像是失序的底片,只有在生活中不經意的片段,才會有突然的顯像。當我騎車時,特別害怕公車的輪胎,那一定很重很痛,聽大伯說,當初到醫院看到堂姊時,她的雙唇緊閉,法醫才發現她痛得把牙齒都咬碎了。又或者我看到她工作的房屋仲介公司、經過那家醫院……。每次看到滿樹的櫻花,就想到她柔軟溫淳的笑語,姊姊的名字就是「櫻月」,我們總喊她「櫻月姊姊櫻月姊姊」,就這樣喊著喊著,即使到了此時此刻,這樣的呼喊往往能夠成全我最深情的訴願。也是在無意間驚覺自己的行跡竟一步步陪在她的身旁,高中三年都在板橋,偶爾望向公車外熟悉的現場,我們用白幡和呼喊鋪一條回家的路,每一次經過都會激起思念的漩渦,不小心耽溺,同學就笑我太愁。
愁不是錯,錯在我將生之偶然視為當然,卻又以為死亡是生命的意外。
一個人的離去,是龐大的秘密,也是整個家族的遺憾,而遺憾產生之後,好像這個家就不再那麼完整,好像快樂也不再那麼乾脆。至今我們完全隱瞞阿公,只是擔心他羸弱的身軀禁不住這樣的打擊。這些年來他究竟知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呢?他會不會是假裝不知道呢?阿嬤每天都會誦經,久了也就成為生活的一部份。當時,她放棄見堂姊一面,不讓阿公知道也是她提出的意見。她嘴上不說,卻總是為家裏每個人祈願,我也明白在她的心中,永遠不忘記幫堂姊多添點福氣的。就這樣一點一滴,自己的心也越來越寬慰。
在大家逐漸淡忘的時候,我才真正鼓起勇氣,向過去索取記憶,企圖覓尋和堂姊的互動。記憶在夢中,跟著偷偷長大,我長成了櫻月姊姊的年紀,而姊姊卻永遠也不老。
那一年,我們悄悄掩埋了一個秘密。
我才國中,距離阿公倒下已經三年。當初,說是因為骨刺壓到神經,使得他往後的日子必須仰賴阿嬤和輪椅。剛開始阿公很用心地復健,家中的每個人都小心翼翼陪伴他,後來到臺大醫院住院觀察,準備進行連醫生都沒有把握的手術。偌大的房屋少了老人家顯得寂寞,偏偏多餘的空間並沒有造成一種寧靜舒緩的節奏,大哥成天在外打架鬧事,時常深夜不歸,爸爸總歸咎於媽媽疏於管教。一次又一次,媽媽在客廳靜靜地等,靜得沒有一點情緒,我請她先去睡,她只是搖頭。低氣壓使整個家無法呼吸,我戒慎恐懼地活著,深怕再多一口誰的喟嘆,會立刻引起強烈的風暴。
只是誰也不可能想到,釀成風暴的,竟是一陣急促的電話聲響。堂姐發生車禍,必須立刻進行手術,當時聯絡不到大伯,爸媽立刻趕過去,才出門五分鐘,電話又再一次響起,大哥放下電話之後,只說:「死了。」「死了?」至今仍然能夠感受當時不可置信的恐懼,兩層樓的房子,留下詭異的節奏。我輕抱著熟睡中的弟弟,用力緊閉眼睛:睡吧,睡吧,這只是一場太過真實的噩夢。夢不知道進行了多久,在暗黑的意識中聽見爸媽的惋惜:這麼年輕的一個孩子。
失序的生活使我忘了悲傷,只是在每次的祭奠中,聽著法師的喃喃,按照規矩重複一次又一次的祝禱。偶爾,也會很不誠懇地想著還沒算完的數學、回去要背英文單字,升學的壓力並不趁此悲憫我,總覺得好累好想睡……。死亡好冷,夜深的寒風迸發冥紙堆砌起的巨大火光,那是僅有的光明溫暖的意象。殯儀館大概是世界上最少笑聲的地方,而我卻不知道該怎麼哀悽,只能平平整整放好五官,不笑不語是我唯一的表情。
我的情緒異常地凹陷,思量著街坊鄰居對堂姊的讚美與追念,到底有什麼價值,只是為了加強一嘆可惜的語氣嗎?這些問題根本禁不住疑問。我變得更加尖銳,用冰冷的視野審視每個人的行為。當全家人準備驅車前往殯儀館,鄰居問我們要去哪,不等爸媽回答便搶著說:﹁要去拜你!﹂爸媽倒不甚介意我的無禮,反正所有失常的行為,在他們眼中都只是一時的叛逆。
是的,我是生而叛逆的,提早來到這個世界,被家族賦予莫大的罪孽。關於我早產的故事聽聞太多了,不管是怎樣的情節與邏輯,結論一定是我的存在耗盡了阿公阿嬤的錢。「你知道那些錢可以買多少房子嗎?」這個問號是所有長輩給我的考題,無法回答,我只能相信自己的命很值錢,在毫無能力決定任何事情的時候,已虧欠太多。於是我顯得乖巧,彷彿是一種贖罪的姿態,向所有的長輩宣示:「大家,對不起。」但是這樣的乖巧除了得到無關痛癢的讚美外,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與包容,甚至慢慢地失去存在感。我真是耗盡力氣想要爭取一點關心,管他是誰都好;可我知道,當我懂得把自己的一切打理得好好時,很有可能在長輩忙碌的生活中,成為最不起眼的那個。
我開始厭惡這個家,以及家裏的每個人,甚至上演了翹家的戲碼,每次被爸媽拎回家就展開冷戰。我只要學習大哥翹課打架,父母的注意力就不得不放在我身上了。無奈,我嚥不下氣又狠不下心。
只有堂姊安慰我。
那是在一個昏黃的午後,我和媽媽到臺大醫院探望爺爺,在那剛好遇到了堂姊。媽媽向阿公抱怨我一連串失去理智的行為,說到激動處,窗外的餘暉把雪白的牆壁燃燒起來,同時引爆我所有的不滿,胡亂說了些賭氣的話,把頭別過去,一語也不發。堂姊看我已經拒絕與媽媽溝通,就坐在我旁輕輕地說;要懂事、要體諒。我難掩激動的情緒告訴姊姊自己的委屈。她說她懂,只是大家都在忙的時候就要更懂得忍讓。
「你現在的功課好不好?」整個家,不會有人管好不好。
「我的數學不好,我覺得線性函數很難。」
堂姊答應要教我數學的那一年剛好畢業,回到了板橋,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房屋仲介公司上班,她的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份合約,預計在晚上簽訂,就是當晚我們接到電話,那份合約再也簽不了了。原來,當我紅著眼眶,在醫院和媽媽生氣,想著堂姊細細的安慰,望著烏黑的長髮,米白色的長裙使得醫院的色澤柔軟了些。那個緩緩離去的背影,款款的道別,竟是我這些年來任憑記憶如何模糊也無法忘記的,充滿光影的印象。
再次見到她,靜靜地躺著,只要不呼喚,那和睡著沒兩樣。但我總還是忍不住地偷偷問:姊姊,妳什麼時候醒來?
告別式當天,起了個大早,到了殯儀館的時候一切尚未就緒,坐在外面守候,看見爸爸從廳堂走了出來,泛紅的眼眶想必是目睹了堂姊的遺照。照片真美,彩色的半身照,照片中的她微微側著身子,對著鏡頭展現略帶羞澀的笑容。那種笑,彷彿可以從葬儀隊的冰冷喧鬧中滲透出來。那樣的生活照,比起在相館正襟危坐的大頭照美多了。我甚至在心中暗暗決定,一定要為自己預留一張滿意的照片。
儀式結束,靈柩要送往火化,我們向她深深鞠躬,到了此時,才出現一道清晰的聲音告訴自己:姊姊沒了。也是至此,才深刻明白這些日子以來的冷靜,其實不是不傷悲而是不死心。一直都以為是夢是夢,總認為事情不可能就這樣發生,這樣結束。其實只是自己一廂情願的妄想,就是不甘心。我就是存了這麼一點痴心,心中隱隱希冀死者復生,當時的我就是如此渴望著大夢乍醒。
該醒的人太多,但堂姊是不會醒的。我們帶她來到一個悠靜的寺廟,眾人合議替她挑選了一個位置,一尊尊的佛像都是一個個的故事,所有關於她的往日都要塵封深埋於選定的佛像中。把骨灰慢慢移到罈中,過程中,我緩緩蹲下執起意外掉落的,手卻抖得厲害,這是我姊,這就是我姊呀!一切都結束了,我們只能誠心祝禱,生死殊隔,願諸佛菩薩能夠渡化亡者。
往後我對她的想念像是失序的底片,只有在生活中不經意的片段,才會有突然的顯像。當我騎車時,特別害怕公車的輪胎,那一定很重很痛,聽大伯說,當初到醫院看到堂姊時,她的雙唇緊閉,法醫才發現她痛得把牙齒都咬碎了。又或者我看到她工作的房屋仲介公司、經過那家醫院……。每次看到滿樹的櫻花,就想到她柔軟溫淳的笑語,姊姊的名字就是「櫻月」,我們總喊她「櫻月姊姊櫻月姊姊」,就這樣喊著喊著,即使到了此時此刻,這樣的呼喊往往能夠成全我最深情的訴願。也是在無意間驚覺自己的行跡竟一步步陪在她的身旁,高中三年都在板橋,偶爾望向公車外熟悉的現場,我們用白幡和呼喊鋪一條回家的路,每一次經過都會激起思念的漩渦,不小心耽溺,同學就笑我太愁。
愁不是錯,錯在我將生之偶然視為當然,卻又以為死亡是生命的意外。
一個人的離去,是龐大的秘密,也是整個家族的遺憾,而遺憾產生之後,好像這個家就不再那麼完整,好像快樂也不再那麼乾脆。至今我們完全隱瞞阿公,只是擔心他羸弱的身軀禁不住這樣的打擊。這些年來他究竟知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呢?他會不會是假裝不知道呢?阿嬤每天都會誦經,久了也就成為生活的一部份。當時,她放棄見堂姊一面,不讓阿公知道也是她提出的意見。她嘴上不說,卻總是為家裏每個人祈願,我也明白在她的心中,永遠不忘記幫堂姊多添點福氣的。就這樣一點一滴,自己的心也越來越寬慰。
在大家逐漸淡忘的時候,我才真正鼓起勇氣,向過去索取記憶,企圖覓尋和堂姊的互動。記憶在夢中,跟著偷偷長大,我長成了櫻月姊姊的年紀,而姊姊卻永遠也不老。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