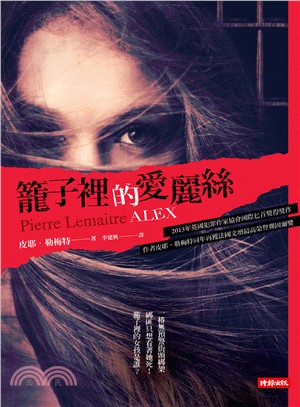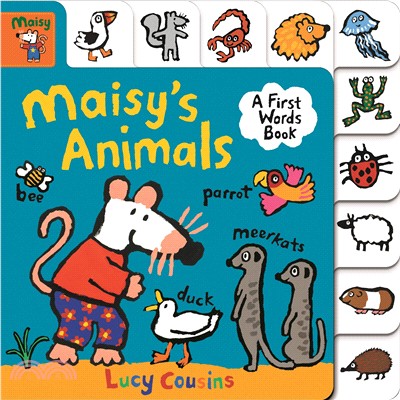商品簡介
「比真相更重要的,是正義!」
2013年英國犯罪小說國際匕首獎得獎小說
(2013CWA International Dagger, Winner!)
光天化日下少女在大街遭到強擄──
沒有線索、如何破案?為何大街綁架?
尖叫的女孩到底是誰?
法國暢銷犯罪作家皮耶‧勒梅特Pierre Lemaitre
以本書勇奪2013年國際匕首獎,同年再榮獲龔固爾獎
成為繼史提格拉森、尤奈斯博之後,最轟動國際文壇的犯罪小說家
──頂尖犯罪小說──
綁架案件發生的頭幾個小時是最關鍵的黃金救援時刻,錯過這段關鍵時間,肉票生還的機會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一本節奏緊湊、情節無懈可擊、電翻書頁的犯罪驚悚傑作。
故事一開場,少女愛麗絲在街頭遭到綁架。綁架她的人只想看著她死。
負責此案的卡繆‧范赫文探長當然不這麼想。
可是現場目擊者舉證不全:嫌犯不明,沒有線索。唯一確認遭綁架者的是年輕女子。
探長決定從她著手:「女被害人愛麗絲為何遭到綁架?」
這個謎團將范赫文探長捲入一場布局複雜且時間緊迫的競賽──
一切宛如命運的安排。對於身體和心理都曾有過悲慘缺陷的卡繆‧范赫文探長,
救回愛麗絲有期限的性命,僅僅將是重重艱難挑戰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項。
為了拯救在吊籠中生死垂危的愛麗絲,時間殺人,
即將掀起一場陰森駭人的毀滅風暴。
作者簡介
1951年生於巴黎,法國作家、編劇,龔古爾文學獎得主。
曾任文學教師多年。他迄今的小說作品備受各界讚賞,譽為犯罪小說大師,曾經榮獲2006年干邑處女作小說獎、2009年最佳法語推理小說獎,以及2010年Le Point週刊歐洲犯罪小說獎。《籠子裡的愛麗絲》是他第一本被翻譯成英語的小說,贏得了2013年CWA國際匕首獎最佳犯罪小說。
2013年11月,皮耶‧勒梅特以描寫一次大戰的作品 Au revoir la-haut ,榮獲龔古爾文學獎。
譯者簡介
李建興
台灣台南市人,輔仁大學英文系畢。曾任漫畫、電玩、情色、科普、旅遊叢書等編輯,路透新聞編譯,現為自由文字工作者。譯有《地獄》、《亡命伊斯坦堡》、《失落的符號》、《殺手的祈禱》等數十冊。
名人/編輯推薦
迷人又有原創性,難以預料的每個階段都扣人心弦。
──Marcel Berlins,《泰晤士報》
嚴苛、猛烈又有法國味的犯罪小說寫法。由已故的楚浮導演翻拍成黑白片也不會突兀。
──Geoffrey Wansell,《每日郵報》
從令人迫不及待的驚悚轉變成精密布局、朝向黑暗真相的狂奔。
──Alison Flood,《觀察家報》
很快就會發現勒梅特不負盛名,而愛麗絲本身原來是作者暗藏的王牌。閱讀到一半左右你可能以為正迎向令人脈搏加速的結局。但是你錯了;在某個程度上,小說從這裡才剛開始。
──Barry Forshaw,《獨立報》
不像許多同類型小說,煽情的前提逐漸消逝,本書有著驚人的情節轉折,戲劇張力隨著死亡人數逐步升高──是一本提神駭人又一氣呵成的讀物。
──Laura Wilson,《衛報》
被譽為自史提格‧拉森的《龍紋身的女孩》以來最重要的犯罪小說,本書主角同樣是個有缺陷卻迷人、決心復仇的女性主義者,很可能成為今年犯罪小說的大作。
──Declan Burke,《愛爾蘭時報》
皮耶‧勒梅特,又一個註定要家喻戶曉的犯罪小說大師。
──Adam Sage,《泰晤士報》
一開始的尋找失蹤人口很快變成與巴黎版的莎蘭德──愛麗絲相關的一連串吸引人的調查。捉摸不定、聰明又矮小的卡繆也是同樣迷人的角色。
──John Dugdale,《週日泰晤士報》
書摘/試閱
第1章
愛麗絲宛如置身第七層天堂。她已經試戴假髮與接髮一個多小時了,猶豫,離開,回來,再試戴。她在這裡可能耗上一整個下午。
她三四年前純粹湊巧在史特拉斯堡大道上發現了這家小店。其實她沒在找什麼,但是出於好奇走進去,驚訝地看見自己變成紅髮女,脫胎換骨的樣子,她當場買下了那頂假髮。
愛麗絲幾乎戴什麼都行,因為她真的很漂亮。不是一直都這樣的;轉變發生在她青少女時期。之前她是個相當瘦弱、醜陋的小女孩。但是當她終於開花,就像潮汐,像快轉的電腦變形程式;短短幾個月內愛麗絲變成了迷人的小女人。或許因為當時每個人──尤其愛麗絲自己──都已經放棄了她會變漂亮的希望,她也從來不認為自己漂亮。即使是現在。
例如,她從來沒想到她能戴紅假髮。那是個啟示。她無法相信自己現在的外貌多麼不同。假髮似乎很膚淺,但她一戴上的瞬間,感覺自己的整個人生都改變了。
結果她很少再戴第一頂假髮。她一回到家就發現它看起來很俗氣、廉價。她扔掉了。不是丟進垃圾桶,而是丟進梳妝台的最底層抽屜。偶爾她會把它拿出來,試戴,看著鏡中的自己。雖然確實很難看,擺明是「庸俗的尼龍嚇人假髮」那種東西,愛麗絲在鏡中看到的東西燃起一股她想要相信的希望。於是她回到史特拉斯堡大道那家店徘徊,尋找有點超過護士所需,但是看起來逼真得驚人的高雅優質假髮。她下定決心嘗試。
起初並不容易;至今亦然,這需要勇氣。對愛麗絲這種害羞、缺乏安全感的女孩,光是鼓起勇氣就要花上半天。畫上適當的妝,找出完美的衣服,搭配的鞋子和提包(呃,搜索衣櫃找出可能搭配的東西,因為她沒錢每次都買新衣……)。但是到了變身成別人上街的時刻。不盡然,但是很接近。雖然算不上驚世駭俗,但能殺時間,尤其對現實生活失望的時候。
愛麗絲偏愛有強烈主張的假髮,彷彿在說「我知道你在想什麼」或「我不只臉蛋漂亮還是個數學天才」的假髮。今天她戴的假髮說「你在臉書上找不到我這種人」。
當她拿起一頂稱作「都市震撼」的假髮,她瞄向商店櫥窗外看到了那個男的。他站在街道遠端假裝等人之類的。這是她兩小時內第三次看見他了。他在跟蹤她。現在她發現一定是。她第一個念頭是「為什麼找我?」,彷彿她能理解男人為何跟蹤除了她之外的其他女人。彷彿她並非向來被男人注目,在公車上,在街上。在商店裡。愛麗絲總是吸引不分老幼的男性注意。這是三十歲的好處之一。但是每次發生,她還是會驚訝。「外面有比我漂亮得多的女人。」愛麗絲總是缺乏安全感,苦於自我懷疑。從她小時候就是這樣。到了青春期她有嚴重的口吃。即使現在她緊張時還是會結巴。
她不認得那個男人;以前從未見過他──像那種體型,她會記得。況且,五十歲的男人跟蹤三十歲的女人似乎很怪……並非她有年齡歧視,絕對沒有,她只是驚訝。
愛麗絲低頭看著假髮,假裝猶豫,然後走到店內能看清楚街上的另一邊。從他衣服的剪裁看得出來他曾經是某種運動員,重量級的。她撫摸著一頂灰金色假髮,努力回想第一次是什麼時候見到他。她記得在地鐵上看過他;四目交會了片刻──足以讓她注意到對她露出的微笑,顯然意圖表示善意與好感。她困擾的是他眼神中的執迷。還有他的嘴唇,薄得幾乎不存在。她本能地起疑,彷彿不知怎地所有薄唇的人都在隱瞞什麼,某種沒說的秘密,可怕的罪惡。還有他高聳圓頂狀的額頭。不巧,她沒多少時間觀察他的眼睛。眼睛從不說謊,愛麗絲認為,她用眼睛來判斷別人。顯然,在地鐵上有那樣的人,她不想久留。
她謹慎地、幾乎偷偷地轉身背對著他,在包包裡翻找她的iPod。她播放〈Nobody’sChild〉,同時回想昨天或前天是否看過他在她的大樓外徘徊。記憶很模糊,她無法確定;如果她回頭去看,或許會更清楚,但她不想鼓勵他。她確定的是在地鐵看到他的兩小時後,她走到史特拉斯堡大道上一回頭又發現了他。她突發奇想決定回到店裡試戴中等長度有劉海的紅褐色假髮,她轉身,發現他站遠了一點,他靜止著假裝在看櫥窗裡的東西……在女裝店。他怎麼假裝也沒用……
愛麗絲放下假髮。她的雙手毫無理由地發抖。她想太多了。這傢伙喜歡她;跟蹤她,自以為有機會──他在街上很難吸引到她。愛麗絲搖搖頭彷彿想要下定決心,當她再看向外面街道,男子已經不見了。她向左右兩邊俯身觀望,但是沒人;他走了。她感到的解脫似乎有點不合比例。「我只是想太多了,」她又想,呼吸開始恢復正常。在店門口,她忍不住停步再看看街上。感覺像是他失蹤令她擔心。
愛麗絲看看錶,仰望天空。天氣溫和,至少還有一小時才會天黑。她不想回家。她必須去採購糧食。她努力回想冰箱裡還有什麼。她採購雜貨向來有點草率。她總是把精力專注在工作、舒適感(愛麗絲有點偏執強迫症),還有──即使她不願意承認──衣服與鞋子上。加上包包和假髮。她希望她的感情生活會有不同結果;那算是敏感話題。她的情史是一場災難。她希望,她等待,最後她放棄。最近,她盡量不去想它。但她很小心不讓遺憾轉變成速食餐點和看電視過夜,小心不發胖,不自暴自棄。雖然單身,她很少感覺孤單。她有很多重要計畫讓她保持忙碌。她的感情生活或許糟糕,但這就是人生。而且她讓自己保持單身比較輕鬆。雖然寂寞,愛麗絲努力過正常的生活,享受微小的愉悅。想到可以自我放縱令人安慰,就像其他人一樣她也有權自我放縱。例如今晚,她就決定招待自己到沃吉拉街的Mont-Tonnerre餐廳吃晚餐。
她有點太早到。這是她第二次來。上次是一週前,員工顯然記得獨自用餐的紅髮美女。今晚他們把她當熟客迎接,侍者搶著服務她,笨拙地和這位漂亮顧客調情。她向他們微笑,輕鬆地迷倒他們。她要了同一張桌子,背對陽台,面向室內;她點了同樣的半瓶亞爾薩斯冰酒。她嘆氣。愛麗絲熱愛美食,愛到她必須小心。她的體重總是不穩定,但她學會了怎麼控制。有時候她會胖上十或十五公斤,變得幾乎讓人認不出來,但是過兩個月她又回到原始體重。這是幾年前她無法逃脫的循環。
她拿出書來,並且多討了一根叉子把書撐開,以便吃飯時閱讀。坐在她對面的是上週在此看過的淡褐髮男子。他跟朋友共進晚餐。目前只有兩人,但從他們言談中顯然很快會有其他人加入。她一踏進餐廳他就看到她了。她假裝沒發現他注視著她。即使其餘朋友來了,展開關於工作、女孩、女人的無窮談笑,輪流述說自我吹噓的故事,他可以整晚盯著她。同時,他會偷瞄她。他不難看──四十歲,或許四十五歲──而且顯然跟年輕人一樣帥;他有點喝多了,所以苦著一張臉。他的臉激起了愛麗絲內心一些感觸。
她喝掉她的咖啡,而且──算是她的讓步──在離開時看了他一眼;她做得很技巧。短暫的一瞥,愛麗絲做得很完美。看見他眼中的渴望,有一瞬間她感覺腹中刺痛了一下,哀傷的提示。在這種時候愛麗絲從不表現出她的感受,當然對自己也是。她的人生是一連串凍結的畫面,裝在放映機裡的一捲影片──她不可能倒帶,修改她的故事,找出新的字眼。下次來這裡晚餐,她或許會留晚一點,她離開時他可能會在門外等她──誰曉得呢?愛麗絲知道。愛麗絲太熟悉這種事怎麼進行了。老是同樣的情節。她跟男人的短暫邂逅從未演變成愛情故事;影片的這一段她看過太多次,她都記得。情況就是這樣。
這時已經天黑,夜晚溫暖。有輛公車剛要駛離。她加快腳步,司機從照後鏡看到她,等了她一下,她趕上公車,但是正要上車時改變主意,決定走點路。她向無奈聳肩的司機示意,彷彿在說,唉,人生就是這樣。他還是打開了車門。
「我後面沒有車了喔。我是今晚最後一班……」
愛麗絲微笑,揮手謝謝他。沒關係。她可以走完剩下的路。她會走法吉耶街再轉到拉布魯斯特街。
她住在范夫城門附近已經三個月了。她經常搬家。之前,她住在克里南庫城門附近,再之前是在商業街。大多數人討厭搬家,但這對愛麗絲是種需要。她很喜歡。或許因為,跟戴假髮一樣,感覺好像她改變了人生。這是不斷重複的主題。總有一天她會改變她的人生。
在她前方,有輛白色廂型車停在人行道上。為了通過,愛麗絲必須擠過廂型車和大樓之間。她察覺有人,是男人;她沒時間轉身。一顆拳頭擊中她肩胛骨之間,讓她無法呼吸。她失去平衡,向前撲倒,額頭猛撞到廂型車上發出一聲悶響;她丟下攜帶的所有東西,焦急地揮舞雙手想找東西抓住──但是什麼也沒摸到。男子揪住她頭髮,但假髮脫落在他手中。他咒罵,她沒聽清楚是什麼字眼,然後一手猛扯她的真髮,另一手用足以打暈蠻牛的力氣拳擊她腹部。愛麗絲沒時間慘叫;她彎下腰嘔吐。男子一定非常強壯,因為他能像一張紙似的把她翻過來面對他。他的手摸到她腰際,拉她貼緊同時把一團面紙塞進她嘴裡直到喉嚨。是他:她在地鐵,在街上,在商店外看到的男人。是他。有一瞬間他們眼神交會。她想要掙扎,但他緊抓著她的雙手,她無計可施,他太強壯了,他推她倒下,她膝蓋屈服,跌向廂型車地板上。他痛下殺手,猛踢她背後中央,讓愛麗絲跌進廂型車,地板磨擦到她的臉頰。
他跟著她爬上車,猛力把她翻過來拳擊她的臉。他很用力打她…………這傢伙真的想傷害她,想要殺她──愛麗絲挨打時腦中只想到這點。她的頭顱撞擊著廂型車地板又反彈,她感覺後腦劇痛──那叫做枕骨,愛麗絲想,枕骨。但除了這個詞,她能想的唯一念頭是,我不想死,不能像這樣,不是現在。她蜷縮成胚胎姿勢,嘴裡充滿嘔吐物,感覺雙手被猛扭到背後緊緊捆綁,然後綁腳踝。「我不想死,」愛麗絲想。廂型車的門大聲關上,引擎怒吼發動,車子尖叫著駛離人行道。「我不想死。」
愛麗絲暈眩卻又清楚發生在她身上的事。她在哭,被眼淚嗆到。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我?
我不想死。現在不行。
第2章
當卡繆打電話來時,尚‧勒關分局長不給他任何選擇。
「我不在乎你的顧慮,卡繆,你真的把我搞毛了。我這兒沒人了,我說真的,所以我會派車給你,你非去不可!」
他暫停一下,然後,以防萬一,補充說:「還有別再來煩我了。」
他掛斷。這是勒關的作風。衝動。通常卡繆不甩他。通常他知道怎麼應付分局長。
這次的差別是發生了綁架案。
卡繆一點也不想管。他的立場很清楚:他不願碰的案子很少,但綁架就是一種。自從艾琳死後就這樣。他老婆倒在街上,懷孕八個月,被緊急送醫;然後她被綁架了。後來她再也沒有活著出現。卡繆悲痛欲絕。狂亂還無法形容;他深受創傷。他癱瘓了好幾天,發呆。當時他出現了妄想症狀,必須被隔離。他被精神病診所丟給療養家庭收容。他能活著就是奇蹟了。沒人料想得到。請病假離開警局──刑事組──的幾個月期間大家都懷疑他能否露面復職。當他終於回來,怪的是他跟艾琳死前沒兩樣,只是老了一點。此後,他只接過一些小案子:性犯罪,同事打架,鄰居謀殺。死者已經靜止,不會移動。沒有綁架案。卡繆希望他的死者死得透徹,是不會留下後遺症的屍體。
「饒了我吧,」勒關告訴他很多次了──他已經盡量為卡繆設想──「你不能迴避活人;這樣沒有未來。還不如去當殯葬業者。」
「可是……」卡繆說,「我們就是收屍的啊!」
他們認識二十年了,彼此都喜歡對方。勒關像是放棄出外勤的卡繆。卡繆像是放棄追求權力的勒關。兩人最明顯的差異是薪資等級與五十二磅體重。此外,身高相差約十一吋。這麼說聽起來有點荒謬,當他們站在一起確實很像卡通人物。勒關不太高,但卡繆明顯發育不良。他看世界的視角大約像十三歲小孩。這是他的母系遺傳,畫家慕德‧范赫文。她的畫在海外有十幾家博物館收藏。她是個傑出畫家與活在煙霧中的老菸槍,宛如永久的光環;很難想像她身邊沒有煙霧的樣子。卡繆有兩個特徵拜她之賜。畫家部分留給他傑出的繪畫天賦;菸槍部分留給他先天性發育不良,意思是他的身高從未超過四呎十一吋。
他很少遇到比他矮的人;他這輩子都在仰望別人。他的身高不只是殘障的程度。在廿歲時簡直是可怕的羞辱,到卅歲是詛咒,但是從一開始顯然就是宿命。這種殘障讓人喜歡用冗長字彙。
有了艾琳,卡繆的身高變成一種力量。艾琳讓他內心堅強。卡繆從未感覺這麼……他尋思適當字眼。少了艾琳,他連話都不會說了。
反過來說,勒關可以算是巨人。沒人知道他體重多少;他拒絕談論。有些人宣稱他至少有120公斤,也有人說130公斤,還有人認為更多。那不重要:勒關很胖,像隻臉頰豐滿的大象,但因為他有閃爍著智慧的大眼睛──這點沒人能夠解釋,男人都不願意承認,但是大多數女性同意──分局長是很迷人的男人。自己想吧。
卡繆習慣了勒關的脾氣;他不喜歡裝腔作勢的人。他們認識太久了。他冷靜地拿起電話回撥給分局長。
「聽著,尚:我會去,我會處理你們這個綁架案。但是莫瑞一回來你得叫他接手,因為……」他呼吸一下,然後用充滿威脅的冷靜清晰地念出每個音節,「我不會接這個案子!」
卡繆‧范赫文從不叫嚷。或者說他幾乎不叫嚷。他是有威嚴的人。他或許又矮又禿又瘦弱,但大家都知道這一點。卡繆像剃刀一樣。勒關小心地不發一語。有惡意八卦說卡繆是他們同性戀關係中的一號。他們不拿這種事開玩笑。卡繆掛斷。
「操!」
他只需要這樣。反正又不是天天有綁架案;這裡不是墨西哥市。怎麼不發生在別的日子,他在辦別的案子或休假時,或別的地方,哪裡都好!卡繆一拳搥在桌上。但他動作放慢,因為他是理性的人。他不喜歡發飆,即使是對別人。
時間不多。他站起來,抓了外套和帽子,兩步併作一步走下樓梯。卡繆的腳步很沉重。艾琳死前,他走路像是裝了彈簧。他老婆總是說,「你像鳥一樣跳躍。我都以為你要飛起來了。」艾琳去世已經四年了。
車子停在他前面。卡繆爬上車。
「你叫什麼名字來著?」
「亞歷山大,老大—」
司機匆忙忍住。人人知道卡繆討厭被稱作「老大」。認為聽起來像電視警匪劇。這是卡繆的作風:他非常呆板,總是消極被動。有時候他會分心。他總是有點古怪,但是年齡與鰥居讓他敏感易怒。內心深處,他有怨氣。艾琳說過,「達令,你為什麼總是這麼生氣?」挺起四呎十一吋的身高,把反諷放到一旁,卡繆會說,「妳說得對。我是說……我有什麼好生氣的呢?」他性急又無趣,粗魯又多疑,初次見面的人很少摸得清楚卡繆。很難喜歡他。或許也因為他算不上開朗。連卡繆都不太喜歡自己。
從三年前復職以來,卡繆就負責指導所有實習生,讓不願意當保母的外勤巡佐們如釋重負。自從他的搭檔崩潰之後,卡繆要的只是重建一個忠誠的團隊。
他看看亞歷山大。怎麼也不像叫亞歷山大的人,但他足以高出卡繆四顆頭,這樣不怎麼好看,他沒等卡繆下令就出發,至少顯示出他有點勇氣。
亞歷山大開車像個瘋子;他喜歡駕駛,看得出來。GPS系統似乎趕不上他。亞歷山大想向探長證明他是個好駕駛──警笛大作,車子快速衝過街巷、交叉路口、大馬路;卡繆雙腳離地廿公分,右手緊抓著安全帶。十五分鐘內他們就到了犯罪現場。現在晚上九點五十分。不算很晚,但巴黎已經顯得安詳,半睡半醒,不像有人被綁架的城市。「有個女人,」根據顯然在震驚狀態報警的目擊者說,「就在我眼前被綁架。」那個男士不敢相信。話說回來,這種事確實罕見。
「在這裡放我下車吧,」卡繆說。
卡繆下車,整理一下帽子;司機離去。他們在街尾,距封鎖線大約五十米。卡繆走過剩餘路程。有時間的話,他一向喜歡從遠處看問題──他喜歡這樣子工作。第一眼很重要,所以最好看清整個犯罪現場;不知不覺間你會陷入無數線索、細節,沒辦法抽身。這是他遠離等待著他的人群一百米的檯面上理由。另一個真正的理由是,他根本不想來。
當他走向閃爍著警示燈映在建築物上的警車時,他努力猜想著自己有何感受。
他的心臟狂跳。
他感覺很糟。他寧可折壽十年也不想來。
但是無論走得多麼緩慢又勉強,他已經來了。
四年前的情形多多少少也像這樣。在他住的街上,看來有點像這條街。艾琳不在。她預定幾天內就要生下兒子。她應該在婦產科才對。卡繆跑來跑去,到處找她,當晚盡了一切努力找她……他像個瘋子似的,但是無能為力。當他們找到她,她已經死了。
卡繆的惡夢就從這種時刻開始。所以他的心臟跳到差點炸開,還有耳鳴。他的罪惡感,以為已經休眠的罪惡感,甦醒了。他感到不舒服。腦中有個聲音大叫,快逃;另一個聲音說,留下來面對;他的胸口好悶。卡繆怕自己可能暈倒。相反地,他移開一座路障踏入封鎖區。外勤警員從大老遠向他揮手招呼。連沒有直接認識范赫文探長的人也認得出是他。這並不意外。即使他算不上傳奇人物,他們也知道他的身高。還有他的遭遇……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