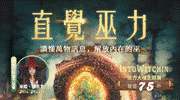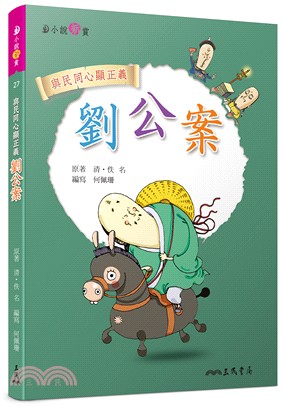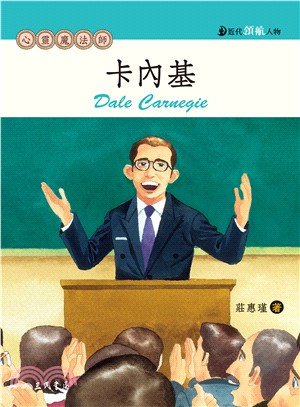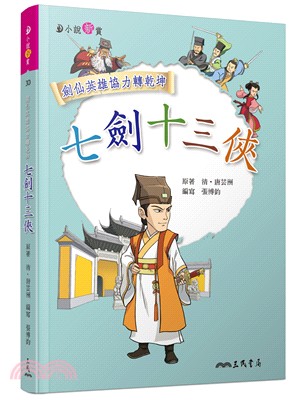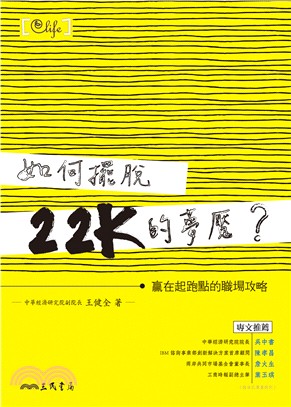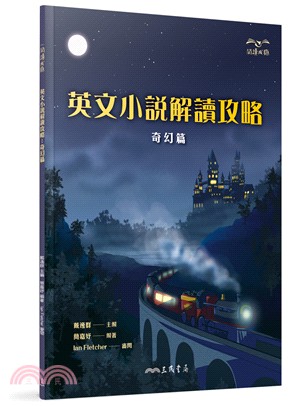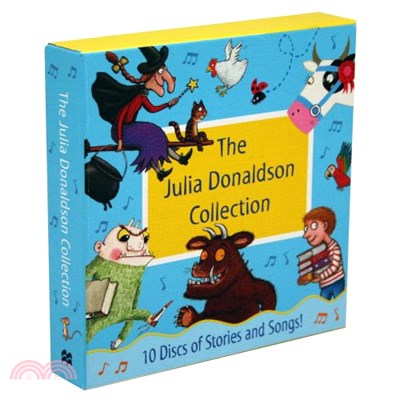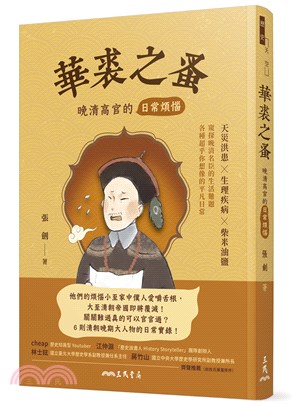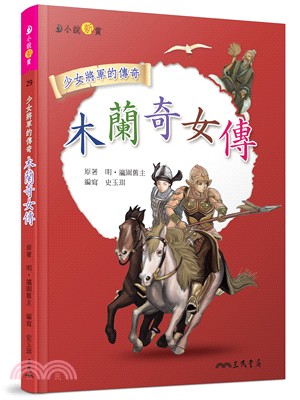商品簡介
她想找回失去的人生,
但真相卻似被層層包裹在蠶繭中,無法觸及……
在倫敦街頭目睹好友車禍昏厥的艾蘿,醒來後躺在醫院病床上,遍體鱗傷的她被告知出了車禍。
她強忍身體不適尋找好友斐恩,但護士不但告訴她沒有斐恩這個人,醫院中所有人像是熟識她一般稱她為「尹芳」,而且還多了一位醫師未婚夫?!
她走進洗手間,注視著鏡中的影像,這再熟悉不過的面容卻隱約透露出一股莫生感,彷彿將一張張透明投影片疊起,明明同款同樣,上面的字跡圖形就是無法準確拓合。
猶如鬼魅的護士、與現實交錯的夢魘,讓她懷疑是否有人要害她,而她也快要分不清自己究竟是「艾蘿」還是「尹芳」……
作者簡介
韓商羚
臺大中文系、英國約克大學藝術史碩士畢。高中時開始寫作,於當時課本中讀到曹丕《典論‧論文》,以及劉勰《文心雕龍‧情采》,遂以此二文為創作圭臬,至今不改。曾擔任澳洲《東方郵報》「光陰博物館」專欄作者、發表各類作品於報章及文藝月刊。曾獲金筆文學新詩獎、紫絲帶小說獎、中華電信大賞文學組小說獎。現居住於美國西雅圖。
序
引言
仲夏午後,勻透的日光散漫渙滯於城市每一處,車來人往,忙碌擾攘的廣場、街道氤氳着一貫淡漠模糊的氛圍——一貫印象式,繽紛而無從定位的色調,喧鬧但難以辨認的話音。
四點正,鐘聲響起,飄飄揚揚,如一則清亮而遙遠的背景配樂。噹——噹——噹……
倏地,一陣無預警的尖銳煞車聲破空而至,緊伴一聲砰然巨響,這場突來的車禍闖入城市原來沒有主軸般的懸浮構景,停格了匆緩步調;四處人潮開始以事端為圓心不斷收斂、收斂,直至將橫躺地上的受害人緊緊包圍。
混亂之中,又是一次輪胎與路面粗魯磨擦的刺耳聲響。肇事車輛眼見闖禍,急速迴轉,倉皇逃離。
鐘聲已止,圍觀人群前仆後繼俯身相視,只見受害人偏着頭,安安靜靜躺着,後腦勺血液汩汩而出,沿着柏油路面流過細礫,滲染了肩頭靛藍襯衫,並迅速暈染成一大片不規則的血泊。群眾無不駭然,指手劃腳陷入焦躁浮動之局。
而這樣驚心動魄的畫面狠狠擊上了艾羅的頭顱,但覺渾身冷冽而乏力,未及在人潮?掙扎,已先虛脫暈厥。
少頃,鳴笛四起,趕抵現場的警察及救護人員各自穿梭於雜亂人潮間封場、堪察、救援,朦朧中,艾羅感覺有人過來搬動她那支離破碎的身軀,在失去意識前她眩目地看着染血的天空、染血的大笨鐘、染血的歌劇院以及一雙雙陌生的眼睛快速交替旋轉、交替旋轉、交替……旋轉……
後記
《情繭》是十多年前構思的故事,久到已經記不清正確年代、記不清靈感的來源。初始只預計寫成四、五千字的短篇,人物也只有艾羅、斐恩、凱諾,都規劃好了段落大綱,卻遲遲沒有寫出。幾年後我到英國念書,想起這小說背景設定正好也在那,不如藉着情境將其完成,此後便日日把稿紙攤在房間那張大木桌上,每每要趕報告、寫論文、查字典,需要空間,才暫時收進抽屜?,課餘之暇再拿出來,如此反反覆覆不知收放了多少回,稿紙都弄得皺巴巴了,小說進度卻始終停在初始的段落,最終還是淹沒在繁忙的行旅以及課業之中,不了了之。
又過幾年,我修「變態心理學」的課,某次上到「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這一節,講師說起了一個案例:有一個青年,騎車載他的小表妹出門遊玩,天氣冷,他便把防風外套反着穿,忽然一陣風吹過,外套翻起,罩住他的頭,他一時視線受阻,撞上了卡車,重傷下雖得倖存,後座的小表妹卻因此喪生了。傷癒之後,這青年認定是自己害死了表妹,他走不出那場車禍的陰影,長年將自己纏困在愧責與懊悔的罪惡裡,飽受精神疾患的折磨。那時,我又想起這篇小說來,想着:「哪一天把這個故事重新寫了吧!」卻也沒有真的付諸行動。
二〇一二年是個多事之秋,特別是下半年,要忙着從澳洲搬到美國(這些年來搬家常以國家為單位),中間空檔回臺灣一趟。八月八日夜晚才抵臺,外婆卻在八月十二日去世,他們都說,外婆向來與我最親,她這樣是在等我回來見最後一面。適逢鬼月,依習俗告別式順延至九月下旬,因此赴美行程必須更改,項目和細節之冗雜直教人心力交瘁,這期間我昏憒傷神,逢單七去作法會,三不五時由公館搭接駁車到二殯祭悼,我向來不太相信異世之說,那卻是我第一次虔誠希望靈魂的存在,希望殊途之外仍聚合有時。寫到這,心中仍曲折不堪……
告別式隔天我們直飛美國,頭兩個月住在公司提供的臨時寓所,那房子像個半穴居,必須走下幾格階梯才開得大門,屋裡不分晝夜昏昏暗暗(艾羅蘭貝斯住處的由來),我也昏昏暗暗地延續着悲戚,成日渾渾噩噩,練習用豎琴彈奏外婆喜愛的曲子,調時差,強振精神打理日常俗務,找房買車,偶爾讀讀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用電腦觀看「稼軒詞」和「東坡詞」的大學開放課程。
年底,驚覺韶光暗換,絕境之中我又想起了寫作來。《情繭》前三章是在那半穴居房舍寫的,那裡沒有多餘的房間,每天夜裡,我就坐在客廳唯一一張書桌前,腳下是轟轟運轉的暖氣出風口,落地窗外樹影颯颯。
原先,我只是想在頹靡中找寄託,當時心境荒蕪、時間破碎,一開始並沒有抱太大期望,但愈寫愈投入,到了後來,每天像走火入魔般惶惶不安,焦躁又亢奮,連睡覺時都夢到人物的對白,比原本預計的字數還多了一倍,排好的大綱,到後期全數徹下重擬,我寫作方式有些老派,靈感雖然即興,下筆前卻總要琢磨至架構臻備,因此這樣失控的情況,是前所未有的,讓我不得不相信小說中的人物真的會違逆作者的駕馭,自行表現個性、發展情節。
以上略記此書創作歷程,從冬季寫到了春季,都忘了冬天應該要寒冷。完稿時,已是在那光線充足的新家書房中。當人真是一件奇怪又困惑的事,我忽然想起梵谷說過:「如果還想畫圖,便應該努力存活。」並癡癡相信着過客中總還有幾個知己,我想寫作之於我亦如是。
最後,謝謝我的外婆。也謝謝Tim,我的繆斯兼幕後功臣。
書摘/試閱
一.
「斐恩?」
靜寂的子夜,艾羅在漆黑病房中醒轉,微弱視線裡並沒有她所找尋的身影。她啞着嗓低聲探問,聲音在清冷的房間中自行盤旋消散之後,不聞任何回音。
艾羅半張着嘴,空洞的雙眼彷彿再度聚焦於倫敦街頭:那渙散的日光、熙來攘往、如速寫般的街景,她兀自悠閒徘徊等待,尚在《阿依達》動人的歌劇旋律之中心馳神遊,一身靛藍襯衫的斐恩在對街笑得燦爛,並穿越馬路快步朝她走來。突來的煞車聲、砸碎的街景、逃逸的駕駛、血泊中奄奄一息的斐恩、暈眩而顫抖的自己……這一切,如影帶在她腦中迴還往復,一次比一次更加瘋狂而激烈地播放,終於凝成一股莫大氣力──她大喊:
「斐恩!」
但過了許久依舊沒有回應。
艾羅仰躺着,兩眼平視,垂地淡綠色簾子沿着天頂金屬軌道環床拉攏,將她的視線牢牢困在這個狹窄的長方體之中;耳邊隱約的醫療器材聲規律而細瑣,身上繁雜線路纏繞連結,轉換對應成機器上富含邏輯的顯示數據。
她全身出着冷汗,像遭逢惡兆的恐慌,架空的移動式輪床稍一動彈便隨之搖晃,鐵支桿亦跟着發出咯嘎聲響。她思緒紛亂,不停想着,要不是自己硬纏着斐恩到倫敦看歌劇,豈會發生這樣的慘事?而她竟親眼目睹了事件始末,染血一幕至此也染進她腦海中,成為滲入畫布纖維的顏料無從抹滅修改,像是對她任性的懲罰。
事件尚未結束──她必須弄清楚斐恩的安危下落,刻不容緩。
有了這個念頭,艾羅再不能安分留置於此。她撐起孱弱的身體、拔去手背上的點滴針管、掀開被單踉蹌地下了床。她揭開床簾,比鄰的病床上床單平坦張展着,枕被整齊疊放,房間?空蕩蕩,毫無她急尋的蹤影。
她強忍着懊悔以及身上的痛楚,在漆黑病房中潛行摸索,近乎神經質地小心翼翼,深怕錯過任何相關音息。
拉開房門,刨光磨石廊道冷清緘默地向兩端無止盡延展,明亮燈光一絲不苟地投下,艾羅眨眨眼,以適應這瞬間切換的幽暗與蒼白。四顧不聞生息、沒有人跡,她扶着牆搖搖晃晃走着,看見了一扇門,便跌撞而入,以犀利的目光仔細檢索病床上的面孔,那病患見她闖入,嚇了一跳,連問:「妳是誰?」她也不搭理,逕自轉身離開,一任厚實房門在背後自行粗魯地闔上,她已扭開下一道門把邁步走進。
艾羅連闖了幾間病房,遍尋不著斐恩身影,卻驚擾了多名病患。儘管身子搖搖欲墜,她的腳步卻愈發急促慌亂,直到聞訊趕來的護士們將她攔下,問:「尹芳小姐,妳怎麼私自離開病房?」艾羅蹎躓上前,如溺水者攀住浮木般地,緊抓住其中一名護士的雙肩問道:「斐恩呢?」
護士們交換了一個不明就裡的眼神。
艾羅見狀,催促道:「快告訴我呀,斐恩呢?下午和我一起被送進醫院的那男孩呢?」護士們皆搖頭,道:「對不起,我們沒看到任何人和妳一同送到醫院來。」
聽了這樣的回答,艾羅眉頭緊蹙,心底不祥之感又加了幾分,正想再次開口發問,一名年齡稍長的護士朝眾人走來,一面問道:「發生什麼事了?」原本圍繞着艾羅的護士們齊時回頭道:「護理長。」
年長的護士在眾人身旁停步,神情肅然略帶了責備,說道:「怎麼大半夜在這兒吵嚷?打擾了病患們休息可不好。」一名護士答道:「護理長,是尹芳小姐,她、她……」
護理長視線隨着移至艾羅身上,換上了關切口吻,問道:「尹芳小姐,好些了嗎?怎麼不在病房多休息?雖然只是場小車禍,但還是得好好調養才行。」
艾羅一時啞然,緊貼着牆壁,戒備而充滿疑惑地看着眾人,久久才怯聲說道:「妳……是不是認錯人了?車禍的不是我,而且、而且我也不叫什麼……尹芳小姐……」
護士們面面相覷,護理長微上前一步,伸出手試着安穩她的情緒,並柔聲說道:「妳先別慌,妳仔細看看我。我是護理長麥緹,妳認得我的,對吧?」艾羅搖頭道:「妳能不能先告訴我,斐恩現在情況怎麼樣了?」
一名護士向護理長靠近,在她耳邊低聲說道:「尹芳小姐從醒後便一直念着這個名字。」護理長點點頭,對艾羅道:「妳先回房間休息好嗎?妳要找的這個人,我再幫妳查查住院名單,好不好?」
說着,便要兩名護士過去攙扶,但艾羅仍不死心,續道:「他是今天……嗯,應該說是昨天下午和我一起入院的。他在歌劇院前發生了車禍,後腦勺一直流血……對了,他是一個奧地利男孩,年齡和我差不多,穿着一件靛藍色襯衫,你們有人有印象嗎?」艾羅眼光認真地向眾人巡邏一回,卻不見有人點頭,一名護士道:「尹芳小姐,昨天因車禍入院的就只有妳一人,而且目前醫院裡並沒有奧地利病患。」
「怎麼可能?」艾羅低眉喃着。護理長對攙扶的那兩名護士道:「妳們先送她回去休息吧。」
艾羅並無回房意願,忽然間,她似乎領悟了什麼,凌厲地看着眾人,冷冷逼問:「斐恩是不是死了?妳們怕我受不了刺激才故意瞞我,對不對?快告訴我真相,他死了嗎?下午和我一起送到醫院那個男孩死了嗎?」攙着她的其中一名護士有些不耐煩地說:「從來就沒有個叫斐恩的男孩存在。尹芳小姐,那可能只是妳作的一個惡夢,妳身體正值虛弱,記憶難免混淆不清……」
未待說完,艾羅突然奮力抽開雙臂,掙出眾人,在走廊上賣命奔跑着,一面哭道:「妳們騙我……我、我自己去找……」說着又要伸手去開一個病房房門,但她傷勢未癒,精神不足,護士們很快地便已趕上前攔阻,護理長指揮將她強行帶回病房,並旋即令道:「快通知凱諾醫生。」
艾羅哭哭鬧鬧,死命掙扎,還是給護士們合力帶回病房,並壓制在病床上。她撕裂般地尖聲喊着斐恩的名字,一會,護理長隨着一名英挺的醫生走進,護士們主動讓出了一個位置,只見那醫生手中拿着一只針筒,彎下身,俐落地將藥物注射於她的手臂。艾羅在淚眼迷濛中似見他嘴唇張合,像是在說些什麼安撫的話;他的面容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熟悉感,如這荒誕陌生的境地中,她唯一能夠信任的安全庇護。艾羅定下神想將他看仔細,然而在藥物發作下她的視線再不能準確對焦,他的五官不斷擴散、模糊……她慢慢失去了力氣,靜默躺着像失水的魚睜着眼喘着微弱的氣,激動的哭喊也逐漸悄然如囈語:「放開我……我要……去……找斐……斐……」
終於,她沉沉睡去。
************
艾羅再次醒來,已是當日晌午。邊側窗簾並未拉上,明媚的陽光透過玻璃窗探入房內;她張開眼,身上覆着被單,拔掉的點滴針頭已重新釘回她手背皮膚裡,並以透氣膠帶固定,床邊機器規律運行,彷彿一度遭打亂的拼圖又經收拾拼起。
「妳醒了?」原本站在儀器旁寫着例行紀錄的年輕護士向她問候道,語氣和表情都似招呼一個素舊。
經過一夜折騰,艾羅知道強求不得,況且她渾身鬆軟疲憊,也無力再戰。她冷靜下來,見這護士親切和善,心中不由寬慰幾分,啞聲問道:「請問這是哪裡?」那護士道:「這裡當然是金達爾醫院呀!」艾羅問:「金達爾醫院?在倫敦嗎?」那護士笑道:「是呀!」並問:「要喝點水嗎?」
艾羅點頭。
那護士替她將病床搖起,體貼地把枕頭直豎,遞上插着吸管的水杯,道:「拿得住嗎?」艾羅道:「可以。」接過杯子吸了幾口,看着那護士問道:「護士小姐,我們以前認識嗎?我是指……不是醫病關係的那種認識。」那護士點頭道:「尹芳小姐,我是潔兒,妳真的不記得了嗎?」艾羅仔細回想,口中喃喃唸道:「潔兒……潔兒……」想着,不免一陣頭疼。
潔兒取過艾羅手?的水杯,放回床邊的櫃子上,淡笑道:「沒關係,這可能是遭逢變故,因驚嚇產生的暫時性失憶。妳現在要做的,是把身體養好、心情放寬,嗯。」
艾羅擡起頭,潔兒溫暖的笑容讓她心防卸下不少。理理思緒,欲重新還原事件過程脈絡,問道:「潔兒,妳能不能告訴我,我到底是怎麼了?為什麼我會在醫院呢?」潔兒道:「昨天下午,妳在倫敦街頭發生了車禍,是路人即時打電話將妳送醫的。」艾羅問:「是在歌劇院前的馬路嗎?肇事的駕駛呢?他逃走了嗎?」潔兒搖頭道:「這我就不清楚了。」又說:「不過妳若想追究,可以聯繫警方幫忙處理。」
艾羅鎖着眉,疑道:「妳確定車禍的是我?」
潔兒瞇着眼笑,好似她問了個幽默的反語,指着她身上多處包紮道:「可不是,不然這些傷憑空而來?幸好沒什麼嚴重內傷。不過妳似乎有失憶症狀,必須進一步檢查才能斷定是否能出院,或者得進行治療。」
順着潔兒手勢,艾羅看見自己身上貼着紗布或纏着繃帶之處,這些傷如此千真萬確,即使層層包裹依然隱隱透着血跡與藥色,卻與她原有的記憶違和。這樣的矛盾抵觸,教她一時之間竟無從判決虛實真偽,原本急切而強烈的念頭也撼動混淆了。
「尹芳小姐,尹芳小姐!」潔兒輕喚陷入苦思的艾羅,安慰道:「別擔心了,我們都會盡全力幫助妳的。」艾羅問道:「潔兒,我到底在醫院住了多久?」潔兒道:「從昨天下午到現在──兩天一夜。」艾羅道:「以前呢?我常住院嗎?我是這?的常客嗎?」潔兒笑道:「常客,嗯,算吧,但妳健康無恙自然不必住院。」艾羅道:「那為什麼醫院?的護士們,好像個個認得我似的?」潔兒有些戲謔地笑道:「因為,妳是凱諾醫生的未婚妻呀!」
潔兒的答覆教艾羅微微一震,期艾道:「凱諾醫生……他,他是誰?妳是指……『尹芳小姐』是他的……呃……未婚妻嗎?」潔兒佯扳起臉,以宣布鄭重要事的口吻俏笑道:「是。尹芳小姐,『妳』正是凱諾醫生的未婚妻。」
艾羅無心與她談笑,這個突兀的身分令她憂懼不已,霎時又武裝起來,凜然質疑道:「妳們誰能證明我是『尹芳小姐』?」
潔兒眨眨眼,道:「這個簡單,人證不消說了,從院長到清潔工,人人都可為證。物證嘛……醫院病歷算不算呢?」她頓了頓,靈光一現,拿起櫃子上的皮包遞上,說道:「妳翻翻,裡面有妳的證件沒有?」
艾羅一臉疑惑,她甚至不記得擁有這個皮包,但事關緊要──她迫切想證明自己並非那個「尹芳小姐」──她接過皮包,打開拉鏈,從中找到了一只紅色皮夾,皮夾?有着圖書證、銀行卡、一些商店會員卡等。她看着卡片上的署名,正想着:「就算這樣,也不能證明什麼,這皮夾根本不是我的!」
潔兒彷彿摸透她的心思,湊過來,伸手抽出了一張證件,道:「喏,妳的駕照,上面有照片,還有妳的名字──現在妳該相信了吧,尹芳小姐。」
艾羅仔細看着那證件,雖然她不記得什麼時候拍過這張照片,但那的的確確是她的臉,五官輪廓分毫不差,連微笑方式也慣熟。稍晌,又發覺不對勁,心想:「我怎麼可能有駕照?」
潔兒的話音打斷了她的思考:「好了,妳先別煩惱這些了,醫院已經替妳安排了腦部檢查,嘉洛醫生是這方面的權威,到時候妳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他。」
時間在談話之中過了大半。潔兒抱起資料檔案,正欲離開,又折返說道:「對了,麥緹護理長要我轉告妳,她幫妳查過住院名單了,但結果並沒有找到妳說的那個男孩。」
提起斐恩,艾羅不免一陣心悸。另一方面,她原以為查找住院名單僅只是護理長在混亂中試圖安撫她的一句虛話,難得面對一個病患失去理智的吵嚷還認真相待,想來這醫院的人也不少誠信可愛,便為自己昨夜與眾人為敵的鬧騰愧疚起來。
見她沉默不語,潔兒探問道:「那男孩……是什麼人?妳為什麼急着找他?」
艾羅嘆口氣,垮下了肩,道:「他是我們學校的交換學生,今年暑假……」她中斷敘述,像在確認密碼般地問:「現在是夏天,八月,對吧?」潔兒點頭。艾羅續道:「我和斐恩是上個月才認識的,他是來自奧地利的暑期國際交換學生,是個很開朗健談的男孩。初識不久,我們便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斐恩熱愛歌劇,時常滔滔不絕地講述着歌劇的淵源、流派、各式各樣離奇曲折的故事情節,心血來潮還哼上兩句,斐恩的歌聲低迴鏗鏘,有一種很獨特的魅力,讓我這個門外漢也開始對這門輝煌華麗的藝術心神嚮往……」她說着,沉醉在回憶之中,唇邊不由牽起了笑容,續道:「前幾天,一個朋友給了我們兩張歌劇票,斐恩起先還猶豫着,畢竟從M鎮到倫敦得花上四、五個小時的火車車程,但我卻興致勃勃地不斷慫恿他;斐恩不忍心拒絕我,便答應了。如果……如果……總之是我害了他,我真的好後悔……我好後悔……」
艾羅說着,不禁悲愴哽咽。潔兒則是站在一旁,輕聲嘆氣,不似同情艾羅所陳述的遭遇,倒似幾分迷惑,幾分惋惜她病中幻構的人事,伸手拍了拍她的肩頭,勸道:「不要這樣激動,對身體不好。」
艾羅抓住潔兒的手,苦求道:「現在妳知道事情來龍去脈,應該明白為什麼我那麼急着找他了吧!我把斐恩害慘了,要是不能確定他平安,我怎能放心休養?潔兒,告訴我真相,無論好壞,我總是得面對這結果的!」潔兒好生使力,才將手抽回,答道:「我真的不知道呀……」艾羅察覺她眼神?的輕率,微慍道:「妳認為這一切都是我的幻想?」潔兒道:「我不知道,說不定……說不定那男孩給送到了別家醫院。說不定,他回奧地利去了……要不,妳問問凱諾醫生吧。」
潔兒再度提起「凱諾醫生」這名字,使艾羅的憂心分了神。她有些排斥地說:「為什麼要問他?」潔兒道:「妳是他的未婚妻,他自然比我們還更清楚妳的事。」
艾羅雖不願接受成為一名陌生人未婚妻的身分,卻覺得潔兒的提議不無道理,應道:「好吧,他在哪裡?」潔兒道:「他一早就到瑞士出席一場重要的國際醫學研討會了,要過幾天才會回來。對了,凱諾醫生說,他很抱歉在妳出事的時候不能留在身邊陪妳,這行程是幾個月前便排定的,希望妳能原諒他。」又建議道:「尹芳小姐,妳還是在這?好好靜養,等凱諾醫生回來,說不定所有的謎題都會真相大白了。」
艾羅閉上眼,無奈地喃喃說道:「看來也只有如此了。」
**********
傍晚,又陸續來了些人,除了例行巡房的醫護人員,還有些是以熟人身分順道探訪「尹芳小姐」的。包括了護理長麥緹、昨晚和她糾纏的兩名護士、一名未曾謀面(或者遭她遺忘)的醫生、一名學生志工。她沒再向來人問及斐恩的消息,面對這些友善、但卻是懷着關心另一人而來的招呼問候,艾羅著實不知該熱絡抑或者冷淡應對。
吃過晚飯以後,艾羅獨自怔怔坐在病床上,窗外落日斜紅,雲幕層層疊疊、疏淡有致,無聲無息地推移捲湧。
其實艾羅並不認為自己失憶。
「失憶」,當指忘却過往的人、事,如記憶遭到刪除般茫然空白。但她並無此症候。她清楚地記得她的名姓、生日、血型。她來自M鎮。她毫無困難地默想了一遍家?的地址、電話、房屋格局以及臨近縱橫的街道名,她父母的名字、年齡、相處時曾有的對話場景、她慣有的日常作息、親戚朋友的臉孔、興趣嗜好……這些,繁簡遠近皆如檔案般完整收納於她的記憶,她隨心調閱,輕而易舉。
再說她此刻置身倫敦的醫院,不正是因為昨天一早與斐恩一同由家鄉M鎮搭車南下,看完歌劇《阿依達》後,斐恩發生車禍,她則因驚嚇暈厥而送醫,這一切仍歷歷在目。為什麼再次醒來,她的世界完全改變了?地點、時間、季節都確認無誤,她卻被賦予了新的名字、身分,有一群與她相熟的陌生人,甚至有個她毫無印象的未婚夫?
尹芳是誰?艾羅是誰?
如果她是艾羅,為什麼身上有着車禍留下的傷處?為什麼斐恩無故蒸散消失?那些證件作何解釋?她才十六歲,還是個高中生,怎麼能考駕照?怎麼會在這時候計劃結婚?醫院那些人又是誰?這是一場惡作劇嗎?那些人其實是演員?假造她的身分?刻意弄傷她的身體?聯手編演這齣戲碼?可能嗎?如此大費周章、天衣無縫?目的呢?
如果她是尹芳……真是荒謬!她甩甩頭,卻不能自己地思索下去:如果她是尹芳,那艾羅又是誰?現下於她記憶中的那些人事時地是真的嗎?艾羅存在嗎?M鎮存在嗎?她的父母(或者說,艾羅的父母)存在嗎?那齣歌劇存在嗎?那場車禍存在嗎?斐恩呢?斐恩存在嗎?想到這裡,她只覺得不寒而慄。
天色漸暗,夜幕高張,深湛天空?寒星點點,冷月孤寂,流雲如煙似霧,虛實難以臆測。
艾羅倦極了,她躺下來,眼瞼如鉛、精神迷幻。儘管疲睏,卻不敢鬆動警覺。在身心的雙重折磨之下她片刻都不得平靜──她一個人,在異地,身負着傷且舉目無親,連過去的人生也一併遭到撤換。她的心情分秒無不強烈拉鋸,猜疑或者相信,那些誠摯關懷的面孔與說詞孰真孰假?是她記憶真的出了問題,還是這根本是場偷天換日的大陰謀?她腦中忽然出現一個畫面:那些白天曾來與她寒暄熱絡的人此刻正脫下喬裝的白色制服,在她看不見的地方群聚慶功、訕笑嗤哼,高舉酒杯碰杯笑道:「敬謊言!」但旋即又想:「也許他們是真的,我不是艾羅,而是尹芳,那麼斐恩出車禍一事便未曾發生,這何嘗不是件可喜之事?看來當尹芳也未必全然不好。」
如此思緒或正或反,昏昏沉沉斷斷續續,醒醒睡睡也不知輾轉幾回。
及至中夜,似覺寒風如刺,被衾不暖。她翻身側睡,身體蜷縮如蝦,半晌,耳邊幽幽聽聞一聲嘆息:
「眾口鑠金,三人成虎,唉──愚蠢。」
艾羅不及聽辨,話音已止,消散如一縷輕煙。她下意識昵昵問着:「斐恩?是你嗎?斐恩……」
四壁靜寂,毫無回應,但身旁猶似一股刀刃般冷酷鋒利的寒意迫臨。她再無以入眠,掙扎着睡意強張開眼,視線開闔之間,似見冰雪般的一對瞳眸在黑暗裡閃爍着,如燐火般祕異詭譎。
艾羅霎時清醒,發現自己其實仰躺着,而那雙眼睛正以四十五度的俯視之姿直勾勾逼視着她。她不確定地輕喚道:「斐恩?」聲音出了口才想起斐恩俊朗縱逸,那燦如日光的赤子笑靨,壓根與這雙帶着怒意的眼神天壤之別。
一會,她的眼睛慢慢適應了黑暗,憑藉窗外微光,勾勒出床邊人影輪廓來:那是一名女子,身著護士服,口罩遮住了大半個臉,柔順的瀏海斜在額前,呈露着濃密睫毛下,一雙銳利如冰的眼,不眨不轉地盯着她瞧。縱使一身白衣端整,卻與醫護身分格格不入。
艾羅有些怯懾,問道:「護士小姐,這麼晚了,有事嗎?」
雖然光線不足,未能細睹,這臉龐髮質、阿娜的身姿卻清楚透露了年輕的訊息。想來必不是護理長麥緹或年齡長者,而這對瞳眸犀利明盼,炯炯有神,艾羅迅速回想着目前為止她接觸過的每一名年輕護士的眼神……
那護士並不理會艾羅的問話,直起腰桿,身子側了側,微弱的光線投射在她向窗的右半邊身體,從艾羅的方位看去,則是帶着黯淡光暈的左半剪影。
那護士緩緩擡舉左肘,攤開的手掌上置放着一顆球狀物,其表面泛白,曲折不平,大小約如一粒蘋果。她把左掌伸向床邊,那柔荑修指、細鍊銀戒,是一隻很迷人的手。
艾羅輕問:「這是什麼?」
黑暗中依稀可辨,那球狀物紋理脈絡略似一個人腦的縮小模型。
那護士不答,收回左掌,右手握着一把亮晃晃的手術刀。艾羅還未及害怕或疑竇,那護士已低下頭,用刀子切入了球狀物,不消片刻便俐落地從中挖下一小塊來。
此刻艾羅倒不擔心她以那把手術刀傷害自己,直覺這護士縱非善類,卻無意害人性命。雖幾番相詢未果,仍再度開口問道:「妳是誰?妳到底想做什麼?」對方仍不答應,艾羅又猜道:「妳是不是有什麼話想對我說,妳……妳知道我是誰?還是、還是妳認識……斐恩……」後面兩個問題是在開口提問後忽而閃現的靈感,出口之後艾羅不禁心驚膽跳,聲音逐漸虛微。
那護士依然沉默,收回左掌,低下頭,再次舉起右手將手術刀切入那球狀物,不一會又從中取下了一塊。
艾羅屏氣凝神,那護士向床邊挪近了一小步,再次把左掌伸下,並半瞇着那懾魂雙眼緊緊逼視。艾羅躺着,垂眼看她手中那挖截缺陷的人腦模型,心中一凜,伸手欲碰觸,那護士卻已迅速握拳收肘,在艾羅不及反應前似聞嘲諷般地哼聲一笑,緊接着「唰」的聲,床簾已經拉上。艾羅的手還停在半空中──
續舉,收回?她一時竟忘了決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