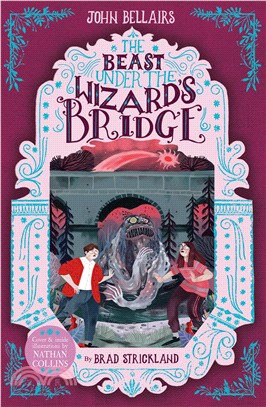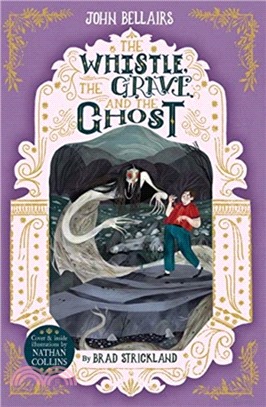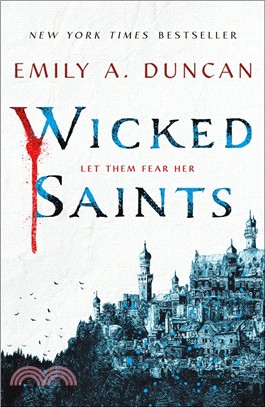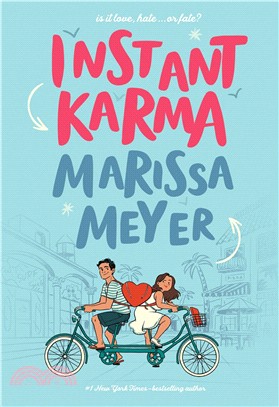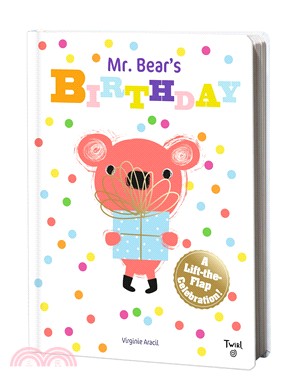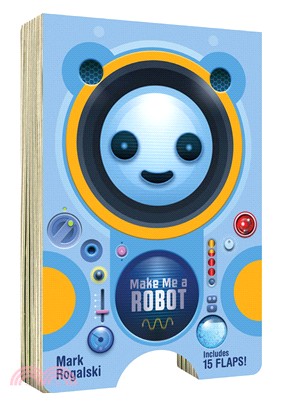楊氏女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愛可以滋長一切,也可以毀滅一切,既像水一樣,又像火一樣。
三十多年了,我所熟悉的女囚大多離開了塵世,
其實,他們的幽靈仍然活著,並以更加囂張的氣勢,
更加世俗的手段殘酷地引誘與被引誘。
她們是犯罪,罪不可赦。但我喜歡她們,我也是犯罪。
他們互吻,彼此激動著對方。不知過了多久,楊芬芳用力掙脫了何無極的臂膀,背轉身去,兩手摀臉,嗚嗚地哭了,眼淚從指間滾落。何無極伸出長長的手臂從後面摟住,手掌撫摸著楊芬芳的胸部,胸和脣一樣,厚而軟。
《楊氏女》是章詒和女囚系列小說的第二部,寫的是勞改營裡女囚自述的畸戀故事。因犯通姦罪而入獄的楊芬芳,有個雖相愛卻未能結為連理的青梅竹馬,卻在半推半就之下嫁給了一個她不愛的軍官,身心受盡折磨。亟需救贖的她於是周旋在兩人之間,屢屢玩火,終釀大禍。入獄之後,又與監獄指導員苟合,甚至暗結珠胎……
作者自述:
我在想:生命是一個故事,還是一個事故?年輕的時候,總以為一個問題只能有一個答案。經歷了許多之後才明白:其實生活中每個問題都有無數個解,而其中沒有一個是絕對正確的。請問《楊氏女》中,誰正確?可能我也不正確。
在楊芬芳身上,愛情與婚姻是悖理的,敵對的:既是勇敢追求性愛的少女,又是怯懦被動的性奴。既有毫無顧忌地對性愛的渴望與擔當,也有愚昧、屈從物欲權勢的自欺,自己也始終在真偽之間搖擺掙扎,「看無主花枝可嗟,一任他東風相嫁。」最可悲可憐的是楊芬芳每次的選擇,幾乎都是錯的,包括最後拒絕趙勇海。無奈啊!楊氏女是以真實情節作基礎的,表現出世俗的天性。這個並非百邪不侵的玉女,最後成為屢屢受害的罪犯,就很可理解了。善與惡,罪與罰,天道,人倫,我真不知該如何描述歸結她的命運。《楊氏女》多多少少蘊含著這個民族久遠文化痼疾的印記吧。
──章詒和《楊氏女筆談》
作者簡介
章伯鈞之女。一九四二年生於重慶,中國戲曲學院畢業,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著有:《往事並不如煙》、《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伶人往事》、《雲山幾盤江流幾灣》、《這樣事和誰細講》、《總是淒涼調》等書。
書摘/試閱
楔子
心不在焉的楊芬芳把最後一口白米飯,送進了嘴裡。
「你再吃一碗吧?」問話的,是她的親姐姐楊婉芳。
「飽了。」
「現在能吃上一碗白生生的大米飯,不容易啊。芬芳,你再吃一碗,算是給我面子了。」說話的叫劉慶生,現役軍人,連長,也是唯一的賓客。
另一個是做東的,楊婉芬的丈夫趙勇海。
四人餐,像宴會那樣鄭重其事,氣氛莊重;又彷彿做出了什麼重大決議,要用一個飯局來紀念。
說準了,真的有重大決議,決議在飯前就已經開始了謀劃……
第一節
楊婉芳是縣城石壁公社的婦聯主任,性格活潑,人也算漂亮。還是拖著一雙小辮子時候,就被公社副書記趙勇海看中。不奇怪,她每次來到公社大院,都要和同村的收發室老大爺閒聊幾句。那銀鈴般的笑聲,引起站在一側讀報看書的趙書記的注意。那時,趙勇海剛提拔起來,巴望事業有成,不想過早成家。但對這個穿來走去的姑娘已有所留意。一打聽,人家還在讀書,心想:很好,事情不必著急;再打聽,人家就姊妹倆,心想:這更好了,不像自己一大家子人,那麼拖累。
趙勇海高個子,眉清目秀,愛動腦筋,說話謙和。縣城高中畢業後,因為是老大,急需替父母分擔養家的責任,就沒有繼續讀書。他的數學、物理成績都不錯。擔任班主任的老師覺得可惜,趕到家裡做說服工作,說:「孩子考師範類院校是十拿九穩,上學的費用全免,還有助學金。」趙勇海挺猶豫。公社領導聽說他的數學好,正逢他所在的石壁公社石壁大隊缺會計,便遞話過來:「若留下來,保證給你當大隊會計。」
趙勇海的父母知道後,興奮得一個勁兒地攛掇兒子留下來,好處擺了一大堆。最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一條,就是:「你從此就叫幹部,不是社員啦。你有補貼工分,你到公社開個會,都算工分的;你分稻穀、分紅薯、分麥稈,都會比別人分得好,也分得多;一家人全年吃不了幾頓葷,你到公社開會就有一碟紅燒肉。葵瓜子嗑不完,還可以往家帶……」絮絮叨叨,雖說趙勇海聽得心煩,但畢竟聽進去了,遂留了下來。一個年輕後生對誰都客客氣氣,彬彬有禮。到公社開會,旮旯一坐,一言不發。問到他,則靦腆道:「我就會算帳,別的不懂,也不行。」就這麼個年輕後生,很快贏得上下左右的好感。
一次,遇到縣裡換屆開會,縣、公社、大隊三級幹部代表參加。公社老書記提出:最好補上趙勇海。一老一小去了,會議期間趙勇海鞍前馬後照顧老書記。選舉那天,需要點票的人。老書記大喊:「我們石壁公社的趙勇海數學好,最合適!」
點票算個啥,既非代數,也非幾何,整潔文靜的趙勇海點得麻利,唱得清晰,連任的縣委書記對他也有了印象,會後對公社老書記說:「我看小趙不錯,你們好好培養吧。」
培養就是提拔。沒多久,趙勇海當上了公社的會計。上任後,把前任的帳徹底清理了一番,很快發現了漏洞。他私底下跟老書記說了。
老書記問:「你打算怎麼辦?」
「我把帳擺平了,但以後不行。公社開個會,吃頓飯,買盒菸都要上帳。到時候上級查帳,找的是趙勇海,老人家得替我想想,家有父母,下有弟妹,我還沒結婚哪!」老書記服了,覺得他不單是會計,還是「把門」的,「放哨」的。
歲尾年初,照例有縣裡幹部到公社查帳。有的公社會計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可趙勇海早早睡下:你們查吧,一分錢不差。之後,他被提拔為副書記,還主動提出兼任公社會計,無人反對。他把工作安頓得井井有條,忙起來就住在公社。
一個黃昏,他走出院子,站到後面的小山坡上,兩眼呆呆地直視前方。太陽終於落下,斂盡了光芒。他的前面,彷彿是個無窮的宇宙;自己的內心也有一個巨大的空洞,而靠自己一個人是無法把這個空洞填滿的。趙勇海意識到:自己該結婚了。這時,楊婉芳的影子便浮現在眼前,二人沒交往多久,婚姻大事就提上了日程。趙勇海的擇偶標準就一條,要心腸好。因為家裡成員多,誰都需要照顧。給點錢啦,送些糧票啦,買點副食品啦,這些事情若老婆橫加干涉,那就難辦了。巧了,楊婉芳挑選對象也不苛刻,就是要找個比自己強的,而趙勇海在職務、工資、文化以及政治前途等各方面,都比自己強多了。婚姻從外表看是愛情的結合,其實功利因素遠遠超過感情成分。
趙勇海對即將成為妻子的楊婉芳說:「你說想要點什麼吧?」
楊婉芳說:「我啥也不要,就是要你把我妹妹也調上來。我住在公社,不能讓她一人臉朝黃土背朝天過一輩子。」趙勇海很感動:難得一個女人不貪圖財禮。
「行呀。不過要等些時候。」
楊婉芳急了:「我的要求就這一條,你還要拖著。趙副書記,你是辦不成,還是不願意辦呀?」
趙勇海拍著她的肩膀:「不是辦不成,也不是不願意辦,是還沒想出調她的好辦法。你是公社的婦聯幹部,現在又要調小姨子,影響多不好,說起來也難聽。我答應你,但是得找個正當理由。」經他一說,楊婉芳也覺得有道理,不再嘮叨。趙勇海沒見過楊芬芳,便要求到楊家看看。
楊婉芳笑了:「我家有啥看頭?兩間瓦房,是父母留下來的。一個比我小十歲的妹妹,幾分自留地由她收拾,好賴不管。」說到妹妹總是一人在家,眼圈竟紅了。
「那我更得去看了。」
這是一個星期日,天氣大好,一個新鮮幽麗的清晨,陽光透過雲層均勻地灑下來,把大地抹上一層金黃。遠處的山巒,一副似醒未醒的惺忪樣子。路邊的野花,頂著露珠開了。小溪的水,清得一眼看到底。他們是騎自行車去的。石壁大隊,從前叫石壁村,它緊挨著石壁公社。二人一路說笑,不知不覺到了。房子是泥牆瓦頂,兩間一明一暗。外間最顯眼的家具是一張八仙桌,桌上,噴著花卉圖案的搪瓷盤子裡放著幾個茶杯,一塵不染。牆上掛著一個小小的月分牌和一面大大的鏡子,鏡面擦拭的光潔如新。一張兩屜桌,上面碼著不多的書籍,手工編織的白色繡花巾搭在一個小收音機上。
趙勇海摸著光滑的八仙桌說:「有些年頭了吧?」
楊婉芳點點頭:「這是父母的遺物。我們楊家的成分是中農。老人走的時候,給我倆一人一對銀鐲子,其他就沒啥東西了。那陣大煉鋼鐵,要不是我和芬芳死命拖住煮飯的鐵鍋,大概就餓死了。」
太陽從敞開的木門直射進來,趙勇海看到屋子外面,左右架著兩個籬笆,一邊掛滿絲瓜,豆莢,一邊開滿喇叭花。所有的綠色沐浴在陽光下,給人一種恬靜,柔和的感覺。他想,只有女人住在這裡,才如此清雅。正在屋檐下徘徊,一聲「姐!」讓他抬起了頭。
迎面而來的是一個比楊婉芳高大得多,豐滿得多,也漂亮得多的年輕姑娘。
楊婉芳拉著妹妹的手,說:「這就是趙勇海。」
楊芬芳叫了聲:「趙書記。」
「別叫書記,叫我趙哥或姐夫,都好。」
都坐下來了,趙勇海漸漸琢磨出她與楊婉芳的區別。姐妹的眼睛形狀差別不大,可眼神極為不同:姐姐的像潭水,妹妹的似海洋;一個是黑眼珠,一個怎麼會是栗色呢?兩人頭髮的顏色不同:姐姐是黑色,妹妹的是黃褐色。兩姊妹的嘴唇也很不一樣:楊芬芳的嘴要比楊婉芳大多了,雙唇相交的線條呈現出一條弧線。他暗想—楊芬芳若生氣地撅嘴,一定很好看。趙海勇不知道,這樣的雙唇不是為了說話,是為了顫動,天生最合適接吻。誰做她的情人,就是誰的福分。再,就是她的鼻梁又直又高,把整張臉龐撐得飽滿而生動。
原來,楊婉芳準備在家裡做點湯麵就算了。可趙勇海覺得,第一次見到小姨子就吃一碗麵,於禮不周。他提出:「我要請芬芳去公社食堂吃米飯炒菜。」
楊婉芳自是高興,未婚夫能對妹妹有個好印象,也就為以後的調動打下了底子。「三人怎麼回去?自行車不夠啊?」她有些犯難。
楊芬芳聽說去公社吃好的,高興極了。說到自行車,她馬上說:「姐,這好辦,我去借一輛。」
「跟誰借?」
「何家,找無極呀。」
「哦,那好,快去。」
何家兒子太出眾了,楊婉芳怎能忘記?從小的鄰居,兩姐妹和他一起打打鬧鬧,還先後在同一個小學讀書。辮子散了,背過身叫他給重新編起來,他編的比自己梳得還好,辮花整齊密實。何無極是獨子,身體壯碩,濃眉大眼,禮貌謙恭。要不是被「地主子女」的階級成分的大帽子壓著,小夥子早就被好人家搶走了。何無極本事多了:下地一把手,木工,瓦工也在行,還會踩縫紉機。很多人家也愛找他幫忙,砌個灶臺,給小孩縫個褲衩,他都攬下來。白天,忙裡忙外,只有晚上才是他一個人的世界。他感到孤獨,男人的孤獨。自己並非不想找個對象,但是想到家庭成分,就不急了。俗話說:「醜妻薄地家中寶。」何無極偏偏不信,一心盤算能遇上個好看的、也不在乎階級出身的女孩子。他寧願苦等,等候上蒼的垂憐。
何家與楊家是老鄰居了。所謂鄰居,是指兩家同在一面坡,相隔不過幾十米,有條蜿蜒小路相通。楊芬芳年幼,不諳風情,對異性基本是麻木的。因為年齡的接近,又知他能幹,就常喊他幹這幹那:「無極,給我磨磨菜刀吧,連青菜都切不動了。」他大步流星地過來,拿過菜刀就走。過不了一會兒,一把鋒利的菜刀就遞到楊芬芳手上。
楊芬芳咧著嘴笑:「謝謝了。」
「不用謝。我問你,等你出嫁了,還要我給你磨刀嗎?」
「我不嫁,就要你磨吔。」
「你要不嫁,那我就把你的自留地包了。」說罷,兩人相視大笑,誰也沒往心裡去。
何無極幹活兒,決不讓楊芬芳插手。她也不客氣,站在一邊看,連水都不倒一杯。也不知為啥,兩人處得那麼逍遙自在,似一家人,像親兄妹。
此時,楊芬芳氣喘吁吁地跟他借那輛破自行車,何無極一口答應。車推了出來,他說:「這車是別人不要了,我撿過來用破舊零件攢的。我騎沒問題,你騎要當心了。」
「沒關係,還有趙勇海呢。出了毛病,他會修理。」
「他會修車?未必吧。」何無極似乎有點生氣,又突然追問:「你這是要去哪兒?」
「去公社,姐姐和他要請我吃飯。」
「他們為什麼請你吃飯?」
「這不是姐夫第一次見小姨子嘛。」
「今晚你回來嗎?」話從嘴裡脫口而出,自己也沒想到居然會問這樣的問題。
「我也不知道。」
「要是太晚了,一個人走夜路,你就別回來了。」
「哦。」楊芬芳推車離去,忽然想起家裡的幾隻小雞,掉頭就喊:「無極,我不在,替我照管一下小雞啊。」沒想到何無極依舊站在那裡,一步未挪。不覺心頭一熱,臉猛地紅了。
第二節
當趙勇海在縣城人武部(人民武裝部)辦公室結識了回家探親的現役軍人、連長劉慶生的時候,他的心活泛起來。
認識的場合極其偶然,他到縣裡開年終總結幹部大會。這樣的會,作為管著公社帳本的人是必須參加的。他不愛抽菸,可會場裡總是煙霧繚繞,避也避不開。到了會議午間休息的時候,他就去人武部辦公室坐坐,因為人武部部長老金不抽菸。他的兒子小金在徐州服兵役,每年要給父親寄一大包綠茶。趙勇海最喜喝茶。就這麼點小緣故,趙勇海到縣城開會,有了空閒,就到老金辦公室小憩,呷一口茶,雙眼微闔,全身舒坦了。
這次進門,見著一陌生人。經介紹,知道這叫劉慶生的軍官是小金的上級,也是本地人。很早參軍了,從副班長開始起步,班長,副排長,排長,一步一步做到了連長。劉連長個頭不高,四方臉,身材偏瘦,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雙狹長的細眼睛,目光一閃一閃的。老金說了,能當上連長的人一定是政治覺悟高,熱愛學習;生活上一定是為人正派,艱苦樸素。至於缺點嘛,老金說,就是多少有些刻板。
劉慶生這次返鄉度假,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想談個對象。他很現實,到了這個年齡,也有了這個能力,婚姻大事自然就提上日程,這符合唯物論,也符合最早原始人類的生存需要。剛提出打算在這裡解決婚姻問題,趙勇海一下子就想到了楊芬芳。一番交談,他感到劉連長還真的刻板,說話無趣。轉而又想,不能怪他,興許是長期待在部隊的結果。一旦劉慶生懂了女人,人自會活潑起來。而一旦婚事定下,作為現役軍官家屬,把楊芬芳調到公社,別人再有意見,也無話可講。趙勇海斷定:這事若說給老婆聽,楊婉芳肯定滿意。那麼楊芬芳呢,她會答應嗎?會的—趙勇海自問自答,因為擇偶是極其現實的事,看家庭出身,看階級成分,看本人政治面目,看工作單位,再看工資多少。以上條件於劉慶生而言,是條條夠格。那麼,劉連長會滿意楊芬芳嗎?趙勇海很有把握:小姨子不必收拾打扮,就是從泥塘裡拔腿出來,往田埂一「戳」,那個清麗的樣子,也得叫姓劉的好一陣耳熱心跳。
就這樣,趙勇海在返回公社的路上,豪情滿懷。也不知為什麼,快到石壁公社的時候,好心情突然沒了。畢竟是讀了幾本書的,知道愛情兩個字。自己把兩個背景不同、性格各異的一對男女用介紹的方式拉在一起,把楊芬芳的幸福和未來都撮合了進去,是否有些危險呢?她與那姓劉的會相愛嗎?日子幸福嗎?決定結婚是很快的,而愛情要過很久,才會明白。在交換各自生命過程中,要是楊芬芳後悔了,自己該承擔什麼責任?想到這些,趙勇海似乎不敢往下想了。回到公社,已是正午。人在陰涼下打著呵欠,連雞狗都無精打采,一個婦女一手抱著熟睡的孩子,一手驅趕惱人的蒼蠅。
楊婉芳還在廚房做飯的時候,趙勇海就把劉慶生的事情說了。
妻子樂了,用鍋鏟敲打著鍋沿兒:「你真有兩下子,神不知鬼不覺地把芬芳的事辦妥了!你等著,我到小店買點滷菜。咱倆得先慶賀一下。」
「算了,兩人還沒見面,別高興得太早了。」
誰知劉慶生挺急,第二天就帶著用全國糧票買的點心,用高價買的兩斤豬肉和從老金那裡抓來的茶葉,一溜煙兒跑到石壁公社來了。
他與趙勇海夫婦見面,又是鞠躬,又是敬禮。開門見山地說:「幫人幫到底嘛!我這次探親無論如何也要我和楊芬芳見上一面。」特別是看到楊婉芳長相還算清秀的時候,決心就鐵定了:「要不答應,我就在你們的公社住下,不走了。」
趙勇海帶著笑,說:「等明年再安排見面,也不遲呀。」
老劉面帶苦相,朝天伸出三根手指:「一等就是一年,我可過了三十五,別飽漢不知餓漢飢啊。」趙勇海與楊婉芬互相交換了一個眼神。老劉看出了希望,忙說:「哪怕讓我只看一眼,我保證,看完就走!」
一身戎裝,滿嘴軟話,倒讓趙勇海夫婦多少有些為難。為難處就在於事先一點都沒跟楊芬芳通個氣兒。太突兀了,人家還是個不到二十歲的大姑娘。終究拗不過這位軍官,商量一陣後,答應了。定的見面地點在縣城的一家飯館。而時間則要看楊芬芳的態度了。
這時,爽快的楊婉芳也直言不諱了:「看一眼,也是相親。對女孩兒家來說,可是關係到後半輩的大事!可我們對你的情況,真的都不很了解,你不能甜言蜜語騙我妹妹!就算婚事成了,你連長可是風光在外,而我妹妹就要苦守寒窯。有句話你知道嗎?叫『鳳凰落地不如雞』。」話一出口,讓劉慶生一時無法應對,細長的眼睛閃了好半天。
趙勇海出面打了圓場:「你先回城裡,等我們的消息。時間定下,我就打電話到人武部,讓老金轉告你。」事情說妥,夫婦把劉連長送出了公社大院。
他倆站在公社大門的石階上,望著眼前未熟的莊稼。有風從田野吹來,穿過不遠的一片竹林,發出簌簌的響聲。
楊婉芳用徵詢又謹慎的口氣,向妹妹介紹了劉慶生以及要求見面的事情。沒想到楊芬芳大笑,把個臉朝向天空,說:「好呀,我好久好久沒進城了,好久好久沒吃席了。真想啊!」
姐姐搖著妹妹的肩膀,說:「你的話是真是假呀?人家可是相親。」
楊芬芳說:「我不開玩笑。見面就見面,不就是想看我長得好不好嗎?至於願不願嘛,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這個態度,令楊婉芳很有些吃驚。平素,村裡的人都說,楊家姊妹搭配得多好,一個潑辣能幹,一個溫和守家。情況還真是這樣,楊芬芳一年下來的工分,糊口都不夠,大半要靠姐姐的幫補。但她心靈手巧,能把個家擺弄得花花綠綠,鮮亮整潔。沒見她怎麼學幹活,一旦幹起來,也是有模有樣的。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