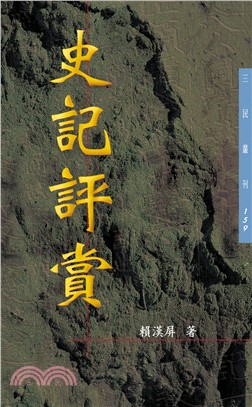商品簡介
把自己託給風,一個人行旅在他方,獨坐,寸走,看盡眾生與時光。
「別忘了出發時刻已到,風已吹起,你眺望著遠方。」
而我,終於啟程了;
旅途中記錄一次次的邂逅,也掇拾一片片的自己。
世界公民島計畫主持 呂學海
作家 王盛弘、李時雍
──飛揚推薦──
「必須是人的故事才好看」,馮平說。
柏林的愛人同志雁茲與烏法、西雅圖狂癲旅伴K、巴黎憂鬱的音樂創作人歐嘿利安、在布魯塞爾奮力繪畫渴望成名的魯本……旅行中在這裡所看的人,和在那裡所遇的人,除了語言風俗不同外,還有什麼不一樣?旅行的意義是什麼?──旅行無非或者莫非,就是在走走看看時,與一個又一個人,瞬間凝結彼此的時空?
從克里夫蘭的湖木公寓出發,行過阿姆斯特丹、伊斯坦堡,停留布達佩斯、柏林,駐足巴塞隆納、里斯本……馮平一個人揹起行囊,飛越千重山,來到一座城市;橫越萬里洋,走進一條街道,與旅途中相遇、相識、相惜的人們,學一句話,吃一頓飯,交一場朋友,攝一張相片。是那城、那街、那些人,豐富了馮平行旅的內涵,也加深了遠足的意義:原來獨自飛揚的自己,流寓他鄉,愁的是一個人,想的也是一個人,在漠漠天涯裡,更覺隻身孤寂,卻也在旅行當中,拾起一片片的自己。
他是風中的一片飛揚雪花,記住異地的氣味、旅者的神色,流動與遠行的痕跡;他用雙腳記憶城市,用相機捕捉迎面而來的人,將彼此錯開的零點一秒的邂逅凝結在瞬間;用心靈體會每一隻漂泊的飛鳥,每一雙駐足街角的眼睛。在未來到的日子裡,馮平寫在風中,卻也不禁嘆問,流蕩天地間獨身的自己:「即或一座座城巿已走進心圖裡,還是要問:怎樣才算認識一座城巿?怎樣才能屬於一座故鄉」
■ 本書特色
卷一「人在世界角落」,以十三篇散文書寫十三座城市,從阿姆斯特丹到台北,遇見的人走過的街,都寫在筆下若即又若離。
卷二「人在伊比利半島」,用日記隨筆,紀錄巴塞隆納與里斯本的每一日,驚險遇劫、墓地神思、街弄散走,彷彿臨場卻又疏離。
卷三「人在伊利湖畔」,寫克里夫蘭居住的湖木公寓,想鄰居、憶街景,此處伴他度過八、九個冬天,然而,何處才是他真正的家?
附錄「人在瞬間」,「期待一座城市」、「說照片」,像是長長旅行的返回後,一頁一頁翻過照片,回味當時的人物與景色,淡雅、流暢,安靜地貫穿與濃縮過去未來的時空。
作者簡介
馮平
生於三重埔,長於台北市,飄泊於新大陸。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畢,現居美國任出版社主編。心懷台灣,身在世界中。贊同《世界公民島》計劃,但願是一隻文學鳥,鳴啼於人的生命處境,自由地飛。作品獲文學獎若干。著有散文集《我的肩上是風》(有鹿文化)。
名人/編輯推薦
名人推薦
「寫在風中,寫完就被風吹掉。荒唐時代,有人依然相信文學、眷戀文字,像蟬一樣堅持在夏天的焚風中厲聲寫作。馮平像是一隻蟬其實已在地底下活過了七年,現在又回到微溼的空氣中,用這本書叫喚另一隻他以為還存在的蟬。」──呂學海
「馮平的旅遊文章好看,正因他喀擦一聲,照相機般捕捉住了一個個與他擦身而過的男人女人,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有交會的瞬間,唇齒之間如有話將啟、眼神裡似有熱量交流,充滿暗示與誘惑,任他進行想像與召喚。」──王盛弘
「三十歲到四十的生命和書寫,因轉折,被你歸結為『風』,但我始終記憶的,卻是『雪』。雪跡。雪路。雪封北國。那晚深陷在深可及膝的雪泥中的車輪,引擎急掣令前蓋冒起了如霧白煙,轍痕如淚,異鄉寓居的日子你寫下『我單身一人沒有家仍一心想回家』……」──李時雍
【推薦序】
風中少年
◎呂學海
寫在風中,寫完就被風吹掉。荒唐時代,有人依然相信文學、眷戀文字,像蟬一樣堅持在夏天的焚風中厲聲寫作。寫給誰看呢?馮平離開台灣的十五年來,台灣早已不是當年的台灣了,可是他的記憶還是,情懷還是,想念和寫作的文風也還是。他像是一隻蟬其實已在地底下活過了七年,現在又回到微溼的空氣中,用這本書叫喚另一隻他以為還存在的蟬。
「有人還依然相信文學、眷戀文字嗎?」知了,難了。在經歷過幾番政權更迭、多年媒體亂國之後,群眾庸俗造成知識分子性格懦弱,菁英怠惰造就人民大眾心靈萎縮。二十一世紀之前的大學畢業生還講得出幾個自己尊敬的名字,甚至認為自己廣義說來還是個知識分子,這十五年來台灣最大的改變是這樣的階層沒了,讀者沒了。
文學讀者是一個有情有義世界的最終守護者,幫助人間度過亂世而不墜不毀。杜甫、蘇東坡、李清照的讀者曾如此;吳濁流、鍾肇政、李喬的讀者亦如此,而那些在課堂上推薦他們、熱心幫著學生劃撥課外書籍的國文老師們,則是人生價值的螢火。你們要繼續發出溫度啊!不管中外統獨,只管用暗暗長夜中曾經感動你的作品感動你的學生。
價值混亂而文學、史學、哲學缺席的世界叫做:亂世。一整代的讀者消失,原因並不複雜,父母、學校、電子裝置、網路社群都不讓孩子孤獨,所有在孤獨中才能產生的品味和深思,自然就慢慢絕跡了。一整代的作者消失比較可怕,他們都已是曾經孤獨的靈魂,如今卻因為缺乏共鳴,沒有人想要扛起一個時代,沒有人願意繼續發出蟬聲。
遠走他鄉的海外遊子如馮平,也許因為美麗而錯誤的記憶,反而臨風高歌了。他在風中,以為夏天滿山滿谷都是蟬,台灣還是昔日台灣。台灣有幾個永遠的風中少年,史作檉、林懷民、王文興、喻肇青……無論世界如何敗壞,他們都在他們該在的位置,永遠是少年。馮平也許是他這一代風中少年中──最執著不只要喚回一隻蟬,而是要喚回一季夏的。
【推薦序】
琥珀般凝結血色青春
◎王盛弘
在一則題為「哈曼」(Hammam,土耳其澡堂)的小品裡,馮平先略述人文沿革,次敘洗浴程序,幾筆飛白之後便引出了「哈曼,最開放的社交所」,圖窮匕首見,他真正想要記錄的是,發生於這個最開放的社交場所的一段,旅途上的邂逅。
有過一些旅遊經驗、寫過一些旅遊文字,我也就有了這樣的體會:「旅人與他所造訪的城市,彷彿隔著一扇瀏亮玻璃窗,看似穿透這扇窗子見識穎新的世界,有了前所未有的眼光;而其實,窗外的光影晃動重疊上投射於窗玻璃的臉孔,看見的是以客觀世界為布景的主觀映像。旅遊文學所捕捉的,無非也就是這個一轉開身即不復存在的片刻。」(注)
因此,同樣寫哈曼,建築出身的李歐納‧科仁(Leonard Koren)著眼於它的結構、設備、機能,最終聚焦於光線與聲音,聲光交織,惚兮恍兮,渲染得澡堂裡的氛圍似醉似醒如幻如真;而費爾南多‧卡倫科(Fernando Caruncho),西班牙知名園藝景觀設計師,解讀加泰隆尼亞一座阿拉伯浴場,則說這是一座石頭化的花園;石砌的八角形水井,井欄矗立八根圓柱,頂端浮雕棕櫚葉片,一根根圓柱便化身為一棵棵棕櫚樹,由它們所撐起的拱頂則宛如森林裡繁密的枝葉交纏,這座阿拉伯浴場是卡倫科的靈感來源,對他灌注以驚人的能量。
至於馮平,無視於哈曼的物理特質,不細數它在時間長河裡的變身,也不打算為如何洗一場正統的土耳其浴做導覽;馮平寫哈曼,為的是一個承諾:在一座小哈曼裡,他偶遇八名翹課高中生,浴巾也遮不住渾身流淌的青春與風流,他與他們「由陌生,到交談,到邊搓背、邊嬉鬧,度過一個歡然的午後時光」。臨別,拍了合照,少年們問,可以放上Facebook嗎?馮平沒有帳號,但他是作家呢,他可以寫成文章發表於報端。哇,這群少年一聽,興奮地抱在一塊兒,「覺得自己像電影明星一樣了」。
也不只為了承諾而寫,多半更是,當他記下這個故事,他相信,他便也琥珀般凝結住少年們的歡聲笑語。許多眷顧,許多留戀,許多緬懷,許多徘徊不肯離去,難捨也不願捨,讀馮平的旅遊文章(讀者與他所閱讀的文本也隔著一扇瀏亮玻璃窗),他所置身的街衢商鋪山巒湖泊,人文風光自然造化,都像為了建構一段段不期然而遇、旋即道別,偶然投影於波心並激起漣漪久久無法平復的舞臺。
旅遊已是全民運動了吧,但每個人為了不同的理由而出發,馮平說他,「旅行無非或者莫非,就是在走走看看時的飲食男女而已」──在阿姆斯特丹,旅館裡他遇見一名美人,有生命初熟的飽滿,晶瑩中帶一分爽朗、一股暗香,兩人似有情意流動;咖啡館裡,青年服務生收下小費後,答以一個微笑一個眨眼,讓他又驚又喜。在伊斯坦堡,同樣是咖啡館,撞見兩名少年忘情接吻,一方尷尬、一方臉紅。在柏林,他又為一名刺青少年所吸引,道別了而仍掛念著......每一段旅程每一座城市,甚至每個角落,都有讓馮平「慾望不平靜」的偶遇,與發生於腦內小劇場的「豔遇」。
讀著讀著我就笑了。我認識馮平,多少年了,他始終善良,不夠世故不夠老成(儘管他的口音像我國中時教公民與道德的外省籍老師),一顆心還像少年般柔軟而澄淨;因為柔軟,所以微如羽毛也落有痕跡,因為澄淨,所以敏銳感映天光雲影的變化。
馮平的旅遊文章好看,正因他喀擦一聲,照相機般捕捉住了一個個與他擦身而過的男人女人,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有交會的瞬間,唇齒之間如有話將啟、眼神裡似有熱量交流,充滿暗示與誘惑,任他進行想像與召喚。正如他自己說的,「必須是人的故事才好看」,何況他記下的,又都是好看的人,血色的青春。
注:引自《十三座城市》後記〈像我這樣一名觀光客〉。
【推薦序】
路標
◎李時雍
我在西一一七街和水邊道的交界迷了路。遍尋不著一幢名之為「湖木公寓」的標的建築。指尖且試著拖曳屏幕影像,縮小一點、或再放大一點。如果全景,陸路北緣,便浮現一片比想像中廣闊的伊利湖藍;唯色塊延伸,令人難以辨別湖底深淺,風起漣漪或整個午後的水文浪靜,而沿著湖畔走,大片綠色林地就是湖木公園吧。如果深入街道,彷彿可見有貓繾綣、有一對年輕戀人行過,甚或一條道路的哀傷,但其實,僅只一些橫縱抽象的線條。
說是迷路,不過是在搜尋的框格裡,鍵入你所身在的城市,克里夫蘭。手邊一側有遠方間續寄來的消息,終令我不禁好奇地將陌生的地名,逐一鍵入虛擬的地圖集裡索詢。迷惑的模樣,是否一如曾經一篇〈圖解〉(注)的你,記著了收到那人寄至手中的摺疊圖紙,攤開,是親手描繪的舊;線索是長路、是書報攤、是公車站牌、是一本本隨身的詩集,或是有人相伴走過的一段,「解開地圖,猶如解開一場生命轉折的圖像」,你說,面對靜默的說服和質問,「而我,只能把這張地圖解釋一遍。」
擱在桌案上的《我的肩上是風》和《寫在風中》於我竟亦如舊事畫像,而我,只能循你的地圖解釋一遍。
三十歲到四十歲的生命和書寫,因轉折,被你歸結為「風」,但我始終記憶的,卻是「雪」。雪跡。雪路。雪封北國。那晚深陷在深可及膝的雪泥中的車輪,引擎急掣令前蓋冒起了如霧白煙,轍痕如淚,異鄉寓居的日子,日常聚會散後困身的夜歸路上,你寫下「我單身一人沒有家仍一心想回家」一句,成為我遙想你遷徙北國蒙特婁、克里夫蘭......唯一的身影印象。
那也是最初收到你的來信時。時差夜與日的午後,尋常上班日,一封信,安靜躺在收信匣中,附件一篇短文,〈雪中回家〉,字句靜謐如人,就此開啟往後三、 四年,往來斷續的通信。
今春雪融,你起筆「克里夫蘭故事」,寫有時稱為家(home)、有時稱為地方(place)、有時公寓(apartment)的居所,寫對門新搬來的鄰居〈彩虹男女〉、寫所屬城市的NBA隊伍、寫一一七街哀傷亡命的小松鼠,當春來、夏去、〈親愛伴侶〉常伴身邊的貓兒阿妹戍守家屋,而終於二○一四年九月,一人一貓搬離了寓居近九年的〈再見!湖木公寓〉,集成我手裡這本散文集的壓軸卷「人在伊利湖畔」。我逐一將隱現的地名鍵入地圖,對照文字故事,拼湊著那城那些人,抽象的線條在紙頁中遂建築起來,有了立體的地勢,方形的幾何可以俯仰,就近看窗格的細緻雕飾,電梯,可以直上十樓,在一扇門前停下,扣門、撳鈴。
「馮平,在嗎?」喵語回聲細細,代你回答是乖巧阿妹。如此行走間,我漸也知道,原來,湖木公寓不叫湖木公寓,而叫水邊塔。原來,你以文字為譯,譯寫了屬於自己的水邊道、伊利湖;以文字為記,標記了流浪的足跡,是故在還沒有名字的新址,你寫給我:「新住所該叫什麼,我不知道,也說不上來。總之不是家,不是公寓,不是宿舍。這問題沒人能替我回答;他們跟我一樣,找不到完美稱意的表達方式。」
原來不是迷路,而是未有名字、找不到心意的表達。令我想起最初的圖輿,如何註記悲傷喜樂的行經,解釋雪深和風聲,獵獵迴旋如筆跡,你的每個字,寫在風中飄零,盡似哲人思索的路標;我用心辨識,尋跡而至,一個個未曾到過的舊址。
注:出自馮平散文集《我的肩上是風》(二○一四)。
序
代序
必須是人的故事才好看。
離台前,呂董(注)引《今生今世》卷頭語:「桃花難畫,因要畫得它靜。」說我的人是飛揚,難處也是飛揚。飛揚的人不懂得犧牲,還不能承擔。飛揚的人眷戀自己的浪漫,恣意的翱翔;風之子。
嫁秋風;曆書亦言:立秋,涼風至,宜出行。
千禧年出行,這一去,我連人都移出去了,落腳他鄉。新世界展開在我眼前,我真覺得天空高遠,行者無疆。於是一日,我人在這裡;又一日,我人在那裡。多年來,職暇行旅,或者伴隨工作的短居,都使我胸壑清朗,暢意快樂。但另一面,我也更加思人,更覺隻身寂寞。
原來飛揚的另一面,是飄零,是孤寂。如楓橋夜泊。常想:江楓漁火下,詩人愁什麼?夜半還睡不著,他想什麼?答案或許是:流寓他鄉,他愁的是一個人,想的也是一個人。終究是人。
什麼樣的人喜歡看人?
旅途中發現,沒有比人更矛盾的了。人跟人貼得近了,想獨立出去;離得遠了,想走入市囂。人是那麼自我,卻孤孤單單;人是那麼群集,卻爭爭鬧鬧。人哪,總是絕對的一個人,又是相對的一個人。然而離開了人,我不知道該寫什麼。
我飛越千重山,來到一座城市;我橫越萬里洋,走進一條街道;是那城那街那些人,豐富了我行旅的內涵,也加深了我遠足的意義。與他們邂逅,是佛說的前世五百次回眸才換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過;與他們交會,是徐志摩說的一片雲在波心裡的偶然。更不必說與他們學一句 話,吃一頓飯,交一場朋友。
這裡記錄的是多年行旅所履所見,異域所遇所感,以及他鄉生活隨筆。想起《山野掇拾》作者孫福熙寫的一句話:「我本想盡量掇拾山野風味的,不知不覺的掇拾了許多掇拾者自己。」原來說來說去,是說到了自己;在世界公民的寰圖上拾掇了自己。但願這掇拾的,會是一個可愛的、可貴的自己。
注:呂董,社會大學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現任世界公民文化協會理事長。
目次
【推薦序】風中少年◎呂學海
【推薦序】琥珀般血色凝結青春◎王盛弘
【推薦序】路標◎李時雍
代序
卷一:人在世界角落
「巴黎,我已經造訪她三次了,對這城巿還是既熟悉又陌生。怎樣才算認識一座城巿?怎樣才能屬於一座故鄉以外的城巿?」
男歡女愛,阿姆斯特丹
落日之後,北京
伊斯坦堡素描
伊斯坦堡補遺
艾瑪,安納托利亞高原
走向光,布達佩斯
布拉格之春
柏林八帖
再見巴黎
成名之前,布魯塞爾
K,西雅圖
京都手記
去年夏天,台北
卷二:人在伊比利半島
「十月十五日,來此第十二日,終於感受除卻却目的的步行,實在是一身輕鬆自在。沒有高第,沒有多梅內切,沒有推薦餐廳,改了步調,轉悠悠,悠悠轉,逍遙一閒人也。」
巴塞隆納日記
行過里斯本
卷三:人在伊利湖畔
「我在哪裡呢?當這問題從地理位置,遊走到人生境況而出現模稜兩可,甚至通通被拒絕時,我總是盡力忍受這個尷尬......隨後浮出一種空洞感,晃悠著像踩在雲上水上。」
唐家小館
幸福花茶
呷飯配小丸子
哦!咖啡
給貓洗澡
與蒂兒和解
過派翠克的家
耶穌不見了
湖木公寓
附錄:人在瞬間
「他走過來,我走過去,在巴黎的街巷中。瞬間,我舉起相機;瞬間,他迎向鏡頭;瞬間,那即將彼此錯開的零點一秒的邂逅凝結在這裡。」
期待一座城巿
說照片
書摘/試閱
【內文節選一】
伊斯坦堡素描
貓
在伊斯坦堡,你要遇見貓。貓無所不在。公園,停車場,清真寺,大市集,傳統市場,濱海橋邊,露天咖啡座,王宮走廊,博物館門口,斷牆殘壁一角,垃圾堆積處,街頭巷尾房頂上、車盤下......,牠們總在那裡。
像攝貓達人一樣在這城市遊走。一路走,一路攝相,蹲著攝,坐著攝,趴著攝,如此舉止竟也引起本地人和觀光客的注目。常有人幫我吸引貓的目光,好叫他們可以看我的鏡頭,甚至有小孩把貓抓立起來,直接送到我的鏡頭前。
老人指著貓說:「牠們世世代代都在這裡。」又說:「是啊,幾千年來,牠們一直都在這裡。」
月光下,一隻貓跳到我窗前說:「給我一片你晚餐剩下的火腿,我就告訴你那一夜鄂圖曼王如何破水攻城的事。」我正要給牠火腿的時候,又一隻貓說:「不!你把火腿給我,我就告訴你何處是帕慕克常去寫作的咖啡館。」正當我猶豫不決時,又一隻貓跳上來說:「火腿給我吧!我告訴你福樓拜遺留的一分手稿放在哪裡。」不想,頃刻又來第四隻貓,第五隻貓......。牠們七嘴八舌講個不停,爭個不停,最後把太陽都吵醒了。
清真寺
在伊斯坦堡,你要看見清真寺。當你還沒有看見的時候,你就先聽見了。夜色未褪盡沉重幕紗前,清真寺的叫拜塔已經忠實地召喚阿拉的子民們起來禱告,祭司透過擴音器向全城各個角落唸誦經文,這是不容懷疑的神聖時刻,千年如一日的宗教生活。
大市集不遠處有蘇里曼尼耶清真寺(Süleymaniye Camii),由鄂圖曼帝國最偉大建築師錫南所建。此寺是王朝所建兩座最雄偉建築之一。寺旁墓園埋葬蘇里曼王家族。首次入清真寺,拱圓形天頂,一頂接一頂,整片紅絨花紋地毯,巨型圓盤吊燈,牆上惟窗櫺、惟書法經文,無偶像。拜偶像,乃屬靈淫亂。我愛清真寺。教堂太作工,寺廟太仄迫,清真寺潔敞,只給你崇高穹頂,給你神的啟示,給你一片天!
但伊城最經典的天際線,卻是拜占庭所建蘇菲亞教堂(Hagia Sophia)以巨碩圓頂領著四座伊斯蘭叫拜塔臨視山居水灣。偽清真寺。然一座教堂,四座叫拜塔,丘巒群居,峽灣水波,著實是一幅時空交合的絕美剪影。
船行在水上,東正教徒說:「看哪,我們的蘇菲亞!」回教徒說:「聽哪,叫拜塔又再召喚我們!」天地不老,只是漸漸捲去。
哈曼
在伊斯坦堡,你會走進哈曼(Hammam)。哈曼就是澡堂,土耳其浴的所在。澡堂歷史已久,自東羅馬帝國即盛行。土耳其澡堂有的已經用了五百年,有的甚至出自大師手筆,如錫南(Sinan)所建的Çemberlita Hamamı,藻井,天窗,大理石床,汲水盆臺,大廳欄杆等等,簡潔或繁飾,無一不是藝術氣魄。
先臥在大理石床放鬆心情,待蒸氣使毛細孔全開,便由師傅抹上全身泡沫,手套搓洗,然後從頭按摩到腳。沐畢,身心舒暢了,可至房間休憩,或在大廳喝茶吸菸聊天。哈曼,最開放的社交所。
一間簡樸小哈曼裡,我遇見八個蹺課高中生。紅白格子麻浴巾遮住他們下身,遮不住他們身上盎然無盡的青春。風流少年。我們由陌生,到交談,到邊搓背、邊嬉鬧,度過一個歡然的午後時光。
留下email時,他們問我:「可以把相片放在Facebook上嗎?」
我說:「我沒有Facebook帳戶,但我可以投稿到報紙上。」
「真的?」
「嗯。」
他們快樂地抱在一起,覺得自己像電影明星一樣了。
獨立大道
在伊斯坦堡,你會來到獨立大道。一四五三年,東羅馬帝國亡,鄂圖曼土耳其建朝;一九二三年,一次大戰結束,民族解放領袖凱末爾,自英、法、俄的半殖民統治中,宣布獨立,建成土耳其共和國。
獨立大道長約三公里,行人徒步區,只走輕軌叮噹車,兩旁餐廳、銀行、百貨行、名牌衣飾店、咖啡館、禮品店、書局、音樂行、戲院、藝廊......。資本主義商業大街。人稱這裡如巴黎香榭大道或紐約第五大道,我更以為像台北東區,因大道橫生許多小道,小道又接許多小巷,巷道中小鋪小店、酒吧市場,布爾喬亞的歡快世景,墮落天使的時髦樂園。
人多得看不完;眾生相,好男好女。徘徊多時,我竟無跟一人交談,也無一人對我感興趣。坐進咖啡館,點了一杯茶,拿起筆記本,一面寫文章,一面觀看客人。來者清一色男。室內菸霧繚繞。上樓解手,廊外撞見兩少年忘情接吻,我尷尬說抱歉,他們臉紅喜笑。
一日無語,是想著他們唇上的溫暖嗎?
加拉太橋
在伊斯坦堡,你會造訪加拉太橋。若伊城是一個圓,切開左右兩邊的中線即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左半邊再上下對切的中線則為金角灣(Golden Horn)。金角灣為內海灣,隔開伊城歐洲區為上新城、下舊城。從舊城到新城要過橋,那座最重要、最有名、最便利的橋,就是加拉太橋(Galata Bridge)。
橋分兩層,上層走電車、汽車、行人,橋欄邊日夜有人下竿垂釣;下層兩側一律酒吧餐廳,間雜一兩家魚具店。立在橋上,能遙望海峽對岸的亞洲,更能看見新城山丘上的加拉太塔、歐風新式建築,也能看見舊城山丘上櫛比鱗次的圓頂尖塔,以及近在眼前的葉尼清真寺和香料市場。清風徐來,水光接天,伊斯坦堡收攏在一座橋上。
橋下層的商家均設戶外座椅,有酒吧擺置塑料沙發,外型如一隻肥大手掌,任人隨意坐臥。橋下離水極近,行坐在此,如行坐在江心上,凌波微步,或泛舟遊於茫然。尤其是夏夜,和風連翩,燈火相映輝煌,想像三五好友相聚,在此把酒言歡,兼歎千古名城,或誦明月之詩,或歌窈窕之章,何其人間情趣!
可惜,我只是一個不結伴的旅人。我是我一個人的伴侶。
博斯普魯斯海峽
在伊斯坦堡,你會遊覽博斯普魯斯海峽。起點在舊城Eminonu碼頭,加拉太橋邊。十點三十五分出發,下午四點返回,一天一班(夏季據說有兩班,另一班六點回)。海峽上接黑海,下連馬爾馬拉海(Sea of Marmara)和地中海,全長三○‧四公里,最寬處三‧六公里,最窄處七○八公尺,於此架有一長虹,世界第四大吊橋,橫跨歐亞兩洲。
船上點一杯紅茶,沿岸所見:村莊、漁港、餐廳、皇宮、民宅、清真寺、古堡要塞、富豪別墅、山坡綠林。今日陰時有雨。中午停亞洲岸,吃烤肉飯,尋訪城堡,因雨太重而作罷。
返航,又點一杯紅茶,五十分錢(一里拉相當台幣二十元),見一葉扁舟行在水中央。水原是水,但這道水獨一無二,它的象徵永不可破,東與西。一東一西,東方與西方。東方鄂圖曼,西方拜占庭。東西方各淵遠流長。鄂圖曼乘水而來,拜占庭航海而去,伊城是水與水的沖積,西方的底蘊,東方的沉澱,世界文明的奇葩。
浪潮汩汩,風雨吹迷了兩岸景色,我仍看見,一個分明的界線,一個必然的原點,一個美麗的環扣,一個詩意的漩渦。
秋之栗
在伊斯坦堡,你至少會光顧一名小販。到處都有小販,有推小餐車的,有擺地攤的,有擎兩隻手兜售的。賣的多是水煮玉米,炭烤玉米,芝麻燒餅,雞絲蓮子飯,手機吊飾,筆記本,鑰匙圈,項鍊手環,毛線襪,明信片,旅遊圖冊,一杯紅茶,甚至擦皮鞋。沒有貨物可賣的,可能是某地毯、陶瓷店的薦介人,更可能是愛情騙子,或純粹的騙子。滿街都有騙子。
秋來了,一場秋雨一場寒。也常金光燦漫,清風送爽,惟日頭一偏,色調全變,蕭蕭然,冷氣一步一步逼上來,人更一點一點把自己收緊起來。
華燈點上後,獨立大道人潮愈見繁多。一走出咖啡館,便見一對父子拉一臺小車,賣水煮玉米,也賣炭烤栗子。秋天吃栗子正合時。我向少年索一包栗子,他在包裝秤兩時,我攝了這張相片。想起在他這年紀的時候,約十三歲吧,我就莫名地喜歡上秋的味道。人生是一部秋光奏鳴曲,流轉啊再流轉。
從少年手上接過熱烘烘的栗子。我的十三歲已流轉。
遺憾的事
在伊斯坦堡,你總會留下一件遺憾的事。照片中的男子立在那裡做什麼呢?獨立大道如滾滾流水,行人摩肩接踵,何曾一刻歇停過,他卻獨自立在那裡,單手持舉一分刊物,面目莊嚴,神思專注,如念天地之悠悠,傲然不忮不求。
是宣道者?是革命者?是異議者?明明全身都是信息,一肚子話,卻挺胸昂然,一言不語,等你自己情願,等你自己來問。
不只是他,走七八步,又有一個他,一個她,如憲兵站崗成列。個個都是年輕人,如組織成形的青年軍。我想向前和他攀談,卻被他的認真嚇住了。太認真,以至於更顯得胸中有思想,有不可違逆的真理,有殉道可行的執著──啊,不!似乎又有一點憤恨,一口未平怨氣。
我遲疑了,退回原來觀望的距離。也許直覺上,我已猜出他是誰,他的另一同伙濃長鬈髮、明亮大眼、獨特長臉,使我想起古蹟浮雕上的亞美尼亞人。他們是亞美尼亞人?亞美尼亞人大屠殺!此事真相未明,土耳其仍竭力否認。控訴!若這是控訴,我覺得他應該這樣站立著,他的沉默顯得多有力量,他的孤影顯得勇敢正直,他的憤鬱顯得天地不容。
遺憾的,至今我仍不確定他是誰,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說什麼。只知道,他一直站立在那裡。他似乎一直站立在那裡。
【內文節選二】
行過里斯本
青春瀲灧
九十一號巴士進入巿區向南,經新城,抵舊城南端Praca do Comercio,即看見偌大廣場盈滿清銀色海光,中間立一青銅像;這是整座城巿的原點。管他丘坡鱗次,管他路徑起伏,站在這裡就站在中心,如手握漁網,以此收,以此放。
里斯本並不直接面向大洋,她是南隔一泓海水,面對自己的國土,因此,這泓瑩藍海水,彷彿一條大江河;行在岸邊看去,如從淡水漁人碼頭看八里觀音山。
自青銅像處走起,通過一扇白石青苔海神門,就步入Augusta街;此街長約一公里,接Rossio廣場;而從廣場再向左上方、右上方鍬形伸展,就是里斯本的主幹道,其中尤以左向的Liberdad大道為最重要。Liberdad大道修築於一五○二年,八線道,左右四線,中間四線兩側有大分隔島,島上種樹開餐廳咖啡館;走在島上向大道兩旁看去,多是劇院,銀行,精品店,博物館,高級旅館。
青年旅館位於Augusta街八十九號民宅。不愧為青年旅館,客廳,欄臺,電腦室,觀影室,餐廳,廚房,到處都是青年人!茱麗亞向我要護照,在她登記出生年日時,我突然有一點心虛,怕被嫌老。預訂的是四人房,今晚這裡住的二男二女。
機場巴士票,猶如一日乘車券(one day pass),可於當日無限制搭乘巿內交通工具。據旅遊書上說,搭乘電車的第一選擇便是二十八號。電軌嵌在石道間,整座城巿幾乎一半全是小方塊石道,而行人步道又以磁磚鋪成──以黑入白,或以白入黑交織成各種圖紋。二十八號電車上坡下坡,走的是老城精華區。人說的不錯,這裡的步調比巴塞隆納慢得多。是啊!你想,上坡怎麼快,下坡也要謹慎;這樣的慢,這樣的陽光漫漫,真是只能深呼吸,一步步走去。
但事實上,幾百年來,這樣的慢,已經叫這城巿走得乏累了。一七五五年,一場連續三次主震的大地震後,里斯本就像失足滑跌一跤的老人,再站起來,步履只是更艱難,更為老氣,布滿滄桑皺紋。
哎,十八元一晚青年旅館!流動在這裡的更像是一場自由無拘束的家庭派對;啤酒一瓶才半塊錢,而來往的又都是二十歲上下的血氣男女。不羈夜;他們聊天,喝酒,彈吉他,聽音樂,笑語充盈。男的裝帥,女的裝俏,這是青春烈焰、火石交撞的激情甩尾。
我因今晨早起,所以看了一回雍正就睡。如我所料,夜半時分,不停有人開門,關門,開燈,又關燈;一名女的把男的帶進來,忽然覺得不妥,又帶出去。清晨四點,同室一男一女才回房,酒氣味,挑情語,今宵千金不忍分。他們說,數十下一起脫褲子上床。「天呀,是一起上我上鋪的床嗎?」......八,九,十,褲子脫下,匆匆登梯上床。辨聽動靜,呼!謝謝老天爺,是各上自己的床。
隔天用早餐,滿室青年人又談又笑,精神依然好,皮膚依然嫩,氣血依然旺,髮色依然亮;飯後,我決定去他處找第二晚的住宿。想起他們的昨夜今晨,只有一句話可形容:青春瀲灩。
啊灩光下,我無處可藏,遂逃之夭夭。
拉娜阿曼達
聽過里斯本的人不少,去過的不多。該怎麼說她呢?如果在山城九份身上,加上舊金山的電車風情,加上巴塞隆納的明燦陽光,加上老北京的輝煌滄桑,加上阿姆斯特丹的流利英文,加上尼斯的緩慢步調,再加上台北的自覺未覺,或許能拼出一幅粗略的里斯本印象。但是,里斯本畢竟是自己的,一把老吉他,一名唱遊藝人,將Fado的悲愴情懷,不斷吟唱在大街小巷中。
我搬到老城的住宅區,Bairro Alto;此區聚集各式酒吧,餐廳,書店,藝廊,網咖,咖啡館,雜貨店,輕服飾店,一片波希米亞風。平日夜晚,這裡的人潮燈火已夠熱鬧;一遇週末,那些藝團表演,吟唱者,以及飲酒者,無不都是通宵達旦。白日走在石路上,能看見婦人們一邊在欄杆外拉繩子吊掛衣物,一邊將留聲機的歌曲大股地流洩出來。除了出入的門板,全區牆上滿滿塗鴉,可用體無完膚來形容;這樣花,這樣亂,這樣狂肆,是否就是創作?塗鴉的藝術精神到底是什麼?
小旅館有一間不編號,卻號稱大老闆(big boss)的房間,旺季一晚收二十塊,淡季十二點五塊。名約大,其實最小,連老闆自己也覺得開了一個玩笑。而我就住在這裡。房間開一小天窗,天窗三公分外就是一堵鄰居的牆;稀奇的,整片面積約兩坪大的大老闆的房間,除一張小床,一個小床頭櫃,竟還容得下一間衛浴室。
早晨未從青年旅館退房前,我隨性走走。不遠山頭有一座大教堂,向教堂走去的路上,看見民宅與民宅間,露出水天一色;走著走著,又發現從任一街口看去,都可見得鐘塔,城堡,圓頂建築等等,不一而足。金光,藍海,橘瓦,黃牆;黃牆亦有新有老,有明有淡,層次重疊。里斯本一山連一山,處處不可忽視,不忍忽視,遂決定再買一臺立可拍。
這像是一座被遺忘了、又忽然被記起的城巿,好比母親招孩子們來,分糖時忘了一個,後來忽然記起。從新旅館走出來,我就拿起立可拍來照。鏡頭下,我總覺得面對亮麗景點是一刻的,而那一刻已有專業攝影師來代勞,旅途中見最多、最能陳明現場的,無非是人生街景。若我來出一本里斯本攝影集,可以稱作〈那山‧那海‧里斯本〉。
大教堂旁一小路Sao Joao Da Praqa,九十三號綠漆大門,九十五號落地玻璃,兩戶聯通,設一咖啡館「pois, CAFÉ」;老木桌,土石牆,環牆一排書,桌上鮮花、檯燈,看著悅目,就進去吃午餐。(說到吃,來此第一餐是站在一間傳統糕餅店裡吃的,這種店在里斯本好幾家,其中自然以葡式蛋塔最知名、也最出色。除了糕餅,店家還賣新鮮水果百匯,柳橙汁,髮菜馬鈴薯湯。我點一湯兩個蛋塔,共二點五歐元;吃飽了笑嘻嘻走出來,不只為便宜,更為那兩個純正葡式蛋塔。)
週六顧客多是來吃早午餐(brunch)的,進門一看,已無位子,只有一方桌坐一女士,我請她容我坐一塊。她戴太陽眼鏡正讀報,不笑不怒說好。侍者很忙,我讀雍正,一面讀一面看她,儘管她在室內戴黑眼鏡看報有些奇特,但她臉上、身上所散發出的氣質,直叫人恍惚,叫人神迷,叫人安詳。那分氣質,應只有一字可以形容:嫻雅。
「能不能給她照一張相呢?」我十分想望,又不敢出口。時間一分一秒逝去,我還找不到機會開口。突然她抬頭,一位看似印度人的女士走過來,原來她不是獨自一人,她在等朋友。她的朋友入座,看見我,點了一下頭,似乎已經猜出我是因人多而來共桌的。
她和朋友說話,她說的多,聲音不乾不潤,有點澀帶著磁性,也正因此,叫人聽得麻醉。哎!此時,我的雍正已渺渺不知所云。她的女友點了餐,尋盥洗室去,而我則是見她已出口說話,必不是自閉於外的人,便壯足勇氣,忐忑說明攝相之意。不想她說好,我喜出望外。相機已拿在手上,「咔嚓」,她進入我的底片。
我告訴她,也許有一天,這照片能發表出來;她聽了一笑,寫下地址,要我寄給她。她寫字時,我又趁機照一張。臨行前,我才想起她忘了寫下名字,請她補寫;又說,那分午餐,她的,我的,她女友的,都買單了。她驚呼一聲說:「太叫人難忘了!(So impressive!)」見她臉上喜悅,我亦喜悅。走在街上,我遇見鄰家門前有隻蹲伏曬太陽的貓,拿起相機攝牠;貓知我在那裡,不理我,再照一張。將相機收到書包裡去的時候,我把那嫻雅女子寫在里斯本旅行書上的名字拿出來看,原來她叫:Lana Almeida(拉娜‧阿曼達)。
人生街景
我迫不及待想把昨天照的相片沖洗出來,正好坐落半坡處的Fnac入門右手邊有一家沖洗店,說是一小時可交貨,便填了單。等待時刻,就到樓上飲食街吃早餐。進入一家店,見沒有葡式蛋塔,便到下一家,有了,「請給我一杯拿鐵,一個蛋塔。」
「二塊四毛錢。」
「阿普利卡多(Obrigado)。」
找回零錢時我用葡文說謝謝。
上三步臺階,向靠窗位子走去,未坐下,人呆住了,「美景啊!」一時幸福感充滿心田。藻綠的木窗外金光迤邐,清潤無煙塵;光照在錯落櫛次的橘瓦民宅上,一坡連著另一坡,直到另一坡山頂老城牆,伴蔥鬱樹木,襯著明淨藍天,遙向右前方輪船碼頭。窗外不見巷間小路,所以無車穿越;也不見有人開窗活動,所以無人聲;一切都靜謐如永晝。
隨喜安然,不知能否這樣說里斯本?她有點不快樂,不滿足,卻又依依戀戀自己的所是。像昨晚和我聊天的小旅館女櫃臺人員,伊麗莎,她在這裡打工,也抱怨老闆吝刻,可她身上還是帶著喜氣,笑得安適。看去不超過五十,身材團圓,行動穩健,尤其英文說得真不錯,比西班牙人強得多。
我因此區有點陰暗頹廢,十一點就早早回來,又因房間無電視,還不想睡,便下半樓來看節目。問她去過美國沒有?她說沒有。問過好些歐洲人都沒來過美國,為什麼?有的說受不了美國官員的刁難,有的說就是不想去,如伊麗莎。伊麗莎倒是去過巴西。在她看來,巴西也是葡萄牙,就好像有些法國人看魁北克也就是法國。
問伊麗莎:「此區治安到底安不安全?」她是我問的第三個人。一個說絕對安全,這是老闆卡蜜達;一個眼神閃爍說安全,這是全職員工馬歇羅;但伊麗莎說,半夜兩點後不安全。做歹的多半是毒販。又說,午夜兩點後,人喝醉了,意志也弱,毒販結伙做生意,其中一個賣毒,等你走到街一頭,另一個就來搶你的毒品和錢,再把毒品回收給伙伴,繼續賣下去。
天光柔亮溢滿室內,還有十五分鐘可拿相片。我看窗景,看雍正,又喝咖啡;幸福感太滿,一時變得憂心沉重。太快樂以至於不快樂。中國人說物極必反,我是太快樂,所以憂心將有不好的事發生。放下咖啡,我心裡咯噔一下,突然有流淚的衝動。
照片洗出來,Lana第一張沒有照好,第二張還可以;大教堂邊的民宅構圖還行,遠方水天卻顯不出湛藍。倒是商店街那張很不錯;老闆午休正關門,我站店外,原想照櫥窗酒瓶、茶壺、咖啡機,見他未離開,又看過來,趕緊一起連他攝進來,結果人與物皆明淨也。
還有一張也不壞,但看了心裡難過,是一名坐在Ouro街上的少年,抱手風琴,帶一隻吉娃娃在賣藝。我在巴塞隆納看過乞者帶著動物坐在路旁,有貓,有狗,有兔子,而路人果真被那些動物引起惻隱之心,紛紛投錢。少年一面彈琴,一面令小狗銜一寶特瓶做成的小筐子,站在鞋盒上,向行路者討賞一些零錢。
Augusta街上也有一名一模一樣的賣藝者。伊麗莎說他們真的都是無家可歸的人,自學的手風琴,住遊民收容所,沒有領受過愛,只記得誰欺負他們。沒有愛,只求溫飽,難怪面容如此僵硬,如此灰暗。記得坐在Augusta街上的那人,頭壓得很低,偶爾抬頭,才知也是少年,眼神總是迴避,而被我攝入鏡頭的這名,他和小狗眼神都淒苦。
路過Augusta的兩名操著英格蘭口音的女士,看見小狗銜錢筐,開心起來,說:「好可愛呀。」我聽了卻說:「很可愛,也很殘忍。」旁邊也有人說:「看那小狗累得發抖。」是啊,遊客們把愛心投在可愛的小狗的錢筐裡,零錢愈壓愈重,小狗依然坐立不動,只能發抖。少年或許也知道筐子裝不下太多錢,所以又另放一個鞋蓋在地上。「該不該給他錢呢?」我問自己。那一名英格蘭口音的女士,說:「不給。」不給,我心裡也苦。我終於給照片中的少年二十分錢,放進鞋蓋裡,然後蹲下來,照了這張相。
午後隨上下起伏的山路,走到Liberdad大道旁愛德華七世公園(Parque Eduardo VII)。公園亦在坡上,沿坡中心闢植一大片草地,草地兩旁有白淨石板大道,大道一側再種樹木。走到坡頂,才知道此處乃城巿中軸線,直線連接Praca do Comercio廣場青銅像。站在這裡看去,整個里斯本一部分新城,和整個老城,臨接海水粼粼波光,盡入眼底。
【內文節選三】
再見!湖木公寓
第一步是扔;凡不必要的、用不到的,例如那張藍色沙發床,就扔掉;重複的東西也扔掉。我一向不喜歡累贅物,能不留的統統不留(後來證明我無遠見,某些東西往後見需時才發現扔掉了)。曾經我自豪向人說:「有一天要搬家或回台灣,我兩個行李就能走!」看來這句話也給自己打臉了。
再來是撤走日常暫用不到的,好比說書,莎士比亞全集,旅行書,攝影集,藝術畫冊等等。書最單純,也最麻煩,因為重。所有鍋碗瓢盆,衣物雜物,都一一撤走。書桌,五斗櫃,床架子,請朋友開小貨車來運走。務必清除一空,不落下一物。
最後是大整潔;廚房,浴室,地毯,都爬上彎下仔細清洗,手指擦拭不沾一粒灰塵。湖風大把大把灌進公寓來,環看四周,這裡已看不見我的事物,找不到我的形跡,更聞不到我生活作息所瀰漫的味道。
我搬走了,二○一四年九月,我告別湖木公寓,換去另一個地方住。那裡有兩房兩廳十一個大小窗戶,供我一個人使用。仍在克里夫蘭,距離也不過開車十分鐘之遙,但是不再緊依伊利湖。
是啊,將近九年,我早晚看窗前光影湖色,啟動一天工作,或者滌濾一身疲煩。將近九年,我每日行經西一一七街,或去上班採買,或去圖書館、美術館,或遠行去他方。將近九年,我一年三季散步於水邊道,看別人漂亮的房子,思想自己的人生和未來。
我走了,無一物,一塵,一味留下。清清蕩蕩,好像不曾有過什麼一樣。對於這裡,我已說了一些,愈說愈覺得有更多沒說的。馬修走了以後,又來幾位維修員,西爾是做得最久的一位,我走時他還在;他身材壯實,幫我把舊電視機回收到垃圾場。瑪姬幾個月沒繳房租,半夜偷偷搬走,叫房東氣惱無奈。韋伯的工作似乎有了眉目,可能留在美國。
崔西因為幫我看顧阿妹,覺得有恩(殊不知,我前後已送她許多禮物),就常來敲門告窮借錢,理由是買菸和看病;我給她二十塊,不准她再來說錢的事。麥克沒有新戀情,仍一個人進出,只是養了一隻貓;他的貓和我的貓偶爾在走廊上相遇,阿妹總是呲牙咧嘴,與人不善。從布告欄訃聞上才知道,慘死在公廁裡的人,原來不是B,B還是一個有氣息而不言語的活人。
阿妹對新環境適應極快,她仍是我最親密的伴侶。新住所該叫什麼,我不知道,也說不上來。總之不是家,不是公寓,不是宿舍。這問題沒人能替我回答;他們跟我一樣,找不到完美稱意的表達方式。即或這樣,我的電話還是響起來了──
「你在哪裡?」有人問我。
是啊,我在哪裡呢?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