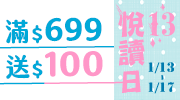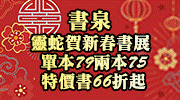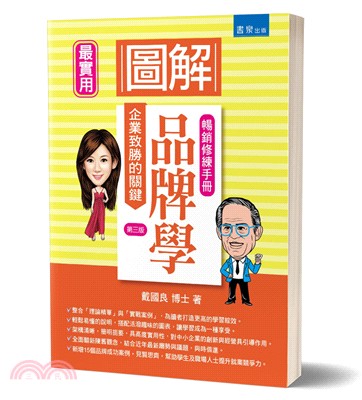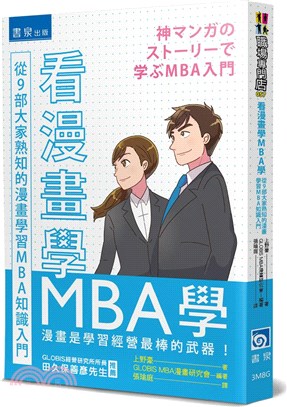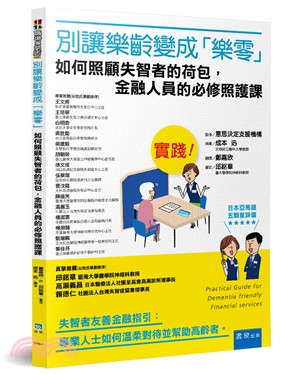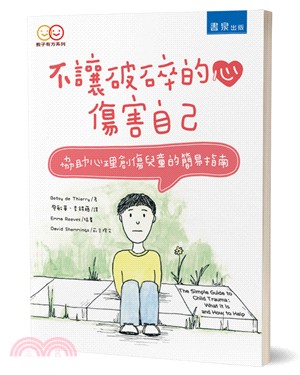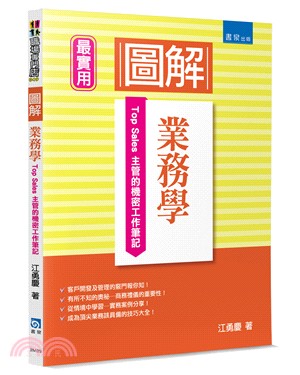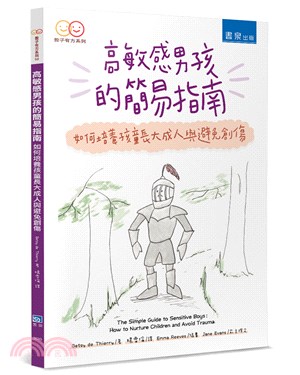風沙星辰
商品資訊
系列名:文學花園
ISBN13:9789865813642
替代書名:Terre des hommes
出版社:二魚文化
作者:安東尼.聖修伯里
譯者:徐麗松
出版日:2015/10/16
裝訂/頁數:精裝/360頁
規格:17.6cm*13.5cm*3cm (高/寬/厚)
重量:472克
版次: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因為飛行,因為墜落,因為擁抱整個宇宙的溫柔與殘忍,
,我們才自渾沌中看見了真正的星星。
── 若沒有這本書,你永遠不會認識《小王子》。
★ 《小王子》作者聖修伯里的自傳體散文集
從「飛航員」的視角讀世界經典,看見當代最偉大的靈魂在天空中的哲思
★ 1939年法蘭西學術院小說大獎、美國國家圖書獎年度最佳書籍
將人類最貼近天空的時刻帶回地面,甫出版即得獎無數
★ 紐約時報盛讚
「這是一本既美麗又英勇的書,在此價值混亂的時代,每個人都該讀它,使我們重拾人性的驕傲與奮激。」
★ 胡晴舫專文導讀推薦
知名作家、文化評論家,也是「聖修伯里迷」。宏觀呈現《夜間飛行》、《風沙星辰》、《小王子》交織出來的風景,讓讀者深刻了解聖修伯里飛行員的經驗如何成就世紀經典。
★ 知名譯者徐麗松執筆,法中直譯,並考證英文版融入
譯有多本法文重要著作如《法式誘惑》、《父親的失樂園》、《夜訪薩德》,並因翻譯《小王子經典珍藏版》而對聖修伯里生平有透徹的研究及理解。
★ 風沙中看見真正的星星-必收藏的燙金精裝版
「霧室」工作室精緻設計,高級裝禎,適宜永久典藏
「我呼吸過遠洋的風,我在唇梢嚐過大海的味道。
只要品嘗過那個滋味,就永遠不可能把它忘記。
我熱愛的不是危險。我知道我熱愛什麼:我熱愛生命。」
《風沙星辰》法文原名為《人類的大地》(Terre des hommes),出版於一九三九年,英文版同年於美國問世,書名為《風沙星辰》(Wind, Sand and Stars)。以細膩感性的文字刻劃他以法國航空郵政公司飛行員身分航行於歐洲、非洲與南美,在撒哈拉沙漠墜機、與死神擦身而過等生命經歷。
《風沙星辰》觸及了文學與哲學的極「高度」。以一個飛行員的高海拔視角展開書寫,書中種種意象與思考不久後逐漸幻化為既抽象又清明的心靈關照故事──《小王子》中的許多情節。
藉著飛機,聖修伯里得以以清澈的眼與心俯瞰一切,學會去「從宇宙的規格衡量人類」(胡晴舫)。墜機後歷劫歸來、幾度被這片人類的大地殘酷吞噬,他終於在文字中點明了自身最在意的核心價值──那不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愛,而是「全人類之間」的愛。
於是,他說──「愛絕不是互相凝視,而是一起往相同方向凝視。」
,我們才自渾沌中看見了真正的星星。
── 若沒有這本書,你永遠不會認識《小王子》。
★ 《小王子》作者聖修伯里的自傳體散文集
從「飛航員」的視角讀世界經典,看見當代最偉大的靈魂在天空中的哲思
★ 1939年法蘭西學術院小說大獎、美國國家圖書獎年度最佳書籍
將人類最貼近天空的時刻帶回地面,甫出版即得獎無數
★ 紐約時報盛讚
「這是一本既美麗又英勇的書,在此價值混亂的時代,每個人都該讀它,使我們重拾人性的驕傲與奮激。」
★ 胡晴舫專文導讀推薦
知名作家、文化評論家,也是「聖修伯里迷」。宏觀呈現《夜間飛行》、《風沙星辰》、《小王子》交織出來的風景,讓讀者深刻了解聖修伯里飛行員的經驗如何成就世紀經典。
★ 知名譯者徐麗松執筆,法中直譯,並考證英文版融入
譯有多本法文重要著作如《法式誘惑》、《父親的失樂園》、《夜訪薩德》,並因翻譯《小王子經典珍藏版》而對聖修伯里生平有透徹的研究及理解。
★ 風沙中看見真正的星星-必收藏的燙金精裝版
「霧室」工作室精緻設計,高級裝禎,適宜永久典藏
「我呼吸過遠洋的風,我在唇梢嚐過大海的味道。
只要品嘗過那個滋味,就永遠不可能把它忘記。
我熱愛的不是危險。我知道我熱愛什麼:我熱愛生命。」
《風沙星辰》法文原名為《人類的大地》(Terre des hommes),出版於一九三九年,英文版同年於美國問世,書名為《風沙星辰》(Wind, Sand and Stars)。以細膩感性的文字刻劃他以法國航空郵政公司飛行員身分航行於歐洲、非洲與南美,在撒哈拉沙漠墜機、與死神擦身而過等生命經歷。
《風沙星辰》觸及了文學與哲學的極「高度」。以一個飛行員的高海拔視角展開書寫,書中種種意象與思考不久後逐漸幻化為既抽象又清明的心靈關照故事──《小王子》中的許多情節。
藉著飛機,聖修伯里得以以清澈的眼與心俯瞰一切,學會去「從宇宙的規格衡量人類」(胡晴舫)。墜機後歷劫歸來、幾度被這片人類的大地殘酷吞噬,他終於在文字中點明了自身最在意的核心價值──那不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愛,而是「全人類之間」的愛。
於是,他說──「愛絕不是互相凝視,而是一起往相同方向凝視。」
作者簡介
法國作家、飛行員,一九〇〇年生於法國里昂,以經典作《小王子》 ( Le Petit Prince )聞名於世。一九四〇年移居美國;一九四四年執行飛航任務時失蹤。其作品常聯結自身飛行經驗,著有《南方郵航》 ( Courrier Sud )、《夜間飛行》( Vol de nuit )、《風沙星辰》 ( Terre des hommes )、《給某人質的一封信》 ( Lettre à un otage )、《小王子》等書。
目次
導讀〈看哪,星星在說話〉 胡晴舫
譯序 徐麗松
I. 航線
II. 夥伴們
III. 飛機
IV. 飛機與星球
V. 綠洲
VI. 在沙漠
VII. 在沙漠的中心VIII. 人類
譯序 徐麗松
I. 航線
II. 夥伴們
III. 飛機
IV. 飛機與星球
V. 綠洲
VI. 在沙漠
VII. 在沙漠的中心VIII. 人類
書摘/試閱
VII. 在沙漠的中心
……
3
我們居然還活著,這真是一件沒道理的事。我拿著手電筒,沿著飛機在地面劃出的痕跡往回走。距離飛機最後打住的地方兩百五十公尺左右,就已經看得到它在滑行過程中撒落在沙地上的捲曲鐵皮和金屬部件。天亮之後,我們發現飛機幾乎是以切線角度撞擊一處沙漠高原頂端的緩坡。撞擊點上留下了一個大坑,彷彿巨大的犁鏵在沙地上挖出的深溝。飛機沒有翻滾,而是像爬蟲動物般搖擺尾巴,怒氣沖沖地用腹部往前移動。這架飛機的堅固牢靠是個奇蹟,當它與桀驁不馴的大地交手,它就是因為這個奇蹟而沒有粉身碎骨,而我們也因此保住一命。散佈在地面上的黑色小圓石顯然也救了我們的命,它們可以自由滾動,使這塊高地儼然像是一具滾珠軸承,讓飛機在撞擊地面後得以往前滑去。
普雷沃把蓄電池的線路拔掉,以免事後發生短路引起火災。我背靠引擎站著,心裡想:我在高空中可能連續四小時十五分鐘被時速五十公里的風在後面吹著飛,而確實我不斷感覺到氣流的震動。可是如果風向改變,跟天氣預測有所不同,我又無法知道它的方向變成什麼。所以我現在可能置身於某個四百公里見方區域中的任何地點。
普雷沃到我身邊坐下,他說:
「能活著實在太棒了……」
我沒有答腔,也沒有任何喜悅之情。我腦海中開始浮現一件事,使我覺得有點煩惱。
我請普雷沃把他的手電筒點亮,作為方位點,然後拿著我的手電筒往正前方走去。我仔細查看地面。我慢慢往前移動,繞了個大半圓,好幾次改變行進方向。我不斷搜索地面,像在找不小心掉落的戒指。方才在空中,我也是這樣努力在黯黑中搜尋生命的火源。我繼續在黑暗中前進,在燈光照出來的圓形範圍內聚精會神地觀察。果然……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慢慢往飛機的方向走去,在機艙旁邊坐了下來。我試著在紛亂的思緒中找到可以懷抱希望的理由,但我找不到。我設法尋找生命發出的訊號,但生命沒有向我發出任何訊號。
「普雷沃,我連一棵小草都沒看到……」
普雷沃沒有回話,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了我的意思。或許等到夜幕拉起、天色亮起來以後,我們才能知道真相。但此刻我只感到一股強烈的無奈,我心想:「在方圓四百公里的沙漠裡!……」忽然我跳了起來。
「水!」
汽油箱、機油箱都爆了。儲水箱也爆了,沙已經把所有水都喝掉了。我們在一個損毀的保溫壺裡找到半公升咖啡,在另一個壺裡找到四分之一公升白葡萄酒。我們把這些液體過濾以後混合起來。我們也找到一點葡萄和一顆柳橙。可是我心裡做了計算:「頂著沙漠的大太陽走路,不出五個小時這些就都沒了……」
我們回到機艙中坐著等天亮。我躺了下來,我想睡覺。還沒入睡前我在心裡總結了一下我們的處境:我們完全不知道自己置身何處,我們能喝的東西不到一公升。假如我們的位置是在直線路徑上,或許七八天後會有人找到我們,這已經算是最樂觀的期望,可是這樣還是來不及。假如我們在飛行過程中偏離原有航向,可能半年後才會有人找到我們。我們不能指望飛機很快找到我們——搜尋範圍高達三千公里。
「啊!好可惜……」普雷沃對我說。
「為什麼?」
「本來可以一下就了結的!……」
可是不可以這麼快就放棄。普雷沃和我設法振作起來。無論我們變得多麼虛弱,都不可以放棄任何讓飛機找到我們的機會,不可以忘記奇蹟獲救的可能。我們也不可以一直待在原地,結果錯過可能就存在於不遠處的綠洲。今天我們要走一整天,然後我們要回到飛機這邊。我們在出發往外走以前,一定要把預定路線用斗大字體寫在沙石地上。
然後我把身體蜷縮起來,一直睡到天亮。我很高興能夠睡著。巨大的疲倦使我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下感覺彷彿有許多不同的東西包圍著我。我在這沙漠中不是獨自一人,我的夢境中有各種不同的聲音、記憶和低聲訴說的秘密。我還不覺得口渴,我甚至覺得舒暢,我像進行一場冒險般投入周公的懷抱。現實退去,讓夢幻如潮水般湧來……
啊!天亮時的情景跟夢中所見真是天差地別!
4
我向來很喜歡撒哈拉。我在叛亂地區度過許多個夜晚。我曾在這片金黃色的遼闊大地中醒來,看到風像吹皺海面般在沙地上留下一道道痕跡。我曾經睡在我的飛機翅膀底下,知道天亮以後就會有人來救我。但那個撒哈拉不是眼前這個撒哈拉。
丘陵彎彎曲曲,我們沿著山坡前行。整個砂質地面上鋪著一層光滑的黑色小石頭,彷彿長了金屬鱗片,四周所有圓丘則像盔甲般在豔陽下閃閃發光。我們掉進一個礦物質世界中,我們被關進一片用鐵打造的風景。
翻越第一座山脊之後,不遠處又有另一座類似的山脊,看起來又黑又亮。我們邊走邊用鞋子地上刮,設法留下導引線,以便隨後循原路返回。我們面向太陽前進。往東方走的決定違反任何邏輯,因為無論從氣象預測或飛行時間等因素看來,所有條件都顯示我應該已經飛越尼羅河。可是稍早我試著往西邊走了一段路,結果感到一股我完全無法解釋的不安,於是我決定西邊的部份等明天再說。我暫時也把北方擱在一邊,雖然照理說往北走應該會接近海岸。三天之後,當我們在幾乎失去一半意識的狀態下決定放棄飛機,一直往前走到倒下為止,我們還是朝東邊走去,比較精確地說是東北東。這似乎也完全違反常理,而且不會有任何希望。後來,在我們獲救以後,我們發現其他方向都無法讓我們走出沙漠,因為就算往北走,在抵達海岸之前,我們的身體早就透支枯竭了。雖然感覺起來很荒謬,可是今天我知道,在沒有任何客觀因素可以指引我們做出正確決定的情況下,我選擇往東走只有一個原因──我的好友基佑美在安地斯山脈失事時,我為了找他飛了好久,結果他是靠著往東方走撿回一條命。對我而言,東方就這樣隱約成為生命的方向。
走了五個小時之後,景物有了改變。山谷中似乎有一條沙河,於是我們沿著那個谷地前進。我們大步走路,因為我們必須盡可能走遠,然後假如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東西,我們還得趕在夜色降臨前回到原點。我忽然停下腳步。
「普雷沃。」
「什麼事?」
「足跡……」
我們多久以前就開始忘了在身後留下痕跡?萬一我們走不回去,那就死定了。
我們往回走,但方向稍微偏右。這樣一來,只要我們走得夠遠,到時轉個直角往左走,遲早就可以找到先前我們留下的痕跡。
終於找到那個線索以後,我們又重新上路。氣溫越來越高,於是沙漠幻景也開始出現。但這時還只是一些最簡單的景象。大湖出現在遠方,等我們再走一段,它又會逐漸消失。我們決定跨越沙谷,爬上最高的山崗,以便眺望遠方。我們已經邁大步走了六小時路,算算一共有三十五公里了。我們抵達這座黑色山丘頂端,靜靜地坐著。下方的沙谷蜿蜒在一片沒有石頭的沙原中,那片大地散發眩目的白色光芒,彷彿在灼燒我們的眼睛。放眼望去,四周盡是一片空寂。但是,在遙遠的地平線上,光線已經建構出更令人不安的海市蜃樓。堡壘、宣禮塔,各種垂直線條的幾何造景。我還觀察到一片深色東西,看起來很像樹林,它的上方飄浮著些許雲朵。原來那塊深色物體只是一片積雲的影子。這天,雲在天亮以後逐漸消散,現在只剩天邊幾朵雲,等到夜幕低垂時,天空中又會堆積起雲層。
再往前走只是白費力氣,今天的步行顯然無法讓我們抵達任何地方。該回到我們的飛機那邊了,那個紅白相間的物體至少是個明顯座標,或許能讓某個從天邊飛來的夥伴找到。雖然我對救援搜尋完全不抱希望,但那似乎是我們獲救的唯一機會。更重要的是,我們最後一點點飲料還在那裡,而我們現在非回去喝不可。只有回去,我們才有一絲存活的可能。我們被束縛在一個鋼鐵般無法改變的循環中,口渴宰制著我們,使我們無法長久維持自主。
可是,當我們可能正朝生存的機會走去,折返原點是多麼痛苦的決定!在海市蜃樓後方某處,天際線上可能有數不清的真正城市、淡水河道及青青草原。我知道折返原點是正確的決定,但當我轉身,一股可怕的倦意襲來,我覺得彷彿隨時可能永遠沉淪。
5
清晨,我們用抹布擦拭潮濕的機翼,擠出一丁點露水到杯底,其中混合了油漆和污油。看起來很噁心,可是我們還是把它喝了下去。在沒有更好的選擇時,這樣我們至少潤濕了一下嘴唇。甘泉饗宴結束,普雷沃對我說:
「幸好還有手槍。」
我忽然覺得自己兇了起來,我帶著深刻的敵意轉身面向他。在這種時候,沒有什麼比無意義的自憐自艾更令我憤恨。我極度需要能夠認為一切都可以很簡單。出生可以很簡單,長大可以很簡單,渴死一樣可以很簡單。
我用眼角觀察普雷沃,他要是再開口說蠢話,我不惜揍他幾拳。可是普雷沃是用非常平靜的態度向我說那句話。先前他跟我聊過衛生的事;現在他提到這個問題時,那樣子彷彿是在說:「我們應該把手洗乾淨。」我們的想法終究還是一致的。昨天,當我的目光瞄到那皮套,其實相同的想法也在我心中掠過。那時我的思緒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不帶哀傷。人只有在社會情境中才會真正感到哀傷。因為我們無力使需要我們照顧的人安心而感到哀傷。手槍本身並不讓人哀傷。
依然沒有人來找我們,或者該說,他們想必是往別處找去了。或許他們在阿拉伯半島找。我們要到隔天才終於聽到飛機聲,在我們已經決定拋棄我們的飛機以後。飛機就那麼一次出現在遙遠的天邊,我們對它也只能感到一股漠然。我們只是兩個小黑點,跟無數小黑點一起混在遼闊沙漠中,我們無法奢望有人會注意到我們。任何人認為我在苦難煎熬中可能產生的思緒都不會是真確的;我並沒有遭受苦難的煎熬。我只覺得救難人員似乎是在另一個象限中執行任務。
要在三千公里範圍中搜尋一架掉進沙漠而且沒有留下任何訊息的飛機,少說也要兩個星期;而且他們如果展開搜尋,範圍很可能是在的黎波里塔尼亞到波斯之間。然而,今天我還是為自己保留了這個微薄的機會,因為沒有任何其他機會。但我改變了策略,我決定一個人出發探索。普雷沃留在原地準備篝火,在有人出現時點燃信號,只不過一直沒有人出現。
於是我出發了,但我連我是否會有體力回來都不知道。我重新想起我對利比亞沙漠的既有認知:整個撒哈拉的平均濕度是百分之四十,但這個地區的溼度低到只有百分之十八。生命在這裡就像水蒸氣般迅速蒸發。貝都因人(12.)、沙漠旅人、殖民地軍官們異口同聲地說,人在這裡要是沒能喝水,頂多能撐十九小時。過了二十個小時,眼睛就會充滿亮光,大限隨即駕到:渴死的進程既迅速又恐怖。
可是這一直吹來的東北風,這騙了我們的、不正常的風,這個跟所有氣象預測作對,把我們吹到這片高原中的風,現在想必是它讓我們能苟延殘喘。但在亮光開始充斥在我們眼中之前,這風又能給我們多少時間?
於是我出發了,但我覺得自己彷彿是將一艘小獨木舟划向汪洋。
不過,因為黎明的關係,這片荒寂的風景顯得沒有那麼陰森。一開始我把雙手插在口袋裡,以掠奪者的姿態走路。昨天晚上,我們在幾個神祕的洞穴口佈置了陷阱,於是我內心那個偷獵者甦醒了過來。我出發後第一個就是去檢查那些陷阱,結果那裡空空如也。
看來我是沒機會茹毛飲血了。老實說,我也沒指望這個奇蹟會出現。
雖然我並不覺得失望,但我感到非常好奇。在這片沙漠裡,動物都靠什麼生活?那些動物應該是「耳廓狐」,也就是沙漠小狐狸,那是一種體型跟兔子差不多大,但耳朵長得特別大的肉食性動物。我無法抗拒內心的欲望,於是我跟著其中一條足跡走去。那足跡把我引到一條狹窄的沙河,所有足跡似乎都輕輕印在那上面。我開心地欣賞沙地上那以三個腳趾形成的扇形掌狀圖案。我想像我的可愛朋友在黎明時分靜悄悄地來到這裡,在石頭上輕輕舔食朝露。動物腳印之間的距離在這裡變大了──我的小狐狸奔跑了起來。在某個地方,牠的夥伴來找牠,然後牠們並肩前進。我就這樣帶著奇異的喜悅之情進行這場晨間漫步。我喜歡這些生命的徵象。我稍微忘了我有多口渴……
最後我終於發現我的狐狸朋友們的膳房了。這一帶的泥土每隔一百公尺左右會長出一棵湯碗般大的迷你乾燥灌木,枝幹上爬了許多金色蝸牛。耳廓狐在黎明時分出發覓食。在這裡,我撞見了大自然的一個偉大秘密。
我的狐狸朋友不會在每一棵小灌木旁耽擱。有些灌木上爬滿了蝸牛,但小狐狸卻對它視而不見。有些灌木牠是繞著轉了一圈,但顯然態度非常審慎。牠會在某些灌木周邊流連,但不會大肆破壞。牠只抓取兩三隻小貝殼,然後就換到另一座食堂。
牠是不是在跟自己的飢餓感玩遊戲,不要一下子就完全滿足食慾,藉此讓美食樂趣瀰漫在整個晨間漫步過程中?我不相信是這樣。牠的遊戲跟某種不可或缺的生存策略太不謀而合了。假如耳廓狐走到第一棵灌木就賴在那裡,直到吃飽為止,牠只要吃個兩三頓,就會把上面的食物都吃光。於是,從這棵灌木到下一棵灌木,牠很快就會把所有食物消耗殆盡。可是耳廓狐小心翼翼地不要危害到物種的繁殖。牠不只願意為了吃一頓飯逛遍一百棵棕色小灌木,甚至在同一根樹枝上牠也不會採集兩隻相鄰的蝸牛。一切彷彿都顯示牠對風險有清楚的意識。假如牠每次都毫無顧忌地只顧馬上吃飽,那很快就不會再有蝸牛。而假如沒有了蝸牛,很快就不會再有耳廓狐。
足跡把我帶回洞穴。耳廓狐想必正在那裡面聽我的聲音,被我腳步踏地發出的震動嚇得渾身發抖。但我跟牠說:「我的小狐狸,我已經沒救了,可是奇怪的是,我竟然不會因為這樣而對你的心情毫無興趣……」
於是我在那裡做白日夢,我覺得似乎萬物都能順應周遭環境。一個人就算知道他三十年後會死,也不會因此永遠悶悶不樂。三十年,三天……這只是觀點的問題。
不過有些意象還是忘了好……
------------------------
現在我繼續前進,而隨著疲倦感益發強烈,我也產生了某種質變。當我沒在遠方看到幻景時,我會自己打造海市蜃樓……
「喂!」
我高舉雙臂喊著,但那個比手畫腳的人只不過是一塊黑色岩石。沙漠中的一切似乎都活動了起來。我想把那個在睡懶覺的貝都因人叫起來,但他立刻化成一根黑色樹幹。化成樹幹?這東西的存在使我非常驚訝,我傾身仔細看了一下。我想把一根斷落的樹枝抬起來——它竟是大理石做成的!我重新站起來,環視周遭;我又看到其他一些黑色大理石。一座大洪水前形成的原始森林在地面留下樹幹殘根。十萬年前,在創世紀的一場風暴中,它像大教堂般坍塌、荒廢了。無數個世紀向我席捲而來,把這些石化了、玻璃化了,碳化成墨色,像金屬部件般光滑的巨大圓柱底座帶到我面前。這座森林曾經蟲鳴鳥唱、樂音流轉,但它遭到詛咒,化成了鹽礦堆。我感覺這個景色對我充滿敵意。這些肅穆、陰沉的殘骸比鋼鐵甲冑般的黑色山丘更漆黑,它們更嚴厲地排斥我。我這個活著的人為什麼到這裡,站在這些不會腐朽的大理石塊之間是要做什麼?我這個很快就會腐朽的生物,這副終究要解體的軀殼,為什麼出現在這片無聲無息的永恆之中?
從昨天到現在我已經走了將近八十公里路。我感到強烈暈眩想必是因為口渴。或者因為太陽。太陽照射在這些彷彿塗上一層油霜的圓柱。太陽猛烈照射在這塊屬於全世界的甲殼上。這裡既沒有沙也沒有狐狸,這裡只剩下一塊無盡延伸的鐵砧。我踩在這灼熱的鐵砧上,感覺陽光在我腦海中激盪。啊!那邊……
「喂!喂!」
「那邊沒有東西,那只是你的幻覺,別再神經兮兮了。」
我就這樣對自己說話,因為我需要召喚我的理智。明明看到了什麼東西,卻得強迫自己拒絕承認它的存在,這是多麼困難的事。看到那個移動中的駱駝商隊,但卻無法衝過去跟他們會合,這是多麼困難的事……就在那邊啊……沒看到嗎?
「傻瓜,你明知那都是你的幻想……」
「這樣的話,世界上就沒有什麼是真的了……」
------------------------
沒有什麼是真的,除了二十公里外那山丘上的十字架。十字架,或燈塔……
但那不是大海的方向。所以那是十字架。我一整晚研究地圖,但這工作只是徒然,因為我連自己的方位都不知道。但我還是要探身查看任何可能向我指點人類存在的徵象。在某個位置,我發現一個小圈圈,上面標了一個類似的十字架。我查了一下圖說,那裡寫著:「宗教建築」。十字架旁邊有一個黑點,我又查了一下圖說,那裡寫著:「永久井」。我心裡大驚,我大聲唸了出來:「永久井……永久井……永久井!」相較於一座永久井,阿里巴巴和他的寶藏又還有什麼重要?再遠一些,我注意到兩個白色圓圈。我在圖說上看到:「臨時井」。這就遜色一些了。然後再往周邊看,什麼都沒有。空空如也。
那就是我的宗教殿堂!僧侶在山丘上立起一座大十字架,召喚落難者!只要朝它的方向走就對了。只要往那些道明會(13.)修士的方向跑去……
「可是利比亞這邊只有科普特基督徒(14.)的修道院。」
「……投奔那些潛心修行的多明我會修士。他們有一座用紅色磁磚打造的廚房,又清爽又漂亮,他們的院子裡有一具美妙無比、生了鏽的汲水泵。你應該猜到了……在那生鏽的汲水泵底下,就是永久井!啊!等我到那裡敲門,等我拉響那裡的大鐘,一場盛宴就要展開……」
「傻瓜,你在描述的是一座普羅旺斯的住宅,那裡不會有什麼鐘。」
「……等我去拉響那座大鐘!門房會把雙手往上一揚,然後對我大喊:『你是天主的使者!』然後他會把所有修士喚來。他們都會趕忙跑來。他們會像照顧一個窮小孩那樣讓我盡情饗食。他們會把我推進廚房,然後告訴我:『等一下,小夥子,等一下……我們一起跑到永久井那裡去……』」
於是我幸福得顫抖起來……
可是不行,我不要哭,不要只因為山丘上的十字架沒有了就哭。
------------------------
西方的許諾只是謊言。我轉向正北方。
北方至少蕩漾著大海的歌聲。
啊!翻過這個山脊,地平線就會在眼前展開。那裡有全世界最美的城市。
「你很清楚這只是海市蜃樓……」
我很清楚這只是海市蜃樓。的確,沒有人騙得了我!可是,如果我心甘情願要朝海市蜃樓奔去呢?如果我心甘情願地喜愛那座擁有美麗城郭、灑滿金色陽光的城市呢?如果我心甘情願地邁開矯健步伐直往前去,因為我不再感到疲倦,因為我覺得快樂……普雷沃和他的手槍,別讓我笑掉大牙了!我寧可像我這樣自我陶醉。我醉了。我渴死了!
暮色使我清醒,我驟然停下腳步,因為覺得自己走得太遠而害怕。暮色中不會再有幻景。地平線上沒有了那些汲水泵、宮殿、僧袍,那就只是一條沙漠的地平線。
「你走得很遠了!夜色就要包圍你,你得在這裡等天亮才行,然後明天你的足跡就消失了,你就不知身在何處了。」
「那就不如繼續往前直走……往回走有什麼用?假如我可能就要張開……假如我可以張開雙臂迎向大海,我不想白費力氣走回頭路……
「你在哪看到大海了?而且你永遠也走不到那裡。你離那裡恐怕有三百公里遠。而且普雷沃還在那架席姆恩號旁邊守候!說不定已經有駱駝商隊看到他了……」
對,我會回去,可是我要先向人類呼喚:
「喂!」
老天,這座星球上明明就住了人……
「喂!有人嗎!……」
我的聲音啞了。我沒有聲音了。我覺得自己這樣呼喊真是荒唐……我又一次使勁喊:
「有人嗎!」
那聲音很堅持,也很造作。
我掉頭往回走。
------------------------
走了兩個小時以後,我看到火光。想必普雷沃以為我走失了,嚇得趕緊造了一座大篝火,讓火焰直往天上衝。啊!……我根本毫不在意……
又走了一個小時……又走了五百公尺。又走了一百公尺,五十公尺。
「啊!」
我驚愕不已地停下腳步。喜悅之情淹沒我的心,我竭力防止它猛然爆發。焰火照亮普雷沃,他正在跟倚靠在飛機引擎上的兩個阿拉伯人說話。他還沒看到我。他已經沉浸在自己的喜悅中。啊!假如我跟他一樣等在這裡……我早就已經解脫了!我高興地喊了一聲:
「喂 !」
那兩個貝都因人驚跳了一下,往我這邊看。普雷沃離開他們身邊,獨自朝我走來。我張開手臂。普雷沃抓住我的手肘,難道我差點倒下去?我說:
「謝天謝地!」
「什麼?」
「阿拉伯人啊!」
「什麼阿拉伯人?」
「跟你一起在那邊的阿拉伯人啊!……」
普雷沃露出好笑的表情看著我,我感覺他似乎心不甘情不願地向我吐露一個沉重的秘密:
「這裡沒有阿拉伯人……」
這次我是真的要哭了。
6
我們已經在這裡度過十九個小時沒水喝的時間。從昨天晚上到現在,我們喝了什麼?黎明時喝了幾滴露水!可是東北風依然在吹,緩和了我們水份蒸發的速度。輕盈的水霧飄向天空,可望貢獻於宏偉壯麗的雲朵形成。啊!要是雲朵能往我們這邊飄來,要是雨水能降下!但沙漠裡永遠不會下雨。
「普雷沃,我們來把一個降落傘剪成三角形的帆布塊,然後用石頭固定在地上。如果風沒有改變方向,黎明時我們就可以把這些布塊拿起來,找個油料箱,把上面的露水擰進去收集起來。」
於是我們把六塊白布陳列在星空下。普雷沃拆下一個油箱。現在我們只要等天亮就行了。
普雷沃在飛機殘骸中奇蹟似地發現一顆柳橙,我們把它分了吃。在我們需要二十公升水的時候,一顆柳橙是多麼微不足道,但我的心情卻激動不已。
我躺在我們的夜間火堆旁,凝視著這顆發亮的水果,我心想:「人類不懂柳橙是什麼……」我又想到:「我們已經走到窮途末路,但這個鐵般的事實並沒有使我灰心到無法享受眼前的樂趣,我握在手裡這半顆橙子又是一個明證,它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喜悅之一……」我躺了下來,一邊吸吮鮮美的果實,一邊數著天上的流星。在一分鐘時間中,我在這裡感受無盡的幸福。我又想到:「就人類目前所處的世界秩序而言,我們無法知道是不是我們把自己關進去了。」我到今天才懂得一支香菸和一杯蘭姆酒在一名死囚手中所代表的意義。我一直無法明白他何以能接受那樣的悲慘處境。然而,他確實從中感受到極大的快樂。假如他露出微笑,我們會想像他是個勇敢面對死亡的人。但他微笑只是因為他喝了那杯蘭姆酒。我們不知道他已經改變了觀點,他讓最後那一小時化成了他的全部生命。
------------------------
我們收集到很多水,可能足足有兩公升。不會再口渴了!我們得救了,可以喝水了!
我用馬口鐵杯從這個大水箱裡舀出一杯水,但那水呈現美麗的黃綠色澤,我喝了一小口,那味道可怕至極,儘管我渴得快要發瘋,我還是得猛吸一大口氣才敢把水吞進去。這時要是有一杯泥水,我倒不介意喝它,可是那帶著有毒金屬味道的水比口渴更讓我覺得恐怖。
我看到普雷沃眼睛盯著地面在兜圈子,彷彿他在仔細找什麼。忽然間,他彎身嘔吐,而且人還繼續兜圈子。三十秒鐘以後輪到我了。我的身體嚴重痙攣,我跪在地上,雙手緊抓泥地。我們沒有說話,在一刻鐘時間中,我們就這樣全身發抖,到最後只能吐出一點膽汁。
☆ ☆ ☆
完了。現在我只隱約感覺到一股彷彿從遠方傳來的噁心。我們連最後的希望也落空了。我不知道這個失敗的原因是降落傘的塗料或油箱內的四氯化物沉澱。我們應該找別的容器、用別種布料才對。
所以,趕緊吧!天亮了,快點出發!我們要逃離這個被詛咒的高原,大步往前走,直到倒下為止。我效法在安地斯山落難的基佑美:從昨天開始,我經常想到他。我決定違反墜機後必須留在飛機殘骸旁邊的正式規定。要找我們,到別的地方找吧。
又一次,我們發現落難者並不是我們。那些在等待的人才是落難者!我們的沉默嚴重威脅著他們。他們已經被一個可怕的錯誤撕裂。我們不能不向他們奔去。基佑美也是,他從安地斯山出來之後,向我描述過他是如何奮力朝落難的人奔去!這是個普世皆然的事實。
「假如我在這世上無親無故,」普雷沃告訴我:「我會躺下來。」
於是我們往東北東方向直直走去。假如我們已經跨越尼羅河,現在我們踩下的每一步都會把我們帶到阿拉伯大沙漠更深處。
------------------------
我記不得多少那天的事。我只記得我匆忙趕路。匆忙趕往不知什麼,就直到我倒下吧。我也記得自己只是低頭看著地面一直走,因為抬頭看到的幻景會讓我覺得反胃。有時候我們會根據指南針稍微調整一下方向,有時候我們也會躺下來伸展身子喘口氣。還有,我在某個地方把我留著在晚上用的橡膠墊丟掉了。其他我就不再記得什麼了。我的記憶一片空白,直到那晚氣溫涼快下來為止。我也變得跟一望無際的沙一樣,我內在的一切都被消除了。
日落時我們決定停下來過夜。我知道我們應該繼續走:這沒水的一夜恐怕會讓我們再也起不來。不過我們帶了降落傘切成的帆布片。假如帆布塗料不是有毒物質,明天早上我們可能就真的有水喝了。我們必須再一次把捕捉露水的陷阱張開在星空下。
但是北方的天空今晚純淨清爽,沒有一片雲朵。但是風已經改變了它的氣味。它也改變了方向。來自沙漠中央的熱風已經開始吹拂在我們身上。猛獸甦醒了!我已經感覺牠正舔著我們的雙手和臉龐。
但是假如我繼續走,我恐怕走不了十公里。三天以來,在沒水喝的情況下,我已經走了至少一百八十公里……
但是,就在我們停下來時:
「我跟你打賭那是一個湖,」普雷沃對我說。
「你瘋了!」
「在這麼個黃昏時候,那有可能會是幻景嗎?」
我沒答腔。我已經很久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那或許不是幻景,但它可能是我們在瘋狂中想像出來的東西。普雷沃怎麼還會相信這些呢?
普雷沃很堅持:
「應該二十分鐘就走到了,我去看看……」
他的固執使我很生氣:
「你去看吧,去透透氣……這樣走走對身體很好。可是就算你的湖存在,它也是鹹的,這點你很清楚。總之不管它鹹不鹹,它就是一座惡魔湖。更重要的是,它根本不存在。」
普雷沃目光篤定,他已經邁步離開。我知道那些誘惑物可以多麼令人心動!我心想:「甚至還有夢遊的人會往火車頭底下跳呢。」我知道普雷沃不會回來。一股空寂的眩暈將佔據他的身心,他將無法掉頭回來。他將在前方某處倒下。他會獨自死去,留下我在這裡獨自死去。這一切又有什麼重要!……
一種毫不在乎的心態正在淹沒我,我覺得這不是個好兆頭。曾經,我眼看自己就要被淹死,卻感覺到同樣這種平靜。可是這次我利用這個機會,俯臥在石頭地上寫遺書。我的信寫得很美,很有尊嚴,裡面提供各種明智的建議。我寫完讀它時,心裡隱約感到一股虛榮。以後的人會說:「這封遺書寫得多麼令人讚嘆!真可惜這樣的人死了啊!」
我也想知道自己目前的狀況。我試著擠出唾液。我有多少小時沒吐唾液了?我是不是連唾液都沒了?如果我把嘴巴閉著,一種黏稠物質會把我的上下唇黏起來。黏稠物乾了以後,會在嘴唇上結成一層硬硬的外殼。不過幸好我還有辦法做出吞嚥的動作。我的眼睛還沒有充滿光線。當光輝燦爛的情景開始在我眼前展現,我就只剩下兩小時可活了。
黑夜降臨。月亮比前一晚顯得更肥大。普雷沃沒有回來。我躺在地上,反覆思索著這些明顯事實。我心中出現某個年代久遠的印象,我設法想出那到底是什麼。我是……我在……我上了船!我正搭船前往南美洲,我就這樣躺在上層甲板上。桅杆頂端彷彿插進滿天星斗中,慢慢地前後左右晃動。這裡沒有桅杆,不過我還是上了船,前往一個再也無法取決於我的目的地。一群黑奴已經把我綁了起來,丟到這艘船上。
我想到沒有走回來的普雷沃。我一直沒聽到他發出任何怨言。這樣很好。我恐怕無法忍受聽到別人唉聲嘆氣。普雷沃是個男子漢。
啊!距離我五百公尺左右,他正在搖晃他的手電筒!他走失了!我沒有手電筒可以回應他,我站起來呼喊,可是他聽不到……
第二盞燈在距離他兩百公尺的地方亮了起來,然後是第三盞燈。老天,有人在搜索,他們在找我!
我大叫一聲:
「喂!」
可是沒有人聽到我。
三盞燈繼續發出呼叫訊號。
今天晚上我沒發瘋。我感覺很好。我很平靜。我仔細觀察,五百米外確實出現三盞燈。
「喂!」
可是仍然沒有人聽到我。
一時間我慌了起來。這是我唯一一次感覺到驚慌。啊!我還可以跑:「等等……等等……」他們要轉身走了!他們就要離開,到別的地方找了!而我就要在這裡倒下!有人已經張開手臂等著迎接我,我卻要在生命的門檻上倒下!
「喂!喂!」
「喂!」
他們聽到我了。我喘不過氣,真的喘不過氣,可是我還是一直跑。我跑向那個聲音:「喂!」我看到普雷沃,然後我倒在地上。
「啊!我看到好多盞燈!……」
「什麼燈?」
沒錯,他只有一個人。
這次我沒有感覺到絕望,只是在心裡生悶氣。
「你的湖呢?」
「我一直往前走,湖就一直往後退。我走了半個小時。半小時之後,它就變得太遠了。所以我就回來了。可是現在我可以確定那是一個湖……」
「你瘋了,徹底瘋了。啊!為什麼你要這麼做?……為什麼?」
他做了什麼?他為什麼那麼做?我氣憤填膺地哭了起來,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氣憤填膺。普雷沃用哽咽的聲音告訴我:
「我多麼想找到可以喝的水……你的嘴唇完全發白了……」
啊!我的氣消了……我把手擱上額頭,彷彿我剛清醒過來。我覺得很難過。然後我輕聲說:
「我看到……就像我現在看著你,我清楚看到三盞燈,我不可能搞錯……我跟你說,普雷沃,我看到三盞燈!」
普雷沃沉默了一下,最後終於說:
「果然情況不妙。」
周遭環境沒有一絲水氣,大地很快就開始發出亮光。這時已經變得很冷了。我起身走路。可是我很快就全身顫抖得難以忍受。我的血液失去水分,循環非常困難。冰冷的感覺穿透我的身體,而那不只是夜晚的冰冷。我的上下顎不斷打顫,我整個身體都在嚴重打哆嗦。我的手抖得連手電筒都無法操作。我對冷向來沒什麼感覺,但現在我居然就要冷死,口渴的效應多麼奇怪!
我把我的橡膠墊丟在某個地方了,因為我受不了繼續在酷熱中扛著它走。風勢越來越猛。我發現沙漠裡沒有任何掩蔽處……沙漠就像大理石一樣平滑。白天沒有任何陰影,晚上任憑寒風吹襲。沒有一棵樹,沒有籬笆,沒有岩石讓我遮風。風就像一支騎兵隊在曠野中攻擊我。我不停兜圈子想躲它,我躺下,又站起來。無論我躺著或站著,那冰冷的鞭子一樣無情地往我揮來。我沒法跑,我已經沒有這種體力,刺客在追我,但我跑不動,我跪倒在地,在他們的大刀下,我只能用手緊緊抱著頭!
我後來才意識到這時我站了起來,往前直直走去,身體一直猛打哆嗦!我在哪裡?啊!我才剛離開,就聽到普雷沃的聲音!是他的叫聲把我喚醒……
我回到他身邊,整個身體依然不停打顫,猛烈震動。我心想:「這不是冷,是別的東西。最後一刻到了。」我已經脫水得太嚴重了。前天,我們走了太多路,還有昨天我一個人也走了太多路。
被凍死這件事令我非常難過。我寧可投奔心中那些海市蜃樓。那個十字架,那些阿拉伯人,那些燈。總之,那些東西開始讓我產生濃厚興趣。我真不想像奴隸一樣被無情地鞭鞭笞……
我又跪了下來。
我們隨身帶了一些藥。一百公克純乙醚,一百公克九十度的酒精,以及一瓶碘藥水。我試著喝兩三小口乙醚。我覺得自己彷彿在吞嚥刀刃。然後我喝了一點九十度酒精,但那簡直把我的喉嚨封住了。
我在沙地中挖了一條溝,躺了進去,用沙子把自己蓋起來。我只讓臉露到外面。普雷沃找到一些小樹枝,他點了火,但火一下就熄了。普雷沃拒絕把自己埋進土裡。他寧可站著走動。但他錯了。
我的喉嚨依然緊繃,這不是好兆頭,不過我覺得舒服了些。我覺得很平靜。我覺得超乎所有預期地平靜。我被黑奴綁在船橋上,被迫在星辰下航向大海。但或許我並不會非常不快樂……
只要我不拉動任何肌肉,我就不再感覺寒冷。於是,我忘了自己那副沉睡在沙中的軀體。我不再移動,這樣我就不會再感到痛苦。而且真的,受苦的程度非常低……在這所有痛苦的背後,是疲倦和幻想在聯手操縱。一切都變成了圖像書,變成一個有點殘忍的童話故事……方才,風無情地追獵著我,為了躲避它,我像野獸般兜圈子。然後我覺得呼吸困難,彷彿一個膝蓋壓迫住我的胸膛。一個膝蓋。於是我在天使的沉重身軀下掙扎。過去我從不曾在沙漠中感到寂寞。現在我不再相信周圍的一切,我把自己關進內心,閉上眼睛,不再眨動一根睫毛。我可以感覺無數影像化為滾滾洪流,把我捲向一個寧靜的夢:江河在海洋的深厚中沉靜了下來。
再會了,我愛過的人們。假如人體無法承受三天沒有一滴水的折磨,那畢竟不是我的錯。我沒想到自己受制於水泉的程度如此之深,我沒料到自己的自主能力如此淺薄。我們以為人類可以挺直身軀不斷勇往直前,我們以為人類是自由的……我們沒看到那根把他繫在井口上的繩子,沒看到它像一條臍帶般把他連到大地的腹腔。如果他多走一步,他就沒有了生命。
除了你們的痛苦以外,我沒有任何懊悔。總的算來,我這輩子過得夠好了。假如我能回去,我會依樣畫葫蘆。我需要活著。但在城市裡,人類卻已經不再有生命。
這裡說的不是飛行。飛機並不是目的,只是一個手段。人不是為了飛機而甘冒生命危險。農夫也不是為了那具犁而耕田。但藉由飛機,人可以離開城市,離開那些忙著計算、忙於算計的凡夫俗子,人找到了農夫耕耘土地那般的真實。
飛行員做的是終究是人的工作,我們都懂得身為凡人的憂慮。我們與風,與星辰,與黑夜,與沙,與大海接觸。我們設法跟自然力量周旋。我們等待黎明,就像園丁等待春天。我們等著抵達中繼站,彷彿那是一個應許之地。我們在星辰中尋找屬於我們的真實。
我不會有怨言。三天以來,我一直走路,我口渴,我在沙漠中循著一些蹤跡而行,我讓露水成為我的希望。我不斷設法連繫上我的族類,但我已經忘記他們生存在大地上的哪些角落。這些都是人類活著的時候關心憂慮的事。我無法不認為這些事比晚上為了上哪家夜總會而煩惱更重要。
我也不明白那些靠郊區火車移動的人類族群,那些人以為自己是人類,但卻被一種他們已經感受不到的應力壓縮得彷彿螞蟻,只能發揮螞蟻般的功能。當他們有了點自由,他們是怎麼填滿那些荒謬的小小星期天?
有一次,在俄羅斯,我在一家工廠中聽到莫札特的音樂。我把這件事寫了出來,結果收到兩百封罵人的信。我不是對喜歡上低級歌廳的人有意見,他們不懂得別種音樂。我有意見的是低級歌廳的老闆。我不喜歡看到人毀壞人類的心靈。
我在我這個行業裡是快活的。我覺得自己是耕耘航線中繼站的農夫。搭乘郊區火車時,我感受到的痛苦跟這裡截然不同,但卻更加椎心刺骨!總的算起來,能夠身在此處,是何等的奢侈!……
我沒有遺憾,賭注是我自己下的,輸了也是我的事。這是我們這個行業中命定的部份。但無論如何,我呼吸過遠洋的風,我在唇梢嘗過大海的味道。
只要品嘗過那個滋味,就永遠不可能把它忘記。不是麼,我的夥伴們?這跟選擇危險的生活方式完全無關。「玩命」是個自命不凡、矯揉造作的概念。鬥牛不是我會佩服的事。我熱愛的不是危險。我知道我熱愛什麼:我熱愛生命。
------------------------
東邊的天空似乎逐漸露出魚肚白。我從沙裡伸出一隻手臂。夜裡我在伸手可及之處放了一塊帆布,我現在摸了它一下,它是乾的。再等一會吧。露水是在黎明形成的。可是天空已經開始泛白,帆布上卻毫無濕氣。我的思緒有點混亂了起來,我聽到自己說:「這裡有一顆乾枯的心……一顆乾枯的心……這裡有一顆乾枯的心,它不知該怎麼製造眼淚!……」
「上路吧,普雷沃!我們的喉嚨還沒有完全封閉,我們得繼續走。」
(以上截取第七章之第3、4篇,描述作者墜機於撒哈拉沙漠中心的片段。)
……
3
我們居然還活著,這真是一件沒道理的事。我拿著手電筒,沿著飛機在地面劃出的痕跡往回走。距離飛機最後打住的地方兩百五十公尺左右,就已經看得到它在滑行過程中撒落在沙地上的捲曲鐵皮和金屬部件。天亮之後,我們發現飛機幾乎是以切線角度撞擊一處沙漠高原頂端的緩坡。撞擊點上留下了一個大坑,彷彿巨大的犁鏵在沙地上挖出的深溝。飛機沒有翻滾,而是像爬蟲動物般搖擺尾巴,怒氣沖沖地用腹部往前移動。這架飛機的堅固牢靠是個奇蹟,當它與桀驁不馴的大地交手,它就是因為這個奇蹟而沒有粉身碎骨,而我們也因此保住一命。散佈在地面上的黑色小圓石顯然也救了我們的命,它們可以自由滾動,使這塊高地儼然像是一具滾珠軸承,讓飛機在撞擊地面後得以往前滑去。
普雷沃把蓄電池的線路拔掉,以免事後發生短路引起火災。我背靠引擎站著,心裡想:我在高空中可能連續四小時十五分鐘被時速五十公里的風在後面吹著飛,而確實我不斷感覺到氣流的震動。可是如果風向改變,跟天氣預測有所不同,我又無法知道它的方向變成什麼。所以我現在可能置身於某個四百公里見方區域中的任何地點。
普雷沃到我身邊坐下,他說:
「能活著實在太棒了……」
我沒有答腔,也沒有任何喜悅之情。我腦海中開始浮現一件事,使我覺得有點煩惱。
我請普雷沃把他的手電筒點亮,作為方位點,然後拿著我的手電筒往正前方走去。我仔細查看地面。我慢慢往前移動,繞了個大半圓,好幾次改變行進方向。我不斷搜索地面,像在找不小心掉落的戒指。方才在空中,我也是這樣努力在黯黑中搜尋生命的火源。我繼續在黑暗中前進,在燈光照出來的圓形範圍內聚精會神地觀察。果然……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慢慢往飛機的方向走去,在機艙旁邊坐了下來。我試著在紛亂的思緒中找到可以懷抱希望的理由,但我找不到。我設法尋找生命發出的訊號,但生命沒有向我發出任何訊號。
「普雷沃,我連一棵小草都沒看到……」
普雷沃沒有回話,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了我的意思。或許等到夜幕拉起、天色亮起來以後,我們才能知道真相。但此刻我只感到一股強烈的無奈,我心想:「在方圓四百公里的沙漠裡!……」忽然我跳了起來。
「水!」
汽油箱、機油箱都爆了。儲水箱也爆了,沙已經把所有水都喝掉了。我們在一個損毀的保溫壺裡找到半公升咖啡,在另一個壺裡找到四分之一公升白葡萄酒。我們把這些液體過濾以後混合起來。我們也找到一點葡萄和一顆柳橙。可是我心裡做了計算:「頂著沙漠的大太陽走路,不出五個小時這些就都沒了……」
我們回到機艙中坐著等天亮。我躺了下來,我想睡覺。還沒入睡前我在心裡總結了一下我們的處境:我們完全不知道自己置身何處,我們能喝的東西不到一公升。假如我們的位置是在直線路徑上,或許七八天後會有人找到我們,這已經算是最樂觀的期望,可是這樣還是來不及。假如我們在飛行過程中偏離原有航向,可能半年後才會有人找到我們。我們不能指望飛機很快找到我們——搜尋範圍高達三千公里。
「啊!好可惜……」普雷沃對我說。
「為什麼?」
「本來可以一下就了結的!……」
可是不可以這麼快就放棄。普雷沃和我設法振作起來。無論我們變得多麼虛弱,都不可以放棄任何讓飛機找到我們的機會,不可以忘記奇蹟獲救的可能。我們也不可以一直待在原地,結果錯過可能就存在於不遠處的綠洲。今天我們要走一整天,然後我們要回到飛機這邊。我們在出發往外走以前,一定要把預定路線用斗大字體寫在沙石地上。
然後我把身體蜷縮起來,一直睡到天亮。我很高興能夠睡著。巨大的疲倦使我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下感覺彷彿有許多不同的東西包圍著我。我在這沙漠中不是獨自一人,我的夢境中有各種不同的聲音、記憶和低聲訴說的秘密。我還不覺得口渴,我甚至覺得舒暢,我像進行一場冒險般投入周公的懷抱。現實退去,讓夢幻如潮水般湧來……
啊!天亮時的情景跟夢中所見真是天差地別!
4
我向來很喜歡撒哈拉。我在叛亂地區度過許多個夜晚。我曾在這片金黃色的遼闊大地中醒來,看到風像吹皺海面般在沙地上留下一道道痕跡。我曾經睡在我的飛機翅膀底下,知道天亮以後就會有人來救我。但那個撒哈拉不是眼前這個撒哈拉。
丘陵彎彎曲曲,我們沿著山坡前行。整個砂質地面上鋪著一層光滑的黑色小石頭,彷彿長了金屬鱗片,四周所有圓丘則像盔甲般在豔陽下閃閃發光。我們掉進一個礦物質世界中,我們被關進一片用鐵打造的風景。
翻越第一座山脊之後,不遠處又有另一座類似的山脊,看起來又黑又亮。我們邊走邊用鞋子地上刮,設法留下導引線,以便隨後循原路返回。我們面向太陽前進。往東方走的決定違反任何邏輯,因為無論從氣象預測或飛行時間等因素看來,所有條件都顯示我應該已經飛越尼羅河。可是稍早我試著往西邊走了一段路,結果感到一股我完全無法解釋的不安,於是我決定西邊的部份等明天再說。我暫時也把北方擱在一邊,雖然照理說往北走應該會接近海岸。三天之後,當我們在幾乎失去一半意識的狀態下決定放棄飛機,一直往前走到倒下為止,我們還是朝東邊走去,比較精確地說是東北東。這似乎也完全違反常理,而且不會有任何希望。後來,在我們獲救以後,我們發現其他方向都無法讓我們走出沙漠,因為就算往北走,在抵達海岸之前,我們的身體早就透支枯竭了。雖然感覺起來很荒謬,可是今天我知道,在沒有任何客觀因素可以指引我們做出正確決定的情況下,我選擇往東走只有一個原因──我的好友基佑美在安地斯山脈失事時,我為了找他飛了好久,結果他是靠著往東方走撿回一條命。對我而言,東方就這樣隱約成為生命的方向。
走了五個小時之後,景物有了改變。山谷中似乎有一條沙河,於是我們沿著那個谷地前進。我們大步走路,因為我們必須盡可能走遠,然後假如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東西,我們還得趕在夜色降臨前回到原點。我忽然停下腳步。
「普雷沃。」
「什麼事?」
「足跡……」
我們多久以前就開始忘了在身後留下痕跡?萬一我們走不回去,那就死定了。
我們往回走,但方向稍微偏右。這樣一來,只要我們走得夠遠,到時轉個直角往左走,遲早就可以找到先前我們留下的痕跡。
終於找到那個線索以後,我們又重新上路。氣溫越來越高,於是沙漠幻景也開始出現。但這時還只是一些最簡單的景象。大湖出現在遠方,等我們再走一段,它又會逐漸消失。我們決定跨越沙谷,爬上最高的山崗,以便眺望遠方。我們已經邁大步走了六小時路,算算一共有三十五公里了。我們抵達這座黑色山丘頂端,靜靜地坐著。下方的沙谷蜿蜒在一片沒有石頭的沙原中,那片大地散發眩目的白色光芒,彷彿在灼燒我們的眼睛。放眼望去,四周盡是一片空寂。但是,在遙遠的地平線上,光線已經建構出更令人不安的海市蜃樓。堡壘、宣禮塔,各種垂直線條的幾何造景。我還觀察到一片深色東西,看起來很像樹林,它的上方飄浮著些許雲朵。原來那塊深色物體只是一片積雲的影子。這天,雲在天亮以後逐漸消散,現在只剩天邊幾朵雲,等到夜幕低垂時,天空中又會堆積起雲層。
再往前走只是白費力氣,今天的步行顯然無法讓我們抵達任何地方。該回到我們的飛機那邊了,那個紅白相間的物體至少是個明顯座標,或許能讓某個從天邊飛來的夥伴找到。雖然我對救援搜尋完全不抱希望,但那似乎是我們獲救的唯一機會。更重要的是,我們最後一點點飲料還在那裡,而我們現在非回去喝不可。只有回去,我們才有一絲存活的可能。我們被束縛在一個鋼鐵般無法改變的循環中,口渴宰制著我們,使我們無法長久維持自主。
可是,當我們可能正朝生存的機會走去,折返原點是多麼痛苦的決定!在海市蜃樓後方某處,天際線上可能有數不清的真正城市、淡水河道及青青草原。我知道折返原點是正確的決定,但當我轉身,一股可怕的倦意襲來,我覺得彷彿隨時可能永遠沉淪。
5
清晨,我們用抹布擦拭潮濕的機翼,擠出一丁點露水到杯底,其中混合了油漆和污油。看起來很噁心,可是我們還是把它喝了下去。在沒有更好的選擇時,這樣我們至少潤濕了一下嘴唇。甘泉饗宴結束,普雷沃對我說:
「幸好還有手槍。」
我忽然覺得自己兇了起來,我帶著深刻的敵意轉身面向他。在這種時候,沒有什麼比無意義的自憐自艾更令我憤恨。我極度需要能夠認為一切都可以很簡單。出生可以很簡單,長大可以很簡單,渴死一樣可以很簡單。
我用眼角觀察普雷沃,他要是再開口說蠢話,我不惜揍他幾拳。可是普雷沃是用非常平靜的態度向我說那句話。先前他跟我聊過衛生的事;現在他提到這個問題時,那樣子彷彿是在說:「我們應該把手洗乾淨。」我們的想法終究還是一致的。昨天,當我的目光瞄到那皮套,其實相同的想法也在我心中掠過。那時我的思緒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不帶哀傷。人只有在社會情境中才會真正感到哀傷。因為我們無力使需要我們照顧的人安心而感到哀傷。手槍本身並不讓人哀傷。
依然沒有人來找我們,或者該說,他們想必是往別處找去了。或許他們在阿拉伯半島找。我們要到隔天才終於聽到飛機聲,在我們已經決定拋棄我們的飛機以後。飛機就那麼一次出現在遙遠的天邊,我們對它也只能感到一股漠然。我們只是兩個小黑點,跟無數小黑點一起混在遼闊沙漠中,我們無法奢望有人會注意到我們。任何人認為我在苦難煎熬中可能產生的思緒都不會是真確的;我並沒有遭受苦難的煎熬。我只覺得救難人員似乎是在另一個象限中執行任務。
要在三千公里範圍中搜尋一架掉進沙漠而且沒有留下任何訊息的飛機,少說也要兩個星期;而且他們如果展開搜尋,範圍很可能是在的黎波里塔尼亞到波斯之間。然而,今天我還是為自己保留了這個微薄的機會,因為沒有任何其他機會。但我改變了策略,我決定一個人出發探索。普雷沃留在原地準備篝火,在有人出現時點燃信號,只不過一直沒有人出現。
於是我出發了,但我連我是否會有體力回來都不知道。我重新想起我對利比亞沙漠的既有認知:整個撒哈拉的平均濕度是百分之四十,但這個地區的溼度低到只有百分之十八。生命在這裡就像水蒸氣般迅速蒸發。貝都因人(12.)、沙漠旅人、殖民地軍官們異口同聲地說,人在這裡要是沒能喝水,頂多能撐十九小時。過了二十個小時,眼睛就會充滿亮光,大限隨即駕到:渴死的進程既迅速又恐怖。
可是這一直吹來的東北風,這騙了我們的、不正常的風,這個跟所有氣象預測作對,把我們吹到這片高原中的風,現在想必是它讓我們能苟延殘喘。但在亮光開始充斥在我們眼中之前,這風又能給我們多少時間?
於是我出發了,但我覺得自己彷彿是將一艘小獨木舟划向汪洋。
不過,因為黎明的關係,這片荒寂的風景顯得沒有那麼陰森。一開始我把雙手插在口袋裡,以掠奪者的姿態走路。昨天晚上,我們在幾個神祕的洞穴口佈置了陷阱,於是我內心那個偷獵者甦醒了過來。我出發後第一個就是去檢查那些陷阱,結果那裡空空如也。
看來我是沒機會茹毛飲血了。老實說,我也沒指望這個奇蹟會出現。
雖然我並不覺得失望,但我感到非常好奇。在這片沙漠裡,動物都靠什麼生活?那些動物應該是「耳廓狐」,也就是沙漠小狐狸,那是一種體型跟兔子差不多大,但耳朵長得特別大的肉食性動物。我無法抗拒內心的欲望,於是我跟著其中一條足跡走去。那足跡把我引到一條狹窄的沙河,所有足跡似乎都輕輕印在那上面。我開心地欣賞沙地上那以三個腳趾形成的扇形掌狀圖案。我想像我的可愛朋友在黎明時分靜悄悄地來到這裡,在石頭上輕輕舔食朝露。動物腳印之間的距離在這裡變大了──我的小狐狸奔跑了起來。在某個地方,牠的夥伴來找牠,然後牠們並肩前進。我就這樣帶著奇異的喜悅之情進行這場晨間漫步。我喜歡這些生命的徵象。我稍微忘了我有多口渴……
最後我終於發現我的狐狸朋友們的膳房了。這一帶的泥土每隔一百公尺左右會長出一棵湯碗般大的迷你乾燥灌木,枝幹上爬了許多金色蝸牛。耳廓狐在黎明時分出發覓食。在這裡,我撞見了大自然的一個偉大秘密。
我的狐狸朋友不會在每一棵小灌木旁耽擱。有些灌木上爬滿了蝸牛,但小狐狸卻對它視而不見。有些灌木牠是繞著轉了一圈,但顯然態度非常審慎。牠會在某些灌木周邊流連,但不會大肆破壞。牠只抓取兩三隻小貝殼,然後就換到另一座食堂。
牠是不是在跟自己的飢餓感玩遊戲,不要一下子就完全滿足食慾,藉此讓美食樂趣瀰漫在整個晨間漫步過程中?我不相信是這樣。牠的遊戲跟某種不可或缺的生存策略太不謀而合了。假如耳廓狐走到第一棵灌木就賴在那裡,直到吃飽為止,牠只要吃個兩三頓,就會把上面的食物都吃光。於是,從這棵灌木到下一棵灌木,牠很快就會把所有食物消耗殆盡。可是耳廓狐小心翼翼地不要危害到物種的繁殖。牠不只願意為了吃一頓飯逛遍一百棵棕色小灌木,甚至在同一根樹枝上牠也不會採集兩隻相鄰的蝸牛。一切彷彿都顯示牠對風險有清楚的意識。假如牠每次都毫無顧忌地只顧馬上吃飽,那很快就不會再有蝸牛。而假如沒有了蝸牛,很快就不會再有耳廓狐。
足跡把我帶回洞穴。耳廓狐想必正在那裡面聽我的聲音,被我腳步踏地發出的震動嚇得渾身發抖。但我跟牠說:「我的小狐狸,我已經沒救了,可是奇怪的是,我竟然不會因為這樣而對你的心情毫無興趣……」
於是我在那裡做白日夢,我覺得似乎萬物都能順應周遭環境。一個人就算知道他三十年後會死,也不會因此永遠悶悶不樂。三十年,三天……這只是觀點的問題。
不過有些意象還是忘了好……
------------------------
現在我繼續前進,而隨著疲倦感益發強烈,我也產生了某種質變。當我沒在遠方看到幻景時,我會自己打造海市蜃樓……
「喂!」
我高舉雙臂喊著,但那個比手畫腳的人只不過是一塊黑色岩石。沙漠中的一切似乎都活動了起來。我想把那個在睡懶覺的貝都因人叫起來,但他立刻化成一根黑色樹幹。化成樹幹?這東西的存在使我非常驚訝,我傾身仔細看了一下。我想把一根斷落的樹枝抬起來——它竟是大理石做成的!我重新站起來,環視周遭;我又看到其他一些黑色大理石。一座大洪水前形成的原始森林在地面留下樹幹殘根。十萬年前,在創世紀的一場風暴中,它像大教堂般坍塌、荒廢了。無數個世紀向我席捲而來,把這些石化了、玻璃化了,碳化成墨色,像金屬部件般光滑的巨大圓柱底座帶到我面前。這座森林曾經蟲鳴鳥唱、樂音流轉,但它遭到詛咒,化成了鹽礦堆。我感覺這個景色對我充滿敵意。這些肅穆、陰沉的殘骸比鋼鐵甲冑般的黑色山丘更漆黑,它們更嚴厲地排斥我。我這個活著的人為什麼到這裡,站在這些不會腐朽的大理石塊之間是要做什麼?我這個很快就會腐朽的生物,這副終究要解體的軀殼,為什麼出現在這片無聲無息的永恆之中?
從昨天到現在我已經走了將近八十公里路。我感到強烈暈眩想必是因為口渴。或者因為太陽。太陽照射在這些彷彿塗上一層油霜的圓柱。太陽猛烈照射在這塊屬於全世界的甲殼上。這裡既沒有沙也沒有狐狸,這裡只剩下一塊無盡延伸的鐵砧。我踩在這灼熱的鐵砧上,感覺陽光在我腦海中激盪。啊!那邊……
「喂!喂!」
「那邊沒有東西,那只是你的幻覺,別再神經兮兮了。」
我就這樣對自己說話,因為我需要召喚我的理智。明明看到了什麼東西,卻得強迫自己拒絕承認它的存在,這是多麼困難的事。看到那個移動中的駱駝商隊,但卻無法衝過去跟他們會合,這是多麼困難的事……就在那邊啊……沒看到嗎?
「傻瓜,你明知那都是你的幻想……」
「這樣的話,世界上就沒有什麼是真的了……」
------------------------
沒有什麼是真的,除了二十公里外那山丘上的十字架。十字架,或燈塔……
但那不是大海的方向。所以那是十字架。我一整晚研究地圖,但這工作只是徒然,因為我連自己的方位都不知道。但我還是要探身查看任何可能向我指點人類存在的徵象。在某個位置,我發現一個小圈圈,上面標了一個類似的十字架。我查了一下圖說,那裡寫著:「宗教建築」。十字架旁邊有一個黑點,我又查了一下圖說,那裡寫著:「永久井」。我心裡大驚,我大聲唸了出來:「永久井……永久井……永久井!」相較於一座永久井,阿里巴巴和他的寶藏又還有什麼重要?再遠一些,我注意到兩個白色圓圈。我在圖說上看到:「臨時井」。這就遜色一些了。然後再往周邊看,什麼都沒有。空空如也。
那就是我的宗教殿堂!僧侶在山丘上立起一座大十字架,召喚落難者!只要朝它的方向走就對了。只要往那些道明會(13.)修士的方向跑去……
「可是利比亞這邊只有科普特基督徒(14.)的修道院。」
「……投奔那些潛心修行的多明我會修士。他們有一座用紅色磁磚打造的廚房,又清爽又漂亮,他們的院子裡有一具美妙無比、生了鏽的汲水泵。你應該猜到了……在那生鏽的汲水泵底下,就是永久井!啊!等我到那裡敲門,等我拉響那裡的大鐘,一場盛宴就要展開……」
「傻瓜,你在描述的是一座普羅旺斯的住宅,那裡不會有什麼鐘。」
「……等我去拉響那座大鐘!門房會把雙手往上一揚,然後對我大喊:『你是天主的使者!』然後他會把所有修士喚來。他們都會趕忙跑來。他們會像照顧一個窮小孩那樣讓我盡情饗食。他們會把我推進廚房,然後告訴我:『等一下,小夥子,等一下……我們一起跑到永久井那裡去……』」
於是我幸福得顫抖起來……
可是不行,我不要哭,不要只因為山丘上的十字架沒有了就哭。
------------------------
西方的許諾只是謊言。我轉向正北方。
北方至少蕩漾著大海的歌聲。
啊!翻過這個山脊,地平線就會在眼前展開。那裡有全世界最美的城市。
「你很清楚這只是海市蜃樓……」
我很清楚這只是海市蜃樓。的確,沒有人騙得了我!可是,如果我心甘情願要朝海市蜃樓奔去呢?如果我心甘情願地喜愛那座擁有美麗城郭、灑滿金色陽光的城市呢?如果我心甘情願地邁開矯健步伐直往前去,因為我不再感到疲倦,因為我覺得快樂……普雷沃和他的手槍,別讓我笑掉大牙了!我寧可像我這樣自我陶醉。我醉了。我渴死了!
暮色使我清醒,我驟然停下腳步,因為覺得自己走得太遠而害怕。暮色中不會再有幻景。地平線上沒有了那些汲水泵、宮殿、僧袍,那就只是一條沙漠的地平線。
「你走得很遠了!夜色就要包圍你,你得在這裡等天亮才行,然後明天你的足跡就消失了,你就不知身在何處了。」
「那就不如繼續往前直走……往回走有什麼用?假如我可能就要張開……假如我可以張開雙臂迎向大海,我不想白費力氣走回頭路……
「你在哪看到大海了?而且你永遠也走不到那裡。你離那裡恐怕有三百公里遠。而且普雷沃還在那架席姆恩號旁邊守候!說不定已經有駱駝商隊看到他了……」
對,我會回去,可是我要先向人類呼喚:
「喂!」
老天,這座星球上明明就住了人……
「喂!有人嗎!……」
我的聲音啞了。我沒有聲音了。我覺得自己這樣呼喊真是荒唐……我又一次使勁喊:
「有人嗎!」
那聲音很堅持,也很造作。
我掉頭往回走。
------------------------
走了兩個小時以後,我看到火光。想必普雷沃以為我走失了,嚇得趕緊造了一座大篝火,讓火焰直往天上衝。啊!……我根本毫不在意……
又走了一個小時……又走了五百公尺。又走了一百公尺,五十公尺。
「啊!」
我驚愕不已地停下腳步。喜悅之情淹沒我的心,我竭力防止它猛然爆發。焰火照亮普雷沃,他正在跟倚靠在飛機引擎上的兩個阿拉伯人說話。他還沒看到我。他已經沉浸在自己的喜悅中。啊!假如我跟他一樣等在這裡……我早就已經解脫了!我高興地喊了一聲:
「喂 !」
那兩個貝都因人驚跳了一下,往我這邊看。普雷沃離開他們身邊,獨自朝我走來。我張開手臂。普雷沃抓住我的手肘,難道我差點倒下去?我說:
「謝天謝地!」
「什麼?」
「阿拉伯人啊!」
「什麼阿拉伯人?」
「跟你一起在那邊的阿拉伯人啊!……」
普雷沃露出好笑的表情看著我,我感覺他似乎心不甘情不願地向我吐露一個沉重的秘密:
「這裡沒有阿拉伯人……」
這次我是真的要哭了。
6
我們已經在這裡度過十九個小時沒水喝的時間。從昨天晚上到現在,我們喝了什麼?黎明時喝了幾滴露水!可是東北風依然在吹,緩和了我們水份蒸發的速度。輕盈的水霧飄向天空,可望貢獻於宏偉壯麗的雲朵形成。啊!要是雲朵能往我們這邊飄來,要是雨水能降下!但沙漠裡永遠不會下雨。
「普雷沃,我們來把一個降落傘剪成三角形的帆布塊,然後用石頭固定在地上。如果風沒有改變方向,黎明時我們就可以把這些布塊拿起來,找個油料箱,把上面的露水擰進去收集起來。」
於是我們把六塊白布陳列在星空下。普雷沃拆下一個油箱。現在我們只要等天亮就行了。
普雷沃在飛機殘骸中奇蹟似地發現一顆柳橙,我們把它分了吃。在我們需要二十公升水的時候,一顆柳橙是多麼微不足道,但我的心情卻激動不已。
我躺在我們的夜間火堆旁,凝視著這顆發亮的水果,我心想:「人類不懂柳橙是什麼……」我又想到:「我們已經走到窮途末路,但這個鐵般的事實並沒有使我灰心到無法享受眼前的樂趣,我握在手裡這半顆橙子又是一個明證,它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喜悅之一……」我躺了下來,一邊吸吮鮮美的果實,一邊數著天上的流星。在一分鐘時間中,我在這裡感受無盡的幸福。我又想到:「就人類目前所處的世界秩序而言,我們無法知道是不是我們把自己關進去了。」我到今天才懂得一支香菸和一杯蘭姆酒在一名死囚手中所代表的意義。我一直無法明白他何以能接受那樣的悲慘處境。然而,他確實從中感受到極大的快樂。假如他露出微笑,我們會想像他是個勇敢面對死亡的人。但他微笑只是因為他喝了那杯蘭姆酒。我們不知道他已經改變了觀點,他讓最後那一小時化成了他的全部生命。
------------------------
我們收集到很多水,可能足足有兩公升。不會再口渴了!我們得救了,可以喝水了!
我用馬口鐵杯從這個大水箱裡舀出一杯水,但那水呈現美麗的黃綠色澤,我喝了一小口,那味道可怕至極,儘管我渴得快要發瘋,我還是得猛吸一大口氣才敢把水吞進去。這時要是有一杯泥水,我倒不介意喝它,可是那帶著有毒金屬味道的水比口渴更讓我覺得恐怖。
我看到普雷沃眼睛盯著地面在兜圈子,彷彿他在仔細找什麼。忽然間,他彎身嘔吐,而且人還繼續兜圈子。三十秒鐘以後輪到我了。我的身體嚴重痙攣,我跪在地上,雙手緊抓泥地。我們沒有說話,在一刻鐘時間中,我們就這樣全身發抖,到最後只能吐出一點膽汁。
☆ ☆ ☆
完了。現在我只隱約感覺到一股彷彿從遠方傳來的噁心。我們連最後的希望也落空了。我不知道這個失敗的原因是降落傘的塗料或油箱內的四氯化物沉澱。我們應該找別的容器、用別種布料才對。
所以,趕緊吧!天亮了,快點出發!我們要逃離這個被詛咒的高原,大步往前走,直到倒下為止。我效法在安地斯山落難的基佑美:從昨天開始,我經常想到他。我決定違反墜機後必須留在飛機殘骸旁邊的正式規定。要找我們,到別的地方找吧。
又一次,我們發現落難者並不是我們。那些在等待的人才是落難者!我們的沉默嚴重威脅著他們。他們已經被一個可怕的錯誤撕裂。我們不能不向他們奔去。基佑美也是,他從安地斯山出來之後,向我描述過他是如何奮力朝落難的人奔去!這是個普世皆然的事實。
「假如我在這世上無親無故,」普雷沃告訴我:「我會躺下來。」
於是我們往東北東方向直直走去。假如我們已經跨越尼羅河,現在我們踩下的每一步都會把我們帶到阿拉伯大沙漠更深處。
------------------------
我記不得多少那天的事。我只記得我匆忙趕路。匆忙趕往不知什麼,就直到我倒下吧。我也記得自己只是低頭看著地面一直走,因為抬頭看到的幻景會讓我覺得反胃。有時候我們會根據指南針稍微調整一下方向,有時候我們也會躺下來伸展身子喘口氣。還有,我在某個地方把我留著在晚上用的橡膠墊丟掉了。其他我就不再記得什麼了。我的記憶一片空白,直到那晚氣溫涼快下來為止。我也變得跟一望無際的沙一樣,我內在的一切都被消除了。
日落時我們決定停下來過夜。我知道我們應該繼續走:這沒水的一夜恐怕會讓我們再也起不來。不過我們帶了降落傘切成的帆布片。假如帆布塗料不是有毒物質,明天早上我們可能就真的有水喝了。我們必須再一次把捕捉露水的陷阱張開在星空下。
但是北方的天空今晚純淨清爽,沒有一片雲朵。但是風已經改變了它的氣味。它也改變了方向。來自沙漠中央的熱風已經開始吹拂在我們身上。猛獸甦醒了!我已經感覺牠正舔著我們的雙手和臉龐。
但是假如我繼續走,我恐怕走不了十公里。三天以來,在沒水喝的情況下,我已經走了至少一百八十公里……
但是,就在我們停下來時:
「我跟你打賭那是一個湖,」普雷沃對我說。
「你瘋了!」
「在這麼個黃昏時候,那有可能會是幻景嗎?」
我沒答腔。我已經很久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那或許不是幻景,但它可能是我們在瘋狂中想像出來的東西。普雷沃怎麼還會相信這些呢?
普雷沃很堅持:
「應該二十分鐘就走到了,我去看看……」
他的固執使我很生氣:
「你去看吧,去透透氣……這樣走走對身體很好。可是就算你的湖存在,它也是鹹的,這點你很清楚。總之不管它鹹不鹹,它就是一座惡魔湖。更重要的是,它根本不存在。」
普雷沃目光篤定,他已經邁步離開。我知道那些誘惑物可以多麼令人心動!我心想:「甚至還有夢遊的人會往火車頭底下跳呢。」我知道普雷沃不會回來。一股空寂的眩暈將佔據他的身心,他將無法掉頭回來。他將在前方某處倒下。他會獨自死去,留下我在這裡獨自死去。這一切又有什麼重要!……
一種毫不在乎的心態正在淹沒我,我覺得這不是個好兆頭。曾經,我眼看自己就要被淹死,卻感覺到同樣這種平靜。可是這次我利用這個機會,俯臥在石頭地上寫遺書。我的信寫得很美,很有尊嚴,裡面提供各種明智的建議。我寫完讀它時,心裡隱約感到一股虛榮。以後的人會說:「這封遺書寫得多麼令人讚嘆!真可惜這樣的人死了啊!」
我也想知道自己目前的狀況。我試著擠出唾液。我有多少小時沒吐唾液了?我是不是連唾液都沒了?如果我把嘴巴閉著,一種黏稠物質會把我的上下唇黏起來。黏稠物乾了以後,會在嘴唇上結成一層硬硬的外殼。不過幸好我還有辦法做出吞嚥的動作。我的眼睛還沒有充滿光線。當光輝燦爛的情景開始在我眼前展現,我就只剩下兩小時可活了。
黑夜降臨。月亮比前一晚顯得更肥大。普雷沃沒有回來。我躺在地上,反覆思索著這些明顯事實。我心中出現某個年代久遠的印象,我設法想出那到底是什麼。我是……我在……我上了船!我正搭船前往南美洲,我就這樣躺在上層甲板上。桅杆頂端彷彿插進滿天星斗中,慢慢地前後左右晃動。這裡沒有桅杆,不過我還是上了船,前往一個再也無法取決於我的目的地。一群黑奴已經把我綁了起來,丟到這艘船上。
我想到沒有走回來的普雷沃。我一直沒聽到他發出任何怨言。這樣很好。我恐怕無法忍受聽到別人唉聲嘆氣。普雷沃是個男子漢。
啊!距離我五百公尺左右,他正在搖晃他的手電筒!他走失了!我沒有手電筒可以回應他,我站起來呼喊,可是他聽不到……
第二盞燈在距離他兩百公尺的地方亮了起來,然後是第三盞燈。老天,有人在搜索,他們在找我!
我大叫一聲:
「喂!」
可是沒有人聽到我。
三盞燈繼續發出呼叫訊號。
今天晚上我沒發瘋。我感覺很好。我很平靜。我仔細觀察,五百米外確實出現三盞燈。
「喂!」
可是仍然沒有人聽到我。
一時間我慌了起來。這是我唯一一次感覺到驚慌。啊!我還可以跑:「等等……等等……」他們要轉身走了!他們就要離開,到別的地方找了!而我就要在這裡倒下!有人已經張開手臂等著迎接我,我卻要在生命的門檻上倒下!
「喂!喂!」
「喂!」
他們聽到我了。我喘不過氣,真的喘不過氣,可是我還是一直跑。我跑向那個聲音:「喂!」我看到普雷沃,然後我倒在地上。
「啊!我看到好多盞燈!……」
「什麼燈?」
沒錯,他只有一個人。
這次我沒有感覺到絕望,只是在心裡生悶氣。
「你的湖呢?」
「我一直往前走,湖就一直往後退。我走了半個小時。半小時之後,它就變得太遠了。所以我就回來了。可是現在我可以確定那是一個湖……」
「你瘋了,徹底瘋了。啊!為什麼你要這麼做?……為什麼?」
他做了什麼?他為什麼那麼做?我氣憤填膺地哭了起來,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氣憤填膺。普雷沃用哽咽的聲音告訴我:
「我多麼想找到可以喝的水……你的嘴唇完全發白了……」
啊!我的氣消了……我把手擱上額頭,彷彿我剛清醒過來。我覺得很難過。然後我輕聲說:
「我看到……就像我現在看著你,我清楚看到三盞燈,我不可能搞錯……我跟你說,普雷沃,我看到三盞燈!」
普雷沃沉默了一下,最後終於說:
「果然情況不妙。」
周遭環境沒有一絲水氣,大地很快就開始發出亮光。這時已經變得很冷了。我起身走路。可是我很快就全身顫抖得難以忍受。我的血液失去水分,循環非常困難。冰冷的感覺穿透我的身體,而那不只是夜晚的冰冷。我的上下顎不斷打顫,我整個身體都在嚴重打哆嗦。我的手抖得連手電筒都無法操作。我對冷向來沒什麼感覺,但現在我居然就要冷死,口渴的效應多麼奇怪!
我把我的橡膠墊丟在某個地方了,因為我受不了繼續在酷熱中扛著它走。風勢越來越猛。我發現沙漠裡沒有任何掩蔽處……沙漠就像大理石一樣平滑。白天沒有任何陰影,晚上任憑寒風吹襲。沒有一棵樹,沒有籬笆,沒有岩石讓我遮風。風就像一支騎兵隊在曠野中攻擊我。我不停兜圈子想躲它,我躺下,又站起來。無論我躺著或站著,那冰冷的鞭子一樣無情地往我揮來。我沒法跑,我已經沒有這種體力,刺客在追我,但我跑不動,我跪倒在地,在他們的大刀下,我只能用手緊緊抱著頭!
我後來才意識到這時我站了起來,往前直直走去,身體一直猛打哆嗦!我在哪裡?啊!我才剛離開,就聽到普雷沃的聲音!是他的叫聲把我喚醒……
我回到他身邊,整個身體依然不停打顫,猛烈震動。我心想:「這不是冷,是別的東西。最後一刻到了。」我已經脫水得太嚴重了。前天,我們走了太多路,還有昨天我一個人也走了太多路。
被凍死這件事令我非常難過。我寧可投奔心中那些海市蜃樓。那個十字架,那些阿拉伯人,那些燈。總之,那些東西開始讓我產生濃厚興趣。我真不想像奴隸一樣被無情地鞭鞭笞……
我又跪了下來。
我們隨身帶了一些藥。一百公克純乙醚,一百公克九十度的酒精,以及一瓶碘藥水。我試著喝兩三小口乙醚。我覺得自己彷彿在吞嚥刀刃。然後我喝了一點九十度酒精,但那簡直把我的喉嚨封住了。
我在沙地中挖了一條溝,躺了進去,用沙子把自己蓋起來。我只讓臉露到外面。普雷沃找到一些小樹枝,他點了火,但火一下就熄了。普雷沃拒絕把自己埋進土裡。他寧可站著走動。但他錯了。
我的喉嚨依然緊繃,這不是好兆頭,不過我覺得舒服了些。我覺得很平靜。我覺得超乎所有預期地平靜。我被黑奴綁在船橋上,被迫在星辰下航向大海。但或許我並不會非常不快樂……
只要我不拉動任何肌肉,我就不再感覺寒冷。於是,我忘了自己那副沉睡在沙中的軀體。我不再移動,這樣我就不會再感到痛苦。而且真的,受苦的程度非常低……在這所有痛苦的背後,是疲倦和幻想在聯手操縱。一切都變成了圖像書,變成一個有點殘忍的童話故事……方才,風無情地追獵著我,為了躲避它,我像野獸般兜圈子。然後我覺得呼吸困難,彷彿一個膝蓋壓迫住我的胸膛。一個膝蓋。於是我在天使的沉重身軀下掙扎。過去我從不曾在沙漠中感到寂寞。現在我不再相信周圍的一切,我把自己關進內心,閉上眼睛,不再眨動一根睫毛。我可以感覺無數影像化為滾滾洪流,把我捲向一個寧靜的夢:江河在海洋的深厚中沉靜了下來。
再會了,我愛過的人們。假如人體無法承受三天沒有一滴水的折磨,那畢竟不是我的錯。我沒想到自己受制於水泉的程度如此之深,我沒料到自己的自主能力如此淺薄。我們以為人類可以挺直身軀不斷勇往直前,我們以為人類是自由的……我們沒看到那根把他繫在井口上的繩子,沒看到它像一條臍帶般把他連到大地的腹腔。如果他多走一步,他就沒有了生命。
除了你們的痛苦以外,我沒有任何懊悔。總的算來,我這輩子過得夠好了。假如我能回去,我會依樣畫葫蘆。我需要活著。但在城市裡,人類卻已經不再有生命。
這裡說的不是飛行。飛機並不是目的,只是一個手段。人不是為了飛機而甘冒生命危險。農夫也不是為了那具犁而耕田。但藉由飛機,人可以離開城市,離開那些忙著計算、忙於算計的凡夫俗子,人找到了農夫耕耘土地那般的真實。
飛行員做的是終究是人的工作,我們都懂得身為凡人的憂慮。我們與風,與星辰,與黑夜,與沙,與大海接觸。我們設法跟自然力量周旋。我們等待黎明,就像園丁等待春天。我們等著抵達中繼站,彷彿那是一個應許之地。我們在星辰中尋找屬於我們的真實。
我不會有怨言。三天以來,我一直走路,我口渴,我在沙漠中循著一些蹤跡而行,我讓露水成為我的希望。我不斷設法連繫上我的族類,但我已經忘記他們生存在大地上的哪些角落。這些都是人類活著的時候關心憂慮的事。我無法不認為這些事比晚上為了上哪家夜總會而煩惱更重要。
我也不明白那些靠郊區火車移動的人類族群,那些人以為自己是人類,但卻被一種他們已經感受不到的應力壓縮得彷彿螞蟻,只能發揮螞蟻般的功能。當他們有了點自由,他們是怎麼填滿那些荒謬的小小星期天?
有一次,在俄羅斯,我在一家工廠中聽到莫札特的音樂。我把這件事寫了出來,結果收到兩百封罵人的信。我不是對喜歡上低級歌廳的人有意見,他們不懂得別種音樂。我有意見的是低級歌廳的老闆。我不喜歡看到人毀壞人類的心靈。
我在我這個行業裡是快活的。我覺得自己是耕耘航線中繼站的農夫。搭乘郊區火車時,我感受到的痛苦跟這裡截然不同,但卻更加椎心刺骨!總的算起來,能夠身在此處,是何等的奢侈!……
我沒有遺憾,賭注是我自己下的,輸了也是我的事。這是我們這個行業中命定的部份。但無論如何,我呼吸過遠洋的風,我在唇梢嘗過大海的味道。
只要品嘗過那個滋味,就永遠不可能把它忘記。不是麼,我的夥伴們?這跟選擇危險的生活方式完全無關。「玩命」是個自命不凡、矯揉造作的概念。鬥牛不是我會佩服的事。我熱愛的不是危險。我知道我熱愛什麼:我熱愛生命。
------------------------
東邊的天空似乎逐漸露出魚肚白。我從沙裡伸出一隻手臂。夜裡我在伸手可及之處放了一塊帆布,我現在摸了它一下,它是乾的。再等一會吧。露水是在黎明形成的。可是天空已經開始泛白,帆布上卻毫無濕氣。我的思緒有點混亂了起來,我聽到自己說:「這裡有一顆乾枯的心……一顆乾枯的心……這裡有一顆乾枯的心,它不知該怎麼製造眼淚!……」
「上路吧,普雷沃!我們的喉嚨還沒有完全封閉,我們得繼續走。」
(以上截取第七章之第3、4篇,描述作者墜機於撒哈拉沙漠中心的片段。)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